余华的冷漠叙述
- 格式:doc
- 大小:32.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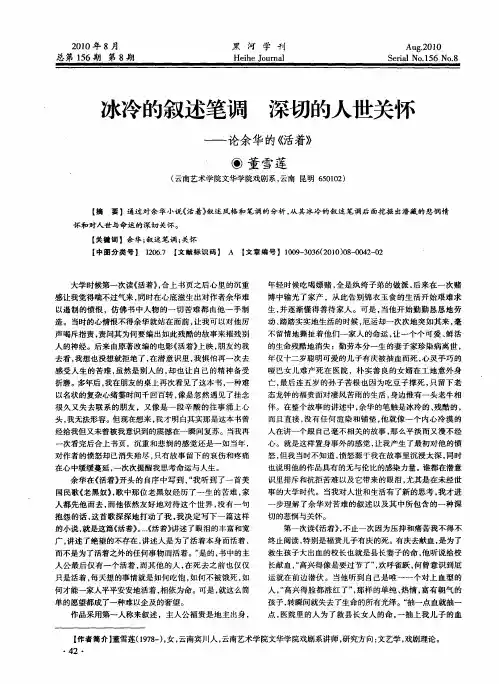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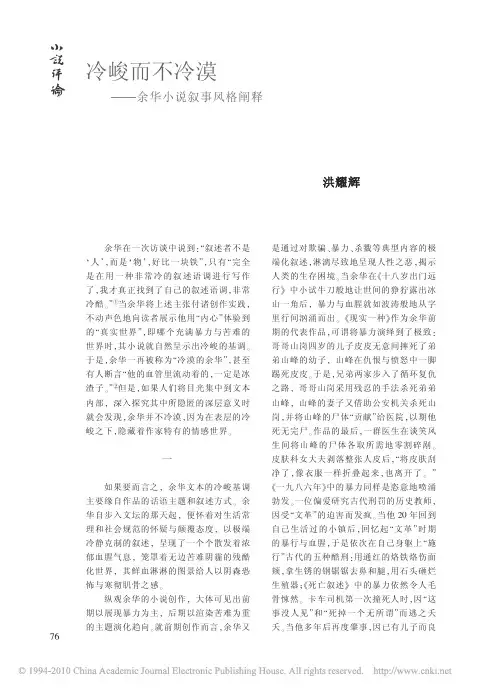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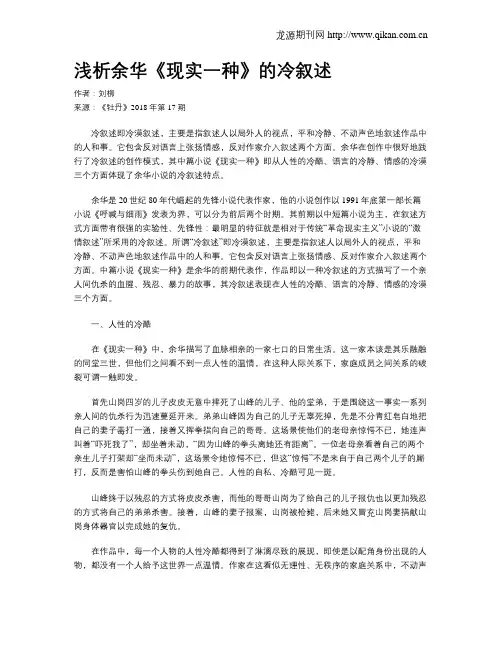
浅析余华《现实一种》的冷叙述作者:刘柳来源:《牡丹》2018年第17期冷叙述即冷漠叙述,主要是指叙述人以局外人的视点,平和冷静、不动声色地叙述作品中的人和事。
它包含反对语言上张扬情感,反对作家介入叙述两个方面。
余华在创作中很好地践行了冷叙述的创作模式,其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即从人性的冷酷、语言的冷静、情感的冷漠三个方面体现了余华小说的冷叙述特点。
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以1991年底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发表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其前期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在叙述方式方面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先锋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对于传统“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激情叙述”所采用的冷叙述。
所谓“冷叙述”即冷漠叙述,主要是指叙述人以局外人的视点,平和冷静、不动声色地叙述作品中的人和事。
它包含反对语言上张扬情感、反对作家介入叙述两个方面。
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是余华的前期代表作,作品即以一种冷叙述的方式描写了一个亲人间仇杀的血腥、残忍、暴力的故事,其冷叙述表现在人性的冷酷、语言的冷静、情感的冷漠三个方面。
一、人性的冷酷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描写了血脉相亲的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
这一家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同堂三世,但他们之间看不到一点人性的温情,在这种人际关系下,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破裂可谓一触即发。
首先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无意中摔死了山峰的儿子、他的堂弟,于是围绕这一事实一系列亲人间的仇杀行为迅速蔓延开来。
弟弟山峰因为自己的儿子无辜死掉,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自己的妻子毒打一通,接着又挥拳指向自己的哥哥。
这场景使他们的老母亲惊愕不已,她连声叫着“吓死我了”,却坐着未动,“因为山峰的拳头离她还有距离”。
一位老母亲看着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打架却“坐而未动”,这场景令她惊愕不已,但这“惊愕”不是来自于自己两个儿子的厮打,反而是害怕山峰的拳头伤到她自己。
人性的自私、冷酷可见一斑。
山峰终于以残忍的方式将皮皮杀害,而他的哥哥山岗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报仇也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将自己的弟弟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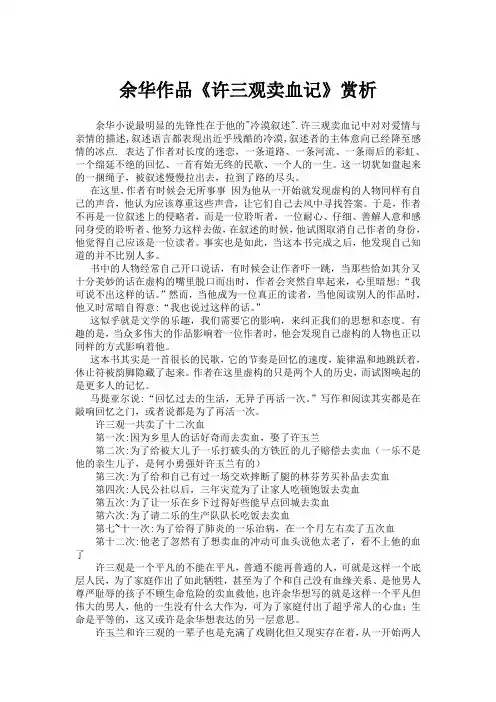
余华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赏析余华小说最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许三观卖血记中对对爱情与亲情的描述,叙述语言都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经降至感情的冰点. 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
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
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
”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们需要它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
有趣的是,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
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子再活一次。
”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许三观一共卖了十二次血第一次:因为乡里人的话好奇而去卖血,娶了许玉兰第二次:为了给被大儿子一乐打破头的方铁匠的儿子赔偿去卖血(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何小勇强奸许玉兰有的)第三次:为了给和自己有过一场交欢摔断了腿的林芬芳买补品去卖血第四次:人民公社以后,三年灾荒为了让家人吃顿饱饭去卖血第五次:为了让一乐在乡下过得好些能早点回城去卖血第六次:为了请二乐的生产队队长吃饭去卖血第七~十一次:为了给得了肺炎的一乐治病,在一个月左右卖了五次血第十二次:他老了忽然有了想卖血的冲动可血头说他太老了,看不上他的血了许三观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在平凡,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民,为了家庭作出了如此牺牲,甚至为了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是他男人尊严耻辱的孩子不顾生命危险的卖血救他,也许余华想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但伟大的男人,他的一生没有什么大作为,可为了家庭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心血;生命是平等的,这又或许是余华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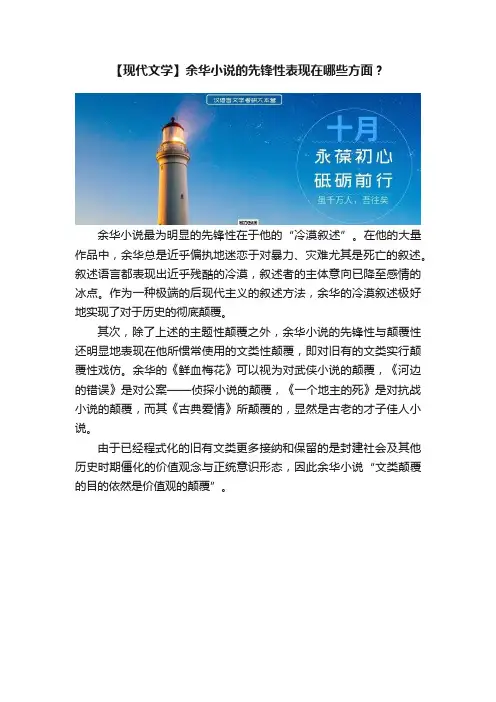
【现代文学】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
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余华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于对暴力、灾难尤其是死亡的叙述。
叙述语言都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
作为一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法,余华的冷漠叙述极好地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彻底颠覆。
其次,除了上述的主题性颠覆之外,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与颠覆性还明显地表现在他所惯常使用的文类性颠覆,即对旧有的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
余华的《鲜血梅花》可以视为对武侠小说的颠覆,《河边的错误》是对公案——侦探小说的颠覆,《一个地主的死》是对抗战小说的颠覆,而其《古典爱情》所颠覆的,显然是古老的才子佳人小说。
由于已经程式化的旧有文类更多接纳和保留的是封建社会及其他历史时期僵化的价值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因此余华小说“文类颠覆的目的依然是价值观的颠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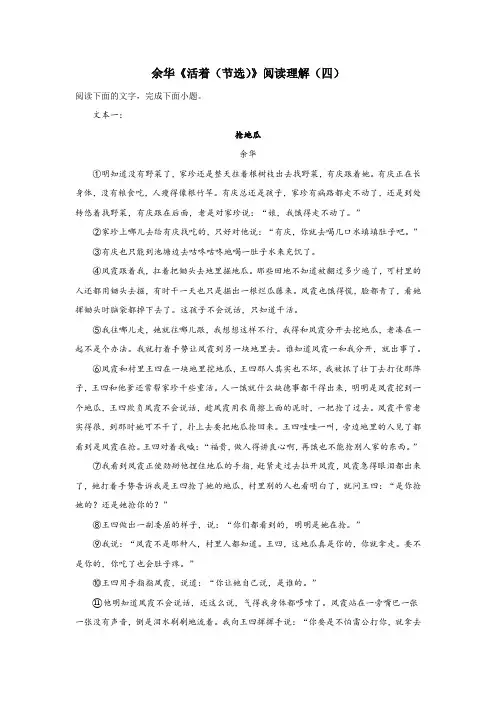
余华《活着(节选)》阅读理解(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抢地瓜余华①明知道没有野菜了,家珍还是整天拄着根树枝出去找野菜,有庆跟着她。
有庆正在长身体,没有粮食吃,人瘦得像根竹竿。
有庆总还是孩子,家珍有病路都走不动了,还是到处转悠着找野菜,有庆跟在后面,老是对家珍说:“娘,我饿得走不动了。
”②家珍上哪儿去给有庆找吃的,只好对他说:“有庆,你就去喝几口水填填肚子吧。
”③有庆也只能到池塘边去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水来充饥了。
④凤霞跟着我,扛着把锄头去地里掘地瓜。
那些田地不知道被翻过多少遍了,可村里的人还都用锄头去掘,有时干一天也只是掘出一根烂瓜藤来。
凤霞也饿得慌,脸都青了,看她挥锄头时脑袋都掉下去了。
这孩子不会说话,只知道干活。
⑤我往哪儿走,她就往哪儿跟,我想想这样不行,我得和凤霞分开去挖地瓜,老凑在一起不是个办法。
我就打着手势让凤霞到另一块地里去。
谁知道凤霞一和我分开,就出事了。
⑥凤霞和村里王四在一块地里挖地瓜,王四那人其实也不坏,我被抓了壮丁去打仗那阵子,王四和他爹还常帮家珍干些重活。
人一饿就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明明是凤霞挖到一个地瓜,王四欺负凤霞不会说话,趁凤霞用衣角擦上面的泥时,一把抢了过去。
凤霞平常老实得很,到那时她可不干了,扑上去要把地瓜抢回来。
王四哇哇一叫,旁边地里的人见了都看到是凤霞在抢。
王四对着我喊:“福贵,做人得讲良心啊,再饿也不能抢别人家的东西。
”⑦我看到凤霞正使劲掰他捏住地瓜的手指,赶紧走过去拉开凤霞,凤霞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打着手势告诉我是王四抢了她的地瓜,村里别的人也看明白了,就问王四:“是你抢她的?还是她抢你的?”⑧王四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你们都看到的,明明是她在抢。
”⑨我说:“凤霞不是那种人,村里人都知道。
王四,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
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会肚子疼。
”⑩王四用手指指凤霞,说道:“你让她自己说,是谁的。
”⑪他明知道凤霞不会说话,还这么说,气得我身体都哆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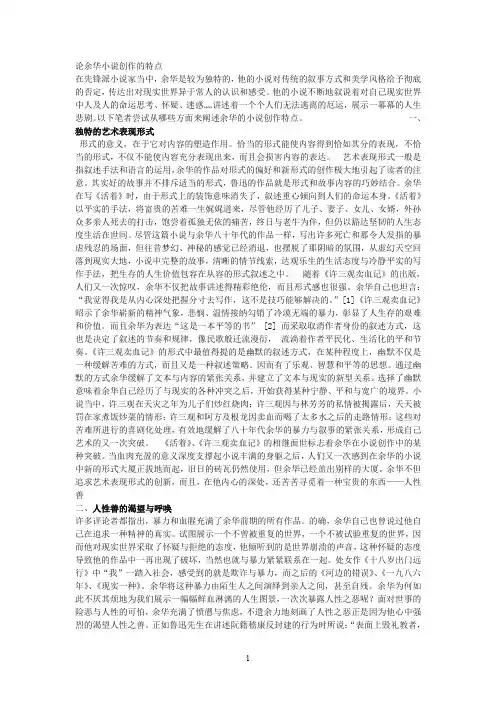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
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
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
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
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
《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
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
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
”[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
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 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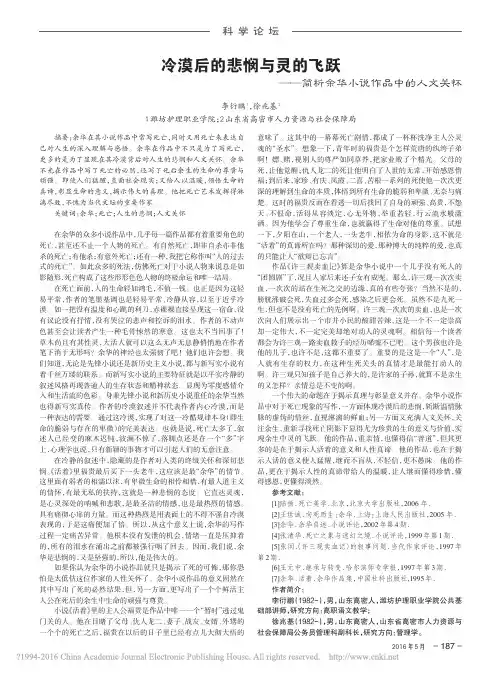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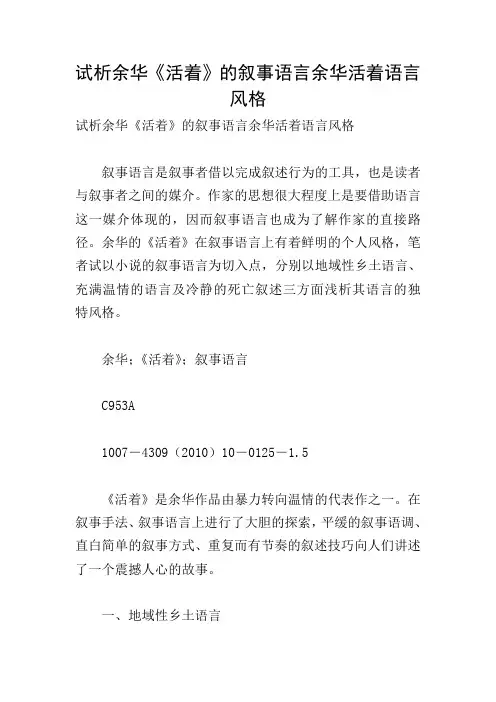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余华;《活着》;叙事语言C953A1007―4309(2010)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
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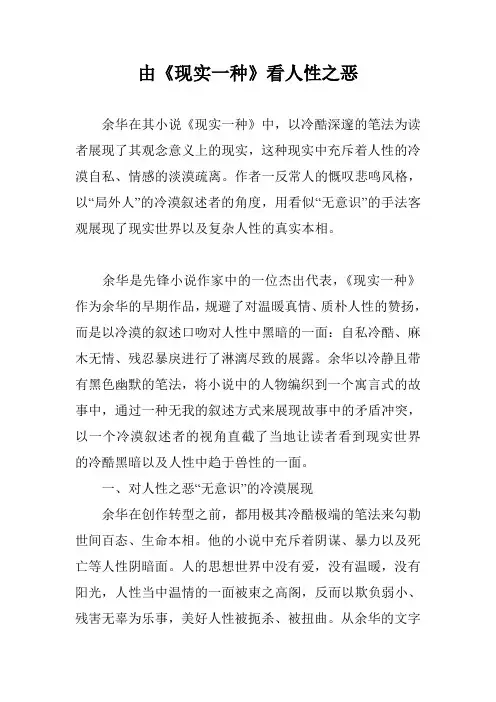
由《现实一种》看人性之恶余华在其小说《现实一种》中,以冷酷深邃的笔法为读者展现了其观念意义上的现实,这种现实中充斥着人性的冷漠自私、情感的淡漠疏离。
作者一反常人的慨叹悲鸣风格,以“局外人”的冷漠叙述者的角度,用看似“无意识”的手法客观展现了现实世界以及复杂人性的真实本相。
余华是先锋小说作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现实一种》作为余华的早期作品,规避了对温暖真情、质朴人性的赞扬,而是以冷漠的叙述口吻对人性中黑暗的一面:自私冷酷、麻木无情、残忍暴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露。
余华以冷静且带有黑色幽默的笔法,将小说中的人物编织到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中,通过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来展现故事中的矛盾冲突,以一个冷漠叙述者的视角直截了当地让读者看到现实世界的冷酷黑暗以及人性中趋于兽性的一面。
一、对人性之恶“无意识”的冷漠展现余华在创作转型之前,都用极其冷酷极端的笔法来勾勒世间百态、生命本相。
他的小说中充斥着阴谋、暴力以及死亡等人性阴暗面。
人的思想世界中没有爱,没有温暖,没有阳光,人性当中温情的一面被束之高阁,反而以欺负弱小、残害无辜为乐事,美好人性被扼杀、被扭曲。
从余华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人性中“恶”的因素实际上也是十分强大的,只是人们用理智与意志控制了它,才使得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得以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恶”真实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当理智与意志无法压制的时候,便会无意识地展现出来。
从主题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连环报复式的小说情节在各种民间故事中并不罕见,通常意义上来说,这种复仇母题的小说都会有一个事件起因,而且较为琐屑,一旦在特定条件下受到某种外界因素的催化,就会爆发、扩大,愈演愈烈,显示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远远敌不过恶劣的一面。
但是,余华的创新点在于将故事情节中的起因取消,将这种亲人之间的残忍仇杀视为一种盲目冲动,并将仇杀的对象主要设置在两兄弟之间,使人性中的恶性因素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将一个古老的复仇主题的故事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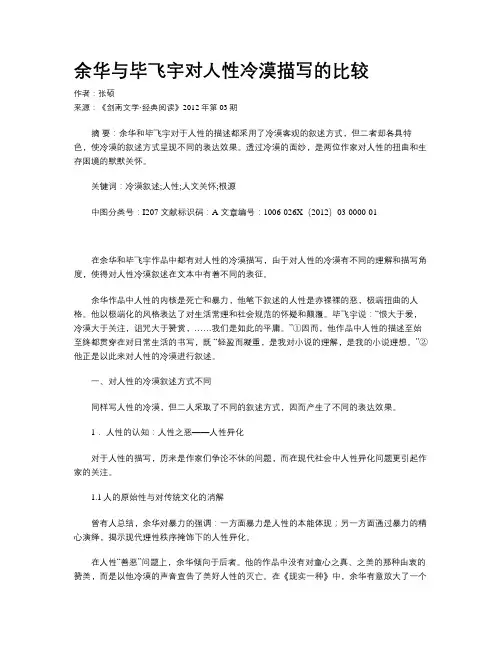
余华与毕飞宇对人性冷漠描写的比较作者:张硕来源:《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年第03期摘要:余华和毕飞宇对于人性的描述都采用了冷漠客观的叙述方式,但二者却各具特色,使冷漠的叙述方式呈现不同的表达效果。
透过冷漠的面纱,是两位作家对人性的扭曲和生存困境的默默关怀。
关键词:冷漠叙述;人性;人文关怀;根源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在余华和毕飞宇作品中都有对人性的冷漠描写,由于对人性的冷漠有不同的理解和描写角度,使得对人性冷漠叙述在文本中有着不同的表征。
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内核是死亡和暴力,他笔下叙述的人性是赤裸裸的恶,极端扭曲的人格。
他以极端化的风格表达了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和颠覆。
毕飞宇说:“恨大于爱,冷漠大于关注,诅咒大于赞赏,……我们是如此的平庸。
”①因而,他作品中人性的描述至始至终都贯穿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既“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
”②他正是以此来对人性的冷漠进行叙述。
一、对人性的冷漠叙述方式不同同样写人性的冷漠,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表达效果。
1.人性的认知:人性之恶——人性异化对于人性的描写,历来是作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问题更引起作家的关注。
1.1人的原始性与对传统文化的消解曾有人总结,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人性异化。
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余华倾向于后者。
他的作品中没有对童心之真、之美的那种由衷的赞美,而是以他冷漠的声音宣告了美好人性的灭亡。
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有意放大了一个幼童身上的暴力因子,借此告诉我们暴力就是天生罪恶的一种,即使在孩子身上也是难以逃脱。
1.2 人性的弱点与被异化毕飞宇的作品,着力为我们展现当下社会里人们身上所发生的精神裂变。
这期间是人性弱点的膨胀、是对自我身份重新确认定位的迷失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离破碎。
浅谈余华小说《第七天》的叙事特色作者:杨兆青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1期[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1-0-01《第七天》是当代实力派作家余华即《兄弟》之后沉寂七年推出的力作,跟《兄弟》问世之际一样遭受到两个极端的评价。
但正如余华所说,这是最能代表他全部风格的小说。
冷静的叙事态度,苦难叙事,死者叙事视角,散而不乱的叙事结构,这些呈现余华过去二十多年小说写作轨迹和作品由内及外的风格在《第七天》中都得以具体体现。
一、冷静的叙事态度同《活着》一样,《第七天》也一贯继承了余华冷静的叙事态度,借死者来冷眼叙事。
既然是死者就没有喜怒哀乐任何世人的情感,在叙事的时候自然可以不带感情色彩,冷眼旁观现实社会,冷漠地叙述现实社会中各种令人发指、愤激、悲悯的社会现象。
《第七天》中市长淫乱纵欲而亡,为推卸责任掩盖商场大火遇难人数,暴力拆迁导致郑小敏父母被埋,人们日常生活充斥着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作者在叙述这些时对当下官场没有丝毫的批判,对食品安全危机重重也没有表示出自己的担忧,仿佛自己是脱离于现实的人,可以冷眼旁观。
《第七天》书中援引大量的社会热点新闻,给人的感觉是像在堆砌事实而不是文学创作,但这正是余华一贯冷静叙事的表现。
作家如何才能够零距离表现社会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创作时尽少融入个人情感,让小说人物通过自身的苦难命运揭示出作者的情感倾向和社会现实的荒诞绝望。
二、苦难叙事的延续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公司职员死后,亡灵游走七天的所见所闻。
在叙事阳间和阴间的所见时,延续了余华一贯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苦难意识。
但与《活着》不同的是,他这次关注的不再是父辈们遥远的贫穷与无望,而直接选择关注我辈当下生活里的无奈与悲哀:被暴力拆迁致残,因病致贫致死、爱慕奢华未果而自杀、卖肾买墓地。
这些看似荒诞,但无法否认这是小人物卑微生活的典型体现。
《现实一种》里的先锋叙事《现实一种》余华在1986-1987年写作的小说,每一篇小说都可以被称为一个寓言。
他企图建构一个封闭的个人的小说世界,通过这种世界,赋予外部世界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图象模型。
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解释世界的冲动,仿佛一个少年人突然发现他掌握着世界的秘密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到处宣讲,他表面摹拟的老成中夹杂着一种错愕:事实上,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也确实发现了世界的另一面。
但这一时期他所刻意追求的“无我”的叙述效果迫使他不得不创造一个面具:一个冷漠的叙述者,结果,是他的冷漠而不是他的震惊留给当时的读者很深的印象。
余华在小说集《现实一种》的自序中说:“《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
”确实在作品中,冷酷寂寥的叙事语气,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人物形象,精确、无情的暴力场景描写,以及细微沉着的血腥刻画等等,无不使读者毛骨悚然,目瞪口呆,现实原来还存在这样的一种。
其实,通过对小说的仔细阅读和体会,恰恰相反,作者其实在试图进行一个充满童心、彰显人性、关怀终极的模式建构。
作者是热血奔腾的,对人生充满关爱和激情,只是他采取的叙事策略以及修辞风格的特殊性,都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冷酷、血腥、暴力背后的深层内涵。
叙事对世界的解释构成了作品所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一般哲学、伦理学、历史等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解释不是概念,而是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体验和情感态度,也就是故事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形态。
那么,在《现实一种》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作者所讲述的是一个近乎于丧失人性的极端冷血的家庭走向自我毁灭的故事,骨肉相残的循环和往复,是人性中残忍一面的真实表现,反省的是人性深层的劣质和污浊。
虽然其中也不乏还有人性尚存的几丝暖意,但这并不能改变作品整体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
浅析余华小说的冷漠叙述作者:孙崴崴来源:《科教导刊》2014年第31期摘要余华是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综观余华的作品,无论是描写罪恶、暴力还是死亡都体现出一种冷漠的叙述。
本文试从余华小说冷漠叙述的原因,以及从死亡、暴力、亲情中看余华的冷漠叙述来解读余华独特的写作风格,从而更好地理解余华的作品。
关键词余华冷漠叙述死亡暴力亲情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An analysis of Yu Hua's Novels inDifferent NarrativeSUN Weiwei(Liaoyuan Branch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Liaoyuan, Jilin 136200)Abstract Yu Hu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from Yu Hua's works, whether is the description of evil, violence and death are embodied a kind of indifferent narrative. This paper from the cause of Yu Hua's novel cold narrative, and see Yu Hua from death, violence, affection of indifferent narrative to interpretation of Yu Hua's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th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s of Yu Hua.Key words Yu Hua; Indifferent narrative; death; violence; family affections1 余华小说中冷漠叙述的原因余华本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被父亲安排成为一名牙科医生。
父女情感的温情与冷漠《活着》的角色分析《活着》的角色分析父女情感的温情与冷漠《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福贵一生的起伏经历,展现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父女情感中所蕴含的温情与冷漠。
本文将对小说中的角色进行分析,探讨父女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在情感交流中的不同表现。
一、父亲福贵福贵是本书的主人公,他经历了中国的革命、战乱以及经济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他与女儿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他温情与冷漠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温情的一面:福贵对女儿的温情体现在他对女儿生活的精心照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上。
在小说中,福贵竭尽全力为女儿寻找寄托和安慰,尽管自身生活处境困苦,却依然用心维系着父女之情。
他的爱体现在从小到大的悉心照料,无论是为女儿找老师学习,还是经济条件允许时给予的物质支持,都表现出他对女儿的深爱。
冷漠的一面:然而,福贵也存在着冷漠的一面。
尤其是在女儿离婚后,福贵对女儿的处境不闻不问,甚至没有主动关心的举动。
他似乎对女儿的问题毫不关心,对她的苦难毫无同情心。
这种冷漠的表现反映了父亲在困境面前的无奈和无力感。
二、女儿女儿是福贵与妻子之间的结晶,她在小说中扮演着情感交流的关键角色。
她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既是依恋又是矛盾的。
依恋的一面:女儿从小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在福贵的呵护下长大。
她对父亲的依赖和感激贯穿整个故事,在生活困境中,她经历着与父亲的相依为命,互相扶持的坚持。
父亲的爱让她感到温暖和安全,她对福贵的情感充满着依恋和感激。
矛盾的一面:然而,女儿对父亲也有着一定的矛盾情感。
尽管她对福贵的依赖和感激,但她也感受到父亲在情感交流中的冷漠。
福贵对她的失去兴趣以及对她婚姻问题的冷淡态度,让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害。
这种矛盾在女儿心中形成了一种对父亲的爱与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三、父女情感的温情与冷漠《活着》通过父亲福贵与女儿之间的亲情描写,展现了温情与冷漠交织的父女情感。
温情的体现:父亲福贵对女儿的温情体现在他艰苦生活环境中的精心照料和关怀,以及他对女儿的无私付出。
由《现实一种》谈余华的冷漠叙述
崔金英
摘要:
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现实一种》围绕人与人,尤其是亲人之间的暴力及死亡而一一展开。
在作品中,余华以一种纯审美的冷酷性和客观性一丝不苟地描述着人性作恶的每一步程序。
《现实一种》这种在内容上的杀气与形式上的平静则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他的冷漠叙述。
关键词:余华;《现实一种》;冷漠叙述
作为新时期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种因报复欲而膨胀起来的攻击性本能刻画得淋漓尽致,由此,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他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于对暴力、小说推演出了人生命中内在的一种兽性本能,对人性恶的现灾难,第2期上推出他的中篇新作,以其内容上的杀气及形式上的平静恰如其分地阐释了尤其是死亡的叙述,从某种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人性恶的象作了直接的暴露与暗示,这也无疑体现了余华冷漠叙述中证明。
在《现实一种》里,暴力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线索性话语。
作家对人性沉沦状态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暴力的特殊把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家既然要亵渎和消解“大写的人”,暴力自然是他们所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现实一种》里,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亲人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
山峰是成人暴力音符的第一个奏响者,皮皮摔死了他的儿子,某种意义上说,他本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更多的时候,他又把自己演变为暴力的制造者。
得知儿子被摔死后,山峰首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妻子毒打一通,接着向山岗狠揍两拳,而后对皮皮的施暴更是达到了极致:“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
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
他看到侄子挣扎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地不动了。
”山峰对侄子令人发指的残杀演示出人类某些不能自控的攻击性,从而彻底嘲笑了传统道德上的血肉亲情。
当山峰无限放大自己的复仇欲望时,他的存在就成为别人的一种灾难,尽管暴力把山峰武装成了他人的凶手,但受害的却是他自己。
皮皮的死直接导致了山岗对山峰的仇恨:在山岗的策划下,山峰经由一只小狗的舐舔,暴笑四十分钟而痛苦地死掉。
小说通过对夫妻之间、叔侄之间及兄弟之间的暴力描述,开始揭开了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对亲情的崇高和神圣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小说对暴力还原为一种日常的家庭化状态,把人性深层中那对暴力的人性恶还原除涉及普通成年人的生活化状态外,还从更深层面上触及到了儿童的暴力品性,这种暴力的表现应该更能代表余华探索“人性恶”所达到的深度。
皮皮虽说只有四岁,但他对于堂弟的施暴却激情万分:“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
..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
他就这样不断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爆破似的哭声。
后来当他再松开手时,堂弟已经没有那种充满激情的哭声了,只不过是张着嘴一颤一颤地吐气。
于是他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便走开了。
”在这段描写中,余华一反常人对童心之真、童趣之美的那种褒扬与赞美,再次以他冷漠的声音宣告了美好人性的灭亡。
他告诉我们人性本恶,而暴力就是天生罪恶的一种,即使在孩童身上也是锋芒毕露,就更不要说那些在社会的黑色染缸里浸泡过的成年人了。
如果说在其他先锋作家如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小说中,暴力更多的是土匪、流氓、恶棍这类边缘状态中的“人”的话,那么到了余华的《现实一种》里,暴力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它不再是那些恶人的行为特征,而是几乎所有人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的一种普遍性。
虽说山峰的老母亲和山岗的妻子并没有赤裸裸的暴行,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人施暴过程中她们所持有的那种漠然抑或欣赏的心态,就使暴力更具有了某种残酷性。
她们虽说
没有亲自动手杀人,可谁又能说她们身上潜藏的暴力倾向会不如他人呢?人们说余华是中国作家中一个最冷酷的人性杀手,我想从余华对暴力与人性的洞悉来看,这种论断还是正确的。
二
余华是写死亡小说的好手,《现实一种》同样如此。
余华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描写死亡的作家,然而,他对死亡的强烈关注及其直接体验性地抒写却打破了中国“重生轻死”的传统生命哲学。
余华对死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热情,作为其冷漠叙述内容的一部分,死亡这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频频出现。
当山峰的儿子和皮皮相继成为死亡的实践者后,山峰又被其哥哥推向了死亡之海的浪尖。
余华对山峰死亡过程的描述不是为一个普通生命的消失,而是通过山峰死亡过程中凶手及旁观者态度的描写,来展示人世间最冰冷的亲情。
当一个人将杀死亲弟弟当作自己最大的心愿时,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黯然神伤的呢?当一个人的施暴欲望无限扩大时,死亡在小说中真可谓遍地开花了。
皮皮施暴而被山峰踢死,山岗处死山峰,山岗又被山峰的妻子决绝地送上刑场并被解剖。
这一连串互为因果的死亡事件几乎渗透到了小说的字里行间。
一方面,施暴者以自己的无人性疯狂地残夺着他人的生命;,作为一种报应,死亡又以毫无商量地来到了他们面前。
暴力是人性沉沦光下的菜花地。
”余华将常人眼中令人肮脏的东西(尸体解剖后流动的脂肪)比喻为“棉花”与“阳光下的菜花地”,这样的描写使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对死尸的厌恶或恐惧,而只能体会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冷漠,从而获得一种纯审美的抒情意味。
也就是说,余华总是心安理得地在悲剧故事的背后寻找那种冷漠的感觉,使那些苦难的悲剧场景转变为一种无关痛痒的生动。
在《现实一种》里,余华沉浸在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审美状态中,犹如摄像机一样在冷静客观的状态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些悲剧场景。
余华对所讲述的一切不作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不流露丝毫的主体情感,而恰恰就是这种纯审美的冷酷和客观性的叙事风格,使对暴力与死亡不露声色的言说更具有血腥意味,生发出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三
如果说余华小说“冷漠叙述”内容上的杀气是由对暴力与死亡的言说构成,那么其形式上的平静则具体体现为对暴力与死亡的讲述所展示的那种纯审美的冷酷性和客观性。
作为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余华对于传统文学叙事风格的不以为然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没有叙事风格上的这种颠覆,《现实一种》至少在形式上就会逊色不少。
《现实一种》的故事本身是沉重且充满窒息的悲剧气息的,但在这里,暴力与死亡不仅不具有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懑和呼天抢地的痛苦,反而呈现出一种把玩和欣赏的态度。
我们通常对暴力与死亡的那种畏惧,却被一种看似理性的“乐观主义”态度所化解了。
小说中对“死亡”的冷观性的“远视”和审美化的造型随处可见:皮皮有着“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的死;山峰母亲有“笑容像是相片一样固定下来”的死。
余华对此不仅显得无动于衷,而且当他描写山岗被解剖的过程中,有一种欣赏和抒情意味跃然纸上:“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
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
于是医生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阳下的菜花怎样开花。
四
余华的这种冷漠叙述也许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余华生活在杭州湾里的一座小城:海盐。
这里有幽深的胡同,长满青苔的院墙,晃晃悠悠的石板小街,头顶上是灰暗的天空,窗外流着一条肮脏的小河..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余华一直强烈地感到被束缚被禁锢,他常常梦到自己滑到一个周围长满青苔的黑黝黝的井里,然后就是杀人,惊险追捕,于是梦想头脑状态的一种表现;死亡是个体生命在客观上的消失。
山峰等人在施暴后的死亡倒是一种幸运,至少他们可以
在客观上完成个人对人性沉沦状态的告别。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实一种》正是以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使人性恶的漫漫黑夜显现出了一丝闪亮的豁口。
参考文献
[1]朱伟.关于余华[J ].钟山, 1989, ( 4).
[2]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这种梦境常常缠绕着他,使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
这种对生存的惊恐感慢慢造就了余华对人生冷酷的敏感,使他笔下的语言失去了情感色彩,我们看到的只是暴力剧增、罪恶泛滥这样一幅幅丑恶的图景。
在《现实一种》里,我们看到,即使是充满温馨气息的亲情,在他笔下那无休止的暴力及杀戮甚至解剖中也不堪一击,一切有关亲情的崇高和神圣,都被其不露声色地颠覆与瓦解了。
他轻易抹杀了人性中温馨的亲情面纱,拒绝用虚假的小说为读者提供纯娱乐性的作品,而是道出了人类生存的恐惧。
有人把作家对于人的生存黑暗及人性罪恶的夸张言说看作是“人文关怀的失落”。
[2]其实不然,生活中虽不乏有蓝天白云,但也有余华所生存着的“灰暗的天空”和“肮脏的小河”;人性固然有真善美的一面,但也有阴暗角落。
在《现实一种》里,余华没有丝毫的媚俗,他没有使小说成为某种道德的说教,而是以其特有的冷漠叙述完成了对人类生存阴暗面的揭示。
这位当过医生因而其笔触显得更加犀利的小说家,其笔端流露出的往往是饱含理性的真实,但理性与真实有时是不讲究伦理温情的,而这种理性的真实也会使读者通过人物来冷静客观地审视自身,其精神的最终指向是光明的。
《现实一种》虽然没有拘泥于一时一地具体而微的事实,它却以深切的思索和体察,更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最高限度地描写和展示“人性中阴暗的真实”而引起人类自身的醒悟与警戒,对于作家,这也是一种人文关怀! 1997,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