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 格式:pdf
- 大小:200.88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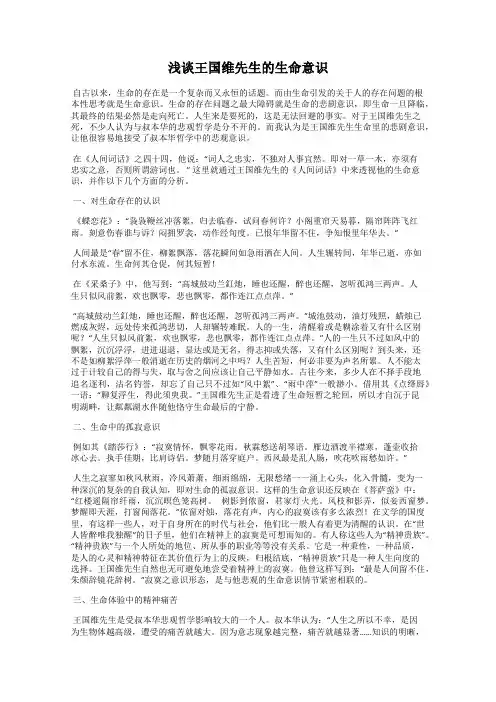
浅谈王国维先生的生命意识自古以来,生命的存在是一个复杂而又永恒的话题。
而由生命引发的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就是生命意识。
生命的存在问题之最大障碍就是生命的悲剧意识,即生命一旦降临,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死亡。
人生来是要死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对于王国维先生之死,不少人认为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是分不开的。
而我认为是王国维先生生命里的悲剧意识,让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叔本华哲学中的悲观意识。
在《人间词话》之四十四,他说:“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
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 这里就通过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来透视他的生命意识,并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对生命存在的认识《蝶恋花》:“袅袅鞭丝冲落絮,归去临春,试问春何许?小阁重帘天易暮,隔帘阵阵飞红雨。
刻意伤春谁与诉?闷拥罗衾,动作经旬度。
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
”人间最是“春”留不住,柳絮飘落,落花瞬间如急雨洒在人间。
人生辗转间,年华已逝,亦如付水东流。
生命何其仓促,何其短暂!在《采桑子》中,他写到:“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
”“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城池鼓动,油灯残照,蜡烛已燃成灰烬,远处传来孤鸿悲切,人却辗转难眠。
人的一生,清醒着或是糊涂着又有什么区别呢?“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
”人的一生只不过如风中的飘絮,沉沉浮浮,进进退退,显达或是无名,得志抑或失落,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头来,还不是如柳絮浮萍一般消逝在历史的烟河之中吗?人生苦短,何必非要为声名所累。
人不能太过于计较自己的得与失,取与舍之间应该让自己平静如水。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沽名钓誉,却忘了自己只不过如“风中絮”、“雨中萍”一般渺小。
借用其《点绛唇》一语:“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
”王国维先生正是看透了生命短暂之轮回,所以才自沉于昆明湖畔,让粼粼湖水伴随他恪守生命最后的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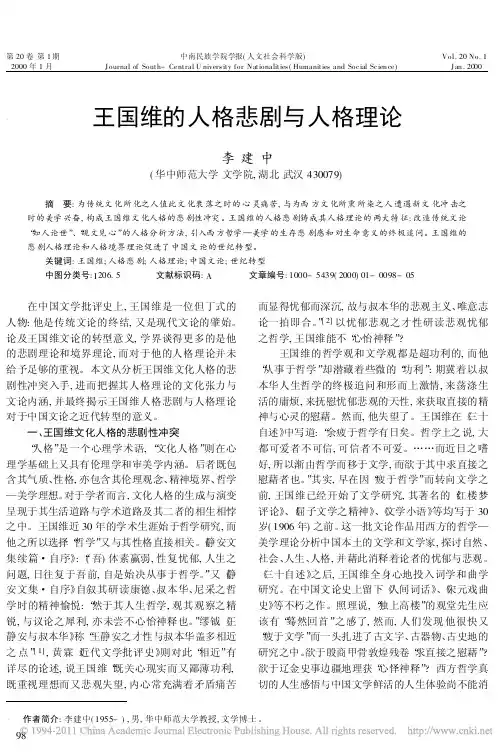
第20卷第1期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0No.1 2000年1月 J 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 ce) J an.2000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李建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人格悲剧;人格理论;中国文论;世纪转型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1-0098-05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是一位但丁式的人物:他是传统文论的终结,又是现代文论的肇始。
论及王国维文论的转型意义,学界谈得更多的是他的悲剧理论和境界理论,而对于他的人格理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从分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入手,进而把握其人格理论的文化张力与文论内涵,并最终揭示王国维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对于中国文论之近代转型的意义。
一、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文化人格”则在心理学基础上又具有伦理学和审美学内涵。
后者既包含其气质、性格,亦包含其伦理观念、精神境界、哲学—美学理想。
对于学者而言,文化人格的生成与演变呈现于其生活道路与学术道路及其二者的相生相悖之中。
王国维近30年的学术生涯始于哲学研究,而他之所以选择“哲学”又与其性格直接相关。
《静安文集续篇・自序》:“(吾)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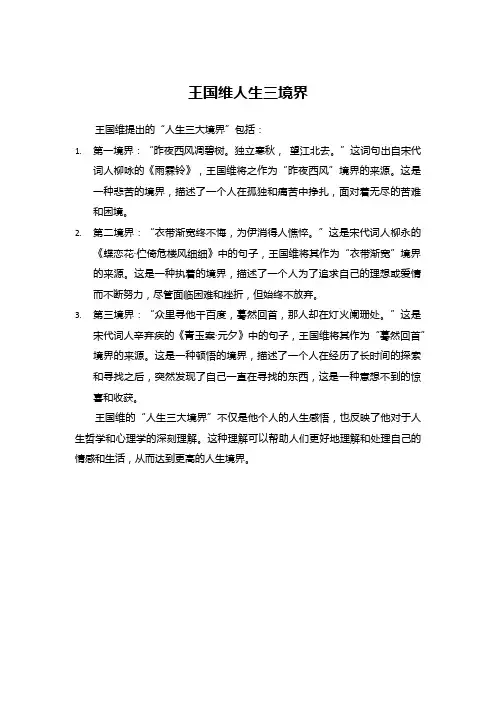
王国维人生三境界
王国维提出的“人生三大境界”包括:
1.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立寒秋,望江北去。
”这词句出自宋代
词人柳咏的《雨霖铃》,王国维将之作为“昨夜西风”境界的来源。
这是一种悲苦的境界,描述了一个人在孤独和痛苦中挣扎,面对着无尽的苦难和困境。
2.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宋代词人柳永的
《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中的句子,王国维将其作为“衣带渐宽”境界的来源。
这是一种执着的境界,描述了一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或爱情而不断努力,尽管面临困难和挫折,但始终不放弃。
3.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
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句子,王国维将其作为“蓦然回首”
境界的来源。
这是一种顿悟的境界,描述了一个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寻找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
王国维的“人生三大境界”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感悟,也反映了他对于人生哲学和心理学的深刻理解。
这种理解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从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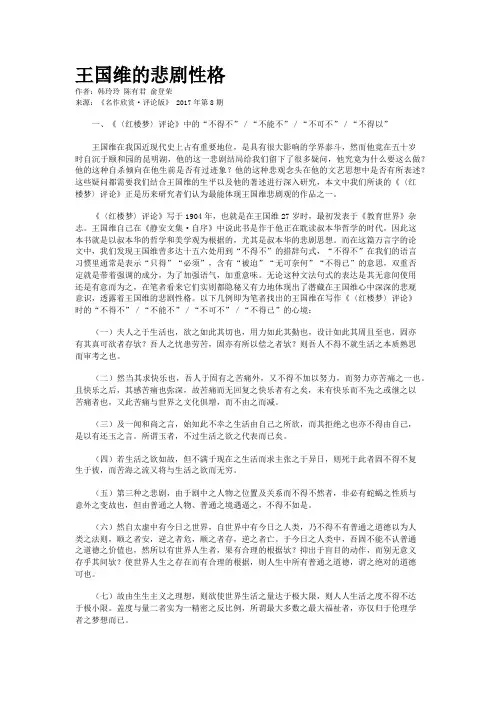
王国维的悲剧性格作者:韩玲玲陈有君俞登荣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8期一、《〈红楼梦〉评论》中的“不得不”/“不能不”/“不可不”/“不得以”王国维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学界泰斗,然而他竟在五十岁时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他的这一悲剧结局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疑问,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这种自杀倾向在他生前是否有过迹象?他的这种悲观念头在他的文艺思想中是否有所表述?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结合王国维的生平以及他的著述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中我们所谈的《〈红楼梦〉评论》正是历来研究者们认为最能体现王国维悲剧观的作品之一。
《〈红楼梦〉评论》写于1904年,也就是在王国维27岁时,最初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
王国维自己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此书是作于他正在耽读叔本华哲学的时代,因此这本书就是以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观为根据的,尤其是叔本华的悲剧思想。
而在这篇万言字的论文中,我们发现王国维曾多达十五六处用到“不得不”的措辞句式,“不得不”在我们的语言习惯里通常是表示“只得”“必须”,含有“被迫”“无可奈何”“不得已”的意思,双重否定就是带着强调的成分,为了加强语气,加重意味。
无论这种文法句式的表达是其无意间使用还是有意而为之,在笔者看来它们实则都隐秘又有力地体现出了潜藏在王国维心中深深的悲观意识,透露着王国维的悲剧性格。
以下几例即为笔者找出的王国维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的“不得不”/“不能不”/“不可不”/“不得已”的心境:(一)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二)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
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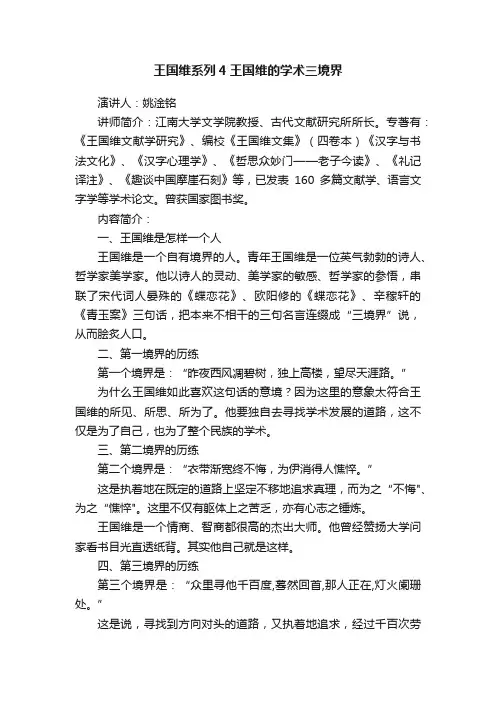
王国维系列4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演讲人:姚淦铭讲师简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专著有:《王国维文献学研究》、编校《王国维文集》(四卷本)《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礼记译注》、《趣谈中国摩崖石刻》等,已发表160多篇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术论文。
曾获国家图书奖。
内容简介: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一个自有境界的人。
青年王国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
他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宋代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脍炙人口。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喜欢这句话的意境?因为这里的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
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为之“憔悴"。
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都很高的杰出大师。
他曾经赞扬大学问家看书目光直透纸背。
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次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入真理之长河,这是何等地令人欣慰!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
王国维这样一个大学者,上课的时候,对研究生们讲过:我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
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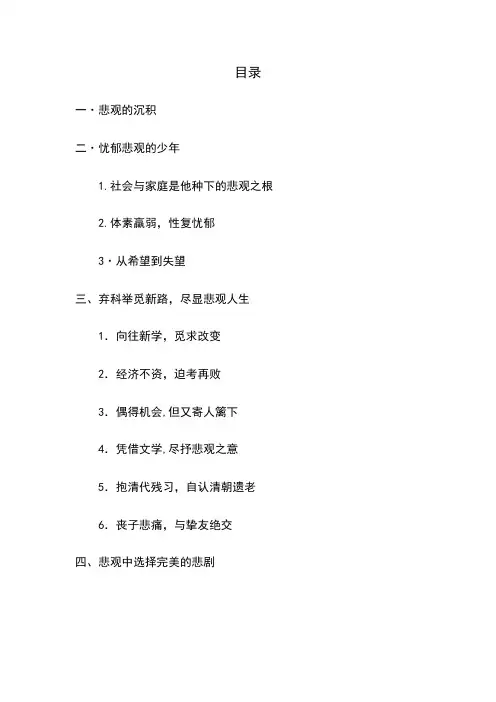
目录一·悲观的沉积二·忧郁悲观的少年1.社会与家庭是他种下的悲观之根2.体素羸弱,性复忧郁3·从希望到失望三、弃科举觅新路,尽显悲观人生1.向往新学,觅求改变2.经济不资,迫考再败3.偶得机会,但又寄人篱下4.凭借文学,尽抒悲观之意5.抱清代残习,自认清朝遗老6.丧子悲痛,与挚友绝交四、悲观中选择完美的悲剧内容提要社会与家庭是他种下的悲观之根.从小就体素羸弱的他在时间与实践不断演化下慢慢地形成复性忧郁的性格,他的人生也就开始了悲观的路程,最后也以完美的悲观的方式结束人生.时间在点滴地消逝,王国维的死因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思,他选择维护他的尊严,学术尊严,感觉自己信仰的文化体系已不复存在,悲观的色彩沉浸了他整个人生,只有选择理性地结束生命,打下最后一个句号,凄怨的灵魂,忧郁悲观的大师在昆明湖饰演了完美的悲剧。
岁月沧桑呼吸着是上世纪头二十年的空气,文化续写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是否我们也会有哲人之举,用我们毕生的时间和生命来灌注我们的文化,愿我们能在哲人的庇佑下让我们及我们的文化能走得越远越久。
关键词:王国维悲观主义忧郁悲观人生悲剧略谈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一·悲观的沉积1927年6月2日,一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遗留下来的一条长辫纵身一跃,自杀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下,这可以说是震惊中外,至今,对于他的死因还是众说疑云,有为清朝,为政治,为人事纠葛,还有说只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而我认为这都是王国维先生在他的悲观人生中所存在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些都带走了,带走的堪称悲剧性完美。
时间在点滴地消逝,王国维的死因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思,而他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点燃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轨迹,他的悲观主义人生也时刻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伴随他一生。
二·忧郁悲观的少年1.社会与家庭是他种下的悲观之根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社会被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尝试以不同的方法去寻找救国的道路,,然而这社会的悲惨现实让王国维不堪入目,开始怀疑社会,怀疑儒家道德宿命论,也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寻找这就过路线,寻找自身目标,改变社会现实,在他的《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里写道:“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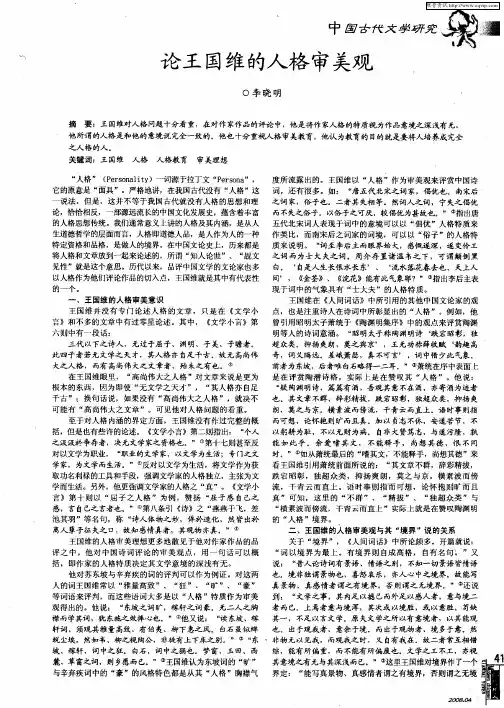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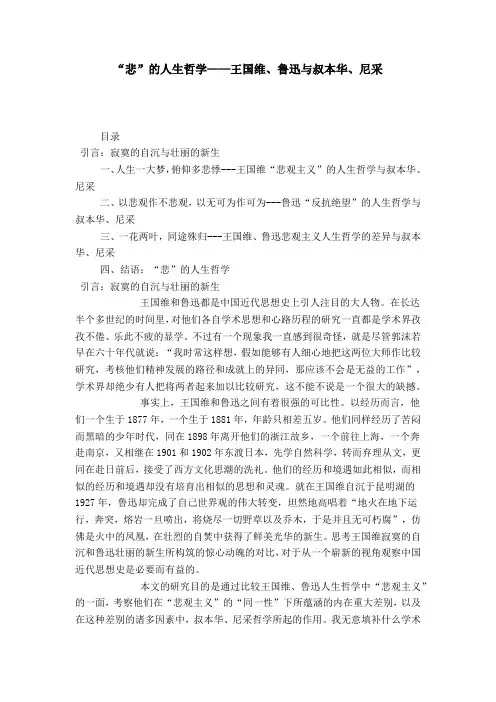
“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目录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
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
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
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
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
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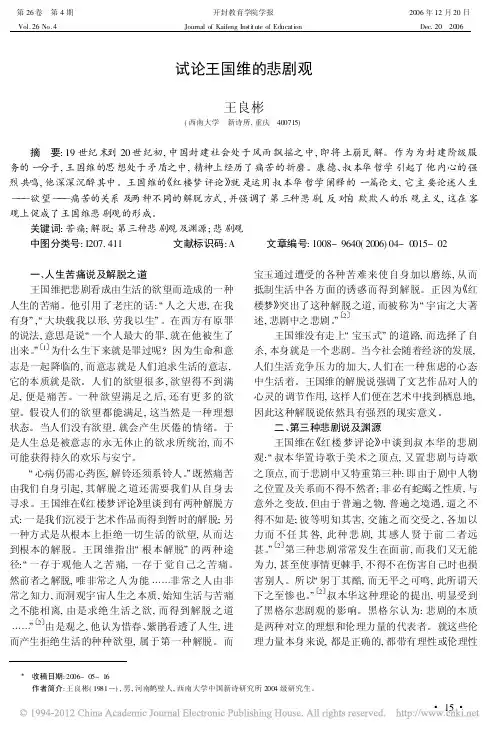
第26卷第4期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12月20日Vol.26No.4Journal of Kaifeng Ins ti tute of Educati on Dec.202006试论王国维的悲剧观王良彬(西南大学新诗所,重庆400715)摘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即将土崩瓦解。
作为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一分子,王国维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精神上经历了痛苦的折磨。
康德、叔本华哲学引起了他内心的强烈共鸣,他深深沉醉其中。
王国维的5红楼梦评论6就是运用叔本华哲学阐释的一篇论文,它主要论述人生)))欲望)))痛苦的关系及两种不同的解脱方式,并强调了第三种悲剧,反对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王国维悲剧观的形成。
关键词:苦痛;解脱;第三种悲剧观及渊源;悲剧观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40(2006)04-0015-02一、人生苦痛说及解脱之道王国维把悲剧看成由生活的欲望而造成的一种人生的苦痛。
他引用了老庄的话:/人之大患,在我有身0,/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0。
在西方有原罪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人最大的罪,就在他被生了出来。
0112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罪过呢?因为生命和意志是一起降临的,而意志就是人们追求生活的意志,它的本质就是欲。
人们的欲望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便是痛苦。
一种欲望满足之后,还有更多的欲望。
假设人们的欲望都能满足,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
当人们没有欲望,就会产生厌倦的情绪。
于是人生总是被意志的永无休止的欲求所统治,而不可能获得持久的欢乐与安宁。
/心病仍需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
0既然痛苦由我们自身引起,其解脱之道还需要我们从自身去寻求。
王国维在5红楼梦评论6里谈到有两种解脱方式:一是我们沉浸于艺术作品而得到暂时的解脱;另一种方式是从根本上拒绝一切生活的欲望,从而达到根本的解脱。
王国维指出/根本解脱0的两种途径:/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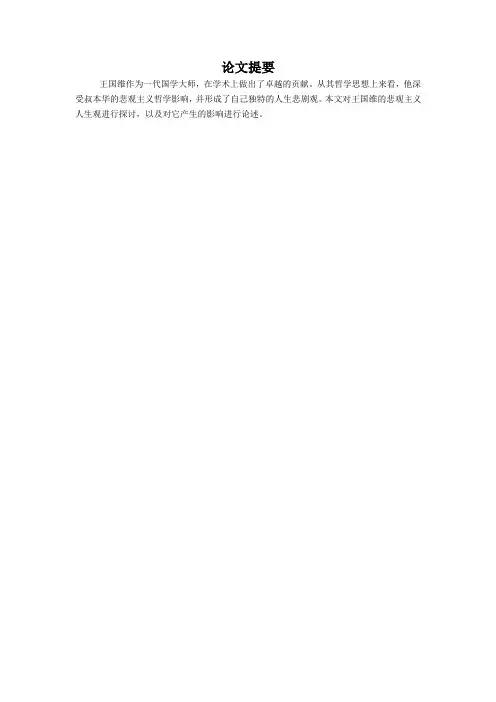
论文提要王国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在学术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其哲学思想上来看,他深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悲剧观。
本文对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进行探讨,以及对它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
浅谈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的风雨飘摇中。
面对着政局的动乱,文化的多元纷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被王国维所接受,并与其自身的坎坷经历、以及与传统文化中悲观厌世哲学所交汇,形成了王国维所固有的悲观主义哲学。
王国维重视引进西方哲学,促进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认识。
关键词: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王国维的一生充满着“悲情”,这种“悲情”在他的代表作《红楼评论》、《人间词话》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可以说他的思想深处受叔本华的影响,并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人生实践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悲观主义人生观一直伴随着王国维的始终,使他成为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悲壮的实践者。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之成因从王国维思想的内因出发,王国维的这种悲观主义人生观离不开其忧世情怀与忧生情结。
而从外因来看,他受西方思想特别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尤为的重要。
(一)独具的忧世情怀与忧生情结忧世、忧国情怀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比较突出。
王国维先祖忠勇壮烈,为国捐躯。
其父曾做过县府幕僚,希望作为长子的王国维可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少年时的王国维就曾写下:“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读剑南诗”,这已表明了他已经有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安邦济业的志向。
他关心实事,仰慕康、梁,曾为六君子事件有“颇有扼腕,捶胸,搔首问天之慨”。
忧生情结贯穿人生的始终。
王国维幼失母怙,父亲又在外经商从幕,而作为长子身上的责任较重。
加之考科举时多次落第,在《时务报》工作时的诸多不快,长子早逝,与罗振玉绝交等等,这些造就了他悲观忧郁的性格。
王国维在《游通州湖心亭》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
据考证,他的《静安诗稿》共27首,其中带“苦”字的就有10首。
收稿日期:2005-12-05作者简介:邱艳艳(1980-),女,河南唐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思想邱艳艳(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人类的历史就是悲剧相伴的历史。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开始注目中国的悲剧,中国学者也尝试引进西方观点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
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悲剧理论开拓了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新视野。
关键词:悲剧;红楼梦;王国维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06)01-0117-02 悲剧最早形成于古希腊,是人类对生命、对灵魂、对艺术、对世界和宇宙探索的结果。
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和西方历史上的悲剧相比,中国古代的悲剧基本上都有完美的结局,属于悲喜相间的混合剧,所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悲剧,更没有出现悲剧理论,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有关悲剧的论述,不仅具有典型意义,且弥补了中国传统悲剧美的空白。
要了解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就要了解其美学,要了解其美学,就要了解其哲学。
而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其悲观主义的人生必有着悲观主义的哲学。
王国维生活在时局频繁更替,形势瞬息万变的社会时代,他的哲学就是要探索人生真理,以便对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类未来的前途,获得一种根本的回答。
他从叔本华、康德那里所接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使他所追求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给他带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也使其一生在思想上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充满着悲观主义。
王国维美学思想受西学与国学的影响。
在西学中,主要以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尤以叔本华的影响最为突出,他的人生哲学建立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观念。
人生悲剧的解脱在于拒绝意志,美的本质及作用在于无利害及对人生的解脱,这些思想也即成了他的美学思想和悲剧观念的基础。
另一方面,王国维深受老庄哲学的厌世思想和对梦境的追寻的影响,这些又同叔本华哲学中的悲观主义融合在一起(虽然二者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经过王国维的过滤、熔炼、体验和深刻反思,已成为他自己的思想了。
王国维自杀分析及其启示【摘要】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死因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谜,本文从静安先生之性情,亲情和友情的变故及变乱时代三个角度探究先生真正死因。
死亡值得每个人严肃的生活人思考,尤其是自杀。
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先生的自沉引发了许多的思考和启示。
本文分析先生死因时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在得出启示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谈起。
【关键词】王国维;自杀;启示;和谐社会。
王国维狩猎领域覆盖哲学、文学、戏剧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敦煌文献和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诸多学科,其学问磅礴令学人折服。
但在其学术生涯如日中天时,他却以自杀的方式辞别了这个世界。
他的死因一直成为世人关注,各种揣测各抒其理,却又不能完全让人们信服。
笔者资质浅,学养薄,但前人之分析尚觉有不妥之处。
对于自沉之因,各立场不同的人士,有不同说法,主要有几种:有为故国前清殉葬说; 有静安先生之死是罗振玉迫害之说;有缘于对国民革命军恐惧一说等等。
笔者每每念及先生之自沉,为之叹息,为之思索。
自杀是一种极端的毁灭自我的方式,若是其人无大悲痛,无大孤独,无心灵之极度折磨岂能自杀?本文将从静安先生之性情、亲情和友情的变故和变乱的时代三个角度分析先生之死亡真正原因。
一、静安先生之性情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行为.静安先生的自沉和他的性格中两上因素不可分:一个是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性格,另一个就是他的忧郁悲观性格。
下面我们分别展开。
㈠、理智与情感的矛盾。
先生从事考证和器物研究等是理性十足的人,但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出这样严谨的学人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
“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从这句诗中可见他在学知的同时也是彷徨困惑甚至悲哀的。
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导致他几度绝望。
叶嘉莹定义为“知”与“情”,两者导致他的悲剧人生。
“知与情都发达的性格,虽然在学术方面造成了静安先生的过人的地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却又造成静安先生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走向自杀的一项重要因素” [1]。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
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
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
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
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
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
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
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
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
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
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
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
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
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
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
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
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
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
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王国维的境界说作者:叶水涛来源:《七彩语文·教师论坛》2020年第08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现今谈词学免不了要谈到王国维,谈到《人间词话》。
王国维及他的《人间词话》,名气很大,有点文史常识和文学修养的,侃大山常常会提及。
说到王国维,少不了说他是教授的教授,是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齐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论词,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的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界也。
”今天一些做学问的人,常常会提及这几句词,以此自勉,也以此教导后之来者。
做学问而不知道这三种境界,则属孤陋寡闻无疑。
香港有位才子叫董桥,有段时间在内地颇有名声。
“读点董桥”,甚至成为文化人圈子里的流行语。
董桥也提出治学的三境界,他说:“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頒,十万工农下吉安。
”此为第一重境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此为第二重境界;“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此为第三重境界。
这三句都出自毛泽东所写的词。
董桥的治学三境界的新论,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董桥的确很有些学问,散文独具一格,但似乎也没有到非读不可的程度。
新创治学三境界说,比肩王国维,调侃一下当然可以,但就学术水准而言,当然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今天我们常把王国维论“境界”的表述抽离出来,不仅仅用于象征治学的境界,而且看作是理想追求与完美人格的隐喻。
三句话构成既相互呼应,又层次分明的完整意境,有美感,有张力,极富象征意义,也有充分的可阐释性。
从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作中摘句来形容三种“境界”,这当然需要有独到的眼光和丰富的学识,非王国维他人断难做到。
2013.07学教育28王国维悲剧理论管窥谢建文(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0)[摘要]王国维是将“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从西方输入中国的第一人。
其思想深受西学和国学的双重影响。
本文将从悲剧的分类、悲剧的价值等几个方面理解《〈红楼梦〉评论》阐释的悲剧理论。
[关键词]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理论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塘,又号永观。
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一个兼营商业的地主家庭,对哲学、史学等均有研究,著作颇丰。
他是最早运用西方美学观念审视中国文学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发展的新阶段”。
[1]王国维的思想及学术观点是一个驳杂的矛盾集合体,受到西学和国学的双重影响。
在西学中,主要是以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尤以叔本华的影响最为突出。
他的人生哲学就建立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观念之上。
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意志”本身又表现为“欲”,“欲”永远不能满足,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止无尽的痛苦。
因此,人生就是痛苦,人生悲剧的解脱就在于拒绝意志。
途径有两个,一是“宗教式”的涅槃,另一个是沉浸在艺术欣赏之中,即“美”之中。
这些思想成为王国维美学思想和悲剧观念的基础。
在中学方面,王国维深受老庄哲学厌世思想和对梦境追寻的影响,这些又与叔本华哲学中的悲观主义融合在一起,经过王国维的过滤、熔炼、体验和深刻反思,成为了他思想的一部分。
他对《红楼梦》评价极高,认为《红楼梦》写尽了欲望带给人的苦痛,并指明了解决苦痛的方法。
本文将以《〈红楼梦〉评论》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王国维的悲剧理论。
其一,悲剧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而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本质、人的自我发现、自我觉醒的问题。
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悲剧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悲剧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悲剧的欣赏主要是一种独立于个人利害之外的审美经验。
第20卷第1期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0No.1 2000年1月 J 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 ce) J an.2000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李建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人格悲剧;人格理论;中国文论;世纪转型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1-0098-05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是一位但丁式的人物:他是传统文论的终结,又是现代文论的肇始。
论及王国维文论的转型意义,学界谈得更多的是他的悲剧理论和境界理论,而对于他的人格理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从分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入手,进而把握其人格理论的文化张力与文论内涵,并最终揭示王国维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对于中国文论之近代转型的意义。
一、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文化人格”则在心理学基础上又具有伦理学和审美学内涵。
后者既包含其气质、性格,亦包含其伦理观念、精神境界、哲学—美学理想。
对于学者而言,文化人格的生成与演变呈现于其生活道路与学术道路及其二者的相生相悖之中。
王国维近30年的学术生涯始于哲学研究,而他之所以选择“哲学”又与其性格直接相关。
《静安文集续篇・自序》:“(吾)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又《静安文集・自序》自叙其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哲学时的精神愉悦:“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称“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则对此“相近”有详尽的论述,说王国维“既关心现实而又鄙薄功利,既重视理想而又悲观失望,内心常充满着矛盾痛苦而显得忧郁而深沉,故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一拍即合。
”[2]以忧郁悲观之才性研读悲观忧郁之哲学,王国维能不“心怡神释”?王国维的哲学观和文学观都是超功利的,而他“从事于哲学”却潜藏着些微的“功利”:期冀着以叔本华人生哲学的终极追问和形而上激情,来荡涤生活的庸烦,来抚慰忧郁悲观的天性,来获取直接的精神与心灵的慰藉。
然而,他失望了。
王国维在《三十自述》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其实,早在因“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之前,王国维已经开始了文学研究,其著名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语》等均写于30岁(1906年)之前。
这一批文论作品用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家,探讨自然、社会、人生、人格,并藉此消释着论者的忧郁与悲观。
《三十自述》之后,王国维全身心地投入词学和曲学研究。
在中国文论史上留下《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不朽之作。
照理说,“独上高楼”的观堂先生应该有“蓦然回首”之感了,然而,人们发现他很快又“疲于文学”而一头扎进了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之中。
欲于殷商甲骨敦煌残卷“求直接之慰藉”?欲于辽金史事边疆地理获“心怿神释”?西方哲学真切的人生感悟与中国文学鲜活的人生体验尚不能消98作者简介:李建中(1955-),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弥静安忧郁悲观之万一,何况这些古拙而冰冷的器物文字?当人们在丁卯年夏日的昆明湖发现观堂先生的遗书和遗体时,同时也发现观堂先生所“疲于”的不仅仅是哲学或文学或别的什么学。
从哲学到文学到上古文字器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或治学方法的转换,而是从学术研究的特定角度揭示出王国维心灵的苦痛和心路历程的曲折。
王国维冀望以学术活动来抚慰精神的痛苦来消弥人格的冲突,但这无异抽刀断水、举杯浇愁。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最喜“登临”的观堂先生并没有能够“望尽天涯路”而是走向了昆明湖。
王国维自沉之后,第一位从文化的角度追问王国维之死因的学者是陈寅恪。
1927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P10)[3]死亡是一种生命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死亡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
王国维对死亡的选择,既是对其文化人格的自我塑造,又是其文化人格之悲剧性冲突的必然结果。
文化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构成,深寓其中的是人格主体的文化理想与文化认同,而昭显于外的则是人格主体的文化形象。
考察王国维的一生,其人格形象并不是统一的或首尾一贯的。
50年间,他既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同时也是“为彼文化(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既是新世纪的先行者,又是旧世纪的献祭者。
离开家乡海宁之前,王国维受过长达15年的传统教育,这是他“为此文化所化”的关键时期。
紧随其后的是对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研讨与讲授,他在本世纪初所撰写的哲学—美学论文,他对屈原、《红楼梦》以及崇高、古雅等问题的研究,全然是一位近现代文化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但是,对“彼文化”的信奉与宣传既不足以减缓对“此文化”担当之沉重,更不能改变殉“此文化”结局之悲怆。
在生命的最后四、五年(从“南方房行走”到自沉昆明湖),王国维虔诚地认同于传统文化,并将自己的生命系于此文化而异常痛苦地徘徊于生与死之临界。
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的学问是新的而情感是旧的。
我以为,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对本土文化情有独钟,却又为异域文化“心怡神释”;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却将生命系于一种文化及其该文化之符号(宣统皇帝);虔诚地行走于禁苑皇宫,却又热情地拥抱叔本华尼采;选择“外来之观念”[4]及新思想新文化之同时,却选择与传统文化“共命而同尽”[4]。
王国维的文化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不仅有着新旧、中西的矛盾,还有着体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意识与方法、问学与处世等各种层面的悖立或冲突。
而在所有的冲突背后,是文化的冲突,是文化人格的冲突。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指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
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
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所谓“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实质上就是《王静安先生挽词并序》所指出的“文化精神”。
陈寅恪将“中国文化”定义为“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l者。
”而“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P10-11)[3]旧文化虽“不可救疗”却仍有人“强聒而力持”,新文化虽呼之欲出却阻障重重。
值此中国文化艰难之转型期,王国维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风熏染之中的知识分子对新文化的憧憬,另一方面则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对旧文化的依恋。
既无法抵御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诱惑,更无法卸脱传统文化的重负。
因此,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不可避免,正如王国维的死不可避免。
二、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站在传统文化立场来考察,王国维有着很好看的人格形象,用梁启超的话说,“先生盖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诸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
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梁启超甚至将王国维的自沉与屈原的自沉相提并论。
[5]论其为文与为人,论其情感与情操,王国维的人格形象都是无可挑剔的;而论其最终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取向,王国维的人格形象是悲剧性的。
而这种悲剧性正在于他将自己高洁的人格连同天才学者的生命,真诚地献祭于业已衰颓的文化符号。
99第20卷 李建中: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王国维以他对死亡方式的选择,最终铸成其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内涵;而在王国维自塑其文化人格的同时,也在他的文艺理论中建构起系统、深遽并具有文化张力的人格理论。
“人格”一词既来自于西语,“人格”作为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亦来自西方文化。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受西方文化影响,才开始在自己的文化及文论研究中使用“人格”概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人格”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作出深入探讨的非观堂先生莫属;反过来说,王国维文论中的人格理论,以其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对本土文化的改造,从特定角度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近代转型。
王国维之所以在文学研究中提出人格问题,首先还是受西方文学及文化的影响。
《文学小语》第十四则指出,与西方文学相比,吾国之叙事的文学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
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曲则殊不称是。
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
以东方古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叙事文学之成败在于人物塑造,而人物塑造之关键又在于“描写人格”,丢失了对人格的描写,纵然有“系统之词”亦会丢失“词之性质”,足见人格问题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意义和价值。
王国维认为,东方文学虽有着古老悠久之传统,但在叙事文学的创作上却无法与西方文学匹敌,原因正在于斯。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没有“人格”这一概念,但关于人格的文论思想还是有的。
比如,古文论中“人品”、“才性”、“程器”等等,就不同程度地含有“人格”内涵。
受传统文论“言志”、“载道”、“讽谏”、“教化”等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古代文论家之讨论人格问题,常常局限在伦理道德的区囿之中。
而王国维文论中的人格理论,其对人格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王国维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看法是“超功利”,《文学小语》第一则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并断言“的文学,决非文学也。
”《红楼梦评论》亦指出文学之功能,在于“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基于此,王国维对文学家之人格亦提出“超功利”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