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及其研究视角的综述
- 格式:doc
- 大小:18.5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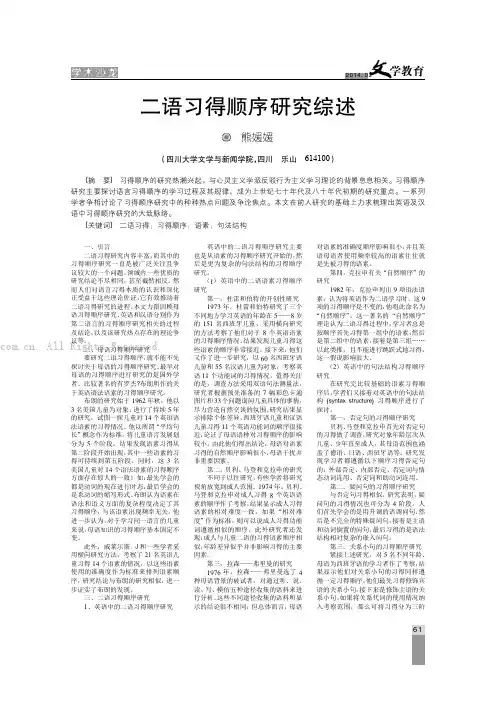
2014.02学教育61二语习得顺序研究综述熊媛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100)[摘要]习得顺序的研究热潮兴起,与心灵主义学派反驳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背景息息相关。
习得顺序研究主要探讨语言习得顺序的学习过程及其规律,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重点。
一系列学者争相讨论了习得顺序研究中的种种热点问题及争论焦点。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梳理出英语及汉语中习得顺序研究的大致脉络。
[关键词]二语习得;习得顺序;语素;句法结构一、引言二语习得研究内容丰富,而其中的习得顺序研究一直是被广泛关注且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
领域内一些优质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然而人们对语言习得本质的认识和深化正受益于这些理论佐证,它有效推动着二语习得研究的进程。
本文力图回顾母语习得顺序研究、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顺序研究相关的过程及结论,以及该研究热点存在的理论争议等。
二、母语习得顺序研究要研究二语习得顺序,就不能不先探讨关于母语的习得顺序研究。
最早对母语的习得顺序进行研究的是国外学者。
比较著名的有罗杰?布朗所作的关于英语语法语素的习得顺序研究。
布朗的研究始于1962年秋,他以3名美国儿童为对象,进行了持续5年的研究,试图一探儿童对14个英语语法语素的习得情况。
他以所谓“平均句长”概念作为标准,将儿童语言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
结果发现语素习得从第二阶段开始出现,其中一些语素的习得可持续到第五阶段。
同时,这3名美国儿童对14个语法语素的习得顺序方面存在惊人的一致!如:最先学会的都是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最后学会的是系动词的缩写形式。
布朗认为语素在语法和语义方面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习得顺序,与该语素出现频率无关。
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学习同一语言的儿童来说,母语知识的习得顺序基本固定不变。
此外,威莱尔斯.J 和一些学者采用横向研究方法,考察了21名英语儿童习得14个语素的情况,以这些语素使用的准确度作为标准来排列语素顺序,研究结论与布朗的研究相似,进一步证实了布朗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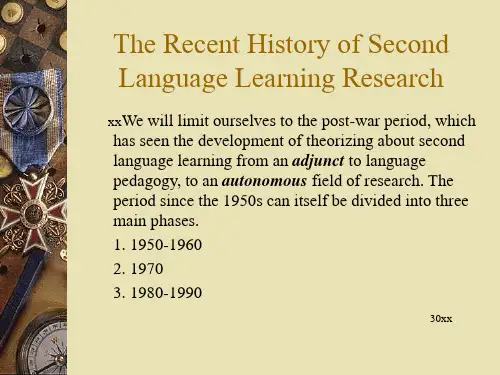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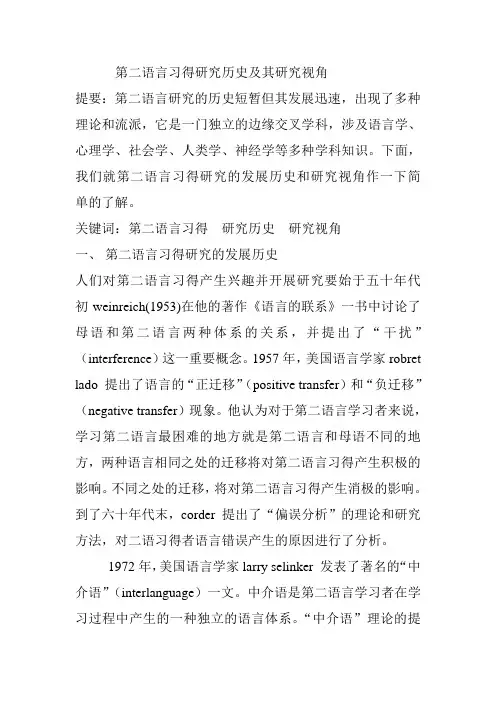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及其研究视角提要:第二语言研究的历史短暂但其发展迅速,出现了多种理论和流派,它是一门独立的边缘交叉学科,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经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下面,我们就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视角作一下简单的了解。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研究视角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人们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兴趣并开展研究要始于五十年代初weinreich(1953)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联系》一书中讨论了母语和第二语言两种体系的关系,并提出了“干扰”(interference)这一重要概念。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obret lado 提出了语言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
他认为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第二语言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二语言和母语不同的地方,两种语言相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消极的影响。
到了六十年代末,corder 提出了“偏误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972年,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 发表了著名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一文。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
“中介语”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
70年代末、80年代初,krashen(1982)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型,这一模型全面的解释了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并且为外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议也最多的语言习得模型。
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以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语言运用的过程。
有人认为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也有观点说语言系统和认知过程分别按大脑的不同部位处理不同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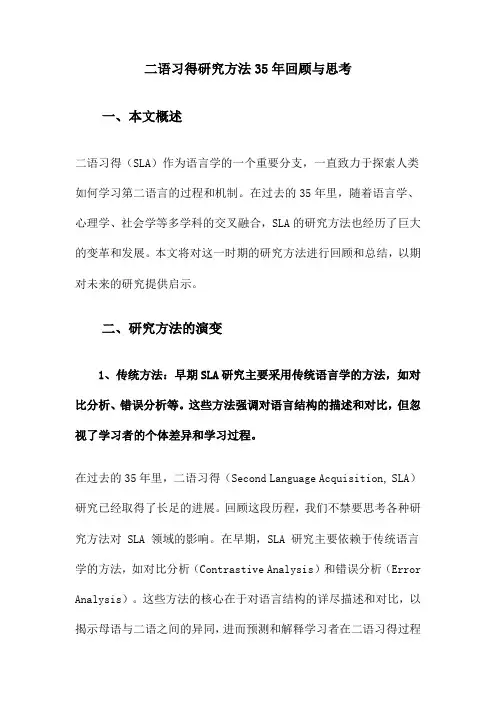
二语习得研究方法35年回顾与思考一、本文概述二语习得(SLA)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致力于探索人类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和机制。
在过去的35年里,随着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SLA的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研究方法的演变1、传统方法:早期SLA研究主要采用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如对比分析、错误分析等。
这些方法强调对语言结构的描述和对比,但忽视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过程。
在过去的35年里,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不禁要思考各种研究方法对 SLA 领域的影响。
在早期,SLA 研究主要依赖于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如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和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
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对语言结构的详尽描述和对比,以揭示母语与二语之间的异同,进而预测和解释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错误。
然而,这些传统方法的一个显著缺陷是忽视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过程。
它们假定所有学习者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和速度发展二语能力,而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人背景、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以及学习环境等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这些方法也未能深入探究学习者是如何逐步构建和发展二语能力的,即学习过程的动态性和互动性。
因此,尽管传统方法在 SLA 研究的初期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们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二语习得的过程和机制,SLA 研究者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和视角,以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二语习得的复杂现象。
2、心理语言学方法: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兴起,SLA研究开始关注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如认知、记忆、注意等。
这些方法强调实验设计和量化分析,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兴起,第二语言习得(SLA)研究开始深入探索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这无疑为SLA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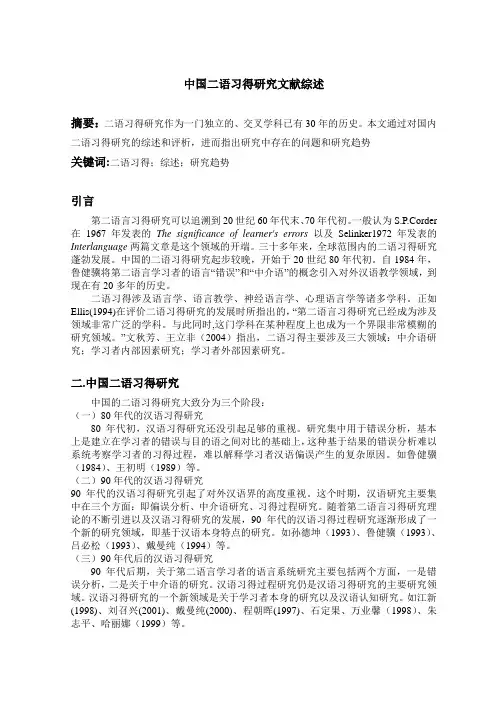
中国二语习得研究文献综述摘要: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已有30年的历史。
本文通过对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综述和评析,进而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关键词:二语习得;综述;研究趋势引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般认为S.P.Corder 在1967年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以及Selinker1972年发表的Interlanguage两篇文章是这个领域的开端。
三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二语习得研究蓬勃发展。
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自1984年,鲁健骥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和“中介语”的概念引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到现在有20多年的历史。
二语习得涉及语言学、语言教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正如Ellis(1994)在评价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时所指出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成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学科。
与此同时,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个界限非常模糊的研究领域。
”文秋芳、王立非(2004)指出,二语习得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中介语研究;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研究。
二.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8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80年代初,汉语习得研究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研究集中用于错误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学习者的错误与目的语之间对比的基础上,这种基于结果的错误分析难以系统考察学习者的习得过程,难以解释学习者汉语偏误产生的复杂原因。
如鲁健骥(1984)、王初明(1989)等。
(二)9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9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引起了对外汉语界的高度重视。
这个时期,汉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习得过程研究。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的不断引进以及汉语习得研究的发展,90年代的汉语习得过程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基于汉语本身特点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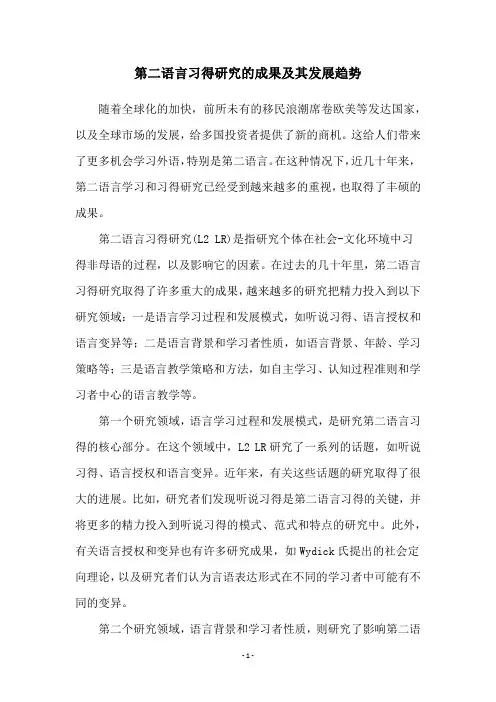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成果及其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席卷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市场的发展,给多国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学习外语,特别是第二语言。
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十年来,第二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L2 LR)是指研究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习得非母语的过程,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精力投入到以下研究领域:一是语言学习过程和发展模式,如听说习得、语言授权和语言变异等;二是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如语言背景、年龄、学习策略等;三是语言教学策略和方法,如自主学习、认知过程准则和学习者中心的语言教学等。
第一个研究领域,语言学习过程和发展模式,是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部分。
在这个领域中,L2 LR研究了一系列的话题,如听说习得、语言授权和语言变异。
近年来,有关这些话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比如,研究者们发现听说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听说习得的模式、范式和特点的研究中。
此外,有关语言授权和变异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如Wydick氏提出的社会定向理论,以及研究者们认为言语表达形式在不同的学习者中可能有不同的变异。
第二个研究领域,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则研究了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特别是它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有关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
研究者们发现,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人口统计学特征都会对第二语言习得造成影响。
此外,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也可能对习得成果有影响,如自主学习和交互学习等。
研究者们还发现,第二语言习得还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如家庭语言环境、学校语言环境以及社会语言环境等。
最后,研究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第三个领域,语言教学策略和方法。
近年来,认知过程准则和学习者中心的语言教学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流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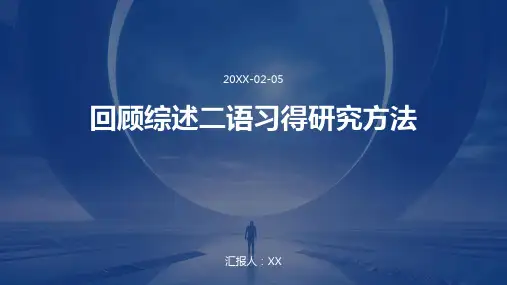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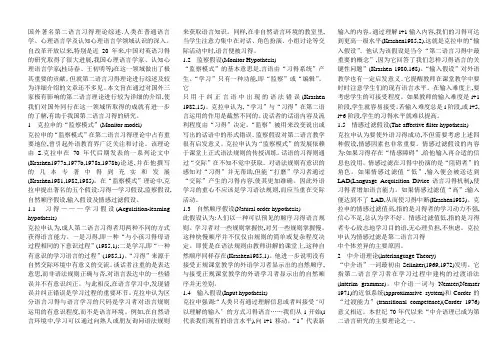
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人类在普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认知心理语言学领域认识的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对英语习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国心理语言学家、认知心理语言学家(桂诗春、王初明等)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就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进行综述及较为详细介绍的文章还不多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三家极有影响的第二语言理论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使我们对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进一步的了解,有助于我国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
1克拉申的“监察模式”(Monitor model)克拉申的“监察模式”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曾引起外语教育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该理论由S.克拉申在7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Krashen1977a,1977b,1978a,1978b)论述,并在他撰写的几本专著中得到充实和发展(Krashen1981,1982,1985)。
在“监察模式”理论中,克拉申提出著名的五个假设:习得—学习假设,监察假设,自然顺序假设,输入假设及情感过滤假设。
1.1习得———学习假设(Acg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克拉申认为,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者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获得语言能力。
一是习得,即一种“与小孩习得母语过程相同的下意识过程”(1985,1);二是学习,即“一种有意识的学习语言的过程”(1985,1)。
“习得”来源于自然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的交流。
谈话者注重的是表达意思,而非语法规则正确与否,对语言表达中的一些错误并不有意识纠正。
与此相反,在语言学习中,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
克拉申认为区分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的尺码是学习者对语言规则运用的有意识程度,而不是语言环境。
例如,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学习可以通过向熟人或朋友询问语法规则来获取语言知识。
同样,在非自然语言环境的教室里,当学生注意力集中在对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交际活动中时,语言便被习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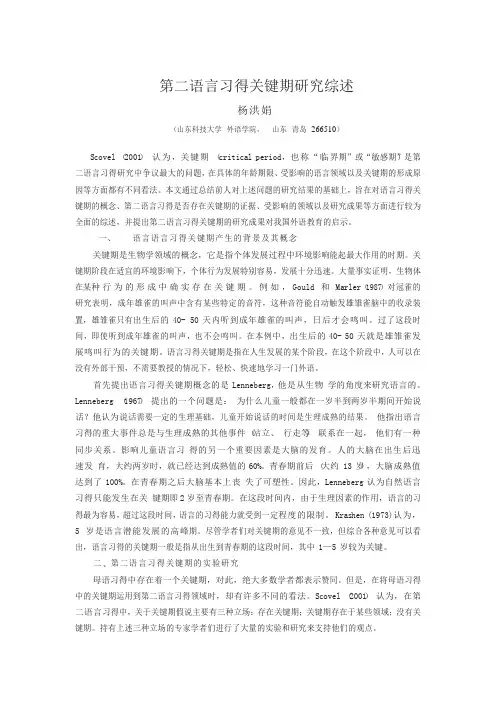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综述杨洪娟(山东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山东青岛266510)Scovel (2001)认为,关键期(critical period,也称“临界期”或“敏感期”)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在具体的年龄期限、受影响的语言领域以及关键期的形成原因等方面都有不同看法。
本文通过总结前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旨在对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概念、第二语言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的证据、受影响的领域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并提出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语言语言习得关键期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关键期是生物学领域的概念,它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能起最大作用的时期。
关键期阶段在适宜的环境影响下,个体行为发展特别容易,发展十分迅速。
大量事实证明,生物体在某种行为的形成中确实存在关键期。
例如,Gould 和Marler(1987)对冠雀的研究表明,成年雄雀的叫声中含有某些特定的音符,这种音符能自动触发雄雏雀脑中的收录装置,雄雏雀只有出生后的40- 50 天内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日后才会鸣叫。
过了这段时间,即使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也不会鸣叫。
在本例中,出生后的40- 50 天就是雄雏雀发展鸣叫行为的关键期。
语言习得关键期是指在人生发展的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可以在没有外部干预,不需要教授的情况下,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外语。
首先提出语言习得关键期概念的是Lenneberg,他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
Lenneberg (1967)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儿童一般都在一岁半到两岁半期间开始说话?他认为说话需要一定的生理基础,儿童开始说话的时间是生理成熟的结果。
他指出语言习得的重大事件总是与生理成熟的其他事件(站立、行走等)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一种同步关系。
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脑的发育。
人的大脑在出生后迅速发育,大约两岁时,就已经达到成熟值的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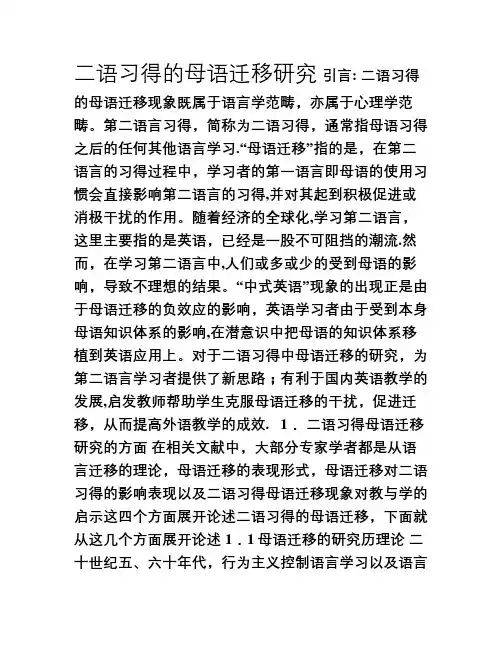
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研究引言: 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现象既属于语言学范畴,亦属于心理学范畴。
第二语言习得,简称为二语习得,通常指母语习得之后的任何其他语言学习.“母语迁移”指的是,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即母语的使用习惯会直接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并对其起到积极促进或消极干扰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学习第二语言,这里主要指的是英语,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在学习第二语言中,人们或多或少的受到母语的影响,导致不理想的结果。
“中式英语”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母语迁移的负效应的影响,英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本身母语知识体系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把母语的知识体系移植到英语应用上。
对于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的研究,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国内英语教学的发展,启发教师帮助学生克服母语迁移的干扰,促进迁移,从而提高外语教学的成效. 1.二语习得母语迁移研究的方面在相关文献中,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是从语言迁移的理论,母语迁移的表现形式,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表现以及二语习得母语迁移现象对教与学的启示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1母语迁移的研究历理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控制语言学习以及语言教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Lado在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20 世纪 60 年末到 70 年代初,乔姆斯基普遍语法观点,过渡语( inter—language,也称中介语) 理论、错误分析( error analysis,也称偏误分析)兴起。
在对比分析研究中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结果确实证实了 Lado 等人的理论但是,也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了“距离 = 难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发现学习者往往是在母语与目的语表面上相似的地方更容易犯错误等,同时对比分析对于学习者错误的预测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标记理论被引入母语迁移现象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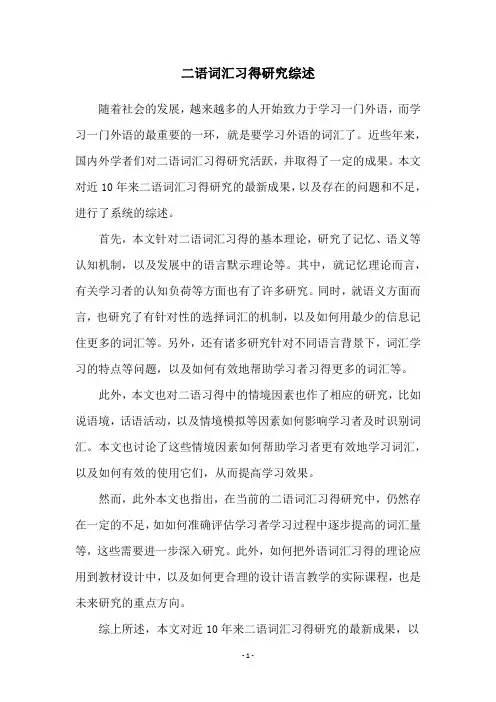
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学习一门外语,而学习一门外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学习外语的词汇了。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对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活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文对近10年来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的综述。
首先,本文针对二语词汇习得的基本理论,研究了记忆、语义等认知机制,以及发展中的语言默示理论等。
其中,就记忆理论而言,有关学习者的认知负荷等方面也有了许多研究。
同时,就语义方面而言,也研究了有针对性的选择词汇的机制,以及如何用最少的信息记住更多的词汇等。
另外,还有诸多研究针对不同语言背景下,词汇学习的特点等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地帮助学习者习得更多的词汇等。
此外,本文也对二语习得中的情境因素也作了相应的研究,比如说语境,话语活动,以及情境模拟等因素如何影响学习者及时识别词汇。
本文也讨论了这些情境因素如何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学习词汇,以及如何有效的使用它们,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然而,此外本文也指出,在当前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如何准确评估学习者学习过程中逐步提高的词汇量等,这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如何把外语词汇习得的理论应用到教材设计中,以及如何更合理的设计语言教学的实际课程,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综上所述,本文对近10年来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最新成果,以
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的综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词汇学习的过程,以及相关学习策略,从而更好地帮助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取得长进。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综述一、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加,第二语言学习已成为教育领域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作为影响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本文旨在对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综述,以期为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为有效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而采取的一系列思维和行为活动。
这些策略涉及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如词汇记忆、语法理解、听力训练、口语表达等。
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不仅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成果,还反映其学习风格和自主学习能力。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学习策略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并探讨了其与学习成绩、学习动力、学习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也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关注如何通过策略培训提高学习者的策略意识和使用能力,进而促进其第二语言学习的发展。
尽管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对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分类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在策略使用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如何将策略培训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等。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理解和应用,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和深远影响的领域。
通过全面综述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旨在为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1. 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及挑战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不仅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更是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拓宽国际视野的必备能力。
第二语言学习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沟通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国际间的合作与发展。
第二语言学习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引言二语习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20 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二语习得不仅涉及所学语言系统本身,还受到学习者母语系统、认知心理、个体差异(年龄、性别、学习态度、动机学习能力等)、语言学习和使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使二语习得要考察这些因素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动态系统研究,考查对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影响。
二语习得涉及的以上因素同时也是其他独立学科(如理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的研究对象。
结合各领域的研究内容,二语习得的研究对象又可划分为三大领域:中介语研究、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研究。
二语习得研究可以是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
它吸收了不同视角下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并利用这些不同领域的有关研究方法。
二语习得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学习者在掌握母语之后如何习得另一套新语言体系。
显然,二语习得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跨学科、多样化特点,而不同研究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对于不同学科研究结果和方法的整合有助于推进二语习得研究科学化发展。
二、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Sharwood曾对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于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研究者试图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进行对比分析,为语言的普遍现象的假设寻找理论上依据。
第二阶段以“中介语”和“创造性的建构”为标志,将第二语言学习同样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学习过程,研究重点转移到分析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学习策略上。
第三阶段注重多种理论引导下的实证研究以及与各领域研究方法结果的结合。
随着二语习得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研究者不断提出新的假设,并利用多种研究方法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
研究方法也从定性研究逐渐转向定量分析,并注重二者的结合,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现代科技快速的发展,计算机模拟语言和功能性磁共振技术(FMRI)、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RPs)等不断使用研究二语习得的神经和生物学基础。
2021回顾综述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范文 1.引言 二语习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概形成于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二语习得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研究者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学习者在掌握母语之后如何学习另一套新语言体系(戴炜栋 2008).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跨学科、多样化特点,而不同研究方法产生了不同研究结果,致使各研究之间的可验证性、可对照性削弱.由此,回顾综述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对于推进二语习得研究更加科学、有效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研究现状 为客观准确地描述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我们采用以下步骤分别检索中文和外文期刊数据库:(1)通过试查相关专业数据库确定中英文检索词及其扩展同义词和近义词:第二语言/二语/语言/外语/英语(secondlanguage or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orEnglish)、习得 / 学习(acquisition or learning)、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2) 厘清专业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编制检索式:不同检索词用"* "或"and"连接,同义词和近义词用"+ "或"or"连接.(3)为保证检索的查准率和查全率,根据检索结果反复调整检索式,得到最切合本研究文献检索的中英文检索式:(第二语言+ 二语 + 语言 + 外语 + 英语)* (习得 + 学习)*(研究方法)(second language or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or English ) and (acquisition orlearning) and (research method*) (外文数据库中"* "指截词符,在此检索式中"* "表示可检索含词干"method"的所有词). 在综合类外文期刊数据库EBSCOhost 中我们以题名为字段对 1984 -2013 年的数据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源自国外知名外语学术期刊的 12 篇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论文.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相同方式进行检索,共得到 25 篇相关论文,其中 10 篇来自外语类核心期刊.由此可见,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较受重视却并不多见.对 37 篇学术论文题名、关键词和摘要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约 65% 的论文是关于二语习得研究某一方面的研究方法,如习得顺序、词汇习得、普遍语法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等的研究方法,约 35%的论文较全面地概述了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这表明全面综述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论文更为少见.此外,这类论文中引用率指数最高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 35 年:回顾与思考》(文秋芳,王立非 2004)一文是概述社会科学研究普适的量化、质化等研究方法,且发表至今已过去十余年.有鉴于此,结合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二语习得研究状况,基于其本身的研究特点和研究焦点对主要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总结,无疑有助于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者从中获得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参考借鉴. 3.研究方法综述框架 在综述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论文中,不同学者对二语习得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归类方法.Ellis和 Barkhuizen(2005) 将学习者语言样本分为非语言使用样本、学习者口头或书面语言样本和学习者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报告,并依此介绍语言样本的收集和分析方法.Litosseliti(2010)将二语习得研究分为观察、实验和准实验研究.Mackey 和Gass(2012)认为二语习得研究框架可主要分为基于语言学的、基于心理学的和基于社会学的框架.吴旭东(2002)根据研究目的将二语习得研究分为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三类.文秋芳、王立非(2004)根据研究方法将二语习得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总体来看,上述学者大致采用两种思路对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进行分类:(1)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适分类,即分为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方法;(2)结合二语习得研究本身的特点,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进行方法归类. 本文采用第二个研究思路,基于二语习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文化、认知等视角梳理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同时,学习者语言样本分析研究一直是描述二语习得过程、解释二语习得特征及启示二语教学实践的重要途径,对二语习得研究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把学习者语言准确性、复杂性、流利性的测量方法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作为补充研究视角. 4.各研究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 4.1 基于语言学的研究视角 语言学研究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关注语言表征,着重分析语言形式.这类研究多以普遍语法为理论框架,以描述和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为目的,以目标语者的语言使用为外部参照标准,认为二语习得由规则主导,并尝试回答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否受到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普遍语法的支配等问题. 基于语言学理论视角的研究者通常将二语习得视为二语语法习得,因此语法判断(gram-maticaljudgment test)的研究方法成为这类研究的主要数据获取手段.国外研究者纷纷运用语法判断来验证二语习得中是否存在普遍语法(如 Ellis 2009;Kweon & Bley-Vroman 2011),国内也有研究者运用语法判断来探究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如刘艾娟,戴曼纯 2009;倪锦诚 2012).这类研究主要运用提示应答(prompted responses)和提示产出(prompted production)方法收集数据,聚焦某些特定语法知识,针对二语学习者特定语法结构的习得情况进行调查探讨. 就我国二语习得研究的实际状况而言,研究者可根据各自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语言水平采用合适的研究设计.研究单个语法形式习得时采用单句语法判断便能满足研究需要,研究学习者对某些语法形式的应用能力时则应结合特定语境设计相关测试任务.对低水平二语学习者一般采用可接受性判断(acceptabilityjudgments)、对错判断(true-value judgments)和句子配对(sentence matching)等任务复杂度较低的提示应答形式,对高水平二语学习者则可采用诱导模仿(elicited imitation)、结构式诱导(structured elicitation)、句子组合(sentence combi-ning)、图画描述(picture description)和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等任务复杂度相对较高的提示产出形式. 普遍语法在研究方法方面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一套可证伪的假设,将其置于解释性的理论框架之下(Larsen-Freeman& Long 2009),但是以普遍语法为理论框架的研究属于理论先于研究的范式,研究结果只能证明习得结果的外在语言形式.语法判断的研究方法源于测量被试母语的隐性语法知识以推断其语言能力,而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语法知识主要通过课堂显性教学获得,凭诱导数据推测所得的语言能力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学习者的实际语言水平,因此这类研究方法通常存在外部效度不高的缺陷.其次,语言学研究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多以目标语者的语言使用为外部参照标准,因此容易出现所谓的"比较谬误"(comparative fallacy). 最后,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大多采用静态描述方法,即很多研究只是采集一个时间点上学习者的语言样本,甚至有些历时研究也只是分别在几个时间点上进行语料收集,并没有建立语类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就很难描述语言习得的过程. 4.2 基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视角 心理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关注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加工机制及影响这些机制的因素.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二语的加工表征、加工机制、加工技能、加工策略、个体差异等因素对加工的影响. 基于心理语言学的二语习得研究在采集学习者二语加工表征的数据时通常关注自然情境下学习者语言产出中的犹豫、停顿、自我修正等现象,在犹豫、停顿的时长及位置与二语系统是否出现故障及故障的位置之间建立关联,从中推测加工是自动化加工(automaticprocessing)还是控制性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加工了语言的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存在加工困难等问题的答案.自我修正是指学习者意识到所产出话语中存在语法、词汇、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而尝试改正的行为.反应时(reaction time)也常常被用作二语加工的测量指标.心理语言学家一般认为,句子反应时越长表明所需的加工"能量"越大,判断不合法语句的反应时比判断合法语句更长. 二语加工机制研究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二语学习者两种语言的概念、词汇、句法等表征是共享还是独立的,即激活一种语言的词汇、句法是否会激活另一种语言的对应部分,二语学习者对两种语言的加工处理是否是交互进行的.对二语加工机制的研究主要借助启动实验(priming).实验设计是呈现启动项和目标项,以某种方式诱导受试对目标项做出反应,当目标项受到启动项影响时即产生启动. 研究者探讨二语加工技能和策略等问题时通常采用词汇联想(wordassociation)的任务设计以分析学习者的语义网络,比较其二语和母语心理词典结构.Wilks 和Meara(2002)设计的词汇联想任务是通过计算机呈现某词语,诱导受试联想其他词语,并通过分析其联想到的词语,比较一语和二语的词汇网络密度(lexical network density). 在探究个体差异对加工的影响时研究者较多采用自控速度阅读、眼动(eyemovement)等在线研究方法准确、科学地记录二语学习者的加工速度和成果.此外,研究者还会采用心理学研究常用的实验方法,如句子解读(sentence interpretation)、词汇判断(lexical decision)、跨模态启动(cross-modal priming,如视觉和听觉模态的启动)、动窗(moving window,屏幕上每次只显示一个词,下一个词出现时前一个词自动消失)、由词和背景色彩构成的斯特鲁普测试(StroopTest)等. 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把时间作为测量二语加工产出的维度之一,能够较好地区分加工过程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运用,因为显性知识运用需要时间.换句话说,研究通过控制反应时间,间接使被试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无法依靠显性知识进行加工,由此对其二语自动化加工能力做出评价,使二语加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视化".但是,因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抽象的理论基础及不太常见的实验设备,大多数教师研究者很难将其运用于实际研究. 4.3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视角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任务类型和对话者的性别、身份、地位等社会语境因素对二语产出的影响,强调语言习得发展的复杂多变性,更关注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文化理论为研究学习者的语言提供了全方位视角,使学习者与社会融为一体,使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使用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理论主要包括Vygotsky 等创建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Bakhtin 的对话理论 ( Dialogic Theory)、Lave 和Wenger 的情景学习理论 ( SituatedLearning Theory).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者与教师或学伴的互动合作对话引导语言学习,最终使语言形式和功能内化,学习者达到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状态.调节理论(MediationTheory)、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和支架理论等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运用较多的理论. 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者认为纯数据统计中的平均值可能会掩盖个体变异性,因此更推崇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日记、对话、个人叙述、个案研究等方法研究语言习得的发展.Bailey(1990)详细描述了日记研究的五个步骤.Schumann(1998)对学习者日记的研究发现,"日记本身也可能成为辅助语言学习的工具",日记中关于焦虑等情感问题的详细描述表明个人情感因素可能促进或阻碍二语学习.由此可见,通过日记可详细了解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反思,学习者在日记中自然流露的对不同社会语境的态度和情感也可作为研究社会和个体变量的证据. 对话研究是从会话参与者的视角按话轮逐一分析学习者在会话过程中如何使用和学习语言,其目的在于发现有助于二语习得的会话特征.对话研究可采用角色扮演(roleplay)、话语完成测验(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录像回放解读(video playback for interpretation)和配对变语(matched guise)等方法. 个人叙述可采用即时或延后的内省、刺激回忆、有声思维、自我评估等方法.诱导叙述可借助访谈、无声电影(silentfilms)、最少对白电影短片(film strips with minimal sound)等开展. 个案研究源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种通过观察、访谈、历史数据和档案材料搜寻等途径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分析数据以得出具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可以是单一个案研究也可以是多重个案研究,可以是描述型个案、解释型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探索型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实施步骤是:(1)选取个案,选取时要坚持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原则;(2)收集材料,材料可来源于文献、档案、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实物、网络资源等;(3)分析,分析技术包括描述性分析(叙事法)、类别构建(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构建证据)、理论建构(分析多重个案的独特"层级",包括"个案内"分析和"跨个案"分析).个案分析除了开展人工分析外,还可运用某些质性分析软件(如NVivo).个案研究具有情境真实性、深入性、全面性、灵活性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主观性、难于普适和推广的局限.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大多采用不操纵环境、不干预受试的主位(emic)原则. 研究出发点是在语言习得的真实环境下对学习者进行全面观察和描写,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发现关键变量(keyvariables)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多角度分析第二语言习得与发展的规律;研究成果推动了语言习得研究与语言教学实践的有效互动.但是,这类研究也存在耗时长、对研究对象的配合要求高等实际困难,材料收集时社会语境的特定性及阐释阶段研究者主观性强等因素也给验证性研究带来了不便.我国二语教师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尝试初步运用课堂话语分析、教学日志、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但因时间跨度大等原因尚未大量采用人种志法、纵向个案研究等方法. 4.4 基于认知的研究视角 认知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关注学习者的语言认知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学习者的语言输入输出、语言学习能力和策略运用能力等问题. 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习得过程具有人类一般认知过程的特点,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可用的认知资源、认知能力成为认知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的焦点. 这类研究常用的测试有学习能力测试、工作记忆测试、语言学习策略量表测试等. 语言学习能力测试为预测学习者未来语言学习成效而设计,其中最常用的测量工具包括Carroll和 Sapon(2002)研制的现代语言学能测试( 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Grigorenko等(2000)设计的外语习得创新认知能力测试(Cognitive Ability for Novelty in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s Applied to Foreign Language Test)、Pimsleur(1966) 研制的皮姆斯勒语言学能量表(Pimsleur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等. 记忆分为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涉及信息储存能力和加工处理能力,与二语习得的加工和产出最为相关.二语习得研究中运用的记忆理论主要有工作记忆的能力论、注意性控制论、激活论等.最常用的记忆测量手段包括计数广度任务(countingspan task)、运算广度任务(operation span task)、阅读广度任务(reading span task)和句子广度任务(sen-tence span task).计数广度任务的要求最低,适合对学龄儿童或语言水平较低非本族语者的测试.测试步骤是先向受试呈现图形,要求受试数出图形的数量并对总数进行记忆.完成系列试题后,受试按试题顺序依次回忆所出现的图形数.运算广度任务是先给受试一道数学算式,让其判断是否正确,随后给出一个单词,再给出几道数学判断题之后要求受试回想之前看到的单词.阅读广度任务是先呈现 2 -6 个句子,让受试判断句子的真实性、可接受性、语法或语义的正确性,然后要求受试回忆每个句子的最后一个词或字母. 二语学习策略研究大多采用Oxford(1990)的二语学习策略理论模式和相应的策略量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认知视角下测量学习者学能、记忆、策略等个体因素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突显组间趋势,从宏观层面刻画语言发展过程,但是将语言认知这一复杂现象分割成单个参数分别加以研究,忽视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往往无法捕捉认知过程的动态变化.此外,这些量表是否能直接运用于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比如,徐爽(2008)证实 Oxford 的二语学习策略理论模式与其研究对象(高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数据拟合,而于元芳、刘永兵(2009)研究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Oxford 策略量表中的六分法不适合参与调查的我国大学英语学习群体.总之,我国二语研究者应结合本土学习者的具体情况设计科学合理的测量量表,同时综合、动态考量各种认知因素对二语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本土化的二语习得理论构建. 4.5 对学习者语言准确性、复杂性、流利性的测量 从语言准确性、复杂性和流利性三方面分析学习者语言有助于更全面、更平衡地得到关于学习者语言的信息(Ellis& Barkhuizen 2005),具体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信息.准确性一般指语言产出接近目标语语言规则的程度(Skehan & Foster 1999).不同研究者对准确性提出了不同测量标准:Foster 和 Skehan(1996)运用无错误句的百分比测量准确性;Wigglesworth(1997)将准确性规定为语言形式与目标语的接近程度,分别使用必需场合诱导得到的目标语产出的正确率和错误的自我改正率;Mehnert(1998)使用每100 个单词的错误率为测量指标;Foster 等(2000)认为准确性还涉及语法层次.刘国忠和秦晓晴(2010)总结指出二语写作准确性的测量工具主要包括整体性测量(holistic scales)、无错误 T 单位总数(number oferror free T-units)和错误总数(number of errors). 流利性指语言产出的流畅性、连贯性和语言可接受性.Lennon(1990)把口语流利性分为广义(口语水平的总称)和狭义(语速和流畅程度)流利性,并列出了12 项可量化指标.Towell等(1996)采用语速、发音时间比、发音速度、停顿间的平均无间断语流长度等时间性指标测量口语流利性.此外,也有研究者使用内容指标和语言指标对口语流利性进行测定,如张文忠和吴旭东(2001)采用所述必要事件与全部必要事件之比考察围绕特定话题展开的信息内容的连贯性及语言的可接受性.在书面语流利性研究方面,Latif(2009)把写作流利性测量指标分为成果指标和过程指标,前者主要包括频数测量、比率测量和总体量表测量;后者是基于写作过程的测量,涉及语段长度、语块和处理负荷等指标,并使用录像、有声思维、眼动跟踪或击键记录(keystroke logging)等方法收集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复杂性研究一般涵盖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测量词汇复杂性的维度主要包括词汇复杂度(lexicalsophistication)、词汇变化性(lexical variation)、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和词汇独特性(lexical originality)等.句法复杂性的量化对象主要包括产出单位的长度、从句嵌入量和结构类型的范围等(Ortega 2003),常用测量指标包括:(1)T 单位长度(T-unit length)和子句长度(clause length);(2)T 单位复杂性比率(T-unit complexity ratio)和从属句比率(dependent clauseratio). 对学习者语言准确性、流利性和复杂性的测量是收集学习者语言水平数据的有效途径,但是研究者应始终关注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在研究中国学习者二语习得时,研究者首先应对中国学习者语言准确性、流利性和复杂性进行本土化的概念界定,从多角度采用多维度、多层面评估方法.其次,研究者应从操作层面关注自然语境下社会文化因素对交际的影响,并注重语言交际能力评估. 4.6 对学习者语言的语料库分析运用语料库分析 学习者语言主要有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approach)和语料库驱动(corpus-driven approach)两种方法(Mackey & Gass 2012),前者利用语料验证假设,后者量化分析收集的语料.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又可分为计算机辅助的错误分析和中介语对比分析,这些方法能够为研究母语迁移、中介语过度概化、中介语发展路径、输入偏见(input bias)、语域影响(genre/register influence)等问题提供语料证据. 语料库研究方法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既可用于检验和发展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研究,又可用于指导教学的二语习得应用研究.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应用语料库的优势在于能够借助丰富的真实使用的语言材料,并且能够运用科学便捷的分析技术,如自动词性赋码器(如Brill,CLAWS7)、语法标注器(如 POSTagger)、词目归并器(如 Lemma)、检索软件(如WordSmith,AntConc)、统计分析软件(如 SPSS)等,获得客观量化的研究数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者在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时,应充分考虑所选用的中国学习者语料库与目标语参照库的语料在库容量和语料来源上的可比性,自建语料库时还应充分考虑语料的代表性、时间性和有效性等问题. 5.国内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及发展方向 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问题对国际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回顾梳理不仅有助于掌握国际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也有助于揭示我国二语习得研究现状,进一步推动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由此,我们总结了我国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并相应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发展建议. (1)二语习得定量研究占多数,定性研究逐渐增加,有机结合两者的研究欠缺(尹丽雯2011).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定性和定量研究都有其不完善之处,这表明各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对错优劣之分,也不专属于某一研究领域.在今后二语习得研究中,研究者可根据具体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灵活恰当选择和组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开展多方验证以推进二语习得研究科学化发展. (2)不少二语习得研究设计都缺少试测(pilotstudy)环节.从上文对不同研究视角下研究方法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样本的采集计划和工具难免会有疏漏之处.为严谨起见,研究者在开始正式研究之前,可通过小规模试测考察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恰当性,并进行相应调整和修改,以便顺利开展客观、科学的研究. (3)复制性二语习得研究尚不多见.二语习得研究通常会因研究方法和研究条件的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致使对某些研究问题的探讨无法形成定论.当然,这与二语习得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研究方法等因素.由此,在二语研究领域进行重复性验证对寻求令人信服、普遍认同的答案非常必要.。
二语习得研究的四个理论模式和发展趋势二语习得研究是应用语言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探索学习、使用、理解和教授第二语言的规律和特点。
在这一领域中,有许多理论模式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路径和思路。
本文将探讨二语习得研究的四个理论模式以及其发展趋势。
我们来介绍传统语言习得理论。
传统语言习得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一种自然、本能的过程,人们在面对语言输入时会自然地习得语言。
这一理论模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受到行为主义学派的影响。
行为主义者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刺激-响应-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即人们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和反馈来逐渐习得语言。
在这一理论模式下,语言习得主要是通过模仿、重复和奖励来实现的。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这一模式逐渐受到了挑战。
认知心理学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注意力、记忆、思维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传统语言习得理论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逐渐趋向于发展为认知语言习得理论。
认知语言习得理论充分考虑了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和心理机制,强调了个体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该理论模式认为语言习得不仅仅是通过模仿和奖惩来实现的,更加强调了学习者在接受语言输入的通过思维加工和认知规律的应用来习得语言。
认知语言习得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假设,比如输入假设、产出假设、近似假设等,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并且,在认知语言习得理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许多相关的分支理论,比如交互认知语言习得理论、社会认知语言习得理论等,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和丰富的研究视角。
情感情感语言习得理论则从情感情感的角度探讨了语言习得。
该理论认为情感和情感是语言习得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学习者的情感状态和情感体验会影响其语言习得过程。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情感情感语言习得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从情感情感角度出发,探讨了语言焦虑、情感投入、情感调节等问题,为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二语言习得心理学方向研究综述摘要:本文关注点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通过阐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描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心理学方向的研究成果,从认知加工研究范式、目的语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迁移以及第二语言阅读中元认知展望心理学方向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未来和发展。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认知加工迁移元认知正文一、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我国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可以说正在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还是外语教学领域,都已经有研究者开始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语言能力结构等(有关综述见王建勤,1997);在外语教学领域,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主要包括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特别是学习风格、学习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为国内开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与国外的差距都比较大。
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范围开始拓展到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众多的方面。
早在20世纪时,桂诗春和宁春岩(1997)就对1993-1995年国内四种外语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中的755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分类统计,发现思辨性研究所占的比例(54%)最大,其次是描述性研究(20%)、介绍性研究(13%)和理论性研究(10%),实验性研究所占比例最小,仅为3%,即在755篇文章中仅有24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
并且他们还发现80%的研究没有数据,12%的研究虽有数据但无统计分析,有统计分析数据的研究只占7%。
根据这次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亟待解决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
随着国内刊物对文章要求的提高,思辨性研究比例在减少,但是依然面临着很大压力。
一般来说我们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定性研究的主要特征有:1随着研究的进展逐渐形成假设;2通过自然的观察和访谈收集资料;3资料来源于自然情境;4对资料进行叙述、描述;5研究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案例。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成果及其发展趋势近年来,写作二语习得的研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包括其解释性研究,及其影响学习者习得水平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以前未曾深入探讨的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也为研究领域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突破。
本文首先回顾了早期写作研究的发展历程,接着探讨了写作二语习得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后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
早期写作研究发展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写作研究从语言学习理论的角度取得了众多深远的发展和突破。
其中,写作的研究倾向于探讨第二语言习得是如何影响学习者文字表达能力的发展。
这些研究不仅关注第二语言习得本身,而且还考察了第二语言习得技术如何影响写作。
早期写作研究的重点是在调查各种口头和书面技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来提高学习者的写作二语习得能力。
研究人员比较了学习者使用不同类型的写作技术,如结构主义,论证和连贯话语,以及如何影响其写作二语习得能力的效果。
研究的发现表明,学习者在使用不同的技术时,其语言习得会有很大不同。
此外,早期的写作研究还开发了一些量化评估量表,用于测量学习者的写作二语习得能力。
这些量表涉及语言能力,如词汇量,语法准确性,句法复杂度,以及论证性写作技巧等,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和改善其写作水平。
最新写作二语习得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写作研究领域的发展,研究人员发现了新的影响学习者写作二语习得能力的因素。
其中,研究表明,以下五个因素对提高学习者写作水平有重要作用:语言语境,学习风格,教学方法,语言背景及文化认知。
首先,语言语境对学习者的写作二语习得有重要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学习者受到不同类型的言语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母语言影响、语境转换方式及外部视角等,这些都会影响学习者写作能力的发展。
其次,学习风格也会影响学习者的写作二语习得。
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学习风格是决定其写作水平的重要因素。
如果学习者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他们的写作能力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此外,教学方法也是影响学习者写作水平的重要因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及其研究视角
提要:第二语言研究的历史短暂但其发展迅速,出现了多种理论和流派,它是一门独立的边缘交叉学科,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经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下面,我们就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视角作一下简单的了解。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研究视角
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
人们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兴趣并开展研究要始于五十年代初weinreich(1953)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联系》一书中讨论了母语和第二语言两种体系的关系,并提出了“干扰”(interference)这一重要概念。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obret lado 提出了语言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
他认为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第二语言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二语言和母语不同的地方,两种语言相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消极的影响。
到了六十年代末,corder 提出了“偏误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972年,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 发表了著名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一文。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
“中介语”理论的提
出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
70年代末、80年代初,krashen(1982)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型,这一模型全面的解释了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并且为外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议也最多的语言习得模型。
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以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语言运用的过程。
有人认为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也有观点说语言系统和认知过程分别按大脑的不同部位处理不同的信息。
同时,越来越多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将普遍语法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形成一种发展趋势。
Chamsky 提出了原则和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到了九十年代,他又提出了“最简方案”。
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语言输入对习得者的影响。
1994年,ellis 在回顾和总结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个人差异研究的框架,该框架由三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变量构成。
第一组变量由个人差异构成,包括学习者的年龄、性别、学习动机等。
第二组变量包括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使用的各种策略。
第三组变量是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果。
关联理论为研究二语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Sperber和
wilson (1986 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认为,理解话语的前提是人类的认知假设,即人类在认知事物是总是借助于与之关联的信息。
进入21世纪后,微变化研究法被引入到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微变化研究法是认知心理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探究认知发展的轨迹和机制,侧重研究群体和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变异性。
例如:belzkinginger运用该方法研究了在网络环境中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
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不同视角
一、认知心理视角
这一研究视角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始就受到了关注,语言与认知关系密切,hinkel 及一些学者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认知过程,其研究的焦点就是研究并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其认知路径的发展从普遍语法开始,到后来的交互论和连接主义,直到近来出现的构思语法,认知的视角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十分清晰。
虽然对语言习得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但专家们在认知心理方面达成的共识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具有专门的神经基础,大量的语言素材的输入和不同的社会语言环境对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
二、社会文化视角
认知心理视角相对的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
社会文化视角的代表性理论有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
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批评理论等。
社会文化理论采取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审视第二语言习得。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在任何环境中,语言学习者都处在一种由社会、政治和文化所塑造的交际环境中,通过学习成为其中有能力的参与者。
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
三、语言学视角
第二语言习得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语言学教授susanM、gass的新作《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是一部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二语习得问题的经典合集,此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了解以语言学为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者内在的自我调节过程,且因人而异,因此,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理念展现给我们的则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把研究的目光转移到怎样学这方面来,起点立足于学教建立在学的基础上。
从学习者的现有水平、知识背景、学习方式、学习动机和情感出发,研究习得的过程。
四、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虽然也承认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于影响,但认为这种作用和影响是通过博弈的方式进行的。
从狭义的角度看是个体心智认知与社会文化活动博弈的结果,
从广义的角度看,二语习得是一个由众多小博弈交汇而成的大博弈,它不仅包括学习者个体的认知发展与社会文化活动的博弈,还包括学习者之间两人或多人的博弈、学习者与老师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博弈、老师之间有关教授方法等的博弈、老师和理论家有关二语习得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博弈等。
二语习得包含了博弈所需所需的全部要素,充满了博弈逻辑思维。
五、浑沌学视角
语言学理论每一个阶段的形成和发展几乎都要受到同时代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物理学、化学等领域发现了大量无序的复杂现象,浑沌学理论又引起了科学家的重视。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多维的开放体系,因此,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要同时研究与之相关的习得者与目的语者的思维和文化等。
由上可知,大多数理论都试图通过其中一个主导因素来解释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第二语言的,而一个全面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应该解释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
吕兆格《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不同视角》
冯丽萍孙红娟《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研究方法述评》
李志刚《近五十年来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李炯英《回顾20世纪中国二语习得研究》王立非《国外二语习得研究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