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代赋体文学 - 副本
- 格式:ppt
- 大小:352.50 KB
- 文档页数: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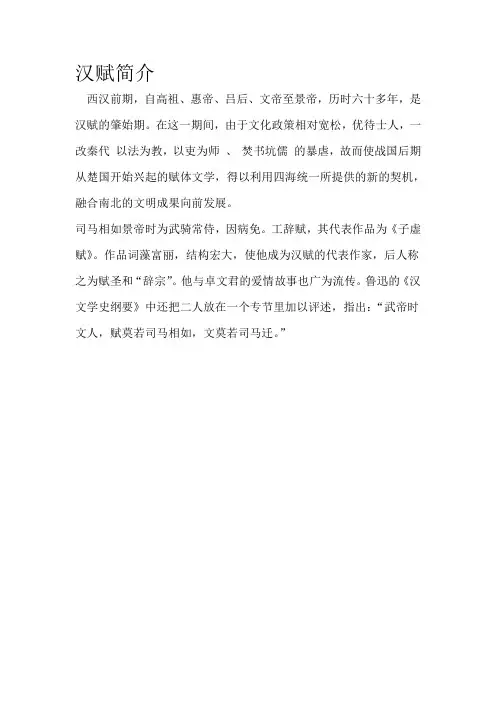
汉赋简介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
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
司马相如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
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
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
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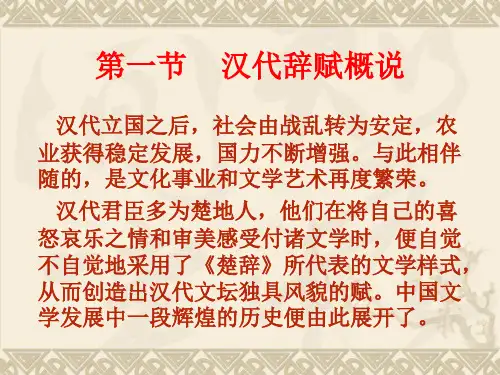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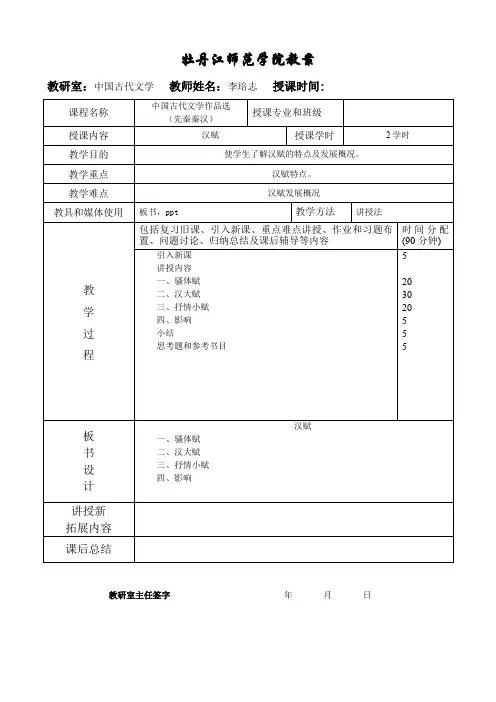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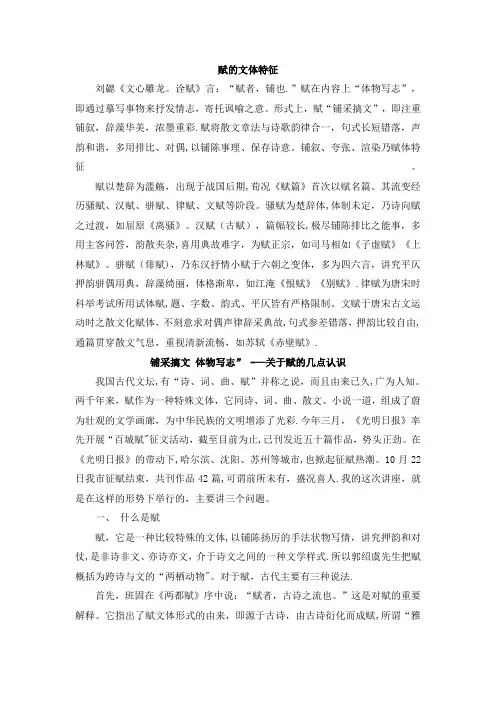
赋的文体特征刘勰《文心雕龙。
诠赋》言:“赋者,铺也.”赋在内容上“体物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寄托讽喻之意。
形式上,赋“铺采摛文”,即注重铺叙,辞藻华美,浓墨重彩.赋将散文章法与诗歌韵律合一,句式长短错落,声韵和谐,多用排比、对偶,以铺陈事理、保存诗意。
铺叙、夸张、渲染乃赋体特征。
赋以楚辞为滥觞,出现于战国后期,荀况《赋篇》首次以赋名篇。
其流变经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阶段。
骚赋为楚辞体,体制未定,乃诗向赋之过渡,如屈原《离骚》。
汉赋(古赋),篇幅较长,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多用主客问答,韵散夹杂,喜用典故难字,为赋正宗,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骈赋(俳赋),乃东汉抒情小赋于六朝之变体,多为四六言,讲究平仄押韵骈偶用典,辞藻绮丽,体格渐卑,如江淹《恨赋》《别赋》.律赋为唐宋时科举考试所用试体赋,题、字数、韵式、平仄皆有严格限制。
文赋于唐宋古文运动时之散文化赋体,不刻意求对偶声律辞采典故,句式参差错落,押韵比较自由,通篇贯穿散文气息,重视清新流畅,如苏轼《赤壁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关于赋的几点认识我国古代文坛,有“诗、词、曲、赋”并称之说,而且由来已久,广为人知。
两千年来,赋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它同诗、词、曲、散文、小说一道,组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画廊,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增添了光彩.今年三月,《光明日报》率先开展“百城赋"征文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已刊发近五十篇作品,势头正劲。
在《光明日报》的带动下,哈尔滨、沈阳、苏州等城市,也掀起征赋热潮。
10月22日我市征赋结束,共刊作品42篇,可谓前所未有,盛况喜人.我的这次讲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举行的,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赋赋,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以铺陈扬厉的手法状物写情,讲究押韵和对仗,是非诗非文、亦诗亦文,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郭绍虞先生把赋概括为跨诗与文的“两栖动物"。
对于赋,古代主要有三种说法.首先,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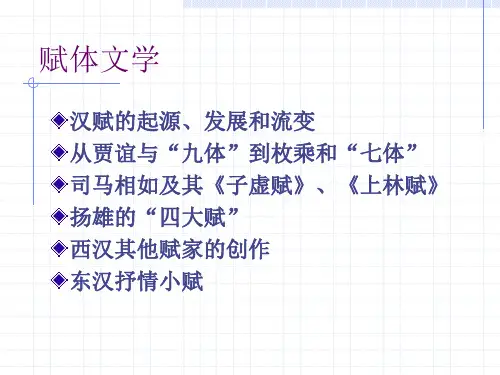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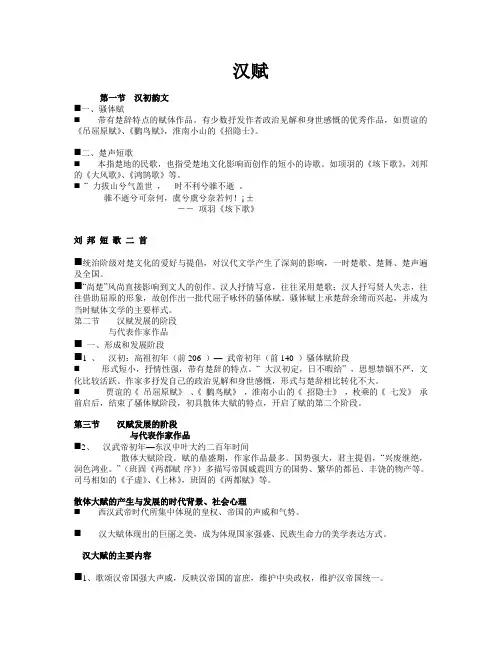
汉赋第一节汉初韵文⏹一、骚体赋⏹带有楚辞特点的赋体作品。
有少数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优秀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二、楚声短歌⏹本指楚地的民歌,也指受楚地文化影响而创作的短小的诗歌。
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等。
⏹“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垓下歌》刘邦短歌二首⏹统治阶级对楚文化的爱好与提倡,对汉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时楚歌、楚舞、楚声遍及全国。
⏹“尚楚”风尚直接影响到文人的创作。
汉人抒情写意,往往采用楚歌;汉人抒写贤人失志,往往借助屈原的形象,故创作出一批代屈子咏怀的骚体赋。
骚体赋上承楚辞余绪而兴起,并成为当时赋体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节汉赋发展的阶段与代表作家作品⏹一、形成和发展阶段⏹1 、汉初:高祖初年(前206 )—武帝初年(前140 )骚体赋阶段⏹形式短小,抒情性强,带有楚辞的特点。
“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 ,思想禁锢不严,文化比较活跃。
作家多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形式与楚辞相比转化不大。
⏹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承前启后,结束了骚体赋阶段,初具散体大赋的特点,开启了赋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节汉赋发展的阶段与代表作家作品⏹2、汉武帝初年—东汉中叶大约二百年时间散体大赋阶段。
赋的鼎盛期,作家作品最多。
国势强大,君主提倡,“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班固《两都赋·序》)多描写帝国威震四方的国势、繁华的都邑、丰饶的物产等。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赋》等。
散体大赋的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心理⏹西汉武帝时代所集中体现的皇权、帝国的声威和气势。
⏹汉大赋体现出的巨丽之美,成为体现国家强盛、民族生命力的美学表达方式。
汉大赋的主要内容⏹1、歌颂汉帝国强大声威,反映汉帝国的富庶,维护中央政权,维护汉帝国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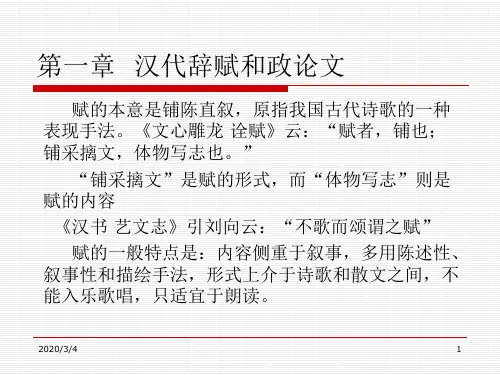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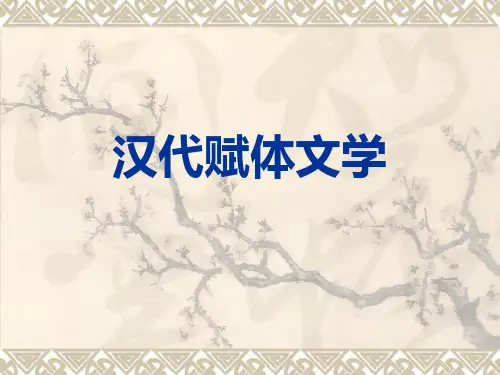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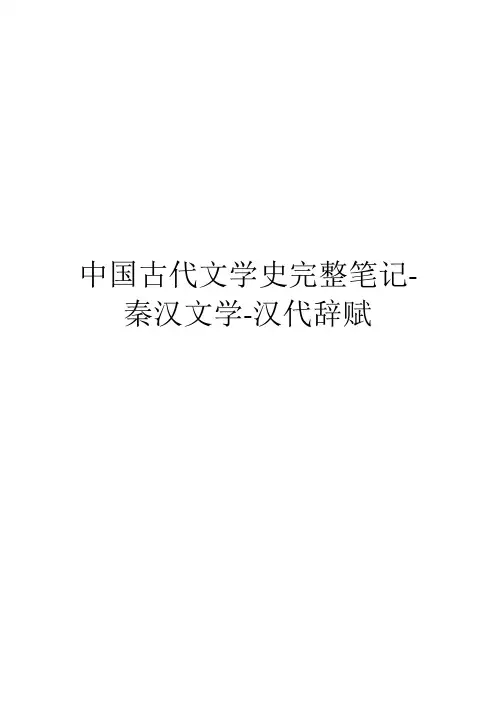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秦汉文学-汉代辞赋名词解释:骚体赋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严戒《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简述贾谊骚体赋的创作特点。
贾谊骚体赋作,今存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惜赋》残局,前散篇是代表作。
一.抒情述志、情感浓郁,是贾谊骚体赋的重要特色,如《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而发述自己征途受挫、怀才不遇的幽愤,情感极为浓郁。
二.从艺术表现看,贾谊《吊屈原赋》《鵩鸟》二作都直述胸臆,议论多于形象。
《旱云赋》描摹云气和大旱的情状,也很有表现力。
简述枚乘开创大赋体式的《七发》及其特点。
一.铺叙描摹,夸饰渲染的文风。
如“曲江观涛”描写江涛的汹涌澎湃。
二.缺乏作者的自我真情实感。
整篇作品不见抒情的语句,没有作者喜怒哀乐的表现。
三.遣词造句趋向整齐、骈偶、繁难、华丽。
四.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
这些特点,标志着大赋这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了汉代文坛。
简述《天子游猎赋》所代表的汉大赋的主要特点。
《天子游猎赋》采用问难的体式,整齐排偶的句式,已于楚辞不甚相同,而更大的不同表现在:一.它丧失了真情实感。
这是它与楚辞本质的不同。
二.空间的极度排比。
《天子游猎赋》没有时间的纵向穿插,唯任空间的繁细铺排。
三.以直接而单纯的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
繁细的铺叙、夸张的摹绘,是《天子游猎赋》最主要的表现手法。
以宫殿苑猎、山水品物为主要描摹对象。
四.遣词用语更加繁难辟涩。
《天子游猎赋》上述特点,表明它的根本特色不在抒情写志,而在于文才和游戏文字。
论述杨雄大赋的创作特点一.拓展了大赋的题材领域。
1.写祭祀,如《甘泉》、《河东》;2.把笔触从京师移到外郡,从田猎发展到描摹都市、郡邑的繁华,如《蜀都赋》。
二.进一步加强了大赋“劝百讽一”的“劝”的色彩。
杨雄的大赋几乎无讽谏。
如《蜀都赋》同篇铺夸蜀郡山水之雄伟,物产之丰饶。
三.杨雄的大赋在写作上还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篇幅相对缩短,描摹对象集中。
汉赋汉赋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种有韵的散⽂,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是渲染宫殿城市;⼆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
⽽以前⼆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或统治者的⽂治武功⾼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赋和⼩赋。
⼤赋⼜叫散体⼤赋,规模巨⼤,结构恢宏,⽓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赋的⾏家、⼩赋扬弃了⼤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赋的⾼⼿。
汉赋形成于汉初。
贾谊⾸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真正创⽴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家枚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这⼀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虚》、《上林》、《⼤⼈》、《长门》、《美⼈》、《哀⼆世》6赋。
其中,他的《天⼦游猎赋》包括《⼦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赋的最⾼成就。
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的体制。
⾃西汉末期⾄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法超越前⼈,故模拟之风⼤盛,汉赋进⼊模拟期。
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末年,汉赋进⼊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向转化。
张衡的《归⽥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赋基础。
辞赋在两汉时期的传播辞赋是我国古代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体裁。
它产生于战国,兴盛于两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赋体占据了整个时代的文学重心,无数文人骚客为之趋之若鹜,上至帝王诸侯,下至游士文人普遍作赋、读赋、评赋,使赋体文学成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实现了较为成功的文学传播。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以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归纳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赋在两汉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环境、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效果几个方面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复原辞赋在两汉时期传播情况的原貌,总结辞赋的传播规律。
本文主体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首先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接着确定了辞赋的范围,说明本文主要是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讨论辞赋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不涉及辞赋在汉代以后的传播研究。
第二部分正论,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对两汉时期辞赋传播各要素进行分析,又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辞赋在汉代的传播环境。
本章运用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把传播环境相似的历史时期合并,将汉代分为汉初、武帝至东汉中期、东汉中后期三个时间段,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
第二章分析两汉辞赋的传播者。
赋家往往既创作辞赋又直接传播辞赋,赋家在创作时形成以思考为核心的内向传播,又在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发挥其主体作用;校书郎和史官也是辞赋的主要传播者。
第三章论述两汉辞赋的传播内容。
将两汉辞赋分为描写帝王游猎、渲染城市宫殿、抒发人生感慨、歌咏禽木器乐四类进行分析。
第四章论述两汉辞赋的传播媒介。
语言和文字是辞赋在汉代传播的主要媒介。
与汉乐府相比,文字媒介在辞赋传播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
第五章分析两汉辞赋的受传者。
统治阶级是两汉时期辞赋传播最主要的受传者,赋评家是特殊的一类传播者,创作型的赋家是最佳的受传者。
第六章论述两汉辞赋的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辞赋传播带来的娱乐效果、政治效果、抒情效果同样具有复杂性。
汉代赋体文学汉代赋体文学第一节赋体名称的来源以赋名篇,始于荀子。
荀子曾作《礼》、《知》、《云》、《蚕》、《箴》“赋”五篇,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但作为文体来说,尚不具备,仍属于“赋”的萌芽阶段。
《文选》所收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文体特点如汉代赋,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作品至少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不可能是生活在战国时光楚襄王之际的“宋玉”作品。
可以说,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
一、赋的特征: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原指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
《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chī)文,体物写志也。
”意思是:赋,就是铺叙,通过铺陈辞采写成文章,通过描绘物象来抒发情志。
“铺采摛文”是赋的形式,而“体物写志”则是赋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引刘向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意思是赋为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由上述两点,可概括赋的一般特点是: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手法,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二.诗和赋的关系: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赋是由古诗演变而来。
《艺文志》说:“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可见诗与赋的区别是,前者为可歌的,而后者是不歌而颂的。
三、楚辞和赋的关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又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称:“其文弘博典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离骚序》)可见,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汉代人认为“辞”与“赋”没有区别,他们把屈原的作品也称作赋。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将“骚”与“赋”划为两体。
他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意思是到屈原创作《离骚》时,才开始扩展绘声绘形的特色。
赋,起源于诗人,而由《楚辞》开拓出新的疆界。
两汉文学历史文化背景文学发展分期汉代史传文学:史记、汉书汉代诗歌与赋体文学第一讲秦汉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1、秦:燔灭文章,历史空白2、汉初:无为之治文学:反思历史关注现实3、武帝:文化交流与思想一统文学:散体赋、史记大气磅礴4、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文学:复古思潮注重模拟5、东汉前期:强化思想统治文学:客观严整由文转质6、东汉后期:社会危机加重文学:抒情小赋发现自己第二讲汉代散文概说与桓宽的《盐铁论》一是汉初的政论文:讨论国策,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二是以董仲舒文章为代表:内容注重解释封建君主集权的合理性,在形式上则崇尚质拙朴实;三是历史散文巨著《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成一家之言” ;四是在西汉末年复古之风:这场复古之风始于刘歆的学术复古,而文章复古是由扬雄完成的;汉代论辩文代表作桓宽《盐铁论》;五是东汉初期王充《论衡》,对天人感应、灾异祥瑞之说以及今文经学者媚附政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反对复古,主张独创,文章深入浅出,反复论证,表现出浓厚的哲学思辩色彩;六是东汉初年班固父子所著的《汉书》,它明显地适应新的封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在思想上维护当时的儒学统治,在形式上注重语言的锤炼,文风洗练谨严。
桓宽的《盐铁论》:记录“文学”、“贤良”与“臣相”、“御史”关于盐铁问题辩论的论文集,堪称汉代论辩文的代表作。
主要观点:“国不与民争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论辩艺术:一是针锋相对,言语直率;二是铺陈排比,情采并重;三是暗合戏剧、小说因素;第三讲司马迁与《史记》一、生平20岁以前阅读古籍,接受儒家思想;1.壮游天下(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太史公自序》)宋代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