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1)
- 格式:docx
- 大小:12.54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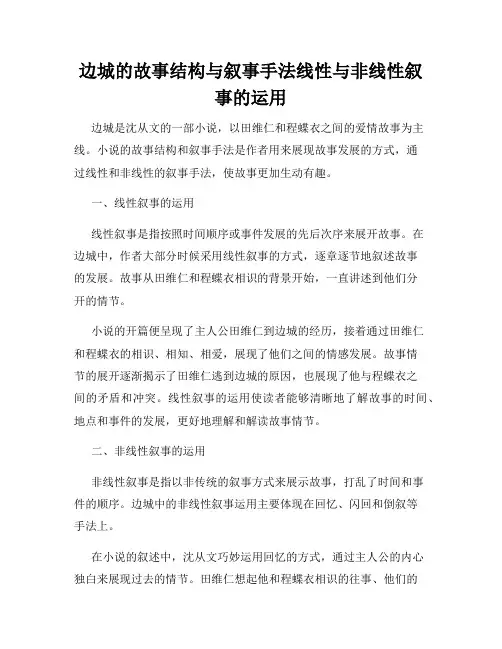
边城的故事结构与叙事手法线性与非线性叙事的运用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小说,以田维仁和程蝶衣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小说的故事结构和叙事手法是作者用来展现故事发展的方式,通过线性和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一、线性叙事的运用线性叙事是指按照时间顺序或事件发展的先后次序来展开故事。
在边城中,作者大部分时候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逐章逐节地叙述故事的发展。
故事从田维仁和程蝶衣相识的背景开始,一直讲述到他们分开的情节。
小说的开篇便呈现了主人公田维仁到边城的经历,接着通过田维仁和程蝶衣的相识、相知、相爱,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发展。
故事情节的展开逐渐揭示了田维仁逃到边城的原因,也展现了他与程蝶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线性叙事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发展,更好地理解和解读故事情节。
二、非线性叙事的运用非线性叙事是指以非传统的叙事方式来展示故事,打乱了时间和事件的顺序。
边城中的非线性叙事运用主要体现在回忆、闪回和倒叙等手法上。
在小说的叙述中,沈从文巧妙运用回忆的方式,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展现过去的情节。
田维仁想起他和程蝶衣相识的往事、他们的约定和承诺,这些回忆不仅增加了故事的韵味,也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田维仁的内心世界。
同时,闪回也是边城中非线性叙事的常用手法。
通过主人公的回忆,读者可以了解到田维仁在边城的生活,他与程蝶衣的相处,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
这种突然切入过去的叙述方式,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也为读者揭示了一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故事情节。
此外,在边城中还出现了倒叙的叙事手法。
比如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展示了田维仁和程蝶衣分开后的情节,然后回到过去对田维仁心理的描写,这一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得读者在回想之后思考更加深入,对整个故事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三、边城故事结构与叙事手法的结合运用边城的故事结构是由线性和非线性叙事手法相互交织而成的,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入胜。
作者通过线性叙事手法将故事情节按照时间顺序逐步展开,同时又通过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回忆、闪回和倒叙等手法来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隐藏的故事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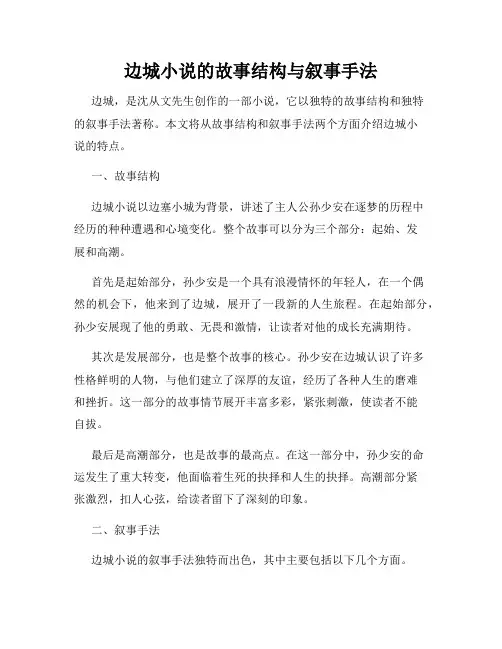
边城小说的故事结构与叙事手法边城,是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它以独特的故事结构和独特的叙事手法著称。
本文将从故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两个方面介绍边城小说的特点。
一、故事结构边城小说以边塞小城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孙少安在逐梦的历程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和心境变化。
整个故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起始、发展和高潮。
首先是起始部分,孙少安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年轻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来到了边城,展开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在起始部分,孙少安展现了他的勇敢、无畏和激情,让读者对他的成长充满期待。
其次是发展部分,也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孙少安在边城认识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历了各种人生的磨难和挫折。
这一部分的故事情节展开丰富多彩,紧张刺激,使读者不能自拔。
最后是高潮部分,也是故事的最高点。
在这一部分中,孙少安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他面临着生死的抉择和人生的抉择。
高潮部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叙事手法边城小说的叙事手法独特而出色,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时间的叙述方式。
边城小说以回忆方式来叙述故事,通过主人公回忆自己在边城的经历,将过去和现在相互交织起来,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种诗意的美感。
其次是人物的叙述方式。
边城小说中的人物丰满而生动,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命运。
小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动机和情感。
再次是语言的叙述方式。
沈从文先生善于运用华丽的词藻和细腻的描写,使整个叙述充满了美感和艺术性。
他的语言曲折含蓄,极具感染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沉浸其中。
最后是符号象征的运用。
边城小说中大量运用了符号象征来增加故事的隐喻和深度。
比如河水象征着生命和潮起潮落,边塞小城象征着世俗和束缚等等。
这些符号的巧妙运用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富有内涵和哲理。
综上所述,边城小说以其独特的故事结构和叙事手法成为了文学经典。
它以深刻的人物形象、极富诗意的语言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完美地诠释了爱情、友情和人生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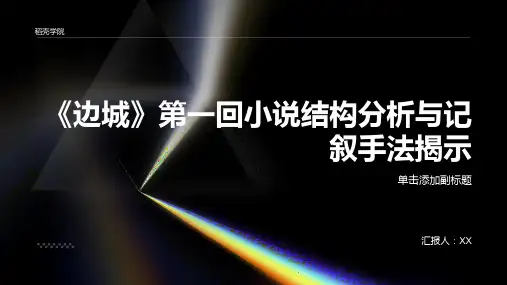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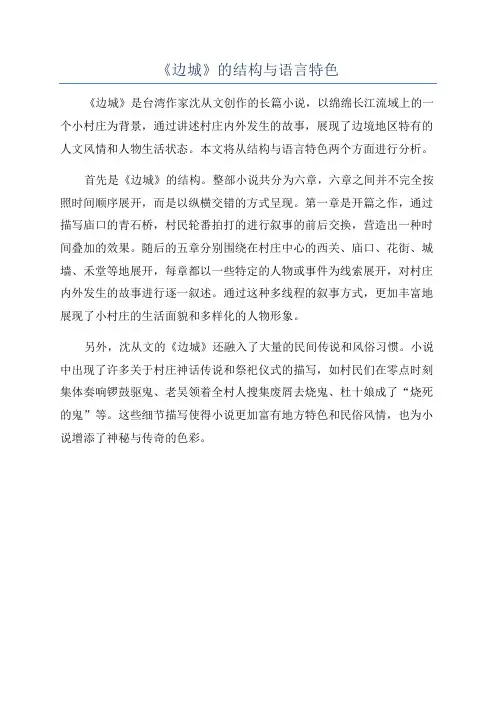
《边城》的结构与语言特色
《边城》是台湾作家沈从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以绵绵长江流域上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通过讲述村庄内外发生的故事,展现了边境地区特有的人文风情和人物生活状态。
本文将从结构与语言特色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边城》的结构。
整部小说共分为六章,六章之间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呈现。
第一章是开篇之作,通过描写庙口的青石桥,村民轮番拍打的进行叙事的前后交换,营造出一种时间叠加的效果。
随后的五章分别围绕在村庄中心的西关、庙口、花街、城墙、禾堂等地展开,每章都以一些特定的人物或事件为线索展开,对村庄内外发生的故事进行逐一叙述。
通过这种多线程的叙事方式,更加丰富地展现了小村庄的生活面貌和多样化的人物形象。
另外,沈从文的《边城》还融入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关于村庄神话传说和祭祀仪式的描写,如村民们在零点时刻集体奏响锣鼓驱鬼、老吴领着全村人搜集废屑去烧鬼、杜十娘成了“烧死的鬼”等。
这些细节描写使得小说更加富有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也为小说增添了神秘与传奇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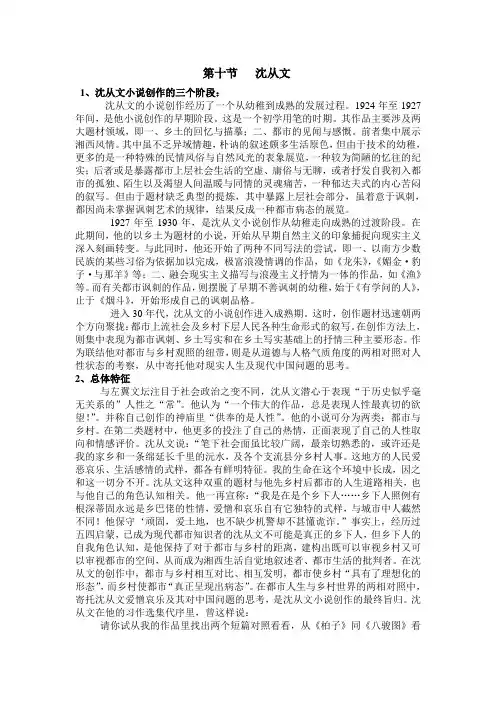
第十节沈从文1、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1924年至1927年间,是他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
这是一个初学用笔的时期。
其作品主要涉及两大题材领域,即一、乡土的回忆与描摹;二、都市的见闻与感慨。
前者集中展示湘西风情。
其中虽不乏异域情趣,朴讷的叙述颇多生活原色,但由于技术的幼稚,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民情风俗与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较为简陋的忆往的纪实;后者或是暴露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空虚、庸俗与无聊,或者抒发自我初入都市的孤独、陌生以及渴望人间温暖与同情的灵魂痛苦,一种郁达夫式的内心苦闷的叙写。
但由于题材缺乏典型的提炼,其中暴露上层社会部分,虽着意于讽刺,都因尚未掌握讽刺艺术的规律,结果反成一种都市病态的展览。
1927年至1930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在此期间,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开始从早期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向现实主义深入刻画转变。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两种不同写法的尝试,即一、以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为依据加以完成,极富浪漫情调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二、融会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抒情为一体的作品,如《渔》等。
而有关都市讽刺的作品,则摆脱了早期不善讽刺的幼稚,始于《有学问的人》,止于《烟斗》,开始形成自己的讽刺品格。
进入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
这时,创作题材迅速朝两个方向聚拢:都市上流社会及乡村下层人民各种生命形式的叙写。
在创作方法上,则集中表现为都市讽刺、乡土写实和在乡土写实基础上的抒情三种主要形态。
作为联结他对都市与乡村观照的纽带,则是从道德与人格气质角度的两相对照对人性状态的考察,从中寄托他对现实人生及现代中国问题的思考。
2、总体特征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
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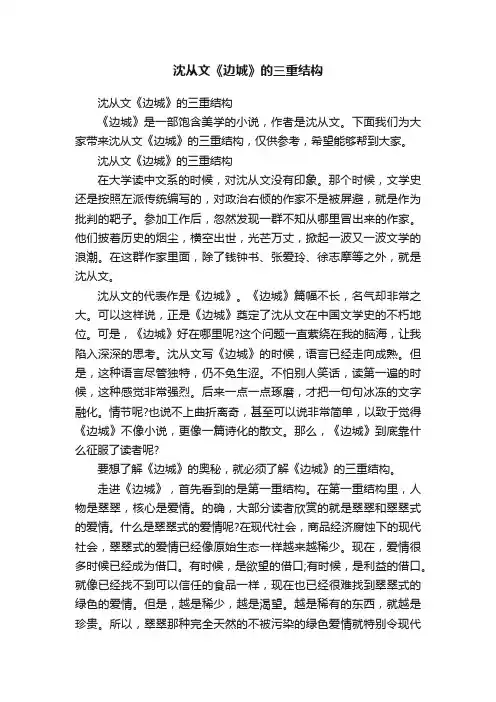
沈从文《边城》的三重结构沈从文《边城》的三重结构《边城》是一部饱含美学的小说,作者是沈从文。
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沈从文《边城》的三重结构,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边城》的三重结构在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对沈从文没有印象。
那个时候,文学史还是按照左派传统编写的,对政治右倾的作家不是被屏避,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
参加工作后,忽然发现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作家。
他们披着历史的烟尘,横空出世,光芒万丈,掀起一波又一波文学的浪潮。
在这群作家里面,除了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等之外,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的代表作是《边城》。
《边城》篇幅不长,名气却非常之大。
可以这样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的不朽地位。
可是,《边城》好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但是,这种语言尽管独特,仍不免生涩。
不怕别人笑话,读第一遍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后来一点一点琢磨,才把一句句冰冻的文字融化。
情节呢?也说不上曲折离奇,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以致于觉得《边城》不像小说,更像一篇诗化的散文。
那么,《边城》到底靠什么征服了读者呢?要想了解《边城》的奥秘,就必须了解《边城》的三重结构。
走进《边城》,首先看到的是第一重结构。
在第一重结构里,人物是翠翠,核心是爱情。
的确,大部分读者欣赏的就是翠翠和翠翠式的爱情。
什么是翠翠式的爱情呢?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腐蚀下的现代社会,翠翠式的爱情已经像原始生态一样越来越稀少。
现在,爱情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借口。
有时候,是欲望的借口;有时候,是利益的借口。
就像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食品一样,现在也已经很难找到翠翠式的绿色的爱情。
但是,越是稀少,越是渴望。
越是稀有的东西,就越是珍贵。
所以,翠翠那种完全天然的不被污染的绿色爱情就特别令现代人向往。
在《边城》里面,翠翠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读完《边城》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翠翠在脑海里就再也挥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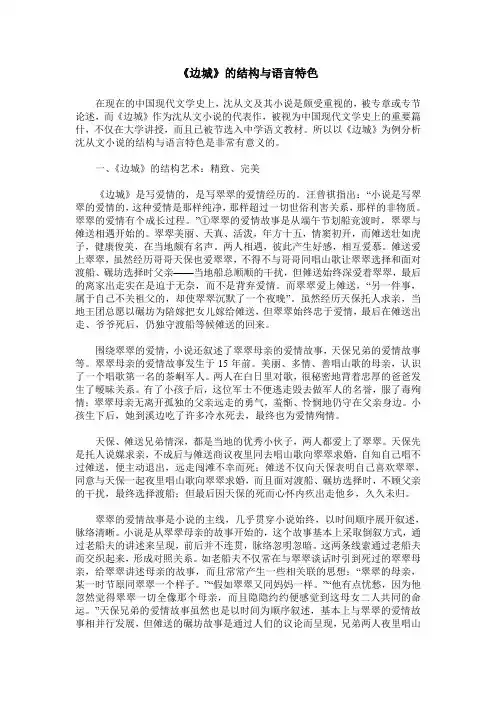
《边城》的结构与语言特色在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及其小说是颇受重视的,被专章或专节论述,而《边城》作为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什,不仅在大学讲授,而且已被节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所以以《边城》为例分析沈从文小说的结构与语言特色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边城》的结构艺术:精致、完美《边城》是写爱情的,是写翠翠的爱情经历的。
汪曾祺指出:“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
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
”①翠翠的爱情故事是从端午节划船竞渡时,翠翠与傩送相遇开始的。
翠翠美丽、天真、活泼,年方十五,情窦初开,而傩送壮如虎子,健康俊美,在当地颇有名声。
两人相遇,彼此产生好感,相互爱慕。
傩送爱上翠翠,虽然经历哥哥天保也爱翠翠,不得不与哥哥同唱山歌让翠翠选择和面对渡船、碾坊选择时父亲——当地船总顺顺的干扰,但傩送始终深爱着翠翠,最后的离家出走实在是迫于无奈,而不是背弃爱情。
而翠翠爱上傩送,“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虽然经历天保托人求亲,当地王团总愿以碾坊为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但翠翠始终忠于爱情,最后在傩送出走、爷爷死后,仍独守渡船等候傩送的回来。
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
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
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
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无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
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
天保、傩送兄弟情深,都是当地的优秀小伙子,两人都爱上了翠翠。
天保先是托人说媒求亲,不成后与傩送商议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过傩送,便主动退出,远走闯滩不幸而死;傩送不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欢翠翠,同意与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面对渡船、碾坊选择时,不顾父亲的干扰,最终选择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怀内疚出走他乡,久久未归。

内容摘要:x【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
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
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
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
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
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
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x【内容提要】【关键词】沈从文/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学院派现代主义“这是一个故事,要慢慢的看,才看得懂……我意思是文字写得太晦,和一般习惯不太相合。
你知道,大凡一种和习惯不大相合的思想行为,有时还被人看成十分危险,会出乱子的!”(沈从文,“看虹录”1992[1943]:47—48)我认为就20世纪中期中国的情况而言,文学中值得一提的现代主义流派至少有三种,沈从文是其中一派的杰出代表。
要给这几个流派冠名并不是简单的事。
我们姑且从中国的立场分别如下:(1)从西方和日本传过来的外来现代主义,(2)上海现代主义,(3)学院派现代主义。
诸多学者如严家炎(1989:100—104),吴中杰和吴立昌(1995),朱寿桐(1998),以及史书美(2001:96—127)等均令人信服地指出20年代许多思想前卫的作家,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对西方现代派都很熟悉。
所以他们的某些作品颇有现代派的特点,不过既不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又异于那种明确流行的“19世纪现代”色彩。
但我这里所谈的中国现代主义既不同于理论上植根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郁达夫所表现的那种实验浪漫主义,更不要说郭沫若了。
我指的是中国主流文学之外所充分展现的那些现代主义流派,甚至与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潮也大相径庭。
学院派现代主义作家们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既不是因为他们熟悉国外现代主义思潮、作家或作品(这方面胡适与徐志摩始终都比沈从文要强,但他们的作品并不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也不是因为选材和主题的现代性(如郁达夫的某些作品),而主要在于这些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不但心仪,且有才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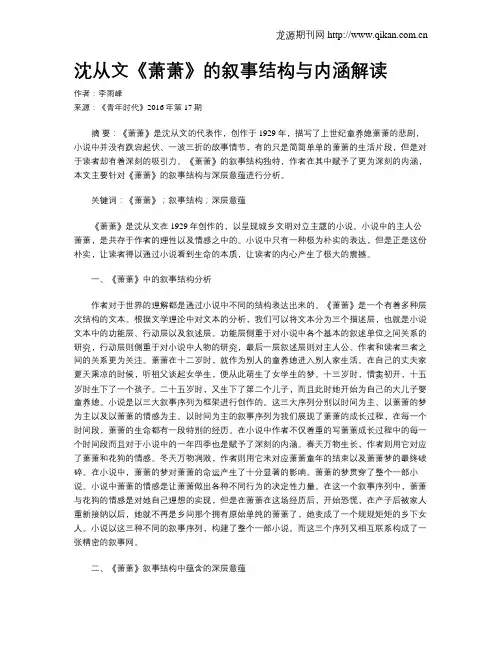
沈从文《萧萧》的叙事结构与内涵解读作者:李雨峰来源:《青年时代》2016年第17期摘要:《萧萧》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创作于1929年,描写了上世纪童养媳萧萧的悲剧,小说中并没有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萧萧的生活片段,但是对于读者却有着深刻的吸引力。
《萧萧》的叙事结构独特,作者在其中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本文主要针对《萧萧》的叙事结构与深层意蕴进行分析。
关键词:《萧萧》;叙事结构;深层意蕴《萧萧》是沈从文在1929年创作的,以呈现城乡文明对立主题的小说。
小说中的主人公萧萧,是共存于作者的理性以及情感之中的。
小说中只有一种极为朴实的表达,但是正是这份朴实,让读者得以通过小说看到生命的本质,让读者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一、《萧萧》中的叙事结构分析作者对于世界的理解都是通过小说中不同的结构表达出来的。
《萧萧》是一个有着多种层次结构的文本。
根据文学理论中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文本分为三个描述层,也就是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层、行动层以及叙述层。
功能层侧重于对小说中各个基本的叙述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行动层则侧重于对小说中人物的研究,最后一层叙述层则对主人公、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
萧萧在十二岁时,就作为别人的童养媳进入别人家生活。
在自己的丈夫家夏天乘凉的时候,听祖父谈起女学生,便从此萌生了女学生的梦。
十三岁时,情窦初开,十五岁时生下了一个孩子。
二十五岁时,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而且此时她开始为自己的大儿子娶童养媳。
小说是以三大叙事序列为框架进行创作的。
这三大序列分别以时间为主、以萧萧的梦为主以及以萧萧的情感为主。
以时间为主的叙事序列为我们展现了萧萧的成长过程,在每一个时间段,萧萧的生命都有一段特别的经历。
在小说中作者不仅着重的写萧萧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时间段而且对于小说中的一年四季也是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春天万物生长,作者则用它对应了萧萧和花狗的情感。
冬天万物凋败,作者则用它来对应萧萧童年的结束以及萧萧梦的最终破碎。
沈从文小说叙事模式研究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沈从文是一个多产出的作家,仅小说创作就多达两百余篇。
沈从文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诗般优美的语言、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巧妙设置的艺术空白,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和研究者前来阅读。
近年来,有关沈从文作品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令人目不暇接。
通过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是从“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叙述主体”、“叙事视角”、“叙事语言”等方面对沈从文的小说进行分析和研究,很少有学者对沈从文小说中蕴含的“叙事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通过大量阅读沈从文的小说,不难发现其小说在叙述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具有一定的叙事模式。
本文有意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以“叙事模式”为切入点对沈从文的小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故事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对沈从文小说中蕴含的叙事模式进行探索,深入挖掘沈从文小说中蕴含的“叙事模式”及其具有的美学价值,努力拓宽沈从文小说的研究领域,更好的展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魅力。
---------------------------------------------------------------范文最新推荐------------------------------------------------------ 从社会学习理论角度解读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摘要: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以其独特性在现代小说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研究其小说的文章很多,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研究的文章还比较少。
本文就是从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角度对沈从文的人格形成进行分析,在其人格特点的基础上对他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研究,从而深入的了解他的乡土小说创作特点。
7193关键字:沈从文;社会学习理论;人格;乡土小说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o analyze Shen Congwen's Local NovelsAbstract: The novels of ShenCongwen with its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 flashing a dazzling light, the stories of many articles, but 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1 / 7view of their research are less. Personality from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ShenCongwen formatio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n his rural novels , so as to understand his rural novels feature.Key words: ShenCongwen; social learning theory;;Personality;;Local Novels前言在星光璀璨的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引言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部小说通过描绘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本论文将深入探讨《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从主题与象征、人物塑造、情节展开、悲剧冲突、叙述手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剖析。
主题与象征《边城》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湘西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和人性的探索。
小说通过描写湘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象征手法,将自然与人物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例如,小说中的渡船象征着湘西人民的命运,而船上的翠翠则代表着湘西女性的柔美与坚韧。
人物塑造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
其中,翠翠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天真无邪,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船总顺顺则代表着湘西地区的权威和力量,他的形象既具有压迫性,又具有包容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而小说中的男主角,二老,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他既有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又有对家族荣誉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情节展开《边城》的情节展开以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主线,通过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小说的情节发展缓慢而自然,通过细节的描写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一些隐喻和暗示的手法,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了线索和暗示。
悲剧冲突《边城》的悲剧冲突主要来自于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社会现实的压迫。
二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小说的核心冲突,而顺顺对家族荣誉的追求则加剧了这一冲突的复杂性。
同时,湘西地区的社会现实也给这个故事带来了悲剧色彩。
例如,船总顺顺对二老的期望和对翠翠的歧视,以及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家族制度的束缚,都使这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
叙述手法沈从文的叙述手法独特而富有诗意。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文体形态和文体结构沈从文创造了三种基本文体形态:
1、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
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
2、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
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
3、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
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文体结构:
在文体创造上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
结构上是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文学之光ENXUNZHIGUANGW Jul. 2016 July 23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颇具特色。
在小说《边城》中,作者通过对叙事结构的把握营造了一种诗意化的氛围。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
”在《边城》中,沈从文运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各种各样湘西人民的生命特征,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
独特的空间化叙事手法、重复的叙事结构、时间结构顺序的重组,作家沈从文在《边城》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意化的结构。
一、独特的空间化叙述结构形式在《边城》的第一章中,作家采用了空间化的叙事手法,具体表现为,从湘西边城的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中介绍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一开头便写到:“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开头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人物。
紧接着,作家沈从文还从边城的地理环境出发,交代祖孙二人的日常生活:住在白塔边上的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五岁的翠翠掌管着小溪上的渡船。
而后,作者继续介绍茶峒城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
“凭山依水而筑”,城外河边设有码头,贯穿码头的是一条河街,河街的房子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中,因此,设置了吊脚楼。
于是乎,小说的另外两个主人公-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便被作者引出。
作者巧妙运用了空间化的叙述形式,在描绘边城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过程中,将小说人物与湘西世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
以此奠定了小说诗意化结构的基础。
二、重复的叙事结构小说《边城》中,沈从文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三次端午节赛龙舟: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因无法忘记上个端午节与傩送的美丽相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内在结构作者:卢思琴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3年第07期摘要:《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之一”。
作者集中为读者展现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通过主人公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为人们呈现出了不同于都市生活的乡村风景。
本文旨在通过《边城》这一文本,从乡村生活与都市生活两个方面解读沈从文小说的内在结构,以此反观作者田园牧歌般笔触下隐藏的对都市生活的批判。
关键词:《边城》乡土都市二元对立纵观沈从文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乡村和城市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两个重点,对于沈从文而言,故乡“湘西”凝结了一切“美”的元素,山美水美景色美,生活在湘西的人更是纯洁质朴,美丽动人,而他对于独立于“湘西”之外的一切城市文明都有一种厌弃情绪,他认为“社会一切都若在一种腐烂中,发霉发臭……更糟糕到无可救药。
”是什么造成沈从文文学创作中这种乡村、都市二元对立的结构呢?当然不得不提沈从文独特的离乡、还乡的经历。
一、沈从文独特的生活背景沈从文自诩为“乡下人”,不论是在其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自传中,还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作者都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对乡村生活无比热爱之情,对下层人民的尊敬、爱戴之感,也在某种程度表达了对都市文明的厌弃,对都市人道德丧失的批判。
在《边城》中,作者为读者极力渲染了一个未经现代都市文明浸染、与世隔绝的边地小镇——茶峒,“湘西世界”的构建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作者对于故乡的点滴回忆也被带进了文本中。
沈从文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祖父、父亲、叔叔都出身行伍,父亲依据当地大多数家长的选择,希望纪律严明的军队可以对从文加以约束,自沈从文念完高小,就将从文送进当地的部队。
沈从文自小跟随军队走南闯北,目睹了种种或悲惨、或血腥、或真实的世界,而他也在这段独特的行伍生涯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底层人物不同形态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向他彰显着生命的顽强与淡然,这些奇特的经历都为他日后创作埋下了伏笔,而湘西的风土人情、奇山异水也在他年少的心中植根发芽,深深震撼着他的心灵。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1)一、“诗人批评家”与“创作室批评”:沈从文的小说批评理论我在《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一个标准的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他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是典型的创作室批评(workshop-criticism)。
“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与论点都很有局限,他只评论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只评论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创作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创作室批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
(1) 目前收集在《沈从文文集》中第十一及第十二卷中的文论,虽然很不齐全(2),但从这些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
他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他对小说作品及理论有特别深广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严密的批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craftsman),他所论的问题全是他人未能道的经验之谈。
他对鲁迅、废名等人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镇小说的见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通过他自己在创作经验中的深入感受与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或分析。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都是在创作之余,把零星创作中的真知灼见,反复地表达在不很正式的文学批评文章中。
第一类,属于序言或后记,把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之新发现或艺术技巧记录下来。
第二类是直接评论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论冯文炳》,这些都是沈从文向他们学习过,或受其影响的作家。
第三类是笔记式的篇幅较长的著作如《烛虚》。
这些论说序跋,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写的小说辩护,另一方面为他所写的小说建设一个理论架构,以便得到承认与建立其权威性。
(3) 沈从文在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开始写作。
大约到了1928年后,才开始写出《柏子》、《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夫妇》、《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代表杰作。
因此他的批评理论在193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
(4)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他自己的作品来考察当代或前辈的作品,因此对那些深感兴趣又影响过他的以抒情笔调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就大为赞赏,但对那些与他创作兴趣背道而驰的就表现冷漠,甚至攻击,对郭沫若小说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着社会现象与梦象的小说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作品建设理论基础,争取承认,因此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沈从文,所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读者解读作品,更不是为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学理论新体系。
他的动机与目的很有局限性,从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来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说理论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这构成了他关于小说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前后,当写实主义、人生文学成为主流时,沈从文注意到很多作家凭着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如为人生),一个不甚坚实的概念(如“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去写作,结果“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11:165-166),因此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除了肯定小说要表现人生,但这绝不止于外在表面的客观事物现象,除了人生现象,应该还有梦幻现象,要不然小说就沦为新闻式的报告了: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
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
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
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文集》,12:113-114)他特别强调人事和梦要相混结合起来,因此这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能分开的。
把它们分开以后,我们小说中的人,生命或灵魂,就会破碎。
沈从文的小说要把它们粘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体。
” 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压力,沈从文说小说家要“贴近人生”,但写作时却要“俨然与外界绝缘”,绝对不能被一些崇高观念左右:我虽明白人应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
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
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
(《文集》,11:41-42)他要“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而感觉是个人的,超现实的。
所以接下去,他再强调写小说要“独断”: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集》,11:42)沈从文在《水云》那篇回忆式的哲理散文里,很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经常陶醉于梦境的经验。
写作对沈从文来说,是“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
《边城》那本中篇小说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虽然“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他为小说中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
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文集》,11:45)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常常写的不是眼见的状态,而是官能的感受、回忆、梦幻,请看下面几段文字: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
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文集》,11:39)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感觉的回忆”。
(《连萃创作—集·序》见吴立昌《沈从文》,34页)超越普通人的习惯,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
(《文集》,11:357)三、探索人的灵魂与意识深处的小说好的小说家,不同于常人,因为他能够从普通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与梦象中,发现一般作家不易发现的东西,打开普通作家不能进入的世界: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
(5)从1928到1947年间,前后约二十年,沈从文写了大量有关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支流各乡村的小说。
中国土地上的湘西,一般人都能前往观光,但是沈从文小说世界中的湘西,不管是茶桐小边城或是玉家母子的菜园,七个野人的山洞,吴甘二姓族居住的乌鸡河,都是当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见,到不了的艺术世界。
(6) 沈从文在文章里,经常强调他五官的敏感性能,他善于通过官能,向自然捕捉声音、颜色、气味,而且幻想与回忆的能力,也超乎常人。
这种能力能促进作品之深度:天之予人经验,厚薄多方,不可一例。
耳目口鼻虽具同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觉吸收外物外事本性。
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
(《文集》,11:280)他自认是一个能表现生命深度的作家,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
相反的,沈从文下面这段文字,很显然是针对当时长久住在北京或上海的现实主义作家,嘲笑他们感觉官能已麻木不仁,因此作品自然没有深度,更没有独创性: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
(《文集》,11:44)沈从文一再说创作描写不是眼见的状态,不是一般人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不是普通作家容易发现的东西。
到底这种小说所表现的由人事与梦象相混合的是什么世界?他在《烛虚》中指出,他的小说最终目的,就在于探索人的灵魂或意识边际,这样才能发现人,说明爱与死的各种形式: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僧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文集》,11:281)接下去,沈从文说在现代文明社会,“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
他的小说便是寻找还未被现代社会文明打破的人,还包括“我”作者自己。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他在作品里把农民“加以解剖与描绘”就是要探索其灵魂深处或意识层面: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指《长河》),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
(《文集》,7:4)因为沈从文在论小说时,从想象、意识,到探索与解剖灵魂,金介甫,吴立昌都肯定他对佛洛依德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有所认识。
(7) 沈从文的《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
在现实层面里,苗族把毒药倒进乌鸡河里毒鱼,这是一年一度的大浩劫。
吴姓兄弟溯河而上,在月夜里进入梦幻中,深入野蛮民族好斗嗜杀的潜意识深处,这条河是历史之河,意识之河,把这对孪生的青年人,带回人类蛮荒时代,人类灵魂之黑暗深处去。
所以在河的上流,他们发现荒滩上有被流血染红的岩石,有哀悼鬼魂而建的庙,还有旧战场,以及唯一甘族生还的女子,这些都是二族互相残杀带来的悲剧。
(8)四、小说是要发现人性,解释人生的形式沈从文要小说家超越现实,进入梦象,进入一般作家不能到达的地方,描写眼睛看不到的状态,探索人类的灵魂或意识底层,他的目的是要发现人,重新对人给予诠释,因为他在寻找中的人类,甚至自我的生命与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的观念把它粘合起来”。
在沈从文眼中,人的生命与灵魂破破碎碎是许多原因所造成,而最常表现在他作品中的是野蛮的风俗与现代文明。
譬如他说湘西的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是指现代都市文明侵入乡村与小城镇后毁灭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与人性。
沈从文在更早的作家如鲁迅的小说中,已看见中国小乡镇及其人民在新的物质文明侵入后,“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
农民性格灵魂固然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城市人,像沈从文小说中的绅士政客,更丧失人性,道德沦丧。
《夫妇》、《三三》中的城市人性已变形,身心都得了病,《菜园》中的乡绅政客,就更加卑鄙丑恶地去残害善良的老百姓了。
所以沈从文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他用小说艺术建设的庙所供奉的是“人性”,因此他要表现真正的人性,请看下面引自各篇论文的段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文集》,11:45)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