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韵白十三辙上口字与原读音之演变
- 格式:xls
- 大小:54.50 KB
- 文档页数: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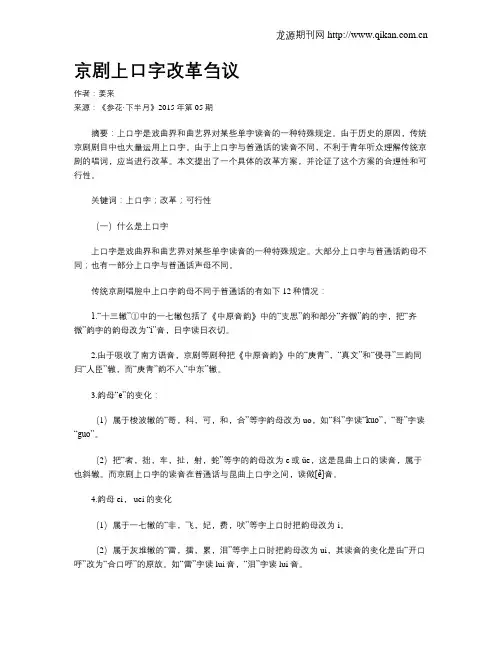
京剧上口字改革刍议作者:姜来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05期摘要:上口字是戏曲界和曲艺界对某些单字读音的一种特殊规定。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京剧剧目中也大量运用上口字。
由于上口字与普通话的读音不同,不利于青年听众理解传统京剧的唱词,应当进行改革。
本文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并论证了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上口字;改革;可行性(一)什么是上口字上口字是戏曲界和曲艺界对某些单字读音的一种特殊规定。
大部分上口字与普通话韵母不同;也有一部分上口字与普通话声母不同。
传统京剧唱腔中上口字韵母不同于普通话的有如下12种情况:1.“十三辙”①中的一七辙包括了《中原音韵》中的“支思”韵和部分“齐微”韵的字,把“齐微”韵字的韵母改为“i”音,日字读日衣切。
2.由于吸收了南方语音,京剧等剧种把《中原音韵》中的“庚青”,“真文”和“侵寻”三韵同归“人臣”辙,而“庚青”韵不入“中东”辙。
3.韵母“e”的变化:(1)属于梭波辙的“哥,科,可,和,合”等字韵母改为uo,如“科”字读“kuo”,“哥”字读“guo”。
(2)把“者,拙,车,扯,射,蛇”等字的韵母改为e或üe,这是昆曲上口的读音,属于也斜辙。
而京剧上口字的读音在普通话与昆曲上口字之间,读做[ě]音。
4.韵母ei, uei的变化(1)属于一七辙的“非,飞,妃,费,吠”等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i。
(2)属于灰堆辙的“雷,擂,累,泪”等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ui,其读音的变化是由“开口呼”改为“合口呼”的原故。
如“雷”字读lui音,“泪”字读lui音。
(3)“贼”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e,归入梭波辙,读如“ze”。
5.韵母üe的改变:(1)属于梭波辙的“觉,脚,角,却,确”等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o,如“觉”字读jue音,“蛾”字读ngo音。
(2)属于梭波辙的“学,岳,药,约”等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io。
6.韵母an的变化属于言前辙的“般,伴,番,盘”等字上口时把韵母改为uan,此读音变化是由开口呼改为合口呼的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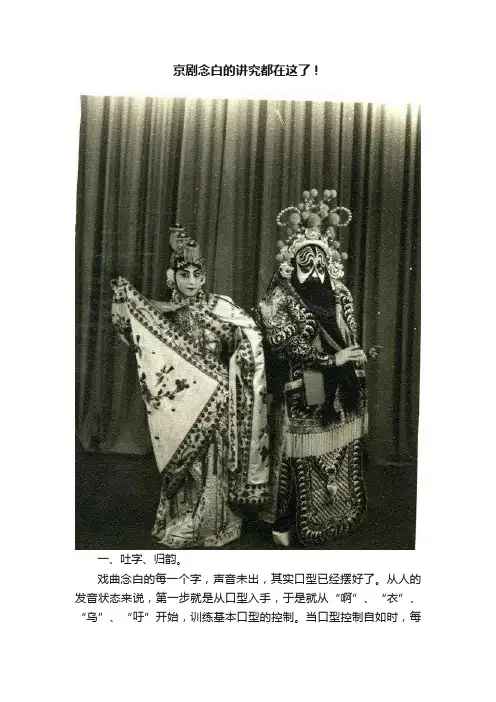
京剧念白的讲究都在这了!一、吐字、归韵。
戏曲念白的每一个字,声音未出,其实口型已经摆好了。
从人的发音状态来说,第一步就是从口型入手,于是就从“啊”、“衣”、“乌”、“吁”开始,训练基本口型的控制。
当口型控制自如时,每一个字音发出的最初阶段,就能达到“吐”出来的一颗珠子那样,是一种趋于“圆”的状态。
口型与口形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
表演者需要把这种区别掌握清楚,同时又借助它们的联系,把每个字都“吐”成“圆”的。
比如《林冲夜奔》中的诗:欲送登高千里目,愁云低锁衡阳路。
鱼书不至雁无凭,几番空作悲秋赋。
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归韵,是指通过不同的口型唱出每个字的音韵,把字的音形准确而完美地表达出来。
归韵与押韵不是一回事。
押韵主要是抓住韵母的韵腹和韵尾,找到语音的相同部分即可。
归韵则需要抓住韵母的韵头、韵腹和韵尾三个部分,尤其是要抓住韵头;抓住了这个韵头,就能给控制住后面的韵腹、韵尾,就可以把每个字的音韵归拢起来。
比如前面所举例子中的“千”——ciān,其中iān是一个有韵头介母的结构,归韵就首先抓住韵头介母——ī,从而把后面的——ān 归拢为统一的“烟”这个声韵中。
二、五音。
“五音”原是音韵学中专门研究字音声母部分的学问。
对京剧表演者与爱好者来说,在唱念中如何掌握声母发音的部位和“分寸”,做到吐字准确,“口劲”饱满,练习“五音”是有很大好处的。
关于“五音”的练习,可借用传统与现代的多种成熟的说法和练习法。
⑴唇音(5个)。
b、p、m、f、v。
b、p、m属重唇音,又叫双唇音;f属轻唇音,又叫单唇音或唇齿音;v是方言声母,也属唇音。
附:唇音训练的绕口令。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⑵舌音(9个)。
d、t、n、l、ň、zh、ch、sh、r。
d、t、n、ň属舌尖音;l属舌尖中音;zh、ch、sh、r属舌尖后音,也叫翘舌音。
附:舌音训练的绕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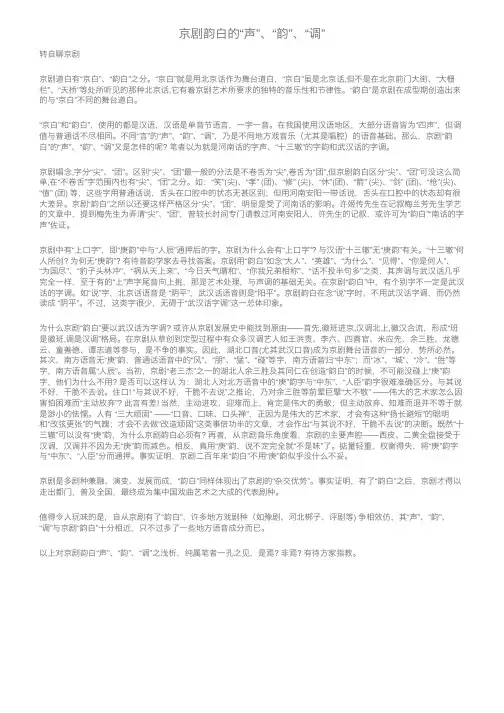
京剧韵⽩的“声”、“韵”、“调”转⾃聊京剧京剧道⽩有“京⽩”、“韵⽩”之分。
“京⽩”就是⽤北京话作为舞台道⽩,“京⽩”虽是北京话,但不是在北京前门⼤街、“⼤栅栏”、“天桥”等处所听见的那种北京话,它有着京剧艺术所要求的独特的⾳乐性和节律性。
“韵⽩”是京剧在成型期创造出来的与“京⽩”不同的舞台道⽩。
“京⽩”和“韵⽩”,使⽤的都是汉语,汉语是单⾳节语⾔,⼀字⼀⾳。
在我国使⽤汉语地区,⼤部分语⾳皆为“四声”,但调值与普通话不尽相同。
不同“⾔”的“声”、“韵”、“调”,乃是不同地⽅戏⾳乐(尤其是唱腔)的语⾳基础。
那么,京剧“韵⽩”的“声”、“韵”、“调”⼜是怎样的呢? 笔者以为就是河南话的字声、“⼗三辙”的字韵和武汉话的字调。
京剧唱念,字分“尖”、“团”。
区别“尖”、“团”最⼀般的分法是不卷⾆为“尖”,卷⾆为“团”,但京剧韵⽩区分“尖”、“团”可没这么简单,在“不卷⾆”字范围内也有“尖”、“团”之分。
如:“笑”(尖)、“孝” (团)、“修” (尖)、“休”(团)、“箭” (尖)、“剑” (团)、“枪”(尖)、“值” (团) 等,这些字⽤普通话说,⾆头在⼝腔中的状态⽆甚区别;但⽤河南安阳⼀带话说,⾆头在⼝腔中的状态却有很⼤差异。
京剧“韵⽩”之所以还要这样严格区分“尖”、“团”,明显是受了河南话的影响。
许姬传先⽣在记叙梅兰芳先⽣学艺的⽂章中,提到梅先⽣为弄清“尖”、“团”,曾较长时间专门请教过河南安阳⼈,许先⽣的记叙,或许可为“韵⽩”“南话的字声”佐证。
京剧中有“上⼝字”,即“庚韵”中与“⼈⾠”通押后的字。
京剧为什么会有“上⼝字”? 与汉语“⼗三辙”⽆“庚韵”有关。
“⼗三辙”何⼈所创? 为何⽆“庚韵”? 有待⾳韵学家去寻找答案。
京剧⽤“韵⽩”如念“⼤⼈”、“英雄”、“为什么”、“见得”、“你是何⼈”、“为国尽”、“豹⼦头林冲”、“祸从天上来”、“今⽇天⽓晴和”、“你我兄弟相称”、“话不投半句多”之类,其声调与武汉话⼏乎完全⼀样,⾄于有的“上”声字尾⾳向上挑,那是艺术处理,与声调的基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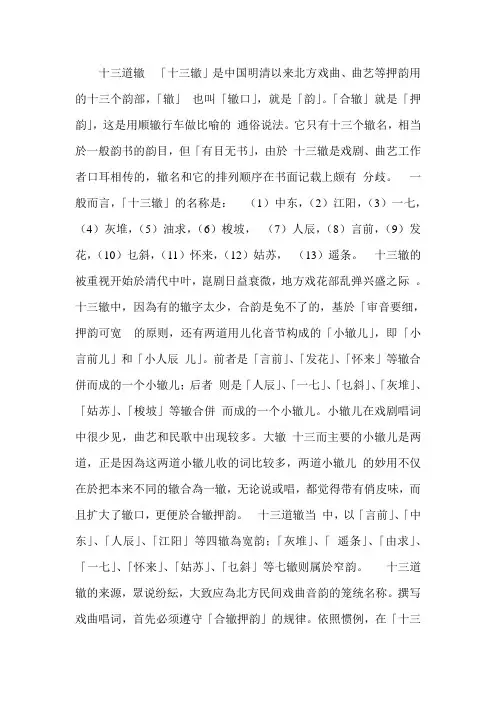
十三道辙「十三辙」是中国明清以来北方戏曲、曲艺等押韵用的十三个韵部,「辙」也叫「辙口」,就是「韵」。
「合辙」就是「押韵」,这是用顺辙行车做比喻的通俗说法。
它只有十三个辙名,相当於一般韵书的韵目,但「有目无书」,由於十三辙是戏剧、曲艺工作者口耳相传的,辙名和它的排列顺序在书面记载上颇有分歧。
一般而言,「十三辙」的名称是:(1)中东,(2)江阳,(3)一七,(4)灰堆,(5)油求,(6)梭坡,(7)人辰,(8)言前,(9)发花,(10)乜斜,(11)怀来,(12)姑苏,(13)遥条。
十三辙的被重视开始於清代中叶,崑剧日益衰微,地方戏花部乱弹兴盛之际。
十三辙中,因為有的辙字太少,合韵是免不了的,基於「审音要细,押韵可宽的原则,还有两道用儿化音节构成的「小辙儿」,即「小言前儿」和「小人辰儿」。
前者是「言前」、「发花」、「怀来」等辙合併而成的一个小辙儿;后者则是「人辰」、「一七」、「乜斜」、「灰堆」、「姑苏」、「梭坡」等辙合併而成的一个小辙儿。
小辙儿在戏剧唱词中很少见,曲艺和民歌中出现较多。
大辙十三而主要的小辙儿是两道,正是因為这两道小辙儿收的词比较多,两道小辙儿的妙用不仅在於把本来不同的辙合為一辙,无论说或唱,都觉得带有俏皮味,而且扩大了辙口,更便於合辙押韵。
十三道辙当中,以「言前」、「中东」、「人辰」、「江阳」等四辙為宽韵;「灰堆」、「遥条」、「由求」、「一七」、「怀来」、「姑苏」、「乜斜」等七辙则属於窄韵。
十三道辙的来源,眾说纷紜,大致应為北方民间戏曲音韵的笼统名称。
撰写戏曲唱词,首先必须遵守「合辙押韵」的规律。
依照惯例,在「十三道辙」中,可以「通押」的辙口,仅有两类:「中东」与「人辰」可通押;「灰堆」与「一七」可通押,偶尔与「怀来」辙也可通押。
“辙韵”与“合辙压韵”汉字的读音是以二十一个声母和三十五个韵母拼和而成的,一个字开头的声母为“声”,收尾的韵母就是我们所说的“韵”。
歌谣每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经常是用相同或者相近的韵母构成的,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声音回环的和谐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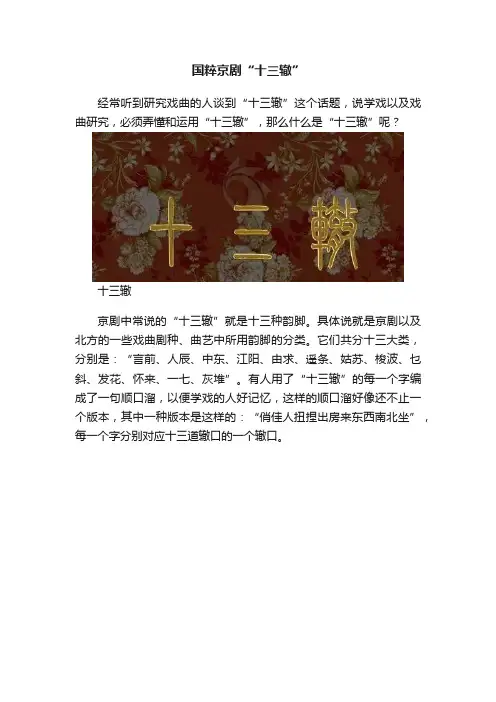
国粹京剧“十三辙”经常听到研究戏曲的人谈到“十三辙”这个话题,说学戏以及戏曲研究,必须弄懂和运用“十三辙”,那么什么是“十三辙”呢?十三辙京剧中常说的“十三辙”就是十三种韵脚。
具体说就是京剧以及北方的一些戏曲剧种、曲艺中所用韵脚的分类。
它们共分十三大类,分别是:“言前、人辰、中东、江阳、由求、遥条、姑苏、梭波、乜斜、发花、怀来、一七、灰堆”。
有人用了“十三辙”的每一个字编成了一句顺口溜,以便学戏的人好记忆,这样的顺口溜好像还不止一个版本,其中一种版本是这样的:“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每一个字分别对应十三道辙口的一个辙口。
十三个字对应十三个辙口“十三辙”的产生来源于元代戏曲,与写诗用韵的“平水韵”相比,它把原来的五声韵变为四声韵,把入声都归到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部里了,当然,创作诗词的人们还是用“平水韵”,只是在戏曲,特别是北方戏曲的创作中,人们才使用十三辙。
那么,作为古典艺术的戏曲之祖昆曲,它和诗词有很深的渊源,它的唱词,就是仿照词的形式,由长句短句所组成。
并且多数时候用“上、去、入”声来押韵,也就是诗词里所说的仄声押韵。
那么,在晚清,作为后来戏曲的新生事物乱弹(也就是梆子、汉剧、徽剧、秦腔、皮黄的总称,这样的称号是相对于昆曲而言),则是多数采用的是诗这种形式,唱词多是七字句和十字句,韵脚也是上句用仄声而下句用平声。
合辙押韵是对诗词的要求,同样戏曲也一样。
元代以前的韵书动辄上百个韵脚,元代《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把戏曲用韵归纳为“十九辙”,清初樊腾凤著《五方元音》再次缩减为“十二辙”,清中晚期的叶元清所著《明心鉴》增加一辙“灰堆”,而固定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十三辙”。
叶元清所著《明心鉴》数百年来,京剧艺人们在戏曲的演唱中运用十三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不过很多艺人会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所偏好。
比如,闭口音比较好的艺人会倾向于编演和演唱“一七”“壬辰”“中东”等辙口的戏,比如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他的嗓音立音脑后音比较好,唱法也是幽咽婉转,耐人寻味,所以,听他的戏闭口音的辙口发来尤为回味无穷,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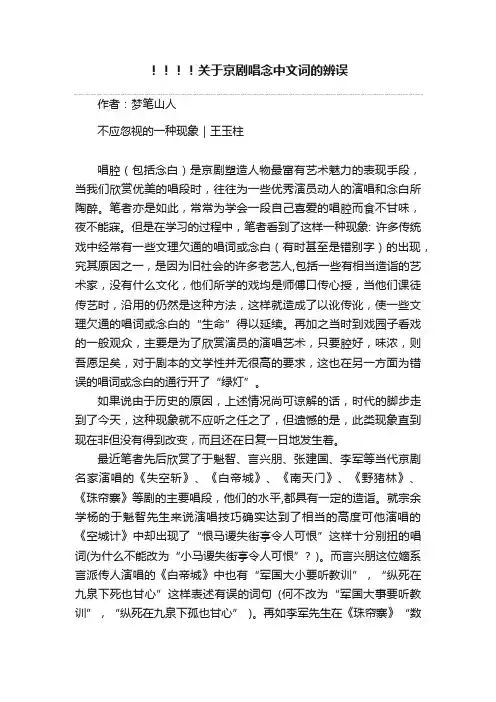
关于京剧唱念中文词的辨误作者:梦笔山人不应忽视的一种现象|王玉柱唱腔(包括念白)是京剧塑造人物最富有艺术魅力的表现手段,当我们欣赏优美的唱段时,往往为一些优秀演员动人的演唱和念白所陶醉。
笔者亦是如此,常常为学会一段自己喜爱的唱腔而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笔者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许多传统戏中经常有一些文理欠通的唱词或念白(有时甚至是错别字)的出现,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旧社会的许多老艺人,包括一些有相当造诣的艺术家,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所学的戏均是师傅口传心授,当他们课徒传艺时,沿用的仍然是这种方法,这样就造成了以讹传讹,使一些文理欠通的唱词或念白的“生命”得以延续。
再加之当时到戏园子看戏的一般观众,主要是为了欣赏演员的演唱艺术,只要腔好,味浓,则吾愿足矣,对于剧本的文学性并无很高的要求,这也在另一方面为错误的唱词或念白的通行开了“绿灯”。
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上述情况尚可谅解的话,时代的脚步走到了今天,这种现象就不应听之任之了,但遗憾的是,此类现象直到现在非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发生着。
最近笔者先后欣赏了于魁智、言兴朋、张建国、李军等当代京剧名家演唱的《失空斩》、《白帝城》、《南天门》、《野猪林》、《珠帘寨》等剧的主要唱段,他们的水平,都具有一定的造诣。
就宗余学杨的于魁智先生来说演唱技巧确实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他演唱的《空城计》中却出现了“恨马谡失街亭令人可恨”这样十分别扭的唱词(为什么不能改为“小马谡失街亭令人可恨”? )。
而言兴朋这位嫡系言派传人演唱的《白帝城》中也有“军国大小要听教训”,“纵死在九泉下死也甘心”这样表述有误的词句(何不改为“军国大事要听教训”,“纵死在九泉下孤也甘心” )。
再如李军先生在《珠帘寨》“数太保”一段唱腔中也有“六太保上阵似白袍“这样比喻欠妥的唱词出现。
另外,作为当之无愧的奚派传人的张建国先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他演唱的《南天门》中把“怕的是到不了大同地面”这个唱句里的“大”字唱成了“代”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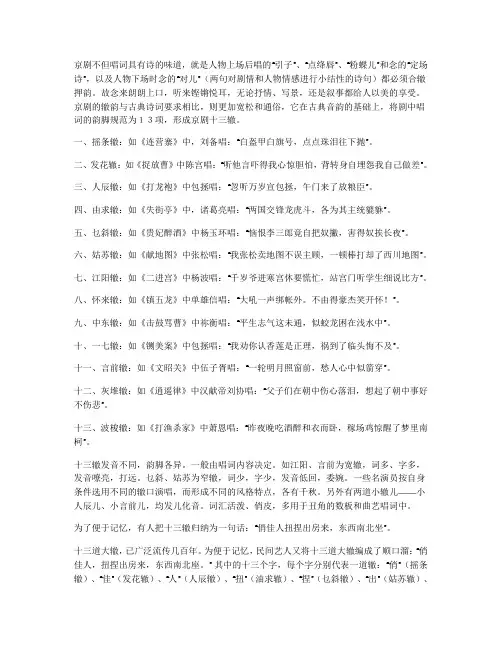
京剧不但唱词具有诗的味道,就是人物上场后唱的“引子”、“点绛唇”、“粉蝶儿”和念的“定场诗”,以及人物下场时念的“对儿”(两句对剧情和人物情感进行小结性的诗句)都必须合辙押韵。
故念来朗朗上口,听来铿锵悦耳,无论抒情、写景,还是叙事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京剧的辙韵与古典诗词要求相比,则更加宽松和通俗,它在古典音韵的基础上,将剧中唱词的韵脚规范为13项,形成京剧十三辙。
一、摇条辙:如《连营寨》中,刘备唱:“白盔甲白旗号,点点珠泪往下抛”。
二、发花辙:如《捉放曹》中陈宫唱:“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
三、人辰辙:如《打龙袍》中包拯唱:“忽听万岁宣包拯,午门来了放粮臣”。
四、由求辙:如《失街亭》中,诸葛亮唱:“两国交锋龙虎斗,各为其主统貔貅”。
五、乜斜辙:如《贵妃醉酒》中杨玉环唱:“恼恨李三郎竟自把奴撇,害得奴挨长夜”。
六、姑苏辙:如《献地图》中张松唱:“我张松卖地图不误主顾,一顿棒打却了西川地图”。
七、江阳辙:如《二进宫》中杨波唱:“千岁爷进寒宫休要慌忙,站宫门听学生细说比方”。
八、怀来辙:如《镇五龙》中单雄信唱:“大吼一声绑帐外。
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九、中东辙:如《击鼓骂曹》中祢衡唱:“平生志气这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
十、一七辙:如《铡美案》中包拯唱:“我劝你认香莲是正理,祸到了临头悔不及”。
十一、言前辙:如《文昭关》中伍子胥唱:“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十二、灰堆辙:如《逍遥律》中汉献帝刘协唱:“父子们在朝中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十三、波梭辙:如《打渔杀家》中萧恩唱:“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十三辙发音不同,韵脚各异。
一般由唱词内容决定。
如江阳、言前为宽辙,词多、字多,发音嘹亮,打远。
乜斜、姑苏为窄辙,词少,字少,发音低回,委婉。
一些名演员按自身条件选用不同的辙口演唱,而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各有千秋。
另外有两道小辙儿——小人辰儿、小言前儿,均发儿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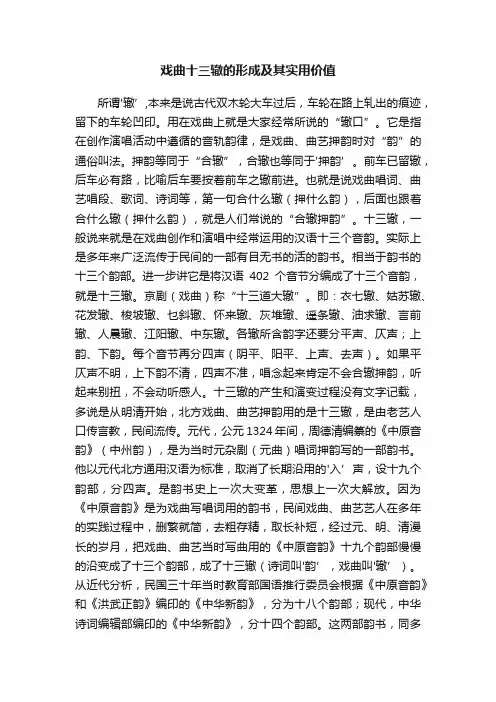
戏曲十三辙的形成及其实用价值所谓'辙’,本来是说古代双木轮大车过后,车轮在路上轧出的痕迹,留下的车轮凹印。
用在戏曲上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辙口”。
它是指在创作演唱活动中遵循的音轨韵律,是戏曲、曲艺押韵时对“韵”的通俗叫法。
押韵等同于“合辙”,合辙也等同于'押韵’。
前车已留辙,后车必有路,比喻后车要按着前车之辙前进。
也就是说戏曲唱词、曲艺唱段、歌词、诗词等,第一句合什么辙(押什么韵),后面也跟着合什么辙(押什么韵),就是人们常说的“合辙押韵”。
十三辙,一般说来就是在戏曲创作和演唱中经常运用的汉语十三个音韵。
实际上是多年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部有目无书的活的韵书。
相当于韵书的十三个韵部。
进一步讲它是将汉语402个音节分编成了十三个音韵,就是十三辙。
京剧(戏曲)称“十三道大辙”。
即:衣七辙、姑苏辙、花发辙、梭坡辙、乜斜辙、怀来辙、灰堆辙、遥条辙、油求辙、言前辙、人晨辙、江阳辙、中东辙。
各辙所含韵字还要分平声、仄声;上韵、下韵。
每个音节再分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如果平仄声不明,上下韵不清,四声不准,唱念起来肯定不会合辙押韵,听起来别扭,不会动听感人。
十三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没有文字记载,多说是从明清开始,北方戏曲、曲艺押韵用的是十三辙,是由老艺人口传言教,民间流传。
元代,公元1324年间,周德清编纂的《中原音韵》(中州韵),是为当时元杂剧(元曲)唱词押韵写的一部韵书。
他以元代北方通用汉语为标准,取消了长期沿用的'入’声,设十九个韵部,分四声。
是韵书史上一次大变革,思想上一次大解放。
因为《中原音韵》是为戏曲写唱词用的韵书,民间戏曲、曲艺艺人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删繁就简,去粗存精,取长补短,经过元、明、清漫长的岁月,把戏曲、曲艺当时写曲用的《中原音韵》十九个韵部慢慢的沿变成了十三个韵部,成了十三辙(诗词叫'韵’,戏曲叫'辙’)。
从近代分析,民国三十年当时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根据《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编印的《中华新韵》,分为十八个韵部;现代,中华诗词编辑部编印的《中华新韵》,分十四个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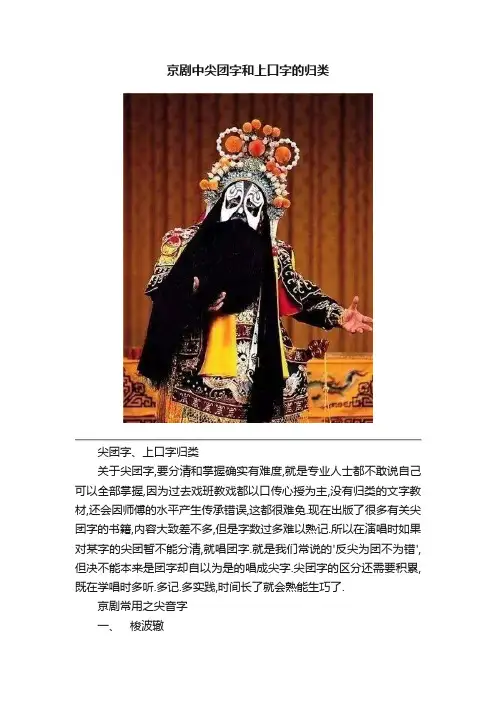
京剧中尖团字和上口字的归类尖团字、上口字归类关于尖团字,要分清和掌握确实有难度,就是专业人士都不敢说自己可以全部掌握,因为过去戏班教戏都以口传心授为主,没有归类的文字教材,还会因师傅的水平产生传承错误,这都很难免.现在出版了很多有关尖团字的书籍,内容大致差不多,但是字数过多难以熟记.所以在演唱时如果对某字的尖团暂不能分清,就唱团字.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尖为团不为错',但决不能本来是团字却自以为是的唱成尖字.尖团字的区分还需要积累,既在学唱时多听.多记.多实践,时间长了就会熟能生巧了.京剧常用之尖音字一、梭波辙阴平:(siao)削。
阳平:(ziao)嚼、爵。
去声:(ciao)雀、鹊、趞。
二、也斜辙阴平:(zie)接、疖、节、嗟,(cie)切,(sie)些,(sue)薛。
阳平:(zie)截、捷、睫、婕、节,(sie)斜、邪,(zue)绝。
上声:(zie)姐,(cie)且,(sie)写,(sue)雪去声:(zie)借、籍,(cie)切、窃、妾、趄,(sie)泻、泄、绁、亵、谢、卸、榭、屑、燮、卨。
三、一七辙阴平:(zi)齑、跻、迹、勣、绩、赍、积、缉,(ci)漆、七、柒、沏、栖、戚、槭、嘁、妻、萋、凄,(si)西、栖、茜、牺、粞、犀、樨、息、熄、悉、膝、蟋、惜、夕、析、淅、晰、皙、蜥、螅、昔、惜、嘶(上口字)、锡,(zv)狙、疽、苴、雎,(cv)趋、蛆,(sv)需、戌、须、胥、谞、鬚。
阳平:(zi)脊、瘠、籍、藉、辑、楫、疾、嫉、蒺、集、即,(ci)齐、脐、蛴,(si)习、袭、席、媳、隰、裼,(sv)徐。
上声:(zi)挤、济、脊,(si)洗、玺、铣、徙,(zv)沮、咀、龃,(cv)取、娶。
去声:(zi)剂、济、荠、霁、际、寂、稷、祭、穄、鲫、迹,(ci)砌、妻,(si)细、舄、澙,(zv)聚、沮,(cv)趣、觑,(sv)续、绪、叙、酗、恤、序、婿、絮。
四、摇条辙阴平:(ziao)椒、焦、蕉、礁、僬、鹪、膲,(ciao)悄、锹、缲,(siao)肖、消、宵、逍、硝、霄、萧、箫、潇、削、蟏、销、魈、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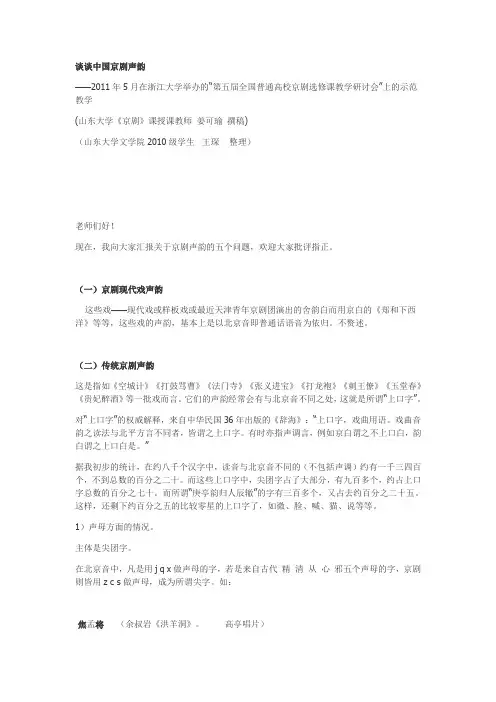
谈谈中国京剧声韵——2011年5月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普通高校京剧选修课教学研讨会”上的示范教学(山东大学《京剧》课授课教师姜可瑜撰稿)(山东大学文学院2010级学生王琛整理)老师们好!现在,我向大家汇报关于京剧声韵的五个问题,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京剧现代戏声韵这些戏——现代戏或样板戏或最近天津青年京剧团演出的舍韵白而用京白的《郑和下西洋》等等,这些戏的声韵,基本上是以北京音即普通话语音为依归。
不赘述。
(二)传统京剧声韵这是指如《空城计》《打鼓骂曹》《法门寺》《张义进宝》《打龙袍》《刺王僚》《玉堂春》《贵妃醉酒》等一批戏而言。
它们的声韵经常会有与北京音不同之处,这就是所谓“上口字”。
对“上口字”的权威解释,来自中华民国36年出版的《辞海》:“上口字,戏曲用语。
戏曲音韵之读法与北平方言不同者,皆谓之上口字。
有时亦指声调言,例如京白谓之不上口白,韵白谓之上口白是。
”据我初步的统计,在约八千个汉字中,读音与北京音不同的(不包括声调)约有一千三四百个,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而这些上口字中,尖团字占了大部分,有九百多个,约占上口字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而所谓“庚亭韵归人辰辙”的字有三百多个,又占去约百分之二十五。
这样,还剩下约百分之五的比较零星的上口字了,如微、脸、喊、猫、说等等。
1)声母方面的情况。
主体是尖团字。
在北京音中,凡是用j q x做声母的字,若是来自古代精清从心邪五个声母的字,京剧则皆用z c s做声母,成为所谓尖字。
如:焦孟将(余叔岩《洪羊洞》。
高亭唱片)我的妻(汪笑侬《马前泼水》。
百代唱片)面前(高庆奎《鱼藏剑》。
百代唱片)血样鲜(赵荣琛《青霜剑》。
人民唱片)怎敢不写(汪笑侬《孝妇羹》。
百代唱片)听端详(言菊朋《打鼓骂曹》。
百代唱片)而团音则是来自古代见溪群晓匣五个声母的字,京剧则皆是用j q x(实际是用的舌面中音)做声母。
如:孙玉姣(言菊朋《法门寺》。
高亭唱片)不可欺(三麻子《徐策跑城》。

什么是京剧唱、念中的“韵白”?
什么是京剧唱、念中的“韵白”?
京剧的唱、念语音中。
有一套与生活语言的语音距离较远的诵读方法,被称为“韵白”。
已故文学家汪曾祺先生,曾把韵白的特征归纳为:“不文不白,似骈似散,抑扬顿挫,起落铿锵,节奏鲜明,很有表现力。
”从语音诵读的状态来推测,韵白应来源于古代诵读韵文的语音方式。
有研究认为,京剧韵白的读音主要来自古代中州韵和近代湖广音。
在京剧唱、念中,韵白通过声调的高低起伏和参差错落,通过字音的节奏顿挫和旋律悠扬,不仅对具体剧情做出清晰的传递,并且形成了一种气势上的夸张,更加有利于凸显人物的特定情感内容。
韵白在京剧中主要运用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而处于奴仆、丫鬟地位的人物一般使用“京白”,不用韵白。
有时候剧中主要人物或重要人物在某些轻松随意的私下场合里,也会偶尔不用韵白,而使用一点京白。
这说明韵白是一种表现社会文化层面的语言标志,代表着一种高雅的社会场合与社会身份。
京剧唱念的咬字、吐音、归韵(朱云鹏)朱云鹏先生《摘缨会》《南天门》剧照京剧唱词和诗词曲的关系很密切,不过它更通俗化。
后来京剧逐渐为王公贵族所欣赏和喜爱,而且还进入了宫廷,为皇帝、后妃所喜爱,越来越走红,发展得很快,在北京天津一带成了一个主要的剧种。
上面谈到的“十三道辙”。
实际上它是由诗韵发展而来。
在唐朝已开始有了诗韵,有人按“切韵”把汉字归纳为206韵;南宋时平水人(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刘渊及金人王文郁合并为106韵。
其中平声三十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合起来共106韵。
因作者是平水人,又称为平水韵。
元周德清辑《中原音韵》将元曲所用的曲韵归纳为19韵,用于戏曲和曲艺。
“曲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在元曲中四声不能通押的,十三辙用于戏曲,似乎可以通押,但一般情况下单句末字可以押仄声,双句末字则应以平声收尾。
单句可以不合辙(撬辙),戏曲俗语“撬单不撬双”(平仄不合也是撬辙)。
如上面提到的《马鞍山》六句唱词中第三、五两句的“月”、“落”两字撬撤。
这和古诗相类似。
如李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其中“光、霜、乡”押的是“阳韵”,在“十三辙”中则为“江阳辙”。
在这诗中第三句不押韵,第一句押韵的。
《马鞍山》第一句的“行”也是合辙的。
再举《空城计》城楼抚琴时一段[西皮二六]为例,共二十二句(唱词从略)。
每句最末一字依次是“景、纷、影、兵、听、行、能、亭、幸、城、等、心、净、兵、敬、军、进、情、个、兵、定、琴。
”全部唱段是“人辰辙”。
其中只有第十九句的“个”字撬辙。
所有双句的末字均为平声字;而单句除第十九句外都合辙,但不是平声字。
京剧唱段中单句合辙的很多,特别是在节奏性强速度快的如[西皮流水]、[西皮二六]和[快板]等板式中比较常见,这恐怕是为了加强音乐性,使人听了乐感较好。
至于原板、慢板中单句撬辙就很常见的了。
但第一句一般都是合辙的。
京剧的唱词中有些字不能按京音念,不然就不押韵了。
京剧上口字的来源、分类上口字的来源及分类上口字主要来自《中原音韵》,其次来自古音和鄂、皖、豫、苏等地的方言。
元代周德清著的《中原音韵》,共分19个韵部,即“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
”京剧中的上口字大都来自于该书,罗培常先生于1935年将上口字归纳为十一个方面:1、《中原音韵》齐微部里舌尖后音zh、ch、sh、r四母字,北京久读zhi、chi、shi、ri,而京剧读zhi:(读似“直衣”)、chi: (读似“池衣”)、shi:(读似“师衣”)、ri:(读似“日衣”)。
京剧归入衣齐辙。
例如“知”不读zhi而读zhi:,“痴”不读chi而读chi:,“世”不读shi而读shi:,“日”不读ri而读ri:。
这里zhi、chi、shi、ri中的i和zhi:、chi:、shi:、ri:中的i:不一样,后者是可以独立存在的韵母,而前者是不能独立存在,须与特定声母相拼的后置性韵母,为了加以区别,将后者i旁边加两点。
2、《中原音韵》鱼模部里的舌尖后音zh、ch、sh、r四母字,北京人读zhu、chu、shu、ru,而京剧中应读zhü、chü、shü、rü,归入衣齐辙。
例如“诛”不读zhu而读zhü,“处”不读chu而读chü,“书”不读shu而读shü,“如”不读ru而读rü。
3、《中原音韵》齐微部的轻唇音f和v(读似英语的v)两母字,北京人读fei、wei,为灰堆辙,而京剧中读fi、vi。
京剧中归入衣齐辙。
例如“飞”不读fei而读fi,“未”不读wei而读vi。
4、《中原音韵》齐微部的l声母字,北京人读lei,属开口呼,而京剧中读luei(lui),属合口呼。
比如“雷”在京剧中读lui而不读lei。
归入灰堆辙。
5、《中原音韵》皆来部j、q、x这三母字,北京人读jie、qie、xie,而京剧中读jiai、qiai、xiai。
京剧十三辙的发音位置详解(文章内容来自网络,作者不详)我当学生时总觉“十三辙”很难记忆于脑海中,但藉著一句話就能朗郎上口,这句话是:“东、西、南、北、走、家、好、派、车、接、姑、娘”。
这样的念法十分好记,十三个字由于辙口不一样,发音的部位着力点也不一样,口腔空间大小也不一样。
下面我根据“十三个辙口字”做详细发音点位的剖析。
“十三辙”吐字、发音的着力点:东:(中东辙)汉语拼音是“d-ong-dong”,属”撮口音“,口型嘬住,气送字出,从硬腭穿鼻到软腭吸起,口腔空间适当加大,内吸感觉明显,要用点脑后音,假如你找不到,可将后颈肌挺立,既能找到这个字的点位。
西:(一七辙)汉语拼音是”x-i-xi”,此音属闭口音,门牙上提,用力啃住,舌尖放平,鼻孔小洞打开,气从鼻梁直到脑门,注意嘴角不要用力横拉变得又挤又扁。
南:(言前辙)汉语拼音是:”n-an-nan”,半开口音,吸起硬腭舌尖放平,口张吧要过大,但内部软腭要依旧吸起,鼻腔要畅通,否则容易出现两种走向:嘴张不开,字腹变形不是安音的延续,归音扭曲:口张过大,下巴用力,字就发咧,变成“半安半啊“音了。
北:(灰堆辙)汉语拼音是”b-ei-bei”唇音字,发音时人中双唇微翘,下唇硬腭吸起到软腭,保持字腹的“ei”音。
走:(由求辙)汉语拼音是”z-ou-zou”,字头“z”过渡“ou”收音,这个辙口与中东辙口腔空间近似,这个字软腭要用点喉音才能字正。
人:(人辰辙)汉语拼音是“r-en-ren”,人以“日”字引出归音,人中双唇微翘,随咬字头,口腔环关节打开,主要舌根不能用力,念这个字舌尖要舔在下牙床位置,否则字音不正,腔不能圆。
家:(发花辙)汉语拼音是“j-ia-jia”,属开口音,一般旦角最怕这个辙口,字头以“鸡”字引发,从“一”音过度到“啊”音,这就要求硬腭到软腭同时吸起,口型要小,堂音要大,共鸣靠前位(不用脑后音)。
这也存在两个走向:张不开不出声,音色发瘪:开口音往往给人们错误的概念认识,就是开口,开口,一开就大,过大口型似喇叭,声音发涩,发炸。
京剧念白中怎样读字词(戏词)生于句,句生于字,腔是字音的延长。
字有头、腹、尾。
字头.腹音、收韵,叫做声、音、韵。
每唱一字,有发声、转声、送声、收韵及承上接下诸法。
须知清浊阴阳以别其声,知长短徐急以定其节。
1)出字立音字头一出来,就要把音立住。
以“天”字为例,先出梯(ti音,圈住i音,把字音立住,再过渡到淹(ian)。
又如姚期唱“小奴才”的“小”字,字头为西(i)音,以一(i)把字音立住,再过渡到(iao)。
字的劲在出口之前,字要弹出来,很有劲,字无阻,则无力,字阻弹则音立。
咬字、吐字,嘴的动作要快、要玲珑、敏捷;嘴不可张得过大,口形要美,这点对旦角更为重要。
要腔随字走,字领腔行;要字正腔圆,声情并茂。
所以说:腔平字侧(倒)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
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予余音始绕梁。
2)过气接脉。
字出来后,中间有一过渡音,即字腹。
由此中间音过渡到字尾,叫作过气接脉。
有怀来之腹:哀、孩,也有由求之腹:侯、欧。
由腹转尾,才有归宿,勿犯以腹当尾之病。
例如:《苏武牧羊》“好不伤怀” 的“怀”字找“哀”音。
“忙回北海。
” “海”字找“孩”音。
《洪羊洞》“比成疾病” “忧”字找“欧”音。
《搜孤》“哀求娘子舍亲生”,“求”字找“欧”音。
3)切韵与收韵字有所出,必有所归。
用力从声母出发,将声母与韵母结合发音,为切韵;最后收到本韵,将字音读完整、读标准,叫做收韵。
如:“天”字,从ti出发,最后收到ian(淹);“巡”字,从xu出发,收到un(云);“东”字,从do出发,收到won9(翁);“朵”字,从du出发,收到uoe(哦),等等。
收韵,关于十三道辙的收法。
中东辙:其字必从喉间反入穿鼻而作收韵,归在“翁”音上。
例如:《洪羊洞》“为国家那何曾半日闲空。
一空”字收韵时穿鼻。
“我也曾平复了塞北西东。
”东”字收韵穿鼻。
《斩黄袍》“孤王酒醉桃花宫。
”韩素梅生来好貌容。
”宫”字、“容”字归韵要穿鼻。
江阳辙:这道辙是“昂”音,归韵时穿鼻。
从⼀些读⾳看出⽼国⾳的魅⼒(原创)其实很长时间港台很喜欢称我们⼤陆这边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咬⽂嚼字,反正说⽩了就是很⽣硬,这个我并不否认,的确我们的普通话确实有这样的弊端,⽼师在教的时候也是咬字很重,⿐⾳也很重,⽽港台不喜欢普通话,⽽喜欢叫国语.国语也就是国家母语的含义,当然国语不是现在的普通话,换句话说在早期很多⼈都是说国语的,国语早期由清朝推⾏,后来民国政府接过棒⼦,推⾏了国语,但是不容易,第⼀版国语为了考虑融合南北的习惯和⽤语,于是乎采取了南北兼存,京⾳为主的想法,也就是主⾳为北京⾳,但同时也必须汲取南北的⾳作为汉字的发⾳,不但考虑到了南北的习惯,也照顾到了不少⼈,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知识的局限性和种种原因,⽼国⾳实⾏不到两年被迫腰斩,甚⾄为此爆发了国⾳与京⾳之间的争⽃.很多⼈⽀持京⾳,反对国⾳,觉得国⾳太⼟,⽽⽼国⾳的⽀持者们则坚持京⾳为主,南北兼并的想法,新国⾳⽀持以北京⾳为标准的国⾳,甚⾄⼀些⼈说出了:注⾳字母连带国⾳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的话为国语的标准”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国⾳彻底以失败告终,⽽⽼国⾳与新国⾳的标准有明确标注:众所周知,民国初年制定的⽼国⾳和新国⾳最⼤的区别是保留尖团分别和⼊声,⽼国⾳委员会还特别说明这是符合北京数百年来⼀脉相承的读书官⾳的,不可因北京⼟话⽆之⽽偏废。
新⽼国⾳除此重⼤异同外,还有些许重要之区别,特择要录之于下:累类泪等字读 uei 韵,u不可⽆;蛇者车惹等字读如英⽂中beg check 中之e韵,哲⾆彻热等⼊声字亦读此韵之⼊声eh;歌科何饿等字读 o 韵,各渴合额等⼊声字亦读此韵之⼊声oh;学略脚岳等字读 io 韵⼊声,此韵惟有⼊声,不读iue(并标注这是⼟话⾳);⽩麦陌帛宅摘等字读 eh 韵,不读ai 或者oh,即⼀等铎药韵读oh,⼆等陌麦韵读eh,分得很清楚;街介械等字读 iai 韵,不读ie;梦蒙翁冯鹏等字读 ong 韵,不读ueng;我昂岸等字有疑母 ng,此声母只限于开⼝呼;主要区别就是上述这些了,其他的都是个别字读⾳的差别,因⽼国⾳⽐较严格地按照古反切审⾳,故⼀些字⾳脱离⽣活,只存活在韵书⾥,就算⽼北京的读书⾳也未必如此。
了解京剧的十三撤京剧的美是全方位的,就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而言,“唱念做打舞”各门功课都具有审美的价值和情趣。
当然第一要素是“唱”,而“唱”的美不仅仅是唱腔,同时唱词一般也很美,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京剧(无论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唱词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唱词不但意境很美,形式也美,一般唱词的上下句很多都是对偶的,要么就是大段的排比句,具有很强的形式美(这是板腔体戏曲的独特魅力);第二,唱词必须“合撤押韵”,即便不是唱,念起来也朗朗上口。
京剧唱词的押韵或者通常人们所说的“顺口”,与古典诗词的韵律有所区别,与现代汉语中的押韵(比如快板书)也不完全相同,因为传统京剧里面的唱与念,发音既不同于普通话,也不同于北京的方言,而是遵循“湖广音,中州韵”的规范,所以另有讲究。
行内把京剧的韵律归纳为十三个韵脚,即通常所说的“十三撤”。
下面就来比较详细来介绍这“十三撤”,供京剧爱好者朋友参考。
十三辙其实是在北方说唱艺术中普遍应用的。
韵母通常按照韵腹相同或相似(如果有韵尾,则韵尾必须相同)的基本原则归纳出来的分类,目的是为了使诵说、演唱顺口、易于记忆,富有音乐美。
十三辙的名目是:发花、梭波、乜斜、一七、姑苏、怀来、灰堆、遥条、由求、言前、人辰、江阳、中东。
特别指出的是,十三辙中每一辙的名目不过是符合这一辙的两个代表字,并没有其他的意义,所以同样也可以用这一辙的其他字来代表该辙,如“梭波辙”也可以叫做“婆娑辙”、“言前辙”也可以称作“天仙辙”,下面就具体介绍“十三辙”的每一辙:1、发花辙:韵母包括a、ua、ia。
举例: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鳎)(目)。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注:带括号的字为合辙的字][注:绕口令]2、梭波辙:韵母包括:e、o、uo。
举例: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那本是奴的前夫名叫蒋兴(哥)。
[注:出自评剧《珍珠衫》,曾被马三立先生在《三字经》中当作学校的校歌]3、乜斜辙:韵母包括ê、ie、ü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