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_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_王明珂
- 格式:pdf
- 大小:365.44 KB
- 文档页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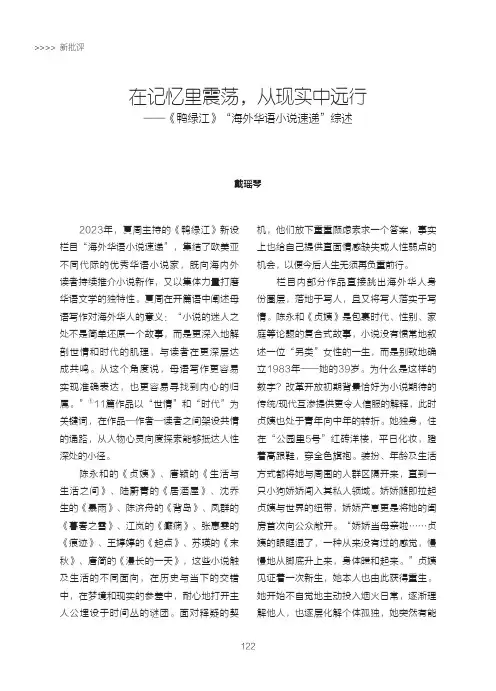
2023年,夏周主持的《鸭绿江》新设栏目“海外华语小说速递”,集结了欧美亚不同代际的优秀华语小说家,既向海内外读者持续推介小说新作,又以集体力量打磨华语文学的独特性。
夏周在开篇语中阐述母语写作对海外华人的意义:“小说的迷人之处不是简单还原一个故事,而是更深入地解剖世情和时代的肌理,与读者在更深层达成共鸣。
从这个角度说,母语写作更容易实现准确表达,也更容易寻找到内心的归属。
”①11篇作品以“世情”和“时代”为关键词,在作品—作者—读者之间架设共情的通路,从人物心灵向度探索能够抵达人性深处的小径。
陈永和的《贞姨》、唐颖的《生活与生活之间》、陆蔚青的《居酒屋》、沈乔生的《暴雨》、陈济舟的《背岛》、凤群的《暮春之雪》、江岚的《癫痫》、张惠雯的《痕迹》、王婷婷的《起点》、苏瑛的《末秋》、唐简的《漫长的一天》,这些小说触及生活的不同面向,在历史与当下的交错中,在梦境和现实的参差中,耐心地打开主人公埋设于时间丛的谜团。
面对释疑的契机,他们放下重重顾虑索求一个答案,事实上也给自己提供直面情感缺失或人性弱点的机会,以便今后人生无须再负重前行。
栏目内部分作品直接跳出海外华人身份圈层,落地于写人,且又将写人落实于写情。
陈永和《贞姨》是包裹时代、性别、家庭等论题的复合式故事,小说没有惯常地叙述一位“另类”女性的一生,而是别致地确立1983年——她的39岁。
为什么是这样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背景恰好为小说期待的传统/现代互渗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此时贞姨也处于青年向中年的转折。
她独身,住在“公园里5号”红砖洋楼,平日化妆,蹬着高跟鞋,穿全色旗袍。
装扮、年龄及生活方式都将她与周围的人群区隔开来,直到一只小狗娇娇闯入其私人领域。
娇娇随即拉起贞姨与世界的纽带,娇娇产崽更是将她的闺房首次向公众敞开。
“娇娇当母亲啦……贞姨的眼眶湿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慢慢地从脚底升上来,身体暖和起来。
”贞姨见证着一次新生,她本人也由此获得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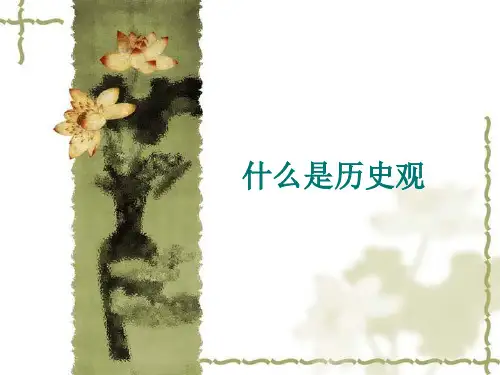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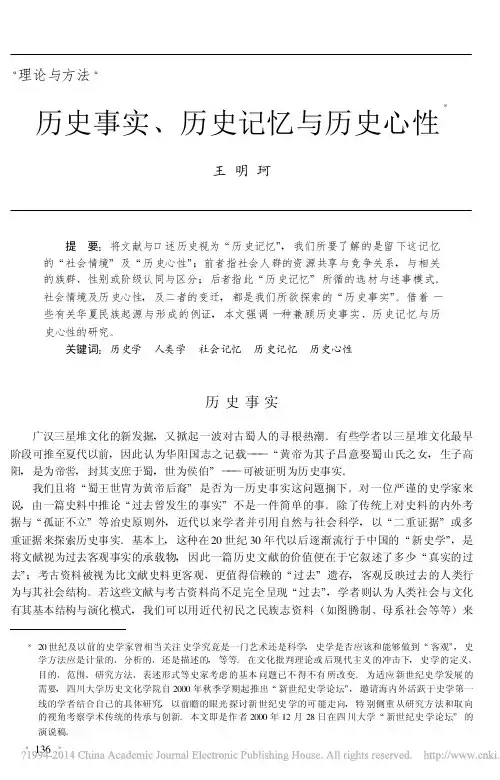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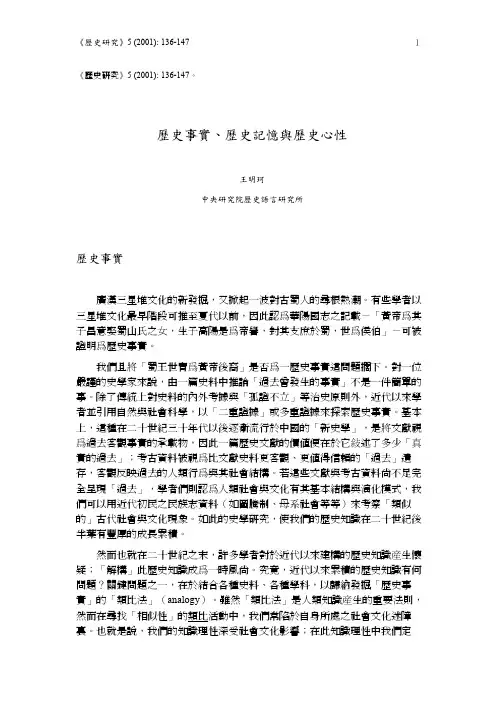
《歷史研究》5 (2001): 136-147。
!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王明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事實廣漢三星堆文化的新發掘,又掀起一波對古蜀人的尋根熱潮。
有些學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階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認爲華陽國志之記載-「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可被證明爲歷史事實。
我們且將「蜀王世冑爲黃帝後裔」是否爲一歷史事實這問題擱下。
對一位嚴謹的史學家來說,由一篇史料中推論「過去曾發生的事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除了傳統上對史料的內外考據與「孤證不立」等治史原則外,近代以來學者並引用自然與社會科學,以「二重證據」或多重證據來探索歷史事實。
基本上,這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逐漸流行於中國的「新史學」,是將文獻視爲過去客觀事實的承載物,因此一篇歷史文獻的價值便在於它敍述了多少「真實的過去」;考古資料被視爲比文獻史料更客觀、更值得信賴的「過去」遺存,客觀反映過去的人類行爲與其社會結構。
若這些文獻與考古資料尚不足完全呈現「過去」,學者們則認爲人類社會與文化有其基本結構與演化模式,我們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資料(如圖騰制、母系社會等等)來考察「類似的」古代社會與文化現象。
如此的史學研究,使我們的歷史知識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有豐厚的成長累積。
然而也就在二十世紀之末,許多學者對於近代以來建構的歷史知識産生懷疑;「解構」此歷史知識成爲一時風尚。
究竟,近代以來累積的歷史知識有何問題?關鍵問題之一,在於結合各種史料、各種學科,以歸納發掘「歷史事實」的「類比法」(analogy)。
雖然「類比法」是人類知識産生的重要法則,然而在尋找「相似性」的類比活動中,我們常陷於自身所處之社會文化迷障裏。
也就是說,我們的知識理性深受社會文化影響;在此知識理性中我們定義、尋找何者是「相似的」、「相關的」與「合理的」,而忽略身邊一些不尋常的、特異的現象。
同樣的,若我們將對歷史的探求當作是一種「回憶過去」的理性活動,此種「回憶」常常難以脫離社會文化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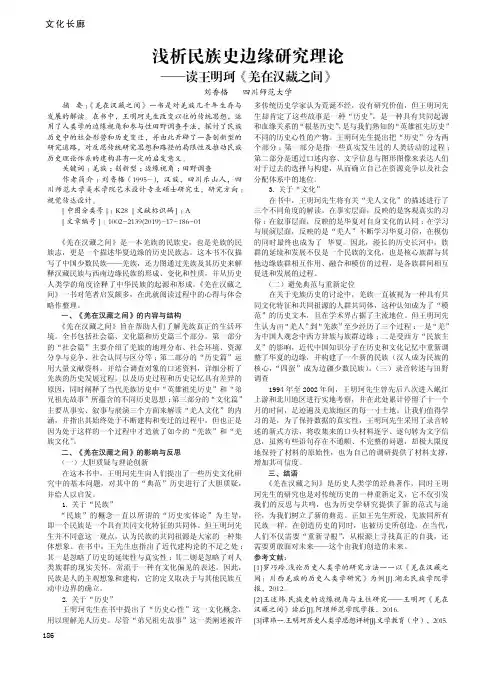
文化长廊浅析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刘香格 四川师范大学摘 要:《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是对羌族几千年生存与发展的解读。
在书中,王明珂先生改变以往的传统思想,运用了人类学的边缘视角和参与性田野调查手法,探讨了民族历史中的社会形势和历史变迁,并由此开辟了一条创新型的研究道路,对反思传统研究思想和路径的局限性及推动民族历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羌族;创新型;边缘视角;田野调查作者简介:刘香格(1995-),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86-01《羌在汉藏之间》是一本羌族的民族史,也是羌族的民族志,更是一个描述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
这本书不仅描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羌族,还力图通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解释汉藏民族与西南边缘民族的形成、变化和性质,并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
《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对笔者启发颇多,在此就阅读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略作整理。
一、《羌在汉藏之间》的内容与结构《羌在汉藏之间》旨在帮助人们了解羌族真正的生活环境。
全书包括社会篇、文化篇和历史篇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社会篇”主要介绍了羌族的地理分布、社会环境、资源分享与竞争、社会认同与区分等;第二部分的“历史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调查对象的口述资料,详细分析了羌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历史过程和历史记忆具有差异的原因,同时阐释了当代羌族历史中“英雄祖先历史”和“弟兄祖先故事”所蕴含的不同历史思想;第三部分的“文化篇”主要从事实、叙事与展演三个方面来解读“羌人文化”的内涵,并指出其始终处于不断建构和变迁的过程中,但也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造就了如今的“羌族”和“羌族文化”。
二、《羌在汉藏之间》的影响与反思(一)大胆质疑与理论创新在这本书中,王明珂先生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对其中的“典范”历史进行了大胆质疑,并给人以启发。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一、《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本书内容与作者简介内容简介: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作者是“化陌生为熟悉”。
在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后,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作者“化熟悉为陌生”,以“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解释自古流传的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之历史,及其对华夏边缘人群造成的影响,藉此作者说明“历史”塑造华夏及当代中国人认同的历史过程。
经由“化陌生为熟悉”与“化熟悉为陌生”所产生的反思性新知,作者期望《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能增进人们对历史与民族的了解。
作者简介: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校教授历史与人类学相关课程。
1994年以来,多次到川西地区进行羌族田野调查。
主要研究范围是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北方游牧社会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
主要著述:《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蛮子、汉人与羌族》、《羌在汉藏之间》、《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二、各章节主要内容以及一些启发性段落句子原序与谢词1.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炎黄子孙”汉系中国人,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弟兄民族”这一称谓的新理解。
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解构”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
相反地,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及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1页)2.反思史学研究,重在历史变迁与相关历史记忆中了解当代情境。
反思性研究强调对外在的、边缘的、陌生的现象和体系,作深入的文本与表征分析以产生认知(化陌生为熟悉),同时,藉此认知,在同一套文本与表征分析逻辑下,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作新的体认与了解(化熟悉为陌生)。
这种新的反思知识能让人们对当代有不偏不倚的了解,有助于认知自身与他者的历史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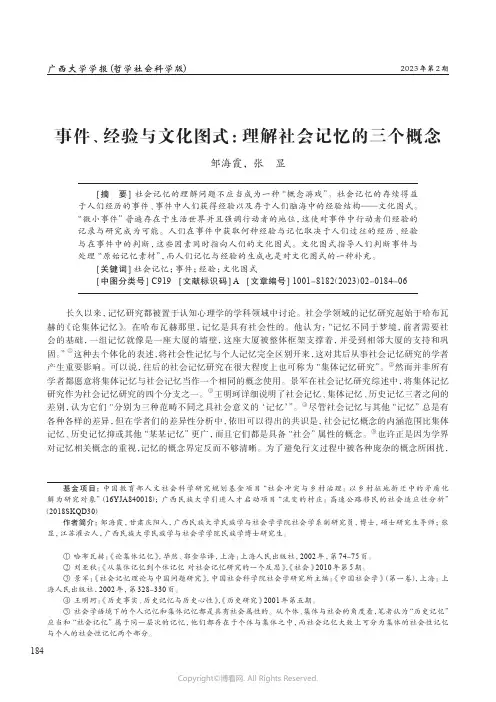
184长久以来,记忆研究都被置于认知心理学的学科领域中讨论。
社会学领域的记忆研究起始于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
在哈布瓦赫那里,记忆是具有社会性的。
他认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
”a 这种去个体化的表述,将社会性记忆与个人记忆完全区别开来,这对其后从事社会记忆研究的学者产生重要影响。
可以说,往后的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称为“集体记忆研究”。
b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愿意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当作一个相同的概念使用。
景军在社会记忆研究综述中,将集体记忆研究作为社会记忆研究的四个分支之一。
c 王明珂详细说明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三者之间的差别,认为它们“分别为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
d 尽管社会记忆与其他“记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在学者们的差异性分析中,依旧可以得出的共识是,社会记忆概念的内涵范围比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抑或其他“某某记忆”更广,而且它们都是具备“社会”属性的概念。
e 也许正是因为学界对记忆相关概念的重视,记忆的概念界定反而不够清晰。
为了避免行文过程中被各种庞杂的概念所困扰,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冲突与乡村治理:以乡村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化“流变的村庄:高速公路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分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
a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
b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c 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8-330页。
d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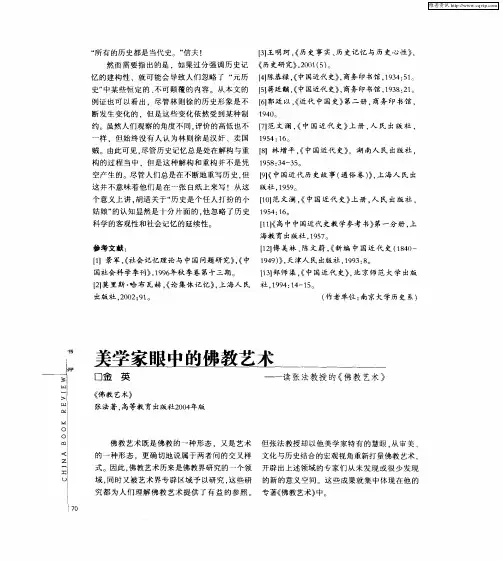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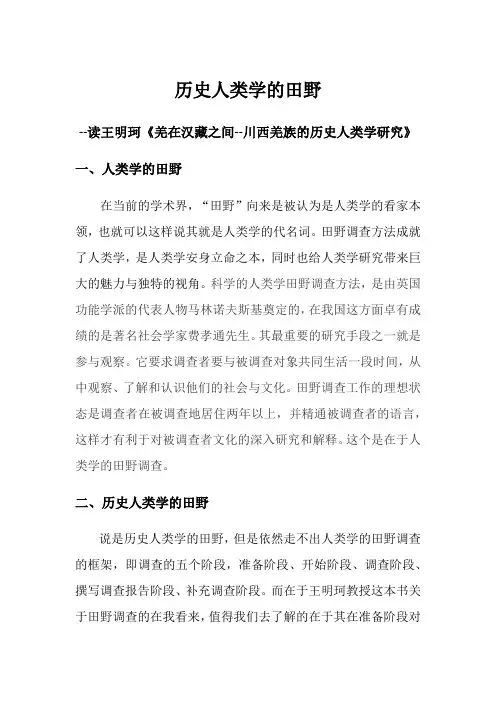
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人类学的田野在当前的学术界,“田野”向来是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也就可以这样说其就是人类学的代名词。
田野调查方法成就了人类学,是人类学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也给人类学研究带来巨大的魅力与独特的视角。
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
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
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
这个是在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二、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说是历史人类学的田野,但是依然走不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框架,即调查的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
而在于王明珂教授这本书关于田野调查的在我看来,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在于其在准备阶段对于资料的认识,也就是其对于历史史实的看法。
王明珂教授在《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这一篇论文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即: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
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实。
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 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
我们能够在这本书的历史篇看到其著名的主观建构历史的研究范式,通过此书似乎可看到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是部分真实的羌族历史与大量的王明珂先生的主观建构及想象的融合。
只是对于王明珂先生关于田野调查的这一部分的看法,我有着和其不一样的认识,既针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表达出一下我的浅见;即历史的书写须重历史史实,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前提。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就连史料的整理与收集,都难以避免个人情感色彩的带入,乾嘉年间的章学诚就曾提出以文济史的治史方法,但是“文学在这里只是辅助者,只有历史才是真正的主体”。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_{期JOURNAl。
OFGUANGXIUNIVERSITYFORNAIIONAIITIES!!!!塞!旦!!些!!£坠!塑!!型墅!些塑!!!!!!■郭宏珍,何星亮/著评王明珂的《华夏边缘》VoL.25、().3MAY2003[中圈分类号](’9124:G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30154【】:目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葺研究昕研究员王H』|珂博士}∈期致力于中【蝴西北、晤南边疆民族史研究.取得r令人瞩日的成就。
其中,《华夏边缘』玎电记忙‘i族群认同》(台湾危晨文化寅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这部々著就娃H中最为突出的成果之~。
浚持是F耍探ij古代羌人和现代羌族的专鲁.也是作軎的成名之作。
本书由六郭仆组成:序论、边缘与内涵、华夏,}态边捍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I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以殷结语“资源环境、忻啦记忆与族群认㈨”.竹若也第一部讣中探讨了近30年来社会人类学界对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并提出“比族史研究边缘理论”。
在第i部舒巾.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华夏”的起源住第二部分中,作者酋先以阿周时期埘人与成人关系的变化.说明华夏边缘的肜成过程。
其次,华夏边缘彤成之n,随着华夏的书1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曲、向南扩张,第四部分探讨r华夏边缘的维持与J鱼迁。
综观全书.该}}有如r儿方l晰的特电:其一,方法独特以f}研究边疆比族历史的学者.人多主要遮川所宦学的A法.理论上也j-要运用人安’学进化学派或历史学派的弹论。
m】该}i圳4:旧,怍蕾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力法.籍坍电’7、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资料.屿JH人类’毕族群理论(ethnici‘ytheory)。
I}{会记匕理论.把传统的历史GXMYxB154学考证、溯源研究}_】曲疗学术界的理论掏架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把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中国边缘的人”.由边缘研究角度探索¨1#夏”及“羌旅”认同的奉质厦其形成过程.从时间、空问和认同的边缘E重构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变迁作?昔精辟地论述r在特定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中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探讨厂与人类族群认I司相关的资游竞争与分配关系.并指出了历史的记忆与失忆在华夏的凝聚和扩张、华夏边缘人群的归属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学是什么?已完成成绩:分【单选题】()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最为重视的。
•、辞章•、考据•、义理•、观点我的答案:得分:分正确答案【单选题】在历史学中,辞章是指(),义理是指()。
•、对原来面貌的追求,表达的形式•、对原来面貌的追求,阐发的理论•、表达的形式,阐发的理论•、对原来面貌的追求,情感色彩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国学”这一概念,从清末民初到现在,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指由于受到认识的限制,我们是无法认识历史的。
()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就遵从原典精神而言,古文经学比今文经学走得更远一点。
()我的答案:×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已完成成绩:分【单选题】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中国传统文献的三个主流是纪传体正史、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私人性文献记载的准确性往往大过官方记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语出克罗齐•、《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的作品我的答案:得分:分【单选题】清代三大史学名著指()。
•、《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读通鉴论》《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史记》的文笔在“二十四”中显得特别,因其叙述带有个人情感。
()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唐律疏议》是唐朝关于职官制度的规定。
()我的答案:×文献分类——历史史料、纪传体、编年体已完成成绩:分【单选题】在进行版本校勘时,选择一个最好版本为主,再辅以其他版本相互校勘,这个最好的版本称为()。
•、选本•、校本•、原本•、底本我的答案:得分:分【单选题】《资治通鉴》的“资”是指()。
•、资质•、资助•、资源•、资格我的答案:得分:分【单选题】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始于()。
•、汉朝•、南北朝•、唐朝•、宋朝我的答案:得分:分【判断题】目前“二十四史”最好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版本。
族群历史与社会记忆的重构*——论王明珂的民族史研究戴昇【摘要】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建立在对传统民族史反思的基础之上,其族群研究以边缘看中心为视角,以社会记忆为研究路径,并强调反思性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族群研究的概念体系,即以“文类—模式化叙事—历史心性—现实情境”来分析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提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民族史新见,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
但其研究中也存在疏于考证、史实不清等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辨别与警惕。
全面评析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王明珂先生的民族史研究贡献,还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族群;社会记忆;民族史;王明珂【作者】戴昇,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近世史研究》执行主编。
上海,200234。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6-0120-008王明珂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边疆民族史名家,他的“华夏边缘”系列研究一经推出,迅速在两岸三地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
其著作至今畅销不歇,以至于洛阳纸贵,不得不一版再版。
内地学者为此有过不少相关学术述评,然而目力所及的这些述评大多是王明珂单本论著的评价,①很少将他的边疆民族史研究进行整体评析。
王明珂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屡次申明:他的多部学术论著之间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
若孤立地评价其单本论著,这既不利于观察他的民族史研究全貌,也有悖于王先生的初衷。
职是之故,笔者不揣冒昧,将王明珂先生的系列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置于中国民族史的学术脉络中去考察评价。
疏漏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一、新视角与新方法的运用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之所以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就在于他的研究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江南基层政权与乡村治理研究”(16YJC770010)。
宗族记忆重构下的祖先认同与关系实践——以河南N 村Z 氏为例台文泽,赵玉蝶摘要:围绕宗族记忆对宗族关系认同作用的讨论主要表现为对其促进作用的肯定。
通过考察河南Z 姓宗族近期举行的一次旨在整合全族关系的祖茔立碑活动,揭示了该活动以祖先为中心的谱系记忆重构之于宗族关系的整合作用是十分表面化、短暂性的,其实际效应与其说是拉近了当下日益疏远的族人关系,还不如说在既有的现实背景下会让族人对彼此关系的距离有了更清晰的感知和认识,而无论是宗族记忆重构在关系整合实践中所显现的血缘距离局限与非血缘因素制约,还是在长远意义上反映出的寻求关系整合的动力不足、文化自觉的欠缺,都高度印证了当代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差序格局理性化。
关键词:乡村社会变迁;宗族记忆重构;祖先崇拜:差序格局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 (2021)02-0136-0820世纪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这一概念通常和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研究范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1]。
关于中国本土的研究,则以台湾学者王明珂为代表,他以川西羌族村寨为场域,透过文献与口述史结合阐释了集体记忆如何引起羌族族群的认同与区分[2]。
在族群领域记忆研究的启示下,作为集体记忆之一种的宗族记忆现象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
就已有讨论而言,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宗族记忆可以加强宗族认同。
典型的研究或从历史记忆重构的角度说明宗族记忆对宗族认同的加强,①或从历史记忆对人的性格塑造角度阐述宗族记忆对宗族认同的促进。
②另一种则指出宗族历史记忆及收稿日期:2020-09-1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YJC850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兰州大学“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编号16LZUJBWZX001)作者简介:台文泽(1984-),男,甘肃成县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兰州,730000);赵玉蝶(1998-),女,河南许昌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解读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摘要:集体记忆理论并不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当中内生出来的研究视角,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族群认同”研究框架下具有的很强的灵活性、交叉性和应用性。
本文通过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概要梳理,站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该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价值所在。
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设想。
关键词:集体记忆族群认同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一般通过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来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历史、民族的重大事件。
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通过“集体认同”一方面强化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重构集体记忆,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与实践。
一.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大都不能排除记忆的因素。
但学界对记忆较为完备的理论与研究集中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领域,直到二十世纪80 年代,才有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从比个人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关注记忆,发展出了相关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开辟了记忆研究新的篇章。
(一)“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
在《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反对心理学研究记忆时只注重个体而忽视社会群体的做法1。
个体层面的记忆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与相应生活年代下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个体的记忆活动。
个体之间存着大量共同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
因此,哈布瓦赫认为应当把“集体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由不同社会群体或组织所建构,每个群体的集体记忆都各有特点2。
哈布瓦赫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他在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深受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研究的影响。
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把集体意识作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同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当社会不在集体欢腾的过度兴奋状态时,用什么来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
社会记忆理论的概念一、关于“社会记忆”概念的探讨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还尚未给出“社会记忆”一个明确的概念,但仍有不少学者对此做出了讨论。
比如,哈拉尔德 韦尔策结合彼得 伯克的研究,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
”根据伯克的观点,社会记忆属于回忆社会史的范畴,有“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等内容。
又如,一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将其定义为“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
台湾学者王明珂的见解也颇有见地。
他认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是由人群当中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
此外,他结合华夏民族的发展史,指出至少应该区分三种范畴不同但却具有社会意义的“记忆”。
第一种即是“社会记忆”,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在一个社会中借由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
第二种的范围较小,他称之为:“集体记忆”。
它指的是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的共同记忆。
第三种则是“历史记忆”,人们借此来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
显然,历史记忆的范畴是最小的。
可以看出,王明珂认为,社会记忆的范围较大,而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则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虽然,他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仍提出,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三个概念之间是存在互补、包含与共融的关系的,很难做到割离与具体的区分。
因而,在相当多的论著中,学者们也并未将之划分的泾渭分明,比如,常常会出现社会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集体历史记忆等概念。
视界观 OBSERVATION SCOPE VIEW111传媒观察作者简介:张玉姣(1996-),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硕士在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文化传播。
融媒体语境下国家记忆的建构和传承——以《国家记忆》为例张玉姣(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摘 要:金观涛曾在其著作中提出,现代国家的构成必须具备三种因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其中民族认同是现代国家的文化基础,是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历史记忆、社会集体记忆来建构完成。
在融媒体语境下,形态多样的媒介形式丰富了历史记忆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形态,同时也为历史记忆建构和民族认同注入新的时代内涵[1]。
关键词:历史记忆;民族认同;融媒体近年来,央视做了大量原创历史和文化节目,如《国家宝藏》、《国家相册》、《如果国宝会说话》、《红色气质》等,其中《国家记忆》作为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引起了巨大的点击量和话题讨论量。
《国家记忆》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
本文以《国家记忆》为研究对象,阐述在融媒体语境下,历史纪录片如何建构历史记忆来增加民族认同感以及历史记忆该如何传承的问题。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至少应存在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为“社会记忆”,第二种为“集体记忆”,第三种为“历史记忆”[2]。
笔者认同此观点,历史记忆是一种回忆性的“集体活动”,用来强化民族凝聚感、国家认同感和彼此的情感联系,找到一种民族归属感。
一、结构上真实还原重大历史事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实的事件,实际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虚构的事件,不是叙述者发明的事件。
这意味着,历史事件向一个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
[3]历史是真实的事件,因此作为纪录片的《国家记忆》站在国家和全党的高度上,根据真实的历史档案资料、生动展现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各行各业的发展史。
人类学之解析《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王明珂教授认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在于它记叙的“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呈现的“过去”比文献史料更能反映“历史事实”.而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更能发掘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
因此,挖掘“历史记忆”是前提。
历史记忆不等同于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是“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集体记忆是“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历史记忆范围更小:在社会“集体记忆”中,以“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的记忆。
历史记忆流传于文献与口述中。
文献呈递的记忆,犹如汪洋大海的中的一叶扁舟.后人只能从零星的只言片语中窥见浩瀚历史的冰山一角。
时间的流逝,磨平了记忆的棱角;刻意的保存与失忆,早已使社会记忆丢失了真实的面容.诚然如此,这些史料依旧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重要线索。
口述历史是补充文献记载的必要手段。
人类学研究的正是那些没有文字的人类和历史。
或许口述没有文字记录严谨,但是,我认为口述记录了更多的信息与事实。
不是每个世家都有族谱,更多的人是依靠口述传递了祖祖辈辈的记忆,知道家族的根源.“真正的历史是荷塘中所有青蛙的和鸣”,全体家庭的记忆汇合成历史记忆。
与文献类似,口述的“过去”也未必记录着“历史事实”,但是,这些故事反映了时代的背景,是那个族群认同的记忆。
“兄弟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只需知道,兄弟的血缘象征着那群既合作又竞争的人群.“兄弟故事”就是在在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
在我认为,历史心性是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
拥有历史心性,可以从兵马俑中看见秦朝的强势,从唐诗中联想女性的浪漫,从清明上河图中窥见宋朝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