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散文
- 格式:ppt
- 大小:1.65 MB
- 文档页数: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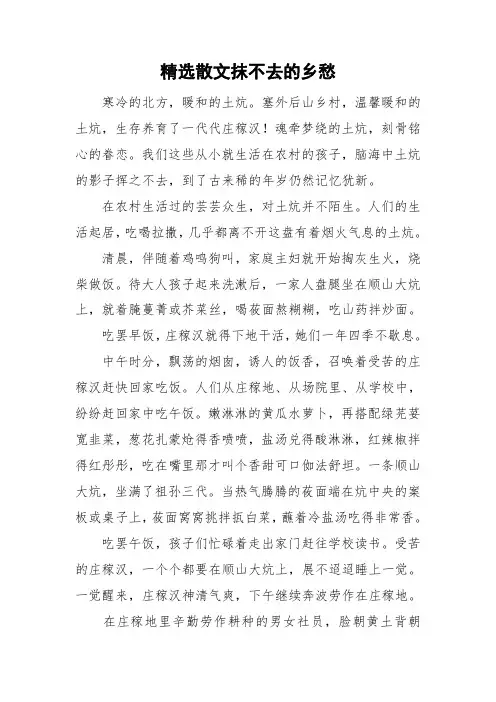
精选散文抹不去的乡愁寒冷的北方,暖和的土炕。
塞外后山乡村,温馨暖和的土炕,生存养育了一代代庄稼汉!魂牵梦绕的土炕,刻骨铭心的眷恋。
我们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孩子,脑海中土炕的影子挥之不去,到了古来稀的年岁仍然记忆犹新。
在农村生活过的芸芸众生,对土炕并不陌生。
人们的生活起居,吃喝拉撒,几乎都离不开这盘有着烟火气息的土炕。
清晨,伴随着鸡鸣狗叫,家庭主妇就开始掏灰生火,烧柴做饭。
待大人孩子起来洗漱后,一家人盘腿坐在顺山大炕上,就着腌蔓菁或芥菜丝,喝莜面熬糊糊,吃山药拌炒面。
吃罢早饭,庄稼汉就得下地干活,她们一年四季不歇息。
中午时分,飘荡的烟囱,诱人的饭香,召唤着受苦的庄稼汉赶快回家吃饭。
人们从庄稼地、从场院里、从学校中,纷纷赶回家中吃午饭。
嫩淋淋的黄瓜水萝卜,再搭配绿芫荽宽韭菜,葱花扎蒙炝得香喷喷,盐汤兑得酸淋淋,红辣椒拌得红彤彤,吃在嘴里那才叫个香甜可口侞法舒坦。
一条顺山大炕,坐满了祖孙三代。
当热气腾腾的莜面端在炕中央的案板或桌子上,莜面窝窝挑拌㧚白菜,蘸着冷盐汤吃得非常香。
吃罢午饭,孩子们忙碌着走出家门赶往学校读书。
受苦的庄稼汉,一个个都要在顺山大炕上,展不迢迢睡上一觉。
一觉醒来,庄稼汉神清气爽,下午继续奔波劳作在庄稼地。
在庄稼地里辛勤劳作耕种的男女社员,脸朝黄土背朝天,脚踏大地肩抗辇。
双手的老茧磨成疤,汗珠子掉下摔八瓣。
爬田拾地勤耕耘,起早贪黑忙种田。
庄户人何日才得闲?傍晚时分,庄稼汉随着落日的晚霞,迈着沉重的脚步,身心疲惫地朝家中走去。
一缕缕青烟,蒸腾着希望。
羊群归了圈,孩子放了学,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回到了家。
女主人端上热气腾腾的面条,还有开花白馒头。
一家人围坐在顺山大炕,呲溜呲溜的吃面条,就着咸菜啃馒头......夜幕降临,圈住绵羊放开狗,撵鸡进窝锁好门。
老头子吧嗒着玛瑙嘴子抽旱烟,老伴子煤油灯下缝补乱衣裳。
媳妇哄着娃娃打瞌睡,学生爬在炕上做作业。
一条大炕写人生,芦席铺炕过光景。
土炕养育了孩童,土炕成就了姻缘,土炕哺育了后代,庄稼汉过着朝起暮落,勤劳俭朴的农家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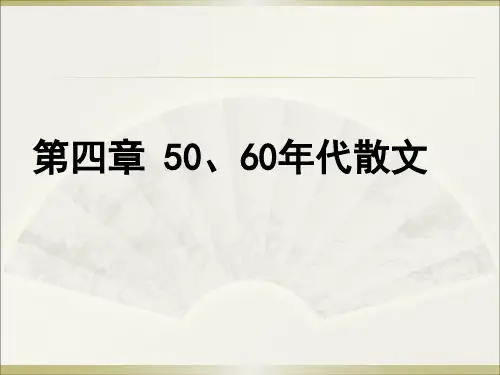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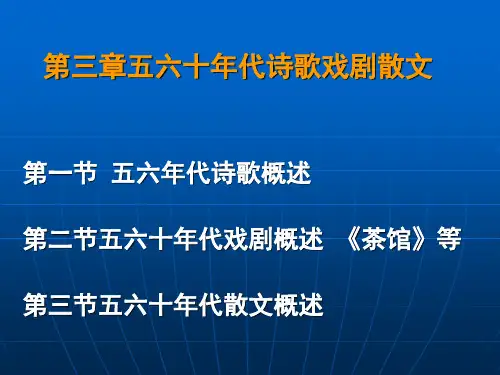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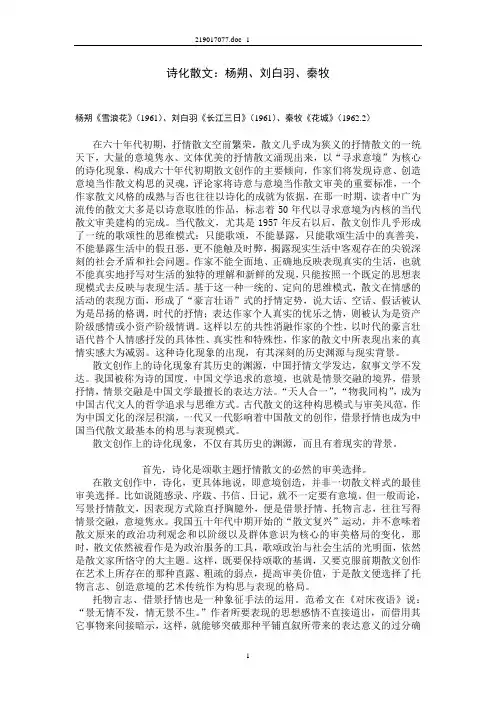
诗化散文:杨朔、刘白羽、秦牧杨朔《雪浪花》(1961)、刘白羽《长江三日》(1961)、秦牧《花城》(1962.2)在六十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空前繁荣,散文几乎成为狭义的抒情散文的一统天下,大量的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以“寻求意境”为核心的诗化现象,构成六十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作家们将发现诗意、创造意境当作散文构思的灵魂,评论家将诗意与意境当作散文审美的重要标准,一个作家散文风格的成熟与否也往往以诗化的成就为依据,在那一时期,读者中广为流传的散文大多是以诗意取胜的作品,标志着50年代以寻求意境为内核的当代散文审美建构的完成。
当代散文,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散文创作几乎形成了一统的歌颂性的思维模式: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不能暴露生活中的假丑恶,更不能触及时弊,揭露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作家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表现真实的生活,也就不能真实地抒写对生活的独特的理解和新鲜的发现,只能按照一个既定的思想表现模式去反映与表现生活。
基于这一种一统的、定向的思维模式,散文在情感的活动的表现方面,形成了“豪言壮语”式的抒情定势,说大话、空话、假话被认为是昂扬的格调,时代的抒情;表达作家个人真实的忧乐之情,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感情或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样以左的共性消融作家的个性,以时代的豪言壮语代替个人情感抒发的具体性、真实性和特殊性,作家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大为减弱。
这种诗化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
散文创作上的诗化现象有其历史的渊源,中国抒情文学发达,叙事文学不发达。
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学追求的意境,也就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是中国文学最擅长的表达方法。
“天人合一”,“物我同构”,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追求与思维方式。
古代散文的这种构思模式与审美风范,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演,一代又一代影响着中国散文的创作,借景抒情也成为中国当代散文最基本的构思与表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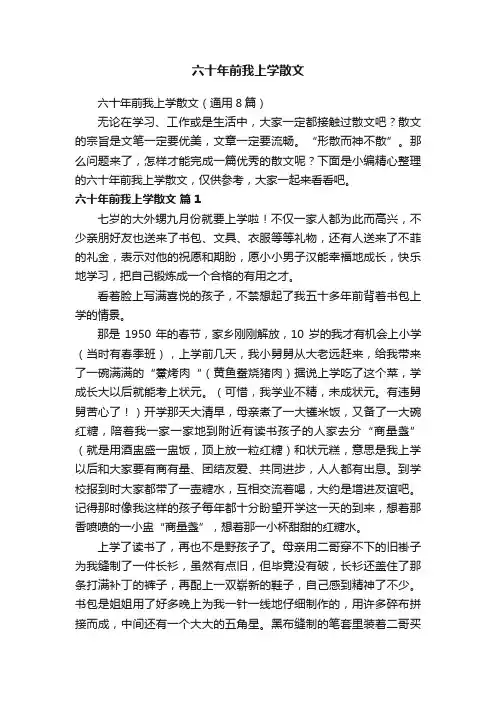
六十年前我上学散文六十年前我上学散文(通用8篇)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的宗旨是文笔一定要优美,文章一定要流畅。
“形散而神不散”。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能完成一篇优秀的散文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六十年前我上学散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十年前我上学散文篇1七岁的大外甥九月份就要上学啦!不仅一家人都为此而高兴,不少亲朋好友也送来了书包、文具、衣服等等礼物,还有人送来了不菲的礼金,表示对他的祝愿和期盼,愿小小男子汉能幸福地成长,快乐地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合格的有用之才。
看着脸上写满喜悦的孩子,不禁想起了我五十多年前背着书包上学的情景。
那是1950年的春节,家乡刚刚解放,10岁的我才有机会上小学(当时有春季班),上学前几天,我小舅舅从大老远赶来,给我带来了一碗满满的“鮝烤肉“(黄鱼鲞烧猪肉)据说上学吃了这个菜,学成长大以后就能考上状元。
(可惜,我学业不精,未成状元。
有违舅舅苦心了!)开学那天大清早,母亲煮了一大镬米饭,又备了一大碗红糖,陪着我一家一家地到附近有读书孩子的人家去分“商量盏”(就是用酒盅盛一盅饭,顶上放一粒红糖)和状元糕,意思是我上学以后和大家要有商有量、团结友爱、共同进步,人人都有出息。
到学校报到时大家都带了一壶糖水,互相交流着喝,大约是增进友谊吧。
记得那时像我这样的孩子每年都十分盼望开学这一天的到来,想着那香喷喷的一小盅“商量盏”,想着那一小杯甜甜的红糖水。
上学了读书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
母亲用二哥穿不下的旧褂子为我缝制了一件长衫,虽然有点旧,但毕竟没有破,长衫还盖住了那条打满补丁的裤子,再配上一双崭新的鞋子,自己感到精神了不少。
书包是姐姐用了好多晚上为我一针一线地仔细制作的,用许多碎布拼接而成,中间还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
黑布缝制的笔套里装着二哥买给我的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支毛笔;书包里还有墨和砚台、石板、石笔以及布做的揩刷等等。
母亲陪着我先去拜见了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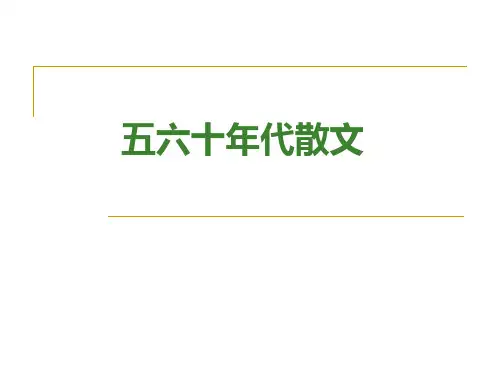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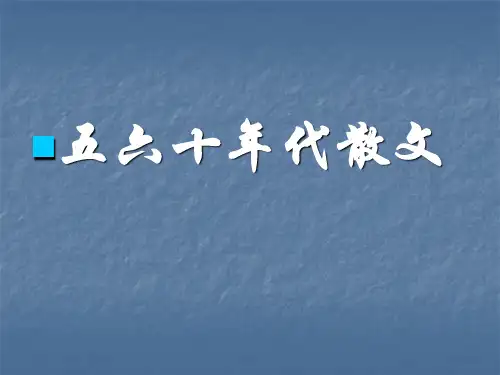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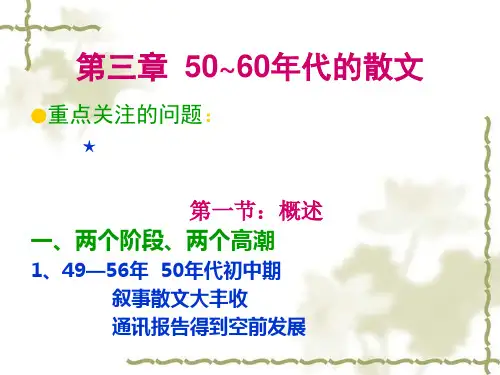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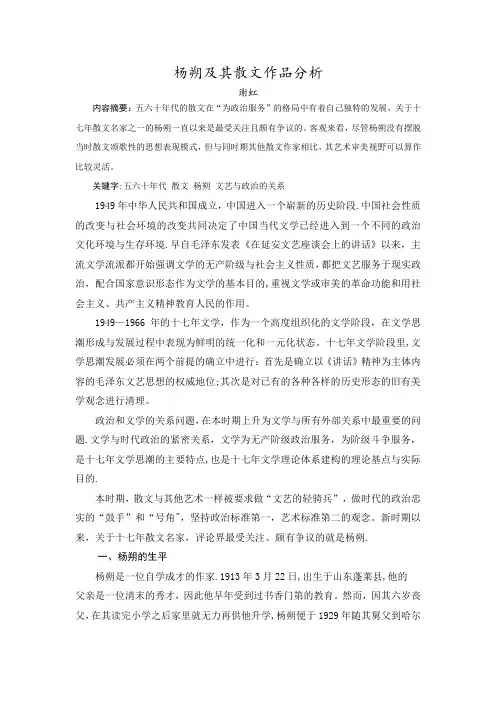
杨朔及其散文作品分析谢虹内容摘要: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在“为政治服务”的格局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关于十七年散文名家之一的杨朔一直以来是最受关注且颇有争议的。
客观来看,尽管杨朔没有摆脱当时散文颂歌性的思想表现模式,但与同时期其他散文作家相比,其艺术审美视野可以算作比较灵活。
关键字:五六十年代散文杨朔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共同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与生存环境.早自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主流文学流派都开始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都把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配合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基本目的,重视文学或审美的革命功能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
1949—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阶段,在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
十七年文学阶段里,文学思潮发展必须在两个前提的确立中进行:首先是确立以《讲话》精神为主体内容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地位;其次是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形态的旧有美学观念进行清理。
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时期上升为文学与所有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与实际目的.本时期,散文与其他艺术一样被要求做“文艺的轻骑兵”,做时代的政治忠实的“鼓手”和“号角",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
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散文名家,评论界最受关注、颇有争议的就是杨朔.一、杨朔的生平杨朔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1913年3月22日,出生于山东蓬莱县,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末的秀才,因此他早年受到过书香门第的教育。
然而,因其六岁丧父,在其读完小学之后家里就无力再供他升学,杨朔便于1929年随其舅父到哈尔滨的一家洋行工作以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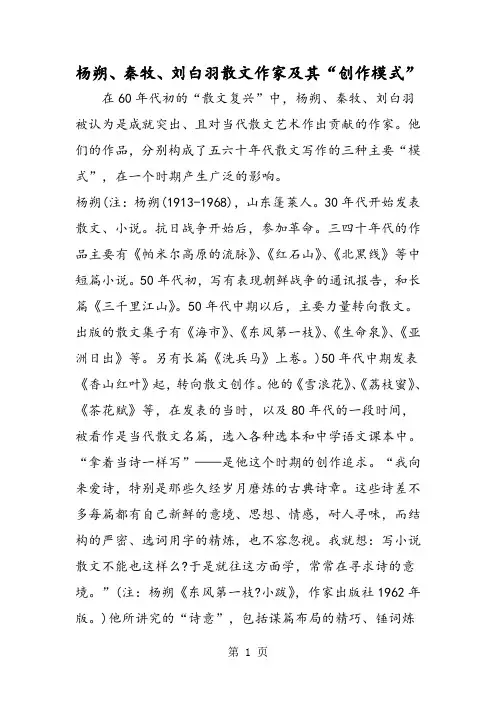
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作家及其“创作模式”在60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且对当代散文艺术作出贡献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在一个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
杨朔(注:杨朔(1913-1968),山东篷莱人。
3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
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革命。
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有《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红石山》、《北黑线》等中短篇小说。
50年代初,写有表现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和长篇《三千里江山》。
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力量转向散文。
出版的散文集子有《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亚洲日出》等。
另有长篇《洗兵马》上卷。
)50年代中期发表《香山红叶》起,转向散文创作。
他的《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中。
“拿着当诗一样写”——是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追求。
“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
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
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词炼字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
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注:杨溯《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
如见到盛开的茶花而联想祖国欣欣向荣面貌,以香山红叶寓示历经风霜、到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将劳作的蜜蜂比喻只问贡献、不求报酬的劳动者等等。
在杨朔写作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
杨朔的散文,在贯彻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给这种已显得相当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至那么直接、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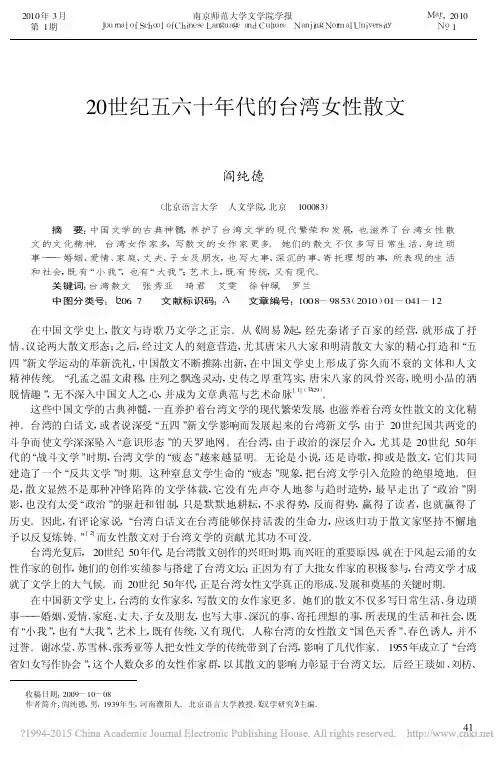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09-10-08作者简介:阎纯德,男,1939年生,河南濮阳人。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主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散文阎纯德(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摘 要:中国文学的古典神髓,养护了台湾文学的现代繁荣和发展,也滋养了台湾女性散文的文化精神。
台湾女作家多,写散文的女作家更多。
她们的散文不仅多写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婚姻、爱情、家庭、丈夫、子女及朋友,也写大事、深沉的事、寄托理想的事,所表现的生活和社会,既有“小我”,也有“大我”;艺术上,既有传统,又有现代。
关键词:台湾散文 张秀亚 琦君 艾雯 徐钟珮 罗兰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0)01-041-12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与诗歌乃文学之正宗。
从《周易》起,经先秦诸子百家的经营,就形成了抒情、议论两大散文形态;之后,经过文人的刻意营造,尤其唐宋八大家和明清散文大家的精心打造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新洗礼,中国散文不断推陈出新,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弥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
“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无不深入中国文人之心,并成为文章典范与艺术命脉[1](P 429)。
这些中国文学的古典神髓,一直养护着台湾文学的现代繁荣发展,也滋养着台湾女性散文的文化精神。
台湾的白话文,或者说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台湾新文学,由于20世纪国共两党的斗争而使文学深深坠入“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
在台湾,由于政治的深层介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战斗文学”时期,台湾文学的“疲态”越来越显明。
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抑或是散文,它们共同建造了一个“反共文学”时期。
这种窒息文学生命的“疲态”现象,把台湾文学引入危险的绝望境地。
但是,散文显然不是那种冲锋陷阵的文学体裁,它没有先声夺人地参与趋时造势,最早走出了“政治”阴影,也没有太受“政治”的驱赶和钳制,只是默默地耕耘,不求得势,反而得势,赢得了读者,也就赢得了历史。
出生在五十年代的我回忆农村生活艰辛散文我出生在五十年代,那会儿日子可比现在苦多了。
在农村,生活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天都得跟老天爷斗智斗勇,就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
天刚蒙蒙亮,公鸡还没打第二遍鸣,咱就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起来。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闹钟,连块手表都是奢侈品。
叫醒我的,是娘的轻声呼唤,还有肚子里的咕咕叫。
一睁眼,就能看到窗外那片黑黢黢的田野,仿佛在告诉我,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咱家离村头的大田不远,几步路的事儿。
一到地里,露水打湿了裤脚,冰凉冰凉的。
但咱顾不上这些,爹娘已经开始挥舞着锄头,一下一下地刨着土。
咱也跟着学,虽然力气不大,但咱知道,多刨一锄头,就能多种一粒粮食。
那时候的人,劲儿都使在庄稼上,心都操在家里。
到了中午,太阳晒得人直冒汗,田里的虫子也嗡嗡地叫。
娘会从家里带几个红薯来,咱们就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啃。
红薯皮儿都不舍得扔,得留着喂猪。
那时候没有零食,红薯就是咱最好的“下午茶”。
娘说,红薯是好东西,吃了耐饿,还能长力气。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咱们得忙着收工回家。
田里的活儿干不完,但家里的事儿也得操心。
娘得忙着做饭,爹得修修补补,我呢,就得去喂猪、捡柴火。
家里养的几头猪,可是咱家的宝贝疙瘩,到了年底,卖了猪才能换点年货。
所以,咱对这几头猪可是上心得很,天天都得去瞅瞅它们吃得好不好,长得壮不壮。
晚上,家里点的是煤油灯,那光线暗暗的,但咱觉得挺温馨。
爹娘会坐在桌子旁,算计着家里的开销,盘算着明年的收成。
咱就趴在桌子上写作业,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困了,娘就会拍拍咱的背,说:“孩子,再坚持一会儿,把书念好了,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的咱,虽然不懂啥叫“好日子”,但知道爹娘说的都是对的。
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有乐趣。
到了夏天,咱就去河里游泳、摸鱼;到了秋天,咱就去山上摘野果、捡板栗。
那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娇气,啥都得自己干,但也因此锻炼得皮实、独立。
冬天就更难熬了,北风呼呼地刮,吹得人脸生疼。
第六章50、60年代的散文第一节散文创作概况(一)此期散文的范畴与整体趋向:1、范畴: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散文”的认识,基本上是承继着“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所确立的“大散文”观念,即将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回忆录、游记、小品、随笔、传记文学、杂文、散文诗等,统统归纳于散文这一体裁。
2、其整体趋向是:个性意识的淡化,群体意识的强化,散文从自我内心的观照转向‘身外大事’的观照;审美观念的削弱,功利观念的强调,‘工具’论取代了‘自娱’论;主观抒情成分减弱,客观记叙成分增强,抒情小品体制让位给通讯特写体制;以文化‘现代化’为核心的‘西方热’消退,民族化、大众化运动勃兴,散文由多元的横向借鉴转向单一的纵向继承。
”(二)发展概况:1、5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1)、从5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前后,是纪实性的散文兴盛的时期。
这期间纪实性散文的主要形式是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也有一部分人物传记和个人自传性质的作品。
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成绩集中在两个重要的题材领域:其一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
主要有专业作家的作品集,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和华山、靳以、菡子等人的作品集,以及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合集《朝鲜通讯报告选》(一、二、三辑)、《志愿军一日》和《志愿军英雄传》等。
魏巍的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期间纪实性散文的一篇出类拔萃的优秀作品。
其二是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这些主要以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的纪实性散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行各业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及新人新事的萌芽与成长,展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这个领域的纪实性散文创作同样既有专业作家也有业余作者,其中特别是一些著名小说家例如柳青、秦兆阳、沙汀等的人物特写和吴运铎、高玉宝等的文学自传,格外引人注目。
记忆里的老街散文范本一份记忆里的老街散文 1我可以承受岁月的离去,留在童年里的一条街却使我牵肠挂肚,在我心里亦真亦幻。
这条街的历史太漫长了,往她的前头走一百年还是这样,或许再往前走一千年也还是这个样子,以后来,我说不准,也许也走不出我的童年的梦,这条街就如永生在童年里一样,就像我喜欢向日葵在金黄色中燃烧一般,正如凡?高所说的,那是爱的最强光。
这条街就在我的家乡陇南山区的西汉水上游,崖城河双手紧紧地抱着她。
据史料记载,这条街在元朝就已经是大居民点了,忽必烈的后裔在这里长期屯过重兵,抗击吐蕃,抚民靖边。
我的灵魂总在这条街上转悠,中间好像没有休止符,即使在天下动荡的时代,吃尽了草根的时期,也没走出八十年代我读过的一位美国黑人作家写的那本叫《根》的书。
家乡的一条街啊,横亘在我的童年里,古朴简陋的两排瓦房站在我的瞳仁里,就像我的没了门牙的爷爷,脸上坑坑洼洼的如枯树上的老树皮,一站就是我的整个一生的岁月,连镇子中间那两棵粗大的中国古槐都站成了满身沧桑。
家乡的街并不是笔直的,就像一张弓佩带在镇子的背上,至今没能走进摇滚的弧线里,从古到今把它的走势定格成了秦腔戏里的帝王将相的御带,漫游在田野上悠长的犁沟里。
乡情啊,就是光知道埋头过日子不知打扮自己的鬓发的农妇。
下雨天里,泥土的街面忍受着日蚀雨*的雕刻,姑娘的白球鞋找不到地方亲吻街道的脸,于是,姑娘和媳妇们的好心情像飞溅的泥花盛开在摊贩的新货上。
家乡的街呀,是陇南山区一条普通的河,从遥远的云海里流来,冲刷着河床上岸边无数颗砾砂的脑袋,就像铁木真的后裔把草原上马头琴的故事屯在崖城河岸边的垂柳里,被崖城的岁月唱成了沧桑老人。
活在我童年深处的这条街啊,一直是这样,不是笔直而是两端略翘曲起,真像压弯了的重担,是沉重的家乡压弯了?还是担负着苍苍岁月?对于我来说,这条街就像家乡山涧的山路,承载着我的童年,少年,中年,还要托付我的老年,是我一辈子走不出的梦。
我儿时偎依在席地的曾祖母的怀抱里,倾听饥饿的红军把玉米秆上的棒子换成银圆的故事,我抱住她的三寸金莲幻想着在军号声里齐刷刷的集合的脚步声是如何唤醒街道两旁民房里的庶民,八个铁骨铮铮的泥腿子站在街上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古老的街面支撑着__缔造者的脚板奔向黎明。
六十年代老门楼底下热闸非凡散文散文一直是几大文体中概念可容纳范围最大,边界最广的一个,广义上的散文几乎能包括任何的文章写作,而相比于三四十年代,散文所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广义上的散文,其包括报告文学,包括杂文,还包括一些回忆录和史传文学,总之,散文可以不是抒情性的,也可以是议论性的和叙事性的。
但是狭义上的散文就是抒情性散文,其相近与五四时代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美文。
另外再补充一点,到了80年代,散文的概念被窄化了,美文、艺术散文等概念被重新提起,似乎只有一类抒情散文(以及一些人文知识性的散文)才能配得上是散文,这也是延续我们至今的散文概念。
而这一波浪潮之后,则是我们当下的潮流,散文概念逐渐被扩展,调查报告式的写作传入重塑了我们的新闻创作,文艺作品的评论杂谈也蔚为大观,历史普及科学普及类文章的发展也产生了不错的成果,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认为散文研究应当重新扩展自己的概念,将这些写作也纳入文学的范围内。
让我们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吧。
五六十年代散文有一个主流类型,那就是报告文学。
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散文特写”通常并举连用,作为一个同义的概念。
五十年代初这一类纪实报告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当时大规模的建设景象和朝鲜战争是其取材的源头。
其中魏巍的创作作为出色,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本合集,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境的提炼,兼顾了抒情的议论,是这部作品能够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其写作也提高了通讯报道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而对纪实性叙事性报告文学的提倡和发展,必然会挤压抒情性散文的地位,不过也一直存在着散文复兴的要求。
五十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施行的时候,对文学写作的限制有所减弱,因而在56-57年,出现了短暂的复兴现象。
而下一次的复兴现象发生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为期四年的调整时期,文学界其时也有调整,一般认为是61到62年,其中心是调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和风格上倡导有限制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