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散文读书笔记
- 格式:docx
- 大小:23.36 KB
- 文档页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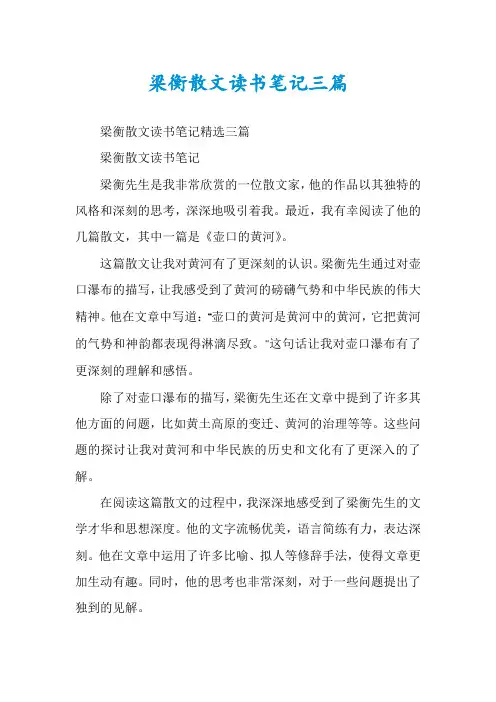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三篇梁衡散文读书笔记精选三篇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梁衡先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考,深深地吸引着我。
最近,我有幸阅读了他的几篇散文,其中一篇是《壶口的黄河》。
这篇散文让我对黄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梁衡先生通过对壶口瀑布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了黄河的磅礴气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他在文章中写道:“壶口的黄河是黄河中的黄河,它把黄河的气势和神韵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句话让我对壶口瀑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除了对壶口瀑布的描写,梁衡先生还在文章中提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黄土高原的变迁、黄河的治理等等。
这些问题的探讨让我对黄河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阅读这篇散文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梁衡先生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
他的文字流畅优美,语言简练有力,表达深刻。
他在文章中运用了许多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得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同时,他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对于一些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总的来说,梁衡先生的散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作品不仅让我对黄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他的作品将会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梁衡,原名梁富国,字晋华,1946年出生,山西霍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
那么,读完他的散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是我对梁衡散文的读书笔记。
首先,梁衡的散文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他的散文常常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生活中的点滴,表现出他对于自然、人生、历史的深深热爱和真挚情感。
比如在《壶口瀑布》中,他描述了瀑布的壮丽景色,不仅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赞美,也流露出他对于生命的敬畏和感慨。
其次,梁衡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他的散文不仅具有抒情性,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他常常通过对于历史、文化、社会的思考,表达出他对于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比如在《大无大有:忆范家而论》中,他通过回忆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表达出对于家庭、亲情、友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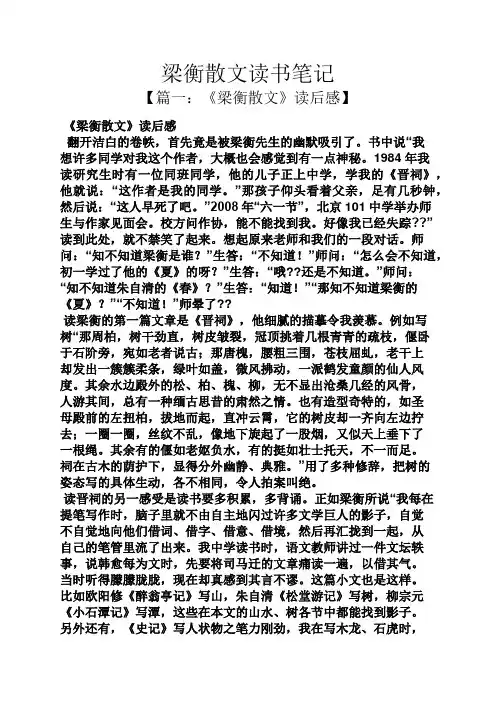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篇一:《梁衡散文》读后感】《梁衡散文》读后感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
书中说“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
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
”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吧。
”2008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
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
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就不禁笑了起来。
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
师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是不知道。
”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生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晕了??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
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
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
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
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
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
”用了多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
正如梁衡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
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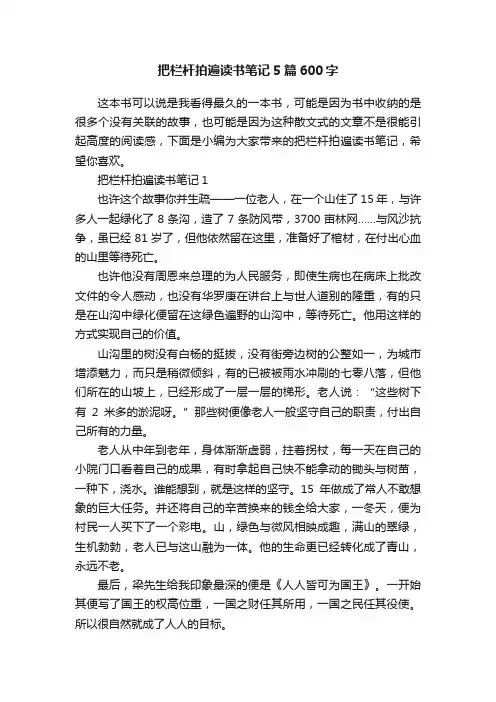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5篇600字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看得最久的一本书,可能是因为书中收纳的是很多个没有关联的故事,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散文式的文章不是很能引起高度的阅读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1也许这个故事你并生疏——一位老人,在一个山住了15年,与许多人一起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带,3700亩林网……与风沙抗争,虽已经81岁了,但他依然留在这里,准备好了棺材,在付出心血的山里等待死亡。
也许他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为人民服务,即使生病也在病床上批改文件的令人感动,也没有华罗庚在讲台上与世人道别的隆重,有的只是在山沟中绿化便留在这绿色遍野的山沟中,等待死亡。
他用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山沟里的树没有白杨的挺拔,没有街旁边树的公整如一,为城市增添魅力,而只是稍微倾斜,有的已被被雨水冲刷的七零八落,但他们所在的山坡上,已经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梯形。
老人说:“这些树下有2米多的淤泥呀。
”那些树便像老人一般坚守自己的职责,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老人从中年到老年,身体渐渐虚弱,拄着拐杖,每一天在自己的小院门口看着自己的成果,有时拿起自己快不能拿动的锄头与树苗,一种下,浇水。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坚守。
15年做成了常人不敢想象的巨大任务。
并还将自己的辛苦换来的钱全给大家,一冬天,便为村民一人买下了一个彩电。
山,绿色与微风相映成趣,满山的翠绿,生机勃勃,老人已与这山融为一体。
他的生命更已经转化成了青山,永远不老。
最后,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人人皆可为国王》。
一开始其便写了国王的权高位重,一国之财任其所用,一国之民任其役使。
所以很自然就成了人人的目标。
但接着梁先生就说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的时候长短并不是绝对的,王亦有局限。
王也有其所不能得到的。
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想成为王,有的人只喜欢游山玩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不被权势而折腰。
但其实如今的社会是多元的,国王也是多元的,每个人在其行业中在其领域内都可成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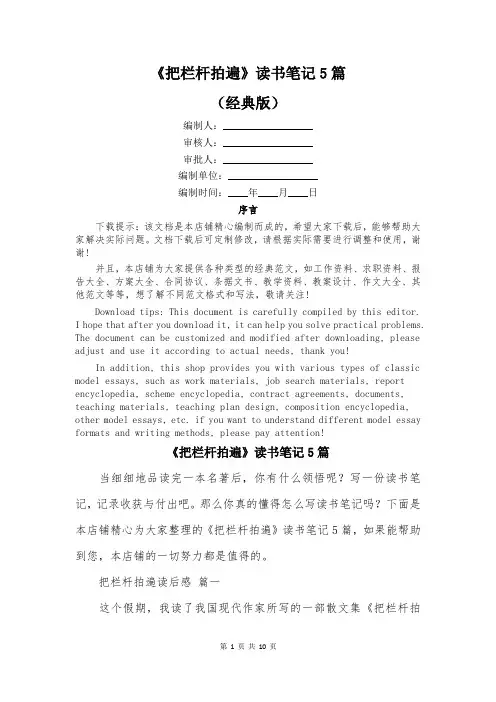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5篇(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工作资料、求职资料、报告大全、方案大全、合同协议、条据文书、教学资料、教案设计、作文大全、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classic model essays, such as work materials, job search materials, report encyclopedia, scheme encyclopedia, contract agreements, documents,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plan design, composition encyclopedia, other model essays, etc.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model essay formats and writing methods, please pay attention!《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5篇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写一份读书笔记,记录收获与付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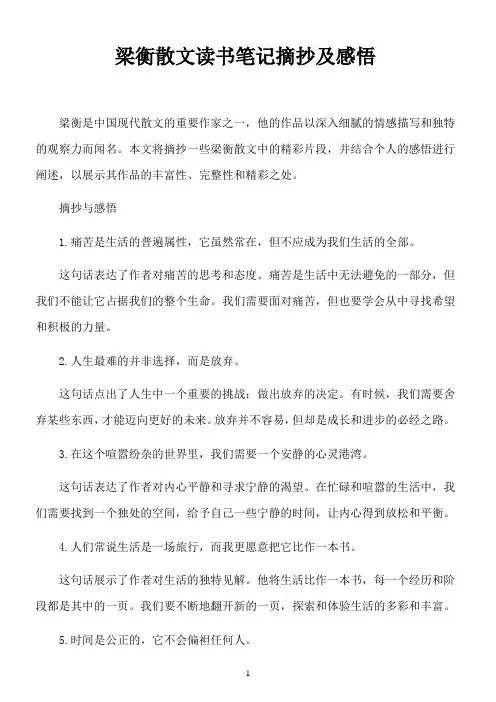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梁衡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深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独特的观察力而闻名。
本文将摘抄一些梁衡散文中的精彩片段,并结合个人的感悟进行阐述,以展示其作品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精彩之处。
摘抄与感悟1.痛苦是生活的普遍属性,它虽然常在,但不应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痛苦的思考和态度。
痛苦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让它占据我们的整个生命。
我们需要面对痛苦,但也要学会从中寻找希望和积极的力量。
2.人生最难的并非选择,而是放弃。
这句话点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做出放弃的决定。
有时候,我们需要舍弃某些东西,才能迈向更好的未来。
放弃并不容易,但却是成长和进步的必经之路。
3.在这个喧嚣纷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心灵港湾。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内心平静和寻求宁静的渴望。
在忙碌和喧嚣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给予自己一些宁静的时间,让内心得到放松和平衡。
4.人们常说生活是一场旅行,而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本书。
这句话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见解。
他将生活比作一本书,每一个经历和阶段都是其中的一页。
我们要不断地翻开新的一页,探索和体验生活的多彩和丰富。
5.时间是公正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
这句话提醒我们时间的无情和公正。
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有,年轻还是老去,时间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应该珍惜时间,充分利用它,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感悟通过阅读梁衡的散文作品,我深受其思想和情感的触动。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类内心的复杂情感,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和美好。
以下是我对梁衡散文的一些感悟:1.真实与勇敢:梁衡的作品展示了对真实生活的勇敢面对。
他不回避痛苦和困境,而是通过文笔表达出对生活的深切思考和认知。
这启发着我要勇敢地面对现实,珍惜每一个生命中的瞬间。
2.内心的宁静:在喧嚣纷杂的世界中,梁衡强调了内心的宁静和平静的重要性。
我意识到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去反思和放松,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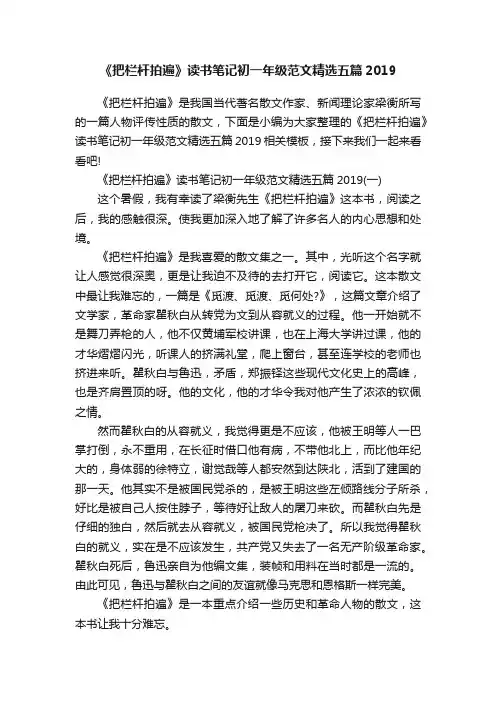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初一年级范文精选五篇2019《把栏杆拍遍》是我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梁衡所写的一篇人物评传性质的散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初一年级范文精选五篇2019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初一年级范文精选五篇2019(一)这个暑假,我有幸读了梁衡先生《把栏杆拍遍》这本书,阅读之后,我的感触很深。
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许多名人的内心思想和处境。
《把栏杆拍遍》是我喜爱的散文集之一。
其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感觉很深奥,更是让我迫不及待的去打开它,阅读它。
这本散文中最让我难忘的,一篇是《觅渡、觅渡、觅何处?》,这篇文章介绍了文学家,革命家瞿秋白从转党为文到从容就义的过程。
他一开始就不是舞刀弄枪的人,他不仅黄埔军校讲课,也在上海大学讲过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人的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
瞿秋白与鲁迅,矛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置顶的呀。
他的文化,他的才华令我对他产生了浓浓的钦佩之情。
然而瞿秋白的从容就义,我觉得更是不应该,他被王明等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在长征时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的,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人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的那一天。
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被王明这些左倾路线分子所杀,好比是被自己人按住脖子,等待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
而瞿秋白先是仔细的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被国民党枪决了。
所以我觉得瞿秋白的就义,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共产党又失去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瞿秋白死后,鲁迅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一流的。
由此可见,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完美。
《把栏杆拍遍》是一本重点介绍一些历史和革命人物的散文,这本书让我十分难忘。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初一年级范文精选五篇2019(二)辛弃疾,一个武者,一个著名的爱国诗人。
年少时杀反贼,摛叛将,一腔报国热血,却不料,性直烈,久置闲,只得泪洒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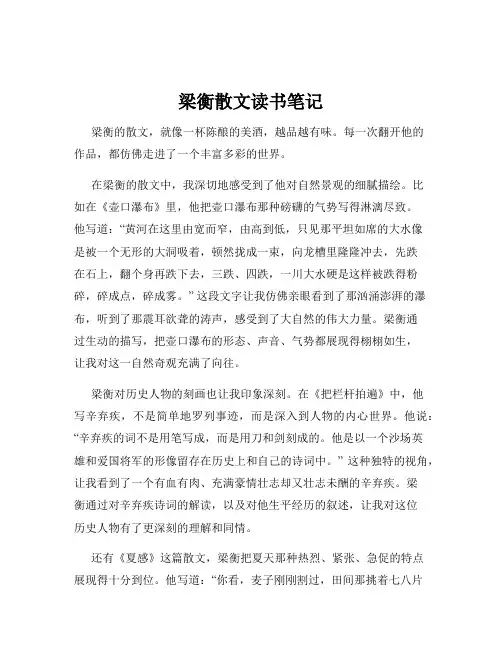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梁衡的散文,就像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品越有味。
每一次翻开他的作品,都仿佛走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梁衡的散文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
比如在《壶口瀑布》里,他把壶口瀑布那种磅礴的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他写道:“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
” 这段文字让我仿佛亲眼看到了那汹涌澎湃的瀑布,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涛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梁衡通过生动的描写,把壶口瀑布的形态、声音、气势都展现得栩栩如生,让我对这一自然奇观充满了向往。
梁衡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也让我印象深刻。
在《把栏杆拍遍》中,他写辛弃疾,不是简单地罗列事迹,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他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
” 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豪情壮志却又壮志未酬的辛弃疾。
梁衡通过对辛弃疾诗词的解读,以及对他生平经历的叙述,让我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还有《夏感》这篇散文,梁衡把夏天那种热烈、紧张、急促的特点展现得十分到位。
他写道:“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度过的夏天,烈日下田地里忙碌的人们,树上不知疲倦鸣叫的蝉儿,还有夜晚池塘边此起彼伏的蛙声。
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梁衡的散文语言简洁明快,但又富有韵味。
他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让文章增色不少。
比如在《青山不老》中,“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
他是真正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了。
” 这里的“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用夸张的手法高度赞扬了老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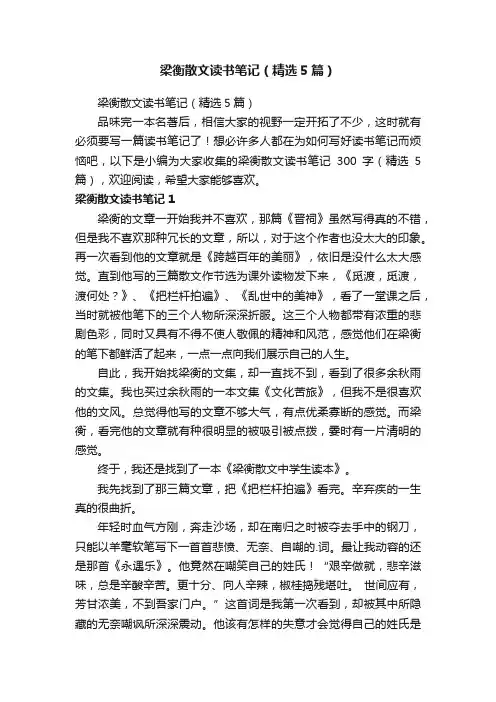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精选5篇)梁衡散文读书笔记(精选5篇)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书笔记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书笔记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梁衡散文读书笔记300字(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1梁衡的文章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篇《晋祠》虽然写得真的不错,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冗长的文章,所以,对于这个作者也没太大的印象。
再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就是《跨越百年的美丽》,依旧是没什么太大感觉。
直到他写的三篇散文作节选为课外读物发下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乱世中的美神》,看了一堂课之后,当时就被他笔下的三个人物所深深折服。
这三个人物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同时又具有不得不使人敬佩的精神和风范,感觉他们在梁衡的笔下都鲜活了起来,一点一点向我们展示自己的人生。
自此,我开始找梁衡的文集,却一直找不到,看到了很多余秋雨的文集。
我也买过余秋雨的一本文集《文化苦旅》,但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文风。
总觉得他写的文章不够大气,有点优柔寡断的感觉。
而梁衡,看完他的文章就有种很明显的被吸引被点拨,霎时有一片清明的感觉。
终于,我还是找到了一本《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
我先找到了那三篇文章,把《把栏杆拍遍》看完。
辛弃疾的一生真的很曲折。
年轻时血气方刚,奔走沙场,却在南归之时被夺去手中的钢刀,只能以羊毫软笔写下一首首悲愤、无奈、自嘲的.词。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那首《永遇乐》。
他竟然在嘲笑自己的姓氏!“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这首词是我第一次看到,却被其中所隐藏的无奈嘲讽所深深震动。
他该有怎样的失意才会觉得自己的姓氏是“艰辛”“酸辛”“悲辛”“辛辣”,觉得自己就是不能够拥有美好的事物!还有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总理诞辰百年之时所写。
那些冗长的历史在梁衡的笔下一点不显繁复,反而,每一件都令周总理无私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明,深深被这个自己无缘亲眼见到的总理所感动。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最近读了梁衡的散文,真的是让我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梁衡的文字,就像是一位老友在你耳边娓娓道来,不紧不慢,却又能一下子抓住你的心。
他写人,能把人物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写景,能让你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他叙事,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思考。
就拿他写的《把栏杆拍遍》来说吧。
这篇文章写的是辛弃疾,可跟我以前读过的那些写辛弃疾的文章完全不一样。
梁衡没有一上来就罗列辛弃疾的诗词成就,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入手。
他写辛弃疾南归之后的落寞,那种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的苦闷,被梁衡描写得淋漓尽致。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身材魁梧、目光坚定的辛弃疾,一次次地登上高楼,拍打着栏杆,心中的愤懑无处发泄。
梁衡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这句话真的太妙了!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辛弃疾词中的那种豪迈与悲壮。
还有《夏感》这一篇,他写夏天的热烈,那真叫一个细致入微。
他说:“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芊芊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
”瞧瞧,这比喻多形象啊!我读着读着,眼前就浮现出了夏天里草木蓬勃生长的画面。
他还写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
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
”这样的描写,让我对夏天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仅仅觉得夏天是炎热的,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梁衡的散文里,还有很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特见解。
比如他写《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在他的笔下,诸葛亮不再是那个被神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自己的无奈和坚持的普通人。
他通过对武侯祠的描写,对诸葛亮一生的回顾,让我对这位历史名人有了更深的思考。
读梁衡的散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特别善于观察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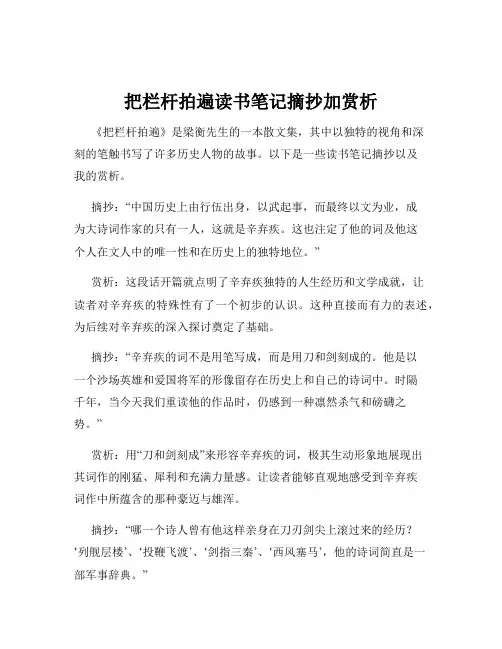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加赏析《把栏杆拍遍》是梁衡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其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笔触书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
以下是一些读书笔记摘抄以及我的赏析。
摘抄:“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
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赏析:这段话开篇就点明了辛弃疾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让读者对辛弃疾的特殊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这种直接而有力的表述,为后续对辛弃疾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摘抄:“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
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赏析:用“刀和剑刻成”来形容辛弃疾的词,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其词作的刚猛、犀利和充满力量感。
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辛弃疾词作中所蕴含的那种豪迈与雄浑。
摘抄:“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
”赏析:这一连串的词语,如“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辛弃疾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也突显了他在军事方面的丰富阅历和深刻体验,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词作与他的战场经历紧密相连。
摘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赏析:通过描写辛弃疾南渡后的境遇转变,从手握刀剑到只剩笔杆,从战场厮杀到纸上抒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他的无奈和痛苦,以及壮志未酬的悲愤。
摘抄:“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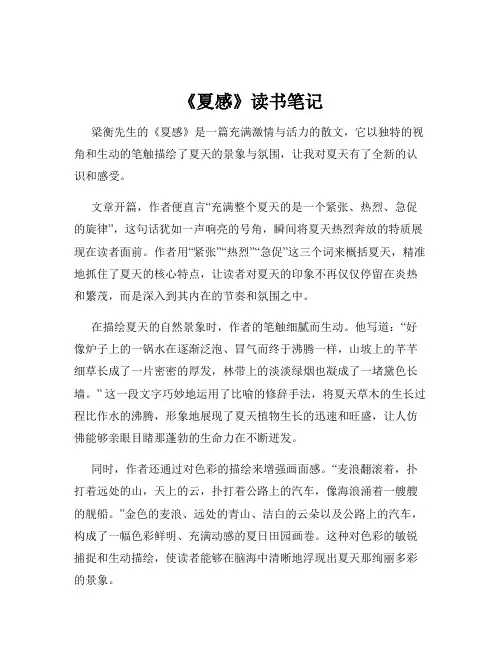
《夏感》读书笔记梁衡先生的《夏感》是一篇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散文,它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夏天的景象与氛围,让我对夏天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感受。
文章开篇,作者便直言“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这句话犹如一声响亮的号角,瞬间将夏天热烈奔放的特质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用“紧张”“热烈”“急促”这三个词来概括夏天,精准地抓住了夏天的核心特点,让读者对夏天的印象不再仅仅停留在炎热和繁茂,而是深入到其内在的节奏和氛围之中。
在描绘夏天的自然景象时,作者的笔触细腻而生动。
他写道:“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芊芊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
” 这一段文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夏天草木的生长过程比作水的沸腾,形象地展现了夏天植物生长的迅速和旺盛,让人仿佛能够亲眼目睹那蓬勃的生命力在不断迸发。
同时,作者还通过对色彩的描绘来增强画面感。
“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的舰船。
”金色的麦浪、远处的青山、洁白的云朵以及公路上的汽车,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充满动感的夏日田园画卷。
这种对色彩的敏锐捕捉和生动描绘,使读者能够在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夏天那绚丽多彩的景象。
夏天不仅是自然的舞台,更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景。
作者写道:“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
”在这里,作者将夏天置于春与秋之间,赋予了它独特的意义。
夏天是收获的前奏,是希望的延续,人们在这个季节里辛勤劳作,为了未来的丰收而付出汗水。
文中对农民劳作场景的描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你看,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通过对各种农作物的细致刻画,展现了农民们的辛勤耕耘和对土地的深情眷恋。
他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生活的希望,这种勤劳和坚韧的精神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
把栏杆拍遍每章读书笔记最近读了梁衡先生的《把栏杆拍遍》,感触颇深。
这本书中的每一章都仿佛是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探那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先来说说第一章吧,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穿越回了那个久远的时代。
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历史课本中冰冷的名字和干巴巴的事迹,而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鲜活形象。
比如写到辛弃疾,他那壮志未酬的悲愤,那种欲报国而不得的无奈,仿佛都能透过文字传递到我的心里。
我仿佛看到辛弃疾在战场上奋勇杀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回到朝堂,却备受猜忌和排挤,一腔热血无处挥洒。
他一次次地拍打着栏杆,那栏杆都快被他拍断了,可又能如何呢?这种悲愤和无奈,真的让人揪心。
第二章里,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更加细腻了。
作者就像是一位高超的画师,用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画面。
其中有一位人物,原本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可经过作者的描绘,他的形象一下子清晰起来。
我能看到他的喜怒哀乐,能感受到他的挣扎和坚持。
这一章里的故事,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那些人物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情感,他们也会迷茫,也会痛苦。
第三章,那简直是一场文字的盛宴。
作者用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人物,让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比如说,以前我只知道某位人物的功绩,却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艰辛。
但在这一章里,作者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一点点地展现出来,让我明白了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
就像一个人要攀登山峰,途中会遇到荆棘、会迷路、会疲惫,但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就能够一步步地向上攀登。
第四章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作者描写一位古人在困境中的抉择,那种纠结和痛苦仿佛就发生在我眼前。
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煎熬,一边是道义,一边是利益,他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定。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个细节让我思考了很久,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到底该如何选择,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内心呢?第五章里,作者通过一些小事展现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
《夏》梁衡读书笔记小学生范文精选五篇500字梁衡先生笔端的《夏》是他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多年驻节在黄河流域所亲密接触的夏。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夏》梁衡读书笔记小学生范文精选五篇500字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夏》梁衡读书笔记小学生范文精选五篇500字(一)半夜以后,阳台那雨蓬的叮咚声告诉我,这天,酣畅淋漓地下了场透雨。
这似乎告诉我,夏,在向人们告別了。
人们用太多的赞美献给了春的温暖,秋的清凉;春的嫩绿,秋的金黄;春的生机,秋的收获。
唯独,对夏的炎热、夏的火红、夏的沸腾是如此的吝啬。
以致连散文大家梁衡也感叹:“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
若要提起夏,则多称之为苦夏-----汗水是苦涩的,炎热是要苦熬的。
其实,夏天是值得赞美的!我十分赞同梁衡:这夏的气氛是沸腾的;旋律是紧张的;气势是磅礴的!夏日,在工人的挥之如雨的汗水中,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桥飞架天堑,一条条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向远方......也在夏日,农民兄弟的汗水滋润着那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
地里的庄稼“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这时她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慢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
没有谁为夏天唱赞歌?---不要紧,那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那铺天盖地的暴风骤雨,便是自然界献给夏天的最壮美的颂歌。
夏天的色彩,梁老先生认为是金黄的。
------夏的颜色应当是中性的黄色。
我却以为:夏,并不中性。
它应当是,而且就是红色的!-----夏日烘烤的火热,人们劳动热情的火热,-----一切的一切,红得好象燃烧的火。
这燃烧着的火,炼出了钢锭,催熟了庄稼!-----没有夏的火红,哪有秋的金黄!夏天要暂离我们而去了,但我知道,过了秋的金黄,冬的雪白,春的嫩绿,我们又会迎来夏的火红!《夏》梁衡读书笔记小学生范文精选五篇500字(二)前一段时间我们学了《夏感》一课,主要写了作者抓住夏天热烈、急促、收获已有而希望未尽的特点,描绘了夏天金黄色大地上万物蓬勃生长的景象,表达作者对夏天之情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深情赞颂。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最近读了梁衡的散文,那感觉就像是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偶遇了一位智慧而风趣的老友,听他娓娓道来那些或深刻、或动人的故事。
梁衡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将平凡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比如在他的《夏感》中,对夏天的描写简直绝了!他说“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把夏天的热烈那种逐渐升温的过程形容得恰到好处。
读着他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夏日景象,阳光炽热地烤着大地,树叶都被晒得蔫蔫的,蝉在枝头拼命地叫着。
还有他写的《把栏杆拍遍》,讲述了辛弃疾充满波折的一生。
梁衡没有单纯地罗列辛弃疾的生平事迹,而是通过对他的诗词的解读,以及对其人生经历中关键节点的细腻刻画,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壮志未酬的辛弃疾。
他形容辛弃疾“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
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这样的描述太有画面感了,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目光坚毅、背负着家国重任的英雄形象。
梁衡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诠释也让我深受启发。
在《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他没有把诸葛亮神化,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诸葛亮的智慧、忠诚以及他所面临的困境。
他写道:“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让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读梁衡的散文,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旅行。
他带着我穿越历史的长河,领略那些伟大人物的风采;又领着我走进大自然,感受四季的更替和生命的律动。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正读着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窗外突然下起了小雨。
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原本有些烦躁的心,在梁衡的文字中渐渐平静下来。
他笔下的瞿秋白,那坚定的信仰和悲壮的命运,让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我放下书,走到窗前,看着雨中的世界。
街道上的人们匆匆忙忙地走着,有的打着伞,有的则在雨中奔跑。
梁衡散文集读后感我最近读完了梁衡的两部散文集《觅渡》与《洗尘》,不禁为其中睿智而深刻的语言所折服。
散文集中很大一部分由历史散文构成。
其中《把栏杆拍遍》与《乱世中的美神》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
《把栏杆拍遍》化用了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诗句,散文中评论了他由武到文的一生。
辛弃疾年轻时曾起义抗金,南下归宋后,本想为国出力,却终生不受重用。
尽管报国无门,他仍然心系天下,那颗藏于乡间的爱国之心仍跳动不止。
《乱世中的美神》则是以李清照为主题,她的前半生幸福完美,但突如其来的丧夫、亡国之痛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尽管往昔安逸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李清照却未对生活失去希望,这几乎致命的打击反而让她登上了古典诗词的巅峰。
散文集的另一大组成部分便是游记散文了。
这些散文不仅有着鲜明生动的语言,它们所表达的主旨更是超乎“游”之外。
如《乌梁素海,带伤的美丽》中,就以乌海当年湖中跃起的鱼儿如“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的生动景象与如今船尾翻起的浪“黄中带黑,像一条刚翻起的犁沟”形成对比,突出了作者对此感到的痛惜与无奈,呼吁人们保护那正在逝去的自然之美。
而《一颗怀抱炸弹的老樟树》中,描绘了那棵接住炸弹的老樟树旺盛的生命力:“简直就是火山喷出地面后突然凝固的一座石山”,或许这段描写不仅是为了表现树的顽强生命力,更是象征着革命力量的永不消逝。
在散文集中,由物及理的文章也不少。
比如《人与石头的厮磨》,从描写不同的人在石上刻下各种内容,探究到了古人的心理:统治者想借石巩固统治,为官者想借石留下美名,百姓想借石铭记恩情……这两部散文集,不仅体现了梁衡高超的文化功底,更显出了他深刻睿智的哲思。
梁衡散文集读后感(二)国庆期间,我阅读了梁衡先生的散文集《把栏杆拍遍》,这本书将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只来得及将第一单元中的内容细细品读。
这本书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作者是通过___个历史名人来谈政治,谈人生,论哲学;第二个单元,是在讲一个作曲家,一个歌唱家,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在生活的艰辛中创造奇迹的老人家的事迹;第三个单元,则是在写关于艺术的内容。
梁衡《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梁衡《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梁衡《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这是一篇写得很美的散文,有以下特点:一、联想丰富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
本文作者就是这样。
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惹来诽谤,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
再如,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种忧思的词作。
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
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
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
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
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
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
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
梁衡散文《青山不老》读后感(精选4篇)梁衡《青山不老》篇1今天,我读了一篇叫《青山不老》的短文,使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青山是不会老的.这篇短文主要讲了:山沟所处的环境很差,是干旱.霜冻.沙尘等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的盘踞之地.但是,却有一位老人创造了这块绿洲,使作者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青山是不会老的.为什么说青山是不会老的?是因为老人创造出了这块绿洲,给了它们新的生命,它们永远是这样永远是充满生机勃勃,永远都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所以说它是不会老的.读了这篇短文,我感受非常深.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老人一样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生存的家园,那么,我们的生活不知该有多美好.早上起床,新的一天开始了,睁开的第一眼就望到了充满生机的绿,那将是多么美好!想到这里,不仅文中的老人有这样高尚的品质,我的表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环境意识力很强,她从来不伤害树木.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外面散步,这时,看见了一棵小树被人家连根拔起,也不知是谁干的坏事.妹妹对我说:“姐姐,你看,它在流泪.“ 哪有啊,别多管闲事,快走吧!”我说.“不行,姐姐,我们应该保护树木,做一个好孩子.”我被妹妹的话吓了一跳,想:一个比我小的妹妹也能这样想,我怎么就…….!想到这里,我和妹妹一起把小树扶起来,我跑回家取水.经过我们的一番抢救,小树终于又直起了腰.我和妹妹高兴极了!同学们,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保护大自然,爱护我们生存的家园!梁衡散文《青山不老》读后感篇2今天,我读了一篇叫《青山不老》的短文,使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青山是不会老的。
这篇短文主要讲了:山沟所处的环境很差,是干旱。
霜冻。
沙尘等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的盘踞之地。
但是,却有一位老人创造了这块绿洲,使作者领悟到了一个道理:青山是不会老的。
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
我们的植树英雄:马永顺。
国家需要木材,马永顺伐树36500棵。
他为了补回这些树,每年春季都植树。
1982年马永顺还有8000棵树没栽上。
梁衡散文读书笔记【篇一:《梁衡散文》读后感】《梁衡散文》读后感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
书中说“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
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
”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吧。
”2008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
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
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就不禁笑了起来。
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
师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是不知道。
”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生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晕了??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
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
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
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
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
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
”用了多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
正如梁衡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
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
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
这篇小文也是这样。
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
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
”只有“厚积”才能“薄发”。
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
作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
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江之娜。
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
”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其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
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的散文,精美,朴实,独特,而富有韵味。
【篇二:梁衡散文读后感梁衡谈阅读】《梁衡散文》读后感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
书中说“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
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
”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吧。
”2008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
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
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就不禁笑了起来。
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
师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是不知道。
”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 生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晕了??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
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
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
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
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
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
”用了多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
正如梁衡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
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
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
这篇小文也是这样。
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
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
”只有“厚积”才能“薄发”。
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
作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
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江之鲫。
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
”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其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
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我的阅读经历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由两大背景决定的,一是他的生活;二是他的阅读。
经常有人问我,你读过些什么书,能不能向年轻人推荐一些。
我就面有窘色,一时答不上来。
一般作家谈阅读时都能很潇洒地说出那些大部头,读过多少外国名著。
我却不能,就算读过几本,也早已忘掉了。
我不是小说作家,是写文章的,正业曾是新闻写作、公文写作,业余是散文写作。
这些都强烈地针对现实,不容虚构情节、回避问题,否则写出的文章就没有人看。
所以,从作家角度来说我的阅读是一种另类阅读,是“撒大网、采花蜜”式的阅读。
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人人经历过的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只不过可能我更认真些并且与写作联系起来。
这种方式对学生、记者、公务员和业余写作爱好者可能更合适一些,我就都曾有过这些身份。
下面是我阅读和写作的简要经历。
一、关于诗歌的阅读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
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
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
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
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
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唅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几分钱一张。
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
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
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
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
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
总之是在蒙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幼儿学钢琴,学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