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
- 格式:doc
- 大小:37.0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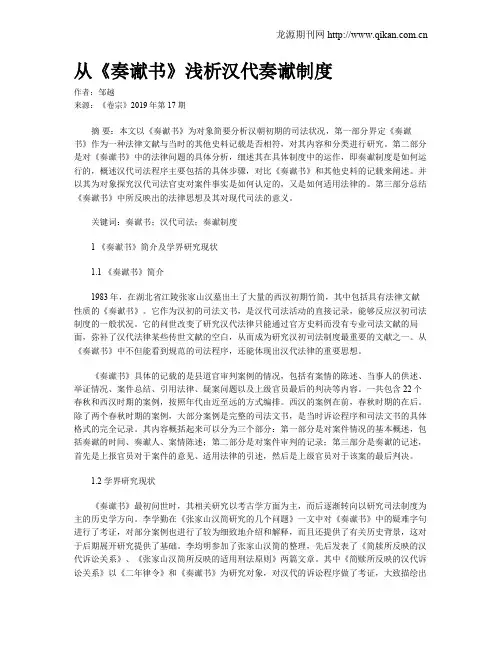
从《奏谳书》浅析汉代奏谳制度作者:邹越来源:《卷宗》2019年第17期摘要:本文以《奏谳书》为对象简要分析汉朝初期的司法状况,第一部分界定《奏谳书》作为一种法律文献与当时的其他史料记载是否相符,对其内容和分类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是对《奏谳书》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分析,细述其在具体制度中的运作,即奏谳制度是如何运行的,概述汉代司法程序主要包括的具体步骤,对比《奏谳书》和其他史料的记载来阐述。
并以其为对象探究汉代司法官吏对案件事实是如何认定的,又是如何适用法律的。
第三部分总结《奏谳书》中所反映出的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司法的意义。
关键词:奏谳书;汉代司法;奏谳制度1 《奏谳书》简介及学界研究现状1.1 《奏谳书》简介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西汉初期竹简,其中包括具有法律文献性质的《奏谳书》。
它作为汉初的司法文书,是汉代司法活动的直接记录,能够反应汉初司法制度的一般状况。
它的问世改变了研究汉代法律只能通过官方史料而没有专业司法文献的局面,弥补了汉代法律某些传世文献的空白,从而成为研究汉初司法制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从《奏谳书》中不但能看到规范的司法程序,还能体现出汉代法律的重要思想。
《奏谳书》具体的记载的是县道官审判案例的情况,包括有案情的陈述、当事人的供述、举证情况、案件总结、引用法律、疑案问题以及上级官员最后的判决等内容。
一共包含22个春秋和西汉时期的案例,按照年代由近至远的方式编排。
西汉的案例在前,春秋时期的在后。
除了两个春秋时期的案例,大部分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书,是当时诉讼程序和司法文书的具体格式的完全记录。
其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案件情况的基本概述,包括奏谳的时间、奏谳人、案情陈述;第二部分是对案件审判的记录;第三部分是奏谳的记述,首先是上报官员对于案件的意见、适用法律的引述,然后是上级官员对于该案的最后判决。
1.2 学界研究现状《奏谳书》最初问世时,其相关研究以考古学方面为主,而后逐渐转向以研究司法制度为主的历史学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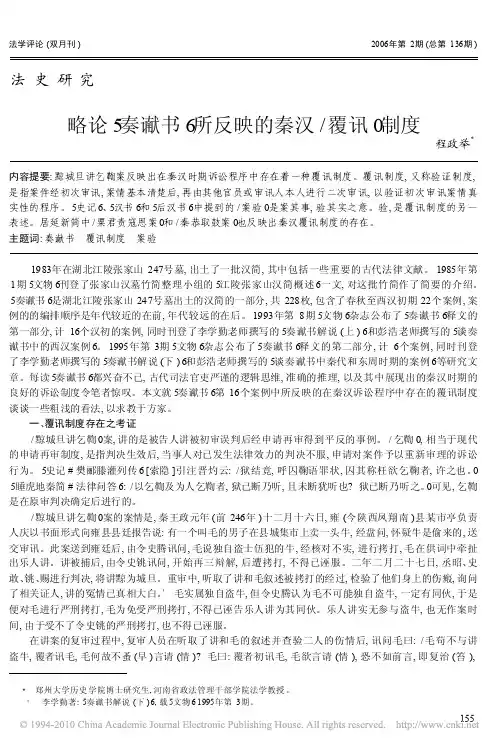
法学评论(双月刊)2006年第2期(总第136期)法史研究略论5奏谳书6所反映的秦汉/覆讯0制度程政举*内容提要:黥城旦讲乞鞫案反映出在秦汉时期诉讼程序中存在着一种覆讯制度。
覆讯制度,又称验证制度,是指案件经初次审讯,案情基本清楚后,再由其他官员或审讯人本人进行二次审讯,以验证初次审讯案情真实性的程序。
5史记6、5汉书6和5后汉书6中提到的/案验0是案其事,验其实之意。
验,是覆讯制度的另一表述。
居延新简中/粟君责寇恩案0和/秦恭取鼓案0也反映出秦汉覆讯制度的存在。
主题词:奏谳书 覆讯制度 案验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古代法律文献。
1985年第1期5文物6刊登了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5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6一文,对这批竹简作了简要的介绍。
5奏谳书6是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汉简的一部分,共228枚,包含了春秋至西汉初期22个案例,案例的的编排顺序是年代较近的在前,年代较远的在后。
1993年第8期5文物6杂志公布了5奏谳书6释文的第一部分,计16个汉初的案例,同时刊登了李学勤老师撰写的5奏谳书解说(上)6和彭浩老师撰写的5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6。
1995年第3期5文物6杂志公布了5奏谳书6释文的第二部分,计6个案例,同时刊登了李学勤老师撰写的5奏谳书解说(下)6和彭浩老师撰写的5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6等研究文章。
每读5奏谳书6都兴奋不已,古代司法官吏严谨的逻辑思维,准确的推理,以及其中展现出的秦汉时期的良好的诉讼制度令笔者惊叹。
本文就5奏谳书6第16个案例中所反映的在秦汉诉讼程序中存在的覆讯制度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覆讯制度存在之考证/黥城旦讲乞鞫0案,讲的是被告人讲被初审误判后经申请再审得到平反的事例。
/乞鞫0,相当于现代的申请再审制度,是指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申请对案件予以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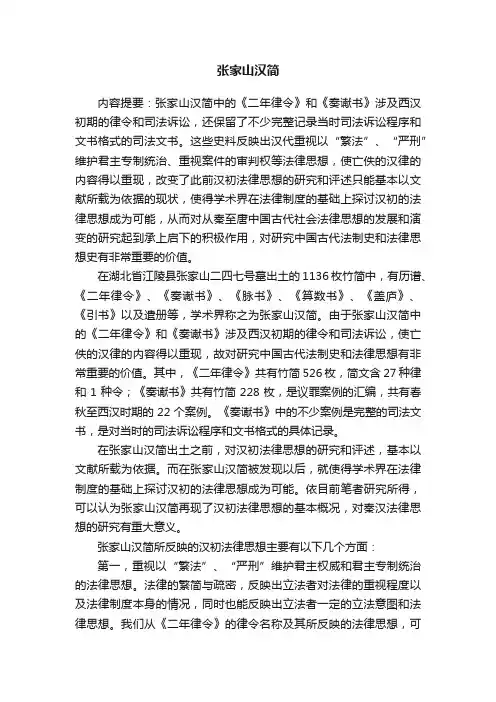
张家山汉简内容提要: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涉及西汉初期的律令和司法诉讼,还保留了不少完整记录当时司法诉讼程序和文书格式的司法文书。
这些史料反映出汉代重视以“繁法”、“严刑”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重视案件的审判权等法律思想,使亡佚的汉律的内容得以重现,改变了此前汉初法律思想的研究和评述只能基本以文献所载为依据的现状,使得学术界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探讨汉初的法律思想成为可能,从而对从秦至唐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起到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的1136枚竹简中,有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以及遣册等,学术界称之为张家山汉简。
由于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涉及西汉初期的律令和司法诉讼,使亡佚的汉律的内容得以重现,故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中,《二年律令》共有竹简526枚,简文含27种律和1种令;《奏谳书》共有竹简228枚,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共有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
《奏谳书》中的不少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书,是对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和文书格式的具体记录。
在张家山汉简出土之前,对汉初法律思想的研究和评述,基本以文献所载为依据。
而在张家山汉简被发现以后,就使得学术界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探讨汉初的法律思想成为可能。
依目前笔者研究所得,可以认为张家山汉简再现了汉初法律思想的基本概况,对秦汉法律思想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汉初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以“繁法”、“严刑”维护君主权威和君主专制统治的法律思想。
法律的繁简与疏密,反映出立法者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以及法律制度本身的情况,同时也能反映出立法者一定的立法意图和法律思想。
我们从《二年律令》的律令名称及其所反映的法律思想,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力图通过“繁法”来维护其政权和统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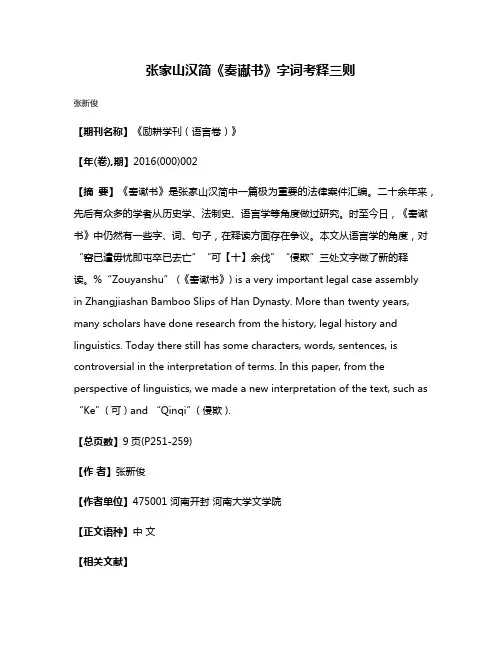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字词考释三则张新俊【期刊名称】《励耕学刊(语言卷)》【年(卷),期】2016(000)002【摘要】《奏谳书》是张家山汉简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法律案件汇编。
二十余年来,先后有众多的学者从历史学、法制史、语言学等角度做过研究。
时至今日,《奏谳书》中仍然有一些字、词、句子,在释读方面存在争议。
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窑已遣毋忧即屯卒已去亡”“可【十】余伐”“侵欺”三处文字做了新的释读。
%“Zouyanshu” (《奏谳书》) is a very important legal case assemblyin Zhangjiashan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More than twenty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one research from the history, legal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Today there still has some characters, words, sentences, is controversial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rm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we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such as “Ke”( 可) and “Qinqi”( 侵欺 ).【总页数】9页(P251-259)【作者】张新俊【作者单位】475001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相关文献】1.《为狱等状四种》标题简“奏”字字解订正——兼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题名问题 [J], 陶安;2.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初步比较 [J], 劳武利;李婧嵘3.西汉初年徭役制度——由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毋忧案”说起 [J], 万荣4.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之形成过程 [J], 水间大辅[日]5.《为狱等状四种》标题简“奏”字字解订正——兼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题名问题 [J], [德]陶安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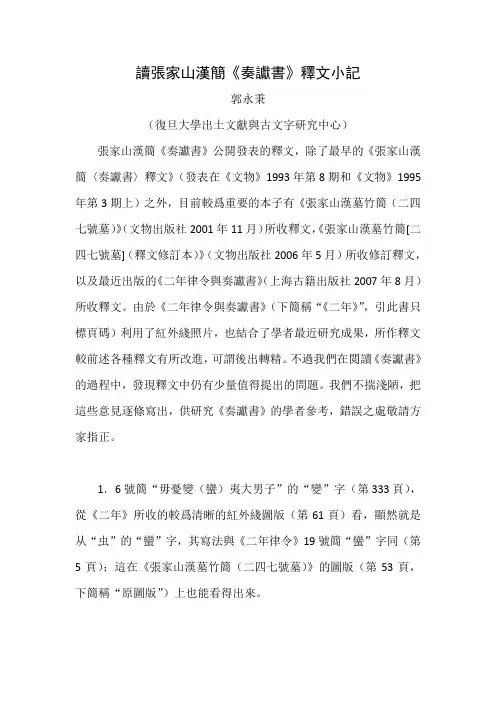
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小記郭永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公開發表的釋文,除了最早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發表在《文物》1993年第8期和《文物》1995年第3期上)之外,目前較爲重要的本子有《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所收釋文,《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5月)所收修訂釋文,以及最近出版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所收釋文。
由於《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下簡稱“《二年》”,引此書只標頁碼)利用了紅外綫照片,也結合了學者最近研究成果,所作釋文較前述各種釋文有所改進,可謂後出轉精。
不過我們在閲讀《奏讞書》的過程中,發現釋文中仍有少量值得提出的問題。
我們不揣淺陋,把這些意見逐條寫出,供研究《奏讞書》的學者參考,錯誤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1.6號簡“毋憂變(蠻)夷大男子”的“變”字(第333頁),從《二年》所收的較爲清晰的紅外綫圖版(第61頁)看,顯然就是从“虫”的“蠻”字,其寫法與《二年律令》19號簡“蠻”字同(第5頁);這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的圖版(第53頁,下簡稱“原圖版”)上也能看得出來。
2.22號簡末字和64號簡倒數第五字,各本釋文皆逕釋“鞫”,從原圖版和紅外綫圖版看,皆當釋為“鞠”,括注“鞫”,和32號簡、90號簡等以“鞠”表“鞫”的習慣相同。
施謝捷先生《張家山M247漢簡釋文》(未公開發表)早已根據原圖版正確改釋為“鞠”。
3.49號簡“公大夫昌苔(笞)奴相如”(第345頁)的所謂“苔”字,從圖版看(第65頁)其實本就是从“竹”的“笞”字。
《奏讞書》“笞”一詞多見,皆用“笞”字(如112號簡)或“治”字(如107號簡)表示,卻從未見使用“苔”字者;秦漢文字的“竹”頭和“艸”頭有個別例子確實難以分別,1但是此字所从的卻是明確無疑的“竹”頭,其寫法與《奏讞書》112號“笞”字、51號“符”字等“竹”頭寫法全同;而17、18、19、23號簡“菑”字的“艸”頭則與此顯然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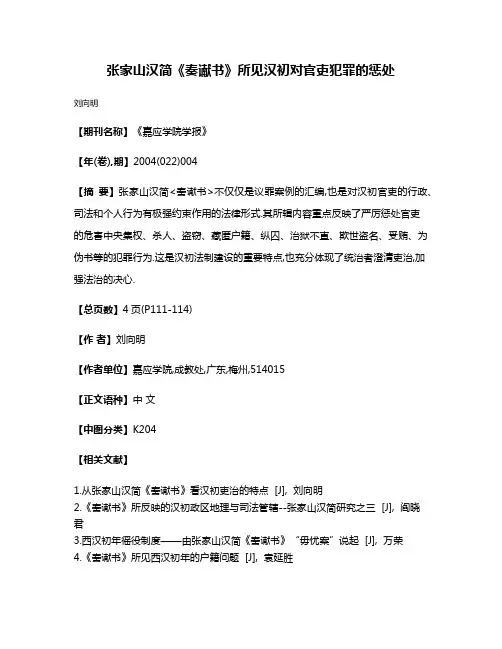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汉初对官吏犯罪的惩处
刘向明
【期刊名称】《嘉应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22)004
【摘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不仅仅是议罪案例的汇编,也是对汉初官吏的行政、司法和个人行为有极强约束作用的法律形式.其所辑内容重点反映了严厉惩处官吏
的危害中央集权、杀人、盗窃、藏匿户籍、纵囚、治狱不直、欺世盗名、受贿、为伪书等的犯罪行为.这是汉初法制建设的重要特点,也充分体现了统治者澄清吏治,加强法治的决心.
【总页数】4页(P111-114)
【作者】刘向明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成教处,广东,梅州,51401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4
【相关文献】
1.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看汉初吏治的特点 [J], 刘向明
2.《奏谳书》所反映的汉初政区地理与司法管辖--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三 [J], 阎晓
君
3.西汉初年徭役制度——由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毋忧案”说起 [J], 万荣
4.《奏谳书》所见西汉初年的户籍问题 [J], 袁延胜
5.《汉初典型诉讼案例》——首部研究湖北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西方语言专著[J], 吕德凯[德]; 劳武利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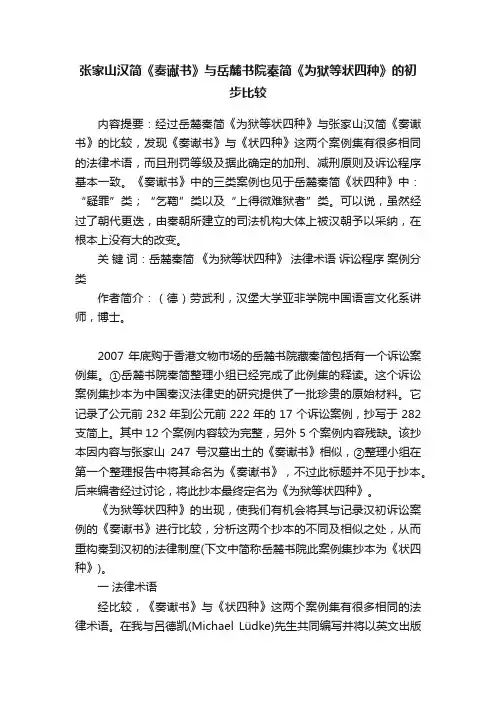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初步比较内容提要:经过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比较,发现《奏谳书》与《状四种》这两个案例集有很多相同的法律术语,而且刑罚等级及据此确定的加刑、减刑原则及诉讼程序基本一致。
《奏谳书》中的三类案例也见于岳麓秦简《状四种》中:“疑罪”类;“乞鞫”类以及“上得微难狱者”类。
可以说,虽然经过了朝代更迭,由秦朝所建立的司法机构大体上被汉朝予以采纳,在根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关键词: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法律术语诉讼程序案例分类作者简介:(德)劳武利,汉堡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讲师,博士。
2007年底购于香港文物市场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包括有一个诉讼案例集。
①岳麓书院秦简整理小组已经完成了此例集的释读。
这个诉讼案例集抄本为中国秦汉法律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材料。
它记录了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22年的17个诉讼案例,抄写于282支简上。
其中12个案例内容较为完整,另外5个案例内容残缺。
该抄本因内容与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相似,②整理小组在第一个整理报告中将其命名为《奏谳书》,不过此标题并不见于抄本。
后来编者经过讨论,将此抄本最终定名为《为狱等状四种》。
《为狱等状四种》的出现,使我们有机会将其与记录汉初诉讼案例的《奏谳书》进行比较,分析这两个抄本的不同及相似之处,从而重构秦到汉初的法律制度(下文中简称岳麓书院此案例集抄本为《状四种》)。
一法律术语经比较,《奏谳书》与《状四种》这两个案例集有很多相同的法律术语。
在我与呂德凯(Michael Lüdke)先生共同编写并将以英文出版的《中国秦汉法律术语字典》(Dictionary of Early Chinese Legal Terminology)一书中,我们分析了《奏谳书》中出现的125种法律术语。
其中有至少78种法律术语(68%)出现在《状四种》中。
同时《状四种》中只有11种法律术语不见于《奏谳书》,而这11种术语中除了表示“调查报告”的“状”以外,其他10种均见于从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法律抄本③或从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抄本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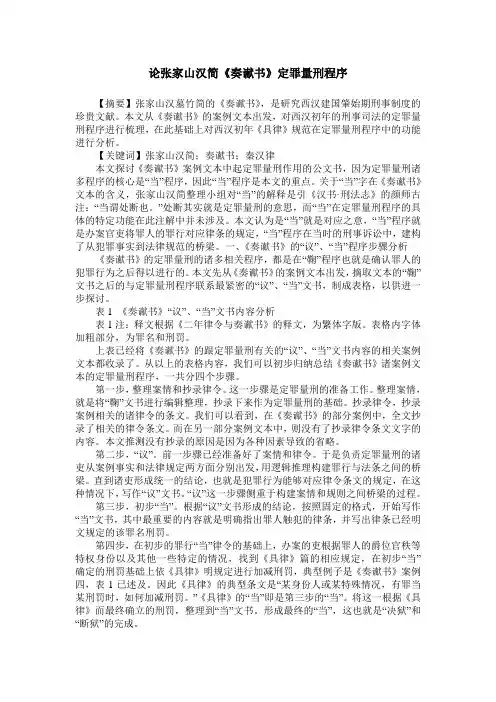
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摘要】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奏谳书》,是研究西汉建国肇始期刑事制度的珍贵文献。
本文从《奏谳书》的案例文本出发,对西汉初年的刑事司法的定罪量刑程序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西汉初年《具律》规范在定罪量刑程序中的功能进行分析。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秦汉律本文探讨《奏谳书》案例文本中起定罪量刑作用的公文书,因为定罪量刑诸多程序的核心是“当”程序,因此“当”程序是本文的重点。
关于“当”字在《奏谳书》文本的含义,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当”的解释是引《汉书·刑法志》的颜师古注:“当谓处断也。
”处断其实就是定罪量刑的意思,而“当”在定罪量刑程序的具体的特定功能在此注解中并未涉及。
本文认为是“当”就是对应之意,“当”程序就是办案官吏将罪人的罪行对应律条的规定,“当”程序在当时的刑事诉讼中,建构了从犯罪事实到法律规范的桥梁。
一、《奏谳书》的“议”、“当”程序步骤分析《奏谳书》的定罪量刑的诸多相关程序,都是在“鞠”程序也就是确认罪人的犯罪行为之后得以进行的。
本文先从《奏谳书》的案例文本出发,摘取文本的“鞠”文书之后的与定罪量刑程序联系最紧密的“议”、“当”文书,制成表格,以供进一步探讨。
表1 《奏谳书》“议”、“当”文书内容分析表1注:释文根据《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的释文,为繁体字版。
表格内字体加粗部分,为罪名和刑罚。
上表已经将《奏谳书》的跟定罪量刑有关的“议”、“当”文书内容的相关案例文本都收录了。
从以上的表格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归纳总结《奏谳书》诸案例文本的定罪量刑程序,一共分四个步骤。
第一步,整理案情和抄录律令。
这一步骤是定罪量刑的准备工作。
整理案情,就是将“鞠”文书进行编辑整理,抄录下来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
抄录律令,抄录案例相关的诸律令的条文。
我们可以看到,在《奏谳书》的部分案例中,全文抄录了相关的律令条文。
而在另一部分案例文本中,则没有了抄录律令条文文字的内容。
本文推测没有抄录的原因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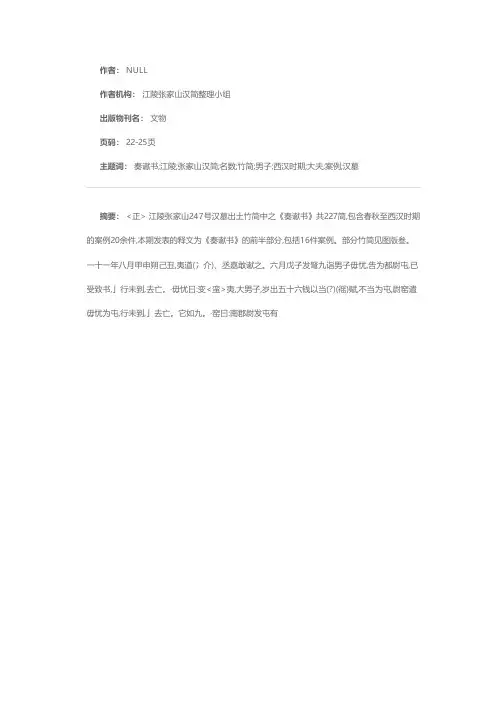
作者: NULL
作者机构: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22-25页
主题词: 奏谳书;江陵;张家山汉简;名数;竹简;男子;西汉时期;大夫;案例;汉墓
摘要: <正> 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竹简中之《奏谳书》共227简,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案例20余件,本期发表的释文为《奏谳书》的前半部分,包括16件案例。
部分竹简见图版叁。
一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冫介)、丞嘉敢谳之。
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毋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
·毋忧曰:变<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窑遣毋忧为屯,行未到,」去亡。
它如九。
·窑曰:南郡尉发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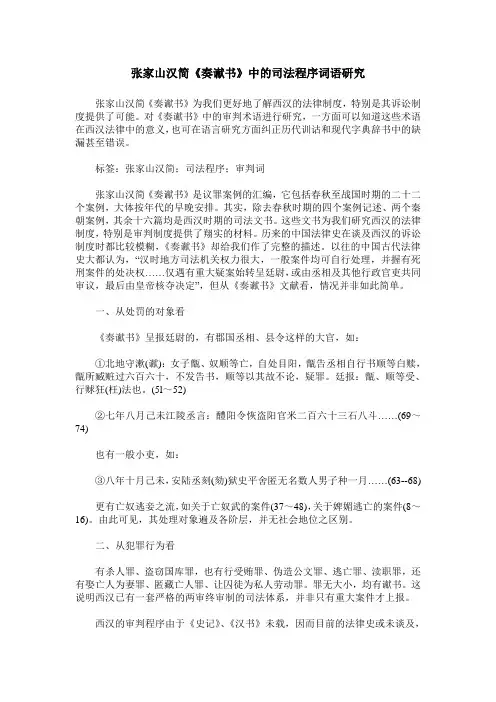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司法程序词语研究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其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能。
对《奏谳书》中的审判术语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知道这些术语在西汉法律中的意义,也可在语言研究方面纠正历代训诂和现代字典辞书中的缺漏甚至错误。
标签:张家山汉简;司法程序;审判词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它包括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二十二个案例,大体按年代的早晚安排。
其实,除去春秋时期的四个案例记述、两个秦朝案例,其余十六篇均是西汉时期的司法文书。
这些文书为我们研究西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审判制度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历来的中国法律史在谈及西汉的诉讼制度时都比较模糊,《奏谳书》却给我们作了完整的描述。
以往的中国古代法律史大都认为,“汉时地方司法机关权力很大,一般案件均可自行处理,并握有死刑案件的处决权……仅遇有重大疑案始转呈廷尉,或由丞相及其他行政官吏共同审议,最后由皇帝核夺决定”,但从《奏谳书》文献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一、从处罚的对象看《奏谳书》呈报廷尉的,有郡国丞相、县令这样的大官,如:①北地守漱(谳):女子甑、奴顺等亡,自处目阳,甑告丞相自行书顺等白赎,甑所臧赃过六百六十,不发告书,顺等以其故不论,疑罪。
廷报:甑、顺等受、行赇狂(枉)法也。
(5l~52)②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阳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 (69)74)也有一般小吏,如:③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刻(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人男子种一月……(63--68)更有亡奴逃妾之流,如关于亡奴武的案件(37~48),关于婢媚逃亡的案件(8~16)。
由此可见,其处理对象遍及各阶层,并无社会地位之区别。
二、从犯罪行为看有杀人罪、盗窃国库罪,也有行受贿罪、伪造公文罪、逃亡罪、渎职罪,还有娶亡人为妻罪、匿藏亡人罪、让囚徒为私人劳动罪。
罪无大小,均有谳书。
这说明西汉已有一套严格的两审终审制的司法体系,并非只有重大案件才上报。
西汉的审判程序由于《史记》、《汉书》未载,因而目前的法律史或未谈及,或一笔带过,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张家山汉墓竹简研究述评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枚,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内涵十分丰富,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中《二年律令》的发现,不仅使秦汉法律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汉、唐法律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而《奏谳书》则是秦汉司法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可以了解秦汉律的实施情况;《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数学发展水平。
诚如李学勤先生在《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一文中所说:“张家山汉律竹简的发现,不仅使我们能够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而且得以同秦律比较(包括云梦睡虎地、龙岗的秦律竹简),研究由秦到汉法律的演变过程。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简的情况和意义轮廓,尤其对有关汉律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做了说明,同时也简要介绍了《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简的内容,并猜测墓主可能是专精法律的学者,但他的藏书除法律外,还有医书、兵阴阳、数学等书籍及算筹,说明他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
这一介绍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纷纷期待这批珍贵竹简能够早日问世,以弥补西汉初年法律史研究的空白。
张家山汉简最早公布的是《脉书》和《引书》两部医学简的释文,部分内容可与马王堆帛书相互印证。
其中《脉书》可以确证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书》卷前佚书应是由《足臂十一脉炙经》和《脉书》构成,可补充帛书《脉法》中的不少缺字,书中的一些疾病名称也可与《五十二病方书》对应;《引书》是专门讲述导引、养生、治病的著作,与马王堆帛书《导引图》互为发明。
连劭名在《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文物》1989年第7期)一文中,对《脉书》做了介绍,并对释文进行校正,同时说明《脉书》在中国医学史上的意义。
《奏谳书》“受致书为屯,去亡”案三个司法术语再探第31卷第1期V01.31No.1许昌学院JOURNALOFXUCHANGUNIVERSITY2012年第1期No.1,2012《奏谳书》"受致书为屯,去亡"案三个司法术语再探周敏华(东吴大学中文学系,台湾台北111)摘要:《张家山247号汉墓?奏谳书》出土后,史料未及备载的秦汉时期司法制度彰显于世.研读《奏谳书》案例,除了通读简文,对其中的司法术语,法律规定,更需确切的掌握,方能理解该案记述的历史背景及司法制度的实际运用.《奏谳书》"受致书为屯,去亡"案中,"署狱史曹发","吏当","它县论"等三项司法术语,备受学界争议,对其进行若干梳理和解析,对认识秦,汉时期的奏谳流程,应有着极大的关键性作用.关键词:奏谳书;署狱史曹发;吏当;它县论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824(2012)01—0083—05 《奏谳书》中第一则"受致书为屯,去亡"案,是至今所出土的秦,汉时期奏谳案例中,相当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其中所记述的司法术语,司法流程,大致还算完整,研读此案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汉时期究竟是如何提请奏谳,及司法审判的运作流程.唯研读此案时,有三个司法术语,学界解读不一,此势必将影响到对秦,汉时期奏谳程序的认知歧异.本文试图在各家的研究成果上,再次梳理史料,以便于对此三项司法术语进行析解.在解读此案前,先节录该案之简文内容: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渝,丞嘉敢谳之.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无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简1],行未到,去亡.无忧日:变(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繇(徭)赋,不当为屯,尉窑遣无忧为屯,行未到[简2],去亡.它如九.窑日: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日勿令为屯,即遣之,不智(知)亡故,它如无忧.[简3]诘无忧:《律》变(蛮)夷男子岁出寅钱,以当繇(徭)赋,非日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窑已遣,无忧[简4]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无忧日:有君长,岁出寅钱,以当繇(徭)赋,即复也,存吏,无解.问,如辞(辞).鞫之:[简5]无忧变(蛮)夷,大男子,岁出寅钱,以当繇(徭)赋,窑遣为屯,去亡,得,皆审.疑无忧罪,它县论,敢谳[简6]之,谒报,署狱史曹发.史当:无忧当要(腰)斩,或日不"-3论.廷报:当要(腰)斩[简7].~11213高祖十一年(前196)八月六日,夷道令和夷道丞嘉共同向南郡郡守,奏谳一难以裁决的疑案.奏谳文书一起始除了写下奏谳的时间,也以司法专用术语:"敢谳之"奏呈此案."敢谳之"三字,除了为恭敬的奏呈用语,同时也表达出,疑狱难以定罪,故而请求上级,给予批覆疑案的判决结果.于是在读鞫之后,文书多会出现:"疑x罪……敢谳之."其中"疑x罪",便表明此案要请示奏谳的对象为谁.本案既言"疑无忧罪",即说明要请示批覆判决的对象,就是收到征调屯戍文书后,却逃亡而未前往服役的男子无忧.本来这起案件只要依法处置即可,但问题就出在无忧所以会逃亡,完全是因他错解了法律规定."《律》:变(蛮)夷男子岁出寅钱,以当繇(徭)赋",即蛮夷男子每年缴交南蛮赋税"寅钱"后,便可以不服役,不纳赋税.但无忧收到县尉窑所征调的,并非是一般的徭役,而是屯戍令.审理人员很清楚地告知无忧,法律并未规定,缴了五十六钱的寅钱,便可以不必屯戍;即使可以不屯戍,但县尉窑的征召令既已发出,就应当前往报到,怎能径自逃亡呢?无忧的答复为曾见过他们的君长,因缴了蜜钱,既免除徭役,赋税,又免除屯戍,故而认为自己也不该被征召屯戍.由此案例,呈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第一,服役与屯戍性质不同,服役仅是一般性的徭役,屯戍则是兵役,征召而未能如期前往,受到收稿日期:201l一09—20作者简介:周敏华(1981一),女,中国台北市人,历史学博士,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秦汉史及秦汉简犊.83?的惩处差异便极大了.《秦律十八种?徭律》简115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地方官吏为中央征发徭役,若耽搁而未征调,要赀二甲.迟到了三至五日,要被训斥;超过六日至十日者,要赀一甲.同样是"失期",屯戍之惩处则与徭役形成天壤之别,《汉书?陈胜传》载:"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发问左戍渔阳九百人,胜,广皆为屯长. 行至蕲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 法皆斩."均为秦时的法令,屯戍失期竞要论"斩". "斩"究竟为斩首或腰斩,史家并未明说,但透过无忧之案例,即知"斩"应为"腰斩".《汉书?韩安国传》如淳曰:"军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斩."亦可证即使失期,当要腰斩.由以上两项材料即可说明, 秦,汉时期对徭役和屯戍的要求本不相同,因两者的内容实有殊异.《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边戍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宋叙五先生释"卒更":"为给郡县之役,一月一更."①由此可知,服徭役的处所是在郡,县,无论其劳动或安全程度,绝对远远胜过危在边境,得时时提防外族入侵的屯戍.秦汉时期逃避屯戍的情况或许相当严重,故法律对其惩处也便规定地格外严厉.第二,秦汉时期只要是收到官方的征召文书,或被缉捕,无论有无冤屈,无论理由多充分,皆要遵照规定,先行前往征调处;对前来缉捕的人员,也必须束手就擒,绝不能顽强抵抗.《奏谳书》第五则"拒捕贼伤人案",士伍武于楚汉争战之际,早已降汉且自占名数,已不再为奴.但高祖十年(前197) 七月,他原先的奴隶主士伍军,却向校长池举告,言大奴武逃亡,如今出现在校长池管辖的亭西,请求校长池前往缉捕.武见前来捉拿他的求盗视,不但拒捕,还以剑刺伤求盗视.审理人员诘问武时即日:"武虽不当受军弩(奴),视以告捕武,武宜听视而后与吏辩是不当状."士伍武见校长池,求盗视来抓拿他,他既早已不再为奴,户籍上便已登记他为士伍的身分.如此,他只需与二位缉捕官员,一道回官府里查询户籍即可,实在没有必要以武力辩护.同样地,本案的无忧即使认为自己已缴纳蜜钱,不当屯戍,也无需逃亡,应当先前往征召所在地报到.无忧经审理人员解说后,虽明嘹法律并未规定,缴纳寅钱可免除屯戍,但他既曾见君长缴了蜜钱,即可无需屯戍,心里尽管再不情愿认罪;或者对法律究竟如何施行,仍感到极度困惑.审理人员既已如此而诘问,无忧也只能以"毋解"回应,因无忧已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只能听凭官府做最终的判决.如此我们便可理解,何以夷道和南郡,皆难以论断无忧罪名的关键,实是因无忧不明法律规定, 加上他曾见君长缴纳寅钱,便无需屯戍.这两项因素,都让无忧难以心服口服的认罪,无忧只是因无辞可辩,而只好听凭法律裁决.先秦法制有"三宥"的规定,其一便是"弗识",②罪责可得到赦免. 无忧不奉征召而逃亡,应当颇符合"弗识"的状况, 或许夷道和南郡仍存留着先秦的法制思维,加上秦,汉之际,法制推行地还不够久远,对"一决于法"的精神也掌握的不够深入.无忧虽无辞可辩, 但又非真心服罪,审理人员在此两难之下,最好的选择,应当是向上奏谳.南郡审理人员讯问完无忧,也将一切实情诊问完毕后,接着便是向廷尉奏谳此案.欲理清此道奏谳程序,必须先对简文所出现之"署狱史曹发","史(吏)当"和"廷报"等流程,进行一番梳理.(一)"署狱史曹发""署狱史曹发"最令人费解的,便是"发"字.学界或释为"发送",如日人池田雄一,高恒等皆主之.③蔡万进虽未明言其意涵,但他指出:汉初各县道向上级机关奏谳的疑狱文书,最原始形式可能也只是由首句"敢谳之"与末句之"敢谳之"间加上主体部分,即告,劾,讯,诘,问,鞫等内容构成.如果考虑到里耶秦简中诸县道上行至郡的文书皆要求给予回复的请求,文中皆日"敢言之,写上,谒报署金布发,敢言之"等字样,作为各县道上谳的疑狱文书,自然亦应当有此项内容……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一至五中诸"谒报,署狱史曹发"等,应该也应当是县道奏谳疑狱文书中常用文书用语,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应属县道奏谳文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蔡氏之意,本案自一起始"敢谳之",至末了"署狱史曹发"止,皆是县,道奏谳疑狱的文书用语.既是如此,此处之"发",应当比较近似"发送"之意.另一释为"拆封"者,如整理者注:"发,拆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与简文同意."…¨汪桂海研究汉代官文书制度,亦提出与整理者相同之论述.其日:"张家山汉简奏谳①详见宋叙五《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1970年9月,页14.②(唐)贾公彦疏:"郑司农云:不识,谓愚民无所识,则宥之过失.若今律过失杀人,不坐死."见《周礼?秋官?司寇》,十三经注疏本,页539.③[日]池田雄一着《(奏谳书)一中国古代的审判记录》:"发,发送."刀水书房,2002年版,38页;高恒着《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狱史曹发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344页.84?书中有'署某官某发'的话,如奏谳书一'署某官某发',奏谳书二'署某官某发',奏谳书五'署狱史如唐发'.有人认为这是奏谳之辞中的'署文,发文狱史之名',把'发'字理解为发文即发送文书,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发'实应释为开启,拆封."_3』】.汪氏之观点,主要是归纳A8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出土之木简,而得出的结论.今各列举一发文及拆封例如下.1.发文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盐言府?一事集封八月庚中尉史常封(136?44).船这是甲渠候官移送给都尉府之文书,文书内容言及士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没有得到廪盐.共一份文书(即"一事"),写成多份集装在一个容器封缄内,①或封检的封泥印信之数超过二处(即"集封").发文时间为八月庚申,是由一名为"常"的申尉史,负责封印及发送.2.拆封居延尉丞,其一封居延仓长,一封王宪印,十二月丁酉令史弘发.(136?43)"居延仓长"应是指居延都尉府下属之居延城仓之长.这份文书之封检上有两个封印,一是"居延仓长"印,一是"王宪"之印.拆封时间为"十二月丁酉",拆封人为令史弘."发"字之前,记录了封泥内容,这是收受文书时应有的记录.《二年律令?行书律》简274—275所记载的规定,可以提供我们了解记录封泥的原因: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简274]一两.书以县次传,及以邮行,而封毁,口县口劾印,更封而署其送徼(檄)日;封毁,更以某县令若丞印封I简275】.封泥是记录行书发文并封缄的最主要根据,秦,汉时期邮人传递行书时,或常见延误传递时间,或不慎毁封状况.收到文书之单位,除了要仔细核对封泥之真假,也要详细记录封泥内容,及收文之时间. 若已毁封但文书又必需继续传递者,则改由收文的县令或县丞之印封缄.透过以上两项材料,可知区分发文与收文的最主要关键,便在最终所记录的,是"封"字或"发" 字."封"表封印并发送;"发"为拆封,且会记录封泥内容和收文时间.拆封之后,必需做收文登记, 再"交由专门办理文书的文吏,或直接呈送本官署长吏审阅批办.""(二)"吏当"由此可知,本案之"署狱史曹发",或是指名为曹的狱史,负责拆封这份奏谳文书,并呈文给所属长官批办.但问题是,此时文书已发送至哪个单位了,究竟是郡(二千石官)?亦或廷尉?学界持有不同看法,且各家之观点,多是围绕在"吏当"或"廷报"上,亦即"吏当"是由哪个层级单位所拟,拆封文书者,大概便隶属于哪个单位.下文先罗列各家对"吏当"层级的归属看法,以资分析.1.郡(二千石官)前文已言及,蔡万进先生主张"署狱史曹发",为县道所发文,但蔡氏对"吏当"之内容,则以为是郡(二千石)所拟.其日: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三"廷报"内容另简书写,反映"廷报"是对诸"吏当"意见的一种裁决."廷报"与诸文书中"吏当"或"吏议"应不属同一个机关提供,具体说应分属郡二千石官及中央廷尉……请求上级"谒报",是要同时将初步审理判决意见提供给上级的.准此,郡成为决谳的最高地方机构,"以其罪名当报之""-3是其工作范畴内的事情,只有"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移廷尉"时,看来是将郡二千石官延所作"吏当,吏议"意见一并上报的.蔡万进从"吏当"之前有"谒报",参考张家山汉简研读班主持者李均明及徐世虹两位先生之意见,说明当郡二千石官难以审断定谳时,会将"吏当"的分歧意见,连同"下辖县道所上奏谳文书一同'移廷尉',由廷尉'以其罪名'当报之."儿观至于"廷报"的内容另简书写,蔡万进先生也推测:"这一部分内容是与县道奏谳的疑狱文书,郡二千石官的包括『吏当』意见的文书一起下达给了疑狱的原奏谳机关一县道的."武汉大学简帛中心虽未对此段内容提供意见,但在"署狱史曹发"下却注日:"谒报"云云亦见于里耶秦简,如J19正面云:"谒报.报署金布发."反观奏谳书"署(发)",似是"报署(发)"之省,是说回报文书署明(发出或开启……狱史曹,中唐,狱西唐恐皆是郡中治狱机构).②武汉大学简帛中心以为"署狱史曹发",是郡的机构来发出或开启.惜"吏当"究竟是哪一个层级所拟,则未进一步说明.2.廷尉明确地指出"署狱史曹发",是已到了廷尉署层级者,为汪桂海.其日:"署狱史曹发"即是说此奏谳书在奏呈廷尉府之后,由狱史曹拆封.这些"署某官某发"一类的文字当是负责拆封者拆开文书的印封后在该文书最末签署的.奏谳书启封后,①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集封'是指封装方式,即将要发生的多份文书集装于一个容器内封缄,亦与事类的多少无关."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15.②彭浩,陈伟,工藤元男着《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一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简首第一字整理本未释,据红外线影像,似'诸'字."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36.85?先交由廷尉府僚属讨论拟定处理意见,再交延尉定夺,所以奏谳书简文中紧接在"署某官某发"之后,便当是"史当"云云,"廷报"一一r3]150石o汪氏以为,文书既是由廷尉署拆封,"吏当"自然是由廷尉署的官员所拟.日人宫宅洁观点与之近似, 且更进一步地说:县级制方的文书毕竞是在第二次r敢谳之处结束,此后的判决意见是由受理的上级机关提出的.县不能援引,对照律令,只能制成记录审讯经过的文书,封缄后向上级报告.在收到文书的机关里,由狱史等开封文书,开封者的姓名以"署某发"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收到文书的机关再次量刑.首先要列举判决意见,这一阶段可视为"史(吏)当一史(吏援引的法律)".廷尉下设"奏谳掾",可参与决疑案.判决意见的推敲拟定,或许正是经由这些掾吏之手.拟定的判决意见在"廷"上报一"廷以闻",以等待裁断.在此,"廷"中的回答为"廷报".两位先生皆共同提出,"吏当"是廷尉署的官员所拟定的意见,拟完后再交由廷尉裁决,此于《奏谳书》第二十一则"杜女子甲和奸"案,可得着印证. 案中的杜女子甲被婆婆素控告,夫死未葬却与男子丙于棺后内中和奸,此案从县廷奏谳至廷尉署,原因便在并未捕获男子丙,捉奸并未成双,也无当庭问讯,难以构成和奸事实.廷尉署的三十位官员,想方设法地从相关条文中,终于议出女子甲犯了"次不孝"及"敖悍"罪.但问题是,这与婆婆素原告的和奸罪何干?更何况和奸罪只需论处"耐为隶臣妾",此案奏谳至廷尉,何以却议出了两项"完为城旦舂"罪呢?廷史申服役返回,提出了五道设问,终于导正三十位廷尉署官员的误判.此案可证,廷尉署确实是由僚属共同商讨议罪.但问题是,即使廷尉署有议罪的事实,也不能因此便断定, "吏当"所拟定的判决意见,必然是出自廷尉掾吏之手.尤其宫宅洁对"廷报"之"廷"字,又提出了如下看法:作出答复的是哪一级机关,未必有明确的记载.按实际等级,可视为郡,或中央廷尉,或皇帝,但措辞一律用"廷".因此这里所说的"廷",不指"廷尉"等特定机关.此段内容与前段引文,显然已出现两个极大的不同观点.首先,"廷报"之"廷",层级若可以由郡延伸至皇帝,则"吏当"所拟,便未必非出于廷尉僚属不可.其次,"廷报"与"吏当"应当是出于不同层级(或单位)之手,若"廷报"为郡,则"吏当"的拟定,便极可能是由郡的僚属,或由奏谳的县廷提出.宫86?宅洁言:"县不能援引,对照律令,只能制成记录审讯经过的文书,封缄后向上级报告."不知所据为何?此外,《奏谳书》一至十三则奏谳案例,第一则是由夷道奏谳,第二,五两则,是由江陵县丞奏谳, 第三,四两则,为胡县县丞奏谳.这五则县,道奏谳案例,皆有"吏当"(或"吏议"),除第二则无"廷报",其余皆有"廷报J(或"廷以闻").第六至十三则奏谳案例,全数由郡(二千石官)所奏谳,但完全不见"吏当"(或"吏议"),而皆有"廷报".虽然我们不能单凭这十三则案例的对比现象,便推测"吏当"只有在县,道奏谳时才可见,但却或可由此而排除,"县"未必不为"吏当"拟定者的可能性.既然学界皆认为,"署狱史曹发"与后文的"吏当"有关,或许我们便可从"署狱曹发"处,再进行探究.首先是"署"字,汪桂海及宫宅洁二氏,皆释为负责拆封者所做的签署记录;武汉大学简帛中心释为"署名",即指定由哪个单位收文或发送.三位先生之意见,多着力在"书之"之意涵上,此于史料中确实可见.如《汉书?郑当时传》:"翟公大署其门."师古日:"署谓书之."其次为"狱史曹"三字,文献未见此三字并称,仅可见"狱史"之官名. 唯"狱史"究竟隶属于哪个层级?我们仍需透过史料,以进行梳理.《后汉书?百官志?廷尉》载:"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日: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狱,皆处当以报."李贤注:"《汉官旧仪》日:员吏百四十人……十三人狱史."除了廷尉之下设有"狱史",县及乡也有设之,《汉书?于定国传》:"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后汉书?百官志?县乡》李贤注引《汉官旧仪》:"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西汉宣帝时之丞相于定国(?一前40),其父曾担任县狱史及郡决曹之官职;《汉官旧仪》亦列举乡设狱史五十六人,此即说明乡,县皆有"狱史"之职.除了乡,县,郡也设置"狱史".严延年出任河南太守,曾"察狱史廉."师古云:"延年察举其狱史为廉."九十''其狱史"所指即为郡狱史.透过以上史料,知"狱史"一职,乡,县,郡及廷尉皆有之,徒据"署狱史曹发",实在难以断定,其究竟当隶属于哪个层级.不过,既然"发"为拆封,便表示签署此记录者,绝对是收到奏谳文书后之单位;此案既是由夷道所奏谳,收到文书者便应当是郡以上之层级.若如此,则郡及廷尉署官员,便皆有可能是拆封文书后,对廷尉奏呈"吏当"者.笔者只言奏呈,却不言拟定,实是因"吏当"的确切提出者,简文并未记录.笔者初步假设:"吏当"之拟定,应是县至廷尉署的官员皆可为之.因秦汉时期,县是决狱的最基层单位,县即使对疑狱难以裁决,而需向上奏谳,应当也有拟定"吏当"的职责.何况"吏当"不过是裁决的初步意见,拟定全是依据法令,"廷报"的回复,也与"吏当"之内容相同.显然,无论是哪一层级所拟定之"吏当",皆没有背离当代的法律规定,其所以需奏谳,恐是认知上出现疑惑,或所判定的罪刑极重,为了慎重其事,故而往上提请奏谳.此推论若无误,则"吏当" 之拟定,便未必是向廷尉奏呈的最终层级,其可以是县,道,是郡,甚至是廷尉署之僚属.总之,此案之"吏当",夷道至廷尉署官员皆有权拟定,但最终只奏呈至廷尉,因"廷报"为廷尉对此案的答复.①若是奏谳至皇帝,则会以诏令颁布,甘肃武威缠山村磨嘴子汉墓所出土(王杖诏令册)简7—8,即是如此.②(三)"它县论"简六"疑毋忧罪,它县论,敢谳之"一句,其中的"它县论",是厘清所奏谳对象的关键术语.《奏谳书》中之案例一,二,三,四,十四,十六均可见"它县论",其中案例十四最为特殊,直接写出"种县论"."种县论"是解答"它县论"的关键钥匙,学界对此早已关注,最早做出分析者为张建国先生. 张先生日:"种县论"就是说种作为普通人直接由县里处治了(耐为隶臣),而舍匿平,因为是狱史,又有五大夫的爵位,所以需要上奏.这些报实际是一种法定的上报审批制度.③张先生从罪犯的身份而说明:种既无高爵也不担任公职,此案也没有疑狱奏谳的必要,县里可以直接对男子种进行判决,故曰"种县论".日人初山明先生亦持相同观点,且进一步地说:在上奏处分藏匿了"种"这个没有户籍之成年男子的狱吏的《奏谳书》之中,可见"种县论"——句(63—68,pp.218—219).因为很清楚这是指"关于种在县论处",所以如果是那样则"它县论"这一定型句序就可以理解为"关于其它的人在县里论处"的意思.学习院大学汉简研究会译作"其它的案件(关于符的)已在县论罪",这是近于正确的解释.…高恒先生释"种县论"时,亦直接释为:"种的罪行县廷已处决."释"它县论"时,也说:"其它问题,县廷已作结论."日人宫宅洁先生,基本上也是持相同意见.④不过学界对"它县论"也有另一套说法,即"悬而未论",⑤若将此套入"种县论"中,则无名数种之罪名,也将"悬而未论".然种之罪名已经太明确了,应当不至于"悬而未论",种之罪名若悬而未论,便一定会进行疑狱奏谳.倘若如此,则"种县论"之后所当接续的用语,便当为"敢谳之",而非是"敢言之"."敢言之"是向上级报告此案,不是疑狱奏谳,此于《奏谳书》第一至第十三则疑狱奏谳案例,或以"敢谳之"起始,以"敢谳之"结束,即可得证.参考文献:。
汉简《奏谳书》和秦汉刑事诉讼程序初探1983年末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的247号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包括重要的古代法律文献。
1985年第1期《文物》登载了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一文,对这批汉简作了简要的介绍。
经整理小组几年来的整理,现已分两次公布了汉简中属于《奏谳书》的释文。
《奏谳书》是竹简原有的标题,共有简227支,计22件案例,有的学者指出这是一些议罪案例的汇集,案例的编排次序,大体是年代较晚的汉代案例在前,年代较早的汉代以前的案例居后。
《文物》杂志1993年第8期公布了《奏谳书》释文第一部分,计有16件汉初案例,同时刊载了李学勤先生撰写的《奏谳书解说》和彭浩先生撰写的《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
1995年第3期的《文物》又公布了《奏谳书》释文的第二部分,计有6件案例,同期刊载了李学勤撰写的《奏谳书解说》和彭浩撰写的《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等研究文章。
笔者感到高兴的是,出土已经十几年的文献经过整理小组的辛勤工作终于公开发表,从中可以感受到各位学者付出了相当的心血。
李学勤和彭浩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释读和分析,使古朴难懂、现存史料又缺乏记载的古代案例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所初步理解,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扫除了一些障碍。
笔者不揣浅陋,在钦佩整理小组和李、彭二位先生总体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同时,想再就总体分析和其他案例以及相关问题谈些看法。
关于《奏谳书》标题,《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一文着重诠释了“谳”字,文中说:《说文》:“议罪也。
”刑狱之事有疑上报称为“谳”,所以此字又训为请或疑。
汉制,“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
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
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竹简《奏谳书》正是这种议罪案例的汇集。
笔者以为说它们是“议罪案例的汇集”似乎欠妥。
既然是疑案上报才称为“谳”,那么通观22件案例,其中有些并非疑案亦非议罪是可以肯定的。
张家山汉简汉律十六章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法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其中的汉律十六章,更是展现了汉代法律体系的严密与丰富。
这十六章法律涵盖了多个方面。
首先是贼律,主要针对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如谋反、叛乱等。
盗律则侧重于打击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的犯罪。
具律规定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和通用条款,相当于现代法律中的总则部分。
囚律涉及到对囚犯的管理和审判程序。
捕律明确了追捕罪犯的相关规定和流程。
杂律包含了各种较为琐碎的违法行为及处罚方式。
户律与户籍管理、家庭婚姻等方面有关。
兴律关注的是徭役征发、工程建设等事务。
厩律针对畜牧养殖和相关管理制定了规则。
钱律着重规范货币的使用和管理。
效律主要是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规定。
傅律涉及到人口登记和赋税徭役的征发。
置吏律规定了官吏的设置和任免。
均输律与物资的调配和运输有关。
市律与市场交易的管理密切相关。
汉律十六章的特点十分显著。
其一,法律条文较为具体细致,对各种犯罪行为和处罚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其二,注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有所区别。
其三,强调道德伦理在法律中的作用,许多法律条款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在司法实践中,汉律十六章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为各级官员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有助于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也对民众的行为起到了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汉律十六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限制,某些法律条款可能存在不合理或不公正之处。
而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法律的实施效果打折扣。
汉律十六章对后世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许多法律原则和制度在后世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十六章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它不仅反映了汉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The Principle for Applicable Penal Law Reflected in the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Zhangjia Hill
作者: 李均明
作者机构: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29
出版物刊名: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7-123页
主题词: 张家山汉简;适用刑罚;罪刑相应
摘要: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依法律条款定罪,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又
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作者: 李学勤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26-31页
主题词: 奏谳书;二年律令;案例;张家山;汉书;历史文化;法律文献;汉初;成年男子;刑法志
摘要: <正> 湖北江陵张家山近年屡次发现竹简,内容珍异,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其中1983年末发掘的247号墓、1988年初发掘的336号墓,所出都有汉初的法律文献,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有极重要的关系,与云梦睡虎地、龙岗出土的秦律堪相辉映。
张家山247号墓的竹简,经整理小组几年的努力,业已基本整理就绪,释文陆续发表。
简中属于法律一类的,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
《奏谳书》的释文在《文物》本期起刊出,《二年律令》随后也将公布,相信会引起各方面学者的注意和反响。
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摘要】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奏谳书》,是研究西汉建国肇始期刑事制度的珍贵文献。
本文从《奏谳书》的案例文本出发,对西汉初年的刑事司法的定罪量刑程序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西汉初年《具律》规范在定罪量刑程序中的功能进行分析。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秦汉律本文探讨《奏谳书》案例文本中起定罪量刑作用的公文书,因为定罪量刑诸多程序的核心是“当”程序,因此“当”程序是本文的重点。
关于“当”字在《奏谳书》文本的含义,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当”的解释是引《汉书·刑法志》的颜师古注:“当谓处断也。
”处断其实就是定罪量刑的意思,而“当”在定罪量刑程序的具体的特定功能在此注解中并未涉及。
本文认为是“当”就是对应之意,“当”程序就是办案官吏将罪人的罪行对应律条的规定,“当”程序在当时的刑事诉讼中,建构了从犯罪事实到法律规范的桥梁。
一、《奏谳书》的“议”、“当”程序步骤分析《奏谳书》的定罪量刑的诸多相关程序,都是在“鞠”程序也就是确认罪人的犯罪行为之后得以进行的。
本文先从《奏谳书》的案例文本出发,摘取文本的“鞠”文书之后的与定罪量刑程序联系最紧密的“议”、“当”文书,制成表格,以供进一步探讨。
表1 《奏谳书》“议”、“当”文书内容分析表1注:释文根据《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的释文,为繁体字版。
表格内字体加粗部分,为罪名和刑罚。
上表已经将《奏谳书》的跟定罪量刑有关的“议”、“当”文书内容的相关案例文本都收录了。
从以上的表格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归纳总结《奏谳书》诸案例文本的定罪量刑程序,一共分四个步骤。
第一步,整理案情和抄录律令。
这一步骤是定罪量刑的准备工作。
整理案情,就是将“鞠”文书进行编辑整理,抄录下来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
抄录律令,抄录案例相关的诸律令的条文。
我们可以看到,在《奏谳书》的部分案例中,全文抄录了相关的律令条文。
而在另一部分案例文本中,则没有了抄录律令条文文字的内容。
本文推测没有抄录的原因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省略。
第二步,“议”。
前一步骤已经准备好了案情和律令。
于是负责定罪量刑的诸吏从案例事实和法律规定两方面分别出发,用逻辑推理构建罪行与法条之间的桥梁。
直到诸吏形成统一的结论,也就是犯罪行为能够对应律令条文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议”文书。
“议”这一步骤侧重于构建案情和规则之间桥梁的过程。
第三步,初步“当”。
根据“议”文书形成的结论,按照固定的格式,开始写作“当”文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指出罪人触犯的律条,并写出律条已经明文规定的该罪名刑罚。
第四步,在初步的罪行“当”律令的基础上,办案的吏根据罪人的爵位官秩等特权身份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的情况,找到《具律》篇的相应规定,在初步“当”确定的刑罚基础上依《具律》明规定进行加减刑罚,典型例子是《奏谳书》案例四,表1已述及。
因此《具律》的典型条文是“某身份人或某特殊情况,有罪当某刑罚时,如何加减刑罚。
”《具律》的“当”即是第三步的“当”。
将这一根据《具律》而最终确立的刑罚,整理到“当”文书。
形成最终的“当”,这也就是“决狱”和“断狱”的完成。
《奏谳书》部分案例在郡级出现了“吏议”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定罪意见的情况,也就是议而不决。
这样不同的定罪量刑意见各自写作“议当”文书,上谳廷尉。
引律令、对应律令规定罪名、对应刑罚,都是定罪量刑程序要完成的任务。
由于秦汉律的罪名与刑罚,同一罪名,相应的刑罚用当代的术语描述就是“绝对确定法定刑”。
当时的司法官吏没有被赋予类似于当代法官在法定刑区间内裁量刑罚轻重的空间,官吏将罪人行为对应罪名后,就只得对罪行给出律令条文明文规定的刑罚。
于是可以说,《奏谳书》所记录的当罪名就是当刑罚。
所以说《奏谳书》案例文本可以只记录当罪名或当刑罚,而不必同时给出这两个内容。
关于对应了律令条文就等同于对应了具体刑罚的论点,我们可以看我们文献中的例证。
《汉书·张冯汲郑传》记载张释之奏当故事:“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釋之治問。
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
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所與天子公共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颜师古注:“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据上述分析的《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可推理张以《乙令》规定“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这一令条,对应罪人的行为,然后张对罪人的刑罚意见就只能是给出该条明文规定的罚金。
汉文帝认为过轻,然而加重刑罚必然违反法律规定。
因此张释之坚持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并表述了关于不可破坏法律之“信”的道理。
《奏谳书》案例四的例子可以说明根据《具律》加减刑罚的程序。
我们在此通过推理而还原案例四的定罪量刑过程。
在此仅取第一步骤的准备工作,案情整理如案例四的“鞠”文书,而抄录律令则是《亡律》的相关律条,也就是“娶亡人為妻”这个罪名,我们可以在《二年律令·亡律》的第一六八简看到这一罪名的规定:“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及所取,为媒者,智其请,皆黥以为城旦舂。
……(二年j168)”在以上案情和律条的基础上,吏展开了“议”的“当”,最终诸吏有一派认为罪人解的犯罪行为对应律条的规定,适用“黥以为城旦舂”的刑罚。
在这初步的对应刑罚以后,这一派吏在写作“当”文书的时候,结合已经查明的“解故黥劓”的情况,引用了相关的《具律》规定,我们可以在《二年律令·具律》的第八八简看到:“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
……(二年j88)”也就是《具律》这条规定,有犯罪行为已经初步对应律条而得出适用“黥”的刑罚,以前接受过劓刑的处以“斩左止”,因此对已初步当为“黥以为城旦舂”刑罚的解,吏根据其“故黥劓”的情况,最终确定了“斬左止為城旦”的刑罚。
以上推论就能解释这一派议当意见最后的文本:“·或曰:符雖已(j33)詐書名數,實亡人也。
解雖不知其情,當以娶亡人為妻論,斬左止為城旦。
”也就是对应的罪名“娶亡人為妻”,到刑罚“斬左止為城旦”,两者中间有一个根据《具律》规定加重罪人刑罚的规定。
二、《具律》诸规定在定罪量刑程序中所起的功能在《奏谳书》诸案例的定罪量刑程序中,作为成文律令体系特殊部分的《具律》诸规定在技术层面起了特定的作用。
如前所述,《奏谳书》的定罪量刑程序,在初步将罪人行为对应律条规定的刑罚后,在罪人具有特殊身份或者案例存在特定情况之时,有一个根据《具律》特定规定来对刑罚进行加减的程序。
在这一程序完结后,《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才最终确定了对罪人的量刑结论。
同样是将律令条文引用于案例的定罪量刑程序,如前述的案例四,运用《亡律》的罪名对应刑罚的规定,与运用《具律》的罪人身份如何加减刑罚的规定,这两者的运用是在定罪量刑的不同步骤,因此可以说这两类律条具有不同的功能,而这两位条文的结构也是不同的。
《亡律》、《贼律》等规定具体罪名的刑罚的条文,固定格式是“某行为者,处某刑罚”。
而《具律》规定罪人特殊身份加减刑罚的规定,固定格式为“某身份人,当某刑罚,如何加减此刑罚。
”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
(二年j82)”这个“当”字就是前文归纳的初步“当”,表示定罪量刑程序已经完成了前述的第三步骤,也就是初步的对应刑罚已经完成。
《具律》的这些规定,功能就发挥于已经初步对应刑罚后。
《具律》的这一功能,可见《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也就是《具律》的功能在于“具其加减”,当然是在其他五篇的具体罪名规定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们查阅《二年律令》的《具律》,会发现整理小组确定的《具律》的诸多条文,除了“具其加减”的一类条文,同时存在相当多的条文是对具体罪名的规定。
这就对上述的《具律》规范的功能界定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关于张家山整理小组确立的《具律》内容,李均明、王伟和彭浩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具律》拆分,将其部分条文整理进其他律篇如《囚律》或《告律》里。
李均明的论点从秦汉律篇的沿革出发,《唐律疏义》记载《法经》有《囚法》一篇,而西汉武帝以后时期的敦煌悬泉置汉简和居延新简出现明文书写的“囚律”字样,《晋书·刑法志》记载的《魏律序》讲述从汉律到曹魏律的变化,明文提到当时也就是东汉末年汉律存在的《囚律》一篇及其相关内容,因此李均明认为,年代在《法经》和悬泉置汉简之间的西汉初年必定存在《囚律》一篇,在《二年律令》中也有《囚律》的内容,因此李主张拆分整理小组确定的《具律》篇。
另外,李从出土状况考察,认为整理小组确立的《具律》内容“中间尚间隔其他内容的简”[1]。
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同样从律篇沿革和出土状况两方面论述了从《具律》中分出《囚律》的观点[2]。
彭浩认可了李均明等学者的观点,并进一步逐条梳理《二年律令》的内容,将原整理小组确定的《具律》和《告律》分成《告律》、《囚律》和《具律》,并给出对应的具体简号[3]。
本文是从《具律》条款在《奏谳书》定罪量刑程序中的功能来探讨《具律》的拆分问题。
可以发现,彭浩集大成的“《具律》应该拆分说”,正是将具备“具其加减”功能的律条留在了《具律》篇,而把可以考订为《囚律》等篇目的条文拆分出《具律》。
这样,本文能够从《奏谳书》研究的角度为“《具律》应该拆分说”提供支持,而这一说的成果也支撑了本文的观点。
正因为《具律》在定罪量刑的初步当刑罚之后发挥功能,所以其在《法经》六篇的位置位于最后,而规定具体罪名的五篇在其之前。
从技术层面看,定罪量刑的前几个步骤需要查阅引用规定具体罪名的律篇目,因此这五篇在具律前是有技术层面的考虑。
但到了后世,《具律》位于律篇最后的技术考虑逐渐为人忽略乃至遗忘,其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固定在律的最后一篇,因此《晋书·刑法志》记载的《魏律序》会说:“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
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中国古代法典开始了总则性篇章位于首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