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十的小说与电影 PPT
- 格式:ppt
- 大小:1.25 MB
- 文档页数: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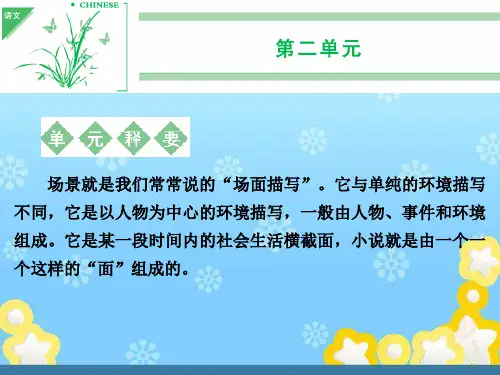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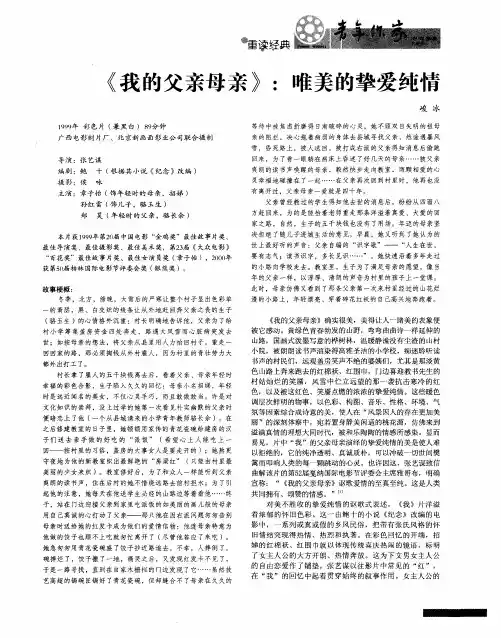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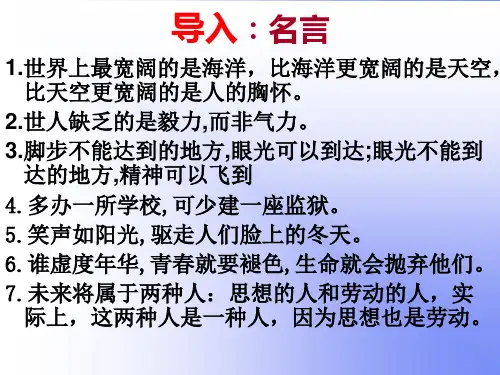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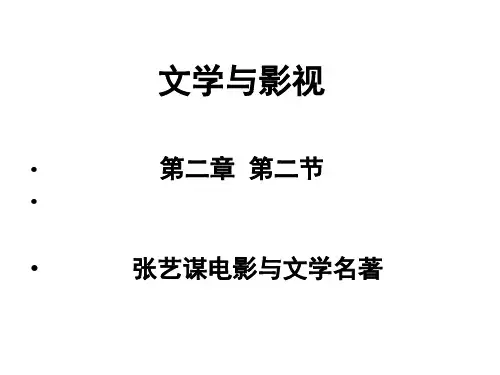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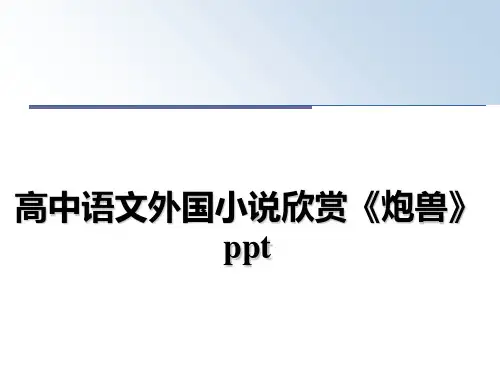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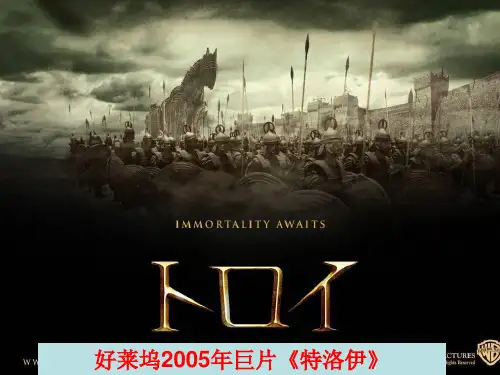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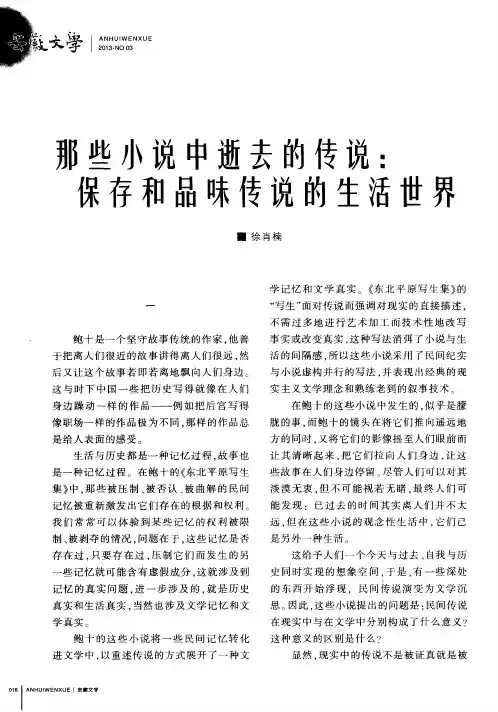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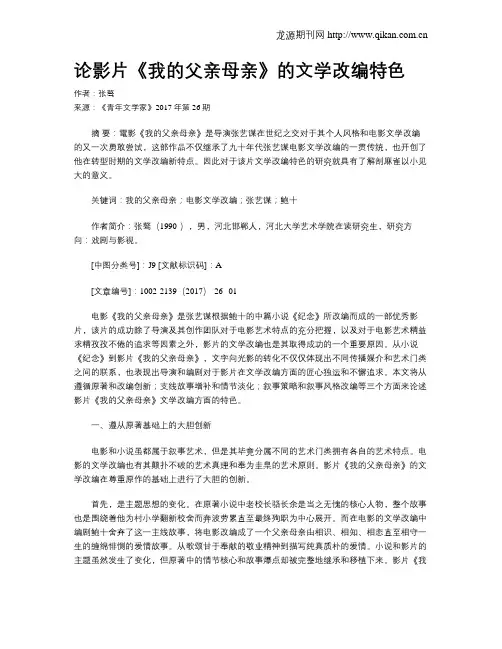
论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文学改编特色作者:张骜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6期摘要:電影《我的父亲母亲》是导演张艺谋在世纪之交对于其个人风格和电影文学改编的又一次勇敢尝试,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九十年代张艺谋电影文学改编的一贯传统,也开创了他在转型时期的文学改编新特点。
因此对于该片文学改编特色的研究就具有了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的意义。
关键词:我的父亲母亲;电影文学改编;张艺谋;鲍十作者简介:张骜(1990-),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1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根据鲍十的中篇小说《纪念》所改编而成的一部优秀影片,该片的成功除了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对于电影艺术特点的充分把握,以及对于电影艺术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追求等因素之外,影片的文学改编也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小说《纪念》到影片《我的父亲母亲》,文字向光影的转化不仅仅体现出不同传播媒介和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也表现出导演和编剧对于影片在文学改编方面的匠心独运和不懈追求。
本文将从遵循原著和改编创新;支线故事增补和情节淡化;叙事策略和叙事风格改编等三个方面来论述影片《我的父亲母亲》文学改编方面的特色。
一、遵从原著基础上的大胆创新电影和小说虽都属于叙事艺术,但是其毕竟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拥有各自的艺术特点。
电影的文学改编也有其颠扑不破的艺术真理和奉为圭臬的艺术原则。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文学改编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首先,是主题思想的变化。
在原著小说中老校长骆长余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整个故事也是围绕着他为村小学翻新校舍而奔波劳累直至最终殉职为中心展开。
而在电影的文学改编中编剧鲍十舍弃了这一主线故事,将电影改编成了一个父亲母亲由相识、相知、相恋直至相守一生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从歌颂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到描写纯真质朴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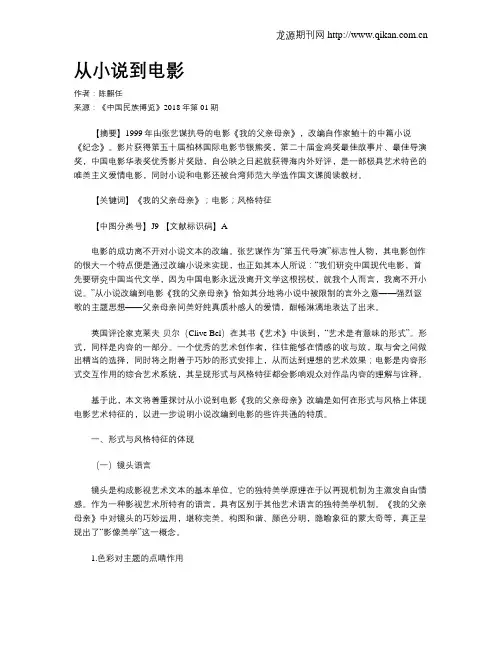
从小说到电影作者:陈麒任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第01期【摘要】1999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作家鲍十的中篇小说《纪念》。
影片获得第五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第二十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影片奖励,自公映之日起就获得海内外好评,是一部极具艺术特色的唯美主义爱情电影,同时小说和电影还被台湾师范大学选作国文课阅读教材。
【关键词】《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风格特征【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对小说文本的改编。
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标志性人物,其电影创作的很大一个特点便是通过改编小说来实现,也正如其本人所说:“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
”从小说改编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恰如其分地将小说中被限制的言外之意——强烈讴歌的主题思想——父亲母亲间美好纯真质朴感人的爱情,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
英国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在其书《艺术》中谈到,“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同样是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优秀的艺术创作者,往往能够在情感的收与放,取与舍之间做出精当的选择,同时将之附着于巧妙的形式安排上,从而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电影是内容形式交互作用的综合艺术系统,其呈现形式与风格特征都会影响观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与诠释。
基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从小说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改编是如何在形式与风格上体现电影艺术特征的,以进一步说明小说改编到电影的些许共通的特质。
一、形式与风格特征的体现(一)镜头语言镜头是构成影视艺术文本的基本单位。
它的独特美学原理在于以再现机制为主激发自由情感。
作为一种影视艺术所特有的语言,具有区别于其他艺术语言的独特美学机制。
《我的父亲母亲》中对镜头的巧妙运用,堪称完美。
构图和谐、颜色分明,隐喻象征的蒙太奇等,真正呈现出了“影像美学”这一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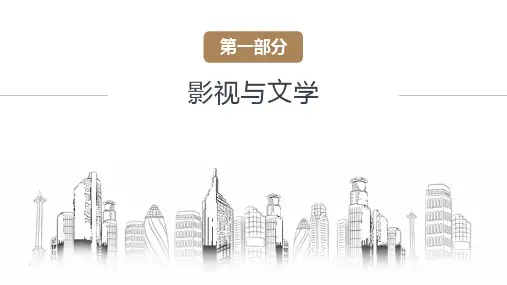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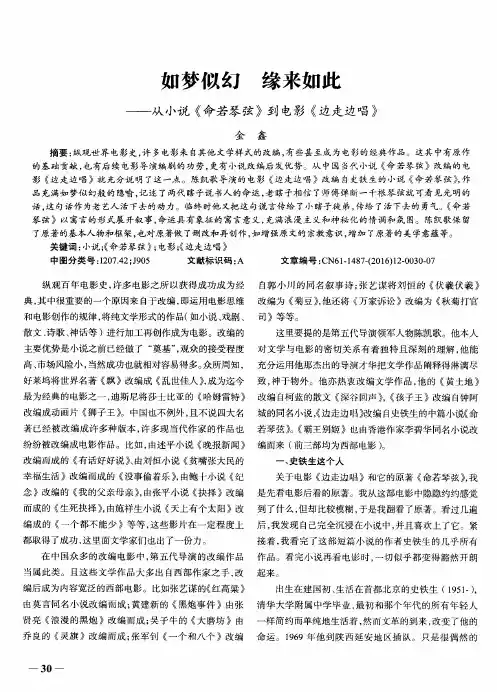
《喊·山》:从小说到电影的三重审美转换作者:陈群来源:《电影评介》2017年第24期文学与电影审美方式不同,决定了两者审美接受途径的差异。
与电影相比,文学散发出“精英化”的气息,是作者个人理想的文本化结晶,相对缺乏直观性。
与之相反,电影在通过具体场景的设置、人物“塑形”的同时,还必须根据具体直观的表现方式对故事框架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才能最终呈现为画面。
电影《喊·山》改编自山西著名女作家葛水平的小说《喊山》,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集编导于一身的杨子是忠实于原著的,它保留了小说中绝大部分内容,包括最为重要的悬疑、人物冲突等情节。
但从本质上看,电影和小说属于差异显著的两种传播方式,因此电影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自身的特征对小说进行“适当”审美转换。
一、从“女权”到爱情的叙事主题小说《喊山》的叙事中心是女权主义。
哑巴和其他人的关系是辐射式的,韩冲和其他人一样,是驱赶、包围哑巴的角色之一。
而《喊·山》从观众的普遍观念出发,淡化了女权主义色彩,同时考虑到电影的一贯表现方式,让韩冲和哑巴红霞同时成为中心角色,以两人的爱情为主要叙事线索。
在小说中,叙事最后揭露的是哑巴不哑,哑巴从哑到承认自己会说话统领所有故事情节,连韩冲也是在被关起来以后,他的父亲告诉他哑巴不哑这个事实真相的。
哑巴在腊宏的威逼之下失去“话语”,同时也意味着她失去了作为女人所应有的“权力”。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曾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
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
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我们看到三种禁律的运作,它们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
”[1]葛水平正是希望有更多的“哑巴”能够走出卑微的生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有“权力”的人。
分析小说《纪念》和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纪念》是广州平民作家鲍十上世纪 90 年代在东北时创作的中篇小说。
《我的父亲母亲》则是张艺谋 1999 年根据《纪念》改编的电影。
作为文字叙事艺术的小说《纪念》,与作为影像叙事艺术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在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上。
一、人物故事: 父亲和母亲小说主要人物是父亲骆长余,叙述父亲在三合屯当了四十多年小学教师和校长的经历。
他22 岁那年,乘坐一辆马车来到村里做小学老师,与18 岁的母亲( 招娣) 喜结连理,从此落地生根,四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村里的教育上,教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60 岁,他还在为学校盖新校舍殚精竭虑,四处奔波筹集资金,不料在到镇上买木材的归途中,遭遇大雨浇淋,诱发心脏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在昏迷中溘然去世。
村里的老老少少怀着悲痛的心情,都来为尊敬的骆老师骆校长送行。
小说重点反映父亲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穿插描写了父母之间经久不减的醇厚感情,讲述了父亲母亲朴实无华的爱情故事,以及父亲母亲与儿子我的深厚感情。
小说《纪念》曾经被作者鲍十收录在其自选集《葵花开放的声音》里出版,与集子里的许多部作品一样,它写的是故里乡亲的人生故事,情节内容简单,然而却像一幅简约的水墨画,隽永动人,人们能够从中读清水痕的泼度,墨影的深邃,以及那泼度和深邃后边隐含的温情与悲悯。
电影主要人物是母亲招娣,着重表现年轻母亲美丽纯朴,敢于打破传统观念,挣脱旧式束缚,追求自由恋爱,对爱情的执着,以及恋爱中期待与渴盼的刻骨铭心。
影片故事内容简单,一是现实部分的奔丧、抬棺二是回忆部分的看先生送公饭织红打水、反复的田野奔跑和半路等待。
其实,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纪念》没有着力刻画母亲招弟这位人物,没有关于青年母亲和青年父亲谈恋爱的描写。
导演在忠实于原著主题、充分尊重小说作者创作意图的基础上,没有拘泥于小说原著,不是对小说的原样复制,而是基于对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根据自己的创作理念、表达需求和艺术表现手段,对原著进行全新的诠释,进行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