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汉学家江沙维
- 格式:ppt
- 大小:419.50 KB
- 文档页数: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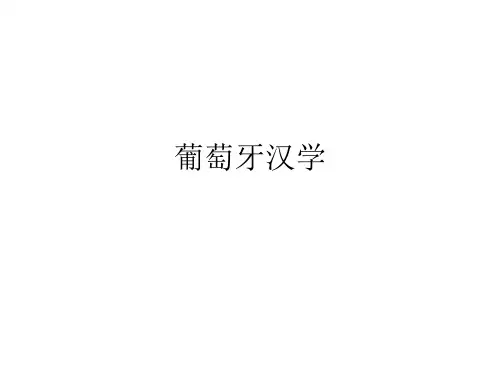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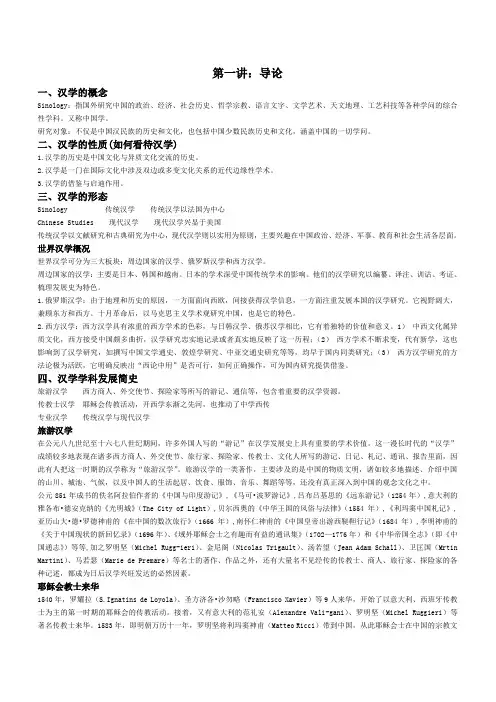
第一讲:导论一、汉学的概念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
二、汉学的性质(如何看待汉学)1.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
2.汉学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变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学术。
3.汉学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三、汉学的形态Sinology 传统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Chinese Studies 现代汉学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传统汉学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现代汉学则以实用为原则,主要兴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层面。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
日本的学术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
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1.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
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
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2.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四、汉学学科发展简史旅游汉学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探险家等所写的游记、通信等,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
传教士汉学耶稣会传教活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专业汉学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旅游汉学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许多外国人写的“游记”在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介绍(一)[大全]](https://uimg.taocdn.com/548dd3c785254b35eefdc8d376eeaeaad1f316c8.webp)
中国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介绍(一)中国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介绍(一)编者按: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老一辈无党派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开辟"人物春秋"栏目,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敬请关注。
郭沫若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早年就学于嘉定高等小学、嘉定中学堂、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
童年时便开始广泛接触文学作品。
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
阅读了泰戈尔、歌德、席勒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受到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和同学组织夏社,开始初期的文学活动。
1921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
同年出版诗集《女神》。
1923年大学毕业回国后,参加《创造周报》、《洪水》的编辑工作,并出版诗集《星空》等。
1924年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
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不久,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27年3月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
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媚日反共政策,激励人民的斗志。
1948年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抵达北平(今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并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早期欧洲汉学[中国文化研究]](https://uimg.taocdn.com/b1456885680203d8ce2f24aa.webp)
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早期欧洲汉学(Jean-François Foucquet,S.J. and the Beginning of Sinology in Europe)南开大学历史系吴莉苇谈到17、18世纪在华传教士对萌芽期欧洲汉学的贡献,通常从这几个指标衡量:传教士本人的中文造诣和有关中国之研究成果的价值,传教士在欧洲传播普及中国知识的程度,传教士与早期欧洲汉学家的来往。
然而照此看来,本文的主人公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在哪方面都只是个边缘人物,尽管他的中文造诣足以使他成为耶稣会士的翘楚,但他数量不菲的著述绝大多数不曾公开,即使公开也难以获得很高评价,这都是因为他佩有一个醒目的身份标志——“索隐派”1,他终身执着的此种立场被致力于顺应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目为异端,也被18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学者视为荒谬,于是不仅导致耶稣会对其作品的封杀,甚至也影响他不能更为积极地参与欧洲汉学的奠基。
但不管怎么说,他算是“耶稣会士汉学家”这个整体中的一员,他在汉学发展史上依然留下了不应被遗忘的踪迹。
传播中文图书傅圣泽在中国22年(1699-1721),可谓博览群籍,儒、道、诸子,古代经典,近人注疏,都有涉猎,对此笔者已另外撰文介绍,并分析其阅读范围与索隐主义思想的关系,在此就不再赘言。
本文主要介绍傅圣泽对欧洲汉学一些直接性的贡献。
傅圣泽对欧洲汉学发展真正重大的贡献是带去数量巨大的中文书籍,而这些书籍与他后半生的命运相伴随。
1720年11月,他遵耶稣会总会长之命离开北京准备返回法国,这是对他屡次不服从传教区长上的一项惩罚,但也是他自己曾经要求的结果。
他于1721年2月赶到广州,直到年底才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起程,次年秋天抵达法国。
由于耽搁广州期间已接受传信部主教的指示去罗马陈述礼仪问题,故又在1723年6月4日到达罗马。
他因反对同僚们对礼仪问题的立场,失去耶稣会总会长的欢心而无法在耶稣会士住院容身,但又得到教皇象征性的奖励,1725年3月被封为传信部主教,一直赋闲于传信部,直至1741年3月14日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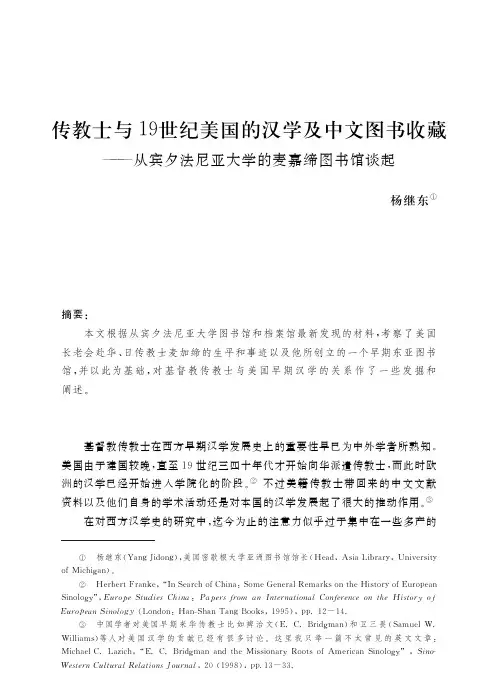
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嘉缔图书馆谈起杨继东①摘要:本文根据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最新发现的材料,考察了美国长老会赴华㊁日传教士麦加缔的生平和事迹以及他所创立的一个早期东亚图书馆,并以此为基础,对基督教传教士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关系作了一些发掘和阐述.基督教传教士在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学者所熟知.美国由于建国较晚,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向华派遣传教士,而此时欧洲的汉学已经开始进入学院化的阶段.②不过美籍传教士带回来的中文文献资料以及他们自身的学术活动还是对本国的汉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③在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中,迄今为止的注意力似乎过于集中在一些多产的①②③杨继东(Y a n g J i d o n g),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H e a d,A s i aL i b r a r y,U n i v e r s i t yo fM i c h i g a n).H e r b e r tF r a n k e, I nS e a r c h o f C h i n a:S o m eG e n e r a l R e m a r k s o n t h eH i s t o r y o f E u r o p e a n S i n o l o g y ,E u r o p eS t u d i e sC h i n a:P a p e r s f r o m a n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C o n f e r e n c eo nt h e H i s t o r y o f E u r o p e a nS i n o l o g y(L o n d o n:H a nGS h a nT a n g B o o k s,1995),p p.12-14.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比如裨治文(E.C.B r i d g m a n)和卫三畏(S a m u e l W.W i l l i a m s)等人对美国汉学的贡献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我只举一篇不太常见的英文文章: M i c h a e l C.L a z i c h, E.C.B r i d g m a na n dt h e M i s s i o n a r y R o o t so fA m e r i c a nS i n o l o g y ,S i n oGW e s t e r nC u l t u r a lR e l a t i o n sJ o u r n a l,20(1998),p p.13-33.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卷,2011年3月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主流学者身上,而对那些为数众多但学术成果相对有限的研究人员则不太重视.事实上,正是后者构成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学术界的主体,他们的集体思维方式和研究兴趣的演变也决定着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要讲述的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麦嘉缔(D i v i eB e t h u n e M cC a r t e e)就是这样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物.但是他跟许多同时代的传教士一样,对美国早期东方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对麦嘉缔产生兴趣纯属偶然.几年前,我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该馆的中文图书.宾大是美国东北部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美国东亚图书的收藏史时,很少注意到该校,因为它的东亚文献收藏量比同属常春藤联盟的哈佛大学㊁普林斯顿大学㊁哥伦比亚大学㊁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校要小得多.宾大的中国研究专业肇始于1938年,那一年该校的东方学系聘请到了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卜德(D e r k B o d d e)担任中国学教授.尽管只有三十来岁,卜德当时俨然已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颗新星,并与北京等地的政学两界保持着紧密联系.①他到达宾大以后,对该校图书馆的中文资源作了一番调查,发现馆内有若干箱中文线装书.这些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政府的捐赠.原来早在192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150周年的时候,费城曾经举办过一次世界博览会.②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即北洋政府)选送了一批国内印刷最为精致的图书参展,其中包括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首版以及清光绪年间刻«大清会典»(全套含图)等.博览会结束后,中国方面将这批书籍无偿捐赠给宾大.卜德在了解这些大套书籍的来源后,没有对图书馆里其他一些中文书籍的来源进行深究,并在此后发表的两篇①②2003年卜德去世后,其家人将他的一些私藏书籍和文物捐赠给宾大图书馆.我在整理时发现许多来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信件和礼物,其中包括黎元洪㊁冯友兰等人书写的字幅.作为美国独立运动和宪法起源地的费城总共举办过两次世界博览会,而且每次都值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上一笔.第一次是在18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举行.清政府派遣到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幼童参观了该博览会并受到格兰特总统的接见,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从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了解到此次博览会的盛况.李圭此书近年由C h a r l e sD e s n o y e r s译成英文(AJ o u r n e y t ot h eE a s t:L iG u i sA N e w A c c o u n to f a T r i p A r o u n dt h e W o r l d.A n n A r b o r:U n i v e r s i t y o fM i c h i g a nP r e s s,2004).译者在书中公布了现藏于费城公共图书馆(F r e e L i b r a r y o fP h i l a d e l p h i a)的一些清政府所送展品的照片.短文中均表示宾大的中文图书收藏起源于1926年的世界博览会.①这个结论从1939年形成以后一直维持到2007年.那年5月的一天,我在翻阅一本馆藏清嘉庆年间刻«经余必读»的时候,在扉页上发现一个藏书章,其内容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 麦嘉缔图书馆 (L i b r a r y o f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T h eM cC a r t e eL i b r a r y).由于在今天的宾大图书馆系统内没有这样一个分馆,我立刻对此章产生了兴趣,翻开书本后又在正文首页的书眉发现一行暗淡但仍可依稀辨认的手写字迹: D.B.M c C a r t e e,1869 ,这更使我感觉意义重大.在此后若干星期内,我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调查,最后终于初步复原了美国最早的东亚图书馆之一麦嘉缔图书馆的历史.作为一个在亚洲度过其鼎盛年代的人物,麦嘉缔在中国的知名度比在美国要高得多.多种研究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论著都提到过他.但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要数浙江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田力于去年完成的一篇学位论文.②此文对相关的中文材料以及在中国所能获得的英文材料搜罗得相当详尽,完整地勾画了麦嘉缔在东亚时期的主要经历.我在这里先以田文为基础,对麦氏的生平作一个简单归纳.对于田文里已经有的内容,将不再提供注解.麦嘉缔于1820年出生在美国一个基督教新教长老会(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 h u r c h)牧师的家庭.其家庭原先居住在纽约,但在麦嘉缔出生之前已经迁到费城.从英国殖民时代开始直到19世纪前半叶,费城是美国政治㊁经济㊁文化㊁教育和科学活动的中心③,长老会等教会组织的总部亦坐落于该城.1840年,麦嘉缔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④1843年10月,他作为美国长①②③④B o d d e,D e r k. O u rN e w C h i n e s eC o l l e c t i o n. T h e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L i b r a r yC h r o n i c l e,7.3-4(1939),60-65; O u rC h i n e s eC o l l e c t i o n. T h e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L i b r a r y C h r o n i c l e,12.1(1944),p p.38-43.田力:«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2日答辩通过.美国最早的银行㊁公园㊁公立学校㊁图书馆㊁剧院㊁植物园㊁动物园㊁艺术博物馆㊁医院㊁药学院㊁法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A m e r i c a n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S o c i e t y)和美国医学学会(A m e r i c a n M e d i c a l S o c i e t y)均成立于费城.参看h t t p://w w w.u s h i s t o r y.o r g/P h i l a d e l p h i a/p h i l a d e l p h i a f i r s t s.h t m l.麦氏的博士学位论文尚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与手稿部,书号为378.748P OM1840.1.8.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卷,2011年3月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老会教会派遣到中国的第一批医务传教士之一,从纽约启程坐船去中国.①在香港㊁澳门等地作短暂停留后,麦嘉缔于1844年6月抵达其传教的目的地宁波.此后三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住在中国,主要在宁波地区传教,不过足迹最远曾到达山东烟台地区.在到达中国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麦嘉缔迅速掌握了中文口语,包括官话和宁波地区的吴方言.②他是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国方言的两个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出版了数十种著作,其内容涉及宗教㊁历史㊁天文和地理.其中有些传播现代科学的著作如«平安通书»曾经对晚清思想家魏源等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③在宁波,麦嘉缔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基督教男校,该校后来发展成为之江大学.他抚养的一个早逝教友的女儿金韵梅(又名金雅妹,英文作Y a m e iK i m)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海外的女学生,20世纪初归国后对清末民初的中国医学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麦嘉缔逐渐参与了中西之间及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中.他因中文口语能力出色被在沪美国外交使团看中④,并在西人与太平天国的接触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此后他还在美国驻沪领事馆①②③④田力的论文提到了家庭影响在麦嘉缔决定投身于传教事业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美国赴华医务传教士的先驱伯驾(P e t e rP a r k e r,1804-1888)曾于1841年访问费城,宣传其在华传教的经历并征募更多的教士加入其行列.他的访问在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中造成不小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两个与中国有关宗教社团的成立,即 费城中国医务传教协会 (C h i n aM e d i c a l M i s s i o n a r y S o c i e t y o fP h i l a d e l p h i a)和 费城妇女中国协会 (L a d i e s C h i n e s e A s s o c i a t i o no fP h i l a d e l p h i a).参见P e t e r P a r k e r, R e p o r t o f t h eM e d i c a lM i s s i o n a r y S o c i e t y, T h e C h i n e s e R e p o s i t o r y,12(1843),198-199.另参见K a i y i C h e n,S e e d s f r o mt h eW e s t:S t.J o h n s M e d i c a lS c h o o l,S h a n g h a i,1880-1952(C h i c a g o:I m p r i n t P u b l i c a t i o n s,2001),p p.57-59.伯驾的访问应该对麦嘉缔产生相当影响.田文已经根据英文资料指出麦嘉缔高超的语言水平.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卷麦嘉缔去世前遗赠给母校的丝质中文卷轴,这是麦氏离开中国以前得自宁波当地的一个绅士的赠别题诗.诗中提道: 君产欧西我浙东,本来言语不相通.羡君三寸玲珑舌,为我声声操土风.中华文艺熟能详,朗诵雎逑第一章.旁及二三才子笔,闲来喜与友评量. 其下还有小注云: 君自谓好观演义三国及水浒传. 这是麦氏的中国友人对其语言能力的评价.P e t e r M.M i t c h e l l, T h e L i m i t so f R e f o r m i s m:W e i Y u a n s R e a c t i o n st o W e s t e r n I n t r u s i o n, M o d e r nA s i a nS t u d i e s,6.2(1972),200.美国在华外交使团对麦嘉缔语言能力的评价可参见E l d o n G r i f f i n,C l i p p e r sa n d C o n s u l s:A m e r i c a nC o n s u l a ra n d C o mm e r c i a lR e l a t i o n sw i t h E a s t e r n A s i a,1845-1860(A n n A r b o r:E d w a r d sB r o t h e r s,1938),p.113.里担任过副领事等职,但是最后因不喜闲杂公务而辞职.从1872年起,麦嘉缔受清廷指派,赴日本交涉遣返被扣押的玛也西船上华工事宜.事后受到日方邀请,在新式的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讲授拉丁文和自然科学.此时他原先用中文出版的«真理易知»一书早由美国长老会的著名赴日传教士赫本(J a m e sC.H e p b u r n,与麦嘉缔同样毕业于宾大医学院,以创立日文罗马字体系而著称)译成日文,成为整个东亚在19世纪最普及的基督教通俗读物.①1877年后,他往来于中日之间,并一度加入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团,担任秘书及英文翻译等职,俨然成了中国的外交官员,并且颇受何的器重.1880年,麦嘉缔从日本携家人一起回到美国.此后七年间他基本上一直在费城和纽约度过.但是到了1887年,他再一次接受长老会的委派启程前往东亚,此后12年里他基本上都在日本从事传教事业,只是在1888年短暂去过厦门.1899年8月,高龄而且患病的麦嘉缔最后一次离开东亚,坐船回美国.但是他的健康状况显然已经不允许他长途跋涉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费城.1900年7月17日,麦嘉缔在旧金山去世,终年八十岁.麦嘉缔是19世纪美国传教士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不仅在东亚度过了生命的一大半时间,而且与中日两国均建立深厚关系.他的日语能力水平可能不如中文出色②,但是应该也相当不错.至少在何如璋看来,此君 于汉和文字语言无不通晓 ③.他去世以后,立刻有人指出像他这样熟悉两个东亚国家的人在美国是前无古人的.④麦嘉缔一生的主要写作和出版活动是用中文进行的,显然他将传教所在地的民众视作自己最主要的读者和听众.但是与许多其他来华西方传教士一样,麦嘉缔始终与母国的知识界保持着联系,并向美国的机①②③④有关麦嘉缔在日本的经历,除了田力论文引用到的已经译成中文的若干日文文献外,尚可见吉田寅,«マッカーティ»(即麦嘉缔名字的日文拼写),载于«日本キリスト教歴史大事典»(東京:教文館,1988),1323页.以及同氏,«入華宣教師マッカーティーと中国語布教書»,载于«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第94期(1991年),19-29页.我作此推断的根据是麦嘉缔用中文写作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但是似乎没有用日文出版过.麦嘉缔于光绪六年(1880)离开日本以前,何如璋赠送给他一个字幅,上书 相助为理 四个字,底下还有一段文字记述了麦氏的生平和成就.此字幅现存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H e n r y W.R a n k i n, M e m o i r o fD i v i eB e t h u n eM c C a r t e e, T h eN e w E n g l a n d H i s t o r i c a l a n dG e n e a l o g i c a lR e g i s t e r,S u p p l e m e n t a r y N u m b e r(1900),x l i i-x l i i i.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卷,2011年3月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构㊁组织㊁民众和学者不断传播有关东亚的信息.下面就根据我个人所见的有关资料介绍一些情况.作为一名医学博士,麦嘉缔跟当时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对研究自然界有着浓厚兴趣,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博物学者(n a t u r a l i s t).①到达中国以后的最初几年内,对宁波地区的动植物尤其是昆虫进行研究似乎成了他最主要的业余兴趣.在传教之余,他收集和制作了大量的标本,并将它们发送回家乡的科研机构.出版于1851年的«费城自然科学院公报»提到,该院收到了麦嘉缔捐赠的216件中国昆虫标本,它们分属120个物种.②显然,这是麦嘉缔在中国最初几年的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出版于1859年的«美国地理与统计学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中也提到麦氏是该会的通讯会员③,这说明当时他对母国的自然科学界的最新动态有密切的跟踪,并积极加入合乎自己兴趣的新组织.不过作为一名传教士,麦嘉缔的主要使命是在异国他乡传播他所信仰的宗教观念.而深入了解所在国的语言㊁文化和民俗则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宗教使命感的驱动下,他的学术兴趣慢慢地从自然科学转向了人文科学尤其是东方学.有证据表明,在整个传教生涯中,麦嘉缔与美国东方学会(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始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成立于1842年的东方学会是19世纪美国研究亚洲的最重要学术团体.该学会的学报显示,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麦嘉缔就开始向该会赠送自己出版的中文书籍.④但是他积极参加该学会的学术活动似乎是60年代末的事情.1869年,麦嘉缔曾经携妻子和养女金韵梅回过一趟美国.当年10月下旬,他参加了美国东方学会①②③④N a t u r a l i s t一词在19世纪末以前被广泛用来指称研究自然界及其历史的科学家.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日益细致,这个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R e p o r t o f t h e C u r a t o r s, P r o c e e d i n g s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N a t u r a l S c i e n c e s o f P h i l a d e l p h i a,5(1850-1851),p.131.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M e m b e r s, J o u r n a l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a n d S t a t i s t i c a l S o c i e t y,1.1(1859),i i i.A d d i t i o n s t o t h eL i b r a r y a n dC a b i n e t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M a r c h,1851-A p r i l,1852, J o u r n a l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3(1853),x x v i; A d d i t i o n s t o t h eL i b r a r y a n dC a b i n e t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F e b.,1853-J u l y,1854 ,J o u r n a l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 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4(1854),v i.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 e w H a v e n)市召开的一次大会.两年后出版的学会学报里有一篇对这次年会的详细报道.①会议收到的九篇论文中,有三篇的作者是分布于亚洲各地的美国传教士,他们与来自耶鲁大学㊁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教授一起宣读论文并进行讨论.这个事实本身反映出传教士在19世纪美国的亚洲研究学界的重要地位.麦嘉缔是这三个传教士中的一个,其报告的内容摘要刊登在两年后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据此文献,麦嘉缔在会上展示了一幅郑板桥(被拼写为C h e uP a nGk i a u)于乾隆十二年(1747)所作并书的«潍县新修城隍庙碑»的拓片,然后解释了碑文的内容,并对其中反映的中国士绅阶层的宗教观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此文更接近于一篇翻译作品,而不是研究性的论文.报告结束以前,麦嘉缔还展示了一套精美的出自杭州某佛教寺院的十八罗汉石雕拓片,并将它们赠送给了东方学会.大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麦嘉缔被接受为学会的正式会员.②如前文所述,在19世纪80年代,麦嘉缔曾从东亚回国并停留数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东方学会的活动.1881年10月,学会在纽黑文召开会议.麦嘉缔本人当时在纽约,因故未能列席,但是他委托他人向学会赠送了一些日本佛教的文物,包括拓片㊁经卷和照片等,并对这些物品上的中日梵文字作了解释.③1884年,麦嘉缔出席了东方学会举办的两次大型学术会议.第一次会议于5月在波士顿(B o s t o n)市举行,麦嘉缔在会上发言,追忆刚刚去世不久的东方学会前主席㊁耶鲁大学以及整个北美地区的第一个汉学教授㊁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先驱之一卫三畏④,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与卫氏的长期交往以及从后者获得的鼓励和影响.10月,麦嘉缔又参加了东方学会在巴尔①②③④ P r o c e e d i n g a tN e w H a v e n,O c t o b e r21s ta n d22n d,1869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S o c i e t y,9(1868-1871),l x-l x i i.19世纪美国学术团体的刊物经常刊登会员名单.麦嘉缔的名字出现在东方学会学报刊登的会员名单里好几次,参看J o u r n a l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9(1868-1871),l x x;10(1872-1880),c x c i x;等等.P r o c e e d i n g sa t N e w H a v e n,O c t.26t h,1881 ,J o u r n a l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 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11(1882-1885),l x x i i.P r o c e e d i n g s a tB o s t o n,M a y7t h,1884, J o u r n a l o f t h e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S o c i e t y,11(1882-1885),c l x x x v i i i.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卷,2011年3月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的摩(B a l t i m o r e)市召开的研讨会.从后来发表的会议纪要①看,此次会议上总共收到了14篇论文,其涉及的对象从早期希腊文«圣经»到西亚楔形文字起源,从5世纪的叙利亚文文献到梵文词汇的语源问题,涵盖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极大,充分反映出当时美国东方学的初级性以及该学科的包容万象.美国研究中国西藏的先驱者柔克义(W i l l i a m W.R o c k h i l l)也参加了会议并第一次发表了他对密勒日巴«十万歌集»的研究.麦嘉缔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宣读论文«论中国和朝鲜文字的起源»(O n t h eO r i g i no f t h eC h i n e s ea n d K o r e a n W r i t i n g).相较于他在15年前的东方学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这篇报告看上去更像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原创精神,也反映出他对朝鲜文字及其历史有相当的了解.他将八卦图案解释为上古时代不成熟的记事工具,认为毛笔的广泛使用导致了楷书在中国的推广以及假名在日本的起源.他还指出在东亚三国中,只有朝鲜发明了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并对其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毫无疑问,麦嘉缔的这次的演讲尽管只留下了一篇长度不超过一页的摘要,但是在美国的东亚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之地的,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对东亚三种文字的综合比较研究.除了美国东方学会以外,在19世纪后半叶,麦嘉缔还参加过其他一些人文科学的组织.当他于19世纪70年代供职于清政府驻日使馆期间,加入了 日本亚洲协会 (A s i a t i cS o c i e t y o f J a p a n).②该学会成立于1872年,最初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英美两国在日本的外交官㊁商人和传教士.③几乎是与此同时,麦嘉缔也加入了 新英格兰历史系谱协会 (N e w E n g l a n d H i s t o r i cG e n e a l o g i c a l S o c i e t y),成为该会的海外通讯会员.④这个创办于1845年的协会是19世纪美国东北部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学和家谱学组织之一.⑤除了参加有关学会的活动并提交论文外,麦嘉缔等西方传教士对本国汉学①②③④⑤ P r o c e e d i n g sa tB a l t i m o r e,O c t o b e r29t ha n d30t h,1884, J o u r n a l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O r i e n t a lS o c i e t y,11(1882-1885),c c i i i-c c x x x i.L i s t o fm e m b e r s,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o f t h eA s i a t i cS o c i e t y o f J a p a n,8(1880),x x v.有关该协会的历史可参考其网站:h t t p://w w w.a s j a p a n.o r g.S o c i e t i e s a n d T h e i r P r o c e e d i n g s, T h e N e w E n g l a n d H i s t o r i c a l a n d G e n e a l o g i c a l R e g i s t e r,31(1877),123.详情可参见该协会网站:h t t p://w w w.n e w e n g l a n d a n c e s t o r s.o r g.研究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捐献各种研究资料,尤其是书籍.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各公私教育机构及图书馆中的零星中文收藏绝大部分来源于个人㊁团体以及外国政府的捐赠,而传教士在这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麦嘉缔也属于这些慷慨捐赠的传教士之一.本文已经提到他赠予费城自然科学院和美国东方学会的大量礼物,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捐赠显然是给予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他可能在去世以前十几年就决定要向母校的图书馆捐赠其所有的中日文藏书,而且很有可能于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他在美国居住时间就已经开始移交一部分私人藏书.根据现有的证据,宾大的麦嘉缔图书馆正式成立时间不会晚于1891年.这一年的2月,宾大总图书馆的新楼建成.在新楼启用仪式的讲话中,时任馆长已经提到了麦嘉缔图书馆.①不过麦嘉缔私人藏书的大部分显然是在他去世以后被当作遗赠(b e q u e s t)转交给宾大图书馆的.该馆的一本旧登录簿显示,1900年11月22日,也就是麦嘉缔去世4个月后,大约1000册他捐赠的中日文书籍进入了馆藏.②就这样,美国最早的东亚图书馆之一的麦嘉缔图书馆成立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图书馆独立存在的历史很短.在我的调查过程中,我没有能够找到这个图书馆正式结束的时间.但是很显然,当卜德于1938年来到宾大任教并调查该校图书馆的中文资源时,学校里已经没有人记得曾经还有个麦嘉缔图书馆.造成这个美国早期东亚图书馆神秘消失的原因实际上也很简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中日文书籍在宾大图书馆内只是一个摆设,而没有真正的读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方学相当发达,其东方学系(D e p a r t m e n t o fO r i e n t a l S t u d i e s)拥有美国东方学会的多名重量级成员以及学会学报的主要编辑.③不过该校的东方学侧重于中东和南亚地区,对于东亚则①②③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L i b r a r y,e d.P r o c e e d i n g s a t t h eO p e n i n g o f t h e L i b r a r y o f t h e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7t ho f F e b r u a r y1891.P h i l a d e l p h i a:U n i v e r s i t y o fP e n n s y l v a n i a P r e s s,1891.U n i v e r s i t y o fP e n n s y l v a n i aL i b r a r y,A c c e s s i o n s.现藏宾夕法尼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R a r e B o o k a n d M a n u s c r i p t L i b r a r y,V a n P e l tGD i e t r i c h L i b r a r y C e n t e r,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n n s y l v a n i a).李克(A l l y n R i c k e t t), A B r i e f H i s t o r y o f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o f O r i e n t a lS t u d i e sa t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P e n n s y l v a n i a. 未刊手稿,作于1980年左右.我本人曾于2007年5月27日采访现已退休的李克教授,谨在此对其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卷,2011年3月传教士与19世纪美国的汉学及中文图书收藏长期没有人关注,也没有开设过相关的课程.由于麦嘉缔图书馆的过早夭折,现在要全面复原其收藏的内容已经相当困难.尽管所有这些中日文书籍上都盖有为该馆特制的藏书章,但是它们已经分散于宾大图书馆的总馆㊁善本与手稿部㊁东亚部㊁旧书仓库㊁考古和人类学图书馆等好几个部门和分馆,而且在馆藏目录中对其来源也没有注明.我曾经花了一定时间进行搜罗,并找到若干种明末清初的版本如«老庄郭注汇解»㊁«芥子园重订本草纲目»和«尚友录»,以及若干日文旧书如«职原抄»和«王代一览».但是由于我本人于2008年离开宾大图书馆,此项工作只能暂时中断.麦嘉缔及其图书馆的故事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审视传教士与美国19世纪的汉学和中文图书收藏的关系.尽管麦嘉缔不是一个大学者,而且其思想观点带有很强烈的基督宗教因素,但他与同时期的许多来华传教士一起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传教士关心和研究的重点,如中国的语言和民众的宗教意识等,跟他们的传教事业需要密切相关,同时在塑造美国早期汉学的基本特征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19世纪的特征在今日的美国中国学中仍可以找到.麦嘉缔图书馆的历史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发是,在美国还有相当多 隐藏 的与中国有关的材料有待发掘.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尽管有不少中国书籍和其他文物通过各种途径来到美国,但是由于当时亚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以及民众对东方事物兴趣的平淡,很多珍贵的东西被埋没,直到现在仍不为专业学者所知.我在费城期间,除了麦嘉缔图书馆的旧藏以外,还发现过其他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比如现已被拆除的原费城公民中心(C i v i cC e n t e r)收藏的清政府与美国商团的往来信件,长老会教会档案馆所藏赴华传教士的报告,费城公共图书馆所藏近代中国两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与照片,美国哲学学会所藏中文书,以及位于费城北郊的赛珍珠故居里的材料,等等.在费城市内以及附近郊区的各种古董店里,19世纪来自中国的文物也比比皆是.可以想见,今后对这类材料的不断发掘,将为对中国文献在海外的流传以及早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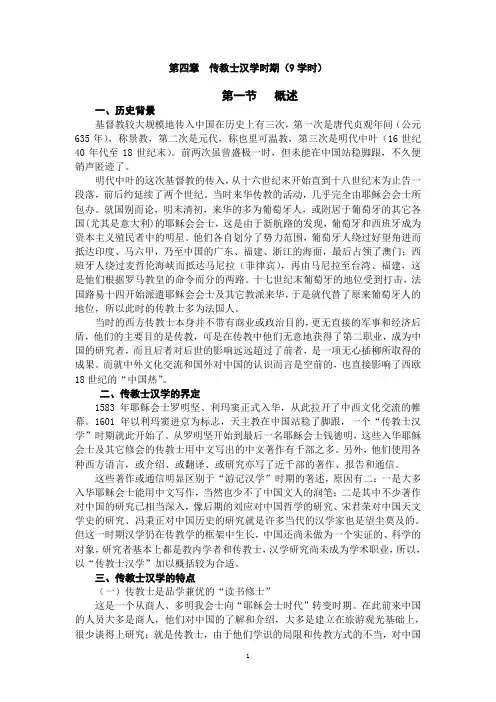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第一节概述一、历史背景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
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
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
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
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
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
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
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
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
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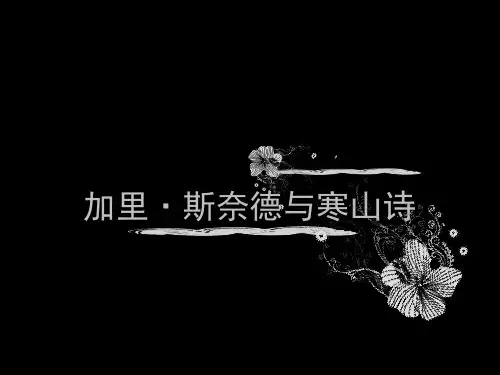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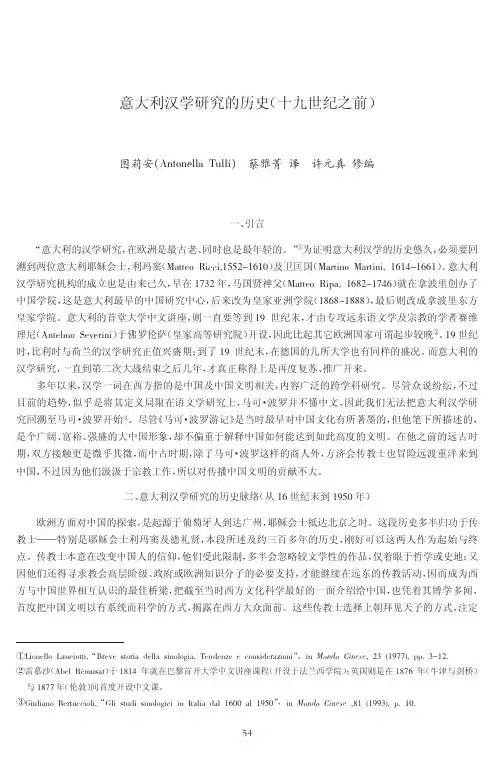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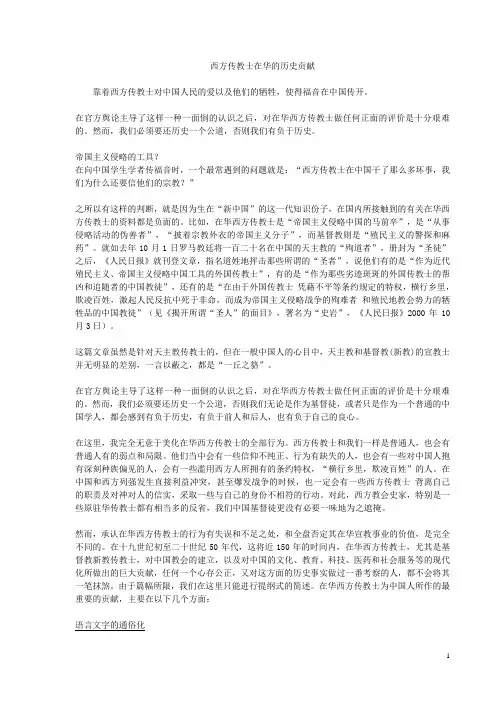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
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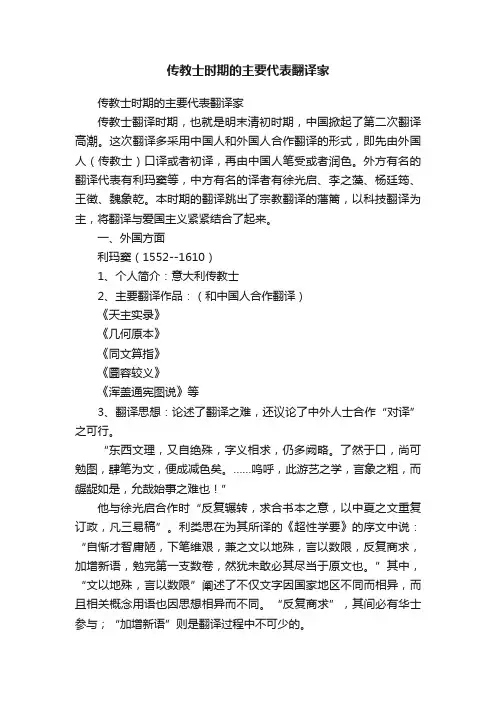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翻译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
这次翻译多采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翻译的形式,即先由外国人(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笔受或者润色。
外方有名的翻译代表有利玛窦等,中方有名的译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魏象乾。
本时期的翻译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以科技翻译为主,将翻译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一、外国方面利玛窦(1552--1610)1、个人简介:意大利传教士2、主要翻译作品:(和中国人合作翻译)《天主实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3、翻译思想:论述了翻译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减色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龌龊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为其所译的《超性学要》的序文中说:“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其中,“文以地殊,言以数限”阐述了不仅文字因国家地区不同而相异,而且相关概念用语也因思想相异而不同。
“反复商求”,其间必有华士参与;“加增新语”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少的。
二、中国方面徐光启(1562--1633)1、个人简介: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翻译家,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2、主要翻译作品:《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3、翻译思想: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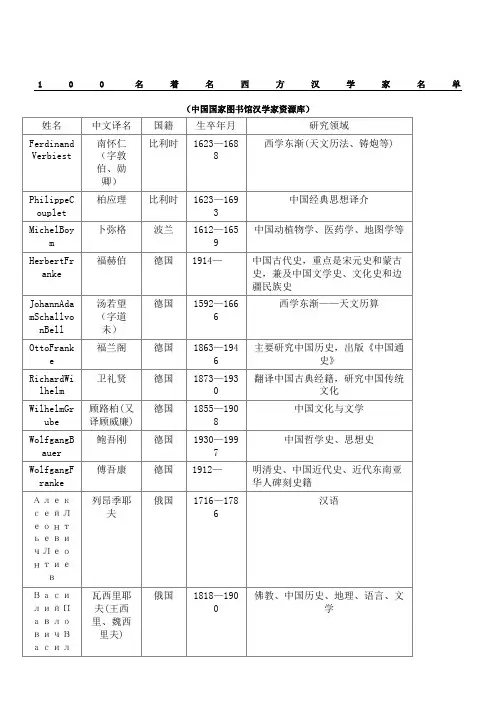
第9卷第3期南阳理工学院学报V o l .9N o .32017年5月J O U R N A L O F N A N Y A N G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E C H N O L O G Y M a y.2017作者简介:何永涛(1992-),男,硕士生,研究方向:近代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㊂E -m a i l :792237299@q q.c o m 浅析晚清南阳教案何永涛(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摘 要:1861年,外国传教士依靠传教特权,企图霸占南阳城内的江浙会馆,由此引发南阳还堂案㊂教案发生后,法国传教士倚仗驻京法使,捏造伪证,肆意妄为地采取多种策略企图夺占江浙会馆㊂地方官碍于上司命令,不得不委曲求全,在传教士㊁绅民和上司间寻找平衡,处境极为尴尬㊂士绅在反洋教斗争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与官民保持着复杂关系㊂民众受谣言鼓动或是出于宣泄报复,坚决反对洋教进城㊂研究南阳教案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教关系和官员在对外交涉中的困境,更能透射出南阳近代的社会变动㊂关键词:晚清;南阳;教案;传教士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132(2017)03-0125-04一 教案缘起近代以降,条约制度在中国逐步确立,一些传教士根据不平等条约赋予的传教特权,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引起无数教案㊂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通商口岸和内地解除教禁㊁发还教产㊁租地设堂等一系列特权㊂1858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其第八款规定: 凡大法国人欲至内地及船只不准进入之埠头游行,皆准前往,然务必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领中㊁法合写盖印执照,其执照上仍应有中华地方官钤印以为凭㊂ [1]105此款条约确立了法国在在华天主教势力中的代理人身份,为法国日后的教案交涉提供了条约依据㊂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 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㊁学堂㊁坟茔㊁田土㊁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㊂ [1]147从此传教士索还旧址 之风横扫各省,引发多起还堂案,南阳教案便是其中之一㊂1861年,靳岗意大利籍传教士安恩理格见南阳城内江浙会馆富丽堂皇,便想据为己有,以此为据点,作为在南阳地区发展天主教势力的前沿阵地㊂安恩理格向法国公使哥士耆谎称江浙会馆所在地为康熙年间天主教所建教堂旧址,企图以条约特权强行夺取江浙会馆㊂ 每一次教案的出现,教民的后面总是站着牧师㊁神甫和教堂,牧师和神甫们的后面站着外国公使和领事,外交官的后面再站着各自的殖民政府和巨舰重炮,外交官压迫和讹诈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和官吏,政府和官吏则以 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为词,转手出卖祖国权益,杀国人以媚洋人㊂ [2]外国传教士依靠条约特权及其背后的强权政治,采取各种方式强取豪夺江浙会馆,最终导致南阳教案的爆发,其持续时间长达35年之久㊂因此,南阳教案成为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教案㊂二 南阳教案中的利益群体南阳教案交涉期间,传教士㊁封建官绅㊁普通民众等涉案利益群体,从自身的利益及立场出发,采取各种形式相互斗争,三者间形成了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㊂(一)传教士纵观南阳教案交涉的过程,法国传教士为夺取江浙会馆无所不用其极,捏造证据,进京向法国公使进言,企图施压清政府夺取江浙会馆㊂在教案交涉过程中,南阳地方传教士与法国驻华公使沆瀣一气,采取各种策略夺取江浙会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㊂第一,无中生有,肆意捏造㊂传教士要求还堂的所谓 证据 主要有两个: 一,教士指出,据年老住户讲:南阳府城内天主堂改为捕署,复经徐县令卖于春源等字号,建成江浙会馆,故要求将其归还给外国教士;二,意大利传教士安西满在 节略 中声称:据 西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第9卷史 记载,康熙五年,外国传教士曾在南阳活动,雍正2年,因清廷禁教,外国施姓教士丢下南阳城内的教堂逃走,该堂被改为捕署,后道光十三年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春源等字号,改作江浙会馆,并有碑记和西洋圣物为凭㊂ [3]传教士所说的证据纯属子虚乌有,是其为霸占江浙会馆捏造的伪证㊂据学者赵树好研究,江浙会馆完全是江浙绅商所建,和传教士毫无关系㊂[4]经南阳地方官员走访,年老住户从未听说江浙会馆为天主教堂旧址㊂因此,南阳府官员拒绝了法国传教士的还堂要求㊂但是,法国传教士并未因此而罢休,仍通过各种方式企图霸占江浙会馆㊂第二,图谋在城内置产设堂㊂1866年9月,为进入南阳城内传教,舞阳教徒刘清波唆使周宗耀将其南阳城内房产卖给传教士贺安德,但未报官交税㊂此前,南阳县民周宗耀早已将地产卖给举人曹学彬,并已立契约㊁报官交税,符合法定程序㊂1865年, 中法议定章程 规定: 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约内写明 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人姓名)卖与本处天主堂公 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以明仍系中国土地 嗣后卖业之人,须令於未卖之先,报明该处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不得径将己业私行卖给,如有私卖者,立加惩处㊂ [1]227因此,周宗耀将其地产卖给传教士的行为完全是非法的㊁无效的㊂1867年9月,清政府按照 中法议定章程 判定房产归先买之人曹学彬,宣布贺安德的买房契约作废㊂然而,法国传教士并不死心,通过拒交非法房契的无赖手段,阻碍置产风波的解决㊂为了置产风波的彻底解决,河南巡抚李鹤年建议总理衙门,将靳岗地区借给南阳天主教㊂这一建议得到南阳地区法国传教士的积极响应,因此,置产风波至此结束㊂得到靳岗的天主教会立刻建起高大教堂,进一步对南阳地区进行宗教扩张㊂第三,拉拢人心,反复无常㊂1863年,法国公使请求将南阳城内的废旧县衙及其旁边的老盐店转让给传教士,以筹资建堂㊂此要求遭到南阳地方官员的拒绝㊂1878年,南阳地区发生旱灾,颗粒无收㊂在宛天主教势力趁机赈济灾民并收养了300多名婴儿,以此来笼络人心,以便进城夺取土地,但未奏效㊂为达到进城传教的目的,1879年2月,法国天主教进一步要求南阳府官员允许其在南阳城内购置土地,建造天主教堂㊂由于南阳地区士绅及民众的反对,官府不敢贸然答应此要求㊂置产风波中,传教士安西满答应归还周氏地产并保证不再要求进城传教,据此,总理衙门照会驻华法国公使称南阳教案已结案㊂7月,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安西满并未答应不再进城传教㊂法国传教士的出尔反尔,使南阳教案的交涉旷日持久㊂第四,干涉地方政务㊂在不平等的条约制度下,外国传教士可以通过一系列特权干预中国的地方政务,如果地方官与其抗衡,便会被罢官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因长时间不能 索回 江浙会馆和达到进城传教的目的,传教士便迁怒于南阳府的官员㊂法国传教士向驻京法国公使报告称,因南阳地方官员从中作梗,才导致江浙会馆迟迟不能 索回 ,请求将南阳知府张仙保㊁委员袁铣撤职㊂在驻京法国公使的胁迫下,清政府被迫将袁张两人撤职㊁调任㊂此后,继任的南阳地方官只能帮助传教士夺取江浙会馆,不敢忤逆传教士的旨意㊂因此,此案也使得南阳府官员的权威受损㊂法国天主教谎称江浙会馆为天主教堂旧址,出尔反尔,企图夺取江浙会馆,但遭到南阳府官员及绅民的反对,未能得逞㊂法国传教士又企图购买周氏地产在城内设堂传教,仍未达到目的,便迁怒于南阳府官员㊂为了南阳教案的及时解决,南阳地方官员将靳岗地区让给传教士,让其建堂㊂(二)封建官绅官绅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上,有一定的功名资历;经济上,与封建土地制度联系密切;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威望,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和号召力㊂但官与绅又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他们两者在反洋教斗争中既合作又斗争㊂晚清官绅民一体反教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士绅的制衡作用,官员必须依靠地方士绅去鼓动民众反教㊂ [5]89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官绅对传教士的 还堂 要求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和抵制,但在与传教士的交涉中,地方官和士绅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㊂晚清地方外交机构分为两类:其一,直属于中央的五口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大臣);其二,各地的督抚和将军㊂地方当局官员无对外交涉的权力却需直接同外来传教士交涉,身处传教士㊁绅民㊁上司三方之间,处境为难㊂蛮横的外国传教士依靠条约赋予的特权和驻华公使的保护,肆意妄为;南阳绅民因传教士的强盗行径激愤不已,导致南阳地方官处于为难境地㊂南阳教案的交涉过程就是地方官由抗争,进而妥协,最后到屈从的过程㊂南阳城内老住户从未听说江浙会馆为天主教旧址,南阳府官员依据事实,拒绝了传教士的非法要求㊂1866年,南阳知府张仙保迫于上司压力,劝江浙商人交出会馆㊂张知府的委曲求全导致南阳城内 群情汹汹 ,绅民同仇敌忾,声言欲杀尽传教士㊂贺㊃621㊃第3期何永涛:浅析晚清南阳教案安德等人 趁夜移避乡村,数日不出 [6]463㊂1867年2月,清政府勒限南阳知府 务于一月内妥议结案,或给江浙会馆,或另外择地赔给,以资信守,否则,即将其严行揭参 [6]463㊂但是,因南阳绅民坚拒洋教入城,南阳府县官员不知所措㊂7月14日,知府张仙保以 令地方紧要公事,未能办理妥速 而被撤任[6]485㊂1867年11月,河南南汝光(南阳㊁汝南㊁光州)道蒯贺荪受命处理南阳还堂案㊂在与法国传教士交涉时,蒯贺荪指出江浙会馆不是教堂旧址,因此实难应许㊂然而,传教士执意索取江浙会馆,蒯氏进而劝说绅商让出会馆,绅商誓死不从,还堂案一时难以解决㊂地方官处理教案的心情和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从文献资料几乎看不出官吏对传教士的偏袒,即使有也是出于对自己的官位的保护㊂南阳府官员处于传教士和绅民之间,位置尴尬,处理南阳教案的难度可想而知㊂士绅集团最显著的特征是亦官亦民,在朝为官,在籍为民,双重角色赋予士绅在近代教案中具有特殊的能量和作用[5]64㊂士绅反教的原因已有研究,本文不再赘述,笔者着重探讨南阳士绅在教案交涉中的策略和作用㊂南阳教案交涉多由士绅所主持,即使是驱逐教士或杀戮教士,拆毁㊁焚烧教堂及教民住宅,也多半出于他们的影响或支持㊂第一,南阳士绅据理力争㊂有士绅在南阳还堂案发生时便指出: 查南阳自开国以来并无天主教在此立堂,郡志可考而知,即职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自祖父乙递更,故老之传闻,亦并不知有天主堂者㊂ [6]517置产风波中,南阳绅民坚决反对,高树序等144名绅士联名上书,河南巡抚李鹤年认为民意不可违,担心激起民变,因此上奏总理衙门表示不能退还江浙会馆,建议将靳岗地方借给南阳天主教了结此案㊂第二,组织群众斗争,进行舆论宣传㊂1868年10月间,南阳士绅在城内向绅民散发传单时称: 风闻府㊁县官府已与本地士绅勾通,欲将江浙会馆给天主教会,我等久沐朝廷之化,素习孔孟之书,断不可信从其教,致令终身有垢,后悔无及,应互相稽查,如有入天主教者,共同驱逐㊂ [7]他们还 沿街挨门撒帖造旗,邀聚府城煌庙局,演戏设席,议定三㊁五日内,誓要寻杀逐赶天主教 [6]541㊂由于南阳地方官的镇压,这次斗争受到挫折㊂乡绅们发布的各种反教言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极大的鼓动效力㊂士绅能够扮演反教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在中国社会上的优越地位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官绅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同一性和矛盾性㊂传教士的 还堂 触动了地方官和士绅的切身利益,导致二者间的反教具有同一性㊂士绅负责组织宣传,地方官员在暗中支持,甚至是士绅的坚强后盾㊂南阳地方官对传教士的无理要求难以应付,碍于上司命令,不得不委曲求全来迎合传教士,导致两者在反洋教问题上矛盾重重㊂(三)普通民众南阳民众是南阳教案交涉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虽然较少直接参与反洋教斗争,但却是南阳还堂案达到目标的重要因素㊂学者苏萍认为 民众反教可分为受谣言鼓动和因实质利益冲突所致二种类型 [5]131㊂南阳民众认为外来教会势力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因此,对洋教普遍地反感㊁仇视,积极参与反洋教斗争㊂南阳民众在教案交涉中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㊂第一,中国农民阶级的双重个性:勤劳朴实而又保守愚昧㊂勤劳朴实的个性可引导为高尚的爱国主义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广大民众始终坚持反对传教士进城传教的立场,在靳岗修筑圩寨时民工也敷衍应付,准备发动武装暴动㊂光绪皇帝虽赐书 御敕修建 四字,仍难以糊弄人民㊂河南当局命令总兵王明山前往镇压,拨发毛瑟枪100多支㊂中外反动势力的威逼利诱,并没有成功收买绅民㊂保守愚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走入误区,成为盲目排外的根源㊂南阳绅民本与南阳天主教积怨甚深,又听闻法国入侵,于是南阳绅民欲拆毁南阳天主教堂,逐杀传教士,主教安西满仓皇逃亡汉口避难㊂第二,南阳民众受士绅和谣言的控制与引导㊂士绅制造并散布有关基督教的种种不齿的谣言,这是最能使百姓信以为真的手段,这些谣言以公呈㊁檄文㊁匿名揭帖等形式到处张贴,然后官员再以奏折㊁禀文㊁告示等权威文书予以认可㊂但每当地方官退让出卖绅商利益时,士绅就以演戏㊁吃酒席等方式集众,造成群情浮动的情况,迫使官府不敢贸然结案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针对传教士的霸道无理,南阳官绅及民众间既合作又猜忌,成功挫败了传教士霸占江浙会馆及进城置产设堂的阴谋㊂最终,南阳教案以在靳岗修筑圩寨的结果而结束,其结果有别于其他教案的惩凶㊁赔款㊁道歉等结案方式㊂三结语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依靠传教特权,借口归还天主教 旧产 ,导致南阳还堂案的发生㊂外国传教士为夺取江浙会馆,依靠驻京法使的撑腰,采取多种卑劣行为抢夺地产,表现出极强的侵略性和殖民性㊂㊃721㊃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第9卷经过南阳绅民几十年的斗争,成功阻止了外国传教士企图夺取江浙会馆及进城传教的卑劣行为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因各自利益及地位的不同,在反洋教斗争中,官㊁绅㊁民三个阶层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趋向㊂清政府迫于驻京法使的胁迫,施压南阳府官员及时处理南阳教案,以满足传教士的要求㊂因绅民的竭力反对,南阳府官员不敢贸然答应,招致撤职或调任,难以满足各方需求,处境尴尬㊂士绅作为南阳地区的实权阶层,他们以维护礼教为借口,成为反洋教斗争的组织者及支持者㊂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肯定,但也夹杂着盲目性和妥协性,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这一点㊂通过南阳教案,我们可以看到 官㊁绅㊁民之间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传统中既合作又猜忌的复杂关系 [8]㊂南阳教案为我们认识近代南阳地区各个阶层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及所处的不同处境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加深了对近代南阳社会变动的了解㊂参考文献[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2]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新探[M].合肥:黄山出版社, 1993:38.[3]赵树好.南阳还堂案述评[J].黄淮学刊,1993(6):51 -52.[4]赵树好.晚清教案交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18-120.[5]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7]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486.[8]李亦钊.近代 南阳教案 的特点和动因分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4):52-54.(责任编辑:李建中)AB R I E FA N A L Y S I SO FT H EN A N Y A N GC H U R C HC A S EI NT H EL A T E Q I N GD Y N A S T YH EY o n g-t a o(C o l l e g e o f H i s t o r y a n dc u l t u r e,H u n a n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C h a n g s h a410081,C h i n a)A b s t r a c t:I n1861,f o r e i g nm i s s i o n a r i e s r e l y o n t h e i r p r i v i l e g e,t o t a k e J i a n g s u a n dZ h e j i a n g H a l l i nN a n y a n g c i t y,s o t r i g g e r e d t h eN a n y a n g C h u r c hC a s e.A f t e r t h eN a n y a n g C h u r c hC a s e,t h eF r e n c hm i s s i o n a r i e s r e l y o n t h eF r e n c h a m b a s s a d o r i nC h i n a t o f a b r i c a t e p e r j u r y a n da c t s r e c k l e s s l y t o a d o p t v a r i o u s s t r a t e g i e s t o a t t e m p t t o g r a b t h e J i a n g s u a n dZ h e j i a n g H a l l.L o c a l o f f i c i a l s d u e t o s u p e r i o r c o mm a n d,h a d t om a k e c o m p r o m i s e s,f i n dab a l a n c eb e t w e e n m i s s i o n a r i e s a n d g e n t r y a n dh a v e,i ne x t r e m e l y a w k w a r da n de m b a r r a s s i n gp o s i t i o n.T h e g e n t r y,i nt h ea n t i-c h u r c hs t r u g g l e,t o p l a y t h er o l eo fo r g a n i z e ra n de x e c u t o r, m a i n t a i n s a c o m p l e x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w i t h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t h e p e o p l e.P e o p l e a r e e n c o u r a g e db y t h e r u m o r s o r o u t o f r e v e n g e,a n d r e s o l u t e l y o p p o s e dC a t h o l i c i s mi n t o t h e c i t y.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N a n y a n g C h u r c hC a s ew i l l h e l p u s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b e t w e e n t h e p e o p l e a n d t h eo f f ic i a l sa t t h e t i m e t h ed i f f i c u l t ie sof f o r e ig nr e l a t i o n s,m o r e t r a n s m i s s i o no fN a n y a n g s o c i e t y i n m o d e r n s o c i a l ch a n g e s.K e y w o r d s:l a t eQ i n g D y n a s t y;N a n y a n g;t h eC h u r c hC a s e;t h em i s s i o n a r i e s㊃821㊃。
作者: 司佳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433
出版物刊名: 史林
页码: 90-97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3期
主题词: 圣谕广训 传教士 卫三畏 方言直解 美国汉学
摘要: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档案中藏有十多种有关清代《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件,从历史学与语言学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并结合当时其他传教士所作的多种翻译、评论史料,可以探讨19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入门材料这一“传统”之源起。
传教士关注《圣谕广训》与《广训衍》及《直解》的不同出发点在于从《圣谕广训》的翻译文本中获取根本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借鉴《广训衍》、《直解》之类的浅文理形式,将之作为习得汉语的捷径。
作为初入异文化空间的新教传教士,面对“他者”的文化根基,其早期的学习态度与相应之传教策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出生于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当时他的专业是哲学,他的第一本论著是与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写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本源》。
沙畹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这使他后来同中国和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一位中国学者——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
一年后译完《封禅书》一卷并在《北京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
译文原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
在这一时期,因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6vi)的要求,沙畹暂时放下了中国研究工作,转而翻译佛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
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并担任多种社会职务: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
这一年他还成为了法兰西学会会员。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等地进行考古考察,收集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他的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畹带来了灾祸。
他为法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工作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忍的毅力继续学习,顽强练习汉语口语。
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
花园山天主教教区该教区为意大利、英国天主教区,位于昙华林街中部以南的花园山山顶上,是所有昙华林历史遗迹中面积最大,同时存留建筑物最多的文物区,目前共有四座宗教建筑物。
一是位于湖北中医院内西边的嘉诺撒小教堂,建于1888年;二是1880年有意大利主教江成德设计修建的主教公署大楼(现在是中南神哲学院);三是花园山天主堂,1891年修建,据说同武汉市上海路的天主堂为姊妹堂;四是1928年由武昌主教艾原道创设的育婴堂大楼。
(花园山天主教堂)(中南神哲学院)从穿过花园山的胭脂路左侧上山,沿着湖北中医院职工住宅区的小路前行,几经辗转,在一片废墟之中,孤独地矗立着一栋破败的老房子。
从外墙上依稀可见的雕花装饰,以及大门结构,可以看出是欧式建筑,多年来在这里任由雨打风吹。
这就是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小教堂。
育婴堂位于花园山2号,建于1928年,为砖木结构建筑。
该堂由艾原道主教创设,委托德籍女士主持,开始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成活率较高。
以后不断发展,集中堂内抚养。
1929年圣若瑟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
现为市儿童福利院。
崇真堂位于戈甲营44号,是由基督教英国伦敦会的杨格非牧师于1865年兴建的,它是外国列强在武昌建立的第一座基督教堂。
1924年,该教堂经过维修保存至今。
该教堂主体是一座平面拉丁十字形的单层哥特式建筑,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做礼拜。
崇真堂的兴建,象征着基督教(新教)传入武昌的历史开端。
如今,杨格非牧师在武汉兴建的教堂除了崇真堂外,其他的都消失了,崇真堂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加突出武昌昙华林特1号文华书院古建筑群现位于湖北省中医学院(昙华林特1号)校园内的古建筑群,是原基督教美国圣公会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
1903年成立文华书院正馆,1909年在美国注册为文华大学,1924年在文华大学的基础上,建成了华中大学。
1952年组建为华中师范大学。
所以这些古建筑成为百年华师源头。
主要有:翟雅各健身房、文华公书林遗址及辅楼书库、圣诞堂、文华大学教育学院、理学院、文华大学女生宿舍、华中大学文学院等多处。
中国民族报/2013年/1月/25日/第007版理论周刊・时空陶然士:羌族原来是“犹太人”?周永健1896年,24岁的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来到中国。
在华期间,他曾参与华西边疆研究协会的实地调查与相关研究活动,先后发表多篇有关羌族研究和四川考古的学术论文。
截至1937年返回英国,陶然士在华生活长达40年。
1918年,陶然士进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传教和田野调查。
据《汶川县志》载:“民国九年(192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托伦士(即陶然士),群众称为陶牧师,在县城绵虒建立福音堂传教。
”每年七八月,陶然士就会在羌族地区开展传教旅行,因此,他对羌族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陶然士认为川西的羌族山区就像“巴勒斯坦或中东,因为建筑是如此的相似”,平顶石头房和高塔“让人联想起这样形式的房子从小亚细亚,跨越北印度和中亚,再从甘肃到达华西的传播路径”。
密密麻麻沿山脉而建的寨子,“其外观很像扩大了若干的中世纪城堡”,此景此物似乎“使人回到了大主教时代”。
他认为羌族女子发饰上的银圈让西方女性的头饰“在后面掉了一大段路,没有一个欧洲人能描绘出它的天然动人处,只有心爱的情郎用他的热忱才欣赏得出来”。
1920年,陶然士出版专著《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较为系统地阐述他对羌族历史、习俗和宗教的研究。
陶然士谙熟西南方志等地方文献,并对川、黔、滇的少数民族文化颇有兴趣。
他认为最早进入四川的并不是汉族人,“汉人是较后才逐渐占领大部分四川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大量非汉族的残余居住在这里。
”他所关注的羌族就是其中之一。
陶然士认为,“即使这些非汉族的后代们,在今天因为环境的限制,相较于他们的‘领主’更贫困,但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
没有人会瞧不起一片美丽的陈旧的瓷器,即使它的颜色可能暗淡,或边缘有裂痕,或者被钉上铆钉以防脱落。
每一个种族都代表它自己的古老文明,即使他们早期的艺术、技能在汉人的侵犯浪潮中淹没遗失,但总有一种美和价值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