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中国先锋小说回眸
- 格式:pdf
- 大小:248.13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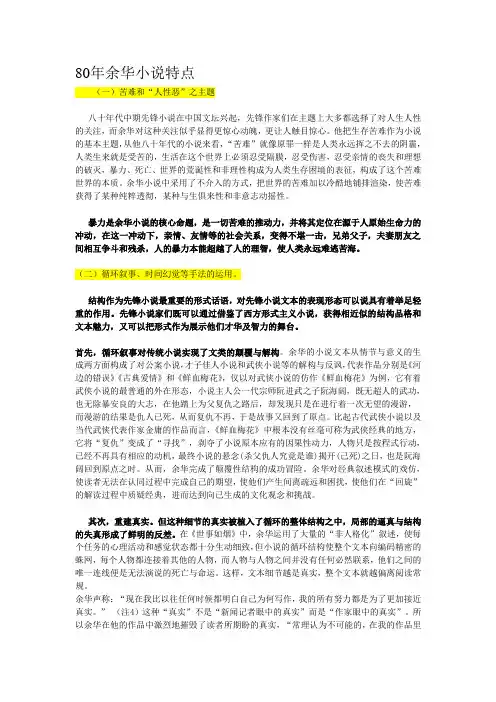
80年余华小说特点(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
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二)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
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首先,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
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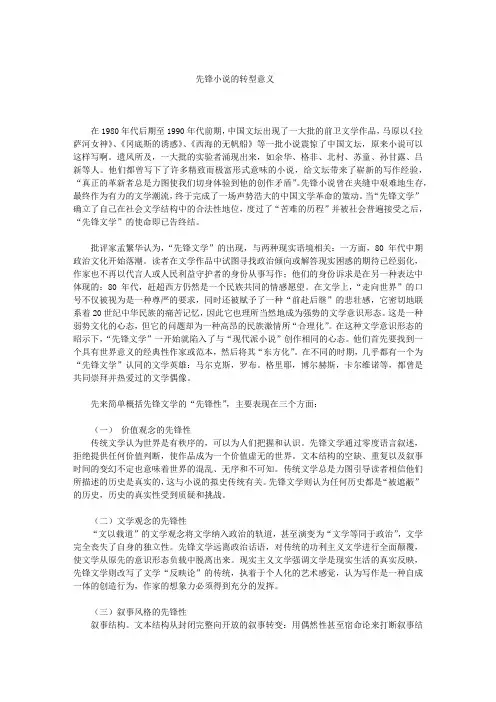
先锋小说的转型意义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的前卫文学作品,马原以《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等一批小说震惊了中国文坛,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
遗风所及,一大批的实验者涌现出来,如余华、格非、北村、苏童、孙甘露、吕新等人。
他们都曾写下了许多精致而极富形式意味的小说,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写作经验,“真正的革新者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
先锋小说曾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最终作为有力的文学潮流,终于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学革命的策动。
当“先锋文学”确立了自己在社会文学结构中的合法性地位,度过了“苦难的历程”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先锋文学”的使命即已告终结。
批评家孟繁华认为,“先锋文学”的出现,与两种现实语境相关:一方面,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开始落潮。
读者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寻找政治倾向或解答现实困惑的期待已经弱化,作家也不再以代言人或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身份从事写作;他们的身份诉求是在另一种表达中体现的:80年代,赶超西方仍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愿望。
在文学上,“走向世界”的口号不仅被视为是一种尊严的要求,同时还被赋予了一种“前赴后继”的悲壮感,它密切地联系着20世纪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因此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强势的文学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心态,但它的问题却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激情所“合理化”。
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昭示下,“先锋文学”一开始就陷入了与“现代派小说”创作相同的心态。
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性作家或范本,然后将其“东方化”。
在不同的时期,几乎都有一个为“先锋文学”认同的文学英雄:马尔克斯,罗布。
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都曾是共同崇拜并热爱过的文学偶像。
先来简单概括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价值观念的先锋性传统文学认为世界是有秩序的,可以为人们把握和认识。
先锋文学通过零度语言叙述,拒绝提供任何价值判断,使作品成为一个价值虚无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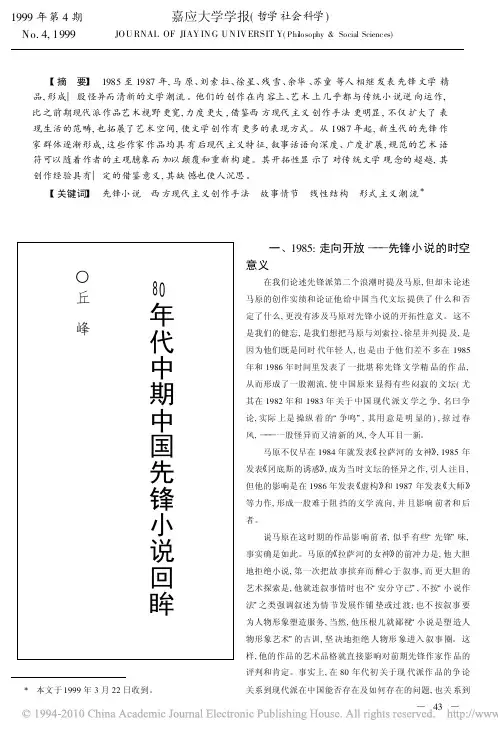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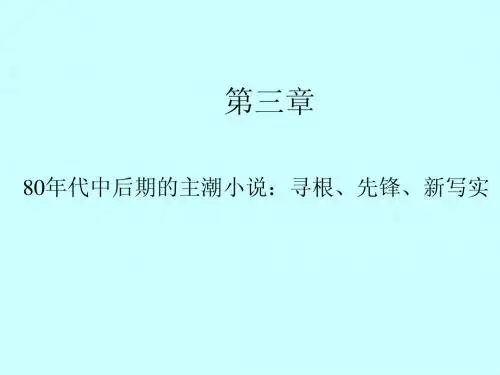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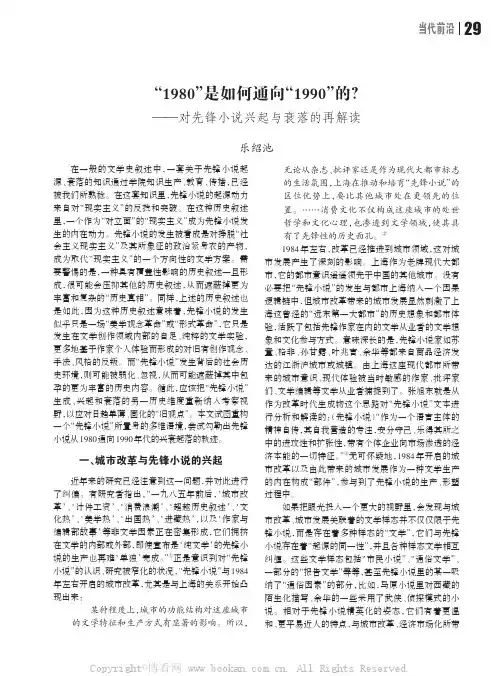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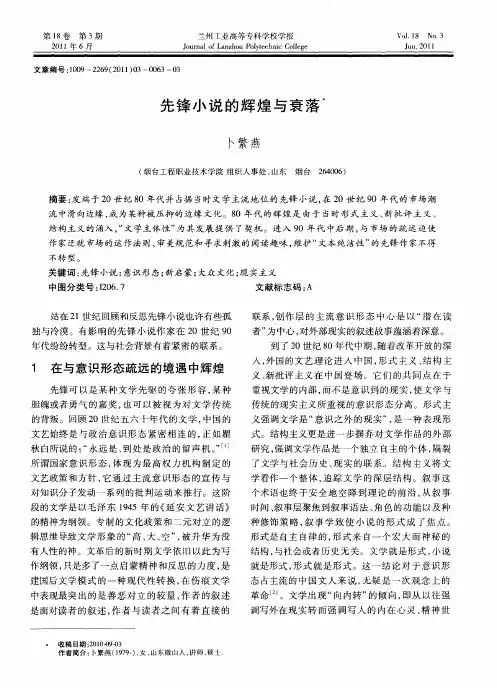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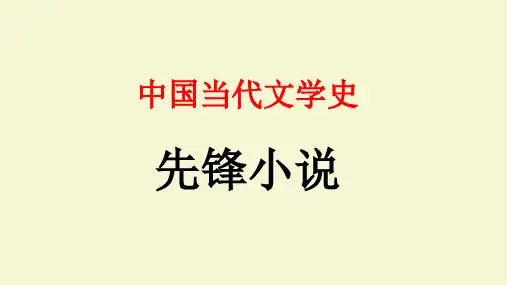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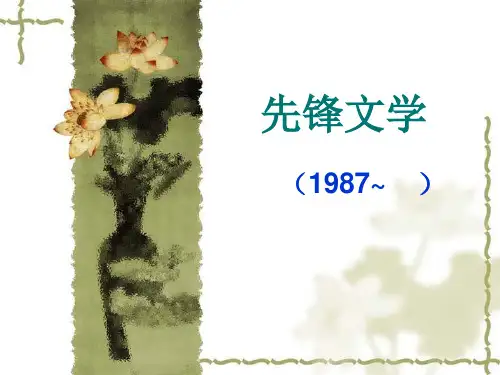
80年代小说综述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
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
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
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
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
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论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论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也是中国先锋小说崛起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先锋作家们对传统文学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以此来突破传统文学的束缚,并表达自己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与感受。
本文将从语言实验的角度来探讨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特点和意义。
80年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方便,同时也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由主义思潮与西方文化的涌入,打破了过去封闭的文化秩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先锋作家们对语言的使用有了新的要求。
首先,先锋小说强调了一种变革的语言风格。
传统的文学语言多以庄重、正式为主,而先锋小说鲜明地摒弃了这种形式,使用更为自由、流畅的语言风格。
他们追求真实、直接地反映生活,使用白话体与读者产生更直接的对话。
这种语言风格的变化,使小说更具有现代感,更能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其次,先锋小说注重语言的多样性和创新。
他们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如口语、方言、俚语等,不拘泥于旧有的文学规范和束缚。
例如,杨绛的《洗澡》中大量运用北京方言,使人物形象显得亲切可爱;马原的小说《笑中有算盘》则充斥着大量的当地方言,使作品充满地方色彩和个性。
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和创新使作品更加鲜活生动,令人耳目一新。
另外,先锋小说关注日常话语的重构与重塑。
他们试图通过对日常的对话和琐碎生活琐事的描述,来窥探人性的真实与复杂。
例如,王朔的小说《黄金时代》中,通过主人公的自我表述和对话,呈现出性别观念的变动与矛盾,具有一种时代特色的语言风格。
这种关注日常话语的重构与重塑,使小说更真实、更具有个体和时代的独特性。
此外,先锋小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髓,如意识流、碎片化叙事等,将之融入中国的小说创作中。
这种借鉴与吸收使中国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更加丰富多样。
王蒙的小说《寂寞的乡愁》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更加复杂,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写作观念和风格。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体式之争锋王鍾陵一80年代,特别是其中期,小说文体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这一变化主要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可以上承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化与诗化的倾向,一是先锋派小说。
小说文体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两点上:一是超脱于情节模式之外,一是模糊以至避免现实主义的“实指性”。
前者表现为线性叙述的中断,非情节小说、非性格人物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应的对于塑造典型人物及写出典型环境兴趣的降低乃至漠视;后者则有莫言式的写感觉、马原式的设置叙述圈套和残雪式的写梦呓。
而情节模式的弃置与“实指性”的模糊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着的。
汪曾祺在40年代就认为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并将短篇小说家定义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家”[1]。
汪曾祺在写于1986年5月的《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一文中,将上述两点结合起来,阐述了“诗化小说语言”这一概念,张扬起诗化小说的旗帜。
为了使论证能有一种根本性,汪曾祺首先从“语言是本质的东西”[2]1讲起,强调“探索一个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观察他的倾向性,首先必需掌握他的叙述的语调。
”[2]2接着,汪曾祺进而说明小说家的语言,既应“能产生具体的实感”,又应“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2]3。
他说:“语言写到‘生’时,才会有味,语言要流畅,但不能‘熟’。
援笔即来,就会是‘大路活’。
”[2]5此外,“一篇小说,要有一个贯串全篇的节奏”,“所谓‘可读性’,首先要悦耳”[2]7。
对诗化小说语言,汪曾祺阐述道:“废名说过:‘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
’何立伟的一些小说也近似唐人绝句。
所谓‘唐人绝句’,就是不着重写人物,写故事,而着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
物我同一,作者的主体意识很强。
这就使传统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小说和诗变得难解难分。
这种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
这种小说的语言也就不能不发生变化。
这种语言,可以称之为诗化的小说语言——因为它毕竟和诗还不一样。
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
《中国当代文学》题库及答案一、填空1.今天派的代表诗人是:1. ,其代表作是、。
2. ,其代表作是、。
2.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是:、。
3. 、、,等作家通常被称为“知青作家”。
4.张贤亮的主要作品有:A________、B __________。
5.杨朔的主要作品有:A ___________、B ____________。
6.现代派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是:A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
7.A ________、B__________、C____________,等作家通常被称为“70后作家”。
8.九十年代初“陕军东征”的五部长篇小说是:A__________、B__________、C__________、D_________、E__________。
9.赵树理建国后的代表作是:A __________、B__________。
10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是: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革命现代交响音乐。
11.现代派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是:A 的B 的C 的12.七月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是:A__________、 B ___________、C二、名词解释1.伤痕文学2.三红一创3.归来派4.“朦胧诗”5.寻根文学6.双百方针7.现代派小说8.生活的原生态:9.元叙述三、简答题请说明以下作品的作者、文体和主要特点:1.《致橡树》2.《现实一种》3.《妻妾成群》4.《一代人》5.《百合花》四、论述题1.简论先锋小说的实验性。
2.简论归来派诗歌的共同特征3.谈谈你对本体实验的理解4.谈谈寻根文学在文革后文学思潮中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业参考答案一、填空1.今天派的代表诗人是:1.北岛,其代表作是《回答》、《宣告》。
2.舒婷,其代表作是《致橡树》、《祖国啊,亲爱的祖国》2.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是:池莉、方方。
3.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等作家通常被称为“知青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