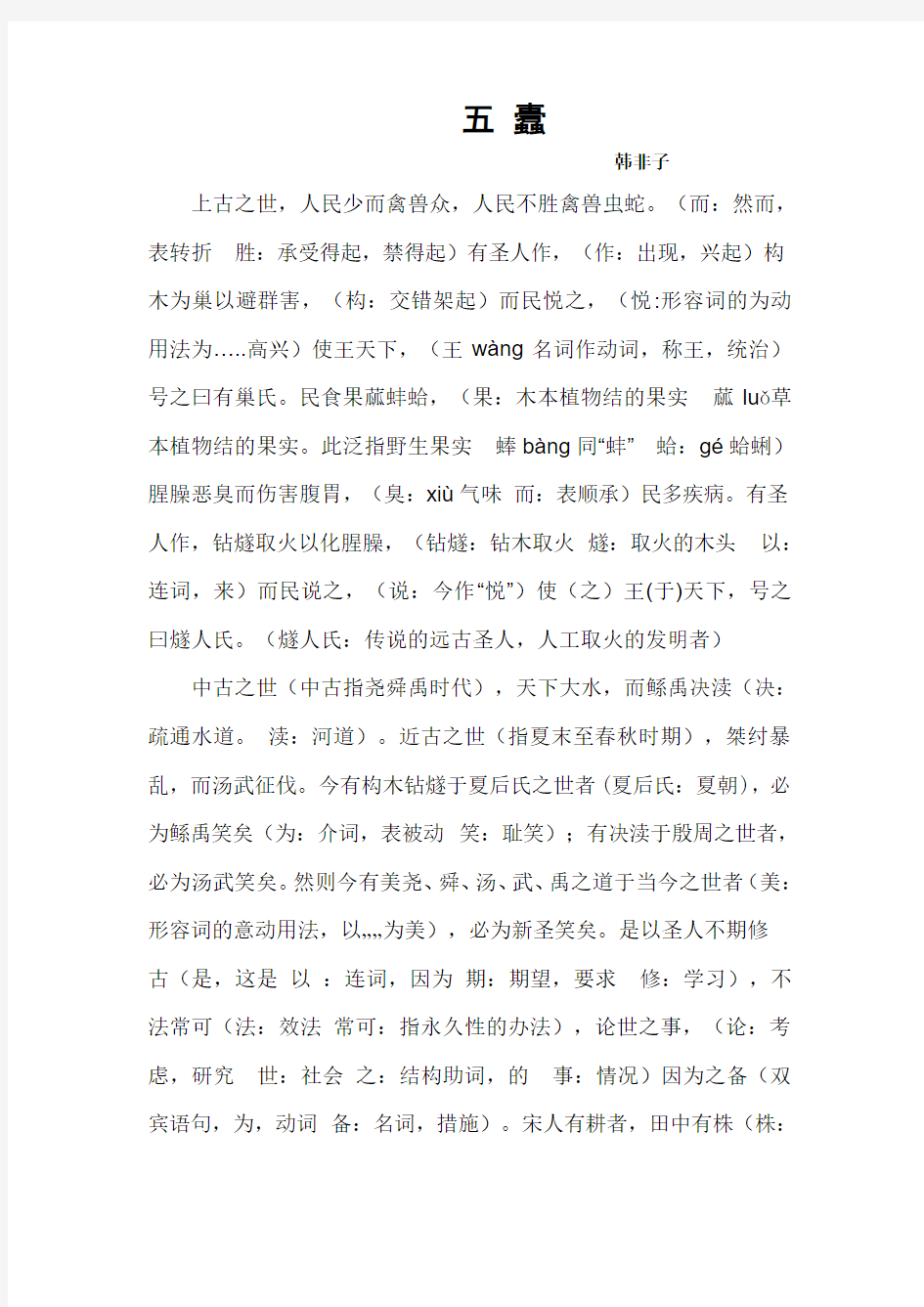

五蠹
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而:然而,表转折胜:承受得起,禁得起)有圣人作,(作:出现,兴起)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构:交错架起)而民悦之,(悦:形容词的为动用法为…..高兴)使王天下,(王wàng名词作动词,称王,统治)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果:木本植物结的果实蓏luǒ草本植物结的果实。此泛指野生果实蜯bàng同“蚌”蛤:gé蛤蜊)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臭:xiù气味而:表顺承)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钻燧:钻木取火燧:取火的木头以:连词,来)而民说之,(说:今作“悦”)使(之)王(于)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燧人氏:传说的远古圣人,人工取火的发明者)中古之世(中古指尧舜禹时代),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决:疏通水道。渎:河道)。近古之世(指夏末至春秋时期),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夏后氏:夏朝),必为鲧禹笑矣(为:介词,表被动笑:耻笑);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美),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是,这是以:连词,因为期:期望,要求修:学习),不法常可(法:效法常可:指永久性的办法),论世之事,(论:考虑,研究世:社会之:结构助词,的事:情况)因为之备(双宾语句,为,动词备:名词,措施)。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株:
树春子 ),兔走触株(走:跑),折颈而死(折:zh é,折断,而:连词,表顺承);因释其耒而守株(因,于是 释:放开 耒l ěi :古代一种翻土的农具),冀复得兔(冀:希冀。希望 复:再,又 ),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身:自身自己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者,……也。判断句 以:用 治:治理 皆:全,都)
蠧: 名词,形声。“螙”是“蠹”的本字
蠹,木中虫。——《说文》
本义:蛀虫
臭:ch ?u
1、不好的气味,与“香”相对。 臭味,恶臭
2、香气 左佩刀,右备容~,烨然若神人 。《送东阳马生序》宋濂 xi ù
1、 气味的总称:无声无~。
2、 同“嗅”。
伐
(会意。从人,从戈。甲骨文字形,像用戈砍人的头。本义:砍杀)
伐,击也。——《说文》
↗砍,劈(扩大引申)伐竹取道。 柳宗元《小石潭记》
伐:武力杀戮,攻打,征战 → 夸耀(词义引申) 不伐己功,不矜己能。
----《 淮阴侯
列传》
↘ 胜利,勤劳(词义引申) 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史记 ? 魏公子列传》 身: (象形。象人之形。本义:身躯的总称
)
身,躬也。象人之形。——《说文》。身的本义是人的躯干
株:(形声。从木,朱声。本义:露出地面的树根)
株,木根也。——《说文》。
本义树干→棵(词性引申,量词)
古者丈夫不耕(丈夫:成年男子),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衣yì:穿)。不事力而养足(事力:使用劳力,即进行生产劳动而:连词,表转折养:给养,生活资料),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厚:重行:实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自治:自然安定无事)。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大父:祖父)。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财货:同义连用,指财务财产),事力劳而供养薄(劳:辛劳,辛苦),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虽:即使,倍:加倍累:成倍增加)
厚: (会意。从厂(hǎn),表示与山石有关。本义:地壳厚。与“薄”相对) 造字本义:在巨大岩体里开凿的帝王陵寝,即“崖墓”,墓内设计模仿帝王生前的阳间世界,有大量陪葬品,此即古代所谓“厚葬”的本义。
↗形容词,矮的,不厚的→形容词,含量不足,轻,微,浅→动词,轻
薄:→本义蔓延生长的草丛
↘通“迫”靠近日薄西山
尧之王天下也(之:取独),茅茨不翦(茅茨cí:用茅草盖得屋顶;翦jiǎn:修剪,剪的异体字),采椽不斫(采椽chuán:乐木做的椽子;斫zhu?:坎削,此指加工修整);粝粢之食,藜之羹;
(粝lì:粗米;粢cì:比黍差的粮食;藜li:野菜;羹:菜汤)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麑ni裘:麑皮衣;麑:小鹿;葛衣:葛布做的衣服);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监门:看门的人养:吃的亏:减损,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身:亲自执:拿着耒古代翻土的农具臿:锹,铲先;动词,做出表率,率领),股无胈,胫不生毛(股:大腿胈bá;腿上的细毛胫:jing 小腿);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臣虏:同义词连用,指奴隶)。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让:禅让),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去:离开),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传天下:把天下传给别人不足多:不值得赞赏,多:赞赏,称赞)。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累世:世世代代絜xié:这里只套车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重,看重)。是以人之于让也(让:辞让官位),轻辞古之天子(轻辞:轻易地辞去),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薄厚:指利益的大小实:实际情况)。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山居:住在山上谷汲:到溪谷去打水膢l?u:楚人在二月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古代冬季举行的对百神的祭祀遗wei:赠送);泽居苦水者(泽居:在沼泽地区居住苦: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苦水;水患),买庸而决窦(买庸:雇工决窦:挖渠窦:通凟水沟)。故饥岁之春(饥:五谷不收叫饥),幼弟不饷(饷:供给食物);欀岁之秋,疏客必食(疏客:关系远疏的过客食si:给……吃)。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易财:轻视财务易:轻视),非仁也,财多也;今之
争夺,非鄙也(鄙:贪吝,小气),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高:道德高尚),势薄也;重争士橐,(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认为……重要,看重士:做官橐tuō:同“託”投靠,依附)非下也(下:卑下),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议:研究,考虑同下文的论多少:财务的多少薄厚:指利益的大小)。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诛:惩罚戾:暴虐),称俗而行也(称chèn 适应)。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因:传承随着备:方法,措施)。
韩非子《说难》原文及翻译 韩非子 原文: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上抛弃了他。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说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
浅谈韩非子思想的非道德倾向阐释- 非道德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怀疑论和某些诡辩论者的伦理思想。经过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及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发挥,使非道德主义成为一种反对道德及其作用的系统理论。但随着一股进口西方哲学某些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热潮到来,这种被称为反向格义的研究方法变得普遍起来。那么,本文就从非道德主义的视角来反向阐释韩非子,力图洗尽韩非子是非道德主义者的嫌疑,以此证明韩非子具有严重的非道德倾向,而绝非是曾界定的非道德主义者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内核在于法而非道德,因其思想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所以在道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与异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道德本身及其与法的关系展开,有人认为是以法代德,是对道德的彻底否定;有人主张是道德无用论,对道德本身进行否定;另有观点认为,韩非之说仅仅是否定儒家这一特殊道德,而非否定一切道德。这些观点在其思想体系中都有所反映,且是在道德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尝试。郭沫若认为,韩非子的术毁坏了一切伦理价值。这说明韩非子的道德已经脱离道德本身,被驱逐于道德范式之外。 第一,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新编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显学》,以下仅注篇名)这句话是把韩非子思想定性为非道德主义的突出论点和铁证。持此观点者忽略了这句话的主体和对象,主体是为治者对象是众。韩非子也说过仁、义、礼、智、信皆为乱国之术也,孔墨乃愚诬之学。但韩非子是站在为治者,即称王为君为民主的立场上来用众。用众就是寻求一种外在普遍的规定性一法也;舍寡即是指一种内
在特殊的个体性一圣人孔者,所以不务德而务法。作为君主,应行众者之事,道德修养是寡者圣人之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集解显学》),为王者必须舍德务法。 第二,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韩非子集解外储说右下》)。意思是说君不仁,臣不忠,那么霸王之业可行矣。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道德上的人情关系,而是人性恶而导致的自私自利的冷酷的政治关系。作为王者,要维护自己的霸业与统治,实行非道德的政治策略,这是术的一种体现。这是赤裸裸地揭示君臣之间纯粹的利益算计关系,君尚威尚法尚术,臣等平民皆为其自上而下的对象。尽管站在为治者的角度,君不仁,臣不忠,可以王矣,但作为统治术的一种,并未排除其它多种统治的可能性。反之,若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他要遵守法律,要服从法律的暴力,但在经过暴力的教训或者说是威吓一最初是害怕犯法,长此以往他会意识到法制是为了每一个人能变得更加道德。只不过韩非把他的严刑峻法思想推向极端,导致法术势统治集团的破产,所以韩非子所谓君不仁、臣不忠是在以利益实现为核心的商卖原则基础上的法治范畴内的概念,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内涵,这其中既有通权逻辑的利弊权衡,又有维护客观制度公平运作的理性考量,不能简单笼统地将其定性为否定道德价值的非道德主义。 由此可见,韩非子是在特定语境中反对旧道德,具有严重的非道德主义倾向。韩非子把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斥为五蠢的乱国之学,他说: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韩非子集解五蠢》)这说明仁义辩智只是不能持国而已,作为持国者来说,他提倡的是反身外求的人性恶的外在规范,一种形而下的仅仅作为统治的动机法。但他并没有否定特殊个体之间的内在道德,所
韩非子《五蠹》原文和翻译 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
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
《韩非子》选读 编稿:商章红审稿:姜虹 学习目标 1.了解韩非子及其作品; 2.积累文言词汇; 3.体会法家思想的内涵。 知识积累 文学常识 作家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在政治上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等诸项政策,主张君主集权,反对贵族操纵政治。作品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书中重点宣扬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寓言 一种文学体裁,在短小的故事里寄寓较深刻的道理,以进行劝喻和讽刺,常用手法有比喻、拟人、夸张、排比。 写作背景 韩非所处的时代为战国末期,当时诸侯国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大国日益壮大,小国岌岌可危。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眼见自己的国家日益衰微,屡次向韩王建议变法图强,却未被信任和采用。于是,韩非发愤著成《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反映了他革新救国的愿望,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 字词汇总 字音 果蓏(luǒ)蚌蛤腥臊恶臭(è xiù)不胜(shēng)决渎(dòu) 钻燧取火(suì)鲧禹(gǔn)耒(lěi)不宜今乎(yí) 郢书(yǐng) 子圉见孔子(yǔ)太宰噽(pǐ)土簋(guǐ) 似蠋(zhú)孟贲(bēn)嘬其母(zuō) 彘臞(zhì qú) 通假字 而民说.之通“悦” 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通“情” 卜子妻写弊.裤也通“敝” 燕相白王,王大说.通“悦” 而置之其坐.通“座” 反.归取之通“返” 鳣.似蛇通“鳝” 亡.其富通“忘”
简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皮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内容提要: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只有制定严酷的律法,掌握好赏罚二柄,才能有效的对国家加以管理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本文从“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两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法治”的提出,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商君书》中又称“垂法而治”、“缘法而治”。“法治”中的“法”,指的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规范;“治”指的是以这种规范作为约束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这种“法治”的理念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1]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法治”思想。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吸收了前期法家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一、“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一个是“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韩非的历史观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和保守。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时代的变化,国家的治国方法也应当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如果在当今之世仍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韩非提出这种历史观的目的,显然是在为当时法家所推行的法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社会风俗变了,政治制度亦应当变化。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就是用暴力解决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代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义说教都已不合时宜,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急世之民”。 韩非的人性论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教化而改变,即不可能“化性起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比较。他以舆人和匠人为例:“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不仅如此,韩非认为即使是亲子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从以上的观点出发,韩非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不计厉害关系的仁义道德,也不承认有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圣人”。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这种本性无法改变,因此所有的道德教化对人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达到维护统治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且只能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严酷的刑法来制止民众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用利益为诱饵,使民众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以赏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 韩非根据他进化的历史观和“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指出了道德教化的失败和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要求“不务德而务法”,从而比较系统的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理论。
五蠹(节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
浅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好利”说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他以人的生理需求为根据认为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性好利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是利益的结合。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说以“利”为出发点,以“得到利益”为最终的归宿,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均是出于“人性好利”说。从“人性好利”观念出发,韩非子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私自利的,本性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利益的驱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如夫妻、父兄、侍从以及君臣之间,都是凭利益关系的驱使来保持的,这也是人与人交往当中最为危险的几种社会关系,由于人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这势必导致各自社会身份的不纯粹性。他与儒家学说突出人性本善、和谐相处之道有所不同,而是一针见血刻画出私有社会条件下人性趋利的本质,说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只有明白这点,君主在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社会制度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既有求利的本性,就会趋利避害,体现在人性上就是畏惧错误,害怕被惩罚,称其“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这种观点随后成为其法家思想的根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那么,人就会畏惧法律,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要将“法治”推行到国家治理中,非常时期必需严法,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很多法家学说及治国方法,又将其总结与升华,使之更能与当时秦国的社会相融合,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其“人性好利”说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国家社会缺乏中央集权制,人口等流动性太大,文化也多元化,思想与思想的碰撞空前旺盛,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个性存在成风,韩非子的学说正符合这种思潮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符合统治阶级对政权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威的体现,所以其对道德的理解、发扬,正是为了迎合他后来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对法治的推崇更是有着绝对的实践价值。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概念,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韩非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一)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和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因而他主张明法,要求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既反对法外行仁,又反对“释法任私”。他甚至赞同商戟的观点,要求统一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禁止一切有俘于法令的思想、言论。韩非曾设想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法治国”的理境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是故无事则富国......”,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认为要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
韩非《重轻罪》原文及译文赏析 重轻罪 韩非 公孙鞅①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 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②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
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予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选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注释】①公孙鞅:即商鞅。②辜: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磔(zhé):分裂肢体的酷刑。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无离其所难离:离开 B.得而辄辜磔于市得:捉住 C.比降北之罪比:比照 D.罪夫当丧者当:主持 【答案与解析】A(离:通“罹”,遭受)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A.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 B.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C.然则功且安至?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浅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董蕾 (管理科学系行政管理专业学号:091424026 指导教师:郭红娟) 摘要:韩非,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变法历史经验,在批判继承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现今探究其思想要义,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关键词:法治;法;术;势 韩非,世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变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治理论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为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从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法治的基本理论以及推行法治的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以研究。 一、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理论的产生必有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因素,同
时也是思想意识主观因素交流融合的必然。 (二)从经济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实行如“初税田”“量入修赋”等经济政策,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开始列入社会变革的日程。 (三)从政治上看,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各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已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的法治思想由“法”“术”“势”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的理论 韩非的法治理论中的“法”为新兴者倡法,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法规是由封建君主来颁布,官吏来贯彻法令,人人要遵从,是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也即《八说》所说的“治事”。“治事”的中心是尊公废私。《诡使》说:“夫
读《韩非子》 ——韩非的法治思想 传统将《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它集中宣扬了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论。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并不仅仅是集先秦法家于一体,更是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使得韩非在论述法治思想时左右逢源,更具合理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难三》篇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由此可见,韩非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集”的法律条令,是一种“设之于官府”的统治工具,是一种“布之于百姓”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在于赏罚。表面上,他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来都只是当权者安抚民心,骗取人心的一套华而不实的说辞。 在《韩非子》中,韩非并没有系统的罗列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只是务虚的论述立法执法等方面应该贯彻的一些基本准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立法方面,韩非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八说》说:“法所以治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制定法令,必然会有利弊之分,所以立法时必须考虑其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无完法”,韩非 在立法前先权衡利弊,是颁布的法律符合实际而非理想,实际上是追求法律的最大合理性。 第二,立法是必须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立法的因时制宜原则实际上是功利原则的延伸,法律的制定因时因地而变,符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法律的最大功效,这反映了韩非的变法论精神。 第三,法令必须统一,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一条看似与上一条所说的变法论相矛盾,其实不然。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说,这就是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法令一旦制成,就必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否则法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因为法律是全国臣民奉行的行为准则,统一固定,百姓才好遵守,朝令夕改,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且“不擅其法”,也给奸臣贼子造就了可乘之机。“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利则道之”。所以,韩非认为“法其如一而固”。 第四,法令必须适应于人的性情,容易了解,便于实行。《用人》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明主之表易见,故约之;其教易之,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 法既然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就必须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具有其通俗性和可行性。如果深奥难懂,或通过努力也做不到,人们就会“私怨生”、“伏怨结”,就会背叛君主。 常言道:“法不责众。”如果制定的法令人们都无力做到而只能违反,那就会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法就是有违情理的,是行不通的。 第五,法应该详尽明白。《八说》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制定法令,既要简明,又要详尽。法律太深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不能达到容易了解容易实行的要求; 法律太简单,有些情况找不到法律的依据,就会有人趁机钻营。所以,法要简明详尽,构建一个明确的标准。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 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 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 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 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 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 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 (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 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 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 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 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 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 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 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 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 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 摘要: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在春秋战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历史变革之际,诸子百家分别提出了自身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其中以法家韩非子“因时制宜”的认识最为深刻,从而提出了当时最有助于国家统一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本文首先介绍韩非子历史观产生的背景基础,然后分析韩非子其他主张观点与其的联系,并综合的与其他诸子百家观点进行比较,最后阐明韩非子历史观对当今社会的启发。 关键词:社会历史观;韩非子;因时制宜 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社会历史观不仅是对以往历史的回顾,更重要的是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总结,以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策略或未来发展的设想。一般来说,社会历史观决定了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就会有一套相应的认识并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哲学,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关于社会历史的思维架构和考察方法主要是复古主义和循环论,即习惯于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在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社会历史观中均可体现,我们会在后文较为详细地对比介绍。在古代的哲学中,世界本体往往是一种不变的永恒之物,由于本体的宏大无边和静止无感,古代哲学习惯于对世界的静态观察。具体说来,世界万物只能在固定的量的界限内运动,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故而谈不上什么质变和飞跃。而韩非子站在的他的那个正经历着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因时制宜”
的社会历史观,主张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在国家社会制度方面进行相应的合适的变革。这对中国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直接为它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甚至对中国今天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的启发。对此,本文将立足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力图对其社会历史观的形成与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1.0文献综述 有相当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关立新(2009)[1]在现代角度上比较了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历史观,评价了韩非子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历史及现代发展的影响;黄柏成(2013)[2]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对中国当代法律建设和改革的启示; 陈冬(2013)[3]通过深入地分析韩非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仪”的观点,以从侧面表现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宋洪兵(2008)[4]再次对比了儒家与法家的社会历史观,考证了这两派对于“复古”与“应时”的观点,得出了“这两大家均是认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只是寻求的变革方法不同”这一新的重要结论;林光华(2014)[5]通过分析韩非子《解老》而深刻地对比了韩非子与老子关于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异同。本文将具体分析韩非子社会历史观的产生背景,并阐述其与韩非子其他主要观点的联系,以从整体全局上展现韩非子的历史观,再与其他诸子百家的观点进行综合的比较,最后阐述其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时代背景
《五蠹》原文及对照翻译 《五蠹》原文及对照翻译 出处或作者:《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 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 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动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 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 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 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 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 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 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 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 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 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 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
论韩非子的法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班级:104 学号:35 姓名:许雯 关键词:重法,安国,执法,奉法,赏罚 摘要:“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奉行法度的君主强劲有力,坚决实行法制,国家就会强盛;相反,奉行法度的君主软弱无力,不坚决实施法制,国家就会衰弱。“能去死曲就公法者,民安则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能远离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追求实施国法的国家,民众就安定,国家就太平;能远离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法,兵力就会强大,而敌人变得相对弱小了。 韩非,生活于七雄争霸战国时期。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卿,才华出众,但口吃,不善言谈而擅长著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年轻时,韩国国势弱小,屡败于秦国,割地损兵。为此,他曾多次上书韩王以法治国的计策,均未被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于是发奋著书立说,以求闻达。后秦王赢政读了其著作,大加赞赏。但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却并未受到重用。与此同时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言加以陷害,最后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学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和批评先秦法家尤其是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大量吸纳了黄老道学,邢名学以及兵家,儒家,墨家,纵横家的观念,形成了当时最具综合性,最具实用性价值的管理理论。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和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和研究其思想的局限性,对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新旧体制转变、新旧观念更替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韩非的法制思想 韩非虽然出自荀子的门下,但却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战国后期,此时,旧的贵族制度向新的制度转变,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适应了新兴阶级变革需要的法家思想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此之前,许多诸侯国已经由新派人物的代表掌握了政权,任用法家人物进行变法,从事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改革。不难看出,从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体现了法家思想的逐渐壮大的趋势。而韩非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中。 1.韩非的法本思想 韩非子说:“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就是说国家要强大,在于国家要做好法治工作,国家
《韩非子.说难》阅读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 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8.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则见下节而遇卑贱下节:节操低下 B.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显:显赫 C.人间往夜告弥子间:抄小路 D.柔可狎而骑也狎:戏弄 9.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 而说之以厚利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B. 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 武公怒而戮之 C. 因问于群臣 我欲因之梦吴越 D. 厚者为戮,薄者见疑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10.下列对文中语句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大凡游说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让自己的说法适合他 B. 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 C. 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 D. 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
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只有制定严酷的律法,掌握好赏罚二柄,才能有效的对国家加以管理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法治”的提出,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商君书》中又称“垂法而治”、“缘法而治”。“法治”中的“法”,指的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规范;“治”指的是以这种规范作为约束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这种“法治”的理念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法治”思想。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吸收了前期法家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一、“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一个是“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韩非的历史观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和保守。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时代的变化,国家的治国方法也应当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如果在当今之世仍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韩非提出这种历史观的目的,显然是在为当时法家所推行的法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社会风俗变了,政治制度亦应当变化。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就是用暴力解决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代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义说教都已不合时宜,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急世之民”。韩非的人性论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教化而改变,即不可能“化性起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比较。他以舆人和匠人为例:“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不仅如此,韩非认为即使是亲子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从以上的观点出发,韩非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不计厉害关系的仁义道德,也不承认有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圣人”。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这种本性无法改变,因此所有的道德教化对人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达到维护统治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且只能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严酷的刑法来制止民众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用利益为诱饵,使民众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以赏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韩非根据他进化的历史观和“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指出了道德教化的失败和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要求“不务德而务法”,从而比较系统的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理论。 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法、术、势就是律法、权术、权力。从思想来源上看,韩非的法、术、势思想一方面来自荀子,另一方面主要来自于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将荀子思想中的法治思想加以发展,并对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者的思想进行比较,认为商鞅的缺点是“徒法而无术”,申不害的缺点是“徒术而无法”,以为“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2]而推行“法”和“术”还需要有统治权力,也就是“势”。所以,韩非又吸取了慎到的“势”,创造出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1、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像前期法家一样,韩非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才可以谈“法治”。统治者要维护其统治和富国强兵,首先要制订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发展有利于国家的“自为心”,制止不利于国家的“自为心”。这种行为规范就叫做“法”。在韩非看来,“法”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必须要公开颁布,是百姓全体周知,即具有公开性。他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至于百姓。”(《韩非子·难三》)将律法成文的颁布公开,不但可以使百姓有所遵循,同时也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从而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在怎样保障“法”的有效执行方面,韩非认为关键在于君主要掌握刑、赏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这里的“德”不同于儒家德仁义道德,韩非所谓的“德”,是指以利为钓饵的“赏”。赏罚之所以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其合乎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因而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认为,“法”应该是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拥有绝对的权威,除它以外不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