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
- 格式:doc
- 大小:27.0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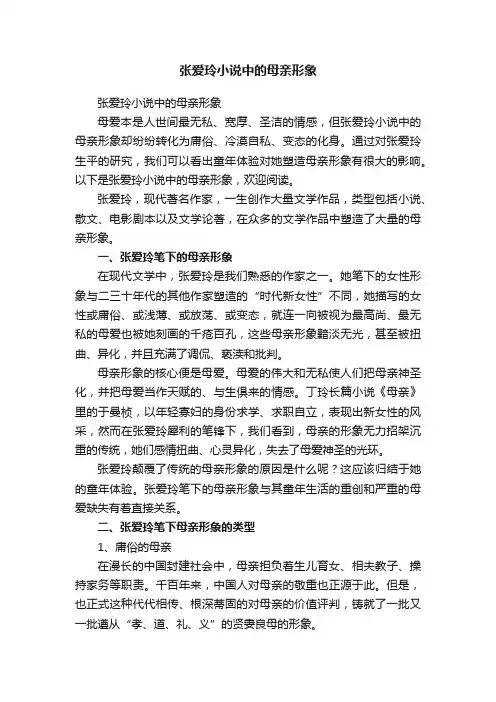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母爱本是人世间最无私、宽厚、圣洁的情感,但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却纷纷转化为庸俗、冷漠自私、变态的化身。
通过对张爱玲生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童年体验对她塑造母亲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以下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欢迎阅读。
张爱玲,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母亲形象。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之一。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庸俗、或浅薄、或放荡、或变态,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刻画的千疮百孔,这些母亲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并且充满了调侃、亵渎和批判。
母亲形象的核心便是母爱。
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使人们把母亲神圣化,并把母爱当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情感。
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的于曼桢,以年轻寡妇的身份求学、求职自立,表现出新女性的风采,然而在张爱玲犀利的笔锋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无力招架沉重的传统,她们感情扭曲、心灵异化,失去了母爱神圣的光环。
张爱玲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归结于她的童年体验。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1、庸俗的母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源于此。
但是,也正式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
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的事实,也只是忍气吞声。
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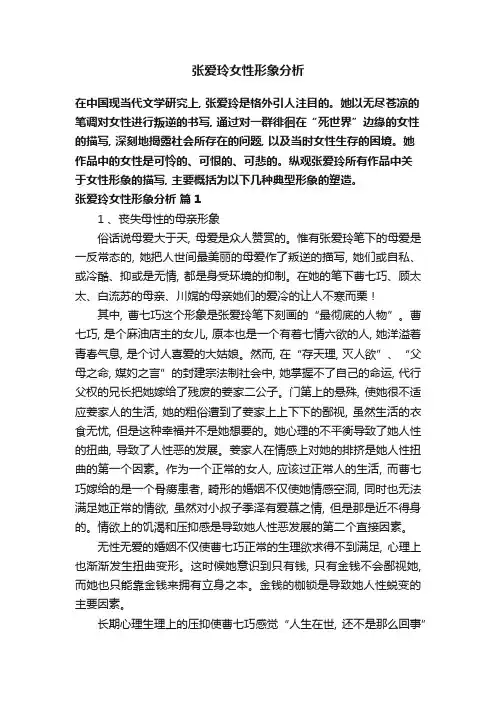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 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 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 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
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
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篇1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俗话说母爱大于天, 母爱是众人赞赏的。
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 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 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 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
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其中, 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
曹七巧, 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洋溢着青春气息, 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
然而, 在“存天理, 灭人欲”、“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 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
门第上的悬殊, 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 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 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 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 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
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 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 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 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 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
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
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 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 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
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 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 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 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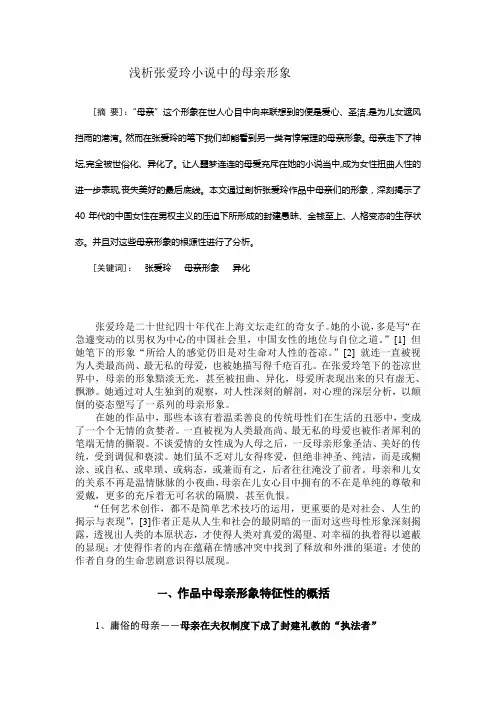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
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
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
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
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
”[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
”[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
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
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
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
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
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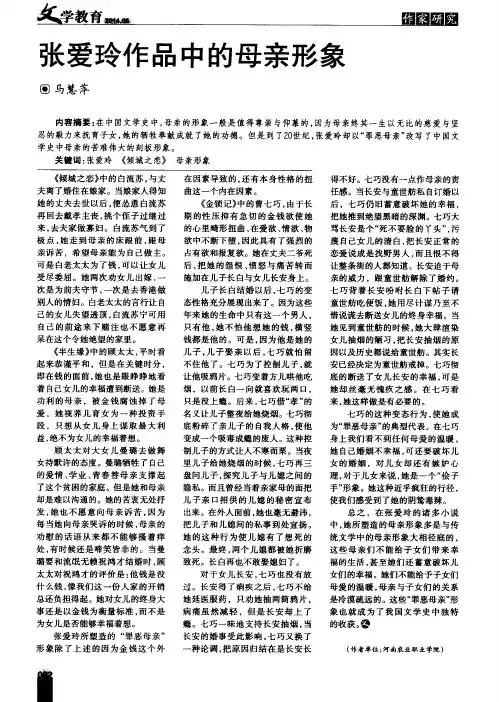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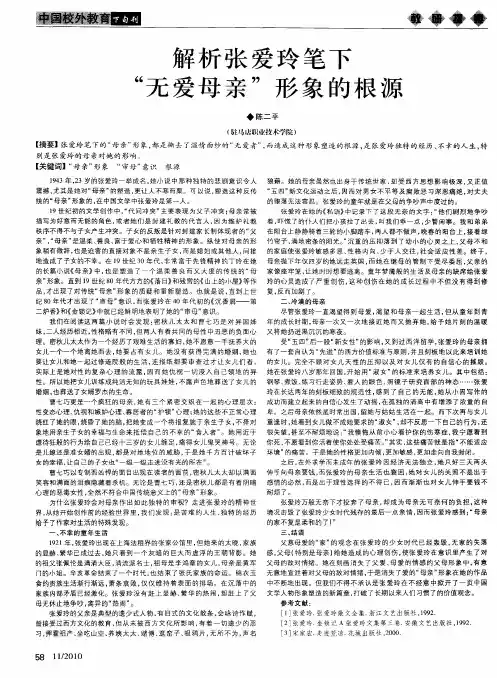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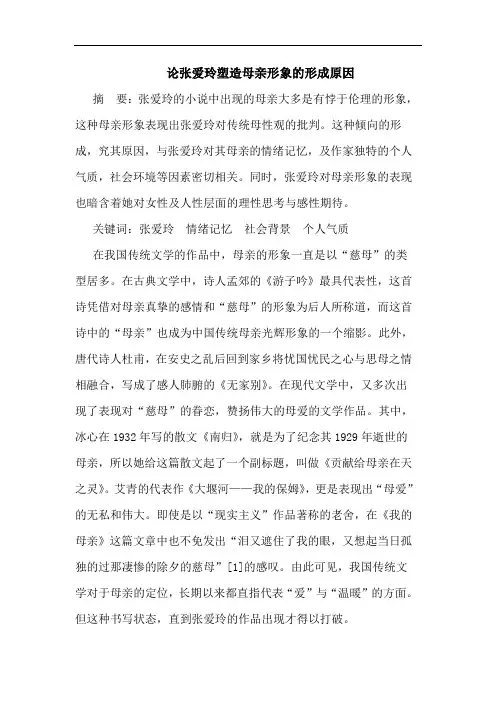
论张爱玲塑造母亲形象的形成原因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的形象,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
这种倾向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及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表现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情绪记忆社会背景个人气质在我国传统文学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一直是以“慈母”的类型居多。
在古典文学中,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最具代表性,这首诗凭借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和“慈母”的形象为后人所称道,而这首诗中的“母亲”也成为中国传统母亲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
此外,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家乡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写成了感人肺腑的《无家别》。
在现代文学中,又多次出现了表现对“慈母”的眷恋,赞扬伟大的母爱的文学作品。
其中,冰心在1932年写的散文《南归》,就是为了纪念其1929年逝世的母亲,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表现出“母爱”的无私和伟大。
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作品著称的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也不免发出“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1]的感叹。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的定位,长期以来都直指代表“爱”与“温暖”的方面。
但这种书写状态,直到张爱玲的作品出现才得以打破。
《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的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
《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并且作家选择以两性、婚姻和亲情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生活。
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书写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
她笔下的母亲大都是自私,软弱,狠毒,愚昧的形象,并呈现出扭曲和病态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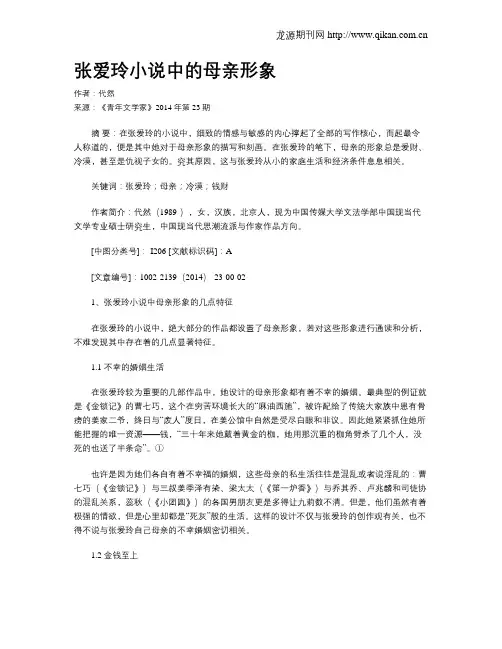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者:代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3期摘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细致的情感与敏感的内心撑起了全部的写作核心,而起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其中她对于母亲形象的描写和刻画。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总是爱财、冷漠,甚至是仇视子女的。
究其原因,这与张爱玲从小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条件息息相关。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冷漠;钱财作者简介:代然(1989-),女,汉族,北京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021、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几点特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设置了母亲形象,若对这些形象进行通读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几点显著特征。
1.1 不幸的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较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中,她设计的母亲形象都有着不幸的婚姻。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金锁记》的曹七巧,这个在穷苦环境长大的“麻油西施”,被许配给了传统大家族中患有骨痨的姜家二爷,终日与“废人”度日,在姜公馆中自然是受尽白眼和非议。
因此她紧紧抓住她所能把握的唯一资源——钱,“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①也许是因为她们各自有着不幸福的婚姻,这些母亲的私生活往往是混乱或者说淫乱的:曹七巧(《金锁记》)与三叔姜季泽有染、梁太太(《第一炉香》)与乔其乔、卢兆麟和司徒协的混乱关系,蕊秋(《小团圆》)的各国男朋友更是多得让九莉数不清。
但是,他们虽然有着极强的情欲,但是心里却都是“死灰”般的生活。
这样的设计不仅与张爱玲的创作观有关,也不得不说与张爱玲自己母亲的不幸婚姻密切相关。
1.2 金钱至上张爱玲小说母亲形象的第二点特征,是他们都将金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为了钱,母亲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是女儿。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半生缘》,顾曼祯的姐姐以其做诱饵,致使祝鸿才逼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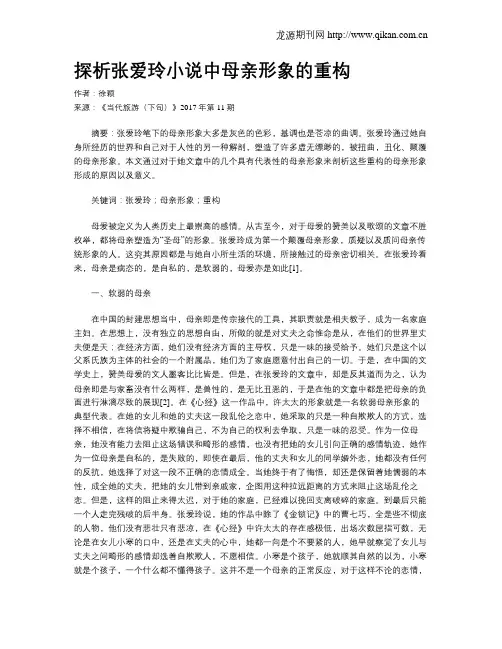
探析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重构作者:徐颖来源:《当代旅游(下旬)》2017年第11期摘要: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大多是灰色的色彩,基调也是苍凉的曲调。
张爱玲通过她自身所经历的世界和自己对于人性的另一种解剖,塑造了许多虚无缥缈的,被扭曲,丑化、颠覆的母亲形象。
本文通过对于她文章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母亲形象来剖析这些重构的母亲形象形成的原因以及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重构母爱被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感情。
从古至今,对于母爱的赞美以及歌颂的文章不胜枚举,都将母亲塑造为“圣母”的形象。
张爱玲成为第一个颠覆母亲形象,质疑以及质问母亲传统形象的人。
这究其原因都是与她自小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过的母亲密切相关。
在张爱玲看来,母亲是病态的,是自私的,是软弱的,母爱亦是如此[1]。
一、软弱的母亲在中国的封建思想当中,母亲即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其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在思想上,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所做的就是对丈夫之命惟命是从,在他们的世界里丈夫便是天;在经济方面,她们没有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只是一味的接受给予。
她们只是这个以父系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的一个附属品,她们为了家庭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于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赞美母爱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
但是,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却是反其道而为之,认为母亲即是与家畜没有什么两样,是兽性的,是无比丑恶的,于是在他的文章中都是把母亲的负面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2]。
在《心经》这一作品中,许太太的形象就是一名软弱母亲形象的典型代表。
在她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一段乱伦之恋中,她采取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选择不相信,在将信将疑中欺骗自己,不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只是一味的忍受。
作为一位母亲,她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错误和畸形的感情,也没有把她的女儿引向正确的感情轨迹,她作为一位母亲是自私的,是失败的,即使在最后,他的丈夫和女儿的同学婚外恋,她都没有任何的反抗,她选择了对这一段不正确的恋情成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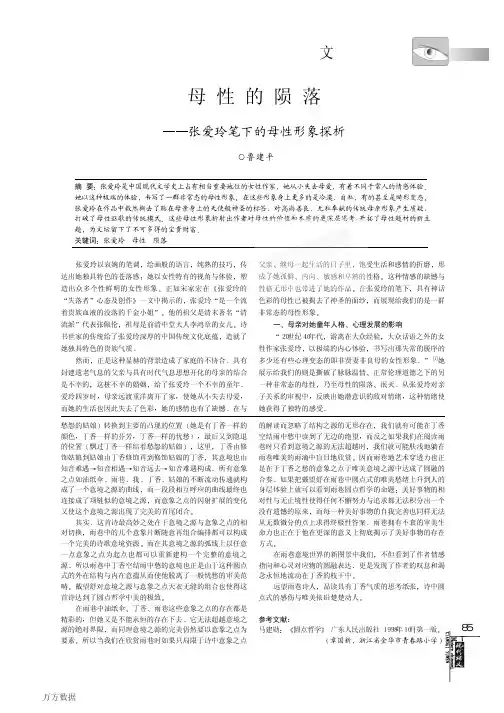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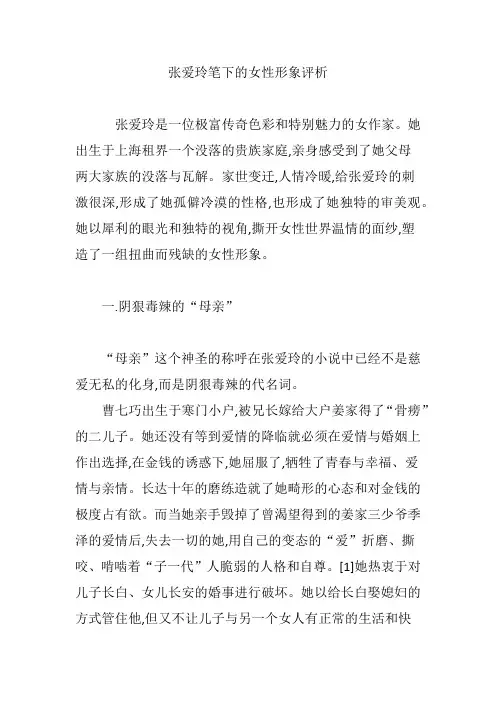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评析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
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
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
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一.阴狠毒辣的“母亲”“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不是慈爱无私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
曹七巧出生于寒门小户,被兄长嫁给大户姜家得了“骨痨”的二儿子。
她还没有等到爱情的降临就必须在爱情与婚姻上作出选择,在金钱的诱惑下,她屈服了,牺牲了青春与幸福、爱情与亲情。
长达十年的磨练造就了她畸形的心态和对金钱的极度占有欲。
而当她亲手毁掉了曾渴望得到的姜家三少爷季泽的爱情后,失去一切的她,用自己的变态的“爱”折磨、撕咬、啃啮着“子一代”人脆弱的人格和自尊。
[1]她热衷于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婚事进行破坏。
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
她整夜不睡地盘问儿子的私生活,并且在亲家母在场的麻将桌上将儿子与儿媳的隐私公之于众,并百般羞辱儿媳,使亲家母都不忍听下去而离开,直至把儿媳妇活活逼死。
因为在儿媳身上她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
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对于女儿迟来的爱情,曹七巧不但没有祝福,反而处心积虑的加以破坏,看到女儿与童世舫和谐交往,并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与童世舫谈婚论嫁,便大骂童世舫是看上了她家的钱财,后来又无端地辱骂女儿长安不守妇道,品行不端,并对女婿童世舫散布阴森的谎言,说女儿是一个断不了瘾的烟鬼,从而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如此母亲,如此婆婆!正是她对儿子变态的占有,对女儿变态的嫉妒使她迸发出了无穷的复仇欲,最终驱使她失掉了与生俱来的母性。
密秋儿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川娥的母亲(《花凋》)、顾太太(《十八春》)等人物跟曹七巧一样都是狠毒异常、残害人命的暴君“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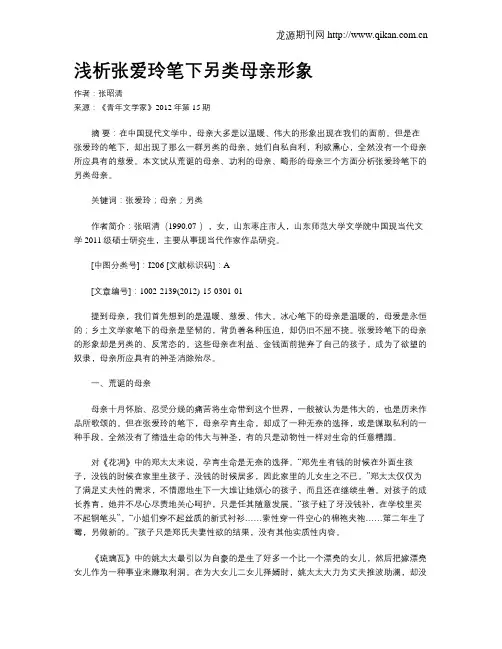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笔下另类母亲形象作者:张昭清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5期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母亲大多是以温暖、伟大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出现了那么一群另类的母亲,她们自私自利,利欲熏心,全然没有一个母亲所应具有的慈爱。
本文试从荒诞的母亲、功利的母亲、畸形的母亲三个方面分析张爱玲笔下的另类母亲。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另类作者简介:张昭清(1990.07-),女,山东枣庄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5-0301-01提到母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温暖、慈爱、伟大。
冰心笔下的母亲是温暖的,母爱是永恒的;乡土文学家笔下的母亲是坚韧的,背负着各种压迫,却仍旧不屈不挠。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的形象却是另类的、反常态的。
这些母亲在利益、金钱面前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了欲望的奴隶,母亲所应具有的神圣消除殆尽。
一、荒诞的母亲母亲十月怀胎、忍受分娩的痛苦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一般被认为是伟大的,也是历来作品所歌颂的。
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孕育生命,却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或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手段,全然没有了缔造生命的伟大与神圣,有的只是动物性一样对生命的任意糟蹋。
对《花凋》中的郑太太来说,孕育生命是无奈的选择。
“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郑太太仅仅为了满足丈夫性的需求,不情愿地生下一大堆让她烦心的孩子,而且还在继续生着。
对孩子的成长养育,她并不尽心尽责地关心呵护,只是任其随意发展。
“孩子蛀了牙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
”孩子只是郑氏夫妻性欲的结果,没有其他实质性内容。
《琉璃瓦》中的姚太太最引以为自豪的是生了好多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女儿,然后把嫁漂亮女儿作为一种事业来赚取利润。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引言:简要概括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她成长、生活的背景和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
“母亲”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歌颂性形象,但张爱玲小说中母亲的形象有多种面貌并且大多是冷漠的负面形象。
对其作品中塑造的母亲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概括,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对母亲形象的颠覆,源于张爱玲独特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思考。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在张爱玲笔下所呈现的女性是悲剧的,是无主张的,异化的。
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剧,在张爱玲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然而,在这些作为悲剧的女性中,母亲这一形象奴化变态且面目皆非似乎更让人感到凉入骨髓。
现把她们分为三大类型:1、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母亲2、病态的母亲。
3、传统世俗的母亲(一)被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母亲1、《十八春》中的顾太太眼睁睁地看着二女儿近乎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将要被无情地断送,却在金钱的诱惑下心安理得地走开了,独自留下曼桢在那呼天抢地。
2、《花凋》里的郑夫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私房钱而不肯给女儿治病,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
3、《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都是在亲情与金钱之中选择了金钱。
4、小结(二)病态的母亲1、《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家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歇斯底里。
当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她的变态心理,愈发不可收拾。
2、《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真的不在乎葛薇龙的遭遇感受。
她不把薇龙当成亲人,反而视之为手中的一名棋子、一项财产、一副工具,好让她能不断吸引更多有钱有权势的男人,以维持她纸醉金迷的生活。
3、《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畸形家教导致女儿靡丽笙、素西斯视正常的性行为为兽行,结果逼死了两个女儿的丈夫。
她不但毁了子女的人性,也毁了子女的幸福生活。
㊀㊀收稿日期:2020G12G29㊀㊀作者简介:杜淑娟(1983 ),女,安徽宿州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0卷㊀第2期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 o l .20N o .22021年4月J O U R N A LO F HU A I B E IV O C A T I O N A L A N DT E C HN I C A LC O L L E G EA pr .2021论张爱玲小说中母爱的缺失杜淑娟(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阜阳㊀236037)摘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里,童年缺失母爱的体验和特殊的成长经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她以独特的视角和技巧,在作品中颠覆着母亲的慈爱形象㊁流露着母爱的缺失对子女一生的影响,并以细腻的笔法在不同作品中诉说着这种缺失,以及隐藏在母爱缺失背后的复杂人性.关键词:张爱玲;母爱缺失;人性中图分类号:I 206.6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1G8275(2021)02G0068G03㊀㊀母亲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中被赋予神圣的形象,提到母亲这个话题,让人不由自主地会想到母爱.冰心的作品中歌颂母爱㊁赞扬母爱,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幅充满温情的母爱画面.而在张爱玲笔下,却毫无留情地打破了笼罩在母亲头上的各种神圣光环.她以犀利的语言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在缺少母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那么,张爱玲小说中母爱缺失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母爱缺失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母爱缺失的背后又体现了她对人性怎样的洞察和解剖.本文尝试着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解读,以期对张爱玲获得一个更深入㊁更全面的认识.一㊁小说中母爱缺失的成因 成长的经历童年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童年的经历和遭遇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作家的创作无形中会受到其早期生活的影响,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没落官宦家庭,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四岁时,母亲黄逸梵就远离家乡出国留学,直到张爱玲八岁时,母亲才重新回到家.张爱玲由此欣喜地感受到 一切都不同了 .[1]118但这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就伴随着父母的离婚而结束.母亲又动身去了国外,临行前,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小小的张爱玲虽有太多不舍,但依然只能望着母亲的背影渐渐消失.留下张爱玲 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1]120.母亲地离开使童年的张爱玲于没落的阴影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但另一方面,缺失母爱的心灵伤痛也在煎熬着她,并伴随着她的成长,影响着她以后的创作. 这损伤并未因 辽远而神秘 的诗意想象稍有减缓,而是在 几次来了又走了 的持续磨损中,结成难以平复的硬痂.[2]39母亲对于张爱玲而言只是一个冷漠而又生疏的影子.父亲再婚后,她与后母互相仇视,两个母亲在幼小的张爱玲心中种下了没有爱的种子.张爱玲在«流言»中写道:我后母也吸鸦片 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但她的内心还是渴望母爱的: 母亲这一去便是数不清的年华.一日一日,燕子在每个春日里衔泥而来,小爱玲在窗口郁郁地等待一个叫作 母亲 的美丽女人.这样的等待使得爱玲的童年极为不愉快. [3]陈思和在其«读张爱玲的‹对照记›»一文中这样分析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 我过去读张爱玲的书,一直有一种感觉,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母亲的压抑而生出逆反心理 牺牲了对儿女的母爱和对家庭的依赖 是以牺牲子女对母爱的渴望为代价的.其代价的结果,是张爱玲本能地背离了她母亲的道路㊁文化和人生追求. [4]正是这种母爱缺失的童年经历,使她无法像冰心那样写出歌颂母爱的文字.她把这种体验都写在了她笔下的人物里,在自由的文学世界里倾诉着母亲形象的坍塌和母爱的缺失.以致 成年后的张爱玲内敛孤僻,略含冷意的处世态度里,有一种难以亲近的生硬与偏狭,这样的性格形成与其缺乏温暖的童年记忆,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2]39二㊁张爱玲小说中母爱缺失的表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张爱玲凭借着她的才华和个性大放异彩.她的86小说正如她的人生一样:美丽而苍凉.夏志清称张爱玲 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张爱玲忠实于自己童年缺失性母爱的情感体验,多次流露出对母爱的质疑,似乎在潜意识里把这种缺失性的情感体验带入到她的小说中,将长白㊁长安㊁白流苏㊁曼桢㊁川嫦等置于和自己相似的经历,以求得情感上的共鸣.曾被傅雷誉为 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 .[5]158曹七巧在黄金的光环和长期的性压抑下,开始对生活在她周围的人进行报复.面对一双儿女,这位母亲已完全变成施虐者,她亲手破坏了长白㊁长安的幸福.儿子娶了媳妇,并占了她的儿子, 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 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 他娶了亲. [6]154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她将儿子留在身边吸鸦片,又百般地挖苦儿媳,致使芝寿凄惨地死去,也葬送了长白的一生.而对女儿长安,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七巧就去学校大吵大闹,为此也葬送了长安的学业.她逼女儿缠脚,她看不得长安在恋爱后日渐红润,背地里不知恨了多少回,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嚷 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 [6]161她随便撒个谎: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 就断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在这里,七巧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位母亲对子女最基本的关爱,她变态扭曲的心理已经容不下任何美好的东西,更不用说母爱了.她要用那沉重的黄金枷锁去疯狂地扼杀身边的一切,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张爱玲与母亲之间是一种难以诉说的关系,她感到的也只是一种生疏,除了冷漠还是冷漠. 文学作品抒写的对象,有时隐含着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轨迹.阅读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我们不难窥见她不幸的自身经历,以及社会环境㊁战争因素㊁西方文化的浸润给她带来的影响. [7]«倾城之恋»中,离婚后的白流苏在接到前夫去世的消息,一家人在谈论她的去留问题时,哥嫂的恶言恶语充斥着白流苏的耳朵.她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抛下一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 . 母亲的冷漠和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明白了她所要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作为母亲,白老太太在女儿寻求安慰和依靠的时候是缺席的,母爱是缺失的.在«十八春»中,曼桢的母亲顾太太身上更多的是市侩性,她对女儿的爱都被金钱给腐蚀完了.被软禁在大姐曼璐家达一年之久的曼桢又何尝不是盼望着母亲的帮助和营救,整个骗局过程,顾太太是知道的,但当她拿钥匙开门,手触碰到曼璐贿赂她的钞票时, 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 面对世钧,她守口如瓶,该说的没说,眼睁睁地看女儿曼桢跳进火坑.顾太太看到的只有物质和金钱,看不到母爱与女儿,她在抛弃女儿曼桢的同时也抛弃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和温存.所以,在张爱玲看来, 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 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1]184G185三、母爱缺失的背后是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张爱玲是一位最具才情的作家.在熠熠发光的文学星河中,她用文字和才华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画面.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因为战争,她奔波于上海和香港之间,这其中的悲与凉㊁痛和恨,无形中成了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和底色记忆.她的小说多写市井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 她以家 这个小世界来体现平常人的世间悲欢离合,以及隐藏在悲欢下的丰富多彩的人性,表现了她对历史意义上追崇的 伟大的人生 的消解,以及对个体生命千姿百态的生存状态的尊重.文学的切入点永远是 人 ,永远是对人性的考察和探究. [8]20张爱玲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人性的洞察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在«金锁记»中,我们不能只看到七巧对儿女母爱的扭曲毁掉了长白㊁长安的幸福,还应体会在母爱缺失的背后,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曹七巧是一位市井之女,家里是开麻油店的,曾经与猪肉店老板打情骂俏,她的身体充满着情欲和欲望,而嫁到姜公馆后守着一位骨痨病的丈夫,长期的欲火的煎熬,让她对子女的爱是扭曲的㊁变态的.爱情折磨了七巧的一生, 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 [5]156作为市井之女的曹七巧,她身上也有着对爱的渴望和向往,但为了守住黄金的链条,婆家恨她㊁自己的孩子也恨她.最后的眼泪只让它渐渐自己干了,显然这里有作者对七巧的怜悯.尽管曹七巧身上寄托着张爱玲对黄金枷锁如何扼杀人性的批判,但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曹七巧的同情与关爱,正是因为七巧没有96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1年第2期㊀获得正常的人生之爱,她才扭曲了灵魂成为变态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仍然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所以,在创作曹七巧之后,张爱玲一再表白自己不愿创造 彻底的人物 ,是因为她害怕人们将七巧全然冷漠,从而不能体会七巧的生存处境.在这里,对于人性的异化㊁变态㊁扭曲,以及孤独㊁冷漠㊁缺少爱,张爱玲的刻画是细致入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以其传奇的色彩在不断绽放,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更是大放光芒.她小说的伟大之处,不是对时代主题的探讨而是对人性的洞察.她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人性真相,母亲也不例外,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冷漠㊁无情㊁残忍地对待周围的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花凋»中的郑夫人 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因为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自私自利,不愿意给女儿看病,导致川嫦一寸一寸地死去.«十八春»中的顾太太为了金钱是可以卖女儿的,纵容曼璐荒唐的行为并成了曼璐的帮凶.同时,曼璐去做舞女,她是默认的,她那仅有一点的母性也被金钱给淹没了.母爱的缺失达到这种程度,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张爱玲对人性自私劣根性地揭露,人性自私的劣根性被人与人之间蒙上了一层面纱,哪怕是最亲近的母女关系.当张爱玲赤裸裸地揭开这层面纱,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了利益的需求,母爱也不再是伟大无私的神话.张爱玲正是用她那华丽的文笔书写着无奈的人性.她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场景中,拷问出人性的真.张爱玲自认其小说中 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1]92G93作者正是在这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人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越读越能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散发着芳香的气息.傅雷在他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以«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为例,也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了解读和评价.他认为张爱玲的作品 中西融合,通透如玉,新旧糅合,意境交错,收放自如,火候把握得好. [8]16是 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 [5]158虽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定位上,张爱玲与鲁迅不能并列, 但是在人性探索这一方面,张爱玲的确是可以和鲁迅先生并称的,他们都试图在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来谈论人性. [9]胡兰成也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10]四㊁结语张爱玲以独特的才情和细腻的笔法,在文学天地中独占一席之地.她的作品正如她的一生一样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苍凉.张爱玲小说中母爱的缺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与她的家庭环境㊁母亲的远离㊁不愉快的童年经历都有关系.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 不愉快的童年. [11] 这不是真理,但此话对张爱玲至少是适用的 .[12]正是这种成长经历让她的小说中处处流露着母爱的缺失,并把这种缺失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行着对人性的洞察和解剖.张爱玲的小说是社会日常生活的写照,更是对人性复杂性㊁多元性地考察和探究.参考文献:[1]㊀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2]㊀罗玛.凝视张爱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㊀李清秋.张爱玲传[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4G15.[4]㊀陈思和.写在子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32.[5]㊀傅雷.傅雷谈文学[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6]㊀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G].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7]㊀陈坤.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 审母 情结[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5.[8]㊀杨春.叙事学理论视角下的张爱玲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㊀徐仲佳.中国现代性爱叙事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70.[10]㊀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230.[11]㊀乔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见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6.[12]㊀余斌.张爱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56.责任编辑:孙杰军07杜淑娟/论张爱玲小说中母爱的缺失。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博爱与阴性 ——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颠覆张玉琼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摘 要: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描写女性人物为主,一切缘起与因果皆是围绕女性角色铺展开来。
其中一系列母亲的形象更以“自私、卑怯”的特性被世人所知。
本文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子为例,分析张爱玲“丑化”母亲形象的原因,及张爱玲与其他五四时期的作家对母亲的不同认识,进而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形象所具有的人性弱点。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阴性[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34-02张爱玲一直都以神秘或是标新立异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无论是曾经显赫非凡的家世背景,抑或是一部部在文学界引发巨大争议的小说。
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小团圆》,母亲形象以各种性格频繁出现,她以独特的眼光对母亲形象做了颠覆,使覆盖在“母亲”这两个字上的神圣荣光被揭开,还原了一个母亲最本真的面目。
与五四文学中被神化的母亲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出了人性中固有的一些弱点,如自私、残忍、卑怯等。
一、阴冷青涩的母爱体验在张爱玲出生的时候,张氏家族显赫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她的父亲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她的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却深受五四新风的影响与感召,是一个在新时代的洪流中勇于冲破封建世俗的一个女性。
她面对丈夫的喝酒,赌博,抽鸦片,养姨太太这些恶习,不但没有纵容,或者忍气吞声,而是选择捍卫自己的权利。
时代在进步,她自然不能忍受自己的丈夫依旧保持这旧式的做派。
在她对自己的婚姻心灰意冷的时候,她选择了出国,这时的张爱玲才四岁,一分别就是四年,时间与距离将母女的感情慢慢淡化。
“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1]从小就缺失母爱的张爱玲对母亲的态度是疏离的,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过最真切的母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待她的父母离婚以后,她与母亲的距离愈发远了。
母亲形象的异化作者:温文华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2期摘要:母亲形象的典型塑造是张爱玲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视角。
因不幸的自身经历、社会环境、战争因素和西方文化等影响,张爱玲塑造的母亲形象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形象,构造的多是自私自利、乖戾粗暴、冷酷无情的形象,难逃世俗的人性丑陋,到底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金钱关系。
张爱玲无情地撕破了伟大母爱的温情面纱,展示了“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1],母性只是“兽性的善”人生观。
母爱的缺失性体验让张爱玲作品有着强烈的审母意识,让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更为立体化和人性化,同时也为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更是对时代的思考。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悲凉;人性思考[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2-0-02“她一方面以理性理智的视点观察着,又以奢华古韵的文锋描绘着人性的荒凉与悲哀。
另一方面她却以自身的故事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2]张爱玲作品展示的是人精神的堕落和不安,揭露的是人性的脆弱和悲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入木三分的母亲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
那么张爱玲的审母情结是何处而来,又是“情”归何处呢?一、“审母”情结从何处来(一)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张爱玲所处的复杂的社会背景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观。
她生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但过惯了贵族小姐生活的她却与这殖民色彩浓厚、充斥现代文明的大都市格格不入。
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现代消费的刺激下,外来文化的多元化,让都市人渐渐形成可恶的拜金主义,过着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新时代”下的旧东西在变化,那就是传统伦理道德一种的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发建立在金钱权力上,直接导致在日渐动荡的冷漠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畸形的渴望是小说世界中人物荒凉,母爱异化的现实基础。
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
[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审母”意识根源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
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
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
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
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
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
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
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
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
她用近于虐待狂般的行为给自己已经十三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
无论是儿媳还是准女婿的出现,都是对她地位的威胁,于是她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让自己的子女也“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以专制而凶悍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密秋儿太太却以满面笑容和满面的泪痕隐藏着杀机。
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密秋儿都是有着阴暗心理的恶毒女
性,全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
为什么张爱玲会对母亲作出如此独特的审视?走进张爱玲的精神世界,从她开始创作前的经验世界里,我们发现:是苦难的人生、独特的经历给予了作家对生活的特殊发现。
一、不幸的童年生活
1921年,张爱玲出现在上海法租界的张家公馆里,但她来的太晚,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过去,她只看到一个灰暗的巨大而虚浮的王朝背影。
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
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张氏家族的命运。
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渐行渐远,萧条衰败,仅仅维持着表面的排场。
在沉落中的家族内部矛盾已经激化。
张爱玲没有赶上显赫、繁华的热闹,却赶上了父母无休止地争吵,离异的“热闹”。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条,会咏诗作赋,曾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但从未被西方文化所影响,有着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养姨太太、赌博、逛窑子、吸鸦片,无所不为,声名狼藉。
她的母亲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对男女不平等及腐败恶习深恶痛绝,对丈夫的堕落无法容忍。
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
张爱玲在她的《私语》中记录下了这段无奈的文字:“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
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沉重的压抑落到了幼小的心灵之上,父母不和的家庭使张爱玲敏感多思、性格内向、少于人交往,社会适应性差。
终于,母亲抛下年仅四岁的她远走英国,而她在继母的管制下受尽委屈,父亲的家像座牢笼,让她时时想要逃离。
童年梦魇般的生活及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这种创伤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加剧了。
二、冷漠的母亲
尽管张爱玲一直渴望得到母爱,渴望和母亲一起生活,但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抛弃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黒沉沉的寒夜。
受“五四”后一股“新女性”的影响,又到过西洋留学,张爱玲的母亲拥有了一套自认为“先进”的西方价值标准与原则,并且刻板地以此来培训她的女儿。
完全不顾对女儿天性的压抑以及对女儿仅有的自信心的摧毁。
她在张爱玲八岁那年回国,开始用“淑女”的标准来培养女儿。
其中包括:钢琴、煮饭、练习行走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的神态……张爱玲在长达两年的刻板细致的规范性,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她从小因写作的成功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在孤独的清高中有增添了浓重的自卑。
之后母亲依然是时常出国,留她与姑姑生活在一起。
而下次再与女儿重逢时,她看到女儿做不成她要求的“淑女”,却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还很失望,甚至不耐烦地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到你死,不愿看到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其实,这些痛苦就是指“不能适应环境”的痛苦。
于是她的性格更加内倾,更加敏感,更加走向自我封闭。
之后,在外求学而未成年的张爱玲因经济无法独立,她只好三天两头伸手向母亲要钱,而张爱玲的母亲生活也窘困,她对女儿的关照不是出于感情的必然,而是出于理性选择的不得已,因而渐渐也对女儿伸手要钱不耐烦了。
张爱玲万般无奈下才投奔了母亲,却成为母亲无可奈何的负担,这种境况击毁了张爱玲少女时代残存的最后一点亲情,因而张爱玲感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三、结语
父慈母爱的“家”的观念在张爱玲的少女时代已经轰毁,无家的失落感,父母(特别是母亲)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张爱玲在意识里产生了对父母的敌对情绪。
她在刻画消失了父爱、母爱的情感的父母形象中,有意无意地宣泄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于是消失了爱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张爱玲在不经意中掀开了一页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篇章,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宋家宏.走进荒凉.花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