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精选)
- 格式:doc
- 大小:47.00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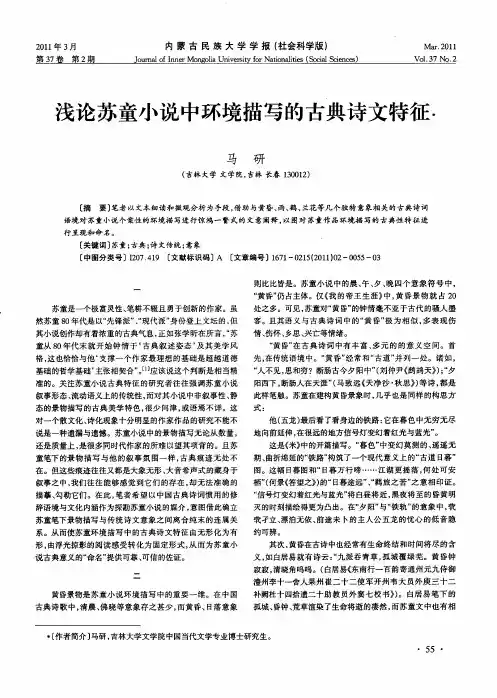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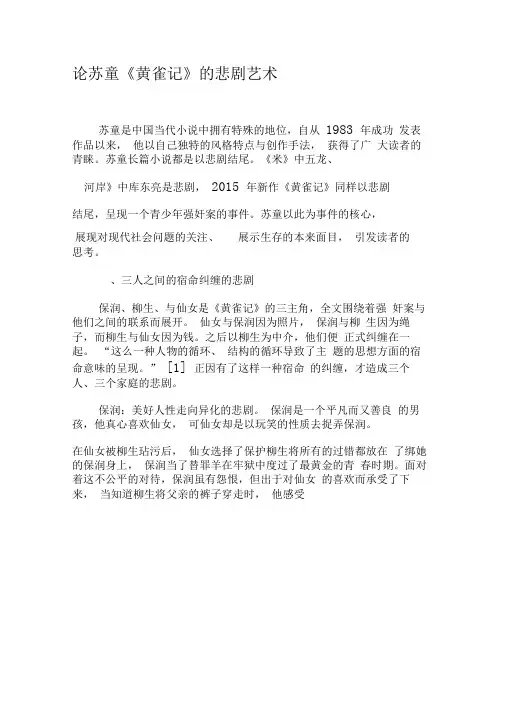
论苏童《黄雀记》的悲剧艺术苏童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拥有特殊的地位,自从1983 年成功发表作品以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与创作手法,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苏童长篇小说都是以悲剧结尾。
《米》中五龙、河岸》中库东亮是悲剧,2015 年新作《黄雀记》同样以悲剧结尾,呈现一个青少年强奸案的事件。
苏童以此为事件的核心,展现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展示生存的本来面目,引发读者的思考。
、三人之间的宿命纠缠的悲剧保润、柳生、与仙女是《黄雀记》的三主角,全文围绕着强奸案与他们之间的联系而展开。
仙女与保润因为照片,保润与柳生因为绳子,而柳生与仙女因为钱。
之后以柳生为中介,他们便正式纠缠在一起。
“这么一种人物的循环、结构的循环导致了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
” [1] 正因有了这样一种宿命的纠缠,才造成三个人、三个家庭的悲剧。
保润:美好人性走向异化的悲剧。
保润是一个平凡而又善良的男孩,他真心喜欢仙女,可仙女却是以玩笑的性质去捉弄保润。
在仙女被柳生玷污后,仙女选择了保护柳生将所有的过错都放在了绑她的保润身上,保润当了替罪羊在牢狱中度过了最黄金的青春时期。
面对着这不公平的对待,保润虽有怨恨,但出于对仙女的喜欢而承受了下来,当知道柳生将父亲的裤子穿走时,他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在柳生婚礼后的新房将其杀害,三人之间的纠缠彻底断了。
柳生:“逃避”责任到最终“死亡”的悲剧。
柳生在青春期犯下了强奸事件,但他没直面错误,选择了逃避,让保替他遭受牢狱之灾。
柳生虽获得了一时的人身自由,但付出了一生的心灵怕。
她一回来,他犯罪的青春也回来了,一个紊乱的记忆也回来了。
” [2] 那隐藏的不安,随时可以将柳生吞没。
当保润出来,当初的三人又一次聚集在了一起,柳生愧对于仙女,也愧对于保润。
柳生照顾保润的祖父、为仙女讨债、照顾怀了孕的仙女,只为承担自己曾经逃避过的过错。
当柳生放下曾经,迈向美好未来时,却又被保润所杀。
柳生只有死亡,才可以得到最后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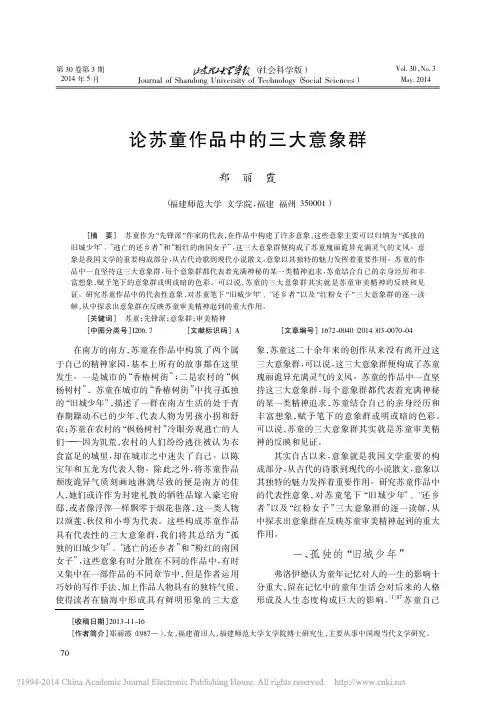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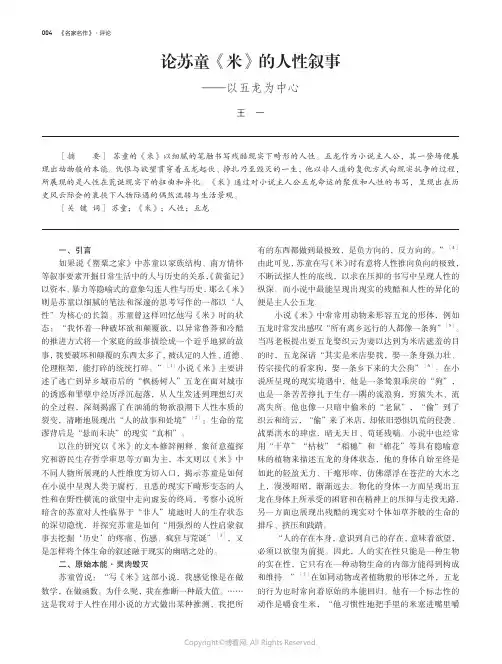
004《名家名作》·评论[摘 要] 苏童的《米》以细腻的笔触书写残酷现实下畸形的人性。
五龙作为小说主人公,其一登场便展现出动物般的本能。
仇恨与欲望贯穿着五龙起伏、挣扎乃至毁灭的一生,他以非人道的复仇方式向现实抗争的过程,所展现的是人性在荒诞现实下的扭曲和异化。
《米》通过对小说主人公五龙命运的聚焦和人性的书写,呈现出在历史风云际会的裹挟下人物际遇的偶然流转与生活景观。
[关 键 词] 苏童;《米》;人性;五龙论苏童《米》的人性叙事——以五龙为中心王 一一、引言如果说《罂粟之家》中苏童以家族结构、南方情怀等叙事要素开掘日常生活中的人与历史的关系,《黄雀记》以资本、暴力等隐喻式的意象勾连人性与历史,那么《米》则是苏童以细腻的笔法和深邃的思考写作的一部以“人性”为核心的长篇。
苏童曾这样回忆他写《米》时的状态:“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
”[1]小说《米》主要讲述了逃亡到异乡城市后的“枫杨树人”五龙在面对城市的诱惑和罪孽中经历浮沉起落,从人生发迹到理想幻灭的全过程,深刻揭露了在汹涌的物欲浪潮下人性本质的裂变,清晰地展现出“人的故事和处境”[2]:生命的荒谬背后是“悬而未决”的现实“真相”。
以往的研究以《米》的文本修辞阐释、象征意蕴探究和游民生存哲学审思等方面为主,本文则以《米》中不同人物所展现的人性维度为切入口,揭示苏童是如何在小说中呈现人类于腐朽、丑恶的现实下畸形变态的人性和在野性横流的欲望中走向虚妄的终局,考察小说所暗含的苏童对人性临界于“非人”境地时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隐忧,并探究苏童是如何“用强烈的人性启蒙叙事去挖掘‘历史’的疼痛、伤感、疯狂与荒诞”[3],又是怎样将个体生命的叙述融于现实的幽暗之处的。
二、原始本能·灵肉毁灭苏童曾说:“写《米》这部小说,我感觉像是在做数学,在做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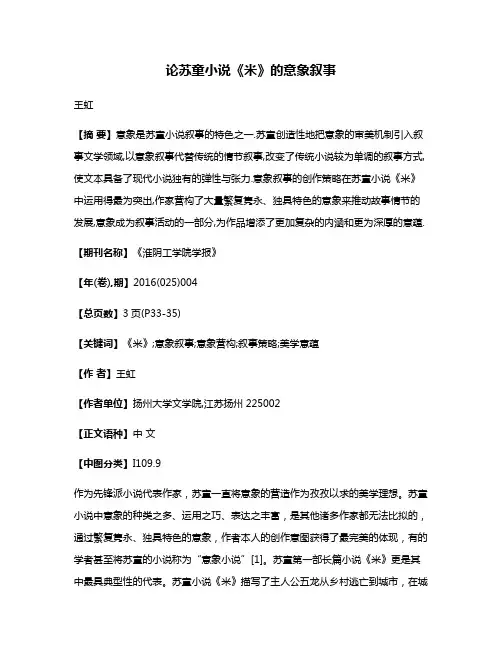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米》的意象叙事王虹【摘要】意象是苏童小说叙事的特色之一.苏童创造性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叙事文学领域,以意象叙事代替传统的情节叙事,改变了传统小说较为单调的叙事方式,使文本具备了现代小说独有的弹性与张力.意象叙事的创作策略在苏童小说《米》中运用得最为突出,作家营构了大量繁复隽永、独具特色的意象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意象成为叙事活动的一部分,为作品增添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和更为深厚的意蕴.【期刊名称】《淮阴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25)004【总页数】3页(P33-35)【关键词】《米》;意象叙事;意象营构;叙事策略;美学意蕴【作者】王虹【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9.9作为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苏童一直将意象的营造作为孜孜以求的美学理想。
苏童小说中意象的种类之多、运用之巧、表达之丰富,是其他诸多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通过繁复隽永、独具特色的意象,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获得了最完美的体现,有的学者甚至将苏童的小说称为“意象小说”[1]。
苏童第一部长篇小说《米》更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
苏童小说《米》描写了主人公五龙从乡村逃亡到城市,在城市里发迹和幻灭,最终死于归乡途中的“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2]。
作者巧妙地将伦理叙事和意象写作结合起来,在小说中精心营造大量独具特色的意象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叙事的明晰性和意象的含蓄性相得益彰,达到了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和对亲情伦理关系更为彻底的拆解。
可以说,《米》就是一个“意象集”。
“米”是小说的中心意象,是与食欲、情欲、权欲等欲望皆有所关联的意象。
作者构思精巧,实在近乎一米一世界的意境了。
回顾五龙的一生:逐米而来——拥米而生——为米而死。
米,已经不仅是五龙生命的保障,而且已经与他的一生发生了根本的关联,使五龙的一生有了宿命和轮回的意味。
“火车”也是小说《米》中的典型意象之一,具有象征逃亡、回归和死亡的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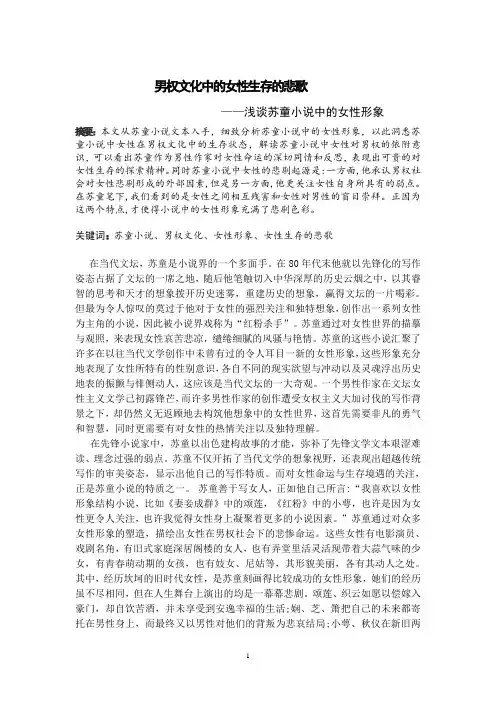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
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
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
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
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
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
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
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
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
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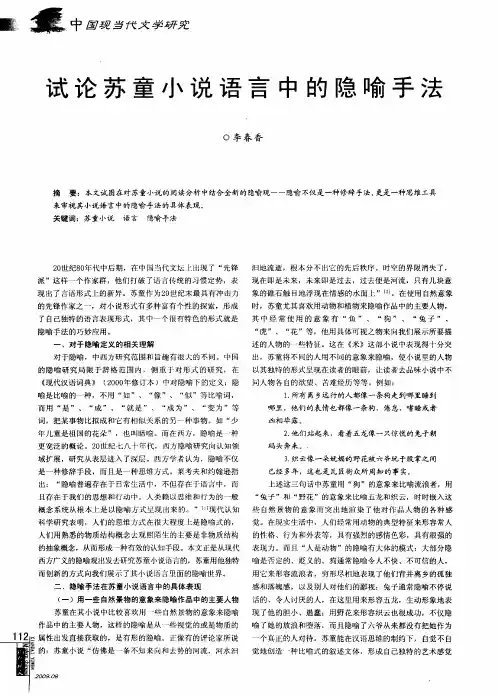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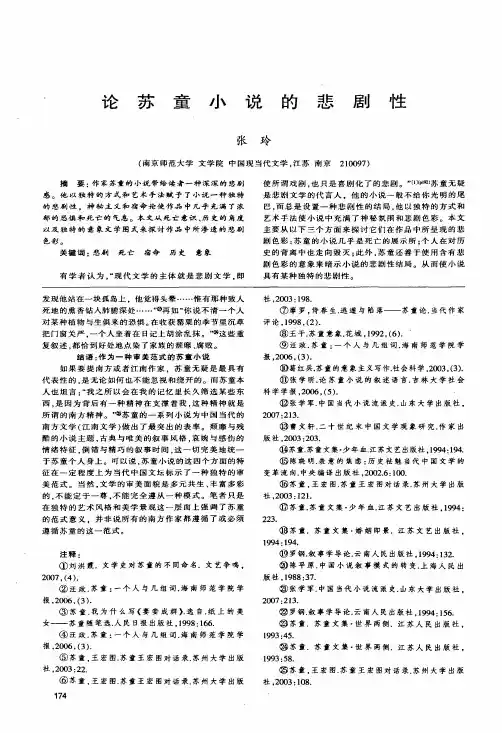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悲剧性张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苏南京210097)摘要:作家苏童的小说带给读者一种深深的悲剧感。
他以独特的方式和艺术手法赋予了小说一种独特的悲剧性.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使作品中几乎充满了浓郁的恐惧和死亡的气息。
本文从死亡意识、历史的角度以及独特的意象文学图式来探讨作品中所渗透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悲剧死亡宿命历史意象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的主体就是悲剧文学,即使所谓戏剧,也只是喜剧化了的悲剧。
”…(-m’苏童无疑是悲剧文学的代言人.他的小说一般不给你光明的尾巴.而总是设置一种悲剧性的结局.他以独特的方式和艺术手法使小说中充满了神秘氛围和悲剧色彩。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悲剧色彩:苏童的小说几乎是死亡的展示所:个人在对历史的背离中也走向毁灭;此外,苏童还善于使用含有悲剧色彩的意象来暗示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从而使小说具有某种独特的悲剧性。
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他觉得头晕……惟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o再如“你说不清一个人对某种植物与生俱来的恐惧。
在收获罂粟的季节里沉草把门窗关严.一个人坐着在日记上胡涂乱抹。
”o这些重复叙述,都恰到好处地点染了家族的颓靡、腐败。
结语:作为一种审美范式的苏童小说如果要提南方或者江南作家.苏童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和绕开的。
而苏童本人也坦言:“我之所以会在我的记忆里长久筛选某些东西.是因为背后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
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南方精神。
”@苏童的一系列小说为中国当代的南方文学(江南文学)做出了最突出的表率。
颓靡与残酷的小说主题,古典与唯美的叙事风格,哀婉与感伤的情绪特征。
倒错与精巧的叙事时间,这一切完美地统一于苏童个人身上。
可以说,苏童小说的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文坛标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
当然,文学的审美面貌是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完全遵从一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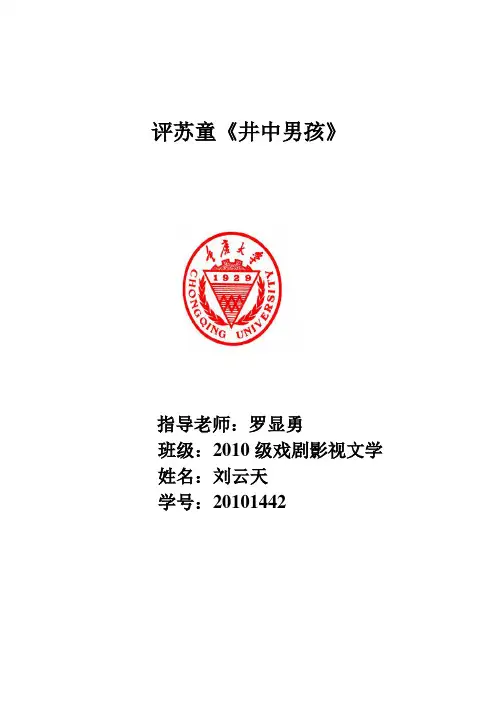
评苏童《井中男孩》指导老师:罗显勇班级:2010级戏剧影视文学姓名:刘云天学号:20101442苏童的小说,读起来总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井中男孩》也不列外。
读了很久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像一个疯子语。
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有支离破碎的几段。
读不下来,很想放弃,然而又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在牵引着你继续读下去。
这种感觉很不好却又感觉很好似得,真奇怪。
整个故事似乎读懂了,又觉得未曾读懂。
故事的有大学生同居,女孩崇拜明星,明星不断换女孩子这些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故事。
作者又似乎根本不在乎去讲这些故事,他想告诉我们故事后面的东西,又好像在让我们去猜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作者不断的写好像跟故事没有任何联系的井中男孩。
男孩(书中的我)为了去看井中倒影的男孩,去看井中男孩后面的那片天,他跳入了井中,差点淹死,父亲却救及时了他。
“我”却在大学里写了一本《井中男孩》的书,那个跳进井中的男孩却死了。
故事似乎很离奇,离奇得读不懂,又似乎这个社会的许多东西,就像随意的同居,明星崇拜等等许多表面新潮的东西,就像那个好奇的男孩的行为,怀着好奇的探究和进入,却是没有料想到的“死亡”的结局。
苏童文章的语言极富有魅力,在《井中男孩》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我想在四个方面细致分析《井中男孩》其中蕴含的奥秘。
其中包括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隐藏于冷静表述背后的情感,唯美的诗意化语言。
1,细致的动作语言我的父亲,那个南方小城里的中学老师,那个手持摇篮带子把我摇大的父亲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
他的信中闪耀着中国男人婆婆妈妈的智慧和敏感的火花。
他在信中说如今的孩子都在学习做一条现实恶棍。
你从前是那么的纯洁可爱啊。
你现在远离我们其实是在躲避我们。
你不敢让我们看见你的鬼模样,你的牙齿已经让烟熏得发黑,你的屁股让牛仔裤包得即将爆炸,你甚至有可能犯过什么罪儿进几处了吧?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回家?你不回家我也闻得见你的心脏的臭味。
你还是抽空回家吧,我们都老了,我们不放心你孤身在外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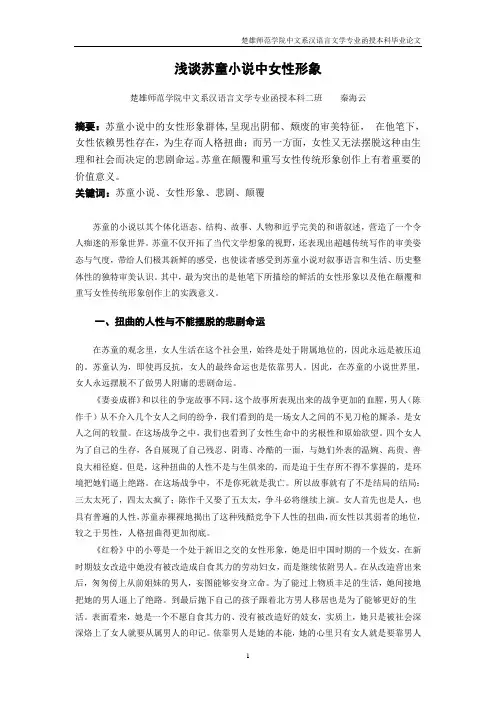
浅谈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二班秦海云摘要: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群体,呈现出阴郁、颓废的审美特征,在他笔下,女性依赖男性存在,为生存而人格扭曲;而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摆脱这种由生理和社会而决定的悲剧命运。
苏童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悲剧、颠覆苏童的小说以其个体化语态、结构、故事、人物和近乎完美的和谐叙述,营造了一个令人痴迷的形象世界。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想象的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与气度,带给人们极其新鲜的感受,也使读者感受到苏童小说对叙事语言和生活、历史整体性的独特审美认识。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以及他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的实践意义。
一、扭曲的人性与不能摆脱的悲剧命运在苏童的观念里,女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此永远是被压迫的。
苏童认为,即使再反抗,女人的最终命运也是依靠男人。
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女人永远摆脱不了做男人附庸的悲剧命运。
《妻妾成群》和以往的争宠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战争更加的血腥,男人(陈作千)从不介入几个女人之间的纷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女人之间的不见刀枪的厮杀,是女人之间的较量。
在这场战争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生命中的劣根性和原始欲望。
四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展现了自己残忍、阴毒、冷酷的一面,与她们外表的温婉、高贵、善良大相径庭。
但是,这种扭曲的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迫于生存所不得不掌握的,是环境把她们逼上绝路。
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故事就有了不是结局的结局:三太太死了,四太太疯了;陈作千又娶了五太太,争斗必将继续上演。
女人首先也是人,也具有普遍的人性,苏童赤裸裸地揭出了这种残酷竞争下人性的扭曲,而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较之于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女性形象,她是旧中国时期的一个妓女,在新时期妓女改造中她没有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是继续依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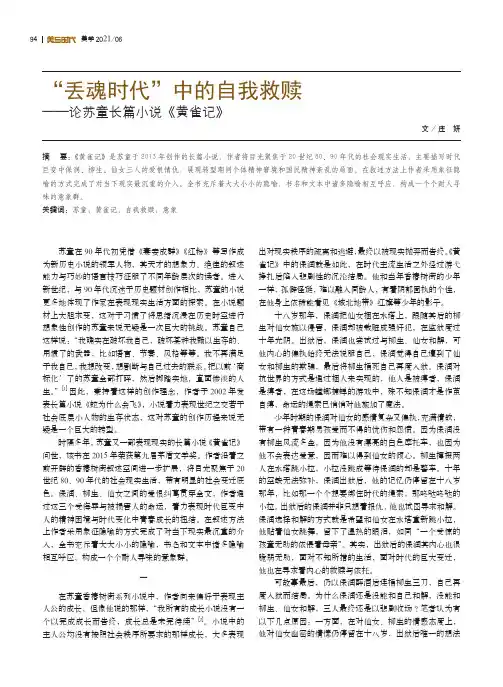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中意象的隐喻意义作者:李宁来源:《山东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04期摘要:随着社会生活中意象形态的凸显,文学作品也随之有了反映社会和人类的新角度和新方式,作家的言说方式也因之越加隐喻化和象征化。
本文观览苏童作品《妻妾成群》中的“京戏”、“菊花”、“紫藤花架”以及“井”的意象,并由此窥探这些意象背后的深层蕴含。
关键词:意象隐喻宿命女人意象以“象”为基础,经过创作者的审美筛选和读解者的审美体验,融合成一个意象整体。
小说意象是融入创作者与读解者情感意味的某种物象,它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有机结合。
苏童小说中对意象的营造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通过一种隐喻性的言说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神秘性的阅读体验。
小说《妻妾成群》中意象丰富, 这些意象所包含的隐喻性特征又为作品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美学维度。
我们可以透过文本辨析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内容。
一、京戏——宿命外生命价值的终极探寻梅珊是陈家所有女子中最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一个,她的一生走了一条与封建践道者南辕北辙之路。
但是,她的真正的生命性情又是怎样的呢?她又是通过什么在宿命之外去探寻生命的价值的呢?梅珊嫁入陈家之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戏子。
京剧这一微小的技艺使她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得以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然而,这一点表面的安稳并不能抹去梅珊心头因孤零的身世而给她带来的不安。
加上多年唱戏,被底层生活打磨出来的敢爱敢恨的个性,梅珊不甘心只成为男人们的消遣,她一定要用短暂的青春貌美换得一份持久的荣华富贵。
可是,嫁入豪门的日子并不好过,三个女人之间的争斗以及在争斗中欲盖弥彰的几代陈家女人的遭际,反而让梅珊日渐清晰地看到自己未来在陈家的命运走向。
当时的整个陈家大院是混乱的,除了与几个女人斗智斗勇之外,这个曾是京城名旦的三太太梅珊惟一的爱好便是唱戏。
她越来越怀念那段似水流年。
那时,她是众星捧月的角儿。
现在,她却成了牢笼里的金丝雀,只能自顾自美丽,只能唱着寂寞的京剧。
【高考语文】2023届第一轮复习小说专题练习——苏童小说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人民的鱼苏童春节临近,鱼的末日也来临了。
鱼在香椿树街来来往往。
多少鱼呀!有的鱼威风,是从小轿车上下来的,有的鱼坐着面包车拖拉机来,也有的鱼挂在自行车把上,委屈地晃荡了一路,撅着嘴来到居林生家的天井。
那么多鱼把柳月芳忙坏了。
她刚出门倒去一大盆污水,想起缸不够用,就跑到张慧琴家,说是腌雪里蕻。
张慧琴撇着嘴,什么雪里蕻,你们家的鱼腥一条街了。
柳月芳有点尴尬,就那么几条鱼,哪能腥一条街!我们家老居最反感别人送年货了。
不骗你,腌菜用。
柳月芳借回缸却忘了盆,后来张慧琴就敲门了。
张慧琴侧着身子看天井里的鱼,整整齐齐,像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张慧琴笑起来,腌这么多雪里蕻?人家亲眼看见,柳月芳也就不瞒了,不瞒你,都是内部价,便宜。
张慧琴也不点破,指着一只缸笑着说,怎么把鱼头扔了?柳月芳说,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张慧琴天生热心肠,后来就蹲在居家的天井里,和柳月芳组成一条流水线。
这么大一条鱼,够一大家子吃两天了。
张慧琴抚摩着一条大青鱼,你好福气呀。
什么好福气?柳月芳偏要装傻。
你好福气呀!张慧琴叹了口气。
柳月芳在昏暗的灯光下偷偷地瞟了她一眼,看见的说是一张充满妒意的脸,不如说是女邻居哀伤自怜的表情。
柳月芳没说什么,拎出一条大鲤鱼往张慧琴脚下一掷,别跟我客气,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张慧琴没有推辞,说,你不要跟我客气的。
柳月芳突然发现盆里还有一堆鱼头,原准备送给王德基,柳月芳决定改送张慧琴。
鱼头你们吃不吃?本来送王德基的,他老是帮我家拉煤,你要,就给你。
怎么不吃?张慧琴说,鱼身上的东西,除了胆都能吃,不瞒你说,我最爱吃鱼头了。
隔天柳月芳走过张慧琴家的厨房,闻到一股扑鼻的鲜香,什么菜这么香?你给我的鱼头呀,进来尝一尝?柳月芳说,我们家不吃鱼头。
话一出口便后悔,把好好的一份人情弄薄了。
鱼促进了柳月芳和张慧琴的感情。
她们互赠拿手好菜,柳月芳善于做腌鱼,这大家也能想见,但张慧琴不一样,她是巧妇能做无米之炊,菜馄饨好吃,盐水毛豆好吃,白切肚肺好吃。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摘要】苏童短篇小说《茨菰》深刻展现了悲剧意识。
人物命运的无奈、社会现实的残酷、内心矛盾的抉择、情节发展的悲情走向,交织出一幅悲剧画面。
故事结局让人扼腕叹息,意义深远而悲凉。
《茨菰》中的悲剧意识不仅反映了时代特征,更引发了人们对命运的深思。
这些深刻的描写和情感共鸣,对读者产生了启示,引发了对生活和人性的思考。
这种悲剧意识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启发了更多作家去关注人性的悲剧和内心的矛盾。
苏童通过《茨菰》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场故事,更是一次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与审视。
【关键词】引言: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正文:人物命运的无奈、社会现实的残酷、内心矛盾的抉择、情节发展的悲情走向、意义深远的结局结论:《茨菰》中悲剧意识的体现、对读者的启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 引言1.1 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是一部充满悲剧意识的作品。
通过对人物命运、社会现实、内心矛盾、情节发展以及结局的描写,苏童深刻展现了人类命运的无奈、社会现实的残酷、内心矛盾的抉择以及情节发展的悲情走向。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
在小说的结局中,苏童展现了一种深远而震撼人心的意义,为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茨菰》中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对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触碰。
这种悲剧意识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苏童通过《茨菰》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中的困境和挣扎,让我们意识到命运的无常和社会的现实,使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与快乐,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2. 正文2.1 人物命运的无奈在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中,人物命运的无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主人公茨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中,家里缺乏温暖和关爱,与母亲的关系也并不融洽。
在这样的环境下,茨菰注定了他的命运将是悲惨的。
尽管他努力地工作和努力学习,但他始终无法逃脱困境,命运的无情使他陷入了绝望之中。
2020年12月第17卷第12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Dec.2020Vol.17No.122018年苏童小说研究综述张诗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33)摘要:2018年苏童小说研究呈现着异彩纷呈的局面。
这一年,学界涌现了一系列研究苏童的学术文章,书籍等,其中不乏精深独到的优秀文章等等研究资料。
如下,本文将主要从三方面进行2018年的苏童小说研究综述:第一,内容与主题:从历史与现实;红颜与悲歌;童年与成长;逃亡与返乡;死亡与宿命;人性与欲望六类进行综述。
第二,艺术与审美:从语言与叙事,想象与意象,审美风格三个角度进行综述。
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领域和电影领域比较文学研究进行综述。
这对于苏童小说研究以及认识其研究状况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苏童小说;研究综述;主题内容;艺术审美;比较研究一、前言苏童(1963-),原名童忠贵,江苏苏州人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自从1983年,在《青春》杂志第七期发表第一篇小说《第八个铜像》,苏童便开始步入文坛。
尤其在1989年,苏童未至而立之年便写出了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
闻名遐迩的《妻妾成群》与“枫杨树系列”中的众多作品都是此时完成的。
时至今日,苏童35年连绵不断的文学创作生涯为读者、学者带来了文学盛宴,同时也为学界带来了可供探讨的文学研究资料。
而仅仅2018年期间,学界就涌现了一系列研究苏童的学术文章,书籍等,对苏童小说的内容与主题,艺术与审美,比较文学研究等方面做了分析与争鸣。
综述2018年苏童小说的研究利于更加系统理性地认识苏童小说研究现状,也利于指引未来的研究方向遥二、苏童小说主题与内容对苏童小说主题与内容的研究目前最为广泛与透彻,苏童小说涉及的主题主要分为历史与现实;红颜与悲歌;童年与成长;逃亡与返乡;死亡与宿命;人性与欲望六类。
论苏童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摘要:苏童的语言极富魅力,本文选取苏童小说中的语句,从五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其中蕴含的奥秘: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隐藏于冷静表述背后的情感、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唯美的诗意化语言。
关键词:苏童细节描写情感性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诗意化语言苏童的语言,是极富魅力和创造力的。
他总能悠闲地玩弄着诡异绮丽的诗意般语言,利用娴熟的笔触,让一个个性格扭曲而倍受忽略的人物鲜活起来。
他的作品不断地在农村和城市,过去和现在之间转换,在时空与地域的交错中,在种种充满悲观、孤独、荒谬的情节中,苏童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
一、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苏童对“白纸上好画画”满怀信心,他的小说语言常常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
在创作过程中,他仿佛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对声色、光影、触觉和味道的感觉以及那些细碎琐屑的细节,并把它们细腻地表达出来。
1、细微的动作描写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回头又看那个紫藤架,架上倏地落下两三串花,很突然的落下来,颂莲觉得这也很奇怪。
——《妻妾成群》井中的世界对颂莲来说是个黑色的诱惑,她的一系列动作都表明她想将它看清楚以便使自己不再莫名地恐惧,所以她“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 可是她却永远也不敢靠近,“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这种恐惧既是对阴森的井和那个不祥的传说,更因为对自己不可掌控的,随时可能被幽黑深井般生活所吞噬的命运的恐惧,所以她永远摆脱不了那口井的阴影。
通过动作的细微描写,含蓄地表现出颂莲矛盾、恐惧、不安的内心。
小武汉发现他的生活是被手毁坏的,也要让手来挽救,但是除了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用一只手惩罚另一只手,他并不知道怎样用一只手去挽救另一只手。
——《手》从搬尸工小武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真切感受到他人性所遭到的扭曲、毁灭与戗残。
2、景物及静物描写凝视着自己手里的一只紫檀木球,从木球上散发的是她所熟悉的那股幽香,它熏香了锦带罗裙,与女孩特有的乳香融为一体,那是媚娘的母亲与姐妹啧啧称奇的香味。
——《武则天》在武则天中作者反复描写紫檀木球的香味,这一细节描写直接关系着小说主角的心理转变,紫檀木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意象.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
端白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我看见我的手腕上、石案上还有书册上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
——《我的帝王生涯》用破碎的蛋黄来形容太阳,一方面写出了在晨雾缭绕中,阳光昏暗不明,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帝王驾崩,宫中的诡谲气氛和王朝日渐式微的命运.颂莲朝井边走去,她的身体无比轻盈,好像在梦中行路一般,有一股植物腐烂的气息弥漫井台四周,颂莲从地上拣起一片紫藤叶子细看了看,把它扔进井里。
她看见叶子像一片饰物浮在幽篮的死水之上,把她的浮影遮盖了一块,她竟然看不见自己的眼睛。
——《妻妾成群》植物腐烂的气息, 幽篮的死水,烘托出阴森恐怖的气氛,颂莲的反常举动,泄露出她虚弱,不安的内心.3、色彩描写在美学上色彩包含两方面内容:主观色彩和客观色彩,客观色彩的涂抹、渲染,可以造成一种特定的氛围、色调。
苏童在作品中习惯运用鲜艳的红色来抒情,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这个凄艳的“红”有关:如红菱、颂莲、灵虹、段红等。
去年冬天我和你们一起喝了白酒后打翻一瓶红墨水,在墙上画下了我的八位亲人。
我还写了一首诗想夹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历史书里。
那是一首胡言乱语口齿不清的自白诗。
诗中幻想了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幻想了横亘于这条血脉的黑红灾难线。
有许多种开始和结尾交替出现。
最后我痛哭失声,我把红墨水拚命地往纸上抹,抹得那首诗无法再辨别字迹。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无论是在《妻妾成群》、《城北地带》中,还是在《罂粟之家》中,红色成为了一种象征。
盛开的罂粟花、鬼火般的夜繁花和深夜里的红灯笼,在漆黑的夜晚,在荒僻之所,它们兀自鲜艳火红,但却如斯邪媚。
红色和沉重的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更具张力和撞击力,更渲染了一种颓废感伤的氛围。
二、隐藏于冷静的表述背后的情感美学家朱光潜曾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
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
”“小说中的诗”,实际上是一种“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意境,而在这意境中萦回的便是情感之流了苏童从不轻易在小说中泄露自己的情感和褒贬,他的叙述是极为冷静的,波澜不惊。
我还听说杨夫人也已被赐死殉葬,她拒死不从,她光着脚在宫中奔逃,后来被三个宫役追获,用白绢强行勒毙了。
七口红棺拖上王陵时,有一口棺木内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众人大惊失色。
后来我亲眼看见那口棺盖被慢慢地顶开了,杨夫人竟然从棺中坐了起来,她的乱发上沾满了木屑和赤砂,脸色苍白如纸,她已经无力重复几天前的呐喊。
我看见她最后朝众人摇动了手中的遗诏印件,很快宫役们就用沙土注满了棺内,然后杨夫人的红棺被重新钉死了,我数了数,宫役们在棺盖上钉了十九颗长钉。
——《我的帝王生涯》杨夫人被活活钉死在棺材内的情景极其残忍和血腥,令人不忍卒读,但作者冷静地,不厌其烦地详尽描述酷刑的过程,宫廷内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爱哭的废妃们被小皇帝剜去了舌头;何其惨烈!作者的笔却应是平静地写道: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而对起义失败的李义芝的”空前绝后的极刑”更是让人不忍去读。
可作者的语言永远是平静的,从容的,而这种冷静得近乎游戏的文字背后,是作者的一种颓废而绝望的情绪,是末世纪的孤独和叛逆,反而能给读者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颤三、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客观世界的多样性,人的思维、情感、审美价值的多元性,导致了言语运用的多样性。
在小说中,叙事、写人、绘景、状物,超乎常理的语言变异运用,可以使言语代码突破其自身的容量,而带上了浓郁的审美意味。
于是,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变异言语世界。
这个世界,无法用理性来领会,却可以由解码者借助语境,凭借审美经验去解读。
①苏童是个变换组合语言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极具颠覆性的语句和陌生感的意象1、将相互矛盾的事物现象在同一语言时段表达出来苏童很擅长闻一多《死水》式的以美写丑法寒光四溅中,有猩红的血火焰般蹿起来,斑驳迷离。
陈玉金女人年轻壮美的身体迸发出巨响扑倒在黄泥大路上” “那天早晨黄泥大路上的血是如何洇成一朵莲花形状的呢?陈玉金女人崩裂的血气弥漫在初秋的雾霭中,微微发甜”。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是《1934年的逃亡》中展示陈玉金弑妻的场景,美艳的色彩和意象用于形容杀戮的场景,甜的滋味也用于形容血的气息,估计没有读者会觉得美好,反而有一种作呕之感。
这便是以美写丑所能带来的效果。
2、有时,言语代码的组织突破了正常的思维意向,给人以出奇不意的感觉“老秦不懂小武汉心里的苦,只是一味地劝导小武汉,我们这行当怎么了?也是个铁饭碗呢,人嘛,一生一死,谁没个那一天?死人其实是最安全的了,没思想了嘛,像个睡沉的孩子一样,很软,很听话,我这几年看东西有时候看花眼,上次给小美她爷爷穿衣服,老觉得他肩膀在动,好像配合我,自己要翻身呢。
”搬尸工的工作和”铁饭碗”,恐怕是无法联系到一起的,但乐观的老秦突破正常思维, 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就产生了俏皮、幽默和讽刺的效果,四、唯美的诗意化语言苏童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表达技巧上,不但吸收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技法,同时他的审美情趣具有古典化特征,着力于意境的营造,注重语言的诗意化。
苏童小说语言诗意化首先表现在他运用了很多具备中国传统特殊风韵的词语和意象,这一点葛红兵曾加以精辟的论述:“夏天的海棠,秋天的紫藤;凄清的雨,肃煞的雪;等等;它们在小说中构成了一幅幅中国古代文人画,”“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梅珊唱戏、飞浦吹箫、陈左仟阳痿、颂莲醉酒,等等,也都是意象,”“它接续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的传统,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以一种书画同源的风格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 我更愿意说,苏童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息的、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土壤上的作家,也因为他身上的这种气息,使他获得了飞越枫杨树故乡,穿过香椿树街,在鲁迅、茅盾力所不及的地方回顾历史,瞻望现实的能力,”②其次表现在他苏童的这种收发自如的叙事风格,读他的小说,我们仿佛看到有个人站在小说的意境里面,平视着小说中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之后平静地向你述说,呈现出一种干净而透明的意境,“如华丽而质地绵实的苏州丝绸”。
③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初歇的日子,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与街平行的那条护城河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
在去火葬场的途中,男孩小拐多次撩起死者的衣袖,察看他左手臂上的猪头刺青,它在死者薄脆的皮肤上放射着神奇的光芒。
——《刺青时代》这段环境描写只截取了北风中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结了冰的护城河这三个片段,但是已经让人感到了环境的险恶,可以想象如果是大雪纷飞的日子是怎样一副光景了。
第二天起了雾,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
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50里乡土美丽而悲伤。
——《罂粟之家》这段描写中,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淡淡的一笔却让人感到无限韵味。
但是在这些充满古典韵味的景与物、比与喻的后面,赫然而立的却是人性的被扭曲与戕害、人生的孤独与痛苦等等现代的主题。
在苏童那里,对古典审美风格的追求与对现代主题的表现融合得天衣无缝。
总之,苏童小说既有奇特绮丽的现代感又有唯美诗意的古典感,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隐藏于冷静表述背后的情感、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唯美的诗意化语言,构成了苏童小说语言的个性标志和审美韵味。
先锋实验小说作家苏童及其小说创作风格苏童,原名童中贵,1963年生于苏州。
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到南京工作,一度担任《钟山》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百十万字,其中中短篇小说集七部,长篇小说二部。
随着其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声蜚声海内外。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妻妾成群》、《井中男孩》、《你好,养蜂人》、《离婚指南》、《平静如水》、《后宫》、《米》、《罂栗之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