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中的悲剧人物
- 格式:doc
- 大小:40.00 KB
- 文档页数:3

现当代文学余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分析吉 丽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摘要:余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通常采用男性视角,对“父亲”的形象刻画尤为深刻。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的形象特质表述,小说中的母亲们更多的像是一个苍白的背景,在父权笼罩的阴影下发出啜泣的声音。
无法摆脱身体孱弱与受虐影响的母亲们,寄托了余华小说中的另一种感情,为此,本文透过小说中母亲角色的映射,对其塑造的母亲形象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孱弱;受虐;坚韧一、母亲形象特质形成的背景在余华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像是一抹浓重的水彩,使得读者的目光总是先着眼于父亲所刻画的情感。
纵观余华的文学作品,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其阐述情感的重点,作者将对家庭关系的质疑,对现实秩序的反抗以描写父子之间复杂关系链的形式表达出来,以至于延伸出了“父子互审”这一现象。
余华的这种创作思想在先锋时期就有所体现,其小说中充斥着荒诞与叛逆,无法对父权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理性思维产生共鸣。
在九十年代后期,这种反叛的思想逐渐转化为经历苦难后的坚强,人性本质蕴含的善良。
“父亲”的形象总是带有一定的特性,像一座固化的基座,不同小说中父亲形象从基座中衍生出来,父权如同一座大山一样,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压迫在整个家庭上。
小说中描写的“父亲”或是荒诞暴力、或是蛮横无礼,这种以男性视角描写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引导读者了解家庭中父亲的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
然而,这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将女性角色弱化为背景,她们被遮蔽在父亲的阴影中,孱弱、受虐的形象仿佛成为女性的代名词,我们却隐约可以听到从父权压迫阴影中传来的哭泣声。
二、孱弱的形象特质在余华先生小说中塑造的母亲形象通常都带有孱弱的特点,这种脆弱不仅体现在女性的外在表述,更进一步深化到了母亲孱弱产生的原因中。
如果说人物柔弱产生的原因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余华小说中母亲孱弱特质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可以归类为身体因素,细化为衰老、病弱。
母亲衰老的形象出现在余华小说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其大部分中短篇的小说描写中,母亲这一角色从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就已经是一种老母亲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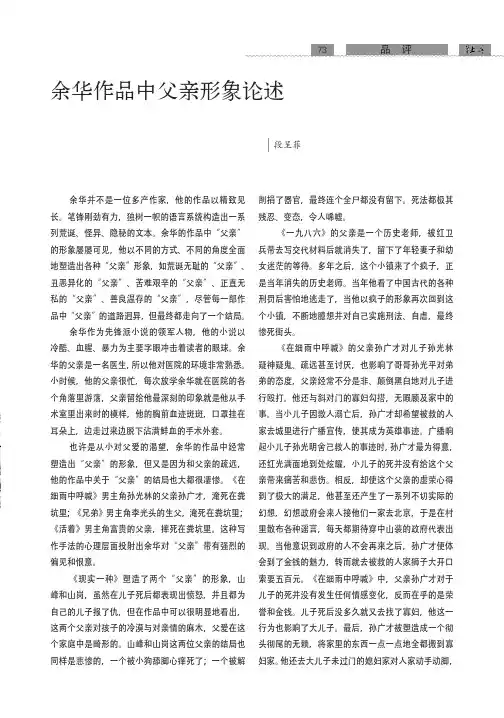
73品 评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论述段呈菲余华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
笔锋刚劲有力,独树一帜的语言系统构造出一系列荒诞、怪异、隐秘的文本。
余华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屡屡可见,他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全面地塑造出各种“父亲”形象,如荒诞无耻的“父亲”、丑恶异化的“父亲”、苦难艰辛的“父亲”、正直无私的“父亲”、善良温存的“父亲”,尽管每一部作品中“父亲”的道路迥异,但最终都走向了一个结局。
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以冷酷、血腥、暴力为主要字眼冲击着读者的眼球。
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医院的环境非常熟悉。
小时候,他的父亲很忙,每次放学余华就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父亲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血迹斑斑,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外套。
也许是从小对父爱的渴望,余华的作品中经常塑造出“父亲”的形象,但又是因为和父亲的疏远,他的作品中关于“父亲”的结局也大都很凄惨。
《在细雨中呼喊》男主角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淹死在粪坑里;《兄弟》男主角李光头的生父,淹死在粪坑里;《活着》男主角富贵的父亲,摔死在粪坑里。
这种写作手法的心理层面投射出余华对“父亲”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恨意。
《现实一种》塑造了两个“父亲”的形象,山峰和山岗,虽然在儿子死后都表现出愤怒,并且都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但在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与对亲情的麻木,父爱在这个家庭中是畸形的。
山峰和山岗这两位父亲的结局也同样是悲惨的,一个被小狗舔脚心痒死了;一个被解剖捐了器官,最终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
死法都极其残忍、变态,令人唏嘘。
《一九八六》的父亲是一个历史老师,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就消失了,留下了年轻妻子和幼女迷茫的等待。
多年之后,这个小镇来了个疯子,正是当年消失的历史老师。
当年他看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刑罚后害怕地逃走了,当他以疯子的形象再次回到这个小镇,不断地臆想并对自己实施刑法、自虐,最终惨死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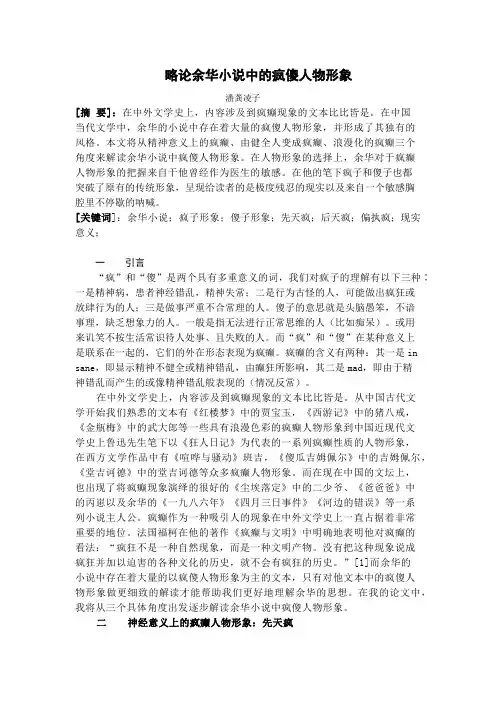
略论余华小说中的疯傻人物形象潘龚凌子[摘要]:在中外文学史上,内容涉及到疯癫现象的文本比比皆是。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余华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疯傻人物形象,并形成了其独有的风格。
本文将从精神意义上的疯癫、由健全人变成疯癫、浪漫化的疯癫三个角度来解读余华小说中疯傻人物形象。
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余华对于疯癫人物形象的把握来自于他曾经作为医生的敏感。
在他的笔下疯子和傻子也都突破了原有的传统形象,呈现给读者的是极度残忍的现实以及来自一个敏感胸腔里不停歇的呐喊。
[关键词]:余华小说;疯子形象;傻子形象;先天疯;后天疯;偏执疯;现实意义;一引言“疯”和“傻”是两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词,我们对疯子的理解有以下三种∶一是精神病,患者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二是行为古怪的人,可能做出疯狂或放肆行为的人;三是做事严重不合常理的人。
傻子的意思就是头脑愚笨,不谙事理,缺乏想象力的人。
一般是指无法进行正常思维的人(比如痴呆)。
或用来讥笑不按生活常识待人处事、且失败的人。
而“疯”和“傻”在某种意义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外在形态表现为疯癫。
疯癫的含义有两种:其一是in sane,即显示精神不健全或精神错乱,由癫狂所影响,其二是mad,即由于精神错乱而产生的或像精神错乱般表现的(情况反常)。
在中外文学史上,内容涉及到疯癫现象的文本比比皆是。
从中国古代文学开始我们熟悉的文本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西游记》中的猪八戒,《金瓶梅》中的武大郎等一些具有浪漫色彩的疯癫人物形象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笔下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疯癫性质的人物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喧哗与骚动》班吉,《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等众多疯癫人物形象。
而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也出现了将疯癫现象演绎的很好的《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爸爸爸》中的丙崽以及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主人公。
疯癫作为一种吸引人的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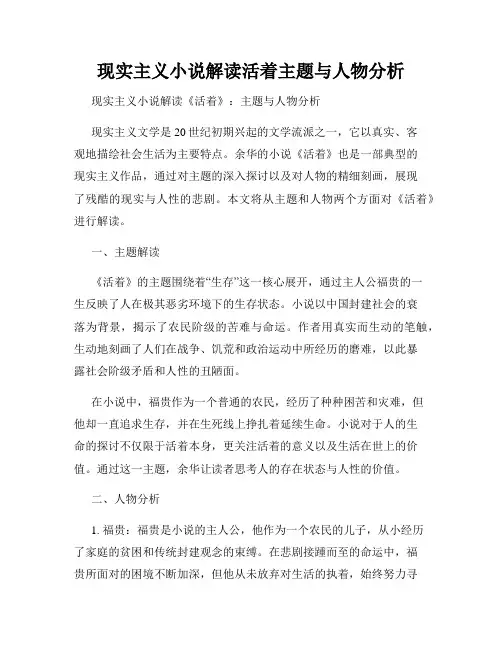
现实主义小说解读活着主题与人物分析现实主义小说解读《活着》:主题与人物分析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文学流派之一,它以真实、客观地描绘社会生活为主要特点。
余华的小说《活着》也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对主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人物的精细刻画,展现了残酷的现实与人性的悲剧。
本文将从主题和人物两个方面对《活着》进行解读。
一、主题解读《活着》的主题围绕着“生存”这一核心展开,通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反映了人在极其恶劣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小说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为背景,揭示了农民阶级的苦难与命运。
作者用真实而生动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人们在战争、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磨难,以此暴露社会阶级矛盾和人性的丑陋面。
在小说中,福贵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经历了种种困苦和灾难,但他却一直追求生存,并在生死线上挣扎着延续生命。
小说对于人的生命的探讨不仅限于活着本身,更关注活着的意义以及生活在世上的价值。
通过这一主题,余华让读者思考人的存在状态与人性的价值。
二、人物分析1. 福贵:福贵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经历了家庭的贫困和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
在悲剧接踵而至的命运中,福贵所面对的困境不断加深,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执着,始终努力寻找生存的希望。
福贵的形象展现了小人物的坚强与勇敢,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2. 福贵的妻子:福贵的妻子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在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与帮助作用。
尽管她也经历了诸多的痛苦,但她始终保持了对家庭的忠诚和对福贵的无私支持。
她的形象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和温暖的力量。
3. 尤四姐:尤四姐是福贵的妹妹,她是一个爱情的受害者。
尽管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她却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压迫。
她的形象体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无助和受制于男性的命运。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小人物在动荡年代中的生存状态和家庭关系。
这些人物形象的丰满刻画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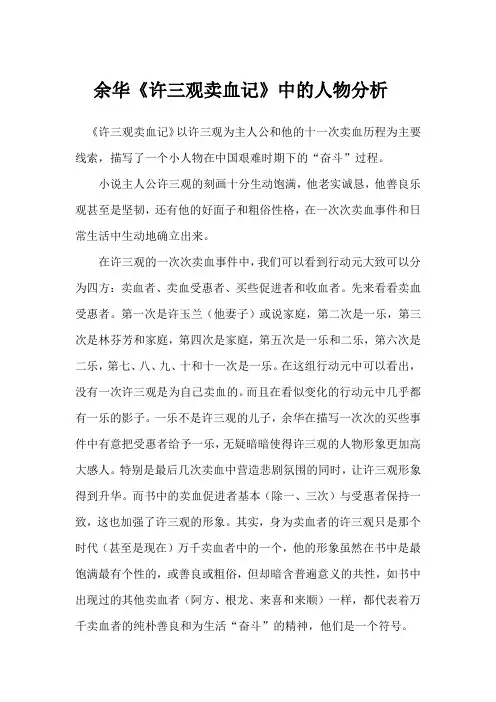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人物分析《许三观卖血记》以许三观为主人公和他的十一次卖血历程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一个小人物在中国艰难时期下的“奋斗”过程。
小说主人公许三观的刻画十分生动饱满,他老实诚恳,他善良乐观甚至是坚韧,还有他的好面子和粗俗性格,在一次次卖血事件和日常生活中生动地确立出来。
在许三观的一次次卖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行动元大致可以分为四方:卖血者、卖血受惠者、买些促进者和收血者。
先来看看卖血受惠者。
第一次是许玉兰(他妻子)或说家庭,第二次是一乐,第三次是林芬芳和家庭,第四次是家庭,第五次是一乐和二乐,第六次是二乐,第七、八、九、十和十一次是一乐。
在这组行动元中可以看出,没有一次许三观是为自己卖血的。
而且在看似变化的行动元中几乎都有一乐的影子。
一乐不是许三观的儿子,余华在描写一次次的买些事件中有意把受惠者给予一乐,无疑暗暗使得许三观的人物形象更加高大感人。
特别是最后几次卖血中营造悲剧氛围的同时,让许三观形象得到升华。
而书中的卖血促进者基本(除一、三次)与受惠者保持一致,这也加强了许三观的形象。
其实,身为卖血者的许三观只是那个时代(甚至是现在)万千卖血者中的一个,他的形象虽然在书中是最饱满最有个性的,或善良或粗俗,但却暗含普遍意义的共性,如书中出现过的其他卖血者(阿方、根龙、来喜和来顺)一样,都代表着万千卖血者的纯朴善良和为生活“奋斗”的精神,他们是一个符号。
书中人物中的收血者包括几个血头也是时代的符号,代表那个时期各个医院的血头。
在收血者行动元变化中身在救死扶伤的医院的他们却惊人的相似—自私残忍甚至无人性。
在一个情节中,李血头不让许三观卖血是怕连累自己,却告诉他可以去其他医院。
这暴露了那个年代黑暗的一角。
幸好书中其他人物大都可爱的,家人的互相扶持(特别是危难中),路人的友好举动,街坊邻里的帮助,他们中也可能有卖血者,他们身份不一,但都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温情,人们的简单纯朴。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个赞扬和讽刺的悲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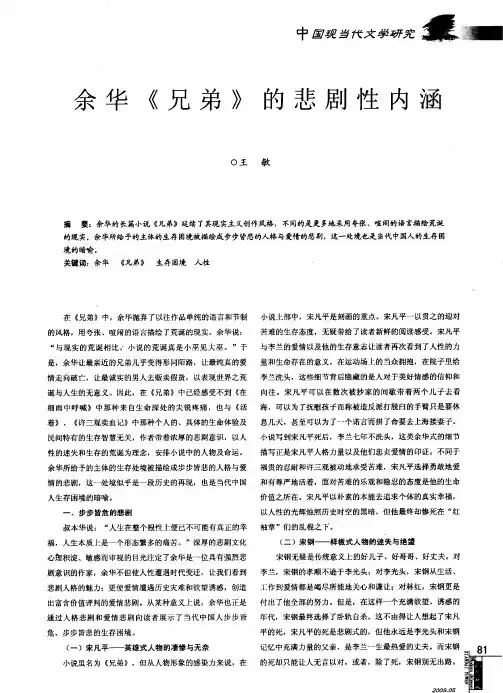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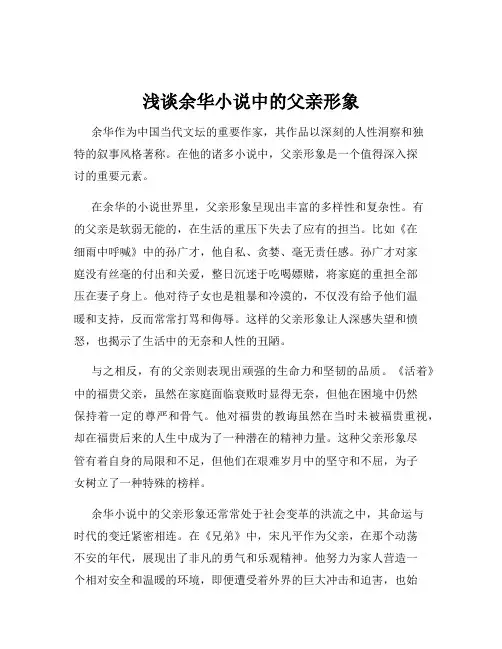
浅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以深刻的人性洞察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在他的诸多小说中,父亲形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元素。
在余华的小说世界里,父亲形象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的父亲是软弱无能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失去了应有的担当。比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他自私、贪婪、毫无责任感。孙广才对家庭没有丝毫的付出和关爱,整日沉迷于吃喝嫖赌,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身上。他对待子女也是粗暴和冷漠的,不仅没有给予他们温暖和支持,反而常常打骂和侮辱。这样的父亲形象让人深感失望和愤怒,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无奈和人性的丑陋。
与之相反,有的父亲则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质。《活着》中的福贵父亲,虽然在家庭面临衰败时显得无奈,但他在困境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尊严和骨气。他对福贵的教诲虽然在当时未被福贵重视,却在福贵后来的人生中成为了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这种父亲形象尽管有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但他们在艰难岁月中的坚守和不屈,为子女树立了一种特殊的榜样。
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还常常处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其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在《兄弟》中,宋凡平作为父亲,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乐观精神。他努力为家人营造一个相对安全和温暖的环境,即便遭受着外界的巨大冲击和迫害,也始终用自己的爱和力量守护着家庭。然而,时代的悲剧最终还是让他失去了生命,他的离去成为了家庭的巨大伤痛,也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残酷。
余华通过这些父亲形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多面性。他不仅仅是在塑造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更是在通过这些人物揭示社会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困境。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艰辛、人性的复杂以及命运的无常。
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他们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理想化的父亲形象,而是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这些形象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引发对家庭、社会以及人性的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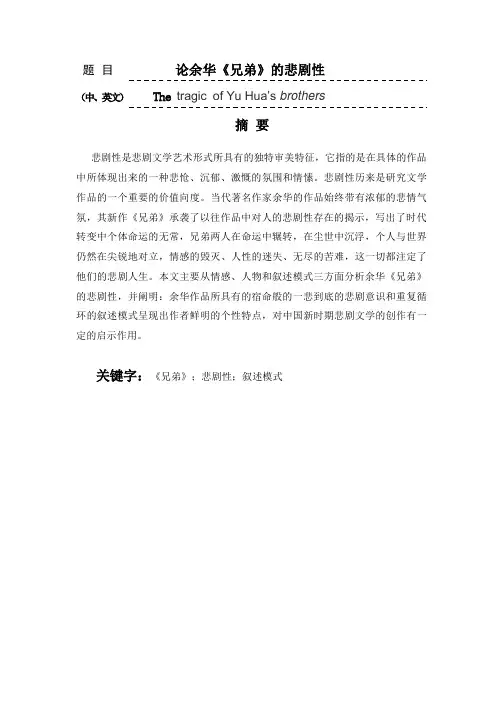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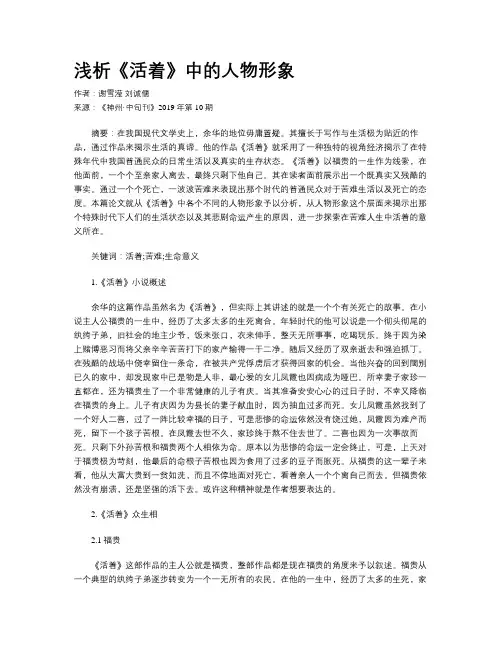
浅析《活着》中的人物形象作者:谢雪滢刘诚儒来源:《神州·中旬刊》2019年第10期摘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余华的地位毋庸置疑。
其擅长于写作与生活极为贴近的作品,通过作品来揭示生活的真谛。
他的作品《活着》就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经济揭示了在特殊年代中我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真实的生存状态。
《活着》以福贵的一生作为线索,在他面前,一个个至亲家人离去,最终只剩下他自己。
其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个既真实又残酷的事实。
通过一个个死亡,一波波苦难来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对于苦难生活以及死亡的态度。
本篇论文就从《活着》中各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予以分析,从人物形象这个层面来揭示出那个特殊时代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其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探索在苦难人生中活着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活着;苦难;生命意义1.《活着》小说概述余华的这篇作品虽然名为《活着》,但实际上其讲述的就是一个个有关死亡的故事。
在小说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生死离合。
年轻时代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旧社会的地主少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整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
终于因为染上赌博恶习而将父亲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产输得一干二净。
随后又经历了双亲逝去和强迫抓丁。
在残酷的战场中侥幸留住一条命,在被共产党俘虏后才获得回家的机会。
当他兴奋的回到闊别已久的家中,却发现家中已是物是人非,最心爱的女儿凤霞也因病成为哑巴。
所幸妻子家珍一直都在,还为福贵生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儿子有庆。
当其准备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时,不幸又降临在福贵的身上。
儿子有庆因为为县长的妻子献血时,因为抽血过多而死。
女儿凤霞虽然找到了一个好人二喜,过了一阵比较幸福的日子,可是悲惨的命运依然没有饶过她,凤霞因为难产而死,留下一个孩子苦根。
在凤霞去世不久,家珍终于熬不住去世了。
二喜也因为一次事故而死。
只剩下外孙苦根和福贵两个人相依为命。
原本以为悲惨的命运一定会终止,可是,上天对于福贵极为苛刻,他最后的命根子苦根也因为食用了过多的豆子而胀死。
活着中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活着中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余华的《活着》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它以朴实的文字描绘了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主人公福贵充满苦难却又坚韧不屈的一生。
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近现代,这是一个历经了巨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
从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到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再到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民国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福贵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然而,他年少轻狂,挥霍无度,沉迷于赌博,最终输光了家产,从一个富家少爷沦为了贫苦农民。
这一身份的巨大转变,正是当时社会动荡和不确定性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福贵被迫带着家人四处逃难,忍受着饥饿、疾病和战争带来的恐惧。
这个时期,生命变得无比脆弱,人们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运动展开。
福贵分到了土地,本以为生活会逐渐好转,但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人们盲目追求高产,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福贵一家再次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复杂。
福贵和家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们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福贵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
他先是失去了家产,然后父亲离世,母亲也在他被抓去当兵期间病故。
他的儿子有庆,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被过度抽血而死;女儿凤霞在分娩时大出血去世;妻子家珍因长期劳累和疾病缠身,最终也离开了他。
就连女婿二喜在工作中意外身亡,外孙苦根也因吃豆子被撑死。
命运似乎对福贵格外残酷,一次次地夺走他身边的亲人,让他承受着无尽的痛苦和孤独。
然而,尽管命运多舛,福贵却从未放弃过活着的希望。
《活着》人物形象分析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作家放弃先锋探索重返写实之路的乡土力作。
这部小说反映了福贵这一小人物在建国前至70年代末三十年的时代浪潮中命运的跌宕沉浮,并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生存状态告诉世人活着的自为性与终极性。
“《活着》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福贵不仅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亦是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作者在文本中让我们看到了对传统的人性价值和道德信念的坚持和固守。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福贵一生的故事。
这部有12万多字的长篇,虽然只是刻意突出了几个农民的个人命运和细碎生活,但于平凡中达到奇妙的效果,几近写出了一种民族苦难史和民族生命力。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旧时代吃喝嫖赌,把祖上的家产败光,他的这一行为气死了老父亲,接着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回来时老母亲已经死去。
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还赶上了分土地,洗心革面的他一心要和家人守在一起“好好的活着”。
可是,公社化和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都波及到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气质家珍患了不治之症,最后死去,儿子友庆为了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女儿凤霞终于嫁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二喜,让福贵感到生活的幸福,却不料凤霞在分娩时难产而死,随后女婿二喜在劳动中死于意外事故。
包产到户后。
衰老的福贵体力不支,他的外孙苦根小小年纪就帮助他干农活。
先是淋雨得了病,又因为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了。
最后只有可怜的福贵孤独终老。
一、死亡意象《活着》中的人物都不经意地“遭遇”死亡,死亡意象似乎构成了这部小说最鲜明醒目的一道风景。
通过密集而频繁的死亡叙述,我们不能不说作家具有一种对死亡的偏爱,在余华笔下,死亡只是作家达到自己创作目的的一个阶梯、工具或手段,它不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作家将其还原为一种生命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存方式,并以死亡为跳板,以达到升华主题和剖析人生的目的。
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奇曾指出:“只有能够死亡的才是有生命的。
- 44 -2023年 第3期《文城》讲述的是北方小伙林祥福和南方姑娘小美的悲剧爱情故事。
余华在作品中通过正篇和补篇完整讲述了林祥福、小美、阿强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本文将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四个方面来分析《文城》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文城》采用了不同以往的叙事结构——正篇和补篇的形式。
余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也尝试过让林祥福和小美的故事并行展开,马上发现两条线索无法穿插,小美小时候离开西里村到溪镇沈家再到与林祥福相见,差不多是补篇里的一半的篇幅,把林祥福架空时间太久,如果把两边的故事切碎了交叉来写,很难做到,有关小美童年描写很多,有关林祥福的童年只是一笔带过,无法交叉,交叉以后会在叙述里显得磕磕绊绊。
”[1]因此,从作者这一角度,余华选择了最为合适的正补结合的方式,使得叙述更加顺畅。
其次,以文本来说,《文城》包括分开的两部分。
正篇是讲述林祥福的故事,林祥福家庭还算富裕,在父亲去世后其与母亲相依为命,二十四岁时在门前遇见令余华《文城》的叙事策略□ 胡 聪摘 要:余华的《文城》是一部传奇悲剧爱情故事。
在内容上,它是林祥福、小美、阿强三人之间的爱情悲剧,也是林祥福寻妻的传奇故事。
叙事上,它以正篇和补篇的叙事结构进行叙述;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全文,但是从林祥福和小美两个角度一点一点展开故事情节;以叙事时间变化影响故事发展节奏;以南方和北方为故事的两大叙事空间,另外小说也展示出了人物的生活空间以及“文城”这一想象空间。
关键词:《文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2023年第3期- 45 -他为之心动的小美。
之后,经历了小美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最后走上寻妻的道路。
补篇讲述了小美的故事,穷苦的家庭使小美在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童养媳,之后和阿强逃离家乡见识到了上海繁华大都市,然后遇见林祥福开启“骗钱”之路。
余华作品中的悲剧人物
摘要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坛闯将,曾以描写血性和暴力见长,他的先锋小说也曾经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最生动地体现了“世纪末精神”的作品。
余华的小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手法直面描写生活中最丑陋而远离理性的区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且对当代文学共鸣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本文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小说为例,来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以及深刻的个人、文化、社会原因的影响。
关键词余华、小说、悲剧人物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已读过余华的作品的人,第一印象就是:作者余华本人可能是一个思想消极阴暗,有着对社会愤世嫉俗的心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人。
他喜好揭露人类的劣根性的一面,喜欢把人类的那种愚昧、无知、野蛮、粗鲁以及肮脏的一面淋于纸上,并且喜欢把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结局都要安排成一种悲剧或带上悲剧的色彩,源引一位作家的话说:“余华在用文字制造疼痛”。
一、余华小说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即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
余华小说的悲剧意识则主要表现在:
1、对人性的探索。
其中体现在对“恶”饿极度渲染和夸张,对人性的深刻揭露。
2、对命运无常和苦难的描写。
3、对死亡的描写。
很多伟大的作品很难不触及死亡,大量的死亡事件充斥在余华早期暴力
血腥的作品中。
二、余华小说的悲剧人物
(一)、悲剧男性
《活着》,深刻的勾画出富贵的生活随着家庭、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余华曾说: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于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年轻时的福贵承袭了其父的恶劣遗风,败尽万贯家财。
苦难和兄弟一样紧随着他。
气死了父亲,病死了母亲,接着儿子有庆在医院因抽血过多而丧命,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而死,再是妻子家珍积劳成疾,女婿二喜遇难横死,小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
一个个亲人离他而去,而他却活着。
或许他身边的这三个女人成了他活着的支柱。
《兄弟》,以少年视角展示了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宋凡平在文本中是道德完美的化身,有着善良及正义的品德,独立及尊严的人格。
即使是罹难时的痛楚与绝望,对李兰的爱让他成为负载完美人性最光华的人物,衬托出文革时期人性的肮脏与邪恶。
宋钢,善良孝顺却简单狭隘,为了妻子能做出一切即使是撕掉男人的尊严做丰胸手术卖丰乳霜。
是一种缺乏独立理性的爱,显得脆弱苍白。
与兄弟断绝情谊,将自己的生存意志交给林红支配,因为林红的背叛,出于一份挚爱,选择卧轨自杀。
小人物的生活,铺开了文革时期暴虐的客观事实,突出了人物和时代残暴的极端性。
《许三观卖血记》不仅是一个“为自己,为儿女,承担着庄严生活的小人物构成的历史”,更是一个包含余华精神历程的隐喻。
文本中主线当然是许三观卖血,但文辞中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卖血的苦难——“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许三观更可贵的却是他客观的态度。
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艰辛的人,被生活折腾了近一生,始终笼罩着一丝悲凉的色彩。
吃炒猪肝喝黄酒成了他最幸福的时刻。
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却是一个家的的顶梁柱。
把自己的一切给了许玉兰和一乐,他的悲凉是我们这些没有感受过大风大浪的人所不能体会到的。
但是他却自己一人撑起了所有的一切,他用他的血养起了整个家。
(二)女性形象
《活着》中的家珍和《兄弟》中的李兰,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更为隐秘:在福贵眼中家珍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温顺听话、忍辱负重、勤劳能干、守身如玉(直到死从没人对她飞长流短),她完全符合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也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的要求;李兰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志同道合、高大英俊的宋凡平组成美满的家庭。
然而在宋凡平为了她付出生命之后,她为了丈夫七年没有洗过头,这样的行为正暗合了封建社会女性为夫守节的传统要求。
对爱情忠贞,为丈夫守节正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和最大希望,作者让李兰用这样的举动来彰显她对爱情的忠诚和对爱人的怀念,正是余华对女性的想象与要求,是余华内心需要的直接反映。
家珍和李兰是小说的叙述者和作者合谋制造的女性镜像,她们在被男性从男性视角进行人为叙述和书写的同时,已经成为男性理想的投射物和象征体,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就在男性叙述者和作者共同赠予的“好女人”的牌坊下,被干净地涂抹去,而她们在这个“美丽的标签”下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反而有了些许心安理得。
除此之外,富贵的女儿凤霞因难产而死;大胆表露爱意追求幸福的林红,却背叛了宋钢成了丈夫兄弟的情人,在宋刚死后抛弃情爱,最终成了红灯区老板。
余华笔下的女性,多数都是为身边的男性付出无意义的牺牲和无价值的毁灭,是一种女性化的爱。
既是女性弱势群体自身的一种文化选择,更是男性强势文化对女性心理的一种硬性灌输和强迫塑造。
迎合了男权意识和男性心理,让女性无限的承担苦难和不幸,从而减轻男人生存压力和生活痛苦,送给女性“好女人”的奖章,让他们在男权社会中心甘情愿得俯首称臣,被遗忘。
三、悲剧人物形成的原因
凡是出现和产生,肯定有一定的时代或是自身的原因,作家的写作也不例外,余华作品中浓郁的悲剧意识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其成长经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童年生活以及成长中的经历
余华1960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在他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海盐,便度过了人生三十多年的时光。
余华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
童年的他因为父母上班没时间照看便经常把他和哥哥锁在家里。
他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窗外石板铺成的大街和远处的田野里耕作的农民。
从小在医院长大的缘故,见惯了医院里血肉模糊的情景与病人在面对亲人死亡哀嚎痛哭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难免刻下印迹,或许也左右了他以后在文学写作道路上的思想。
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
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
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
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
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①余华童年时,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常常在炎热的夏天独自一人跑进里面乘凉。
那时的余华几乎听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哭声,时间长了,面对亡者亲属的哭声,他渐渐失去了常人的恐惧与震撼,以至于竟然“觉得那已经不是哭泣了,它们是那么的漫长持久,那么的感动人心,哭声里充满了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
”②另外余华在从事写作以前是一名国家医院的牙医,见惯了各种痛苦的人。
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对痛苦与灾难的习以为常成就了他作品中悲剧意识的自然流露,无须任何的雕饰与做作,总是水到渠成。
(二)性格潜在的悲剧意识与时代背景
如果说童年的生活经历是对余华创作无法避免的客观因素,性格潜在的悲剧意识与时代背景对于余华创作的影响则是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的结合。
余华是真实的经历过文革,虽然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只会听从哥哥指挥的小孩,可是对于文革的印象却依然记忆犹新,据余华回忆那段经历时说:“文革开始后,他玩耍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可是这草棚搭起来没多久就被他和哥哥的一次消防队救火上午游戏中烧掉了。
”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余华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语言暴力,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可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生活中的信任破灭。
这或许就使余华产生了一种认识,即暴力是惟一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暴力便与悲剧是息息相关。
(三)阅读及其他作家的影响
当然,童年经历和儿时记忆决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迷恋悲剧小说的全部原因。
余华的创作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他作家,还与他的阅读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余华主要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在这些外国作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国作家中,则只有鲁迅一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力叙述的慢镜头特写和鲁迅的冷峻笔法使余华在进入血腥的暴力世界时,能够不动声色游刃有余。
余华在阅读了无数的书籍后从作家和作品中吸取了精华丰富了他的思想和写作思路,感受到了生活与人生中的悲剧,写出了许多悲剧性很强的作品,同时他也被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影响着不得不去感受自己用文字制造的痛疼,感受疼痛又超越疼痛。
余华笔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群皮影人偶,黑暗与光明的舞台成了时代的象征,以不同的姿态默默行进。
而余华作品较高的文学价值在于不断营构具有独特意义的写作空间,就悲剧这个角度,在不同时期,作家在内容上的书写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当代文坛有关悲剧性的探索中,余华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书目:
1、①、②余华《医院里的童年》/yuhua
2、《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兄弟》,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4、《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