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两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
- 格式:doc
- 大小:45.00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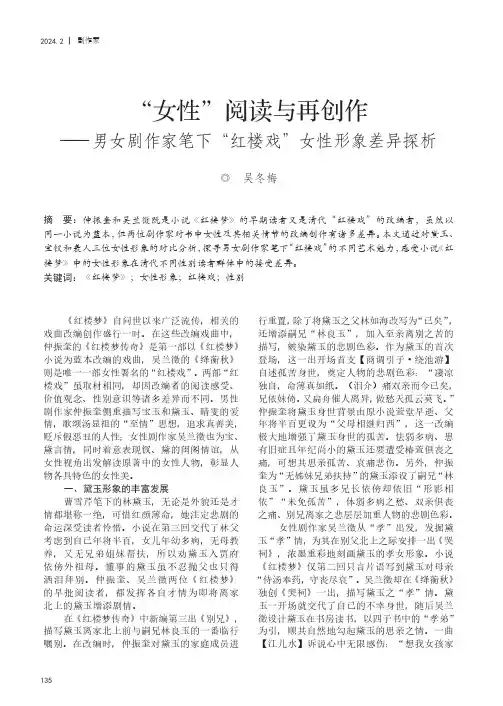
2024.2┃ 剧作家135《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相关的戏曲改编创作盛行一时。
在这些改编戏曲中,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是第一部以《红楼梦》小说为蓝本改编的戏曲,吴兰徵的《绛蘅秋》则是唯一一部女性署名的“红楼戏”。
两部“红楼戏”虽取材相同,却因改编者的阅读感受、价值观念、性别意识等诸多差异而不同。
男性剧作家仲振奎侧重描写宝玉和黛玉、晴雯的爱情,歌颂汤显祖的“至情”思想,追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人性;女性剧作家吴兰徵也为宝、黛言情,同时着意表现钗、黛的闺阁情谊,从女性视角出发解读原著中的女性人物,彰显人物各具特色的女性美。
一、黛玉形象的丰富发展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无论是外貌还是才情都堪称一绝,可惜红颜薄命,她注定悲剧的命运深受读者怜惜。
小说在第三回交代了林父考虑到自己年将半百,女儿年幼多病,无母教养,又无兄弟姐妹帮扶,所以劝黛玉入贾府依傍外祖母。
懂事的黛玉虽不忍抛父也只得洒泪拜别。
仲振奎、吴兰徵两位《红楼梦》的早批阅读者,都发挥各自才情为即将离家北上的黛玉增添剧情。
在《红楼梦传奇》中新编第三出《别兄》,描写黛玉离家北上前与嗣兄林良玉的一番临行嘱别。
在改编时,仲振奎对黛玉的家庭成员进行重置,除了将黛玉之父林如海改写为“已矣”,还增添嗣兄“林良玉”,加入至亲离别之苦的描写,皴染黛玉的悲剧色彩。
作为黛玉的首次登场,这一出开场首支【商调引子•绕池游】自述孤苦身世,奠定人物的悲剧色彩:“凄凉独自,命薄真如纸。
(泪介)痛双亲而今已矣,兄依妹倚。
又扁舟催人离异,做愁天孤云莫飞。
”仲振奎将黛玉身世背景由原小说萱堂早逝、父年将半百更设为“父母相继归西”,这一改编极大地增强了黛玉身世的孤苦。
怯弱多病、患有旧症且年纪尚小的黛玉还要遭受椿萱俱丧之痛,可想其思亲孤苦、哀痛悲伤。
另外,仲振奎为“无姊妹兄弟扶持”的黛玉添设了嗣兄“林良玉”。
黛玉虽多兄长依傍却依旧“形影相依”“未免孤苦”,体弱多病之愁、双亲俱丧之痛、别兄离家之悲层层加重人物的悲剧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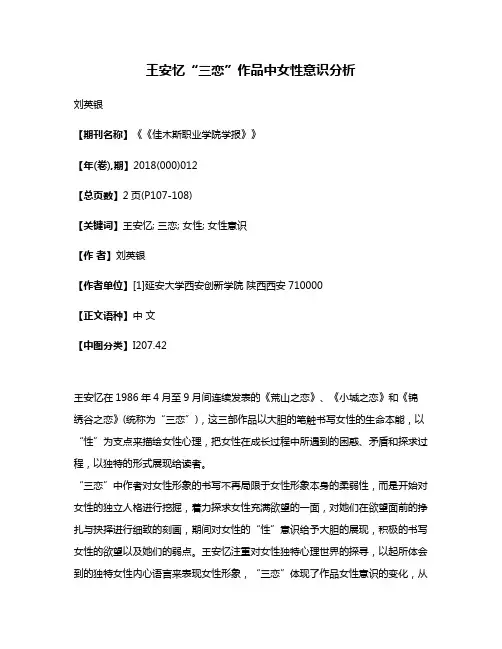
王安忆“三恋”作品中女性意识分析刘英银【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00)012【总页数】2页(P107-108)【关键词】王安忆; 三恋; 女性; 女性意识【作者】刘英银【作者单位】[1]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7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王安忆在1986年4月至9月间连续发表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统称为“三恋”),这三部作品以大胆的笔触书写女性的生命本能,以“性”为支点来描绘女性心理,把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和探求过程,以独特的形式展现给读者。
“三恋”中作者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不再局限于女性形象本身的柔弱性,而是开始对女性的独立人格进行挖掘,着力探求女性充满欲望的一面,对她们在欲望面前的挣扎与抉择进行细致的刻画,期间对女性的“性”意识给予大胆的展现,积极的书写女性的欲望以及她们的弱点。
王安忆注重对女性独特心理世界的探寻,以起所体会到的独特女性内心语言来表现女性形象,“三恋”体现了作品女性意识的变化,从性——恋——爱的女性意识蜕变历程,表现了女性不断自我成长与完善的心里路程。
一、“三恋”中的独特的女性形象分析王安忆自己也认为自己作品中的男女各有不同,女性的刻画时站在纯粹的人的视角,而男性形象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她笔下的女性与男性有着显著的性别差异,本身作为女性作家,王安忆的创作视角也是以女性视角为主,以此来对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摆脱了传统女性形象的刻板与顺从,对了一丝对欲望的呈现以及对自我的真实展现。
《小城之恋》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小城里,两个年轻人相遇以后就产生了源自于性本能的欲望交织,女主人公陷入到一种独特的性爱旋涡,当时的性爱充满了蒙昧与压抑,正如那个紧张而又慌乱的时代一样,两性的关系也显得异常无序,但是作者并非站在道德角度来对女主人公进行批判,但是从心理视角出发来对女性在经历无序的两性关系后的成长进行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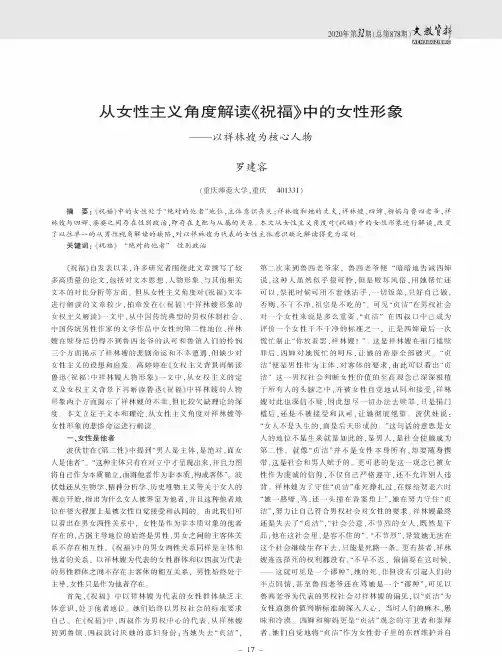
2020年第3"期(总第878期)丈敖冬‘科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祝福》中的女性形象----以祥林嫂为核心人物罗建容(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摘要:《祝福》中的女性处于“绝对的他者”地位,主体意识丧失;祥林嫂和她的丈夫,祥林嫂、四婶、柳妈与鲁四老爷,祥林嫂与四婶、婆婆之间存在性别政治,即存在支配与从属的关系。
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祝福》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从男性视角解读的缺陷,对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女性主体意识缺乏解读得更为深刻。
关键词:《祝福》“绝对的他者”性别政治《祝福》自发表以来,许多研究者围绕此文章6写了较多高质量的论文,包括对文本思想、人物形象、与其他相关文本的对比分析等方面。
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祝福》文本进行解读的文章较少,柏章发在《〈祝福〉中祥林嫂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一文中,从中国传统典型的男权体制社会、中国传统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第二性地位、祥林嫂在赎身后仍得不到鲁四老爷的认可和鲁镇人们的怜悯三个方面揭示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和不幸遭遇,但缺少对女性主义的设想发-高在《女权主义解读〈祝福〉中祥林嫂人物形象》一文中,从女权主义的义及女权主义背景下再解读《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两个方面揭示了祥林嫂的,但比较欠缺理论的深度。
本文文论,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祥林嫂等女性形象的悲惨命运进行解读-一、女性是他者在《第二性》中提到“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主体在对立中来,并将自作质,他者作质,体”。
波从物学、分析学、物主义等关女人的,女人他者,他者地位在度上是被女性自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是作为非本质对象的他者存在的,主地位的男性,男女的主体关系不存在相互性。
《祝福》中的男女性关系同样是主体和他者的关,以祥林嫂的女性体以的男性体在主体的相关,男性主,女性作他者在。
,《祝福》中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缺乏主体意识,他者地位。
她们始终以男权社会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祝福》中,四叔作为男权中心的代表,从祥林嫂初到鲁镇,就讨厌她的寡妇身份;当她失去“贞洁”,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鲁四老爷便“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但是败坏风俗,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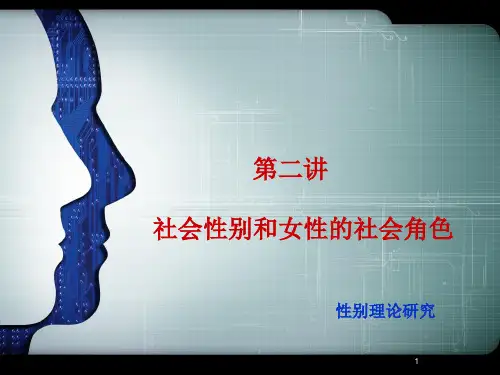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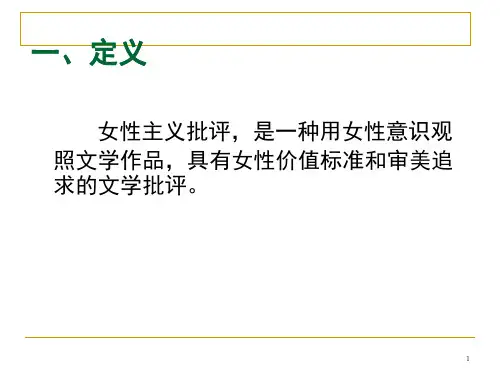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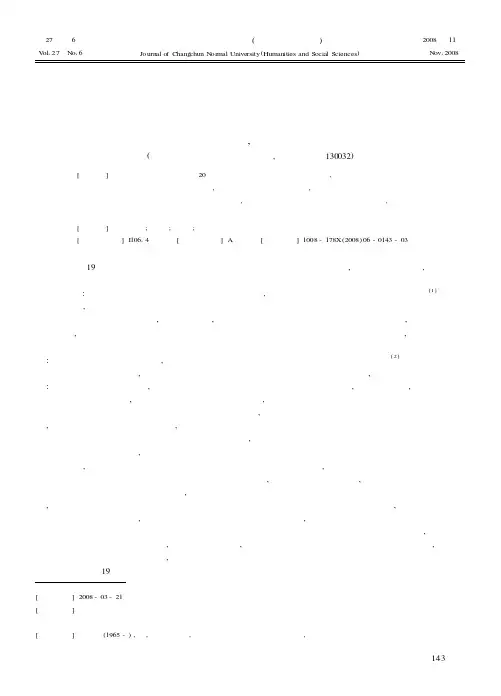
第27卷第6期V ol 127 N o 16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 al o f Chang chun N ormal University (Human 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年11月N ov 12008性别视角下的透视———哈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贺 萍,侯 旭(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摘 要]女性意识是很难界定的。
20世纪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明智地承认,一些女性作家的笔力和叙事话语不一定就能代表女性世界的呼声,而在杰出的男性作家笔下,却能显现出女性的情怀与爱心。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性格与环境小说”中,就敢于超越“天使或魔鬼”的传统偏见,真正吐露出西方一代女性的心声。
[关键词]性别视角;哈代;小说;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1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08)06-0143-03[收稿日期]2008-03-21[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全球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研究的走向———从男性作家作品中发掘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贺 萍(65),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教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
哈代是19世纪最后十年饮誉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在英国文学史上,他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女性人物性格、心理、行为和命运大异于一般男性作家的兴趣和同情。
英国作家伍尔夫早就评论过哈代:“他对女人比对男人表现了更为温情的关切,这也许是他对她们有更加强烈的兴趣。
”[1]作为一名女性读者,笔者拟用性别视角来重新阅读审视他的创作。
综观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都是以男性为轴心的。
在这个父权文化世界中,男性是一个时代的主宰,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
男性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性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陪衬、一个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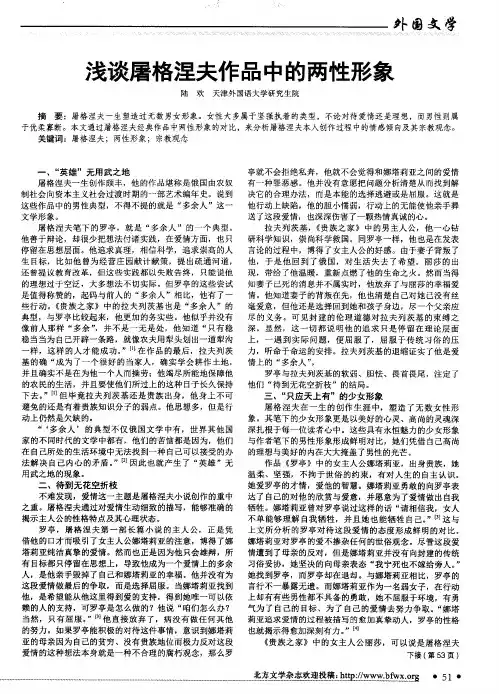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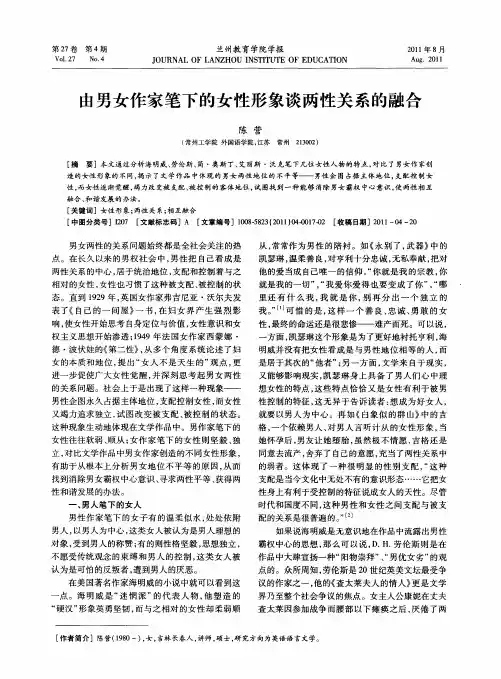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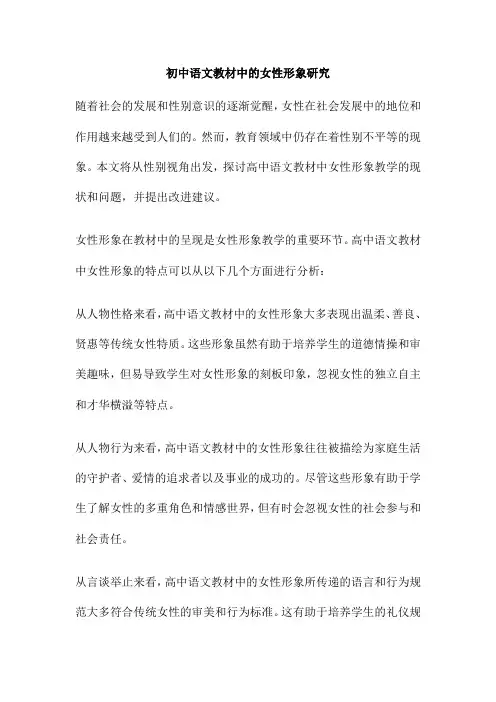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性别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然而,教育领域中仍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本文将从性别视角出发,探讨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女性形象在教材中的呈现是女性形象教学的重要环节。
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人物性格来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大多表现出温柔、善良、贤惠等传统女性特质。
这些形象虽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趣味,但易导致学生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忽视女性的独立自主和才华横溢等特点。
从人物行为来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描绘为家庭生活的守护者、爱情的追求者以及事业的成功的。
尽管这些形象有助于学生了解女性的多重角色和情感世界,但有时会忽视女性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
从言谈举止来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所传递的语言和行为规范大多符合传统女性的审美和行为标准。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礼仪规矩和行为习惯,但同时也可能限制学生对女性多元形象的认知。
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教材中女性形象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由于教材编写者的性别观念和意识固化,导致女性形象过于单一,缺乏多元性和真实性。
这不仅会影响学生对女性形象的全面了解,还会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教学过程中对女性形象的度不够。
教师往往更多地于课本内容的知识点,而忽视了对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这就会使得女性形象教学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教师对女性形象教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影响着教学效果。
有些教师对女性形象的理解存在偏差,无法客观地评价教材中的女性形象,从而导致学生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产生误解。
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为了改进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教学,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新审视教材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增加多元、真实的女性形象。
编写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女性形象的多样性,融入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女性形象,让学生全面了解女性的多重身份和多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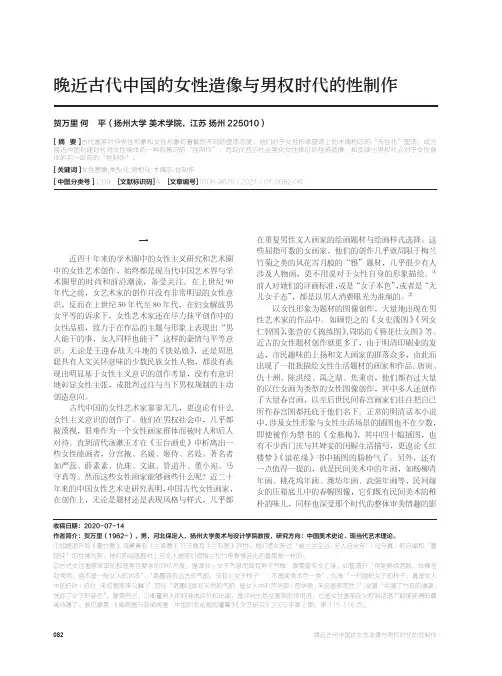
晚近古代中国的女性造像与男权时代的性制作贺万里 何 平(扬州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10)[ 摘 要 ]古代画家对待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塑造态度,他们对于女性形体塑造上的木偶相态的“无性化”塑造,成为晚近中国封建时代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有意识的“性制作”。
而现代西方社会强化女性体征的性感造像,却反映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另一取向的“性制作”。
[ 关键词 ]女性图像;类型化;男相化;木偶态;性制作[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1)01-0082-06收稿日期:2020-07-14作者简介:贺万里(1962-),男,河北保定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论、现当代艺术理论。
①如管道升有《墨竹图》,薛素素有《兰草图》,马守真有《兰石图》存世。
他们借此表达“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马守真)的自喻和“喜轻侠”的性情写照。
她们的绘画题材上与文人画家们借梅兰松竹等寄情自比的套路是一样的。
②古代女性画家采取的都是男性要求的评价尺度,强调非小女子气息而具有男子气概,寥雯曾专文汇录。
如管道升“用笔熟练洒脱,纵横苍劲秀丽,绝不是一般女人的状态”,“笔墨具有远古的气韵,没有小女子样子……不是闺秀本色一类”;仇珠“一扫脂粉女子的样子,真是女人中的伯时(伯时,宋名画家李公麟)”;范珏“笔墨间具有天然的气韵,是女人中的范华原(范华原,宋名画家范宽)”;寇湄“点缀了竹石的情调,洗却了女子的姿态”。
寥雯指出,以衡量男人的标准做评价和比喻,是评判出色女画家的常用语,也是女性画家在父权制话语下能够获得的最高待遇了。
参见寥雯:《闺阁画与新闺阁画:中国妇女绘画的藩篱》《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5-116页。
一近四十年来的学术圈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和艺术圈中的女性艺术创作,始终都是现当代中国艺术界与学术圈里的时尚和前沿潮流,备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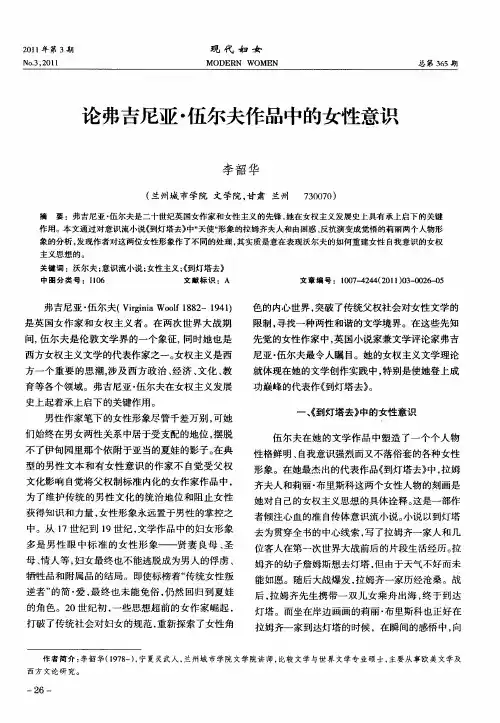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研究摘要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是东西方的文学巨匠,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他们饱含人文主义情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照人、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他们讴歌和赞美的女性身上表现出的特征,都是他们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
但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地位,又使他们看待女性的眼光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莎士比亚关汉卿人文主义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奉格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它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和人的价值,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
英国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在作品中,他不仅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更主张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对女性有权追求幸福爱情的肯定,则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
莎士比的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不再是中世纪文学中男性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个性和鲜明性格的大写的人。
而在13世纪的中国,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则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关汉卿的杂剧多以妇女为题材,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社会底层妇女形象。
他的杂剧创作不单单是反映当时元代社会的妇女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她们的内心追求,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这两个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家,饱含人文主义情怀,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关注女性命运,讴歌和赞美女性形象。
一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古今中外作家不惜笔墨着力渲染的话题。
莎士比亚的作品总是生动地展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遭遇,揭示女性有追求自己幸福爱情的权利。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反对封建教会的禁欲思想,塑造了众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主的大胆叛逆的女性形象。
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大胆叛逆,不畏父权和政权的威逼,为寻求真爱而违背父亲“三匣择婚”的意愿。
她的择偶条件不是门第和财富,而是个人的人品、相貌和才能;《驯悍记》中的阿德里安娜尽管身背“河东吼狮”的恶名,但她真诚地渴望甜蜜爱情和大胆追求现实生活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
现当代文学从《红玫瑰与白玫瑰》到《青蛇》看女性失衡的爱情观和悲剧的命运杨晶 四川大学摘 要:本文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玫瑰”的意象之境谈到李碧华《青蛇》的人物重塑。
通过“红玫瑰”、“白玫瑰”和“青蛇”、“白蛇”的对比分析,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描写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失衡的爱情观和悲剧命运。
进一步比较了两位女作家在写作风格,故事架构,人物塑造,创作背景等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张爱玲;“玫瑰”张爱玲曾经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以男性的角度说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比喻:“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这个比喻是这样的一针见血,直抵人心,让女性感慨此岸与彼岸心境是如此的不同,爱情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严重的失衡。
李碧华在《青蛇》里也对这段话进行了模仿和重新解读:“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
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
——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脆爽刮辣的嫩叶子。
当他得到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
”同样的结构,同样的隐喻,指出了女性尴尬的处境,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成为男人心中完美的女性,都无法将温柔与热情,妻性与情人等全人格融为一体。
两位女作家都以细腻敏感的目光,探索了失衡的情爱世界的悲喜苦乐,描写了红尘男女的挣扎沉浮。
张爱玲是民国时期的才女,李碧华是近代香港文坛上的奇女子,两人生活相差半个世纪之久,却总被人们加以比较。
她们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两朵奇葩,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擅长写情,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但她们不止于写情,在写情中融入了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意蕴,所以书中人物独具一格,故事别出心裁。
但是她们的叙述模式,写作风格,人物形象却是大不相同的。
论王安忆《天香》中的人性书写--以小绸为例摘要:从2011年王安忆《天香》发表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天香》整篇小说也给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探讨。
一方面是关于天香的小说价值,本身在语言、描写方面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是小说人性的书写。
在王安忆的笔下,《天香》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社会传统女性,仅仅是男人的附属品。
她们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她们具备时代的特征,具有传统性,另一方面王安忆赋予了她们新的灵魂,她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女性的角色。
他们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结合。
在王安忆的《天香》笔下,虽然生活着众多男男女女,但是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不同的人生境遇。
当男性在天香园中不断隐退的时候,女性登场了。
她们用她们的善良、坚韧、勇敢、聪慧支撑起了整个家族的重担。
她们没有抱怨,依然组织学习刺绣技艺。
天香园中男性女性便是小说的人性抒写。
本文主要以小绸为例,来分析《天香》中的人性书写,以及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和思考。
关键词:人性抒写、天香、小绸、女性一、引言人性就日常用语上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上是指人的本质心理属性,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属性,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广义上是指人普遍所具有的心理属性,其中包括人与其它动物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属性。
无论是人的本质心理属性,还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属性,由于它们都是人所共有的心理属性,那么这种属性也就不可能是后天的结果,只能是人类天性,属于无条件反射。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
一部优秀的佳作的产生,总是少不了扣人心悬的情节,整个故事的精彩连贯、语言的生动有色。
而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任务人性的描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它能让整篇小说更加鲜活,有色。
王安忆当代知名女作家,2011年她的长篇新作《天香》在《收获》杂志上成功发表。
女性作家的思维不同于男性作家,在女性描写方面会有更深刻层次的理解。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也往往离不开爱情和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
就总体性而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显得比男性更加鲜活而积极。
因为在世界在向机械化、技术化发展的同时,展示给人们的将是一个越来越冰冷的一面;而女性世界却是充满温暖的,未来世界需要的正是女性才能给予的温暖。
这种思想使得昆德拉常常以男性为标本分析人类恶的一面,把人类善的一面赋予女性。
他塑造女性形象所倾注的情感与希望在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告别圆舞曲》、《不朽》等小说中得到了体现。
昆德拉在《小说艺术的谈话》中提到,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
只要创造一个想象的存在,一个人物,你就必然面临“自我”的问题。
他曾经引用但丁的话说,“在任何行动中,人的第一个意图就是揭开自己的面貌。
”[l‘,由此可见,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也必定离不开对自我的关注。
因此,在此部分我们将超越传统伦理道德的层面更加注重人本主义的视角,从对自我的关注方面来分析昆德拉文本中展示出来的女性形象,依据以上探讨的本真与沉沦之含义将其分类,并站在对自我关注和人性理解的立场上,对她们进行新的关于本真或沉沦的定位与解读。
一、沉沦的代表这一类女性形象丧失了独立的个性,处在一种平均状态和两可之间。
要么活在丈夫的视线下,要么生活在儿子的无形管束中,要么在渴求灵与肉的统一中倍受煎熬,或企图成为男性赏玩女性时的助手,或希望于被男人注视的目光中获得自我满足。
代表人物有卡米拉(((告别圆舞曲》中小号手克利玛的妻子)、玛尔凯塔(((笑忘录》中的女主人公)、寡妇(((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特蕾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女性形象。
在昆德拉看来,这一类人物形象处于传统的理性主义时代,就像《圣经》中的“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
上帝耶和华在创造了万物,又创造了亚当之后说: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于是,上帝便“使他沉睡”,“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辛夷坞小说两性形象及相处模式探析辛夷坞是一位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畅销作家,其作品多以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为主线展开。
其小说中的男女形象及相处模式是其作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本文将从两性形象、相处模式两个方面来探析辛夷坞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形象及相处方式。
一、两性形象辛夷坞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形象多种多样,但具有一定的特点。
1.男主角形象辛夷坞笔下的男主角大多是外表英俊、性格坚毅、事业有成、善于保护女主角的男性。
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韩大爷,他有着坚定的信仰和追求,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左耳》中的顾里,他是一个聪明、独立、有责任感的男人,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负责。
他们都勇往直前,成为女主角心中的依靠。
辛夷坞的女主角则多是天真可爱、善良温柔、坚强独立的女性。
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陈末,她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孩,能够为自己的爱情和梦想勇敢地去争取;《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贝微微,她善良而有智慧,对待事情也非常果断。
她们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最终都赢得了自己的幸福。
二、相处模式1.尊重和信任在辛夷坞的小说中,男女主角之间的相处模式非常注重尊重和信任。
男主角尊重女主角的意见和决定,同时也给予女主角自由的空间,不会过于干涉她们的生活和工作。
女主角也信任男主角,能够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真实感受。
比如《微微一笑很倾城》中,贝微微有自己的事业,顾漫也很支持她,不担心她会把自己抛在脑后。
同时,在生活中,两人都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和生活方式,十分和谐。
2.相互鼓励和支持在辛夷坞小说中,男女主角之间常常会相互鼓励和支持。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另一个人总是不断地为他加油鼓劲,帮他渡过难关。
比如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韩大爷的信仰和追求源自于林微微鼓励和支持。
在《微微一笑很倾城》中,贝微微在面对困难时,顾漫总是默默地支持她,鼓励她。
这种相互扶持的关系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牢固。
3.有爱无争在辛夷坞的小说中,男女主角之间的争吵和矛盾很少,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有爱无争。
狄更斯的女性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在赞扬女性的同时又无意地贬低了女性。
他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作品中为男女两性设定了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他肯定了女性的地位,认为和谐的家庭一定会有一个理想的女性;但又要求女性内外兼修,这些宜室宜家的女性既要温柔、无私、善良,又要美丽、柔弱、质朴。
标签:狄更斯;女性观;女性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十九世纪英国甚至世界文坛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被称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神明”。
他毕生创作了一百多部短篇小说,几十部中篇小说,还有十五部长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随笔等。
狄更斯认为男女两性在才智上的发展是不同的:女性是感性的象征,是爱和善的化身;而男性是理性的化身,是责任与力量的象征。
因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女性就需要待在家里。
当男性在外面拼搏得累了,家就成了温情的港湾。
狄更斯所认为的理想女性是温柔善良的,而不是自私冷漠的;她们能管理好各种家务,并能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她们可以用爱感化周围的所有人,并不要求回报。
这种家庭天使般的女性,正是狄更斯突出笔墨所要赞扬的。
维多利亚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被狄更斯巧妙的融于他的小说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女性观。
一、承认男女两性的差异两性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由于男女两性生理上的不同,就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不同。
男性一般被认为是强大和健壮的,女性则被认为是柔弱和娇小的。
因为男女两性存在根本的差异,所以他们的社会职责也有所不同。
男性因为强大的身体和较强的心理素质,他们大多数从事着家庭以外的职业,例如速记员、牧师、记者、律师等;女性受第二性的影响只能从事与家务相关的工作,如相夫教子、管理佣人、装扮家庭等。
狄更斯作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深受男权主义和性别差异的影响,也很难摆脱对女性的偏见。
在他的笔下塑造了一大批从事家务工作的理想女性,他反对妇女像男性一样在外工作。
男女两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摘要:本文男女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美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使我们从千姿百态女性的形象中,从男女两性的差别,力图将两性中各自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创造和谐完满的人类世界与文化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思想;女性意识;双性同体纵览古今文学,女性历来是文学中的“第一性”,即男性创造出来的供欣赏和消遣的“器物”。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强烈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使男性作家在其女性形象的描写中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感为目的。
这实际上是指男性主宰一切,女性完全被排除在主动范畴之外的概念,女人无形中被固化为“附属”和“他者”。
这种思想在已有的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者对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有了清醒、深刻的看法。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认为,在两性关系的权力结构中,男性通过性政治支配女性。
性政治“把女性局限在性和生育的事务中,而让男子便于获得有别于女性的人生经验……它把男子在自己身上感到满意的东西标榜为男性优越的证明,而把女性身上有利于受控制和支配的特征说成是女人的天性。
”[1]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二十被造就的”[2]本文试图从男女两性的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的的异同,来挖掘潜在的女性意识,实现两性的更加和谐。
同时也使我们看出女性作家的创作艺术才华,可同男性作家相媲美。
一,他们眼中的她们“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3]。
从人类的文学起源—神话起,一直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女性始终是作为主要人物陈述的对象,或作为次要、点缀性人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能接受文化教育且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是凤毛麟角,所以绝大多数的女性形象都是出自男性作家的笔下。
而在这些传统的书写中,女性形象常常给予概念化、模式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天使型;二是魔鬼型。
1 家中的“天使”“家中天使”是男性作家塑造出来的能满足男性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都有着天使般的美丽、纯洁、善良和无私。
长期以来,“家中天使”一直维系着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和人性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
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常常根据这些文学女性形象来调整、设计自己的生活。
西方文学中的天使女性人多传承了圣母的美德:贞洁温顺、恬静安宁 .富有母性。
歌德笔下的绿蒂是“一位天使!……那么理智却又那么单纯,那么坚强却又那么善良,那么切实地生活和操劳着,心灵却又那么宁静……”[4]她体贴父亲,悉心照顾弟妹,而对少年维特则始终待之以友情,拒之以礼仪。
绿蒂成为了那个时代淑女的典范。
狄更斯的艾妮斯也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她温柔、聪慧、克己、坚强,一生遵奉“于人有利,于己有利”的信条。
她不断支持备尝艰辛的人卫,成为他的知音。
这些天使般美丽、纯洁、顺从、无私的理想女性成为了现实社会中妇女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她们变成了艺术对象还是圣徒,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或自我愿望,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那些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妇女的最主要的行为,更确切地说,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和天堂。
因为,无私不仅意味着高贵,还意味着死亡。
”[5]在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这种将女性理想化、神圣化的行为,无疑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这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正是男性中心文化用以压制女性的性政治策略之一。
男性通过塑造“天使形象”来左右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她们树立榜样,使她们乐于扮演模范角色,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意识,充当“家中天使”的角色。
2生活中“魔鬼”在男性文本中,凡是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成魔鬼。
长期以来,这种女性一直都是被世人攻击和唾弃的对象。
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便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习俗和要求,努力规避这种女性形象。
《圣经》故事中,亚当因为受到夏娃的蛊惑偷吃了智慧之果,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而且,此罪还祸及后世子孙,成为了人类水远的原罪。
希腊神话中,美丽的女人潘多拉将一切灭祸从匣子中放出来祸害人类,却将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水远地关在了匣子中。
从此,女人被认为是人类罪恶和灭难的根源。
在很多古代神话中,凶恶而可怕的妖精也往往被描绘成年轻漂亮的女性,她们总是以美色诱惑男性,使其丧失理智,沉沦堕落。
因此,女人又成为男人堕落和毁灭的根源。
这些女人的罪过都在于她们的美貌,它会使“无辜”的男人走上歧途。
于是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个性强悍、凶狠狂暴的女性形象—悍妇形象。
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悍妇形象: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塑造了美狄亚这个“悍妇”形象。
美狄亚为了帮助爱人伊阿宋获得金羊毛,不惜残杀并肢解了自己的亲兄弟。
当后来她得知伊阿宋另有新欢,意欲抛弃她时,她用巫术烧死新娘及其父亲,还亲手杀死自己的一双爱子,以达到让伊阿宋绝嗣的目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让美狄亚成了魔女的化身。
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野心比其丈夫更甚,心肠比丈夫更狠,在使丈夫从国家的功巨堕落为血腥的拭君篡权的过程中,麦克白夫人的邪恶怂恿起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其短篇《瑞普·凡·温克尔》,描述了具有一个欺凌丈夫恶名的“悍妇”形象。
她整日地喋喋不体,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
“凶悍的性情、也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温和,尖刻的舌头却是一柄惟一的愈用愈锋利的刀子。
”至此作者对她欺负丈夫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二分,形象生动。
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和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破坏了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这显然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
女人的不顺从、不放弃,既是对男人尊严的蔑视,也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挑战。
于是,男性作家便将女人的这种特点描绘成不能容忍的“恶德”,而具有这种“恶德”的女性便不可避免地遭到社会的攻击和唾弃。
事实上,“女人身上被指责为‘恶德’的品行未必就是邪恶的,它之所以被指责为‘恶德’,只是因为它表现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气”。
它使男性在生活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男性会为此进行抗辩,于是在男性的文本中出现了悍妇形象。
男性文本中也不乏将富于魅力、以姿色迷人的女性描绘成妖精的事例。
萨克雷笔下的交际花贝基 夏普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妖精:“在描写这个能歌善笑、花言巧语的妖精时作者不卑不亢地求证于诸位读者,诸位是否以为他有失风雅之趣,让诸位看见这妖精把尾巴翘出了水而?非也。
诸位可向清澈的水下窥视,她的尾巴在那里滑溜溜地扭摆,十分可怕,在自骨中拍打,缠着尸体;但在水而上,她处处都显得温良恭检……”[6]作者无疑是在告诉读者,女人的另一面是妖怪,是魔鬼,并警告男人提防她美丽外表之下的狰狞面目。
事实上,男性文本中这些歪曲和贬低女性的妖精、悍妇荡妇和女巫或女尼等“魔鬼”所反映的正是男性文学中的厌女症传统,是男人为了掩盖他在某些方而对女性的恐惧面对她们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是男人将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和主题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重要表现。
二,她们眼中的自己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到女人应该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寻求自己经济的独立,无需依赖他人和余男人平等的意识。
美国肖瓦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作家从勃朗蒂到莱辛》,详细论述了女作家的自我意识如何在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时间内变成一种文学形式,这种自我意识如何变化和发展,并且可能导向哪里。
正是像她们这样的女性主义先驱唤醒了女性的意识,从而使女人们勇敢的把积聚在心中所有的压抑与不平诉之笔端,向男权社会及男性中心论发起反抗,为女性平反,谋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1女性意识的觉醒凯特·肖班的《觉醒》最自觉、最大胆地描写女性意识的作品。
这它描写美国南部一位富商的妻子爱德纳·邦迪里埃太太的苦闷—对婚姻的不满和生活的无意义.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家庭的奴隶”之时起,她的作人的意识就开始觉醒。
她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丈夫的奴隶,甚至阴谋诡计们也是她的主人,要把她“拖进灵魂的奴役之中”,她不愿再扮演奴隶的角色了.但当她想寻找新的出路时,却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只能以投身大海作为最后的归宿,死亡也正是“觉醒”最好的答案。
她的另一篇作品《一小时的故事》虽然是个短篇,但和这篇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表现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然发现,但故事更富于戏剧性。
作者选择了玛拉德太太突然得知丈夫遇车祸身亡,开始还感到非常悲痛,但继而感到一阵轻松,如释重负,因为自己是跟一个多么平庸、无聊的人过了大半辈子。
她开始幻想未来独立的生活,毋须屈从任何人。
她一遍又一遍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
”她快速地祷告,希望生命再长久一点。
但颇具讽刺惫味的是作者笔锋一转,熟悉的钥匙开门的声音令她大吃一惊,继而她看到丈夫活生生地走进来时,她突发心脏病而身亡。
医生说是“过度兴奋”,的确是“过度兴奋”,但兴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她重新获得了“自由”,还是丈夫的“复活”?如果不是由于“过度兴奋”,她也不致于在见到丈夫生还的一刹那而丧失生命.她为了这一刹那的自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不难看出,妇女的觉醒需要付出何其惨重的代价,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被压抑的真实的心理感受又是很难从表面现象观察出来的,但它象火山一样,到一定的时候总要喷发出来。
2有抗争转向平等伍尔夫是第一个提出“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者,她摒弃了生物学上的涵义而发挥了心理学上的寓意。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伍尔夫借“双性同体”探讨了创作问题,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7]伍尔夫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索质,只有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小同的性别元索才能创造出再现生活全部的伟大作品。
“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另一种双性”:“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8]西苏所说的双性同体既是对立的消解,又是差异的表达。
双性没有特别尖锐的对立,也不排斥任何一性,可以通过互相交流激发巨大的活力。
在多丽丝 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就有这一思想的明显体现,安娜得了“写作障碍症”,无法继续创作。
在她的梦里反复出现一个时而男性、时而女性的矮人形象,令她惊恐不已。
这时,她遇见了同样遭受写作障碍痛苦的美国作家索尔·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