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之“物哀”美传承论文
- 格式:doc
- 大小:29.0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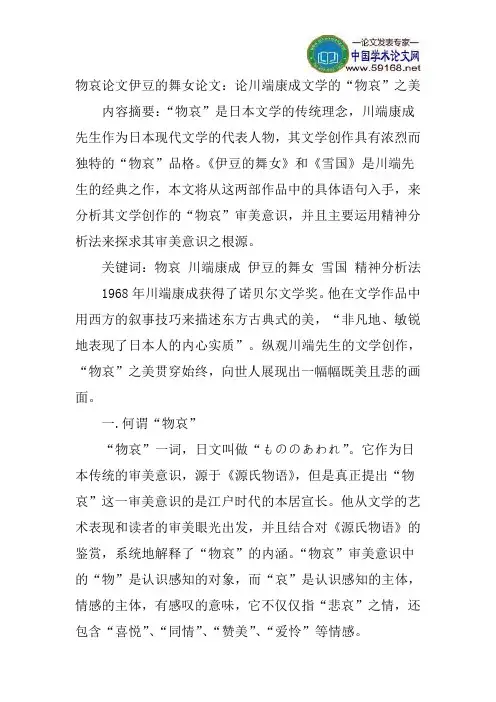
物哀论文伊豆的舞女论文:论川端康成文学的“物哀”之美内容摘要:“物哀”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理念,川端康成先生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其文学创作具有浓烈而独特的“物哀”品格。
《伊豆的舞女》和《雪国》是川端先生的经典之作,本文将从这两部作品中的具体语句入手,来分析其文学创作的“物哀”审美意识,并且主要运用精神分析法来探求其审美意识之根源。
关键词:物哀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雪国精神分析法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文学作品中用西方的叙事技巧来描述东方古典式的美,“非凡地、敏锐地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实质”。
纵观川端先生的文学创作,“物哀”之美贯穿始终,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既美且悲的画面。
一.何谓“物哀”“物哀”一词,日文叫做“もののあわれ”。
它作为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源于《源氏物语》,但是真正提出“物哀”这一审美意识的是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
他从文学的艺术表现和读者的审美眼光出发,并且结合对《源氏物语》的鉴赏,系统地解释了“物哀”的内涵。
“物哀”审美意识中的“物”是认识感知的对象,而“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情感的主体,有感叹的意味,它不仅仅指“悲哀”之情,还包含“喜悦”、“同情”、“赞美”、“爱怜”等情感。
我国的叶渭渠教授将“物哀”分为对人的感动、对世相的感动和对自然的感动三个层次。
“物哀”就是情感主观接触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产生的幽深玄静的情感。
这大概就和我国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意境相似吧。
二.川端文学的“物哀”之美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始终追求着“物哀”这一审美情趣。
他把一切看作“美”,并且在这些“美”的背后隐含了作者深刻的细腻的哀愁。
他所描写的大自然、季节以及女性等既美且悲。
本节将通过《伊豆的舞女》和《雪国》两部代表性的作品,从自然、女性和死亡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川端文学的“物哀”之美。
1.自然美打开川端康成的作品,一幅幅美丽的自然风景浮现眼前,并且这些自然风景似乎都笼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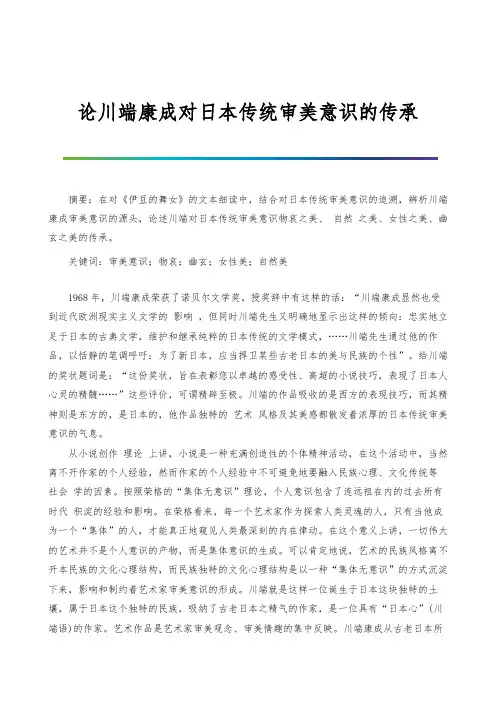
论川端康成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传承摘要:在对《伊豆的舞女》的文本细读中,结合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追溯,辨析川端康成审美意识的源头,论述川端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物哀之美、自然之美、女性之美、幽玄之美的传承。
关键词:审美意识;物哀;幽玄;女性美;自然美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辞中有这样的话:“川端康成显然也受到近代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同时川端先生又明确地显示出这样的倾向: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和继承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川端先生通过他的作品,以恬静的笔调呼吁:为了新日本,应当捍卫某些古老日本的美与民族的个性”。
给川端的奖状题词是:“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这些评价,可谓精辟至极。
川端的作品吸收的是西方的表现技巧,而其精神则是东方的,是日本的,他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美感都散发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气息。
从小说创作理论上讲,小说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个体精神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当然离不开作家的个人经验,然而作家的个人经验中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社会学的因素。
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个人意识包含了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时代积淀的经验和影响。
在荣格看来,每一个艺术家作为探索人类灵魂的人,只有当他成为一个“集体”的人,才能真正地窥见人类最深刻的内在律动。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伟大的艺术并不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意识的生成。
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的民族风格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沉淀下来,影响和制约着艺术家审美意识的形成。
川端就是这样一位诞生于日本这块独特的土壤,属于日本这个独特的民族,吸纳了古老日本之精气的作家,是一位具有“日本心”(川端语)的作家。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审美观念、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
川端康成从古老日本所承继的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正是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而完美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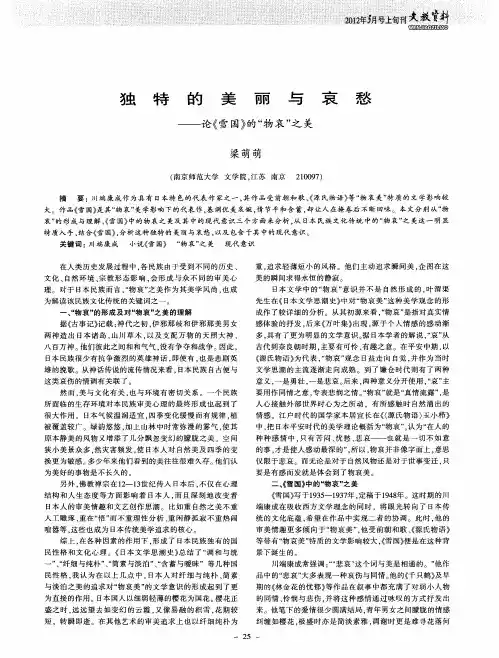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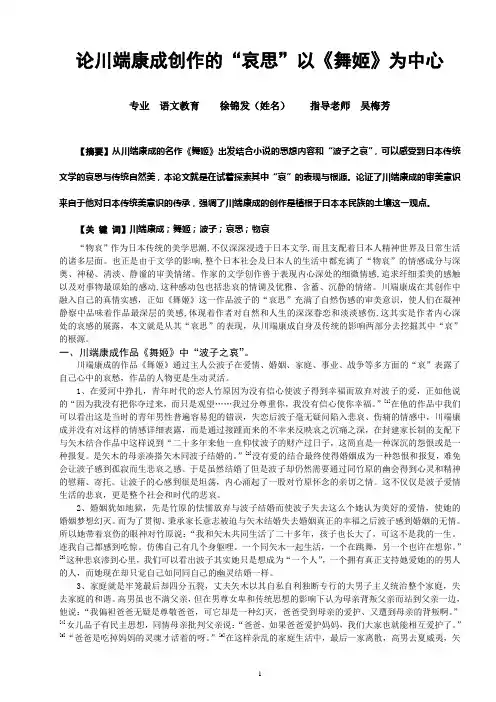
论川端康成创作的“哀思”以《舞姬》为中心专业语文教育徐锦发(姓名)指导老师吴梅芳【摘要】从川端康成的名作《舞姬》出发结合小说的思想内容和“波子之哀”,可以感受到日本传统文学的哀思与传统自然美,本论文就是在试着探索其中“哀”的表现与根源。
论证了川端康成的审美意识来自于他对日本传统美意识的传承,强调了川端康成的创作是植根于日本本民族的土壤这一观点。
【关键词】川端康成;舞姬;波子;哀思;物哀“物哀”作为日本传统的美学思潮,不仅深深浸透于日本文学,而且支配着日本人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
也正是由于文学的影响,整个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物哀”的情感成分与深奥、神秘、清淡、静谧的审美情绪。
作家的文学创作善于表现内心深处的细微情感,追求纤细柔美的感触以及对事物最原始的感动,这种感动包也括悲哀的情调及优雅、含蓄、沉静的情绪。
川端康成在其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正如《舞姬》这一作品波子的“哀思”充满了自然伤感的审美意识,使人们在凝神静察中品味着作品最深层的美感,体现着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深深眷恋和淡淡感伤,这其实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哀感的展露,本文就是从其“哀思”的表现,从川端康成自身及传统的影响两部分去挖掘其中“哀”的根源。
一、川端康成作品《舞姬》中“波子之哀”。
川端康成的作品《舞姬》通过主人公波子在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战争等多方面的“哀”表露了自己心中的哀愁,作品的人物更是生动灵活。
1、在爱河中挣扎,青年时代的恋人竹原因为没有信心使波子得到幸福而放弃对波子的爱,正如他说的“因为我没有把你夺过来,而只是观望……我过分尊重你,我没有信心使你幸福。
”[1]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当时的青年男性普遍容易犯的错误,失恋后波子毫无疑问陷入悲哀、伤痛的情感中,川端康成并没有对这样的情感详细表露,而是通过接踵而来的不幸来反映哀之沉痛之深,在封建家长制的支配下与矢木结合作品中这样说到“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仰仗波子的财产过日子,这简直是一种深沉的怨恨或是一种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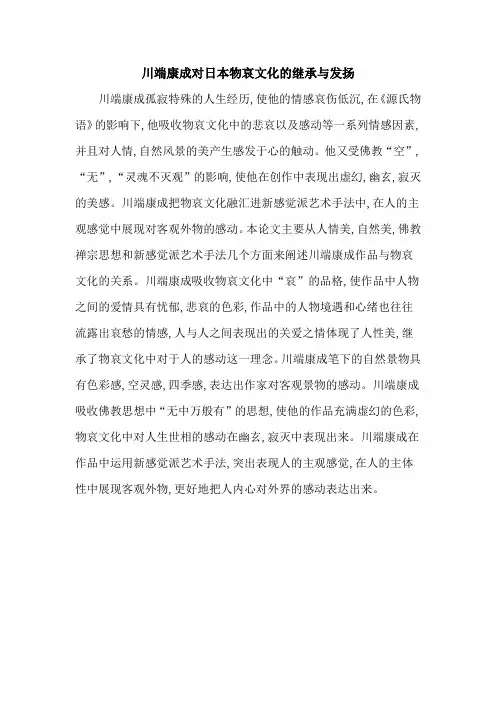
川端康成对日本物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川端康成孤寂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情感哀伤低沉,在《源氏物语》的影响下,他吸收物哀文化中的悲哀以及感动等一系列情感因素,并且对人情,自然风景的美产生感发于心的触动。
他又受佛教“空”,“无”,“灵魂不灭观”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虚幻,幽玄,寂灭的美感。
川端康成把物哀文化融汇进新感觉派艺术手法中,在人的主观感觉中展现对客观外物的感动。
本论文主要从人情美,自然美,佛教禅宗思想和新感觉派艺术手法几个方面来阐述川端康成作品与物哀文化的关系。
川端康成吸收物哀文化中“哀”的品格,使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爱情具有忧郁,悲哀的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境遇和心绪也往往流露出哀愁的情感,人与人之间表现出的关爱之情体现了人性美,继承了物哀文化中对于人的感动这一理念。
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景物具有色彩感,空灵感,四季感,表达出作家对客观景物的感动。
川端康成吸收佛教思想中“无中万般有”的思想,使他的作品充满虚幻的色彩,物哀文化中对人生世相的感动在幽玄,寂灭中表现出来。
川端康成在作品中运用新感觉派艺术手法,突出表现人的主观感觉,在人的主体性中展现客观外物,更好地把人内心对外界的感动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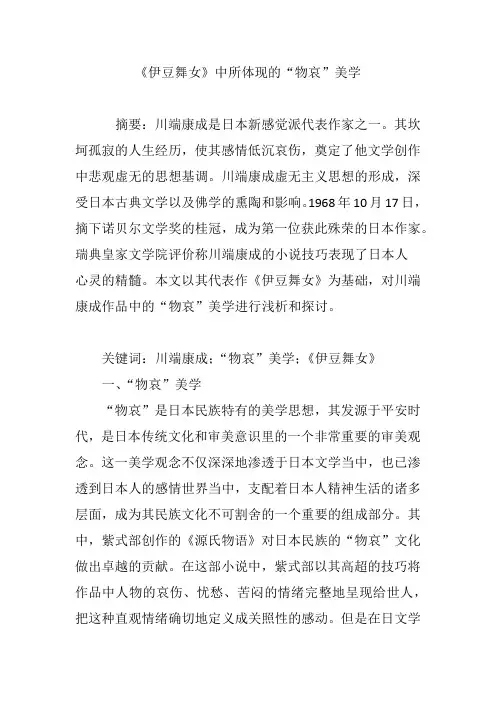
《伊豆舞女》中所体现的“物哀”美学摘要: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
其坎坷孤寂的人生经历,使其感情低沉哀伤,奠定了他文学创作中悲观虚无的思想基调。
川端康成虚无主义思想的形成,深受日本古典文学以及佛学的熏陶和影响。
1968年10月17日,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
瑞典皇家文学院评价称川端康成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本文以其代表作《伊豆舞女》为基础,对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美学进行浅析和探讨。
关键词:川端康成;“物哀”美学;《伊豆舞女》一、“物哀”美学“物哀”是日本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其发源于平安时代,是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观念。
这一美学观念不仅深深地渗透于日本文学当中,也已渗透到日本人的感情世界当中,支配着日本人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对日本民族的“物哀”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这部小说中,紫式部以其高超的技巧将作品中人物的哀伤、忧愁、苦闷的情绪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把这种直观情绪确切地定义成关照性的感动。
但是在日文学界学者们却一致认为,“物哀”这一美学思想是由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所创立。
他认为,凡是目所能及耳所能听的事物,将其放在心中去品味,身体力行地去体验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了物之哀。
而其后的出现的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博士又将物哀的性质分为五种类别,即感动,优美,调和,情趣和哀愁,其中又以哀愁最能体现“物哀”之美。
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诵读《源氏物语》的川端康成,深受作品中感伤、哀愁、低沉的语句和情感的影响。
对其日后的文学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川端康成的文学艺术创作浸润着“物哀”美学,悲与美的统一是贯穿了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审美基调。
二、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生于大阪市北区的一个医生之家。
两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三岁时母亲也因感染结核病而辞世。
自此,川端康成由祖父母领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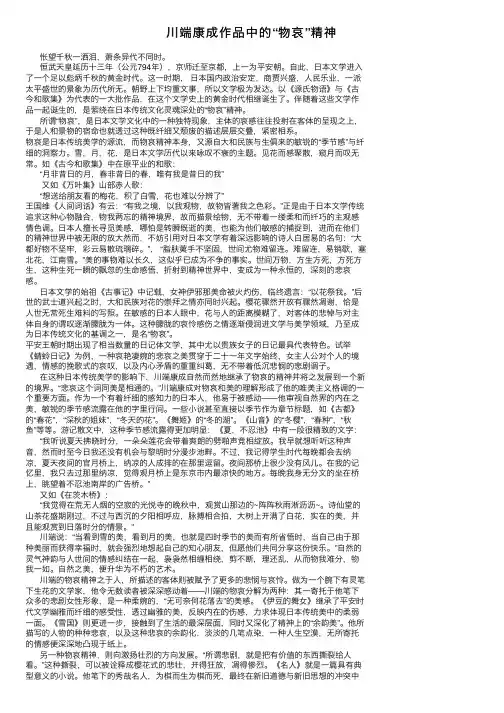
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精神怅望千秋⼀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恒武天皇延历⼗三年(公元794年),京师迁⾄京都,上⼀为平安朝。
⾃此,⽇本⽂学进⼊了⼀个⾜以彪炳千秋的黄⾦时代。
这⼀时期,⽇本国内政治安定,商贾兴盛,⼈民乐业,⼀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为历代所⽆。
朝野上下均重⽂事,所以⽂学极为发达。
以《源⽒物语》与《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批作品,在这个⽂学史上的黄⾦时代相继诞⽣了。
伴随着这些⽂学作品⼀起诞⽣的,是萦绕在⽇本传统⽂化灵魂深处的“物哀”精神。
所谓“物哀”,是⽇本⽂学⽂化中的⼀种独特现象,主体的哀感往往投射在客体的呈现之上,于是⼈和景物的宿命也就透过这种既纤细⼜颓废的描述层层交叠,紧密相系。
物哀是⽇本传统美学的源流,⽽物哀精神本⾝,⼜源⾃⼤和民族与⽣俱来的敏锐的“季节感”与纤细的洞察⼒。
雪,⽉,花,是⽇本⽂学历代以来咏叹不衰的主题。
见花⽽感聚散,窥⽉⽽叹⽆常。
如《古今和歌集》中在原平业的和歌:“⽉⾮昔⽇的⽉,春⾮昔⽇的春,唯有我是昔⽇的我”⼜如《万叶集》⼭部⾚⼈歌:“想送给朋友看的梅花,积了⽩雪,花也难以分辨了”王国维《⼈间词话》有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彩。
”正是由于⽇本⽂学传统追求这种⼼物融合,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故⽽描景绘物,⽆不带着⼀缕柔和⽽纤巧的主观感情⾊调。
⽇本⼈擅长寻觅美感,哪怕是转瞬既逝的美,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到,进⽽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被⽆限的放⼤然⽽,不妨引⽤对⽇本⽂学有着深远影响的诗⼈⽩居易的名句:“⼤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 “脂肤荑⼿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
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美的事物难以长久,这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间万物,⽅⽣⽅死,⽅死⽅⽣,这种⽣死⼀瞬的飘忽的⽣命感悟,折射到精神世界中,变成为⼀种永恒的,深刻的悲哀感。
⽇本⽂学的始祖《古事记》中记载,⼥神伊邪那美命被⽕灼伤,临终遗⾔:“以花祭我。
”后世的武⼠道兴起之时,⼤和民族对花的崇拜之情亦同时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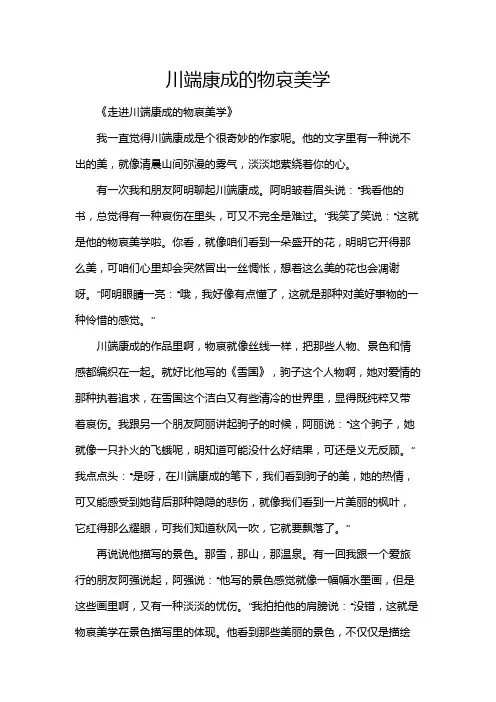
川端康成的物哀美学《走进川端康成的物哀美学》我一直觉得川端康成是个很奇妙的作家呢。
他的文字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就像清晨山间弥漫的雾气,淡淡地萦绕着你的心。
有一次我和朋友阿明聊起川端康成。
阿明皱着眉头说:“我看他的书,总觉得有一种哀伤在里头,可又不完全是难过。
”我笑了笑说:“这就是他的物哀美学啦。
你看,就像咱们看到一朵盛开的花,明明它开得那么美,可咱们心里却会突然冒出一丝惆怅,想着这么美的花也会凋谢呀。
”阿明眼睛一亮:“哦,我好像有点懂了,这就是那种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怜惜的感觉。
”川端康成的作品里啊,物哀就像丝线一样,把那些人物、景色和情感都编织在一起。
就好比他写的《雪国》,驹子这个人物啊,她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追求,在雪国这个洁白又有些清冷的世界里,显得既纯粹又带着哀伤。
我跟另一个朋友阿丽讲起驹子的时候,阿丽说:“这个驹子,她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呢,明知道可能没什么好结果,可还是义无反顾。
”我点点头:“是呀,在川端康成的笔下,我们看到驹子的美,她的热情,可又能感受到她背后那种隐隐的悲伤,就像我们看到一片美丽的枫叶,它红得那么耀眼,可我们知道秋风一吹,它就要飘落了。
”再说说他描写的景色。
那雪,那山,那温泉。
有一回我跟一个爱旅行的朋友阿强说起,阿强说:“他写的景色感觉就像一幅幅水墨画,但是这些画里啊,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没错,这就是物哀美学在景色描写里的体现。
他看到那些美丽的景色,不仅仅是描绘它们的美,还会把自己内心那种对美好易逝的感叹融入进去。
比如说那雪,洁白无瑕,可雪总会融化的呀。
当他描写雪的时候,就像是在和雪对话,既赞叹雪的美,又惋惜雪不能永远留存。
”我有次试着自己去模仿川端康成描写物哀的感觉。
我看到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我写道:“老槐树的枝丫在风中静静地伸展着,那斑驳的树皮像是岁月刻下的印记。
它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可我却仿佛看到了秋天时它的萧瑟,那些叶子会变黄、飘落,只剩下干枯的枝丫在寒风中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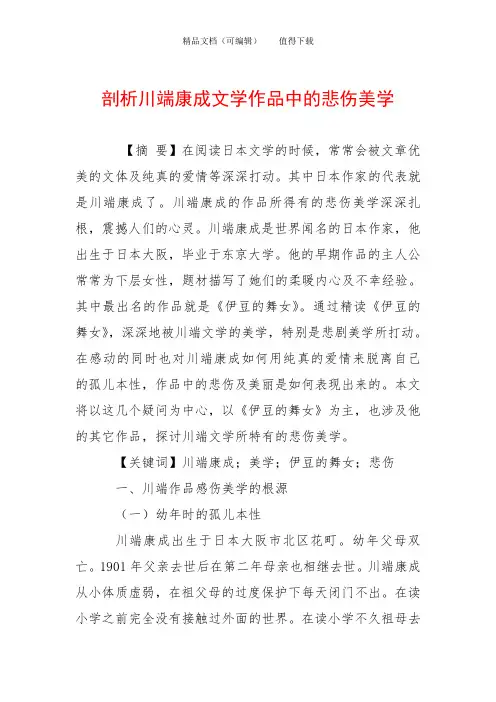
剖析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中的悲伤美学【摘要】在阅读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会被文章优美的文体及纯真的爱情等深深打动。
其中日本作家的代表就是川端康成了。
川端康成的作品所得有的悲伤美学深深扎根,震撼人们的心灵。
川端康成是世界闻名的日本作家,他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
他的早期作品的主人公常常为下层女性,题材描写了她们的柔暖内心及不幸经验。
其中最出名的作品就是《伊豆的舞女》。
通过精读《伊豆的舞女》,深深地被川端文学的美学,特别是悲剧美学所打动。
在感动的同时也对川端康成如何用纯真的爱情来脱离自己的孤儿本性,作品中的悲伤及美丽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本文将以这几个疑问为中心,以《伊豆的舞女》为主,也涉及他的其它作品,探讨川端文学所特有的悲伤美学。
【关键词】川端康成;美学;伊豆的舞女;悲伤一、川端作品感伤美学的根源(一)幼年时的孤儿本性川端康成出生于日本大阪市北区花町。
幼年父母双亡。
1901年父亲去世后在第二年母亲也相继去世。
川端康成从小体质虚弱,在祖父母的过度保护下每天闭门不出。
在读小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在读小学不久祖母去世不久外出的姐姐也去世了。
1912年读初中时最后的亲人祖父也去世,不得不被黑田家收养后开始了住校,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时候,川端康成已经是一名彻彻底底的孤儿。
这样的经历给川端康成幼年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二)“物哀”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读出日本传统美及自然美,精神上的余韵美,女性特有的柔美。
高中时期川端康成被《源氏物语》所打动内心,成为了他最初的精神摇篮。
此外,他的作品不仅处处充满悲伤,也处处能够感受到美丽。
所以我认为《源氏物语》中的“物哀”精神也影响到了他对美的意识。
所以,“物哀”的精神是川端康成悲伤美学的根源之一。
(三)佛教“禅”精神此外,川端康成也吸收了佛经中有关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文学。
受到佛教禅的影响,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也与佛教意识息息相关。
用理想的光芒来照亮读者苦闷内心,拯救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思想特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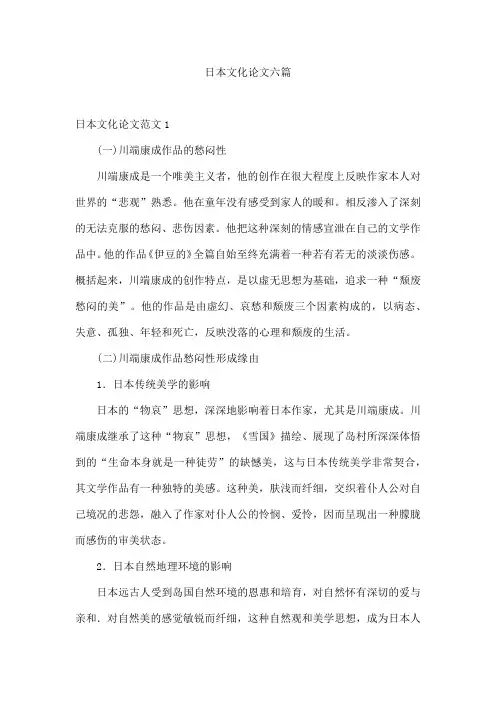
日本文化论文六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1(一)川端康成作品的愁闷性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熟悉。
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暖和。
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愁闷、悲伤因素。
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
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愁闷的美”。
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年轻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愁闷性形成缘由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现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非常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这种美,肤浅而纤细,交织着仆人公对自己境况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仆人公的怜悯、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制造艺术美的底流。
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
日本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难,无所不在的恐惊.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
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愁闷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愁闷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缘由。
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颜色。
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愁闷”、“悲”的颜色。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物哀”观翟文颖【摘要】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物哀”的意蕴,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早期作品表达了孤儿寂寞孤独之悲情,暗合了本居宣长所倡导如实记载人心的主张;二是中期作品所描述的男女恋慕而又不得之哀情,与本居宣长认为恋情最能表现“物哀”的主张一致;三是后期作品表达了人生而必死之苦情,符合本居宣长不论善恶只知“人情”的“物哀”观.川端康成的“物哀”观深受《源氏物语》与日本法西斯战败的影响,其对“物哀”为首的日本传统美的追求,既是他个人身世、性格与“物哀”论的高度契合,也是作为日本作家建立民族文化的一种举措.【期刊名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17)001【总页数】5页(P86-90)【关键词】川端康成;本居宣长;“物哀”观【作者】翟文颖【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014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313.44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唯美伤感,延续了日本“物哀”审美传统。
“物哀”是日本文学的关键词。
本居宣长将《源氏物语》的主旨定义为表现“物哀”,从此“物哀”作为独立概念使用。
为了排除“汉意”,他将“物哀”抬高到代表“大和魂”的地位。
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政府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建立在本居宣长“天皇神道”说的基础上。
此时,本居宣长才广为人知,“物哀”论还处于学术边缘地位。
日本法西斯战争失败后,本居宣长及其“天皇神道”说成为学术敏感话题,“物哀”论也销声匿迹。
20世纪60年代末,“物哀”论一转成为日本传统的审美理念、国家的文化象征。
其中,川端康成的贡献巨大。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他发表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高度赞美《源氏物语》等日本传统文化。
自此,谈到川端康成文学就涵盖了“物哀”、日本传统文化等丰富含义。
“物哀”是研究川端康成文学的一把钥匙。
一、早期作品之孤儿悲情在《紫文要领》和《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的创作动机和主题意义都是“物哀”。
川端康成的哀美艺术摘要:川端文学的哀美风格,是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川端康成数十年艺术心血的凝结,构筑了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作家,他继承了日本的传统美,以特有的纤细和敏锐的感受捕捉了“清淡而纯真之美,向世界展示了东方之美”—哀哀美。
《雪国》、《古都》、《千只鹤》在意象、境界、意识、情感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哀美风格。
此文试通过其孤独哀凉的人生、深刻的时代背景以及日本传统美三方面的影响来阐述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独特之美。
关键词:川端康成哀美物哀美学风格日本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浓郁审美情愫的民族。
川端康成的小说就充分展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内在美,他的小说将凝重与冷清,浓艳和颓废,不可捉摸地结合在一起,精致而富有朦胧的诗意,其中贯穿着一种淡淡的东方宿命,蕴含着人生的徒然与美的终结,以及无端的人生哀愁,这些使川端的小说产生了一种空幻而无从把握的艺术美感,并使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独特的美学风格。
川端康成的小说之所以形成既美且哀的独特风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孤独哀凉的人生川端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双亡,少年时代,祖母和姐姐又相继作古,从此与眼瞎耳背的祖父相依为命,使这位敏感的少年沉浸在哀哀之中,在他稚幼的心灵里投下了寂寞的暗影。
因此,幼年的川端康成更多体会到的是孤独与哀伤:1岁丧父,两岁丧母,8岁失去祖母,11岁失去胞姐,16岁与祖父死别,其命运如同被抛到庙里的小和尚一样。
这对人生是不幸的,但对作品却有着特殊的力量。
久而久之,他的内心不断涌现出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
这种孤独和痛苦的心情不免流露在作品之中,反映了他的个人隐私和想象力想混合而构成的人事情景,一部分来自夹杂着他童年孤寂的诗意,另一部分则有纯粹实体与神秘感情相间的意蕴。
川端康成的幼年时代,死为寻常事,因而他能够凝视生之界限—死,在死中了解生的本质,在他看来,死与所爱之人无关,也无法替代,也无法跨越,它只是个人的死,人只是一种走向这种死亡的存在。
谈川端康成文学中的“物哀"理念刘伟娜(f f肥学院外国语语言文学系,安徽合肥230601)摘要:川端康成,日本著名文学家。
以代表作《雪国》而闻名世界.成为日本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中大都渗透着“物哀”理念.本文从介绍川端康成及“物哀”含义入手.通过分析川端康成的经历和代表作《雪国》浅谈其文学中的“物哀”理念。
关键词:川端康成“物哀”《源氏物语》《雪国》1.川端康成及“物哀”的含义川端康成(1899—1972)。
日本著名文学家,1968年,因“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被诺贝尔基金会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他善用意识流手法展示人物内心世界,以其代表作《雪国》而闻名世界,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细读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会发现其中大都渗透着“物哀”理念。
“物哀”一词源于《源氏物语》(据统计:该物语中“哀”的感叹表达多达1044次.其中13次用了“物哀”一词)。
其中的“哀”有“悲哀”、“感动”、“爱怜”等诸多含义。
但正式提出“物哀”理念的是江户时代文学批评家本居宣长.他指出“物哀”理念中的“物”是认识感知对象,即物语中讲到的事物,生活中见到的事物,是一个泛指之词:“哀”则是指认识感知的主体所见所闻触动心思而发出的感叹之声,“哀”不限于悲哀之情,还包括其他的情绪,“悲愁”、“忧郁”、“恋慕”、“动人至深”等。
“物哀”就是情感主观接触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产生的情感.它包含“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等诸多因素。
“物哀”的思想结构可概括为三个层次: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
在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中继承发扬了日本美的源流,将“物哀”的“感人”、“感事”、“感物”三层思想融为一体。
创作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
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笔下的“物哀”之美一、《雪国》里的“物哀”渊源首先,从川端康成的恋爱经历来看,无疑,叶子成了他未完美的爱情的代替品,22岁时川端康成遇到了伊藤初代,从恋爱订婚到毁约,这段爱情在川端康成心中不可取代,而初代成了他记忆中深刻的痛,她像叶子又像驹子,美丽而不得,使人热切过也绝望过,作者给叶子的结局是死亡,这似乎给我们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对于作者而言,那曾美丽而令人叹息的东西最终是要被放生的,给那些记忆自由,也就是给自己自由。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作者自我内心中的一种释怀,对爱的释怀,对恨的释怀。
我们说,一个人难得把过往看得透,看得清,要是真做到了,那么该是庆幸还是悲哀呢,川端康成是做到了,但是这种做到或者说释然,该是有多么美丽与哀愁呢。
其次,从整个文章的氛围来说,不得不承认读川端康成的作品有一种或轻或重,或远或近的气质,无论是细致的情绪表达,还是优美独特的风景描写,都似乎在给人传达一种淡淡的美丽与哀愁,无疑这与作家本身的气质是相投的,川端康成自幼就失去父母,后来又经历了姐姐和祖父母相继离世的悲惨境遇。
他的童年少年几乎都是在亲人的一场场葬礼中度过的,因此我们相信川端康成对于死亡的概念比同龄人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参悟,过早的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对于其后来的写作有了最本质的影响,他的字里行间的疏离感、缺失感以及敏感细致入微无不体现着作家对于人生的思考。
最后,“物哀”是日本文学特有主题,它可以向上追溯到奈良时代,直至今日,尽管日本社会及文化同以往相比有了巨大变化,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对“新潮”文学作品中看到“物哀”的影子。
它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从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到室町时代、江户时代,物哀的内容趋于完备,成为一种有自足性的社会文化元素及文学主题。
最早我们能看到“物哀”二字的文学作品当属《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作品中的神话、歌谣等文学样式都是表达对自然神的感动。
相对较晚的《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这两部作品中的“物哀”基本形成其初态。
试论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之“物哀”美传承摘要:“物哀”作为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表达的是一种物与心交融后的感动。
川端康成在他的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和发扬“物哀”美,使自己崇尚的日本传统之美在淡淡的哀愁中不断升华。
本文在探究“物哀”内涵的基础上,解读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物哀”美的传承。
关键词:川端康成“物哀”同情传承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一生写了100余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那些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悲惨遭遇,刻画她们对生活、爱情和艺术追求的作品,如《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
在这些作品中,川端用大量的笔墨表现出了对以薰子、驹子、千重子等渺小人物的特有悲哀与同情,同时又以咏叹的方式表露出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同情、怜悯和哀伤的真实情感。
作品中主人公的悲哀感与作家自身的同情哀感相融合,再加上借用自然美的作用,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得到塑造。
在这些作品中,他致力于追求美,创造出有所感觉的美,并由此继承和发扬富有日本传统美学特色的“物哀”美。
本文拟在探究“物哀”内涵的基础上,解读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中日本式“物哀”美的传承与发展。
一何谓“物哀”1 “物哀”之起源“物哀”作为日本文学审美理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及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之后的世界首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
据《源氏物语论》的作者藤井贞和统计,在“《源氏物语》中用了一千多次‘哀’和‘物哀’”。
据此,体现“物心合一”审美情趣的日本文学传统审美理念——“物哀”基本形成。
在此之后,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家本居宣长(1730-1801)就《源氏物语》加以研究、整理,对“物哀”做出了如是概述:其一,“凡‘哀’者,本来是耳闻、目睹、感触到外在事务时,内心有所触动而发出的叹息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啊’‘哦’之类。
”其二,“‘哀’不单指悲哀,高兴、有趣、快乐、可笑,但有‘啊’‘哦’之叹,都是‘哀’。
”至此,“物哀”理念较完整地得到最终确定。
2 “物哀”之内涵“物哀”之“物”最初指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后升华到泛指人、社会世相、人情百态等客观存在之一切;“哀”即感叹,意指人在接触包括自然景物在内的外界事物时自然生成的一种主观情感。
“物哀”即客观与主观的结合。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物哀”的理解已远远超出其初始的内涵——睹物伤情、物我同悲。
叶渭渠先生就解释说:“‘物哀’除了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外,还包括哀怜、同情、感动、壮美的意思。
”由此可见,“物哀”是一种发自人内心的审美方式,是人凭借直觉来感受到的美,即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的美。
他还说:“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
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
”用一句话总结:“物哀”是日本民族移情于物、睹物生情的一种特有审美观念,其特点是将人的情感置于种种具体的物象,由此展现以“哀”为主线的真情美感世界,兼有对人、自然及世相的感动等基本特征,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
源于《万叶集》等而成于《源氏物语》的“物哀”这一日本式美学理念,自形成以来已深深渗透在日本人民的感情世界中。
它影响着一代代日本人的生活、思维方式,繁衍成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经川端康成等众多作家的进一步传承,也成为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之一。
二川端文学作品对《源氏物语》“物哀”美的传承川端康成就读中学阶段时就熟读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言:“《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内心底里的。
”因此,川端在其文学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对人、自然及世相的感动”这一“物哀”美重要特征,揭示出他对“物哀”最忠实、完整的传承与发扬。
表现悲哀与同情是川端小说的一大特点,以其成名小说《伊豆的舞女》为例。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20岁的高中生——“我”与一位14岁的卖艺舞女——薰子在伊豆的汤岛邂逅相遇的故事。
小说中的“我”与薰子的关系若即若离、似有非有。
在小说的结束部分,薰子独自一人到码头为“我”送行:“快到码头,舞女蹲在岸边的倩影。
赫然映入我的心中。
我们走到她身边以前,她一动不动,只顾默默地把头耷拉下来。
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了我的情思。
眼角的胭脂给她的秀脸添了几分天真、严肃的神情,使她像在生气……舢板猛烈的摇晃着。
舞女依然紧闭双唇,凝视着一个方向。
我抓住绳梯,回过头去,舞女想说声再见,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然后再次深深地点了点头……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
”整个送别场面舞女没说一句话,而她沉默无语的神情越发突显出她的楚楚可怜。
船就这样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唯有那洋溢着悠长低回、哀怨缠绵、深沉细腻的日本式“物哀”美意识,弥漫着《源氏物语》般的虚幻、哀伤情调。
《雪国》同样描述了岛村与艺妓驹子、叶子没有结果的交往故事,可以说是《伊豆的舞女》的进一步深入。
男主人公岛村来到原始的山区雪国观光,他的身边有着一显一隐的两位女性驹子与叶子,而小说便是由岛村对这两个美丽女子和对雪国的风景描述展开的。
岛村,因为驹子的出身提出离别,驹子追求的“真实”的恋爱,终成泡影;叶子也因一场大火而死去。
被刻画为美的象征的驹子与叶子的遭遇,显然是与悲哀相联系的,她们仿佛就是《源氏物语》中“源氏”身边的女子,个个命运悲惨。
而岛村俨然就是源氏的再世,性格忧郁,朝三暮四。
小说通篇渗透着一种忧生伤世的“物哀”情调,更浸润着日本古典文学的古典情趣。
显而易见,川端的作品处处显露出深深的“物哀”痕迹,悲情哀感自然地植入于其笔下人物,尤其是薰子、驹子等渺小人物悲剧结局的同情、哀怜,成功地渲染出一种悲哀与同情所交融的美感,充满了幽玄和余情,折射出《源氏物语》对川端文学的巨大影响。
三川端文学作品中“物哀”美传承的独特性川端康成在对自《源氏物语》以来日本古典文学“物哀”审美意识进行悉心传承的同时,他还以其独特的笔触发展日本式“物哀”美,即在其作品中渲染自然与世相给人带来的感动、感慨及无奈,形成其特有的日本传统的风雅精神。
1 情景交融的“物哀”观细心观察自然,抒发对自然美景的特殊情感,并将爱情融入其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
川端康成在文学创作方面通常都选择客观的自然物象加于运用,并把自我心绪巧妙地植入其中,以特有的写作手法创造出“物哀”美传承的独特性。
在《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就将故事及人物置于画境之中:跌宕的山峦、繁茂的森林、深邃的幽谷、浓郁的秋色、恬静的天空……所有这些景色都交织着人的美好情感,即“我”对薰子那种朦胧的初恋、纯真的情感。
此外,川端还在多处将“雨”这一大自然的物象借用来烘托人物情感。
如小说开篇:“骤雨白亮亮地罩在茂密的杉林上,以迅猛之势从山脚下向我追赶过来”。
此时的“雨”被赋予人性,将“我”和舞女联结,“我”急切想见舞女的心境在雨的烘托下表露无遗。
他就是这样巧夺天工般将情置入自然之万物,将写自然美同写人物美、人情美融合在一起,勾画出一幕幕日本式“物哀”的“物心合一”情境。
相同的创作方法也被用在了《雪国》当中,小说中情景交融的描述不胜枚举,《雪国》中对驹子的描述即是典范之一:“盈盈皓月,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
”如此精美的一句,巧妙地将驹子与明月联系在了一起,既写出了明月的美丽,又道出了驹子的容颜之美,更让我们读到川端对女性的赞美之情。
寄情于景,以景托情,使人物的感情和自然的美天衣无缝的融合的写作手法乃川端康成的过人之处。
这样的描述在《雪国》中俯拾皆是,如“银河好像从他们的后面倾泻到前面”、“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等,假托出川端的“物哀”之美。
《伊豆的舞女》、《雪国》等所表现出的对自然之美的崇尚、把自然与人的心灵合一的美学追求,始终贯穿川端的整个创作生涯。
2 哀伤与无奈相交的世相观所谓的“世相”即人对所处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态度。
孔夫子认为文学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其中的“观”即为世相之“观”,是文学所应有的反映社会现实,代言民情民意,颂扬美好精神,针砭时弊的一种功能所在。
川端在其文学作品中虽然追求美意识,但也反映出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有的“观”,即哀伤与无奈的世相观。
《雪国》的创作期恰逢日本最黑暗的十年侵略战争时期,而在此期间,川端没有为战争唱一句赞歌,而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古典文学的世界里,《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的研读成了他的“惟一”,这也许就是川端对战争的最佳回应,对时政的反抗、讽刺抑或无奈。
此时的川端内心记挂的对象实际上是战争下的日本民众,但他却无法直白的表露,故此借着“雪国”这一背景,反映和揭示当时的日本人民所经受的苦难。
有人认为驹子和叶子两位女子的遭遇描述是川端自身不幸童年生活之写照,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川端是在借由驹子和叶子委婉地为普通民众代言述求,表现同情与支持,体现自己的某种关照。
但多少有点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对日本民众的处境报以同情,也不时慨叹,却没有化为愤怒,化为批判力量,有的只能是一种交织着忧伤与无奈的一种哀鸣。
同样的创作手法也运用在《古都》、《山音》的写作中。
《古都》中的千重子与苗子是一对姐妹,由于贫寒的家境,原本同根而生的姐妹两人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人生离别之痛。
以至于身为弃儿的千重子常常哀叹:“我是个弃儿呀”。
“弃儿”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令千重子忧伤、无助而又无奈。
川端亦借由千重子与苗子这两个人物,道出了普通民众的悲惨命运,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川端对普通百姓的特有关照也表露无遗。
另一部战后小说《山音》则着重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心理创伤、心理失衡、社会巨变。
有观点说,《山音》晦涩难懂,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凸显主题与完整情节,小说中信吾对菊子畸形爱恋的描写更是受到各种非议,但谁又能否定这不是川端对战后日本混沌现实的最真实描述。
敢于对以信吾为代表的战后老人复杂心理世界进行深层挖掘的,舍川端又取谁?在一如既往地对以菊子为代表的女性悲惨命运表达哀伤与感叹同时,他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美军占领下的战后日本社会时势变迁和社会失衡等现实所表示的担忧,虽然有些许隐晦,却不失其特有的世相关照。
凡此种种的世相观,都不是川端康成的一时而就,而是与他孤寂的童年及其创作手法密切相关。
川端的文学创作侧重于人物心理的诠释,只可惜哀伤的成分过多,重抒情而少言志,导致其世相观中积极向上的成分较少,更多的是哀伤与无奈。
三结语尽管如此,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源氏物语》式“物哀”美无处不在,日本传统美的气息无处不存,进而发展成川端式美学世界。
其成功之处正是出自他对日本传统“物哀”美的忠实传承与发展。
川端的文学作品清淡却不失隽永,委婉中充满含蓄,质朴中追求真实,使读者在受到悲的感染、感动以及震撼的同时,自然感受到日本式传统“物哀”美的魅力所在,从中获取一种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