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根本恶和心灵的转变
- 格式:doc
- 大小:26.74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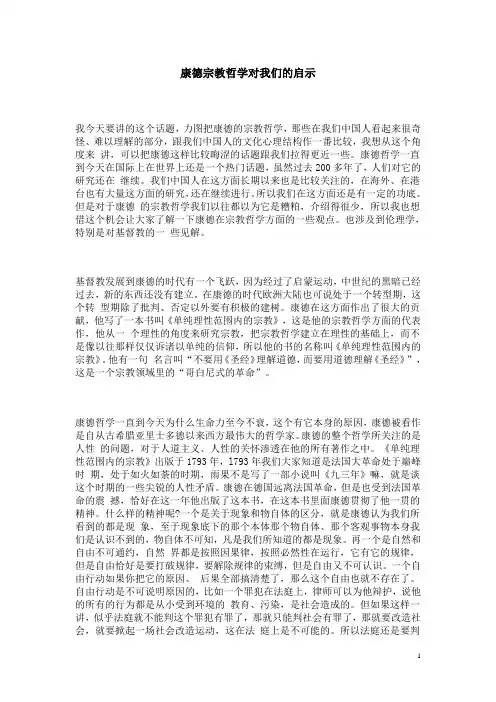
康德宗教哲学对我们的启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力图把康德的宗教哲学,那些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奇怪、难以理解的部分,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一番比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康德这样比较晦涩的话题跟我们拉得更近一些。
康德哲学一直到今天在国际上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过去20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在继续。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也是比较关注的,在海外、在港台也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功底。
但是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我们以往都以为它是糟粕,介绍得很少,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康德在宗教哲学方面的一些观点。
也涉及到伦理学,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一些见解。
基督教发展到康德的时代有一个飞跃,因为经过了启蒙运动,中世纪的黑暗已经过去,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
在康德的时代欧洲大陆也可说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除了批判、否定以外要有积极的建树。
康德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了一本书叫《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是他的宗教哲学方面的代表作,他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研究宗教,把宗教哲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诉诸以单纯的信仰,所以他的书的名称叫《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他有一句名言叫“不要用《圣经》理解道德,而要用道德理解《圣经》”,这是一个宗教领域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哲学一直到今天为什么生命力至今不衰,这个有它本身的原因,康德被看作是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
康德的整个哲学所关注的是人性的问题,对于人道主义、人性的关怀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之中。
《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出版于1793年,l793年我们大家知道是法国大革命处于巅峰时期,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雨果不是写了一部小说叫《九三年》嘛,就是谈这个时期的一些尖锐的人性矛盾。
康德在德国远离法国革命,但是也受到法国革命的震撼,恰好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康德贯彻了他一贯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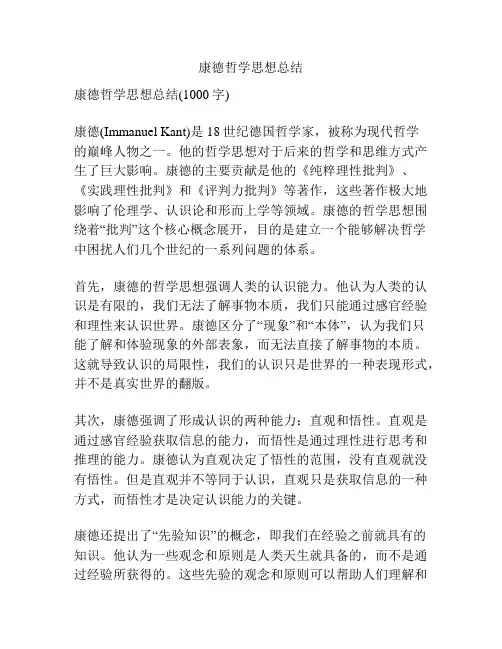
康德哲学思想总结康德哲学思想总结(1000字)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被称为现代哲学的巅峰人物之一。
他的哲学思想对于后来的哲学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康德的主要贡献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评判力批判》等著作,这些著作极大地影响了伦理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领域。
康德的哲学思想围绕着“批判”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解决哲学中困扰人们几个世纪的一系列问题的体系。
首先,康德的哲学思想强调人类的认识能力。
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了解事物本质,我们只能通过感官经验和理性来认识世界。
康德区分了“现象”和“本体”,认为我们只能了解和体验现象的外部表象,而无法直接了解事物的本质。
这就导致认识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只是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真实世界的翻版。
其次,康德强调了形成认识的两种能力:直观和悟性。
直观是通过感官经验获取信息的能力,而悟性是通过理性进行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康德认为直观决定了悟性的范围,没有直观就没有悟性。
但是直观并不等同于认识,直观只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而悟性才是决定认识能力的关键。
康德还提出了“先验知识”的概念,即我们在经验之前就具有的知识。
他认为一些观念和原则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而不是通过经验所获得的。
这些先验的观念和原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认识能力。
康德认为先验知识是人类理性的框架,它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道德行为应该建立在自由意志和目的论上。
康德提出了“普遍法则”的道德原则,即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行为看作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规律,而不是只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强调了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和道德责任。
康德的哲学思想还涉及到宗教和美学等领域。
他对于上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宗教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不是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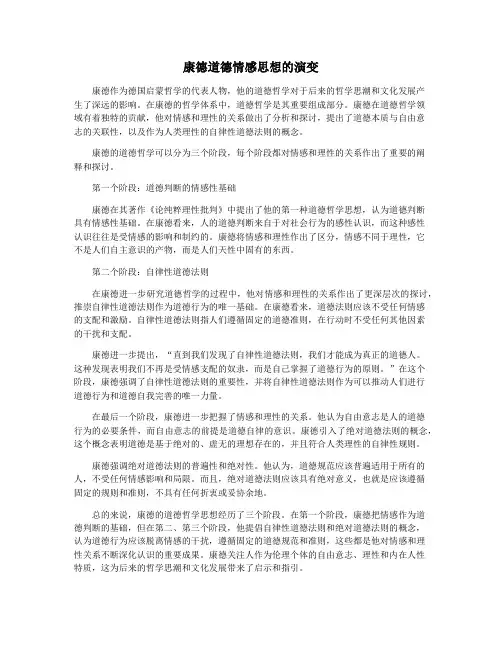
康德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康德作为德国启蒙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哲学对于后来的哲学思潮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哲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康德在道德哲学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他对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道德本质与自由意志的关联性,以及作为人类理性的自律性道德法则的概念。
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阐释和探讨。
第一个阶段:道德判断的情感性基础康德在其著作《论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他的第一种道德哲学思想,认为道德判断具有情感性基础。
在康德看来,人的道德判断来自于对社会行为的感性认识,而这种感性认识往往是受情感的影响和制约的。
康德将情感和理性作出了区分,情感不同于理性,它不是人们自主意识的产物,而是人们天性中固有的东西。
第二个阶段:自律性道德法则在康德进一步研究道德哲学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作出了更深层次的探讨,推崇自律性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行为的唯一基础。
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应该不受任何情感的支配和激励。
自律性道德法则指人们遵循固定的道德准则,在行动时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和支配。
康德进一步提出,“直到我们发现了自律性道德法则,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人。
这种发现表明我们不再是受情感支配的奴隶,而是自己掌握了道德行为的原则。
”在这个阶段,康德强调了自律性道德法则的重要性,并将自律性道德法则作为可以推动人们进行道德行为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唯一力量。
在最后一个阶段,康德进一步把握了情感和理性的关系。
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而自由意志的前提是道德自律的意识。
康德引入了绝对道德法则的概念,这个概念表明道德是基于绝对的、虚无的理想存在的,并且符合人类理性的自律性规则。
康德强调绝对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他认为,道德规范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受任何情感影响和局限。
而且,绝对道德法则应该具有绝对意义,也就是应该遵循固定的规则和准则,不具有任何折衷或妥协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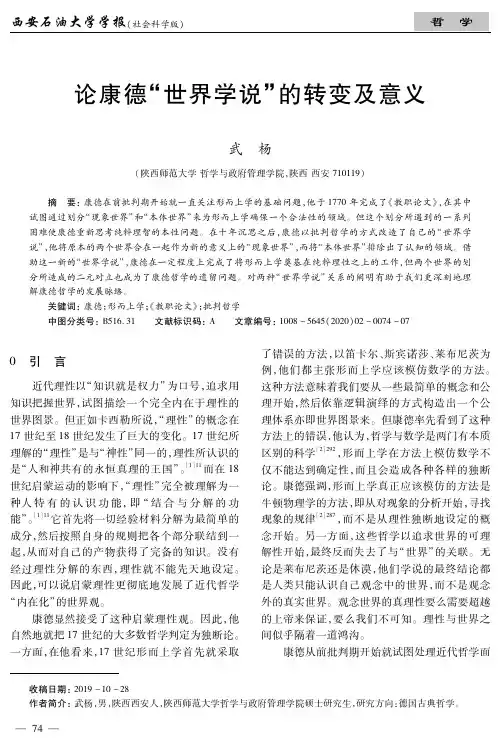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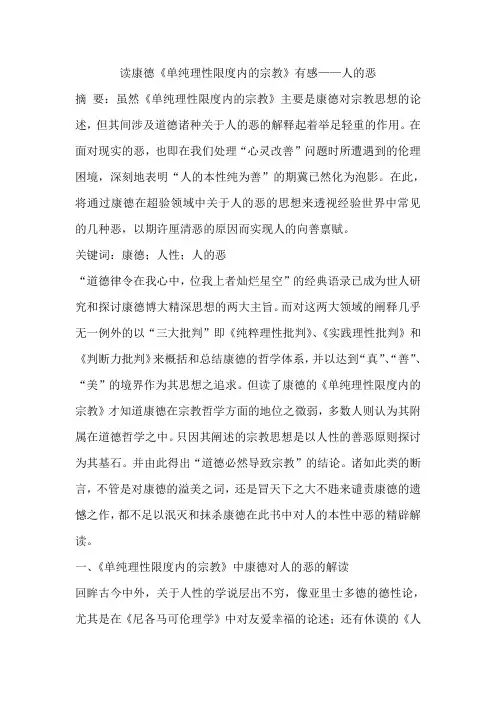
读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有感——人的恶摘要:虽然《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主要是康德对宗教思想的论述,但其间涉及道德诸种关于人的恶的解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面对现实的恶,也即在我们处理“心灵改善”问题时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深刻地表明“人的本性纯为善”的期冀已然化为泡影。
在此,将通过康德在超验领域中关于人的恶的思想来透视经验世界中常见的几种恶,以期许厘清恶的原因而实现人的向善禀赋。
关键词:康德;人性;人的恶“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的经典语录已成为世人研究和探讨康德博大精深思想的两大主旨。
而对这两大领域的阐释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概括和总结康德的哲学体系,并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作为其思想之追求。
但读了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才知道康德在宗教哲学方面的地位之微弱,多数人则认为其附属在道德哲学之中。
只因其阐述的宗教思想是以人性的善恶原则探讨为其基石。
并由此得出“道德必然导致宗教”的结论。
诸如此类的断言,不管是对康德的溢美之词,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谴责康德的遗憾之作,都不足以泯灭和抹杀康德在此书中对人的本性中恶的精辟解读。
一、《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对人的恶的解读回眸古今中外,关于人性的学说层出不穷,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尤其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友爱幸福的论述;还有休谟的《人性论》,康德对休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对其思想的精华还是起到了传承的作用。
所以诸多关于人性的思想是迥然各异,但是大家之谈不外乎两种根本之说即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
可是,康德却另辟蹊径,不仅详细的分析了人的本性内涵,并且他既没有主张人性本善,也没有坚持人性本恶,而是把人的本性分析为具体的向善的原初禀赋和趋恶的自然倾向。
在恶的探讨上(《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起初就是以考察人的本性为始),他指出有两种起源,即时间上的起源和理性上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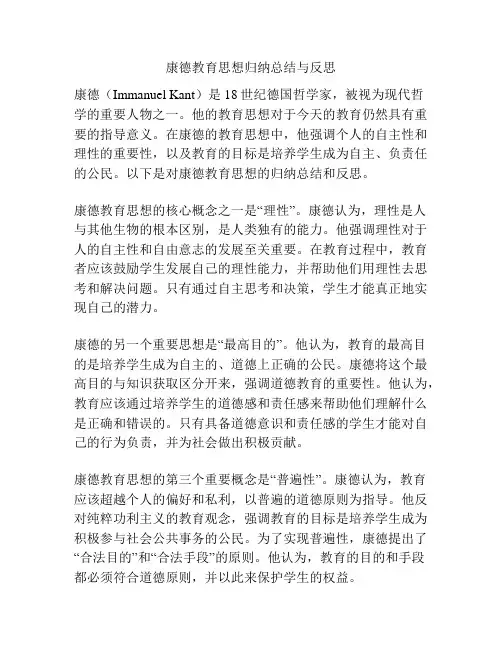
康德教育思想归纳总结与反思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被视为现代哲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康德的教育思想中,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理性的重要性,以及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自主、负责任的公民。
以下是对康德教育思想的归纳总结和反思。
康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
康德认为,理性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他强调理性对于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并帮助他们用理性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只有通过自主思考和决策,学生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潜力。
康德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最高目的”。
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自主的、道德上正确的公民。
康德将这个最高目的与知识获取区分开来,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教育应该通过培养学生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来帮助他们理解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
只有具备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的学生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康德教育思想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普遍性”。
康德认为,教育应该超越个人的偏好和私利,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为指导。
他反对纯粹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
为了实现普遍性,康德提出了“合法目的”和“合法手段”的原则。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和手段都必须符合道德原则,并以此来保护学生的权益。
康德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他的强调个人自主和理性能力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决策能力,而不是简单灌输知识。
其次,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提醒我们,培养学生成为道德正确的公民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教育者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发展,指导他们正确判断和处理问题。
最后,康德的普遍性原则提醒我们,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社会的福祉。
我们应该教育学生成为具有广泛的视野和责任感的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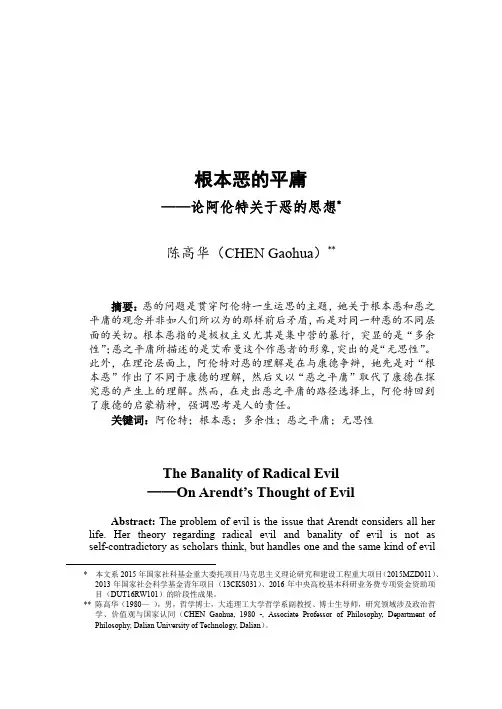
根本恶的平庸——论阿伦特关于恶的思想*陈高华(CHEN Gaohua)**摘要:恶的问题是贯穿阿伦特一生运思的主题,她关于根本恶和恶之平庸的观念并非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前后矛盾,而是对同一种恶的不同层面的关切。
根本恶指的是极权主义尤其是集中营的暴行,突显的是“多余性”;恶之平庸所描述的是艾希曼这个作恶者的形象,突出的是“无思性”。
此外,在理论层面上,阿伦特对恶的理解是在与康德争辩,她先是对“根本恶”作出了不同于康德的理解,然后又以“恶之平庸”取代了康德在探究恶的产生上的理解。
然而,在走出恶之平庸的路径选择上,阿伦特回到了康德的启蒙精神,强调思考是人的责任。
关键词:阿伦特;根本恶;多余性;恶之平庸;无思性The Banality of Radical Evil——On Arendt’s Thought of EvilAbstract: The problem of evil is the issue that Arendt considers all her life. Her theory regarding radical evil and banality of evil is not as self-contradictory as scholars think, but handles one and the same kind of evil*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15MZD011)、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KS031)、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UT16RW101)的阶段性成果。
** 陈高华(1980—),男,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哲学、价值观与国家认同(CHEN Gaohua, 1980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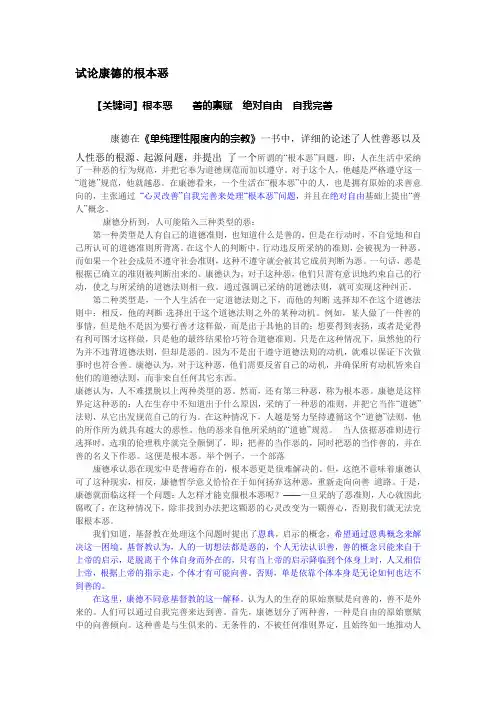
试论康德的根本恶【关键词】根本恶善的禀赋绝对自由自我完善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详细的论述了人性善恶以及人性恶的根源、起源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根本恶”问题,即:人在生活中采纳了一种恶的行为规范,并把它奉为道德规范而加以遵守。
对于这个人,他越是严格遵守这一“道德”规范,他就越恶。
在康德看来,一个生活在“根本恶”中的人,也是拥有原始的求善意向的,主张通过“心灵改善”自我完善来处理“根本恶”问题,并且在绝对自由基础上提出“善人”概念。
康德分析到,人可能陷入三种类型的恶:第一种类型是人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也知道什么是善的,但是在行动时,不自觉地和自己所认可的道德准则所背离。
在这个人的判断中,行动违反所采纳的准则,会被视为一种恶。
而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不遵守社会准则,这种不遵守就会被其它成员判断为恶。
一句话,恶是根据已确立的准则被判断出来的。
康德认为,对于这种恶,他们只需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动,使之与所采纳的道德法则相一致。
通过强调已采纳的道德法则,就可实现这种纠正。
第二种类型是,一个人生活在一定道德法则之下,而他的判断-选择却不在这个道德法则中;相反,他的判断-选择出于这个道德法则之外的某种动机。
例如,某人做了一件善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因为要行善才这样做,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想要得到表扬,或者是觉得有利可图才这样做,只是他的最终结果恰巧符合道德准则。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行为并不违背道德法则,但却是恶的。
因为不是出于遵守道德法则的动机,就难以保证下次做事时也符合善。
康德认为,对于这种恶,他们需要反省自己的动机,并确保所有动机皆来自他们的道德法则,而非来自任何其它东西。
康德认为,人不难摆脱以上两种类型的恶。
然而,还有第三种恶,称为根本恶。
康德是这样界定这种恶的:人在生存中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采纳了一种恶的准则,并把它当作“道德”法则,从它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是努力坚持遵循这个“道德”法则,他的所作所为就具有越大的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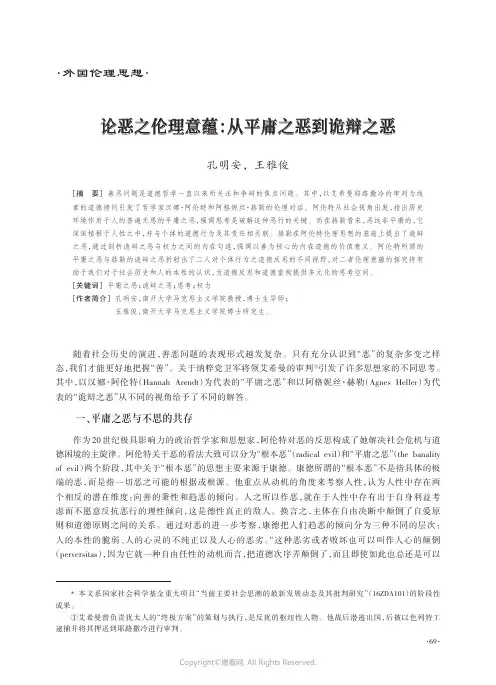
·外国伦理思想·论恶之伦理意蕴::从平庸之恶到诡辩之恶论恶之伦理意蕴孔明安,王雅俊[摘要]善恶问题是道德哲学一直以来所关注和争辩的焦点问题。
其中,以艾希曼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线索的道德拷问引发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阿格妮丝·赫勒的伦理对话。
阿伦特从社会视角出发,指出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普遍无思的平庸之恶,强调思考是破解这种恶行的关键。
而在赫勒看来,恶远非平庸的,它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并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相关联。
赫勒在阿伦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诡辩之恶,通过剖析诡辩之恶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勾连,强调以善为核心的内在道德的价值意义。
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与赫勒的诡辩之恶折射出了二人对个体行为之道德反思的不同视野,对二者伦理意蕴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的本性的认识,为道德反思和道德重构提供多元化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平庸之恶;诡辩之恶;思考;权力[作者简介]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雅俊,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善恶问题的表现形式越发复杂。
只有充分认识到“恶”的复杂多变之样态,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善”。
关于纳粹党卫军将领艾希曼的审判①引发了许多思想家的不同思考。
其中,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平庸之恶”和以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为代表的“诡辩之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一、平庸之恶与不思的共存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阿伦特对恶的反思构成了她解决社会危机与道德困境的主旋律。
阿伦特关于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和“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两个阶段,其中关于“根本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
康德所谓的“根本恶”不是指具体的极端的恶,而是指一切恶之可能的根据或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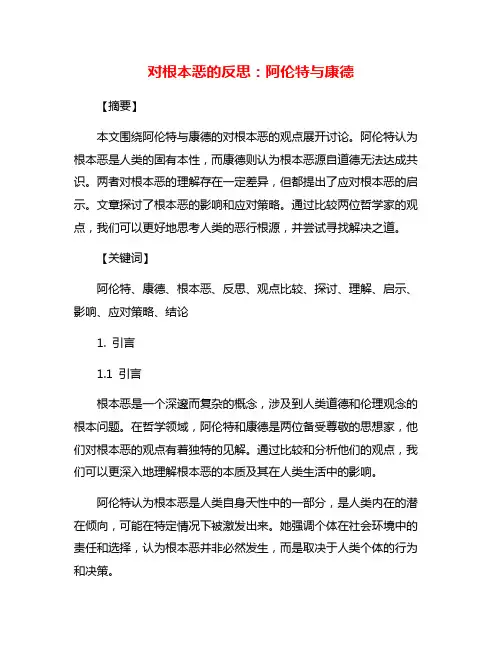
对根本恶的反思:阿伦特与康德【摘要】本文围绕阿伦特与康德的对根本恶的观点展开讨论。
阿伦特认为根本恶是人类的固有本性,而康德则认为根本恶源自道德无法达成共识。
两者对根本恶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提出了应对根本恶的启示。
文章探讨了根本恶的影响和应对策略。
通过比较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人类的恶行根源,并尝试寻找解决之道。
【关键词】阿伦特、康德、根本恶、反思、观点比较、探讨、理解、启示、影响、应对策略、结论1. 引言1.1 引言根本恶是一个深邃而复杂的概念,涉及到人类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根本问题。
在哲学领域,阿伦特和康德是两位备受尊敬的思想家,他们对根本恶的观点有着独特的见解。
通过比较和分析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根本恶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
阿伦特认为根本恶是人类自身天性中的一部分,是人类内在的潜在倾向,可能在特定情况下被激发出来。
她强调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责任和选择,认为根本恶并非必然发生,而是取决于人类个体的行为和决策。
相比之下,康德则认为根本恶是人类有限理性和自私心理的产物,源于人类自身无法完全控制的欲望和冲动。
他提出道德法则作为对抗根本恶的方法,主张个体应该以理性为准则,超越自我的私欲和欲望。
通过对阿伦特和康德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根本恶在人类道德观念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应对根本恶的不同方式和策略。
这种启示能够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本质,以及如何在面对根本恶时保持理性和责任感。
2. 正文2.1 阿伦特与康德对根本恶的观点比较阿伦特与康德都对根本恶进行了探讨,尽管两者的角度和方法略有不同。
阿伦特认为根本恶是人类内在的、无法控制的冲动和欲望,源自人类的贪婪和渴望权力的本性。
她认为根本恶是一种集体行为,可能导致暴力和压迫,是集体主义和权力滥用的结果。
康德则将根本恶视为人类的道德倾向,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本性,会导致人们违背道德法则和原则。
在对根本恶的理解上,阿伦特更注重集体层面,认为根本恶可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产生严重后果,导致暴力和独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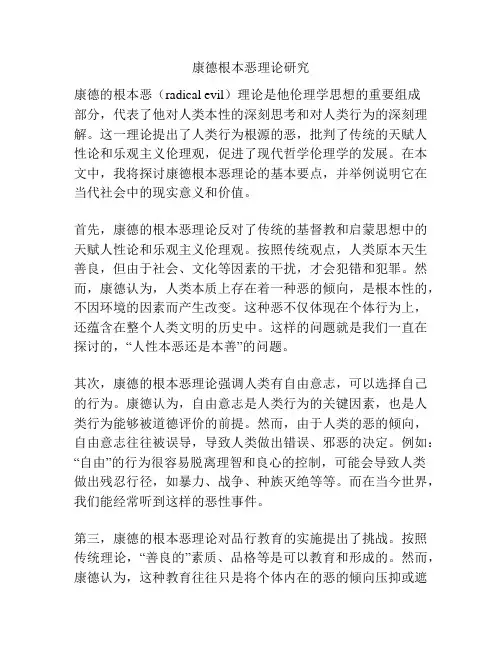
康德根本恶理论研究康德的根本恶(radical evil)理论是他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他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行为的深刻理解。
这一理论提出了人类行为根源的恶,批判了传统的天赋人性论和乐观主义伦理观,促进了现代哲学伦理学的发展。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康德根本恶理论的基本要点,并举例说明它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首先,康德的根本恶理论反对了传统的基督教和启蒙思想中的天赋人性论和乐观主义伦理观。
按照传统观点,人类原本天生善良,但由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干扰,才会犯错和犯罪。
然而,康德认为,人类本质上存在着一种恶的倾向,是根本性的,不因环境的因素而产生改变。
这种恶不仅体现在个体行为上,还蕴含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
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问题。
其次,康德的根本恶理论强调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
康德认为,自由意志是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也是人类行为能够被道德评价的前提。
然而,由于人类的恶的倾向,自由意志往往被误导,导致人类做出错误、邪恶的决定。
例如:“自由”的行为很容易脱离理智和良心的控制,可能会导致人类做出残忍行径,如暴力、战争、种族灭绝等等。
而在当今世界,我们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恶性事件。
第三,康德的根本恶理论对品行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挑战。
按照传统理论,“善良的”素质、品格等是可以教育和形成的。
然而,康德认为,这种教育往往只是将个体内在的恶的倾向压抑或遮盖,而并非真正地改造和转化。
因此,对于品行教育,我们必须注意不仅要灌输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还要从内心出发进行培养。
例如,全世界的学校都是推崇“德育教育”,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仅仅讲道理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去真正的改变教育的方式,去切实的培养青少年的心性。
第四,康德的根本恶理论批判了强权主义政治。
按照强权主义的理论,“政治权力就是实现人类永恒幸福的最佳方式”。
然而,从康德的根本恶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恶的倾向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压迫和剥削其他人,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康德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哲学史上许多领域的发展。
其中,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情感思想是他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部分。
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道德哲学和情感思想的演变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
本文将从康德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介绍康德对于情感的看法以及其演变过程。
一、康德道德哲学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是其“绝对道德规律、人的自由意志和最高善”的概念。
康德认为,道德规律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意志是唯一的,并且最高善是自由选择和遵守道德规律。
康德在《纯粹理性哲学》上提倡“行为的动机才是行为的真正价值所在”,即区分行为的良心和后果,而把道德行为的良心看作是行为的最高价值。
他认为,人应该通过自己的道德意志去寻求真理和伦理标准,而不是被传统习俗或权威所影响。
除此之外,康德还提出了“人民最高目的”(即幸福安康)的概念,认为人民最高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道德原则的实施,而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
由此可见,康德的绝对道德规律、人的自由意志和最高善的思想构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康德关于情感的看法最初是比较消极的。
在《纯粹理性哲学》中,他认为情感与理性是背离的,他认为情感只会阻碍人们理性的思考,使人迷失在感性世界中,最终导致道德行为的堕落。
但是,随着他思想的深化,他对情感的看法也有了变化。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道德美”的概念,认为真正的美是在人通过自己内部的自我制约和道德原则的指引下实现的。
他认为这种“道德美”是一种优秀的情感,可以激励或指导人们实施道德行动。
此外,他还提出了“道德情感”和“感知情感”的概念,认为这两种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道德激励的作用。
到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进一步强调了情感的重要性。
他认为,没有情感的支持和促进,人们无法形成道德情操,也无法做出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
他将道德感情分为团体感情、家庭感情和个人感情三个层次,认为情感的表达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康德哲学精髓三大批判我是吟风者,欢迎您关注我。
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著作简介是需要些勇气的,因为觉得太累脑子,还怕写不好表达不了人家的思想,就算是写好了这么无聊的东西也不一定有人会看。
所以挣扎良久,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因为要写的不是别人,是康德啊!在说三大批判之前要先简要讲一下康德的认识论,康德说人们在认识事物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事物的一个先天范畴,如果没有对事物的先天范畴人是不可能认识事物的。
这也算是解释我们所有人的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范畴,我们就都是瞎想乱想了。
康德的三大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大作。
分别论述了他的认知论、伦理学和美学的见解。
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标志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
在康德之前,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对实体或者是本体的研究,诸如斯宾诺莎等哲学大家。
但在康德之后,哲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人们开始研究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
知识的来源问题,是来自经验?还是先天具有知识,我们能否得到正确的知识。
认识正确的知识何以可能,在认识知识之前要先对认识本身加以批判等,这些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大约内容。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就是解释我们能知道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大体结构相同,但在划分的细节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常。
这是由于两个批判的任务、对象和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所决定的。
在这个第二批判中,康德主要讨论人的实践伦理的问题。
比如,自由的问题,康德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可为,而不为的自由。
这种“自由”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标志。
举个例子,下雨了我应该躲雨,但人有“自由”,我可以自由的选择冒雨去扶起在雨中摔倒的小女孩。
康德的认为这种才是,人的“自由”,而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与《目的的判断力批判》两部分,它是前两个批判的桥梁,在这个两个批判之间建构一个反思批判。
上帝、自由与根本恶——康德宗教哲学的致思之路康德是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他的著作涉及道德哲学、认识论、宗教哲学等多方面。
其中,康德发表的对于上帝、自由以及根本恶问题的探讨,引发了许多哲学家的争议和思考。
康德认为,上帝、自由以及根本恶是哲学家角度下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对个体行为具有指导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上帝、自由以及根本恶的概念,并举出5个例子说明康德所说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我们来探讨康德对上帝的理解。
康德在他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上帝视为纯粹理性的概念。
在康德看来,上帝是一个超越我们世界的存在,是我们理性的最高原则和目标。
他认为,我们无法直接认知上帝的存在,但我们可以从观察自然的规律性和秩序性,推断上帝的存在。
他认为,上帝是统一并掌管着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我们道德行为的指导原则。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康德对上帝的理解。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期,许多人感到惶恐和不安,总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毒肆虐,上帝为什么不保护我们?在康德的观点下,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上帝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类尊重自然规律,并努力寻求治愈病毒的方法,从中寻找上帝的指引和安慰。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康德对自由的思考。
康德强调个体行为的信念和自由。
他认为,自由是价值最高的东西,可以对我们的道德行为产生指导作用。
在康德看来,一个道德行为的行动,必须是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并根据道德法则行事。
同时,个体自由也付责任于个体行为的后果,并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制约。
我们来给出一个例子,以证明康德对道德自由的概念。
当一名服务员忘记了把他自己的钱包带到餐厅时,在他得到一名客人吃剩下的食物时,他可以选择偷窃客人的钱包,或者借钱买食物。
康德认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选择道德的行为,例如诚实、努力工作,或者从其他人的帮助中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
这种情形下,服务员应该接受自己失误的后果,并努力恢复自己的错误。
康德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他的道德情感思想对当代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道德理论,以此来解决伦理学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道德行为的基础、义务的来源以及道德判断的准则。
康德的道德情感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下面将对其主要演变过程进行介绍。
康德在其最早期的著作中,强调了道德行为的理智性基础。
按照康德的理论,道德行为应该是基于理性的原则和准则,而不是基于感情和欲望。
他认为,人的行为应该基于他们的意志和决定,而不是凭借感觉和情感的冲动。
康德将道德行为与动物的本能行为区分开来,强调道德行为必须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基础上。
康德很快意识到,纯粹的理性并不能完全解决道德问题。
他认识到人类具有情感和欲望,这些情感和欲望可能对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康德在其后期著作中扩展了他的道德情感思想。
他认为,道德行为应该不仅基于理性的原则,还应该考虑到人类的情感和欲望。
康德主张,在道德行为中,人们应该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意志和感受。
他认为,道德行为应该是一种基于理性原则的自由选择,但也应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康德认为,人们的情感和欲望并不一定是道德行为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们可以与道德行为相容。
康德将这种基于理性和情感的道德行为称为“道德情感”。
康德的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还包括对道德判断准则的重新思考。
最初,康德认为道德判断应该是博弈论思想中的“无差别契约”。
换句话说,人们应该根据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普遍利益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仅仅基于自己的利益。
这种无差别契约的思想强调了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康德后来改变了对道德判断准则的看法。
他认为道德判断应该基于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基于普遍的契约。
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理性能力,能够在道德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内在的道德准则来做出道德判断。
康德的道德情感思想的演变体现了他对道德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反思。
《康德三大批判》读后感《康德三大批判》宛如一座巍峨的哲学丰碑,在思想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引导我们对人类的认识、道德和审美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索。
他试图为人类知识划定界限,区分现象与自在之物。
他指出,我们的认识开始于经验,但并非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因为我们的知性中有先天的认识形式。
时间和空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使得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成为可能。
而范畴则是知性的先天形式,它们对感性杂多进行综合统一,从而形成知识。
例如,因果范畴让我们能够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当我们试图超越经验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这使我们明白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它在认识领域有其边界,不能盲目地追求对超验对象的认识,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局限性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实践理性批判》则将我们带入了道德的王国。
康德认为,道德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是先天的、普遍的。
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要求我们的行为准则要能够成为普遍的立法原则。
这种道德观强调了道德的自主性和无条件性,与基于经验或功利的道德理论划清了界限。
比如,诚实是一种道德要求,并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义务。
康德的道德哲学让我们重新审视道德的本质,将道德从外在的功利考量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人的内在理性和自由意志,促使我们在行为选择时遵循道德的绝对命令,追求道德上的完善。
《判断力批判》像是一座桥梁,连接了认识与道德的鸿沟。
判断力在康德这里有其独特的地位,特别是审美判断力。
审美判断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当我们在欣赏一朵花时,它没有具体的实用目的,但却给我们一种合目的性的美感。
这种美感是主观的,但又具有普遍可传达性。
康德还探讨了崇高感,崇高与美不同,它往往伴随着一种对无限的敬畏和超越感性的精神体验。
通过审美判断力,康德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沟通自然与自由、认识与道德搭建了一座美学的桥梁,丰富了我们对人性和世界的理解。
康德论人性中的“根本恶”作者:王晓艳来源:《文教资料》2019年第26期摘; ; 要:善恶是道德哲学的首要关切。
在此问题上,康德认为善与恶不能从行为的后果判断,应从行为者的意念和动机出发,根据“准则”断定善恶。
善与恶是人性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可能性,自由的任性既受感性自爱影响,又受道德法则影响,行为的恶劣在于道德法则与感性自爱两种动机的次序颠倒;人类作为理性主体拥有绝对自发的“根本自由”,根本恶实质正是人类自由的体现。
关键词:根本恶; ; 任性; ; 意志; ; 根本自由自基督教时代已降,西方人关于恶的理论总是与自由意志纠缠一处。
因为在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创世前提之下,恶的问题难以解释,于是宗教思想家们普遍的办法是从存在论层面将恶解释为善的缺失,取消恶作为实体的存在位置。
但这种解释与恶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事实相矛盾,为了解释何以在现实生活中会有各种恶行存在,自由意志被引入作为恶行出现的原因。
康德在探讨恶的问题时虽然想要以理性为宗教奠基,但其实还是处在这个思想方向上。
一、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第一版序言中,康德开章明义地表明了自己探讨的乃是道德问题。
在行文中他多次提及该书是“为了说明人身上的道德上的恶的根据”[1](35),而且一再表明“恶本来只能产生自道德上的恶”[1](43)。
康德的思路可以称为“道德恶”的思考进路:将恶联系与人作为理性主体的绝对自由,从个体道德层面考察恶的现象。
它仍然与奥古斯丁开创的“内在意志决定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奥古斯丁开始将恶思考为恶行,将恶行的发生联系于个体的自由意志,才为判断个体道德之善恶提供了可能性。
不同之处在于康德对“自由意志”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将其一分为二:一方是颁布法则的意志,另一方是进行选择的任性,二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自由意志。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康德曾写道:“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理性。
”[2](419)是仅仅选择理性认作实践上必然的亦即善的东西的能力。
康德论根本恶和心灵的转变原文作者:蔡秦摘要:康德的根本恶学说中存在着两个张力,即恶是归因于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生而具有的趋恶倾向之间的张力,以及在心灵的转变中人自身的努力和神圣的帮助之间的张力。
为了消解这种张力,道德上的恶可以被理解为是行动者在自由的观念下选择的结果,趋恶的倾向只是使得恶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人类仍旧必须对自身的恶负责。
也正是因为道德上的恶必须归咎于人类自身,心灵的转变首先在于人类自身的努力。
但同时康德对根本恶的经验解释是有限度的,去恶从善的过程是以恩典为理论预设的。
关键词:根本恶;准则;品性;禀赋;倾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XX)11-0134-07 康德的道德哲学通常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立足于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尊重,试图“仔细地排除掉一切经验的东西”,探索“纯粹理性在实践领域内能做多少事情,以及它借助于什么资源去教导”①。
在这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框架下,似乎并没有为对任何超自然的权威和神秘力量的宗教诉求留下多少空间,因为“人类必须使他自己成为道德意义上所是的样子或者应该成为的样子,无论是善还是恶”②。
但是,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康德的晚期著作,尤其是《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的“根本恶”学说时,这一图景变得复杂而令人不解起来。
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上:首先康德认为人类对恶负有完全的责任,但同时人性当中又有一种趋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不可能仅通过人类的力量而被消除的,那么这之间的张力就在于如果恶是在我们的本性当中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道德上的恶能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并能合理地归因于我们自身?其次,康德认为对根本恶的消除是一种道德上的更新和重生,其关键在于“心灵的转变”,而在谈及这种转变何以可能的时候,他明确地提到了神圣的帮助以及“超自然的合作”,那么这种对于恩典的诉求又如何可能同他对自主性的强调协调一致?本文的任务就在于通过梳理和澄清相关概念,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准则与道德上的恶[论文]对于康德来说,道德上的恶存在于准则之中[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6:21.]。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把准则定义为“行动的主观原则……它是由理性根据主体的条件(通常是它的无知或爱好)所决定的并由此是主体行动所依据的原则”[注:Lewis White Beck, trans., 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9,,,]。
换句话说,准则是行动者事实上所遵循的实践原则或者说事实上所采用的行动理由,它表达了在某种经验情境下行动者想要实现的目的和相应的行动方式。
这个概念是康德解释“理性如何可以是实践的”一个关键部分。
当康德谈论“行动”以及“行动的准则”时,他总是指向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言的。
他们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按照法则而起作用。
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拥有按照法则的观念而行动的能力——即,按照原则而行动——仅仅因此他拥有一个意志。
”③这里意志被康德解释为实践理性,这是一种属于理性存在者的因果性,确切的说,一种形成实践原则的能力,以及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去行动,并在现象世界中引发变化的力量。
同时,对于康德来说,这也意味着人类是在“自由的观念”下行动④,即理性行动者既不是机械地服从外在的权威也不是自动地对最强烈的欲望做出反应,这些因素作为动机而存在,而“一种动机无法决定意志去行动,除非人类已经将这种动机结合到他的准则中去(已经使它成为一条适用于他自己的普遍规则,据此他意愿这样来行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动机,无论它是什么动机,才能与意志(即自由)绝对的自发性共存”[注:Allen Wood,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6:23,6:29,6:36,6:36.]。
也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为任何一种动机所必然化的存在者,他们能够在动机中间进行权衡和评价,然后决定它们之间的秩序,这种决定是可以归因于行动者本身的。
而准则就是对这种决定的表达。
进而,康德说“我们只能基于其准则才能判断意志是善的还是恶的”⑥,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判断、善恶的归属都必须是针对准则而做出的。
康德在《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进一步澄清了准则的善恶究竟应该依据什么进行判断的问题:一个善人和恶人之间的区别决不在于他们结合进入准则中的动机(即准则的质料)之间的差别;而在于动机之间的从属关系(即准则的形式)上的差别:即他们究竟以两种动机中的哪一个为另一个的条件。
⑦这里首先涉及到准则的质料和形式之间的区分。
质料即准则中所包含的经验要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某种情境,某种具体的行为过程以及某种实质性的目标,而目标也往往是作为驱使一个行为的动机而出现的。
这里康德尤其关注的是动机这样一个要素,他区分了两种动机:对道德律的尊重和对幸福的渴望,这又被分别称之为道德的动机和感性的动机,由于在康德看来人类既是有理性的同时又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人类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道德律和自爱的法则的影响,所以任何准则都必然包含着这两种动机⑧,而一个准则的道德价值就不可能在于究竟是道德律还是感性欲望充当着行为动机的问题,换言之,判断准则的善恶不可能基于准则的质料。
既然如此,道德上的恶就只能在于准则的形式。
康德用“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即关键在于行动者究竟是以哪种动机作为主导,或者说决定以哪种动机为另一种的先决条件。
在康德看来这两种动机在道德上恰当的秩序应该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占据着支配地位,自爱的动机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自然欲望只能是以此为前提的。
而道德上的恶就在于颠倒了这种秩序,使得自爱的动机成为遵守道德律的前提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康德来说感性的动机本身并不是恶的,他甚至说“就自然倾向本身来说,它们是善的,即,它们并不是应受指责的东西,要想灭绝它们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也是有害且值得责备的”[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58.]。
也就是说,感性的动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拥有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它在我们形成准则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如当我们出于道德的动机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同情心作为一种自然的情感也会发生作用),而善恶的分野就在于这种作用究竟是压倒性的还是以尊重道德律为条件的[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主要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道德律的要求和同情的自然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行动者很有可能会违背道德律的要求,例如,一个人主要出于同情的动机帮助一个无辜的乞丐,那他也完全有可能去帮助一个毒瘾发作的人去买毒品,从而他做道德上善的事情是没有保障的。
对于康德动机理论的详细探讨,参见Barbara Herman,“On the Value of Acting from the Motive of Duty,”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换句话说,恶并不在于我们选择了本身就是恶的东西,而在于当本身都是善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颠倒了它们之间本应具有的从属秩序。
二、品性与根本恶由于恶产生于我们决定这种从属秩序的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过程,所以恶与自由紧密在一起。
但是这又接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恶在于准则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又不是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给予而是由我们自己所决定的,那么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来决定一个准则的形式呢?对此,康德回答说准则的形式是由“一个根本的共同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个准则)”自由地决定的[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0,6:25,6:37,6:30,6:21,6:25.]。
而这样一种根本的共同基础被康德称之为“品性(disposition)” ,品性是“运用准则的最终的主观基础”,它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统一而连贯的基础,它普遍地决定着具体的准则的产生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品性的败坏被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这种恶是根本的,因为它腐蚀了所有准则的基础”⑤,“由此心灵的面貌(就道德品性而言)从根基上被腐蚀了”⑥。
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是理解根本恶的关键[注:对这个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探讨,参见Daniel O’Connor,“Good and Evil Disposition”, inKant-Studien,76:3 (1985), 288-302。
]。
一般而论的道德上的恶体现在具体的准则中伦理秩序的颠倒,这样一种颠倒本身并不使我们把有些恶视为是更根本的,当我们引入品性这个概念后发现所有的准则都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也就是品性)中获得其源泉,当这样一个根基腐败的时候,道德上的恶才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弥漫遍布了行动者的心灵。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连贯而一致地将道德动机置于感性动机的支配之下,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他的行动的道德价值。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人不可能做出任何在法律意义上善的事情,他们并不一定把所有根据道德律判断为善的东西都当作是恶,他们甚至也会做出符合道德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