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嬗变
- 格式:doc
- 大小:25.0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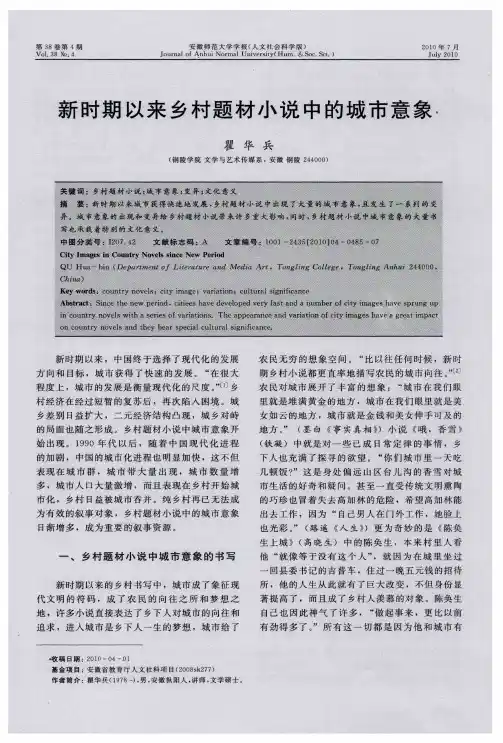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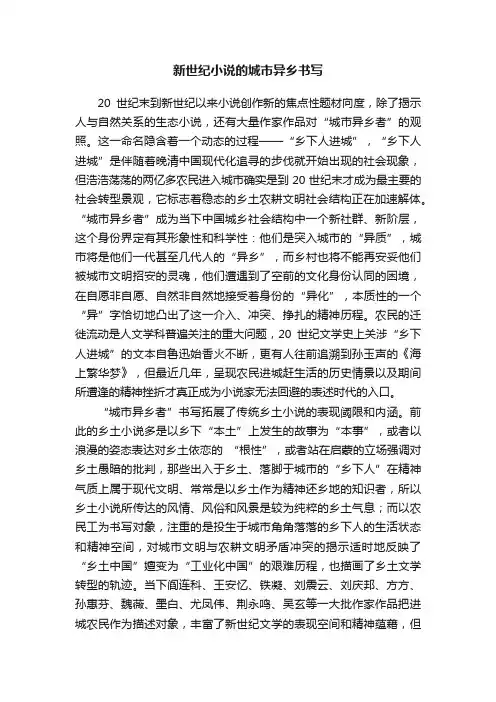
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20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新的焦点性题材向度,除了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小说,还有大量作家作品对“城市异乡者”的观照。
这一命名隐含着一个动态的过程——“乡下人进城”,“乡下人进城”是伴随着晚清中国现代化追寻的步伐就开始出现的社会现象,但浩浩荡荡的两亿多农民进入城市确实是到20世纪末才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景观,它标志着稳态的乡土农耕文明社会结构正在加速解体。
“城市异乡者”成为当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中一个新社群、新阶层,这个身份界定有其形象性和科学性:他们是突入城市的“异质”,城市将是他们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异乡”,而乡村也将不能再安妥他们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他们遭遇到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自愿非自愿、自然非自然地接受着身份的“异化”,本质性的一个“异”字恰切地凸出了这一介入、冲突、挣扎的精神历程。
农民的迁徙流动是人文学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20世纪文学史上关涉“乡下人进城”的文本自鲁迅始香火不断,更有人往前追溯到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但最近几年,呈现农民进城赶生活的历史情景以及期间所遭逢的精神挫折才真正成为小说家无法回避的表述时代的入口。
“城市异乡者”书写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
前此的乡土小说多是以乡下“本土”上发生的故事为“本事”,或者以浪漫的姿态表达对乡土依恋的“根性”,或者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暗的批判,那些出入于乡土、落脚于城市的“乡下人”在精神气质上属于现代文明、常常是以乡土作为精神还乡地的知识者,所以乡土小说所传达的风情、风俗和风景是较为纯粹的乡土气息;而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注重的是投生于城市角角落落的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对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适时地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工业化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
当下阎连科、王安忆、铁凝、刘震云、刘庆邦、方方、孙惠芬、魏薇、墨白、尤凤伟、荆永鸣、吴玄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把进城农民作为描述对象,丰富了新世纪文学的表现空间和精神蕴藉,但总体上,此类创作还需要更为坚实的现代理念和审美情感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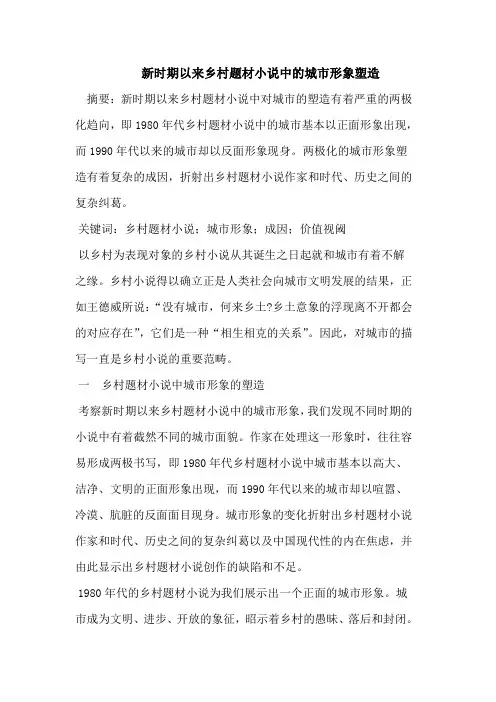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塑造摘要: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对城市的塑造有着严重的两极化趋向,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基本以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反面形象现身。
两极化的城市形象塑造有着复杂的成因,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乡村题材小说;城市形象;成因;价值视阈以乡村为表现对象的乡村小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乡村小说得以确立正是人类社会向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它们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
因此,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乡村小说的重要范畴。
一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形象的塑造考察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
作家在处理这一形象时,往往容易形成两极书写,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基本以高大、洁净、文明的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喧嚣、冷漠、肮脏的反面面目现身。
城市形象的变化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焦虑,并由此显示出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缺陷和不足。
1980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正面的城市形象。
城市成为文明、进步、开放的象征,昭示着乡村的愚昧、落后和封闭。
《陈奂生上城》(高晓生)通过陈奂生上城的“奇遇”对新时期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进行批判,揭示出“当代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阴影下走出,新时期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
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是通过进入城市彰显出来的,城市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进步意义。
虽然陈奂生在城市遭遇到一系列尴尬,但这丝毫没有损毁城市的高大形象,最后陈奂生病倒街头,还得到县委书记的救助,这是城市善的体现。
《哦,香雪》(铁凝)中的城市形象是通过对列车员“北京话”的描写体现出来的。
“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列车员是乡村姑娘对城市的认识,是城市所显现出来的面孔,“北京话”无疑是城市的化身,代表着城市对乡村的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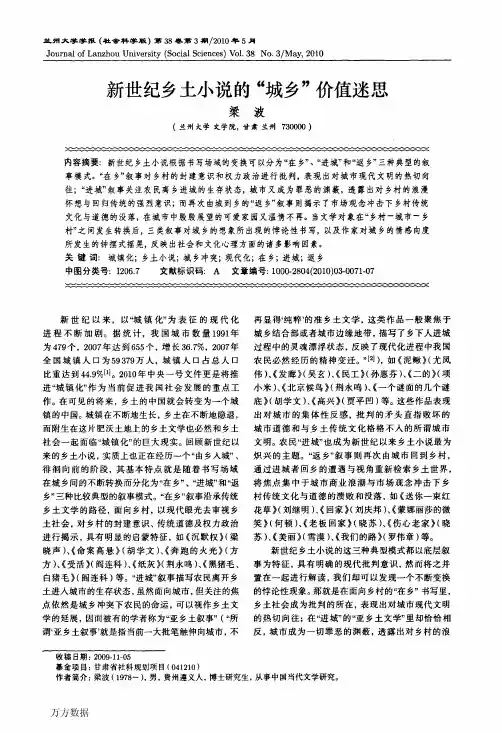
-“-.qtl大学学报(社会科掌版)第38卷第3-期/2010年5月Jour 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01.38 N o.3/M ay,2010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梁波(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内容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根据书写场域的变换可以分为“在乡”、“进城”和“返乡”三种典型的叙事模式。
“在乡”叙事对乡村的封建意识和权力政治进行批判,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进城”叙事关注农民离乡进城的生存状态,城市又成为罪恶的渊薮,透露出对乡村的浪漫怀想与回归传统的强烈意识;而再次由城到乡的“返乡”叙事则揭示了市场观念冲击下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没落,在城市中殷殷展望的可爱家园又温情不再。
当文学对象在“乡村一城市一乡村”之间发生转换后,三类叙事对城乡的想象所出现的悖论性书写,以及作家对城乡的情感向度所发生的钟摆式摇晃,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乡土小说;城乡冲突;现代化;在乡;进城;返乡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10)03-0071.07新世纪以来,以“城镇化”为表征的现代化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进程不断加剧。
据统计,我国城市数量1991年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为479个,2007年达到655个,增长36.7r%,2007年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全国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
”【2】),如《泥鳅》(尤凤比重达到44.9%Il】。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推伟)、《发廊》(吴玄)、《民工》(孙惠芬)、《二的》(项进“城镇化”作为当前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工小米)、《北京候鸟》(荆永鸣)、《一个谜面的几个谜作。
在可见的将来,乡土的中国就会转变为一个城底》(胡学文)、《高兴》(贾平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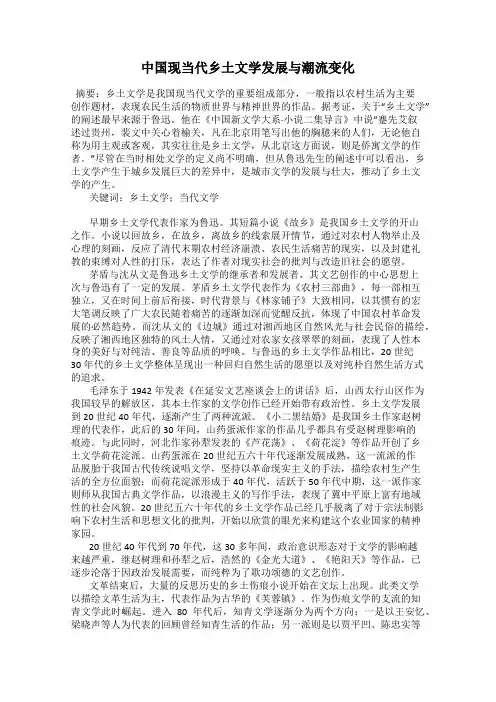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发展与潮流变化摘要:乡土文学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表现农民生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作品。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源于鲁迅。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尽管在当时相处文学的定义尚不明确,但从鲁迅先生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乡土文学产生于城乡发展巨大的差异中,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与壮大,推动了乡土文学的产生。
关键词:乡土文学;当代文学早期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为鲁迅。
其短篇小说《故乡》是我国乡土文学的开山之作。
小说以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线索展开情节,通过对农村人物举止及心理的刻画,反应了清代末期农村经济崩溃、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对人性的打压,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改造旧社会的愿望。
茅盾与沈从文是鲁迅乡土文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文艺创作的中心思想上次与鲁迅有了一定的发展。
茅盾乡土文学代表作为《农村三部曲》,每一部相互独立,又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时代背景与《林家铺子》大致相同,以其惯有的宏大笔调反映了广大农民随着痛苦的逐渐加深而觉醒反抗,体现了中国农村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沈从文的《边城》通过对湘西地区自然风光与社会民俗的描绘,反映了湘西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又通过对农家女孩翠翠的刻画,表现了人性本身的美好与对纯洁、善良等品质的呼唤。
与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品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整体呈现出一种回归自然生活的愿望以及对纯朴自然生活方式的追求。
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山西太行山区作为我国较早的解放区,其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开始带有政治性。
乡土文学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逐渐产生了两种流派。
《小二黑结婚》是我国乡土作家赵树理的代表作,此后的30年间,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几乎都具有受赵树理影响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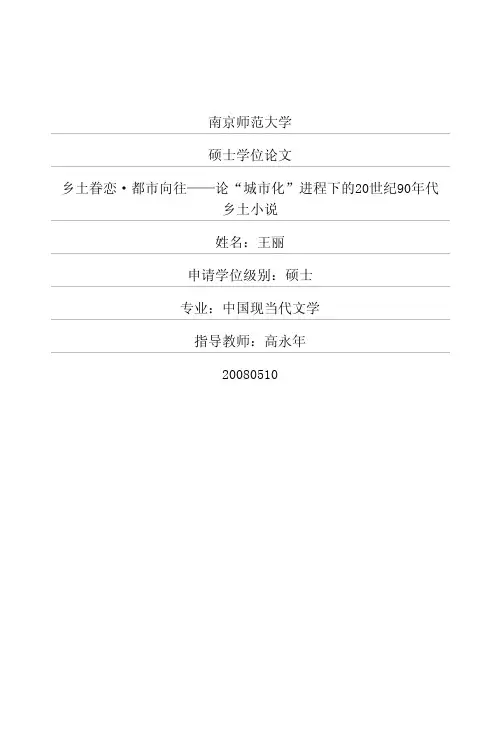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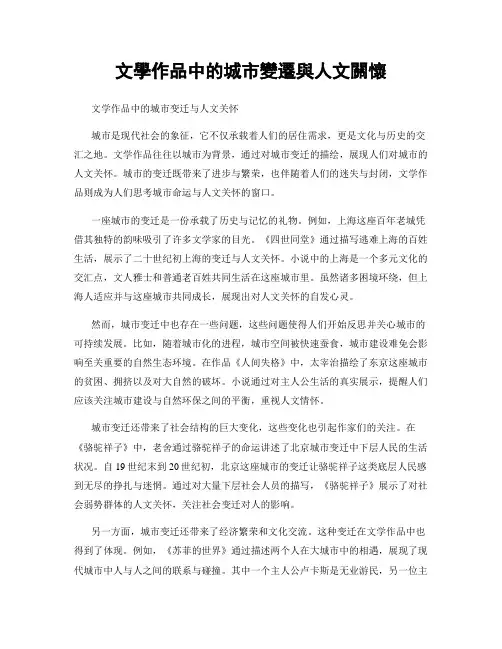
文學作品中的城市變遷與人文關懷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变迁与人文关怀城市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它不仅承载着人们的居住需求,更是文化与历史的交汇之地。
文学作品往往以城市为背景,通过对城市变迁的描绘,展现人们对城市的人文关怀。
城市的变迁既带来了进步与繁荣,也伴随着人们的迷失与封闭,文学作品则成为人们思考城市命运与人文关怀的窗口。
一座城市的变迁是一份承载了历史与记忆的礼物。
例如,上海这座百年老城凭借其独特的韵味吸引了许多文学家的目光。
《四世同堂》通过描写逃难上海的百姓生活,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变迁与人文关怀。
小说中的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文人雅士和普通老百姓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虽然诸多困境环绕,但上海人适应并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展现出对人文关怀的自发心灵。
然而,城市变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并关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空间被快速蚕食,城市建设难免会影响至关重要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作品《人间失格》中,太宰治描绘了东京这座城市的贫困、拥挤以及对大自然的破坏。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生活的真实展示,提醒人们应该关注城市建设与自然环保之间的平衡,重视人文情怀。
城市变迁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引起作家们的关注。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通过骆驼祥子的命运讲述了北京城市变迁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京这座城市的变迁让骆驼祥子这类底层人民感到无尽的挣扎与迷惘。
通过对大量下层社会人员的描写,《骆驼祥子》展示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
另一方面,城市变迁还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这种变迁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例如,《苏菲的世界》通过描述两个人在大城市中的相遇,展现了现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碰撞。
其中一个主人公卢卡斯是无业游民,另一位主人公苏菲是一个独立而富有的艺术家。
这次相遇不仅改变了卢卡斯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苏菲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

论“新时期”前期“右派”和“知青”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摘要:在“新时期”前期的文学中,“右派”和“知青”小说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但它们共同关注的是城市空间。
在城市空间中,这两种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人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焦虑和追求。
通过对这两种小说的比较分析,文章探讨了“新时期”前期城市空间的现状,以及城市空间中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新时期”前期、右派、知青、城市空间、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一、前言“新时期”前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关键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空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中的城市形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右派、知青两种不同的文学现象呈现出来。
右派文学与知青文学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对城市空间的关注点却是相似的。
两种小说中都有城市的身影,但是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所代表的意义有所差异。
本文将对这两种小说的城市空间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中国“新时期”前期城市空间的现状,以及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二、右派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右派小说常常将城市作为反面教材,将城市视为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混合体。
城市空间在右派小说中并不代表积极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未来,而是代表了伦理道德经济的崩溃和文化价值的颠覆。
右派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价值观、习俗和道德的认识上。
右派小说家胡风的小说《冼铁梅》反映了上海的社会层次,城市空间在小说中内含着一种疏离的特殊性。
上海被划成为住宅区和商业区两部分,住宅区多是木板房,居民多为移民,人们之间没有常规联系。
而商业区则被分为富裕和贫穷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的隔阂表明了阶级之间的界限极为明显。
《冼铁梅》中的城市空间,象征着人民生活的困难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幸。
此外,右派小说家曹文轩的小说《红旗垦荒记》也体现了城市空间的这种特殊性。
在《红旗垦荒记》中,城市空间的“城市”意义被大大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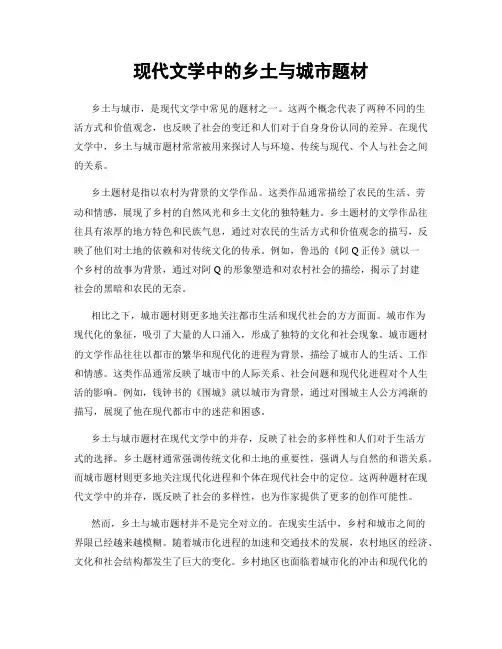
现代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题材乡土与城市,是现代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之一。
这两个概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们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差异。
在现代文学中,乡土与城市题材常常被用来探讨人与环境、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乡土题材是指以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这类作品通常描绘了农民的生活、劳动和情感,展现了乡村的自然风光和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气息,通过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描写,反映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以一个乡村的故事为背景,通过对阿Q的形象塑造和对农村社会的描绘,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无奈。
相比之下,城市题材则更多地关注都市生活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以都市的繁华和现代化的进程为背景,描绘了城市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
这类作品通常反映了城市中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例如,钱钟书的《围城》就以城市为背景,通过对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的描写,展现了他在现代都市中的迷茫和困惑。
乡土与城市题材在现代文学中的并存,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乡土题材通常强调传统文化和土地的重要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城市题材则更多地关注现代化进程和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
这两种题材在现代文学中的并存,既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也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
然而,乡土与城市题材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乡村地区也面临着城市化的冲击和现代化的挑战。
因此,现代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题材也常常交织在一起,揭示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
总之,乡土与城市题材是现代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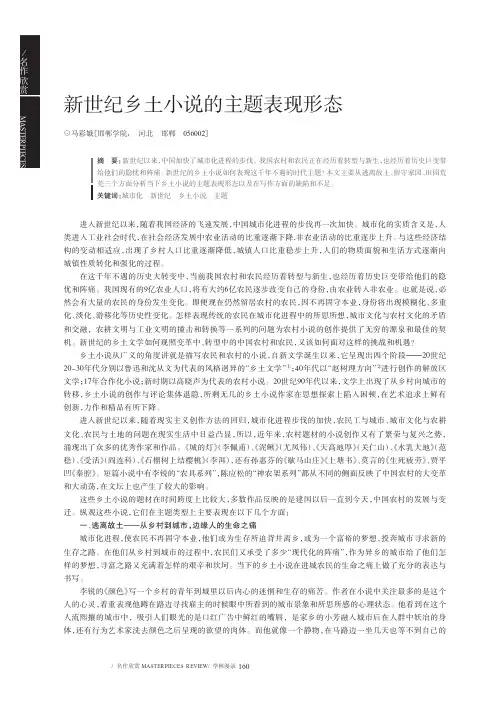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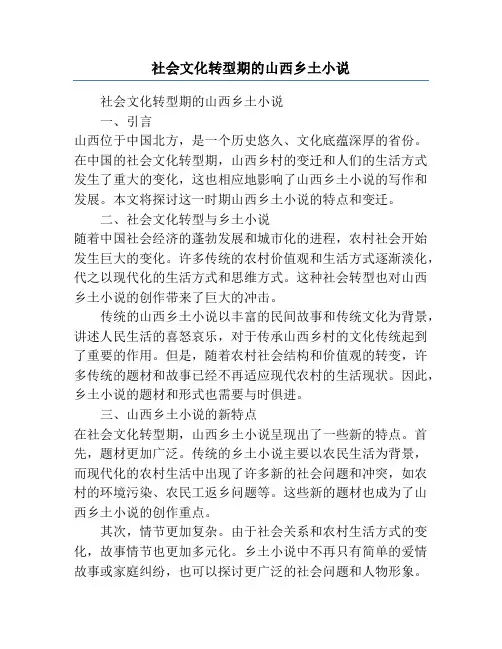
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山西乡土小说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山西乡土小说一、引言山西位于中国北方,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山西乡村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也相应地影响了山西乡土小说的写作和发展。
本文将探讨这一时期山西乡土小说的特点和变迁。
二、社会文化转型与乡土小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农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淡化,代之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这种社会转型也对山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山西乡土小说以丰富的民间故事和传统文化为背景,讲述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对于传承山西乡村的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转变,许多传统的题材和故事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农村的生活现状。
因此,乡土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三、山西乡土小说的新特点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山西乡土小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题材更加广泛。
传统的乡土小说主要以农民生活为背景,而现代化的农村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如农村的环境污染、农民工返乡问题等。
这些新的题材也成为了山西乡土小说的创作重点。
其次,情节更加复杂。
由于社会关系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故事情节也更加多元化。
乡土小说中不再只有简单的爱情故事或家庭纠纷,也可以探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人物形象。
第三,乡土小说的语言更加现代化。
传统的山西方言在现代乡土小说中逐渐减少,而普通话则成为主要的语言表达方式。
这也与现代农村青年接受教育的普及有关。
四、乡土小说作家的变迁乡土小说作家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
一方面,他们需要面对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农村生活现实,同时也需要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
因此,他们不仅需要拓宽自己的创作思路和题材选择,还需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化素养。
另一方面,乡土小说作家在市场竞争中也面临着挑战。
随着城市读者对于文学作品需求的变化,传统的乡土小说市场逐渐衰退,许多乡土小说作家也面临着生存困境。
乡村主题的变奏与城市形象的改写自《那山那人那狗》与《暖》之后,霍建起电影的乡村(故乡)主题书写发生了明显的变奏,而进入到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书写的框架。
由《那山那人那狗》和《暖》所建构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被打破,乡村已不能维持一种自足的空间存在。
到了《1980年代的爱情》,隐藏在乡村背后的城市正式登场,恬静的乡村书写与被压缩、被省略的城市时间书写形成强烈的反差。
因而城市的形象遭到改写,由彼时的憧憬、眺望与想象变为和乡土田园相对的一个掠夺式的符号或象征,而霍建起的田园理想也在变奏中呈现出某种悲凉的意味,犹如一首挽歌。
标签:霍建起;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书写;自足性;城市形象;田园理想2015年上映的《1980年代的爱情》,或许可以看做是对《那山那人那狗》、《暖》的回顾与总结。
在这部影片中,霍建起继续沿着《那山那人那狗》和《暖》所建构的乡村田园美学的思路进行深入开拓,而正式进入到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书写的范畴。
乡村主题的延续及进入城市的变奏,包括对城市形象的改写,反映出霍建起对乡村与城市关系进一步思考的同时,也不无悲情地吟唱出的一首乡土田园理想在城市的挤压下的破败挽歌。
一、乡村(故乡)主题的变奏——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书写①从1996年的浪漫爱情剧《赢家》开始,到2016年的人物传记片《大唐玄奘》,霍建起共执导了14部影片。
从主题的延续、深入以及开拓上看,只有《那山那人那狗》(1998)、《暖》(2003)以及《1980年代的爱情》(2015)三部涉及“乡村主题的变奏与城市形象的改写”这一话题。
从影片拍摄的时间顺序上看,这三部影片构成了研究这一话题紧密相连的互文本。
1998年的《那山那人那狗》根据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西部偏远山区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老乡邮员因腿病提前退了休,儿子接过父亲的班,安守故乡,做了一名乡邮员的故事。
80年代初的湖南西部偏远山区,乡土社會还未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
乡村与城市还处于两个天然空间,城市或者逐渐开始的商业化的喧嚣气息对乡土社会的影响还相当有限,而乡土社会的自足性保证了家庭或者个人的自足状态,对人生出路的困惑或者焦虑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化过程与社会变迁一、引言城市化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趋势之一。
随着城市不断膨胀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文学作品作为对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的记录和反映,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本文将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化描写,探讨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城市化之繁荣与喧嚣城市化带来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繁荣和喧嚣。
在文学作品中,城市往往是具有魅力和活力的象征。
城市中的繁华街道、灯红酒绿的夜景以及霓虹灯下的人流如织,都成了作家们描绘城市魅力的素材。
例如,鲁迅的《阿宝儿》中,描述了上海老街的繁荣景象,以及人们在城市中追求自由与进步的梦想。
然而,城市化过程中的喧闹和快节奏也不可忽视。
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对城市生活的负面描写。
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国的首都埃尔辛诺斯城市化后的变化令人不安,城市中的勾心斗角、物欲横流成为了主题。
三、城市化之冷漠与孤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与人之间的距离往往拉大了。
城市中大楼林立,车水马龙,人们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城市的冷漠和孤独感成为不少文学作品的背景。
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都市孤独”的主题,可以追溯到卡夫卡和包括张爱玲在内的现代作家们。
例如,张曼娟的《恶魔在城市的梳妆台上》中,描述了都市生活中普通人的孤独和焦虑,城市化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丰富,但却剥夺了人们情感交流的机会。
四、城市化之价值观念演进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传统的观念和道德准则开始受到质疑,新的思潮逐渐浮出水面。
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可以看作是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演进的写照。
城市化让人们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对传统道德准则的质疑和反叛开始充斥在文学作品中。
人们开始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尤其是女性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觉醒,成为了不少文学作品的主题。
五、城市化之互联网与虚拟空间城市化过程中,互联网的兴起和虚拟空间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城市化状态。
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发展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也是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迁的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城市化发展常常成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化发展,并分析其对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的影响。
首先,城市化发展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件和冲突,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题材和角度。
例如,城市中的人际关系、职业压力、家庭问题等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描写,作家可以深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样性。
其次,城市化发展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描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变得快节奏、多样化,这也使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现实感和复杂性。
城市中的人们常常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惑,他们的情感体验也更加多元化。
作家通过对这些情感的描写,可以更加真实地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使作品更具有共鸣力和感染力。
例如,城市中的年轻人常常面临着职业选择、爱情困惑等问题,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通过对这些情感的描写,作家可以深入探讨人的成长和自我认知的过程。
此外,城市化发展也对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和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使得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例如,城市中的人们常常面临着信息爆炸、快节奏的生活节奏等问题,这使得作家在叙事结构上更加注重节奏感和紧凑性。
同时,城市中的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使得作家在叙事风格上更加注重细节描写和多线索的交织,以展现城市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之,城市化发展对文学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城市化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丰富了作品的题材和角度。
城市化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描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作品更具有现实感和共鸣力。
呐喊:乡村与都市的分化现象引言《呐喊》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描绘了乡村和都市之间日益加剧的差距。
本文将探讨乡村与都市分化现象在鲁迅的作品中的揭示以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乡村与都市的反差在《呐喊》中,鲁迅生动地展示了乡村和都市之间的反差。
他通过对人物形象、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刻画,清楚地展示了今昔之间的巨大落差。
1. 人物形象《呐喊》中塑造了许多乡村和都市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痞子蔡和牛仔帮。
痞子蔡代表着忍受艰辛生活却不愿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体,而牛仔帮则代表着逃离农村生活、追求更好未来机会的年轻人。
2. 社会环境乡村和都市社会环境也有着明显的反差。
乡村地区受到封建主义和社会制度束缚,生活贫困、闭塞;而都市则是现代化的象征,充满活力、机会更多。
3. 生活方式在《呐喊》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乡村和都市的不同。
农民们过着劳作繁重、收入微薄的贫困生活,而都市居民则享受着便利的交通、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等优势。
现实生活中的分化现象鲁迅揭示的乡村与都市分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明显痕迹。
以下是一些典型例子:1. 经济差距乡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较低,而都市地区则拥有更多机会和资源,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这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平衡的财富分配问题。
2. 教育差距由于教育资源集中在都市地区,农村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造成了教育差距的扩大。
3. 城乡医疗差异都市地区拥有更现代化、高水平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地区则缺乏这些条件。
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医疗服务不平衡问题。
对策和展望为了解决乡村与都市的分化现象,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下是一些建议:1. 改善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交通、电力等方面的条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2. 平衡教育资源通过政府调配教育资源,保障农村地区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3. 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医疗和社会福利服务建设,让农民享受到与都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嬗变【摘要】新时期乡土小说在对城市形象的书写有一嬗变,即由80年代的赞美与向往到90年代后的“丑化”。
其原因与时代文化经济的转型、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相关联。
【关键词】乡土小说;城市形象;嬗变及成因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下共生发展。
在此背景下,乡土小说中所书写的城市形象,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进步以及作家自身的因素,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发生了新的转型和嬗变。
一、向往与想象:八十年代的城市形象
改革开放后,城市文明风吹进乡村,对城市的向往与想象成为这时乡土文学创作的共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谈到历史发展中城市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1]作家们看到城市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创作时不自觉地把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关系的理解赋予其中,致使80年代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乡村人对城市的追求与向往与赞赏。
对长期受束缚压抑的乡村,城市新物品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视野上的需求,更是精神上的向往。
“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
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
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追求新的空间的努力。
”[2]此外,铁路、公路、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使80年代封闭落后的村庄受到了一次新的城市文明的洗礼,人们对于城市形象的想象与追求便有了途径。
铁凝《哦、香雪》、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张一弓《黑娃照相》中,大量出现代表城市意象的物品:牙膏、牙刷、香皂、电话、皮鞋、衬衫等,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生活及观念。
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城市夜景的灯火等景观,“现代城市常常被人们形象称作钢筋水泥的森林。
”[3]与低矮茅屋的鲜明对立。
生活在乡村的高加林,烟峰,禾禾,陈焕生们,熟悉乡村的一草一木,当他们进入城市时,花花绿绿的商店、各色的旅社酒店、卖小吃的小摊以及各种交易市场,整个城市的整体印象让他们艳羡不已,充满着崇敬和憧憬。
作家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城市发展与改观,体验着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需求。
并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环境等城市文化的外现,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冲击来展开描绘和刻画。
二、存在与徘徊:九十年代以后的城市形象
进入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转型,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开始成为重要形态之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此背景下乡村人进入城市“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赖关系的人生。
”
并且“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长旅中,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4]。
与80年代相比,乡土小说中城市形象的描写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作家及作品数量大幅增多,二是对城市形象的构建,由赞美转变为批判为主,从精神层面的追求转变到在具体的城市实体中去审视。
三是从对城市客观实在物的描写转向了对城市人性的反思。
如刘庆邦《家园何处》中何香停进城打工,则是被城市嘲笑与玩弄,最后城市让何香停以“独特的身份”,成为各种形形色色男人的玩物。
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特殊的一员——捡破烂者。
在城市的生活中,刘高兴帮邻居开门,帮老太太搬袋米,换来的不是真心感谢,而是钱的回报。
张宇《乡村情感》中形象比喻到“我是乡下进城来的一只风筝”,与城市没有任何的真情。
城市另眼相看乡村,乡村人又何尝不是冷眼审视呢?城市虽有着华丽的外观,可进入其中的这些乡村人感受最深的则是城市的罪恶与污浊。
阎连科《黄金洞》中的城市女人来到农村,由于她的出现,金钱的力量,致使父子、兄弟之间人性沦丧、互相仇视。
刘醒龙《大树还小》中描写返回城市的知青,任意把农村进城打工的自己救命恩人的女儿玩弄成自己的小三。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城市知识分子祝队长等人对去做挑夫的农村人的不信任、不理解、不同情的态度,最后因二十块钱,引发了一场血案。
这一系列城市人,也许正是农村与城市在现代性影响之下的结果,不仅表现出了城市人性的沦丧,也表现出了乡村人在城市社会影响之下
的变化,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日益激烈。
三、审美与嬗变:城市形象变异的原因
从80年代起一直到新世纪,对城市形象的书写一直在发生着变异。
在紧跟时代步伐的乡土文学创作,对城市的审美观念、乡土人物的性格特征、艺术风格等的表现则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作家生活的体验及审美观念在不断变化,致使城市形象也发生着嬗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户口管理等各项国家政策的松动,使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之上的农民得以解放,可自由进城。
此时,广大农村对现代化下的城市的各种新事物的追求日趋迫切,城市成了农民们的理想生活之所,因此对城市形象的书写以赞美为主。
90年代后,随着已有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逐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城乡矛盾日益严重。
“农民工进城”成为了主要社会现象,进城后的农民对城市的姿态与审美情感因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较80年代乡村人眼中的城市而不同,甚至出现了厌恶与报复的心理。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作家们,也在创作中影射出对社会、对生活的感受。
“生活经验为艺术创造提供动力、酵母,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存在着激发、诱导从而为生活经验最终转化为艺术形象提供形式与可能。
”[5]大批乡土作家生活在城市,感受并体验着现代都市社会。
众多作家都把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思潮及变迁迹化在自己的创作中,如路遥的《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到《高兴》的变化,铁凝的《哦,香雪》到《谁能让我害
羞》中香雪和城市女人的形象,反应出了两个不同时期作家创作的变化。
另外,90年代的作家越来越感受到在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双重影响之下,人情的冷漠,世俗化、趋利化严重的现象,为此,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们直面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从而去揭露城市人性弊端,如张炜《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的创作。
总之,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不仅与作家自身观念与审美有关,而且受其社会、时代变迁的影响。
但90年代以后的创作,在金钱、权力、欲望等的笼罩之下,城市成了欺骗、矛盾、冷漠的象征,丑化城市、揭露城市弊端太过极端化与个人化,与80年代对城市文明的赞美与歌颂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为此,乡土作家在质疑与反思现代性的各种弊端的同时也因对现代性下政治、经济、文化的所带来文明与进步进行合理的刻画与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