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
- 格式:docx
- 大小:15.2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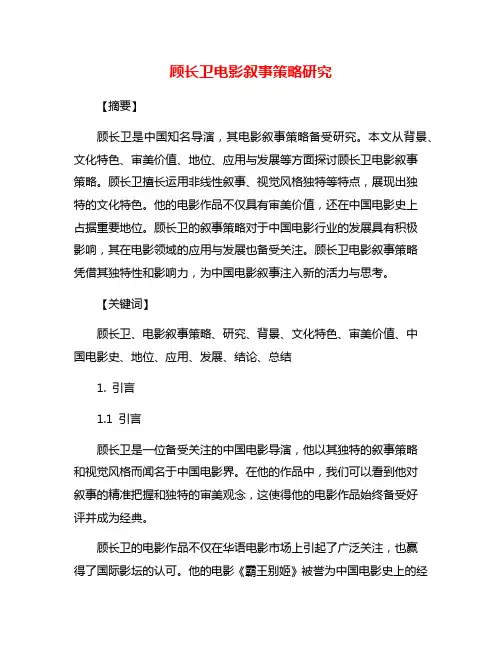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摘要】顾长卫是中国知名导演,其电影叙事策略备受研究。
本文从背景、文化特色、审美价值、地位、应用与发展等方面探讨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
顾长卫擅长运用非线性叙事、视觉风格独特等特点,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
他的电影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顾长卫的叙事策略对于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其在电影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也备受关注。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凭借其独特性和影响力,为中国电影叙事注入新的活力与思考。
【关键词】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背景、文化特色、审美价值、中国电影史、地位、应用、发展、结论、总结1. 引言1.1 引言顾长卫是一位备受关注的中国电影导演,他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视觉风格而闻名于中国电影界。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叙事的精准把握和独特的审美观念,这使得他的电影作品始终备受好评并成为经典。
顾长卫的电影作品不仅在华语电影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赢得了国际影坛的认可。
他的电影《霸王别姬》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叙事策略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具有现代审美的特点,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了独特的视听盛宴。
本文将对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背景、文化特色、审美价值以及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
通过对顾长卫电影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理念和叙事风格,从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他的电影作品。
在接下来的我们将逐一探讨以上几个方面,深入挖掘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
2. 正文2.1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的背景顾长卫的电影叙事策略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并且在影迷中拥有着极高的口碑。
他对于镜头运用的独到见解和对情感表达的敏锐感知,使他的电影作品在叙事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的背景也包括他在电影领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通过其多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顾长卫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和叙事特点,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翘楚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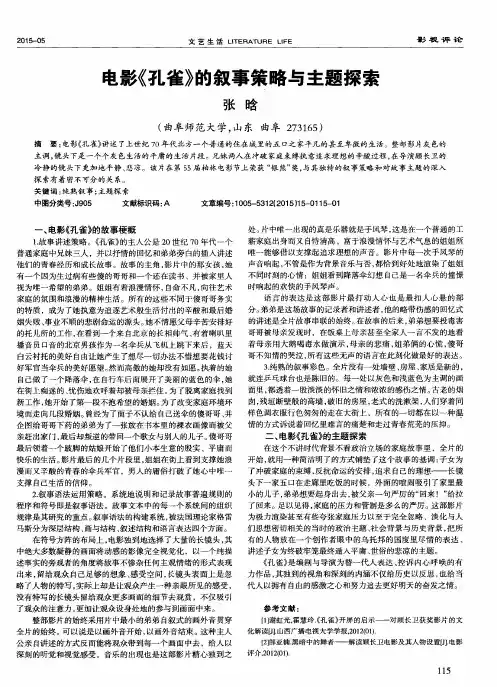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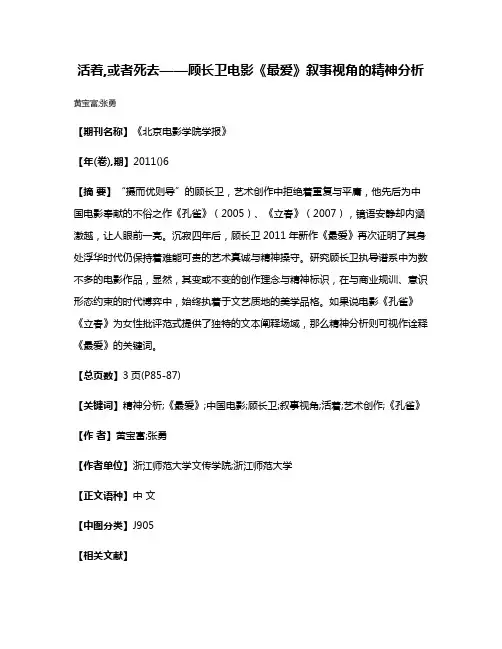
活着,或者死去——顾长卫电影《最爱》叙事视角的精神分析黄宝富;张勇
【期刊名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6
【摘要】“摄而优则导”的顾长卫,艺术创作中拒绝着重复与平庸,他先后为中国电影奉献的不俗之作《孔雀》(2005)、《立春》(2007),镜语安静却内涵激越,让人眼前一亮。
沉寂四年后,顾长卫2011年新作《最爱》再次证明了其身处浮华时代仍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艺术真诚与精神操守。
研究顾长卫执导谱系中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显然,其变或不变的创作理念与精神标识,在与商业规训、意识形态约束的时代博弈中,始终执着于文艺质地的美学品格。
如果说电影《孔雀》《立春》为女性批评范式提供了独特的文本阐释场域,那么精神分析则可视作诠释《最爱》的关键词。
【总页数】3页(P85-87)
【关键词】精神分析;《最爱》;中国电影;顾长卫;叙事视角;活着;艺术创作;《孔雀》【作者】黄宝富;张勇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05
【相关文献】
1.浅析顾长卫电影中的女性生存寓言——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 [J], 何爽;谢燕南
2.主观镜语下的小人物形象建构——以《立春》《孔雀》《最爱》为例解读顾长卫电影 [J], 林亚斐
3.顾长卫经典电影海报的符号学阐释——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 [J], 王芹芹
4.文化“他者”身份认同视角下的顾长卫电影--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J], 魏金梅
5.浅析顾长卫电影中表现边缘化小人物的手法——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 [J], 王泽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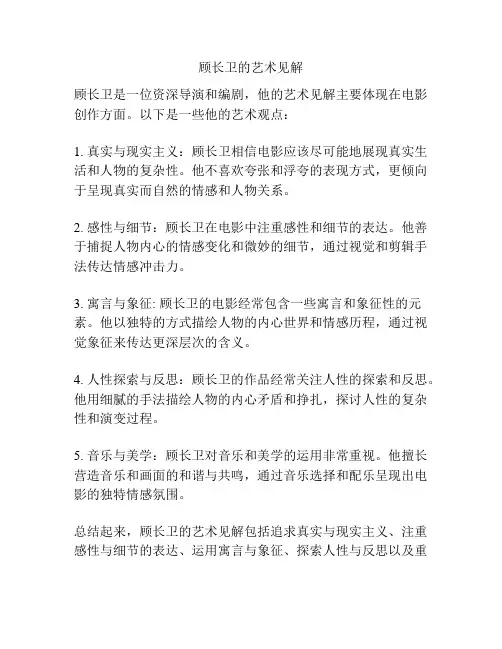
顾长卫的艺术见解
顾长卫是一位资深导演和编剧,他的艺术见解主要体现在电影创作方面。
以下是一些他的艺术观点:
1. 真实与现实主义:顾长卫相信电影应该尽可能地展现真实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
他不喜欢夸张和浮夸的表现方式,更倾向于呈现真实而自然的情感和人物关系。
2. 感性与细节:顾长卫在电影中注重感性和细节的表达。
他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和微妙的细节,通过视觉和剪辑手法传达情感冲击力。
3. 寓言与象征: 顾长卫的电影经常包含一些寓言和象征性的元素。
他以独特的方式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历程,通过视觉象征来传达更深层次的含义。
4. 人性探索与反思:顾长卫的作品经常关注人性的探索和反思。
他用细腻的手法描绘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挣扎,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演变过程。
5. 音乐与美学:顾长卫对音乐和美学的运用非常重视。
他擅长营造音乐和画面的和谐与共鸣,通过音乐选择和配乐呈现出电影的独特情感氛围。
总结起来,顾长卫的艺术见解包括追求真实与现实主义、注重感性与细节的表达、运用寓言与象征、探索人性与反思以及重
视音乐与美学的运用。
这些特点都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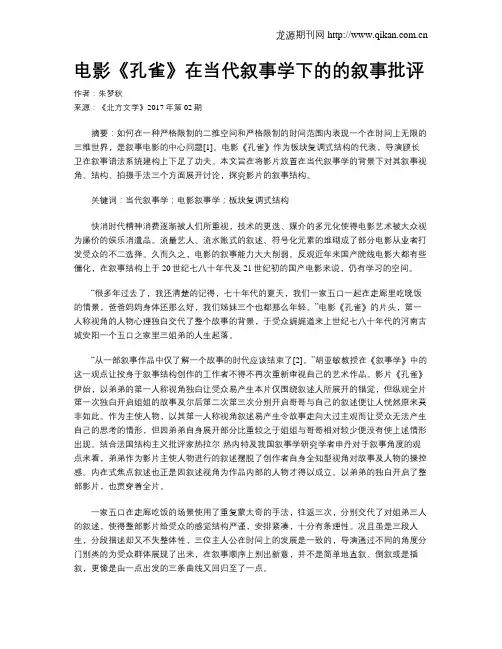
电影《孔雀》在当代叙事学下的的叙事批评作者:朱梦秋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2期摘要:如何在一种严格限制的二维空间和严格限制的时间范围内表现一个在时间上无限的三维世界,是叙事电影的中心问题[1]。
电影《孔雀》作为板块复调式结构的代表,导演顾长卫在叙事语法系统建构上下足了功夫。
本文旨在将影片放置在当代叙事学的背景下对其叙事视角、结构、拍摄手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探究影片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当代叙事学;电影叙事学;板块复调式结构快消时代精神消费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技术的更迭、媒介的多元化使得电影艺术被大众视为廉价的娱乐消遣品。
流量艺人、流水账式的叙述、符号化元素的堆砌成了部分电影从业者打发受众的不二选择。
久而久之,电影的叙事能力大大削弱。
反观近年来国产院线电影大都有些僵化,在叙事结构上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21世纪初的国产电影来说,仍有学习的空间。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的记得,七十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在走廊里吃晚饭的情景,爸爸妈妈身体还那么好,我们姊妹三个也都那么年轻。
”电影《孔雀》的片头,第一人称视角的人物心理独白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于受众娓娓道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河南古城安阳一个五口之家里三姐弟的人生起落。
“从一部叙事作品中仅了解一个故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2]。
”胡亚敏教授在《叙事学》中的这一观点让投身于叙事结构创作的工作者不得不再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作品。
影片《孔雀》伊始,以弟弟的第一人称视角独白让受众易产生本片仅围绕叙述人所展开的错觉,但纵观全片第一次独白开启姐姐的故事及尔后第二次第三次分别开启哥哥与自己的叙述便让人恍然原来莫非如此。
作为主使人物,以其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易产生令故事走向太过主观而让受众无法产生自己的思考的情形,但因弟弟自身展开部分比重较之于姐姐与哥哥相对较少便没有使上述情形出现。
结合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内特及我国叙事学研究学者申丹对于叙事角度的观点来看,弟弟作为影片主使人物进行的叙述摆脱了创作者自身全知型视角对故事及人物的操控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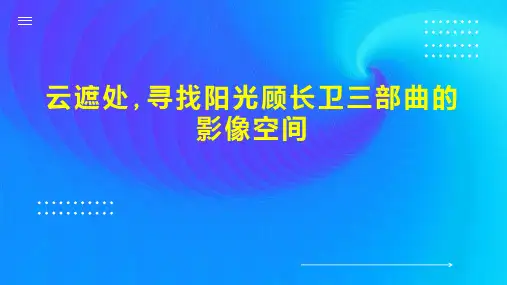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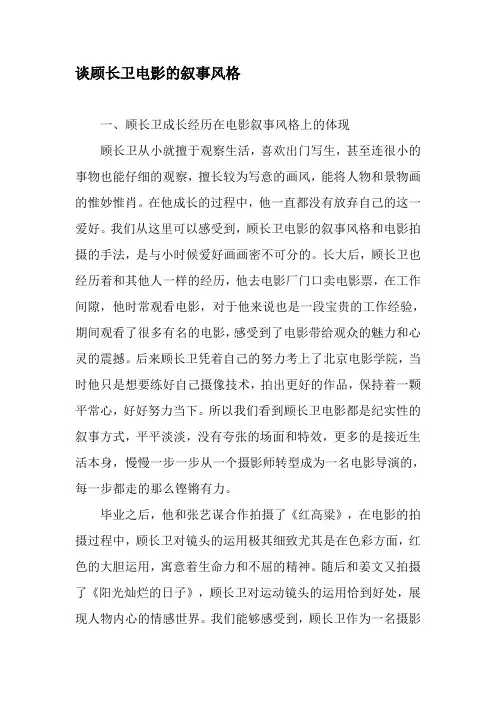
谈顾长卫电影的叙事风格一、顾长卫成长经历在电影叙事风格上的体现顾长卫从小就擅于观察生活,喜欢出门写生,甚至连很小的事物也能仔细的观察,擅长较为写意的画风,能将人物和景物画的惟妙惟肖。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一爱好。
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顾长卫电影的叙事风格和电影拍摄的手法,是与小时候爱好画画密不可分的。
长大后,顾长卫也经历着和其他人一样的经历,他去电影厂门口卖电影票,在工作间隙,他时常观看电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工作经验,期间观看了很多有名的电影,感受到了电影带给观众的魅力和心灵的震撼。
后来顾长卫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时他只是想要练好自己摄像技术,拍出更好的作品,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好好努力当下。
所以我们看到顾长卫电影都是纪实性的叙事方式,平平淡淡,没有夸张的场面和特效,更多的是接近生活本身,慢慢一步一步从一个摄影师转型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每一步都走的那么铿锵有力。
毕业之后,他和张艺谋合作拍摄了《红高粱》,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顾长卫对镜头的运用极其细致尤其是在色彩方面,红色的大胆运用,寓意着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
随后和姜文又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顾长卫对运动镜头的运用恰到好处,展现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
我们能够感受到,顾长卫作为一名摄影师的认真和努力,在拍摄和叙事上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电影导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做了充足的准备。
综上所述顾长卫成长的经历,为他以后电影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做了铺垫,叙事作为电影的主要部分,它贯穿电影始终,在电影讲述过程中很重要,通过电影叙事在时间,空间和结构方面来讲述所要传达给受众自己内心的想法。
二、纪实性的叙事空间电影是讲故事的,通过故事把这个空间填充完满,而故事的表达是通过叙事来实现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围绕着一个环境而发生的,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所发生的某一场景。
所谓的电影叙事空间有着不同的含义,既可指电影当中故事发生的空间,又可指人物心理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可以指画面构图所形成的的空间,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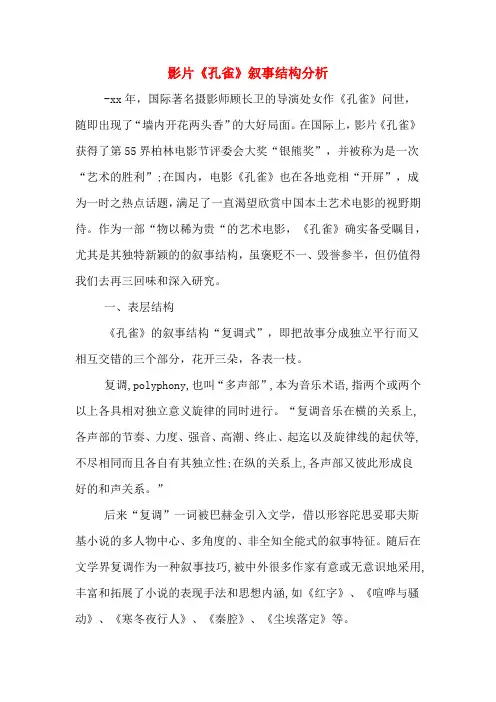
影片《孔雀》叙事结构分析-xx年,国际著名摄影师顾长卫的导演处女作《孔雀》问世,随即出现了“墙内开花两头香”的大好局面。
在国际上,影片《孔雀》获得了第55界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并被称为是一次“艺术的胜利”;在国内,电影《孔雀》也在各地竞相“开屏”,成为一时之热点话题,满足了一直渴望欣赏中国本土艺术电影的视野期待。
作为一部“物以稀为贵“的艺术电影,《孔雀》确实备受瞩目,尤其是其独特新颖的的叙事结构,虽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仍值得我们去再三回味和深入研究。
一、表层结构《孔雀》的叙事结构“复调式”,即把故事分成独立平行而又相互交错的三个部分,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复调,polyphony,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相对独立意义旋律的同时进行。
“复调音乐在横的关系上,各声部的节奏、力度、强音、高潮、终止、起迄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不尽相同而且各自有其独立性;在纵的关系上,各声部又彼此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
”后来“复调”一词被巴赫金引入文学,借以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多人物中心、多角度的、非全知全能式的叙事特征。
随后在文学界复调作为一种叙事技巧,被中外很多作家有意或无意识地采用,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如《红字》、《喧哗与骚动》、《寒冬夜行人》、《秦腔》、《尘埃落定》等。
复调小说的先锋实验为电影叙事提供了范例和启示。
视觉图像是电影的媒介方式和表现语言,索绪尔指出:“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于是,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利用复调机制而构思精良的电影,如《广岛之恋》、《罗拉快跑》、《暴雨将至》等。
国产片《孔雀》,在国外电影叙事结构启发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和实践了复调原理,将姐姐(高卫红)、哥哥(高卫国)、弟弟(高卫强)的故事处理成管弦乐队的不同声部,可以进行齐奏、对位演奏与赋格曲式等多种选择,既保持独立性,又形成对话性,使其形成一种哀怨凄婉的和声关系以表现影片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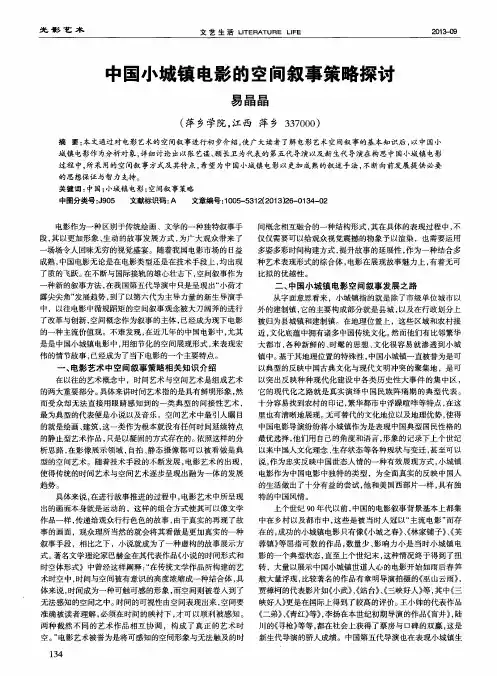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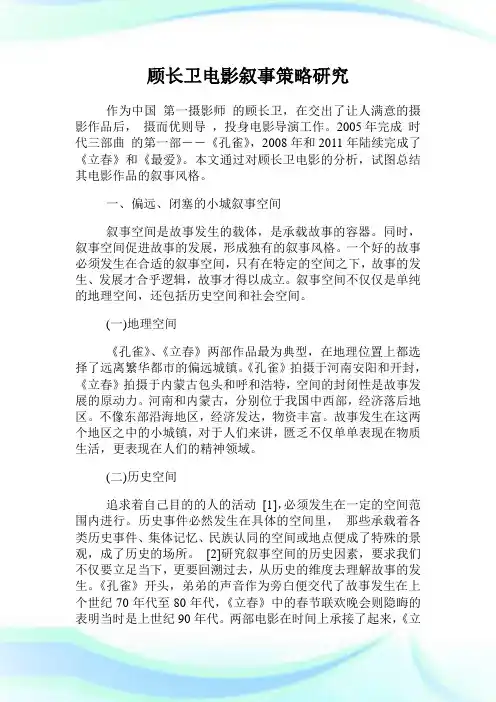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作为中国第一摄影师的顾长卫,在交出了让人满意的摄影作品后,摄而优则导,投身电影导演工作。
2005年完成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孔雀》,2008年和2011年陆续完成了《立春》和《最爱》。
本文通过对顾长卫电影的分析,试图总结其电影作品的叙事风格。
一、偏远、闭塞的小城叙事空间叙事空间是故事发生的载体,是承载故事的容器。
同时,叙事空间促进故事的发展,形成独有的叙事风格。
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发生在合适的叙事空间,只有在特定的空间之下,故事的发生、发展才合乎逻辑,故事才得以成立。
叙事空间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还包括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
(一)地理空间《孔雀》、《立春》两部作品最为典型,在地理位置上都选择了远离繁华都市的偏远城镇。
《孔雀》拍摄于河南安阳和开封,《立春》拍摄于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空间的封闭性是故事发展的原动力。
河南和内蒙古,分别位于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不像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物资丰富。
故事发生在这两个地区之中的小城镇,对于人们来讲,匮乏不仅单单表现在物质生活,更表现在人们的精神领域。
(二)历史空间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1],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
历史事件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
[2]研究叙事空间的历史因素,要求我们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回溯过去,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故事的发生。
《孔雀》开头,弟弟的声音作为旁白便交代了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立春》中的春节联欢晚会则隐晦的表明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
两部电影在时间上承接了起来,《立春》可以看做是《孔雀》的再续,表现了我国20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这一段时期。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刚刚过去,人们一方面还在胆战心惊的只想安稳生活,求得生存。
另一方面,新的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唤醒了梦想者心中的理想,他们不满现状,开始苏醒,试图冲破原有的牢笼生活,走出家庭、社会的桎梏,继而追随自己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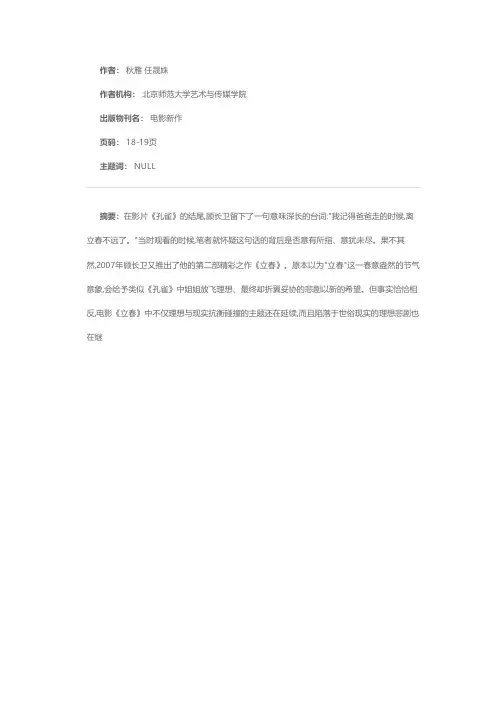
作者: 秋雁 任晟姝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新作
页码: 18-19页
主题词: NULL
摘要:在影片《孔雀》的结尾,顾长卫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
"当时观看的时候,笔者就怀疑这句话的背后是否意有所指、意犹未尽。
果不其然,2007年顾长卫又推出了他的第二部精彩之作《立春》。
原本以为"立春"这一春意盎然的节气意象,会给予类似《孔雀》中姐姐放飞理想、最终却折翼妥协的悲剧以新的希望。
但事实恰恰相反,电影《立春》中不仅理想与现实抗衡碰撞的主题还在延续,而且陷落于世俗现实的理想悲剧也在继。
《孔雀》擦身而过的美丽柏林载誉归来的影片《孔雀》,以三段式的结构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家庭中几个成员的成长历程,描写的是一些平凡人生的琐碎生活。
顾长卫执导的这部处女作像大多数第五代导演一样采用了擅长的“回望”姿态,所不同的是《孔雀》少了几分宏大的政治话语寓意,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的一种关注。
一、姐姐—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与张艺谋电影中巩俐的神话形象及姜文电影中男性的欲望对象不同,《孔雀》中的女性形象是很真实很女性视角的,姐姐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全片最大的一个亮点。
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华民族是最中庸的一个民族,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电影银幕上一直缺少一种浪漫的、神经质的、力图超越庸常生活的女性形象。
而《孔雀》做到了,姐姐这一人物形象不能说是丰满的,但是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在隐忍的、奉献的、坚持的、世俗的、甚至被当作一种图腾仰视着的银幕女性形象之外,还存在着真实的、自我的、带刺的、理想化的、是少女不是女人的女性形象。
相比哥哥、弟弟相对单薄的个人故事,姐姐这个人物的故事基本上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不同的阶段、情节讲述着姐姐这个人物形象不同的性格侧面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遭遇。
影片开始那一幕是姐姐性格一个总的提示,手风琴或者音乐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的追求,一边开着的冒着热气的水壶是形而下的现实的生活,从一开始这个姐姐就有着一种无视现实生活、专注个人的非现实理想的倾向表现。
接下来的幼儿园事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性格侧面,是她对平凡的、现实的、命定的生活的一种不甘。
伞兵的理想是对地上现实生活的逃离,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北京军官可以说是姐姐的初恋,而这段恋情的对象亦是远离她生活范围之外的,接着我们看她对感情的处理:她是喜欢军官的,但她不甘示弱,她自以为是地幻想着通过打赢军官乒乓球换取伞兵录取的资格,这是她的不按常理出牌,自然她的率真是败在另一对更懂得男性心理或者说伪装的姐妹手下。
这里面涉及到一种生活的技巧,我想要什么,我怎样得到它,虽然姐姐从一开始便没有掌握或者说根本不肯屈就于这种技巧、这种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一种人际规范。
电影《孔雀》的叙事技法漫议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荣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其叙事技法是精熟而集大成的。
从叙事结构,与叙事色彩两个方面解析之。
一、精良的叙事结构影片虽然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故事,但却看不到那个时期的动荡历史风云。
从一个个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活生生的70年代中国家庭的生活图景。
和弱化冲突、淡化情节相对应的是,影片更像是若干生活片段或场景组合而成的拼图。
平平淡淡的琐碎场景和片段细节,以饱满的生活气息填充于整个叙述过程,故事已没有了高潮。
但并不是说故事没有高潮就没有了悲剧,悲剧已渗透在各个生活化的细节璽,影片中有一个场景令人难忘:一家人正在做煤球,忽然下起了大雨,做好的煤球来不及遮盖,一家五口站在屋檐下眼睁睁地看着煤球被大雨冲毀、冲走,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
可以说,真实且富有想象张力的细节成就了《孔雀》的灵魂和生命,这些细可能显示出如此强大的情感张力,得益于静止长镜头和音乐的巧妙运用。
所谓长镜头,指镜头在全景状态下纹丝不动,长时间拍摄,以一种完全生活化的旁观姿态记录整个过程。
如一家人吃饭、哥哥相亲、父亲检查弟弟作业、姐姐在车间刷酒瓶,姐弟挨罚跪搓板……所有生命的坎坷与酸涩都在这一瞬间翻腾。
这场无声痛哭的特写镜头持续了足足有一分多种,人物内心惨痛而剧烈的撕扯、挣扎、在观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和回响。
《孔雀》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一种言表冷静下的人性深度和情感张力,最典型的莫过下影片结尾孔雀开屏的一个长镜头:姐姐、哥哥、弟弟三人一起定过孔雀,期望看到孔雀开屏,最后孔雀却在他们走过之后展现了眩目的羽毛。
这一场面传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过着不完美的生活,很多时候,期许和现实近在咫尺,却又擦肩而过,当中充满了美丽和遗憾。
二、纯熟的叙事色彩(更多最新电影新剧尽在 )色彩在视觉世界里是生命和情感的象征,之于电影的意义不可低估。
《孔雀》以灰色为背景展示了灰色的人生。
顾长卫电影研究
2005年,顾长卫自其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孔雀》开始,就充分利用他自身的敏感性、细腻的感知力、敏捷的洞察力、个性化的镜头语言以及人道主义关怀精神,在表现草根人物故事和传播地域文化这条电影道路上,坚持不懈走了近十年。
在这十年里,顾长卫共导演了三部剧情片、一部纪录片和一部微电影。
本文试图以迄今为止顾长卫的所有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前人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向为参照方法,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展开,去全面把握顾长卫电影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表现形式。
但是在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整合过程中,笔者认为,前人在顾长卫电影的研究上尚有一些不妥和空白之处,存在着诸如主题分类过于繁琐复杂,人物研究只关注主要人物,忽略了次要人物,叙事模式大都从文学方面分析,而不是立足于电影本身等问题,尤其是其纪录片《在一起》和微电影《龙头》,研究更属空白。
因此,本文会在顾长卫电影作品的主题分类、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等三方面做重点解读,探讨其电影作品在这十年里的突破与创新,去审视其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揭示其电影创作的心路历程,关注其电影创作的最新动向,展望其电影创作的未来前景。
也希望借此文章,来促使更多专业影评人和普通观众了解顾长卫个人及其电影作品,关注其电影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思自身的生存处境。
笔者将会借助文本对比以及文献查询的研究方法,分四个章节来深入挖掘顾长卫电影作品的价值,并试图从他的电影创作经验中,寻找到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性启示。
顾长卫电影叙事策略研究
作为中国“第一摄影师”的顾长卫,在交出了让人满意的摄影作品后,“摄而优则导”,投身电影导演工作。
2005年完成“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孔雀》,2008年和2011年陆续完成了《立春》和《最爱》。
本文通过对顾长卫电影的分析,试图总结其电影作品的叙事风格。
一、偏远、闭塞的小城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是故事发生的载体,是承载故事的容器。
同时,叙事空间促进故事的发展,形成独有的叙事风格。
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发生在合适的叙事空间,只有在特定的空间之下,故事的发生、发展才合乎逻辑,故事才得以成立。
叙事空间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还包括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
(一)地理空间
《孔雀》、《立春》两部作品最为典型,在地理位置上都选择了远离繁华都市的偏远城镇。
《孔雀》拍摄于河南安阳和开封,《立春》拍摄于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空间的封闭性是故事发展的原动力。
河南和内蒙古,分别位于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不像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物资丰富。
故事发生在这两个地区之中的小城镇,对于人们来讲,匮乏不仅单单表现在物质生活,更表现在人们的精神领域。
(二)历史空间
“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1],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
历史事件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
”[2]研究叙事空间的历史因素,要求我们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回溯过去,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故事的发生。
《孔雀》开头,弟弟的声音作为旁白便交代了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立春》中的春节联欢晚会则隐晦的表明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
两部电影在时间上承接了起来,《立春》可以看做是《孔雀》的再续,表现了我国20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这一段时期。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刚刚过去,人们一方面还在胆战心惊的只想安稳生活,求得生存。
另一方面,新的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唤醒了梦想者心中的理想,他们不满现状,开始苏醒,试图冲破原有的牢笼生活,走出家庭、社会的桎梏,继而追随自己梦。
浩瀚历史中的这一段,便孕育了顾长卫的“时代三部曲”。
产生了姐姐、王彩玲、胡金权等人物形象,顺承了故事的产生和发展。
(三)社会空间
故事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故事,这就是故事产生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包括不同的因素:人际关系、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状况...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
一方面改革开放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但另一方面,即使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能
从中受益,劳动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治安的情况也在恶化。
在《孔雀》中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缺少交流的冷漠、《立春》中追梦者的迷茫、《最爱》中人情的漠然都呈现出对这一时期的反映,在情节设置上与时代得到了呼应。
二、出走与逃离的叙事模式
(一)离家与归家
《孔雀》运用了连缀式的故事结构,分别讲述了姐姐、哥哥和弟弟的故事,凸显出小城镇生活在精神与物质、梦想和现实、个人与社会、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姐姐的形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一群伞兵的到来,给死水般的小城带来了波澜,也给了姐姐一个五彩的梦――当一个伞兵。
伞兵的梦想被社会打破、也被母亲粉碎。
来自家庭的束缚与压抑,坚定了姐姐离家的心情。
她以决绝的姿态,迫切的把自己嫁了出去,从一个小镇嫁入另一个小镇。
然而生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预示着姐姐对家的回归。
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让弟弟这个沉默的少年逃离到了社会,故事省略了弟弟在社会中的遭遇,镜头一切直接到了若干年后,回到家中的弟弟带来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和她的儿子。
大时代的变化,致使父母欠缺了与孩子之间温情的交流,只剩下来自家庭的秩序,这样的状况和兄妹三个的畸形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再后来,爸爸去世了,妈妈变老了,姐姐又嫁人了,哥哥也有孩子了,这个原生家庭也散了。
(二)逃离与追寻
“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就蠢蠢欲动。
”《立春》中的王彩玲,在立春过后,加紧了逃离这个城镇的步伐,一次次的往返北京,寻求机会、寻求梦想,她虽然没有美丽的外表,却自认为拥有一副好嗓子,即使身在小城却不甘平庸,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唱到巴黎歌剧院。
严冬之下身着芭蕾舞服的男性舞蹈老师胡金泉,燃烧着自己去热爱芭蕾,却被小城秩序所不容。
她(他)们妄图冲破世俗的观念、秩序的束缚,却最终只能被这秩序所规训和惩罚。
追寻梦想的王彩玲,被梦想之城――北京,粉碎了梦想,北京不承认她的才华和天赋,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来自家庭的温暖使王彩玲得到了慰藉,她甘愿领养了一个孩子,成为卖猪肉的个体户,梦想破灭可生活还得继续。
热爱芭蕾的胡金泉,自我放逐到了监狱,这是个体主动选择的逃离,逃离到一个可以继续梦想的地方,即便是禁锢身体自由的监狱,但对于胡金泉来说,这里却是离梦想更近的地方。
《最?邸分械恼缘靡庥肷糖偾伲?两个得了“热病”(HIV)的人产生了感情,但世俗却不允许他们的结合,为了生活在一起,两人逃离村人的目光,住在村郊的石头房里,追求生命中最后的欢乐时光,在有限的生命里燃烧着生命的激情。
顾长卫转行之后,只拍摄了《孔雀》、《立春》、《最爱》,还有一部微电影《龙头》,数量不多,但部部经典,展现出深刻的社会价值和丰富的叙事策略。
对其电影的叙事研究,大多集中在单部影片的独立分析,但随着顾长卫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定能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