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
- 格式:pdf
- 大小:264.16 KB
- 文档页数:12

词汇化与语法化一、本文概述《词汇化与语法化》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语言演变中的两个重要现象:词汇化和语法化。
这两个过程在语言的自然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塑造了语言的形态和结构,也影响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和功能。
词汇化指的是语言中的词汇元素如何通过组合和重新分析形成新的词汇项,而语法化则关注语言中的语法元素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包括词类转变、语法结构的变化等。
本文将首先介绍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阐述它们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性。
接着,我们将通过具体的语言实例来展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具体过程,包括词汇项的形成、词义的演变、语法结构的变化等。
我们还将探讨词汇化和语法化对语言理解和语言教学的影响,以及如何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两个概念。
通过本文的阐述和分析,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视角,同时也为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词汇化现象分析词汇化,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指语言中原本独立的词或词组在某些情况下结合成一个新的词汇单位的过程。
这一过程往往涉及到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个层面的变化。
词汇化现象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词汇库,也对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汇化现象的产生通常与语言的使用环境密切相关。
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人们为了表达更为复杂或特定的概念,往往会将一些常用的词组或短语固定下来,形成一个新的词汇单位。
这种固定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语义的泛化或特指化,使得新的词汇单位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或表达更为精确的概念。
词汇化现象在语言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词汇化使得语言更加简洁、高效,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复杂的交流需求。
另一方面,词汇化也促进了语言的创新和发展,为语言带来了新的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
然而,词汇化现象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一方面,词汇化可能导致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增加,使得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变得更加困难。

现代汉语的语法变化与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
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语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本文将探讨现代汉语的语法变化和趋势,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汉语的语序变化在现代汉语中,语序的变化是最显著的。
传统汉语的语序为“主谓宾”,即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
然而,随着外来语的影响和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汉语的语序逐渐变得更加灵活。
例如,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语序是“主谓宾”,另外还有“主宾谓”、“宾主谓”等。
这种灵活的语序使得表达更加丰富多样,能够更好地满足沟通的需求。
二、洪水猛兽式的借词现象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外来词进入汉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也对汉语的语法产生了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借词现象。
洪水猛兽式的借词使得汉语的语法结构发生了变化,如动词化、名词化、形容词化等。
这些借词的引入使得句子结构更灵活,表达更准确。
三、词类的演变在现代汉语中,一些词类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新的词类。
例如,“有点儿”、“真的”等表语副词被广泛使用,它们既可以修饰形容词,也可以修饰动词。
这些新的词类的出现丰富了词语的表达方式,使得汉语的语法更加灵活。
四、语体的多样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语体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书面语和口语之外,现代汉语还出现了新的语体,如网络语言、微信语言等。
这些新的语体在语法上往往更为简洁、直接,更注重表达的效果。
这些语体的出现使得汉语的语法变得更加多样化,适应了不同场景和用途的需求。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的语法变化与趋势主要体现在语序的变化、洪水猛兽式的借词现象、词类的演变以及语体的多样化等方面。
这些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汉语的语法变化将会持续发展,形成新的趋势。
语言是活的,它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而我们需要跟随时代的步伐来适应和理解这些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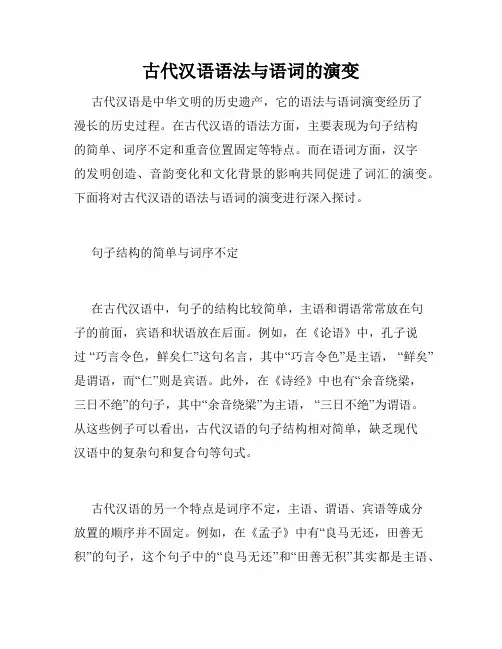
古代汉语语法与语词的演变古代汉语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它的语法与语词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古代汉语的语法方面,主要表现为句子结构的简单、词序不定和重音位置固定等特点。
而在语词方面,汉字的发明创造、音韵变化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共同促进了词汇的演变。
下面将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与语词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
句子结构的简单与词序不定在古代汉语中,句子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语和谓语常常放在句子的前面,宾语和状语放在后面。
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名言,其中“巧言令色”是主语,“鲜矣”是谓语,而“仁”则是宾语。
此外,在《诗经》中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句子,其中“余音绕梁”为主语,“三日不绝”为谓语。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古代汉语的句子结构相对简单,缺乏现代汉语中的复杂句和复合句等句式。
古代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词序不定,主语、谓语、宾语等成分放置的顺序并不固定。
例如,在《孟子》中有“良马无还,田善无积”的句子,这个句子中的“良马无还”和“田善无积”其实都是主语、谓语、宾语结构的简单句,但是它们的词序却是随意的。
因此,古代汉语的句子结构比较灵活,在表达方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重音位置的固定古代汉语中的重音位置比较固定,大多数单音节词的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山”、“水”、“人”等。
但也有例外,例如“我”、“是”等词的重音就在第二个音节上。
此外,古代汉语中还出现了许多双重或多重重音的词汇,例如“华丽”、“互通有无”等,这些词汇的发音演变与历史、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有关,体现了古代汉语的音韵变化和语言发展的多样性。
汉字的发明创造与演变汉字是古代汉语的书写符号,它的发明创造和演变是古代汉语词汇的基础。
据考证,中国的甲骨文可以追溯到商朝晚期,这些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书写形式。
但是,古代汉字的书写形式一直在演变,经过楚、秦、汉、魏晋、唐、宋等历史时期的变革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汉字的书写规范。
古代汉字的演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字的字义演变,二是汉字音韵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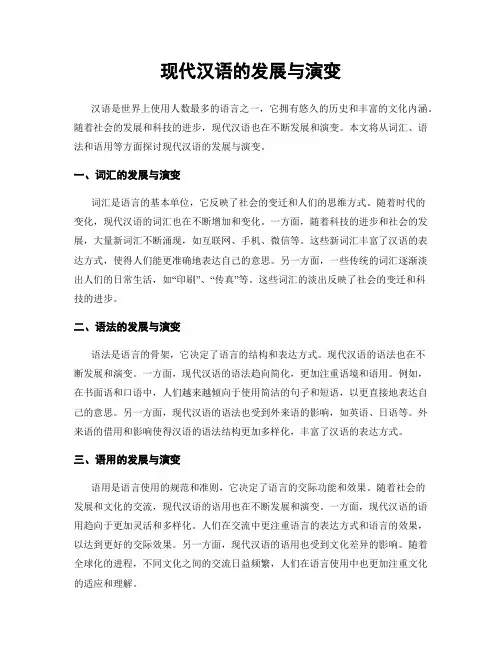
现代汉语的发展与演变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汉语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
本文将从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探讨现代汉语的发展与演变。
一、词汇的发展与演变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它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增加和变化。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量新词汇不断涌现,如互联网、手机、微信等。
这些新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使得人们能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词汇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印刷”、“传真”等。
这些词汇的淡出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
二、语法的发展与演变语法是语言的骨架,它决定了语言的结构和表达方式。
现代汉语的语法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
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语法趋向简化,更加注重语境和语用。
例如,在书面语和口语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简洁的句子和短语,以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语法也受到外来语的影响,如英语、日语等。
外来语的借用和影响使得汉语的语法结构更加多样化,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三、语用的发展与演变语用是语言使用的规范和准则,它决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现代汉语的语用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
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语用趋向于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人们在交流中更注重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的效果,以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
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语用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在语言使用中也更加注重文化的适应和理解。
总结起来,现代汉语的发展与演变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适应的过程。
词汇的增加和变化、语法的简化和多样化、语用的灵活和文化适应,都是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汉语将继续发展和演变,为人们提供更准确、更灵活的交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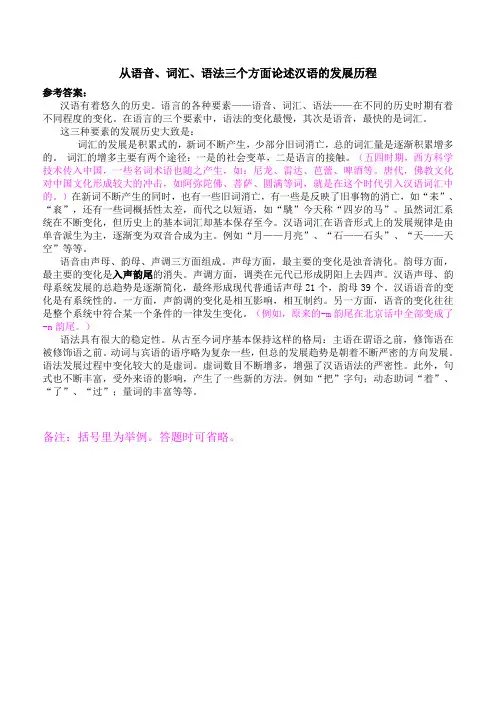
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论述汉语的发展历程参考答案: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
语言的各种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语法的变化最慢,其次是语音,最快的是词汇。
这三种要素的发展历史大致是:词汇的发展是积累式的,新词不断产生,少部分旧词消亡,总的词汇量是逐渐积累增多的。
词汇的增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的社会变革,二是语言的接触。
(五四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名词术语也随之产生,如:尼龙、雷达、芭蕾、啤酒等。
唐代,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形成较大的冲击,如阿弥陀佛、菩萨、圆满等词,就是在这个时代引入汉语词汇中的。
)在新词不断产生的同时,也有一些旧词消亡,有一些是反映了旧事物的消亡,如“耒”、“衮”,还有一些词概括性太差,而代之以短语,如“駣”今天称“四岁的马”。
虽然词汇系统在不断变化,但历史上的基本词汇却基本保存至今。
汉语词汇在语音形式上的发展规律是由单音派生为主,逐渐变为双音合成为主。
例如“月——月亮”、“石——石头”、“天——天空”等等。
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组成。
声母方面,最主要的变化是浊音清化。
韵母方面,最主要的变化是入声韵尾的消失。
声调方面,调类在元代已形成阴阳上去四声。
汉语声母、韵母系统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简化,最终形成现代普通话声母21个,韵母39个。
汉语语音的变化是有系统性的。
一方面,声韵调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另一方面,语音的变化往往是整个系统中符合某一个条件的一律发生变化。
(例如,原来的-m韵尾在北京话中全部变成了-n韵尾。
)语法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从古至今词序基本保持这样的格局:主语在谓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
动词与宾语的语序略为复杂一些,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不断严密的方向发展。
语法发展过程中变化较大的是虚词。
虚词数目不断增多,增强了汉语语法的严密性。
此外,句式也不断丰富,受外来语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方法。
例如“把”字句;动态助词“着”、“了”、“过”;量词的丰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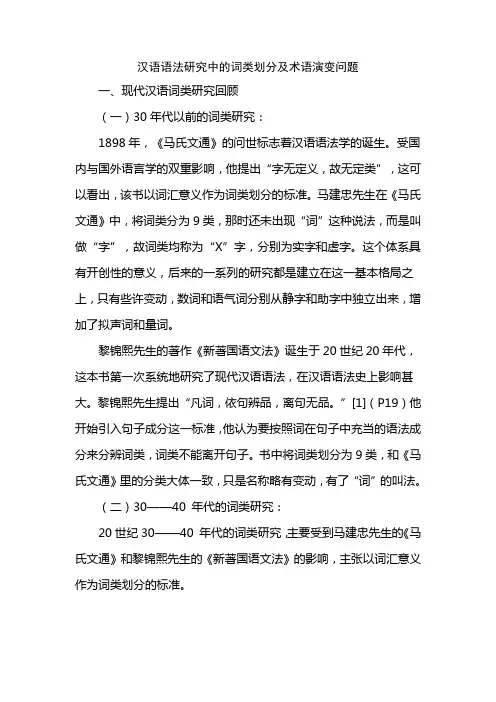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一、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回顾(一)30年代以前的词类研究: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受国内与国外语言学的双重影响,他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这可以看出,该书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中,将词类分为9类,那时还未出现“词”这种说法,而是叫做“字”,故词类均称为“X”字,分别为实字和虚字。
这个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的一系列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格局之上,只有些许变动,数词和语气词分别从静字和助字中独立出来,增加了拟声词和量词。
黎锦熙先生的著作《新著国语文法》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语法,在汉语语法史上影响甚大。
黎锦熙先生提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
”[1](P19)他开始引入句子成分这一标准,他认为要按照词在句子中充当的语法成分来分辨词类,词类不能离开句子。
书中将词类划分为9类,和《马氏文通》里的分类大体一致,只是名称略有变动,有了“词”的叫法。
(二)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20世纪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主要受到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影响,主张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产生于这一时期,书中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在于意义的虚实。
吕叔湘先生按照意义和作用把词归为7类,他认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意义比较实在,归为实义词一类;并指出凡是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一概称为辅助词,属于这一类的有限制词(副词)、指称词(代词)、关系词、语气词;为了便利起见,还添列了一些名称,如方所词、时间词以及日期等等。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既有规律的描述,又有理论的阐述,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语法新体系。
关于词类划分标准,王力先生从意义出发,但虚词的划分考虑到了语法的意义。
他认为“汉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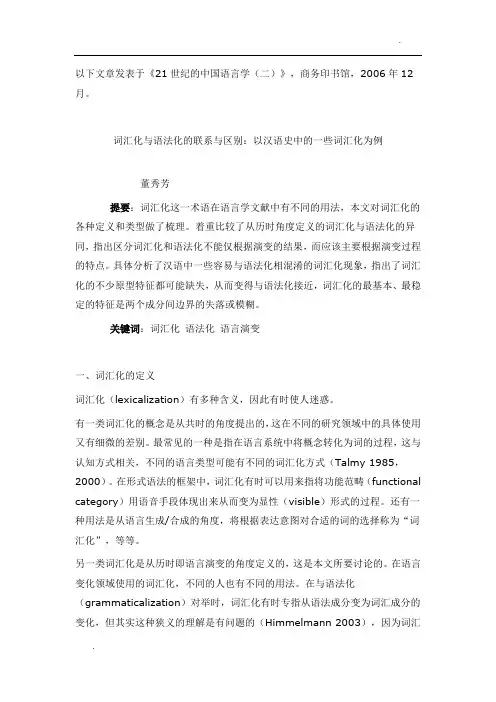
以下文章发表于《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
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以汉语史中的一些词汇化为例董秀芳提要:词汇化这一术语在语言学文献中有不同的用法,本文对词汇化的各种定义和类型做了梳理。
着重比较了从历时角度定义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异同,指出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不能仅根据演变的结果,而应该主要根据演变过程的特点。
具体分析了汉语中一些容易与语法化相混淆的词汇化现象,指出了词汇化的不少原型特征都可能缺失,从而变得与语法化接近,词汇化的最基本、最稳定的特征是两个成分间边界的失落或模糊。
关键词:词汇化语法化语言演变一、词汇化的定义词汇化(lexicalization)有多种含义,因此有时使人迷惑。
有一类词汇化的概念是从共时的角度提出的,这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使用又有细微的差别。
最常见的一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过程,这与认知方式相关,不同的语言类型可能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Talmy 1985,2000)。
在形式语法的框架中,词汇化有时可以用来指将功能范畴(functional category)用语音手段体现出来从而变为显性(visible)形式的过程。
还有一种用法是从语言生成/合成的角度,将根据表达意图对合适的词的选择称为“词汇化”,等等。
另一类词汇化是从历时即语言演变的角度定义的,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在语言变化领域使用的词汇化,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用法。
在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对举时,词汇化有时专指从语法成分变为词汇成分的变化,但其实这种狭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Himmelmann 2003),因为词汇化并不总是与语法化对立(这一点下文将谈到)。
在历时演变领域中定义的词汇化也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即指从非词的单位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是从短语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董秀芳(2002)的研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词汇化的定义。
二、词汇化的类型:文献中提到的历史演变中的词汇化有这样几类:(1)分立的两个词汇成分变为一个词汇成分(univerbation, idiomatization),原来的两个词都有可能还可以独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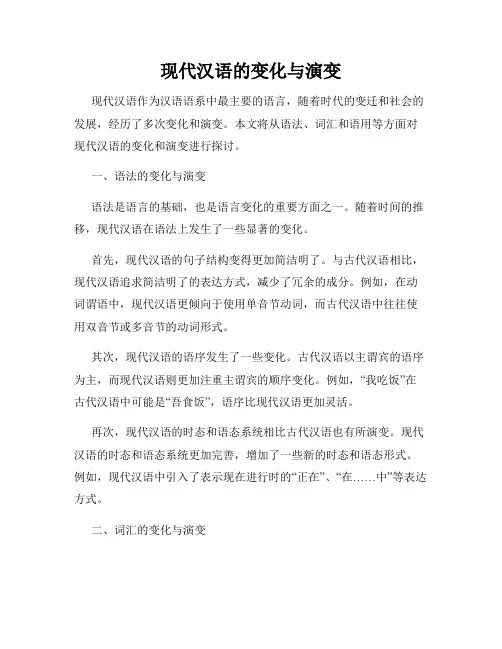
现代汉语的变化与演变现代汉语作为汉语语系中最主要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变化和演变。
本文将从语法、词汇和语用等方面对现代汉语的变化和演变进行探讨。
一、语法的变化与演变语法是语言的基础,也是语言变化的重要方面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现代汉语的句子结构变得更加简洁明了。
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追求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减少了冗余的成分。
例如,在动词谓语中,现代汉语更倾向于使用单音节动词,而古代汉语中往往使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动词形式。
其次,现代汉语的语序发生了一些变化。
古代汉语以主谓宾的语序为主,而现代汉语则更加注重主谓宾的顺序变化。
例如,“我吃饭”在古代汉语中可能是“吾食饭”,语序比现代汉语更加灵活。
再次,现代汉语的时态和语态系统相比古代汉语也有所演变。
现代汉语的时态和语态系统更加完善,增加了一些新的时态和语态形式。
例如,现代汉语中引入了表示现在进行时的“正在”、“在……中”等表达方式。
二、词汇的变化与演变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也是体现语言变化的重要方面之一。
现代汉语的词汇经历了词义扩展、词义变化和新词的生成等过程。
词义扩展是词汇变化的一种常见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一些词汇的词义得到了扩展。
例如,“手机”原本指的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现在也可以指代可以上网、安装应用程序等功能的智能设备。
词义变化是词汇演变的另一种方式。
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些词汇的词义可能会发生变化。
例如,“酷”原本指的是温暖的、寒冷的,后来演变为形容时髦、时尚的意义。
此外,现代汉语也产生了大量新词。
新词的生成涉及到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
例如,“微信”、“支付宝”等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新词,它们代表了新的概念和技术。
三、语用的变化与演变语用是语言实际运用中的一种变化和演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现代汉语的语用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现代汉语中逐渐出现了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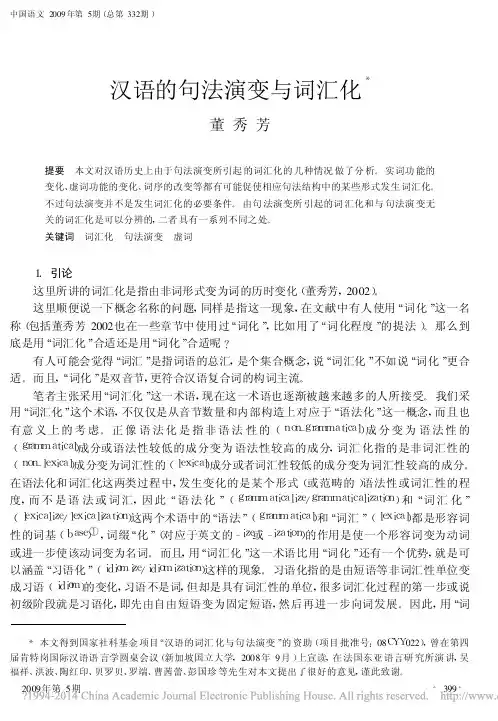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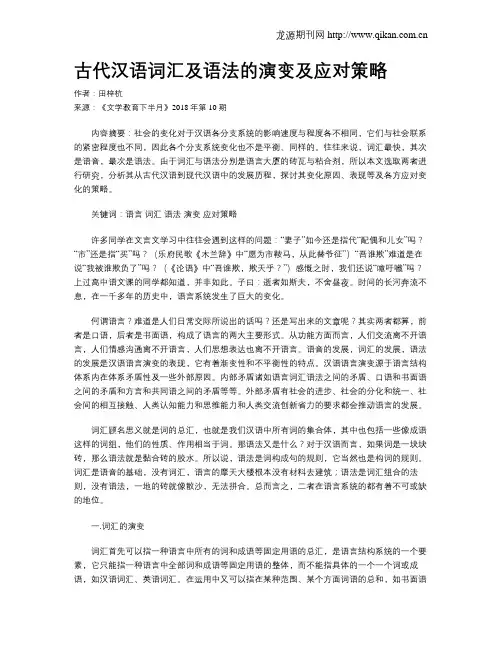
古代汉语词汇及语法的演变及应对策略作者:田梓杭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8年第10期内容摘要:社会的变化对于汉语各分支系统的影响速度与程度各不相同,它们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也不同,因此各个分支系统变化也不是平衡、同样的。
往往来说,词汇最快,其次是语音,最次是语法。
由于词汇与语法分别是语言大厦的砖瓦与粘合剂,所以本文选取两者进行研究,分析其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中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变化原因、表现等及各方应对变化的策略。
关键词:语言词汇语法演变应对策略许多同学在文言文学习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妻子”如今还是指代“配偶和儿女”吗?“市”还是指“买”吗?(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吾谁欺”难道是在说“我被谁欺负了”吗?(《论语》中“吾谁欺,欺天乎?”)感慨之时,我们还说“噫吁嚱”吗?上过高中语文课的同学都知道,并非如此。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语言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何谓语言?难道是人们日常交际所说出的话吗?还是写出来的文章呢?其实两者都算,前者是口语,后者是书面语,构成了语言的两大主要形式。
从功能方面而言,人们交流离不开语言,人们情感沟通离不开语言,人们思想表达也离不开语言。
语音的发展,词汇的发展,语法的发展是汉语语言演变的表现,它有着渐变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汉语语言演变源于语言结构体系内在体系矛盾性及一些外部原因。
内部矛盾诸如语言词汇语法之间的矛盾、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矛盾和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矛盾等等。
外部矛盾有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分化和统一、社会间的相互接触、人类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和人类交流创新省力的要求都会推动语言的发展。
词汇顾名思义就是词的总汇,也就是我们汉语中所有词的集合体,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成语这样的词组,他们的性质、作用相当于词。
那语法又是什么?对于汉语而言,如果词是一块块砖,那么语法就是黏合砖的胶水。
所以说,语法是词构成句的规则,它当然也是构词的规则。
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演变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经历了许多演变和变化。
本文将探讨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演变。
一、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古代汉语是指从汉朝到隋唐时期的汉语形态。
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更注重言辞的典雅和华丽,同时使用的字词也有所不同。
古代汉语中有很多汉字被淘汰或者改变了意义。
例如,古代文献中使用的字词“呦”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
另外,古代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于现代汉语方言的现象,因为古代汉语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
二、外来词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现代汉语中逐渐出现了大量的外来词。
这些外来词来自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例如,“手机”一词就是从英语单词“cell phone”中借用而来。
外来词的引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并且提供了更方便和精确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概念和事物。
三、汉字的简化为了促进汉字的普及和简化书写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汉字的简化改革。
通过减少汉字的笔画和结构复杂度,使得汉字更易于书写和认读。
这一简化改革大大改变了汉字的形态,并且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和使用。
四、网络新词的兴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新词逐渐进入了现代汉语中。
这些网络新词通常由短语、缩写或拼音组成,并且往往涉及到特定的网络文化和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666”被用来表示赞美或称赞,而“爆照”则指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
这些网络新词的兴起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
五、方言的存续尽管现代汉语趋于标准化,但在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方言和口音的差异。
方言在人们日常的生活和交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些方言词汇在现代汉语中依然有影响力,并且在特定的地区或者文化群体中得到广泛使用。
六、语法结构的变化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代汉语中更倾向于使用主谓宾的句子结构,同时也更注重语序的顺序。
同时,现代汉语中的口语化表达和特殊的语法结构也得到了广泛使用,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汉语词汇语法化的情况词汇语法化也就是狭义的语法化它包括两种情形:(l) 实义向虚义的变化;(2) 不太虚向更虚义变化;.1 实义向虚义的变化这类虚化一般是名、动、形三类实词虚化成副词等意义比较虚的词,如刘坚等认为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将”、“着”、“取”、“得”等是由动词演变而来。
“将”、“取”、“得”是由句法位置改变虚化的。
它们大致都经历这样一个语法化过程:连动式→表示动作结果(补语)→表示动作完成、持续(助词)另外,该文中还分析名词“时”到晚唐五代演化为语气词,表“附着”义的动词“着”到六朝乃至唐五代演化为介词,这都属于词汇语法化的第一类。
.2 不太虚向更虚义变化此类虚化如刘坚等认为,反诘副词“敢”是由表“可、能、会”的助动词“敢”虚化而来。
其实,词汇语法化的第二类还应该包括意义具体的词变成意义抽象的同,如一般动词变化为能愿动词。
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原因一、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外因交流的需要是语法化首要的和根本的动力。
交流的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话语中,体现为交流必须满足便于表达和便于交流两个条件。
表达和交流同人类的认知规律息息相关,认知规律对具体的语法化过程及原因有很强的解释性。
(一)交流的需要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思维简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含混、笼统,用名、动、形、数等实词组成的语言可基本满足交流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以及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原先只由实词组成的简单含混的语言开始无法满足交流的需要。
为了表达错综复杂的事物、性质之间的关系,为了表达变幻多端的行为、状态之间的关系,原先的语言系统不得不进行调整、变化,这就从语言外部为语法化提供了动力。
如没有交流的需要,便没有语法化,交流的需要是语法化首要的动力和原因(二)认知的规律认知规律作为语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交流需要密切相关。
交流需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语法化的动力、原因,认知规律是从微观的角度寻求某一类词、某一个词具体的语法化原因。
现代汉语词汇的变迁与演化当我们谈论现代汉语词汇的变迁与演化时,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社会背景、科技发展、文化交流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现代汉语词汇的变迁和演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语言和文化带来的影响。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与词汇变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些变化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外来词汇的引入快速增加,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传统词汇因为社会变迁而逐渐淡化或消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汉语词汇也在不断更新。
比如,互联网的出现给汉语带来了许多新的词汇,如网购、微信、微博等。
这些新词汇不仅满足了人们迅速变化的生活需求,也代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文化交流与词汇演化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
这种文化交流引入了许多外来词汇,例如英语中的loanwords(借词),在汉语中也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外来词汇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然而,文化交流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随着外来词汇的引入,一些汉语传统词汇受到冲击,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保护和传承汉语的经典词汇,同时接纳外来词汇。
第三部分:社会因素与词汇变迁除了历史背景和文化交流外,社会因素也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变迁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新的社会现象和概念不断涌现,这需要创造新的词汇来表达。
例如,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兴概念的出现,催生了一批新词汇。
这些新词汇反映了社会对于新事物的描述和理解。
同时,社会因素也会对汉语词汇的使用产生影响。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会导致一些词汇的使用频率增加或减少。
例如,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词汇逐渐进入日常用语。
总结:现代汉语词汇的变迁与演化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句法结构是语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词汇组合成句子的规则和方式。
词汇化则是将句法结构转化为具体词汇的过程。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句法结构的词汇化。
1.词义和句法结构的融合词义和句法结构是语言中两个重要的维度,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词汇化过程中,词义和句法结构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完整的语句意义。
这种融合方式可以通过词类转换、形态变化、语境调整等方式实现。
2.词序的句法效应词序是决定句法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词汇化过程中,词序的句法效应表现为传达语法信息和语篇连贯的作用。
比如在英语中,主语、谓语和宾语的顺序通常是固定的,而在汉语中则比较灵活。
这种顺序的不同会影响句子的意义和语气。
3.句法结构的缩略句法结构的缩略是指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为了提高交流效率,将较长的句子简化、缩短或压缩成较短的形式。
这种缩略方式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很常见,它可以通过省略某些成分、使用缩写、合并词语等方式实现。
虽然缩略后的句子可能在语法上不够规范,但它仍然能够传达出原句的基本意义。
4.语态和时态的词汇化语态和时态是句法结构中重要的语法范畴。
在词汇化过程中,语态和时态通常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实现。
比如在英语中,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有特殊的形式,而在汉语中则通过添加时间状语或虚词来表示时态。
这些变化不仅使句子具有时间上的参照,还能够表达出动作的状态和语气的变化。
5.句法结构的语义解读句法结构的语义解读是指从词汇化和句法结构中挖掘出句子所表达的深层含义。
这种解读需要结合语境、词义、句法结构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例如,“John likes Mary”这个句子,从句法结构上来看是主语+谓语+宾语的组合,但从语义上理解,它表达了“约翰对玛丽有好感”的意思。
因此,在词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这种深层语义信息融入句子中,使语言表达更加准确和丰富。
6.词类的句法功能词类是语言中词汇的分类,不同类型的词汇在句法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中国语文2009年第5期(总第332期)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3董秀芳提要 本文对汉语历史上由于句法演变所引起的词汇化的几种情况做了分析。
实词功能的变化、虚词功能的变化、词序的改变等都有可能促使相应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形式发生词汇化。
不过句法演变并不是发生词汇化的必要条件。
由句法演变所引起的词汇化和与句法演变无关的词汇化是可以分辨的,二者具有一系列不同之处。
关键词 词汇化句法演变虚词1.引论这里所讲的词汇化是指由非词形式变为词的历时变化(董秀芳,2002)。
这里顺便说一下概念名称的问题,同样是指这一现象,在文献中有人使用“词化”这一名称(包括董秀芳2002也在一些章节中使用过“词化”,比如用了“词化程度”的提法)。
那么到底是用“词汇化”合适还是用“词化”合适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词汇”是指词语的总汇,是个集合概念,说“词汇化”不如说“词化”更合适。
而且,“词化”是双音节,更符合汉语复合词的构词主流。
笔者主张采用“词汇化”这一术语,现在这一术语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采用“词汇化”这个术语,不仅仅是从音节数量和内部构造上对应于“语法化”这一概念,而且也有意义上的考虑。
正像语法化是指非语法性的(non2gra mmatical)成分变为语法性的(gra mmatical)成分或语法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语法性较高的成分,词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的(non2lexical)成分变为词汇性的(lexical)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
在语法化和词汇化这两类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某个形式(或范畴的)语法性或词汇性的程度,而不是语法或词汇,因此“语法化”(gra mmaticalize/gra mmaticalizati on)和“词汇化”(lexicalize/lexicalizati on)这两个术语中的“语法”(gra mmatical)和“词汇”(lexical)都是形容词性的词基(base)①,词缀“化”(对应于英文的2ize或2izati on)的作用是使一个形容词变为动词或进一步使该动词变为名词。
而且,用“词汇化”这一术语比用“词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涵盖“习语化”(idi om ize/idi om izati on)这样的现象。
习语化指的是由短语等非词汇性单位变成习语(idi o m)的变化,习语不是词,但却是具有词汇性的单位,很多词汇化过程的第一步或说初级阶段就是习语化,即先由自由短语变为固定短语,然后再进一步向词发展。
因此,用“词3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的词汇化与句法演变”的资助(项目批准号:08CYY022),曾在第四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2008年9月)上宣读,在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演讲,吴福祥、洪波、陶红印、贝罗贝、罗端、曹茜蕾、彭国珍等先生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此致谢。
汇化”这一术语在指称上更为准确全面。
董秀芳(2002)说明词汇化的源头很多都是具有内部结构关系的句法形式。
本文将证明,从句法形式变为词汇形式,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句法系统在某方面所发生的演变。
句法演变造成某类结构形式不再是合法的句法形式,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词汇化的方式进入了词库。
由句法演变引发的词汇化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下面分别讨论。
2.实词句法功能的变化造成的词汇化当一个实词的句法功能发生改变时,这个实词与某些词的组合就会失去能产性,最终发生词汇化。
以下是两类个案。
2.1动词直接做定语功能的衰落与“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的词汇化董秀芳(2007)考察了动词做定语功能的历时变化。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可以在句法层面直接充当定语(即不借助结构助词直接出现在定语位置)。
根据内部语义关系,动词做定语的结构可以分为三类:“动作+受事”、“动作+施事”、“动作+非论元成分”。
其中,“动作+施事”(如“示威群众”)和“动作+非论元成分”(如“比赛时间”)这两类古今变化不大,都可以在句法层面出现。
略举几例如下:动作+施事:(1)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2)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韩非子・十过》)(3)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
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
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
(《史记・酷吏列传》)②动作+非论元成分:(4)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论语・乡党》)(5)民有饥色。
(《孟子・梁惠王上》)(6)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
(《孟子・公孙丑下》)而“动作+受事”一类则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汉语中“动作+受事”型一般需要出现结构助词,如“喝的水、骑的马、买的酒”,否则就不能出现在句法层面。
古代汉语中“动作+受事”型的动名定中结构如:(7)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诗・魏风・伐檀》)(8)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论语・尧曰》)(9)沽酒市脯不食。
(《论语・乡党》)(10)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
(《孟子・滕文公下》)(11)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
(《孟子・尽心上》(12)平公即位……命归侵田。
(《左传・襄公十六年》)(13)季文子卒。
大夫入敛,公在位。
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
(《左传・襄公五年》)(14)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二年》)(15)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
於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
(《韩非子・八奸》)(16)譬如幻师于旷大处化作二大城,作化人满其中。
(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一)(引自张永言1991)(17)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
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
(《论衡・累害》)(18)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
(《后汉书・戴就传》)(19)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
”(《世说新语・规箴》)(20)(父祖伯叔)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
(《颜氏家训・风操》)(21)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
(《颜氏家训・涉务》)以上例子中由黑体的动词与其后的名词性成分构成的形式是“动词+名词”式的定中短语。
说以上例子中处于定语部分的加黑的词是动词,有以下理由:1)这些词在古汉语中经常可以在句中做谓语,其后带宾语。
2)这些词与名词的定中式搭配不常见,如果是形容词,应该有更多的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用例。
说以上例子中的VN是短语结构而不是词,有以下理由:1)这些动词后的中心语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如例(13)、例(15),说明VN并未构成一个复合词,因为汉语最初的复合词一般都是双音节的。
2)从语义上看,以上各例中的VN也不像词,其意义的组合带有很大的临时性,不是表达一个凝固性的概念。
3)古汉语的“动作+受事”型定中结构虽然比之“动作+施事”、“动作+非论元成分”型为少,但与现代汉语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其使用广泛,出现频率相对较高。
4)具体到每个“动作+受事”的实际用例,大多再现频率不高(如“覆船”),具有偶发性,因此可以看作是句法上的临时组合。
以上例子中的VN,从语义上看可以粗略表示为“被V之N”。
在英语中,构成被动语态的动词的过去分词可以转化为形容词,如br oken、s poken、given、driven、done等。
那么古汉语中定语位置上在语义上支配中心语的动词是否也有可能转为形容词呢?答案是肯定的。
汉语中的一些形容词在上古时只有动词用法。
徐丹(2005)指出,“破”类动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从动词被重新分析为形容词,发生重新分析的语境就是“破+N”,也就是本文说的“破”以动词身份充当定语、中心词为其语义上的受事的环境。
胡敕瑞(2005)也观察到类似现象。
我们认为,如果动词长期处于定语位置,就有可能转化为动形兼类词或纯粹的形容词。
古汉语中“形+名”构成的定中短语一概不加“之”(赵世举,2000),“动作+受事”类型的定中短语中也不加“之”,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更为“动作+受事”型定中短语中的动词向形容词的转化提供了可能。
这种“动作+受事”型的动名定中结构后来在句法层面逐渐消失了,动词丧失了直接进入这种定中结构做定语的能力而必须借助于结构助词“的”③,结果原来的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这类定中组合形式就发生了词汇化,由句法层面转入了词汇层面,如“遗言”、“藏书”等。
在发生词汇化的形式中,动词并没有转化成独立的形容词,否则就可以继续直接出现在定语位置上了。
整个动名组合只是作为过去的句法的遗迹而化石化,在整体上具有凝固性。
以“遗”做定语的结构的变化为例。
“遗”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粘着语素,可以组成“遗言、遗像、遗作、遗体、遗产、遗址、遗物”等,但在古汉语中最初是动词,其中一个意思是“遗留”:(22)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之人,使永监焉。
(《国语・周语下》)(23)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史记・项羽本纪》)“遗”在古汉语中像其他许多动词一样也可用于定语位置,组成“遗德、遗训、遗命、遗则、遗芳、遗风”等定中短语。
当“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在句法层面消失之后,一些“遗”与其所修饰的单音中心名词组成的定中结构就发生了词汇化,作为过去的句法形式的化石而保留在词汇中。
这些形式之所以可以词汇化,除了使用频率高之外,后代文人在书面语创作中的仿古使用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郭锐(2002)指出,现代汉语中31%的动词可以直接做定语,其中45%是名动词,但他没有区分各种语义类型,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动词直接做定语的定中短语大部分都属于“动作+非论元成分”这一语义类型。
这一语义类型也是历时发展中最为稳定的一个类型,从古至今一直使用广泛。
“动作+施事”的类型在现代汉语中使用也比较多,但是出现在定语部分的一般不允许是及物动词,而这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的(董秀芳,2007)。
不带结构助词“的”的“动作+受事”型定中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最为受限,一般情况下不再能够出现在句法层面,只出现于词汇层面④。
从古到今,无标记的“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由句法转入词汇系统,但是并不是完全丧失了能产性,一些新词可以比照这种模式造出来。
比如“爱”可以充当修饰性语素出现在定中式复合词中(爱车、爱女、爱妻、爱将、爱生、爱犬)。
但当“爱”充当定中复合词中的定语时,使用时在韵律上要受到限制,不能修饰双音节或双音节以上的名词,如可以说“爱生”,但不能说“爱学生”(表示“所喜爱的学生”)(董秀芳,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