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_高三作文
- 格式:docx
- 大小:38.21 KB
- 文档页数: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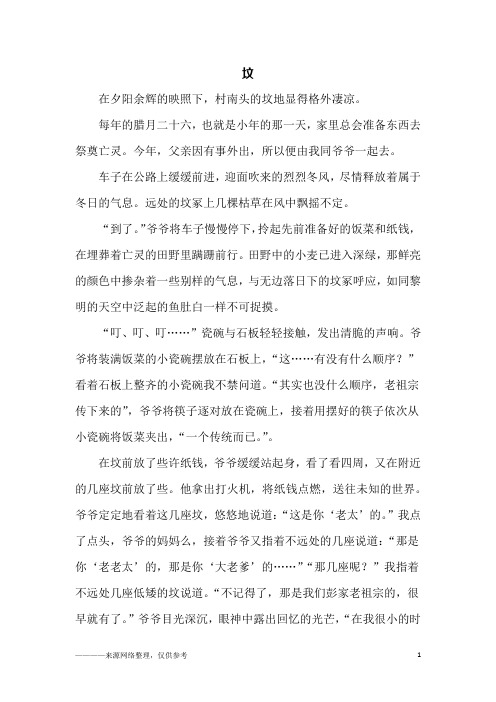
坟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村南头的坟地显得格外凄凉。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也就是小年的那一天,家里总会准备东西去祭奠亡灵。
今年,父亲因有事外出,所以便由我同爷爷一起去。
车子在公路上缓缓前进,迎面吹来的烈烈冬风,尽情释放着属于冬日的气息。
远处的坟冢上几棵枯草在风中飘摇不定。
“到了。
”爷爷将车子慢慢停下,拎起先前准备好的饭菜和纸钱,在埋葬着亡灵的田野里蹒跚前行。
田野中的小麦已进入深绿,那鲜亮的颜色中掺杂着一些别样的气息,与无边落日下的坟冢呼应,如同黎明的天空中泛起的鱼肚白一样不可捉摸。
“叮、叮、叮……”瓷碗与石板轻轻接触,发出清脆的声响。
爷爷将装满饭菜的小瓷碗摆放在石板上,“这……有没有什么顺序?”看着石板上整齐的小瓷碗我不禁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顺序,老祖宗传下来的”,爷爷将筷子逐对放在瓷碗上,接着用摆好的筷子依次从小瓷碗将饭菜夹出,“一个传统而已。
”。
在坟前放了些许纸钱,爷爷缓缓站起身,看了看四周,又在附近的几座坟前放了些。
他拿出打火机,将纸钱点燃,送往未知的世界。
爷爷定定地看着这几座坟,悠悠地说道:“这是你‘老太’的。
”我点了点头,爷爷的妈妈么,接着爷爷又指着不远处的几座说道:“那是你‘老老太’的,那是你‘大老爹’的……”“那几座呢?”我指着不远处几座低矮的坟说道。
“不记得了,那是我们彭家老祖宗的,很早就有了。
”爷爷目光深沉,眼神中露出回忆的光芒,“在我很小的时————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 1候他们就这么矮了。
”风卷起纸钱燃烧后的纸灰,将它们送往另一个世界,送到我们祭奠的人的手中,倾诉着这个世界的思念。
我看着这些坟,想起了王羲之,想起了他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而妄作”,想起了他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没有人可以从死神的手中逃脱,我们终将躺入那座窄窄的,阴暗潮湿的坟。
或许我们的后人也会牵起他们后辈的手,指着我们,又或许我们化作那些矮矮的坟,躺过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生命总会经历生老病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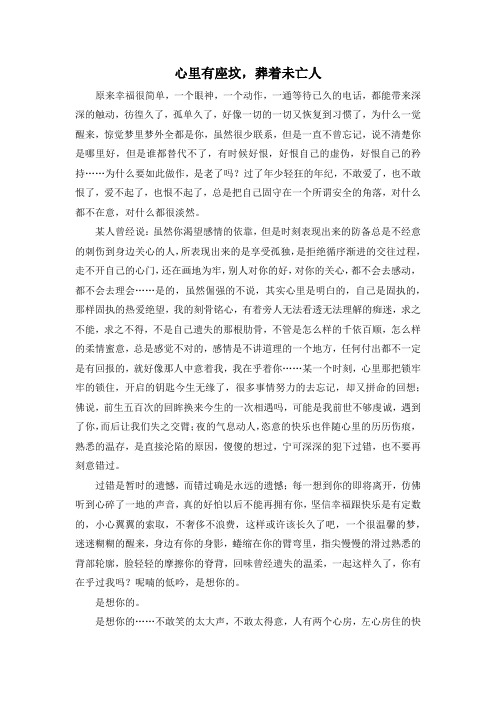
心里有座坟,葬着未亡人原来幸福很简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通等待已久的电话,都能带来深深的触动,彷徨久了,孤单久了,好像一切的一切又恢复到习惯了,为什么一觉醒来,惊觉梦里梦外全都是你,虽然很少联系,但是一直不曾忘记,说不清楚你是哪里好,但是谁都替代不了,有时候好恨,好恨自己的虚伪,好恨自己的矜持……为什么要如此做作,是老了吗?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不敢爱了,也不敢恨了,爱不起了,也恨不起了,总是把自己固守在一个所谓安全的角落,对什么都不在意,对什么都很淡然。
某人曾经说:虽然你渴望感情的依靠,但是时刻表现出来的防备总是不经意的刺伤到身边关心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享受孤独,是拒绝循序渐进的交往过程,走不开自己的心门,还在画地为牢,别人对你的好,对你的关心,都不会去感动,都不会去理会……是的,虽然倔强的不说,其实心里是明白的,自己是固执的,那样固执的热爱绝望,我的刻骨铭心,有着旁人无法看透无法理解的痴迷,求之不能,求之不得,不是自己遗失的那根肋骨,不管是怎么样的千依百顺,怎么样的柔情蜜意,总是感觉不对的,感情是不讲道理的一个地方,任何付出都不一定是有回报的,就好像那人中意着我,我在乎着你……某一个时刻,心里那把锁牢牢的锁住,开启的钥匙今生无缘了,很多事情努力的去忘记,却又拼命的回想;佛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吗,可能是我前世不够虔诚,遇到了你,而后让我们失之交臂;夜的气息动人,恣意的快乐也伴随心里的历历伤痕,熟悉的温存,是直接沦陷的原因,傻傻的想过,宁可深深的犯下过错,也不要再刻意错过。
过错是暂时的遗憾,而错过确是永远的遗憾;每一想到你的即将离开,仿佛听到心碎了一地的声音,真的好怕以后不能再拥有你,坚信幸福跟快乐是有定数的,小心翼翼的索取,不奢侈不浪费,这样或许该长久了吧,一个很温馨的梦,迷迷糊糊的醒来,身边有你的身影,蜷缩在你的臂弯里,指尖慢慢的滑过熟悉的背部轮廓,脸轻轻的摩擦你的脊背,回味曾经遗失的温柔,一起这样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呢喃的低吟,是想你的。

长满杂草的坟描写作文在我老家村子的后头,有一片荒地,荒地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坟茔。
其中有一座坟,特别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它的高大雄伟,而是因为那上面长满了杂草,杂乱无章,肆意生长,仿佛在诉说着一些被遗忘的故事。
这座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存在了,那时候,我总是对它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每次路过那片荒地,我都会忍不住远远地看上一眼,然后加快脚步跑开。
记忆中,那坟上的杂草总是绿油油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思想。
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大人们都躲在家里避暑,而我们这群小孩子却闲不住,总想着到处去探险。
不知是谁提议,说要去那片荒地看看,大家一开始都有些害怕,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是壮着胆子一起去了。
当我们靠近那座长满杂草的坟时,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杂草长得很高,几乎把整个坟头都覆盖住了,有的甚至垂到了地上。
草丛中,还能看到一些不知名的野花,五颜六色的,在这片荒凉的地方显得格外扎眼。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那些杂草。
有细长的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用手轻轻一摸,痒痒的;还有一些叶片宽大的野草,上面布满了细小的锯齿,不小心碰到,会在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
在杂草的缝隙里,我发现了一只小蚂蚱,它正蹦跶着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正当我看得入神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原来是一个小伙伴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小土坑,摔倒在地,吓得脸色苍白。
大家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去扶他,有的则吓得转身就跑。
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了,跟着大家一起跑回了村子。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靠近那座坟。
但它却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那些杂草、野花和小蚂蚱,仿佛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谜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座长满杂草的坟不再那么恐惧,反而多了一些感慨。
我常常想,这座坟里埋着的是谁呢?他(她)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这座坟会如此荒凉,无人打理?也许是逝者的后人已经搬离了村子,也许是时间的流逝让人们渐渐遗忘了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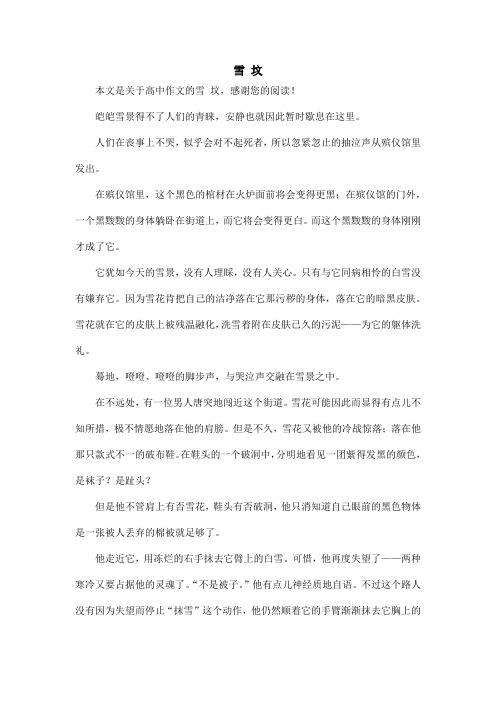
雪坟本文是关于高中作文的雪坟,感谢您的阅读!皑皑雪景得不了人们的青睐,安静也就因此暂时歇息在这里。
人们在丧事上不哭,似乎会对不起死者,所以忽紧忽止的抽泣声从殡仪馆里发出。
在殡仪馆里,这个黑色的棺材在火炉面前将会变得更黑;在殡仪馆的门外,一个黑黢黢的身体躺卧在街道上,而它将会变得更白。
而这个黑黢黢的身体刚刚才成了它。
它犹如今天的雪景,没有人理睬,没有人关心。
只有与它同病相怜的白雪没有嫌弃它。
因为雪花肯把自己的洁净落在它那污秽的身体,落在它的暗黑皮肤。
雪花就在它的皮肤上被残温融化,洗雪着附在皮肤已久的污泥——为它的躯体洗礼。
蓦地,噔噔、噔噔的脚步声,与哭泣声交融在雪景之中。
在不远处,有一位男人唐突地闯近这个街道。
雪花可能因此而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极不情愿地落在他的肩膀。
但是不久,雪花又被他的冷战惊落;落在他那只款式不一的破布鞋。
在鞋头的一个破洞中,分明地看见一团紫得发黑的颜色,是袜子?是趾头?但是他不管肩上有否雪花,鞋头有否破洞,他只消知道自己眼前的黑色物体是一张被人丢弃的棉被就足够了。
他走近它,用冻烂的右手抹去它臂上的白雪。
可惜,他再度失望了——两种寒冷又要占据他的灵魂了。
“不是被子。
”他有点儿神经质地自语。
不过这个路人没有因为失望而停止“抹雪”这个动作,他仍然顺着它的手臂渐渐抹去它胸上的雪,腹上的雪……此刻,白雪觊觎淹没它的一切的企图被暂时打破了。
白雪的企图被路人打破至它的脖子时,路人的手突然抖动,甚至比打冷战时还要抖得猛烈。
他不敢继续往它的脖子抹雪,好象生怕这样做会亵渎了什么似的,或者他不想看到不久将来的自己。
毕竟,他现在还不是死者,既然还不是死者就有存活在世上的权利,为了争取这种权利,路人必须抢走死者身上的唯一一件单薄衬衫来维持这种权利。
当死者的衣服将要更换主人时,两个纸片突然从衬衫的胸袋中掉出。
那个路人急遽地穿上稍有余温的衣服后,才捡起那两个纸片儿。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张伍圆纸币。
他端详着照片:左边的男人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黑得像一块被烧伤的木头,唯一雪白的就只有勉强列在照相机前的牙齿;疲惫的眼皮半盖着无神的眼珠,眼神似乎并没有落在照相机的镜头上,仿佛望着远处无尽的路;两颊凹陷到颧骨之下,显得颧骨格外的突出;可能因为他身材瘦弱的缘故,乍眼看下去显得他的个儿比一般人高,同时又显得他可能承受过多年的饥饿,像一个饿汉。

今天去上坟写一篇作文
今天一大早就被老妈从被窝里薅起来,说要去上坟。
我心里那个不情愿啊,这大周末的,我还想多睡会儿呢。
但是没办法,祖宗最大嘛,只好迷迷糊糊地跟着家人出发了。
到了墓地,那场景,一排排的墓碑,看着还有点阴森森的。
我心里直犯嘀咕:“老祖宗们,可别来找我麻烦啊。
”
大人们忙着摆祭品,什么水果、点心、酒,摆了满满一地。
我在旁边站着,也不知道能干点啥,就瞅着那些祭品心想:“老祖宗们能吃得着不?”
开始烧纸的时候,那火苗呼呼地往上窜,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生怕被
烫着。
我爸还在那念叨着:“祖宗保佑,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
我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也保佑我考试别挂科。
”
烧完纸磕完头,总算是完事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妈说:“这上坟啊,就
是让咱们别忘了根,记住先辈。
”我点点头,虽然一开始不太情愿来,但想想
这也是咱中国人的传统,是对先人的一种怀念和敬意。
今天这上坟之旅,虽然有点小累,但是也让我对家族的传承有了那么一点
点的感触。
希望老祖宗们真能保佑咱们一家子都好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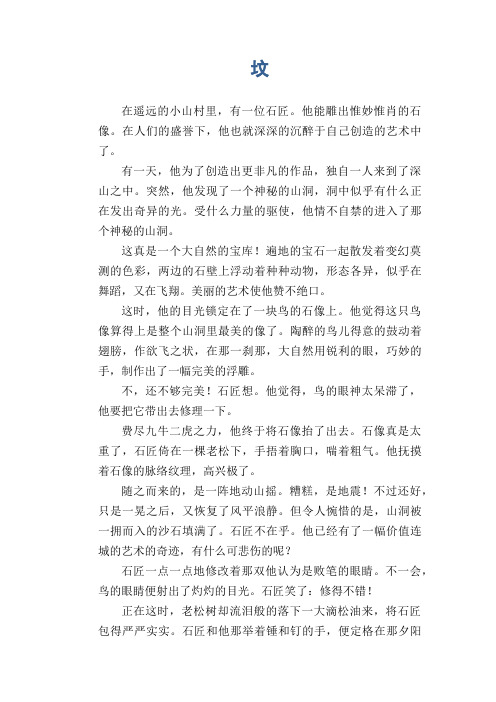
坟在遥远的小山村里,有一位石匠。
他能雕出惟妙惟肖的石像。
在人们的盛誉下,他也就深深的沉醉于自己创造的艺术中了。
有一天,他为了创造出更非凡的作品,独自一人来到了深山之中。
突然,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洞中似乎有什么正在发出奇异的光。
受什么力量的驱使,他情不自禁的进入了那个神秘的山洞。
这真是一个大自然的宝库!遍地的宝石一起散发着变幻莫测的色彩,两边的石壁上浮动着种种动物,形态各异,似乎在舞蹈,又在飞翔。
美丽的艺术使他赞不绝口。
这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一块鸟的石像上。
他觉得这只鸟像算得上是整个山洞里最美的像了。
陶醉的鸟儿得意的鼓动着翅膀,作欲飞之状,在那一刹那,大自然用锐利的眼,巧妙的手,制作出了一幅完美的浮雕。
不,还不够完美!石匠想。
他觉得,鸟的眼神太呆滞了,他要把它带出去修理一下。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将石像抬了出去。
石像真是太重了,石匠倚在一棵老松下,手捂着胸口,喘着粗气。
他抚摸着石像的脉络纹理,高兴极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地动山摇。
糟糕,是地震!不过还好,只是一晃之后,又恢复了风平浪静。
但令人惋惜的是,山洞被一拥而入的沙石填满了。
石匠不在乎。
他已经有了一幅价值连城的艺术的奇迹,有什么可悲伤的呢?石匠一点一点地修改着那双他认为是败笔的眼睛。
不一会,鸟的眼睛便射出了灼灼的目光。
石匠笑了:修得不错!正在这时,老松树却流泪般的落下一大滴松油来,将石匠包得严严实实。
石匠和他那举着锤和钉的手,便定格在那夕阳的映照下了。
数千年后。
一对父子。
博物馆。
儿子吃惊的大叫了一声:“爸爸,快看!”众人被他的喊声吸引住了,顺着他的指向看去,有一块琥珀。
围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欣赏着它,纷纷发出赞叹的声音:“真壮观啊!”一位考古学家叹息着:“这琥珀的一切都那么完美,只是因为鸟像的眼睛而毁坏了全局……”可怜的石匠。
可怜的人类。
今天,在博物馆里,有一块巨大的琥珀,它美丽极了,它的名字叫做“坟”。
人类的坟……。
坟春去春来年复年,潮起潮落涨又退。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自然得回老家上坟,可看着那一座座青草萎萋的坟墓,和去年坟墓前上坟的人留下的纸灰,发了霉的糕点,干瘪了的苹果……泡在血一样的夕阳里,山丘间此起彼伏不时响起清亮的鞭炮声,风吹过,一阵阵压抑或放肆的哭声就在空洞的山间回荡,好生凄凉!那声声呼唤,好似生者在期待着着亲人能再入梦中相见,可从此上穷碧落,下落黄泉,生死两茫茫!便忍不住的有了几分感慨。
死——这命运的归宿,万物都避免不了,谁不会有这死亡的宿命呢?不论你生前或伟大或平凡,却终会有一死。
死后便躺在这坟里,有时是豪华的墓园,有时是小小的土丘。
可不管如何,尸体终是在里面逐渐腐烂,留下残骨,证明曾在世间来过,短短地逗留过便又走了。
可如今故去的亲人成了一堆黄土,健在的亲人却成了一棵朽木,不知怀念,不知孝敬,渐渐遗忘。
回过神来,坟依旧静静的立在面前,见证着我究竟是死是活。
初二:张威欲清明,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笑还颦,最断人肠。
——题记秋叶凋零,缓慢的从树上落下。
忍不尽的秋意盎然,散发着秋天的味道。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便仅仅只有腐烂的命运,随之消散,迷茫在这命运的轮回中。
于是怎会有人愿意永生永世困在这小小的土丘中,被人遗忘,沦落地狱,干一杯孟婆汤,忘却一切。
于是总得拼尽一切的活下去,可是该怎样才能挣脱这粘湿的空气;该怎样才能让回忆没有悲伤;该怎样才能让自己足够坚强,足够成功。
想想只得竭尽全力。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想想这次月考,我无疑是顺流而下的,不经惶恐,生怕就此漂入那座小小的土丘,于是想做条活鱼,可能强大,可能弱小但终会拼尽一切逆流而上的活鱼。
细雨如歌,滋润春风细细,望极春愁。
潇潇春雨,一番洗大地。
清明,这意义非凡的日子,虽是无断肠之雨,却永留心中!。
坟作文1000字坟在去年,我参加了一项社区志愿活动,帮助清理一处荒废多年的山坟。
当时我在那里工作了一整天,太阳热得让人难受,但是我的工作伴侣却是一位神秘的老人,他一个人默默地清理着,有时还会蹲下来仔细地看看每个墓碑。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们的祖先付出了那么多,我感到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墓地。
”这个经历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坟的意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坟是一种仪式,向已故亲友表达敬意、缅怀他们,但是坟也是一种历史记录,它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录了许多旧的故事。
当我们站在坟头,看着那些古老的墓碑时,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还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纹理。
在我看来,坟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坟是家族历史的记录。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因为时间而逐渐被遗忘,但是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我们的家族历史。
通过坟,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居住地、职业、婚姻史、成就等等,这些记录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祖先,也能够让我们了解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方式。
其次,坟是家族情感的表达。
家族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的联系被视为最重要的情感纽带。
坟提供了一个表达敬意、追忆逝者的场所,它让我们维系自己和亲人之间的联系和情感。
第三,坟是社会文化的凝聚。
墓地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切片,一个地区的坟可以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色。
在我所在的社区,坟通常是家族一起维护;在一些其他地方,坟可能具有更多的雕刻装饰,显现出当地文化的特点。
坟还有其他的意义,例如它们可以有助于生态平衡、防止土地沙漠化。
当我们看待坟时,我们经常会说谁被埋葬在坟里。
但其实坟本身也有其价值。
它们代表过去的态度和文化,也是我们为后代准备的一份礼物。
通过坟,我们可以把家族的历史、价值和传统代代相传。
这也是我们应该尊重这些建筑和场所的原因。
假如我被埋葬在坟里,我会希望我的家庭、朋友和社区的人们会继续维护我的坟,让它成为我们家族的历史记录、家族情感的表达,以及社会文化的凝聚。
【高二作文】坟枯草丛生。
我,回来了。
从酷暑炎到秋意浓,从飞雪天到花开日,恍惚半载光阴乍已远逝,他却依旧安静地在那座小土包里沉默,只有坟上青青似是欢迎。
毫不在意地扯去那些据说留不得的杂草,就这样沉默地对着面前齐身高的黄土——好似他的肤色。
从前我是断断不敢与他直视的,他身上的气势太强,强到我怕他,却也以为他的肩膀是天底下最坚强的地方,就算前路再多风再多雨他也会替我挡着,于是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庇护下一路阳光。
直到有一天他倒下了,直到有一天那些他曾为我挡住的风刀霜剑不留情面的朝我砸来,直到有一天我明白,那些风雨,那么冰冷。
我才知道天底下没有谁是坚不可摧的,我才知道他为我挡了多少风雨,我才知道他曾经有多疼。
可现在,不过是一座坟罢了。
罢了。
黄土被雨水冲得有些黏重,窒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知他还有什么想对我说,只可惜没来得及。
他的妻在坟前酹一樽酒,又默默地去理坟。
我也只默默地瞧着。
我是见证着他们十多年的光阴长大的,之前的岁月也许是我妈去见证的。
我记忆里的他,从来都是不苟言笑的,那周身的气势,端的像军官一般,一点不似他温婉的妻。
然而孩提时代的我似乎更中意这位铁面无情的“军官”,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里大多是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刀刻般深邃。
他却尤其喜欢小孩子,像个大小孩一样。
我能清楚地记起他手里攥着棒棒糖逗孩子们跳兔子舞,也能清楚地记起他用摩托给我当跷跷板玩得比我开心,还能清楚地记起他遍寻我不见时的焦急和我回家后无奈的轻斥。
家里的教育向来严格,饶是他温柔的妻也打过我不少次。
而他从未打过我,这和他向来铁血的性格颇为不符,可是,他真的从未打过我,至死不曾。
雨后空气似乎是清新的,他如愿葬在这绿荫环抱的地方。
林子里的鸟时不时的划过天际,在羽翼般的白云身边留下轻巧的无痕。
映着温暖的阳光,我看见坟上的光影掠过,尚未被拔掉的野草被风吹得颤巍巍的,好似这尘世只它孤苦无依。
其实哪只是它啊。
感谢您的阅读,希望文章能帮助到您。
恍惚间我想起他病重时眼睛里浑浊而朦胧的光。
坟照例是上坟,从我记事起,每年的大年初一是一定要走这么一遭的。
妈妈说,你外婆,就在下面。
那是老家的后山包上,有着南方姑娘的纤柔苍翠欲滴的嫩竹此时已爬满了山坡。
和着清风流水,微微扬起婀娜的裙摆。
那长长的从一端渐渐向两边延伸变得丰满最尾又回到细尖的不知名的叶片,疯长在坟前。
外公一个人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劳作了一上午,把它们连根的堆向两侧,“那不好。
”他说。
老家的大门用棕红的油漆涂了厚厚一层,妈妈有些若失的望着,仿佛又觉得什么不对了。
老家,我何曾在这儿住过一天?这是我当年逃到这儿,你外婆就打不到的高台,这是我和你幺舅最爱的厨房,你外婆经常偷着给我们煮开水蛋,这是你外婆和祖母站在那儿等你外公回来的院子。
妈妈紧紧拽着我,兴高采烈的指指点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来。
我望着妈妈,脸上跳跃着欢快的光,眉眼都成了一条线,两鬓突出的银丝在昏暗的房间中竟毫无察觉,恍惚间,我觉得妈妈回到了20岁之前的样子,那个还偎依在外婆膝下,在祖母身旁蹦蹦跳跳的那个瘦瘦小小的,那个在院子那棵600多年的银杏树下看书的她。
客厅正中间,是我外婆的遗照。
我从未细细端详过。
远远勾勒出她的轮廓,一顶似乎绒线织的小帽儿,稍稍向两侧翘起的头发。
嘴也许是抿着,眼神在我看来是空洞的。
脸上的肌肉没有收缩亦没有拉伸一下,那种神情,说不上是快乐,但更无需悲哀。
三姨推了推我妈,“看,妈走得好安详。
”妈妈动了动嘴,没有说什么,四姨接过“对啊”,然后和三姨相视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
妈跪下了,在外婆的坟前。
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妈,我们来看你了。
”压低了声音,轻轻的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念着,我没听懂。
拿起一张纸币,面值是一个8后面10个0,印着天地银行。
大火一触碰到就张牙舞爪的吞噬,从四周到中间,彩色一点一点的褪去,一缕长长的青烟缓缓上升,仅使留下一层土灰。
风起了,扬起的星星点点飘悬在空气中,像一个一个跃动着的精灵。
妈妈说,那是你外婆高兴啊。
浮起的稚气,与雷厉风行,坚强泼辣的她判若两人。
我记得那个深秋的午夜,我和妈游走在姨妈楼下的公园。
坐在冰冷的石凳上,两个人毫无主题的慢聊。
我边哈着热气,边跺着脚。
妈妈把手放在大腿上,用手撑着头。
没有月亮,深黑色的天空将一切都消融在其中。
远处的灯光倾斜下来,柔软得像剔透缓慢的流水。
“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不是我没考起学校——我尽力了,我无话可说。
最遗憾的是,我妈,活着一天,不曾享受过什么。
我们苦,她跟着我们一起苦。
好不容易,日子看着好起来了,她,却不在了。
”说到后面,轻得只听到了气声。
我抬头,正好望见她抹眼泪,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姨妈姨父们总说,老六每年过节,给妈带的最多。
这话不假,我是亲眼看见爸妈用摩托车载着两个胀鼓鼓的长编织袋上坟的。
我妈总是笑笑,最多也不过答应声“是啊”。
爸爸总也站在旁边,抿抿嘴,望着她。
我一直想,妈妈与爸爸结婚的这二十年来是怎么过的?她有没有真的后悔过。
爸爸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踏着大山的厚实,汲取了那篇黑土地给他的营养,有着山里人的勤劳,节俭,忠厚和朴实。
但也经常是话不多,甚至偶尔一两句格外刺耳。
妈说,这二十几年里,没说过一句夫妻的甜言蜜语。
这是学文科,有着天生浪漫主义气质的妈妈所不能忍受的。
我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黑白照片上的她,带有一点青涩,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风韵的嘴唇,现在即便是老了,但深深浅浅的皱纹也衬托出干练的气质,稍稍打扮一下,就像个贵妇人。
而又煮得一手好菜,操家理事样样不落下。
这样的爸妈,难道是般配的吗?婆婆和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婆婆喜欢小儿,对我爸爱理不理,面对早产又体弱多病的我,毫无经验的妈焦坏了,一激动竟就地给爸跪下,一把泪求婆婆帮忙带着。
山里人的冷漠最终没能让婆婆答应。
我妈心一横,咬紧牙关,硬是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儿,硬是要把我养大。
直到今天,都还有人说,你能活下来长大,真不容易啊。
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教我读书认字了。
有时她还会翻开陈年旧事簿,得意洋洋地对相熟十几年的老邻居说:“我们思思3岁就会从1数到100了。
”那片笑意绽放在脸上,久久不肯消散。
但其实我妈并没有对我的学习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即便现在上了高中,她也仅仅是轻描淡写一句“尽力就好”。
印象中妈妈极少体罚我。
只是偶尔她看到我的房间杂乱无章,偏着头,无不焦虑的说:“怎么又这样了嘛!”我总会照例是上坟,从我记事起,每年的大年初一是一定要走这么一遭的。
妈妈说,你外婆,就在下面。
那是老家的后山包上,有着南方姑娘的纤柔苍翠欲滴的嫩竹此时已爬满了山坡。
和着清风流水,微微扬起婀娜的裙摆。
那长长的从一端渐渐向两边延伸变得丰满最尾又回到细尖的不知名的叶片,疯长在坟前。
外公一个人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劳作了一上午,把它们连根的堆向两侧,“那不好。
”他说。
老家的大门用棕红的油漆涂了厚厚一层,妈妈有些若失的望着,仿佛又觉得什么不对了。
老家,我何曾在这儿住过一天?这是我当年逃到这儿,你外婆就打不到的高台,这是我和你幺舅最爱的厨房,你外婆经常偷着给我们煮开水蛋,这是你外婆和祖母站在那儿等你外公回来的院子。
妈妈紧紧拽着我,兴高采烈的指指点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来。
我望着妈妈,脸上跳跃着欢快的光,眉眼都成了一条线,两鬓突出的银丝在昏暗的房间中竟毫无察觉,恍惚间,我觉得妈妈回到了20岁之前的样子,那个还偎依在外婆膝下,在祖母身旁蹦蹦跳跳的那个瘦瘦小小的,那个在院子那棵600多年的银杏树下看书的她。
客厅正中间,是我外婆的遗照。
我从未细细端详过。
远远勾勒出她的轮廓,一顶似乎绒线织的小帽儿,稍稍向两侧翘起的头发。
嘴也许是抿着,眼神在我看来是空洞的。
脸上的肌肉没有收缩亦没有拉伸一下,那种神情,说不上是快乐,但更无需悲哀。
三姨推了推我妈,“看,妈走得好安详。
”妈妈动了动嘴,没有说什么,四姨接过“对啊”,然后和三姨相视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
妈跪下了,在外婆的坟前。
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妈,我们来看你了。
”压低了声音,轻轻的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念着,我没听懂。
拿起一张纸币,面值是一个8后面10个0,印着天地银行。
大火一触碰到就张牙舞爪的吞噬,从四周到中间,彩色一点一点的褪去,一缕长长的青烟缓缓上升,仅使留下一层土灰。
风起了,扬起的星星点点飘悬在空气中,像一个一个跃动着的精灵。
妈妈说,那是你外婆高兴啊。
浮起的稚气,与雷厉风行,坚强泼辣的她判若两人。
我记得那个深秋的午夜,我和妈游走在姨妈楼下的公园。
坐在冰冷的石凳上,两个人毫无主题的慢聊。
我边哈着热气,边跺着脚。
妈妈把手放在大腿上,用手撑着头。
没有月亮,深黑色的天空将一切都消融在其中。
远处的灯光倾斜下来,柔软得像剔透缓慢的流水。
“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不是我没考起学校——我尽力了,我无话可说。
最遗憾的是,我妈,活着一天,不曾享受过什么。
我们苦,她跟着我们一起苦。
好不容易,日子看着好起来了,她,却不在了。
”说到后面,轻得只听到了气声。
我抬头,正好望见她抹眼泪,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姨妈姨父们总说,老六每年过节,给妈带的最多。
这话不假,我是亲眼看见爸妈用摩托车载着两个胀鼓鼓的长编织袋上坟的。
我妈总是笑笑,最多也不过答应声“是啊”。
爸爸总也站在旁边,抿抿嘴,望着她。
我一直想,妈妈与爸爸结婚的这二十年来是怎么过的?她有没有真的后悔过。
爸爸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踏着大山的厚实,汲取了那篇黑土地给他的营养,有着山里人的勤劳,节俭,忠厚和朴实。
但也经常是话不多,甚至偶尔一两句格外刺耳。
妈说,这二十几年里,没说过一句夫妻的甜言蜜语。
这是学文科,有着天生浪漫主义气质的妈妈所不能忍受的。
我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黑白照片上的她,带有一点青涩,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风韵的嘴唇,现在即便是老了,但深深浅浅的皱纹也衬托出干练的气质,稍稍打扮一下,就像个贵妇人。
而又煮得一手好菜,操家理事样样不落下。
这样的爸妈,难道是般配的吗?婆婆和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婆婆喜欢小儿,对我爸爱理不理,面对早产又体弱多病的我,毫无经验的妈焦坏了,一激动竟就地给爸跪下,一把泪求婆婆帮忙带着。
山里人的冷漠最终没能让婆婆答应。
我妈心一横,咬紧牙关,硬是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儿,硬是要把我养大。
直到今天,都还有人说,你能活下来长大,真不容易啊。
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教我读书认字了。
有时她还会翻开陈年旧事簿,得意洋洋地对相熟十几年的老邻居说:“我们思思3岁就会从1数到100了。
”那片笑意绽放在脸上,久久不肯消散。
但其实我妈并没有对我的学习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即便现在上了高中,她也仅仅是轻描淡写一句“尽力就好”。
印象中妈妈极少体罚我。
只是偶尔她看到我的房间杂乱无章,偏着头,无不焦虑的说:“怎么又这样了嘛!”我总会照例是上坟,从我记事起,每年的大年初一是一定要走这么一遭的。
妈妈说,你外婆,就在下面。
那是老家的后山包上,有着南方姑娘的纤柔苍翠欲滴的嫩竹此时已爬满了山坡。
和着清风流水,微微扬起婀娜的裙摆。
那长长的从一端渐渐向两边延伸变得丰满最尾又回到细尖的不知名的叶片,疯长在坟前。
外公一个人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劳作了一上午,把它们连根的堆向两侧,“那不好。
”他说。
老家的大门用棕红的油漆涂了厚厚一层,妈妈有些若失的望着,仿佛又觉得什么不对了。
老家,我何曾在这儿住过一天?这是我当年逃到这儿,你外婆就打不到的高台,这是我和你幺舅最爱的厨房,你外婆经常偷着给我们煮开水蛋,这是你外婆和祖母站在那儿等你外公回来的院子。
妈妈紧紧拽着我,兴高采烈的指指点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来。
我望着妈妈,脸上跳跃着欢快的光,眉眼都成了一条线,两鬓突出的银丝在昏暗的房间中竟毫无察觉,恍惚间,我觉得妈妈回到了20岁之前的样子,那个还偎依在外婆膝下,在祖母身旁蹦蹦跳跳的那个瘦瘦小小的,那个在院子那棵600多年的银杏树下看书的她。
客厅正中间,是我外婆的遗照。
我从未细细端详过。
远远勾勒出她的轮廓,一顶似乎绒线织的小帽儿,稍稍向两侧翘起的头发。
嘴也许是抿着,眼神在我看来是空洞的。
脸上的肌肉没有收缩亦没有拉伸一下,那种神情,说不上是快乐,但更无需悲哀。
三姨推了推我妈,“看,妈走得好安详。
”妈妈动了动嘴,没有说什么,四姨接过“对啊”,然后和三姨相视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
妈跪下了,在外婆的坟前。
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妈,我们来看你了。
”压低了声音,轻轻的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念着,我没听懂。
拿起一张纸币,面值是一个8后面10个0,印着天地银行。
大火一触碰到就张牙舞爪的吞噬,从四周到中间,彩色一点一点的褪去,一缕长长的青烟缓缓上升,仅使留下一层土灰。
风起了,扬起的星星点点飘悬在空气中,像一个一个跃动着的精灵。
妈妈说,那是你外婆高兴啊。
浮起的稚气,与雷厉风行,坚强泼辣的她判若两人。
我记得那个深秋的午夜,我和妈游走在姨妈楼下的公园。
坐在冰冷的石凳上,两个人毫无主题的慢聊。
我边哈着热气,边跺着脚。
妈妈把手放在大腿上,用手撑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