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一)
- 格式:docx
- 大小:14.31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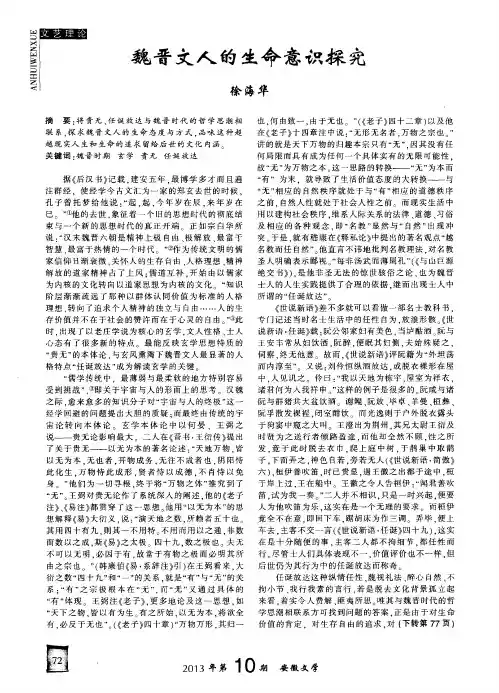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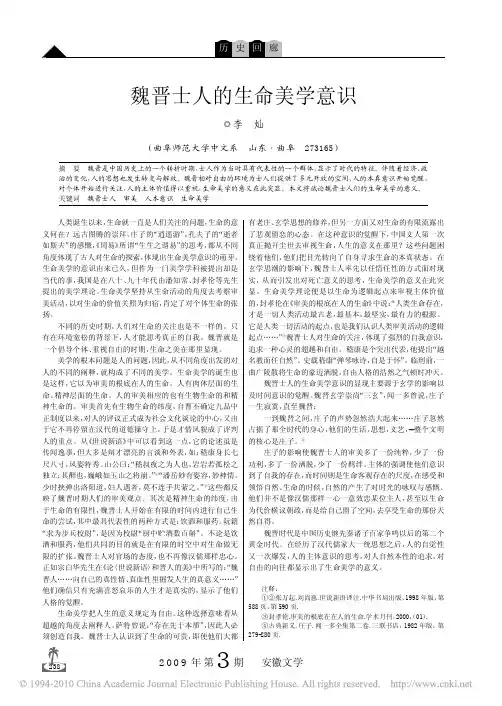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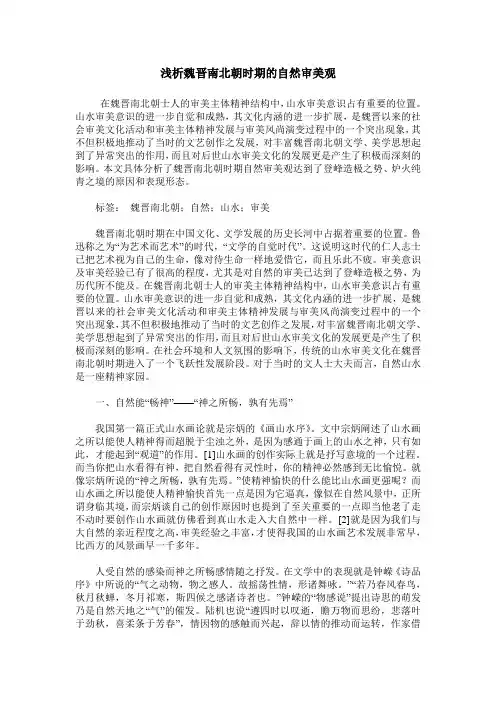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审美观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具体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观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炉火纯青之境的原因和表现形态。
标签:魏晋南北朝;自然;山水;审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鲁迅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说明这时代的仁人志士已把艺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生命一样地爱惜它,而且乐此不疲。
审美意识及审美经验已有了很高的程度,尤其是对自然的审美已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为历代所不能及。
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下,传统的山水审美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飞跃性发展阶段。
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自然山水是一座精神家园。
一、自然能“畅神”——“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我国第一篇正式山水画论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
文中宗炳阐述了山水画之所以能使人精神得而超脱于尘浊之外,是因为感通于画上的山水之神,只有如此,才能起到“观道”的作用。
[1]山水画的创作实际上就是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
而当你把山水看得有神,把自然看得有灵性时,你的精神必然感到无比愉悦。
就像宗炳所说的“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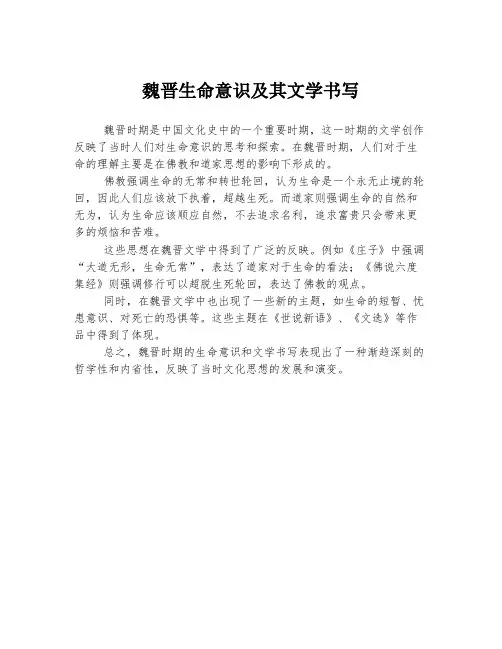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思考和探索。
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主要是在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佛教强调生命的无常和转世轮回,认为生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轮回,因此人们应该放下执着,超越生死。
而道家则强调生命的自然和无为,认为生命应该顺应自然,不去追求名利,追求富贵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和苦难。
这些思想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例如《庄子》中强调“大道无形,生命无常”,表达了道家对于生命的看法;《佛说六度集经》则强调修行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表达了佛教的观点。
同时,在魏晋文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主题,如生命的短暂、忧患意识、对死亡的恐惧等。
这些主题在《世说新语》、《文选》等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总之,魏晋时期的生命意识和文学书写表现出了一种渐趋深刻的哲学性和内省性,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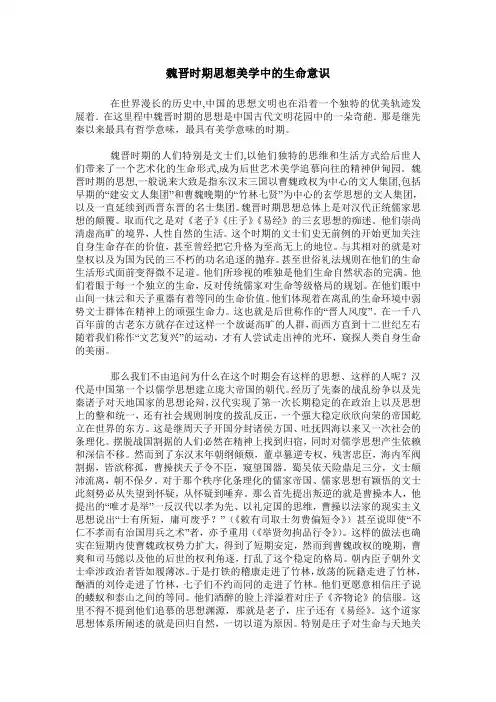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
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
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
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
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
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
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
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
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
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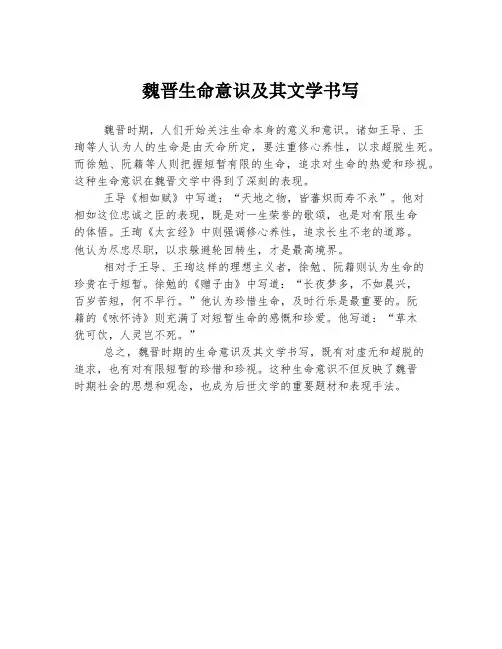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意识。
诸如王导、王
珣等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天命所定,要注重修心养性,以求超脱生死。
而徐勉、阮籍等人则把握短暂有限的生命,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和珍视。
这种生命意识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王导《相如赋》中写道:“天地之物,皆蕃炽而寿不永”。
他对
相如这位忠诚之臣的表现,既是对一生荣誉的歌颂,也是对有限生命
的体悟。
王珣《太玄经》中则强调修心养性,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
他认为尽忠尽职,以求躲避轮回转生,才是最高境界。
相对于王导、王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徐勉、阮籍则认为生命的
珍贵在于短暂。
徐勉的《赠子由》中写道:“长夜梦多,不如晨兴,
百岁苦短,何不早行。
”他认为珍惜生命,及时行乐是最重要的。
阮
籍的《咏怀诗》则充满了对短暂生命的感慨和珍爱。
他写道:“草木
犹可饮,人灵岂不死。
”
总之,魏晋时期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既有对虚无和超脱的
追求,也有对有限短暂的珍惜和珍视。
这种生命意识不但反映了魏晋
时期社会的思想和观念,也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题材和表现手法。

2023-11-04CATALOGUE目录•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概述•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的具体表现•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的历史意义与价值•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研究展望01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概述社会政治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相对较为混乱。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普遍追求自由和超越世俗的境界,自然美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文化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盛行,这些宗教信仰对于当时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士人们追求雅致的生活方式,自然美育思想成为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美育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美学思想逐渐兴起。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开始关注自然之美,并试图将自然元素融入到艺术创作中。
例如,当时的园林设计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育的思想。
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美育思想逐渐发展并传承下来。
在唐代,自然美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宋代以后,自然美育思想逐渐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美育思想对于后世的文学、艺术、园林设计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园林设计中,"山水园林"的兴起就是受到自然美育思想的影响。
传承自然美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传承至今。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美育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环保、教育等领域中,自然美育思想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02魏晋南北朝自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规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美育思想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反对人为干预,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
追求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注重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认为人与自然应当相互融合、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美的极致。
自然情感体验人们应当深入体验自然之美,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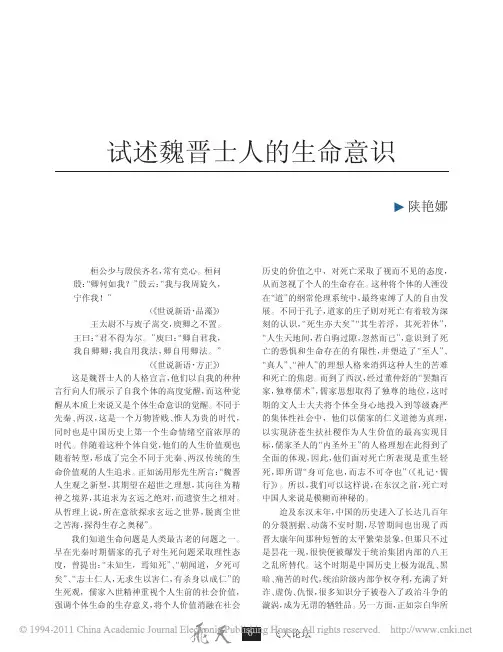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
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
”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
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
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
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
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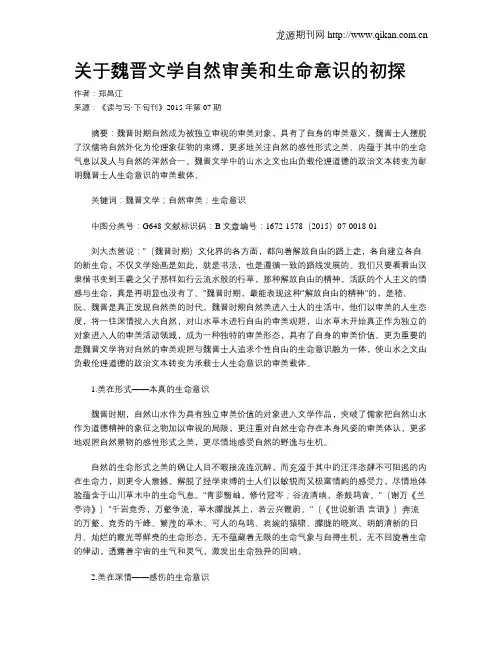
关于魏晋文学自然审美和生命意识的初探作者:郑昌江来源:《读与写·下旬刊》2015年第07期摘要: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
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关键词: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生命意识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7-0018-01刘大杰曾说:"(魏晋时期)文化界的各方面,都向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各自建立各自的新生命,不仅文学绘画是如此,就是书法,也是遵循一致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只要看看由汉隶楷书变到王羲之父子那样如行云流水般的行草,那种解放自由的精神,活跃的个人主义的情感与生命,真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魏晋时期,最能表现这种"解放自由的精神"的,是嵇、阮。
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
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1.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
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
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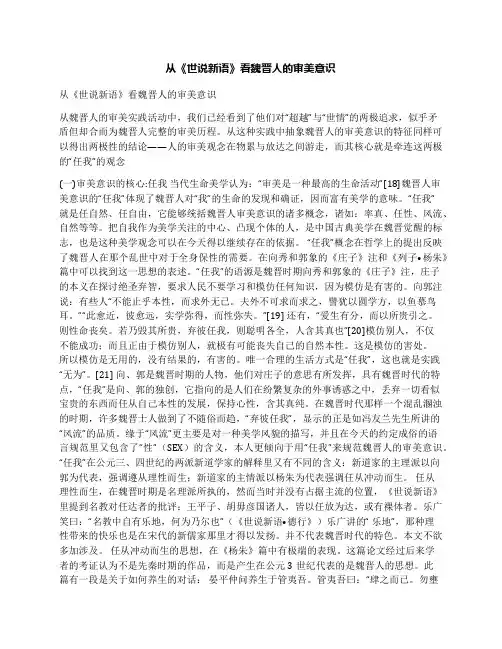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意识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意识从魏晋人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超越”与“世情”的两极追求,似乎矛盾但却合而为魏晋人完整的审美历程。
从这种实践中抽象魏晋人的审美意识的特征同样可以得出两极性的结论——人的审美观念在物累与放达之间游走,而其核心就是牵连这两极的“任我”的观念(一)审美意识的核心:任我当代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18]魏晋人审美意识的“任我”体现了魏晋人对“我”的生命的发现和确证,因而富有美学的意味。
“任我”就是任自然、任自由,它能够统括魏晋人审美意识的诸多概念,诸如:率真、任性、风流、自然等等。
把自我作为美学关注的中心、凸现个体的人,是中国古典美学在魏晋觉醒的标志,也是这种美学观念可以在今天得以继续存在的依据。
“任我”概念在哲学上的提出反映了魏晋人在那个乱世中对于全身保性的需要。
在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和《列子•杨朱》篇中可以找到这一思想的表述。
“任我”的语源是魏晋时期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庄子的本义在探讨绝圣弃智,要求人民不要学习和模仿任何知识,因为模仿是有害的。
向郭注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
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
”“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
”[19] 还有,“爱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
则性命丧矣。
若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也”[20]模仿别人,不仅不能成功;而且正由于模仿别人,就极有可能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
这是模仿的害处。
所以模仿是无用的,没有结果的,有害的。
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这也就是实践“无为”。
[21] 向、郭是魏晋时期的人物,他们对庄子的意思有所发挥,具有魏晋时代的特点,“任我”是向、郭的独创,它指向的是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外事诱惑之中,丢弃一切看似宝贵的东西而任从自己本性的发展,保持心性,含其真纯。
在魏晋时代那样一个混乱溷浊的时期,许多魏晋士人做到了不随俗而趋,“弃彼任我”,显示的正是如冯友兰先生所讲的“风流”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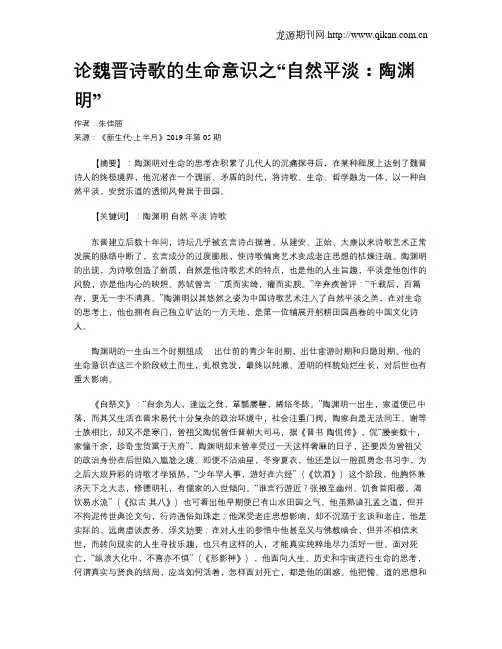
论魏晋诗歌的生命意识之“自然平淡:陶渊明”作者:朱佳丽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9年第05期【摘要】:陶渊明对生命的思考在积累了几代人的沉痛探寻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魏晋诗人的终极境界,他沉潜在一个瑰丽、矛盾的时代,将诗歌、生命、哲学融为一体,以一种自然平淡,安贫乐道的透彻风骨居于田园。
【关键词】:陶渊明自然平淡诗歌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为诗歌创造了新质,自然是他诗歌艺术的特点,也是他的人生旨趣,平淡是他创作的风貌,亦是他内心的映照。
苏轼曾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辛弃疾曾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陶渊明以其悠然之姿为中国诗歌艺术注入了自然平淡之美,在对生命的思考上,他也拥有自己独立旷达的一方天地,是第一位铺展开躬耕田园画卷的中国文化诗人。
陶渊明的一生由三个时期组成----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出仕宦游时期和归隐时期。
他的生命意识在这三个阶段破土而生,虬根竞发,最终以纯澈、澄明的样貌灿烂生长,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自祭文》:“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
”陶渊明一出生,家道便已中落,而其又生活在晋宋易代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社会注重门阀,陶家自是无法同王、谢等士族相比,却又不是寒门,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据《晋书·陶侃传》,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陶渊明却未曾享受过一天这样奢靡的日子,还要因为曾祖父的政治身份在后世陷入尴尬之境。
即便不沾油星,冬穿夏衣,他还是以一腔孤勇念书习字,为之后大放异彩的诗歌才学预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这个阶段,他胸怀兼济天下之大志,修德明礼,有儒家的入世倾向。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其八》)也可看出他早期便已有山水田园之气。
魏晋美学浅析浅析魏晋美学中的生命意识【书法,例如陶潜、谢灵运、顾恺之、钟繇、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唐以后的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开启作用。
这个时代艺术理论,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更为后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弼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这个命题,也就是说,无法言传的意绪、情思,用“象”来表现最合适,然而最后要真正把握的是“意”,也就是要“忘象”。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推动了美学领域中“象”的范畴向“意象”这个范畴的转化。
也为后人把握审美观照的特点(即对有限物象的超越、对概念的超越)提供了启发,也为文学艺术家认识艺术形式和艺术整体形象之间的辨证关系(即艺术美不应该突出自己,而应该否定自己,从而把艺术的整体形象突出地表现出来)给了很大的启示。
意境可视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核心,“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是“观物取象”之意。
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
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
嵇康在音乐创作和欣赏方面,提出了“声无哀乐”的命题。
他认为,音乐是自然产生的声音,不包含、也不能使听者产生哀乐的情感。
嵇康否认艺术美和欣赏者的美感之间的因果联系,否认音乐具有情感内容,否认音乐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否认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但是从他反对无限夸大音乐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对音乐加强控制的角度来说,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美学史的发展来看,嵇康的“声无哀乐”的命题,反映了人们对于艺术审美形象的认识的深化,所以也有它积极的意义。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意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在魏晋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意识逐渐从封建的宿命论转变为个体的自我意识。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个体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在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不稳定,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力量和价值。
他们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而不再被命运所束缚。
这种转变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魏晋文学以个体的生命为主题,关注个体的情感和命运。
例如《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都以个人的经历和命运为背景,通过生动的细节和真实的情感,展现了个体在动荡的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
同时,《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思考。
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还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
在动荡的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他们意识到生命是短暂的,随时都可能被战乱和疾病夺去。
因此,他们更加珍惜生命,追求快乐和幸福。
这种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
例如《琅琊榜》中的人物形象,他们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他们的命运时常会发生剧变。
这些作品通过描绘人物的生死境遇,表达了对生命短暂性的思考和对生命的珍惜。
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还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
在动荡的时代,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
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追问人生的价值。
这种思考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
例如《庄子》中的许多篇章,以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都表现了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命的价值的追问。
这些作品通过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引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魏晋时期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以及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
这种转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丰富了魏晋文学的内涵。
许宜兰丨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作者:许宜兰(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摘要: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 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
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 把思想引向了玄学。
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
人们主张个性张扬, 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
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 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
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 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 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玄学、书学、自然、道家正文一、崇尚“自然”是书法神韵的美学基础魏晋时期由于汉末社会急剧变化, 人们开始对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等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
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儒学黯然失色, 以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的经学也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哲学, 受到了魏晋士人的质疑与反叛。
魏正始年间, 何晏、王弼等人在思想领域宣扬老庄思想。
《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初霸, 术兼名法。
何晏之徒, 始盛玄论。
” 一般士大夫需要用道家之学作为躲避灾祸, 调适心态的工具;他们用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来远离世俗;在崇尚自然和物我融一的生活中来表现他们的精神人格。
在此思想影响下, 士人们的自我意识膨胀。
他们重新思考自我价值, 崇尚一种率性而动、自然而然的生活。
思想精神获得了空前解放和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
因此, 魏晋时代被史家称为是人的意识觉醒的时期。
这也就形成了书法艺术自觉的时期。
近人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 亦以晋人为最盛。
晋之书, 亦犹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具体表现其一:成批书法家的出现。
从蔡邕、张、钟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等:其二:对书法艺术的研学成为时尚。
如张芝学书法“家之衣帛, 必书而后练。
临池学书, 水为之黑” (王愔《文字志》) , 其三:书法理论著作大量出现。
如崔瑗《草书势》、赵壹《非草书》、蔡邕《笔论》、《九势》等;其四:对书法各要素有严格的美学要求。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王桂丽【摘要】"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
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
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
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1)006【总页数】3页(P11-13)【关键词】魏晋玄学;自然;生命本体论;自由性【作者】王桂丽【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35“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主要范畴之一,其基本的含义有三个方面:其一,表达事物存在的本性、状态;其二,表达与“文明异化”相对的“自然界”;其三,指涉“自然”状态的生命存在,即对本真生命状态的向往与渴慕,对人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一、先秦“自然”范畴的“道性”本体道家美学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最早建构了“自然”范畴,陈鼓应认为,“自然观念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1]170。
“自然”一词在《老子》中一共出现五次,但能将“自然”作为本体存在的在“自然”与“道”的联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老子·五十一章》)可以看出,《老子》将“自然”作为“道性”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
汉代河上公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1]168道即自然,自然即道,“道”作为宇宙的存在即是存在自身,因此,“道”无所法,它自身决定自身,自身显现自身。
魏晋嵇阮派美学之自然审美意识
李天道
【期刊名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在魏晋美学中,竹林派的代表嵇康、阮籍极力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推崇随意任心、顺其自然的审美意识。
认为“越名任心”审美域的生成来自自由洒脱、任心自然。
所谓“越名任心”,即自然而然、任其自然,其美学意义表征着对现实世界与“名教”的超越,对自我种种欲望的超越,实质上则意味着对超尘绝俗、一往不复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注重。
在此意义上,淡泊、恬淡、自然、随意任心、顺其自然则成为嵇阮派美学自然审美意识的内在逻辑。
这种越名任心、顺其自然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诉诸于一己心灵体验的随意任心、顺其自然,可以称之为存在论美学的然其所然,是其所是。
【总页数】9页(P100-108)
【作者】李天道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3-02
【相关文献】
1.嵇阮派玄学的“越名任心”论 [J], 黄应全
2.诗性自然——游观美学视域下的《楚辞》自然审美意识探微 [J], 孙玉茜
3.理性的超越与感性的生动——魏晋玄学与自然审美意识关系论 [J], 刘敏
4.入之于哲学,出之于美学——试论玄学与魏晋审美意识的发生 [J], 郝敬胜;张允熠
5.真与美:魏晋科学理性精神与文人自然审美意识 [J], 刘敏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一)
【内容提要】
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
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关键词】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生命意识
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
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
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
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
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
“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
(《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
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
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
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
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
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
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
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
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
死灰的人也是美的。
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
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
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
”“瑶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
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
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
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
”(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
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
二、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
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
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
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
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
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
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
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