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旧诗关系的再发现
- 格式:doc
- 大小:16.86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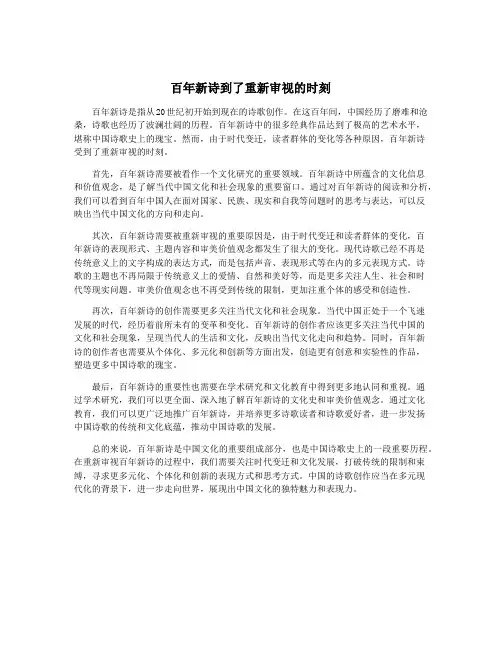
百年新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百年新诗是指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的诗歌创作。
在这百年间,中国经历了磨难和沧桑,诗歌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
百年新诗中的很多经典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
然而,由于时代变迁,读者群体的变化等各种原因,百年新诗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
首先,百年新诗需要被看作一个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
百年新诗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是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的重要窗口。
通过对百年新诗的阅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人在面对国家、民族、现实和自我等问题时的思考与表达,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方向和走向。
其次,百年新诗需要被重新审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时代变迁和读者群体的变化,百年新诗的表现形式、主题内容和审美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诗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构成的表达方式,而是包括声音、表现形式等在内的多元表现方式。
诗歌的主题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自然和美好等,而是更多关注人生、社会和时代等现实问题。
审美价值观念也不再受到传统的限制,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和创造性。
再次,百年新诗的创作需要更多关注当代文化和社会现象。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变化。
百年新诗的创作者应该更多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呈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文化,反映出当代文化走向和趋势。
同时,百年新诗的创作者也需要从个体化、多元化和创新等方面出发,创造更有创意和实验性的作品,塑造更多中国诗歌的瑰宝。
最后,百年新诗的重要性也需要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中得到更多地认同和重视。
通过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百年新诗的文化史和审美价值观念。
通过文化教育,我们可以更广泛地推广百年新诗,并培养更多诗歌读者和诗歌爱好者,进一步发扬中国诗歌的传统和文化底蕴,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
总的来说,百年新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段重要历程。
在重新审视百年新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打破传统的限制和束缚,寻求更多元化、个体化和创新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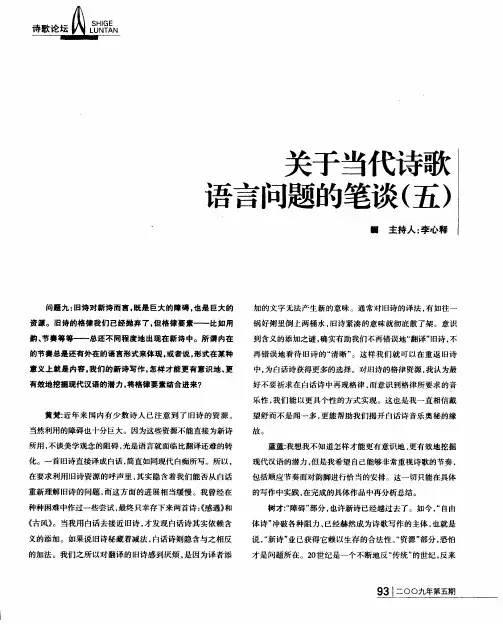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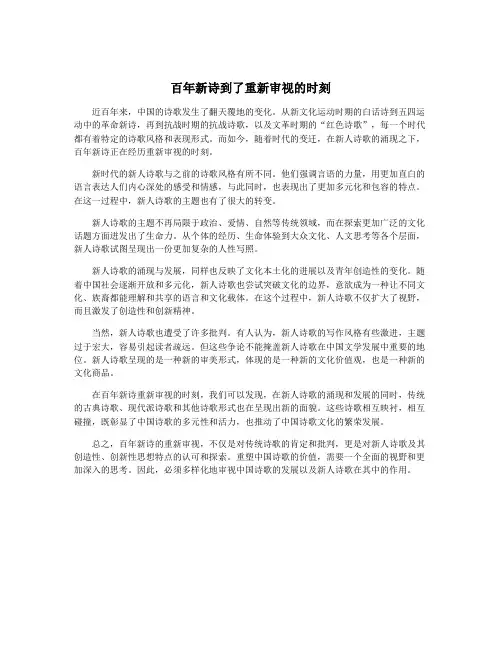
百年新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近百年来,中国的诗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诗到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新诗,再到抗战时期的抗战诗歌,以及文革时期的“红色诗歌”,每一个时代都有着特定的诗歌风格和表现形式。
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新人诗歌的涌现之下,百年新诗正在经历重新审视的时刻。
新时代的新人诗歌与之前的诗歌风格有所不同。
他们强调言语的力量,用更加直白的语言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情感,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特点。
在这一过程中,新人诗歌的主题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新人诗歌的主题不再局限于政治、爱情、自然等传统领域,而在探索更加广泛的文化话题方面迸发出了生命力。
从个体的经历、生命体验到大众文化、人文思考等各个层面,新人诗歌试图呈现出一份更加复杂的人性写照。
新人诗歌的涌现与发展,同样也反映了文化本土化的进展以及青年创造性的变化。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开放和多元化,新人诗歌也尝试突破文化的边界,意欲成为一种让不同文化、族裔都能理解和共享的语言和文化载体。
在这个过程中,新人诗歌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激发了创造性和创新精神。
当然,新人诗歌也遭受了许多批判。
有人认为,新人诗歌的写作风格有些激进,主题过于宏大,容易引起读者疏远。
但这些争论不能掩盖新人诗歌在中国文学发展中重要的地位。
新人诗歌呈现的是一种新的审美形式,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商品。
在百年新诗重新审视的时刻,我们可以发现,在新人诗歌的涌现和发展的同时,传统的古典诗歌、现代派诗歌和其他诗歌形式也在呈现出新的面貌。
这些诗歌相互映衬,相互碰撞,既彰显了中国诗歌的多元性和活力,也推动了中国诗歌文化的繁荣发展。
总之,百年新诗的重新审视,不仅是对传统诗歌的肯定和批判,更是对新人诗歌及其创造性、创新性思想特点的认可和探索。
重塑中国诗歌的价值,需要一个全面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因此,必须多样化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以及新人诗歌在其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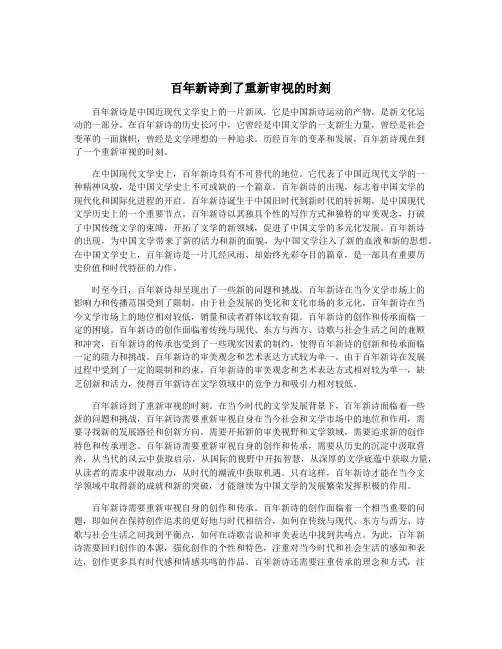
百年新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百年新诗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片新风,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产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在百年新诗的历史长河中,它曾经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新生力量,曾经是社会变革的一面旗帜,曾经是文学理想的一种追求。
历经百年的变革和发展,百年新诗现在到了一个重新审视的时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百年新诗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代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种精神风貌,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
百年新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开启。
百年新诗诞生于中国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折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百年新诗以其独具个性的写作方式和独特的审美观念,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束缚,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百年新诗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百年新诗是一片几经风雨、却始终光彩夺目的篇章,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特征的力作。
时至今日,百年新诗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百年新诗在当今文学市场上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受到了限制。
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百年新诗在当今文学市场上的地位相对较低,销量和读者群体比较有限。
百年新诗的创作和传承面临一定的困境。
百年新诗的创作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兼顾和冲突,百年新诗的传承也受到了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使得百年新诗的创新和传承面临一定的阻力和挑战。
百年新诗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方式较为单一。
由于百年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百年新诗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方式相对较为单一,缺乏创新和活力,使得百年新诗在文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相对较低。
百年新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
在当今时代的文学发展背景下,百年新诗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百年新诗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在当今社会和文学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创新方向,需要开拓新的审美视野和文学领域,需要追求新的创作特色和传承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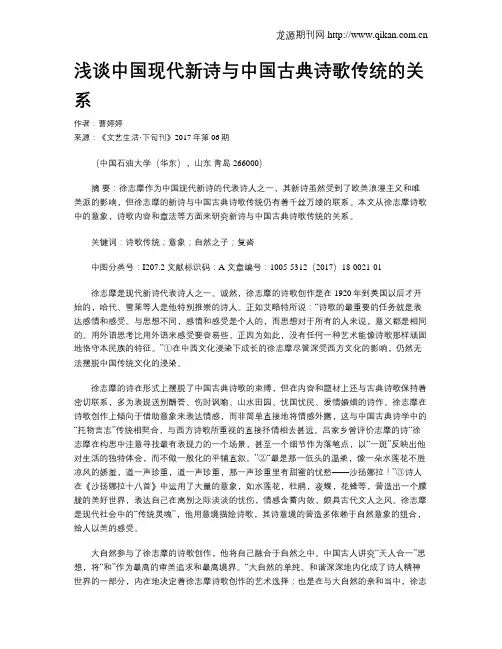
浅谈中国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作者:曹婷婷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第06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青岛 266000)摘要: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其新诗虽然受到了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的影响,但徐志摩的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从徐志摩诗歌中的意象,诗歌内容和章法等方面来研究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
关键词:诗歌传统;意象;自然之子;复沓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021-01徐志摩是现代新诗代表诗人之一。
诚然,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是在1920年到英国以后才开始的,哈代、雪莱等人是他特别推崇的诗人。
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
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
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
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
”①在中西文化浸染下成长的徐志摩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徐志摩的诗在形式上摆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束缚,但在内容和题材上还与古典诗歌保持着密切联系,多为表现送别酬答、伤时讽喻、山水田园、忧国忧民、爱情婚姻的诗作。
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倾向于借助意象来表达情感,而非简单直接地将情感外露,这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托物言志”传统相契合,与西方诗歌所重视的直接抒情相去甚远。
吕家乡曾评价志摩的诗“徐志摩在构思中注意寻找最有表现力的一个场景,甚至一个细节作为落笔点,以“一斑”反映出他对生活的独特体会,而不做一般化的平铺直叙。
”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③诗人在《沙扬娜拉十八首》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如水莲花,杜鹃,夜蝶,花蜂等,营造出一个朦胧的美好世界,表达自己在离别之际淡淡的忧伤,情感含蓄内敛,颇具古代文人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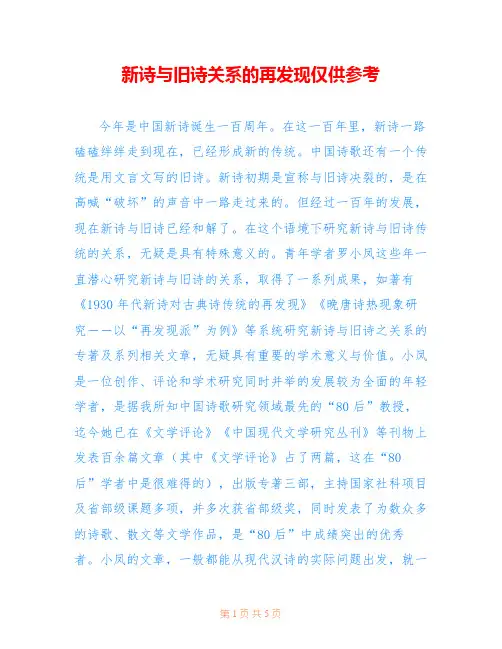
新诗与旧诗关系的再发现仅供参考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在这一百年里,新诗一路磕磕绊绊走到现在,已经形成新的传统。
中国诗歌还有一个传统是用文言文写的旧诗。
新诗初期是宣称与旧诗决裂的,是在高喊“破坏”的声音中一路走过来的。
但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在新诗与旧诗已经和解了。
在这个语境下研究新诗与旧诗传统的关系,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青年学者罗小凤这些年一直潜心研究新诗与旧诗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著有《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晚唐诗热现象研究――以“再发现派”为例》等系统研究新诗与旧诗之关系的专著及系列相关文章,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小凤是一位创作、评论和学术研究同时并举的发展较为全面的年轻学者,是据我所知中国诗歌研究领域最先的“80后”教授,迄今她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百余篇文章(其中《文学评论》占了两篇,这在“80后”学者中是很难得的),出版专著三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并多次获省部级奖,同时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是“80后”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者。
小凤的文章,一般都能从现代汉诗的实际问题出发,就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理论话题做比较深入的探讨,总试图有自己的“发现”与表述。
譬如她在《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文中重新审视了“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学界一直认为新诗与传统是“断裂”的,小凤对此做出了批驳与细致阐述,她认为:“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过,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歌传统。
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后来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显然是大胆、创新的独特发现,这或许是这篇文章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关键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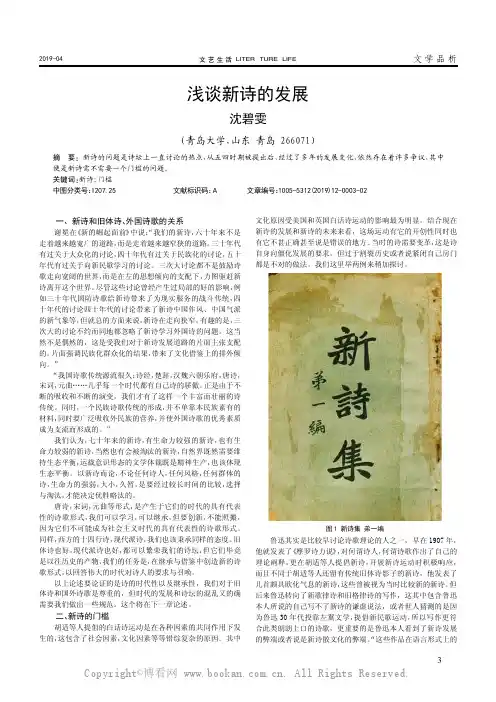
2019-04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文学品析浅谈新诗的发展沈碧雯(青岛大学,山东青岛266071)摘要:新诗的问题是诗坛上一直讨论的热点,从五四时期被提出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变化,依然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便是新诗需不需要一个门槛的问题。
关键词:新诗;门槛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9)12-0003-02一、新诗和旧体诗、外国诗歌的关系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说:“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
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
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
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狭窄。
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
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诗的骄傲。
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
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成为支流而形成的。
”我们认为,七十年来的新诗,有生命力较强的新诗,也有生命力较弱的新诗,当然也有会被淘汰的新诗,自然界既然需要维持生态平衡,运载意识形态的文学体裁既是精神生产,也该体现生态平衡。
以新诗而论,不论任何诗人,任何风格,任何群体的诗,生命力的强弱,大小,久暂,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比较,选择与淘汰,才能决定优胜略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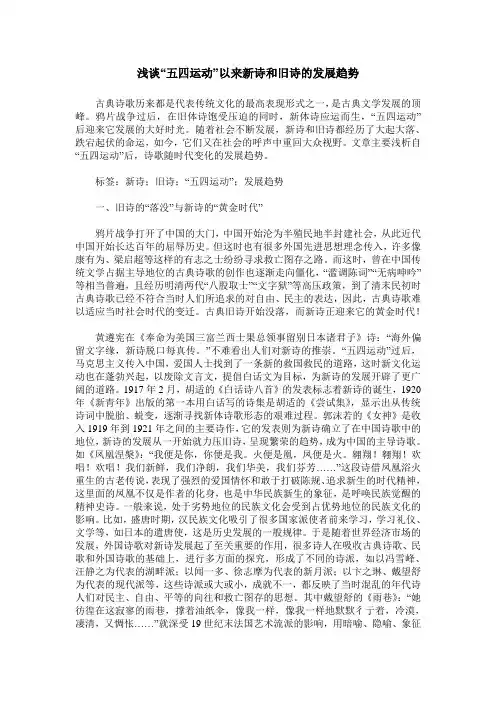
浅谈“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和旧诗的发展趋势古典诗歌历来都是代表传统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古典文学发展的顶峰。
鸦片战争过后,在旧体诗饱受压迫的同时,新体诗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迎来它发展的大好时光。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新诗和旧诗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命运,如今,它们又在社会的呼声中重回大众视野。
文章主要浅析自“五四运动”后,诗歌随时代变化的发展趋势。
标签:新诗;旧诗;“五四运动”;发展趋势一、旧诗的“落没”与新诗的“黄金时代”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近代中国开始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但这时也有很多外国先进思想理念传入,许多像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
而这时,曾在中国传统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诗歌的创作也逐渐走向僵化,“滥调陈词”“无病呻吟”等相当普遍,且经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到了清末民初时古典诗歌已经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对自由、民主的表达,因此,古典诗歌难以适应当时社会时代的变迁。
古典旧诗开始没落,而新诗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黄遵宪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真传。
”不难看出人们对新诗的推崇。
“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爱国人士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新文化运动也在蓬勃兴起,以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目标,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的发表标志着新诗的诞生,1920年《新青年》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新体诗歌形态的艰难过程。
郭沫若的《女神》是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它的发表则为新诗确立了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力压旧诗,呈现繁荣的趋势,成为中国的主导诗歌。
如《凤凰涅槃》:“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凤便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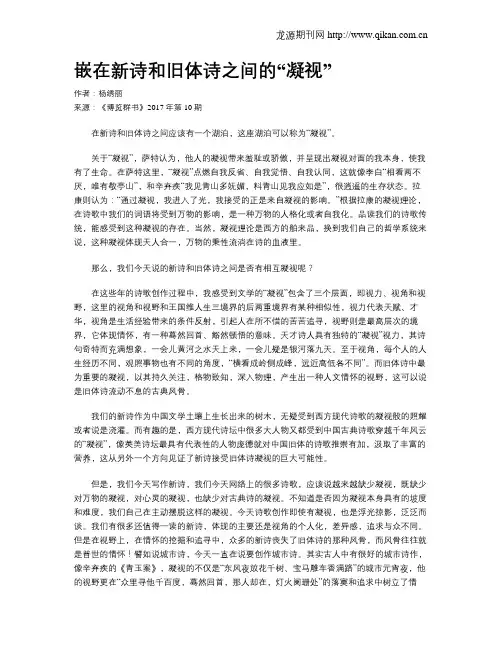
嵌在新诗和旧体诗之间的“凝视”作者:杨绣丽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在新诗和旧体诗之间应该有一个湖泊,这座湖泊可以称为“凝视”。
关于“凝视”,萨特认为,他人的凝视带来羞耻或骄傲,并呈现出凝视对面的我本身,使我有了生命。
在萨特这里,“凝视”点燃自我反省、自我觉悟、自我认同,这就像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和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很逍遥的生存状态。
拉康则认为:“通过凝视,我进入了光,我接受的正是来自凝视的影响。
”根据拉康的凝视理论,在诗歌中我们的词语将受到万物的影响,是一种万物的人格化或者自我化。
品读我们的诗歌传统,能感受到这种凝视的存在。
当然,凝视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换到我们自己的哲学系统来说,这种凝视体现天人合一,万物的秉性流淌在诗的血液里。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新诗和旧体诗之间是否有相互凝视呢?在这些年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我感受到文学的“凝视”包含了三个层面,即视力、视角和视野,这里的视角和视野和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后两重境界有某种相似性,视力代表天赋、才华,视角是生活经验带来的条件反射,引起人在所不惜的苦苦追寻,视野则是最高层次的境界,它体现情怀,有一种蓦然回首、豁然顿悟的意味。
天才诗人具有独特的“凝视”视力,其诗句奇特而充满想象,一会儿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会儿疑是银河落九天。
至于视角,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观照事物也有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而旧体诗中最为重要的凝视,以其持久关注,格物致知,深入物理,产生出一种人文情怀的视野,这可以说是旧体诗流动不息的古典风骨。
我们的新诗作为中国文学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树木,无疑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凝视般的照耀或者说是浇灌。
而有趣的是,西方现代诗坛中很多大人物又都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穿越千年风云的“凝视”,像英美诗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庞德就对中国旧体的诗歌推崇有加,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从另外一个方向见证了新诗接受旧体诗凝视的巨大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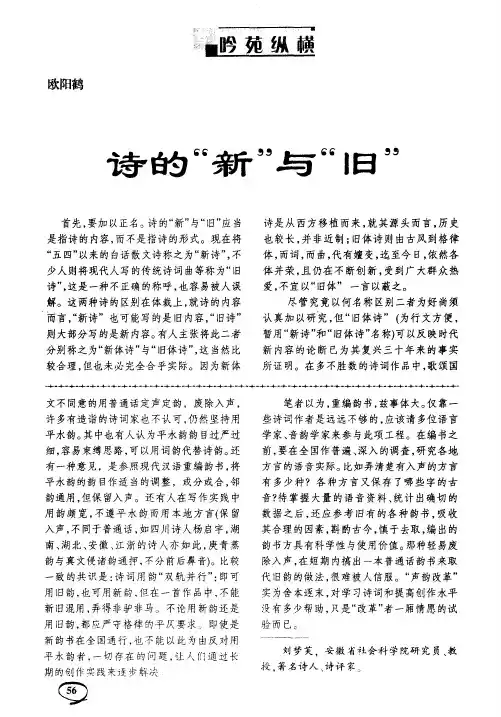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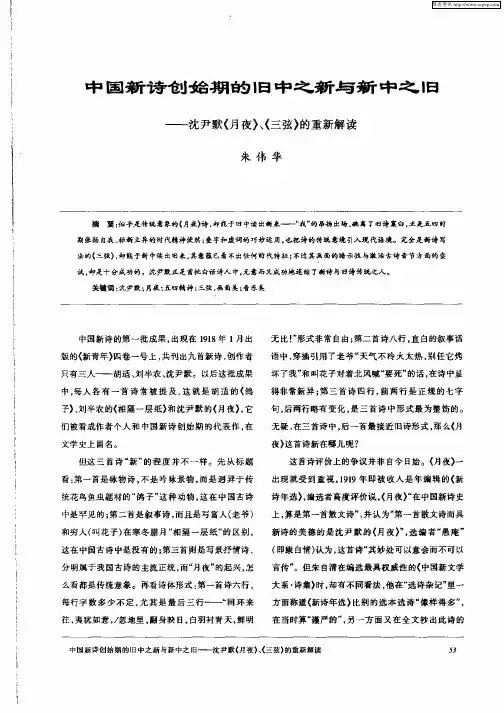
百年新诗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百年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诗人们不仅有承前启后之意,而且在表现方式、意象语言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贡献。
然而,对于这个时期的诗歌,我们也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诗人们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背景。
百年新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政治动荡、民生苦难的时期,这些背景给了诗人们无尽的灵感和压抑,他们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痛苦和希望。
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作品质量,不仅关注诗歌形式和艺术性,更关注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命体验。
其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诗歌风格和表现方式。
百年新诗时期,诗人们在表现方式上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他们不拘于传统的诗句格律和表现方式,而是尝试新的手法和思路,如自由诗、象征主义、意象派等。
这些尝试丰富了诗歌表现方式,让诗歌更具现代性和世俗感。
但是,也有一些诗人在追求新颖和激进的同时忽视了传统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造成了一定的风格上的难以理解和市场上的局限。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诗歌风格和作品质量,正视其中的优缺点和局限性。
最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诗歌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
作为现代诗歌的代表阶段,百年新诗时期的诗歌不仅要关注形式和艺术性,更要关注思想和社会价值。
在这个时期,诗人们对于人性、自由、爱情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一些独具匠心的作品,如朱自清的《背影》、余光中的《乡村四月》,也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诗歌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关注其中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综上所述,百年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诗人们和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体验和思考。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正视其中的优缺点和局限性,更充分地认识百年新诗对于中国诗歌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历史贡献。
鉴赏割裂还是继承——浅谈中国现代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杜楠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摘要:五四新文化时期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现代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这一问题始终伴随着诗歌现代化的发展。
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青年学者就开始要求打破传统诗歌的形式和韵律然而其作品中仍存在着割舍不掉的“传统意识”。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可谓是“彻底的现代化”,然而其诗歌虽然具有现代的词藻、现代的意象以及工业发展时代的人们能够改变一切的气势,全然脱去了传统诗歌的影子,然而郭沫若说对自己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屈原。
现代诗歌发展的第一个接受高峰要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出现,他们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才更能引起共鸣。
关键词:现代新诗;传统诗歌;关系;胡适;郭沫若;“新月派”在早期的现代诗歌起步阶段,胡适、郭沫若等皆主张新诗应与传统文化、古体诗决裂,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文学形式的革新绝不像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一般简单。
一旦废除古体诗的格律,随之而来便是诗歌创作形式的“极端”自由,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新诗来说,旧的诗歌形式被“废除”,新的诗歌理论尚未建立,这时是诗坛最混乱的时候,许多新诗人简单地将白话当作白话诗。
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时期部分人士反对白话诗,认为新诗不是诗,即便是当时提倡并写作新诗的俞平伯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1],“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要拿机器来试验的。
”[2]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新诗”在诞生之时便强调要打破传统诗歌的形式,割裂与传统诗歌的联系。
然而这个联系真的就这么容易被打破吗?答案是否定的。
当代著名诗人任洪渊说:“那么多文字的/明月压低了我的/星空/没有一个/殒/蚀/等你的第一声呼叫/抛在我头上的全部月亮/张若虚的/王昌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
“新时代诗歌”的三个向度作者:程继龙来源:《诗歌月刊》2019年第02期新诗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恰在此时,中国当代社会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为当前的新诗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新诗如何回望过去,更深地进入时代,表达时代,又如何面向未来更好地展开,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言说、思考的问题。
首先,更合理地处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
一百年来,新诗面对“旧诗”,总是充满了仇视、犹疑、眷念、渴慕等复杂感情。
一方面,我们信奉诗的“现代性”,唯新是问。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唐诗宋词自卑、感伤不已。
“五四”初期,志在革传统诗歌的命。
但同时,白话派诗就潜在地接续了国风、汉魏古风、宋诗的某些传统。
三十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重新发现了“晚唐诗风”“宋诗传统”。
现代知识青年青春的苦闷,都市怀乡病正好在细腻、玄微的唐宋诗歌传统中找到了共鸣点,形成一种亦古亦今、新旧辉映的诗歌风貌。
四十年代,艾青、穆旦、冯至,一面深入学习西方诗歌,一面也都在自己身上恢复着“杜甫传统”,通过对杜甫诗学的审视,重新获得了一种实现“整体性”的能力,都能自如地把握时代,把诗性的自我有效地置入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新时期以来,我们在舒婷的抒情诗中,能反复感受到宋词阴柔的腔调。
顾城的“童话性”离不开伟大、精绝、明亮的唐绝句的滋养。
韩东高度克制的日常化书写,以及那种精准的哲学化命名能力,一再流露着东方禅者的智慧。
同一时期或前后的陈东东、张枣、朱朱等都是在西与中、现代与古典的相互激发中找到了建构各自诗性世界的可能。
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废名就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论断:在新诗、旧诗之上,还有一个更永恒、久远的诗在。
新诗须获得一种独立不惧的品质和气度。
废名这一思想来源于周作人的启发,后来在他的追随者沈启无、朱英诞那里得到了贯彻和完善。
这一论断几乎与T.S.艾略特对传统的认识是平行的关系。
“废名圈”诗人的见解富于历史的穿透力,到现在还是活泼泼的。
华语诗歌论坛》诗坛论剑:新诗与古典诗歌的辩证关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臧棣
在新诗将迎百年之际,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
新诗如果与古典诗脱离关系后,新诗的存在性、根基都存在质疑。
在新诗越写越自由、越写越开放时,新诗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
当现在与古典失去联系,新诗的意境、境界都出现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经有外国学者质问,如果你们写的东西与古典无关,所学的又是西方,那么我们的原创性在哪?其实新诗与古典诗具有非常丰富的联系。
新诗也要继承古典才会有出路。
但是,我们却需要更改新诗与古典的描述方式,应该从关联性对古典和新诗重新描述。
新诗之于古典,不是反传统,也不是判离,在谈及新诗与古典诗关联的把握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诗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新的东西,玩出新花样,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主题性的东西。
因此,这也是说,在古典诗歌与新诗的关联中上,我们应该从现代的出发点,再去接近传统,挖掘传统,从传统中去勾勒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
同时,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新诗与古典诗的关系。
对于古典诗,我们应该是回眸,回望,而不是回归。
来源:遂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