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肺复苏中的病理生理
- 格式:pptx
- 大小:5.44 MB
- 文档页数: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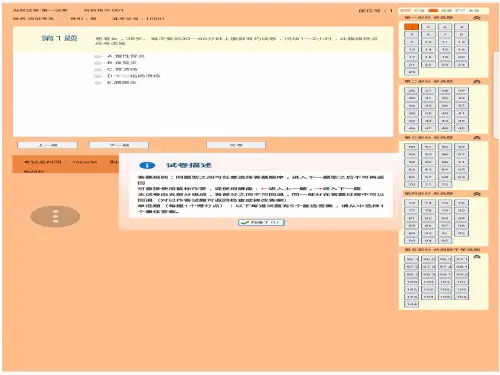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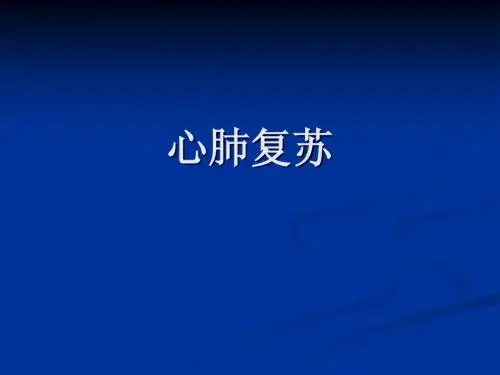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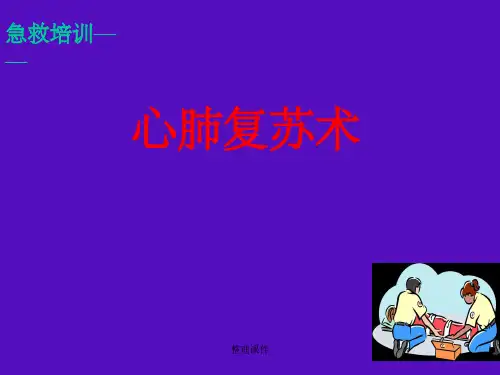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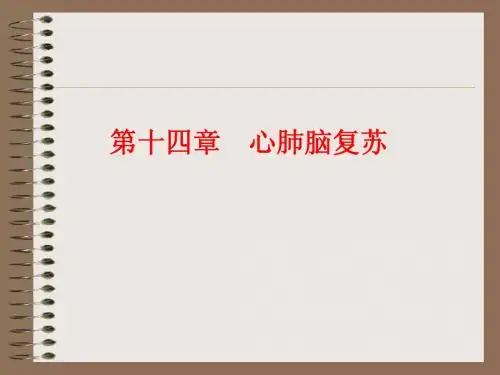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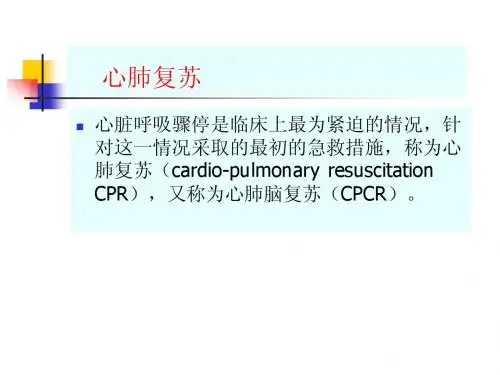

心脏骤停后心肺复苏成功1例病例介绍患者侯明春,女,35岁,于2012年01月01日晚22时10分突然出现全身抽搐,神志不清,烦躁不安,面颊发红,双目上视,喉中闻及痰鸣音,予按压人中、合谷穴。
约3分钟后患者突然出现窒息,大动脉搏动摸不清,意识丧失,面色苍白,口唇青紫,压眶反射及角膜反射消失。
立即施行CPR持续不间断徒手胸外心脏按压,并予开口器撑开口腔、夹出后坠舌头、吸痰、吸氧、心电血压血氧监护,吸痰器吸出大量白色粘液痰。
3分钟后患者出现深大呼吸,面色较红。
22时25分患者再次出现面色青紫,口唇发绀,呼吸停止,颈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听不到,心电监护示:室性逸搏,HR:78次/分,BP:0mmHg,,继续施行CPR,迅速开放静脉通路,给予副肾、多巴胺、阿托品、可拉明、洛贝林等药物抢救,并请医疗总值班及二线到场参与抢救。
22时30分麻醉科到场,气管插管成功并予人工气囊辅助通气,约16次/分。
患者偶有自主呼吸,约2-3次/分。
心电监护示:心电图呈一条直线。
双侧瞳孔约4mm,对光反射消失,压眶反射消失,立即给予电除颤200焦耳,继续施行CPR。
并分别于5min、15min、35min后予电除颤200焦耳。
苏显红主任、焦富英主任、周文波主任、乔世举主任及于雪峰主任等到场积极配合抢救。
苏显红主任指示:目前予患者心肺复苏术已1小时余,但患者较年轻,仍有心肺复苏成功的可能,继续施行CPR。
23时40分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140次/分,BP:98/60mmHg,抢救成功。
患者处于昏迷状态,人工气囊辅助通气中,面色较红润,双瞳孔等大正圆,直径约4mm,对光反射迟钝。
2012年01月02日01时20分患者状态较平稳,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中(A/C模式),呼出潮气量:525ml;频率:16次/分;吸呼比:1:2;峰值压力:20cmH2O,吸入氧浓度:30%;心电监护示:BP:110/75mmHg,HR:121次/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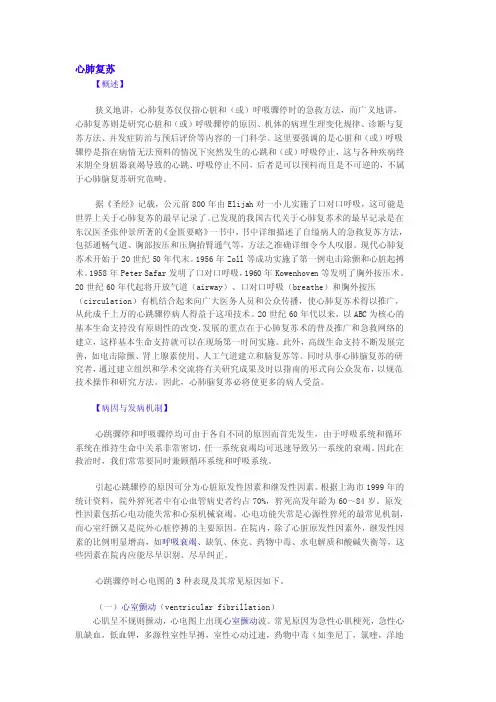
心肺复苏【概述】狭义地讲,心肺复苏仅仅指心脏和(或)呼吸骤停时的急救方法,而广义地讲,心肺复苏则是研究心脏和(或)呼吸骤停的原因、机体的病理生理变化规律、诊断与复苏方法、并发症防治与预后评价等内容的一门科学。
这里要强调的是心脏和(或)呼吸骤停是指在病情无法预料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心跳和(或)呼吸停止,这与各种疾病终末期全身脏器衰竭导致的心跳、呼吸停止不同,后者是可以预料而且是不可逆的,不属于心肺脑复苏研究范畴。
据《圣经》记载,公元前800年由Elijah对一小儿实施了口对口呼吸,这可能是世界上关于心肺复苏的最早记录了。
已发现的我国古代关于心肺复苏术的最早记录是在东汉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一书中,书中详细描述了自缢病人的急救复苏方法,包括通畅气道、胸部按压和压胸抬臂通气等,方法之准确详细令今人叹服。
现代心肺复苏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
1956年Zoll等成功实施了第一例电击除颤和心脏起搏术。
1958年Peter Safar发明了口对口呼吸,1960年Kowenhoven等发明了胸外按压术。
20世纪60年代起将开放气道(airway)、口对口呼吸(breathe)和胸外按压(circulation)有机结合起来向广大医务人员和公众传播,使心肺复苏术得以推广,从此成千上万的心跳骤停病人得益于这项技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ABC为核心的基本生命支持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发展的重点在于心肺复苏术的普及推广和急救网络的建立,这样基本生命支持就可以在现场第一时间实施。
此外,高级生命支持不断发展完善,如电击除颤、肾上腺素使用、人工气道建立和脑复苏等。
同时从事心肺脑复苏的研究者,通过建立组织和学术交流将有关研究成果及时以指南的形式向公众发布,以规范技术操作和研究方法。
因此,心肺脑复苏必将使更多的病人受益。
【病因与发病机制】心跳骤停和呼吸骤停均可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而首先发生,由于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在维持生命中关系非常密切,任一系统衰竭均可迅速导致另一系统的衰竭。
心跳骤停后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心脏复苏药物应用进展更新日期:10-31 朱华栋周玉淑心脏骤停是临床上最危险的情况,必须争分夺秒进行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时除了进行心脏按压和呼吸支持等基本生命维持措施外,合理应用复苏药物也是决定心肺复苏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对复苏药物的应用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对提高心肺复苏的成功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对心脏骤停后的某些病理生理变化以及药物应用综述如下。
一、心脏骤停后的一些病理生理变化1.血循环中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心脏骤停后,血中内源性儿茶酚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急剧升高近50倍[1]。
如此高水平的儿茶酚胺却不足以维持动脉血压,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一些内源性的代谢产物抑制了儿茶酚胺的作用。
当给予外源性肾上腺素0.01~0.1mg/kg后,平均动脉压及舒张压比未用肾上腺素的对照组明显升高,这就是应用肾上腺素进行心脏复苏的理论依据。
2.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变化:心跳停止后,严重的缺氧和酸中毒使肾上腺素能α受体脱敏感或受体下调。
武建军等[2]观察了大鼠心脏停搏期间α1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变化,结果示心脏骤停早期心脏和肾脏α1受体数量明显下降,随心脏停搏时间延长,其数量又有增加趋势,可能的机制是心跳停止早期产生的大量内源性儿茶酚胺和受体结合,使细胞对受体的内吞作用加强,从而把细胞表面受体转移到细胞内,造成受体下调,随缺氧时间延长,细胞膜成分发生变化,细胞膜上原来隐匿的受体又重新显现出来,表现为受体上调。
3.血中其他血管活性肽类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心脏复苏成功后,血中血管加压素、血管紧张素Ⅱ和心房利钠因子较复苏前均有明显升高[3]。
血管加压素、血管紧张素Ⅱ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外周循环阻力,恢复自主循环,而心房利钠因子则可拮抗儿茶酚胺、血管加压素、血管紧张素Ⅱ的缩血管效应。
心跳停止后,内源性血管加压素、血管紧张素Ⅱ的水平增加,但并不足以恢复自主循环,而补充这些缩血管肽类可能对复苏有利。
心肺复苏研究的若干新进展作者:李春盛吴彩军来源:《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4年第01期自2010年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与心血管病急救(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ECC)指南(简称国际CPR指南)修订已经三年时间,每次指南的实践和推广,都会引起新的研究热点和理论争议。
随着循证医学与转化医学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CPR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通气在心肺复苏中的作用2010年国际CPR指南将成人和儿童(不包括新生儿)基本生命支持修订为“胸外按压-打开气道-人工呼吸”,将有效持续的胸外按压提高到CPR的首要位置[1]。
CPR基础生命支持中的通气与按压比一直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
按压与通气比从1992年5∶ 1,2000年15∶ 2一直到2005年和2010年30∶ 2的指南修订。
其目的是增加在实施心肺复苏过程中血液循环中断的血氧含量,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在CPR时是否需要进行通气。
研究表明,按压时不进行通气较按压时通气可以使研究对象的自主循环恢复成功率增加一倍[2]。
同时2010年CPR指南也指出,如果施救者不愿意做人工呼吸时可以仅行胸外按压。
笔者的实验研究证实,单纯胸外按压时被动通气可与低水平的肺血流灌注相匹配(V/Q比值稳定),同时叹息样呼吸也能提供一定量有效肺泡通气量,可满足机体复苏初期代谢的需要[3-4],但是对于长时间和非心源性心搏骤停(如窒息)的复苏,及早进行气道开放与管理仍然是必要的。
随着一系列新型气管插管设备的研发,不中断胸外按压进行高级人工气道的建立将成为可能[5]。
气管插管的重要性似乎被大众理所当然地接受。
因为理论上认为畅通气道,人工呼吸增加了肺泡通气量可能增加体内氧合,这种情况在窒息型的心搏骤停是有益的,但在大样本的院外心搏骤停复苏中人工气道并没有带来好处。
2013年JAMA杂志发表的一项纳入了649 359例成人院外心搏骤停患者院前不同气道管理方式与远期预后的研究发现,气管插管等高级气道管理与传统的面罩辅助通气相比较,有增加远期不良预后的风险[6],产生这样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在进行CPR时过度关注了高级人工气道的建立而延误或中断了胸外按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