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周作人的小品文
- 格式:ppt
- 大小:65.50 KB
- 文档页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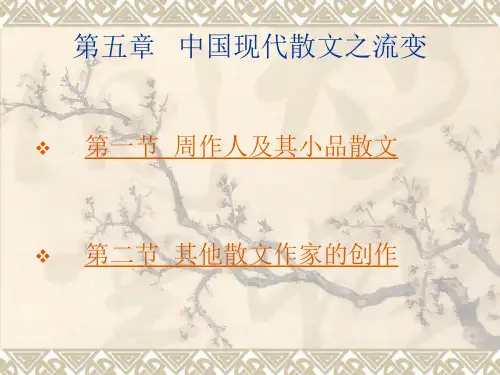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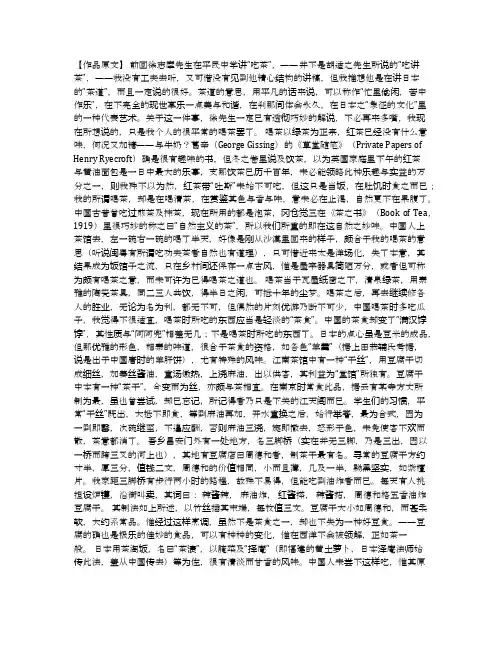
【作品原文】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而且一定说的很好。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在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吐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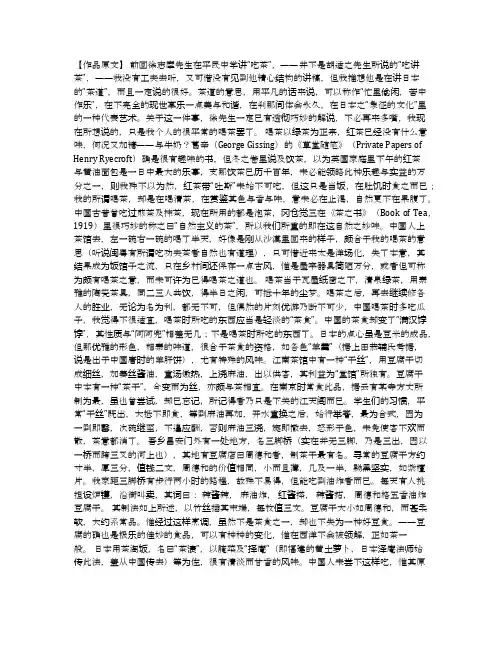
【作品原文】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而且一定说的很好。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在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吐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
![论周作人小品文中怀乡意识[论文]](https://uimg.taocdn.com/752a560ba6c30c2259019e47.webp)
论周作人小品文中的怀乡意识摘要:作为现代散文史的“开风气之先师”,周作人凭借独特的乡土理想,通过故乡的民俗化描写,寄托怀乡之情。
这些极具趣味性的民俗小品不仅是其独特审美特质的凝聚,还是其现实生活中矛盾复杂情绪的投射。
怀乡意识作为周作人笔下或隐或现的一条主线,联结了他的散文小品,也联结他备受争议的一生。
关键词:怀乡意识民俗大乡土理想泛乡五四以来,文学史上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诗歌之上,而被誉为“小品文之王”的周作人更是不可忽略。
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标记,为新文学印上“人”的标记,为散文打上“美文”的标记,为乡土文学打上“民俗”的标记。
在民俗散文的创作中,他主张“地方文艺”,力求开垦“自己的园地”,实现“生活的艺术”。
尤其在二十年代复归书斋与自我本位后,其文学创作迎来了全新的高峰。
乡土文学的“浙江潮”中,周作人笔下的故乡最具传统的水乡气息。
虽然他并非乡土文学的领军者,但是却在乡土的范围内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乡土世界。
周作人在乡土作家中的独特性在于在其怀乡意识,我认为他的“怀乡”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怀乡意识及复杂体现,另一部分是他的大乡土理想表现出的泛乡观。
两部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民俗小品文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可作为研究周氏乡土理论的合理切入点。
这种怀乡意识表现在散文中的就是对家乡风物的倾尽描绘。
周作人在自编文集中引言“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致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
浙东的民俗风物无疑是其创作灵感的源泉,而衍生出的水乡文化对周氏的精神气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笔下的民俗意象可以分为水意象、极富水乡气息的江南人文意象及鬼意象三类。
他说,“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
”[1]对于水意象,也坦言“生平与水太相习了,自有一种情分,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
其笔下的水意象是一个群体,其中不仅包含真实的雨、河流、溪水一类的自然事物,还包含与水相关的事物和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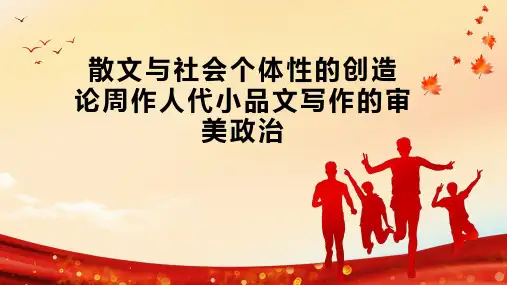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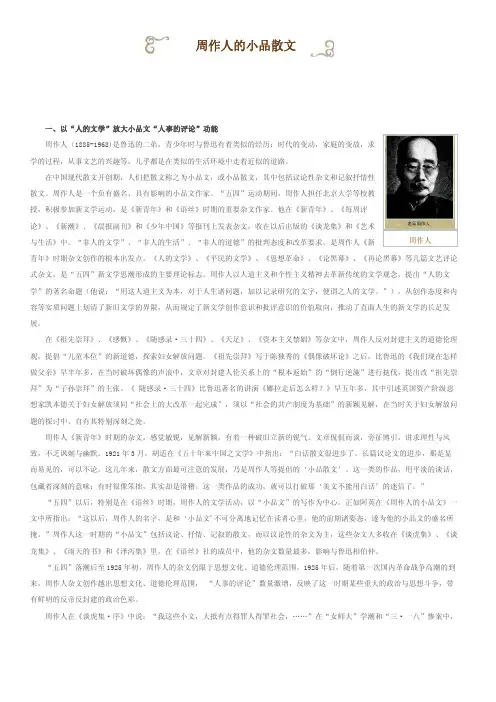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一、以“人的文学”放大小品文“人事的评论”功能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道路。
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人们把散文称之为小品文,或小品散文,其中包括议论性杂文和记叙抒情性散文。
周作人是一个负有盛名、具有影响的小品文作家。
“五四”运动期间,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和《语丝》时期的重要杂文作家。
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和《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收在以后出版的《谈龙集》和《艺术周作人与生活》中。
“非人的文学”、“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的批判态度和改革要求,是周作人《新青年》时期杂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再论黑幕》等几篇文艺评论式杂文,是“五四”新文学思潮形成的主要理论标志。
周作人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从创作态度和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从而规定了新文学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的价值取向,推动了直面人生的新文学的长足发展。
在《祖先崇拜》、《感慨》、《随感录·三十四》、《天足》、《资本主义禁娼》等杂文中,周作人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提倡“儿童本位”的新道德,探索妇女解放问题。
《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之后,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早半年多,在当时破坏偶像的声浪中,文章对封建人伦关系上的“根本返始”的“倒行逆施”进行挞伐,提出改“祖先崇拜”为“子孙崇拜”的主张。
《 随感录·三十四》比鲁迅著名的讲演《娜拉走后怎么样?》早五年多,其中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在当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自有其特别深刻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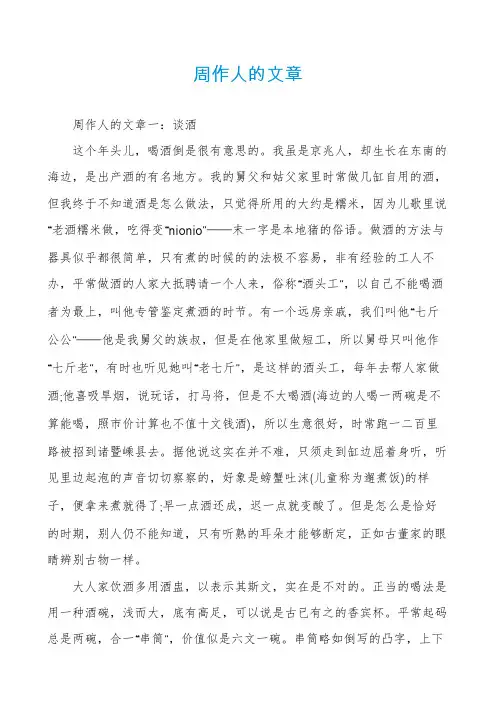
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的文章一:谈酒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
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
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猪的俗语。
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的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
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马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
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象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邂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成,迟一点就变酸了。
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
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宾杯。
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
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
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值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
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
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
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响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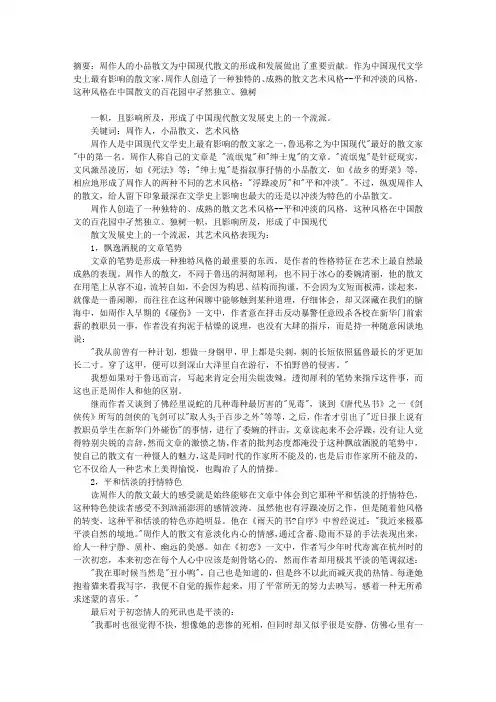
摘要: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独立、独树一帜,且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关键词: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风格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之一,鲁迅称之为中国现代"最好的散文家"中的第一名。
周作人称自己的文章是 "流氓鬼"和"绅士鬼"的文章。
"流氓鬼"是针砭现实,文风激昂凌厉,如《死法》等;"绅士鬼"是指叙事抒情的小品散文,如《故乡的野菜》等,相应地形成了周作人的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
不过,纵观周作人的散文,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在文学史上影响也最大的还是以冲淡为特色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独立、独树一帜,且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其艺术风格表现为:1,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文章的笔势是形成一种独特风格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性格特征在艺术上最自然最成熟的表现。
周作人的散文,不同于鲁迅的洞彻犀利,也不同于冰心的委婉清丽,他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不会因为构思、结构而拘谨,不会因为文短而板滞,读起来,就像是一番闲聊,而往往在这种闲聊中能够触到某种道理,仔细体会,却又深藏在我们的脑海中,如周作人早期的《碰伤》一文中,作者意在抨击反动暴警任意殴杀各校在新华门前索薪的教职员一事,作者没有拘泥于枯燥的说理,也没有大肆的指斥,而是持一种随意闲谈地说:"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
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
![[解读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文化情怀]周作人小品散文的特点](https://uimg.taocdn.com/6c8ed56d793e0912a21614791711cc7931b778e1.webp)
[解读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文化情怀]周作人小品散文的特点在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盛极一时,而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情怀更是为当时及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所激赏、神往。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中一以贯之的追求趣味、表现趣味的审美态度,亲切、自然地导引读者从平凡生活走进美的所在,在平淡冲和的文字中得到净化和启悟。
周作人“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的文化情怀贴近人性,自然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
一周作人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小品散文,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喝茶》等,大都是谈人生与艺术的“趣味之文”。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一般都认为是西方随笔的“自我表现”与我国明代文人小品的“独抒性灵”的完美融合。
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他所倡导的“言志”,是“抒我之情”、“载自己之道”,而非代人之言,“载他人之道”。
从1922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作人就与各种各样的“大名义”自觉保持距离。
1924年在《喝茶》一文中声言“茶道”。
即“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27,这成为日后周作人的生活信条。
现实人生注定是不完满的,然而周作人认为我们依然有可能体会生活之美和人生之乐。
他说快乐的真意是能在心灵放松的瞬间求得“美与和谐”。
他将这样的瞬间称作“偶然的片刻优游”,而获取的方式很多,你可以“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或者,坐在乌篷船里,以“游山的态度”(当然“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口,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周作人有自己的坚持:我们在生活中,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
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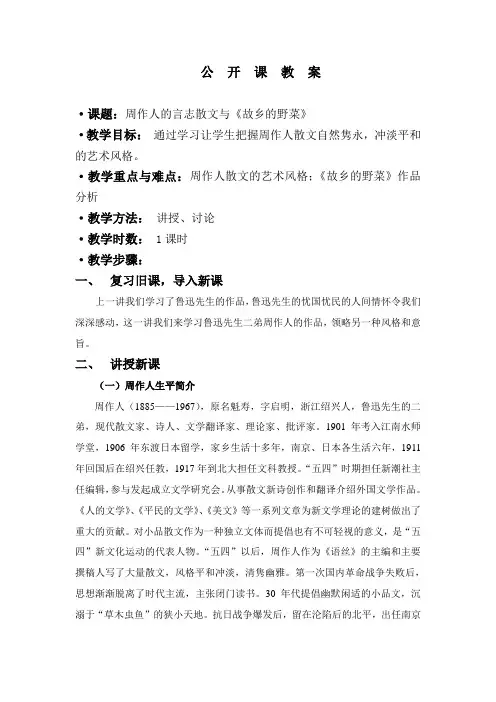
公开课教案·课题:周作人的言志散文与《故乡的野菜》·教学目标:通过学习让学生把握周作人散文自然隽永,冲淡平和的艺术风格。
·教学重点与难点: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故乡的野菜》作品分析·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教学时数: 1课时·教学步骤: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上一讲我们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的忧国忧民的人间情怀令我们深深感动,这一讲我们来学习鲁迅先生二弟周作人的作品,领略另一种风格和意旨。
二、讲授新课(一)周作人生平简介周作人(1885——1967),原名魁寿,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的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理论家、批评家。
1901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家乡生活十多年,南京、日本各生活六年,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教,1917年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担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美文》等一系列文章为新文学理论的建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小品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而提倡也有不可轻视的意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主张闭门读书。
30年代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1945年以叛国罪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写一些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文章,1967年死于文革。
(二)周作人散文创作分期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代宗师,“美文”的首倡者。
他的散文创作极其丰富,从“五四”前后到1945年,二十二部散文集加上未成集的总计有三千多篇,大多数为小品散文,有小品散文之王的美称。
[复习]周作人《乌篷船》赏析《乌篷船》一、周作人及其散文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
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
1949年1月保释出狱。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
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
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周作人的散文中令人感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感不到有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
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蓄于中的激情舒缓的、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周作人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到来,无所拘束。
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得枝蔓。
因而,读他的散文,有和与老朋友无拘无束闲谈的感觉。
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周作人的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无论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讽刺性的杂文,写得不板滞,有趣味。
文中有时庄中有谐,有时谐中有庄,有时又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
神人共同参与的宇宙庆典,天子、诸侯、卿大夫以至于士子、庶民,由此突破了生死形魂、人神幽明的界限,在至诚的爱敬之心中,摆脱私心妄念的羁绊,与天地鬼神一体共存,此即所谓“乐”。
《礼记》云:“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
”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通过全民参与祭献而生发的天人一体之“乐”得以弥合。
古代祭祀尤其祭祀天地神明,是社会性、国家性的大典,需要聚合百工万民的人力和资源才能举行。
凭借祭祀,天下之人心、物力皆被引向超越的存在,从而得到洁净、转化,凝聚成为符合天道、天志的积极力量。
考古发现证实了祭祀在礼制社会的重要性,从出土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王几乎每天都忙于各种献祭活动。
刘师培先生认为上古之时,祭礼包摄一切礼制宗法,一切政治制度,所谓“舍祭礼而外无典礼,亦舍祭祀而外无政事也”。
甚至连学术都源于祭祀,“既崇祭祀则一切术数之学由是而生”。
此外,华夏上古也有颇类似于吠陀种姓法的等级制度。
这一点,刘先生在《阶级原始论》中早已指出:“大约古代居上位之人,祭司最尊,武人次之,富民次之,而祭司必有学,如印度之有婆罗门是也。
”刘师培并且认为“古代之时阶级有贵贱之分,职业无贵贱之分”,“此则古制之迈于天竺者也”,其实,以德、业分判种姓,正是吠陀种姓法之理想。
(待续)周作人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又是现代民俗学理论的引介者。
文学实践与民俗考察的相互融合构成他写作生涯中庞大而关键的一环,正如《地方与文艺》中所述:“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
”周作人以小品文为主要体例的文学创作历来对习俗民风、神话传说、花鸟虫鱼、器物吃食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源自民间生活经验的“土气息泥滋味”浸淫着他的笔端,无疑是造就其思想谱系与美学风貌的重要部分。
周作人的民俗学写作大多集中于其创作早期,即五四精神作为文化底色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梁实秋《雅舍小品》忆周作人先生梁实秋《雅舍小品》忆周作人先生引导语:梁实秋与周作人的友谊是如何的呢?下面是有关《雅舍小品》中的会忆周作人先生的事情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湾,看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胡同。
但是在这个陋巷里却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
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
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
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
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
地上铺着凉席。
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
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
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
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
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后来他改斋名为“苦茶庵”了)。
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
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
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
周作人散文我不是清教徒,并不反对有娱乐。
明末谢在杭著《五杂俎》卷二有云:“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锄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损比也,”清初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
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
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
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塞川使之不流,无怪具决裂溃败也。
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爱以图治,不亦难乎。
”又清末徐仲可著《大受堂札记》卷五云:“儿童臾妪皆有历史观念。
于何征之,征之于吾家。
光绪丙申居萧山,吾子新六方七龄,自塾归,老佣赵馀庆于灯下告以戏剧所演古事如三国志水游传等,新六闻之手舞足蹈。
乙丑居上海,孙大春八龄,女孙大庆九龄大庚六龄,皆喜就杨媪王媪听谈话,所语亦戏剧中事,杨京兆人谓之曰讲古今,玉绍兴人谓之曰说故事,三孩端坐倾听,乐以忘寝。
坷于是知戏剧有启牖社会之力,未可以淫盗之事导人入于歧途,且又知力足以延保姆者之尤有益于儿童也。
”三人所说都有道理,徐君的话自然要算最浅,不过社会教育的普通话,刘君能看出六经的本相来,却是绝大见识,这一方面使人知道民俗之重要性,别一方面可以少开儒者一流的茅塞,是很有意义的事。
谢君谈民间习俗而注意经济问题,也很可佩服,这与我不赞成禁止社戏的意思相似,虽然我并不着重消费的方面,只是觉得生活应该有张弛,高攀一点也可以说不过是柳子厚题毛颖传里的有些话而已。
我所谓娱乐的范围颇广,自竞渡游者以至讲古今,或坐茶店,站门口,嗑瓜子,抽旱烟之类,凡是生活上的转换,非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者,都可算在里边,为得要使生活与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这种休养是必要的,不过这里似乎也不可不有个限制,正如在一切事上一样,即是这必须是自由的,不,自己要自由,还要以他人的自由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