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资料共75页
- 格式:ppt
- 大小:7.57 MB
- 文档页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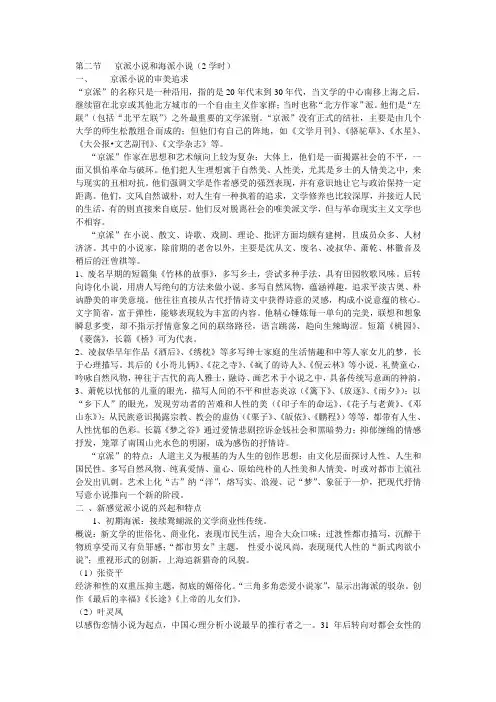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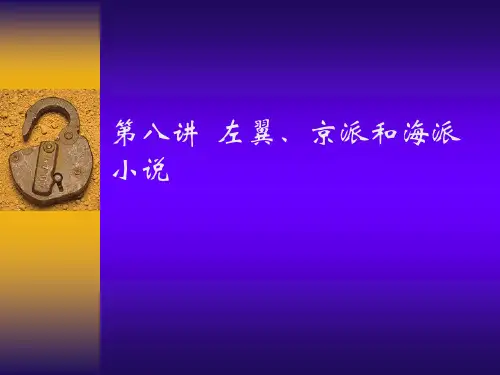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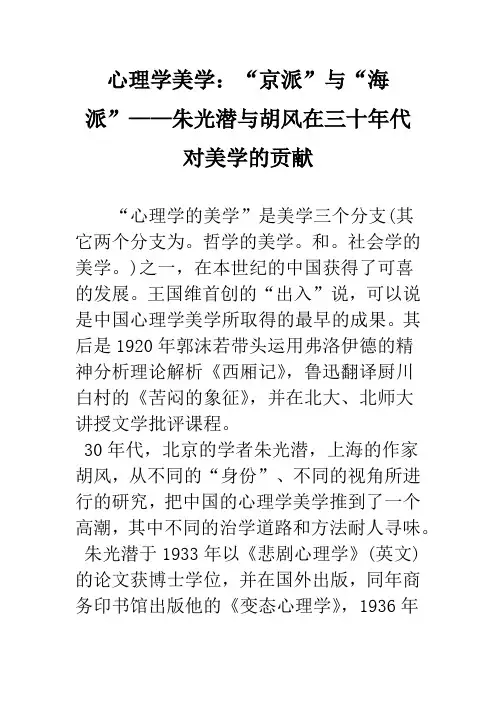
心理学美学:“京派”与“海派”——朱光潜与胡风在三十年代对美学的贡献“心理学的美学”是美学三个分支(其它两个分支为。
哲学的美学。
和。
社会学的美学。
)之一,在本世纪的中国获得了可喜的发展。
王国维首创的“出入”说,可以说是中国心理学美学所取得的最早的成果。
其后是1920年郭沫若带头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析《西厢记》,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北大、北师大讲授文学批评课程。
30年代,北京的学者朱光潜,上海的作家胡风,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把中国的心理学美学推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不同的治学道路和方法耐人寻味。
朱光潜于1933年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变态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早于1931年完成的《文艺心理学》。
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正式成熟。
特别是《文艺心理学》一书,将西方本世纪以来文艺心理学的几个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加以消化,结合中国古代的诗论以及古今中外的创作实例,作出了专题研究,尽管其观点未必周严,但为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意图是“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那么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美感经验”。
这样作者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美感经验的特征”,对此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1、美感经验是一种凝神的境界。
在凝神境界中,我们不但忘却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并且忘记我们自己的存在。
欣赏的对象成为孤立绝缘的意象,欣赏者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它、赏玩它。
这种把一切都忘却的境界,也就是形象的直觉,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
美感经验就是直觉欣赏中的形象,而把物与我以外的事物的关系置之度外,在聚精会神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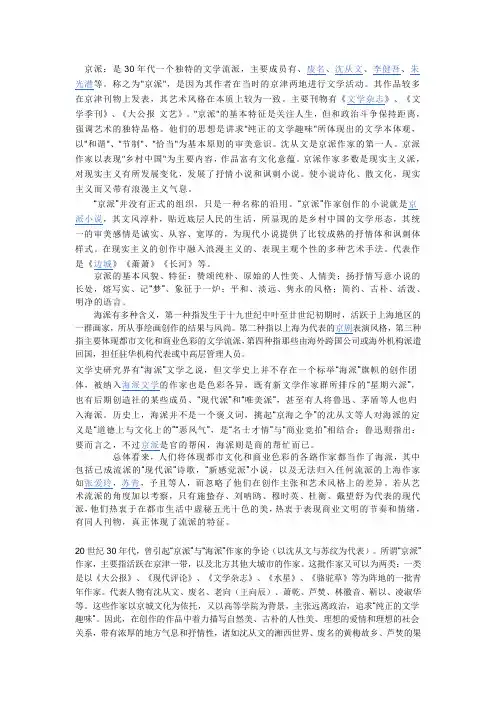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
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
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
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
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
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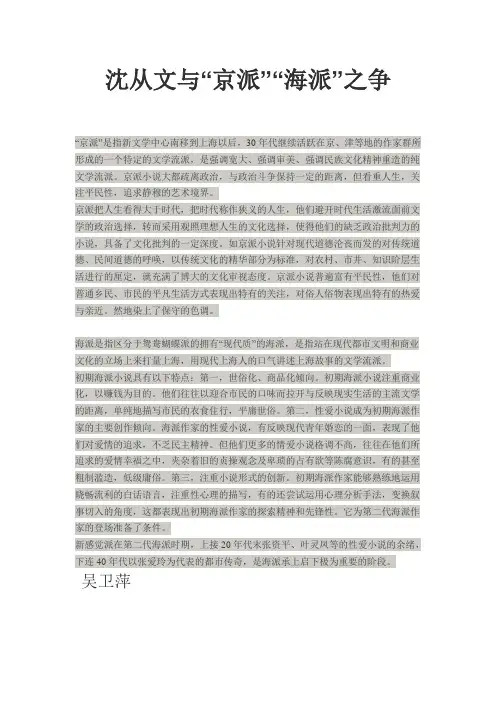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
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
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
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
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
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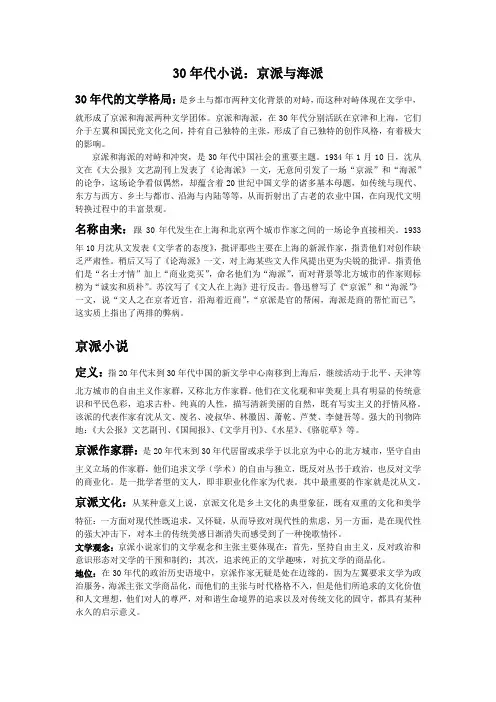
30年代小说:京派与海派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
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名称由来:跟30年代发生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严肃性。
稍后又写了《论海派》一文,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更为尖锐的批评。
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竞买”,命名他们为“海派”,而对背景等北方城市的作家则标榜为“诚实和质朴”。
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进行反击。
鲁迅曾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着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实质上指出了两排的弊病。
京派小说定义:指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国的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继续活动于北平、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又称北方作家群。
他们在文化观和审美观上具有明显的传统意识和平民色彩,追求古朴、纯真的人性,描写清新美丽的自然,既有写实主义的抒情风格。
该派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芦焚、李健吾等。
强大的刊物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报》、《文学月刊》、《水星》、《骆驼草》等。
京派作家群: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丛书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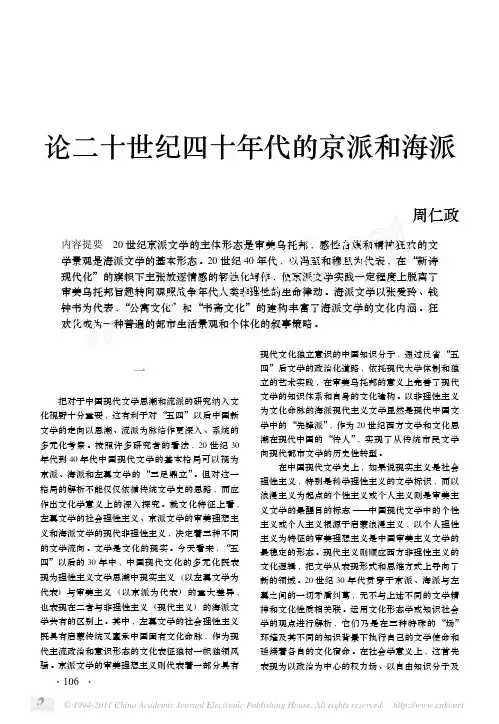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周仁政内容提要 20世纪京派文学的主体形态是审美乌托邦,感性自娱和精神狂欢的文学景观是海派文学的基本形态。
20世纪40年代,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在“新诗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放逐情感的智性化写作,使京派文学实践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审美乌托邦旨趣转向观照战争年代人类非理性的生命律动。
海派文学以张爱玲、钱钟书为代表,“公寓文化”和“书斋文化”的建构丰富了海派文学的文化内涵。
狂欢化成为一种普遍的都市生活景观和个体化的叙事策略。
一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纳入文化视野十分重要,这有利于对“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走向以思潮、流派为脉络作更深入、系统的多元化考察。
按照许多研究者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可以视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的“三足鼎立”。
但对这一格局的解析不能仅仅依循传统文学史的思路,而应作出文化学意义上的深入探究。
就文化特征上看,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和海派文学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决定着三种不同的文学流向。
文学是文化的现实。
今天看来,“五四”以后的30年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既表现为理性主义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以左翼文学为代表)与审美主义(以京派为代表)的重大差异,也表现在二者与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海派文学共有的区别上。
其中,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既具有启蒙传统又禀承中国固有文化命脉,作为现代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则代表着一部分具有现代文化独立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反省“五四”后文学的政治化道路,依托现代大学体制和独立的艺术实践,在审美乌托邦的意义上完善了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自身的文化建构。
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命脉的海派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派”,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人”,实现了从传统市民文学向现代都市文学的历史性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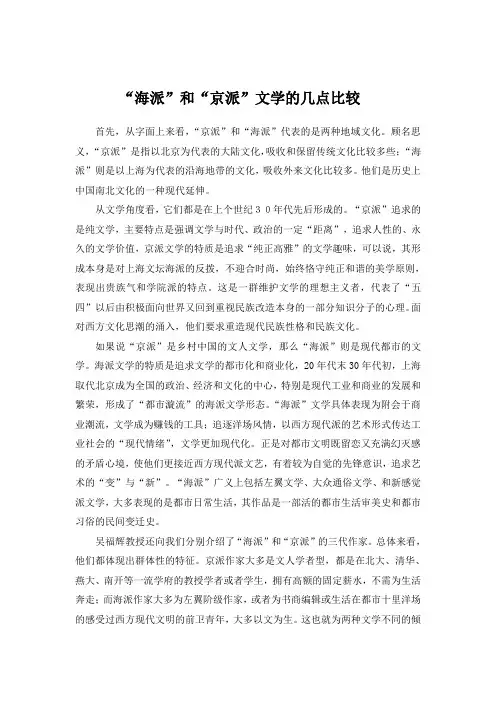
“海派”和“京派”文学的几点比较首先,从字面上来看,“京派”和“海派”代表的是两种地域文化。
顾名思义,“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京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纯正高雅”的文学趣味,可以说,其形成本身是对上海文坛海派的反拨,不迎合时尚,始终恪守纯正和谐的美学原则,表现出贵族气和学院派的特点。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他们要求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文学的都市化和商业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学形态。
“海派”文学具体表现为附会于商业潮流,文学成为赚钱的工具;追逐洋场风情,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形式传达工业社会的“现代情绪”,文学更加现代化。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海派”广义上包括左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大多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吴福辉教授还向我们分别介绍了“海派”和“京派”的三代作家。
总体来看,他们都体现出群体性的特征。
京派作家大多是文人学者型,都是在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一流学府的教授学者或者学生,拥有高额的固定薪水,不需为生活奔走;而海派作家大多为左翼阶级作家,或者为书商编辑或生活在都市十里洋场的感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前卫青年,大多以文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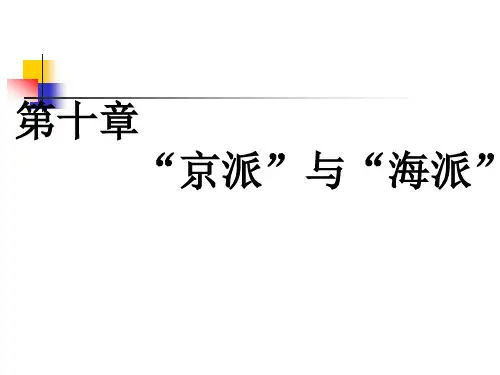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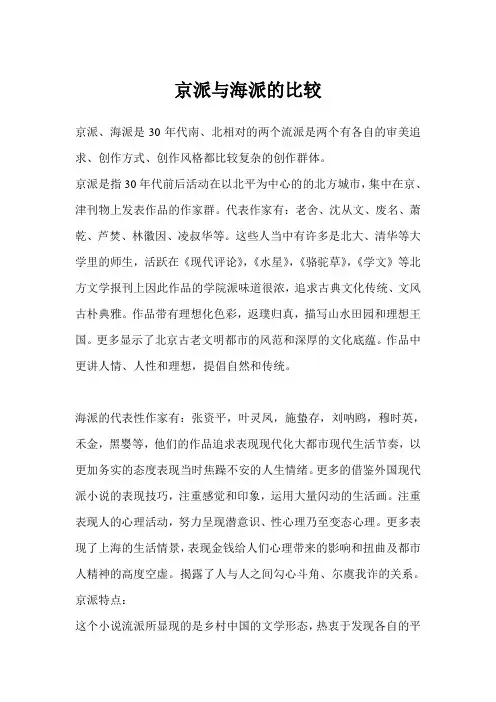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
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
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学文》等北方文学报刊上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
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
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
海派的代表性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禾金,黑婴等,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
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
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
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
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
京派特点: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等。
它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态度使他们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
在新旧变革的漩涡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
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其避开当年激烈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
它是主张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
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但其作品均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哀伤的,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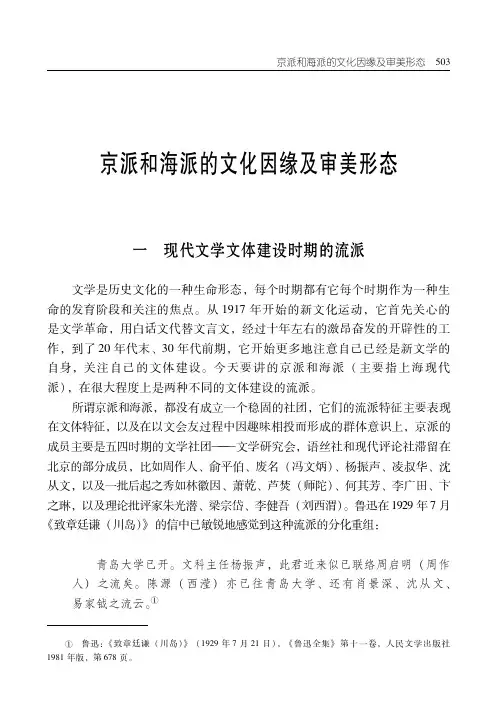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 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的流派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每个时期都有它每个时期作为一种生命的发育阶段和关注的焦点。
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关心的是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经过十年左右的激昂奋发的开辟性的工作,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它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已经是新文学的自身,关注自己的文体建设。
今天要讲的京派和海派(主要指上海现代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建设的流派。
所谓京派和海派,都没有成立一个稳固的社团,它们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体特征,以及在以文会友过程中因趣味相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上,京派的成员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滞留在北京的部分成员,比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理论批评家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刘西渭)。
鲁迅在1929年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已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流派的分化重组:青岛大学已开。
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
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①305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①鲁迅:《致章廷谦(川岛)》(1929年7月21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8页。
沈从文作为流派中人,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回忆道: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
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闲话海派与京朝派之新戏今日推送之《闲话海派与京朝派之新戏》录自《戏剧旬刊》1936年第17期,作者署名为叶慕秋,其在文中发表了对海派与京朝派所编新戏的看法,并借此提出了对旧剧改革的一些观点与言论。
近来颇有大部份人诋专在做工上轩轾人材,即谓海派专以做工取胜,其实亦非盲也,京朝派诸老角,亦何尝不在神情上或气度上舒展天才,如孙(菊仙)谭(鑫培)二人,以师承论,以格调论,孙高于谭多矣,而一则有口皆碑,一则褒贬互见者何也,叫天能体贴戏情,而菊仙不能体贴戏情也。
至于脚本,京朝派新戏,如四大名旦,皆按主演者之身份而编排,是其佳点,亦即系使其失败之处,如梅兰芳之《天女散花》《麻姑献寿》《晴雯撕扇》等,全集以花衫一人为重心,视花衫以外之角色,无足轻重,于主演者,自能发挥其天才,博观客之称赏,然意识方面,则殊缺乏,并嫌或贵族性质,故名旦陈德霖尝对其友论梅之新戏谓其一举一动,不越规矩,台步极有尺寸,细细味之,当能辨也,并谓当年昆剧中有《盘舞》一戏,今失传矣,梅之舞姿,纯脱胎此剧也,其《天女散花》诸戏,陈亦曾为参酌之,可见陈之重视于新戏也。
梅兰芳之《天女散花》海派新戏又不然,往往每一角于一剧中,连演数角,或小生或须生,或武生,博未一定,确实海派杰出人材,如用信芳等演戏未尝不认眞,更不可谓不善于体贴戏情者,然其演新戏无一定之专工,尤不免生疏,或过火之病,虽能迎合中下流人口味,然于戏剧之要旨,则难以附合矣,故其新戏不足一观也,而其脚本,极力赶重神怪、迷信,于京朝派有过之,规模结构,多就事实敷衍,而少裁制精神,身段唱工,又皆临时安排,乏研究之价值,故仅仅一般好奇而无智识之人,所附和,曩年多为一种不尚唱工之新戏,如《鄂州血》《新茶花》,以徧于社会,不久遭人厌弃,数年之间,遂形衰落,乃欲再祟尚旧戏,而是时京伶身价渐高,包银亦大,虽能哄动顾客,而支出既钜,维持亦难,故仍编排新剧,以布景欺人,不复顾及名誉,与舞台之价值,直是乌糟一片,大类乡间耍戏性质,不得称之为戏也,而海上人士,从而哄传,演必满座,后来者至无立足地,虽叫天兰芳,其盛况亦不过如是,此虽小道,而有关社会风尚,及民众之趋向至巨也,迄于今日,仍不知改革,且有甚于前者,一般之评剧家宗旨,亦复相同,不论其戏情,或戏之演出,但炫于美观,弃其菁华,存其渣泽,有益于旧剧,如是而已,确实此辈之行为心理,及眼光之卑劣,而欲其以改良风俗为前题,宁非缘木求鱼,且足使世风日益浇漓,多一般之伶人,亦根本不知责任所在,会亦云自欺欺人,纯盗灵声,人格二字,终其生不知尊重,以致为人唾弃,遭人斥责,伶人自取之耳,讵不惜哉。
曹聚仁:京派与海派京派与海派曹聚仁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三十二期,畅论海派文人的丑态。
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这就是所谓海派;邀集若干新斯文人,相聚一堂,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也就是所谓海派。
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也就是所谓海派。
”结末说:“妨害新文学健康处,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皆为这种海派的风气作祟。
”海派之罪大恶极至此,虽用最黑的咒语诅咒它灭亡,亦不为过。
然而,今日之“京派”有以异于“海派”乎?“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吾友”辛祖敛先生《论北平与上海》说,“京派的艺术家有梅博士足以代表,海派的艺术家则刘大师当仁不让。
”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
梅博士若笑刘大师卖野人头,刘大师必斥梅博士不懂文艺复兴。
试就京派之现状申论之,胡适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讲哲学史,也谈文学革命,也办《独立评论》,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异于沈从文先生所谓投机取巧者乎?曰:无以异也。
海派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而京派则独揽风雅,或替摆伦出百周纪念千周纪念,或调寄“秋兴”十首百首律诗关在玻璃房里,和现实隔绝;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文化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菊坛走马关于京剧,“京派”和“海派”的那些纷争你了解吗?说起京戏,一直有南北之分,所谓“京朝派”、“外江派”,也称之“京派”和“海派”。
“海派”也叫“南派”,但海派与南派却有所不同。
个人认为,南派是主要与京派相对立,京派主要指北京天津之地,而南派则是特指江南地区,“海派”似有贬义,相对于“京朝派”而言,那些野路子,只为混口饭吃,舞台上一招一式不按规矩,讨好观众,无端撒狗血的演员被京津地区的演员统称之“海派”。
但近些年,“海派”京剧雄起,观众市场不断扩大,似有垄断之意。
对于京剧来说,我认为“京朝”该向“海派”学习了。
迄今为止,京剧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以至于到达如今的局面。
但目前来看,京剧的未来到底如何?我想应该是要好好考虑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的文化也是百花齐放。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淘汰的艺术不胜枚举,能坚持走下去的艺术必定有其独特的魅力。
纵观过往,一门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必定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观众基础。
二百多年的时光对于人而言,已经足够长了,但对于历史来说,可能只是弹指一挥间。
对于京剧而言,我想,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只要能接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年轻的观众喜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够长久的存活下去。
是京派还是海派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谈到“京朝派”,不得不提朱家溍、刘曾复、吴小如、吴同宾、欧阳中石等诸位先生,这些先生是“京派”名票,而且都是京剧研究家,甚至得其梨园名宿们的真传。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京朝派”拥护者,也是坚定的“顽固派”。
他们对于京剧也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样的先生们常人认为他们一定对“海派”京剧持有怀疑态度。
但先生们不仅不排斥“海派”,而且极其支持海派。
吴小如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中提到麒派发展的时候,说到很多京派演员比不过南派演员。
明确的支持赞同海派。
这里想到一件事,吴小如先生对天津的武生厉慧良一直不赞同,认为他路子太野,随便改戏,实则毫无戏理。
什么是京派、海派、外江派?“京派”、“海派”、“外江派”的说法都是京剧向全国流布后的产物。
乾、嘉年间,中国有两大戏剧活动的中心,一是北京地区,一是以扬州为中心包括苏、沪、皖、浙的广大地区。
首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就是来自扬州的安庆徽部。
道、咸以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逐渐取代了扬州的地位而成为南方戏剧活动的中心。
京剧在北京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全国流布。
由于上海戏剧活动的繁盛,在同治年间不少京津的京剧名角被邀组班赴沪演出,很快在上海赢得了观众,站稳了脚跟。
原在上海演出的徽、昆班社大为冷落,不得不走向京班寻求出路。
于是在上海出现了徽京合流的新现象。
这一方面有助于京剧在上海和南方各地的流传,另一方面也使流传在南方的京剧带有更多的徽调色彩,从而带来了与北京的京剧多少有些不同的艺术特点。
更重要的,由于上海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使得当地观众的审美心理、艺术追求都更加倾向于求新、求变、求奇。
这也使得这里的京剧艺术在发展上呈现了与北方不同的取向。
京剧中最早的时事戏、外国戏、机关布景戏、真刀真枪戏、新连台本戏和京剧中最早的女演员、女班社都出现在上海,这不是偶然的。
上海京剧一般具有动作强烈、表演夸张、唱工花巧、剧情曲折、布景新奇等特色。
汪笑侬、潘月樵、夏氏兄弟(月珊、月润)、周信芳等植根于南方的京剧艺术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色。
南方京剧的以上特色与北京京剧界讲求唱、念、做、打功夫的扎实、严整,追求功架、板眼的中规中矩,服饰、道具的“宁破不错”,剧目、表演的师承有自等等,形成了很突出的差异。
北京的京剧界多少形成了一种故步自封的倾向。
这样,就出现了“京派”(或称“京朝派”)和“海派”(或称“外江派”——“外江派”一般除指上海的京剧外,还兼指全国其它地区的一些京剧流派,例如辽宁的唐(韵笙)派等)的称呼。
在北京的京剧界心目中,“海派”或“外江派”的称呼往往是带有某种轻蔑意味的。
但事实上,在京剧的发展中,京派与海派的壁垒也并非坚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