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de 女性主义解读
- 格式:doc
- 大小:20.5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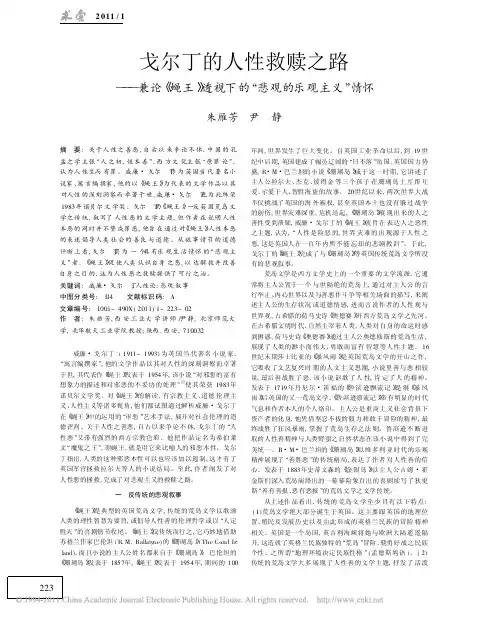
2011/1戈尔丁的人性救赎之路 兼论 蝇王 透视下的 悲观的乐观主义 情怀朱雁芳 尹 静摘 要:关于人性之善恶,自古以来争论不休,中国的孔孟之学主张 人之初,性本善 ,西方文化主张 原罪论 ,认为人性生而有罪。
威廉 戈尔丁作为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寓言编撰家,他的以 蝇王 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卓著于世,威廉 戈尔丁也为此殊荣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
戈尔丁的 蝇王 一反英国荒岛文学之传统,叙写了人性恶的文学主题,但作者在说明人性本恶的同时并不赞成罪恶,他旨在通过对 蝇王 人性本恶的表述倡导人类社会的善良与道德。
从故事情节的道德评断上看,戈尔丁实为一个具有乐观生活情怀的 悲观主义 者。
蝇王 促使人类认识自身之恶,以达解救并改善自身之目的,这为人性恶之救赎提供了可行之治。
关键词:威廉 戈尔丁;人性论;悲观叙事中图分类号:I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1)1-223-02作 者:朱雁芳,西安工业大学讲师/尹静,北京师范大学,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032威廉 戈尔丁(1911-1993)为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寓言编撰家 ,他的文学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卓著于世,其代表作 蝇王 发表于1954年,该小说 对邪恶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和对邪恶的不妥协的处理 使其荣获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
对 蝇王 的解读,有宗教主义、道德伦理主义、人性主义等诸多视角,他们都试图通过解析威廉 戈尔丁在 蝇王 中的运用的 审恶 艺术手法,展开对社会伦理的道德评判。
关于人性之善恶,自古以来争论不休,戈尔丁的 人性恶 又带有强烈的西方宗教色彩。
他把作品定名为希伯莱文 魔鬼之王 ,即蝇王,就是用它来比喻人的邪恶本性。
戈尔丁指出,人类的这种邪恶本性可以也应该加以遏制,这才有了英国军官拯救拉尔夫等人的小说结局。
至此,作者阐发了对人性恶的拯救,完成了对悲观主义的救赎之路。
一 反传统的悲观叙事蝇王 是典型的英国荒岛文学,传统的荒岛文学以歌颂人类的理性智慧为要旨,或倡导人性善的伦理哲学或以 人定胜天 的喜剧情节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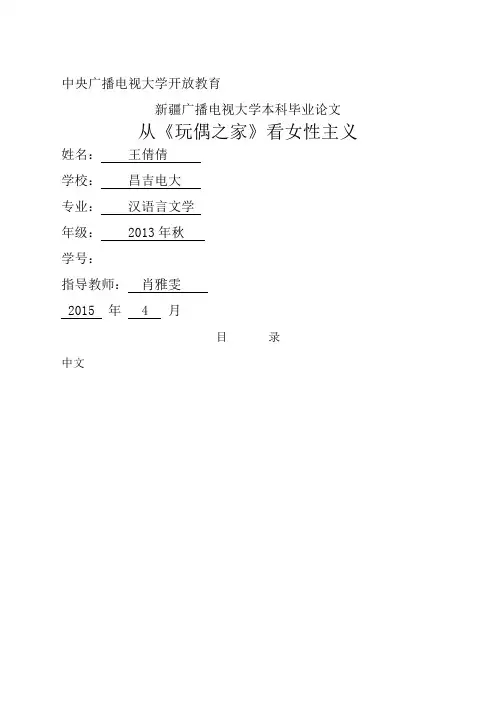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从《玩偶之家》看女性主义姓名:王倩倩学校:昌吉电大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 2013年秋学号:指导教师:肖雅雯2015 年 4 月目录中文摘要:从理论上讲“女性主义”就是强调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是对女性的一种价值肯定。
而“女性主义”的议题历来也是被人们普遍关注的。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出版于1879年,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剧作。
作品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提出了女性精神觉醒问题,并通过描写女主人公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玩偶”地位和她的丈夫海尔茂的伪善,展现给人们一幅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真实图景。
作品的女性精神觉醒主要是体现在女主人公娜拉身上,她从深爱、顺从、依赖丈夫到看清了丈夫的虚伪、自私、卑劣、渺小,最后她冲出了这个把她当做“玩偶”的家庭。
以行动宣告了一位女性同剥夺了做人的自由权的家庭的彻底决裂,表达了一位女性人格的转型和个性的最终觉醒《玩偶之家》的创作稍早于第一次女性主义高潮,却及时深刻的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了“女性主义”观点。
“娜拉”女性自我意识的树立和内在精神的独立充分体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不管是对西方还是中国的女性意识开启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社会地位婚姻家庭精神解放一、序论对于女性主义思想,挪威着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他的剧作《玩偶之家》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玩偶之家》于1879年出版,是易卜生创作中期中较早的一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剧作,是易卜生“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提出了妇女觉醒问题,并生动细致地展现了一位争取独立人格、具有时代精神的妇女的丰富内心世界的发展过程。
该剧从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出走而宣告“玩偶”生活的结束以及同剥夺了她自由权的家庭彻底决裂。
表达了一位女性人格的转型和人性的最终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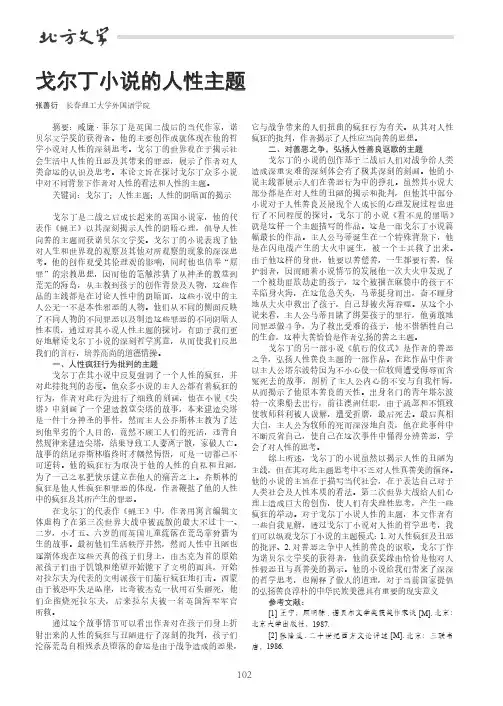
102戈尔丁小说的人性主题张善衍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威廉·菲尔丁是英国二战后的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他的主要创作成就体现在他的哲学小说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戈尔丁的世界观在于揭示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丑恶及其带来的罪恶,展示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及思考。
本论文旨在探讨戈尔丁众多小说中对不同背景下作者对人性的看法和人性的主题。
关键词:戈尔丁;人性主题;人性的阴暗面的揭示戈尔丁是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英国小说家,他的代表作《蝇王》以其深刻揭示人性的阴暗心理,倡导人性向善的主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戈尔丁的小说表现了他对人生和世界观的观察及其他对所观察的现象的深深思考。
他的创作观受其伦理观的影响,同时他也信奉“原罪”的宗教思想,因而他的笔触涉猎了从神圣的教堂到荒芜的海岛,从主教到孩子的创作背景及人物,这些作品的主线都是在讨论人性中的阴暗面,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本性邪恶的人物。
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罪恶以及制造这些罪恶的不同阴暗人性本质,通过对其小说人性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戈尔丁小说的深刻哲学寓意,从而使我们反思我们的言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一、人性疯狂行为批判的主题戈尔丁在其小说中反复强调了一个人性的疯狂,并对此持批判的态度。
他众多小说的主人公都有着疯狂的行为,作者对此行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他在小说《尖塔》中刻画了一个建造教堂尖塔的故事,本来建造尖塔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件,然而主人公乔斯林主教为了达到他卑劣的个人目的,竟然不顾工人们的死活,违背自然规律来建造尖塔,结果导致工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故事的结尾乔斯林临终时才幡然悔悟,可是一切都已不可逆转。
他的疯狂行为取决于他的人性的自私和丑陋,为了一己之私把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乔斯林的疯狂是他人性疯狂和罪恶的体现,作者鞭挞了他的人性中的疯狂及其所产生的罪恶。
在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中,作者用寓言编辑文体虚构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被疏散的最大不过十一、二岁,小才五、六岁的而英国儿童流落在荒岛靠狩猎为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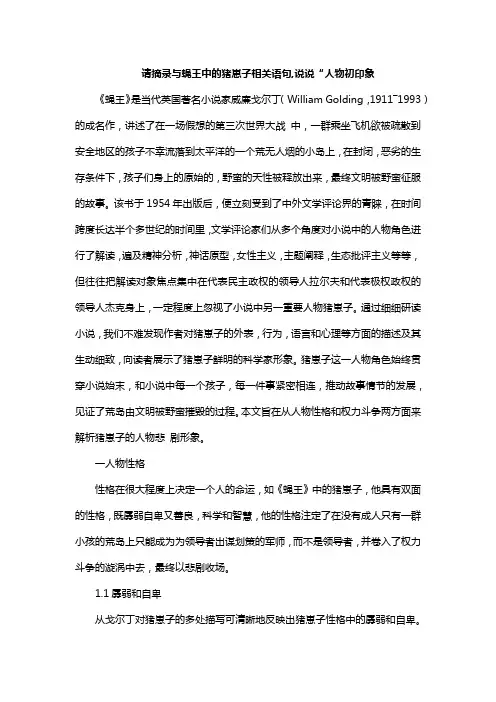
请摘录与蝇王中的猪崽子相关语句,说说“人物初印象《蝇王》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的成名作,讲述了在一场假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群乘坐飞机欲被疏散到安全地区的孩子不幸流落到太平洋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在封闭,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孩子们身上的原始的,野蛮的天性被释放出来,最终文明被野蛮征服的故事。
该书于1954年出版后,便立刻受到了中外文学评论界的青睐,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文学评论家们从多个角度对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进行了解读,遍及精神分析,神话原型,女性主义,主题阐释,生态批评主义等等,但往往把解读对象焦点集中在代表民主政权的领导人拉尔夫和代表极权政权的领导人杰克身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猪崽子。
通过细细研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猪崽子的外表,行为,语言和心理等方面的描述及其生动细致,向读者展示了猪崽子鲜明的科学家形象。
猪崽子这一人物角色始终贯穿小说始末,和小说中每一个孩子,每一件事紧密相连,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见证了荒岛由文明被野蛮摧毁的过程。
本文旨在从人物性格和权力斗争两方面来解析猪崽子的人物悲剧形象。
一人物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蝇王》中的猪崽子,他具有双面的性格,既孱弱自卑又善良,科学和智慧,他的性格注定了在没有成人只有一群小孩的荒岛上只能成为为领导者出谋划策的军师,而不是领导者,并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去,最终以悲剧收场。
1.1孱弱和自卑从戈尔丁对猪崽子的多处描写可清晰地反映出猪崽子性格中的孱弱和自卑。
首先,与拉尔夫等其他小孩相比,猪崽子身体条件比较弱。
猪崽子身形矮胖,是个近视,三岁就开始戴眼镜,从小就患有哮喘病,不能剧烈运动,行动缓慢。
小说中哮喘病已经超越了其医学含义,与猪崽子的人物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维拉伯兰特说:“患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
在文学介体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世界中的意义丰富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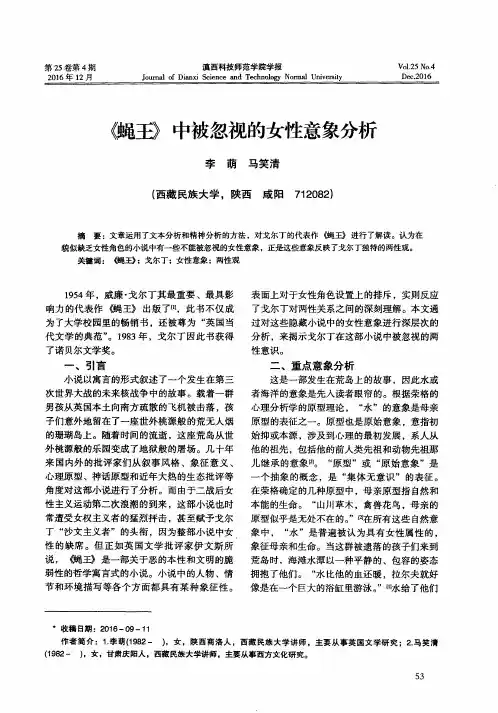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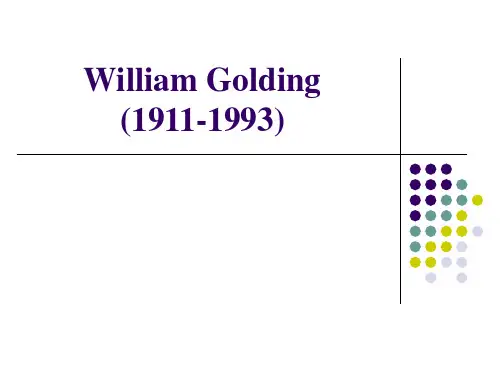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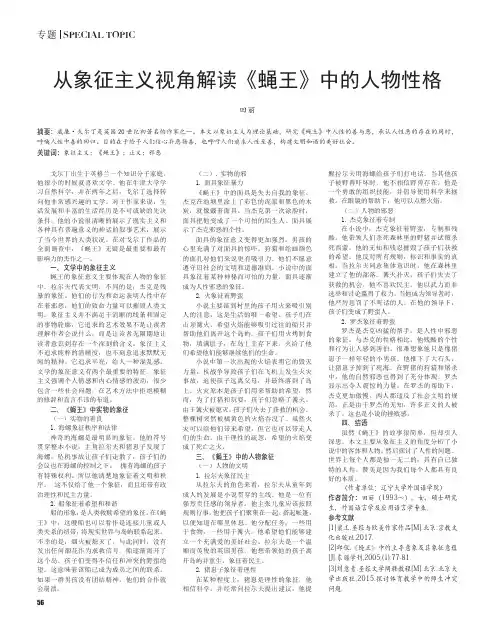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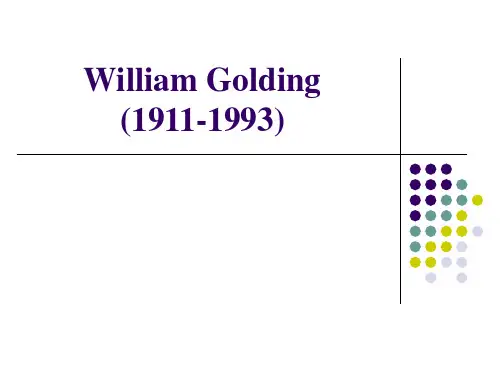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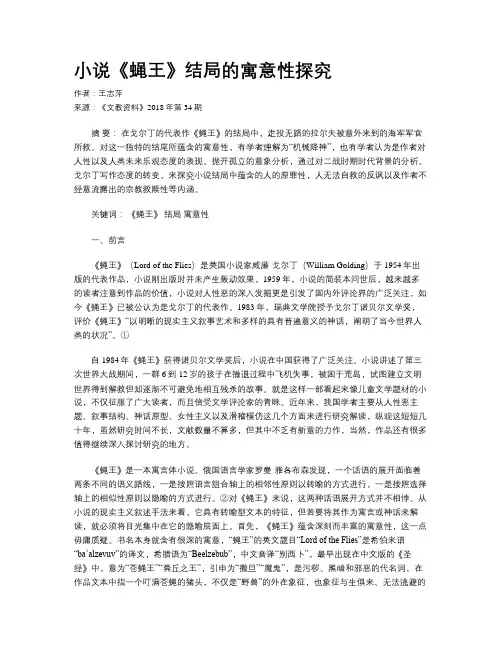
小说《蝇王》结局的寓意性探究作者:王志萍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34期摘要:在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的结局中,走投无路的拉尔夫被意外来到的海军军官所救。
对这一独特的结尾所蕴含的寓意性,有学者理解为“机械降神”,也有学者认为是作者对人性以及人类未来乐观态度的表现。
抛开孤立的意象分析,通过对二战时期时代背景的分析、戈尔丁写作态度的转变,来探究小说结局中蕴含的人的原罪性,人无法自救的反讽以及作者不经意流露出的宗教救赎性等内涵。
关键词:《蝇王》结局寓意性一、前言《蝇王》(Lord of the Flies)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于1954年出版的代表作品,小说刚出版时并未产生轰动效果,1959年,小说的简装本问世后,越来越多的读者注意到作品的价值,小说对人性恶的深入发掘更是引发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如今《蝇王》已被公认为是戈尔丁的代表作。
198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戈尔丁诺贝尔文学奖,评价《蝇王》“以明晰的现实主义叙事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
①自1984年《蝇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
小说讲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6到12岁的孩子在撤退过程中飞机失事,被困于荒岛,试图建立文明世界得到解救但却逐渐不可避免地相互残杀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部看起来像儿童文学题材的小说,不仅征服了广大读者,而且倍受文学评论家的青睐。
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从人性恶主题、叙事结构、神话原型、女性主义以及滑稽模仿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解读,纵观这短短几十年,虽然研究时间不长,文献数量不算多,但其中不乏有新意的力作,当然,作品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研究的地方。
《蝇王》是一本寓言体小说。
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发现,一个话语的展开面临着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一是按照语言组合轴上的相邻性原则以转喻的方式进行,一是按照选择轴上的相似性原则以隐喻的方式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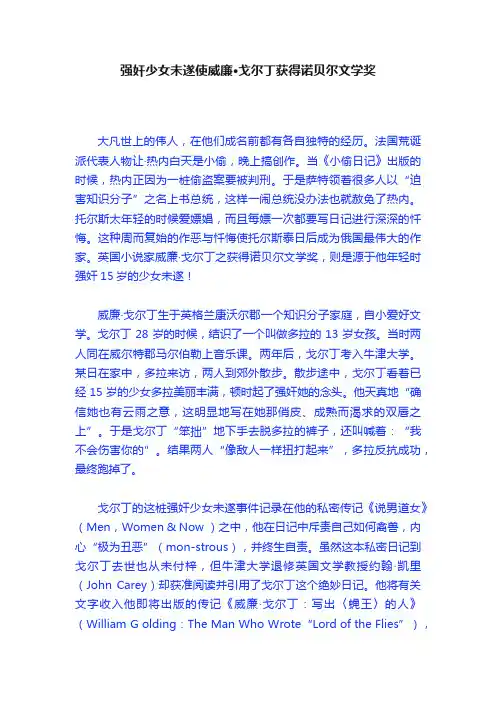
强奸少女未遂使威廉·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凡世上的伟人,在他们成名前都有各自独特的经历。
法国荒诞派代表人物让·热内白天是小偷,晚上搞创作。
当《小偷日记》出版的时候,热内正因为一桩偷盗案要被判刑。
于是萨特领着很多人以“迫害知识分子”之名上书总统,这样一闹总统没办法也就赦免了热内。
托尔斯太年轻的时候爱嫖娼,而且每嫖一次都要写日记进行深深的忏悔。
这种周而复始的作恶与忏悔使托尔斯泰日后成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是源于他年轻时强奸15岁的少女未遂!威廉·戈尔丁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爱好文学。
戈尔丁28岁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叫做多拉的13岁女孩。
当时两人同在威尔特郡马尔伯勒上音乐课。
两年后,戈尔丁考入牛津大学。
某日在家中,多拉来访,两人到郊外散步。
散步途中,戈尔丁看着已经15岁的少女多拉美丽丰满,顿时起了强奸她的念头。
他天真地“确信她也有云雨之意,这明显地写在她那俏皮、成熟而渴求的双唇之上”。
于是戈尔丁“笨拙”地下手去脱多拉的裤子,还叫喊着:“我不会伤害你的”。
结果两人“像敌人一样扭打起来”,多拉反抗成功,最终跑掉了。
戈尔丁的这桩强奸少女未遂事件记录在他的私密传记《说男道女》(Men,Women & Now )之中,他在日记中斥责自己如何禽兽,内心“极为丑恶”(mon-strous),并终生自责。
虽然这本私密日记到戈尔丁去世也从未付梓,但牛津大学退修英国文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 Carey)却获准阅读并引用了戈尔丁这个绝妙日记。
他将有关文字收入他即将出版的传记《威廉·戈尔丁:写出〈蝇王〉的人》(William G olding:The Man Who Wrote“Lord of the Flies”),才使读者对戈尔丁的这则逸闻趣事得以了解,并进而探讨为什么戈尔丁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性恶。
试析《蝇王》中人性的善与恶作者:李哲来源:《科技视界》 2015年第30期李哲(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北京 100083)【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四位主人公拉尔夫、杰克、西蒙和猪仔的人物性格的分析,揭示在荒岛这种特定环境中人性的善与恶的,以期加深对现实中人性善恶的感悟与理解,以及善恶之间的转换所造成的巨大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了作家威廉戈尔丁及其作品《蝇王》,继而讲述了四位主人公在荒岛的遭遇和经历,并对其性格做出分析,最后探讨了生活中的人性善恶,得出了人性的善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因素,并诠释了减少战争造成的的危害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人类的理性和善性。
【关键词】人性;善;恶;文明;性格0导言1)威廉·戈尔丁威廉·戈尔丁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
它曾在1940年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二战后,他又回到了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他在写作《蝇王》期间还在学校教书,之后他相继写作《继承者》、《平彻·马丁》、《赢得自由》、《金字塔》、《看得见的黑暗》、《航程祭典》、《纸人》、《近方位》、《巧语》等作品,他的作品惯用象征、荒诞、逆说、讽刺等,小说语言平淡又凝重。
《蝇王》出版于1954年,很快便成为畅销书,现如今已经成为英美国家课堂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书之一。
1983年,威廉·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文学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作家,《蝇王》对于威廉获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使他成为世界级的作家。
2)蝇王《蝇王》是威廉·戈尔丁最出名的小说,被誉为英国文学的典范,于1963年改编成一部电影。
《蝇王》突出了威廉·戈尔丁一直在探讨的主题:人性的善与恶,该书也奠定了戈尔丁的世界声誉,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文学瑰宝。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四个小男孩的生活展开:在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飞向南方,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机舱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他们为了生存相互争斗、杀害,充分展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
[作者简介]赵阳,内蒙古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蔡卫华,内蒙古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从《蝇王》中解读戈尔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赵阳蔡卫华(内蒙古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摘要]成廉·戈尔丁代表作小说《蝇王》自出版就受到广泛阅读和广受争议。
小说背景处于未来的一场核战争,记录了荒岛上男孩的生存。
就此小说,除了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辩论,批评家们还从多个角度对其主题意义以及叙事结构进行剖析。
但同时这部小说也体现了戈尔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谴责了西方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而小说中女性的缺席,却正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来抨击当时社会上蔓延的“父权制”,并进一步为读者展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紧密的联系。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充满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威廉·戈尔丁;《蝇王》;生态女性主义;女性缺席[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6-0113-02威廉·戈尔丁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 )于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赢得巨大的声誉,从而享有“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的称号。
《蝇王》是一部颇有争议的小说,完稿付梓时,曾遭到21家出版社的拒绝,但公开发表后,又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蝇王》创作的历史背景以二战为依托。
二战期间,威廉·戈尔丁参加了英国的皇家海军。
战争改变了他以前对人类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他决定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人性中邪恶的一面。
《蝇王》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的。
小说主要角色为一群6到12岁的孩子,背景是未来发生的一场核战争。
在运送儿童们去往安全之地的过程中,飞机被炸弹击中,孩子们被迫降落到一个荒岛上。
以拉尔夫为首的“文明”派试图建立规章制度,过有秩序的文明生活。
然而随着“野兽”的出现,孩子们身上原始野蛮的天性暴露出来,被杰克所利用。
第27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l27第3期Journal o fH ube iN or m a lU n i ve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 ence)N o.3,20075蝇王6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思考王勣(湖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北黄石435002)1摘要2 威廉#戈尔丁代表作小说5蝇王6自出版就受到广泛阅读和激烈争论,其中小说女性缺场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传统女性主义批评视之为男性主义经典,戈尔丁被冠以男性至上主义者。
但是,从5蝇王6的立意构思、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写作特征,以及从戈尔丁的家庭背景和他其余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入手进行新的思考,可知情况并非如此。
1关键词2 威廉#戈尔丁;5蝇王6;女性主义批评;回顾;新思考1中图分类号2I065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1009-4733(2007)03-0072-04一、引言威廉#戈尔丁(W illia m G o l d i ng)1954年出版的5蝇王6(L ord o f the F lies),获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从而享有/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0的称号。
5蝇王6是一部颇遭争议的小说,完稿付梓时,曾遭21家出版社拒绝,但公开发表后不久,又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1]。
它貌似一部科幻寓言神话、一本少年历险记,但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以及叙事语言使小说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普通儿童文学所能触及的。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揭开小说所展现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启示。
5蝇王6很多细节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断引发讨论和假设。
例如,小说描写人性,却在小说始终排斥了女性角色的出场。
/戈尔丁0专家莱利曾提出:/5蝇王6有父亲和儿子,却没有母亲和女儿,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省略。
[2]0在作者假想的核战争中,用飞机疏散孩子逃亡南方为什么没有带女孩子?飞机不幸被敌方击落,孩子们被迫降落在珊瑚岛上,美丽富饶的岛上为什么没有女性的出现?如果这群迷失自我的男孩子中有女性角色的参与,他们互相嗜血残杀的悲惨结局会不会避免?岛上唯一具有雌性特征的母猪被孩子们猎杀是否影射着作者对女性的某些观点?猎猪场景和猪头幻化为蝇王是对女性形象的诋毁还是对男权凶残的控诉和嘲弄?诸如此类的疑问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和大胆的女性文学再创作。
论文:《蝇王》的人性解读摘要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描写了人在失去约束时所表现出来的本性恶以及人性中潜在的善与恶的斗争。
自古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
戈尔丁无疑倾向于“人性恶”的观点,《蝇王》的写作主题便是人性恶。
戈尔丁用他所塑造的人物描绘了纯洁人性的丧失,以及潜伏在人性中的恶意识的膨胀。
戈尔丁之所以揭示人性中的恶、承认人性中的恶,是要摆脱他们,而非认同他们。
然而他却找不到救赎的途径,本来能担当救赎重任的理性和文明在人性恶意识的膨胀下败的一塌糊涂。
然而正是由于看见了人性之极恶才唤醒了内心深处的善。
关键词:戈尔丁;《蝇王》;人性恶;人性丧失;救赎幻灭;借恶扬善AbstractGolding made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rd of the Flies" in describing the loss of restraint shown by the time this cachexia and human potential in the struggle of good and evil. Since ancient times o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good and evil opinion, roughly as follows: On Xingshan, cachexia theory, there are good and evil are on. Golding undoubtedly tend to "people cachexia" point of view, "Lord of the Flies" is the theme of writing people cachexia. Golding used by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s he portrayed the loss of the purity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hidden in the sense of evil in the expansion. Golding has revealed the evil in human nature, to recognize the evil in human nature, is to steer away from them, rather than agree with them. However, he can not find the way to salvation and redemption have been able to play a heavy responsibility in a rational and civilized people cachexia lost consciousness expansion under the mess.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very human nature to see the evil only awakened the hearts of goodKeywords:Golding; "Lord of the Files"; t he man was born of evil nature; Loss of humanity; Salvation dashed; Yangshan by dioxin目录一、人性恶的主题 (1)二、纯洁人性的丧失 (3)三、理性救赎的幻灭 (6)四、借恶扬善 (9)五、结语 (10)注释 (10)参考文献 (11)谢辞 (11)威廉·杰拉尔德·戈尔丁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他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世界和社会所存在的缺陷而身感不安,他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蝇王》:海岛文学实验与生态寓言李道全【摘要】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经典小说<蝇王>,重新阐释戈尔丁的海岛文学实验.有别于以往的海岛叙事,戈尔丁关注海岛的命运,传递了强烈的生态关怀.然而长期以来,小说中"在场"的海岛遭受忽略,或是被视为"荒岛",这无疑归咎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无意识"的作祟.借由海岛文学实验,小说<蝇王>以生态寓言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了澳视生态责任的危害,要求反思和重构人类自身的文化.【期刊名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8)001【总页数】5页(P129-133)【关键词】《蝇王》;威廉·戈尔丁;生态批评;海岛;环境无意识【作者】李道全【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4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 illiam Golding, 1911—1993)在1954年发表了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奠定了自己的文坛地位。
阮炜认为这部小说“清楚地标示着英国小说未来发展的实验主义新方向”[1]。
的确,通过海岛文学实验戈尔丁展开想象,赋予小说《蝇王》丰富的潜能,让这部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
然而,这部小说在中国却长期陷入了“人性恶”主题定式。
自陈焜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发表《人性恶的忧虑:谈谈威廉·戈尔丁的〈蝇之王〉》以来,“人性恶”成为界定这部小说最为常用的标签语汇。
针对这一现象,张和龙指出,“从新时期之初一直到上世纪末,人们对《蝇王》的主题阐释与接受构成了一个突不破的人性恶的神话”[2]。
这一观点在王卫新《中国的〈蝇王〉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也得到呼应。
根据他的总结,小说《蝇王》的阐释主要有“人性恶的主题、叙事结构、神话原型解读、女性主义解读和滑稽模仿研究”几大研究趋势,认为“其他批评方法的应用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3]。
《金字塔》的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金字塔》进行解读。
从对父权制的反抗和对待爱情的态度两个角度,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两位主要女性角色在父权制压迫下不断追求自我的过程,表现了戈尔丁对女性的尊重和认同。
用女性视角来对《金字塔》的重新审视,有利于加深对该小说的研究。
关键词:威廉戈尔丁;《金字塔》;女性主义批评
一、引言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67 年出版《金字塔》(The Pyramid)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
它一改戈尔丁自《蝇王》起逐渐形成的寓言风格,而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置于典型的英国小城镇,将视线转向当代英国社会生活的现实。
小说从男主角奥利弗的第一人称的角度,将艾薇和彭斯等几名女主人公的命运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表现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压力对人格塑造的影响。
奥利弗是作者的“化身”,通过讲述他与几位女主人公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追求自我发展持积极肯定态度。
二、主要女性形象分析
1 艾薇――堕落女孩
艾薇的父亲巴伯科姆中士是一个残酷、专制的人,他把艾薇当成他的私人财产,不关心她的身心发展。
他还严格限制艾薇的自由,并因为她犯的小错而无情地惩罚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十分珍惜女儿的金十字项链,上面刻有“爱可以征服
一切”的题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给予艾薇父爱和温暖。
他所看重的只是金项链代表的物质财富,而不是上面铭刻的爱的力量。
这可以解释艾薇与奥利弗最后一次相遇时,对父亲的死表现的感情并不十分悲痛。
父亲的死彻底将艾薇从他的严重抑制中解放出来,并切断艾薇和斯城之间最后的联系。
她反抗父权制的勇气和决心令人钦佩,但她作为一个单身女孩,仍被束缚在一个更大的男权统治的笼子里。
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她尽一切努力保持精神的独立,并拒绝做男人的附属品,甚至不惜选择放荡作为反抗和报复的手段。
艾薇不同于以往传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
她在爱情中从没失去独立感,而是始终保持主体意识。
当她爱上罗伯特时,她并没表现出一般女孩面对男人的诱惑时的被动,相反却很活跃、勇敢。
她也能够从她自己的意志出发,选择奥利弗作为新男友,这表现了她想掌握主动权、追求男女平等和明智的生活态度。
当艾薇发现奥利弗像罗伯特一样,只是打着爱她的幌子而玩弄她时,她愤怒地哭诉:“你所要的只不过是我该死的身体,不是我!没有人要我,要的只是我该死的身体。
”……“你从来不爱我,谁也没有爱过我!我要人爱我,要人善待我”。
[1]这标志着艾薇对自身情况的觉醒和幻想的最终破灭。
在男权社会中,贞节被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它强化了男人对女人单方面的限制。
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幻想破灭和对环境的失望,艾薇采取放荡这一极端的方式与所谓的女性美德抗争,并离开斯城,前往伦敦寻求更高的物质生活。
艾薇离开斯城是其“堕落行为”――在琼斯医生嘴角留下吻痕被小镇居民发现的结果。
斯城赶她走,她也同样厌恶这个地方,因此选择放荡作为对这个肮脏的世界的反抗。
她将走上堕落的道路作为一种手段,来反抗她从男权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因为这些人利用她来满足自己,她也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艾薇实际上比斯城道貌岸然的男人更纯洁。
两年后,艾薇回到斯城参加父亲的葬礼时,与奥利弗最后一次见面。
她在公共场合谎斥奥利弗在她十五岁时强奸了她,用极端的方式报复奥利弗之前给她带来的伤害。
奥利弗对她肆无忌惮的行为感到震惊,但也认识到自己给艾薇带来的痛苦,当他“伫立着,既羞愧又迷惑,尽管一腔怒意,却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另外的一个艾薇,一个一生都在挣扎着要成为纯洁可爱的人的艾薇”。
[2]奥利弗的心理变化标志着男人开始承认女性的作为人而不是附属品的存在,并开始将他们视为平等的独立的人。
这表明女性为她们的价值观获得社会认可的斗争最终对传统父权文化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
2 彭斯――疯女人
彭斯的父亲老道利什先生是一个专横的人,在彭斯小时候经常因为彭斯犯的微不足道的错误而体罚她。
彭斯在父亲的压迫下成长,并逐渐获得了沉闷的性格。
老道利什先生通过强调他的口头禅“天堂即音乐”将彭斯从精神上变为音乐的奴隶。
这个所谓的格言,更像一个诅咒,印在彭斯的一生,甚至伴随她走进坟墓(彭斯的墓碑上也刻着这句话)。
在父亲的严厉约束下,彭斯在不知不觉中抹去自己的个性和对生活的热情,将自己降低为无性生物――至少在外表上她似乎是无性的。
在彭斯的故事中对性别的忽略,正是父权制从心理上抑制女性的体现。
奥利弗作为她音乐课的学生,是她的生活片段的见证。
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在彭斯的房间有“一张一个女人头戴帽子身着礼服的棕色大照片,另一张是一个男人阴沉地越过我的头顶凝视着室内的棕色大照片”。
[3]后面那个男人,我们可以从后文得到暗示,正是老道利什先生。
这代表家长制的权威一直在监视着女性,而女性在男权统治下处于被监视中,从而反映出妇女作为附属品的存在。
男性对女性的注视往往包含监督和恐吓,暗示着某种绝对权威。
从彭斯房间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的老道利什先生通过他的冰冷凝视,将整个房间置于他的监督之下。
而另一张照片中,头戴帽子身着礼服的女人,可能是彭斯的母亲或她自己,无论是谁,都没
有办法逃离穿过房间的黯淡目光所代表的男性的精神统治。
因此,彭斯的悲剧虽然与艾薇表面不同,但本质上一致,两人都承受了父权制残酷的统治,阻碍她们对生活的真诚追求与事业的成就。
与来自下层阶级的艾薇不同,彭斯属于斯城的上层阶级。
与下层女孩艾薇靠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愿望并赢得更好的生活相比,彭斯有更有利的条件获得幸福,可她一生孤苦,活在小镇居民的冷漠中。
与艾薇相比,彭斯其貌不扬,并且打扮很中性,因此很少受到男人注意。
漂亮的艾薇从男人那里接受的都是虚情假意,彭斯却连享受男人的虚伪爱情的机会都没有。
彭斯对亨利的爱没有任何世俗的考虑。
她的爱与亨利的有目的爱形成鲜明对比――亨利不过是想利用她的感情和财富获得事业上的物质利益,并在斯城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种讽刺表现出男性和女性对爱情和生活的不同态度。
男人可能会专注于物质利益,而把爱情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相反,女性重视天真的、一尘不染的感情,并更积极和无畏地坚持自己的理想。
彭斯的命运注定是悲剧,因为她的天真与亨利的虚伪格格不入。
亨利让她享受到爱情的短暂如曙光般的欢乐,这激起了她的女性意识。
彭斯在认识亨利前,“看起来更像是中性而非女性”[4],是爱情唤醒了彭斯,引起她对生活的热情,鼓励她实现自我。
彭斯开始从内到外改变自己,她的脸变得“神奇地柔和了,而且容光焕发――如果不可称之为年轻,至少也有着一丝青春的暗示,一抹少女的记忆”。
[5]她努力展示最迷人的一面,这更加深了她的故事的悲剧性,因为她奉献的爱注定没有回报。
彭斯勇敢的爱变成斯城的一个笑柄,因为亨利实际上已经结婚,并当面拒绝了她的求婚。
在绝望和痛苦中,她恢复了以前的中性打扮,带着尊严忍受着这一沉重打击。
从那以后,彭斯一步一步迈向疯狂。
她曾经诚恳地对亨利说:“我所求的只是叫你需要我,需要我!”[6]几年后,彭斯在小镇裸行,这标志着她完全疯狂。
米歇尔?福柯曾说:“疯狂的最
后一种是绝望的爱情……它包括想象中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它用不寻常的喜悦和无意义的勇敢弥补了这一缺陷”。
[7] 彭斯的疯狂不仅是男性压制的结果,也是她自己对男权文化的选择的极端对抗。
男权文化强调意义和秩序,认为理智应该优先于感性。
而彭斯无法学会其他人的虚伪,坚持追求爱情和真诚,注定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
为了否定男性理性的优点,彭斯活在自己的疯狂而混乱的世界中,以此挑战和瓦解父权制的理性秩序。
彭斯最后一次遇到奥利弗发生在很多年后,当她从精神病医院回到斯城时。
她说的话大大震惊了奥利弗:“要是一间房子着了火,而我只能从中救一个孩或者一只鸟,那我就会救那只鸟”[8]。
如果说艾薇只是对男人失望,彭斯则是对所有人绝望。
没有人试图拯救她,她只能从动物那里寻求温暖和安慰。
彭斯的生活激起了奥利弗前所未有的同情和顿悟,他认识到父权制的残酷,决心做个好父亲而不是父权文化机制的帮凶。
当奥利弗抱着他的小女儿索菲,“伴随着一股巨大的冲动,我心中升腾起爱怜、呵护、以及坚定:她绝不该知道这种虚掷年华的一本正经,而要成为一个完满的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9]奥利弗不想让所爱的女儿重蹈彭斯悲剧人生的覆辙,他希望女儿可以过上彭斯所没有体验过得幸福生活。
奥利弗决定做一个和蔼的、合格的父亲标志着对老道利什先生父权制的化身这一形象的否定。
三、结语
本文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威廉?戈尔丁的《金字塔》进行解读,指出《金字塔》呈现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
与一般作家不同,戈尔丁作为男性作家,并没有在小说中流露出大男子主义思想,而是充满了对女性的同情、尊重与认同。
这种女性主义诠释的意义在于,为《金字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