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文库
- 格式:doc
- 大小:36.0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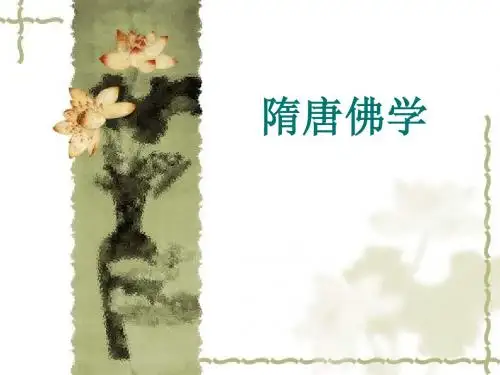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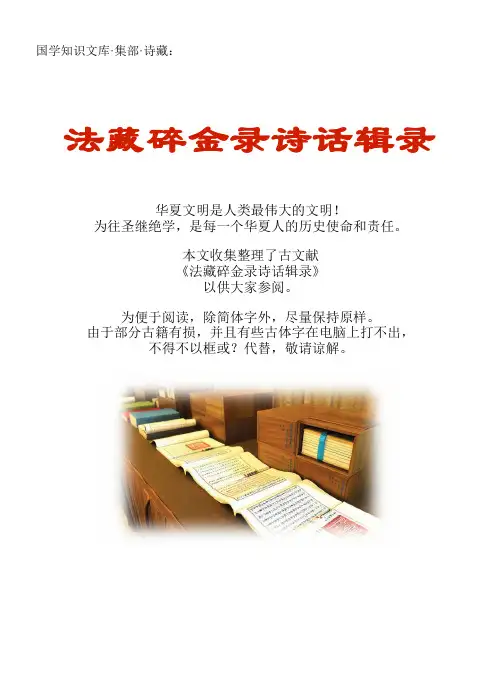
国学知识文库·集部·诗藏:法藏碎金录诗话辑录华夏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为往圣继绝学,是每一个华夏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本文收集整理了古文献《法藏碎金录诗话辑录》以供大家参阅。
为便于阅读,除简体字外,尽量保持原样。
由于部分古籍有损,并且有些古体字在电脑上打不出,不得不以框或?代替,敬请谅解。
法藏碎金录诗话辑录字数:4801 法藏碎金录诗话辑录宋晁迥 余尝爱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
有诗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
”夫如是,则造化阴骘,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卷一 予尝有《晚年勤道自修诗》云:“老来何故惜分阴,如月明亏魄渐侵。
进道不遑求广智,随时随处且冥心。
”因思自说“冥心”二字,盖言四威仪中不拘闲忙,每遇意到,即时随分检情摄念是也。
《晋书隐逸辛谧传》云:“冥心至趣,而与吉会。
”唐贤白乐天《寄酬常州陈使君诗》断句云:“勿使问荣枯,冥心无不可。
”近代僧俗有名者诗僧贯休《怀香炉峰道人诗景联句》云:“冥心同槁木,扫雪带微阳。
”又齐己《山寺喜道者至诗》断句云:“知住南岩下,冥心坐绿苔。
”又吴融《寄贯休诗》断句云:“若得重相见,冥心学半铢。
”如此之类,不可具举。
大约冥心二字,谓以其心,向晦宴息,善入无为,潜符妙道之理也。
同上 唐刺史李繁,述《玄圣蘧庐》十六篇,其序有云:“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见,不在于眼界。
”予因思白乐天有诗云:“东宫白庶子,南寺远禅师。
何处遥相见,心无一事时。
”是知至人之相见,在心不在眼也。
同上 白乐天酷好游观,形于吟咏,有诗句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游。
”又有诗句云:“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
”如此之类,不可具举。
予谓乐天所好者,常游耳;予所好者,游可游,非常游。
予好列子之游。
列子曰:“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
”谓凡人唯睹荣瘁殊观,以为休戚,未觉与化俱往,势不暂停。
予又好壶丘子之游。
壶丘子曰:“务外游不如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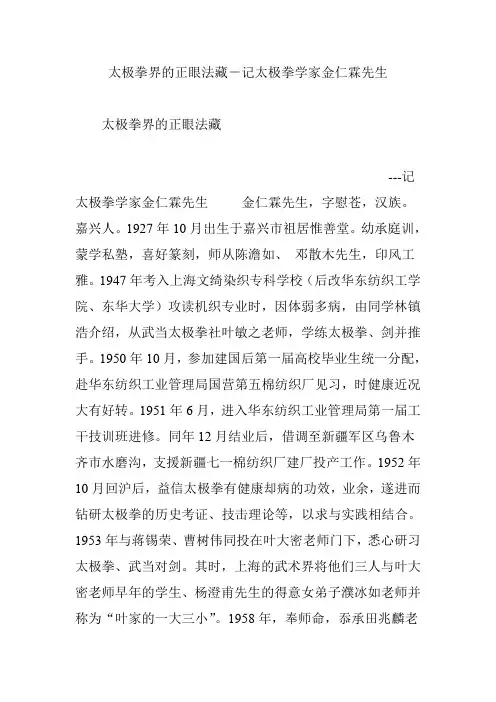
太极拳界的正眼法藏-记太极拳学家金仁霖先生太极拳界的正眼法藏---记太极拳学家金仁霖先生金仁霖先生,字慰苍,汉族。
嘉兴人。
1927年10月出生于嘉兴市祖居惟善堂。
幼承庭训,蒙学私塾,喜好篆刻,师从陈澹如、邓散木先生,印风工雅。
1947年考入上海文绮染织专科学校(后改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攻读机织专业时,因体弱多病,由同学林镇浩介绍,从武当太极拳社叶敏之老师,学练太极拳、剑并推手。
1950年10月,参加建国后第一届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赴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国营第五棉纺织厂见习,时健康近况大有好转。
1951年6月,进入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第一届工干技训班进修。
同年12月结业后,借调至新疆军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支援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建厂投产工作。
1952年10月回沪后,益信太极拳有健康却病的功效,业余,遂进而钻研太极拳的历史考证、技击理论等,以求与实践相结合。
1953年与蒋锡荣、曹树伟同投在叶大密老师门下,悉心研习太极拳、武当对剑。
其时,上海的武术界将他们三人与叶大密老师早年的学生、杨澄甫先生的得意女弟子濮冰如老师并称为“叶家的一大三小”。
1958年,奉师命,忝承田兆麟老师身授,金针度与,得以领略个中三昧。
1960年10月,与张玉、傅钟文、濮冰如、蒋锡荣、傅声远六人,同为上海市第三届运动会武术比赛太极拳组裁判。
1987年,由上海纺织局巾被公司退休后,陆续在《武魂》、《中国太极拳》、《太极》、《上海武术》(内刊)、《武林》等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太极拳历史考证、技击研究等文章数十篇,2007年1月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发行《金仁霖太极拳论文选》一书。
并担任苏州市金阊区杨氏太极拳研究会、河北省太极拳委员会、合肥市吴式太极拳研究会聘为顾问、《太极》杂志特约编委、新加坡传统杨式太极拳协会顾问等。
金仁霖老师兼祧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他以金石鉴赏的眼光与科技工作者的智慧,系统的梳理了太极拳理、太极拳史、太极拳技、太极拳教学法,承上启下,振传统太极拳学于式微之后,传承弘扬传统太极拳文化,其功厥伟,福祉昌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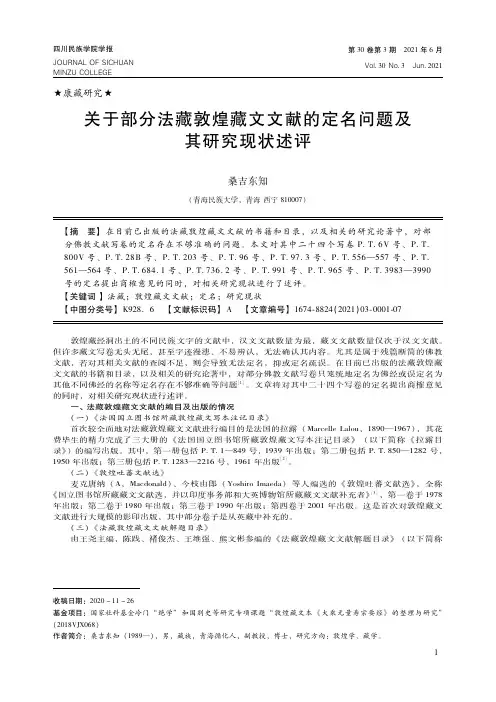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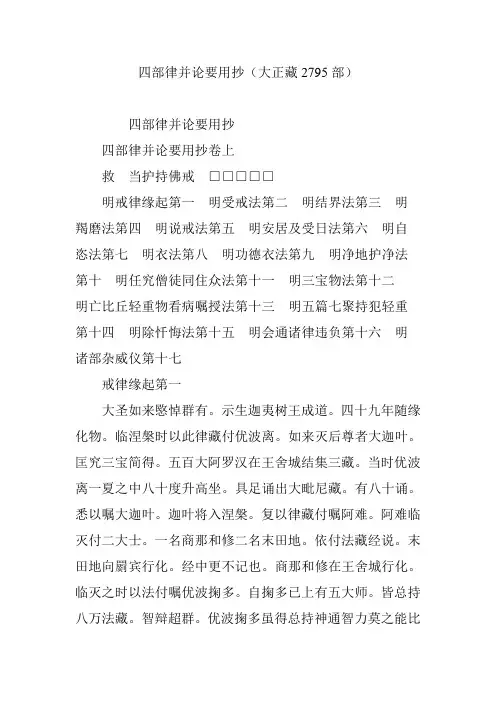
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大正藏2795部)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上救当护持佛戒□□□□□明戒律缘起第一明受戒法第二明结界法第三明羯磨法第四明说戒法第五明安居及受日法第六明自恣法第七明衣法第八明功德衣法第九明净地护净法第十明任究僧徒同住众法第十一明三宝物法第十二明亡比丘轻重物看病嘱授法第十三明五篇七聚持犯轻重第十四明除忏悔法第十五明会通诸律违负第十六明诸部杂威仪第十七戒律缘起第一大圣如来愍悼群有。
示生迦夷树王成道。
四十九年随缘化物。
临涅槃时以此律藏付优波离。
如来灭后尊者大迦叶。
匡究三宝简得。
五百大阿罗汉在王舍城结集三藏。
当时优波离一夏之中八十度升高坐。
具足诵出大毗尼藏。
有八十诵。
悉以嘱大迦叶。
迦叶将入涅槃。
复以律藏付嘱阿难。
阿难临灭付二大士。
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地。
依付法藏经说。
末田地向罽宾行化。
经中更不记也。
商那和修在王舍城行化。
临灭之时以法付嘱优波掬多。
自掬多已上有五大师。
皆总持八万法藏。
智辩超群。
优波掬多虽得总持神通智力莫之能比是。
优波掬多有五弟子。
一萨婆多。
是十诵律主。
二昙无德。
此方名法正。
有大乘根性。
即是四分律主。
三名弥沙塞。
即五分律主。
四名婆粗富那。
即是僧祇律主。
五名迦叶毗。
此土未有此。
之五人亦皆是大阿罗汉。
不能总持八万法藏。
各随己见遂分为五部。
释迦出世当此土周幽王时。
到汉明帝经像始至。
迳百年许方有比丘。
支竺微解汉语。
少翻胡经。
至秦主姚兴深信佛法。
以弘始八年。
于长安草堂寺。
请天竺沙门罗什法师重翻。
旧什法师善晓方音。
明解佛法。
于是佛法广流布也十诵律。
以秦弘始八年。
罽宾国有三藏法师。
名弗若多罗。
受持十诵律来到长安。
共罗什法师翻出译。
一分未讫。
三藏身亡。
又有芦山远法师。
与昙摩流支续翻。
后复有三藏律师。
名卑摩叉。
又复是罗什法师所承习师自来到。
寿春石涧寺重校律本。
复出三卷。
律序置之。
于后此土律兴。
十诵最初四分律。
有晋国沙门支法令。
亲向于阗国得胡本还到秦国。
秦主姚长以弘始十二年。
于长安中兴寺集令德沙门三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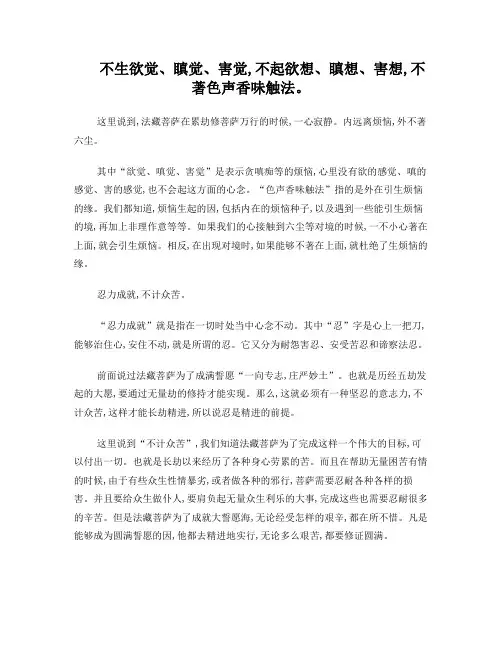
不生欲觉、瞋觉、害觉,不起欲想、瞋想、害想,不著色声香味触法。
这里说到,法藏菩萨在累劫修菩萨万行的时候,一心寂静。
内远离烦恼,外不著六尘。
其中“欲觉、嗔觉、害觉”是表示贪嗔痴等的烦恼,心里没有欲的感觉、嗔的感觉、害的感觉,也不会起这方面的心念。
“色声香味触法”指的是外在引生烦恼的缘。
我们都知道,烦恼生起的因,包括内在的烦恼种子,以及遇到一些能引生烦恼的境,再加上非理作意等等。
如果我们的心接触到六尘等对境的时候,一不小心著在上面,就会引生烦恼。
相反,在出现对境时,如果能够不著在上面,就杜绝了生烦恼的缘。
忍力成就,不计众苦。
“忍力成就”就是指在一切时处当中心念不动。
其中“忍”字是心上一把刀,能够治住心,安住不动,就是所谓的忍。
它又分为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和谛察法忍。
前面说过法藏菩萨为了成满誓愿“一向专志,庄严妙土”。
也就是历经五劫发起的大愿,要通过无量劫的修持才能实现。
那么,这就必须有一种坚忍的意志力,不计众苦,这样才能长劫精进,所以说忍是精进的前提。
这里说到“不计众苦”,我们知道法藏菩萨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可以付出一切。
也就是长劫以来经历了各种身心劳累的苦。
而且在帮助无量困苦有情的时候,由于有些众生性情暴劣,或者做各种的邪行,菩萨需要忍耐各种各样的损害。
并且要给众生做仆人,要肩负起无量众生利乐的大事,完成这些也需要忍耐很多的辛苦。
但是法藏菩萨为了成就大誓愿海,无论经受怎样的艰辛,都在所不惜。
凡是能够成为圆满誓愿的因,他都去精进地实行,无论多么艰苦,都要修证圆满。
我们常常说,菩萨要披着誓愿的铠甲才能发起长劫精进。
也就是法藏菩萨完全是以大悲愿力,纯粹利益众生的心,使得他在长劫以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冤害、打骂、诽谤,或者处在多么艰苦的环境里,遭遇饥、渴、寒、热等的苦,或者受持哪一种甚深的法义时,都能一心安住在法上,毫不动摇。
只有具备这样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事业,成就如此不可思议的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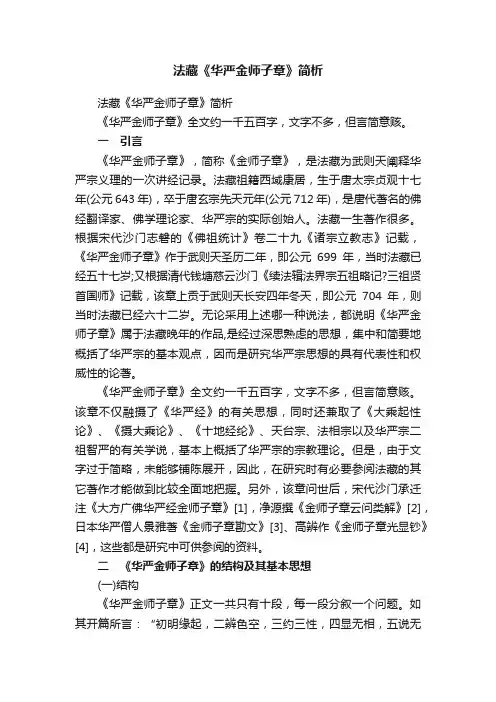
法藏《华严金师子章》简析法藏《华严金师子章》简析《华严金师子章》全文约一千五百字,文字不多,但言简意赅。
一引言《华严金师子章》,简称《金师子章》,是法藏为武则天阐释华严宗义理的一次讲经记录。
法藏祖籍西域康居,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卒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学理论家、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
法藏一生著作很多。
根据宋代沙门志磐的《佛祖统计》卷二十九《诸宗立教志》记载,《华严金师子章》作于武则天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当时法藏已经五十七岁;又根据清代钱塘慈云沙门《续法辑法界宗五祖略记?三祖贤首国师》记载,该章上贡于武则天长安四年冬天,即公元704年,则当时法藏已经六十二岁。
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说法,都说明《华严金师子章》属于法藏晚年的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基本观点,因而是研究华严宗思想的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论著。
《华严金师子章》全文约一千五百字,文字不多,但言简意赅。
该章不仅融摄了《华严经》的有关思想,同时还兼取了《大乘起性论》、《摄大乘论》、《十地经纶》、天台宗、法相宗以及华严宗二祖智严的有关学说,基本上概括了华严宗的宗教理论。
但是,由于文字过于简略,未能够铺陈展开,因此,在研究时有必要参阅法藏的其它著作才能做到比较全面地把握。
另外,该章问世后,宋代沙门承迁注《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子章》[1],净源撰《金师子章云问类解》[2],日本华严僧人景雅著《金师子章勘文》[3]、高辨作《金师子章光显钞》[4],这些都是研究中可供参阅的资料。
二《华严金师子章》的结构及其基本思想(一)结构《华严金师子章》正文一共只有十段,每一段分叙一个问题。
如其开篇所言:“初明缘起,二辨色空,三约三性,四显无相,五说无生,六论五教,七勒十玄,八括六相,九成菩提,十入涅槃。
”用“十”来论述教义、教理是《华严经》的一种格式,法藏继承了这种格式。
法藏说:“依《华严经》中立十数为则,以显无尽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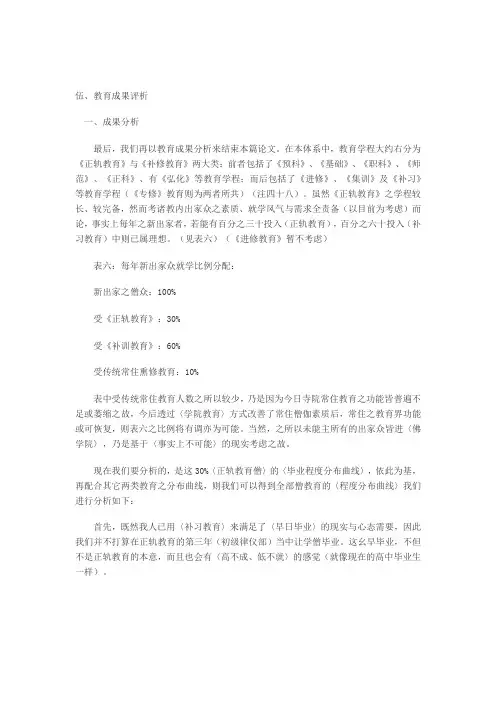
伍、教育成果评析一、成果分析最后,我们再以教育成果分析来结束本篇论文。
在本体系中,教育学程大约右分为《正轨教育》与《补修教育》两大类:前者包括了《预科》、《基础》、《职科》、《师范》、《正科》、有《弘化》等教育学程;而后包括了《进修》、《集训》及《补习》等教育学程(《专修》教育则为两者所共)(注四十八)。
虽然《正轨教育》之学程较长、较完备,然而考诸教内出家众之素质、就学风气与需求全责备(以目前为考虑)而论,事实上每年之新出家者,若能有百分之三十投入(正轨教育),百分之六十投入(补习教育)中则已属理想。
(见表六)(《进修教育》暂不考虑)表六:每年新出家众就学比例分配:新出家之僧众:100%受《正轨教育》:30%受《补训教育》:60%受传统常住熏修教育:10%表中受传统常住教育人数之所以较少,乃是因为今日寺院常住教育之功能皆普遍不足或萎缩之故,今后透过〈学院教育〉方式改善了常住僧伽素质后,常住之教育界功能或可恢复,则表六之比例将有调亦为可能。
当然,之所以未能主所有的出家众皆进〈佛学院〉,乃是基于〈事实上不可能〉的现实考虑之故。
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这30%〈正轨教育僧〉的〈毕业程度分布曲线〉,依此为基,再配合其它两类教育之分布曲线,则我们可以得到全部僧教育的〈程度分布曲线〉我们进行分析如下:首先,既然我人已用〈补习教育〉来满足了〈早日毕业〉的现实与心态需要,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在正轨教育的第三年(初级律仪部)当中让学僧毕业。
这幺早毕业,不但不是正轨教育的本意,而且也会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就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一样)。
由此(初律部)开始(见表三),我们让40%的毕业僧进入(职科)教育、60%进入(正科)教育中。
为了简化讨论着过程,我们在此仅考虑〈正入〉过程的〈升学率〉,由于〈转入〉或〈或入〉的升学率在比例上少得多,因此,暂时不予考虑。
接着我们让〈中律职科部〉有45%毕业,如此约有总正轨教育人数的18%〈下称此为〈毕业总人数比〉投入僧社会中,另外则分别以24%、50%及70%的升学率升入〈普教师范〉、〈普教正科〉及〈预科师范〉部中继续就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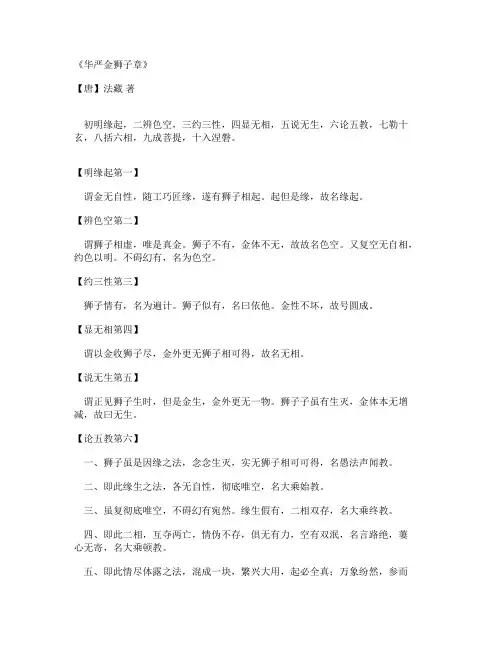
《华严金狮子章》【唐】法藏著初明缘起,二辨色空,三约三性,四显无相,五说无生,六论五教,七勒十玄,八括六相,九成菩提,十入涅磐。
【明缘起第一】谓金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遂有狮子相起。
起但是缘,故名缘起。
【辨色空第二】谓狮子相虚,唯是真金。
狮子不有,金体不无,故故名色空。
又复空无自相,约色以明。
不碍幻有,名为色空。
【约三性第三】狮子情有,名为遍计。
狮子似有,名曰依他。
金性不坏,故号圆成。
【显无相第四】谓以金收狮子尽,金外更无狮子相可得,故名无相。
【说无生第五】谓正见狮子生时,但是金生,金外更无一物。
狮子子虽有生灭,金体本无增减,故曰无生。
【论五教第六】一、狮子虽是因缘之法,念念生灭,实无狮子相可可得,名愚法声闻教。
二、即此缘生之法,各无自性,彻底唯空,名大乘始教。
三、虽复彻底唯空,不碍幻有宛然。
缘生假有,二相双存,名大乘终教。
四、即此二相,互夺两亡,情伪不存,俱无有力,空有双泯,名言路绝,萋心无寄,名大乘顿教。
五、即此情尽体露之法,混成一块,繁兴大用,起必全真;万象纷然,参而不杂。
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果历然。
力用相收,卷舒自在,名一乘圆教。
【勒十玄第七】一、金与狮子,同时成立,圆满具足,名同时具足相应门。
二、若狮子眼收狮子尽,则一切纯是眼;若耳收狮子尽,则一切纯是耳。
诸根同时相收,则一一皆杂,一一皆纯,为圆满藏,名诸藏纯杂具德门。
三、金与狮子,相容成立,一多无碍;于中理事各各不同,或一或多,各住自位,名一多相容不同门。
四、狮子诸根,一一毛头,皆以金收狮子尽。
一一遍狮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
自在成立,无障无碍,名诸法相即自在门。
五、若看狮子,唯狮子无金,即狮子显金隐。
若看金,唯金无狮子,即金显狮子隐。
若两处看,俱隐俱显。
隐则秘密,显则显著,名秘密隐显俱成门。
六、金与狮子、或隐或显,或一或多,定纯定杂,有力无力,即此即彼,主伴交辉,理事齐现,皆悉相容,不碍安立,微细成办,名微细相容安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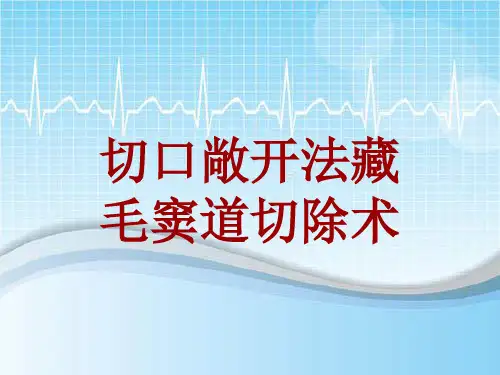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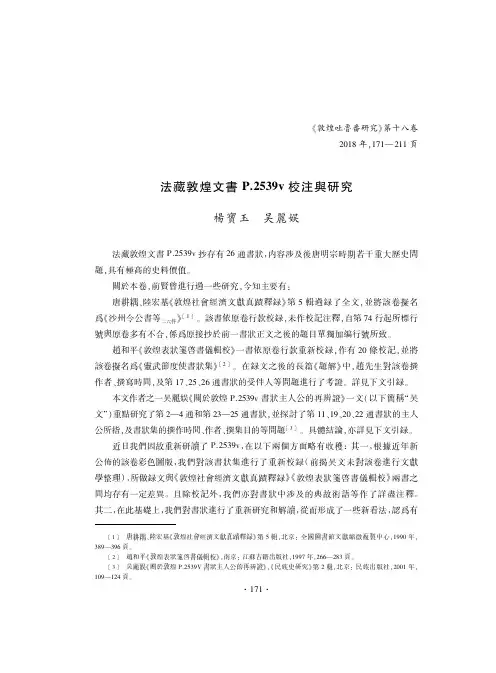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八卷2018年,171—211頁法藏敦煌文書P.2539v校注與研究楊寶玉 吴麗娱法藏敦煌文書P.2539v抄存有26通書狀,内容涉及後唐明宗時期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關於本卷,前賢曾進行過一些研究,今知主要有: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5輯過録了全文,並將該卷擬名爲《沙州令公書等二六件》〔1〕。
該書依原卷行款校録,未作校記注釋,自第74行起所標行號與原卷多有不合,係爲原接抄於前一書狀正文之後的題目單獨加編行號所致。
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依原卷行款重新校録,作有20條校記,並將該卷擬名爲《靈武節度使書狀集》〔2〕。
在録文之後的長篇《題解》中,趙先生對該卷撰作者、撰寫時間,及第17、25、26通書狀的受件人等問題進行了考證。
詳見下文引録。
本文作者之一吴麗娱《關於敦煌P.2539v書狀主人公的再辨證》一文(以下簡稱“吴文”)重點研究了第2—4通和第23—25通書狀,並探討了第11、19、20、22通書狀的主人公所指,及書狀集的撰作時間、作者、撰集目的等問題〔3〕。
具體結論,亦詳見下文引録。
近日我們因故重新研讀了P.2539v,在以下兩個方面略有收穫:其一,根據近年新公佈的該卷彩色圖版,我們對該書狀集進行了重新校録(前揭吴文未對該卷進行文獻學整理),所做録文與《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兩書之間均存有一定差異。
且除校記外,我們亦對書狀中涉及的典故術語等作了詳盡注釋。
其二,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書狀進行了重新研究和解讀,從而形成了一些新看法,認爲有·171·〔1〕〔2〕〔3〕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5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89—396頁。
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266—283頁。
吴麗娱《關於敦煌P.2539V書狀主人公的再辨證》,《民族史研究》第2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109—124頁。
关于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的几个问题作者:陆离来源:《敦煌研究》2019年第01期內容摘要: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应该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当地官府支出粮食等物品的账目记录清单,文书中记载的职官押衙(am va gav)、长史(jang shi,亦可译为长使)、人名ya ya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书中已出现,并非只是在归义军时期才出现的职官,不能据此将该文书定为归义军时期文书。
关键词:吐蕃;敦煌;押衙;长使;人名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93-08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是一件关于当地官府支出粮食等物品的账目记录清单,该件文书最先由王尧、陈践先生进行了汉译,定名为《薪俸支出粮食清册》[1-2],国内学者一般都将其认定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文书[3]①,而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则认为该文书是归义军时期文书,但未对之进行详细论述[4],后来日本学者坂尻彰宏(Akihiro Sakajiri)先生对该件文书重新进行了译解,对武内绍人先生的观点加以引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5]。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照文书原件图版再对该件文书重新进行译解,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的转写及译文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的拉丁文转写:1 [……]gi l[o] v[i] dpyid sla ra bav[i] ngo la//blavi stsang mngan cang vbun an2 [……]shing dang/song vgag gsum gyi gnyer la khre nas las//bla vi chang rgyu dang/bla[vi]3 [……]gzhib rgyu dang/yu mar rgyu zar ma dang/ya ya nas/:phyag rgya gtad de gtan vgo4 du phog pavi mying smar dkar cag du bris pa/:/tshes bdun gyi gdugs la/bla vi chang rgyu khre5 khal sum cu phog ste am va gav hwa lyang sin dang/chang pa cang ham dang sag pig chivu6 rnams la gtad/:/yang de vi gdugs la//han am va gav vi sta chas/dgun7 sla tha cung tshes nyi zhu lnga vi phan cad dang/dpyid sla ra ba tshes bcu tshun cad dgung zhag bcu8 lnga la khre khal lnga phog ste phyag rdzed khang sam sam la gtad/:/yang de vi gdugs la/9 lo pan steng gi vgo shi tse la gro khal gsum dang zar ma khal gcig phog ste khong ta vgo10 she tse dngos la gtad/:/tshesbcu la//sug cu pa hevu kog hang gi vbangs/hivu an tse11 dang shi rdze sheng la stsogspa la/brgyags rgyu khre khal drug dang/gro khal drug phog ste khong12 ta an tse dang rdze sheng stsogs pa la gtad/:/yang de vi gdugs la/kwag tsi lang la13 gro khal bcu dang khre khal bcu phog ste khong ta tsi lang dngos la gtad/:/yang de vi14 gdugs la/dkav mgo vi dkav phye ba vi lha gsol ba vi chang rgyu khre khal bcu phog15 ste chang pa cang ham ham dang khang shin shin dang sag pig chivi rnams la gtad /:/16 yang de vi gdugs la//cang hig tse la chang rgyu khre khal lnga phog ste khong ta dngos la17 gtad/:/tshes bcu bdun la//bla vi chang rgyu khre khal sum cu phog ste am va gav18 hwa lyang sin dang chang pa cang ham ham dang sag pig chivi rnams la gtad/:/19 yang de vi gdugs la//bla vi tshog rkyen yu mar rgyu zar ma khal lnga dang khre drus rgyu khre20 khal lnga phog ste jang shi ceng vbun kyun la gtad/:/yang de vi gdugs21 la//cang hig ce la chang rgyukhre khal lnga phog ste khong ta dngos la gtad/:/tshes nyi22 shu brgyad la//bla vi tshog rkyen phye thag rgyu gro khal bzhi bcu dang yu mar rgyu zar ma23 khal bzhi dang/vbras shol khal gsum phog ste jang shi beng vbun kyun la gtad/24 yang de vi gdugs la/ham am va gavi rta chas/tshe bcu phan cad dang tshes nyi shu bzhi25 tshun cad dgong zhag bcu bzhivi bar du khre khal lnga phog ste phyag rdzed khang sam sam la gtad26 yang de vi gdugs la//bla vi chang rgyu khre khal sum cu phog ste am va gav hwa lyang sin dang/27 chang pa cang ham ham/pig civu rnams la gtad/:/yang de vi gdugs la//sug cu28 pa hevu gog hang gi vbangs/hivu an tse dang shi dzi sheng rnams la/vtshal brgyags/29 gro khal bzhi dang khre khal gsum phog ste khong ta dngos la gtad/:/yang de vi gdugs30 [……]cang hig ce la changrgyu khre khal lnga phog ste khong ta dngos la gtad/:/yang te vi[……] [6]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的汉文译文:1—4:[……]年孟春上旬,官府仓曹(stsang mngan)张文安(cang vbun an)……晟和宋鄂三人从所管的小米和青稞中拨付官府酿酒原料和官府……食用原料和油料胡麻,牙牙盖印,确定付给人员,点名填造清册如下:4—8:七日,官府酿酒原料小米30驮(khal),给予押衙(am va gav)华梁森(hwa lyang sin)、酿酒人张汉和石毕秋等人。
历史与文化丝绸JOURNAL OF SILK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Study on the kasaya pattern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蓝津津,刘元风(北京服装学院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北京100105)摘要: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㊂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㊂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㊁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㊁同心圆联珠纹㊁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㊂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㊁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㊁布局㊁工艺㊁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㊂关键词:唐宋时期;佛教美术;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云水纹中图分类号:TS 941.12;K 879.41㊀㊀㊀㊀文献标志码:B ㊀㊀㊀㊀文章编号:10017003(2024)04011414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4.04.014收稿日期:20230726;修回日期:202403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9BG 102);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 2018 立项第08号)作者简介:蓝津津(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敦煌服饰文化与创新设计㊂通信作者:刘元风,教授,liuyuanfeng 2018@ ㊂㊀㊀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公元7 10世纪的绘画作品,一般统称为 敦煌遗画 ㊂这些遗画属于佛教类绘画,在当时大多用于礼佛供奉,并且由于长期密封保存,画面基本都保持原色㊂20世纪初,敦煌遗画被发现后,以斯坦因㊁伯希和为代表的外国探险家先后前往敦煌莫高窟盗取,目前遗失在外的敦煌遗画总数在1100件以上,主要分藏于英㊁印㊁法㊁俄四国㊂就目前公开的图像资料中,英㊁法两国的部分藏品经过多次整理,以讲谈社出版的‘西域美术“系列图册最为系统全面㊂其中有一批精美的地藏菩萨绘画作品,共计有20身地藏菩萨穿着的袈裟绘有纹样,绘制时间横跨了中晚唐,五代十国与宋代(后文简称五代宋时期),多为敦煌遗画中的经典之作㊂自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学界针对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形象亦展开了诸多研究,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1]一书首开先河,对于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图像做了基础的梳理与考证㊂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地藏菩萨的研究也拓展到许多方面,王惠民[2]针对唐前期的敦煌地藏菩萨图像做了分类,并纠正了一些定名及时代错误㊂袁婷[3]对现存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图像分布概况及研究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统计㊂尹文汉[4]从图像学的角度对中国化的地藏形象及其传播影响作论述,其中便涉略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概况㊂李曼瑞[5]从文学㊁历史㊁美术史及佛学等方面对物象背后的地藏菩萨信仰和法门作了深入研究,并探讨了地藏菩萨艺术形象的发展轨迹㊂综上,目前的学者大多从敦煌文献及佛教史的角度,对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现状进行梳理,并探讨其背后的信仰流变成因㊂有关地藏菩萨图像学近几年也有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但暂未深入袈裟纹样的领域㊂因此,目前专门针对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的研究较少,缺乏对该纹样发展脉络的系统整理与分析㊂通过对比这些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所穿着的袈裟纹样可知,袈裟的纹样内容与绘制布局都与地藏菩萨的身份㊁动作姿态及当时的染织工艺有着紧密联系㊂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西域美术“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图像,梳理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同时追溯传世袈裟实物及唐宋时期的纺织品工艺,与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互证,进一步理解当时人们对地藏菩萨身份职能的解读,探寻唐宋时期地藏信仰中原化对其造像纹样的影响,对敦煌地区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的年代判断和风格研究提供理论参考㊂411第61卷㊀第4期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1㊀袈裟纹样的分期与基本类型地藏菩萨起源于印度,佛教东渐后,成为与观世音㊁文殊㊁普贤并列的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㊂‘地藏十轮经“中形容其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 ,因此称为地藏㊂地藏菩萨具有救济众生的职能,若信众诵念地藏之名,诚心皈依,便能从苦难中获得解脱㊂地藏信仰自隋唐时期在中原兴起,至中晚唐时期逐渐成熟,五代宋时期,地藏信仰进一步本土化㊁民俗化,地藏菩萨的救赎重心从六道转向地狱,最终演化为幽冥教主,形成了地藏十王系统[4]㊂从图像上看,地藏菩萨有别于传统的菩萨仪相,一般为圆顶光头㊁身着袈裟的沙门形象㊂学者尹富[6]认为,在8世纪前的志怪小说中,僧侣是最主要的地狱救赎者,因此身着袈裟的地藏菩萨,更符合当时人们心中救赎者的形象,并于8世纪后逐渐形成地藏十王系统,地藏菩萨也成为了幽冥教主㊂‘西域美术“中刊录的地藏图像可大致分为中晚唐及五代宋两个阶段[7](图1),中晚唐时期大多独立绘于的幡上,且皆为站姿沙门形㊂随着地藏菩萨信仰的中原化,其地位稳步提升,形象也经历了多番演变㊂五代宋时期,地藏菩萨形象较少独立绘制,一般出现在地藏十王图中的主尊位置,并由站姿演变为坐姿,在头部增绘风帽装饰,风帽的纹样也基本与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相配,辅助整体画面的和谐统一㊂在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的袈裟并非全盘遵循佛教仪轨,依据佛典规制,佛及僧侣应穿着三层袈裟㊂袈裟(梵文Kas㊃āya),亦称三衣, 袈裟 是从其衣色得名, 三衣 是从衣之层数得名㊂依据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的 下衣㊁中衣㊁大衣 之说,地藏菩萨所穿着的袈裟层次本应该一一对应这由内而外的三层袈裟㊂但在目前刊录的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一般仅穿着两层袈裟,袈裟纹样也仅绘制于这内外两层袈裟上㊂费泳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8]中提到: 佛教造像中,佛衣的披着方式具有多样性,其中或遵循规制,或是规制的变异,或完全与规制不符㊂ 目前暂未有文献能论证地藏图像中的两层袈裟分别对应的三衣名称,为方便后文阐述,在此将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所穿着的两层袈裟由内而外分别称为内层袈裟和外层袈裟(图2),一般来说内层袈裟无田相形制,外层袈裟绘有田相格㊂并对内㊁外层袈裟的纹样位置做界定:缘边指内层袈裟衣身边缘一圈的窄条;叶即指外层袈裟中间较细的横条和竖条;条为叶与叶间的大块方形区域㊂‘西域美术“已梳理了唐宋时期敦煌遗画的基本信息,除个别绢画有明确的题记之外,这些画作一般仅标有大致的年代,如 唐时期9世纪 等㊂在这些遗画中,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作品共计20幅,其中中晚唐时期6幅㊁五代图1㊀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造像变化Fig.1㊀Changes of statue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Dynasties图2㊀EO.1186及外层袈裟㊁内层袈裟纹样位置示意Fig.2㊀EO.1186and location illustration of the outer andinner kasaya patterns宋时期14幅㊂本文将这20组袈裟纹样进行梳理,绘制其内㊁外层袈裟的单元纹样,并从中晚唐㊁五代宋两个阶段中各提取最具代表性的三例,总结纹样变化规律与联系,如表1所示㊂511Vol.61㊀No.4Study on the kasaya pattern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表1㊀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袈裟纹样Tab.1㊀Currently recorded kasaya s patterns of the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条上绘云水纹及线迹纹条上绘云水纹衣身绘四瓣团花纹条上绘波纹状晕染及水纹缘边贴金单瓣菱形纹叶上贴金单瓣菱形纹;条上绘云纹衣身绘四瓣十字花纹,缘边绘半破式二方连续五瓣团花纹条上绘晕染式云纹及线迹纹缘边绘二方连续同心圆叶上绘四瓣菱形纹;条上绘晕染式云纹及线迹纹611第61卷㊀第4期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㊀㊀通过梳理袈裟纹样可知,中晚唐时期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多绘于外层袈裟的条上,内㊁外层袈裟皆绘有纹样的地藏菩萨目前仅见表1中的EO.1398一例;五代宋时期地藏菩萨的内㊁外层袈裟上大多都绘有纹样㊂这种情况并非突然出现在遗画中,自隋代开始,敦煌莫高窟中的弟子像就有两层袈裟皆绘纹样的样式㊂随着盛唐时期中原地区地藏菩萨信仰的兴盛,莫高窟中也涌现了大量的地藏造像,其中部分地藏也沿用这一样式,身着内㊁外层袈裟上皆绘有纹样的华丽袈裟㊂如莫高窟盛唐第166窟主室东壁南侧的地藏菩萨(图3(a )),内层袈裟的衣身上勾绘五瓣花纹,外层袈裟的叶上点缀线迹纹,条上绘有三色树皮纹,错落有致,十分精美㊂自五代开始,地藏菩萨的内层袈裟上还流行绘制同心圆联珠纹,如榆林窟五代第12窟中的被帽地藏菩萨像(图3(b )),内层袈裟衣缘就绘有二方连续半破式同心圆联珠纹㊂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袈裟纹样皆沿袭了这些绘制特点,自五代开始还在此基础上增贴菱形金箔,这种样式一直延续至宋时期,仅在外层袈裟的云纹色彩及内层袈裟的花纹样式上有区别㊂图3㊀敦煌石窟中内㊁外层袈裟皆绘纹样的地藏菩萨Fig.3㊀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Grottoes with paintedpatterns on his robes and overcoats从画面中出现的服饰纹样来看,单元纹样的使用呈现为两种规律:一种是仅用于地藏菩萨袈裟纹样上的情况,一般多为云水纹㊁线迹纹等,此类纹样一般仅绘于外层袈裟上,暂未于敦煌地区的其他尊像服饰中看到特例㊂另一种是袈裟纹样与其他形象的服饰纹样相同,或在色彩上相呼应,这种情况一般为尊像在画面中呈对称式,如EO.3644中的被帽地藏菩萨,与画面左上方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相对,地藏菩萨内层袈裟缘边的二方连续四瓣十字形花纹,同样绘制于菩萨的络腋及裙上,从服饰纹样的角度体现了二位菩萨无从属关系㊂除地藏菩萨外,其他遗画中穿着绘纹样袈裟的形象也反映了这一规律,如MG.23078中位于药师如来身侧的一老一少两尊僧形,在画面中也呈对称式,叶上皆贴金三瓣菱形纹,与药师如来的袈裟纹样相同,呼应了药师如来佛的主尊身份㊂因此,从同幅画面中袈裟单元纹样的分布情况也可看出着袈裟者在画面中的地位㊂综上,在英法藏唐宋时期的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的绘制数量随时期的变化呈递增式,中晚唐时期的6幅地藏画像皆绘于幡上,为站姿沙门形;五代宋时期,由于地藏菩萨作为幽冥教主身份的确立及地藏十王系统的完善成熟,14幅地藏画像皆以坐姿被帽形绘于绢纸画中,或占据主尊,或与其他尊像呈对称式构图㊂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地藏菩萨内㊁外层袈裟的纹样,并横向对比敦煌石窟中其他人物的服饰纹样,可以将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分为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和袈裟专属纹样㊂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包括贴金菱形纹㊁团花纹和同心圆联珠纹,袈裟专属纹样包括云水纹及线迹纹㊂2㊀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在敦煌莫高窟中,菱形纹㊁团花纹及同心圆联珠纹经常作为壁画的边饰纹样,使石窟更加异彩纷呈㊂为了保持洞窟整体视觉的联系性与和谐度,佛陀㊁菩萨㊁弟子等人物服饰的边饰也多绘制这种装饰纹样相呼应㊂在唐宋时期英法藏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的袈裟亦沿用了此类纹样,且分布广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敦煌石窟与敦煌遗画在装饰手法上的关联性㊂2.1㊀贴金菱形纹在地藏菩萨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中,有一种结合了特殊工艺的纹样十分瞩目,即贴金菱形纹样㊂该纹样早在初唐时期便绘制在敦煌石窟的袈裟上,大多分布在弟子塑像袈裟的叶上,而在目前刊录的敦煌遗画中,直到五代时期才运用于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㊂如图4所示,莫高窟初唐第205窟的佛弟子阿难塑像外层袈裟叶上装饰金色四瓣菱形花,此类单元菱形较为瘦长,在莫高窟初唐第334窟的阿难塑像上也能见到相同的样式㊂莫高窟中唐第368窟主室西壁帐门南北侧的两身药师佛,内㊁外层袈裟皆绘有金色四瓣菱形纹,此例菱形纹更贴近于正方形,与敦煌遗画中的菱形纹形状更为相似㊂在编号为MG.17795的敦煌遗画中,地藏菩萨的袈裟纹样就有将单个菱形内平均分割为四瓣的相同样式㊂自隋唐开始, 凡色至于金,为人间华美贵重,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 [9],遗画中对地藏菩萨装饰贴金的手法,也从袈裟纹样的角度反映了在唐宋时期,金箔被广泛运用于礼佛造像以示虔诚供奉的这一现象㊂在唐宋时期的敦煌711Vol.61㊀No.4Study on the kasaya pattern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Britain andFrance图4㊀袈裟纹样上的贴金菱形纹Fig.4㊀Gilding diamond patterns of kasaya遗画中,这种菱形状金箔也并非是袈裟独有的装饰纹样,它被广泛地运用在幡幢㊁菩萨㊁天王及供养人等形象中,并与在袈裟上的贴绘形式相似,多被装点于织物的条状㊁纯色地区域内㊂在对这批敦煌遗画作断代研究时,韦陀等学者认为这种菱形状纹样是仿叶状,称为 贴金叶 ,并将这种贴金手法作为遗画断代为10世纪晚期以后的线索之一[10],说明该时期在遗画中大量装饰贴金菱形纹已成普遍现象㊂对比中晚唐时期的敦煌遗画,地藏菩萨的服饰上并无贴金的样式,到了五代宋时期,在袈裟及风帽上装点贴金菱形纹已成定式,也从侧面反映了从唐末开始地藏信仰的逐步提升㊂地藏菩萨身为幽冥教主并占据十王图画面的主尊位置,同时,这种结构稳定㊁布局灵活的菱形纹样,能被合适地填充在不同形状的织物区域内,配合彩绘贴金的形式,更显得地藏菩萨庄严大气㊁熠熠生辉㊂2.2㊀团花纹在五代宋时期的敦煌遗画中,团花形纹样仅绘制于地藏菩萨的内层袈裟,暂未发现有分布于外层袈裟的案例㊂当团花纹绘制于内层袈裟衣身时,呈四方连续式排列;当绘制于内层袈裟缘边时,由于缘边呈长条形,团花纹在绘制时皆呈二方连续式排列㊂早在敦煌石窟的隋代时期,其他尊像的袈裟上就已有二方连续式的团花纹边饰(表2),如莫高窟隋代第244窟主室西壁的佛陀塑像,内㊁外层袈裟的缘边皆绘二方连续团花纹,结构清晰,色彩丰富㊂盛唐时期二方连续团花纹的排列方式更多样,有半破式㊁一整二破式等,且愈往后发展,不仅在佛陀或弟子的袈裟㊁僧祇支和裙缘处广泛出现,也盛行于菩萨㊁天王㊁供养人像等的服饰缘边中㊂纵观莫高窟唐代时期的团花纹,唐前期的花瓣呈如意形,皆以花心为中点,呈放射状层层叠压,极具装饰效果,到了中晚唐,又发展出了圆润饱满的茶花纹㊂因此,除在服装缘边使用,二方连续式团花纹在石窟的壁画㊁藻井的边饰上也十分常见㊂反观五代宋时期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其内层袈裟的团花纹边饰大多仅用单色线条或色块来简单概括花型,不似石窟中层次丰富㊁色彩绮丽㊁线迹清晰的花团锦簇㊂如表2中五代时期的EO.3580,地藏菩萨内层袈裟缘边的团花纹由圆弧构成,每朵团花由三瓣圆弧叠压,类似鱼鳞㊂形成这种团花纹的样式,原因一是敦煌遗画较小,画幅尺寸限制了绘画空间,无法像敦煌石窟中大面积的团花纹一样精细勾绘㊂原因二是从晚唐时期的部分敦煌石窟来看,对于团花类题材的趋向随意地描绘和创造力的减弱是一种总体趋势[11],这一风格变化也影响到了同时期的敦煌遗画中㊂除了线形花纹,遗画中还有一种朵瓣状的单色团花纹,主要流行于北宋时期㊂以表2中Stein painting19.Ch.lviii.003及MG.17762的地藏菩萨内层袈裟缘边团花纹为例,这是一种仅表现在织物上的花形㊂区别于极具装饰感的多层团花纹,这种朵瓣状团花纹在敦煌石窟及遗画中皆以单色无勾线的形式表现,且通常仅有单层花瓣,瓣与瓣之间无叠加关系㊂在莫高窟中,朵瓣状单色团花纹主要运用于供养人㊁侍从及地藏菩萨的服饰上,也有部分应用于坐毯等织物纹样装饰(表3)㊂其花形排列结构也较为简单固定,当分布在条状区域内时,一般表现为半破式二方连续结构,在面积较大的织物上则为四方连续式㊂从色彩上看,此类朵瓣状的单色团花纹表现的是双色服饰面料,显现出凸纹版单色印花的工艺特点[12]㊂综上,团花这一服饰纹样并非袈裟中独有的纹样,相比袈裟专属纹样,它更具有普适性,在石窟与遗画中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㊂地藏菩萨袈裟上大量出现的团花纹反映了遗画与敦煌石窟在装饰纹样上的关联性,同时, 花 这一装饰母题所蕴含的以花礼佛的思想,也代表了供奉者对于佛教教义的美好诠释㊂811第61卷㊀第4期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表2㊀袈裟缘边团花纹的演变Tab.2㊀Evolution of the fringe pattern of kasaya表3㊀莫高窟中朵瓣状单色团花纹在织物上的应用Tab.3㊀Application of monochromatic blob patterns in Mogao Grottoes on fabrics时期窟号纹样位置纹样原貌360主室东壁吐蕃侍从袍服911Vol.61㊀No.4Study on the kasaya pattern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续表32.3㊀同心圆联珠纹同心圆联珠纹的单元结构㊁排列方式和团花纹较为相似,皆为中心放射状的边饰纹样㊂这种几何纹的特点是,通过集中排列点㊁线㊁圆环等几何纹,组成一个类圆形的单元纹样,嵌套次序分明,别具美感㊂不论是在敦煌石窟还是敦煌遗画中,同心圆联珠纹的配色都较为统一,这与当时多色夹缬工艺常用的基础色有关,一般为橙红色地,同心圆为石绿或青蓝色,圆上点饰白珠㊂这种布局精巧㊁极具异域风情的联珠纹起源于萨珊波斯,约公元5世纪传入中原,在北周时期的敦煌石窟龛沿边饰中就已出现该纹样(表4)㊂自隋中期开始,联珠纹㊁同心圆等元素开始在敦煌石窟中广泛运用,排列结构与团花纹的规律相似,当运用于边饰时,呈二方连续式排列,当运用于大片面积的织物中,则呈网格状四方连续式排列㊂姜伯勤教授在论及中亚粟特地区艺术对敦煌艺术的影响时指出:联珠纹 是萨珊波斯或粟特人有关的太阳崇拜和光明崇拜有关的图像符号 [13]㊂而与萨珊波斯纺织品中常见的同心圆内嵌套动物纹不同,早期的同心圆联珠纹往往在花心中嵌套莲花,如表4中莫高窟隋代第292窟主室南壁菩萨塑像的下裙纹样㊁初唐第334窟主室西壁龛内的菩萨服饰纹样及盛唐第194窟主室南壁的礼佛王子袍服袖缘纹样,皆为这种组合样式㊂这是联珠纹由中亚传至中原时,受佛教莲花纹的影响而形成的新式联珠纹,是织物纹样在丝路传播中形成交融盛况的侧面反映㊂随着时间的推移,敦煌石窟中的同心圆联珠纹开始往更简略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几何化的变化趋势,其原有的含义在敦煌石窟中也逐渐淡化,主要为装饰作用㊂在敦煌石窟中,自唐代开始,同心圆联珠纹主要出现在许多菩萨㊁天女㊁天王㊁礼佛王子等人物画像的服饰中,唐代时期的地藏菩萨及弟子像袈裟的纹样中暂未采用这种纹饰,但到了五代宋时期,与敦煌遗画相似,同心圆联珠纹也开始绘制于地藏十王图中的地藏菩萨内层袈裟衣缘处,但其形制已较前代更为潦草简略,变化单调㊂表4㊀同心圆联珠纹的演变Tab.4㊀Evolution of concentric linked-pearl motifs21第61卷㊀第4期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续表4㊀㊀同前文提到的团花纹㊁贴金菱形纹一样,同心圆联珠纹并非袈裟专属纹样,其适用于敦煌壁画的边饰及多类人物服饰纹样中㊂但由于联珠纹较早经由中亚传入中原,几何化的同心圆联珠纹在绘制技巧上较团花纹更为简单,在绘制成本上较贴金菱形纹更为低廉,因此也更早在敦煌石窟的人物服饰上广泛使用,并一直延续至五代宋时期㊂但五代宋时期已不复隋代时期具有浓郁西域色彩的同心圆联珠纹,内容布局更加单一和程式化,并广泛绘制于同时期遗画中的被帽地藏菩萨内层袈裟上,且大多为内层袈裟的衣缘区域起到简单的填充作用,丰富袈裟整体的造型与色彩㊂121Vol.61㊀No.4Study on the kasaya patterns of Ksitigarbharaja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3㊀袈裟专属纹样不论是敦煌石窟还是遗画中,云水纹及线迹纹都是袈裟的专属纹样,且一般仅见于外层袈裟,尚未发现内层袈裟或其他人物服饰绘有此类纹样的特例㊂袈裟专属纹样是地藏菩萨的身份及神力在袈裟上的视觉化,在同时期的传世袈裟实物中,也能看到袈裟专属纹样的实际来源,反映了当时佛教造像艺术与纺织品文物的紧密联系㊂3.1㊀云水纹除素色袈裟外,大部分敦煌遗画中的地藏菩萨外层袈裟纹样皆为云水纹㊂但敦煌石窟中早期的地藏菩萨外层袈裟多绘树皮纹,以图3中莫高窟盛唐第166窟为例,唐前期地藏菩萨外层袈裟上的树皮纹一般绘以三色,规律分布㊁构图饱满㊂到了中晚唐时期,地藏菩萨多着石青色间橘红色的树皮纹外层袈裟,在分布上也更错落有致,外层袈裟地色露出更多㊂至盛唐时期,开始出现绘制云纹袈裟的样式,但与遗画中云水组合的样式有明显区别,如盛唐第172窟主室东壁北侧上部的地藏菩萨,其外层袈裟上的云纹以勾线形式来表现,且多为双勾卷朵云纹,具有典型的敦煌盛唐云纹特征[14],不似遗画中的朵块状㊂至中晚唐时期,才在弟子像的外层袈裟纹样上窥见与敦煌遗画类似的云纹样式,以莫高窟中唐第112窟及晚唐第459窟为例,阿难与迦叶外层袈裟云纹形状类似,皆为色块晕染状,云朵底部平缓,无勾线,整体云型更加自然放松㊂在敦煌遗画中,云水纹仅用于地藏菩萨的外层袈裟纹样,云彩一般被绘制为横向的朵块状,波浪式的线条则代表流水㊂‘道明还魂记“(敦煌遗书S.3092)对此有记载,写本在对过去的地藏造像进行勘误时,提到 宝莲承足,璎珞庄严,锡振金环,衲裁云水 的覆顶禅僧样才是地藏的真实形象[15]㊂其中 衲裁云水 中的 衲 ,为 补 缝缀 之义[16],此处写本中提出的云水纹为地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㊂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中的云水纹绘制精细程度有别,主要呈现为五代宋较中晚唐时形状更为粗糙凌乱的发展规律(图5):中晚唐时期的云水纹色彩亮丽,云型清晰㊁晕染层次丰富且水纹线条分明;五代宋时期的云水纹,云纹大多形状模糊,呈现为点块状,分布散乱,且水纹较粗,以至于斯坦因在描述图5中编号为Stein painting23.Ch.0021的遗画时,提到画中的地藏菩萨 穿着一件带黑色㊁红色和绿色杂斑的灰色袈裟 [17],其实斯坦因所说的 杂斑 就是云纹,且该画中地藏菩萨外层袈裟上的云纹仅有红㊁绿两色,由于部分水纹的起伏处墨线较粗,被斯坦因误认为是 杂斑 云纹中的第三种颜色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在中晚唐时期的遗画中,地藏菩萨基本出现在立像幡中,其袈裟受遮挡少,整体样式较五代宋时期更清晰完整㊂以图5中Stein painting118.Ch.lxi.004及TA158为例,画面中的地藏菩萨皆着半披式袈裟,均在外层袈裟条上绘三色云水纹㊂这样的三色云水纹在中晚唐时期的地藏菩萨立像幡中十分常见,于EO.1186及MG.22798中也可见一斑㊂图5㊀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中云水纹对比Fig.5㊀Comparison of cloud and water patterns in Dunhuangpainting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第二,通过比较中晚唐及五代宋时期地藏菩萨在敦煌遗画中的尺寸占比可知(图6),中晚唐时期的地藏立像幡纵向高度在53.0~83.0cm,人物部分几乎占据全画面;五代宋时期的画作在30.0~229.0cm不等,虽在画幅上较中晚唐时更大,但人物也大多只占据整体画面的1∕3左右,因此其外层袈裟纹样的占比面积比中晚唐时的更小㊂且中晚唐时期均为站姿,相比五代宋时期的坐姿地藏像,外层袈裟的衣纹褶皱更少,纹样也得以完整规律地平铺于外层袈裟田相中,形状㊁色彩㊁晕染较五代宋时期更加丰富细致㊂五代宋时期的遗画中,地藏菩萨皆为坐姿,外层袈裟的绘制面积由于动作的改变而缩小,再加之衣纹的影响,田相格被线条切割得更加细碎,前221。
法藏的生平《明末清初临济宗圆悟、法藏纷争始末考论》连载4 第三章汉月法藏及其禅法第一节法藏的生平七百年来临济,被人抹杀无地,惟有者老秃奴,偏要替他出气。
惹得天下野狐,一齐见影嘷吠,不如自家打杀,便与劈脊一击。
──法藏自赞──有关汉月法藏的生平,可参考的文献有(清)黄宗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清)弘储《天寿圣恩藏禅师行状》,以及(清)弘储编《三峰藏和尚年谱》。
明万历元年(1573)十月七日巳时(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法藏于江苏无锡出生,父亲苏兰,母亲周氏。
二岁时,父母依江南习俗让他抓周,没想到他什么都不拿,只是坐在那里笑得很开心。
五岁,当他在剥栗子吃的时候,听到父亲跟学生讲“浩然之气”,忽然丢下栗子站起来,神色很严肃。
父亲看了,感叹着说:“恐苏氏不能有此子。
”(恐怕我们苏家留不下这个孩子。
)七岁那年,发生大水灾,水漫过江岸,整个村子汪洋一片,当时法藏在学校,家人找不到他,正着急时,看到他竟骑在一只大龟上面,冲着波涛而来,赶忙把他接到小艇上。
九岁,法藏开始自动茹素,摒绝肉食。
有人问他:“孺子欲为莲池耶?学其放生!(你要做莲池大师吗?也学他放生呢!)”他因此找到莲池的放生杂文,读后流着眼泪说:“不异我意。
”十一岁,法藏得了重病,因为一位和尚,医术很高明,所以他来到德庆院,没想到才跪下来礼佛,就有很特别的感应,病竟然就好了。
十二岁,立志出家,作《出家好》歌:“秋懊恼,秋懊恼,青山待我回头早。
”当时父亲很不以为然,把歌词撕了,一直到他十五岁,才勉强答应他出家。
法藏出家时,父亲给他田地和仆童,免得他还要乞食、洒扫。
法藏坚持必须先学三年出家法。
三年期满,法藏归家受冠礼,并且告别父母,这才正式落发出家。
并于次年,得到礼部的度牒。
法藏出家之后,并没有很精进的修行。
反而是与文人来往,阄题拈韵,悠哉度日。
可是他又很有自信地告诉人家:“吾四十当悟道,六十岁死矣。
”人家问他:“子不修行,安期悟道?”法藏答:“时未至,尚当游观耳!且公以何法为修行乎?”听到的人,都觉得法藏不是普通的人。
第一辑第1冊:中國佛性論(賴永海)/自相與二諦有無(羅翔)第2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洪修平)/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徐文明)第3冊:宋代禪宗史論(魏道儒)/漢魏兩晉禪學研究(宣方)第4冊:《摩訶止觀》之「圓頓」義(戈國龍)/ 佛教的般若思想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姚衛群)第5冊:太虛之唯識學研究(程恭讓)/智顗佛教哲學述評(張風雷)/淨影慧遠大乘義章佛學思想研究(劉元琪)第6冊:中土前期禪學思想研究(徐文明)/宗杲思想研究(伍先林)第7冊:體用簡別與佛旨真詮(程恭讓)/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張志強)第8冊:出世入世與契理契機(周學農)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彭自強)第9冊:李通玄佛學思想述評(邱高興)/善導淨土思想述評(謝路軍)/印光法師淨土思想及其時代特色(韓劍英)第10冊: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護教辯論(鄭安德)第二辑第11冊:緣起論的基本問題(吳洲)/原始佛教緣起論研究(葉遠厚)/說一切有部的哲學思想探索(江亦麗)/試論佛學對中國本體學說的發展(方光華)第12冊:心性與佛性(楊維中)第13冊:日蓮論(何勁松)/試論清淨道論的禪法(黃夏年)佛教苦樂觀與慈悲觀綜論(王學成)第14冊:智顗思想與宗派佛教的興起(李四龍)/智顗觀心論思想述評(俞學明) /智顗三諦思想研究(李四龍)第15冊:煩惱即菩提(陳堅)第16冊:智圓佛學思想研究(吳忠偉)/隋唐佛學圓融思想研究(郭泉)論隋唐佛教中的圓融思維(許寧)第17冊:宗密的融合論思想研究(董群)第18冊:澄觀佛學思想研究(胡民眾)/澄觀及其佛學思想(胡民眾)/華嚴五教章哲學思想述評(徐紹強)/華嚴宗祖法藏及其思想(邱高興)/宗密的華嚴禪(董群)/宗密禪教一致論與三教一致論探析(黃磊)/宗密判宗說研究(裴勇)第19冊:肇論通解及研究(孫炳哲)/論僧肇哲學(洪修平)第20冊:般若與老莊(蔡宏)/ 從三論玄義看吉藏的中道思想(秦彧)第四辑第31冊:佛教唯識哲學要義(魏德東)/論阿賴耶識的本體論意義(魏德東)/《大乘起信論》與佛學中國化(龔雋)第32冊:境界與言詮(吳學國)/ 唯識學在中國的理論發展(宋玉波)第33冊:《起信論裂網疏》思想探析(單正齊)/論清辯對「空」的邏輯證明(劉威)/《因明正理門論》研究(巫壽康)/陳那因明思想述評(張力力)/《正理門論》探微(姚南強)/因明的現量觀(宋立道)第34冊: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王仲堯)/ 知禮佛教哲學思想及其時代特徵(王志遠)/生存與解脫(蘇軍)/ 因果與自然(何曼盈)/試論勝宗十句義論的哲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姚衛群)第35冊:荷澤宗研究(聶清)/《新唯識論》述記(陳強)/有相無相本義及其應用(翁向紅)/ 宋代佛學心論初探(凌慧)/儒佛交融與朱熹哲學的形成(李作勛)/二程與佛教(周晉)第36冊: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張恒毓)/佛性論與儒家人性論重建(韓煥忠)第37冊:近現代以佛攝儒研究(李遠杰)/ 論梁漱溟先生的儒佛思想(沈昌曖)/李贄與儒佛(楊國平)第38冊:現代新儒家與佛學(徐嘉)/柳宗元與佛教(張君梅)/論蘇軾與佛教(劉石)第39冊:晚明佛學的復興與困境(陳永革)第40冊:晚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何建明)第十一辑第101冊:〈弘明集〉研究(劉立夫)第102冊:根本唯識思想研究(周貴華)第103冊:佛典漢譯之研究(王文顏)/隋代佛教史述論(藍吉富)第104冊:敦煌講經變文之研究(羅宗濤)第105冊:盛唐詩與禪(姚儀敏)/禪宗與宋代詩學理論(林湘華)第106冊: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丁敏)第107冊: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釋永祥)/皎然詩研究(王家琪)第108冊:黃山谷之禪詩研究(柯定君)/《洛陽伽藍記》之文學研究(林晉士)第109冊:宋初九僧詩研究(吉廣輿)第110冊:〈祖堂集〉句法研究(周碧香)第五辑第41冊: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麻天祥)/佛教景教初傳中國歷史的比較研究(張曉華)第42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與日本(蕭平)/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孫永豔)/太虛星雲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張華)第43冊:民國時期的佛學與社會思潮(李少兵)/佛學與現代醫學(尹立)/隋唐五代宋初私社與寺院的關係(郝春文)/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劉雯)/ 中國古代舍利的瘞埋制度(戴俊英)第44冊: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郝春文)第45冊: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侯旭東)/唐代佛教庶民化問題初探(張朝發)/中國歷史上的比丘尼(楊孝容)第46冊:晉唐寺院與寺院經濟研究(謝重光)/試論唐前期的寺院經濟(白文固)/ 試論唐後期寺院經濟的特點(李德龍)/十至十八世紀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戴發旺)第47冊: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宋立道)/十至十五世紀新疆宗教關係研究(孫振玉)第48冊:日本當代佛教與政治(高洪)、白族密宗(李東紅)第49冊:唐代僧侶與皇權關係研究(鄭顯文)/隋唐前期諸帝佛道政策的沿革及其原因(李金水)/ 蒙古汗國及元朝時期的宗教政策(韋明)/吐蕃對河隴的統治及其對敦煌文化的影響(安忠義)/ 試論高昌國的佛教與佛教教團(姚崇新)第50冊:西夏佛教研究(田德新)/元明清時期的河西佛教(公維章)/歸義軍時期的河西佛教(劉惠琴)/吐蕃時期的河西佛教(陳海濤)/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交州佛教及其同中原佛教的關係(何勁松)/ 釋迦八相圖之研究(蔡睿娟)第十辑第91冊:天台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尤惠貞)/天臺「性惡」思想之義涵與辨正(釋覺泰)第92冊:天台判教論(韓煥忠)/試析「佛法身之自我坎陷」與天臺圓教「性惡法門」之關係(林妙貞)第93冊:華嚴「法界緣起觀」的思想探源(黃俊威)/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釋依淳)第94冊:唐初法相宗思想之轉變(阮忠仁)第95冊:憨山禪學之研究(陳松柏)/竺道生頓悟思想之研究(陳松柏)第96冊: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與影響(胡順萍)/東山法門之淵源及其影響(釋常證)第97冊:善導思想之研究(蔡纓勳)/性具與性起思想之比較研究(釋覺華)第98冊:戒律學原理(勞政武)第99冊:慧遠僧肇聖人學研究(盧桂珍)/僧肇之物性論(翁正石)、僧肇〈物不遷論〉第100冊:魏晉佛學格義問題的考察(蔡振豐)/ 世親與普特南對實在論的批判(李潔文)/佛教歷史詮釋的現代蹤跡(朱文光)第三辑第21冊: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李勇)/吉藏二諦思想研究(紀華傳)/金剛經般若思想初探(李利安)/龍樹的空觀與商羯羅的吠檀多不二論(康紹邦)/宗喀巴及其《中論》廣釋(許得存)/否定性的直覺思維(華方田)第22冊: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劉長東)/彌勒信仰述評(張文良)第23冊:慧遠的佛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業露華)/慧遠與羅什關於法身諸問題的討論(張志強)/善導的淨土思想(王公偉)/善導大師的懺悔思想及禮讚儀(聖凱)/智顗的淨土思想(張廷仕)/淨土十要思想研究(何松)/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研究(性源)第24冊:傅大士研究(張勇)第25冊:黃檗禪學思想研究(劉澤亮)/馬祖道一與洪州宗評傳(何雲)第26冊:禪宗與心學(陳利權)/鳩摩羅什禪學思想述評(劉元琪)/黃檗禪學思想述論(道本)/臨濟義玄哲學思想述評(呂有祥)/唐劍南保唐禪派及其禪法思想(黃燕生)/論神會的人生哲學(袁家耀)/宗密會通思想對普照定慧結社之影響(德相)第27冊:南宗禪學研究(邢東風)/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馮煥珍)/《壇經》主旨探析(伍先林)/關於慧能《壇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黃德遠)/《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及其對《壇經》思想的影響(靜岩)/禪宗心性說與王陽明的良知主體論(李霞)第28冊:禪宗與羅教(徐小躍)/禪宗倫理學初探(溫金玉)/中國佛教倫理研究(王月清)第29冊: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夏清瑕)/憨山思想研究(崔森)/元曉佛學思想研究(金勳)/契嵩及其佛學思想(王予文)/一行及其佛學思想(呂建福)第30冊:唯識思想及其發展(徐紹強)/「真唯識量」探討(羅炤)/論佛教唯識學認識論中的主體意識(王健)/《宗鏡錄》的法相唯識思想(施東穎)/玄奘唯識思想之研究(黎耀祖)第九辑第81冊:敦煌淨土圖像研究(王惠民)/北涼石塔造像研究(殷光明)第82冊: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圖像學研究(羅世平)/巴中南龕摩崖造像藝術研究(顧森)/濟南地區石窟摩崖造像調查與初步研究(李清泉)/炳靈寺一六九窟塑像與壁畫的年代(常青)第83冊: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馬德)/天龍山石窟分期研究(李裕群)第84冊: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分類與石窟寺院的組成(晁華山)/敦煌莫高窟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薄小瑩)/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李崇峰)/五─六世紀河西石窟與河西佛教(暨遠志)第85冊:克孜爾石窟的佛傳壁畫(丁明夷)/克孜爾中心柱窟研究(馬世長)/克孜爾洞窟形制的研究(許宛音)/莫高窟中心塔柱窟的分期研究(趙青蘭)第86冊:中原北方地區北朝晚期的石窟寺(李裕群)/須彌山唐代洞窟的類型和分期(林蔚)/遼寧義縣萬佛堂北魏石窟之研究(劉建華)/第87冊:中世紀藏傳佛教藝術(熊文彬)/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陳悅新)/旅順博物館藏犍陀羅佛教石刻(關欣)/伯孜克里克佛教洞窟分期試論(王玉冬)/西藏阿里托林寺與毗鄰的印度塔博寺阿契寺三者早期遺存間相互關係的探討(謝鵬)第88冊: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謝繼勝)第89冊: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林仁昱)90冊: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郭乃彰)第六輯第51冊: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湛如)/悟真事跡初探(續華)第52冊: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方廣錩)第53冊:敦煌變文研究(陸永峰)/敦煌維摩詰文學研究(何劍平)第54冊:禪詩研究(吳言生)第55冊:禪詩研究(吳言生)第56冊: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周裕鍇)/由「不立文字」到「文字禪」(楊維中)/禪學美學思想初探(韓鵬杰)/嚴羽的美學理論思維及其與禪宗的關係(何明)第57冊:宋詞與佛道思想(史雙元)/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黃卓越)/論東晉僧詩(盧寧)第58冊: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李小榮)/魯迅與宗教文化(王家平)/廢名創作中的佛教色彩(吉貞杏)第59冊:佛教與二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關係之研究(哈迎飛)/李贄的童心道家的真人佛家的真如(宋珂君)第60冊: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吳海勇)第七輯第61冊:佛學與人學的歷史匯流(譚桂林)/佛教與中古小說(陳洪)第62冊: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蔣述卓)/佛教與隋唐五代小說(夏廣興)第63冊: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朱慶之)/《洛陽伽藍記》句法研究(蕭紅)第64冊:魏晉南北朝佛經詞彙研究(顏洽茂)/《那先比丘經》試探(方廣錩)漢魏六朝/佛經所見若干新興語法成分(董琨)/中古佛經詞語選釋(黃先義)第65冊:《慧琳音義》語言研究(姚永銘)/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顏洽茂)第66冊: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梁曉虹)/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徐時儀)第67冊:《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盧烈紅)/漢魏六朝佛經意譯詞研究(梁曉虹)/ 魏晉南北朝佛經詞語輯釋(王兵)第68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董志翹)第69冊:《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胡敕瑞)/漢魏六朝佛經代詞探新(俞理明)第70冊:早期漢譯佛典語言研究(陳文杰)/《法顯傳》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語法比較研究(張全真)第八輯第71冊: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周廣榮)/從《正法華經》看竺法護的翻譯特點(葛維鈞)/《五燈會元》動量詞研究(張美蘭)第72冊:《南海寄歸內法傳》研究(王邦維)/《敦煌歌詞總編》校讀研究(曾良)/南宋五山與宋代寺院建築(申國全)/宋元江南佛教建築初探(趙琳)第73冊:漢唐佛教建築發展之研究(王媛)/ 漢傳佛教建築禮拜空間探源(張勃)第74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何孝榮)第75冊:禪與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戴儉)/雲南傣族小乘佛教建築研究(周浩明)/建築?宗教?文化(馮煒青)第76冊:試論西藏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形制的歷史演變(張欲曉)/西藏藏傳佛教建築裝飾題材的淵源及含義(于水山)/郎木寺歷史及現狀研究(牛宏)/ 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及影響(史工會)/ 藏傳佛教禪思想源流初探(邱環)/岷縣藏傳佛教興衰之初探(朱麗霞)第77冊: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王啟龍)/宗喀巴大師的生平及其《障所知論》漢藏對勘/王啟龍/《一切宗派源流與教義善說晶鏡史》一書研究/孫悟湖第78冊:西藏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杜永彬)第79冊:中國佛教雕塑形式體系的建立(王魯豫)/能海法師評傳(王心革)/《一切宗派源流與教義善說晶鏡史》一書研究(孫悟湖)/佛教與中國傳統藝術審美思維(唐忠毛)/中國漢傳佛教藝術與佛教傳播初探(李桂紅)第80冊:敦煌美術與古代中亞阿姆河流派美術的比較研究(劉波)/笈多藝術初探(王鏞)/佛教造像研究(張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