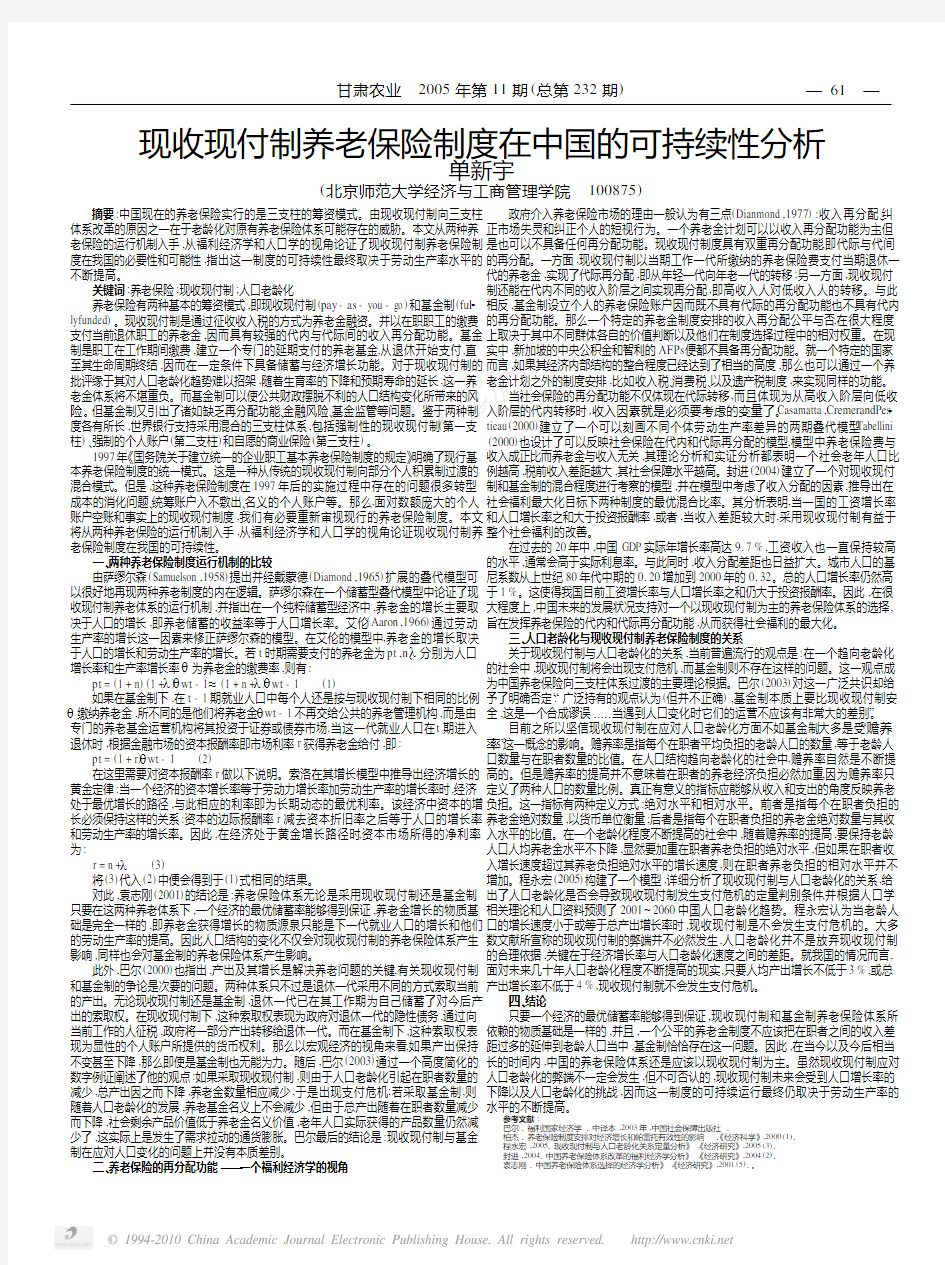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doczj.com/doc/e410876387.html,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分析
单新宇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00875)
摘要: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三支柱的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三支柱
体系改革的原因之一在于老龄化对原有养老保险体系可能存在的威胁。本文从两种养老保险的运行机制入手,从福利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有两种基本的筹资模式,即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 )和基金制(ful 2lyfunded )。现收现付制是通过征收收入税的方式为养老金融资。并以在职职工的缴费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因而具有较强的代内与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基金制是职工在工作期间缴费,建立一个专门的延期支付的养老基金,从退休开始支付,直至其生命周期终结,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储蓄与经济增长功能。对于现收现付制的批评缘于其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招架,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一养老金体系将不堪重负。而基金制可以使公共财政摆脱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但基金制又引出了诸如缺乏再分配功能、金融风险、基金监管等问题。鉴于两种制度各有所长,世界银行支持采用混合的三支柱体系,包括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第一支柱)、强制的个人账户(第二支柱)和自愿的商业保险(第三支柱)。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明确了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这是一种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过渡的混合模式。但是,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在1997年后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转型成本的消化问题、统筹账户入不敷出、名义的个人账户等。那么,面对数额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度,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本文将从两种养老保险的运行机制入手,从福利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论证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可持续性。
一、两种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机制的比较
由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8)提出并经戴蒙德(Diamond ,1965)扩展的叠代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现两种养老制度的内在逻辑。萨缪尔森在一个储蓄型叠代模型中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的运行机制,并指出在一个纯粹储蓄型经济中,养老金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即养老储蓄的收益率等于人口增长率。艾伦(Aaron ,1966)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来修正萨缪尔森的模型。在艾伦的模型中,养老金的增长取决
于人口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若t 时期需要支付的养老金为pt ,n 、
λ分别为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θ为养老金的缴费率,则有:
pt =(1+n )(1+λ)θwt -1≈(1+n +λ)θwt -1 (1)
如果在基金制下,在t -1期就业人口中每个人还是按与现收现付制下相同的比例θ缴纳养老金,所不同的是他们将养老金θwt -1不再交给公共的养老管理机构,而是由专门的养老基金运营机构将其投资于证券或债券市场,当这一代就业人口在t 期进入退休时,根据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r 获得养老金给付,即:
pt =(1+r )θwt -1 (2)
在这里需要对资本报酬率r 做以下说明。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该经济中资本的增长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资本的边际报酬率r 减去资本折旧率之后等于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在经济处于黄金增长路径时,资本市场所得的净利率为:
r =n +λ (3)
将(3)代入(2)中便会得到于(1)式相同的结果。
对此,袁志刚(2001)的结论是: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只要在这两种养老体系下,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对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影响,同样也会对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影响。
此外,巴尔(2000)也指出,产出及其增长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有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争论是次要的问题。两种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无论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退休一代已在其工作期为自己储蓄了对今后产出的索取权。在现收现付制下,这种索取权表现为政府对退休一代的隐性债务,通过向当前工作的人征税,政府将一部分产出转移给退休一代。而在基金制下,这种索取权表现为显性的个人账户所提供的货币权利。那么以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如果产出保持不变甚至下降,那么即使是基金制也无能为力。随后,巴尔(2003)通过一个高度简化的数字例证阐述了他的观点:如果采取现收现付制,则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在职者数量的减少,总产出因之而下降,养老金数量相应减少,于是出现支付危机;若采取基金制,则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基金名义上不会减少,但由于总产出随着在职者数量减少而下降,社会剩余产品价值低于养老金名义价值,老年人口实际获得的产品数量仍然减少了,这实际上是发生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巴尔最后的结论是: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在应对人口变化的问题上并没有本质差别。
二、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一个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介入养老保险市场的理由一般认为有三点(Dianmond ,1977):收入再分配、纠
正市场失灵和纠正个人的短视行为。一个养老金计划可以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主,但是也可以不具备任何再分配功能。现收现付制度具有双重再分配功能,即代际与代间的再分配。一方面,现收现付制以当期工作一代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支付当期退休一代的养老金,实现了代际再分配,即从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的转移;另一方面,现收现付制还能在代内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实现再分配,即高收入人对低收入人的转移。与此相反,基金制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因而既不具有代际的再分配功能也不具有代内的再分配功能。那么一个特定的养老金制度安排的收入再分配公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不同群体各自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在制度选择过程中的相对权重。在现实中,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和智利的AFPs 便都不具备再分配功能。就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如果其经济内部结构的整合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那么也可以通过一个养老金计划之外的制度安排,比如收入税、消费税、以及遗产税制度,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当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不仅体现在代际转移,而且体现为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代内转移时,收入因素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变量了。Casamatta ,CremerandPes 2tieau (2000)建立了一个可以刻画不同个体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两期叠代模型;Tabellini (2000)也设计了可以反映社会保险在代内和代际再分配的模型,模型中养老保险费与收入成正比而养老金与收入无关,其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都表明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税前收入差距越大,其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封进(2004)建立了一个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混合程度进行考察的模型,并在模型中考虑了收入分配的因素,推导出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两种制度的最优混合比率。其分析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GDP 实际年增长率高达9.7%,工资收入也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通常会高于实际利息率。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日益扩大。城市人口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0增加到2000年的0.32。总的人口增长率仍然高于1%。这使得我国目前工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仍大于投资报酬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未来的发展状况支持对一个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旨在发挥养老保险的代内和代际再分配功能,从而获得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
关于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当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在一个趋向老龄化的社会中,现收现付制将会出现支付危机,而基金制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观点成为中国养老保险向三支柱体系过渡的主要理论根据。巴尔(2003)对这一广泛共识却给予了明确否定:“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但并不正确),基金制本质上要比现收现付制安全,这是一个合成谬误……当遇到人口变化时它们的运营不应该有非常大的差别”。
目前之所以坚信现收现付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不如基金制,大多是受“赡养率”这一概念的影响。赡养率是指每个在职者平均负担的老龄人口的数量,等于老龄人口数量与在职者数量的比值。在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社会中,赡养率自然是不断提高的。但是赡养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在职者的养老经济负担必然加重,因为赡养率只定义了两种人口的数量比例。真正有意义的指标应能够从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反映养老负担。这一指标有两种定义方式: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前者是指每个在职者负担的养老金绝对数量,以货币单位衡量;后者是指每个在职者负担的养老金绝对数量与其收入水平的比值。在一个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中,随着赡养率的提高,要保持老龄人口人均养老金水平不下降,显然要加重在职者养老负担的绝对水平,但如果在职者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养老负担绝对水平的增长速度,则在职者养老负担的相对水平并不增加。程永宏(2005)构建了一个模型,详细分析了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给出了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导致现收现付制发生支付危机的定量判别条件,并根据人口学相关理论和人口资料预测了2001~2060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程永宏认为当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小于或等于总产出增长率时,现收现付制是不会发生支付危机的。大多数文献所宣称的现收现付制的弊端并不必然发生,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的合理依据,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面对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只要人均产出增长不低于3%,或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4%,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四、结论
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一样的,并且,一个公平的养老金制度不应该把在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多的延伸到老龄人口当中,基金制恰恰存在这一问题。因此,在当今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还是应该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虽然现收现付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弊端不一定会发生,但不可否认的,现收现付制未来会受到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而这一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最终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巴尔1福利国家经济学1中译本,2003年,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1柏杰1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帕雷托有效性的影响1《经济科学》,2000(1)1程永宏,20051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3)1封进,20041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2)1袁志刚1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5)1。
—
16—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