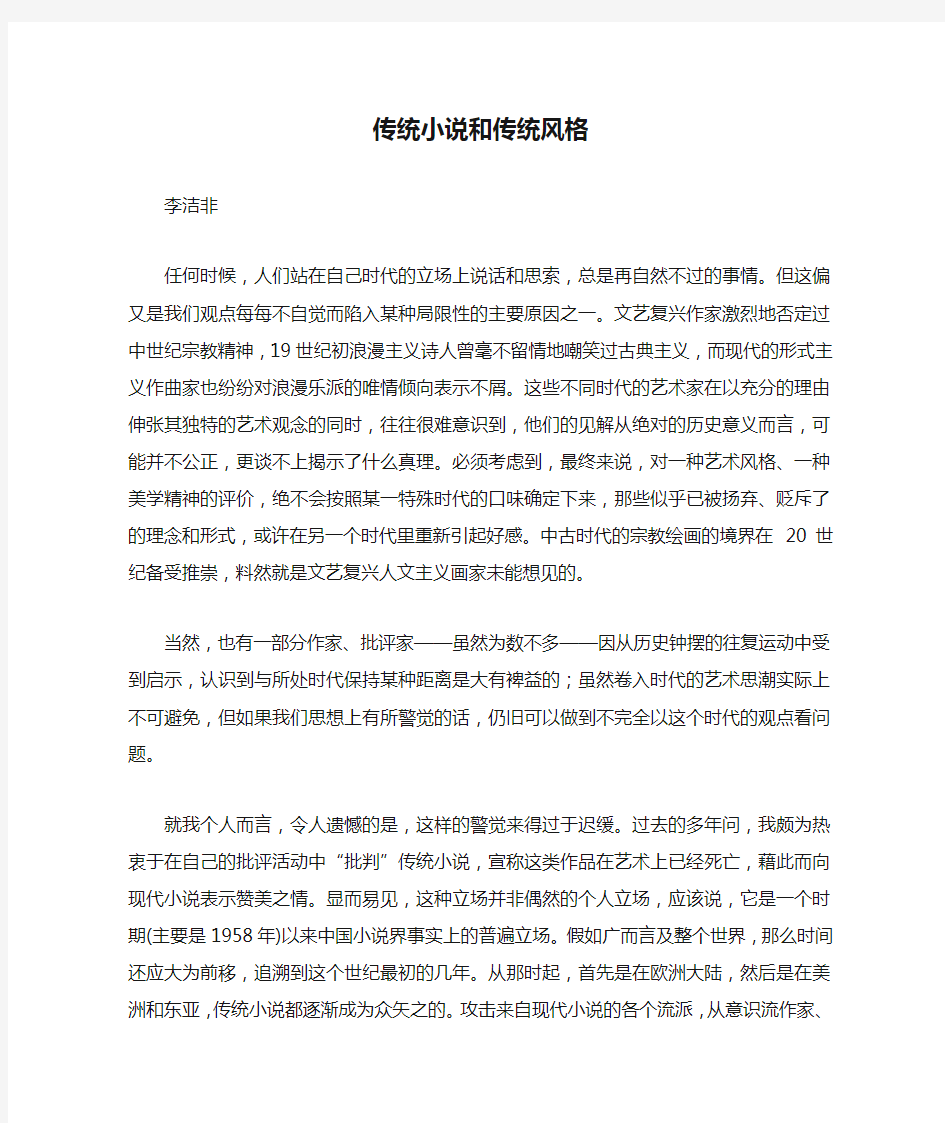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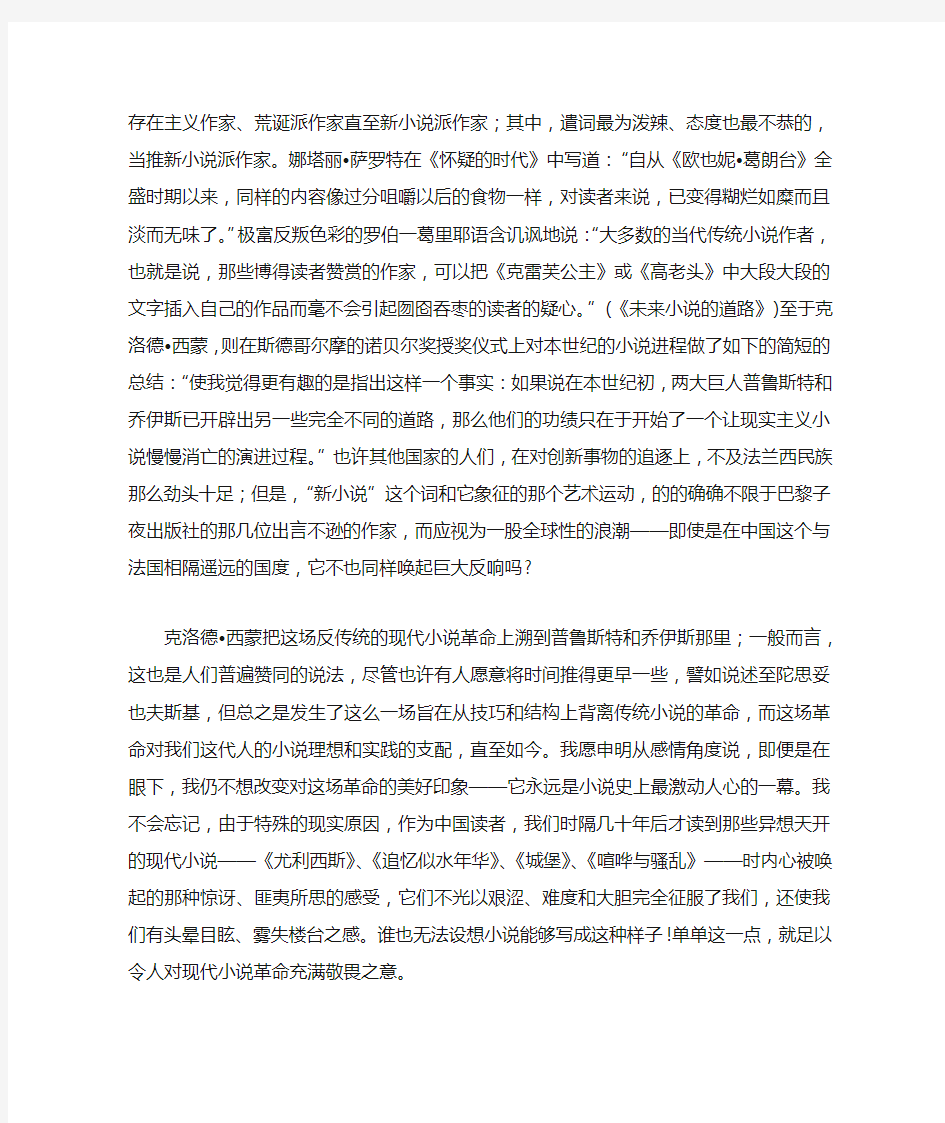
传统小说和传统风格
李洁非
任何时候,人们站在自己时代的立场上说话和思索,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这偏又是我们观点每每不自觉而陷入某种局限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文艺复兴作家激烈地否定过中世纪宗教精神,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曾毫不留情地嘲笑过古典主义,而现代的形式主义作曲家也纷纷对浪漫乐派的唯情倾向表示不屑。这些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以充分的理由伸张其独特的艺术观念的同时,往往很难意识到,他们的见解从绝对的历史意义而言,可能并不公正,更谈不上揭示了什么真理。必须考虑到,最终来说,对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美学精神的评价,绝不会按照某一特殊时代的口味确定下来,那些似乎已被扬弃、贬斥了的理念和形式,或许在另一个时代里重新引起好感。中古时代的宗教绘画的境界在20世纪备受推崇,料然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画家未能想见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批评家——虽然为数不多——因从历史钟摆的往复运动中受到启示,认识到与所处时代保持某种距离是大有裨益的;虽然卷入时代的艺术思潮实际上不可避免,但如果我们思想上有所警觉的话,仍旧可以做到不完全以这个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警觉来得过于迟缓。过去的多年问,我颇为热衷于在自己的批评活动中“批判”传统小说,宣称这类作品在艺术上已经死亡,藉此而向现代小说表示赞美之情。显而易见,这种立场并非偶然的个人立场,应该说,它是一个时期(主要是1958年)以来中国小说界事实上的普遍立场。假如广而言及整个世界,那么时间还应大为前移,追溯到这个世纪最初的几年。从那时起,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然后是在美洲和东亚,传统小说都逐渐成为众矢之的。攻击来自现代小说的各个流派,从意识流作家、存在主义作家、荒诞派作家直至新小说派作家;其中,遣词最为泼辣、态度也最不恭的,当推新小说派作家。娜塔丽?萨罗特在《怀疑的时代》中写道:“自从《欧也妮?葛朗台》全盛时期以来,同样的内容像过分咀嚼以后的食物一样,对读者来说,已变得糊烂如糜而且淡而无味了。”极富反叛色彩的罗伯一葛里耶语含讥讽地说:“大多数的当代传统小说作者,也就是说,那些博得读者赞赏的作家,可以把《克雷芙公主》或《高老头》中大段大段的文字插入自己的作品而毫不会引起囫囵吞枣的读者的疑心。”(《未来小说的道路》)至于克洛德?西蒙,则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对本世纪的小说进程做了如下的简短的总结:“使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在本世纪初,两大巨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已开辟出另一些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他们的功绩只在于开始了一个让现实主义小说慢慢消亡的演进过程。”也许其他国家的人们,在对创新事物的追逐上,不及法兰西民族那么劲头十足;但是,“新小说”这个词和它象征的那个艺术运动,的的确确不限于巴黎子夜出版社的那几位出言不逊的作家,而应视为一股全球性的浪潮——即使是在中国这个与法国相隔遥远的国度,它不也同样唤起巨大反响吗?
克洛德?西蒙把这场反传统的现代小说革命上溯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一般而言,这也是人们普遍赞同的说法,尽管也许有人愿意将时间推得更早一些,譬如说述至陀思妥也夫斯基,但总之是发生了这么一场旨在从技巧和结构上背离传统小说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对我们这代人的小说理想和实践的支配,直至如今。我愿申明从感情角度说,即便是在眼下,我仍不想改变对这场革命的美好印象——它永远是小说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我不会忘记,由于特殊的现实原因,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时隔几十年后才读到那些异想天开的现代小说——《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城堡》、《喧哗与骚乱》——时内心被唤起的那种惊讶、匪夷所思的感受,它们不光以艰涩、难度和大胆完全征服了我们,还使我们有头晕目眩、雾失楼台之感。谁也无法设想小说能够写成这种样子!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对现代小说革命充满敬畏之意。
回想起来,阅读这些作品使我产生的最突出的意识,便是相比之下,传统小说的构造和手法实在过于简单稚拙了。那时我们很顺从地接受了伍尔芙的如下论断:“难以否认的是,今日的小说艺术比旧的小说艺术有进步……古典作家的工具是粗糙的,材料是原始的。他们的杰作显得简单。”(转引自娜塔丽?萨罗特《对话与潜对话》)也许,所有的鄙夷和轻蔑都由此而来。那种喜欢接受挑战、崇尚复杂和高难度的事物的人类本能支配着我们,于是,作家开始耻于运用已被证明是浅显的技巧,批评家们则争相向公众显示自己有充足的智力去理解和解释现代小说隐晦繁难的叙述话语。当然,毋须否认的是,现代小说确以其形式文体的探索、试验及其叙述学的理论建设,反衬出传统小说固有的若干缺陷——例如,奥利维?德?马尼提出了一个批评:“传统小说假设一种接受,一种信赖,一种可靠性。比方说,自然主义者这些悲观的代表实际上表现为在为根本上的乐观主义而奋斗。他们以为能够发掘他们所要解释的那个社会的全部曲折迂回”。(《新小说》)传统小说的这种自以为是,显然大大夸张了小说这门艺术对于社会的功用。就这一点而言,那些被称作反小说的现代作家所说出的偏激之辞,自有可以理解之处;纳博科夫就曾快人快语地表示,在他眼中,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是“三个可憎的平庸作家”。如此放肆的口吻在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而言是很自然的,对纳博科夫来说,小说创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转引自《普宁》中译本之《译者的话》),既然如此,他便决不会对上述三位恰恰提倡着那种小说价值观的代表人物葆有敬意。
实际上,纳博科夫并非主张小说彻底抛弃“目的”和“思想”——《普宁》、《洛莉塔》等作品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反感的乃是那种自命不凡、以为小说家能够扮演济世救人的上帝角色的“目的”,乃是那种企图通过一篇小说建立起人性体系的雄心勃勃的“思想”,而传统小说家多多少少都在这两个方面抱有幻想。英国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特罗洛普、梅瑞狄斯等人把道德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指望由小说来达到的理想跟一个牧师通过宗教要达到的几乎没有区别;在法国,小说创作一度被当作街垒革命的余兴,后来又像巴尔扎克做到的那样,成为解剖社会的一件工具;俄国的作家们,从果戈理、冈察洛夫到契诃夫,都偏爱一种讽刺风格的社会批判方式,以此疗救人的灵魂。
无疑,在这个方面,传统小说陷入了自我夸张的幻觉。这招致了现代作家、批评家的痛快淋漓的奚落,一如任何不自量力的幻想家都使别人忍不住轻慢待之一样。如果说,本世纪初传统小说还是一个死而不僵的庞然大物,那么,到了50年代亦即传统小说已不复对现代小说革命构成威胁后,它竟然成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嘲讽的对象——中国近十年来也是如此。当谈到传统小说那无所不在的全知全能叙述者时,批评家的口气活像是描绘一个神智失常的癔症患者。也许,这种戏弄态度中夹带着实验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终于报了一箭之仇的快感(米歇尔?比托尔就曾提到过,保守人士经常将巴尔扎克“作为一件唬人的法宝,以威吓当代小说中一切革新、创新的意图。”)但除这以外未尝没有另一种快感,即由于旧时代某个象征物的毁坏和倒下而产生的欢庆之情。
20世纪的世界文坛,先后从西至东,渐次举行了关于传统小说死亡的庆祝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无论是曾与传统小说亲自较量过的战士,或是那些本来置身事外的人,都春风得意地围绕着传统小说的尸身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当这一幕也在1985—1988年间的中国出现时,文坛被一种盲目的欣喜淹没了,没有人觉察到其中缺乏对于失败者起码应有的庄严的敬意,也就是说,没有人觉察到我们的情绪和整个场面里已经包含了一丝喜剧意味——我们竞如此兴高采烈地割断了历史,毫不考虑这样做的话未来会不会遭到历史的报复。
传统小说走向危机,部分地可说是咎由自取,它所相信和要证实的某些东西并不存在,因此它在20世纪面临的可悲境地,实际上也是内在于它的那个时代观念的局限所致。然而,传统小说是否因为自身的致命缺陷便一无是处了呢?难道它在长期历史中就没有形成一定的超越时代而具永恒价值的艺术财富吗?后代的小说读者是不是除了对它感到厌烦便不复有别
的感觉?我们发现,现代小说在合乎情理地击败了传统小说的同时,对这样一些问题却避而不谈。正如传统小说曾经错误地做过的那样,如今,现代小说也把自己说成是惟一好的小说模式,概不承认前代小说的艺术价值。
问题又回到了本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任何时候,人们站在自己时代的立场上说话和思索,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美学一历史的逻辑却已经向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对于历史上的亦即旧时代的作品,我们的美学判断究竟听命于什么?是我们内心禀自美感直觉的真实感受,还是时代外加于我们理念的价值取向?如果这样的问题是从纯理论角度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往往恰恰选择的是后者。
这就是症结。倘若今天的小说家、批评家能够撇开他们的现实角色,仅以无倾向的读者的心情重读传统小说,他们真的会觉得这些作品毫无魅力吗?无论如何,这至少应该试试——作为艺术反省,最近,我就试着这样做了一次。基于对先人为主的陈见的警惕,我避开从前熟读过的作品;其次,为在短期内涉及更多作家,我将阅读对象限于短篇小说;再次,所选择的作品有的出自名家,但更多的却非大文豪所作,这可保证从中得到的印象对传统小说具有普遍性。
我首先将谈谈俄国作家库普林的《快乐》。在中国,库普林不太出名,其实他在帝俄时代颇有影响,思想上属于自由民主主义,十月革命后,库普林移居法国。这篇《快乐》是在“五四”时代通过《新青年》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它讲述一个带有民间风味的有趣故事——大皇帝召他国中的许多诗人和哲人到他的面前,要他们回答“怎样才是快乐”的问题。他这么做,纯粹出于无聊而借机找乐罢了。于是,前来回答问题的诗人、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不耐烦的大皇帝喝令手下武士拿下去剜目、割鼻,或扔到大海里。最后一个回答者是个聪明人,他没有像前几位那样提到权力、财产、饱食、爱情之类的东西,却对大皇帝说:“快乐是在人类思想的可爱。”大皇帝糊涂了,他叫起来:“那么,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还恐吓那聪明人,再过5分钟就要绞死他,“到那时你的思想还能够安慰你么?”聪明人痛痛快快地答道:“蠢材,思想是不朽的。”俄国人历来对民间故事情有独钟,他们的童话、寓言非常发达,而叙事学上的里程碑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也是在这个国家诞生的。库普林的《快乐》,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对俄国小说的影响,它那闪烁着智慧光彩的主题、纯朴明净的语言,令人心旷神怡。
粗粗估计——我没有逐字计算过——这篇小说约只一千字。从这样的篇幅,首先可以断定,它的写法必是十分简单的,而写法简单却也正是传统小说的特征之一(一种备受攻击的特征)。的确,对于我们这些头脑已被现代小说搞得复杂不堪的人来说,《快乐》从任何方面看都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则小故事。它没有插入、打乱、颠倒的时态变化,没有迷宫般的情节布局,不必说,也找不到复合的、多重的视角。然而,此时萦绕于我心间的一个疑问却是,眼下的作家中还有几个能够写出如此简单的小说?在小说结构越复杂越好的意识之下,这一点无疑很容易受到忽略。尽管通常说来,总是复杂的事物较简单的难以把握些,但在艺术中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令人踌躇。我们知道,原始艺术的形式看上去肯定简单至极,但它难道因此就比后来文明时代的艺术形式容易把握吗?我们该对小说也问问同样的问题,比方说,对于作者来说,传统风格的小说和现代风格的小说,哪一个更容易把握。当然,如果从最终意义上说,这两者都不容易把握;可是,也许存在着这种可能,即一个善于玩弄表面花样的作者可以借现代小说的复杂结构而鱼目混珠,但他却无法在质朴的传统小说形式里讨巧耍滑。对此,我有一个感觉——仅仅是种感觉——当中国小说仍然处在传统风格中时,新作者似乎很难脱颖而出,然而现在这种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哪个地方崭露头角。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谁都知道,现在写小说仿佛越来越容易了。
陈西滢女士译的英国小说《一杯茶》,作者为曼殊斐尔——也许就是现在通译作曼斯菲尔德的那位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女作家?我因手头缺少相应的资料,难以查证,不过从《一杯茶》的笔调上看,曼殊斐尔极可能就是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小说的笔调始终很温和,一种散文式的温和,不论她描绘怎样的人物——生活优裕的少妇抑或寒碜的老女人。她这样开始了《一杯茶》的叙述:“玫芳费尔,正确的说,并不美丽。不,你不能说她美丽。俏皮么?唉,要是你把她拆开来……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的残忍,好好的把一个人拆开?”
这个名叫玫芳费尔的漂亮、摩登的少妇,在一个冬雨淋漓的寒昏,在她逛过几家奢华的商店后,遇见了一个冻得瑟瑟直抖的年轻、潦倒的女子,她向玫芳费尔讨能买一杯茶的钱。有钱而且富于善心的玫芳费尔怎么做的呢?她不是给那女子钱,而是径直将她带到自己的暖和、温柔、光亮、飘着香气的家里,亲手替她脱衣,让她烤火、给她吃牛油面包、还施舍了三张五镑的钞票!当玫芳费尔慷慨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体验到“富人也有心肝”的欣慰,真是幸福极了。
曼斯菲尔德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对人物做心理分析,小说纯是生活场景的述现,然而,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玫芳费尔行为的心理意味,却令人回味再三。这引起我莫大的兴趣。实际上,相当多的传统小说作品都很擅长这种手法,例如契诃夫的《万卡》、莫泊桑的《项链》、司汤达的《法尼娜?法尼尼》,等等。但自伍尔芙以来,再加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现代小说家差不多一致认为,心理分析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还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让我们设想一下,《达罗威太太》、《都柏林人》、《变形记》、《局外人》、《情人》(玛格丽特?杜拉)……这些现代小说代表作,能否在缺少心理分析的情况下构成它们自身呢?一个法国女批评家在谈到加缪时说道:“加缪希望向我们显示他的主人公内心的空虚,并且通过这个人物的空虚,向我们显示我们自己的空虚。”(C1.Edm.马格尼夫人:《美国小说与电影》,转引自娜塔丽?萨罗特:《从陀思妥也夫斯基到卡夫卡》。)这个概括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现代作家的创作思路,他们确信小说如果不介人人物的意识活动,那么人物就难以写透。这种观念流行以来,传统的从外部行为描写人物的手法基本上被抛弃了,只是偶然才有作家(如海明威)还坚持老的方式。但问题显然在于老的方式是不是当真不能把人物写透,以及怎样才算是写透?固然,现代小说的那种钻人人物心腹的隐身法式的心理分析,几乎有着透视机般的威力;不过,作为相反的见解,我也愿意向人们推荐格特鲁德?斯坦因关于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这位曾和包括乔伊斯在内的诸多名作家过从甚密的、见多识广的夫人说:“海明威是我熟悉的作家中最含蓄……的作者。”(转引自布鲁克斯和华伦编:《小说鉴赏》)如果你读过海明威的那篇几乎全由对话构成,且以此细腻人微地刻画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短篇名作《杀人者》,你就会知道斯坦因夫人所用“含蓄”一词指的是什么——我想,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也配得上这种评价。
以下,我将就两篇作品谈谈传统小说对“性格”的塑造,一篇是左拉的《大密殊》,一篇是匈牙利作家科茨妥朗易的《淡墨画》。左拉毋须介绍了,至于科茨妥朗易的情况,则恕我孤陋寡闻,暂无可告。
塑造人物“性格”,是传统小说在艺术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追求,现代小说则弃之如蔽履。现代小说观念认为,“性格”会导致小说人物的封闭性,而且在哲学上陷入抽象人性论。所以,现代小说主张,去揭示、体现使人物受其制约的生存情况和生存过程,而非人物自身的先验的“性格”。从小说如何更接近于人生真实这一目的而言,“性格化”的人物塑造模式肯定存在局限,但是,如果是从阅读小说的特有趣味来说,“性格”形象又总是极吸引人的。玩味一个小说“性格”形象的创造过程,就像目睹民间艺人凭空用泥巴捏出栩栩如生的人形一样,常令我惊叹其神妙。
作为写实小说大师,左拉当然是塑造“性格”的圣手。《大密殊》我虽是第一次读,但一如既往地立刻就被左拉特有的干练简质的技巧紧紧攫住了。大密殊是个农夫的儿子,人高
马大,智商比别人都低一些,以致快18岁了,仍呆在中学四年级,作者称他“没有一点悟性”。可是,这么个愚钝的人又十分憨直,从不会耍滑头。一次,同学们聚起来闹事,抗议糟糕的伙食,大密殊被推举做了首领。而当校方施加了压力后,别的机灵的同学们纷纷抽身退却了,只有笨拙、认死理的大密殊不识时务,继续绝食,结果最后也只有他一个人被开除。
《淡墨画》是一个关于匈牙利某小镇上的法语女教师玛丽的故事。玛丽属于那种平时人们喜欢谈论的老姑娘,这种女人既古怪又令人同情,因为她们和爱情无缘。读完《淡墨画》,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像玛丽这个人物,如果落在现代小说家笔下,他们会如何刻画她?最有可能的是,玛丽将就被写成一个心理失常的乖张女人吧?可是在《淡墨画》里,她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毋宁说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科茨妥朗易完全从生活行为来观察这个女教师,写她的装束、言语、待人接物的态度,尤其是她的职业习惯。玛丽酷爱法语,不光在教课时死抠字眼,不放过一处文法或发音上的错误,平时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也不停地琢磨着时态、词性之类的问题。玛丽也曾赢得一个写诗的青年的同情,可这青年终于还是受不了她的“冷”而销匿了,玛丽一边想着“他已经走了吗?”的问题,一边在脑子里“用不定过去式,用固定过去式,用完全过去式”反复思考着这句话……
如果只谈鉴赏、不谈哲学,我无疑会把“性格”塑造看作一种精致的小说艺术,其迷人之处正如上述两个例子共同显示的那样,在于对人物性格某一关键特征的成功捕捉。这需要很周密的分析,从人物身上找出最基本的、能解释人物一切遭遇的东西,譬如大密殊的“没有一点悟性”、玛丽的职业癖——这一点,在理论上说出来是丝毫不费工夫的,可真的去解剖一个意欲塑造的人物时,却何止千头万绪!我们听说,传统小说家在塑造“性格”方面,事先都经过艰苦的磨炼,不断地拿生活中的各类人进行“性格”刻画素描的尝试,一如画家的人体写生那样。所以,“性格”塑造的确也可以当成一种令人神往的纯技巧来欣赏,哪怕我们已不接受它背后的小说理念。
随着传统小说一道消失的,还有小说里的生活情趣。就我所读到的现代小说而言,似乎没有一篇曾给予我们对生活的情趣的感怀——这毫不足怪,现代小说是憎视现世的,因为它十分强调反抗现世生活的秩序,不论是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还是意识形态的秩序。最早,在意识流、荒诞派时期,现代小说家笔下的生活景状就已经是令人恶心而捉摸不定的,战后,新小说派又进一步把生活描绘成冰冷的、客体的、“非情的”物化形态。人们之所以感到读现代小说是一种折磨,并不能都在于它的变形的语言形式,应该说,它拒绝表现生活的任何富于情趣的内容,也是造成读者感情障碍的重要原因。不过,现代小说之如此,也是势使其然,20世纪人类的处境——由于工业化、战争、政治对抗、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险恶、困难,这层关系已有许多批评家探讨过了。然而,不论现代小说拒绝表现生活情趣的理由多么充分,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亦即,它毕竟在这个方面呈现了巨大的空白,而读者想要到小说中寻求富于情趣的笔墨,则只能回到传统作品那里去。
当读着传统小说时,我的心情向来是放松的,不论作品里面讲述的是怎样一种故事。我发现,传统小说即便是在描写不幸的生活情景时,也不会使我们真正感到压抑。过去,我们把这一点都归结于传统小说对未来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过于笼统。风趣的态度和乐观主义并不完全相等,有时候,风趣可能仅仅是对生活作出反应的方式,而并不表示对于生活的评判。
例如,法国作家拉萨尔的《狗约》中的那个奇特的故事:有个教士,他心爱的狗病死了。教士怜其聪明如人,就把它埋在教士墓地。贪心的主教知道后,要治这教士的罪;教士辩解道,他把这狗葬到那个去处,只因它很聪明——为了说明狗的聪明,他告诉主教,狗在临死前立了约,要把它的50个金币遗赠主教。主教一听,就改口赞颂这狗确实心诚意善。另一位法国作家李显宾的《恭士丹瞿那》,也充满了风趣。它写一个一心行善、助人为乐却总是遭人误解的好好先生,他虽做了无数好事,但恶的社会竞至不能相信有这种纯洁品质存在,
所以众人纷纷指责他伪装善人而背地却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最后由法庭判决处死。一个真正了解他为人的朋友,要为他立一块碑,岂知石匠又把HOMME DE BIEN(行善的人)刻成一字之差的HOMME DE RIEN(无足轻重的人)。
这两桩故事本来色彩荒诞,但在传统作家手里,它们没有引出现代小说那种痛苦的“荒谬感”,而是成为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诙谐感。
匈牙利作家莫里兹的《七个铜板》描写了一个最悲惨的穷人家庭的一幕——为了能买一块洗衣的肥皂,“我”和妈妈“花整整一个下午来找七个铜板”。然而,在如此窘迫的生活场景中,作者表现给读者的,却是一派轻松超脱的生活情调。正如小说第一句话写道的:“穷人也可以笑”。那位唠唠叨叨、脸上不见一丝愁云的母亲,使破烂的茅屋显得无比充实。这是发自生活本身的生动气息,不是人为制造的乐观主义。
也许,还应该谈谈传统小说家喜欢表现的生活小景——就像法国作家菲伯立在《还家》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小景:一个抛弃了妻子的酒鬼,四年后回家,却见妻子已和他的一个老友一起过日子了;起先是尴尬,然后,他克制着自己要主动离开,妻子和老友却恳求他无论如何要住一夜;两个男人对酒买肉,一起抽着烟,他们仍然是朋友;第二天,他心平气和地告辞了,临别时,他吻了吻妻子,末了又对老友说道:“来,老伙计,让我们也接一个吻。”只要读到这样的故事,我无不感到如沐春风;其问,那素朴、平淡而醇厚的人情,那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生活感慨,永远散发着令人沉醉的馨香。
虽然,我们在这里不仅难以涉及传统小说的更多特点,而且就连已经提到的也暂时无法展开详细讨论,但是我意识到,在这次撇开时代的艺术价值取向、以纯欣赏的目光重读传统小说的过程中,我个人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认识。我相信,这样的认识更加接近于小说史的整体性,也更加接近于小说的未来的长远的利益。传统小说的艺术魅力远非已经从我们的美学需要中扬弃,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将以新的性质再生。这就是说,在19世纪,传统小说是作为小说艺术的一个观念体系存在着,今天,它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已经死去,不过,它却以一种艺术风格的面目焕发出新的生机。我相信,这样的认识更加接近于小说史的整体观,也更加接近于小说未来的长远利益;并且我愿意推测,也许无须太久,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思考和谈论“传统风格”这几个字,并使之重新纳入小说的实践。
至少,在探讨往后小说艺术的各种可能性时,这一种可能性应当考虑在内。
(原载《钟山》1993年第6期)
126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 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 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 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 回到晚清 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 五四 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 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 以一人耳目所及 ( 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 ),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 晚清戏曲小说目 ,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 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 。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 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 ( 略谈晚清小说 )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 晚清小说史 估量的数字, 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 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近代 小说夏晓虹知多少
意识流小说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特别是小说和电影中广为应用的写作技巧。是现代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on The narrator conveys a subject’s thoughts, impressions, and perceptions exactly as they occur, often in disjointed (不连贯的) way and without the logic and grammar of typical speech and writ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on usually i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as in Marcel Proust’s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 but it can also, by means of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be written i n the third person, as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were golden years of the modernist novel. In stimulating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s of novel creation, the theory of the Freudian and Jungian psycho-analysis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exis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human mind, that one's present was the sum of h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that the whole truth about human beings existed in the unique, isolated, and private world of each individual, writers like Dorothy Richardson, James Joyce and Virginia Woolf concentrated all their efforts on digging into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They had created unprecedented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such as Pilgrimage(1915-1938)by Richardson, Ulysses(1922)by Joyce, and Mrs.Dalloway(1925) by Woolf. Among them, James Joyce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ist; in Ulysses, his encyclopedia-like masterpiece, Joyce presents a fantastic picture of the disjointed, illogical, illusory, and mentalmotional life of Leopold Bloom, who becomes the symbol of everyman in the post-World-War-I Europe. Within the realistic perio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ne writer named Henry James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20th-century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and the founder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James's realism is characterized by his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his subject matte. His fictional world is concerned more with the inner life of human beings than with overt human actions. His best and most mature works will rende the drama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convey the moment-to-moment sense of human experience as bewilderment and discovery. And we as readers observe people and events filtering through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experience. This emphasis on psychology and on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proves to be a big breakthrough in novel writing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ming generations. 发展 20世纪20年代起,意识流技巧在小说领域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这是因为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并没有共同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发表宣言,而是一些不同国家的作者,如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和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运用新的概念与方法创作小说。他们的作品着力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方法,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受到某些责难,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承认和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这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
乔丽霞刘家鑫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191) [摘要]夏目漱石,日本近代文坛巨匠。小说《门》是夏目漱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描写了转型期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表现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精神上的孤独。该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野中宗助,这一孤独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正是夏目漱石自身的真实写照。通过该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可以循着夏目漱石的成长经历,更深层次地探究其思想观念。 [关键词]夏目漱石;《门》;思想观念;明治时期;传统文化;文明开化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9-0047-02 夏目漱石,日本近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漱石”这一笔名,源自汉籍《晋书》中“漱石枕流”一词。夏目漱石使用这一笔名的用意,在于形容自己顽固不化,是个怪人和异端者[1]。漱石写下很多小说名篇。《哥儿》,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邪恶势力和唯利是图的人际关系;《我辈是猫》,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明治时期社会的种种弊病;漱石的前三部曲《三四郎》、《其后》和《门》,以及后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和《心》,则主要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迷茫,并严肃地批判了日本盲目地模仿欧美“近代文明”的行为。 一、小说《门》概略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生活百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创作需要在生活中储备材料。但凡创造出优秀作品的作家,均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求获取文学创作的灵感。夏目漱石也不例外。从一定程度上看,漱石作品中刻画的人物,有着其本人的明显烙印。漱石的小说《门》,更是集中地体现出这种意义。《门》的出场人物,是其本人的真实写照,或是其形象的缩影。 小说《门》,1910年3月至6月连载于《朝日新闻》,1911年1月由春阳堂结集出版。该作品主要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主人公野中宗助,原是东京的富家子弟。他生性聪慧,豁达开朗,朋友众多,前途无量;他还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叫敌人的乐天派。 宗助在京都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好朋友安井的女友阿米,两人在不知不觉中相爱。没成想,他们被朋友、父母、亲戚以及整个社会抛弃。宗助和阿米先后辗转京都和广岛,最后定居在东京山崖下一座不见阳光的房子里。虽然日子贫苦,但夫妻二人和睦亲密,六年间未曾有过任何争吵。然而,他们的生活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购买日常必需用品外,极少接触社会,几乎体会不到社会的存在。他俩是怀着身居深山的心境,寄居在大城市里的。宗助“具有罪恶意识”,后来他决定逃到寺院,希望借参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转机。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摆脱世俗的羁绊,也得不到精神上的解脱。 宗助悟出,自己不是一个能走进寺院之门的人,也不是一个不进门也可以安心的人,而是一个伫立门下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这也是该小说以《门》为题的缘由。作品的结尾处写道,宗助不仅逃过了被公司裁员的命运,而且增加了五元的薪水。弟弟小六给房东做书童去了。生活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然而,在这部作品中蕴涵了漱石个人的哪些信息呢? 二、孤独的知识分子 漱石在《门》中写道:“手抓车中的皮革吊环也好,坐在天鹅绒的椅子上也好,宗助从来没有品尝过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温柔的心情。他觉得事实上也不该苛求,大家都无非是仿佛在与机械之类摩肩接踵而过一样同车坐到各自的目的地之后,就下车扬长而去了。”[2] 这段道白,刻画了主人公宗助的孤独形象。他们被社会抛弃,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内心感受不到温情。纵观全文,读者的确感受不到宗助与弟弟、佐伯叔父之间的亲情。这说明,他本身就缺乏“亲情”这种感情元素。即使宗助与妻子阿米亲密无间,未曾有过争吵,他们也仅仅是在一起共同生活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如何乐趣可言。 正如文中所说:“(宗助)夫妇俩,每天晚饭后,都要面对面地坐在火盆的两侧,作一个小时光景的闲聊。话题不外乎日常生活上的事。不过,从来不作青年男女间那种艳情蜜语,关于
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兴起于西方,发端于英国,上世纪20~4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盛行于西方各国。在不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意识流小说在创作上逐渐形成为广大评论家所认同的三大艺术特征,即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语言形式;时空跳跃的叙事结构;音乐化、蒙太奇的表现技巧。 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维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作品通过一个妇女看到墙上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而引起无限联想的意识流动过程,揭示人内在世界的丰富和易于变化。伍尔夫小说不注重表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物思想感情流程的再现上,讲究环境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果。她的文笔富于音乐性,并运用音乐上的“曲式学”结构作品,给读者以美感。 我国大陆较早受到西方意识流小说影响的重要作家王蒙认为,西方意识流文学在表现人的心理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意识流能够逼真地“写人的感觉”;他还认为,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能增大跨度和容量,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于是王蒙开始使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思想,使用放射性结构和跳跃的节奏来缩短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描写人物复杂细微的意识流动。 《风筝飘带》在文革动荡的那个年代,女人公素素本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经历又很曲折的姑娘,但在成长过程中丢失了许多各
种颜色的梦,失去理想的素素犹如被抽去了精神支柱,加之周围庸俗的环境也使她看不出多少人生意义。佳原也同样经历过心灵的苦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追求,放弃做人的真诚,他把被他人撞伤的老太太送回家,虽然遭人误解,但无怨无悔。他用他独特的善良和"憨"感化、影响着素素,唤回了素素的多彩的梦想。小说通过佳原和素素这段热恋情人谈恋爱时所遇到的麻烦反映出了尖锐的社会问 题。小说以人物的心理流动来结构全文,以内在的心理时间取代了客观的现实,素材如浮出"意识"水面的冰块,随着主人公心绪的流动而呈现跳跃性分布。作者特别注重的是人物感觉的描摹,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现人物感觉的天地。作品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素素在等待与佳原约会时思绪和意识的流动,包括素素的梦也是在流动的回忆中闪现出来的,作者在描述她的思绪时使用了内部分析手法,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素素的内心世界: “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是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 《风筝飘带》具有一种立体的美感。这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还体现在主题的多侧面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对文革和知青命运的反思,也可以从社会和青年的关系角度加以阐释,甚至可以提升至“人性”的探究层面。总之,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框架。文中运用的技巧也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 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 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 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 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 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 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 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 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 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 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
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三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 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
我的第一门公共选修课 生活中的第一次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磨灭。而我大学中的第一门公共选修课选择了《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我相信我会将这门课所学到的东西印在脑海中。因为我喜欢小说,喜欢它里面的人物刻画、情节描写、环境烘托等等。然而,在我没学这门课之前,我对通俗小说却知之甚少。给我们讲课的李老师和蔼可亲又不失幽默风趣,这门课我还是很喜欢的。这篇文章我就写在我的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课程中所收获的主要内容。 这门课我们主要学习了历史通俗小说、言情小说、倡门小说、哀情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我知道了通俗小说在一般文学史上是不受重视,甚至是被鄙夷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发展的社会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大都市市民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是报刊、印刷业的发展及稿酬制的确立;第三个原因是江浙两省深厚文化底蕴的才子为创作提供了创作队伍;最后一个原因是梁启超边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通俗小说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是因为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长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残余文学”的一面。实际上,最终它已融入了新文学之中,成为新文学内部的现代通俗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中国新旧文学的决裂十分“戏剧化”事后的复杂融合过程往往遭到历的掩盖,所以反而看不清楚了。通俗小说,就是写法比较传统的、以讲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为主要目的的小说。相对来说,严肃小说在结构、主题和语言方面要求作者有更多的创造性。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通俗小说是小说的一大题材类型,它是满足社会上最广范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挖掘。老师很形象地向我们阐述了现在和原来通俗小说的区别:以前的小市民看通俗小说大多是消遣,爱吃小点心,所以以前的通俗小说只对人们的胃口,不关心你喜不喜欢吃与你吃的健康不健康。通俗小说的通病就是抄袭,集中于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重情节的典型性和真实性。我很赞同老师给我们说的这句话“中国人一生在做两件事:自己演戏给别人看,看别人演戏。”而鲁迅的《野草》《复仇》正好反击了人们的心理——你爱看热闹,我偏不让你看!似乎人生来就喜欢追求刺激,欣赏祥林嫂的痛苦来转移或者发泄自己的痛苦,表现出当时那个似人非人的世界和人们内心的残酷。通俗小说和时代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极大,成分问题很重要,最好的是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在路遥《平凡的世界》有体现。 言情小说包括狭邪小说、倡门小说、哀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张恨水,在二十年代已崭露头角,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顶峰。二十年代以写报人杨杏园与青楼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的故事的长篇《春明外史》一举成名,三十年代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分别以京城国务总理金家七少爷金燕西与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和平民少爷樊家树与天桥唱大古书的少女申凤喜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他在抗战时期写的《丹凤街》、《八十一梦》“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了”,“在故事中尽力开掘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表现出了进一步的雅俗结合。当时男女自由恋爱不被社会,家庭,父母所接受,男女双方不能圆满结局。小说结局尸横遍野,遁入空门。我们的思想是受社会制约的。李泽厚说“中国近代人物比较复杂,新旧观念的交错,先进与保守构成了中国近代时期极为复杂的矛盾”。中国早熟的恋爱多发生在兄妹之中,知音就是你唱我能和,你上句我能接下句。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聊斋里都是男性做的白日梦。社会言情小说,让我深刻 的体会到“你与社会与无法分离”。张恨水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
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鲁迅早年的几篇文言文论文:一九O七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人之历史》,《咤科学史教篇》、《咤文化偏至论》、《咤摩罗诗力说》四篇文言论文 冯至被鲁迅称为现代最抒情的诗人 郭沫若的三个剧本:聂嫈王昭君卓文君 鲁迅的小说创作: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篇 代表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伤逝等 在小说史上的贡献:1、开创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2、开创了乡土小说3、把小说推向成熟,显示出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实绩,加快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步伐 为什么鲁迅的作品一出现就这么成熟、深刻? 这要从几个方面来论述,这是由鲁迅的生活经历,思想基础,审美追求决定的,也是由时代历史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所决定的。 1、生活方面:在人生经历中对国民的劣根性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是彻底反封建的,所以鲁迅的作品一出现就是成熟的,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其实在新文学以前,他就考虑过‘立人’的思想,确立要用文学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职业,以此作为起点,用文学来拯救民主命运,用文学来改变民族的劣根性,所以鲁迅创作的生活与思想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2、审美方面:鲁迅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切体会,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在南京求学和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大量的阅读了西方古典美学著作,接触了最新思潮的报刊,借鉴了外国小说的经验,并且他把外国小说的经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奠定了中国小说的民族化的基础。鲁迅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主要是它在在形式上是新的,成熟的。 小诗的特点是什么? 提示: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形式短小,或缘事抒情,或因物起兴,或寄情于景,以捕捉
绪论 一概念厘定和要素分析 ㈠成长小说的概念厘定 “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成长作为每一个体在生命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的原发性问题,应是文学想像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文学史上,涉及了人的成长,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出现的“成长小说”,最初肇始于西方启蒙时期,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葛利梅豪生的《痴儿西木传》算得上最早的成长小说。到18、19世纪的德语文学,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凯勒的《绿衣亨利》等作品使成长小说在主题内涵、叙事模式上基本成熟定型。相比之下,中国古典文学由于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叙事传统的拘囿,始终未能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直到现代以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个人主义启蒙话语全面开启了新的文学想像,成长小说在现代中国才得以初步开端。 成长小说从上个世纪初期被介绍和引入现代中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理论命名上的统一。研究者和翻译家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成长小说自我发挥为“发展小说”、“教育小说”、“修养小说”等等,直到近几年,仍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只有“类成长小说”而没有成长小说。[1]在中国,最早对成长小说进行概念分析和定位的是几位翻译家。1943年,冯至翻译《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时将成长小说译为“修养小说”、“发展小说”(Entuicklungsroman),他特别指出这类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修养,自然是与这个字广泛的意义:即是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复杂的网,个人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成被动的,失却独立。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断片。”[2] 1979年,刘半九在翻译《绿衣亨利》时将成长小说译为“教育小说”,他认为:“‘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
院系:人文艺术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年级:2011 科目: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 姓名:周一露学号:11303104(理工) 《桃花扇》赏析及李香君形象分析 摘要:《桃花扇》是戏曲发展的巅峰之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秉着“实人实事”的历史反思精神写出了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及其发生的大背景。这篇戏剧的思想内容历来为人传诵,李香君的形象描写栩栩如生,本文简单论述了《桃花扇》内容、成就和作者树立典型名妓-李香君的艺术形象,做抛砖引玉之作。 关键字:桃花扇李香君美丽聪慧坚强不屈凛然正气 《桃花扇》是中国戏曲中一个璀璨的明珠。它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创作的一部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传奇。 一、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及成就 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作者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这就说明作者所说的兴亡不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运,同时还企图指出明朝三百年基业为什么会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 首先,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里,我们看到了明代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原因。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的时候,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勾结四镇迎立福王。他们忘记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虚南下,成立刚刚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马士英、阮大铖对于调黄、刘三镇截防左兵的后果不是没有想到的。由于他们“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认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让步好,就悍然采取了这一着。作品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描绘,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确是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它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活动表现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出上场时唱的〈恋芳春〉里就语含讽刺。后来又写他沉迷声色,几乎为阮大铖所收买,到最后更通过张道士的当头棒喝,指明他的迷误: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出下场诗)作者正是以兴亡之恨批判儿女之情。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
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 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其创作原则强调感性,反映直觉,充分揭示西方的现代意识。 王蒙,因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篇“集束手榴弹”式小说的问世,一时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当时,其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伍尔夫被认为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其创作背景、理念和手法等与该派作家大同小异,其著作能大体反映该派小说的创作特色。所以,我认为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可以从王蒙意识流小说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异同中得出结论。 一、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王蒙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多因为他与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们在艺术手法上的选择上存在一致性。 1、有意淡化情节。 在伍尔夫看来,英国小说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历代小说家都试图用它来讲故事,而故事是文学有机体中最低级的一种,她取消情节或把之降至最低限度。她的《墙上的斑点》就毫无情节可言。《达罗卫夫人》表面上讲的是达罗卫夫人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在街上的经历,但它终不成“情节”,顶多为事件。《海浪》更无故事情节而言,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我们不难看出,在她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一降再降,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意识流。王蒙小说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 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 重在人生的体验。 2、以有限物理时间表现无限心理时间。 两人的创作目的反映到时间的处理上,一个旨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一个意在跨越历史的维度,获取沧桑之 生命体验,他们找到了心理有穿梭时空之自由的切合点。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里的时间跨度仅从上午九点到午夜时分约15个小时;《到灯塔去》象征性地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从傍晚到上午的时间顺序上;《海浪》仅涉及从黎明到黄昏一个白昼的物理时间。但在有限的网络世界里却反映了人物从青年到中年或从童年到老年等几十年的人生历程。而王蒙的《夜的眼》从华灯初上写起到下夜班为止,仅三个小时左右的钟表时间,却涉及到20年前的人生改造;在《风筝飘带》中,“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里重现了两人从初识至今的整个过程;《蝴蝶》里的张思远回城路上追忆了几十年的沉浮变化。往事以回忆的形式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 3、内心独白、象征暗示与“蒙太奇”手法的组合运用。 伍尔夫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不言而喻的,在《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中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王蒙作品也多用内心独白,《布礼》第五章中间标明“1951年到1958年”很长一节中以“我们”自称,写出心中想的没说出来的话。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不仅“灯塔”“浪”“窗”等许多事物有象征性,而且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具象征意义。《到灯塔去》第一二三章长短不一,且对应黄昏、黑夜和黎明,暗示人生悲欢交替,象征人的生与死变化。王蒙小说中的“风筝飘带”“海的梦”“春之声”等都被赋予了象征之意。蒙太奇手法具有时空转换的自由度。在《布礼》《蝴蝶》等反映历史跨度的小说中,镜头时而停在1957年8月,时而飞至1966年6月,随即又回到1949年1月;画面此刻在回城的路上, 顷刻置换为10年前的山村。而在《达罗卫夫人》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转换,随着汽车巨响,闪出达罗卫夫人惊跳的镜头,忽而转为赛普蒂默斯恐慌的场面。显然,他们用蒙太奇技法,或为顺利展现历史变迁,或为成功实现人物在同一时刻内意识活动的交替并置,不过都强化了小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然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等方面存有迥异之处。正如郭宝亮先生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所说:王蒙(小说)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 二、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1、创作背景之别。
第4章通俗小说(一) 一、填空题 1.《玉梨魂》是________派的代表作品。(中山大学2012年研) 【答案】鸳鸯蝴蝶 【解析】《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祖师”徐枕亚的代表作品。小说写书生何梦霞教馆,与主人家无锡富绅崔姓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个殉情一个殉国演成悲剧。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酬答,缠绵悱恻,也合于当时文人读者的欣赏习惯。 2.周作人称________创作的小说《玉梨魂》为“鸳鸯蝴蝶派祖师”,张恨水的长篇小说________被人称为“民国《红楼梦》”。(中山大学2011年研) 【答案】徐枕亚;《金粉世家》 【解析】徐枕亚是近现代小说家,《玉梨魂》是其代表作。其小说不仅以哀感顽艳著称,而且也以骈四俪六之文体为其显著特点,对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从而使徐枕亚成为“鸳鸯蝴蝶派祖师”;《金粉世家》是张恨水早期新闻生涯积累的生活素材的一次喷发,以一个豪门弃妇为贯穿线索,描写平民女子冷清秋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务总理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出走的悲剧过程,被人称为“民国《红楼梦》”。 3.________的言情小说________引发了民初文坛的言情小说热,周作人称这部小说为“鸳鸯蝴蝶派祖师”。(中山大学2010年研) 【答案】徐枕亚;《玉梨魂》
【解析】徐枕亚的《玉梨魂》写书生何梦霞教馆,与主人家无锡富绅崔姓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个殉情一个殉国演成悲剧。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酬答,缠绵悱恻,也合于当时文人读者的欣赏习惯。周作人评价《玉梨魂》“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 二、名词解释 1.鸳鸯蝴蝶派 答:鸳鸯蝴蝶派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2.林译小说 答:林译小说是指清末林纾(琴南)翻译的小说。他一生译著欧美小说一百八十多种,一千二百多万字,其中三十多种为世界名著,其余小说也多有精彩之处。其翻译作品都是与精通外语者合作,译笔传神还是靠他达到各有特色,既有《迦因小传》这样译笔哀婉的作品,也有《块肉余生记》等译笔的质朴古劲风格。除了对西方写实方法的肯定,林纾的文学观念仍是中国的,他将狄更斯比作司马迁、班固。《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哀婉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开始了在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在1898年前后发生。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近代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变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1、西方知识观念对文学的促进 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接受西方的近代科学观念,以此为基点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变革和维新成为时代主潮。 2、社会变革对文学的促进 文学活动和创办报刊有了法律保障,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具有大众化、平民化、民主特征的现代出版业逐步兴盛,为文化和文学的普及奠定了传播基础。科举制度废除,社会出现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出现了职业作家群。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价值取向。 3、文学自身发展的促进。 古典文学形式(诗词文赋)的式微,新的文学形式的孕育。文学自身发展的现代性追求导致传统文学产生新的质变。 二、文学观念的变革 (一)梁启超的“三界革命” 晚清时期,出于“新民”目的和改良社会的需要,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即“三界革命”。 1、“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下形成的文化运动。 “诗界革命”为梁启超首倡,其黄遵宪为主将。 “诗界革命”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要有新语句,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旧瓶装新酒”,要求保留诗歌的旧形式,变革不彻底。其目的主要是以诗歌革命的旗帜为政治改革张目。 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把新思想新材料入诗。他最早提出了用俗语进行文学创作。 “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影响到1918年的新诗运动。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 “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吸收西方的雄辩体、随笔体,结合魏晋文风,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 “新文体”:粱启超借鉴日本和西方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创造出一种“新文体”。其特点是思想新颖,文白夹杂,平易畅达,笔锋饱含感情,具有很强的鼓动力。 3、“小说界革命” 晚清政治改良思想家希望小说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中阐释了他的小说革命主张。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
外国文学与翻译研究 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 孙胜忠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关键词:德国经典成长小说;美国成长小说;自主;社会化;差异 摘 要:从小说主题,主人公性格特征、人生遭际、行为方式和文本的结构等方面,辨析德国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从社会、文化、存在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视角分析成长小说变异和发展的成因。自主和社会化的矛盾构成了人的自由的宿命;思与行的脱节、洞见的消失和混沌、委琐感的弥漫,构成了成长小说的当下魅力。成长小说仍在成长中,它不会衰亡。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5)03-0319-0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man classical Bildungsroman and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 SU N Sheng-zho ng(College of Foreign L anguages,A N U,W uhu241000,China) Key words:G erman classical Bildungsroman;American Bildungsroman;autonomy;socializatio n;differ ences Abstract:T he paper ex plor 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German classical Bildungsroman and its Amer ican coun terpart and closely differentiates one fr om the other fr om the themes of the genre,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pro tag onists,their lot in life,their behav iors,and the tex tual structur e,and analyses the reaso ns for the ev olution of the genre fro m social,cultural,ex istential and psy cho-analyt ical perspectives.I t is argued that the contradict ion between autonomy and socialization predestinates the results o f human freedom,and that the disconnectedness of reflection and action and the alternat ion of insight w ith a sense of confusion and inconsequent iality in moder n Bil dungsroman appeal to the co ntemporary readers.It is predicted t hat Bildungsroman as a genre is still evolving, and w ill never come to its end. 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这一术语同德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一批作家创作的小说紧密相连。[1](P92)它的故乡无疑在德国,而歌德的杰作 维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Wilhelm Meisters L ehrj ahr e,)被公认为是这一文学样式的经典之作,可以说它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成长小说的一块试金石。后来,这种小说风靡欧洲,经英国传入美国,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 成长小说的产生可追溯到德国18世纪70-8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该运动的形成受英法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启蒙思想家强调教育,但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主张依靠反抗来改变社会,其方式是通过抒发个人在社会中的主观感受来揭露社会,表达他们在社会中的体验、经历和感受。特定的社会环境部分地说明了成长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在 维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于1795 1796年间首次出版之际,德国被分成了数以百计由统治王朝成员所控制的独立国家。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的崛起,感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威胁,认为维护和平和秩序是每个公民的首要职责。18世纪下半叶欧洲德语国家拥有一批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在他们看来,早期教育至关重要,孩子们必须接受有明确教育目的的培训: 他们必须要成为自律的公民和在开明统治 第33卷第3期Vol.33 .3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f Anh ui N ormal Univ ersity(Hum.&Soc.Sci.) 2005年5月 M ay2005 收稿日期:2005-03-18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科研专项基金项目(2004xzx1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 规划课题(2002EWY004)作者简介:孙胜忠(1964-),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