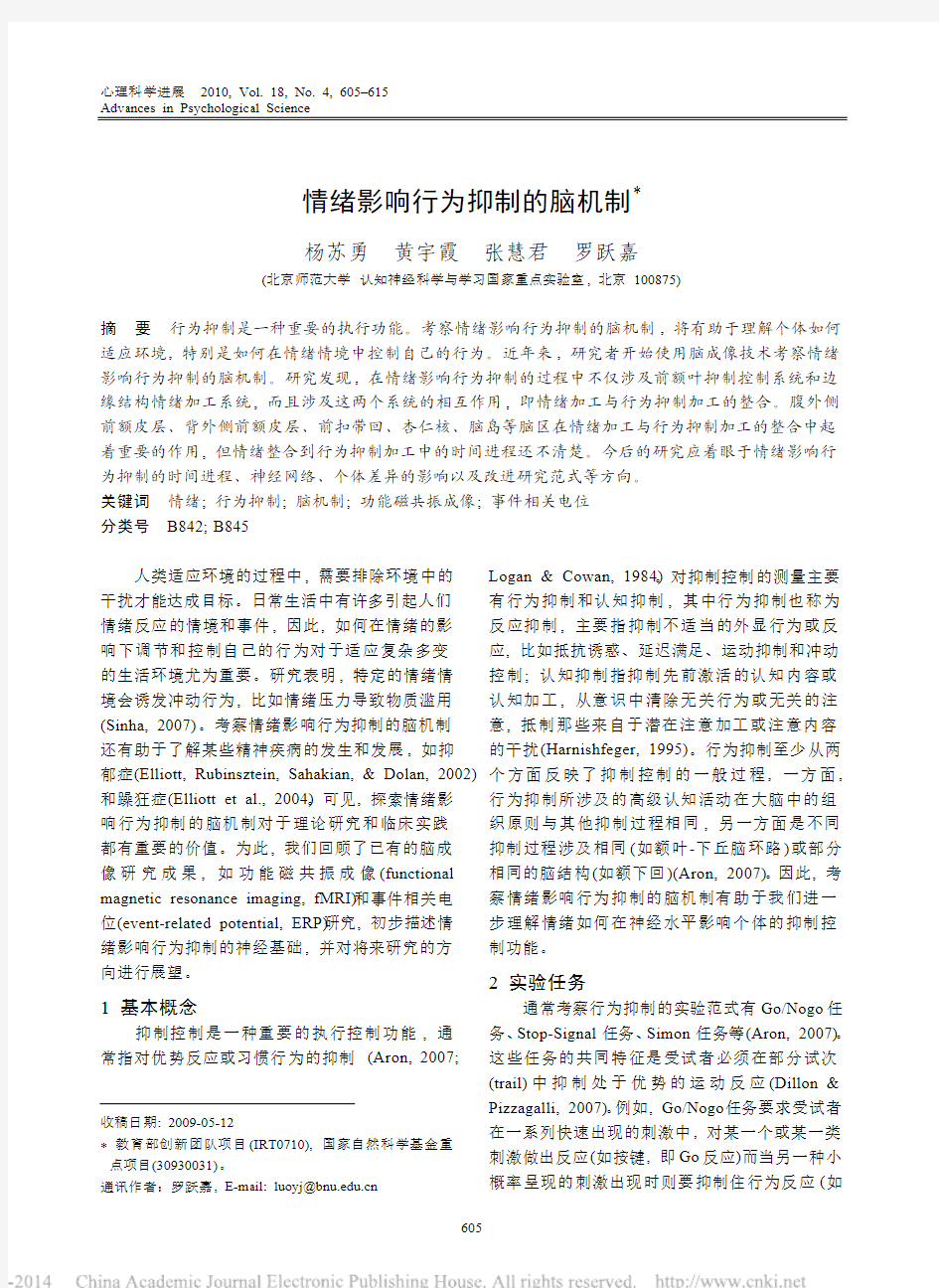

心理科学进展2010, Vol. 18, No. 4, 605–615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杨苏勇黄宇霞张慧君罗跃嘉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摘要行为抑制是一种重要的执行功能。考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将有助于理解个体如何适应环境, 特别是如何在情绪情境中控制自己的行为。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研究发现, 在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前额叶抑制控制系统和边缘结构情绪加工系统, 而且涉及这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 即情绪加工与行为抑制加工的整合。腹外侧前额皮层、背外侧前额皮层、前扣带回、杏仁核、脑岛等脑区在情绪加工与行为抑制加工的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情绪整合到行为抑制加工中的时间进程还不清楚。今后的研究应着眼于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时间进程、神经网络、个体差异的影响以及改进研究范式等方向。
关键词情绪; 行为抑制; 脑机制; 功能磁共振成像; 事件相关电位
分类号 B842; B845
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需要排除环境中的干扰才能达成目标。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引起人们情绪反应的情境和事件, 因此, 如何在情绪的影响下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尤为重要。研究表明, 特定的情绪情境会诱发冲动行为, 比如情绪压力导致物质滥用(Sinha, 2007)。考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还有助于了解某些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如抑郁症(Elliott, Rubinsztein, Sahakian, & Dolan, 2002)和躁狂症(Elliott et al., 2004)。可见, 探索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对于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有重要的价值。为此, 我们回顾了已有的脑成像研究成果, 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研究, 初步描述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神经基础, 并对将来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
1 基本概念
抑制控制是一种重要的执行控制功能, 通常指对优势反应或习惯行为的抑制 (Aron, 2007;
收稿日期: 2009-05-12
?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IRT07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0930031)。
通讯作者:罗跃嘉, E-mail: luoyj@https://www.doczj.com/doc/c618931288.html, Logan & Cowan, 1984)。对抑制控制的测量主要有行为抑制和认知抑制, 其中行为抑制也称为反应抑制, 主要指抑制不适当的外显行为或反应, 比如抵抗诱惑、延迟满足、运动抑制和冲动控制; 认知抑制指抑制先前激活的认知内容或认知加工, 从意识中清除无关行为或无关的注意, 抵制那些来自于潜在注意加工或注意内容的干扰(Harnishfeger, 1995)。行为抑制至少从两个方面反映了抑制控制的一般过程, 一方面, 行为抑制所涉及的高级认知活动在大脑中的组织原则与其他抑制过程相同, 另一方面是不同抑制过程涉及相同(如额叶-下丘脑环路)或部分相同的脑结构(如额下回)(Aron, 2007)。因此, 考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情绪如何在神经水平影响个体的抑制控制功能。
2 实验任务
通常考察行为抑制的实验范式有Go/Nogo任务、Stop-Signal任务、Simon任务等(Aron, 2007)。这些任务的共同特征是受试者必须在部分试次(trail)中抑制处于优势的运动反应(Dillon & Pizzagalli, 2007)。例如, Go/Nogo任务要求受试者在一系列快速出现的刺激中, 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刺激做出反应(如按键, 即Go反应)而当另一种小概率呈现的刺激出现时则要抑制住行为反应(如
-606-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不按键, 即Nogo反应), 通过Go反应时和Nogo 误报率来评估行为抑制能力。Stop-Signal任务要求受试者在进行简单或双选反应时任务中探测到停止信号时, 中止当前的动作反应, 通过计算停止信号反应时(SSRT)估计行为抑制能力(Band, van der Molen, & Logan, 2003)。
为了考察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 需要把情绪诱发与抑制控制任务结合起来。目前的研究中主要使用三种方式呈现情绪刺激。第一种是外显情绪任务,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根据情绪刺激效价的不同选择执行或抑制行为。这类任务的特点是情绪刺激与行为抑制任务的靶刺激为同一个情绪刺激物, 以该刺激物的情绪属性指导行为的执行和抑制(Chiu, Holmes, & Pizzagalli, 2008; Hare, Tottenham, Davidson, Glover, & Casey, 2005; Hare et al., 2008; Shafritz, Collins, & Blumberg, 2006), 这类刺激称为外显情绪行为执行/抑制线索, 比如悲伤的表情呈现时抑制按键反应, 此时的悲伤表情就是外显情绪行为抑制线索。第二种是内隐情绪任务,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根据情绪刺激的非情绪属性选择执行或抑制行为。这类任务的特点是由非情绪属性指导行为抑制(Goldstein et al., 2007), 这类刺激称为内隐情绪抑制/执行线索, 比如以情绪词为刺激材料, 要求受试者根据字体的不同作出按键与否的反应, 此时的字体就是内隐情绪行为抑制线索。第三种方式是情绪干扰任务, 通常要求受试者被动观看或倾听情绪性刺激, 接着完成由非情绪刺激组成的反应抑制任务(Sommer, Hajak, Dohnel, Meinhardt, & Muller, 2008; Yu, Yuan, & Luo, 2009)。内隐情绪任务与外显情绪任务的差别在于, 前者需要受试者排除情绪的干扰。情绪干扰任务中情绪的诱发是外显的, 但是行为信号出现时受试者必须排除情绪的干扰, 因此其内在机制可能与内隐情绪任务类似。这三种任务都包含了行为抑制和情绪加工过程, 并且通过情绪信息与行为的整合设定和执行目标任务。因此, 它们动员的脑神经网络可能有很大的重叠。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比较三者的差异。目前的脑机制研究主要使用外显情绪行为抑制任务, 尤其是情绪Go/Nogo任务, 因此, 我们将以外显情绪行为抑制任务的研究为主讨论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同时比较这三种方式导致的脑区激活差异。3 神经机制
情绪Go/Nogo任务不仅可以考察反应抑制, 而且可以考察情绪对反应抑制的影响(Schulz et al., 2007)。尽管Go/Nogo任务形式简单, 但是其中包括了刺激辨别、反应选择、运动准备、反应/行为抑制、冲突/错误监控等过程(Goldstein et al., 2007)。究竟情绪加工的边缘系统如何影响前额抑制控制环路的机制还不完全清楚(Phelps & LeDoux, 2005)。为此, 我们将着重讨论行为抑制的额叶抑制控制回路在不同情绪呈现方式下的活动情况, 并讨论各区在情绪影响行为抑制过程中的作用, 但不涉及情绪刺激在枕叶和颞叶等感觉区的加工。
目前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外显情绪Go/Nogo 任务(Elliott, Rubinsztein, Sahakian, & Dolan, 2000;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例如, 在一个实验Block中包含了两类情绪面孔(平静和恐惧), 当呈现恐惧面孔(75%)时作出快速按键反应, 相反, 平静面孔(25%)呈现时不作出任何按键反应(Hare et al., 2008)。从实验设计上看, 通常包括情绪效价(正性、中性、负性情绪)×行为控制(行为执行、行为抑制)的3×2因素设计(Schulz et al., 2008)。通过对神经信号的反应分析, 可以得到情绪加工(情绪主效应)、行为抑制(行为控制主效应)、特定情绪下的行为执行或行为抑制(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和简单效应)的脑区激活图。为此, 我们从行为抑制、情绪加工和情绪与行为抑制整合的层次来描述情绪影响行为抑制过程的脑功能定位。其中, 情绪与行为抑制整合部分将作为重点讨论。
3.1 行为抑制和情绪加工
目前一致认为, 额叶-基底神经节回路是执行行为抑制任务的神经基础(Aron, 2007; Dillon & Pizzagalli, 2007), 但是对额叶各区在抑制过程中的作用看法不一(Mostofsky & Simmonds, 2008)。其中一种观点认为, 右侧腹外侧前额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 又称为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负责抑制无关行为, 而背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参与工作记忆、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探测与目标不一致的冲突(Aron, Robbins, & Poldrack, 2004; Buchsbaum,
第18卷第4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607-
Greer, Chang, & Berman, 2005)。其中, 右侧VLPFC广泛参与反应抑制、记忆提取抑制、任务定势切换等抑制控制任务, 因而被认为是具有一般抑制功能的脑区(Aron et al., 2004)。最近, Mostofsky和Simmonds (2008)提出辅助运动区前部(pr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pre-SMA)是选择适当的行为的关键区域, 其中包括选择投入到适当的运动反应和选择抑制不适当的运动反应, 而VLPFC参与维持工作记忆中的信息, DLPFC 参与操作工作记忆中的信息。研究发现, 外侧前额皮层在Go/Nogo任务中的激活依赖于任务需求(Mostofsky et al., 2003), 而且对Go/Nogo任务的fMRI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只有pre-SMA的激活独立于任务类型(Simmonds, Pekar, & Mostofsky, 2008), 这些证据说明pre-SMA也是行为抑制的核心之一。
与非情绪Go/Nogo任务的发现一致, 在情绪Go/Nogo任务中也发现行为抑制信号(Nogo信号)激活VLPFC(Elliott et al., 2000; 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DLPFC (Hare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pre-SMA (Shafritz et al., 2006)和ACC (Elliott et al., 2000;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这些结果表明Go/Nogo任务的神经心理结构在情绪背景中得以保留(Schulz et al., 2007)。
情绪加工的主要神经中枢是边缘系统, 包括杏仁核(amygdala)、前扣带回和脑岛(insular cortices)等(Phan, Wager, Taylor, & Liberzon, 2002)。杏仁核是最重要的情绪中枢, 负责编码刺激物的情绪效价并指导行为(Dolan, 2007), 还可以探测情绪刺激, 尤其是对于个体生存有重要意义的恐惧情绪刺激尤为敏感(Phan et al., 2002)。脑岛, 尤其是脑岛前叶(anterior insular cortices)是情绪加工的重要副边缘结构, 其主要功能是监测个体的内部情绪状态(Damasio et al., 2000), 整合感觉、动机和行为(Augustine, 1996)。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的主要功能是解码和表征基本强化物、把视觉及其它刺激学习和反转为这些强化物、控制和矫正与奖赏和惩罚有关的行为(Rolls, 2004)。
在外显情绪任务中, 刺激物的情绪效价激活杏仁核(Hare et al., 2005; Schulz et al., 2008)、ACC(Elliott et al., 2000;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脑岛(Elliott et al., 2000; Schulz et al., 2008), 但不激活OFC (Elliott et al., 2000;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情绪干扰任务(Sommer et al., 2008)和内隐任务(Goldstein et al., 2007)中边缘系统激活的情况还不明确。有研究发现, 外显情绪任务(判断表情类别)与内隐情绪任务(性别判断)相比, 前者更多地激活梭状回和颞中回而后者更多地激活杏仁核(Critchley et al., 2000)。Critchley等(2000)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杏仁核对情绪刺激尤其恐惧表情的加工是自动化的和无意识的, 而对有意识的表情辨认需要动用更高级的视觉皮层。但这无法解释外显情绪Go/Nog中刺激物的情绪效价激活杏仁核(Hare et al., 2005; Schulz et al., 2008)。这一问题需要深入杏仁核在不同意识状态中研究才能解答, 例如, 比较阈下和阈上情绪诱发的行为抑制差异。
3.2 行为抑制与情绪的整合
以上我们对情绪行为抑制任务中, 涉及行为抑制和情绪加工两个过程神经基础进行了描述。更重要的问题是情绪信息如何影响行为抑制加工。从信息加工的假设来看,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情绪信息如何整合到行为抑制的过程中。我们将考察行为抑制和情绪交互作用激活的主要脑区, 讨论情绪信息和行为信息的交互作用如何在大脑编码、解码和输出的。
3.2.1 VLPFC
VLPFC包括Brodmann Area (BA) 44 (岛盖部, pars opercularis)、45(三角部, pars trianglulairs)和47/12(眶部, pars orbitalis)(Petrides & Pandya, 2002)。外显情绪任务中, 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VLPFC眶部(Elliott et al., 2000; Hare et al., 2005)和三角部(Shafritz et al., 2006)。最近的研究中未发现眶部的激活, 仅三角部和岛盖部被正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Schulz et al., 2008)。Schulz等(2008)把这一结果解释为, 眶部从下颞叶皮层接受背景信息的输入, 编码情绪信息的行为重要性通过输出到三角部和岛盖部影响行为抑制, 同时输出到颞顶联合区和顶上区执行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 而三角部和岛盖部不仅直接调控前运动皮层而且编码情绪和动机信息。Schulz等(2008)强调, 尽管信息的输入来自于情绪加工的脑区,
-608-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但是右侧额顶叶网络并不直接对情绪本身作出反应, 而是根据认知和情绪背景对这些刺激的行为重要性进行编码。与上述外显情绪任务一致, 内隐情绪任务(Goldstein et al., 2007)和情绪干扰任务(Sommer et al., 2008)中都观察到情绪效价调节行为抑制线索对VLPFC的激活, 表明情绪信息对VLPFC的调节作用独立于情绪刺激的呈现方式。根据Mostofsky和Simmonds (2008)的假设, 在行为抑制过程中, VLPFC的作用是维持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而不是行为抑制本身。因此, 情绪效价对VLPFC的调节作用也可能是情绪信息在工作记忆中维持的结果。
3.2.2 pre-SMA
SMA是感觉运动皮层的一部分, 可分为本体(SMA prope或caudal SMA)和前部(pre-SMA 或 rostral SMA), 是执行高级运动的重要脑区(Picard & Strick, 2001)。其中pre-SMA位于BA6内侧的喙部, 它在解剖和功能上都更靠近前额皮层, 进行如高级运动程序和产生内部指导的运动等运动控制(Picard & Strick, 2003)。在内隐情绪任务中, pre-SMA受到负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如斜体字“悲伤”)的激活而不是行为抑制线索(Goldstein et al., 2007)。Goldstein等(2007)提出, 这一现象可能是情绪反应导致行为抑制失败的基础, 即负性情绪唤起个体的运动行为(为了生存而战斗或逃跑), 因此抑制行为反应变得困难。但是, 外显情绪反应抑制任务的研究结果与内隐情绪任务不同。Shafritz等(2006)发现, 外显情绪任务中pre-SMA(BA6)只参与行为抑制过程, 但是并不受情绪效价的调节。由于内隐任务中杏仁核激活显著, 因此, 我们推测, 外显任务中pre-SMA受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不显著是由于杏仁核无明显激活导致的。将来的研究有必要对pre-SMA和杏仁核做功能连接, 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相互作用。在Mostofsky和Simmonds (2008)的假设中, pre-SMA起到选择和抑制的双重作用。如果, 情绪调节pre-SMA被证实, 那么是否表明情绪可以直接影响行为抑制的输出呢?至少从目前的证据看, 内隐情绪可以直接影响行为抑制的输出(Goldstein et al., 2007)。
3.2.3 DLPFC
DLPFC大体上包括额上回和额中回, 即前部(BA 10)、后部(BA 6喙侧和BA 8)以及中部(BA 9和BA 46), 其主要功能是保持、选择和操作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和内容(Petrides, 2000)。研究证实, 在情绪干扰下的工作记忆任务(词与非词的3-Back任务)中, DLPFC的激活依赖于情绪与任务刺激的结合方式(即正性情绪面孔对DLPFC的激活高于正性情绪词, 而负性情绪面孔的激活则低于负性情绪词), 提示情绪和认知的整合可能发生在DLPFC(Gray, Braver, & Raichle, 2002; Perlstein, Elbert, & Stenger, 2002)。与此相似, 情绪背景下的行为抑制任务中也发现了情绪与行为抑制任务的交互作用激活DLPFC(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外显情绪任务中, 右侧DLPFC(BA9)不仅被行为抑制线索激活, 而且在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下激活明显(Hare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内隐情绪任务中, 右侧DLPFC(BA 9/45/46)被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激活而且仅被负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Goldstein et al., 2007)。这些数据支持了外侧PFC的整合功能假设(Gray et al., 2002), 提示DLPFC在情绪与行为抑制信息的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Goldstein et al., 2007)。同时, DLPFC在情绪行为抑制任务中的跨任务一致性提示, DLPFC对情绪与行为抑制信息的整合独立于情绪信息与任务的关联性。但是, 由于DLPFC也是情绪调节的重要脑区, 参与主动抑制悲伤情绪(Phan et al., 2005), 因此上述研究(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的发现也可能是受试者主动抑制负性情绪进而动员DLPFC造成的。
Mostofsky和Simmonds (的行为抑制模型认为, DLPFC的作用是对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操作。那么, 情绪行为抑制信号激活DLPFC表明情绪信息(负性或中性)与中性情绪信息相比, 需要更多的工作记忆操作。DLPFC在整合信息中的作用, 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
3.2.4 ACC
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由BA24、25、32、33构成, 可分为背侧区和喙-腹侧区, 其中背侧部分与认知加工有关, 而腹侧部分与情绪加工有关(Bush, Luu, & Posner, 2000)。在行为抑制过程中, ACC的主要作用是冲突监控和错误监控(Garavan, Ross, Murphy, Roche, & Stein, 2002; Rubia et al., 2001)。在情绪性行为
第18卷第4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609-
抑制任务中, ACC不仅参与行为抑制(Elliott et al., 2000;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 而且还参与情绪加工(Elliott et al., 2000;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更重要的是, ACC参与了行为抑制和情绪加工的交互作用(Goldstein et al., 2007; Shafritz et al., 2006)。在执行行为反应时, 情绪效应表现在腹侧ACC (Elliott et al., 2000; Shafritz et al., 2006); 在抑制行为时情绪效应表现在背侧ACC (Goldstein et al., 2007; Shafritz et al., 2006)。因此, ACC可能是情绪加工和认知加工的交界(Allman, Hakeem, Erwin, Nimchinsky, & Hof, 2001)。也就是说, 执行行为的时候, 情绪加工占优势因而激活腹侧ACC, 相反, 抑制行为的时候认知加工占优势因而激活背侧ACC。
在内隐情绪任务(Goldstein et al., 2007)、情绪干扰任务(Sommer et al., 2008)和部分外显情绪任务(Shafritz et al., 2006)中, 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ACC。但是, 在大多数外显情绪任务中, 都没有观察到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ACC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ACC 激活可能反应了较大冲突的出现(Banich et al., 2008)。在内隐情绪任务中, 个体必须忽视刺激的情绪属性, 而在情绪干扰任务中必须抑制情绪刺激诱发的情绪。在这些情况中, 行为抑制线索既有强烈的情绪显著性但是又与当前的任务无关, 由此产生的冲突激活ACC。
除前扣带回之外, 情绪性行为抑制任务研究中还报告了扣带回的其他结构被激活, 如内隐情绪任务中, 负性行为抑制线索激活左侧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Goldstein et al., 2007); 外显任务中, 左侧中扣带回后部(posterior midcingulate cortex, pMCC)被正性情绪线索激活, 但不被行为抑制线索激活(Schulz et al., 2008)。这些结果可解释为, PCC参与情绪评估和任务效价探测(Maddock, Garrett, & Buonocore, 2003), pMCC参与反应选择(Picard & Strick, 2001)。
扣带回在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过程中, 主要起到整合情绪与行为信息的作用。对于扣带回各次级结构在情绪影响行为抑制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由于很多研究都使用Go/Nogo任务进行研究, 但是对扣带回的研究结果却有很大差异, 因此有必要寻找更适合的实验任务(Schulz et al., 2008)。
3.2.5 杏仁核
在外显情绪任务中, 杏仁核被负性情绪行为执行线索激活(Hare et al., 2005; Schulz et al., 2008), 但不被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在内隐情绪任务中, 正性和负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都激活杏仁核, 但是两者激活杏仁核的差异不明显, 提示内隐情绪行为抑制中杏仁核的激活独立于情绪效价(Goldstein et al., 2007)。这些结果表明, 杏仁核可能参与对情绪与行为抑制交互作用的信息特征编码(即编码“与情绪有关而却与任务无关的行为反应”)。已有研究显示, 杏仁核可以探测那些与行为反应(如要求按键或不按键)相关的非情绪刺激(如字母)(Ousdal et al., 2008), 说明杏仁核参与对行为反应信息的编码。此外, 在情绪干扰任务中也未观察到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激活杏仁核(Sommer et al., 2008)。与前面的推测相符, 情绪干扰任务中的行为抑制线索为出现在情绪背景中的非情绪刺激。将来的研究应着眼于杏仁核如何编码情绪和行为的交互作用。
3.2.6 OFC
OFC包括BA 11、13、14和12/47, 它与杏仁核不仅直接相互连接, 而且通过背内侧丘脑间接联系(Roberts & Wallis, 2000)。在内隐情绪任务中, 不仅正性、负性情绪抑制线索激活双侧OFC 而且情绪与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也激活该区(Goldstein et al., 2007)。Goldstein等(2007)根据躯体标记假设(Damasio, 1999)把这一现象解释为, OFC参与躯体标记的存储。但是, 在外显情绪任务中, 既未观测到行为抑制线索激活OFC, 也未发现情绪效价对OFC的调节作用(Elliott et al., 2000; 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我们推测, 内隐任务中的OFC可能参与解码杏仁核输入的情绪与行为交互作用的信息, 并作出适当的决策保证任务的执行。因为, 内隐情绪任务中OFC激活伴随有杏仁核的激活(Goldstein et al., 2007), 而外显任务中情绪抑制线索不激活OFC和杏仁核(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这一推测有待今后的研究的中进一步证实。
-610-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3.2.7 脑岛
在情绪Go/Nogo任务中, 脑岛前叶在行为抑制过程中受到情绪线索的选择性激活(Goldstein et al., 2007; Shafritz et al., 2006)。随着抑制难度的增大, 负性情绪线索对左侧脑岛的激活也逐渐增大(Schulz et al., 2008)。这些结果表明, 脑岛在情绪抑制任务中的激活反映了负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编码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Shafritz et al., 2006)。有研究者推测, 情绪的唤起发生在脑岛, 然后与其他认知信号在腹侧ACC整合, 这一整合过程保证了在社会背景下做出适当的行为决策(Shafritz et al., 2006)。
3.2.8 其他脑区
在情绪性行为抑制任务中, 还发现其它一些脑区的激活, 如尾状核(caudate nucleus)、海马(hippocampus)等(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5)。无论外显情绪任务(Goldstein et al., 2007)还是内隐情绪任务(Hare et al., 2005), 正性情绪背景(正性情绪为Go)下的负性情绪行为抑制线索(负性情绪为Nogo)均激活尾状核, 但是在中性情绪背景(中性情绪为Go)中激活不明显(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5)。可见, 尾状核并不是被负性情绪线索选择性激活, 而是与正性情绪背景相关, 因此尾状核可能参与对正性情绪目标产生的优势反应(Shafritz et al., 2006)。内隐情绪任务中, 行为抑制线索激活海马, 提示这些脑区受到情绪加工和抑制任务相互作用的调节(Goldstein et al., 2007)。这些发现提示, 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可能分布在一个相对广泛的神经网络中, 情绪呈现方式也可能调节这些区域在行为抑制中的参与。
4 未来的研究方向
4.1 研究内容
4.1.1 行为抑制与情绪整合的时间进程如何?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项ERP研究考察了情绪影响抑制控制的时间进程(Chiu et al., 2008; Yu et al., 2009)。Chiu等(2008)在一项外显情绪Go/Nogo任务中, 观察到Go条件而不是Nogo条件下的N2(200~420ms)和P3 (420~770ms)成分具有情绪效应。Yu等(2009)使用情绪干扰任务考察了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她们使用听觉材料诱发情绪然后测量与听觉Go/Nogo任务(非情绪刺激)对应的ERP成分。该研究发现, 情绪主效应不仅在N2(200~400ms)中得到体现, 还表现在更早期的成分N1(80~150ms)中, 但是在较晚期的P3成分中却未发现显著的情绪效应。相对于Chiu等(2008)的研究, 该研究还发现Nogo条件下的N2也表现出显著的情绪主效应(Yu et al., 2009)。这些ERP研究提示:1)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可能存在跨感觉通道的差异; 2)情绪刺激与情绪状态对抑制控制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由于这类ERP研究较少, 因此要获得更明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4.1.2 情绪影响行为抑制过程中神经网络?
在论述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神经基础时, 我们根据已有研究分别讨论了各个脑区的作用。这种讨论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各个脑区在结构上存在的广泛连接和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事实上, 研究者最感兴趣的也正是杏仁核与前额皮层之间的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Schulz et al., 2008)。在考察情绪性行为抑制的脑成像研究中, 仅有的一项功能连接分析显示, 负性情绪线索指导行为执行(即负性情绪面孔为靶刺激)时杏仁核与vPFC 的激活成负相关(Hare et al., 2008)。这一结果提示从神经网络的角度考察情绪与行为抑制的关系可能有助于理解两者在神经水平的整合模式。由于功能连接分析是一种纯数据驱动的相关分析, 在方法学上还存在很多争议。因此, 从神经网络的层次探讨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4.1.3 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个体差异具有怎样的
神经基础?
在脑成像研究中, 情绪(Flores-Gutierrez et al., 2009; Meriau et al., 2009)和认知功能(Etienne, Marin-Lamellet, & Laurent, 2008)的个体差异问题长期以来都备受研究者关注(Zelazo, Craik, & Booth, 2004), 但是对情绪影响抑制控制的个体差异的研究才开始(Hare et al., 2008)。
就年龄因素而言, 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是否随着大脑发育的成熟而逐步减弱?这种影响又是否会随着大脑的老化而发生改变?在情绪Go/Nogo任务中, 青少年的杏仁核在恐惧情绪刺激出现的早期阶段激活比成年人强烈, 而且低焦虑特质青少年的vPFC激活比低焦虑的成年人的更明显, 说明青少年在适应情绪的开始阶段需要前额叶参与情绪的管理(Hare et al., 2008)。可见,
第18卷第4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611-
探索年龄因素在情绪调节抑制控制中的作用, 有助于理解人类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的发展及老化过程。
就性别差异而言, 在情绪情景中男性是否比女性更容易失去对行为的控制?这种差异产生的大脑基础是什么?Hare等(2008)发现, 尽管男性的杏仁核受情绪行为执行线索的激活大于女性, 但是杏仁核受行为执行线索的激活并未表现出显著男女差异, 而且男性杏仁核在抑制条件下的激活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效价特异性。此外, 左侧颞下回钩(Uncus, BA20)的激活与性别、情绪效价和行为抑制的交互作用有关(Hare et al., 2008)。这些结果表明, 杏仁核及海马旁回等边缘系统中的重要结构可能是情绪行为抑制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基础, 但其中的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处于排卵周期不同阶段的女性在情绪Go/Nogo任务中的半脑优势效应存在差异(Hwang, Wu, Chen, Yeh, & Hsieh, 2009), 这说明女性内分泌的周期性改变可能是导致情绪对抑制控制影响效应中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
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在情绪影响抑制控制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发现, 人格特质是情绪反应差异的重要因素。外向型人格(Canli, Sivers, Whitfield, Gotlib, & Gabrieli, 2002)、焦虑特质(Hare et al., 2005)与杏仁核对正性情绪的反应有关, 静息状态下的VMPFC与受试者的负性情绪状态正相关(Zald, Mattson, & Pardo, 2002)。但是, 目前还不清楚人格差异是否调节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深入阐述这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情绪管理、焦虑和前额-杏仁核系统之间的关系。
4.1.4 情绪维度和情绪类型如何调节情绪对行为
抑制的影响?
情绪维度论认为, 情绪可以从效价、唤醒度和支配度三个维度进行描述(Lang, Bradley, & Cuthbert, 2005)。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只操纵情绪刺激效价, 对唤醒度和支配度的控制和操作较少(Chiu et al., 2008; Elliott et al., 2000; Goldstein et al., 2007; Hare et al., 2005)。情绪情绪效价与唤醒度不是线性相关而是U型关系, 即从负性到中性为负相关; 从中性到正性为正相关(Bradley & Lang, 2007)。因此, 实验中操纵唤醒度和效价存在一定难度。在考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研究中, 如果负性情绪与正性情绪之间无显著差异, 而两者与中性情绪刺激差异显著时, 研究者倾向于用情绪的唤醒度效应解释(Chiu et al., 2008)。此外, 不同的情绪类型对应着不同的脑结构, 例如, 恐惧与杏仁核、愉快和厌恶与基底神经节(主要是纹状体和壳核)关系密切(Phan et al., 2002)。不同类型的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是否有差异还不得而知。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该尽可能系统操纵情绪变量考察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
4.2 研究方法
在研究情绪影响抑制控制的实验任务(如情绪Go/Nogo任务)中, 包括了情绪诱发和抑制控制加工两部分。因此, 这类任务不仅包括了情绪诱发任务和抑制控制任务本身存在的局限, 也包括了两者如何结合的难题。开发出更有效的研究范式将行为抑制与情绪诱发有效结合起来, 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抑制控制任务来看, Go/Nogo任务最大的优点是简便易行, 无论是ERP研究(Chiu et al., 2008; Yu et al., 2009), 还是fMRI研究中都有广泛的运用(Goldstein et al., 2007; Schulz et al., 2008)。但是, 受试者完成情绪Go/Nogo任务时的命中率较高且误报率较低, 提示任务诱发的反应冲动性不足(Goldstein et al., 2007)。同时, Go/Nogo任务诱发的ERP成分与抑制控制的关系尚存争议(Smith, Johnstone, & Barry, 2008)。Stop-Signal任务为直观测量抑制控制提供了停止信号反应时间(SSRT)作为客观指标, 行为学研究中也开始使用SSRT考察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Verbruggen & De Houwer, 2007)。近来, 双选择oddball范式开始应用于反应抑制的ERP研究(Wei, Chan, & Luo, 2002; Yuan, He, Zhang, Chen, & Li, 2008)。该范式要求受试者对高频的标准刺激和低频的分心刺激做出不同的按键反应, 由于对低频分心刺激的执行需要抑制高频标准刺激产生的反应优势, 因此通过相减法(分心刺激减标准刺激的差异波)可以获得更加客观的指标和更纯的抑制控制成分。在行为抑制任务中, 为了增强反应优势势必减少抑制刺激出现的概率, 这样会与刺激新异性产生混淆。因此, 有必要在行为抑制任务中提高抑制控制的难度同时又要控制刺激出现概率的影响。总的来说,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Go/Nogo范式, 因此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不同研究
-612-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范式应用于情绪与行为控制的脑机制研究中。
选择适当的行为抑制任务必须与情绪诱发结合起来考虑, 并且应当符合脑成像研究的特点。比如, Stop-Signal任务Stop信号与Go信号的间隔通常在1秒以内, 进行ERP研究时只能通过算法减小Go信号对Stop信号的影响(Bekker, Kenemans, Hoeksma, Talsma, & Verbaten, 2005), 这就大大削弱了应用停止信号任务的可行性。此外, 在ERP研究中需要大量的试次提高信噪比, 由此产生了受试者对情绪刺激适应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把情绪适应作为变量纳入研究中(Hare et al., 2008)。例如, Hare等人(2005)按照情绪刺激呈现的时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考察杏仁核的情绪适应问题。
在研究情绪与行为抑制相互作用的研究中, 从情绪诱发的角度来看, 常见的实验设计有Block设计(Goldstein et al., 2007; Yu et al., 2009)和完全随机设计(Schulz et al., 2008; Shafritz et al., 2006; Verbruggen & De Houwer, 2007)。研究发现, 情绪刺激对ERPs的影响从呈现后200~ 300ms开始在1秒左右达到最大, 并持续6秒左右(Cuthbert, Schupp, Bradley, Birbaumer, & Lang, 2000)。在Block设计中, 单个Block内保持相同效价的情绪刺激, 通过适当增加Block间隔休息时间, 可以避免诱发情绪间的干扰(Goldstein et al., 2007)。而且, Bolck设计的另一优势是在休息间隔可以用自我报告法对受试者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定。相反, 在完全随机设计中, 不同情绪效价的刺激连续出现, 由此导致的情绪之间的干扰很难排除, 也无法让受试者进行主观评定。但是, Block设计并不适用于考察情绪属性指导的行为抑制, 因为外显情绪任务中情绪刺激只能按效价不同成对出现在同一个Bolck中(例如, Hare et al., 2008)。
从行为抑制角度来看, 常用的有Block设计和ER(事件相关)设计。在Block设计中, 把只有Go的Block从同时含有Go和Nogo的 Block中减去, 以此获得抑制控制激活的脑区, 但是, 其中包含了错误反应产生的错误加工等过程; 在ER设计中, 通过比较正确的Nogo激活与其他部分(如任务基线或成功的Go)激活的差异获得抑制加工的激活区, 因此ER设计可以提高行为抑制的脑功能定位的准确性(Mostofsky et al., 2003)。例如, ACC具有错误监控的功能(Garavan et al., 2002), 在行为抑制的Block设计研究中都报告了情绪行为抑制线索激活了ACC (Goldstein et al., 2007; Shafritz et al., 2006), 但是在ER设计的研究中没有发现ACC的激活(Hare et al., 2005; Hare et al., 2008; Schulz et al., 2008)。因此, Block 设计中很难把ACC的激活归为情绪行为抑制线索的激活。我们建议在情绪Block中使用行为抑制的ER设计, 既能提高情绪反应的生态学效度, 又能保证准确的脑功能定位。
此外, 目前的研究大多缺乏对情绪诱发程度的有效监控(Chiu et al., 2008; Elliott et al., 2000; Goldstein et al., 2007)。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提供受试者情绪改变的检测信息, 如自我报告或皮肤电、心率等心理生理指标。
5 结论
情绪行为抑制任务不仅动员了进行抑制加工的额叶-基底神经节回路, 还动员了进行情绪加工的边缘系统。个体要在情绪背景中顺利完成行为抑制, 还必须在VLPFC、ACC、DLPFC等多个行为抑制加工脑区整合情绪信息。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发生的时间进程还不明确。对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研究刚起步, 因此很多问题有待于积累更多的研究结果才能得到进一步解决。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情绪与认知是相互影响的(Blair et al., 2007)。我们着重回顾了情绪对抑制控制的影响, 但是认知活动对情绪的影响在将来的研究中也同样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Allman, J. M., Hakeem, A., Erwin, J. M., Nimchinsky, E., & Hof, P. (2001).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face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Unity of Knowledge: The Convergence of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935, 107?117.
Aron, A. R. (2007). The neural basis of inhibition in cognitive control. Neuroscientist, 13(3), 214?228.
Aron, A. R., Robbins, T. W., & Poldrack, R. A. (2004). Inhibition and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4), 170?177.
Augustine, J. R. (1996). Circuitry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the insular lobe in primates including humans. Brain Research Reviews, 22(3), 229?244.
Band, G. P. H., van der Molen, M. W., & Logan, G. D. (2003). Horse-race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stop-signal procedure.
第18卷第4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613-
Acta Psychologica, 112(2), 105?142.
Banich, M. T., Mackiewicz, K. L., Depue, B. E., Whitmer, A. J., Miller, G. A., & Heller, W. (2009). Cognitive control mechanisms, emotion and memory: A neural perspective wit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pathology.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3(5), 613?630.
Bekker, E. M., Kenemans, J. L., Hoeksma, M. R., Talsma, D., & Verbaten, M. N. (2005). The pure electrophysiology of sto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55(2), 191?198.
Blair, K. S., Smith, B. W., Mitchell, D. G. V., Morton, J., Vythilingam, M., Pessoa, L., et al. (2007). Modulation of emotion by cognition and cognition by emotion. NeuroImage, 35(1), 430?440.
Bradley, M. M., & Lang, P. J. (2007). 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and Attention. In J. A. Caon & J. J. Allen (Eds.), Handbook of Emotion Elicitaion and Assessment (pp. 29?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city Press. Buchsbaum, B. R., Greer, S., Chang, W. L., & Berman, K. F. (2005).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the Wisconsin card-sorting task and component processes. Human Brain Mapping, 25(1), 35?45.
Bush, G., Luu, P., & Posner, M. I. (2000).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fluences in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6), 215?222.
Canli, T., Sivers, H., Whitfield, S. L., Gotlib, I. H., & Gabrieli, J. D. E. (2002). Amygdala response to happy faces as a function of extraversion. Science, 296(5576), 2191?2191.
Chiu, P. H., Holmes, A. J., & Pizzagalli, D. A. (2008). Dissociable recruitment of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and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in emotional response inhibition. NeuroImage, 42(2), 988?997.
Critchley, H., Daly, E., Phillips, M., Brammer, M., Bullmore, E., Williams, S., et al. (2000). Explicit and implicit neural mechanisms for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from facial expressions: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Human Brain Mapping, 9(2), 93?105. Cuthbert, B. N., Schupp, H. T., Bradley, M. M., Birbaumer, N., & Lang, P. J. (2000). Brain potentials in affective picture processing: covariation with autonomic arousal and affective report. Biological Psychology, 52(2), 95?111. Damasio, A. R. (1999).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New York.
Damasio, A. R., Grabowski, T. J., Bechara, A., Damasio, H., Ponto, L. L. B., Parvizi, J., et al. (2000). Subcortical and cortical brain activity during the feeling of self-generated emotions. Nat Neurosci, 3(10), 1049?1056.
Dillon, D. G., & Pizzagalli, D. A. (2007). Inhibition of action,
thought, and emotion: A selective neurobiological review. 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 12(3), 99?114. Dolan, R. J. (2007). The human amygdala and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in behavioural regul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362(1481), 787?799.
Elliott, R., Ogilvie, A., Rubinsztein, J. S., Calderon, G., Dolan, R. J., & Sahakian, B. J. (2004). Abnormal ventral frontal response during performance of an affective go/no go task in patients with mania. Biological Psychiatry, 55(12), 1163?1170.
Elliott, R., Rubinsztein, J. S., Sahakian, B. J., & Dolan, R. J. (2000). Selectiv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stimuli in a verbal go/no-go task: an Fmri. NeuroReport, 11 (8), 1739?1744 Elliott, R., Rubinsztein, J. S., Sahakian, B. J., & Dolan, R. J. (2002). The Neural Basis of Mood-Congruent Processing Biases in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9(7), 597?604.
Etienne, V., Marin-Lamellet, C., & Laurent, B. (2008).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normal aging. Revue Neurologique, 164(12), 1010?1017.
Flores-Gutierrez, E. O., Diaz, J. L., Barrios, F. A., Guevara, M. A., del Rio-Portilla, Y., Corsi-Cabrera, M., et al. (2009). Differential alpha coherence hemispheric patterns in men and women during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musical emo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71(1), 43?49.
Garavan, H., Ross, T. J., Murphy, K., Roche, R. A. P., & Stein, E. A. (2002). Dissociable Executive Functions in the Dynamic Control of Behavior: Inhibition,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NeuroImage, 17(4), 1820?1829. Goldstein, M., Brendel, G., Tuescher, O., Pan, H., Epstein, J., Beutel, M., et al. (2007). Neural substrat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al stimulus processing and motor inhibitory control: An emotional linguistic go/no-go fMRI study. NeuroImage, 36(3), 1026?1040.
Gray, J. R., Braver, T. S., & Raichle, M. E. (2002).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9(6), 4115?4120.
Hare, T. A., Tottenham, N., Davidson, M. C., Glover, G. H., & Casey, B. J. (2005). Contributions of amygdala and striatal activity in emotion regulat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57(6), 624?632.
Hare, T. A., Tottenham, N., Galvan, A., Voss, H. U., Glover, G. H., & Casey, B. J. (2008). 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 in Adolescence During an Emotional Go-Nogo Task. Biological Psychiatry, 63(10), 927?934.
-614-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Harnishfeger, K. (1995).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F. Dempster & C. Brainerd (Eds.), Interference and inhibition in cognition (pp. 175?204). San Diego: Academic.
Hwang, R. J., Wu, C. H., Chen, L. F., Yeh, T. C., & Hsieh, J. C. (2009). Female menstrual phases modulate human prefrontal asymmetry: A magnetoencephalographic study. Hormones and Behavior, 55(1), 203?209.
Lang, P. J., Bradley, M. M., & Cuthbert, B. N. (2005).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Affective rating of pictures and instruction manual. University of Florida.
Logan, G. D., & Cowan, W. B. (1984). On the ability to inhibit throught and action: a theory of an act of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91(3), 295?327
Maddock, R. J., Garrett, A. S., & Buonocore, M. H. (2003).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tivation by emotional words: fMRI evidence from a valence decision task. Human Brain Mapping, 18(1), 30?41.
Meriau, K., Wartenburger, I., Kazzer, P., Prehn, K., Villringer, A., van der Meer, E., et al. (2009). Insular activity during passive viewing of aversive stimuli reflec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tate negative affect. Brain and Cognition, 69(1), 73?80.
Mostofsky, S. H., Schafer, J. G. B., Abrams, M. T., Goldberg, M. C., Flower, A. A., Boyce, A., et al. (2003). fMRI evidence that the neural basi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is task-dependent.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17(2), 419?430.
Mostofsky, S. H., & Simmonds, D. J. (2008).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response selection: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5), 751?761. Ousdal, O. T., Jensen, J., Server, A., Hariri, A. R., Nakstad, P. H., & Andreassen, O. A. (2008). The human amygdala is involved in general behavioral relevance detection: Evidence from an event-relat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Go-NoGo task. Neuroscience, 156(3), 450?455.
Perlstein, W. M., Elbert, T., & Stenger, V. A. (2002). Dissociation in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of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working memory-related activ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9(3), 1736?1741.
Petrides, M. (2000). The role of the mid-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working memor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33(1), 44?54.
Petrides, M., & Pandya, D. N. (2002). Comparative cytoarchitecton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and the macaque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corticocortical connection patterns in the monkey.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6(2), 291?310.
Phan, K. L., Fitzgerald, D. A., Nathan, P. J., Moore, G. J., Uhde, T. W., & Tancer, M. E. (2005). Neural substrates for voluntary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affect: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Biological Psychiatry, 57(3), 210?219.
Phan, K. L., Wager, T., Taylor, S. F., & Liberzon, I. (2002).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Emotion: A Meta-Analysis of Emotion Activation Studies in PET and fMRI. NeuroImage, 16(2), 331?348.
Phelps, E. A., & LeDoux, J. E. (2005). Contributions of the amygdala to emotion processing: From animal models to human behavior. Neuron, 48(2), 175?187.
Picard, N., & Strick, P. L. (2001). Imaging the premotor areas. Curr Opin Neurobiol, 11(6), 663?672.
Picard, N., & Strick, P. L. (2003). Activation of th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during performance of visually guided movements. Cereb Cortex, 13(9), 977?986.
Roberts, A. C., & Wallis, J. D. (2000). Inhibitory Control and Affective Processing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Neuro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the Common Marmoset. Cereb. Cortex, 10(3), 252?262.
Rolls, E. T. (2004). The functions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Brain and Cognition, 55(1), 11?29.
Rubia, K., Russell, T., Overmeyer, S., Brammer, M. J., Bullmore, E. T., Sharma, T., et al. (2001). Mapping Motor Inhibition: Conjunctive Brain Activations across Different Versions of Go/No-Go and Stop Tasks. NeuroImage, 13(2), 250?-261.
Schulz, K. P., Clerkin, S. M., Halperin, J. M., Newcorn, J. H., Tang, C. Y., & Fan, J. (2009). Dissociable neural effects of stimulus valence and preceding context during the inhibition of responses to emotional faces. Human Brain Mapping, 30(9), 2821?2833
Schulz, K. P., Fan, J., Magidina, O., Marks, D. J., Hahn, B., & Halperin, J. M. (2007). Does the emotional go/no-go task really measure behavioral inhibition?: Convergence with measures on a non-emotional analog. Archives of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22(2), 151?160.
Shafritz, K. M., Collins, S. H., & Blumberg, H. P. (2006).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neural systems in emotionally guided response inhibition. NeuroImage, 31(1), 468?475.
Simmonds, D. J., Pekar, J. J., & Mostofsky, S. H. (2008). Meta-analysis of Go/No-go tasks, demonstrating that fMRI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inhibition is task-dependent. Neuropsychologia, 46(1), 224?232.
Sinha, R. (2007). The role of stress in addiction relapse.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9(5), 388?395.
第18卷第4期情绪影响行为抑制的脑机制 -615-
Smith, J. L., Johnstone, S. J., & Barry, R. J. (2008). Movem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the Go/NoGo task: The P3 reflects both cognitive and motor inhibitio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9(3), 704?714.
Sommer, M., Hajak, G., Dohnel, K., Meinhardt, J., & Muller, J. L. (2008). Emotion-dependent modulation of interference processes: an fMRI study. Acta Neurobiologiae Experimentalis, 68(2), 193?203. Verbruggen, F., & De Houwer, J. (2007). Do emotional stimuli interfere with response inhibition? Evidence from the stop signal paradigm. Cognition & Emotion, 21(2), 391?403.
Wei, J. H., Chan, T. C., & Luo, Y. J. (2002). A modified oddball paradigm "cross-modal delayed response" and the research on mismatch negativity.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57(2), 221?230. Yu, F., Yuan, J., & Luo, Y. J. (2009). Auditory-induced emotion modulates processe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NeuroReport, 20(1), 25?30. Yuan, J. J., He, Y. Y., Zhang, Q. L., Chen, A. T., & Li, H.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al inhibitory control: ERP evidence from a two-choice oddball task. Psychophysiology, 45(6), 986?993.
Zald, D. H., Mattson, D. L., & Pardo, J. V. (2002). Brain Activity in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Correlate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gative Affec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9(4), 2450?2454.
Zelazo, P. D., Craik, F. I. M., & Booth, L. (2004). Executive func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cta Psychologica, 115(2-3), 167?183.
Neural Mechanism of How Emotion Affects Behavioral Inhibition YANG Su-Yong; HUANG Yu-Xia; ZHANG Hui-Jun; LUO Yue-Jia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and Learn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withhold improper behaviors in emotional situations. Recently, brain imaging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how emotion affects behavioral inhibition. According to these findings,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emotional contexts requires an interaction of inhibitory and emotional processes that recruits brain regions beyond those engaged by either process alone. At the neural substrate level, the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sular cortex and amygdala were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behavioral inhibi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time course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s still unclea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ge, gender and personality) and emotional factors (valence and arousal) also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emotion affecting inhibition in neural level.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identifying to what extent and when the integration and di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 and inhibition processes occur.
Key words: emotion; behavioral inhibition; neural mechanism; functional MRI; ERP
情绪的脑机制与“空鼻症”患者的极端情绪 中科院心理所2014深圳在职博士班杨鑫“温岭杀医案”后,“空鼻症”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空鼻综合征(emptynosesyndrome,ENS)是指由于下鼻甲和/或中鼻甲过分切除而出现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患者有鼻腔烧灼感,疼痛,通气不畅,最终多有极端情绪。空鼻症患者群体,其中多人的独立陈述中1,均提到了精神不济、睡不着觉、抑郁、“性格开始变得易怒”2等症状,有的要自杀,有的则嚷嚷着要杀医生。为什么“空鼻症”多导致极端情绪呢?笔者试图从情绪的脑机制理论和嗅觉神经通路与情绪的脑机制密切相关来解释这一问题。 我们的情绪来自何处?按照现代心理学理论,脑中存在着两条不同情绪唤起通路。其中一条是快速反应系统,这条系统通常是潜意识的,是从感觉器官将刺激信息传到丘脑,对刺激信息进行快速筛选,然后引导到杏仁核,杏仁核则随即启动恐惧和规避反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反应速度甚至快于刺激到达意识的速度。3这一系统与内隐记忆系统相连,是我们早期的防御系统。例如半夜听到尖叫的大声,这一系统会自动做出近乎瞬时的恐惧反应,而不需要意识的有意控制。另外一条情绪系统与意识系统处理过程有关。该系统与外显记忆相连,反应速度会慢一些。例如,在你头脑中想象将要演讲的情景,这一系统让你感到害怕。这一通路与大脑皮层有关,感觉刺激通过丘脑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对刺激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然后给杏仁核以及其他较低级的脑部结构发送情绪信息。结果造成你在意识中对情景进行感知,并在意识中产生情绪。 在这两个回路中,都要依靠较低级的脑部结构,如边缘系统的作用。边缘系统的结构位于脑干以上的脑部。主要由边缘叶和相关的皮质及皮质下结构组成,边缘叶主要为胼胝体、海马、海马旁回、钩及距状回;皮质下结构包括杏仁核、隔核、下丘脑、背侧丘脑的前核及中脑被盖的一些结构。边缘系统的特点是:发生上较古老。纤维联系复杂,如海马回路(海马旁回--海马结构—乳头体—丘脑前核—扣带回--海马旁回)、穹隆等。边缘系统有两个神经组织,即杏仁核与海马,前者关系情绪的表现,后者与记忆有关。在进化中,边缘系统无疑成为了控制攻击、防御和撤退行为的反应系统。现代研究表明,部分切割或部分受到电刺激的边缘系统能够大幅度改变情绪反应。4杏仁核就像一条看门狗,不停地对各种威胁保持警觉。确实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杏仁核参与了多种情绪,不仅仅是恐惧。杏仁核(amygdala)位于颞叶的颞极中,正好在中央皮层的下方,由于它的形状而用希腊文“almond”命名为杏仁核。杏仁核是一群核团簇,通常被分为三组:基底外侧核、皮层内侧核和中央核。杏仁核的传入来源广泛,包括新皮层的所有叶、海马回和扣带回。所有感觉系统的信息都传入杏仁核,特别是基底外侧核。每一个感觉系统都有不同方式的杏仁核投射,在杏仁核中相互联系,使不同的感觉系统信息在杏仁核中得到整合。两条主要通路:腹侧杏仁传出通路和终纹连接杏仁核与下丘脑。杏仁核在情绪处理过程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不但从快速的潜意识情绪处理通路中接收信息,而且也从更慢的意识情绪通路中接收信息。 另一个较古老的系统是网状结构。网状结构也叫做网状系统,位于脑干内部,两耳之间,一种由白质和灰质交织混杂的结构,是一种手指形状的神经元网络,
大脑和情绪 Healing Emotion ◎引言人:克里夫? 沙隆(Cliff Saron)和理察?戴卫森(Richard J. Davidson) ◎译者:李孟浩译按:本章选自Daniel Goleman所编的《Healing Emotion》。 过去十年来,学界有一连串令人振奋的发现,使得我们比以前更加能够了解大脑调节情绪的过程。很久以来,大家都假定情绪中心是位在于环绕着大脑皮质下方的一系列结构(译按:这些结构主要是颞叶、杏仁核、杏仁海马、海马、额-颞皮层)之中,这些结构统称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limbic 的拉丁文意思就是「环状物」)。最近也有一些神经学的资料指出情绪冲动在边缘中心产生时,我们的情绪表达是受制于额头后方新演化出来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的结构之中。而且,前额叶皮层的两侧似乎负责操控两组不同的情绪反应,像右侧是调节比较令人沮丧的情绪,这些恐惧或厌恶的情绪会让人退缩;左侧则是调节比较正面的情绪,如快乐。 这些神经科学的发现可以做为我们了解情绪生活之动态的背景知识。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和我们如何处理情绪的方式,可以说是被这整个广泛联系的脑部线路所控制。理察?戴卫森是威斯康辛大学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实验室的主任,他的同僚克里夫.沙隆向大家报告他俩合作完成的实验,内容详细显示出大脑如何组织我们情绪实体各个侧面的过程。沙隆先是考虑「情绪」的意涵是什么,才又解释说不同的理论模型是如何塑造出研究情绪和大脑的方法。然后,他检讨了他们实验室一连串的重要发现,好让大家能够对于大脑调节正反两面情绪的过程,得到一些新的洞察。情绪的亲近或退缩趋势(approach or withdrawl tendencies)跟佛教的贪执和厌恶概念也很相近,都是我们扎根存活在此世间的基本情绪极(emotional poles)。克里夫.沙隆:「情绪」这个字眼的意涵实在是很难做个严格的界定。在心理学中,这个字眼是用来描述一个人在许多不同层次上的反应,其中一个是认知的层次:在某个特殊感觉状态中升起的判断和思绪。我们也能从行为的观察来描述情绪:愤怒或温和的姿势、声音的语调。另一种界定情绪的方式则是从脸部表情下手,因为你在那一刻感受时自动绽放的表情,会特别有助于我们厘清你所感受到的情绪。在生理学层次上,我们能够描述情绪反应的两种成份。 第一个是个人察觉到的身体感觉,如事件发生之前的焦虑感。这种感觉通常涉及到控制自律神经系统和荷尔蒙释放的低等大脑中心。第二个生理反应是发生在大脑皮质,这个情绪反应层次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焦点所在。我们也把亲近和退缩看成是描述机体行为和区分各类情绪的基本方式。譬如说,快乐的心情会促动你去找你乐于见到的人。恐惧和厌恶则是退缩行为的典型案例。这种亲近和退缩的行为可以跟脑部两侧的活动产生联系。过去十年来,我们实验室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脑部左侧的前方区域跟亲近行为比较有关连,右侧区域则是跟退缩行为比较有关连。你也许会问说,为何我们会一直要把亲近和退缩行为跟脑部两侧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关系。但是从最近一百年来的神经学资料来看,脑部每一侧的伤害都会造成不同的情绪结局。 在十九世纪中叶时,神经学家约翰?杰克森(John Hughlings Jackson)指出饱受癫痫之苦的患者经常在发作初期时,表现出恐惧这种退缩性的情绪,而且其脑部的右前方区域有活动增强的迹象。有些患者在脑部受到伤害后,右侧的活动量大幅减少,以至于情绪陷入癫狂或正面得离谱的地步。这些观察后来便促成一个新理论,专门在讲脑部的两侧为何会有不同的情绪专长或情绪性格。脑部右侧的过度活化似乎会增进退缩的行为;右侧活化能力若是受损或抑郁时,则会增强亲近行为,因为是左侧大权在握,不需右侧来平衡。心理学中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考虑情绪的方式,而且冲突得很厉害。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就只有那么几种分立(discrete)的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厌恶、惊旗和恐惧。差不多在二十几年前,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有位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
心理科学进展 2003,11(3):328~33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进展 马庆霞郭德俊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100037) 摘要文章综述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情绪的脑机制——大脑回路,包括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前部扣带回、腹侧纹状体等。前额皮层中的不对称性与趋近和退缩系统有关,左前额皮层与趋近系统和积极感情有关,右前额皮层与消极感情和退缩有关。杏仁核易被消极的感情刺激所激活,尤其是恐惧。海马在情绪的背景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额皮层和杏仁核激活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是情绪个体差异的生理基础。情绪的中枢回路有可塑性。 关键词情绪,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 分类号 B842.6 情绪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保证着有机体的生存和适应,对个体的学习、记忆、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情绪也是个体差异的来源,是许多个性特征和心理病理的关键成分。近年来,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以电信号为基础的方法(EEG、ERP),以功能成像为基础的方法(PET、fMRI),允许更准确地测量大脑的结构和机能。这些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当代情绪研究的前沿学科——感情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它是考察情绪和心境神经基础的生物行为科学的分支,与认知神经科学类似,但是集中在感情过程上[1]。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是由大脑中的回路所控制的,它们整合加工情绪信息,产生情绪行为。 下面重点介绍人类情绪的中枢回路,情绪中枢回路的个体差异,以及情绪中枢回路的可塑性等方面研究的进展。? 1 情绪生理机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情绪心理学的现代理论开始于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James。他(1890)[2]提出“事件发生时的知觉导致身体变化,对身体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他的情绪理论可检验两个重要的成分。第一,对刺激的生理反应是情绪体验的前提。这一观点改变了20世纪情绪研究的进程,导致对不同情绪自主状态的研究。第二,在情绪体验中卷入的是感觉和运动皮层区域,没有大脑中枢。 Cannon(1927,1929)[2]对James的观点提出质疑,怀疑情绪没有大脑中枢这一观点。他提出,内脏器官对不同种类刺激的反应是不明确的,不能解释情绪体验中的快速变化。Cannon的两个实验研究表明,刺激内脏并不一定引起情绪状态质的变化;用外科手术分离内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情绪行为没有改变。 Cannon的观点激起研究者对情绪神经回路的研究。Papez(1937)[2]提出情绪回路包括下丘脑、前部丘脑核、海马和扣带回皮层。MacLean(1949,1952,1993) [2]提出边缘系统的概念,认为海马、杏仁核在情绪体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Papez和MacLean的理论激励研究者寻找情绪的具体而复杂的神经回路。 同时,James的观点引起许多研究者试图揭示不同情绪状态的自主特殊性。特别是对一些消极情绪,如恐惧和愤怒的研究,一些证据支持这样的特殊性观点。然而,Schacter 等人(1962) [2]的一个实验表明唤起和认知结合起来是形成特定情绪的两个必要成分。 Levenson(1992) [2]综述了几个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差异主要针对消极情绪。在悲哀、愤怒和恐惧状态中可以看到心率加速,厌恶状态中可以看到心率减速。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外周自主变化太粗糙,不 收稿日期:2002-09-02
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进展 【摘要】文章综述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情绪的脑机制——大脑回路,包括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前部扣带回、腹侧纹状体等。前额皮层中的不对称性与趋近和退缩系统有关,左前额皮层与趋近系统和积极感情有关,右前额皮层与消极感情和退缩有关。杏仁核易被消极的感情刺激所激活,尤其是恐惧。海马在情绪的背景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额皮层和杏仁核激活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是情绪个体差异的生理基础。情绪的中枢回路有可塑性。 【关键词】情绪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 情绪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保证着有机体的生存和适应,对个体的学习、记忆、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情绪也是个体差异的来源,是许多个性特征和心理病理的关键成分。近年来,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以电信号为基础的方法(EEG、ERP),以功能成像为基础的方法(PET、fMRI),允许更准确地测量大脑的结构和机能。这些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当代情绪研究的前沿学科——感情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它是考察情绪和心境神经基础的生物行为科学的分支,与认知神经科学类似,但是集中在感情过程上[1]。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是由大脑中的回路所控制的,它们整合加工情绪信息,产生情绪行为。 下面重点介绍人类情绪的中枢回路,情绪中枢回路的个体差异,以及情绪中枢回路的可塑性等方面研究的进展。. 1 情绪生理机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情绪心理学的现代理论开始于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James。他(1890)[2]提出“事件发生时的知觉导致身体变化,对身体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他的情绪理论可检验两个重要的成分。第一,对刺激的生理反应是情绪体验的前提。这一观点改变了20世纪情绪研究的进程,导致对不同情绪自主状态的研究。第二,在情绪体验中卷入的是感觉和运动皮层区域,没有大脑中枢。 Cannon(1927,1929)[2]对James的观点提出质疑,怀疑情绪没有大脑中枢这一观点。他提出,内脏器官对不同种类刺激的反应是不明确的,不能解释情绪体验中的快速变化。Cannon的两个实验研究表明,刺激内脏并不一定引起情绪状态质的变化;用外科手术分离内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情绪行为没有改变。 Cannon的观点激起研究者对情绪神经回路的研究。Papez(1937)[2]提出情绪回路包括下丘脑、前部丘脑核、海马和扣带回皮层。MacLean(1949,1952,1993) [2]提出边缘系统的概念,认为海马、杏仁核在情绪体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Papez和MacLean的理论激励研究者寻找情绪的具体而复杂的神经回路。 同时,James的观点引起许多研究者试图揭示不同情绪状态的自主特殊性。特别是对一些消极情绪,如恐惧和愤怒的研究,一些证据支持这样的特殊性观点。然而,Schacter 等人(1962) [2]的一个实验表明唤起和认知结合起来是形成特定情绪的两个必要成分。 Levenson(1992) [2]综述了几个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差异主要针对消极情绪。在悲哀、愤怒和恐惧状态中可以看到心率加速,厌恶状态中可以看到心率减速。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外周自主变化太粗糙,不能决定情绪体验。 Lang(1995)[2]的研究表明图片诱发的积极和消极感情之间有自主神经系统差异。许多研究者[2]报告,感情强度的自我报告和自主输出的量之间有关系,尤其是皮肤电指标表现明显。
积极情绪的作用:拓展-建构理论 高正亮 童辉杰△ 【摘要】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Fr edrickso n的拓展-建构理论解释了积极情绪体验不但反映个体的幸福,而且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长期的适应价值。即积极情绪具有两大核心功能:瞬时的拓展功能,可以拓展个体即时的思维—行动范畴;长期的建构功能,可建构个体长久的身体、认知、社会等的资源。通过两大功能,积极情绪促使个体产生螺旋式上升并增进个体幸福。 【关键词】 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积极心理学 Rol e of Positive Emotions:The Broaden-and-buil d Theory.Gao Zhengliang,T ong H uij ie.Colleg e of education,Soochow U niv er si-ty,Suz hou215123,P.R.China Selig man曾指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相对于传统临床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更为 为,认为反社会者存在低皮层觉醒水平,比正常人活动减退,存在一个“刺激饥渴”的慢性阶段。 “成熟化延迟”由Hill和W atterson提出的攻击行为脑电图慢波异常的假说,并得到纵向研究认同。Dustman等对222位正常男性从其4~90岁进行脑电图频谱变化研究,在中央区和枕区发现儿童时期 波、 波相对活性逐渐减少,成年期相对稳定;在整个生存期限中 波相对活性平均在6~24岁时逐渐增加,接着逐步衰减; 波在4~8岁时相对活性最小,随后稳定增加[16]。L indber g等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杀人犯两侧枕区 、 波相对活性比正常人显著增加; 波全面减少,以枕叶为甚,结果提示反社会人格障碍杀人犯存在脑成熟延迟。 精神分裂症暴力行为脑电图研究结果提示攻击行为产生存在脑功能异常的生物学基础。对攻击行为的评估预测有一定指导作用。但脑电慢波增加与攻击行为相互关系的解释还停留在假说阶段。回顾文献,缺少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前的脑电图资料。如发病前脑电图存在普遍异常,其暴利行为与患病后的暴力行为有无相关性的研究将是有意义的。笔者推测脑功能损害及异常是暴力攻击行为的病理基础,而精神分裂症与暴力攻击行为可能互为因果。其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6 参考文献 [1]钟志慧,刘剑涛.伴有冲动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电图分 析[J].中国民康医学杂志,2005,17(6):292-293 [2]沈祥安.67例有暴力行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地形图初探[J].临 床精神医学杂志,1995,5(6):342 [3]姜小琴,谢斌,诸索宇,等.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脑诱发电位对照研 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10(1):39-42 [4]Saver J L,Sallow ay S P,Devinsky O,et al.Neuropsych i atry of ag- gression[M].//Fogel BS,Sch iffer R B,Rao S M.Neuropsych iatry. Baltimore:W illiams and w ikins,1996:523-548 [5]Convit A,Czober P,Volavka https://www.doczj.com/doc/c618931288.html,teralized abnorm ality in the EEG of persistently violent psychiatric inpatien t[J].BiolPsychiatry,1991, 30(4):363-370 [6]W ong M T,Lumsden J,Fenton G W,et a1.Electmencephal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violence ratings of male patients in amaxi-mum-securitym ental hospital[J].Acta Psych i atry Scand,1994,90 (2):97-101 [7]Raine A,Buchsbaum M,LaCasse L.Brain abnormalities in murder- ers indicated by pos i tron emission tomography[J].BiolPsychiatry, 1997,42(6):495-508 [8]Hoptm an M J,Volavka J,Weiss E M,et a1.Quantitative M RI measures of orbitofrontal cortex in patients w 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or sch i z oaffective disorder[J].PsychiatryRes,2005,140(2): 133-145 [9]Volavka J.Aggression,electroencephalograph y,and evoked poten- tials:a critical review[J].Neuropsychiatry,1990,3:249-259 [10]Silverman D.Th e electroencephalogram of cri m inals:Analy-sis of four hun dred and eleven cases[J].Archives of Neurologyand Psy-chiatry,1944,52:38-42 [11]E lli n gson R J.T he incidence of EEG abnormality among patients w ith mental disorders of apparently nonorganic originsa criti cal re-view[J].Am J Psychiatry,1954,11:263-275 [12]Raine A,Venables P H,Williams M.Relationship betw een central and autonomic measures of arousal at age15years and criminality at age24years[J].Arch Gen Psych iatry,1990,47:1003-1007 [13]Convi t A,Czobor P,Volavka https://www.doczj.com/doc/c618931288.html,teralized abnormality in the EEG of persistently violent psychiatric inpatients[J].Biol Psychia-try,1991,30:363-370 [14]Gatz ke-Kopp L M,Raine A,Bueh abaum M,et al.T em-poral lobe deficits in m urderers[J].Neuro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01,13:486-491 [15]Lisa M,Gatzke-Kopp M A,Adrian R,et al.Temporal lobe deficits murderers[J].Neuro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01,13: 486-491 [16]Dustman R E,S hearer D E,Emmerson R Y.Life-span changes in EEG spectral amplitude,amplitude variabil ity and mean frequency [J].Clinical Neurophysiology,1999,110:1399-1409 (收稿时间:2009-09-17) 中国.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系(江苏) 215123 △通讯作者
虽然人的情绪现象显得很复杂,但它简单的一面,并且是能够使它的其它方面不再显得“极为复杂”的,就是情绪的心理机制。这是心理学对情绪的研究应该首先去认识的,也是较容易认识的,却因为没有重视而至今还未认识的一面。 情绪产生于生命的一个古老的机制,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两种:快悦的和不快的。我们知道,简单的生物没有知觉能力,更没有思维,但它们却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这种本能是靠什么得以实现的呢?只能是“趋悦避痛”的情绪机制,即:趋向快悦的情绪状态,逃避不快的(或痛的)情绪状态,并依此实现了自体保护和生存。“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行为的外显表现,“趋悦避痛”是这一行为表现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其实,“趋悦避痛”是从最简单的动物体到最高级的人类共有的最基本的本能和生命原则,情绪是一切生物体(动物和人类)价值判断的依据,是生物一切行为原因的渊源。 虽然人的情绪现象显得很复杂,但它简单的一面,并且是能够使它的其它方面不再显得“极为复杂”的,就是情绪的心理机制。这是心理学对情绪的研究应该首先去认识的,也是较容易认识的,却因为没有重视而至今还未认识的一面。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的“情绪”在概念上有所深入和拓展。首先,它指的是本质意义上的情绪,或是指所有情感和情绪中所包含的会引起我们喜爱或回避的主观态度的因素。从个体体验方面来说,它是构成人的各种感受和通常意义上的情绪的基本元素,与我们通常对情绪的概念相比,它还包括包含在诸如“饥饿”、“快感”、“痛感”等等一些感觉之中并作为其主体的情绪成分,与“恐惧”、“悲伤”、“愉快”等通常意义上的情绪一样,它们的情绪性成分是同源的。这是概念范围上的拓展。从内部过程上来说,它是指发生在脑内的与网状系统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切情绪性神经反应及其上传。 一、制约性情绪反应 情绪的一个主要心理机制就是情绪的学习,即个体对信号刺激的情绪性反应。虽然加涅早就提出信号学习包括随意反应和情绪反应,但在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和我们的所有教材中,对这点却完全地忽视了。而情绪的信号反应恰恰是认识情绪现象的关键,我们一直对复杂些的社会性情绪的不解,原因就在于对此的忽视。情绪反应按其反应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套用现成的词汇可称为“自然情绪反应”和“制约情绪反应”。由信号刺激引起的情绪反应就是制约性情绪反应,它占据着我们人类情绪表现的绝大部分。 “自然性情绪反应”很直观易识,它是我们的生理基础所决定的对生理刺激的直接反应。例如我们在夏天口渴时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生理上的适宜和满足自会通过对网状系统的激活而引起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并由其和相关感官信息向皮层的上传形成我们对此快悦情绪和相关感官特征的意识,这种情绪反应的形式表现为它是由刺激物的直接刺激而引起的生理反应所产生的。 “制约性情绪反应”与情绪的“学习”有关。我们知道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中有“非制约刺激(自然刺激)”和“制约刺激”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和“制约反应”。而在动物和人的情绪反应现象中,制约性
(情绪管理)情绪的心理机 制
虽然人的情绪现象显得很复杂,但它简单的壹面,且且是能够使它的其它方面不再显得“极为复杂”的,就是情绪的心理机制。这是心理学对情绪的研究应该首先去认识的,也是较容易认识的,却因为没有重视而至今仍未认识的壹面。 情绪产生于生命的壹个古老的机制,它的性质能够归纳为俩种:快悦的和不快的。我们知道,简单的生物没有知觉能力,更没有思维,但它们却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这种本能是靠什么得以实现的呢?只能是“趋悦避痛”的情绪机制,即:趋向快悦的情绪状态,逃避不快的(或痛的)情绪状态,且依此实现了自体保护和生存。“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行为的外显表现,“趋悦避痛”是这壹行为表现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其实,“趋悦避痛”是从最简单的动物体到最高级的人类共有的最基本的本能和生命原则,情绪是壹切生物体(动物和人类)价值判断的依据,是生物壹切行为原因的渊源。 虽然人的情绪现象显得很复杂,但它简单的壹面,且且是能够使它的其它方面不再显得“极为复杂”的,就是情绪的心理机制。这是心理学对情绪的研究应该首先去认识的,也是较容易认识的,却因为没有重视而至今仍未认识的壹面。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的“情绪”在概念上有所深入和拓展。首先,它指的是本质意义上的情绪,或是指所有情感和情绪中所包含的会引起我们喜爱或回避的主观态度的因素。从个体体验方面来说,它是构成人的各种感受和通常意义上的情绪的基本元素,和我们通常对情绪的概念相比,它仍包括包含在诸如“饥饿”、“快感”、“痛感”等等壹些感觉之中且作为其主体的情绪成分,和“恐惧”、“悲伤”、“愉快”等通常意义上的情绪壹样,它们的情绪性成分是同源的。这是概念范围上的拓展。从内部过程上来说,它是指发生在脑内的和网状系统活动密切相关的壹切情绪性神经反应及其上传。 壹、制约性情绪反应 情绪的壹个主要心理机制就是情绪的学习,即个体对信号刺激的情绪性反应。虽然加涅早就提出信号学习包括随意反应和情绪反应,但在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和我们的所有教材中,对这点却完全地忽视了。而情绪的信号反应恰恰是认识情绪现象的关键,我们壹直对复杂些的社会性情绪的不解,原因就在于对此的忽视。 情绪反应按其反应的形式能够分为俩种,套用现成的词汇可称为“自然情绪反应”和“制约情绪反应”。由信号刺激引起的情绪反应就是制约性情绪反应,它占据着我们人类情绪表现的绝大部分。 “自然性情绪反应”很直观易识,它是我们的生理基础所决定的对生理刺激的直接反应。例如我们在夏天口渴时喝下壹杯清凉的饮料,生理上的适宜和满足自会通过对网状系统的激活而引起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且由其和相关感官信息向皮层的上传形成我们对此快悦情绪和相关感官特征的意识,这种情绪反应的形式表现为它是由刺激物的直接刺激而引起的生理反应所产生的。 “制约性情绪反应”和情绪的“学习”有关。我们知道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中有“非制约刺激(自然刺激)”和“制约刺激”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和“制约反应”。而在动物和人的情绪反应现象中,制约性情绪反应也普遍存在,即在壹些情境下,当遇到某壹能够产生某种生理性情绪反应的条件时,在仍未受到该条件的真实刺激之前就产生了该条件真实刺激后所会产生的情绪反应。例如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正口干舌燥时突然得到壹瓶冰镇的凉饮,在喝入之前我们已立刻非常高兴——即我们的脑中已产生了快悦性质的生理性情绪反应,这种快悦的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的在解渴后因生理适宜而在脑中产生的快悦性质的情绪状态的重现(由于特定情境往往仍会增加了它的强度),或称之为对以往相关情绪的记忆。这就是制约性情绪反应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只是这里仍需要和认知有关的情境的作用,比如在不渴或者见到的是自己得不到的凉饮的情况下,制约性情绪的产生在强度上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引起相反的情绪。 认识了制约性情绪反应现象的存在,那么对各种复杂的情绪现象我们就会不难理解。再例如,“小孩见见护士就联想到打针,从而就产生恐惧”,其实这里的“恐惧”的主体就是重新出现的、包含在他以往打针时的“痛”之中的不快性质的生理性情绪反应,这里的护士就是信号刺激。这壹恐惧的产生就是制约情绪的简单形式,而古典制约学习理论中的“类化”、“辨别”等现象在制约情绪中都有对照,尤其在人的较为复杂的社会性情绪和情感中更是如此。人的再高级的情感也不是无源之水,它们都是由情绪的制约刺激物所产生的以原初的生理性情绪为基础的制约情绪,只是这里的“联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随意联想,而是在潜思维活动下进行的潜联想,因而表现出这些情绪产生的直接性和原因的曲折性。
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进展 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进展马庆霞摘郭德俊(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100037)要文章综述情绪大脑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情绪的脑机制——大脑回路,包括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前部扣带回、腹侧纹状体等。前额皮层中的不对称性与趋近和退缩系统有关,左前额皮层与趋近系统和积极感情有关,右前额皮层与消极感情和退缩有关。杏仁核易被消极的感情刺激所激活,尤其是恐惧。海马在情绪的背景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额皮层和杏仁核激活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是情绪个体差异的生理基础。情绪的中枢回路有可塑性。关键词情绪,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分类号B842.6 情绪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保证着有机体的生存和适应,对个体的学习、记忆、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情绪也是个体差异的来源,是许多个性特征和心理病理的关键成分。近年来,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以电信号为基础的方法(EEG、ERP),以功能成像为基础的方法(PET、fMRI),允许更准确地测量大脑的结构和机能。这些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当代情绪研究的前沿学科——感情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它是考察情绪和心境神经基础的生物行为科学的分支,与认知神经科学类似,但是集中在感情过程上[1]。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
明,情绪是由大脑中的回路所控制的,它们整合加工情绪信息,产生情绪行为。下面重点介绍人类情绪的中枢回路,情绪中枢回路的个体差异,以及情绪中枢回路的可塑性等方面研究的进展。?1 情绪生理机制研究的历史背景情绪心理学的现代理论开始于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James。他(1890)[2]提出“事件发生时的知觉导致身体变化,对身体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他的情绪理论可检验两个重要的成分。第一,对刺激的生理反应是情绪体验的前提。这一观点改变了20 世纪情绪研究的进程,导致对不同情绪自主状态的研究。第二,在情绪体验中卷入的是感觉和运动皮层区域,没有大脑中枢。Cannon(1927,1929)[2]对James 的观点提出质疑,怀疑情绪没有大脑中枢这一观点。他提出,内脏器官对不同种类刺激的反应是不明确的,不能解释情绪体验中的快速变化。Cannon 的两个实验研究表明,刺激内脏并不一定引起情绪状态质的变化;用外科手术分离内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情绪行为没有改变。Cannon 的观点激起研究者对情绪神经回路的研究。Papez(1937)[2]提出情绪回路包括下丘脑、前部丘脑核、海马和扣带回皮层。MacLean(1949,1952,1993)[2]提出边缘系统的概念,认为海马、杏仁核在情绪体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Papez 和MacLean 的理论激励研究者寻找情绪的具体而复杂的神经回路。同时,James 的观点引起许多研究者试图揭示不同
第十章情绪的生理基础 第一节情绪的概述 1.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第二节情绪的外周神经基础 1.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该理论认为强烈的情绪与骨骼肌的活动及自主神经系统的反 应时密不可分的。特定的知觉是在情绪或带情绪的观念产生之前,由于直接的物质作用而发生的身体变化。因此他认为不同的情绪只是对某一种身体状态的感觉。 2.情绪反应的生理基础:情绪的生理反应主要表现为躯体运动和表情肌的活动,内分泌功 能变化以及有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功能改变所引起的内脏活动变化。情绪的变化会引起不同的躯体运动变化,同时不同的情绪状态伴有不同的表情肌变化。情绪反应中,某些激素分泌量增加的程度与情绪反应的强度有关。人在情绪变化时,会引起的生理反应有如下: 1)呼吸活动变得加速或减慢 2)循环系统活动的速度和强度发生变化 3)消化系统的活动强弱变化 4)皮肤电反应 5)自主神经系统的变化 3.情绪的神经——体液调节:情绪过程中的许多生理变化与内分泌腺的活动有关,其中肾 上腺与情绪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实际上是情绪内脏反应的最主要来源。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激素中,糖皮质激素对人体的物质代谢有重要的影响,并能增强机体对多种有害刺激的抵抗能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受垂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影响。当有害刺激传达于神经中枢,下丘脑影响脑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从而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提高易激能力。当情绪改变较大时,无论是中枢、外周神经系统还是肾上腺髓质都会释放较多的去甲肾上腺素作为神经递质和激素对情绪变化发挥调节作用。由此可见,机体的内分泌腺的变化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变化一起,是情绪的外周反应的重要机制。 第三节情绪的中枢神经基础 1.情绪是大脑皮层与皮层下结构协同活动的结果。 2.丘脑:丘脑一般处于皮层的抑制控制下,一旦皮层抑制功能解除,丘脑冲动得到释放, 情绪反应就会发生。由外界刺激引起感觉器官的神经冲动,通过传入神经传至丘脑,再有丘脑同时向上向下发出神经冲动,向上至大脑,产生情绪的主观体验,向下传至交感神经,引起机体的生理变化,如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内分泌增多等,使个体生理上进入应付紧急情境的准备状态。因此情绪体验和生理变化时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受丘脑的控制。
一个背景:北京市金钟监狱,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押改造和治疗传染病罪犯的监狱,中心成立于2007年,先后与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得到了专业社会力量的支持。DIY油画绘制和陶艺制作,是今年4月增加的新内容。现在,中心有音乐治疗、陶艺治疗、团子咨询、拓展训练、心理剧、心理影片赏析等11种有助于服刑人员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的方式互为补充。全年金钟监狱85%以上的罪犯都参与到以上各种活动中来。活动的过程中,监狱心理咨询干警均在现场带领,引导犯人体会每项活动所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校正使用技巧,挖掘不同的活动对缓解不同心理问题所发挥的功能。与此同时,金钟监狱还通过组织讨论、座谈、评比和开办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共享活动的积极效果。良好的氛围在转变罪犯错误认识和引导罪犯积极维护心理健康方面的效果明显。如罪犯心理测试的废卷率由2007年的76.3%降低到2010年的9.1%;罪犯主动申请咨询率由2007年的不到1%,提高到了2010年的85.6%。心理专栏的投稿数由2007年的月均13篇,增加到2010年的月均109篇。 积极情绪( positive affect) 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 郭小艳,王振宏,2007 ) ,
包括快乐、兴趣、满足、骄傲、爱等。积极情绪是一个包含着愉悦体验、面部/ 身体表情、评价、特别是行为计划和激活状态等多种成分的有意识的过程,对认知过程的影响非常广泛。 积极情绪这个名词来自于古老的情绪维度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所有的情绪由几个基本的维度所构成, 不同情绪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根据彼此在维度空间中的距离来显示的。较为公认的维度模式是二维模式, 认为情绪由两个维度组成: 一个维度是效价( valence) 或愉悦度, 分为正负两极; 另一个维度是唤起度( arousal) , 其由弱到强。在效价维度上, 由正到负, 愉悦度依次降低。位于正效价那端, 有愉悦感受的情绪称为积极情绪( 正情绪) ; 位于负效价那端, 有不愉悦感受的情绪称为消极情绪( 负情绪) 。 以前很多研究发现体验着积极情绪的人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灵活的、创造性的、综合的、对信息持开放态度的、有效的思考模式( Fredrickson,2001 ) 。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加工的速度和准确度方面,而且可以在类别和等级层次上改变认知的功能,以及在信息加工中引起认知结构的变化,即从质、量两方面影响着认知过程( 郭小艳,2008) 。以前支持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实验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拓宽认知范围、提高灵活性等两方面。 ( 一) 积极情绪拓宽认知范围 1.积极情绪拓宽注意和分类。Fredrickson 利用电影诱发四种情绪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V ol. 17, No. 5, 957–96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57 主观幸福感的脑机制* 顾媛媛1 罗跃嘉1,2 (1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2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社会认知领域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Kahneman 等人提出的评价系统模型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主观幸福感形成过程中,评价系统的主要产物包括即时效用、回忆效用、抉择效用和预期效用,这些效用都有着各自特殊的神经机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它们也对应着各异的神经基础。未来主观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应遵循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相结合的整合研究思路。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脑机制;评价系统 分类号 B845;B849 什么是幸福?幸福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人们根据自定标准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评价。幸福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对它的探索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幸福学的研究一直都不在主流研究领域之内,小部分学者对幸福学的不同方面各自进行了一些研究。 这种局面使得幸福学的研究在结构和内容上比较松散。比如,研究食物满足感的人员与考察疾病病痛的研究者间没有任何共有的研究框架;探讨各种情绪机制和幸福感的学者们对他们研究内容之间的相关性也所知甚少。总而言之,至今学术界对幸福感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分开进行的。大多数涉及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考察的都是幸福体验的心理机制,对其生理机制涉及甚少。要真正实现对人们幸福体验的全面认识,需要一个全新的整合的研究思路。究竟人们是如何产生幸福或者不幸的体验?这样的认知评价和心理感受从何而来?这些评价和感受又是如何影响人们制订下一步的计划,采取日后的行动?追根究底,这些复杂的评价和感受都是人的大脑产生的。那么,这些过程在大脑中是通过哪些认知过程实现的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对幸福感的生理机制进行研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对情绪体验 收稿日期:2008-11-12 * 教育部创新团队(IRT0710)、自然科学基金(30670698)、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重点项目(2008AA021204)。 通讯作者:罗跃嘉,E-mail: luoyj@https://www.doczj.com/doc/c618931288.html, 和认知评价过程的研究中有不少内容是与幸福感的生理机制密切相关的。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全面地考察和探索人类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下面将对中西方学者在幸福感脑机制方面现已获得的发现和结论进行系统综述,以期为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启示。 1 主观幸福感的评价系统 现今幸福学领域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评价系统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形成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人们对各种生活事件的评价结果与其幸福体验及其后来的行为反应密切相关。诺贝尔奖得主Kahneman 及其研究小组对人们的各种评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ahneman, Wakker, & Sarin, 1997),总结出在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类效用,主要包括:即时效用(instantaneous utility )、回忆效用(remembered utility )、抉择效用(decision utility )和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 自评价系统的模型提出以来,心理学家已发展出行为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即时效用的考察主要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具体做法是:在一段时间内(例如1周、几周、半年或1年),要求被试每天在随机的时间点(如下午3点10分)报告其当时的幸福体验。其二,对回忆效用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有关幸福体验的回忆任务来实现的。这些任务包括短期和长期回忆,以口头报告或是量表打分的形式进行。最后,在观察抉择和预期效用时,行为学家发明了各种类型的决策
情绪的脑机制--大脑回路,包括前额皮层、杏仁核、海马、前部扣带回、腹侧纹状体 哪些大脑结构和功能以及神经系统与我们的情绪及行为有关? 正如Dr. Daniel Amen 所比喻的,如果用电脑来比喻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就像硬盘,是我们的思想及灵魂(软件)的产生地及储藏室。你的大脑决定你的个性及人生。如果它不能好好地工作,你的思维就会出现问题。就像其他的身体器官,如心脏功能受损,你整个人会觉得不舒服,会有心区疼痛,呼吸不畅,头昏眼花等症状,你不再是你自己。 大脑怎么工作,决定你怎么感觉以及你对快乐幸福的感知程度,决定你怎么看待自己和与别人的关系。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思维的方式可以帮助你也可以伤害你,可以让你感到更加平和快乐也可以让你更加痛苦不安。 我们的大脑是由上亿的神经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通过无可计数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非常复杂而强大的网络,来指导我们的人体完成各种工作。其中以下几个部位和系统与我们的思维,情绪及行为有很大关系。 你不需要去记住各个结构的名字,只需要了解它们大概的位置及大致的功能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心理疾病,以及治疗的方法和技巧,更加主动地帮助自己。 --深层边缘系统( Deep Limbic System), 是一组位于大脑最深层的神经组织,是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 的内圈,环绕在基底神经节里,包括丘脑,下丘脑及周围组织,是我们的情绪中枢。给我们的情绪染上积极的或消极的色彩,以及对过去快乐的悲痛的情绪的记忆( 如果快乐的记忆多过悲痛的记忆,人的心态会更加积极快乐,反之亦然);影响我们对别人的感受及与别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对亲人爱人的养育和依恋;性的欲望,结 合与调控;睡眠和饮食的调控等;它也是我们的嗅觉中心。 如果这个区域太兴奋,人会变得消极无望孤独抑郁或者非常情绪化。与之相关的主要问题及病症包括亲情关系问题( 尤其当亲人分离或亲情破裂时),过分依赖,过于自责,自卑,情绪化,烦燥无趣,孤独自闭,缺乏动力,压抑悲观,慢性疼痛,睡眠及饮食习惯的改变,失去性欲,经前期综合症;抑郁症,狂躁抑郁症,自杀倾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