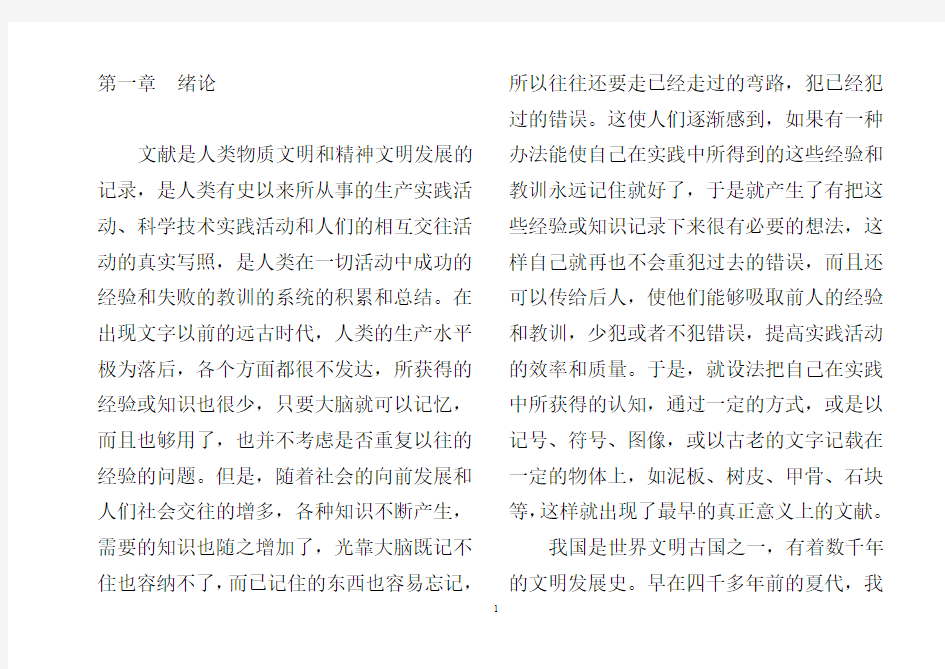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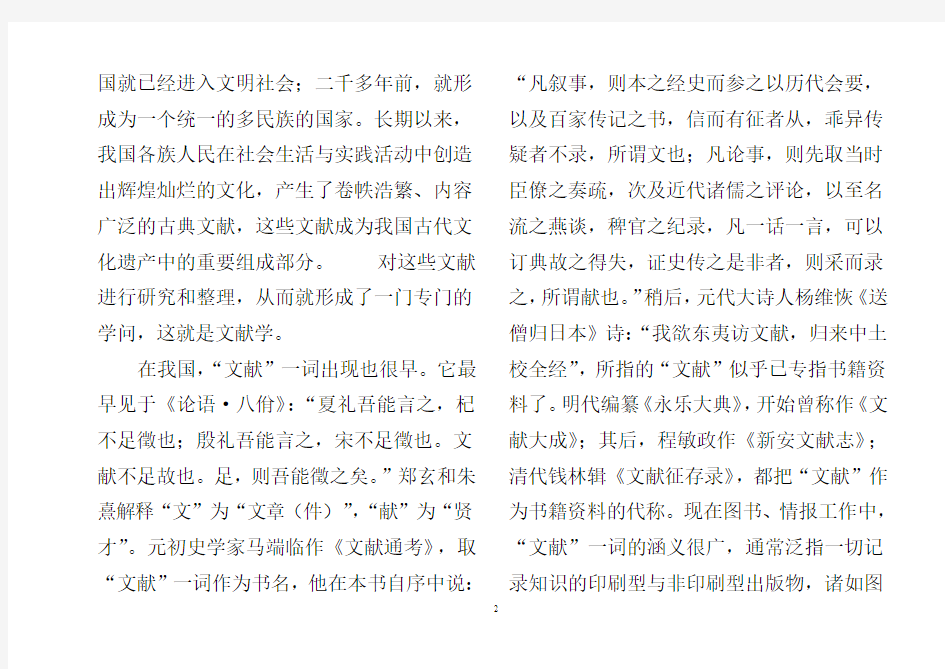
第一章绪论
文献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记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的真实写照,是人类在一切活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系统的积累和总结。在出现文字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各个方面都很不发达,所获得的经验或知识也很少,只要大脑就可以记忆,而且也够用了,也并不考虑是否重复以往的经验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的增多,各种知识不断产生,需要的知识也随之增加了,光靠大脑既记不住也容纳不了,而已记住的东西也容易忘记,所以往往还要走已经走过的弯路,犯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使人们逐渐感到,如果有一种办法能使自己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永远记住就好了,于是就产生了有把这些经验或知识记录下来很有必要的想法,这样自己就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人,使他们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少犯或者不犯错误,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于是,就设法把自己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是以记号、符号、图像,或以古老的文字记载在一定的物体上,如泥板、树皮、甲骨、石块等,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献。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我
国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二千多年前,就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文献学。
在我国,“文献”一词出现也很早。它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件)”,“献”为“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开始曾称作《文献大成》;其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出版物,诸如图
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是指记录“五四”运动以前各种知识信息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典文献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载体,从古到今,所采用的记录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等。文献的体例与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就体裁言,有“无书名”者,有“不题作者”者,有“单篇别行”者,有“序传常置全书之末”者,等等。就文献内容的体裁而言,有著作、编述、抄纂等;就文献编篡形式的体裁言,有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以及方志等。
有了文献,自然就会有围绕文献所进行的工作,我们统称为“文献工作”。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前人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诸如目录的编篡、版本的鉴别、文字的校勘、古书的辨伪与辑佚等。当前几部“文献学”专书,大都把这些文献工作看作文献学的主要或全部内容,它们侧重于讲授文献整理方法,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特设一章,名曰“文献学的三个内容”,并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认为“文献学”只是讲授文献整理方法的,这种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文献学”无非是文字、音韵、训诂加上版本、
目录、校勘而已,文字、音韵、训诂属“古代汉语”范围,因而文献学只须讲讲版本、目录、校勘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我们认为,文献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文献工作,它至少还应该包括文献本身在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分布、发展规律以及文献整理方法。
第二章记录文献的载体
文献产生的早期,其文字就是一些记号、符号,其载体是一些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的物品,如石板、树皮、骨头、竹、木,再稍后就有了经过人加工的载体,如泥板、帛、青铜、竹简、羊皮、布匹等、到了汉朝,公元105年,蔡伦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纸,使得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得以统一。在此后人类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纸一直被当作知识、信息的最好的载体,并迅速广泛地传到全世界,且占着载体的主导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期,出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新的载体,这是胶片。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磁带。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盘、磁鼓上,即磁盘,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到了80年代初,知识、信息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
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多媒体。
纵观以上各种载体,我们可以按着与之相应的记录方法分为四大类型:刻铸型(甲骨、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感应型(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第一节刻铸型载体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总称。上面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盛行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信奉鬼神,《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事情在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吉凶。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为出土于殷代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
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的,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共得1500片。不久,王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所得,刘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选择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
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这是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罗振玉先后所得达3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
甲骨文自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出土的甲骨实物很多,据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的统计,国内有四十多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台湾、香港藏有甲骨30000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26000多片。
自甲骨文发现至今,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性论著约有1400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的字约900余。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
义,他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万多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全书共13册,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特别重要的是后来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著名的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甲骨190多片。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600多个。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青铜器与刻石的总称。《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这就是常说的“金文”。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不象甲骨,本来就有传世的,就
是出土的,也比甲骨要早得多。据统计,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总数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其中可释字约2000个,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青铜器出土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释文和考证,至今仍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吴大澂研究金文,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误,这些研究成果,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
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10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这些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天兴(今陕西宝鸡),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唐代诗人都有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共刻有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竭石和会稽等7石,字体均为小篆。这些刻石大都湮没,琅邪残石残存13行87字,相传为李斯所书,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仅有数字,其余峄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这种做法,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
部书写在石版上,刻成石经,立于首都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据史书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交通往往为之阻塞。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
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原石有48块,至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18块,经过历代沧桑,迁徙破坏,片石不存。晚清以来,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石出土,散存各处,稍稍拓印流传。
唐大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刻了12部儒家经典,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始全)。这部石经,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或“大和石经”。“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它却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但它们的文献史料价值,
都不可与前叙的三部石经同日而语。
第二节书写型载体
一、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
记事者,合称为简牍。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考定。在商代青铜器上,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至今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的,还没有发现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乃成奏牍。”简的制法大致是,将竹断成筒,刀削其皮并剖成竹片,经过烤炙“杀青”,既可去掉水分,又可防腐防虫,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于背面。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成为书写版。
竹简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武威出土的《礼记》木简和《丧服》经竹简同长,约为 55.5-56.5厘米,若以23.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计算,这批经书的简牍约为二尺四寸(55.92厘米)。而医简则在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古时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唐·贾公彦《仪礼·聘礼疏》:“《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故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
便于随身携带,多用于一般记事。湖北望山的杂事札记简长60厘米,“追策”简长64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简竟长达72-75厘米,可见当时列国简策的长度,没有统一规定。
在竹简上写字,字数也不一致,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十个字,超过100字的则又较罕见。武威《仪礼》简,每简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60余字,多的达73字。《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根据出土食物,《汉志》所说的每简22字或25字,只是就几种具体书籍说的,未必是通例。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迄今所见,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漆书从未发现,竹简上的文字,书写有误,可以削去墨迹再写,河南信阳出土楚简,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残笔尚隐约可辨。
关于简牍的编联,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至今发现的战国楚简,多数用2编,其中信阳竹简用3编,望山1号墓简用4编。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5编。《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2编,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3至5编,文献记载所无,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增加编数,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竹简多用皮绳或青
丝编联在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简书编联书写后卷起,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早在汉代就发现过古代的简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战国竹简。《论衡·正说篇》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王古墓,发现竹简数十车,经当代学者束皙整理,得古书75篇16种,写成当时文字,共十余万言,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晋书·束皙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有详细记述。此外,南齐、北周和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简牍。但所有这些,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晋代木简以后,到1949年50年间,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7次,共计出土竹木简牍一万多枚。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罗振玉的《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考释》,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三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建国后,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30余批共计约三万枚。其中湖南长沙、河
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出土竹简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的楚简,从1951年到1965年之间,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的6座墓葬出土过7批800余枚竹简,经过整理拼复,缀合为530多枚。内容包括竹书、杂记、遣策及其它4类,遣策所占比例最大。《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入葬时把亲友所送礼物写于简上,随之下葬,有时把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也包括在内。出土的这批遣策,记述了1000余件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为研究战国中晚期楚国历史、社会经济、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七批楚简共有4200余字,其数量远远超过楚地出土的金文。战国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楚简上的文字,具有不同于商周字体和其他各国文字的独特风格,填补了战国时期竹简文字的空白。这7批楚简的形制及其编连形式,更为研究古代简策制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简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和文书。有秦法律3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
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失传,这次睡虎地发现的3种秦法律竹简,就显得尤其珍贵!《大事记》一卷,分写在53枚竹简上,按年系事,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 100年间的大事,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来补正《史记》,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1959年出土的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三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为木简;乙本是1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
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了大批医药简牍,共计92枚,简文中列药物100种,比较完整的医方30多个,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古老的医方书。我国最早的医方书,当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原书早已散佚,传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辑本。因此,武威医简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972年4月出土竹简4900多枚,多用隶书书写,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此外,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及《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孙武和孙膑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距约二百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后来有不少人提出疑议: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出于后人伪托;也有的怀疑孙武、孙膑原是一人;有的认为现存《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甚至有人断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孙膑所作,否定历史上有孙武的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实为考古界的惊人发现,足以了断近乎千载的聚讼纷争。
《六韬》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但自宋以来,却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书。有的说它“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的说它“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尉缭子》也只见于《汉书·艺文志》,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书目答问》甚至说:“《六韬》伪而近古,《尉缭子》尤谬,不录”。汉人手写的《六韬》和《尉缭子》残简的同时出土,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广为流传,绝非后人伪作。同时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它所载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表》等的差误。
竹木简作为记载文献的材料,比起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可是一枚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移动、阅读都很不方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衡石量书”,每天批阅的文件用衡器称取120斤,又《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可见是非常笨重的。
二、缣帛
正因为简牍笨重,所以,又有缣帛与之同时并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
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取,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扬雄在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不过,缣帛是丝织品,价格较高,所以当时的作者,往往把文字的初稿,写在光滑的白绢或版牍上,改定以后,才写上缣帛。应劭《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抄》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战国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中央折纹处稍有损坏,书系丝质,帛丝的经纬并不匀称,有粗有细,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毛笔墨书,连同边上的文字总共900余字,字若蝇头小楷,笔画匀整。帛书四周,用朱、绛、青几色颜料绘出各种奇特的神怪图像。
1973年12月,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西汉帛书,成为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