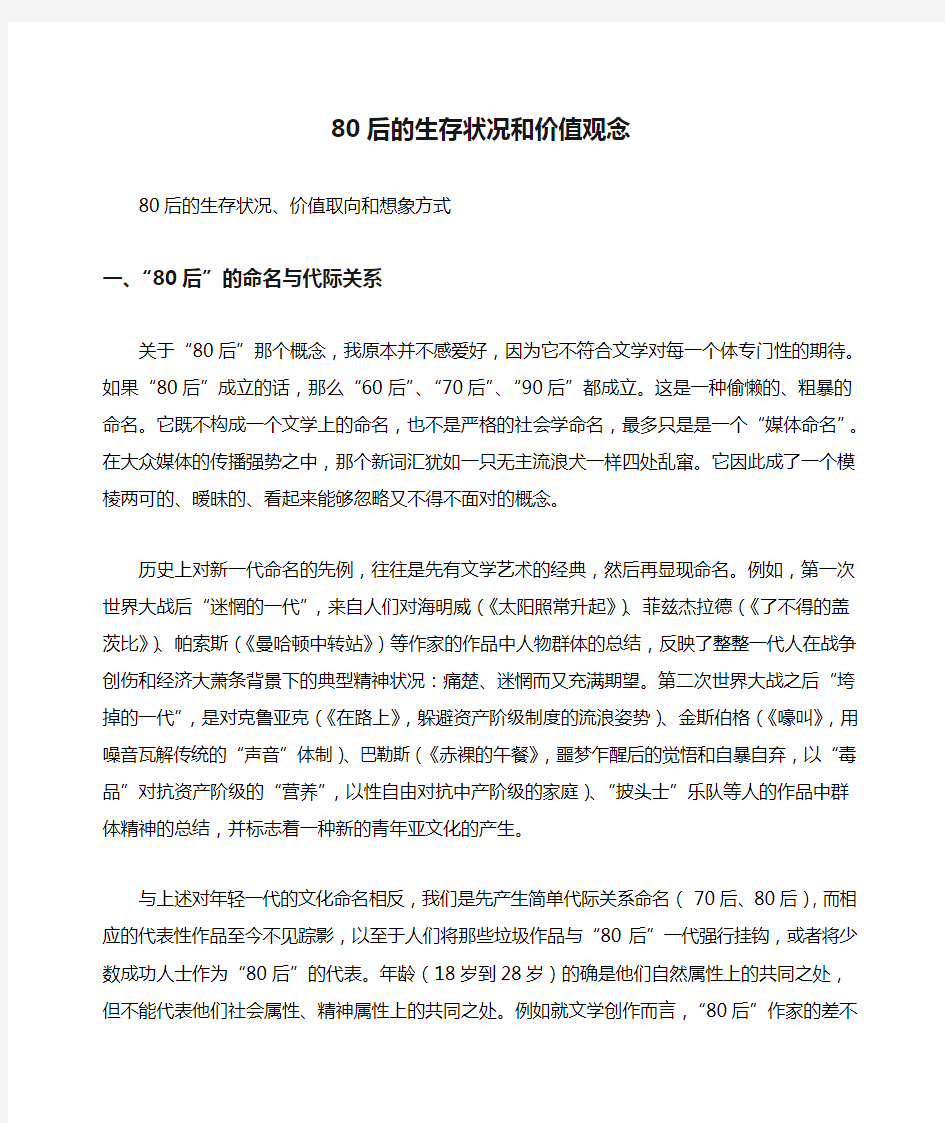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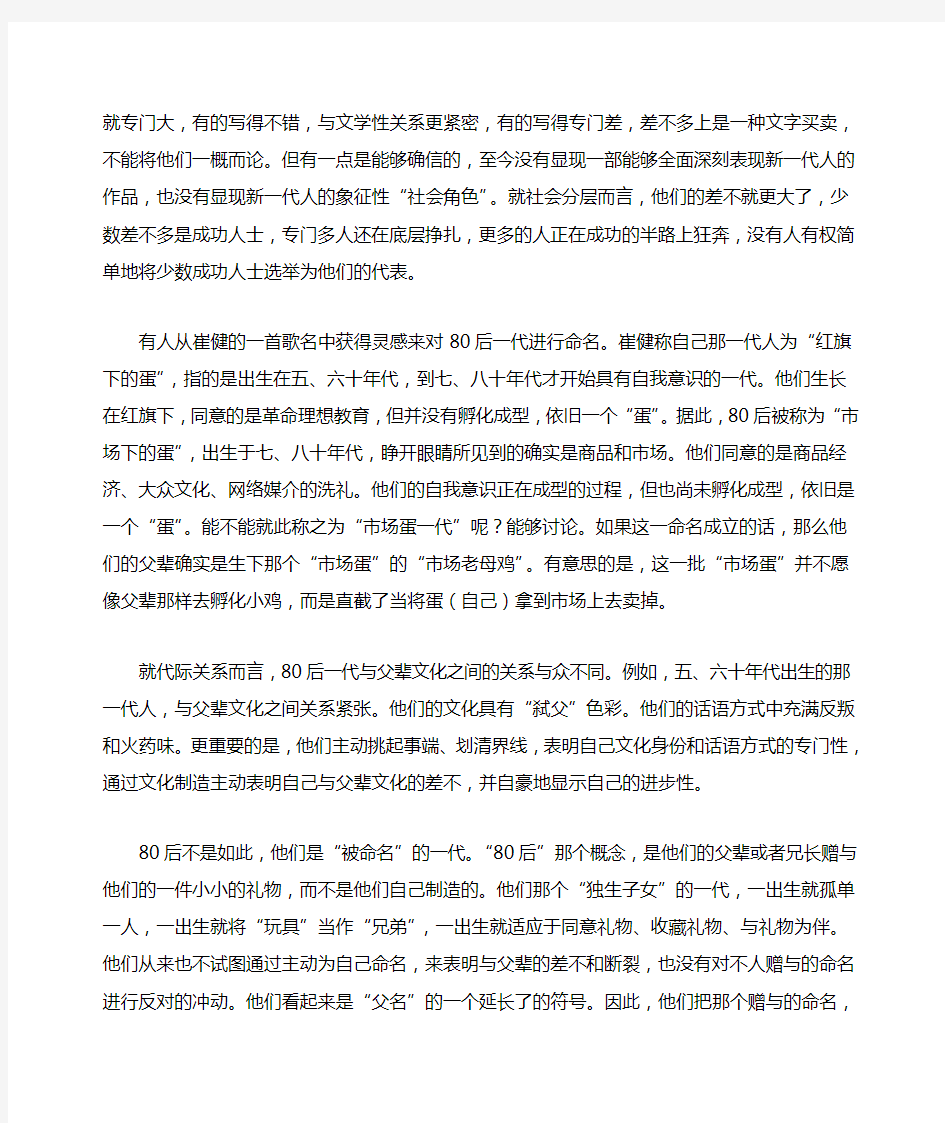
80后的生存状况和价值观念
80后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和想象方式
一、“80后”的命名与代际关系
关于“80后”那个概念,我原本并不感爱好,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对每一个体专门性的期待。如果“80后”成立的话,那么“60后”、“70后”、“90后”都成立。这是一种偷懒的、粗暴的命名。它既不构成一个文学上的命名,也不是严格的社会学命名,最多只是是一个“媒体命名”。在大众媒体的传播强势之中,那个新词汇犹如一只无主流浪犬一样四处乱窜。它因此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暧昧的、看起来能够忽略又不得不面对的概念。
历史上对新一代命名的先例,往往是先有文学艺术的经典,然后再显现命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来自人们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菲兹杰拉德(《了不得的盖茨比》)、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等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群体的总结,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在战争创伤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典型精神状况:痛楚、迷惘而又充满期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是对克鲁亚克(《在路上》,躲避资产阶级制度的流浪姿势)、金斯伯格(《嚎叫》,用噪音瓦解传统的“声音”体制)、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噩梦乍醒后的觉悟和自暴自弃,以“毒品”对抗资产阶级的“营养”,以性自由对抗中产阶级的家庭)、“披头士”乐队等人的作品中群体精神的总结,并标志着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的产生。
与上述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命名相反,我们是先产生简单代际关系命名(70后、80后),而相应的代表性作品至今不见踪影,以至于人们将那些垃圾作品与“80后”一代强行挂钩,或者将少数成功人士作为“80后”的代表。年龄(18岁到28岁)的确是他们自然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但不能代表他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例如就文学创作而言,“80后”作家的差不就专门大,有的写得不错,与文学性关系更紧密,有的写得专门差,差不多上是一种文字买卖,不能将他们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能够确信的,至今没有显现一部能够全面深刻表现新一代人的作品,也没有显现新一代人的象征性“社会角色”。就社会分层而言,他们的差不就更大了,
少数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专门多人还在底层挣扎,更多的人正在成功的半路上狂奔,没有人有权简单地将少数成功人士选举为他们的代表。
有人从崔健的一首歌名中获得灵感来对80后一代进行命名。崔健称自己那一代人为“红旗下的蛋”,指的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具有自我意识的一代。他们生长在红旗下,同意的是革命理想教育,但并没有孵化成型,依旧一个“蛋”。据此,80后被称为“市场下的蛋”,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睁开眼睛所见到的确实是商品和市场。他们同意的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网络媒介的洗礼。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成型的过程,但也尚未孵化成型,依旧是一个“蛋”。能不能就此称之为“市场蛋一代”呢?能够讨论。如果这一命名成立的话,那么他们的父辈确实是生下那个“市场蛋”的“市场老母鸡”。有意思的是,这一批“市场蛋”并不愿像父辈那样去孵化小鸡,而是直截了当将蛋(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就代际关系而言,80后一代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例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与父辈文化之间关系紧张。他们的文化具有“弑父”色彩。他们的话语方式中充满反叛和火药味。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挑起事端、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文化身份和话语方式的专门性,通过文化制造主动表明自己与父辈文化的差不,并自豪地显示自己的进步性。
80后不是如此,他们是“被命名”的一代。“80后”那个概念,是他们的父辈或者兄长赠与他们的一件小小的礼物,而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那个“独生子女”的一代,一出生就孤单一人,一出生就将“玩具”当作“兄弟”,一出生就适应于同意礼物、收藏礼物、与礼物为伴。他们从来也不试图通过主动为自己命名,来表明与父辈的差不和断裂,也没有对不人赠与的命名进行反对的冲动。他们看起来是“父名”的一个延长了的符号。因此,他们把那个赠与的命名,当作父亲或兄长赠与的一个巴比娃娃或者奇异珍宝收藏起来。有人甚至还喜爱将这件礼物挂在颈项上到处招摇。因此,在“代际关系”上,他们是被动的一代、顺从的一代。他们不但处于“被命名”的状态,而且被这一命名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
二、疲乏的身躯和自我表明中的“矛盾修辞”
2008年3月,《记者观看·民声》杂志以《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为总题,刊登了8篇关于80后“京漂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况的报道。随后,网络上以《我们无力摸索以后——80后访谈录》为题予以转载,在网上风靡一时。这8篇文章,从衣(“动批”,即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廉价时装和换季服装)、食(暴食暴饮和饥肠辘辘相伴,有钞票时上酒店,没钞票时吃方便面)、住(合住的出租屋)、行(城铁、地铁、公交)、工作状况(长期加班、频繁跳槽、学用分离)、情感方式(没有时刻恋爱,也不屑于网恋,原有的情感年久失修而面临枯萎)、业余生活(睡觉、打电子游戏)等角度,对“80后”的差不多状况进行了勾勒,尽管粗糙,但大致形状依旧出来了。要补充的是,那个地点没有包括“啃老族”;也专门难涵盖所有的个案,它只是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所谓“啃老族”,尚在父母的卵翼之下,还没有变成独立的“蛋”,最多也只能确实是一个“细胞”。下面我将对这一组访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作者比较熟悉“80后”的生存和思想状况,且有自己的方法和语言,口气专门像是80后代言人。下面引述这篇文章的一些陈述性观点:
1、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宝,但讲究取之有道。
2、往常为理想,现在为妄图。理想可望而不可求,妄图则可随时变成现实。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
3、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宝、积存、成功,他们差不多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
4、力求稳固,又不甘于孤寂;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查找刺激的江湖豪气。
对上面4条陈述的解读和点评:
第一条,“道”事实上确实是规则,只是是一个大规则、大原则,它通过人的德性(行为)出现出来,且具有适用于更多人的普泛性。而“游戏
规则”是小规则,仅属于正在游戏者之间的情况,例如同事、同行。没有小规则,大规则就会落空,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然而,没有大规则,小规则迟早会破产,这是他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合作”必须遵守规则,也确实是遵守契约关系,是对个人自由的部分转让,转让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底线?是不是两个人商量一个游戏规则就行呢?这些都涉及对“道”的明白得。从前对“道”扯得太多,今天关注太少。或者讲,80后对“小规则”依旧专门讲究的,却反感“大规则”。
第二条,毫无疑咨询,理想确实是期望的同义词,妄图确实是欲望的同义词。理想或期望,是一种虚拟的想象状态,指的是一种可能无法实现的、带有幻想色彩的事物,例如,“我期望变成一只小鸟”那个虚拟句式。因此,这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形式,它的最终指向可能是“社会理想”。从辨证的角度(而不是从自然的角度)看,在这两种理想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如果连想象都不存在,这种转换关系就全然不存在。也确实是讲,没有审美理想就不可能有社会理想,人,只能变成现世利益(也确实是一种被操纵的个人欲望)的奴隶。妄图或者欲望,是被现实所压抑的那一部分愿望的想象性替代,只要战胜了压抑,它就能够实现,也确实是讲,它与肉体及其行为有关。然而,肉体愿望或者潜意识的妄图,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能够满足躯体的欢乐原则,不能够满足自我的超越原则。我们从一代人的时刻焦虑症中能够发觉,某些终极价值焦虑症是存在的。
第三条,改良世界(理想)依旧适应世界(成功),与其讲是一种“道德选择”,不如讲是一种“政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然而,将“应然世界”(理应如此)替换为“实然世界”(只好如此)的个人欲望,其结果只能让我们变成“经济动物”。一种合理的选择,事实上并不必定会成为抽象的宏大叙事,它同样也贯穿着我们日常的行为之中。但由于日常生活被一种工具化、数字化的功利主义全面占据,以至于行动的躯体成为一种无主体感的、符号化和商品化的躯体,任由市场宰割。
第四条,是对80后的性格评判,也最为典型地反映出其表明上的“矛盾修辞”,与之相对应的是性格上的“矛盾人格”,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含混
不明状态。这一条是对上面第3条的一个反对。正是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他们不至于完全成为“经济动物”,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可能性,乃至怀疑和质询,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
他们质疑传统“信仰”,却把“爱好”当作“信仰”。他们平复理智,却被各类“发烧友文化”迷住,把“着迷”当“偶像”。他们的“主体意识”看起来专门强,但却没有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完整的身心,而是被商品市场、媒体叙事、数字逻辑肢解了的身心。导致这种“矛盾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社会价值本身紊乱,更直截了当的缘故是他们的身心分裂,价值观念中的幸福感与行为方式上的欢乐感分裂。看看他们隐藏在内心、偶然披露出来的感受:“地铁里惨白疲乏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按揭、物业、水电、煤气。”“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青春生命的能量和激情全部耗尽。”“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就像一场年久失修的爱情,还没如何开始,主人公就已面如死灰、油尽灯灭。”
三、焦虑的心灵、时空关系和价值数字化
毫无疑咨询,80后也有自己深刻的苦恼和焦虑:不成功的苦恼和焦虑,不能进入市场的苦恼和焦虑,还有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生命被“物化”为商品、时刻被剥夺被耗尽、随时可能被市场空间排挤出局的苦恼和焦虑。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父辈们将他们视为“债务人”,而自己扮演着“债权人”的角色,成功了就夸他们是“英雄”,失败了就讲他们是“80后”。
他们的生命和心灵,没有遭受强权的打压,却被某种具有诱惑力的、令人着迷的东西锁住了!这种东西要摧残的不是他们的意识形状,而是他们物质形状上的身心,乃至潜意识,然后微笑着送给他们一个又一个“妄图”,或者讲“梦幻”,像肥皂泡一样。如果讲,“50后”、“60后”一代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是一种“断裂关系”(其中隐含着批判的激情和因对抗而激发的文化制造力),那么,“80后”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则是一种“连续关系”。这种“连续关系”,以成功体会为参照,构成了一
个权力链条,导致了他们只能制造一种“父权文化”阴影下的“游戏文化”。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时尚文化的形式,表演着一出由父辈们撰写或导演的陈旧戏剧,那个“戏剧”中包含着一种衰老的“成人逻辑”——成功逻辑、商品逻辑、市场逻辑。父辈们看起来是“成功逻辑”的教唆犯,而他们自己则变成了实践这一成功逻辑的“雾都孤儿”。这种精神上的“连续关系”,一方面显现出了一种稳固性,但另一方面,代价也是庞大的:整整一代人的文化个性、精神特点将烟消云散。或者讲,他们的精神印记,持续被时时都在更新的网络灌水所覆盖,朝生暮死,仿佛蜉蝣。这一点实际上是一种埋伏着的病根,导致他们的“时刻焦虑症”。
同一期杂志中第二篇较有代表性的访谈文章是《80后的北京时刻》,其中披露了多位80后的自述。而我宁愿将这篇文章看作是一篇以“时刻”和“空间”为主题的特写。“80后”的奋斗、积存、成功的主题,在那个地点第一个体化为“空间”主题,然后再具体化为“时刻”主题。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以商品贸易原则结构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将我们原有的永恒时刻主题(来源于对自然时刻的模拟)和时刻停滞主题(在一国内部自行制定一种进展的时刻表,与外界的总体时刻标准脱节,专门是建国后的3 0年间,因此被视为“停滞”),还有相应的空间上相持和凝视主题,改写为时刻上的滞后(西方发达对应于东方欠发达)和空间上的向心力(西方为中心和东方为边缘)关系。这种现代性的时空关系因此并不仅仅针对“80后”,但他们是最直截了当的感受者。
具体到“80后”走上社会舞台时的国内状况,则显示为城乡对立的进一步扩大化。这种对立不是传统社会行政意义上的强行规定,而是当代市场社会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矛盾。其中留下了一个承诺自由流淌的行动空挡。因此,“成功”第一变成空间上的位移,由乡村移向城镇,由城镇移向中心都市,导致中心都市资源吃紧,最终不得不抬高门槛,将大部分人从那个“黄金空间”挤出去。在没有更多的来自父辈的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支持的情形下,为了免遭空间上的剔除,也确实是为了实现他们所谓“成功”的妄图,惟一的方法确实是在“时刻”上做文章,把所有的时刻都用
于竞争!每天三四个小时用于挤公交、地铁和城铁,然后是打卡上班,然后是加班,再托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出租屋。
毫无疑咨询,他们因为空间关系的重新设定而被“时刻股”套牢。这种将他们套牢的时刻,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物理时刻”,是一种能够运算的“钟表时刻”,是一种能够买卖、交换的“商品时刻”。它与涉及生死咨询题的“生命时刻”和“自然时刻”无关,更于超越生死咨询题的“不朽”时刻和“解放”时刻无关,而是一种死亡(时刻的消费殆尽)的专门表现形式。由此,这一代人普遍患上了一种专门的疾病:由空间的时刻化导致的“时刻焦虑症”。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群因此也不同程度地患有这种疾病,但“80后”的症候更为典型,因为他们身上有双重病菌,家族遗传病态基因和现实生活感染的病菌。
因此,除了压缩时刻(少睡、少玩、少交流,一天当作两天用)之外,还有一种缓解时刻焦虑症的方式,确实是想象自己成功了、解放了、得救了。支持这种想象的,是一种“财宝积存游戏”,实际上也是一种“数字积存游戏”。这种“数字游戏”差不多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年轻一代差不多被各种各样的数字所湮没:银行卡号数据,密码数据,点击量数据,起印量数据,股市、基金、利率数据,等等。成功与否,最终变成了一种小学三年级的加减法。数字积存游戏,导致了一种反向价值的思维方式:个体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威严,变成了以积存的数据为准则而重新定位,也确实是以数字上的“零”为价值思维的原点,向外无限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欲望化思维方式),逐步累加,也确实是落实到银行卡上的数据的累加。只有在这种加减法之中才能积存“解放”或“自由”的感受。与此同时,“解放”或“自由”的主题也就被数据化了;“解放”或“自由”的妄图,就变成了一种数字积存的妄图。
四、价值选择去道德化和偶像人物的功能
80后的矛盾性格,以及他们在自我表明语言中的“矛盾修辞”,同样表现在对偶像人物的认可与否上。在面对面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有偶像,同时力图爱护自己的自我和个性。在背靠背的虚拟世
界里,他们却有自己公认的偶像。同时,他们往往躲避对偶像选择标准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讨论,而用用一种私人化的任性的表述,例如“我喜爱”、“我做主”。也确实是讲,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让自己的“评判标准”完全合法化、合理化,显得并不义正词严,同时还拒绝另觅它途。
他们在选择偶像人物的时候,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准则,确实是“去道德化”,把“道德”评判转换为“超道德”评判。因此,价值判定(对好、坏、善、恶的分析)被搁置,或者讲被一种新的“功能化”的东西所取代。例如,他们将什么行为是“好”与“坏”的评判,与对行为的“善”与“恶”评判分开来。因此,看一种行为是否能够使人的潜能(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成了评判的标准。换句话讲,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人格的“功能化”:什么样的人通过个人奋斗而使得个体最大的功能得以出现,什么人就能够成为偶像。也确实是讲,他们崇拜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人”,而是一个人的某些“功能”。这种“功能”正是他们自己妄图而不能实现的要素,如,速度、高度、力度、和谐能力、应酬能力,等等。
历史地看,这种选择或标准,第一能够视为一种道德评判上的“拨乱反正”。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尺度专门高,脱离了个人功能发挥(感官层面上的自我实现)这一基础,使人觉得高不可攀。从小就让他们学习“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现在,年轻一代从另一个极端(去道德化,强调功能的超道德特性)做出了选择。因此,传统价值判定中被认为“恶”的、“坏”的人物,通过“去道德化”之后,其“功能化”的成分得以凸现,就有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甚至有些年轻人崇拜希特勒的强力);在传统价值判定中并不值得关注的对象,有可能成为追逐的对象。对一些小明星的崇拜更是五花八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偶像,看起来一派多神教的气象。
个人躯体“能量”的完美出现,成了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这与神话时代或诗史时代的价值观念接近,因而隐含着一种“道德返祖”的趋向。代表这种能量化、功能化的角色,其“原型”,确实是美国的“超人”,或者日本的超人“奥特曼”。这些虚拟偶像,在能量一旦耗尽之后,用不着像植物生长时那样的缓慢过程,而是借用现代电力快速补充能量,例如穿上
一件有能量的服装、举起一支惊奇的发光棒、或者吃一种奇异药片,就能快速复原功能,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阻碍,要紧来自动画片和漫画书。这种阻碍在长大之后一直在连续。因此,80后的“偶像”,也要紧是一些功能化的人物。“速度超人”刘翔,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偶像!“高度超人”姚明也是没有争议的。现了一个更快的罗伯斯,或者显现了一个更高的小姚明,作为功能偶像的偶像功能变宣告终结。
还有韩寒,也是公认的80后的偶像,他有什么超人的“功能”呢?他躯体的速度、力度无疑并不杰出;在赛车行内的车速上,也是业绩平平。韩寒的要紧特点在于“思维速度”惊人,确实是小学生中流行的“脑筋急转弯”专门厉害。这一点足以战胜他的同龄人。这种思维速度、脑筋急转弯,第一是表现在语言组合能力、词语生成的速度上。例如,当你面对“文化圈”、“演义圈”等各种“圈子”而仰慕不已的时候,韩寒讲,不管什么“圈”,最终差不多上“花圈”。当一些人面对“文坛”、“商坛”、“政坛”争辩不休的时候,韩寒讲,不管什么“坛”,最终差不多上“祭坛”。在两个“圈”和“坛”之间迅速完成转换。这种“末日审判”式的句式,瓦解了现实功利主义所依靠的历史时刻,体现了思维速度和词语生成的速度,也产生了传播成效专门好的批判性。这是韩寒与同龄人相比的过人之处。韩寒之因此会成为同龄人的“偶像”,是因为他跟同龄人不一样。他反对自己一代人与父辈之间文化上的“连续逻辑”,成了文化“断裂逻辑”的代表。他早期的小讲,尽管叙事和语言形式还专门粗糙,但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教育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们一代人的心声。然而,他在自身能量积存和成长中也主张“断裂”,中途辍学,拒绝耗费时刻的传统教育模式。他期望自己能像“超人”一样,夜晚插上电源,白天能量仍旧。因此,他的“思维速度”专门快这一功能,最终可能只会产生“脑筋急转弯”的成效。而“脑筋急转弯”是有年龄限制的。那些在偶像崇拜“多神教”思维支配下的一代,会迅速找到新的归宿。
五、他们一代人想象性文化的总体特点
以千年为单位研究文明史,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头上的刻痕。以百年为单位研究文化史,我们面对的确实是记录在文献中的想象性文化遗产。想象性文化,是一个时代最能经得起时刻淘洗的文化形状,它最浓缩的出现形式确实是文学艺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讲,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符号。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学艺术史越写越厚,但经得起时刻检验的作品却专门少,总体上不如人意。电影不成熟,白话小讲和诗歌也不成熟,只能讲刚刚开了个头,但也留下了专门多值得借鉴的体会,专门是在扫除现代人表达上的“语言路障”和“思维路障”方面,他们功不可没。1949年至1979年高度“一体化”时期,整整一代作家被耽搁了,好的变差了,差的更差了。像差不多98岁高龄的杨绛先生那样,75岁时才开始写小讲且出手不凡的如何讲少见(其代表作为《洗澡》、《将饮茶》、《我们仨》。施蛰存先生认为《洗澡》兼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双重遗风。我认为她将白话汉语写得像古汉语一样精练、准确,爱护了20世纪白话文的威严。她的小讲全然就不是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直截了当确实是“文学”。如果倒退几十年,杨绛先生在40岁的1951年就开始正常的文学创作,会是什么模样呢?)。
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文学主体的“40后”、“50后”、“60后”一代作家,成绩自有公认,但前景也在预料之中了。“70后”一代作家的可能性还在,我期望他们像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我们刚刚开始”,那个地点不展开讨论。进入了21世纪以来,正是“80后”粉墨登场的时候,目前局势还不明朗。就差不多出现出来的症候来看,趋势并不乐观。他们最大的咨询题确实是在像玩宠物一样玩文学,像给“芭比娃娃”换上各种服装一样玩词语。他们拒绝介入真正的公共生活。他们因此有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明白得,那确实是数字化建构起来的市场。但是,市场不是“公共生活”的全部,而是专门小的一部分。他们的创作世界与他们的现实处境分裂的厉害。他们的词语的产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甚至连浪漫主义也不是,直截了当确实是一个“童话”,一个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听一遍的“儿歌”。
就“想象力”而言,他们看起来专门有想象力,能够奇思妙想,想出各种稀奇惊奇的场景和人物,鬼推磨、鬼吹灯、鬼打墙,无奇不有。然而,真正的想象力必定是生命力之中产生出来的,它必定带着个体生命力遭受压抑、而又再度张扬这一过程的伤痕和欢欣。它借此而介入了真正的“公共生活”。没有这些,就只能显现想象的过剩、想象的堆砌。过剩想象的虚假性,是一剂市场急需的迷幻药,因而专门有市场。
就“审美”而言,他们的语言看起来专门美,许多漂亮的辞藻像“驴友”一样结伴出行:悲伤啊、河流啊、青草啊、爱恋啊。“审美”,是一种极其古老而奢侈的东西。它的现代品行在于对古典“美学”的扬弃,其中专门要强调的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扬弃古典美学的腐朽性、单一性,增加现代人对审美的全新感受和复杂多样性。这种复杂多样性的内部,自始至终包含一个重要的“公共咨询题”,那确实是,美到哪里去了,谁毁坏了美,新的美的显现是否可能?什么样的词汇才能挽救它?这确实是文艺创作上的制造性的前提。没有这些前提,美就会患上王尔德所讲的审美上的“不育症”。
上面所讲的,要紧是针对那个群体的整体而言。想象性文化的最终成效,确实是超越观念批判的局限,制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代表一代人想象方式的综合性文化标本,包括他们用具有时代感的母语所表达的对真正的“审美”形式,以及对死亡和不朽的想象。然而,要真正整理出一代人的审美想象形式及其特点,必须采取“解剖法”而不是“归纳法”。因为真正代表一代人审美想象特点的不是公众那种复制式的、看似多样实则单一的想象方式、被强势大众媒体叙述出来的同质化的文化,而是通过他们中最优秀的个体制造性的想象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也确实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之中。
目前,对80后的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还专门不够,泛泛之论过多,专门是对他们的专门文学形状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发觉和选取代表作进行解剖,并从专门的形式中发觉一代人的精神密码,是一件急需开展的工作。“8 0后”的创作差不多显现了好的苗头,如韩寒的文化反叛及其表达特点(长篇读物《三重门》),李傻傻专门的城乡交叉体会及其对一代人精神创伤的
描述(长篇读物《红X》);春树对都市青年叛逆文化的专门表达(长篇读物《北京娃娃》),桑格格的碎片式写作、及其内在词语形式中包含的经历整合的努力(长篇读物《小时候》),徐来对古典文化意象的解构和对经历的复活策略(长篇读物《经历中的动物》);还有张悦然、颜歌、蒋峰等一批人叙事中的代际特点,等等(没有列上名单的请原谅)。我用了“长篇读物”而没有用“长篇小讲”那个概念,是有自己的理由的,由于篇幅缘故那个地点不展开讨论。我将连续采纳“长篇读物”这一概念,对能够更综合表现一代人精神状态的文学个案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