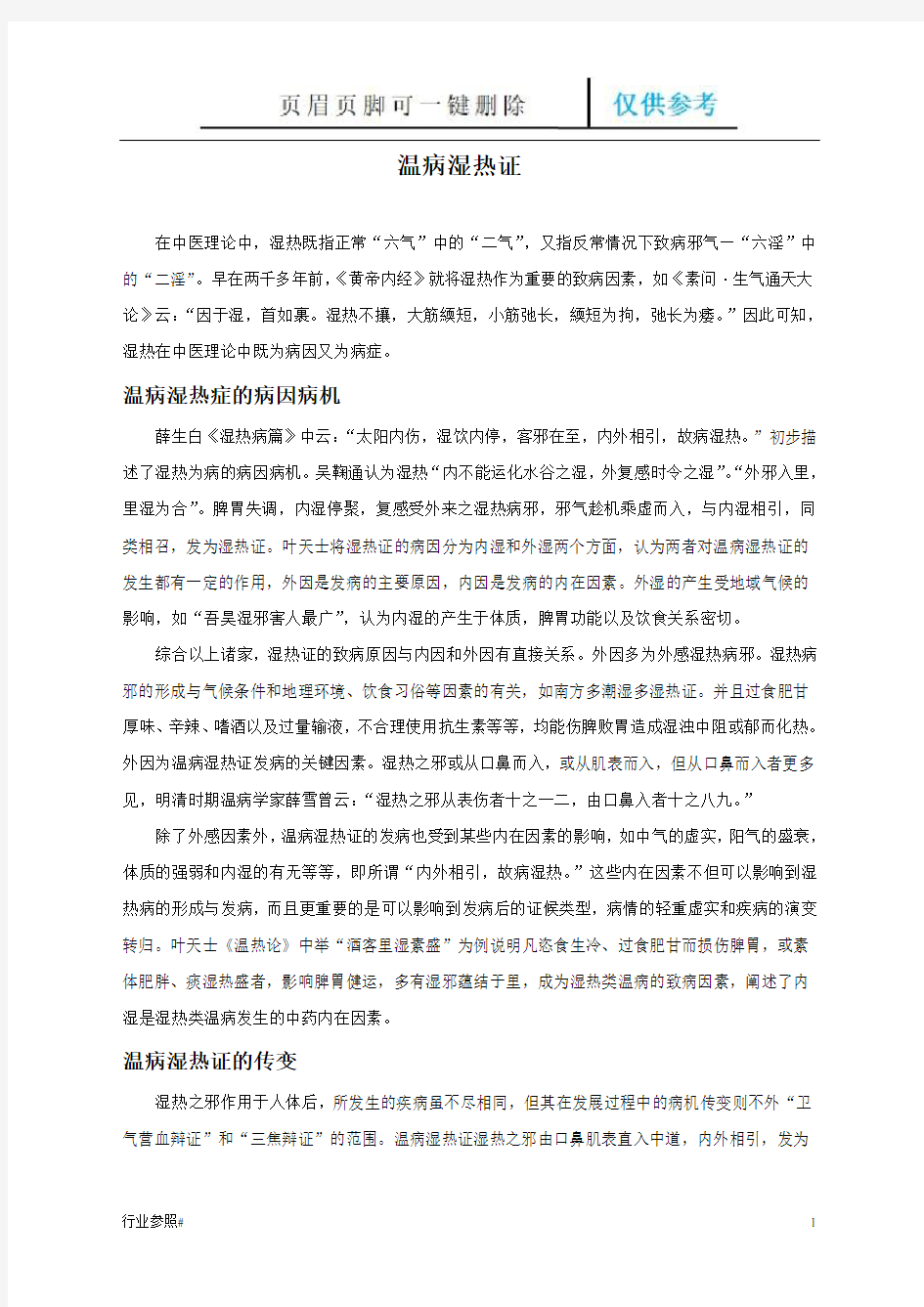

温病湿热证
在中医理论中,湿热既指正常“六气”中的“二气”,又指反常情况下致病邪气—“六淫”中的“二淫”。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就将湿热作为重要的致病因素,如《素问·生气通天大论》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因此可知,湿热在中医理论中既为病因又为病症。
温病湿热症的病因病机
薛生白《湿热病篇》中云:“太阳内伤,湿饮内停,客邪在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初步描述了湿热为病的病因病机。吴鞠通认为湿热“内不能运化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外邪入里,里湿为合”。脾胃失调,内湿停聚,复感受外来之湿热病邪,邪气趁机乘虚而入,与内湿相引,同类相召,发为湿热证。叶天士将湿热证的病因分为内湿和外湿两个方面,认为两者对温病湿热证的发生都有一定的作用,外因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内因是发病的内在因素。外湿的产生受地域气候的影响,如“吾昊湿邪害人最广”,认为内湿的产生于体质,脾胃功能以及饮食关系密切。
综合以上诸家,湿热证的致病原因与内因和外因有直接关系。外因多为外感湿热病邪。湿热病邪的形成与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饮食习俗等因素的有关,如南方多潮湿多湿热证。并且过食肥甘厚味、辛辣、嗜酒以及过量输液,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等等,均能伤脾败胃造成湿浊中阻或郁而化热。外因为温病湿热证发病的关键因素。湿热之邪或从口鼻而入,或从肌表而入,但从口鼻而入者更多见,明清时期温病学家薛雪曾云:“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
除了外感因素外,温病湿热证的发病也受到某些内在因素的影响,如中气的虚实,阳气的盛衰,体质的强弱和内湿的有无等等,即所谓“内外相引,故病湿热。”这些内在因素不但可以影响到湿热病的形成与发病,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发病后的证候类型,病情的轻重虚实和疾病的演变转归。叶天士《温热论》中举“酒客里湿素盛”为例说明凡恣食生冷、过食肥甘而损伤脾胃,或素体肥胖、痰湿热盛者,影响脾胃健运,多有湿邪蕴结于里,成为湿热类温病的致病因素,阐述了内湿是湿热类温病发生的中药内在因素。
温病湿热证的传变
湿热之邪作用于人体后,所发生的疾病虽不尽相同,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病机传变则不外“卫气营血辩证”和“三焦辩证”的范围。温病湿热证湿热之邪由口鼻肌表直入中道,内外相引,发为
邪遏卫气证。湿热证由其性质的特异性,其性重浊黏滞,与热相合,藴蒸不化,胶着难解,致使病势传变缓慢,病程较长,缠绵难愈。故初起一般病势不盛,表邪进而入里,流连气分,随气分湿热证的加重,卫分见证随之消失。脾胃受伤,运化失常,湿邪停聚,阻遏气机,其病变渐趋于中焦脾胃。气分湿邪留恋气分阶段时间较长,发展演变多以脾胃为病变中心。正如吴瑭云“中焦与脾合者,脾主湿之质,为受湿之区,故中焦湿证较多。”又章虚谷云:“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其初起阶段,虽湿中藴热,但多见湿重热轻。
中气的盛衰,决定着湿热的转化,薛生白云:“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既指素体中阳偏旺者,则邪从热化而病变偏于阳明胃,素体中阳偏虚者,则邪从湿化而病变偏于太阴脾。病在太阴者,则湿重热轻,病在阳明者,则湿轻热重。湿热证湿热郁蒸气分,虽然以中焦脾胃为主,但湿热病邪有蒙蔽上窍,流注下焦的特性,故又能弥漫三焦,波及其他脏腑。如上蒙清窍下注小肠、膀胱,内蕴肝胆,外蒸肌凑等,既可伤阴又可伤阳,故病变范围广泛而病情复杂。治疗得当,湿热邪气渐解并转入恢复期;治疗不当,病变进一步发展,湿热之邪可化燥化火伤阴,深入营血,出现神昏、动血等变证;湿浊之邪久郁不解,则湿渐伤阳,发展为寒湿或湿胜阳微等变证。
温病湿热证的辨证论治
A、湿热之证的一般主证:身热不扬,头身困重,汗出不畅,胸闷纳呆,脘痞腹胀,恶心便溏,小
便短赤,舌红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
B、辩证规律
(1)辨湿热的偏重与否。如湿重热轻者,多见热势不扬,早轻暮重,头身重痛,大便溏,小便混浊不清渴不引饮,或口淡无味,苔白腻白滑,或白如积粉,舌质略红脉濡滑等。
(2)辨别邪在三焦所属部位。湿热证虽以脾胃为病变中心,但因湿邪有蒙上留下的特性,故可弥漫三焦。
C、治疗原则
(1)以分消湿热,湿去热孤为原则,开上、宣中、导下,气机得通,湿邪得化。薛生白云:“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吴鞠通:“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
(2)祛湿的同时顾护正气。针对湿热证的治疗中,由于患者体质或过用寒凉之品,往往易使阳气更伤,导致气化不行,则湿邪难祛的特点。叶天士强调治湿应顾护阳气,“面色白者,需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既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湿热
一去,阳亦衰微也。”
(3)注意利小便,古人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4)注意舌苔的辩证
D、论证治疗
a上焦湿热证
湿热之邪初犯人体,病位偏上,主要为:头面清窍,咽喉以及上焦肺及心包。为卫气阶段,以上焦气机被湿热之邪所遏,肺气不得宣化湿邪为主要表现,同时兼有湿邪困脾证的临床表现,主要为湿重热轻。
临床表现:恶寒发热,头肢困重,胸脘闷满,口粘不渴,纳呆便溏,或有咳嗽,咳声闷而有白痰,苔薄白腻,脉濡缓
治法:分消上焦湿热,以宣透湿邪,佐以轻清为法。治宜用芳香之品宣透表里之湿,兼以轻清,以藿朴夏苓汤或三仁汤主之。吴鞠通称:湿阻上焦,“肺病湿,气不得化”,故用芳香辛透之品宣通肺气,常用藿香、佩兰、苏叶、香薷等,肺气得宣,抑郁肌表之湿既散。湿中蕴热者,佐以竹叶、连翘、黄芩等轻清宣透之品,同时配淡渗之品,使邪有出路从小便而去。
b中焦湿热证
湿热之邪在上焦不解、中焦之邪势渐重,此时总病机:湿热蕴蒸,气机阻滞。同时由于湿热之邪具有湿与热的双重性质,所以邪气每随脾胃机能的特性和状态而出现不同的病理变化,由此决定了湿热在中焦的不同发展趋势:从阳而化热化燥;从阴而湿邪偏盛,甚则寒化;也可表现为湿热久蕴不解。中焦湿热证的治疗,应采用燥湿清热之法,祛除湿热邪气,用药宜轻疏灵动,忌守中。在芳香化湿宣降肺气的同时,更用陈皮、半夏、厚朴、木香、大腹皮、白豆蔻、草豆蔻、煨姜、黄连等,辛开于中,调整脾胃功能,使之恢复升降平衡,正如吴鞠通云:“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
中焦湿热证有以下三种类型:
湿重热轻:脾胃阴土主湿,素体脾虚则邪易从湿化。湿浊困脾,脾失健运,热蕴于中。临床表现:身体重楚,四肢清冷,口淡不渴,胸脘痞闷,时作呕恶,大便溏泄,小便清长,或喜热饮,舌苔白腻,脉细濡。治法:辛温开郁,苦燥燥湿。方药:加减正气散(藿香梗、厚朴、杏仁、茯苓皮、广陈皮、神曲、麦芽、绵茵陈、大腹皮)或三仁汤(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苡仁、半夏)加减。
湿热并重:湿郁而热蒸,湿热胶结,耗伤津液。临床表现:身热心烦,脘痞腹胀,恶心呕吐,大便
溏薄,色黄气臭,汗出热不解,舌苔黄腻,脉濡数。治法:苦寒燥湿,辛凉清热。方药:连朴饮(制厚朴、姜汁炒黄连、石菖蒲、半夏炒豆豉、焦栀子、芦根)或黄芩滑石汤(黄芩、滑石、茯苓皮、大腹皮、白蔻仁、通草、猪苓)等。
热重湿轻:胃属阳土主燥,素体阳旺则湿热之邪化热化燥。临床表现,热势壮盛,胸脘痞满,汗多热臭,口渴或苦,尿短赤,苔黄腻舌红,脉濡数或洪数。治法:重在清热,兼以祛湿。张景岳认为“湿热之病宜清宜利,热去湿亦去”“热甚者以清火为主,佐以分利。”方药:白虎加苍术汤(石膏、知母、粳米、生甘草、苍术)
湿邪最易困阻脾胃,而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故治疗中焦湿热证常与祛湿药中配入健脾益气,消导和胃之品,以恢复脾胃功能,促进水湿运化,如茯苓、薏苡仁、白术、砂仁、白蔻仁、神曲、山楂、麦芽、鸡内金等;湿性黏滞,易阻滞气机,故配伍理气行滞药物以宣畅气机或少佐通肺气之品,行提壶揭盖之功,如郁金、枳实、厚朴、大腹皮、陈皮、藿香、佩兰、杏仁、桔梗、全瓜蒌等;湿热兼有郁滞的,辅以活血化瘀药,丹参等;热酿成毒的宜加清热解毒药;佐以通利小便之品,如茯苓、泽泻、淡竹叶、白茅根等。
c下焦湿热证
湿热之邪下注小肠膀胱。临床表现:小便不利或涩痛,甚至于癃闭,小腹胀满,渴不多饮,大便不通或大便溏而不爽,腹胀痛,舌苔腻,脉濡。治法:淡渗利湿。方药:苓皮汤,常用茯苓、滑石、泽泻、生薏苡仁等。所用淡渗利湿之品,性多偏凉,既能渗湿又可泄热,具有祛湿除热之效。
总之,湿热证的治疗总以分消湿热,湿去热孤为原则,先针对湿邪,以化湿为法,同时要针对热邪治以清热。四诊合参,全面分析湿热偏重,病位,并根据病势的缓急,感邪的轻重,人的不同体质,不同兼证,辨证论治。同时注意应避免居于潮湿湿热之处,并重视饮食调养,慎饮食节口味,并且戒酒,忌辛辣,切勿贪凉饮或过食生冷等。应以稀薄饮食,或流质少油腻,无刺激性,易于消化吸收的食物为主,少量多餐,切忌过饱以防食复或变生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