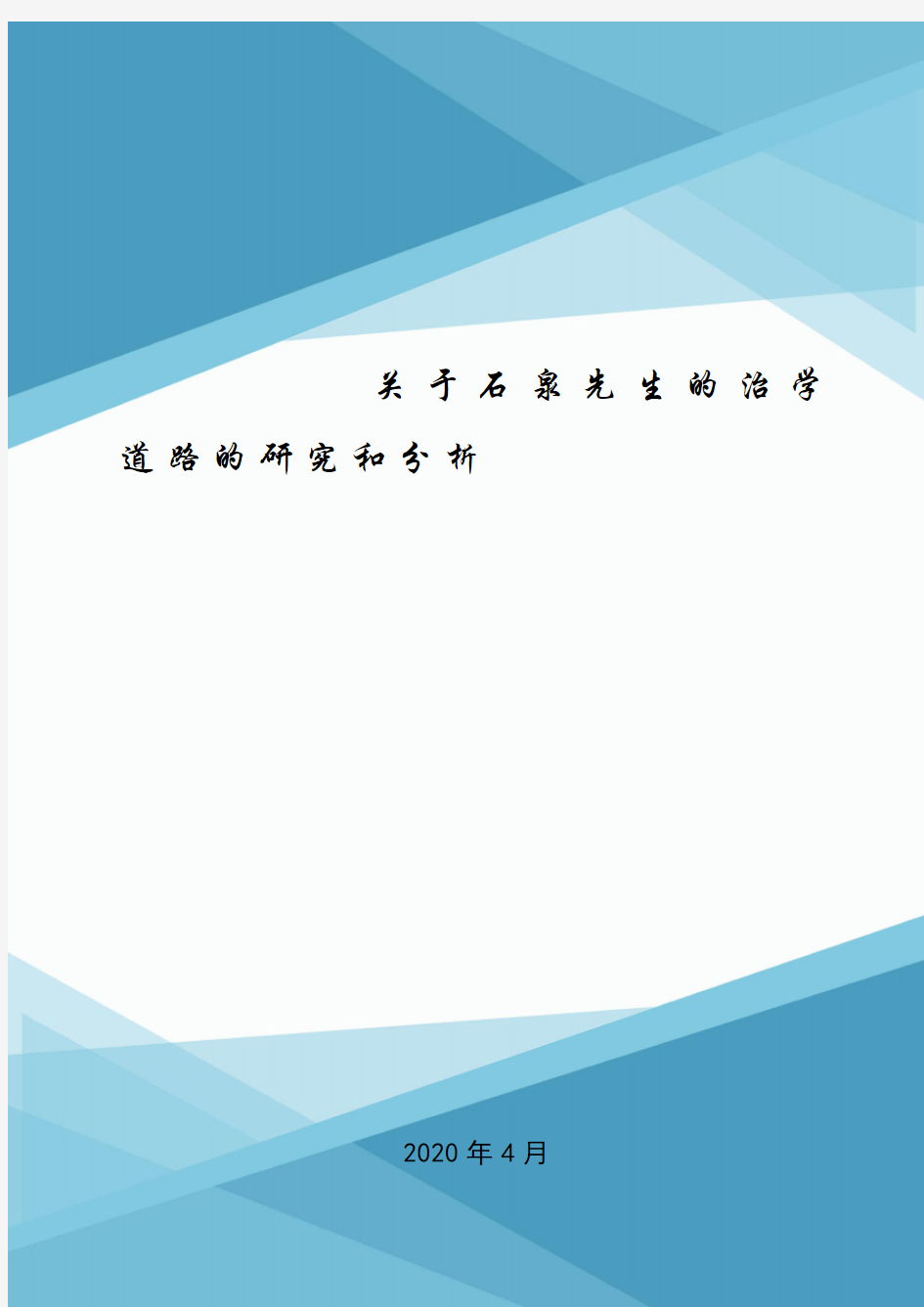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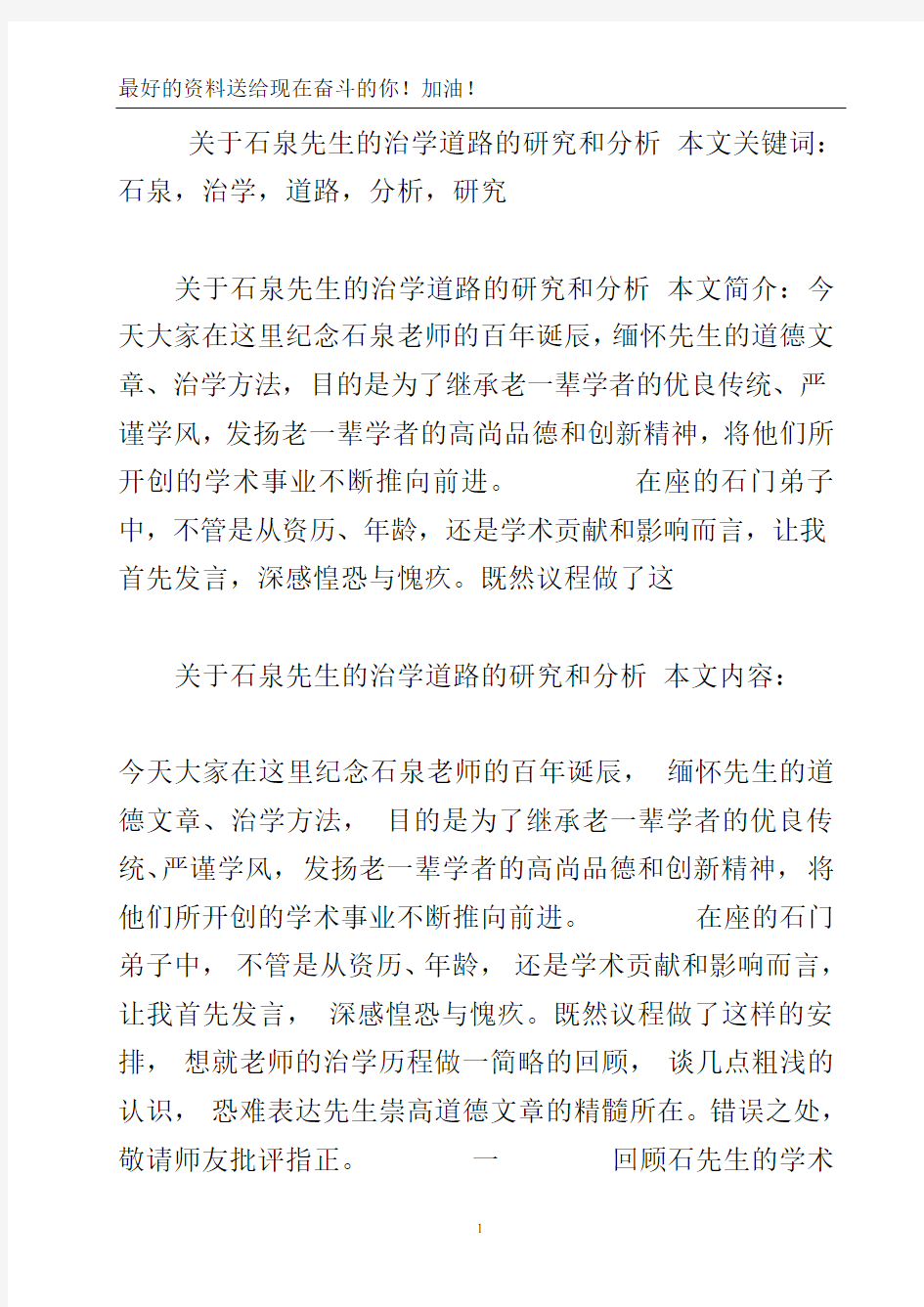
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
2020年4月
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关键词:石泉,治学,道路,分析,研究
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简介: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石泉老师的百年诞辰,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方法,目的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严谨学风,发扬老一辈学者的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将他们所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座的石门弟子中,不管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言,让我首先发言,深感惶恐与愧疚。既然议程做了这
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内容: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石泉老师的百年诞辰,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方法,目的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严谨学风,发扬老一辈学者的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将他们所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座的石门弟子中,不管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言,让我首先发言,深感惶恐与愧疚。既然议程做了这样的安排,想就老师的治学历程做一简略的回顾,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恐难表达先生崇高道德文章的精髓所在。错误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一回顾石先生的学术
道路,与其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诸多曲折和磨难。大致来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4~1960年。1954年2月,石先生由北京高教部调来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因工作需要,曾先后讲授过宋辽金元史、隋唐五代史, 并编写有《隋唐五代两宋讲授提纲》;后又主讲过中国近代史.因石先生是研究生毕业,讲课效果也不错,校、系领导曾几次建议他任副教授,石先生觉得自己刚来武大不久,还是先当讲师为好,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在备课、讲课间隙,石先生便沿着当年由徐中舒先生指导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思路,着手撰写《古郢都、江陵故址考》一文,并于1956年在校内外学术会上印发征求大家的意见。1958年拔白旗运动,石先生的若干近代史观点受到严厉批判,因石师不愿作违心之论,从此不再讲授中国近代史,逐渐转入与政治相对较远、且一直饶有兴趣的历史地理研究,先后撰写了《绿林故址考》、《古竟陵城故址新探》等几篇学术论文。第二阶段,1961~1976年。1961年,学校实行定方向、定任务、定措施的三定方针,石先生经过认真思考,即赴京与侯仁之先生商量,决定今后全力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与教学。通过不长时间的准备,便于当年秋季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还编写了部分讲义。同时修订有关文稿,相继于《江汉学报》发表了《绿林故址考》、《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
初考》等论文。不久,因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石师与师母被先后安排到东升公社和武大襄阳、沙洋五七干校参加政治野营、劳动锻炼五六年,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全部中断。第三阶段,1977~199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石先生的政治生命与学术景况得到根本改观,先后于1978、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同时也迎来了其教学、科研的黄金时节。石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如《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云梦泽研究》、《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等,都是在这一阶段发表、面世的。我们这些及门弟子的入室、问学等大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1985年前后,石师先后担任民进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后又担任民进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等职,各类学术、社会活动与日俱增,异常繁忙,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应对。第四阶段,1999~2005年。1998年11月,石师以八十岁高龄离休,仍担任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此后几年,一直在鲁西奇教授的协助下,坚持他的学术研究,整理旧稿,指导学生。2004年初,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同年9月,获评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接着又集中精力编辑《石泉文集》,直到该年冬天彻底病倒,才停止了他
的学术探索。二石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就其代表性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为核心的相关问题研究核心内容是《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与此密切关联的研究如《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等;其他数篇论文如《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邓国、邓县考》等,也都是与这一主题相互呼应、相互佐证的。后一并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一系列论文,主要探讨先秦至六朝时期以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流行说法的新见解,即古代楚国以及此后七百多年间直至梁陈之际的荆楚地区重心所在,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的宜城平原,而非如隋唐以来千余年间逐渐形成体系的传统解释所云,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
2. 古云梦泽研究按时代顺序,形成了四篇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云梦泽状况的论文,如《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先秦江南之梦)故址新探》、《唐至北宋时期着称的安州云梦泽》、《统一的大云梦泽说之形成与演变》。后一并收入与蔡述明先生合着的《古云
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一书。研究表明,历史上从无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存在,同一时期往往不止一个云梦泽异地存在,但只有一个最着称,而不同时期的云梦泽,又常不在同一地方。这一系列的成果,较大改变了人们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格局的认识,对于探讨本地区的开发层次、重心所在以及开发规律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提出了江汉平原具有典型泛滥平原特征的看法,对流行说法认为江汉平原为典型的陆上三角洲,是古云梦泽经长江、汉水泥沙的长期沉积,湖泊三角洲不断扩展而最后形成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于探索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河床形态的发育过程,及其与两岸江汉洞庭平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汉魏六朝荆楚地理新探对当时这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口城、赤壁之战战场,以及湘、资、沅、澧四水等地名加以考辨,重新定位,形成了《古夏口城地望考辨》、《赤壁之战地理新探》、《古夏水源流新证》、《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面貌的巨变》以及《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等系列论文。后结集为《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些新解的核心观点之一,即认为在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巨大变化。在这次巨变中,以江陵为中心的许多自先秦汉晋以来一直着称的古城邑、山川湖泽地名,由汉水中游地区迁移到今长江中游两岸,并为后世所沿用。唐初编修《括地志》时,对这次巨变的情况已不甚了解,故在说明古地名的地望时,往往以后世同名之地作解释,因而形成了后人观念中关于古代荆楚地理认识的诸多混淆。引起这场混乱的主要契机,是由于梁陈之际荆楚中心地带连遭战争的巨大破坏,并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致地理区划上也相应发生了大变动,原在汉江中游两岸的一系列重要地名南移到长江中游两岸,从而使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带发生了转移。 4.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这是石师当年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原名《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主要探索晚清甲午战争失败的政治因素,日本明治维新晚于洋务新政数年,而甲午一战,成败判然。求自强之新政失败主因在于:(1)传统的守旧观念势盛,掌握清议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明世界大势,又惯发空论不务实,致使新政饱受牵制;(2)掌握中央决策的满族统治者对新兴的湘军、淮军既赖其御外侮,又处处猜防,并大力扶植敢与之对抗的清流势力;(3)满族亲贵之间亦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又分清流、浊流与之相结,最后发展为爱国有维新倾向的帝党, 与
政治经验丰富但极为守旧的后党, 而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又热衷于权力与个人享受,遂使朝廷不可能统一领导晚清的自强运动。该文完成于1948年夏天,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导的唯一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位论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石师保存的底稿于文革期间丢失,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当年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了此文,稍做整理、加工,更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 5. 宋元以来荆楚地理研究之设想一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垸田兴起、经济开发与地理变化。石先生在该领域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并在《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1981年刻印本,后经几位弟子整理,201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讲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和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有较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和思路。考虑到自身的精力和时间不济,石师先后指导张国雄、杨果、梅莉等几位同门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二是武汉市一带历史地理研究。石先生曾提出过一些基本思路和设想,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3~530页。后来又指导袁为鹏博士从事该领域的工作。关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石先生在《新探·续集》的自序中亦曾做过比较具体的说明(第28~29页).上述
五个领域的前三个方面,时代上前后承接,内容上互相关联,其实是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主要是围绕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时期的江陵城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这一整套体系,不仅关系到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地望的考辨和重新定位,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经济开发、社会变迁和重心转移等诸多重要问题,石师曾在不同的地方做过说明,如《新探·续集》自序(第16~18页).三对于石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特色,师门内外的学人曾做过一些总结,我讷于言辞难以尽之,只能谈几点肤浅的认识:1. 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这些因素,部分来源于先生早年的学术训练,部分来源于其自身天赋,但更主要的是其勤奋努力的结果,是石先生一身视学术为生命,契而不舍,不断积累、磨练出来的。石先生早在上中学时,就对史地有浓厚的兴趣,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先后修读过洪煨莲先生的历史方法与实习、郑德坤先生的高级史学方法, 以及陈寅恪、徐中舒等先生的相关课程,特别是从陈、徐诸先生的课中受益良多,眼界、思路进一步打开,学到了具体选用史料说明问题的识见和方法,尤其是陈寅恪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严谨深厚的功底,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人们意想不到而细想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的能力,对石泉先生后来的教学、
研究工作大有启迪和助益。在武大工作的五十余年中,不管是前期的身处逆境、步履维艰,还是后来的条件改善、多重工作叠加、异常繁忙的情况下,石师从不懈怠,稍有空隙就深入到自己的学术探索中,即或是在出差的旅途和住院的病房,也是一包一袋的书籍和材料随身携带,见缝插针地工作和研究,几无例外。曾有几位与石师有较多往来的师长对我讲,石先生的大脑就像一个书库,知识渊博,令人敬佩。我们也经常在同门及学生中坦言,我们大都较早当上了教授、博导,不管是成果, 还是带的学生可能比先生还要多,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若与老师和前辈学者相比,恐怕没有人不心虚脸红的。 2. 严谨的治学态度,敢于怀疑、返本探源、敢于创新的学术追求石先生做人、做事、治学,一生严谨求实,从不草率应付。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对各类史料、各类说法的处理都是这样,从不人云亦云,一定要弄个究竟,直探本源,这样的治学态度、探索精神,自然会出创新性成果。这方面的因素,石先生曾经说过,早年受到顾颉刚、钱穆等先生的影响,因为他们常能提出一些突破传统成说的崭新见解,使我惊异并受到启发。于是我也开始对一些通常为人们视为当然的说法,多问几个为什么。每当遇到一些显然存在矛盾,但又通常被忽视或避而不谈的问题时,就更不愿放过,总想探明究竟,弄清真相。(《新探》自序,
第8~9页)1944年春,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当考订春秋晚期吴、唐、蔡联兵入郢这次大战役的有关地名位置时,对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感到在情理和史料上矛盾甚多,很难讲得通,便对《左传》所记这次大战中涉及的二十几个地名的位置,进行了一番返本探源的考订,跳出隋唐以来直至近世逐步形成的传统框框,主要依靠先秦至六朝(直到齐梁时)的古注和经过认真鉴定的有关史料,与《左传》所记互相印证,得出了与流行说法全然不同、意外而又不得不然的新解。在回忆师从陈寅恪先生读研究生时,石先生曾谈及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练。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证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甚,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以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严谨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晚清政局》自序,第2页)由此可见石师治学态度、科学方法、创新精神的渊源。
3. 注重多学科方法、成果的结合与互补,注重田野调查石先生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由于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他对地理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方法与成果十分重视,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另一方面是求得几方面材料、结论的互证,再就是检验自己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主观失误。石先生曾谈及:侯仁之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对我说过:研究历史地理,光靠文献史料不行,必须进行野外考察。那里往往有很多古代遗迹(特别是古城堡和居民点故址和古河道), 可向我们提供书本上没有的,很有价值的第一手物证。侯先生的这一指点,我一直铭记在心。我是学历史的,未受过考古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正规、系统的田野调查训练,这方面的局限很大。对古文字学我也是个外行。但我一直注意这些相关学科的学者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并争取他们的帮助,迄今在这方面已得到不少有力的支援与配合。(《新探》自序,第8页)长期以来,只要是身体允许,石师总是带着有关问题开展相应的田野调查,走村访户,考察地貌环境的变化,了解古文化遗迹遗物,以与文献分析相佐证。对我们这些及门的学生,先生也一直这样指导和要求,并且以身作则。
4. 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决不半途而废的探索精神多年来,石先生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他选择的这些研究课题,都是硬骨头,最终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颇有得不
偿失的味道。对其所提出的这一整套突破千年传统框框,作了较大翻案,否定久已被公认的流行说法的观点和体系,既有朋友善意地提示他知难而退,也有个别同行私下嘲讽,不以为然。但石先生总是迎难而上,深入探究,从不轻言放弃或半途而废。对此,石师反复呼吁学界就其新解从三个层次进行严格审查:(1)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存在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3)如果对材料的理解不误,是否在运用方面有片面性,或者移花接木现象?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新探》自序,第2~3页;《石泉文集》自序,第36页)不仅体现了老师长期以来独立思考、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亦反映了其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由于攻关难度的巨大,改变甚至否定千年的传统认识并非易事,所以石师的有些文章是一稿、二稿、三稿,多至七稿、八稿,如《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等,经过几十年的修改、打磨后才拿出来发表。这样的学术勇气、这样的钻研精神,不得不令人敬佩。先生向来爱生如子,教书育人,师德风范,堪称楷模;先生毕生优良作风和治学方法,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
真继承、努力发扬;先生多年的言传身教,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勇于开拓,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