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_坡名诗_乌鸦_的早期译介与新文学建设_王涛
- 格式:pdf
- 大小:1.49 M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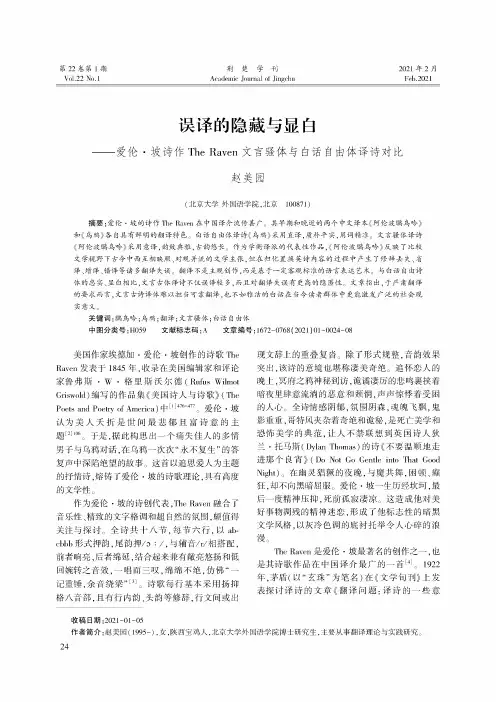
第22卷第]期Vol.22No.1荆楚学刊Academic Journal of Jingchu2021年2月误译的隐藏与显白爱伦•坡诗作The Raven文言骚体与白话自由体译诗对比赵美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摘要:爱伦•坡的诗作The Raven在中国译介流传甚广。
其早期和晚近的两个中文译本《阿伦波鵬鸟吟》和《乌鸦》各自具有鲜明的翻译特色。
白话自由体译诗《乌鸦》采用直译,质朴平实,用词精准。
文言骚体译诗《阿伦波鵬鸟吟》采用意译,韵致典雅,古韵悠长。
作为学衡译派的代表性作品,《阿伦波鵬鸟吟》反映了比较文学视野下古今中西互相映照、对观并流的文学主张,但在归化置换英诗内容的过程中产生了修辞丢失、省译、增译、错译等诸多翻译失误。
翻译不是主观创作,而是基于一定客观标准的语言表达艺术。
与白话自由诗体的忠实、显白相比,文言古体译诗不仅误译较多,而且对翻译失误有更高的隐匿性。
文章指出,于严肃翻译的要求而言,文言古诗译体难以担当可靠翻译,也不如雅洁的白话在当今读者群体中更能激发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鵬鸟吟;乌鸦;翻译;文言骚体;白话自由体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672-0768(2021)0—0024-08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创作的诗歌The Raven发表于1845年,收录在美国编辑家和评论家鲁弗斯•W•格里斯沃尔德(Rufus Wilmot Griswold)编写的作品集《美国诗人与诗歌》(The 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中[|]476-477o爱伦•坡认为美人夭折是世间最悲郁且富诗意的主题[2]|06O于是,据此构思出一个痛失佳人的多情男子与乌鸦对话,在乌鸦一次次“永不复生”的答复声中深陷绝望的故事。
这首以追思爱人为主题的抒情诗,熔铸了爱伦•坡的诗歌理论,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作为爱伦•坡的诗创代表,The Raven融合了音乐性、精致的文字格调和超自然的氛围,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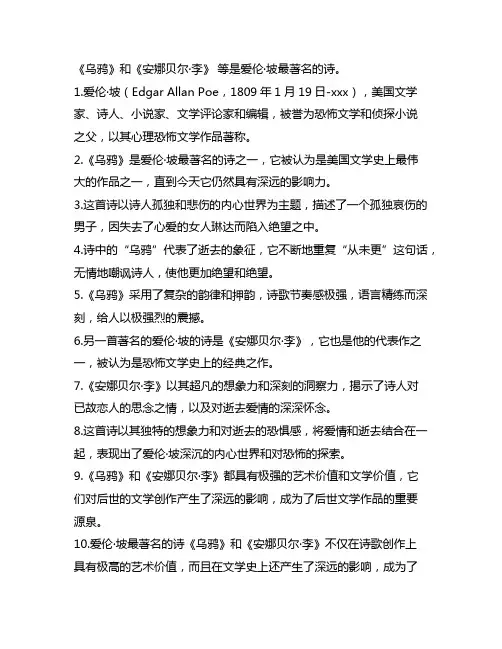
《乌鸦》和《安娜贝尔·李》等是爱伦·坡最著名的诗。
1.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年1月19日-xxx),美国文学家、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被誉为恐怖文学和侦探小说之父,以其心理恐怖文学作品著称。
2.《乌鸦》是爱伦·坡最著名的诗之一,它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3.这首诗以诗人孤独和悲伤的内心世界为主题,描述了一个孤独哀伤的男子,因失去了心爱的女人琳达而陷入绝望之中。
4.诗中的“乌鸦”代表了逝去的象征,它不断地重复“从未更”这句话,无情地嘲讽诗人,使他更加绝望和绝望。
5.《乌鸦》采用了复杂的韵律和押韵,诗歌节奏感极强,语言精练而深刻,给人以极强烈的震撼。
6.另一首著名的爱伦·坡的诗是《安娜贝尔·李》,它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恐怖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7.《安娜贝尔·李》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诗人对已故恋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
8.这首诗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对逝去的恐惧感,将爱情和逝去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爱伦·坡深沉的内心世界和对恐怖的探索。
9.《乌鸦》和《安娜贝尔·李》都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它们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后世文学作品的重要源泉。
10.爱伦·坡最著名的诗《乌鸦》和《安娜贝尔·李》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对人性黑暗面的深刻洞察而闻名。
在他那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乌鸦》和《安娜贝尔·李》这两首诗。
《乌鸦》中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个愉快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丧偶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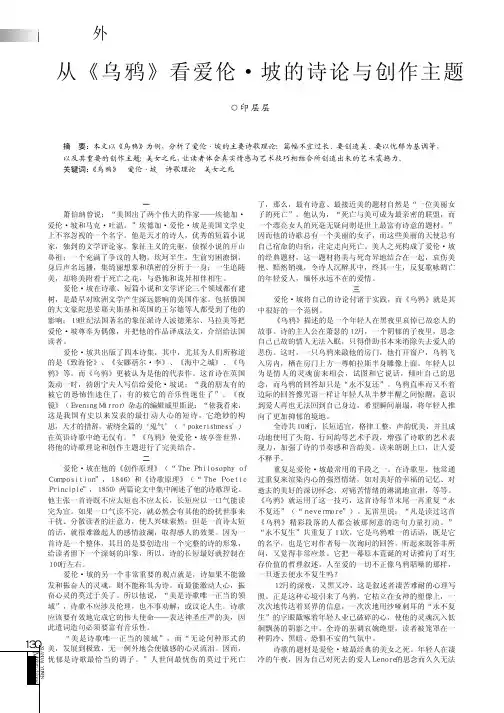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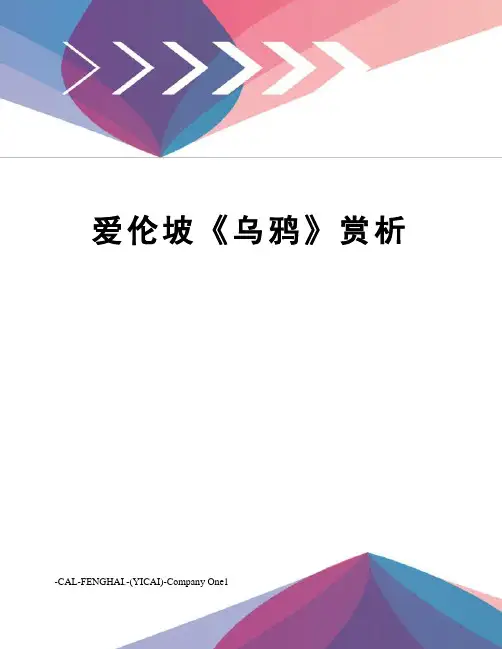
爱伦坡《乌鸦》赏析-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
《乌鸦》赏析
爱伦坡,美国哥特式文学大师与先驱,他深信“诗歌的最好主题是死亡,尤其是美丽尤物的死亡,将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具诗意的主题”。
而其在《乌鸦》中也糅合了具有死亡之美的哥特式元素。
《乌鸦》一开篇就给读者营造了一幅阴森恐怖的画面:在阴郁寒冷的午夜,除寒风呼啸之外只余男子的翻书声,一切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突然而至的敲门声,惊醒屋内之人,应门而去却发现屋外空无一物,只有肆虐的狂风融合在黑夜之中。
旋身离去敲门声又起,乌鸦随声而至,停留在房门的半身雕塑上。
午夜恐怖而阴森,为乌鸦——这来自幽河冥界的使者奠定了基调。
而故事又发生在狭小阴暗的小屋,这就突出显现了哥特式写作手法——恐怖与死亡交融(午夜,封闭小屋,乌鸦,亡魂)。
小屋也曾是男子与妻子的爱巢,紫色窗帘,紫色天鹅绒椅,浪漫温馨,如今物什仍在,人却消亡,空余男子,睹物思人。
此时乌鸦强行进入男子封闭的空间,以它的四字箴言“永不复回”,打碎了男子的幻想。
颤抖的灵魂在呼啸的寒风中追问着冥之使者可有神药忘却相思之苦,红尘之恼,换来的还只是“永不复回”。
永不复回的时光,永不复回的爱人,将会带走沉浸在永恒悲痛中无法醒来的灵魂:既然现世无法再见,那就相约幽冥河畔,彼岸尽头再相遇,相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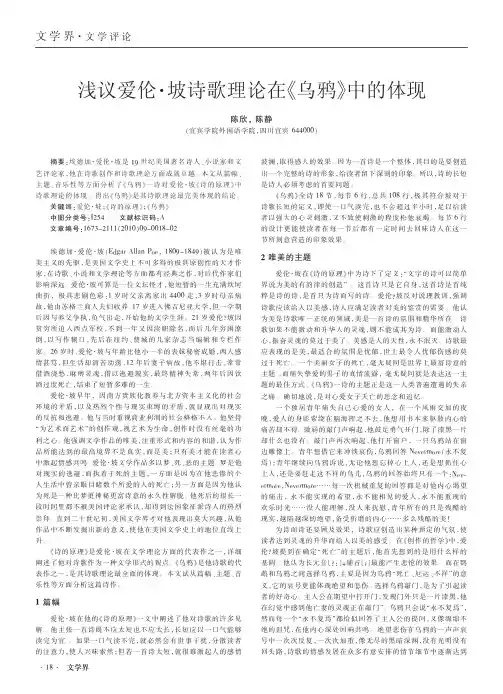
摘要:埃德加·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成就卓越。
本文从篇幅、主题、音乐性等方面分析了《乌鸦》一诗对爱伦·坡《诗的原理》中诗歌理论的体现。
得出《乌鸦》是其诗歌理论最完美体现的结论。
关键词:爱伦·坡;《诗的原理》;《乌鸦》中图分类号:I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0)09-0018-02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被认为是唯美主义的先驱,是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极具原创性的天才作家,在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有经典之作,对后代作家们影响深远。
爱伦·坡可算是一位文坛怪才,他短暂的一生充满坎坷曲折,极具悲剧色彩:1岁时父亲离家出4400走,3岁时母亲病故,他由苏格兰商人夫妇收养。
17岁进入佛吉尼亚大学,但一学期后因与养父争执,负气出走,开始他的文学生涯。
21岁爱伦?坡因贫穷所迫入西点军校,不到一年又因渎职除名,而后几年穷困潦倒,以写作糊口,先后在纽约、费城的几家杂志当编辑和专栏作家。
26岁时,爱伦·坡与年龄比他小一半的表妹秘密成婚,两人感情甚笃,但生活却清苦动荡,12年后妻子病故,他不堪打击,常常借酒浇愁,麻痹灵魂,借以逃避现实,最终精神失常,两年后因饮酒过度死亡,结束了短暂多难的一生。
爱伦·坡早年,因南方贵族化教养与北方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热烈个性与现实束缚的矛盾,就显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和逃避。
他与当时重视商业利润的社会格格不入。
他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视艺术为生命,创作时没有丝毫的功利之心。
他强调文学作品的唯美,注重形式和内容的和谐,认为作品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美;只有美才能在读者心中激起情感共鸣。
爱伦·坡文学作品多以梦、死、恶的主题。
梦是他对现实的逃避,而执着于死的主题,一方面是因为在他悲惨的个人生活中曾亲眼目睹数个所爱的人的死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死是一种比梦更神秘更富诗意的永久性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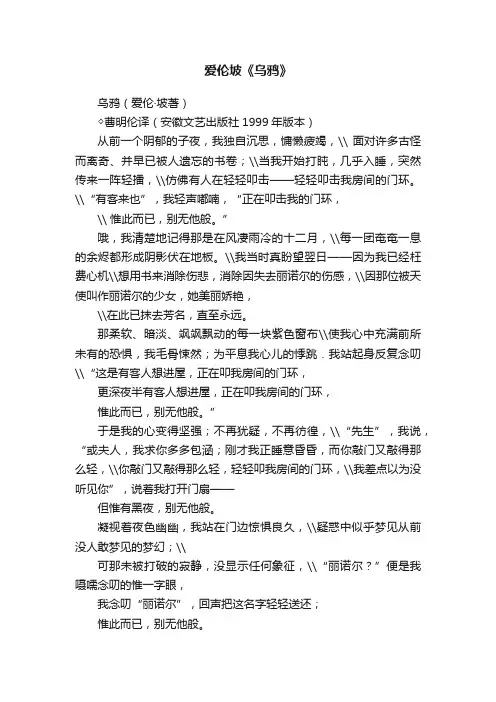
爱伦坡《乌鸦》乌鸦(爱伦·坡著)◇曹明伦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本)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我独自沉思,慵懒疲竭,\\ 面对许多古怪而离奇、并早已被人遗忘的书卷;\\当我开始打盹,几乎入睡,突然传来一阵轻擂,\\仿佛有人在轻轻叩击——轻轻叩击我房间的门环。
\\“有客来也”,我轻声嘟喃,“正在叩击我的门环,\\ 惟此而已,别无他般。
”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风凄雨冷的十二月,\\每一团奄奄一息的余烬都形成阴影伏在地板。
\\我当时真盼望翌日——因为我已经枉费心机\\想用书来消除伤悲,消除因失去丽诺尔的伤感,\\因那位被天使叫作丽诺尔的少女,她美丽娇艳,\\在此已抹去芳名,直至永远。
那柔软、暗淡、飒飒飘动的每一块紫色窗布\\使我心中充满前所未有的恐惧,我毛骨悚然;为平息我心儿的悸跳.我站起身反复念叨\\“这是有客人想进屋,正在叩我房间的门环,更深夜半有客人想进屋,正在叩我房间的门环,惟此而已,别无他般。
”于是我的心变得坚强;不再犹疑,不再彷徨,\\“先生”,我说,“或夫人,我求你多多包涵;刚才我正睡意昏昏,而你敲门又敲得那么轻,\\你敲门又敲得那么轻,轻轻叩我房间的门环,\\我差点以为没听见你”,说着我打开门扇——但惟有黑夜,别无他般。
凝视着夜色幽幽,我站在门边惊惧良久,\\疑惑中似乎梦见从前没人敢梦见的梦幻;\\可那未被打破的寂静,没显示任何象征,\\“丽诺尔?”便是我嗫嚅念叨的惟一字眼,我念叨“丽诺尔”,回声把这名字轻轻送还;惟此而已,别无他般。
我转身回到房中,我的整个心烧灼般疼痛,\\很快我又听到叩击声,比刚才听起来明显。
“肯定”,我说,“肯定有什么在我的窗棂;\\让我瞧瞧是什么在那儿,去把那秘密发现,让我的心先镇静一会儿,去把那秘密发现;那不过是风,别无他般!”然后我推开了窗户,随着翅膀的一阵猛扑,\\一只神圣往昔的乌鸦庄重地走进我房间;它既没向我致意问候,也没有片刻的停留,\\而是以绅士淑女的风度栖到我房门的上面,栖在我房门上方一尊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栖息在那儿,仅如此这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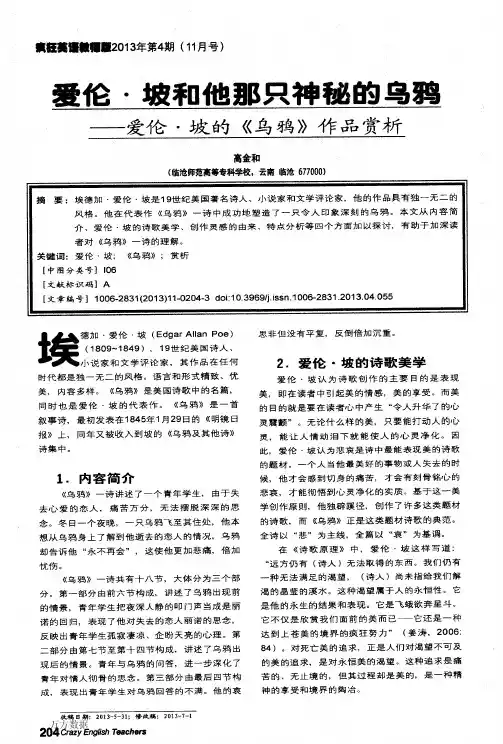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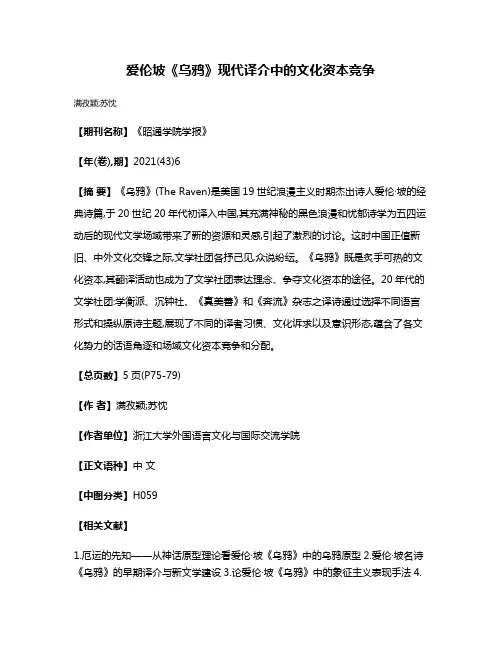
爱伦坡《乌鸦》现代译介中的文化资本竞争
满孜颖;苏忱
【期刊名称】《昭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1(43)6
【摘要】《乌鸦》(The Raven)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杰出诗人爱伦·坡的经典诗篇,于20世纪20年代初译入中国,其充满神秘的黑色浪漫和忧郁诗学为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学场域带来了新的资源和灵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这时中国正值新旧、中外文化交锋之际,文学社团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乌鸦》既是炙手可热的文化资本,其翻译活动也成为了文学社团表达理念、争夺文化资本的途径。
20年代的文学社团:学衡派、沉钟社、《真美善》和《奔流》杂志之译诗通过选择不同语言形式和操纵原诗主题,展现了不同的译者习惯、文化诉求以及意识形态,蕴含了各文化势力的话语角逐和场域文化资本竞争和分配。
【总页数】5页(P75-79)
【作者】满孜颖;苏忱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厄运的先知——从神话原型理论看爱伦·坡《乌鸦》中的乌鸦原型
2.爱伦·坡名诗《乌鸦》的早期译介与新文学建设
3.论爱伦·坡《乌鸦》中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
4.
爱伦·坡《乌鸦》中的重复及其意义5.凄凄宿语杳杳无音——论爱伦·坡的诗学理论在《乌鸦》中的体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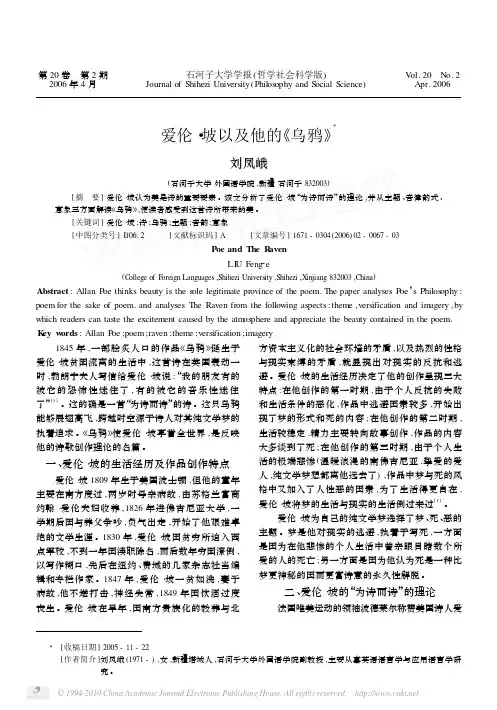
第20卷 第2期2006年4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V ol.20 N o.2Apr.2006爱伦・坡以及他的《乌鸦》Ξ刘凤峨(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 要]爱伦・坡认为美是诗的重要要素。
该文分析了爱伦・坡“为诗而诗”的理论,并从主题、音律韵式、意象三方面解读《乌鸦》,使读者感受到这首诗所带来的美。
[关键词]爱伦・坡;诗;乌鸦;主题;音韵;意象[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06)02-0067-03Poe and The R avenLI U Feng2e(C ollege of F oreign Languages,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X injiang832003,China)Abstract:Allan P oe thinks beauty is the s ole legitimate province of the poem.The paper analyses P oe’s Philos ophy: poem for the sake of poem.and analyses The Rave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me,versification and imagery,by which readers can taste the excitement caused by the atm osphere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contained in the poem.K ey w ords:Allan P oe;poem;raven;theme;versification;imagery 1845年,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乌鸦》诞生于爱伦・坡贫困流离的生活中,这首诗在英国轰动一时,勃朗宁夫人写信给爱伦・坡说:“我的朋友有的被它的恐怖性迷住了,有的被它的音乐性迷住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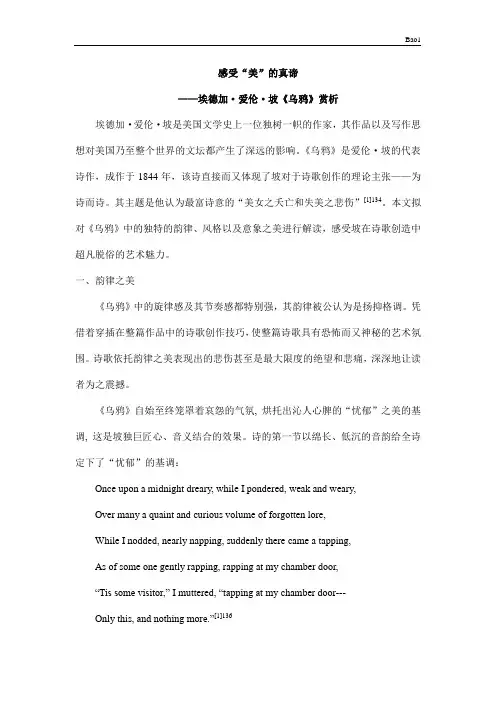
感受“美”的真谛——埃德加·爱伦·坡《乌鸦》赏析埃德加·爱伦·坡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其作品以及写作思想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鸦》是爱伦·坡的代表诗作,成作于1844年,该诗直接而又体现了坡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为诗而诗。
其主题是他认为最富诗意的“美女之夭亡和失美之悲伤”[1]134。
本文拟对《乌鸦》中的独特的韵律、风格以及意象之美进行解读,感受坡在诗歌创造中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
一、韵律之美《乌鸦》中的旋律感及其节奏感都特别强,其韵律被公认为是扬抑格调。
凭借着穿插在整篇作品中的诗歌创作技巧,使整篇诗歌具有恐怖而又神秘的艺术氛围。
诗歌依托韵律之美表现出的悲伤甚至是最大限度的绝望和悲痛,深深地让读者为之震撼。
《乌鸦》自始至终笼罩着哀怨的气氛, 烘托出沁人心脾的“忧郁”之美的基调, 这是坡独巨匠心、音义结合的效果。
诗的第一节以绵长、低沉的音韵给全诗定下了“忧郁”的基调:Once upon a midnight dreary, while I pondered, weak and weary,Over many a qua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gotten lore,While I nodded, nearly napping,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As of some one gently rapping,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Tis some visitor,” I muttered,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1]136这一节中坡精心挑选的词大都是长音, 如:“weak”和“lore”、“door”、“m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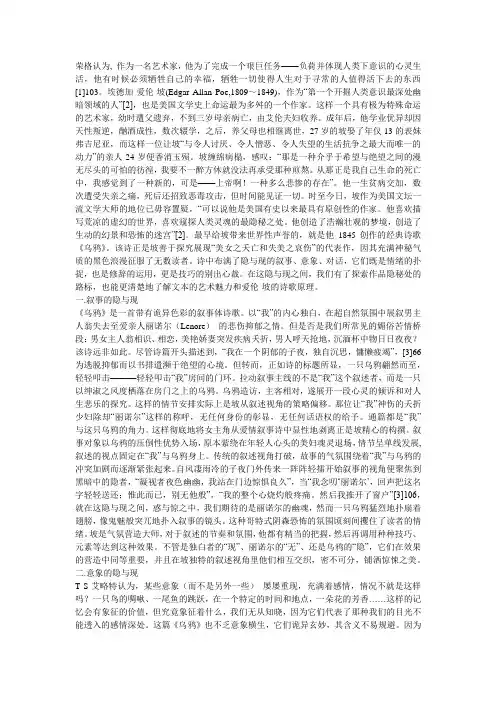
荣格认为, 作为一名艺术家,他为了完成一个艰巨任务——负荷并体现人类下意识的心灵生活,他有时候必须牺牲自己的幸福,牺牲一切使得人生对于寻常的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1]103。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作为“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2],也是美国文学史上命运最为多舛的一个作家。
这样一个具有极为特殊命运的艺术家,幼时遭父遗弃,不到三岁母亲病亡,由艾伦夫妇收养。
成年后,他学业优异却因天性叛逆,酗酒成性,数次辍学,之后,养父母也相继离世,27岁的坡娶了年仅13的表妹弗吉尼亚,而这样一位让坡“与令人讨厌、令人憎恶、令人失望的生活抗争之最大而唯一的动力”的亲人24岁便香消玉殒。
坡缠绵病榻,感叹:“那是一种介乎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漫无尽头的可怕的彷徨,我要不一醉方休就没法再承受那种煎熬。
从那正是我自己生命的死亡中,我感觉到了一种新的,可是——上帝啊!一种多么悲惨的存在”。
他一生贫病交加,数次遭受失亲之痛,死后还招致恶毒攻击,但时间能见证一切。
时至今日,坡作为美国文坛一流文学大师的地位已毋容置疑,“可以说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家。
他喜欢描写荒凉的虚幻的世界,喜欢窥探人类灵魂的最隐秘之处。
他创造了浩瀚壮观的梦境,创造了生动的幻景和恐怖的迷宫”[2]。
最早给坡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就是他1845创作的经典诗歌《乌鸦》。
该诗正是坡善于探究展现“美女之夭亡和失美之哀伤”的代表作,因其充满神秘气质的黑色浪漫征服了无数读者。
诗中布满了隐与现的叙事、意象、对话,它们既是情绪的扑捉,也是修辞的运用,更是技巧的别出心裁。
在这隐与现之间,我们有了探索作品隐秘处的路标,也能更清楚地了解文本的艺术魅力和爱伦·坡的诗歌原理。
一.叙事的隐与现《乌鸦》是一首带有诡异色彩的叙事体诗歌。
以“我”的内心独白,在超自然氛围中展叙男主人翁失去至爱亲人丽诺尔(Lenore)的悲伤抑郁之情。
《乌鸦》的魅力——论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乌鸦》(英文)杨林燕
【期刊名称】《海外英语》
【年(卷),期】2014(000)015
【摘要】《乌鸦》是埃德加·艾伦·坡的著名诗篇,爱伦坡以他独特的视角创作了这一首诗。
这首诗通过"美女之死"表现了美的极致,体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审美。
哥特式是这首诗的另一主题,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背景和形象中。
《乌鸦》的魅力还体现在朗朗上口的诗句上,诗人运用多种修辞方法使这首诗歌简单易读。
埃德加·艾伦·坡的种种努力促成了这首诗的成功。
【总页数】4页(P190-192,209)
【作者】杨林燕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712.072
【相关文献】
1.《乌鸦》的魅力--论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乌鸦》 [J], 杨林燕
2.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与苏轼的《江城子》比较 [J], 郑洁
3.爱伦·坡和他那只神秘的乌鸦——爱伦·坡的《乌鸦》作品赏析 [J], 高金和
4.从《乌鸦》看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艺术 [J], 张磊;闻建兰
5.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与苏轼的《江城子》比较 [J], 郑洁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经典诗歌欣赏乌鸦中英文爱伦·坡经典诗歌《乌鸦》欣赏,及其翻译The RavenOnce upon a midnight dreary, while I pondered, weak and weakry.Over many a qu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gotten lore.While I nodded, nearly napping,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As of some one rapping,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Tis some visitor," I muttered,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Ah, distinctly I remember it was in the bleak December,And each separate dying ember wrought its ghost upon the floor.Eagerly I wished the morrow; -vainly I had tried to borrowFrom my books surcease of sorrow-sorrow for the lost Lenore-For the rare and radiant maiden whom the angels name Lenore-Nameless here for evermoreAnd the silken sad uncertain rustling of each purple curtain Thrilled me-filled me with fantastic terrors never felt before;So that now, to still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I stood repeating " ' Tis some visitor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 Some late visitor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 This it is and nothing more.Presently my soul grew stronger; hesitating then no longer, "Sir," said I, "or Madam, truly your forgiveness I implore;But the fact is I was napping, and so gently you came rapping, And so faintly you came tapping,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That I scarce was sure I heard you"--here I opened wide the door;Darkness there, and nothing more.Deep into that: darkness peering, long I stood there wondering, fearingDoubting, dreaming dreams no mortal ever dared to dream before;But the silence was unbroken, and the darkness gave no token,And the only word there spoken was the whispered word, "Lenore!"This I whispered, and an echo murmured back the word, " Lenore! "Merely this, and nothing more.Then into the chamber turning, all my soul within me burning, Soon I heard again a tapping somewhat louder than before."Surely," said I, "surely that is something at my window lattice;Let me see, then, what thereat is, and this mystery explore- Let my heart be still a moment and this mystery explore;'Tis the wind, and nothing more!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 when, 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 not an instant stopped or stayed he;But, 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 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 Perched, and sat, and nothing more.Then this ebony bird beguiling my sad fancy into smiling,By the grave and stern decorum of the countenance it wore, "Though thy crest be shorn and shaven, thou," I said, "art sure no craven,Ghastly grim and ancient raven wandering from the Nightly shore-Tell me what thy lordly name is on the Night ' s Plutonian shor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Much I marveled this ungainly fowl to hear discourse so plainly,Though its answer little meaning-little relevancy hore;For we cannot help agreeing that no sublunary beingEver yet was blessed with seeing bird above his chamber door-Bird or beast upon the sculptured bust above I us chamber door,With such mime as "Nevermore.But the raven, sitting lonely on the placid bust, spoke only That one word, as if his soul in that ill~ word he did outpour.Nothing farther then he uttered-not a feather then he fluttered-Till I scarcely more than muttered, "Other friends have flown before-On the morrow he will leave me, as my hopes have flown befor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Wondering at the stillness broken by reply so aptly spoken,"Doubtless," said I, "what it utters is its only stock and store,"Caught from some unhappy master whom unmerciful DisasterFollowed fast and followed fastel-so, when Hope he would adjure,Stern Despair returned, instead of the sweet Hope he dared adjure-That sad answer, "Nevermore!"But the raven still beguiling all my sad soul into smiling,Straight I wheeled a cushioned seat in front of bird, and bust, and door;Then upon the velvet sinking, I betook myself to linkingFancy unto fancy, thinking what this ominous bird of yore- What this grim, ungainly, ghastly, gaunt, and ominous bird of yoreMeant in croaking "Nevermore. "This I sat engaged in guessing, but no syllable expressingTo the fowl whose fiery eyes now burned into my bosom's core;This and more I sat divining, with my head at ease reclining On the cushion's velvet lining that the lamplight gloated o'er, But whose velvet violet lining with the lamplight gloating o'er, She shall press, ah, nevermore!Then, methought, the air grew denser, perfumed from an unseen censerSwung by angels whose faint foot-falls tinkled on the tufted floor."Wretch," I cried, "thy God hath lent thee-by these angels he hath sent theeRespite-respite and Nepenthe from thy memories of Lenore!Let me quaff this kind Nepenthe and forget this lost Lenore!"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Prophet!" said I, "thing of evil! -prophet still, if bird or devil! -Whether Tempter sent, or whether tempest tossed thee here ashore,Desolate, yet all undaunted, on this desert land enchanted- On this home by Horror haunted-tell me truly, I implore-Is there-is there balm in Gilead?-tell me-tell me, I implore!"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Prophet!" said I, "thing of evil! -prophet still, if bird or devil!By that Heaven that bends above us-by that God we both adore-Tell this soul with sorrow laden if, within the distant Aidenn , It shall clasp a sainted maiden whom the angels name Lenore-Clasp a rare and radiant maiden whom the angels name Lenore.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Be that word our sign of parting, bird or fiend!" I shrieked, upstarting-"Get thee back into the tempest and the Night's plutonian shore!Leave no black plume as a token of that lie thy soul hath spoken!Leave my loneliness unbroken! -quit the bust above my door!Take thy beak from out my heart, and take thy form from off my door!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the raven, never flitting, 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On the pallid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And his eyes have all the seeming of a demon that is dreaming,And the lamp-light o' er him streaming throve his shadow on the floor;And my soul from out chat shadow that lies floating on the floorShall be lifted-nevermore!乌鸦(爱伦·坡著)曹明伦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本)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我独自沉思,慵懒疲竭,面对许多古怪而离奇、并早已被人遗忘的书卷;当我开始打盹,几乎入睡,突然传来一阵轻擂,仿佛有人在轻轻叩击——轻轻叩击我房间的门环。
论《乌鸦》的戏剧性刘保安【摘要】爱伦·坡的<乌鸦>一诗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其戏剧性主要表现在戏剧场景、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张力、戏剧对话、戏剧独白和戏剧冲突等方面.诗人正是运用这些戏剧手法真实地表现了忧伤、痛苦、绝望这些人类永恒的情感,并以此创造忧郁美和确立忧郁美的价值.坡创造美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欢乐,因为他坚信,"诗之直接目的是欢乐,而非真实".【期刊名称】《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10)002【总页数】3页(P185-187)【关键词】爱伦·坡;乌鸦;戏剧性;美【作者】刘保安【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5105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2爱伦·坡(EdgarAllan Poe,180921849)的《乌鸦》一诗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拜伦出版《洽尔德·哈罗德游记》一样,坡一觉醒来也发现自己出了名。
《乌鸦》出版后赢得的赞誉超过了美国出版的任何一首诗,并不断再版,被人竞相模仿。
《乌鸦》一诗不仅在本土得到许多文人的好评,就连英国女诗人布朗宁夫人也赞不绝口。
她指出,在英国,一些人被《乌鸦》的恐怖氛围所折服,有的则被其音乐所打动。
她说,她的一个熟人不幸有一尊雅典娜像,但从不敢在黑夜里看它一眼。
她认为,《乌鸦》的韵律给布朗宁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坡顿时成了美国文坛的领军人物。
1845年,坡经常以文学界名流的身份出现在上层沙龙。
[1]坡自己认为《乌鸦》是他的得意之作,声称“我写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章”[1]那么,这首诗为何如此深受读者青睐?笔者认为,这首诗除了其优美的旋律和哥特式氛围外,其成功之处还在于诗人有效地运用戏剧性的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了忧伤、痛苦、绝望这些人类永恒的情感,并以此创造忧郁美和确立忧郁美的价值。
在诗歌美的创造方面,坡除了追求优美的诗歌形式和美妙的歌声笛音,还创造性地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将忧郁之美列入诗歌美的范围。
爱伦·坡的《乌鸦》体现的超凡之美论文爱伦·坡的《乌鸦》体现的超凡之美论文摘要:《乌鸦》是美国诗人、文论家埃德加?爱伦?坡的代表诗作。
《乌鸦》以优美的形式、韵律极强的音乐感来表现该诗的主题“美妇人之死”。
主题、形式和语言的选择反映了诗人的创作哲学,而该诗的成功实践也证实了其相关理论。
关键词:爱伦·坡;乌鸦;主题;形式;音乐性埃德加·爱伦·坡被认为是唯美主义的先驱,他与惠特曼、狄更森一起被称为19世纪美国最有创造力的三位诗人。
爱伦·坡的“为诗而诗”的观点决定了他诗歌作品的唯美主义倾向,他的诗歌作品形式精美,音韵优美。
爱伦·坡在《诗歌原理》中写道:“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长诗,‘长诗’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
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能够激动人心,使灵魂升华。
而人们激动的短暂乃是心理的必然。
”因此要创作出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富于美感的诗,根据他的说法,长度在一百行上下的诗歌最为理想。
爱伦·坡在他的着作《创作哲学》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美女之死”这一主题。
他在文中指出:“美是诗的唯一正统的领域”,同时“忧郁是所有诗的情调中最正宗的”,而“死亡”则是所有忧郁的题材中“最为忧郁的”,因此“当死亡与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最具诗意。
爱伦·坡由此得出结论“美妇人之死无疑地是最富有诗意的主题——而这主题如由悼念亡者的恋人口中说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乌鸦》就是以这一主题为基调的。
《乌鸦》是爱伦·坡的代表诗作,坡关于诗歌主张的主题之美、形式之美、音乐之美在这首诗里得以充分体现。
坡在《创作哲学》一文中分析了该诗的创作过程,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乌鸦这个不详之鸟来寄托。
最大限度的悲痛与绝望”,这首诗要表现的就是坡最热衷的主题即由“死亡”所带来的“忧郁美”,即主题之美。
《乌鸦》一诗的形式别具一格。
收稿日期:2012-11-18作者简介:王涛,女,1980年生,四川南充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四川省外国语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埃德加·爱伦·坡报刊叙事体创作的文化样本意义”(编号:SCWY12-05)。
爱伦·坡名诗《乌鸦》的早期译介与新文学建设王涛(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21)摘要:爱伦·坡的名诗《乌鸦》在我国的早期译介过程中,受到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与文学构建的影响,在我国新文学发展脉络中具有隐含性的前奏意义。
《乌鸦》刚译介到我国,就引起了以《创造周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为中心的翻译大讨论,从《学衡》、《沉钟》、《真美善》推出的重译和茅盾的“拟写”这些翻译现象中,反映出我国早期知识分子于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困惑中不同的文化选择以及在不同的文学立场上建构新文学的努力。
关键词:爱伦·坡《乌鸦》新文学建设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1-118-07爱伦·坡的名诗《乌鸦》刚刚译介到我国,就以其哀婉动人的诗风引起了当时文坛上一些社团的注意,并很快展开了对《乌鸦》一诗的翻译讨论,以及后续的不断重译,甚至还出现了对其进行拟写的文学现象。
这反映了深层次的含义,从他们的译介立场以及译介策略上,可以从中一窥我国早期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困惑中产生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以及在不同的文学立场上建构新文学的努力。
这在我国新文学发展脉络中具有隐含性的前奏意义。
一、前奏:有关《乌鸦》的翻译讨论1922年,玄珠(茅盾)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谈译诗的文章《翻译问题:译诗的一些意见》。
在这篇短文中,茅盾谈了一些诗歌翻译的问题,其中提到亚伦坡(Edgar Allan poe )的杰作“乌鸦”。
他充分认识到了爱伦·坡诗歌中的音韵美,赞其为一首极好的诗,但是又认为该诗难以翻译,并举了其中两节做例子,说“直译反而使他一无是处”。
[1]这应该是国人对爱伦·坡《乌鸦》一诗最早的译介和评价。
时隔不久,《文学周报》百期纪念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就刊出了子岩翻译的爱伦·坡的《乌鸦》,这有可能是在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译文。
但是该诗的翻译,出现了很多错误,质量不高,很快引起了张伯符等人的批评。
1924年《创造周报》分别于36卷、37卷两期刊登了张伯符针对子岩的《乌鸦》译诗而写的《〈乌鸦〉译诗的刍言(批评)》,从文后附有的写作时间“写于1923年12月26日”来看,这应当是对子岩译诗做出的最迅捷的批评反应之一。
在卷36中,张伯符认为爱伦·坡是“‘The only American Poet of Significance ’,在近代西洋文学史上,很替不文的美国吐了不少气焰”。
[2](P10)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学者对美国文学的认识和接受状况,其对爱伦·坡诗歌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在第37卷中,张伯符在指出子岩错误的基础上对《乌鸦》一诗进行了重译,并在行文即将结束时,声称“最后我还有一个声明,就是我的试译,不过是在解意,并不在译‘诗’,因此,如有人说我的试译没有现出原文的Rhythm 时,我甘受其责,但是意义上我自信还没有笑话。
”[2]在张伯符看来,对诗歌的译介中最重要的是准确,他对子岩译诗的批评也主要在于纠错上,因此冒着“直译反而使他一无是处”的风险进行试译,自己也坦言试译只8112013年3月第1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r.,2013No.1求达意不出错,而不在于对诗歌韵律的展现上。
随后,1924年,《创造周报》卷45刊登了《乌鸦译诗的讨论(通信二则)》,其中有露明女士(即赵景深)①《关于艾伦·坡〈乌鸦>一诗的翻译》的来信以及郭沫若的答复。
赵景深在这封来信中对张伯符的译诗做了分析,一是指出“Nevermore”在诗中翻译的前后不一致。
同时将张伯符译文中的“再没有了”、“再也不会”“再也不”和子岩的“永不”做比较并认为“我以为要该作‘再也不’的缘故,便在于音调上较好,而不在于意思的悬殊。
”[3]二是提出将lord译作“传说”。
郭沫若就赵景深的来信做了有针对性的答复,其一是“‘Lord’一字呢说的很有至理,张君是过于拘滞了一点;假使由我移译时,我想把那一句译成‘奇古的书史’,还他一个浑涵的情味。
”二是,“Nevermore一语张君只求达意,所以译文随意而异。
假使要兼顾到音调上时,我想于你所提出的‘再也不’之外有些地方应该译作‘再也没’。
这样对于原意可以保存,又因不没音近,原语的面目也还能兼顾。
”[3]二者的通信,还是集中在译文意思的准确性,以及诗歌音韵的翻译上。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乌鸦》一诗本来以优美著称,早期对爱伦·坡《乌鸦》一诗的认识上,在承认爱伦·坡诗歌的优美动人以及他在诗歌创作的地位上还是达成了共识。
《乌鸦》以其高度的审美共鸣深得人们喜爱,但是又正因为其形式优美,用韵讲究,在翻译上很难做到准确达意,这给诗歌的翻译带来了难度和困惑。
这场讨论表面上看是在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的中心围绕着“能不能译”以及“怎么译”的话题展开,关注的是诗歌翻译上的直译和意译,以及在直译中以“意思”为主,还是以“音韵”为主等诗歌翻译形式上的问题。
但是参与论争者却在对这首诗歌的接受中表现出了他们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以这场论争中主张“不译”的主将郭沫若为例。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也颇为爱伦·坡诗歌的哀婉动人所吸引,但是,他们更倾心于诗歌中的澎湃热情,不主张对韵律过度讲究。
郭沫若在论文《由诗的韵律说到其他》中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更从积极的方面而言,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认为不是韵文方面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情绪底自然消张”,“诗是纯粹的内在律底表示,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
”[4](P281-P283)可见,郭沫若是要脱了镣铐跳舞的人,尽管他也深为爱伦·坡诗歌的抒情风格所吸引,但是又对其诗歌过于讲究韵律的古典诗歌之风,深表不满,他在答复赵景深的信中最后说道:末了我想写一点我自己对于“Raven”一诗的意见。
这首诗虽是很博得一般的赞美,但是,我总觉得他是过于做作了。
他的结构把我们中国的文学来比较时,很有点像把欧阳永叔的“秋声赋”和贾长沙的“鵩鸟赋”来溶冶于一炉的样子;但我读诗,总觉得没有“秋声赋”的自然,没有“鵩鸟赋”的质朴。
“Nevermore”一字重复得太多,诗情总觉得散漫了。
[3](P16)在对《乌鸦》一诗的理解中,他很自然地将之和中国古典诗歌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不如它们。
既然这样,自然也不为郭沫若所接受和大力提倡。
这是我国早期新文学发展中追求诗歌内在韵律的一种诗学主张的彰显。
二、《乌鸦》一诗的“重译”在这场争论之后,《乌鸦》一诗吸引了更多的社团和流派的注意,国人陆续推出了对《乌鸦》一诗的重译。
1924年9月,《学衡》杂志第45期上又发表了顾谦吾的骚体译文《鵩鸟吟》。
1927年《沉钟》特刊上又发表了杨晦的译文《乌鸦》;1929年《真美善》第3期上也刊载了黄龙的译文《乌鸦》。
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分别代表了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三个①露明女士即为赵景深。
赵景深在回忆郭沫若的文章中有自证身份“读者诸君倘若不会忘记《创造周报》。
当可记得第四十五期上有露明女士与沫若的《乌鸦译诗的讨论》。
所谓露明女士。
就是我的化名。
我的字很像女人写的。
我的信上说,看到张伯符(即后来在中华书局译文学书的张梦麟。
也就是商务出《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忆秋生的爱伦·坡《乌鸦》译诗的讨论,也想插几句嘴。
但我的英文不行。
请郭先生不要见笑。
信上只写寄自长沙,不曾写地名.沫若信以为真。
便覆信给我,连我的信一同刊出;其中说起张先生人很好,还要替我介绍,要我把通讯处告诉他,也许是想替报做媒呢!昔年狡狯。
至今想起来都是好笑的。
(参见:赵景深,《文人印象》,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4月初版,第203页。
)911流派,即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以翻译与创作并重,艺术旨趣上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文学社团“沉钟社”,以及聚集在曾朴、曾虚白父子所创办的《真善美》杂志下,推崇欧美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文学团体”。
正是通过对他们的翻译立场以及翻译策略的比较,我们可以甄别出面对外来文明,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时期,早期知识分子身上所凝聚的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困惑,不同的文化认同感以及自身对文明构建的努力。
(一)翻译立场:“推新”与“承旧”沉钟社成员杨晦的译文《乌鸦》是在他所在的沉钟社推出爱伦·坡与霍夫曼的作品专辑《沈钟》(特刊)上发表的。
冯至回忆《沉钟》杂志的酝酿和编辑活动时提到:“《沉钟》的四个编辑者思想不尽相同,性格更为悬殊,写作的风格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看法,即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他们把艺术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现实则与文艺为敌,处处给文艺艺术布置障碍”。
[5](P75)这是对这样一群致力于“艺术”创造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
他们热心于文学的“美”,热忱地追求“艺术”。
加之,他们都是学外语出身,异域文学中“美”的文学是他们创作和研究中的主要关注对象。
爱伦·坡以其怀才不遇的“诗人形象”,独特的艺术风格,很快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而1929年刊载了黄龙译文《乌鸦》的《真美善》,是由在上海开办真美善书店的曾朴、曾虚白父子所创办。
该杂志开始为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季刊,一直坚持到1931年7月终刊,前后共出47期。
它所集合的撰稿人主要有曾氏父子,后来加入的有徐蔚南、张若谷、邵洵美、夏莱蒂、叶鼎洛等推崇欧美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文人。
他们所译介的外国文学主要以欧美唯美———颓废主义文学为主。
被誉为是三大“唯美主义”诗人之一的美国作家濮爱伦(即爱伦·坡),自然也在其介绍之列。
就在1929年第3期《真美善》黄龙译诗后还有编者加的小注。
说是1929年5月18日,黄龙“脱稿于cafe renaissance Poe的这篇Raven,本是千古的绝唱,神韵音节决没有那支妙笔可以把他用别国文字表达出来的。
”[6](P19)可以看出其对ca-fe renaissance地点的强调中所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
可见,无论是沉钟社还是聚集在《真善美》杂志下的文人团体,吸引他们的是爱伦·坡诗歌的哀婉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