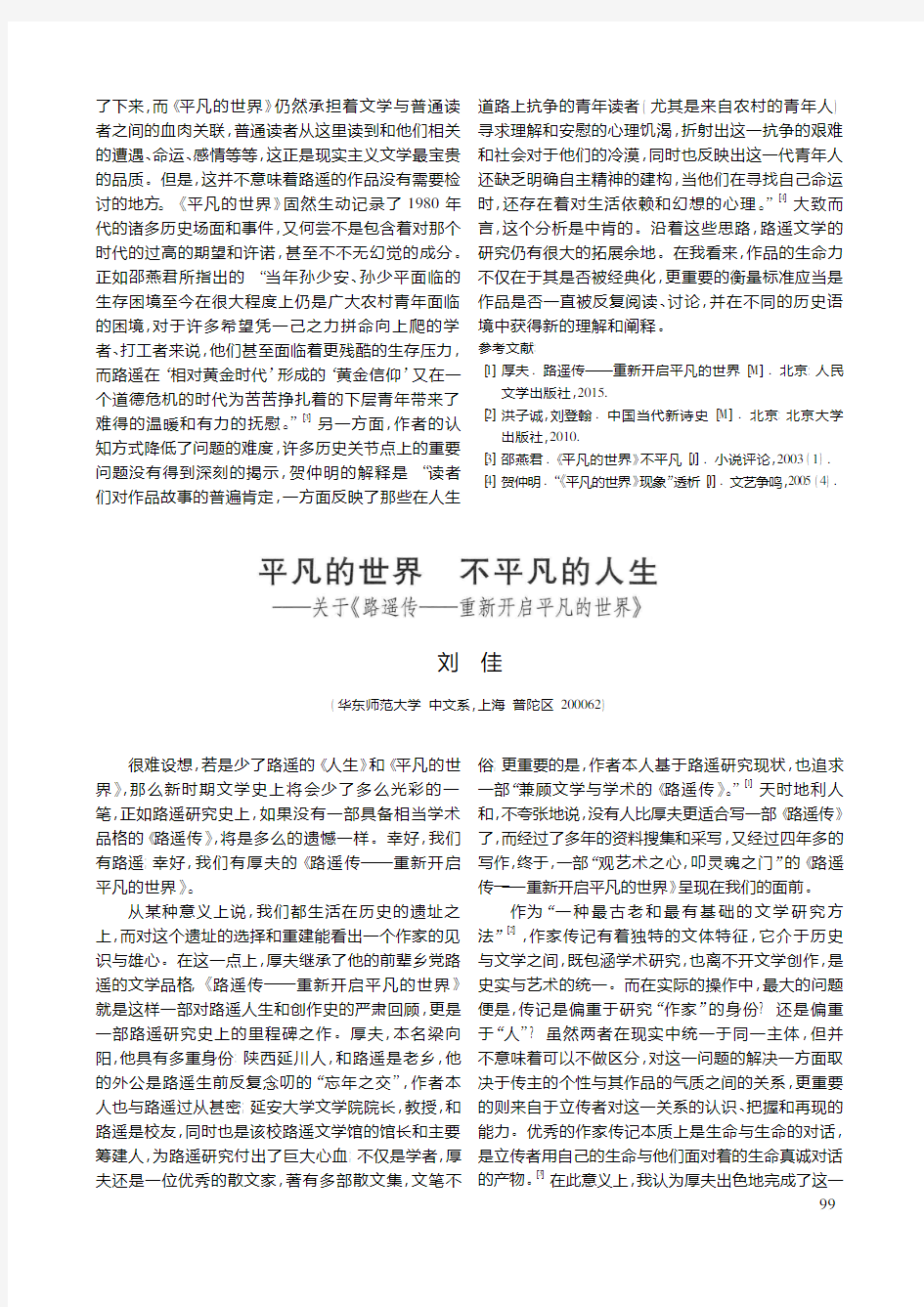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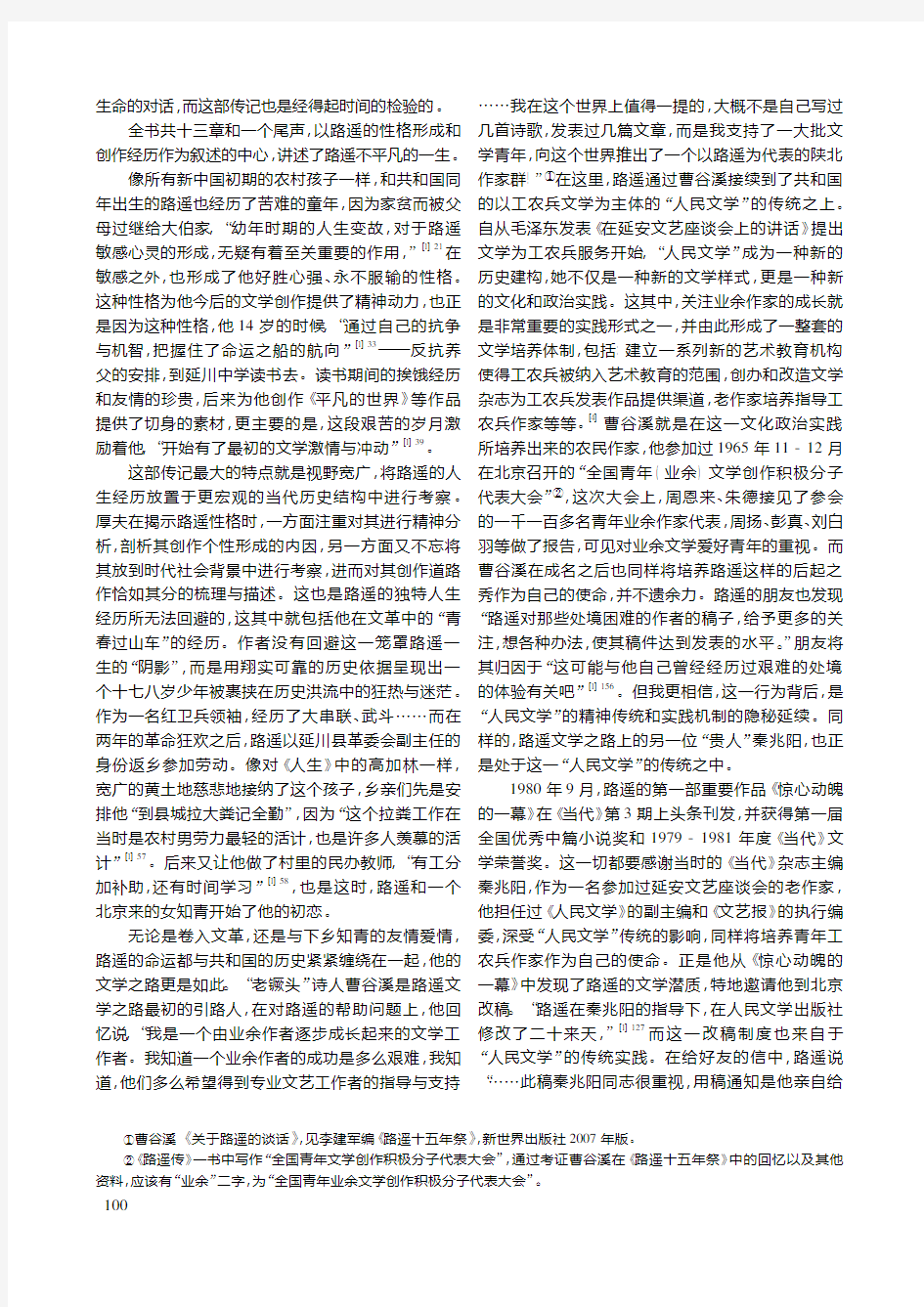
了下来,而《平凡的世界》仍然承担着文学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血肉关联,普通读者从这里读到和他们相关的遭遇、命运、感情等等,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宝贵的品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路遥的作品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平凡的世界》固然生动记录了1980年代的诸多历史场面和事件,又何尝不是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的过高的期望和许诺,甚至不不无幻觉的成分。正如邵燕君所指出的:“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3]另一方面,作者的认知方式降低了问题的难度,许多历史关节点上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贺仲明的解释是:“读者们对作品故事的普遍肯定,一方面反映了那些在人生道路上抗争的青年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寻求理解和安慰的心理饥渴,折射出这一抗争的艰难和社会对于他们的冷漠,同时也反映出这一代青年人还缺乏明确自主精神的建构,当他们在寻找自己命运时,还存在着对生活依赖和幻想的心理。”[4]大致而言,这个分析是中肯的。沿着这些思路,路遥文学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在我看来,作品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是否被经典化,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作品是否一直被反复阅读、讨论,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
参考文献:
[1]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J].小说评论,2003(1).[4]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J].文艺争鸣,2005(4).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关于《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刘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普陀区200062)
很难设想,若是少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那么新时期文学史上将会少了多么光彩的一笔,正如路遥研究史上,如果没有一部具备相当学术品格的《路遥传》,将是多么的遗憾一样。幸好,我们有路遥;幸好,我们有厚夫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遗址之上,而对这个遗址的选择和重建能看出一个作家的见识与雄心。在这一点上,厚夫继承了他的前辈乡党路遥的文学品格,《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就是这样一部对路遥人生和创作史的严肃回顾,更是一部路遥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厚夫,本名梁向阳,他具有多重身份:陕西延川人,和路遥是老乡,他的外公是路遥生前反复念叨的“忘年之交”,作者本人也与路遥过从甚密;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和路遥是校友,同时也是该校路遥文学馆的馆长和主要筹建人,为路遥研究付出了巨大心血;不仅是学者,厚夫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著有多部散文集,文笔不俗;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基于路遥研究现状,也追求一部“兼顾文学与学术的《路遥传》。”[1]天时地利人和,不夸张地说,没有人比厚夫更适合写一部《路遥传》了,而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和采写,又经过四年多的写作,终于,一部“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为“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作家传记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它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既包涵学术研究,也离不开文学创作,是史实与艺术的统一。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最大的问题便是,传记是偏重于研究“作家”的身份?还是偏重于“人”?虽然两者在现实中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做区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取决于传主的个性与其作品的气质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则来自于立传者对这一关系的认识、把握和再现的能力。优秀的作家传记本质上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是立传者用自己的生命与他们面对着的生命真诚对话的产物。[3]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厚夫出色地完成了这一
99
生命的对话,而这部传记也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全书共十三章和一个尾声,以路遥的性格形成和创作经历作为叙述的中心,讲述了路遥不平凡的一生。
像所有新中国初期的农村孩子一样,和共和国同年出生的路遥也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因为家贫而被父母过继给大伯家,“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1在敏感之外,也形成了他好胜心强、永不服输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14岁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抗争与机智,把握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1]33———反抗养父的安排,到延川中学读书去。读书期间的挨饿经历和友情的珍贵,后来为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提供了切身的素材,更主要的是,这段艰苦的岁月激励着他,“开始有了最初的文学激情与冲动”[1]39。
这部传记最大的特点就是视野宽广,将路遥的人生经历放置于更宏观的当代历史结构中进行考察。厚夫在揭示路遥性格时,一方面注重对其进行精神分析,剖析其创作个性形成的内因,另一方面又不忘将其放到时代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进而对其创作道路作恰如其分的梳理与描述。这也是路遥的独特人生经历所无法回避的,这其中就包括他在文革中的“青春过山车”的经历。作者没有回避这一笼罩路遥一生的“阴影”,而是用翔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呈现出一个十七八岁少年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狂热与迷茫。作为一名红卫兵领袖,经历了大串联、武斗……而在两年的革命狂欢之后,路遥以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返乡参加劳动。像对《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宽广的黄土地慈悲地接纳了这个孩子,乡亲们先是安排他“到县城拉大粪记全勤”,因为“这个拉粪工作在当时是农村男劳力最轻的活计,也是许多人羡慕的活计”[1]57。后来又让他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有工分加补助,还有时间学习”[1]58,也是这时,路遥和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开始了他的初恋。
无论是卷入文革,还是与下乡知青的友情爱情,路遥的命运都与共和国的历史紧紧缠绕在一起,他的文学之路更是如此。“老镢头”诗人曹谷溪是路遥文学之路最初的引路人,在对路遥的帮助问题上,他回忆说,“我是一个由业余作者逐步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我知道一个业余作者的成功是多么艰难,我知道,他们多么希望得到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与支持……我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一提的,大概不是自己写过几首诗歌,发表过几篇文章,而是我支持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向这个世界推出了一个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群!”①在这里,路遥通过曹谷溪接续到了共和国的以工农兵文学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传统之上。自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开始,“人民文学”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建构,她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更是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这其中,关注业余作家的成长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形式之一,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学培养体制,包括:建立一系列新的艺术教育机构使得工农兵被纳入艺术教育的范围,创办和改造文学杂志为工农兵发表作品提供渠道,老作家培养指导工农兵作家等等。[4]曹谷溪就是在这一文化政治实践所培养出来的农民作家,他参加过1965年11-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②,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朱德接见了参会的一千一百多名青年业余作家代表,周扬、彭真、刘白羽等做了报告,可见对业余文学爱好青年的重视。而曹谷溪在成名之后也同样将培养路遥这样的后起之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不遗余力。路遥的朋友也发现“路遥对那些处境困难的作者的稿子,给予更多的关注,想各种办法,使其稿件达到发表的水平。”朋友将其归因于“这可能与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艰难的处境的体验有关吧”[1]156。但我更相信,这一行为背后,是“人民文学”的精神传统和实践机制的隐秘延续。同样的,路遥文学之路上的另一位“贵人”秦兆阳,也正是处于这一“人民文学”的传统之中。
1980年9月,路遥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第3期上头条刊发,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这一切都要感谢当时的《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作为一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他担任过《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和《文艺报》的执行编委,深受“人民文学”传统的影响,同样将培养青年工农兵作家作为自己的使命。正是他从《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发现了路遥的文学潜质,特地邀请他到北京改稿。“路遥在秦兆阳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二十来天,”[1]127而这一改稿制度也来自于“人民文学”的传统实践。在给好友的信中,路遥说“……此稿秦兆阳同志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
001①
②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路遥传》一书中写作“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通过考证曹谷溪在《路遥十五年祭》中的回忆以及其他
资料,应该有“业余”二字,为“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我,给了许多鼓励……”[1]127而后,秦兆阳亲自为小说题写标题,并于1982年3月25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由此,路遥才真正成为全国知名作家。路遥是这样评价秦兆阳的,“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1]128
只有认识到了路遥文学的这一隐秘传统,才能真切地感受和理解路遥对于他的精神“教父”柳青的崇敬之情来自何处。“人民文学”的传统哺育了路遥的文学,而路遥也像柳青那样,用自己的创作回报了生养他的黄土地上的人民。《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就是他交给父老乡亲的最好答卷。
本雅明说过,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路遥的文学之路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路遥从自身经历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被三弟王天乐的命运所触动,因此,中国广大农民的出路问题才成为他深入思考和创作的动力。《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均把主人公置于‘城乡交叉地带’,而着力表现他们作为奋斗者的命运,其现实的逻辑起点应该源于他帮弟弟改变命运的过程。”[1]134“可以说,路遥正是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命运的关注,由此下决心创作这种题材的小说”[1]135,在这个意义上,路遥的创作是一种人与文的互文,他的个人精神和经历的深刻性、丰富性与他笔下“平凡的世界”的复杂性建构起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和阐释空间,他和他笔下的文学世界一起构成了一个无比庞杂的互文性文本。而这种互文并非是一种自恋式的的自述传,而是来自于对生活在这一片黄土地之上的青年和人民的深爱,这深刻地体现了人民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因为这一传统,路遥的创作才能超越生命的界限,长久以来被广大人民所喜爱。今天对路遥文学的解读,如果缺少这一维度而单纯陷入一种个人奋斗式的励志型读法的话,那么对于路遥的创作初衷来说,不得不说是让人失望的,因此,厚夫对于这一隐秘传统的挖掘和呈现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路遥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路遥的创作不仅在起源上得益于“人民文学”的传统,同时,在创作的气质风格上也内在地延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写作《人生》时,“他说现代流行的小说写的人都不是人,他要按生活的蓝本来写,如果发出去要他改,他将坚决不改,哪怕不发也不改。”[1]144《文艺报》的阎纲也高度评价《人生》“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劳而无用。”[1]158尤其是在文学上的“85新潮”之后,各种西方现代主义的写法大量涌入,被作家和评论家们所接受和拥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被普遍视为僵化落后的,但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1]295,并用现实主义手法和精神完成了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最初是作为《人生》的下部来构思的,但很快路遥就重新确立了小说框架: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分别是《黄土》、《黑金》、《大城市》,总名是《走向大世界》,小说选取“1975年到到1980年代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进行描绘,路遥立志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像巴尔扎克那样做一个中国历史的“书记官”。创作的过程是艰辛的,路遥“为了彻底弄清楚这十年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便在小说创作中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合订本。”“工作量太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1]183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此同时,路遥也并不排斥其他样式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反复重读了《创业史》和《红楼梦》的同时,他还反复阅读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1]182
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终于在1986年11月由《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并在当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但其实这一部的出版过程是一波三折的,在首先遭到《当代》杂志的婉拒后,“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了三分之一后就干脆直接退给路遥,说这本书不行,不适应时代潮流,属于老一套’恋土派’。”[1]209路遥认识到,文坛风向出了问题,深沉的现实主义风格创作被忽视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着现实主义:“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个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
101
么……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1]210始终坚持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写作;始终牢记自己是黄土地的孩子,人民的儿子;始终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形式为他笔下的生活和人物赋形。这些坚持使得他自然地与那些脱离人民、脱离土地,纯粹追求形式上的自律的“学者专家们”分道扬镳,与文坛上对“纯文学”的孜孜以求拉开了距离,在1980年代文学浪潮中,路遥似乎成了一个僵化的老古董,一个异质的存在。
尽管评论界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评价不高,而且第二部在正式出版前没有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但路遥期待的读者———广大的普通劳动人民———却给了路遥最公正的评价。1988年3月27日,由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正式播送!也正是在倾听自己作品的过程中,5月25日,路遥完成了第三部的写作。“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1]271人民听众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路遥的艰辛和责任感,从3月底开播到6月初,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演播室就已经收到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而在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平凡的世界》也印刷了几十万册!最终,广大读者的热情肯定改变了《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将路遥抬入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茅盾文学奖!路遥将自己的文学献给了黄土地上的人民,就像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而人民也用自己的肯定回报了路遥的这一份“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和责任!
在对路遥短暂的一生所进行的梳理中,尽管作者与路遥之间有着亲密而复杂的关系,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做传者,厚夫并没有因为“立传”而为路遥“树碑”,作者始终没有因为个人感情而为尊者讳,失去一个做传者的客观、一个学者的学术责任感,这也是这部传记的学术品格的另一处所在。对于路遥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作者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呈现。首先是路遥的家庭婚姻状况,作者并没有对路遥的婚姻妄下断言,而是指出作为农村有志青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路遥“在恋爱与婚姻中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而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因为全身心投入创作而无心照顾家庭,朋友们认为夫妻感情的不和主要责任在路遥。其次,对于路遥因为生活窘迫而为稻粱谋的行为,像谋划过做生意,买过股票,也做过有偿写作之事也并不隐讳,但作者并没有做简单地价值判断,而是在事实基础上给予呈现,传记也不会因此而减损路遥的人格魅力,反而使读者对路遥的人生经历和彼时的文学生态有了更生动的了解。最后,对于路遥的病与死亡,路遥对它们的态度,作者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试图通过各种资料探索路遥的精神世界,认为路遥对自己的病况早就知情,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疗的时机,只能抱憾而去。
路遥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但对于路遥,死亡不过是一次转身走开,因为作家的生命长度是由其作品决定的,路遥深信着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所留下的已经不是他创作的文学作品,而是他自己人生的一部大书!如何阅读路遥这一部“人生”的大书,厚夫的《路遥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
参考文献:
[1]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勒内·韦勒克,等.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71.
[3]董炳月.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J].文学评论,1992(1).
[4]周文.论“十七年”文学体制对工农作家的培养———以陈登科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
[责任编辑王俊虎]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