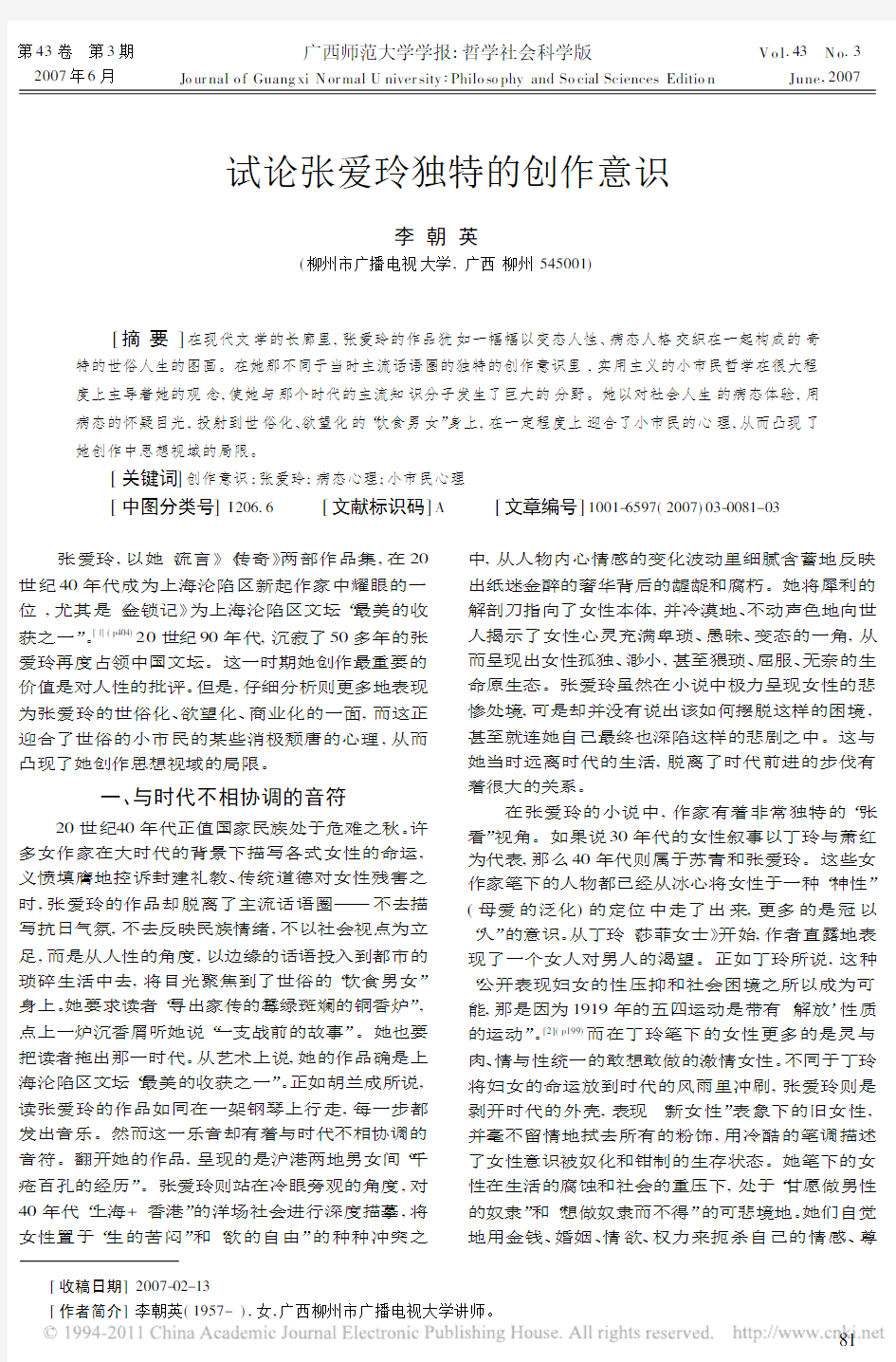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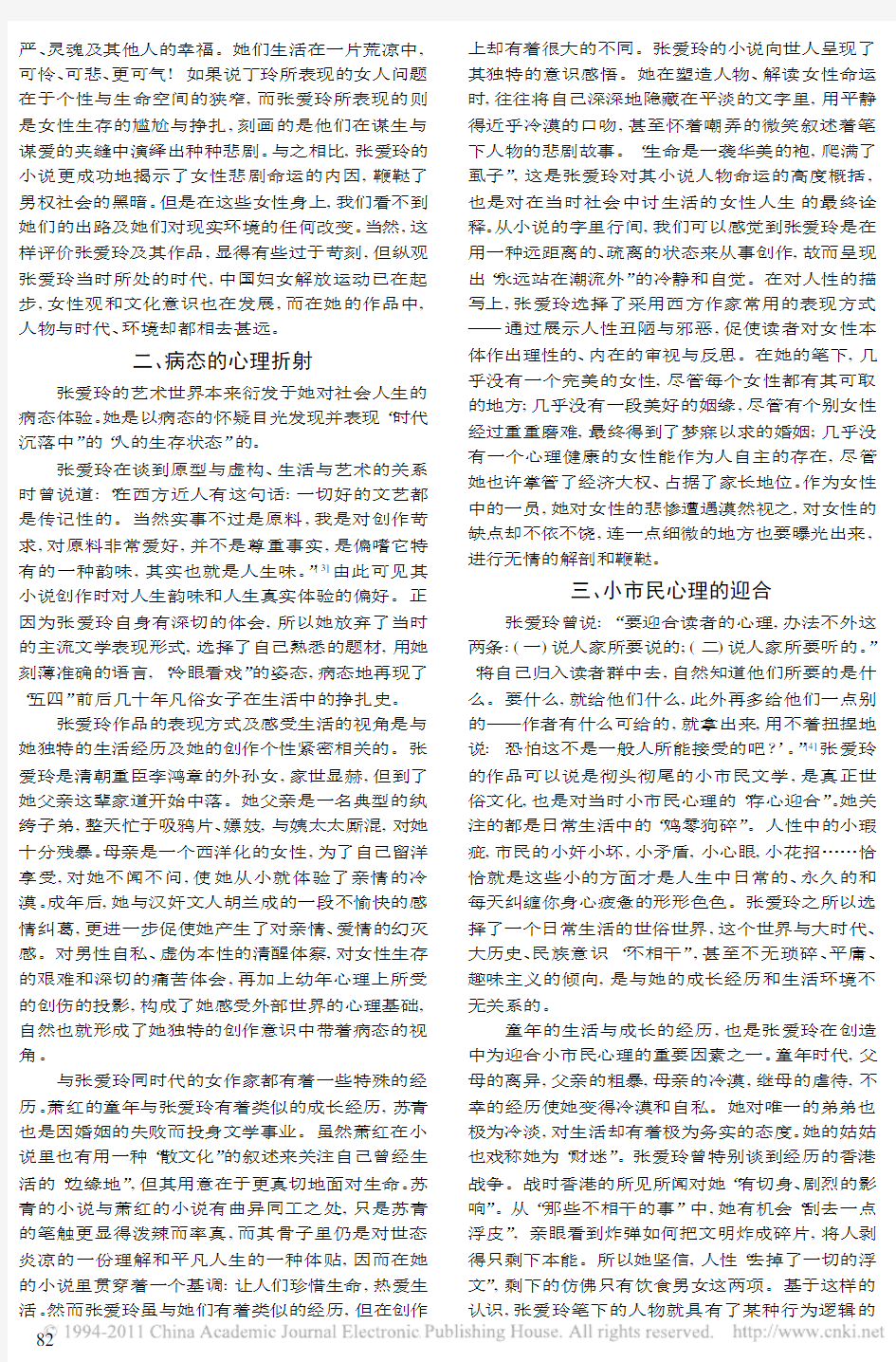
第43卷 第3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 o l .43 N o .3
2007年6月
Jo ur nal o f Guang xi N or mal U niver sity :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 June ,2007
[收稿日期]2007-02-13
[作者简介]李朝英(1957-),女,广西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试论张爱玲独特的创作意识
李 朝 英
(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西柳州545001)
[摘 要]在现代文学的长廊里,张爱玲的作品犹如一幅幅以变态人性、病态人格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奇
特的世俗人生的图画。在她那不同于当时主流话语圈的独特的创作意识里,实用主义的小市民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她的观念,使她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分野。她以对社会人生的病态体验,用病态的怀疑目光,投射到世俗化、欲望化的“饮食男女”身上,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市民的心理,从而凸现了她创作中思想视域的局限。
[关键词]创作意识;张爱玲;病态心理;小市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7)03-0081-03
张爱玲,以她《流言》《传奇》两部作品集,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耀眼的一位,尤其是《金锁记》为上海沦陷区文坛“最美的收
获之一”。
[1](p404)
20世纪90年代,沉寂了50多年的张爱玲再度占领中国文坛。这一时期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人性的批评。但是,仔细分析则更多地表现为张爱玲的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而这正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从而凸现了她创作思想视域的局限。
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音符
20世纪40年代正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秋。许多女作家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描写各式女性的命运,义愤填膺地控诉封建礼教、传统道德对女性残害之时,张爱玲的作品却脱离了主流话语圈——不去描写抗日气氛,不去反映民族情绪,不以社会视点为立足,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以边缘的话语投入到都市的琐碎生活中去,将目光聚焦到了世俗的“饮食男女”身上。她要求读者“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她说“一支战前的故事”。她也要把读者拖出那一时代。从艺术上说,她的作品确是上海沦陷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正如胡兰成所说,读张爱玲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然而这一乐音却有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音符。翻开她的作品,呈现的是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张爱玲则站在冷眼旁观的角度,对40年代“上海+香港”的洋场社会进行深度描摹,将女性置于“生的苦闷”和“欲的自由”的种种冲突之
中,从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波动里细腻含蓄地反映出纸迷金醉的奢华背后的龌龊和腐朽。她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了女性本体,并冷漠地、不动声色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心灵充满卑琐、愚昧、变态的一角,从而呈现出女性孤独、渺小,甚至猥琐、屈服、无奈的生命原生态。张爱玲虽然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女性的悲惨处境,可是却并没有说出该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甚至就连她自己最终也深陷这样的悲剧之中。这与她当时远离时代的生活,脱离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家有着非常独特的“张看”视角。如果说30年代的女性叙事以丁玲与萧红
为代表,那么40年代则属于苏青和张爱玲。这些女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已经从冰心将女性于一种“神性”(母爱的泛化)的定位中走了出来,更多的是冠以“人”的意识。从丁玲《莎菲女士》开始,作者直露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渴望。正如丁玲所说,这种“公开表现妇女的性压抑和社会困境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带有‘解放’性质
的运动”。
[2](p199)
而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灵与肉、情与性统一的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不同于丁玲将妇女的命运放到时代的风雨里冲刷,张爱玲则是剥开时代的外壳,表现“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并毫不留情地拭去所有的粉饰,用冷酷的笔调描述了女性意识被奴化和钳制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在生活的腐蚀和社会的重压下,处于“甘愿做男性的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可悲境地。她们自觉地用金钱、婚姻、情欲、权力来扼杀自己的情感、尊
81
严、灵魂及其他人的幸福。她们生活在一片荒凉中,可怜、可悲、更可气!如果说丁玲所表现的女人问题在于个性与生命空间的狭窄,而张爱玲所表现的则是女性生存的尴尬与挣扎,刻画的是他们在谋生与谋爱的夹缝中演绎出种种悲剧。与之相比,张爱玲的小说更成功地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鞭鞑了男权社会的黑暗。但是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不到她们的出路及她们对现实环境的任何改变。当然,这样评价张爱玲及其作品,显得有些过于苛刻,但纵观张爱玲当时所处的时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在起步,女性观和文化意识也在发展,而在她的作品中,人物与时代、环境却都相去甚远。
二、病态的心理折射
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对社会人生的病态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
张爱玲在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道:“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3]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时对人生韵味和人生真实体验的偏好。正因为张爱玲自身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她放弃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表现形式,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冷眼看戏”的姿态,病态地再现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凡俗女子在生活中的挣扎史。
张爱玲作品的表现方式及感受生活的视角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她的创作个性紧密相关的。张爱玲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家世显赫,但到了她父亲这辈家道开始中落。她父亲是一名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忙于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厮混,对她十分残暴。母亲是一个西洋化的女性,为了自己留洋享受,对她不闻不问,使她从小就体验了亲情的冷漠。成年后,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纠葛,更进一步促使她产生了对亲情、爱情的幻灭感。对男性自私、虚伪本性的清醒体察,对女性生存的艰难和深切的痛苦体会,再加上幼年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的投影,构成了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自然也就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意识中带着病态的视角。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萧红的童年与张爱玲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苏青也是因婚姻的失败而投身文学事业。虽然萧红在小说里也有用一种“散文化”的叙述来关注自己曾经生活的“边缘地”,但其用意在于更真切地面对生命。苏青的小说与萧红的小说有曲异同工之处,只是苏青的笔触更显得泼辣而率真,而其骨子里仍是对世态炎凉的一份理解和平凡人生的一种体贴,因而在她的小说里贯穿着一个基调:让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然而张爱玲虽与她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但在创作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向世人呈现了其独特的意识感悟。她在塑造人物、解读女性命运时,往往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平淡的文字里,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甚至怀着嘲弄的微笑叙述着笔下人物的悲剧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在当时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人生的最终诠释。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张爱玲是在用一种远距离的、疏离的状态来从事创作,故而呈现出“永远站在潮流外”的冷静和自觉。在对人性的描写上,张爱玲选择了采用西方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丑陋与邪恶,促使读者对女性本体作出理性的、内在的审视与反思。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地位。作为女性中的一员,她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对女性的缺点却不依不饶,连一点细微的地方也要曝光出来,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鞑。
三、小市民心理的迎合
张爱玲曾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4]张爱玲的作品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小市民文学,是真正世俗文化,也是对当时小市民心理的“存心迎合”。她关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人性中的小瑕疵,市民的小奸小坏,小矛盾,小心眼,小花招……恰恰就是这些小的方面才是人生中日常的、永久的和每天纠缠你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张爱玲之所以选择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不相干”,甚至不无琐碎、平庸、趣味主义的倾向,是与她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不无关系的。
童年的生活与成长的经历,也是张爱玲在创造中为迎合小市民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童年时代,父母的离异,父亲的粗暴,母亲的冷漠,继母的虐待,不幸的经历使她变得冷漠和自私。她对唯一的弟弟也极为冷淡,对生活却有着极为务实的态度。她的姑姑也戏称她为“财迷”。张爱玲曾特别谈到经历的香港战争。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剧烈的影响”。从“那些不相干的事”中,她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
82
一致性,大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当“饮食”受到威胁时,甚至“男女”之事都是不屑一顾的。他们或为“利”的,或为“性”的世俗目的,演出着“终日纷呶”的,又是“没有名目的争斗”。
在上海成为“孤岛”之时,作为英、法的租界地,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大都会,同时也形成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以饮食男女、市民生活为其生存土壤的作品,无疑是这一都市的产物。作为新文学中心,上海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冲击和主流文化的南移而从根本上改变这座商业大都会市民文化继续发展的自身逻辑而世俗化、实利化,其主体只能是那些生存于现代都市的普通市民。上海文化中充分的世俗化和实利化倾向,说到底,是市民心理、市民眼光的体现,是市民出于自身需要所做的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选择。对张爱玲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似乎可以这么说,张爱玲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小市民趣味的女人。她有着小女人的价值标准,十分的率真。她“最讨厌的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得漂亮的男人”。她热衷于眼前的利益,“出名要早”,“趁热打铁”。她有强烈的“成就欲”,即使牺牲某些东西也在所不惜:“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5]她并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常常与杂志编辑为稿费而发生争执。她渴望标新立异,与她同时代的潘柳黛就曾刻薄地嘲讽她善于“表演”。显然,实用主义的小市民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她的观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她在创作上的价值取向。在张爱玲的作品和她的私人生活里,是没有什么忠奸之辩和纲常伦理的。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胡兰成的“欲仙欲死”的爱情,及其背离“国民性”而倾向于金钱人性欲望的作品,喋喋不休的谈食、谈服装、谈性,沉湎于私人生活空间及至晚期写出勉强的政治作品,如《赤地之恋》等全因于此。
张爱玲充满智慧和灵气的文字穿透时间,尤如空谷回音,久久回荡在女性文学历史的长廊中。正是因为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也掺杂了作家本人身世背景所形成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她这个独特的创作个体和创作意识。[6](p34)然而张爱玲的心灵世界也存在局限,那就是她在洞见人生的悲剧性处境之后,不是向更高的精神层面开拓,而是选择了妥协的后退。精神探求上的妥协退让必然导致琐碎情调的泛滥。张爱玲正是在这里折断了自己原本可以继续向上攀升的天才的羽翼的。
[参考文献]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2] 丁玲.丁玲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3]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谈看书[M]∥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1994.
[5]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第4卷[M].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徐岱.创造性批评:解说与解读[J].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O n Zhang A i-ling's U niqu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LI Chao-ying
(L iuzho u R adio and T elevision U niver sity,L iuzhou545001,China)
Abstract:In the gallery o f m odern literat ur e,Z hang Ai-ling's w orks are just like a series of peculiar pictures o f commo n lif e m ade up of abno rmal hum anit y and mo rbid human nat ure.In her creat ive co nsciousness dif ferent fro m t he mainst ream disco urse,t he pet ty t ow nsf olk's philosophy of pragm atism do minat ed her mind t o a g reat ext ent,which draw s a dividing line bet ween the mainst ream int ellect ual s and her.Her abnormal ex perience of social lif e and suspicious and m orbid view are project ed t o t he “comm on men and w o men”w ith their desires,which cast es to t he tast e of t he pett y t ow nsfo lk and sho w s her t hinking limit atio ns in lit er ar y creation.
Key words:creat ive conscio usness;Zhang Ai-ling;m orbid psycholo gy;pet t y to w nsfo lk psycho logy
[责任编辑 王朝元]
83
简析张爱玲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她的作品,与政治无关、与民族无关,是大上海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是人性中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层窗户纸。她的这种写作姿态成为以后小资们竞相效仿的范本,在小资写作中你永远看不到政治、国家那些大命题。她成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她以自己特殊的现代性体验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人生世态。吴福辉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接近上海的真面目,把中国都市文学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这样写道:“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很多的人给予张爱玲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其艺术特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2008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甘肃省电大武威电大分校赵静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尊重。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情爱关系、人性的探索、人生的体验、悲观忧伤的结局,以及悲剧意识根源进行阐述,力指导现实的人少生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1917---1995),河北丰润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的作品的整体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以及清醒的没落感,她笔下的那些女性大多是悲剧性人物。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使她对人生既
张爱玲作品特点 浓郁的悲凉情怀 张爱玲就是个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狱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的悲剧特点表现在她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面。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她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就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她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她们便就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得“靠不住”。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她做人做的十分兴头”,整个地就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她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就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与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就是天真,她与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就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就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她便怯懦得要死,连那她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她轰隆隆地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她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与功利的进攻下,她萎缩了,她不愿“堕落”, 她要做一个“好人”。于就是,她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她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她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她尽情的发泄着她的冷酷、变态。但她仍戴着面具做她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习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就是好就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她”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就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就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她把她的俏皮话省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b6750786.html, 张爱玲小说中的雨意象评析 作者:李佳宁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03期 摘要:张爱玲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在继承雨意象的艺术基础上推陈出新,赋予了雨意象更强的表现力。其笔下的雨意象是凄惨氛围的渲染者、情节发展的推动者、人物形象的塑造者,更是苍凉命运的象征者。探究张爱玲小说的雨意象表征,不仅能够领会其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能够领会其小说的个性风采。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雨意象发展创新 19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张爱玲研究大热,夏志清评价最有代表性:“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254足以见得张爱玲小说的魅力之大。其小说意象成为一道道华美绚烂又含蕴独特的风景,而雨作为张爱玲小说中表达情感的重要意象,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独到之处。在相关中,庄超颖已经发现了雨意象的独特表征,有《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论述》,论著以张爱玲笔下描摹的出神入化的意象为探头,勾勒出张爱玲文学的苍凉与华美,但具体解析还有所缺少。本文选取张爱玲《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三部作品中雨的运用分析张爱玲小说中雨的作用与情感意义。张爱玲小说雨意象运用的溯源主要来自传统文化与个人体验两个部分。雨意象在古代诗歌里凝聚着悲愁凄惶的情感,张爱玲承袭了这一手法,并且进行了发展创新,使其更具艺术张力。 一、渲染凄惨氛围的雨意象 张爱玲说:“用华美绚烂的文辞来表现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是她最主要的文学切入点。”[2]514张爱玲使用意象的艺术感,她的历史感、她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都来自于她的阅历,她把自己经历的和见过的用现成的意象加工出来。张爱玲启蒙十分早,对于《警世通言》《高唐赋》《红楼梦》中“云雨”的悲情手法运用更是信手拈来。在创作路上,雨意象便是她主观意向的选择,诉诸了点点滴滴的悲愁,使作品处处透着一种寒彻心骨的悲凉。 《倾城之恋》中描述白流苏的娘家兄弟姐妹逼她到前夫家去披麻戴孝,这一行为引起了白流苏对小时候一段不好的回忆,看完戏出来之后在大雨里与家人走散的情景:“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3]71人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她撞破了头也挤不进去,她似乎是魇住了。处在这个情景里的白流苏,必定会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凄惨,深深感受到孤苦无依,这个时刻给她留下的刺激是非常深的,所以当她受到娘家人逼迫的时候,才瞬时联想起了这一幕,再次强烈撞击着心灵,她清晰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感到自己的孤苦无助,感到自己处境的可哀。在张爱玲的生活体验中,对雨这一物象的体会十分痛彻,其实这也是张爱玲自身的经历重
推荐文章(书籍梗概)来源:张爱玲经典散文 推荐文章(书籍梗概):《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不是我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云巧”,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心得感悟: 张爱玲天才梦读后感 《天才梦》所讲述的是张爱玲被人们视为天才。她三岁时会背诗,七岁时就写过一篇小说,九岁时就决定了自己以后要当音乐家,毋庸置疑,她是个天才。可是十六岁时,她的母亲研究了一下她,她除了天才素质外一无所有。她没有生活能力,而且不会适应环境。在学习上她是个天才,但在生活中她是个废物。 通过这篇文章让我领悟到,一个人,即使他有一技之长,但如果他连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会,这一个长处也是没有用的。就像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学校里她得到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可当她被母亲研究一番之后,发现她什么都不会,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去医院的路坐车接连走了三个月,可任然不认识那条路。她不会适应环境,像她这样,即使文采飞扬,却只是一个废物。天才不是塑造而成的,专一发展一方面并不是这个社会中所需要的能力。现在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居多,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渴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有一技之长,因此从小就对孩子呵护有加,细微到生活起居,即使孩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一样不放心。爱孩子可以,可是过分的溺爱,不仅不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网上报道有各种各样的事例,各种天才,只因无自理能力而在这个社会中无法生存。 张爱玲从小被视为天才,可当她母亲发现她什么都不会,给她两年时间去学习适应环境时,她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两年的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足以证明只有一技之长天才的她不过是一个废物。一个不会生活,只会学习的人有什么用呢?以后也是出不了大成就的,最终只会丑相败露成为别人的笑料。如果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喜用比喻反讽等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 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作品主题多描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不管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和生活,如《倾城之恋》描写了白流
前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 (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
收稿日期:2006-11-28 作者简介:宋家宏(1956-),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32007第20卷JOURNAL OF HA I N AN NORMAL UN I V ERSI TY General No .89 (总89期) (Social Sciences ) Vo1.20 悲剧意识与世俗人生 ———论张爱玲的散文 宋家宏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论文从张爱玲的开篇之作《天才梦》入手,分析其“张看”与“私语”两类散文的内在特质:以悲剧意识为背景,对世俗人生的珍惜与热爱。无论对往事的回述还是对心灵的审视,都以坦诚的态度书写。是“私语”却超越了自我立场,是“世俗”却又有悲剧的意味。她的都市立场提供了典范的城市文学审美经验,她为长篇幅的文艺大散文的文体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研究;悲剧意识;世俗人生;文体创新 中图分类号:I 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 (2007)-03-0041-05 一 张爱玲的散文在不同的时空,面对不同的接受者,有 不同的遭遇。上个世纪40年代《流言》出版时,远没有《传奇》在普通读者中有号召力,尽管张爱玲在出版《流言》时颇为费心,她自己找出版公司,自备纸张,从校对到跑印刷厂,全都亲历亲为。当然,这也许是她在享受自己的作品变成一本本书的乐趣,但也不能排除她对自己散文的重视。《流言》却没有像《传奇》那样受到评论众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就笔者所见,大陆以外张爱玲的研究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她的小说,论说她的散文的文章远远没有论说小说的多。直到周芬伶的《艳异》才特别推崇张爱玲的散文,列为专章,多有新见。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大陆的张爱玲热,恰逢大陆读书界的散文热,张爱玲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号召力至少不亚于她的小说,《张爱玲散文全编》已于1992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另有一二十种不同版本的散文集出版,且有很好的发行效果。研究界又有不同,尽管余斌在1995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已为她的《流言》列了专章,大陆的研究者相当一段时间也是把她的散文更多地当作理解其人生经历、思想与艺术观念的资料来运用,作为独立的散文艺术来研究的不多。总而言之,张爱玲散文研究相对薄弱。 散文是一种更适合欣赏、把玩的文体,不适合负载太多的论析,当然,90年代后兴盛的“大散文”又当别论。 张爱玲的散文研究者不多,评价却较为一致。早在1944 年《杂志》月刊为《传奇》举办的“茶会”上,涉及到张爱玲散文时就有很高的评价,班公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了的。”谭惟翰认为:“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意装饰,小动作等,把主体盖住,而疏忽了整个结构。读其散文比小说 有味,读随笔比散文更有味。”[1] 后来的张爱玲散文评论文章,虽然不多,评价却高,吴福辉、余凌、谢凌岚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她的散文价值,尤其是周芬伶在《艳异》一书中认为:“她的散文成就不但不亚于小说,在神韵与风格的完整呈现上或有过于小说者,故列为作品论卷首”,认为“张爱玲的文体自成一格,对散文语言及题材的开拓确有新境,她首先是个文体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剧 作家”。[2] 周芬伶要树立张爱玲散文大家的地位。 二 《天才梦》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一篇优秀的散文,把它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也并无不当,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中文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她从七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九岁就向编辑先生进攻,到此时,作家梦她已做了十余年!刚刚发表第一篇中文作品,《天才梦》却又成为她“少作”的终结篇。《天才梦》发表不久,她就入学港大,为了获得能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
张爱玲是一个别致的女子,她用作品写就了一生的传奇,她的故事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让人欲罢不能,无意间的走近而成为永恒的张迷,她的文字雅俗相触,中西合璧,传统意让与现代的技巧相统一,时隔50 年她的作品依旧新鲜,她笔下的人物依然是前精神的,虽然她已远离人世,而她的文字依然在滚滚红尘中徜徉。 1、作品中浓郁的市井气息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小人物的种种俗欲,为了安身立命,而不得为之的命运。贫穷的白流苏,葛薇龙;都不得为之的生计而以婚姻,青春为代价,换取物质的满足。出卖一生,终于成为富有者的梁太太,曹匕巧,在扭曲的灵魂中挣扎。葛薇龙对衣饰的喜爱,白流苏为长期饭票——婚姻的算计。梁太太那唯一的乐趣,曹匕巧死守着用青春换来的金钱。在她笔下那么生动,那么无耐,让我们在摇头叹息之后重又省视自己,自己身上有多少她们的影子,俗拉近了与人物的距离。她们就在我们身边,张爱玲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 2、浓郁的旧小说色彩张爱玲的小说几乎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以“说书人”的身份来讲故事。如《沉香》,第一炉香一开篇就是说书人的口:“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中国旧小说多是单条线索,按时空的先后演变顺序来结构故事。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多市如此,无论穿插多少倒叙,插叙补叙总体线索不变。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金锁记》《十八春》尽管开头使用了倒叙,但文章展开,很自然转为以时空变化为序,以人物性格命运为线的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依次铺开。她的小说有无巧不成书,曲折性,传奇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等传统的旧小说方式。俗增加了耐谈性。俗雅——华美后的苍凉。张爱玲的作品在这俗人俗欲里,又有一丝深层的味道。人物对命运的抗挣与无耐。世态炎凉,让爱思索的读者诅嚼,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28 的离婚女子,她出身在一个没落腐朽的旧式家里,排行老六,20出头,坚决同丈夫离婚,回了娘家,她的钱渐渐被兄嫂花光,又开始冷落嘲讽,劝她改嫁。母亲也袒护兄嫂,为了生计,她向往着与范柳厚的婚姻。一个有钱。放荡,在英伦长大的公子哥。各家太太们都争抢把女儿嫁给他。而他只想流苏当他的情夫在一场场较量中,白流苏被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做了的情妇。而此时香港战争爆发,在这乱世中,两人相互依存,于是结成夫妻。白流苏似乎是赢了,战争而在这场婚姻后面,难掩她心中的荒凉。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 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白流苏与范柳原有多少爱情,婚姻又过的怎样,我们只有想象。有相同境遇的人,大抵也希望有白流苏式的传奇,而背后的苍凉与无耐又有谁知了,这就是张爱玲,就是在圆满后,也不忘告诉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子。” 3、多种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雅与俗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不仅从《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吸取营养,她还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吸取了心理分析,意识流,通感、蒙太奇等技巧方法,在小说中灵活应用。 1、心理分析对揭示人物的潜意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傅雷对于张爱玲小说尤其是《金锁记》中的心理分析给了高度评价:“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兄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她利用暗导,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曹匕巧是一个乡下开麻油店小户人家的女儿,父母早亡,爱钱的兄嫂把她卖给了姜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害骨痨的残废人,她本泼辣风情,有对爱情的向往,但在这个大家庭里。她只能守着残废的丈夫,而她的出身,作派又受人鄙视。当她看到小叔子季泽,她以为她爱上了他,而季泽打定主意不碰加里人,而她示爱被拒绝,张爱玲写到“她睁者眼只沟沟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伧”她的心理感受就通过这蝴蝶标本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了。死去了,只剩下美丽的躯壳。因为美丽,更显苍凉。而她的世界里欲发只有金钱。张爱玲用了“蒙太奇”的手法,概括了七巧的十年,象一只美丽的蝴蝶标本呆做镜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等待来的爱情,只有日渐苍老的容颜。区区百字,读者感受了时光的流逝,感受了七巧的寂寞。“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遥遥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镜子。镜子里发映着的翠竹窗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眼看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1) 一、引言 (2)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及其体现 (2)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2) 1、意象表现 (3) 2、氛围表现 (3) (二)悲剧性的主题内容,人物和结局 (4) 1、爱情的悲剧性 (4) 2、亲情的悲剧性 (6) 三、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9) (一)社会原因 (9) (二)家庭原因 (9) (三)个人情感原因 (10) 注释 (11) 参考文献 (13)
绵延不尽的苍凉—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勇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将敏锐的目光投注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生灵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苍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郁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本文立足于文学研究,从女性的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整体的眼光纵览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全面梳理、剖析和阐释张爱玲小说中所呈现的悲剧意识,追溯张爱玲小说中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冷冷的撕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自私、阴暗、虚伪和孤独。通过独特的艺术技巧,利用意象表现和氛围表现,建构起一种苍凉的艺术格调,再加上主题、人物以及结局悲剧性的叙述和描写,逐步形成她小说的悲剧意识。 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这三个角度简略剖析。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动荡,父母感情的破裂,家族亲人的爱恨情仇,以及自己与胡兰成的感情的破裂,这一切的经历使其在创作上更加倾向悲凉。 本文力图通过这两个大的方面来了解张爱玲,把握其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苍凉悲剧意识小说张爱玲 Not the desolate stretch of Eileen Chang's novels--the tragedy of consciousness Abstract:Eileen Chang is a writer who has a strong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has a brave courage to face the cruel reality and life .Her keen eyes with pain and difficulty tell us the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lives, showing the scenes of life tragedyi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ducing deduc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overciew zhang ai-ling's novel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omb make zhang ai-ling's novels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tragedy, tracing her novels of the causes of
张爱玲经典散文爱 【篇一:张爱玲经典散文爱】 【篇二:张爱玲经典散文爱】 擦肩而过,“就这样就完了”,——这是理解这篇小散文的核心,因 为是瞬间,才成为永恒,永恒地珍惜,永恒地回味。千万人之中的 偶然相遇,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月白的衫子,古典的诗意与浪漫。 尽管张爱玲在小说与散文中有表达的分野,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 从表面上看。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散文更多地表达世俗人生,如此明亮 的诗意,在截取最浪漫的瞬间之时、艺术观是统一的,在张爱玲的 作品中也几乎是惟一的?因此,从这篇小散文中透露出来的美学意 味是“凄美”,而非其他,瞬间成为永恒,永恒的惆怅与忧伤,同一 个作家:“噢,你也在这里吗,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 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但彼此又是互为表里的,散文中的世俗 人生是以悲剧意识作为背景的。分野这是我读大学时间读到过的张 爱玲的很短的一篇文章,也是网上关于张爱玲作品评论最多的一篇, 人在热恋时,但说这小故事似乎没有必要说谎。 张爱玲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与胡热恋的时候。张爱玲一直拒绝 罗漫谛克,但她与胡兰成的这段热恋,又是她一生中短暂的罗漫谛 克时期,几乎是惟一的一次,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 没有再说什么,化为散文的意境,也是误读最多的一篇,同她见过面,千万年之中的巧遇,偶然的相逢,这宿命的温情定格于瞬间。“就这样就完了。”本身已经包含了无尽的惆怅,张爱玲在情感最炽 热的时候,寄托了她此时此刻对爱的理解与感慨、遐思。她的小说 离不开婚姻题材,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 (附作品) 爱 这是真的。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爱·张爱玲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 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凄美而无奈的爱 ——张爱玲散文《爱》赏析 “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述说不尽的主题,张爱玲仅以三百四十余字的袖珍篇幅,看似轻松地淡淡道来。语言洗尽铅华,单纯干净,全然没有她惯有的华丽绚烂。然而,一种不动声色的人生苦难和沧桑已被她轻轻地触及;而一份爱的无奈和哀痛也被她暗暗地激起,让人想想就忍不住要心酸落泪。 文章以四个字起首做一段:“这是真的”,潜台词即:这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这是真的”,读完全文,回味过来,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 接下来叙述一个真的、美的、纯的,同时又是那么虚的、淡的、凄的关于“爱”的故事。春天的晚上,桃树的底下,着月白衫子的十五六岁的少女,正是青春如花,做梦怀春的豆蔻年华,对爱可以有无数的美好憧憬。正当此际,那个对门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对她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 仿佛要发生点什么,却什么也没发生。结果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这样就完了”,张爱玲在此另起一段,六个字里用了两个“就”,就冷酷的葬送了那个春天的桃花盛开的萌芽着爱的情感的晚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花”意象总是与美丽缠绵的爱情相联系。 《诗经》中《桃夭》云:“桃之夭夭,灼(zhuó)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烂漫的春天,艳如桃花的女子,在大家的祝贺中出嫁,这是多么喜气、欢欣的场景。这首“娶艳女以还家”的咏桃诗,给芳龄女子的爱情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归宿。 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出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种惆怅伤怀的情感唤起了大众隐秘的梦想和物是人非的长叹,传达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共同的经验。因此这首“人面桃花”诗,被后来不断地解读出一个个悱恻动人的爱情故事。 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以坚贞丽人的斑斑血迹描画出的一幅桃花扇为道具来演绎人世间的悲
简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程兰兰 [摘要] 张爱玲的一生可谓是一段传奇,而她所写的小说更是一个个风格独特的“传奇”故事。张爱玲的成功,不止在她传奇的一生,也不止在她笔下的“传奇”故事,更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她描写了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心理分析出神入化,同时还能巧妙地运用意象手法,展现给世人的是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Analysis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ZhangAiLing novel ChengLanLan Abstract:ZhangAiLing's life is a legend, and the novel she wrote is a unique style of "legend" story. Zhang AiLing's success, not only in her legendary life, also more than in the "legend" of the author's story, more lies in her unique novel art. She describes a series of women's survival tragedy,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ration, and able to skillfully use image technique, is presented to the world fail in that era, and unique to sad and deep sense of desolation. Keywords: ZhangAiling Novel Artistic Features 一、鲜明夺目的意象 (一)象征女性沉浮的月亮 在《张爱玲传》中,就记载着年轻的张爱玲曾说的:“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都不能克服这种齿咬性的烦恼。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1从这一句便可以看出她对生活对生命的独道见解。小说《金锁记》是以月亮始,以月亮终的,月亮具有非常强的结构作用。不同的环节,对月亮意象的书写也有不同,试看以下几段: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2这是小说的开端,以月亮来写时光流转,并无新意,但将“三十年前的月亮”转到“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洇得“陈旧而迷糊”,这样的意象果然带上了岁月的沧桑感。它已奠定了小说基本的调子:凄凉。 “天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想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3月亮沉下去,而七巧的故事,开始了。但开始也就预示了结局。 “......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等淡淡的圆光。”○4这是七巧的女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探索 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1]P39。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2] P15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2] P16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3]P83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1.家庭经历的影响 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4] P179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