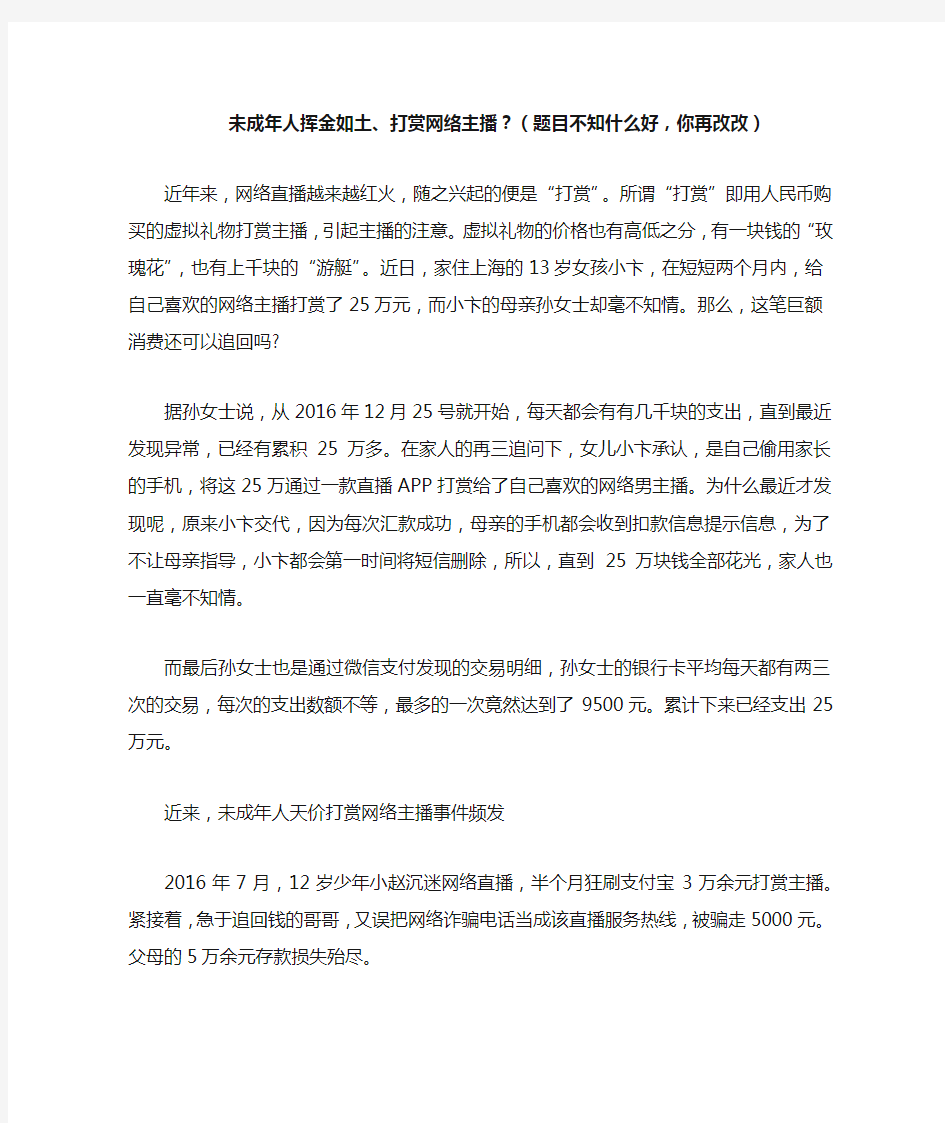

未成年人挥金如土、打赏网络主播?(题目不知
什么好,你再改改)
近年来,网络直播越来越红火,随之兴起的便是“打赏”。所谓“打赏”即用人民币购买的虚拟礼物打赏主播,引起主播的注意。虚拟礼物的价格也有高低之分,有一块钱的“玫瑰花”,也有上千块的“游艇”。近日,家住上海的13岁女孩小卞,在短短两个月内,给自己喜欢的网络主播打赏了25万元,而小卞的母亲孙女士却毫不知情。那么,这笔巨额消费还可以追回吗?
据孙女士说,从2016年12月25号就开始,每天都会有有几千块的支出,直到最近发现异常,已经有累积25万多。在家人的再三追问下,女儿小卞承认,是自己偷用家长的手机,将这25万通过一款直播APP打赏给了自己喜欢的网络男主播。为什么最近才发现呢,原来小卞交代,因为每次汇款成功,母亲的手机都会收到扣款信息提示信息,为了不让母亲指导,小卞都会第一时间将短信删除,所以,直到25万块钱全部花光,家人也一直毫不知情。
而最后孙女士也是通过微信支付发现的交易明细,孙女士的银行卡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的交易,每次的支出数额不等,最多的一次竟然达到了9500元。累计下来已经支出25万元。
近来,未成年人天价打赏网络主播事件频发
2016年7月,12岁少年小赵沉迷网络直播,半个月狂刷支付宝3万余元打赏主播。紧接着,急于追回钱的哥哥,又误把网络诈骗电话当成该直播服务热线,被骗走5000元。父母的5万余元存款损失殆尽。
2016年10月7日至11月27日,浙江丽水14岁男孩小明(化名)打赏5名游戏主播为其代玩玩“酷跑”手机游戏,共计花费3万余元。
一、主播和直播平台是否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基于此类案件,首先,主播和直播平台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进行“打赏行为的未成年人并未产生错误认识,因此也并非是基于错
误认识而处分财产,主播和直播平台取得财产是接受赠与所得,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不构成犯罪。
二、打赏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打赏行为可以被视为是赠与行为,所谓赠与行为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一般要通过签订赠与合同或口头约定等形式来完成。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此类案件中网络主播在线直播,在其直播平台下可以进行打赏,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主播和直播平台向社会的不特定主体发出了要约,而进行打赏行为的人,即接受了要约,与直播平台达成了一个赠与合同。因为赠与是一种合意、双方的法律行为,它需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对网站主播进行打赏即可视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下订立的赠与合同,此为有效合同。
三、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是否有效?
《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知,十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行为能力是受限制的,他们可以进行在其能力范围内的民事活动,比如日常生活中购买小件生活用品、零食、文具等等,但是超出其年龄、智力理解范围的民事活动需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能生效。
虽然现如今的未成年人经常上网,但是他们对于网络规则并不了解,他们仅仅是出于崇拜而将网络主播视为自己的偶像。像文章开篇是笔者提到的小卞的例子,她为了打赏而数次购买“虚拟财产”,而日数额较大,最大的一笔甚至达到9500元,这样数额较大的购买行为完全超出了一个未成年人的认知。小卞作为十三岁的未成年人没有自己的财产,其购买虚拟财产所花费的金钱都是其父母的血汗钱,而且是在其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此类的购买行为均属于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其与网络直播平台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其是否生效需要看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对于该行为是否认可,若其法定代理人不认可该行为,则该效力待定的合同转为无效合同,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向网络直播平台追回购买虚拟财产所花费的金钱。
综上所述,虽然说小卞在直播平台是主动送出礼物给主播,主播
和直播平台不存在欺骗行为,不构成诈骗,但并不意味着家长只能只能吃哑巴亏。由于小卞未满16周岁,是未成年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支付款项是在账户实际拥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法律角度来讲,这笔钱是可以追回的。
互联网化的今天,带动了消费群体的低龄化现象,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事先防范尤为重要。当然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共同努力,培养青少年的网络安全风险意识。同时,网络直播平台应该要尽到监管职责,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保护未成年人,同时平台应加强对网络主播管理,严惩主播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