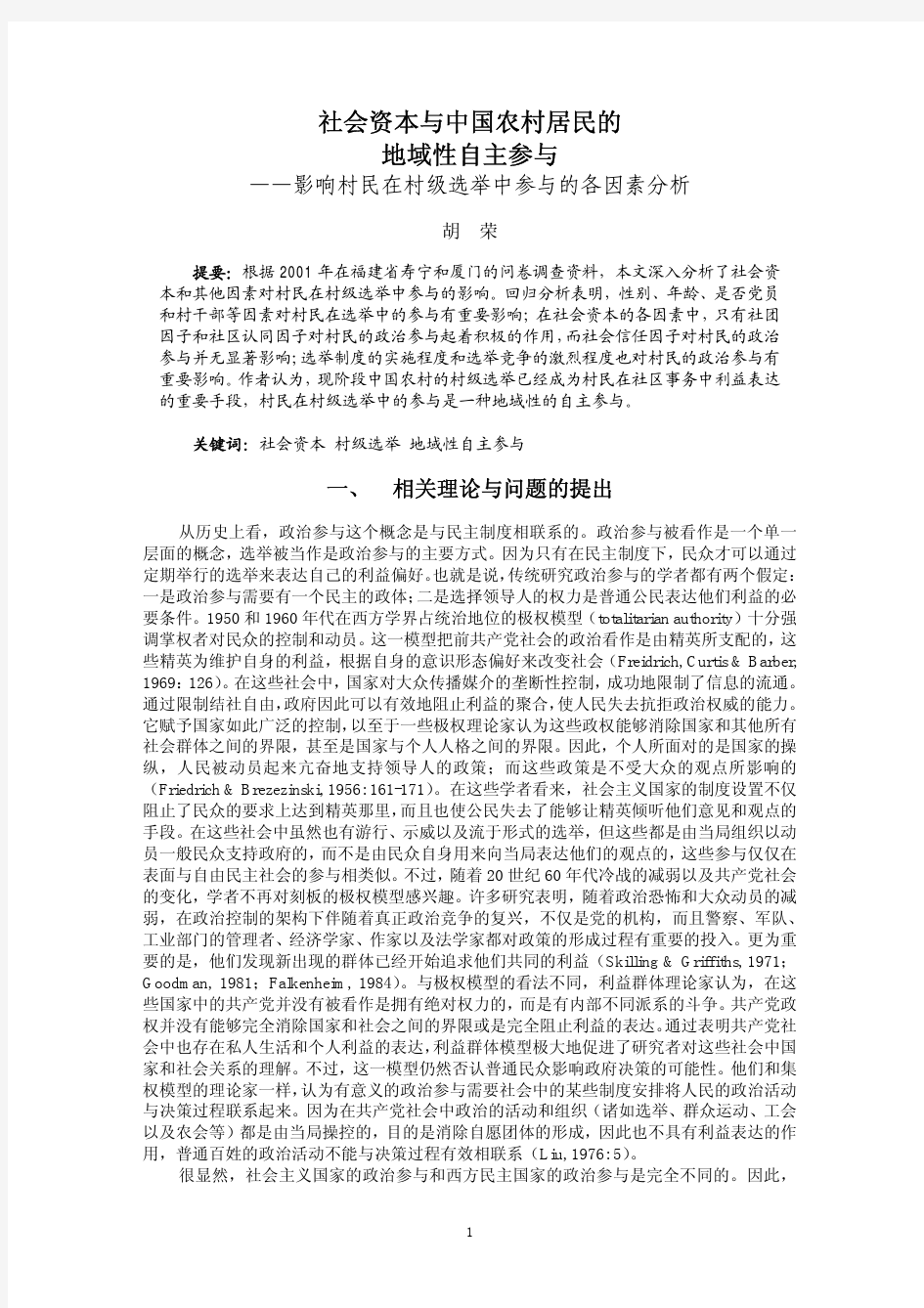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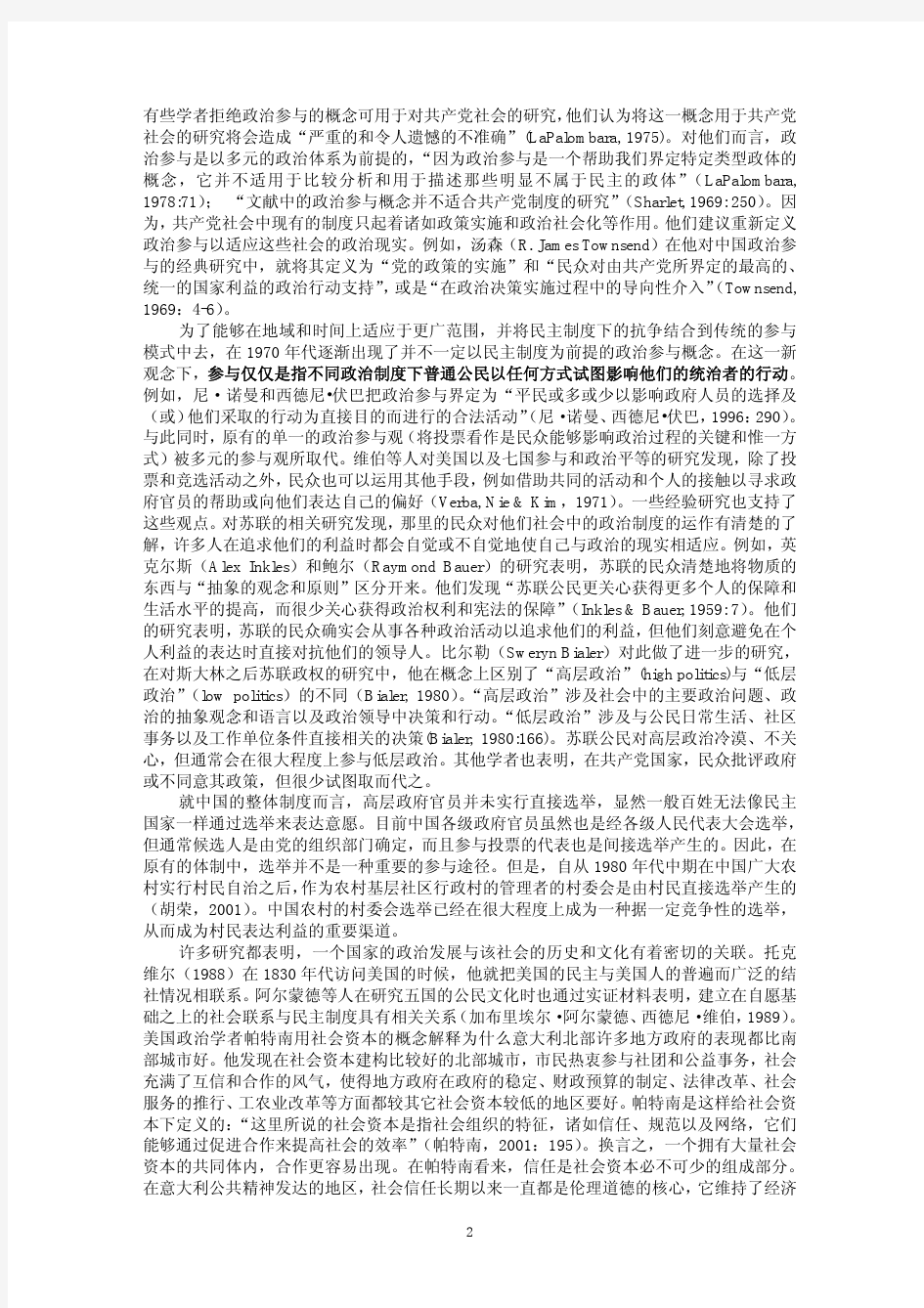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
地域性自主参与
——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
胡荣
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主参与。
关键词:社会资本村级选举地域性自主参与
一、相关理论与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政治参与这个概念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政治参与被看作是一个单一层面的概念,选举被当作是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民众才可以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也就是说,传统研究政治参与的学者都有两个假定:一是政治参与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二是选择领导人的权力是普通公民表达他们利益的必要条件。1950和19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极权模型(totalitarian authority)十分强调掌权者对民众的控制和动员。这一模型把前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看作是由精英所支配的,这些精英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来改变社会(Freidrich, Curtis & Barber, 1969:126)。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通过限制结社自由,政府因此可以有效地阻止利益的聚合,使人民失去抗拒政治权威的能力。它赋予国家如此广泛的控制,以至于一些极权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权能够消除国家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甚至是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因此,个人所面对的是国家的操纵,人民被动员起来亢奋地支持领导人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不受大众的观点所影响的(Friedrich & Brezezinski, 1956: 161-171)。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置不仅阻止了民众的要求上达到精英那里,而且也使公民失去了能够让精英倾听他们意见和观点的手段。在这些社会中虽然也有游行、示威以及流于形式的选举,但这些都是由当局组织以动员一般民众支持政府的,而不是由民众自身用来向当局表达他们的观点的,这些参与仅仅在表面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参与相类似。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减弱以及共产党社会的变化,学者不再对刻板的极权模型感兴趣。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减弱,在政治控制的架构下伴随着真正政治竞争的复兴,不仅是党的机构,而且警察、军队、工业部门的管理者、经济学家、作家以及法学家都对政策的形成过程有重要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新出现的群体已经开始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Skilling & Griffiths, 1971;Goodman, 1981;Falkenheim, 1984)。与极权模型的看法不同,利益群体理论家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并没有被看作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而是有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是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通过表明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表达,利益群体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者对这些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过,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他们和集权模型的理论家一样,认为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需要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将人民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因为在共产党社会中政治的活动和组织(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都是由当局操控的,目的是消除自愿团体的形成,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普通百姓的政治活动不能与决策过程有效相联系(Liu, 1976: 5)。
很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有些学者拒绝政治参与的概念可用于对共产党社会的研究,他们认为将这一概念用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将会造成“严重的和令人遗憾的不准确”(LaPalombara, 1975)。对他们而言,政治参与是以多元的政治体系为前提的,“因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帮助我们界定特定类型政体的概念,它并不适用于比较分析和用于描述那些明显不属于民主的政体”(LaPalombara, 1978:71);“文献中的政治参与概念并不适合共产党制度的研究”(Sharlet, 1969: 250)。因为,共产党社会中现有的制度只起着诸如政策实施和政治社会化等作用。他们建议重新定义政治参与以适应这些社会的政治现实。例如,汤森(R. James Townsend)在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经典研究中,就将其定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民众对由共产党所界定的最高的、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支持”,或是“在政治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导向性介入”(Townsend, 1969:4-6)。
为了能够在地域和时间上适应于更广范围,并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结合到传统的参与模式中去,在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并不一定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参与概念。在这一新观念下,参与仅仅是指不同政治制度下普通公民以任何方式试图影响他们的统治者的行动。例如,尼?诺曼和西德尼?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尼?诺曼、西德尼?伏巴,1996:290)。与此同时,原有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是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惟一方式)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维伯等人对美国以及七国参与和政治平等的研究发现,除了投票和竞选活动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其他手段,例如借助共同的活动和个人的接触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好(Verba, Nie & Kim,1971)。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些观点。对苏联的相关研究发现,那里的民众对他们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有清楚的了解,许多人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与政治的现实相适应。例如,英克尔斯(Alex Inkles)和鲍尔(Raymond Bauer)的研究表明,苏联的民众清楚地将物质的东西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区分开来。他们发现“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个人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Inkles & Bauer, 1959: 7)。他们的研究表明,苏联的民众确实会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以追求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刻意避免在个人利益的表达时直接对抗他们的领导人。比尔勒(Sweryn Bialer)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对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权的研究中,他在概念上区别了“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与“低层政治”(low politics)的不同(Bialer, 1980)。“高层政治”涉及社会中的主要政治问题、政治的抽象观念和语言以及政治领导中决策和行动。“低层政治”涉及与公民日常生活、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 1980:166)。苏联公民对高层政治冷漠、不关心,但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低层政治。其他学者也表明,在共产党国家,民众批评政府或不同意其政策,但很少试图取而代之。
就中国的整体制度而言,高层政府官员并未实行直接选举,显然一般百姓无法像民主国家一样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虽然也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通常候选人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确定,而且参与投票的代表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原有的体制中,选举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参与途径。但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的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胡荣,2001)。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据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
许多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该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托克维尔(1988)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把美国的民主与美国人的普遍而广泛的结社情况相联系。阿尔蒙德等人在研究五国的公民文化时也通过实证材料表明,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系与民主制度具有相关关系(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1989)。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其它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帕特南是这样给社会资本下定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换言之,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
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帕特南,2001:200)。那么,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遵循普遍的互惠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2001:203-204)。
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目前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例如,阎云翔,2000;Bian, 1998),而且也多限于城市社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研究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构成与其社区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打算运用帕特南的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中国农村基层的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探讨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我们将探讨如下这些问题:社会资本是否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政治参与起作用?如果起作用的话,社会资本中的哪些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村民个人情况对他们的参与有何种影响?村级选举相关的制度对村民的参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的测量
本项研究于2001年9月至10月进行。样本按多阶段抽样法抽取。第一阶段采用立意抽样方法,从福建省的范围内抽取寿宁县和厦门市,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农村。寿宁县地区福建省东北部,与浙江省交界,距省政府所在地福州市284公里,全县辖10个乡、4个镇、201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22万人。寿宁县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我们通过立意抽样选出的另一个区是厦门。厦门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济较为发达,农村的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厦门下辖6个区,大部区的城市程度比较高,我们选择城市程度相对较低的同安区,从中选择4个乡镇,另从城市程度较高的厦门岛内的选取1个镇。我们再用随机方法从寿宁的14个乡镇中抽取5个乡镇,具体方法是:先根据各乡镇2000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参看县经管站的数据)由低至高将全县14个乡镇按顺序排列。而后将全县的农业总人口222144除以要抽取的乡镇数5,得44428.8。在44428.8为数内随机确定一个数,即23000,所以选中的第一个乡为大安乡。第二个乡按23000加44428.8的方法确定,为犀溪乡,余类推。抽样结果共选出大安、犀溪、竹管垅、武曲和鳌阳5个乡镇。在厦门同安区也用类似方法随机抽取4个镇,即莲花镇、大嶝镇、马巷镇、大同镇,另加上厦门岛内的禾山镇,共5个镇。而后再从各个乡镇中按随机方法各抽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再按随机方法抽取25个18岁以上村民,共1000人。
调查在2001年9至10月进行。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1998级学生19人担任访问员。这些学生在校期间受过专门的社会学和社会调查训练,在参加调查之前又接受了有关本课题问卷调查的相关培训。寿宁的调查在2001年10月15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厦门的调查于2001年10月29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本次调查共成功访问村民913人。其间,每个村大约成功访问20至25人。在成功访问的对象中,男性占56.3%, 女性占43.7%。从文化程度看,调查对象中读书4-6年者最多,达30.7%, 其次是读书7-9年者, 文盲也占有相当比例, 达18.2%, 上学1-3年者占12.1%, 而接受10年以上教育者的比例则非常之少, 10-12年者只占9.1%, 13年以上者仅为1.6%。从年龄结构来看, 30岁以下者占24.4%, 30-40岁的受访者最多, 占23.6%, 41-50岁占23.6%, 51-60岁占12.9%, 而61岁以上的受访者则较少, 61-70岁占7.5%, 71岁以上只有3.5%。
为了弄清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回归模型,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在选举中参与程度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看作为因变量的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指标。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在问卷中列了16个方面的问题测量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参与候选人的提名、是否参与投票
等。在这些项目中,有的参与者比例较高,如参加投票者占受访者的79.5%, 而其他一些项
目的参与者则比较少(参见表1)。
表1 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
项目人数比例
⒈单独提名候选人 56
6.1%
⒉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 21
2.3%
⒊与其他人一起提名候选人 68
7.4%
⒋毛遂自荐当候选人 16
1.8%
⒌参加预选会 111
12.2%
⒍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
人
48 5.3%
⒎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
票
44 4.8%
⒏参加投票 726
79.5%
⒐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 55
6%
⒑对于不恰当的选举安排提出批评和
建议
44 4.8%
⒒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 69
7.6%
⒓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
提问
30 3.3%
⒔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 59
6.5%
⒕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 29 3.2%
⒖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 拒绝参加
投票
29 1.9%
⒗因为对选举不满意, 动员别人不参
加投票
4 0.4%
我们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6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4个因
子。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预选因子、竞选因子、提名因子和罢选因子。“预选因子”包括这几个项目:“参加预选会”、“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在候选人的竞
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问”、“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以及“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
表看法”。“竞选因子”包括这几个项目:“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劝说别
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以及“参加投票”。“提名因
子”包括的项目有:“单独提名候选人”、“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与其他村民一起提名候
选人”以及“毛遂自荐当候选人”。“罢选因子”只有两个项目:“因为对选举不满意而拒绝
参加投票”和“因对选举安排不满意而动员别人不投票”。为了把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
程度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我们把4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而后相加,即:村民在表2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因子分析
项目预选因
子
竞选因
子
提名因
子
罢选因
子共量
单独提名候选.297 .079 .398 -.063 .257 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189 .382 .531 .106 .474 与其他村民一起提名候选人.110 .007 .651 .036 .437 毛遂自荐当候选人-.039 .249 .622 -.047 .453 参加预选会.566 -.113 .435 .066 .527 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101 .743 .111 .153 .598 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010 .713 .137 .181 .560 参加投票.059 -.351 .333 .187 .273 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339 .681 .168 -.012 .606 对于不恰当的选举安排提出批评和建
议
.462 .359 .118 .261 .424 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788 .016 .215 .026 .668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
.821 .256 .033 -.095 .750
问
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818 -.047 .136 .042 .692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790 .230 -.039 .086 .686
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拒绝参加投票.017 .055 .082 .780 .618
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动员别人不参
.052 .179 -.065 .811 .696
加投票
特征值 3.392 2.158 1.702 1.4678.719
平均方差21.197%13.489%10.638%9.167%54.491%
选举中的参与=预选因子值╳0.21197+竞选因子值╳0.13498+提名因子值╳0.10638+罢选因子值╳0.09167(参见表2)。
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本项研究重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的测量。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差异(参看Lochner, Kawchi & Kennedy,1999;Onyx & Bullen, 2000;Barayan & Cassidy,2001),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帕特南等人定义中的主要内容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在帕特南所讲的社会资本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其他许多研究也谈到这一点(Putnam, 1993;Portes, 1998;Woolcock, 1998)。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密集的关系网络,当然这种网络是平等的和自由的。根据本项研究的目的,我们分别问被访者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情况。我们问被访者是否经常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交往。测量村民与行政村内的不同交往对象的问题共7项,答案按里克特量表的格式设计,分为“经常来往”、“有时来往”、“较少来往”和“很少来往”四个等级,根据受访者的不同回答分别记4至1分。另一方面,我们还测量了村民的社团参与情况。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根据他对意大利的研究,意大利北方的民主运作的比较好,主要原因就是在那里具有众多的横向社团,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这些社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横向社会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共同利益的合作。我们分别列出如下几种社团组织,即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组织、老人会、企业组织、科技组织、民间信用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寺庙组织等,问被访者是否参与这些组织。
相关文献中谈到的社会资本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互惠。帕特南把互惠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则在特定的时间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用泰勒的话说,这是一种短期的利他主义和长期的自我利益的结合(Taylor, 1982),或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是“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这种互惠的规范在农村社区的主要表现是亲友和邻居之间在农忙季节和相互义务帮工,比如今天我帮你割稻,下个月可能你帮我插秧。村民在从事一些需要较多人力的活动时,比如建房子,更需要得到亲友和邻里的帮助。通常建房的村民不为帮工的村民提供报酬,但是当其它村民建房需要帮工的时候,现在的建房者也要提供义务帮工作为回报。不过,近年来,由于建房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村民改为请专门的建筑队建房,这一相互义务帮工的情况有所减少。在这里我们问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去一年被访者是否与亲友之间有过义务帮工,二是过去年被访者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
社会资本的第三方面是信任。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韦伯,1995)。福山(1998)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的其它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一定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在调查中,我们分别问被访者对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测量村民信任程度的7个项目的答案也分为四级,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有点信任”和“不信任”,分别记4至1分。
社会资本的第四方面是规范,帕特南(1993)和科尔曼(1988)都提到这一点。社会规范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从而减少了对正式制度制裁的依赖。社会规范通常是不成文的,但为社会成员所普通理解和接受。科尔曼(1988)和帕特南(1995)都认为,在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犯罪和越轨行为少,不需要太多的警力维持治安,社会成员因而也有更多的安全感。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要求被访者回答他们所在的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家中失窃”和“邻里吵架”这些事情。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如下一些问题以测量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你经常会因为你是本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如何?”“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地里庄稼被盗的事情?”“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被盗的事件?”“你村是否经常发生邻里争吵事件?”。有关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的答案也分别分为4级或5级:“邻村的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很愿意”、“较愿意”、“一般”、“很不愿意”和“较不愿意”5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的答案分为4级,即“很有安全感”、“较有安全感”、“较少安全感”和“没有安全感”,分别赋值4至1分;“你会经常因为你是这个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答案分“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4级,分别记4至1分;“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好不好?”,答案分“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很差”5级,分别记5分至1分;另外3个问题,即“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的事”、“你村是否经常有村民家里的东西被盗”以及“邻居之间是否经常吵架”的答案分为4级,即“经常发生”、“有时发生”、“很少发生”和“没有发生”,分别记1至4分。
以上介绍了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和项目。那么,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它们可以概括为哪几个方面呢?为此,我们进行了因子分析。如上所述,有关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以有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都是按利克特量表的方式设计的,答案分为4级和5级两种。有关社团参与方面的问题的答案只分为“是”“否”两种,凡回答“是”者记1分,“否”者记0分。有关社团的问题共10项,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把每个受访者对这些项目的回答加在一起计为一项,总分的高低表示其参与社团的多少。测量互惠规范的两个问题,即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和是否为邻居义务帮工的答案也只有是否两个答案,凡回答是者记1分,两个问题的得分加在一起作为一个项目,与其他项目一起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
表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项目信任因
子
社会交
往
因
子
社区安
全
因
子
亲属交
往
因
子
社区认
同因
子
社团因
子
共量
与亲戚是否经常来往0.1340.1720.0840.7560.2140.082 0.678 与本家族成员是否经常
来往0.1880.3340.0870.7300.1780.098
0.729
与同姓村民是否经常来
往0.2200.5670.0850.5400.1060.046
0.681
与同小组村民是否经常
来往0.1900.7640.0170.3280.0740.023
0.733
与同自然村村民是否经
常来往0.2180.8440.0250.1900.0580.025
0.801
与同行政村村民是否经
常来往0.1540.8540.0180.0080.0470.002
0.756 与村干部是否经常来往0.1760.450-0.020-0.0470.3190.465 0.553 是否信任亲戚0.672-0.1750.0600.4190.1390.126 0.696 是否信任家族成员0.754-0.0590.0450.4370.1360.078 0.790 是否信任同姓村民0.8470.1410.0540.2570.049-0.022 0.809 是否信任同小组村民0.8650.2550.0300.0850.088-0.060 0.834 是否信任同一自然村的
村民0.8720.323-0.0010.0360.088-0.041
0.876 是否信任同一行政村的0.8130.378-0.001-0.1010.070-0.038 0.820
村民
是否信任村干部0.5810.1980.045-0.1420.2710.351 0.596
邻村姑娘愿意嫁到本村
吗0.0550.0250.1430.0770.565-0.086
0.357
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0.0760.1520.0340.1580.6220.027 0.443
是否因作为村民而感到
光荣0.134-0.0230.0380.0660.6980.140
0.530
本村的社会风气如何0.0940.0750.2820.0870.6440.014 0.516
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
的事0.0200.0470.8030.0230.1190.002
0.661
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
被盗0.033-0.0360.8260.0480.1660.091
0.724
邻居之间经常吵架0.0510.0460.7760.0910.1400.001 0.635
是否为公益捐款和义务
帮工-0.0920.0220.2350.078-0.0770.651
0.500
参与各种组织和社团总
数0.060-0.021-0.1020.0960.0500.666
0.469
特征值 4.536 3.132 2.132 2.083 2.013 1.291 15.187
平均方差19.72%13.62%9.27%9.51%8.75% 5.61% 66.04%
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社会资本的23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6个因素。根据因子负载,我们分别将这些因子命名为:信任因子、社会交往因子、社区安全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和社团互助因子。第一个抽取的因子被称作“信任因子”,所有测量信任的变量都包括在这个因子内,即它包括对亲戚、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与测量信任的变量都可以归到一个因子的情况不同,测量社会交往的7个变量被分作两个因子,即表中的第二个因子“社会交往因子”和第四个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前者包括与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后者则包括受访者与亲戚和本家族成员的交往,而与同姓村民的交往这一变量则横跨在两个因子之间。第三个因子是“社区安全因子”,可以归入这一因子的变量包括庄稼是否经常被盗、家中财物是否经常被盗以及邻居是否经常吵架。第五个因子为“社区认同因子”,包括“邻村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是否因作为本村的村民而感到自毫”以及“在本村生活是否有安全感”等变量。第六个因子为“社团互助因子”,包括“是否为公益事业捐款和义务帮工”和“参与社团总数”两个变量。
在本项研究的回归议程中,除了加入受访者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当过村组干部等,进行预测外,我们还加入村庄离县城距离以及测量选举竞争竞争程度和选举规范实施程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测量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在问卷问了这样的问题:“您村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候选人用下列方法争取选票?”在问题之后我们分别列了9种竞选拉票的方法(参见表4)。根据受访者对这9个项目回答的情况,我们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可以抽取两个因子。第一因子我们称之为“竞选承诺因子”,因为它包括“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实事”、“答应当选后少收甚至不收提留”、“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干部的腐败问题”、“答应当选后带领大家致富”以及“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这几个项目,这些手段主要表现为候选人通过承诺当选做一些事来争取选票;另一个因子叫做“关系拉票因子”,包括“走家串户争取支持”、“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请族长帮帮忙争取选票”以及“动员亲戚朋友帮忙争取选票”,这些手段主要是通过感情联系和关系来争取选票。
表4 选举竞争激烈程度的因子分析
项目竞选承诺
因子
关系拉票
因子
共
量
走家串户,争取支持.067 .830 .693 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068 .763 .587 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202 .816 .707
动员亲戚朋友帮忙争取选票.210 .812 .703
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实事.699 .219 .537
答应当选后少收甚至不收提留.746 .151 .580
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干部的腐败
.788 .045 .624
问题
答应当选后带领大家致富.791 .102 .636
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
.678 .104 .471
福利
特征值 2.847 2.690 5.538
平均方差31.636 29.890 61.526
我们再来看一看测量村委会选举的指标。以往的研究表明,选举是否规范与村民的参与程度有很大关系(参看胡荣,2001)。我们认为选举是否符合选举规范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这里包括候选人如何提名,正式候选人如何产生,以及选举投票的程序等。为此,我们用表5所列的15个项目来测量选举的规范性。在表1中,关于候选人如何提名的问题包括:⒈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包括单独提名和联合提名);⒉党支部提名候选人;⒊乡镇提名候选人;⒋上届村委提名候选人;⒌村民代表提名候选人;⒍村民自荐成为候选人。在这6个问题中,第1、5和6个问题都是正面的问题,越多被访者肯定回答这些问题,表明选举提名的基础越广泛,不是由上面在小圈子划定候选人。第2、3、4三个问题则是负向的问题,越多被访问者肯定回答这些问题,表明提名的程序越不民主,是由少数上级领导圈定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叫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如何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也是十分关键的(Elklit, 1997;Thurston, 1998;Pastor & Tan, 1999;O'Brien & Li, 1999)。根据福建省民政厅的规定,在1994年以前的村委会选举中,正式候选人是通过一个叫做“民主协商”的过程产生的,即由村选举领导小组在征求村民和乡镇领导的意见过程中确定正式候选人(参看福建省民政厅,1994)。这种酝酿协商的结果往往是由村党支部或乡镇决定正式候选人,并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能够使村民的意愿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从1997年开始,福建省民政厅规定正式候选人应由村民代表或选民预选产生,即由村民代表或村民投票决定正式候选人,通过制度保证村民的意愿能够得到体现。那么,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这种制度性的规定是否得到实施了呢?在调查中,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⒎正式候选人是否由村民投票产生;⒏正式候选人是否由党支部决定;⒐正式候选人是否由乡镇决定;⒑正式候选人是否由村代表投票决定。如果被访者对7、10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
表5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采用下列措施的
村庄和比例
项目村庄
比例
数
⒈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22 55%
⒉党支部提名候选人(-) 5 12.5%
⒊乡镇提名候选人(—)11 27.5%
⒋上届村委提名候选人(—) 8 20%
30%
⒌村民代表提名候选人(+)12
⒍村民自荐成为候选人(+) 2 5%
19 47.5%
⒎正式候选人由村民投票产生
(+)
2 5%
⒏正式候选人由党支部决定
(—)
⒐正式候选人由乡镇决定(—) 5 12.5%
5 12.5%
⒑正式候选人由村代表投票决
定(+)
⒒实行差额选举(+)40 100%
40 100%
⒓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
(+)
⒔仍使用流动票箱(—)15 37.5%
⒕设立固定投票站(+)23 57.5%
⒖设立秘密划票间(+)20
50%
的话,表明正式候选人的确定过程是能够体现选民的意愿的;如果被访者对8、9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表明省民政厅的规定没有得到实施,村民的意愿不能得到体现。最后5个问题是关于投票选举方式的:⒒是否差额选举;⒓是否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⒔是否使用流动票箱;⒕是否设立固定投票站;⒖是否设立秘密划票间。为提高选民投票率,在福建省的许多地方过去都使用过流动票箱,由选举工作人员提着票箱上门由选民投票(参看胡荣,2001)。流动票箱在实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选民投票缺乏匿名性,容易出现舞弊,因此福建省民政厅从1997年开始强调在选举过程不要使用流动票箱,而应设立固定投票站和秘密划票间。因此,除了把是否差额选举、是否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作为选举是否规范的指标外,我们还把是否设立流动票箱、是否设立固定投票站以及是否设立秘密划票间作为选举是否规范的指标。不过,对于本项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关于村一级的资料。获得村级选举方面资料的一种方法是查阅民政部门的统计表格。由于正式统计数字可能掺杂一些水分,我们在这里打算运用个人的访问资料进行推测。由于被访者对选举本身的知识的限制和参与程度的不同,同一个村庄的选民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如何把村民个人的回答变成村一级的指标呢?在这里,我们使用多数原则确定村一级的指标。每一个项目都有“是”,“否”和“不知道”三项回答。在每个村庄中我们调查的被访问者人数在20人至25人之间。当每个村庄的被访问者在特定项目上回答“是”的人数超过“否”的人数时,我们确定这个村庄采用这个项目的选举措施。经过推算,不同村庄在17个项目上的频数分布情况见表1。由于我们把这17个项目的问题份为正向问题和负向问题,正向问题肯定回答的得1分,否则0分,负向问题肯定回答的得—1分,否则0分。每个村庄在这17个项目上的得分加在一起就是该村在选举规范性方面的总得分。
三、研究发现
以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上学年限、是否党员、是否村组干部、村庄离县城距离、构成社会资本的6个因子(即信任因子、社会交往因子、社区安全因子、亲属联系因子、社区归属因子和社团因子)、选举规范实施程度以及反映选举竞争程度的两个因子(竞选承诺因子和关系拉票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将因变量“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①在上述自变量中,“性别”、“是否党员”和“是否村组干部”三个变为虚拟变量。分析结果见表6。
我们先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是否担任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参与程度远远高于女性,即男性的参与度要比女性高3.374分, 在村民的平均参与度只有6.6分的情况下这一差异是相当大的。跨国的比较表明,在发达国家,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异不大,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较大(Nie, Verba & Kim, 1974),一个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发达地区男女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小于落后地区(Goel, 1975)。史天健在北京城市社区的研究表明,男女市民的投票参与虽然都受年龄的较大影响,但二者的参与率相去不大(Shi, 1997:170)。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那里的居民素质较高,因此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别不大。但中国农村则是属于落后的地区,居民文化素质较低,在政
表 6 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程度的
因素(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回归系数标准回归系
数
显著性水
平
性别a 3.374 0.128 0.001
年龄0.364 0.388 0.055
年龄的平方-0.004 -0.424 0.031
①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参看边燕杰、李煜,1999)。
上学年限0.033 0.010 0.829
是否党员b 3.580 0.097 0.011
是否当过村组干
4.061 0.113 0.002
部c
村庄离县城距离-0.130 -0.128 0.000
选举规范实施程
1.419 0.154 0.000
度
社会资本:
信任因子-0.636 -0.048 0.173
社会交往因子0.230 0.017 0.627
社区安全因子0.261 0.020 0.578
亲属联系因子-0.362 -0.027 0.446
社区归属感因子 1.274 0.097 0.007
社团因子 1.513 0.117 0.001
竞选激烈程度:
竞选承诺因子 1.954 0.151 0.000
关系拉票因子-0.573 -0.044 0.230
常数-7.194 0.148
N 698
Adjusted R
Square 17.2%
F检定值10.072 0.000
a 参考类别为“女性”;
b 参考类别为“非党员”;
治参与方面男女相差较大。
另一方面,年龄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影响呈倒U型。有关年龄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国外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正如米尔布拉斯所指出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四十和五十岁达到顶峰并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在六十岁以上逐渐下降”(Milbrath, 1965:134)。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政治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在中年达到顶峰,而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下降(Milbbrath & Goel, 1977;Nie, Verba & Kim, 1978)。史天健在北京的调查也发现市民的投票率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以45-53岁年龄的受访者的投票率最高(Shi, 1997:168)。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外学者的发现是一致的,年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则呈倒U 型,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村民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我们通过不同年龄组参与平均值的比较可以发现,30岁以下组村民的选举参与程度较低,参与的平均值是5.07, 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 31-40岁年龄组为6.33, 而到了41-50岁年龄组达到最高, 为8.93, 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村民的参与开始逐步下降, 61-70岁组和71岁以上组的参与均低于30岁以下组, 分别为3.87和3.41。这一结果与相关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为什么生命周期对政治参与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与生命周期相关联的精力。虽然生命周期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加入个人政治面貌和是否村干部等方面的控制变量后,年龄依然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显著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看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些研究表明(参看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rokes, 1960;Verba, Nie & Kim, 1978),教育程度与投票参与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文化程度越高者参与的比例也较高,而对共产党国家的研究则发现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参看Bahry & Silver, 1990)。因为在选举沦为纯粹的形式的情况下,选民无法对候选人进行选择,文化程度越高者越可能以不参与的方式表示不满。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村级选举不同于共产党社会的其他选举,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内有选择的选举(参看胡荣,2001)。如果只从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对参与程度的影响来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的参与平均值有明显不同,较高者参与程度也较高,未上过学者的参与程度为4.32, 上学1-3年者为6.59, 4-6年者为6.83, 7-9年者为6.91, 10-12年者的参与度最高, 为9.19。不过,上学年限在13年以上者的参与程度又有所下降,为5.82。这一
结果与史天健在北京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Shi, 1997: 145-146)。史天键的研究表明,北京市民的投票参与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达到18年以上的受访者来说,他们的参与程度却是最低的。在本项研究中,上学年限13年以上这一组的参与程度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却大大低于10-12年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以后,他们的户口就转为非农业户口,他们的工作也由国家统一安排。近年来由于国家不再分配工作,一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回到农村去自谋职业。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农村较难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因此他们呆在农村往往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有机会他们还是想到城里找工作。这种情况就使得他们文化程度虽然最高,但对村里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程度却不如文化程度比他们低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上学年限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虽然单因素的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总体上能够增进村民的参与程度,但多因素分析回归分析却表明文化程度对参与程度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本身不对村一级选举的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如果说在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需要参与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话,那么,在行政村这一基层的社区里,受教育程度便不是十分重要的了。因为不管是文盲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都一样能够知道谁是否有能力管理村里的事务,谁办事更公正,谁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回归分析还表明,受访者的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组干部这两个变量对他们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有很大影响,二者对因变量的影响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回归系数也比较大。是否党员对因变量影响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3.58, 表明共产党员比一般村民的参与程度高3.58分, 而担任村组干部者比一般村民的参与程度更高出4.061分。
那么, 社会资本的诸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在构成社会资本的6个因子中,只有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区认同因子对因变量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是0.094, 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村民的社区认同感越强,他们越是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越可能较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
第二,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也越高。社团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17。如前所述,虽然在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参与的社团还十分有限,受访者中只有36%的人有参与社团, 而平均每个村民参与的社团只有0.54个,但回归分析清楚地表明, 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他们越可能参与村委会的选举。
第三,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因子对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社会资本的6个构成因子中,除了上述的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其他4个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帕特南看来,社区成员之间的横向交往促进了人际间的信任的建立,因而使得人们之间更容易形成合作关系。为什么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讨。
另外,作为控制变量的选举竞争程度和选举制度实施情况对因变量也有很大影响。在测量村级选举竞争激烈程度的两个变量中,“竞选承诺因子”不仅对因变量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标准回归系数也高达0.151。但是,“关系拉票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以往的一些观察发现,选举竞争越是激烈,特别是候选人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都会采取各种方法争取选票,从而使更多的选民参与到选举中来(参看胡荣,2001)。但是,究竟是哪些手段更能促使选民积极地参与村级选举呢?以往的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因子分析把通常村级选举中候选人经常使用的9种手段分成两个因子,第一因子包括争取选票的5种手段,即候选人在竞选中许诺当选后为民办实事、少收提留甚至不收提留、调查前任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带领大家致富以及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另一个因子涵盖争取选票的另外4种手段,即通过走家串户以争取支持、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以及动员亲戚朋友争取选票。如果第一个因子的5种手段有利村级选举的健康发展的话,后一因子的4种手段的相当一部分手段是不具有正当性和不利于选举的健康发展的。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能够提升村民参与程度的是积极的竞选手段。
选举实施的程度也对因变量有重大影响。我们用15个指标测量村级选举的规范程度。回归分析表明,越是规范,村民的参与程度也越高。另外,村庄距县城所在地的距离也对村民的参与有重要影响,村民离县城越远,村民参与的程度越多。
四、讨论与结论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前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参与有许多类似之处的话,那么在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使得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的政治参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这种参与叫做地域性自主参与,它既不同于过去的那种动员式参与,也与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有很大不同。首先,这种参与是一种自主式的参与,因为村级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不同过去那些流于形式的选举,村民能够通过村级选举表达他们的利益,村民是否参与完全是自身利益算计的结果。相关的研究表明,为了能够在下一次的选举中再次连任,对于当选的村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选民的关系,他们既要通过办一些实事(如建学校、修路等)来获得选民的信任,但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又不能损及村民的利益(参看胡荣,2002)。在本项研究中,有多达25.5%的受访者认为在竞选期间候选人有通过“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事”来争取选票,有24.1%的受访者认为候选人有通过“答应当选后带领村民致富”来争取选票,还有的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有的答应当选后少收提留,有的甚至许诺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村民办实事。正是这种选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农村居民可以定期的选举向村领导表达他们对于本行政村范围的一些重大事务的选择偏好。因此,在中国农村,村一级的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参与基层政治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有了这一参与途径,致使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性质,即从原来毛泽东时代的动员式参与演化为现在的自主式参与。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居民虽然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运动,但普通老百姓并不能通过这种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而是被当政者作为宣传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手段(参看Burns, 1988;周晓虹,2000)。而村级选举中村民的参与却是一种自主式的参与,它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和农民自主性的提高而出现的。作为自主式的参与,农民通过参与选举表达自身的利益。因此,参与与否和参与程度完全是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而不是出于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像参与其他政治活动一样,参与村级选举需要村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付出,因此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村民只有在参与得到的回报大于参与的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参与选举。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上述回归方程中“选举制度实施程度”这一变量会对村民参与有重大影响的原因。“选举实施程度”这一变量综合了问卷中的15个问题,从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到正式候选人的确定以及选举投票等内容。从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实施以来,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以福建省为例,从1997年开始,就把原来确定正式候选人方法由原来的“酝酿协商”改为由村民代表投票预选。如果在开始选举制度不太完善的情况下村民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的话,那么在选举制度得到较好地实施以后,村民更为积极地参与村级选举。因为在选举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选举可能会被操纵,“组织意图”可以更好得到体现,而村民选票的份量则要大打折扣;而在选举制度得到落实和情况下,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村民手中的选票,因此村民参与的效能感得到很大提高,他们更愿意参与选举。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决定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影响大小的因素是参与投票的选民的多少。如果参与投票的选民越多,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小,很小的投票成本都会超过投票的价值;相反,投票的人越少,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大,投票的价值大于投票的成本(Downs, 1957:267)。在村委会选举中,决定每一张选票价值大小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选举是不是真正的选举。如果选举是被操纵的或是流于形式的,那么选票是不重要的。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了。而随着选举程序的改进和选举制度得到实施之后,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增长了,投票的价值超过了投票的成本,村民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也就相应提高了。
但是,这种参与又是地域性的,它与一个由几百到数千人组成的行政村相联系。农村居民不仅生活和生产都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的简陋的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提供的,这使得农村社区(即村民生活的村落)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资本的诸因素中,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对他们的参与程度才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些对社区认同感越强的村民往往更能够积极参与到选举中来。与这种基层政治参与的空间狭隘性相联系,受教育程度对参与程度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在一个只有数百或几千人的小社区里,参与公共事务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教育。
参与的地域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农村居民目前的这种自主式政治参与仅限于行政村
这一基层社区,在更广的范围内,比如乡一级、县一级或是省一级,农民参与的渠道还是十分缺乏,农民仍然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对于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农民不得不诉诸上访、群体抗争等方式(参看Li & O’Brien, 1996;李连江,1997;萧唐镖,2003;于建嵘,2003;陈江棣、春桃,2004)。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而后延伸到城市的。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仍滞后于经济改革。从1980年代开始的村级选举已经实施了近二十年,但目前这种选举也还仅限于行政村一级。要使中国农村居民(同时也包括城市居民)能够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让各个层次的选举都成为利益表达的手段,使更广范围的参与都能成为自主式参与,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边燕杰、李煜,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期。
陈桂棣、春桃,2004,《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福建省民政厅,1994,《村委会选举工作指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山,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口:海南出版社。
郭正林,200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第3期。
胡荣,2001,《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1989,《公民文化》,北京:华夏出版社。
李伟民、梁玉成,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尼·诺曼、西德尼?伏巴,1996,《政治参与》,《政治学手册》(下册),格林斯坦、波尔比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帕特南,2001,《使民主运作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托克维尔,1988,《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伯,1995,《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
萧唐镖,2003,《二十余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香港:《二十一世纪》4月号。
阎云翔,2000,《礼物的流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于建嵘,2003,《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第3期。
周晓虹, 2000,《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7卷,秋季。
Bahry, Donna & Brian Silver 1990,“Soviet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Eve of Democrat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3).
Barayan, Deepa & Michael F.Cassidy 2001,“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Inventory”, Current Sociology. 49(2).
Bialer, Seweryn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ns, John 198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eman, James 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Elklit, Jorgen 1997, "The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oral System." China Information 11(4).
Freidrich, Carl J., Michael Curtis & Benjamin R. Barber 1969,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Friedrich,Carl J. & Zbigmiew Brezezinski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el, Lal M. 197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 India.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Goodman, David S. G.. ed. 1981, Grou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Gordon H. Skilling & Franklyn Griffiths (eds.) 1971,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kles, Alex & Raymond A. Bauer 1959,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LaPalombara 1975, “Monoliths or Plural Systems: Through Conceptual Lenses Darkl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8(3).
Joseph LaPalombara 1978,“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idney Verba & Lucian W. Pye (eds.), The Citizen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mford, Conn.: Greylock Publishers.
Li, Lianjiang & Kevin J. O'Brie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 ol. 22.
Liu, Alan P. L. 1976,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Books.
Lochner, Kimberly, Ichiro Kawchi & Bruce P. Kennedy 1999,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 measurement.” Health and Place, 5. Milbrath &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Milbrath, W. Lester 19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Nie, H. Norma, Sidney Verba & Jae-on Kim 1974,“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Cycle.” Comparative Politics 6(3).
O'Brien, Kevin J. & Lianjiang Li 2000,“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62.
Onyx, Jenny & Paul Bullen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 ol.36. Pastor, Robert A. & Tan Qingshan 2000, “The Meaning of China's Village Elections.”
China Quarterly 162.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arlet, Robert S. 1969,“Concept Form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rederic J. Fleron, Jr.,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Shi, Tianjian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M. 1982,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urston, Anne F. 1998, “Muddling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in Grassroots China.” Peaceworks, No.23,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ownsend, R. James 196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 Jae-on Kim 1971,The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Berkele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
—— 1978,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ictor C. Falkenheim, ed., 1984,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Woolcock, M. 1998,“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Theory and Society, 27.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6-2
中国社会学网https://www.doczj.com/doc/701396467.html,
社会资本嵌入与社会治理 张伟明等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在广大乡村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交织互动,诸如宗房结构、自组织、非正式规则等微观结构深深嵌入乡村社会有机体,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效力。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进行考察和认识,并将隐含于乡村社会有机体中的诸种非正式组织和规则纳入社会资本的分析范畴,指出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将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的运行实现有效衔接。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认识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多元治理、民主政治、国家与社会等视角,对中国社会管理进行透视①,对建构完善的体制进行了探讨(丁元竹,2006;戴均良,2006;侯岩,2005;邓伟志,2006;何增科,2009;杨雪冬,2009)。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发展,来自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多中心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等也对中国社会管理的政策实践和理论创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osenau, 1995;Salamon,2002;俞可平,2002),其中的治理理论强调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对探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罗西瑙,
2001)。 目前,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层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②成为顺利实现我国宏观秩序良性运转的微观结构基石。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治理理论,从乡村微观结构(宗房结构、自组织、非正式规则等)入手,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将存在于乡村基层社会的微观结构与基层社会整体的融合视作一种“嵌入”,并将乡村基层社会非正式组织或制度视作社会资本来进行阐述和解读,尝试通过探讨诸如宗族、房族等微观结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机理和演化路径,来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合理路径选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地域面积广,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和农村社会格局,尤其是我国南方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更是孕育出了极具差异性的社会结构与组织架构。农村作为我国农民的最主要居住区,其对广大农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保障功能不可替代。因此,理解农村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诸多规范、非正式制度以及隐性组织等是理解真实农村的重要基础,如“差序格局”就是处理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费孝通,1988),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农村保甲制度则是推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李伟中,2002;冉绵惠,2005)。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强力带动下,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不同时期政策的不同取向,农村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成为阻碍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需要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宏观而深入的审视,对其弊端和不足加以揭示,在政策取向方面应更加注意发挥政府在农村社保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要求,也是对历史偏差的纠正。 标签: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责任 我国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和对策 马继彬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呼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1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较为落后,集体经济脆弱,大部分劳动者得不到集体帮助,农民家庭经济基础又极为薄弱,单个家庭保险能力有限,一旦风险发生,个人和家庭难以抵御。 2劳动者保障由农民家庭承担,将进一步强化农民“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极不利于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与生育水平及出生性别比的降低。如果向人们提供养老保障,就可使生育率降下来,这已被墨西哥的实践所验证。由此可见,解决我国生育率偏高的途径不在于收紧政策,而在于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的关键之一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破除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从而转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动,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正在退化。就一个社会而言,每一代人都是有能力为自己养老的,代际之间的再分配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它必然要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结构变动力量的抵制和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制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农民家庭的养老功能正在退化,实际作用也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大。总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补偿家庭保障功能,是广大农村劳动者的迫切需要,它关系着亿万农户的家庭幸福。
众所周知,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面积扩大、农村人口净流出、公共资源倾斜,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走向衰落。乡村旅游由于其能够直接将乡村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起到美化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产业能力的作用,而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将它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一剂良药。特别是今年7月底,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乡村旅游将迎来更多机遇。 事实上,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安徽的西递宏村、江西的婺源、 成都的五朵金花、陕西的袁家村和马嵬驿、浙江的安吉……我们随口都能说出很 多知名的旅游乡村。也有很多城市人背着行囊走在了去往乡村的路上,他们或是 寻找一个古镇、山村租下一栋民居,按着自己的喜好进行改造,当起了民宿老板;或是承包数顷良田,种菜养鸡,当上了农场主;再有抱负的就是弄出了像裸心谷 这样的乡村休闲极品。但不能否认,中国的乡村旅游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产业 链条过短,产业体系不健全;旅游业态单一,规模化程度较低;旅游产品同质, 分工协作水平低;低价恶性竞争,服务质量不稳定…… 归结起来,最主要的还是乡村旅游产业化水平低,产业是乡村旅游得以持续 发展的动力,要想做大乡村旅游最关键的是打通一产、二产、三产的联系,形成 产业链。 一、做好一产:一地一品,发展高效精细农业 农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产业基础,因为特色农业既是乡村旅游的景观营造, 也是休闲体验的内容,消费的对象。一村一品、一镇一韵,是现代农业走向规模化、精致化、社会化、差异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地区形成一种产业特色,一 个农户发展一种主导产品,有利于形成明确的专业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依存,构建现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框架,保持以农为本的本色。而建立单一农产品为 主的专业性农场,可以有效的提高农产品产量,形成农业和观光两用园,是乡村 旅游的主力军。 日本的精致农业闻名世界,发展注重“大而专”。一些地区的无土栽培和温室 大棚精细化堪比园艺盆景。而普通农户只种植1-2个品种,一般作为商品出售。专业性的农场则会同时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农业,如葡萄公园农场,可以将葡萄 园景观的观赏、采摘、制品,以及与葡萄有关的品评、写作、绘画、摄影、体验、竞赛与季节、庆典活动融为一体。 二、联动二产:打造IP,深化旅游商品开发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从“乡土社会”到“土社会”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在不断快速的转型中。其中社会结构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而经济体制也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在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下,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从传统农村“乡土社会”逐渐向“土社会”转型。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便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也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围的概念。许烺光先生在《祖荫下》对喜州文化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喜州文化主要由五个因素组成:既父子同一,性别疏远,大家庭的理想,教育的模式,祖先的愿望。这些因素其实也正是构成特定地域围及人们维持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传统的乡村社会便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依赖土地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农民离不了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
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都会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土地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便于持有土地的多少息息相关”。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权力关系的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依村而居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均资源一直处于贫乏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在这个资源匮乏的社会里,个体生存困难重重,再加上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逐渐便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由于同姓同亲的农民住在同一个自然村。同一个村子,同一个祖宗、同一条血脉贯通下来,形成形形色色的共同事业、共同利益,从而具有亲密的关系与情感,也促成了互信互守的行为规、道德礼仪,形成一个或数个血缘群体。中国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中投顾问·让投资更安全 经营更稳健 未来5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前景规划 按照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2018年至2022年这5年间,既要在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又要为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8-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调研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表示,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各地区各部门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得以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体系初步构建,农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乡村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初步构建。探索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投资政策与方法 一、基本原则 1.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依规拓展业务,注重合作共赢,带动农村同步发展、农民同步进步。 2.遵循市场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将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加快建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坚持“放管服”改革方向,建立健全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重点领域。 3.坚持开拓创新。 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市场化、专业化等优势,加快投融资模式创新应用,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开辟更多有效路径,探索更多典型模式。有效挖掘乡村服务领域投资潜力,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保持农业农村投资稳定增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二、投资的重点产业和领域 1,现代种养业。 支持社会资本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种养业,巩固主产区粮棉油糖胶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延伸拓展产业链,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发展青贮玉米、高产优质苜蓿等饲草料生产,发展草食畜牧业。支持社会资本合理布局规模化养殖场,扩大生猪产能,加大生猪深加工投资,加快形成养殖与屠宰加工相匹配的产业布局;稳步推进禽肉、牛羊肉等产业发展,增加肉类市场总体供应。鼓励社会资本建设优质奶源基地,升级改造中小奶牛养殖场,做大做强民族奶业。鼓励社会资本发展集约化、工厂化循环水水产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盐碱水养殖和深远海智能网箱养殖,推进海洋牧场和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投资力度。 2,现代种业。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创新型种业企业,提升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加强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育种创新、品种检测测试与展示示范、良种繁育等能力建设,建立现代种业体系。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建设,推进甘肃、四川国家级制种基地建设与提档升级,加快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畜禽保种场(保护区)、国家育种场、品种测定站建设,提升畜禽种业发展水平。 3,乡土特色产业。 鼓励社会资本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开发特色农业农村资源。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乡土特色产业,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集约化加工基地、仓储物流基地,完善科技支撑体系、生产服务体系、品牌与市场营销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利益联结紧密的建设运行机制,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乡村手工业,发展一批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培育“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规范化乡村工厂、生产车间,发展特色食品、制造、
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2012-07-26 17:07:33) 转载▼ 标签: 杂谈 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王静云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农民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且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因此,无论是基于权利与公平的观点,还是从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所谓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全体国民因各种原因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由于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相对薄弱,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尤为迫切。本文主要论述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构建和谐社会;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现行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长期滞后。总的说来,农村的养老保险情况并不理想,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也非常低。由于我国农民基数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能一蹴而就,以及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成为当前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的人为历史性因素。城市居民享受的国家给予的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住房、粮食和副食补贴等待遇,而这些农民都没有。经过多年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截至2008年底,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面,参保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有财政补贴的约为1000万人。在农村低保方面,全国农村低保对象有4291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5.9%,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222.3亿元,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82元。在农村五保供养方面,全国有543
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 (2009-2015年) (征求意见稿) 乡村旅游具有资源潜力大、覆盖面广、受益群体多、市场需求旺盛、综合带动性强等特点,对拉动社会消费、促进农民就地现代化、优化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提升文化传承与文明程度、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促进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发展和转型升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进一步发挥乡村旅游对拉动消费、促进增长、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特殊功能,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特编制此发展纲要。 一、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实现产业联动和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对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游客旅游文化消费需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各类乡村风光,宣传文化和生活吸引,开展乡村观光、休闲、度假和体验性旅游活动,对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和弘扬民族文化,丰富和优化我国旅游产品
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市场结构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可以实现城乡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实现城乡、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立足自身实际,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特色化,增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就地走向现代化,开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径。 (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难题,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既可以拉动广大的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市场,也可以培育广大农民旅游消费的能力,形成巨大的农民旅游消费市场,通过城镇和乡村两大旅游消费市场的开拓,成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是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业可以有效带动相关旅游服务要素发展,促进农副产品品种、品质结构的调整和农副产品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无公害发展,带动乡村旅店经营、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装修业、建筑业和文化产业等的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可以有效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可以有效利用农村人力资源,吸纳老弱妇等弱势群体就业,实现农民就
“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些年来存在于村庄社区中的政治现象,渐渐成为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可取的治理模式,“村庄能人”能通过个人魅力和个人威望提升公共权威的影响力,减少决策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且通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获得为社区公共事务发展所必备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 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和公共事务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能人治村”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使得其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因此对它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更清晰的去了解“能人治村”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具体的“能人治村”的村组典型上,通过对该村组公共事务的发展的描述,并以该村组内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实例,分析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中,村庄能人对该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具体行为对供给效率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现实状况的准确描述,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很有益处的。 关键词:能人治村;公共事务;农民文化中心供给
ABSTRACT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hat prese nt in the village com mun ities in rece nt year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sirable model of governance in China'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 flue ntial Member"ca n upgrade the in flue nee of Public authority through pers onal charisma and personal prestige, reduce the costs of decision-making,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collective acti on. And through their pers 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ey can accessto the necessary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the n improve the efficie ncy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man ageme nt.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the developme 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have bee n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time in academic area, a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makes its practical sig nifica nee in creas in gly prominent. So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t is very n ecessary. Based on the existi ng theory of the study, I attempt to un dersta 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more clearly.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ill be fixed on a specific village, in which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is typical. Through the descripti on of the public affairs developme nt in the village, and tak ing the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n ter as an example, I will an 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In flue ntial Member on the developme 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impact of his specific act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on the supply efficie ncy. It is worth no ti ng that, this paper is not committed to raise a nu 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xisting issues in reality, I believe that the accurate descripti on of the situati on itself is very useful for the settleme nt of the issues. Keywords: In 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Rural Public affairs;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 nter 摘要....................................................... I…
我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的困境,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但是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构建和民间组织的发展等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 关键词:我国公民社会现状前景发展途径 所谓的公民社会是对civil society 的新译法,是基于社会三分法的逻辑提出的概念。按照社会三分法,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公民社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公民社会当做国家和政府系统以及市场和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包括NGO、公民的自愿性社团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更加宽松、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才悄然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但是由于我国的公民社会脱胎于国家社会不分的中国传统社会,加上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所以与西方国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一)、我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分析 1、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环境是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这也是我国的公民社会组织能过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历史和制度的惯性,也不免会有制度上的障碍。 首先是经济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能过塑造彼此独立的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形成个体的独立性,这正是现代公民的核心精神所在。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利益的多元化,公民有了不同的利益划分,那些利益和价值取向相同的公民为了更好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组成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所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公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践历程 (1) 摘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体经历探索和坎坷,大体经历了以家庭保障特征的初步建立阶段,以集体保障为特征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阶段,改革初期的家庭与土地保障为主的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探索的阶段的四个发展时期,虽然发展至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但是它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改善农民生活、支撑中国工业化战略顺利推进,作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 一、以家庭保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1949—1956年)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的保障主体。农民依靠在土地上的劳作保障自己的生活,当遇到特殊的困难时,往往以求助能够帮助自己的对象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传统的保障形式中,家庭保障起到了无以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以家庭保障为主,辅以社会救助、社会优抚以及农民间互助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阶段,政府根据自己的财力对困难农民的生活给予适当的补
助,但是总体上以家庭保障为主。 由于建国之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交通、就业、粮食等问题,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时期国家就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民进城,划分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待遇,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初步形成。在这一阶段,政府主要对农村救济和优抚安置工作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制定了一些有关的法规和条例,兴办了一些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事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初步建立。虽然这个时期国家已经介入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历史条件和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依然是以家庭保障为主。 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以集体保障为特征的阶段(1957—1977年)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农业高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中国普遍建立,农村中的个体经济也随之转变为集体经济。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由原来的以家庭为单位转变为主要以高级农业合作社为单位组织进行。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之后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探讨 汇报人: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探讨 摘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市的社会保障与农村的社会保障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了解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滞后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对策 中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城乡差距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作法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农村的生产制度与组织结构变迁并没有朝着好的态势发展,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仅要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情发展,而且还要以当前农村所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为前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完善程度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不遗余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一系列政策和有效措施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 2003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236-237。通知颁发以后,2007年已覆盖全国86%的县(市、区),参加农民达到7.3亿人。在2013底,全国开展“新农合”县2489个,参加“新农合”的人数达到8.02亿人,参合率达到98.7%以上,实际住院补偿比也逐年增高。2015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380元[2]。“新农合”的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建立。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推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商品经济,使得农村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就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各个农村立足于现实发展状况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根据规划,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民都能够享有新农保。中国的老年人口75%都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对他们的老年生活起一定的保障作用,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快速发展2007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这就为在农村全面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日期:2006年5月16日点击:138 现代乡村旅游市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新型旅游模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我国的乡村旅游一般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为灵魂,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乡村旅游的相关概念 (一)乡村旅游的定义 西班牙旅游学术界将乡村旅游分为传统乡村旅游和现代乡村旅游。传统的乡村旅游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来源于一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以“回老家”度假的形式出现。虽然传统的乡村旅游对当地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经济影响,并增加了城乡交流机会,但它与现代乡村旅游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传统乡村旅游活动主要在假日进行;没有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没有给当地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实际上,传统的乡村旅游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广泛存在,在中国常常把这种传统的乡村旅游归类于探亲旅游。 现代乡村旅游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明显区别于回老家的传统旅游者。现代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给当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还表现在给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给当地衰弱的传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现代乡村旅游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具有现代人特色的旅游者迅速增加。现代旅游已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庭院、经济作物和地方资源为特色,以为游客服务为经营手段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农家乐”的概念。去年在贵州举行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中国专家们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为灵魂,以此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丰富性;二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充分体现“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民俗特色;三是乡村旅游的目标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 ———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徐姗娜 摘要: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治理;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9)05-0013-07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和可信结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将作为乡村治理重要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置于乡村治理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为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结构、制度、精神文明和信仰上存在的困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乡村治理重要基础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是指在“当代农村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的需要。”①鉴于治理同样存在失效的可能性,为此,人们在省思和克服治理失效中还衍生出了良好治理的理论,也就是“善治”之说。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综合各种观点,俞可平对善治及其特征给出了中国式解读。在他看来,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②从影响乡村治理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角度看,乡村治理内在的人力资源(主要指基层乡镇干部)、政府组织结构、相关制度安排以及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有很大关系。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意味着政府要在其他行动之外,必须着力开发人力资源、实现组织发展、改革(或创造)制度及投资(积累)社会资本。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社会资本维度。 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目前学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定义是帕特南的观点,即把它理解成“社 作者简介:徐姗娜,文学博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委员会副书记。 13
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解 作者: 俞可平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月: 2002-11-01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会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是一本大杂烩,收集着不同的学者文章,反映着学者对公民社会的不同理解,体现着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书中收录了七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比较注重案例研究:王颖、孙炳耀所写的《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一文首先指出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政治环境的宽松是民间组织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背景;俞可平所撰写的《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是对福建漳浦东升村的典型的案例研究。选取该村作为研究个案,是因为从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来看,该村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与前瞻意义;孙立平的《民间公益组织与管理:“希望工程”个案》也是一个个案研究,通过考察希望工程来表现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市民自治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意图通过调查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具体变化及其过程,以揭示我国城市具有真正意义的市民以及市民社会组织正在崛起;《行业协会与经济领域中的民间治理》一文重点关注经济领域的重要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本书的收官文章是俞可平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作者指出公民社会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为政治学意义(更
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乡村治理新实践(上) 一、单选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1. 根据本讲,北宋初期,掌课输的不包括()。 A.里长 B.户长 C.里正 D.乡书手 2. 本讲提到,洪武四年,政府设立(),负责税赋征收,防止胥吏侵贪农民利益。 A.保甲制 B.粮长制 C.里甲制 D.乡和里制 二、多选 ( 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本讲,基层代理人职役化的结果并非像预期那样,反而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缓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包括()。 A.武力镇压 B.实行无为而治 C.将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降至最低限度 D.开辟了官治和民治两条通道 三、判断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1. 本讲提到,唐朝里正的职责比较小,里正属官。 正确
错误 2. 根据本讲,自宋朝以来,乡村组织主要负责人保长、都保、里长、甲首、粮长等来自村民,已被完全排除在官僚等级制之外。 正确 错误 1. 根据本讲,北宋初期,掌课输的不包括()。 A.里长 B.户长 C.里正 D.乡书手 2. 根据本讲,唐朝实行的三级治理模式,不包括()。 A.乡 B.里 C.村 D.族 二、多选 ( 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 1. 本讲提到,基层代理人职役化的后果包括()。 A.在集权制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官员及代表官府办事的胥、吏、役可以随意支使这些乡村领袖,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些乡村精英的尊严 B.额外摊派容易导致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破坏了他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用和社会资本 C.最终担任里长、保长、粮长的常常是一些贫穷且奸巧、刁顽的无赖 D.导致了基层代理人的逆向选择,进而破坏了国家在农村的权威 三、判断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2011年11月 浅析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对策 文/史春泽 摘 要:“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重点是社会保障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1-0098-01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绝大多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成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尤其是社会保障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91年到2003年,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渐趋成熟。但是在全面发展的同时,由于受经济水平的限制,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很大的差距和不足,表现在: 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社会保障体现的是政府的责任,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给予的投入不断增加,2007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为109.1亿元,2008年已达到228.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0.1%和109.6%。虽然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政府投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由于物价上涨,按原来核定的政府投资,其保障能力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少,保障程度可想而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近几年的低保标准都未能达到低农村家庭的衣食住行的消费水平,即使按照最高标准救助农村低保户,也未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影响到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范围小。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2004年虽达15364个,却仅占全国乡镇位数的35%,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行政村仅占24%。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机构的地区,尽管集体也以公益金和合作医疗基金的形式向农民收取社会保障费用,但由于个人缴纳的公益金只是赡养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社会供给性差,而且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农民没有积极性。而且大外分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对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本是空白的。在这种情况下,使国家无法对农村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极不适应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3、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管理与保值增值存在问题。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基金统筹的层次都是在县一级。在县级层次的统筹管理方式下,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合理性较差,另外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这就使得社会保障资金不仅面临着被挪用或非法占用的安全性风险,而且在当前形势下,还会遇到资金投资管理方面的人才瓶颈约束,以至于影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管理与保值增值。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投资运营收益率也不高。现行的政策规定,省级及以下单位结余的社会保障资金不享有投资权,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难以抵御通胀贬值的风险。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1、要加大财政投入,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资金问题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尤其在我国农村现阶段,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必要。首先应增加对农村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在农村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社会救济制度,以保障农民最低生存的需要。其次,要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持。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险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初期,国家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持。同时,由于现行税收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因此各级政府应将其纳入财政预算,以支持农村社保事业。 2、确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诉求。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应首先确立公平公正的理念,对农民实施以社会保障的保护,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去规范、约束制度的实施,使农民能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中生产生活,不能每遇到制度建设的困难就牺牲农民,保全城市公民,让所有农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享受与城市公民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在综合考量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做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的平等、健康发展,实现公平。在现在的形势下,本着公平公正的理念,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开展社会保障建设。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方位为农民服务。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是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有权也有责任为公民实现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民。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必须与其他制度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要想做到宏观上的平衡,必须由国家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实现。农村的风险来自各个方面,农业生产作为一个质弱产业和极强公共物品特质的产业,其高风险性必然要求政府的强力支持,以保证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所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只能,通过制度与财政支持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4、要为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要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走上正轨,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应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及一系列相关的专项法(社会保障基金法、社会保障程序法等),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的完整体系,确保农村的社会保障切实落实到农民的自身利益上。 总结: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社会为总体目标,严格执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使农民切实感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现实利益,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作者简介:史春泽(1987— ),男,河北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铁卫,曾凡涛.当前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难点问题与对策.西安财经学院院报,2005,6-3. [2]杨团,毕天云,杨刚.《21世纪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之路》》. [3]杨小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分析.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8-4. 三农问题 98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