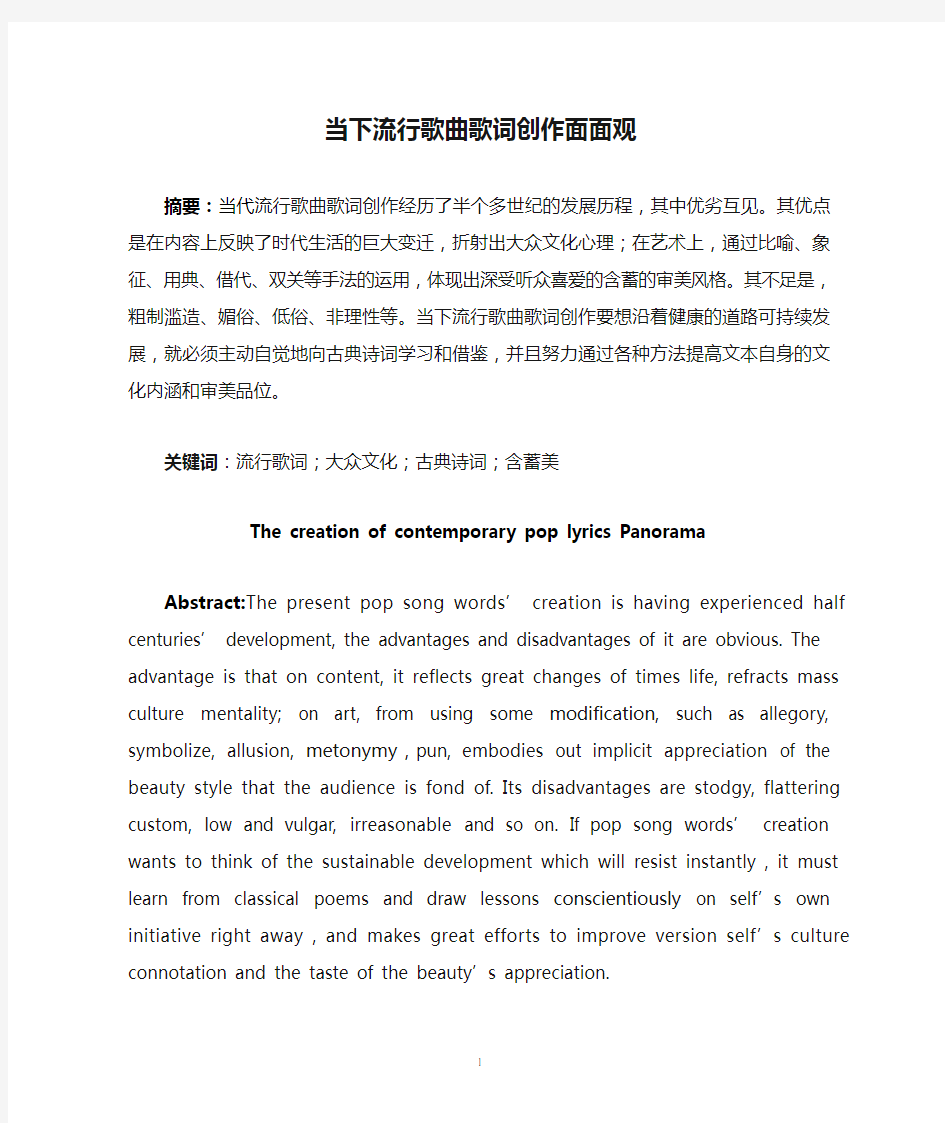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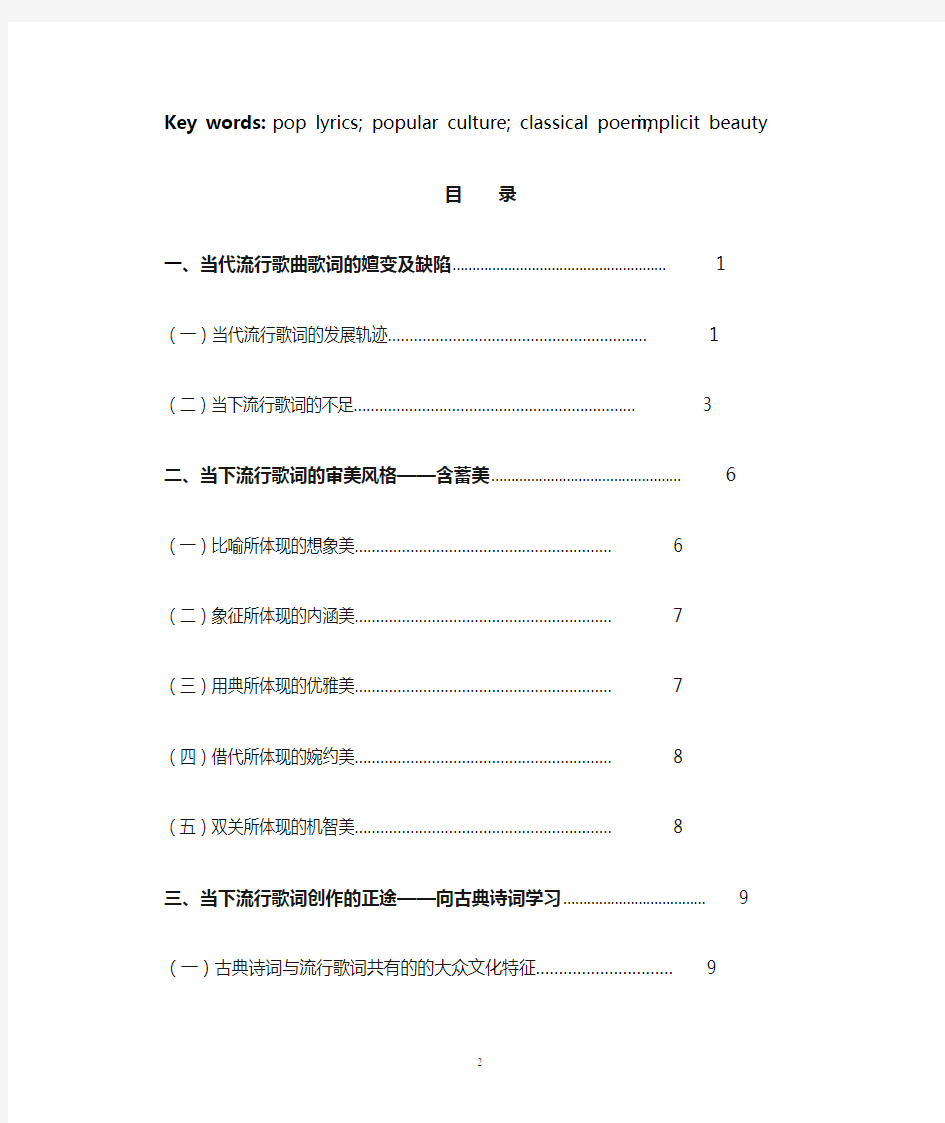
当下流行歌曲歌词创作面面观
摘要:当代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中优劣互见。其优点是在内容上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巨大变迁,折射出大众文化心理;在艺术上,通过比喻、象征、用典、借代、双关等手法的运用,体现出深受听众喜爱的含蓄的审美风格。其不足是,粗制滥造、媚俗、低俗、非理性等。当下流行歌曲歌词创作要想沿着健康的道路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主动自觉地向古典诗词学习和借鉴,并且努力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文本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位。
关键词:流行歌词;大众文化;古典诗词;含蓄美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p lyrics Panorama
Abstract:The present pop song words’ creation is having experienced half centuries’ developmen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t are obvious. The advantage is that on content, it reflects great changes of times life, refracts mass culture mentality; on art, from using some modification, such as allegory, symbolize, allusion, metonymy,pun, embodies out implicit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tyle that the audience is fond of. Its disadvantages are stodgy, flattering custom, low and vulgar, irreasonable and so on. If pop song words’ creation wants to think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will resist instantly , it must learn from classical poems and draw lessons conscientiously on self’s own initiative right away , and makes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version self’s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the taste of the beauty’s appreciation. Key words: pop lyrics; popular culture; classical poem; implicit beauty
目录
一、当代流行歌曲歌词的嬗变及缺陷 (1)
(一)当代流行歌词的发展轨迹 (1)
(二)当下流行歌词的不足 (3)
二、当下流行歌词的审美风格——含蓄美 (6)
(一)比喻所体现的想象美 (6)
(二)象征所体现的内涵美 (7)
(三)用典所体现的优雅美 (7)
(四)借代所体现的婉约美 (8)
(五)双关所体现的机智美 (8)
三、当下流行歌词创作的正途——向古典诗词学习 (9)
(一)古典诗词与流行歌词共有的的大众文化特征 (9)
(二)古典诗词可为流行歌词创作提供丰富素材 (11)
(三)古典诗词能为流行歌词创作提供好的思路与风格 (11)
注释 (13)
参考文献 (14)
流行歌曲的英文作“popular song”。“popular”本身就有流行的、受欢迎的意思。其实,“流行歌曲”中的“流行”一词在先秦已经存在,意思是“广泛传布、盛行”。流行歌曲大致可分为音乐和歌词两部分。本文主要探讨研究流行歌曲歌词(以下简称流行歌词)文本。
当代流行歌词已经成为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宠儿,渗入并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日常语言、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通俗、简洁、形象的歌词常常一道破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说出了人人欲说却又难以言传的心事,成为了一种大众文本,被直接或改版后作为社会话语广为传播,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快速沟通的符号。
中国的大众文化文本,要数流行歌词发端早、受众广、影响大。在文化转型期和全球化语境中已经形成可持续性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流行歌词由于本身固有的商品性与愉悦性。为了取悦听众,获得广泛流行和最大利润,创作者和发行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消费者的舒适、方便、宣泄、休闲、娱乐等世俗追求,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本身的艺术审美追求为代价。因此产生了许多庸俗、媚俗、滥俗、煽情、滥情的流行歌曲作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正视的是流行歌词中的形象系统是丰富多姿的,也存在着大俗大雅、俗中见雅、外俗内雅、雅俗共赏的文本。其中也有可能具有经典诗歌文本的审美价值。现在该到了对流行歌曲资源进行清理、鉴别、筛选、阐释、批判,对其形象的审美功能进行客观审视的时候了。如有学者所说:“在不拘一格的大文学史里,理应有它(即歌词——笔者注)的一席位置,在艺术殿堂里,我们应该郑重其事地为它摆上一把交椅。”[1]这里将从社会心理、语体特征、与传统文化的对接三方面对流行歌曲做一种解读。
一、当代流行歌词的嬗变及缺陷
(一)当代流行歌词的发展轨迹
流行歌词在中国的命运是坎坷的,无论是在上世纪30到40年代,还是它复兴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然而也许是对这种漠视的反动,流行歌词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却顽强地生根发芽,向上生长。1949年后,流行歌曲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歌曲才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复兴,并在上世纪90年代趋于繁盛。时至今日,流行歌词文本也同样已经渗透到
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不可取代的精神产品。
流行歌词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词文本。一个好的流行歌词,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人情、人性、道德等的象征,成为一个时代的丰碑。抗日战争时期,《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歌曲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歌曲激昂的旋律和歌词激励着热血志士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前线。
早在1978年及其后稍晚的时候,文学界已经以《伤痕》和《班主任》表明了一种新的创作态度,“星星画展”和朦胧诗派也已经如日中天,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但在歌词创作领域,却没有出现同步取向。惟有的突破来自两首歌曲,一首是《乡恋》,一首是《军港之夜》。这两首歌的歌词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发展到了近乎于批判的地步。
同一时期影响巨大的港台歌手有邓丽君、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建、刘文正、凤飞飞、徐小凤和蔡琴等。然而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同样属于过去的年代。真正对中国人有影响的则是电视剧《霍元甲》和《陈真》的主题歌: 《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其中含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歌词,尤其是后者与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合流,形成了流行歌词主旋律化的潮流,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认同,并出色地呼应着。
但更重要的是,直接受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里奇等世界著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的影响和罗大佑、张艾嘉等人举办献给世界和平年60名歌星音乐会《让明天更美好》的启发,北京组织了一场献给世界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的《一无所有》和郭峰、陈哲等人的《让世界充满爱》则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场音乐会上问世。《一无所有》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他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冲击和文化反叛,而在于他的歌词中展现出一种新的生存视角和生活态度。陈哲在《让世界充满爱》和其后的《五十亿的我们》、《不曾宣读的未来》、《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等一系列作品中提供了不同于崔健的另一种话语。其主要的特征是对同样“大”题材的个性化诠释。而对苦痛、面对历史时空、面对崇高等中国人熟悉的生存命题,陈哲表现出一种追求真实的不妥协的态度。
这种情况下,另一首来自广州的歌成为流行音乐创作前途的强烈暗示。这就
是《信天游》。它的歌词则透射出遥远的空间感和“淡淡的哀怨”。“白云悠悠轻轻地游,什么都没改变。”这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巨大而迅速的成功并导致它成为北京音乐沙龙的研究样板。其中,孟广征和徐沛东合作的《我热恋的故乡》第一句就以“我的家乡并不美”,完成了对歌颂家乡题材写作话语的颠覆。李文歧和李黎夫合作的《心中的太阳》则以“我不知道”的反复呐喊完成了另一种颠覆。而赵季平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以彻底回归原始民歌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柔美动听的新“民歌”概念的颠覆。这些作品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近乎疯狂的“西北风”歌潮。
1988年下半年齐秦的《狼》的引入,虽然同他一起到来的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也唱疯了天下,但齐秦却俘虏了年轻一代的心。并如此导致了中国流行音乐向自身的回归。而他那句“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则给华人世界的出国梦与出国潮添上了极妙的注脚,成为又一句经典性的语句。
1989年到1992年4年间,港台歌曲再次抢滩成功。齐秦的“北方的狼”、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潘美展的《我想有个家》、郑智化的《水手》、童安格的《花瓣雨》、周华健的《花心》、姜育恒的《再回首》乃至小虎队的《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作品中隐含着强烈的后现代倾向对内地歌词创作者来说是一次撞击。整个80年代中,内地音乐人一向认为港台“没文化”,然而,面对被港台歌星征服的下一代学生,音乐人们目瞪口呆。严肃主题迅速化解在新兴都市“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深刻的追问散失在“岁月不知人生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的哀叹里,英雄的幻梦让位给了现实的明星。
(二)当下流行歌词创作的不足
90年代以后,当代流行歌词中有一部分作品是比较优秀的,但与此同时却也有很多作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大体而言,时下歌词创作中信手涂鸦、粗制滥造的现象几已成为一种风气,大量胡言乱语,不知所云,甚至满纸粗话、脏话的“垃圾作品”随处可见,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小则蔽人耳目,污染大众的视听环境,大则颓人心智,足可导致一场文化危机。以文学创作中最基本的要素语言文字为例,流行歌词中就出现了“错字别字满天飞”、“语言苍白贫乏”、“词意混乱不堪”、“胡乱肢解成语”等“严重症状”和“语法混乱,不合逻辑”、“病句
百出”、“大话连篇”、“陈词滥调,空洞无物”等“十大硬伤”。从语法到句法的种种误用、滥用现象在流行歌词中随处可见。如此混乱的局面就使得一些研究者对流行歌词痛心疾首,或者要为当代流行歌词“把脉”,或为其发下“病危通知”,有人则干脆呼吁将流行歌词中的低劣作品当作“语言垃圾”一样清除掉,以“净化语言环境”。
当代流行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而内容狭窄(局囿于男欢女爱的恋情题材)、作品艺术品味不高,格调低下等现象尤为突出既然题材上难有突破,许多歌词作者为了市场效益,索性选择媚俗搞怪或盲目模仿的创作模式。如不久前风行一时的《老鼠爱大米》一曲,其歌词将美好纯真的爱情表白为“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本来就匪夷所思,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所谓的“新意”和“亮点”,竟然吸引了很多词作者的眼球,于是乎,“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水煮鱼》)“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你让我痴,让我狂,爱你的嚎叫还在山谷回荡”(《披着羊皮的狼》)之类离奇怪异的歌词相继出炉。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流行歌词的出路何在?
流行歌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就本质而言,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它也应该反映特定社会文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同时还对大众的心理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当代流行歌词创作,似乎已经处于“重心失控”和“价值失范”的边缘。透过这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方阵,透过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和火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只是狂热的煽情、做作的粗糙、病态和抒情的苍白。尤其是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使本该产生经典的时代成了滥情和浅薄滋生的温床,正像假冒伪劣商品侵害着我们的物质生活一样,残次病态的流行歌词,正侵害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制造的残次病态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公害。针对时下流行歌词高温发热、胡言呓语、茫然无措的现状,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就曾疾呼:“当代流行歌词创作这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已经约束了我们的创作,盲目者是无法步履雄健的”。
这两年,已经有不少流行歌词屡屡被网友指为低俗无聊,甚至色情。《老婆
老婆我爱你》、《老公老公我爱你》、《香水有毒》、《QQ 爱》、《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求佛》、《狼爱上羊》、《那一夜》等等广泛流行的歌词,都曾被批评为低级趣味。“其实就歌曲本身来说,歌词低俗情况一直都存在。”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说,但这些年网络音乐兴起之后,调动了相当一部分市场,因为这样的歌词看起来比较“草根”,更容易流传。在科尔沁夫看来,过去国内流行音乐的市场比较小,正规的音乐公司不会去制作歌词低俗的歌曲,过去的歌手少,要求也高,一年不见得能出一个专辑,所以每次创作都投入很多。而现在伴随着网络音乐的兴起,音乐制作的门槛降低了。通过网络,很多创作者随便写首歌就能让很多人听到。为了吸引眼球,有些人在创作的时候开始有意往低俗的路子上走。“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急功近利,创作歌词时首先想的是怎么能出名,所以不惜用低级的方式来迎合一部分受众的关注。”科尔沁夫说。由于有争议就能吸引关注,有些创作者就干脆怎么有争议怎么写。一旦引起争议,歌火了,创作者也赚足了眼球。近年来,受网络音乐、无线音乐的影响,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走入低谷。科尔沁夫告诉记者,现在唱片是越做越不赚钱。与之相反,网络音乐的盈利开始出现迅猛增长。有统计显示,2006年网络歌曲就盈利了50 亿元人民币。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部分创作者在创作时放弃高雅,追逐低俗。
这些取巧者往往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一个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的歌词是不可能一直流传下去的。流行歌词文本应该有着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
流行歌词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呈现出低俗化的现象。这些歌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代百姓追求快餐文学的文化心理。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蕴涵丰富、含蓄优美的流行歌词似乎应该很难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找到自己立足的位置。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近来,中国流行乐坛刮起了一股复古风,其歌词大多有古典诗词的韵味,主动的向古典诗词学习借鉴,如方文山的《东风破》《青花瓷》,funck 的《逍遥叹》、小柯的《谁动了我的琴弦》等。这些歌词有着较高的文学内涵,表明了当代职业词作者有别于网络作者的一种专注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也使得当代流行歌词依旧具备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当代流行歌词创作积极的学习和借鉴古典诗词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种借鉴也是有一定渊源的。
二、当下流行歌词的审美风格——含蓄美
中国流行歌曲虽是现代开放社会精神文化的产物,但由于其运用了具有含蓄之美的诸多传统辞格,故总体上其歌词在“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同样不乏“含蓄深沉”的韵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应该更加适合中国人民的审美特征。而当今那些大红大紫的快餐式流行歌词将注定很快被人们所淡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时代记住的文化资本。当代流行歌词的创作在表现手法上也应该相应的注重含蓄的表现手法,使得歌词的意境更加深远,更值得人品味。
(一)比喻所体现的想象美
在流行歌词的各种比喻中,最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要数暗喻和借喻。先看暗喻。与明喻不同的是,这类比喻本体和喻体之间并无明显的“形似”之处,而是由作者人为赋予其某种暂时联系,以达到传神写意之目的,故有人将这种比喻称为“远距离比喻”。从审美角度看,暗喻往往因其彼此关系的陌生化而具有“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的含蓄之美。(叶燮《原诗》) 。以《涛声依旧》为例。此歌述说的是一对已经分手的恋人再度相遇时所激起的感情波澜。本来,“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没想到重逢后“我”竟不自禁,仍想和对方“重复昨天的故事”,但又担心“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于是,只好小心翼翼地作试探性发问:“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末句的设喻可谓巧妙之至。“你”是“客船”,“我”是“船票”,本来直上即可。问题是这是一张过期的“旧船票”,没有“你”的前缘而又忐忑不安、不敢挑明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又含蓄深沉。如果改为“我们是否可以从头再来”则直白无味了。“我的梦是陌生的港口,停泊以后就不打算久留”(《我可以》) 等暗喻佳句也颇耐人寻味。
再看借喻。流行歌曲中的借喻,往往是借花喻人(女性) ,以喻抒情,显得趣味横生。请看《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她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阅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她轻轻地摘”。显而易见,将少女的情窦初开比作悄然绽放的玫瑰,把“我”是否接受其爱说成是该不该“轻摘”,不仅符合东方少女羞涩内向的心理气质,而且因其物我合一而极富情趣,令人遐想。
象征必须思而得知,因而也同样富有含蓄美。如《诗经》中的《硕鼠》、屈原的《桔颂》、舒婷的《致橡树》等名作即是。流行歌词的象征自有其特性。从其在全词中的比例来看,有局部象征和总体象征两种。前者只是在某句某行象征。如“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之“歌谣”(《弯弯的月亮》)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之“风雨”、“彩虹”(《真心英雄》) 等都是虚实结合,另有所指。后者即全词始终围绕某一个意象来展开。
(三)用典所体现的优雅美
流行歌词用典的特色在于:一是从典故的选择上看,都选用具有通俗性、普及性的典故。如《愚公移山》、《孔雀东南飞》等所用典故都是家喻户晓的。这是因为流行歌曲是大众艺术,受众层次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如果所用典故过于冷僻生疏,知者寥寥,就难以流行。二是从典故的数量上看,有单一式和集合式两种。单一式就是一首歌词只用一个典故,上述的《愚公移山》即是; 集合式就是一首歌词中运用数个典故,如《千古绝唱》就用了“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雷锋塔与白娘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六个典故。三是从典故的表达上看,都力求表述的通俗易懂。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故其用典不必也不应像诗那样浓缩概括,而应适当“浅易化”,以便“大众化”。明代戏剧家王骥德在《曲律》[7]中论述“用典”时就指出:“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隐事显使,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如《花梦》一词:“梦里看花花非花,花里有梦梦非梦。如果不是前世许下的约定,今宵我又为谁等。花开花谢已春夏,梦起梦落又秋冬。如果不是梦中相随的花影,今夕谁解不了情。”显然,这首流行歌词是以白居易的《花非花》[8]为“蓝本”拓展而成,但它已不像原诗那么朦胧难解。用典的作用一方面是言简意赅,以少胜多,能用最少的字句去表达最丰富的含意; 另一方面是借古喻今,曲尽其意,可用来抒写一些难言之隐。但用典也有其局限: 一是典故来源极其博杂,非熟读诗书,通古博今者,很难驾驭和理解; 二是容易破坏意境的浑然一体。借典言情,间接曲折; 借典写景,更是隔膜。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9]“‘冷月无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故用典须适当,要谨慎,可用可不用的,最好不用。
流行歌曲中的借代,主要是以下情形富有含蓄美。一是特征代本体。如“不觉我说着说着就天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了一种苦涩”(《心如刀割》)。“苦涩”指什么? 显然是“眼泪”;而“眼泪”又为什么会“苦涩”? 那是因“我”失恋而心里“痛苦”,所以连泪水也觉得“苦涩”。这样,以“苦涩”之味来代指“我”因失恋而流之泪,中间就“跳”过了心理感受的环节,令人非思考不能索解,这就比直说“痛苦”更有“味道”。二是具体代抽象。如“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曲记录下你的日记。”(《把耳朵叫醒》)。显然,这里的“日记”是指“心绪”之意,但如此“换名”而不直说,首先是这样做具有可行性。因为,“日记”、“歌曲”两者的本质都是抒写情思意绪;更主要的是,通过如此借代,因彼此关系的“陌生化”而令人产生新奇感:歌曲怎能记录日记? 三是部分代整体。《味道》这首歌词不直接诉说相思之情,而是用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淡淡烟草味道”、“被爱的味道”等具体意象来代替对方。从表达效果来看,其借体越细越多,就越加显出其思念之深之切,且把对方身上的各种“味道”也都纳入“想念”范畴。这样超常的语言搭配,更令人思味。显而易见,借代因其凝练简洁、生动形象、一物多名而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含蓄美。
(五)双关所体现的机智美
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修辞手法,反映了汉民族表达委婉,追求话语“典雅”和“含蓄”的文化心理。以《记得你陪我躲过雨》为例:“因为注定要相遇,才会有这场大雨。我和你躲在屋檐下,你的目光还是把我淋湿。如今许多年过去,仍记得你陪我躲过雨。躲过了雨滴,躲不过你。躲过了今天,躲不过今世。躲过了瞬间,躲不过记忆。记得你陪我躲过雨,躲进了一个美丽的童话里。”显然,这首歌词写的是曾经相爱的人们的一次雨中邂逅,其“躲雨”实是寓意双关。“我”所遇到的不仅是自然界的“雨”,更是毫无准备又没有结果的感情纠葛。虽然“你”的拒绝令“我”狼狈不堪(淋湿) ,但“我”依然眷恋不已,感情上“躲”不过“记忆”。可以说,这是一首苦涩的单相思恋歌。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双关是“话里有话”,故若恰当运用,便可使歌词富有弹性,含蓄曲折,生动活泼且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当下流行歌词创作的正途——向古典诗词学习
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无论是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凝练的语言形式,还是委婉含蓄的表情达意、意味悠远的艺术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流行歌词已经成为如今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充斥、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流行歌曲其实是一种文化,尽管更广泛地称之为通俗文化,但它和文学作品是相辅相承,殊途同归的,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歌词创作的问题,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歌的范畴。笔者提倡流行歌词创作应向古典诗词学习,原因有如下:
(一)古典诗词与流行歌词共有的大众文化特征
1、商业性
首先唐宋词产生伊始就非为文人孤芳自赏地言其志或怡其情之体,而是“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产物。换句话说,唐宋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消费集体化的商品性质。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把结集的目的说得很明白:“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这说明,整部《花间集》,主要是为歌女于酒宴樽前“浅斟低唱”和听客们佐欢娱乐而备。词既然是消费性的精神产品,那么,它必然要在被消费的过程中体现其商业价值。又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由此可知,一些词在柳永手中,也是用来交换“金”和“物资”的商品。[3]而现代流行歌词同样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旧上海流行歌曲的创作,大约以黎锦晖1929 年前后出于商业需要而创作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上》《花生米》《小小茉莉》等发其端。继黎锦晖之后的大批流行歌曲作家,如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李厚襄、严个凡、梁乐音、严华等等,都是或为电影写作,或为电台和唱片公司写作。他们的作品被广泛传唱于各大歌舞厅、商业电台或被大量灌制成唱片发售,其商业特征显而易见。当代流行歌词则更以其时尚、新潮和另类的姿态站到了城市商品经济大潮的风头浪尖上。制作人对歌手的包装宣传动辄投以成百上千万,各种媒体也大肆炒作,所有这些,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获取市场回报。为迎合市场,不少流行歌曲的创作已呈“批量生产”之势,一张新专辑,从创意、写作、配器到录音都可按“流水线”规程操作,在某
个原创音乐流行榜的获奖“金曲”中,以“爱”字为名的曲目竟有1/ 3 之多,如《改》( 谢明训词) 、《好想好好爱你》( 邬裕康词) 、《爱了就知道》( 姚若龙词) 等等。如果说前些年的革命歌曲是政治的一统天下,那么现今的流行歌曲则难逃市场的左右,当代流行歌词题材片面化和狭隘化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创作者过分强调经济效益的结果。
2、娱乐消闲性
毋庸讳言,唐宋词是当时都市人群中流行的一种娱乐消闲性文艺工具。士大夫文人填词,多为应酒宴间歌儿舞女之请,是逢场作戏,是随意性的应酬;市井细民作词听曲儿,也不过是业余的娱乐消遣和为消愁解闷。前代的词论家早已将词体遣兴佐欢的特点表述无遗。如冯延巳的外孙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说冯“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4]可见冯氏填词的娱宾遣兴之效。而文坛宗师欧阳修填词时,亦是一副闲暇之余为求一时欢乐的悠闲之态:“良辰美景,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而辛弃疾不仅“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得意之处尚“使妓迭歌,益自击节”。[6]从词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士大夫文人私生活的另一面。
与唐宋词的娱乐消闲性相较,当代流行歌词无疑含有更多由现代都市文明催生的消闲和娱乐的因子。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城镇居民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于爱和美的追求也更加热烈,再加上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各种压力加大,在工作学习之余,人们很需要一定的松弛,甚至宣泄来调节生活节奏,减轻心理压力。流行歌词之所以能被大众这样普遍地接受,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迎合了都市人的这种心理和生理需求。它不但舒缓了由城市巨大竞争压力而带来的诸如焦虑、恐慌、错乱、失态、虚弱等不良都市精神症候,并且能使大众在参与时获得某些快感和满足感。流行歌词之成为现代城镇居民最青睐的娱乐消闲内容之一,还在于其精短却多样化的形式符合现代都市人对于娱乐消闲活动的“快餐化”要求;同时,流行歌曲的词之紧随时尚的特点又满足了他们追逐潮流的心理。而且,如果说唐宋词的娱乐休闲性还主要局限在秦楼楚馆,茶舍酒楼或官宴家席等公共消费场所的话,那么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参与流行歌曲的娱乐消闲行为则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更加自由随意,既可以共享,又适于独自品味。
古典诗词能够从街头文学逐步走上案头文学,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是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文学特性的。当代流行歌词与古典诗词有着极其相似的创作背景,这便暗示着当今流行歌词文本有着很大的文学发展的空间。而如今日益衰败的流行歌词主动的对昔日的经典——唐诗宋词的借鉴是相当有必要的。
(二)古典诗词可为流行歌词创作提供丰富素材
流行歌词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曾作为古时代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衍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子,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情感表现力极强。
这方面最有名的当属邓丽君。邓丽君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她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这些足以说明经典诗词与流行歌词的渊源关系。流行歌曲这种通俗的文化形式,在古典诗词的介入下,恰到好处的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其艺术层次也得以较好的提升。
(三)古典诗词能为流行歌词创作提供好的思路与风格
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古典诗词的语言
格式与风格,这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个人愁闷,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如表现友情方面的元曲关汉卿《双调·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饯行杯,别离泪,刚道声保重将息。”流行歌曲《驼铃》化用过来“送战友,踏征程……一路多保重。”歌词古朴而有侠意,唱起来酣畅淋漓,豪情万丈。表现亲情方面,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代歌曲《望乡》“夕阳河边走,举目望苍穹,……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欲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捧一盏乡酒陪伴着你哟,我身在他乡与远方。”唱来情感深沉,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无不与我们对《静夜思》这首诗有较好的领悟与赏析有关。古典诗词所蕴涵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激起现代人丰富的情感,给歌曲以新的情感体验。歌词的写作手法上少不了模仿与借鉴,现代的流行歌词也是从古典诗词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如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采用比兴手法,运用排比、叠音、叠韵、衬字等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古典诗词里更常用到的。如《天不乱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天不乱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开口妹心怎么想”就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歌唱祖国》中运用了比拟的手法:“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层层梯田一片片绿”;《雾里看花》“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与《青藏高原》“呀啦索,哎,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就是运用了衬字。这些手法的运用,为歌词增色了不少,这些例子在现代歌词的创作中,那是举不胜举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流行歌词在写作手法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是很必要同时也是很恰当的。这些手法的借鉴和运用使得流行歌词文本的文学内涵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流行歌词文本本身的文学内涵。流行歌词本身对辞格的运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征。
当代流行歌词在反映社会文化,影响青少年心理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流行歌词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可能没有一个社会学家反映的全面,但是却更加
及时。同时流行歌词受众广大,其中多为年轻人,他们在心智上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一些低俗的歌词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不健全。因此,对流行歌词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流行歌词的创作需要广大词作者自觉提高素质,不断的学习和借鉴;政府应引领广大传媒和集体抵制低俗歌词的传播,切断一些投机取巧者的利益来源,还流行歌词创作一方净土。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10]当代流行歌词文本凭借着强大的媒介优势和广大的受众,已经具备了被人们记住,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文学潜质。甚至有些流行歌词文本已经被选入教材,相信流行歌词在经历一段低谷时期后,必将迎来一个创作的春天,从街头文学成为案头文学被人们重视。
注释:
[1]胡疆锋.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属性[J].词刊,2007(3).
[2]崔黎民.花间集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2.
[3][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
[4]陈世修.阳春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2.
[5]欧阳修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2.
[6]吴敏霞.桯史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87.
[7]王永生.王骥德《曲律》与诗学传统[J].戏剧杂志,1999(6).
[8]郑永晓.白居易诗歌赏析[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147.
[9]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4.
[10]鲁迅全集(卷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56.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金兆钧.颠覆还是捧场[J].读书,2002(2).
[3]傅晓蓉.流行歌曲与校园文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2).
[4]陶东风.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M].杭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5]叶申芗.本事词.[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97.
[6]王一川.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J].艺术广角,2001(2).
[7]陈四益.背时的诗与行时的歌[J].词刊.2000(3).
[8]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N].中国文化报,1996-10-16(4).
[9]许自强.歌词创作美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
[12]夏野.中国音乐简史[M].长沙:音乐教育出版社,1991.
[1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飞林.我写歌词[J].词刊.2000(3).
[15]李松涛.流行歌词走向色情低俗[N].中国青年报,2007-08-26(3).
[16]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7]金民卿.大众文化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8]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9]李名方.得体修辞学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20]耿文婷.论新时期流行歌曲的文化属性[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