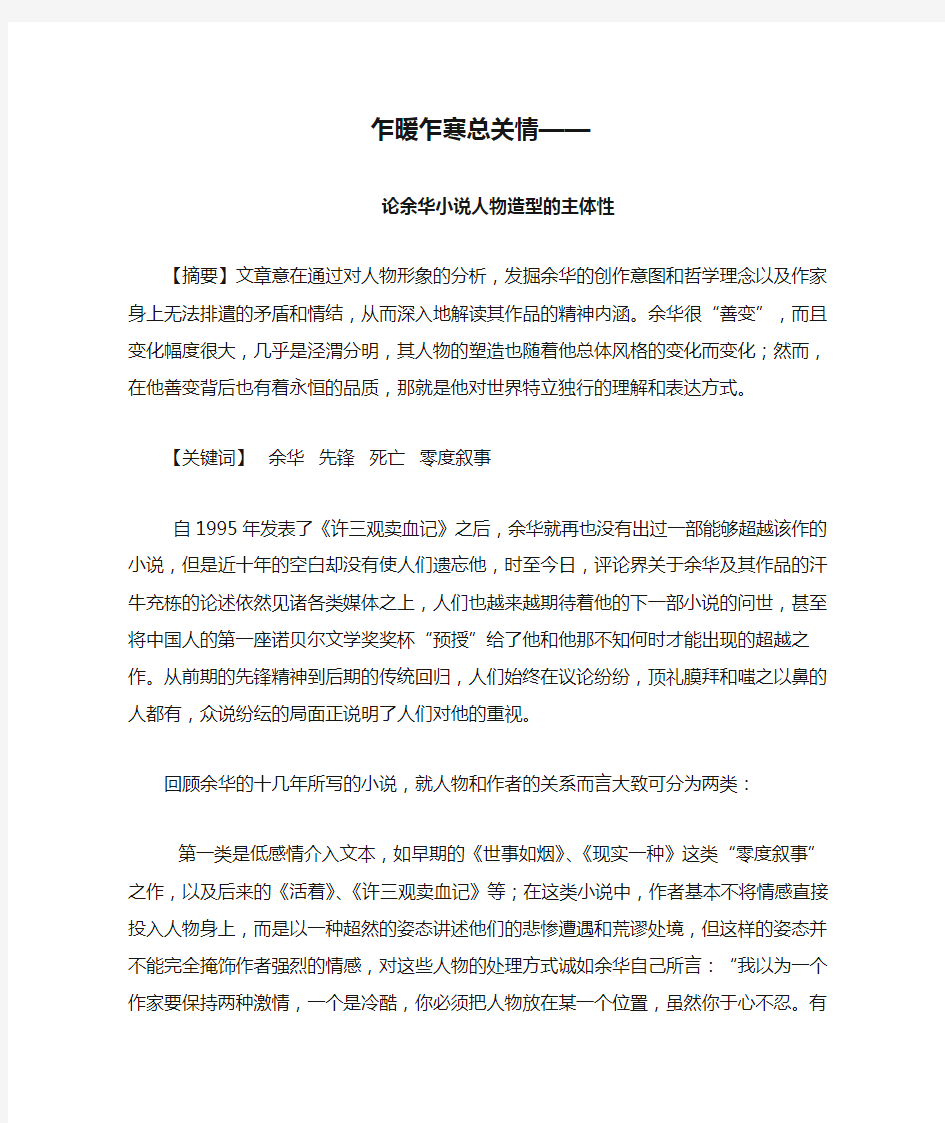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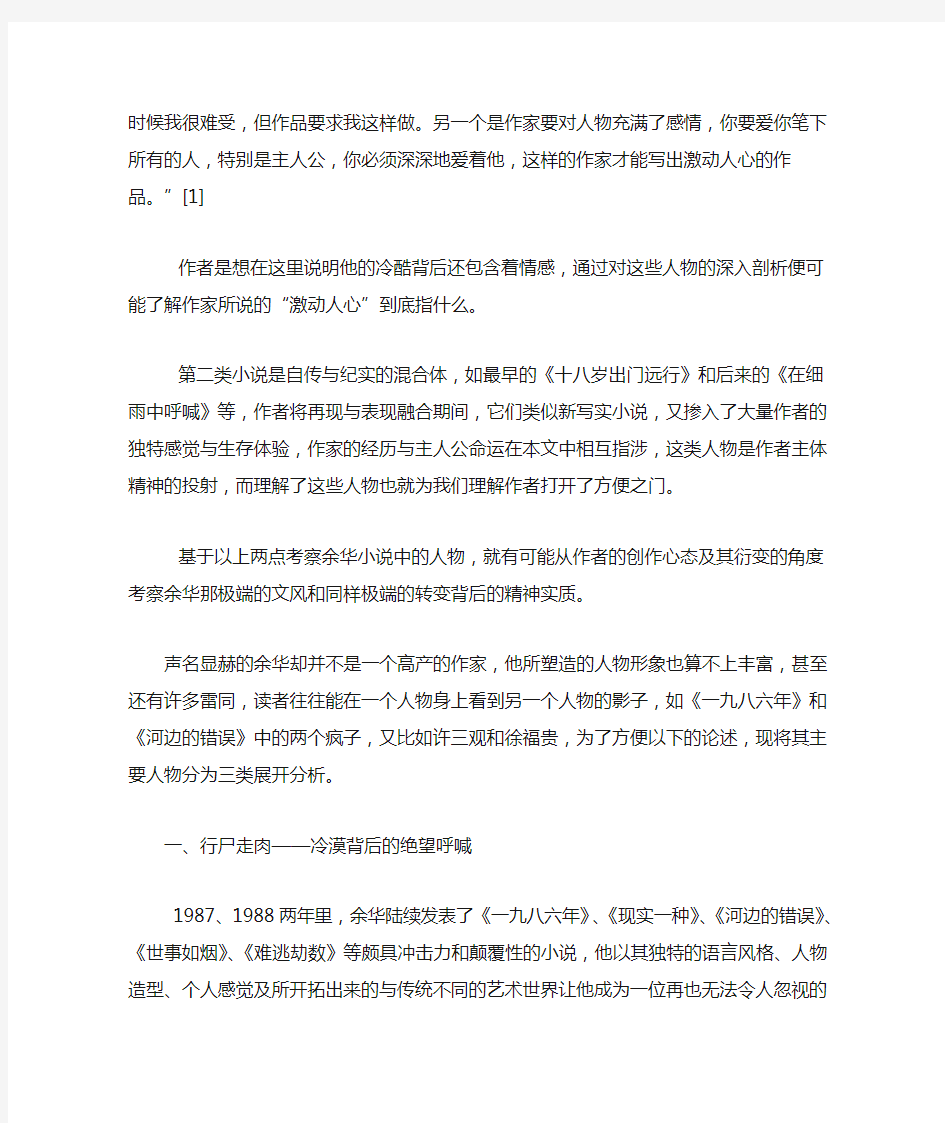
乍暖乍寒总关情——
论余华小说人物造型的主体性
【摘要】文章意在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发掘余华的创作意图和哲学理念以及作家身上无法排遣的矛盾和情结,从而深入地解读其作品的精神内涵。余华很“善变”,而且变化幅度很大,几乎是泾渭分明,其人物的塑造也随着他总体风格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他善变背后也有着永恒的品质,那就是他对世界特立独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关键词】余华先锋死亡零度叙事
自1995年发表了《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就再也没有出过一部能够超越该作的小说,但是近十年的空白却没有使人们遗忘他,时至今日,评论界关于余华及其作品的汗牛充栋的论述依然见诸各类媒体之上,人们也越来越期待着他的下一部小说的问世,甚至将中国人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奖杯“预授”给了他和他那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超越之作。从前期的先锋精神到后期的传统回归,人们始终在议论纷纷,顶礼膜拜和嗤之以鼻的人都有,众说纷纭的局面正说明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回顾余华的十几年所写的小说,就人物和作者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低感情介入文本,如早期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这类“零度叙事”之作,以及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基本不将情感直接投入人物身上,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讲述他们的悲惨遭遇和荒谬处境,但这样的姿态并不能完全掩饰作者强烈的情感,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方式诚如余华自己所言:“我以为一个作家要保持两种激情,一个是冷酷,你必须把人物放在某一个位置,虽然你于心不忍。有时候我很难受,但作品要求我这样做。另一个是作家要对人物充满了感情,你要爱你笔下所有的人,特别是主人公,你必须深深地爱着他,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1]
作者是想在这里说明他的冷酷背后还包含着情感,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深入剖析便可能了解作家所说的“激动人心”到底指什么。
第二类小说是自传与纪实的混合体,如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后来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作者将再现与表现融合期间,它们类似新写实小说,又掺入了大量作者的独特感觉与生存体验,作家的经历与主人公命运在本文中相互
指涉,这类人物是作者主体精神的投射,而理解了这些人物也就为我们理解作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以上两点考察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就有可能从作者的创作心态及其衍变的角度考察余华那极端的文风和同样极端的转变背后的精神实质。
声名显赫的余华却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算不上丰富,甚至还有许多雷同,读者往往能在一个人物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物的影子,如《一九八六年》和《河边的错误》中的两个疯子,又比如许三观和徐福贵,为了方便以下的论述,现将其主要人物分为三类展开分析。
一、行尸走肉——冷漠背后的绝望呼喊
1987、1988两年里,余华陆续发表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颇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小说,他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人物造型、个人感觉及所开拓出来的与传统不同的艺术世界让他成为一位再也无法令人忽视的作家。他与同时代许多理念、风格不尽相同甚至相左的人一起被并称为“先锋派”,曾有人用“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这句话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作者。这种独特的风格突出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塑造上,当时他笔下的人物都跟暴力、血腥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他自己的统计,仅1986年一年间就有多达36个人死在了他杀气腾腾的文本世界里。与之相适应的,余华还从他们身上抽空抽去了常人的理智和情感,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因为当时的余华相信“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于是,他们都成了完全由欲望控制的行尸走肉,他们的麻木和弱智令他们义无反顾地做着不可思议和自取灭亡的事情,其中最极端的场景出现在那部被视为先锋小说“标本”的《现实一种》中,山岗用他发明的“笑刑”惨绝人寰地虐杀了他的亲弟弟山峰,令人战栗不已。
谈论余华初期的作品离不开“暴力”二字,在正常人眼中,那是毫无理由的暴力,恐惧且令人作呕,但是当时的余华及其笔下的行尸走肉们却并不这么看,他们对这样的暴力有着一种别样的亲切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对其所能达到的效果也颇为满意。
从发起暴力的原因和实施暴力的过程看,麻木和弱智并非这些行尸走肉的全部属性,相反他们也有着极度敏感和绝对理性的一面。除了皮皮对堂弟的虐待,《现实一种》中所描述的施暴行为其实都是有着理性的理由的,山峰的妻子借公安机关之手杀死山岗是为了替夫报仇,山岗虐杀山峰、山峰踢死皮皮都是为了替子报仇,既有逻辑基础也符合某种传统道德。皮皮失手杀死堂弟的现实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面对着命运的捉弄,他们脑中只有一个欲念——复仇,这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并非毫无理智,他们清楚地知道两败俱伤的结局,却毅然地迎接它的到来,山峰在踢死皮皮以后主动找上了山岗:“……这时山峰出现在门口,山峰说:‘不用找了。’他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他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了。’说着将一把菜刀递了过去。……”[2]
然而兄弟俩对亲骨肉的爱却并不纯洁,如山岗经常体罚妻儿,他视母子俩为他的财产,不顾一切的复仇欲念是由于贵重财产的损失而产生的。与山岗不同的是,他的妻子对儿子的感情倒完全是血亲之爱(这跟余华早期敌视父亲的情绪有关,后文会有论述),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对复仇都有着强烈的渴望:“……妻子朝他的脸看了很久,接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她将菜刀送回山峰手中。‘你听着。’她对他说:‘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诚然,余华给他们安排的命运实在有些极端,但暂时撇开这个不谈,面对命运给予的苦难,人只有两个选择——忍耐和抗争,当人们面对至爱亲人的惨死而凶手就近在眼前并且要与你朝夕相对的时候,宽容不见得会比复仇更具有人性。
在《世事如烟》中的司机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是,这次悲剧起源于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的刻意行为,而非随机事件,那一幕出现在灰衣女人儿子的婚礼上:“2拿出了一叠钱,对司机说:这四百元买你此刻身上的短裤。……司机听到了一阵狂风在呼啸,他在呼啸声里坐了很久,然后才站起来离开座位朝厨房走去。”[3]
谁都以为囊中羞涩的司机是去脱裤子的,没想到他是去自杀的。当2意识到这一切以后落荒而逃,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已化为厉鬼的司机:“……这时他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像一颗颗小石子节奏分明地掉入某一口深井,显得阴森空洞,同时中间还有一段“咝”的声响。他知道是司机在追出来了……”
这种“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的复仇心态与自我牺精神堪与鲁迅笔下的眉间尺媲美,同时也体现了少年作家对现实的强烈不认同性,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4]
而这种不认同性实在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才存在的,而是缘自作家的精神需求,“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在《活着》的前言里,余华声明过自己写作理念——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虽然这可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原则。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纯属无病呻吟,但愤怒和冷漠之所以出现在他的文本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后来温情和忍受的出现,一样是他发自内心的需要。
我们不会仅满足于那些诸如风格引进、形式试验和美学要求之类的解释,因为这无法解释那冷酷背后明显的敌意,这也是当时余华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区别所在。一个作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的。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余华用冷漠的叙述描写着死亡,这跟他那讳莫如深的童年经历有关。虽然,对一个复杂的人妄下定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为了说明接下来的问题,笔者还是要做一些自以为是的推断。读者应该不难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和《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中感受到作家年青时那敏感和脆弱的气质,这种特质给了他发现生活背后非理性因素的能力,也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异类”而遭到长辈或伙伴的“特殊照顾”,
从而加剧他对于“人性恶”的绝望体验,正是为了表达这样独特的体验才促使他开始形式的探索。
作者曾说:“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5]然而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新技巧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供他借鉴的形式很多,为何这时的他对“零度叙事”情有独钟?这种选择其实并非偶然,因为它正好符合了余华当时的心理防御机制。
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它包括很多形式,其中有一种叫做“反向”的机制,“反向”是指为阻止不能被接受的欲望而做出相反的行为表现。这些欲望或冲动要求表现,但表现出来可能引起不良后果或被惩罚,或引起内心不安,就反而表现出相反的欲望或冲动。如儿童偷吃了母亲不让吃的东西,母亲回来后,就抢先告诉母亲她没有吃那个东西,而余华将世界的黑暗景象以平静如水的方式呈现在文本里,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我不在乎”!但他内心深处却极端地恐惧、焦虑和愤怒,因此,读余华这时期的作品,很容易察觉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的那一股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的心灵的潜流。
另一种机制是“补偿”,是指个体利用某种方法来弥补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从而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由此便可以给行尸走肉们及其极端的行为举止作出一个解释:残忍、冷漠和暴力是对少年作者自身敏感脆弱的一种心理补偿。那些人——从山氏兄弟到东山、广佛,从街上的疯子到河边的疯子,还有《世事如烟》中的那些阿拉伯数字——他们都是些亡命之徒,想杀就杀、快意恩仇;这些都与惶恐、焦虑的作者主体情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是在用这些文学形象弥补或者掩盖自己心中极度的不安,难怪作者会认为暴力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并坦言这种充满激情的形式让他心醉神迷。人类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自觉地运用心理防御机制,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度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多年以后,就在他最后一部合集《黄昏里的男孩》发表的时候,余华越来越相信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此看来,他那通过写小说而运作的防御机制是运用得不错了。
按照余华当时所主张的人物造型理论来看,人物在小说中所享有的地位,的确不会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他认为作品中的人物跟河流、阳光等这些外物是一样的,他们都不过是些傀儡和道具而已,是叙述者要他们发出声音、作出行动。
但事实上他们的命运比道具更悲惨。被剥离了社会属性、历史属性的他们像畜生一样被叙述者推向屠宰场,他们的毁灭比一棵树的倒下刺目得多。极端的形式遮蔽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他的本意是要人们在直面与正视中产生恐惧与战栗,他所要竭力展示的“精神真实”在读者困惑的眼里只是后现代的狂欢,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存在于全局尺度之上的反讽,就将其冠以“绝对的反人文主义者”的称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冷酷叙述者背后忧心忡忡的隐含作者。
二、另类阿Q——无奈人生的积极认同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发现原来充斥于余华文本世界的那些身份可疑、行为极端、情感麻木、没有人性的人物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迟钝无知却又敏感于人情冷暖的傻子来发、温厚淳朴却又不失刚毅坚强的老农福贵、卑劣猥琐却又富于人情味的生产队长等形象鲜明的人物。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物更是具有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效果。许三观平时打妻骂子,也在危急时刻为家庭挑大梁,而且不时表现出父亲、丈夫的温情,既天真无邪又老练世故,既追求生活又随遇而安,既贪婪自私又甘愿奉献,而且人物性格随着故事的演进有所发展;许玉兰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家庭主妇,没有多少知识,惯于撒泼骂街,但又勤俭持家,用自己的精打细算使全家度过的困境。与此同时人物所处的环境也“逼真”了起来,虽然苦难和疯狂依旧,但读者再也不会有身处地狱的迷惘恐惧之感。这种切近人物、切近生活的文风使余华的作品摆脱了以往那夸张变形的极端化倾向,接近了大众的心里承受能力,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余华后期文本中所展示的世界虽有“真实”面目,却仍具“荒谬”本质。尤其是主人公的身份,细究起来依然可疑。都以为来发是傻子,但他在讲述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欺凌的时候不动声色而又恰到好处:“……陈先生也走到药店门口来,看到别人叫我什么,我都答应,陈先生就在那里说话了,他说:‘你们是在作孽,你们还这么高兴,老天爷要罚你们的……只要是人,都有一个名字,他也有,他叫来发……。’”[6]
但是读者对陈先生彬彬有礼的幻觉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们经常这样问我,还问我和他们的妈妈是不是睡过觉……陈先生站在屋檐下指着我说:‘你们这么说来说去,倒是便宜了他,是不是?这么一来他睡过的女人几卡车都装不下了。’”
两相对比,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把陈先生伪善的面孔暴露无遗,这样的叙述真可谓以少总多、深入骨髓,笔者不禁要对来发的真实智力产生怀疑,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大智若愚,如此种种似是而非的描写在《活着》和《徐三观卖血记》中也有存在,只不过作者把这些荒谬的气息隐藏到了现实和历史之后。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只是徒具了现实的面貌,更像是一则则寓言,而这也是与他前期的创作一脉相承的地方。
作为一个“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的作家,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因为他对现实人生的“荒谬”体验从来都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他对本质的看法。
转变之前的作者曾明确地表示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并且坚定地认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可见此时的余华拥有一种对理性的自信,自信能够透过荒谬的现象看清井然有序的本质,于是他在认定世界并非一目了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那个时期,当我每次行走在大街上,看着车辆和行人运动时,我都会突然感到这运动透视着不由自主。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所有的一切(行人、车辆、街道、房屋、树木),都仿佛是舞台上的道具,世界自身的规律左右着它们,如同事先已经确定了的剧情。这个思考让我意识到,现状世界出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有着必然的前提。”[7]
作家在后来的回忆中不无得意地说当时的他已经洞察到艺术永恒之所在,事实上这“艺术的永恒之所在”根源于他对世界本质的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解,这也是作者构建其荒诞世界的哲学基础,而他眼中的本质和真实,就是人性恶、宿命论以及对此的深深绝望。
不知为何,余华忽然“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也许是自我否决令作家有点难堪,余华在他后期的文论中经常说出自相矛盾的句子:“任何知识说穿了都只是强调,只是某一立场和某一角度的强调。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可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8]
这分明是对他以前所建立的“世界结构”的一次颠覆,却还要强调“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更为年轻的我”。以上的对比基本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面对荒谬的世界,作者选择了认同而放弃对内在规律的探求与展示。关于那引人瞩目的转变,作者本人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在不断改变。”
从余华“宁愿相信自己是无知的”时候起,他的文学理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再也不想“给世界一拳”,而要追求“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和“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高尚”,他相信“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按谢有顺的说法,这是一种“精神暮气”,而立之年的余华的确少了少年余华的狂傲和血性,他逐步认同了生活的荒谬属性而无力再为人生寻求形而上的终极意义;他排斥道德、忽略善恶,不再追问人类本质、人生意义、人性尊严和人的价值,而企图用一种形而下的“高尚”(例如他把福贵和牛等同起来)来消解和屏蔽人的荒谬和悲剧的处境。这种无奈的人生体验和把“过程变成目的”的自我选择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有着相通之处,却又在根本上同途殊归。
对比作家前期的创作,可以发现:荒谬还在、绝望依然,不同的只是人物在悲剧处境中的选择。与以往那些动辄拳打脚踢、拔刀子、泼硫酸的暴徒不同,徐福贵、许三观、来发、杨高等人都没有求死之心,无论命运怎样蹂躏他们,他们都选择活下去,只是他们都活得太窝囊,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他们在苟活。他们的憨厚、质朴跟阿Q一样可爱,因为一个不知道来历的陌生人的一句话而产生的许氏家庭批斗会就像阿Q的跟风革命一样令人啼笑皆非;而他们的蒙昧、无知也跟阿Q一样可悲,尤其是许三观和徐福贵,骨子里都有一股子宿命论的奴性,阿Q在被杀头前仍然计较着圆圈问题,对于死亡的困境却不以为然,“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还“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面对爱妻的死亡,麻木的徐福贵却崩出一句“家珍死得很好”,老年许三观在卖血不成反被奚落的时候也能倚老卖老地完成一次精神胜利法:“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不能把这些另类阿Q和鲁迅笔下的阿Q划等号,因为作者在他们身上投射的情感是不同的: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塑造阿Q是为了他的国民性批判,总体情感取向是怒,是否定的;而余华则是“哀其不幸,颂其不争”。在同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鲁迅看见了局限,而余华却看见了力量,他在《活着》
的韩文版自序里面不无自豪地说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
这里的“忍受”是解读余华后期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它不仅局限于《活着》,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许三观卖血记》等作中同样适用。来发、福贵和许三观们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背后对苦难的强大承受能力的确令人钦佩,然而,作者在毁灭了新时期文学所树立的人的神话之后,似乎想把这种逆来顺受作为他构建关于人的新神话的主要基材,这多少有点小材大用之嫌。
虽然余华在论及福贵、三观之时毫不吝啬溢美之辞,但许三观“与邻居的平等”和徐福贵“同命运的友情”实在让人觉得有点自欺欺人,作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人生观可以用加缪那句著名的话得到很好的阐释:“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我并不想知道这是卑下还是反叛,是高雅还是可悲。”[9]
其实余华和加缪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痛感人生荒谬、同样极端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同样拒绝在绝望中沉沦、同样从传统中寻求超越,但巨大的差异就在对传统的寻求中体现了。
在经过了《局外人》阶段的冷漠与彷徨之后,1947年发表的《鼠疫》标志着加缪开始寻求对绝望的超越,其中的里厄医生明知鼠疫的不可战胜,仍拒绝向其俯首称臣,带领大家抗击突如其来的厄运,竭尽全力医治病人,堪称现代人道德典范,这显然比福贵、三观等人的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或者依靠消耗生命(卖血)来延续生命的做法要积极和有意义的多。但从另一方面讲,这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里厄的背后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西方人文底蕴,而福贵和三观身上却有五千年的封建传统,不能苛求他们也带领着妻儿老小去反抗社会的不义、命运的不公,他们能够在命运的捉弄之下不顾一切地顽强地活着,就已经够积极的了,如果说西绪福斯征服顶峰的斗争可以充实他的灵魂,那么穷尽苦难卑微生命的过程也一定能给福贵们带来幸福。
余华肯放下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归深植于民间土壤的传统文化精神,正迎合了世纪末人们对于深度和形而上观念的厌倦,从“发泄”、“控诉”、“揭露”到“展示高尚”,这些人物始终没有逃离悲惨的命运,但至少有更多的读者知道了他们。从行尸走肉到另类阿Q,这些人物体现余华的精神暮气,也见证了作家的思想成长。
三、自画肖像——父子间的战争与和平
叙事文学中的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从叙述者切入叙述内容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内部聚焦即叙述者可以介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物就是叙述视角,如果叙述者只能在某个人物的视线或者感知范围进行陈述,视角是单一和确定的,这即是“叙述者等于人物”。很多时候,叙述者的声音不一定是隐含作者或者作者的声音,但对于余华这样一个视写
作为“第二人生”、当回忆是“再活一次”的作家而言,在这些承担了叙述任务的人物身上多少都会投射作者的主体情感,他们是作者为自己的心灵所画的一幅幅肖像。
写作伊始,作者以其对世界的独特感知方式塑造了一系列悲惨无助的少年形象。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处女作,十八岁是男性成年的标志,小说中的“我”正是在这个充满迷惘的年纪开始了人生之旅,行走在在充斥着欺诈、暴力的阴惨的成人世界里,“我”内心充满了梦魇般的惊异和恐惧,“我”奔上高处去找心中的“旅店”,这儿的“旅店”不仅能提供物质上的温饱,更可以抚慰“我”饥寒交迫的心。最后,身心俱悴的少年却在那个忘恩负义的司机的破车里“找到”了“旅店”:“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10]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体会到温暖实在是因为内心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作者仍通过“我”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无论人世多么残破、阴冷都要保持自己那颗健全、暖和的心。
“余华”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的主人公,这暗示了作者与人物密切的关系。“余华”在一个冬天的中午被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从被窝里拖入了一个毫无因果律的荒谬困境,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死亡,“余华”却要被迫强装悲痛,坐在死人边上的“余华”,他的愤怒、无奈、不安一点都不亚于躺在破车里的“我”。这个故事在它喜剧性的外表下掩藏着残酷现实,其间也充满了暴力,那是一种思想上的暴力,对于少年作者而言,这就跟拳头一样不可抗拒。
《四月三日事件》的叙事视角是单一人物的内部聚焦,里面的“他”完全可以用“我”来置换,虽然余华煞费苦心地引入一个“他”,但这个“他”依然是作者独特体验的传达者,在《虚伪的作品》里,余华说他喜欢这样的一种叙述态度,通俗的说法便是将别人的事告诉别人,而努力躲避另一种叙述态度,即将自己的事告诉别人。即便是他个人的事,一旦进入叙述我也将其转化为别人的事。他诱庋姆椒ㄎ鋈司樽坏淖罴虮阌行У姆椒ǎ?/P>
四月三日就是作家自己的生日,这也是一个关于作者和人物联系的暗示。在《四月三日事件》里,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炼狱一般的世界,这是对少年意识的怪异描写,这是对心灵扭曲的深刻刻画。文中的主人公“他”似是一个“迫害狂”,怀疑周围的人都在制定一个针对他的阴谋,恍惚间觉察到危险的不断迫近,连至亲的父母都觉怀疑。但其实“他”只是沉浸于自己的臆想,无论是对手对他迫害还是他对对手的挫败都只是他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又是那么的真实,似乎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作者强调的“内心真实”。对生于杭州长于海盐的余华来说,他的生活也许与常人无异,极度敏感特质却让他眼中的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为作家的心理经历的确比他的生活经历重要得多。《四月三日事件》
是作者为自己描绘的一幅表现主义的自画像,在这幅画的背景里,一切习以为常的事物都陌生了起来,阴险的水坑、鲜血般的晚霞、被风吹断了的声音……甚至整个小镇都在月光下显得阴郁可怖,如昏迷一般。这一切都反映出此画的表现主义特征,而浸润了作者情思的“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痛苦地挣扎着。
无论是内容的表现方式还是作品传达的精神内涵,《四月三日事件》跟挪威画家蒙克所作的《呐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鲜血般的晚霞、阴险流动的水、居心叵测的人还有那鬼魅一般的城镇,这些也都是蒙克用以构建《呐喊》的要素。
一天晚上蒙克沿着小路漫步,路的一边是城市,另一边在他的下方是峡湾。他又累又病,停步朝峡湾那一边眺望,那时太阳正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象血一样。画家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他仿佛可以听到这一尖叫的声音。他画下了这幅画,画了那些象真的血一样的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喊》。
在这幅画上,蒙克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变形扭曲的人物形象,把人类极端的孤独和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余华笔下的“他”的形象也是变形扭曲的,内心亦充满孤独和苦闷;他们身陷敌意和冷漠的人世间,同样绝望地呐喊着。
“无依无靠”是“他”为自己找到的十八岁生日之夜的主题,其实不仅是《四月三日事件》,《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及后来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一系列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种被遗弃感,而遗弃他们的人就是父亲。
余华在他早期创作的时候一直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来指控父亲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让“我”出门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结果“我”皮开肉绽,《四月三日事件》中的父亲更是与众人一起设计害“他”,到了《世事如烟》和《难逃劫数》,父亲的丑恶发展到了极点。《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不仅诱奸少女,还享用着克子的寿数,《难逃劫数》的老中医残忍地把女儿、女婿推下苦难的悬崖;他们不仅坏,而且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牢牢地控制着儿子们的命运,把他们往死路上逼。此时的父亲成了命运的同谋和帮凶,甚至是阴谋和罪恶的源头,如《难逃劫数》开篇就有这么一句话:“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没有知道已经走入了那个老中医的视线。”
作者仿佛想说明,之后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爱上露珠、被露珠毁容、杀死露珠、背井离乡——这一些都是老中医安排好了的,这样的父亲就不单纯是一个人了,还是一切对立面的象征,作者把他对世界的恐惧和仇恨也投注到了父亲身上。
文学作品中的父子角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上的父与子,在具体性的父子冲突背后往往蕴含着超越性的结构:伦理的、历史的、文化的。作者此时对父亲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他视父亲为儿子的暴君,也不时地让儿子们与强大的父亲针锋相对,《现实一种》就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战例”,皮皮无意间的举动把一个罪恶的家庭给毁灭了,虽然他本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是令父亲
们恐慌的儿子,因为他拥有了毁灭父亲的能力;这则寓言背后的寓意其实没有表面上那样的血腥,作者只不过想表达他对已有价值和秩序的怀疑和抗拒而已。
然而在绝决地审父甚至是弑父之后,作者也陷入到“无父”的焦虑和孤独之中,因为父亲之于儿子,并非血缘那么简单。《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为复仇而踏上征程,但他没有计划、没有目标,就算找到了仇人,以他的武功也只有送死,那个为父报仇的愿望如海市蜃楼般虚无飘渺,他更像是在寻找些什么,梦游般的旅行里充满了作者内心对父亲的渴望,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已经在他的文本世界里和他的内心世界里一同死去了,但他还是在寻找一个精神之父。
曾有记者问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是否跟作者本人有着某种互文性的联系,虽然作家否定了此说法,但还是承认“那个孩子代表了我的许多童年感受”。这是一部弥漫着时光气息的小说,整个故事是通过那个代表了作者的许多童年感受的孙光林的回忆展开的,“控诉苦难、呼唤温情”依然是其不变的主题,只是孙光林较之前任已成熟很多,这是成年人对少年时光的回忆,已不似《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四月三日事件》般身临其境,站在现在看过去,余华更现实也更有自信了。作者创作心态的这种细微变化也体现在了孙光林身上,但文中的孙光林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跟余华笔下的其他未成年人一样,他肯定会被置入一个悲惨的处境之中,然而这回他并未因此而万劫不复,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离开了让他痛不欲生的故乡,这是一次现实的逃避。就算面对最不堪的回忆,他依然于现实之中寻求慰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龟缩进内心。
此时余华仍旧否定血亲之爱,孙光林遭到父亲的嫌弃和兄弟的排挤,却能在朋友和养父母那里得到体恤、关心、尊重、信任,即使这些温情如萤火虫般微弱,也能温暖少年的心,而作为一名父亲,孙广才的面目依然可憎,只是他少了算命先生和老中医的能力,再也当不了命运的合伙人,他跟其他人一样受命运的摆布,也有着悲惨的结局。对于这样的父亲形象,余华仍旧把他放到了主体情感的对立面,但他在批判的同时也依稀流露出一些不曾有过的怜悯之情。
《在细雨中呼喊》被视为余华对前期创作的总结之作,也许作家真的将心中的痛苦有效释放了,再回到童年生活时,便已不再只是一味地漠然和冷酷了,脉脉的温情就这么伴随着他的第一部长篇问世,自此以后,余华再也没有写过一部称得上自传的小说。而作家对于笔下的父亲们也少了一点仇恨,多了一份同情,孙广才之后的徐福贵、许三观和石志康都是体恤子女、无私奉献的好父亲,《我的故事》中的父亲以身示范,不惜与侮辱自己的人同归于尽,立刻激发出儿子在精神与人格上的飞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阑尾》中的父亲还差点让两个调皮的儿子给害死,原先不可一世的暴君现在倒成了受害者。
事易时移,余华已不是那个满腔怒火的愤青,他本人当上父亲之后立场就不同了,切身的体会使他渐渐看清了父亲的局限性和悲剧性。在他的文本世界里,传统的父亲形象渐渐地复活了,传统的父子关系慢慢地回来了,慈爱的父亲和玩劣的儿子——好像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血雨腥风的往事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一般逝去了。
如果将余华的小说作一个编年体的排列,可以发现,作者的主体精神经历了从投入到抽离,再到投入,再抽离的过程;从愤怒指控到冷眼旁观,继而绝望呼喊,最后平静讲述,无论是投入还是抽离都显得那么的极端,此亦体现了余华作为一个性情中人的特点,他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情绪宣泄和思想释放的过程,而这也是本篇“以气论文”的基础之所在。
【注释】:
[1]许晓煜、余华:《余华访谈: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文学世界整理编辑,资料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598811018.html,/wx_hsl/yuhua/hsl_99040.htm。
[2]余华:《现实一种》,《余华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余华:《世事如烟》,《余华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活着·前言》,南海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5][7]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6]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7月版。
[8]余华:《河边的错误·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9]加谬:《西绪福斯的神话》,《加谬文集》第5篇,译林出版社,2001.11版,第664页。
[10]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书目】
1.《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郑国庆文,《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6期。
2.《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昌切、叶李文,《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3.《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夏中义、富华文,《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
4.《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耿传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5.《文学理论》,南帆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6.《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谢有顺文,《钟山》2002年第1期。
7.《审父与驯子的两难——从两篇小说看九十年代的一种精神轨迹》,陆雪琴文,《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
8.《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一位有着独特生活体验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国早期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十八岁远门出行》、《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都是余华的先锋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余华的先锋小说彰显出他理解生活的聪明和敏感,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世事命运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死亡和血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荒诞,等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 一、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1)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和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语言不在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概念化言语的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像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来代替:频临死者标号为“7”,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4”,与十七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3”,垂钓者是“6”。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2)小说的结构---对常识的反叛。就小说的时空而论,小说处于两种时空关系中: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破除了以往小说时空中陈旧的观念、单调的套路,余华对时间的看法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排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他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 前面说到的暴力和死亡等也是余华小说先锋性的体现。 四、余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征 (1)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2)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 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摘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死亡。通过主人翁福贵对孤独的体会,对苦难的承受,对死亡的超越,及对温情的救赎来反映作者对生命意识的探究。本文主要通过以上四个方面论述《活着》中作者所传递出的对于生命的认知。 关键字:《活着》;苦难;生命意识发表论文网站 《活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这部作品名为“活着”,但是给我们讲述的却是一个不断死去的故事。可以说《活着》其实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这篇小说事事都围绕着主人公福贵来展开。作者也正是通过福贵这一人物形象的展示向我们传达了生死之别的真谛。在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也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么《活着》到底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义,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论述余华的生命意识。
一、孤独意识 福贵活着但却孤独,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父亲被他气死,母亲去世,孩子有庆被抽干血而亡,春生上吊自杀,女儿得败血症死去,妻子得软骨病死去,二喜因为工伤丧命,外孙苦根活活撑死。可以说跟福贵有关系的人都不在了,福贵的精神支柱已经是没有的了。这个世界就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了。在小说结尾处有段福贵的话;“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福贵已经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了。后来福贵买了一头老牛,福贵就和这头老牛相依为命,一起孤独到老,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头老牛陪伴他。在内心世界福贵同样也是孤独的,亲人都离去了,自己内心已经没有了寄托,在牛耕田的时候福贵是这样说的:“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可以说福贵把牛当作了自己对亲人的一种思念和寄托,把动物当成了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08级李竹根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以富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活着》以零度情感的叙事视角和重复的叙事手段以及充满民间特色、充满温情的叙事语言为读者打开了一片奇妙的心灵领域: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本文正是从这几方面来探讨《活着》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余华;《活着》;重复;零度情感;语言艺术 《活着》是当代著名先锋作家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像福贵这样经历种种磨难仍执着、坚韧的活着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小说中重复描写了死亡,却没有展示余华以往作品中令人心惊胆战和不安的血腥、暴力、杀戮、阴谋等场面,一扫“荒寒”和“冷漠”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整部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悲悯与关怀,用充满温情的语言亮出了生命的本色,让我们感受到在死亡背后涌动着浓浓的暖意,渗透着人间的温情,为活着的福贵,为活着的人找到了一个生命支点——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下面就从《活着》的艺术特色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重复的叙述手段 在现代派小说中,为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往往让某件事在人物的对话、思想、潜意识中反复出现获让同类事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余华在《活着》中灵活运用了重复的叙述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重复是先锋小说惯用的一种叙事手段,意在通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还原作家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但在表面层次上,作家并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通过重复这一有效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饿价值取向;而很多时候,通过重复,作家又可以巧妙的回避自己在作品中投注的感情,以使读者的思维产生错乱和空缺。 苦难和死亡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彼地加以表现。《活着》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悲剧历程。福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众多亲人的死亡。年少时的福贵嗜赌成性,输掉了所有的财产后,父亲气死;从腰缠万贯到倾家荡产,成为一个每日为三餐奔忙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要珍惜妻子儿女时,却被拉去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家,母亲却不在人世了,女儿凤霞因没钱治病变的又聋又哑;儿子有庆刚懂事,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中年丧子);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她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留下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妻子家珍因得软骨病而亡;女婿二喜搬运时被压死;仅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外孙苦根却因为吃豆子被撑死!大量的死亡而至,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的向那些可爱的生命靠拢,甚至摧毁他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3期
第十六讲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教学目标: 1、了解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发展; 2、掌握余华及其创作; 3、掌握先锋、先锋小说的定义及其特点; 4、掌握余华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变化; 5、了解其他先锋作家的创作变化。 教学方法:重点讲授法。 课时安排: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与五四时期的相比)的发展P332 1、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文革”末期一批青年诗歌和小说作者的地下创作; 2、朦胧诗的出现是现代主义文学从地下浮出水面的一个标志;差不多同时,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夜的眼》、宗璞《我是谁》等现代主义的尝试之作; 3、80年代的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人们不再盲目地将现代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混为一谈,把它仅仅作为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一种武器,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把它当做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距离的主要途径; (2)不再把它作为浪漫主义的附属物,而是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打入一个“集装箱”里,作为引进和移植的主要内容; (3)五四时期和8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引进和移植虽然都有各自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但80年代则明显地偏重与文学自身的建设; (4)两次引进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效果不可相提并论。
二、余华及其创作 1987年1月,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随后几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等中篇和《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等短篇; 1989年,创作谈《虚伪的作品》; 1991年,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 90年代以后,回归世俗,有《活着》《一个地主之死》《许三观卖血记》等。 三、先锋、先锋小说及其特点 1、先锋原意是“先头部队”,主要是指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形式创新运动,它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或者一种倾向,也可以是一种方法或过程。 2、先锋小说 3、先锋小说的性质和特点P338 4、先锋小说的终结命运 (1)先锋小说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 (2)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 (3)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的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 四、余华创作的变化P341 1、1991年以前:在想象的睡眠里前行的梦游,宿命的难以捉摸的潮湿和阴沉,以及波涛般涌动着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即冷酷和残忍。如:《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等等; 2、1991年,转折点:《呼喊与细雨》。作品描写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的污秽、少年在性成熟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审父与仇父的家庭史整理以及儿童对人间温情的寻找等媚俗倾向等等。对这种世俗情感的描写,就意味着对先锋的放弃。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摘要: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同的人的性格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命运,反之,生活道路的不同也会反作用于人的性格。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将这二者的关系表现的十分突出,尤其是在90年代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在文中,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物进行余华式特有的加工处理,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复杂的一面和历经苦难的多舛命运。由此,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再次阐释了性格与命运的错综变换的复杂关系。 关键字:余华人物性格生活命运苦难坚韧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作家是在用内心的绝望与呼喊写作,在他的笔下,将人性的善与恶描摹的真实生动,淋漓尽致。站在人生的高度,他将人物至于苦难的环境下,反复历练,层层盘剥,犹如高炉中的顽石,终数尽磨难,留下警醒与教训的碎片。这位作家正是余华先生。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构成了了解和颠覆。他的早期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但是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读余华的作品,就像是经历了血和泪的洗礼,当文中的纷纷扰扰一次次地从我的心尖碾过时,仿佛深陷其中,常会在心中留下万般感慨,这想必也是笔者喜爱余华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是余华在转型后,在90年代后先后创作的,也是笔者在此文中主要论证的关键作品。而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将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的复杂关系展现的到为全面。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是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 一.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与环境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目录 引言 (1) 一、符号化 (1) 二、类型化 (3) 三、真实性 (5) 四、人物的意义 (7) 结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余华以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符号话、真实性等特点的分析,探求当中所蕴含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物特点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Yu Hua creats a lot of unique characters by his unique knowledge and fresh ins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this article implys the meaning and value through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authent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Yuhua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s the feature the value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诸如读者熟悉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活着》等,无不密集地充斥着许多迥异于传统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建构的某些先锋性探索倾向。本文试从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出发,分析这些人物塑造极具诱惑力同时倍受争议的特点,并力图发掘其背后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意义。 一.符号化 在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成为真理的命题:文学就是人学。世世代代各种文学的成熟形式,也充分地证明和表达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意义。不过,余华却有意与这种传统的文学理念做出偏离,将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符号化。这种卡西尔式表现性“符号”意义的呈现,使得人物与小说中其它形式因素如结构、语言等一样,成为一种形式美学意义的符号。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不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属性,仅仅成为构造故事情节而设置的“道具”,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发动机。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表现,首先体现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形式中。在传统小说的叙事过程里,人名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它不但能够凝炼地体现人物性格,使观众闻其名而知其人,而且还可能暗示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人物形象与其蕴含的客观社会生活的意义紧密相联。许多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都无不如此。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关联具有浓厚的文化凄凉感。而在余华那里,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被多次取消,《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只有“1,2,3,4,5,6,7”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或用“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只用“陌生人”、“刑罚专家”来代替具体人名。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名称,人物自我也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成为小说文本叙述人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最多也只是成为营构叙述情节的一些纽带。 其次,余华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差别。在传统意义上说,人物的工笔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一直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刻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时,对于他们的出场、造型、服装等无一不浓妆重墨,相关的艺术表现效果至今仍为人们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论余华《活着》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一直是反复渲染的主题,而与之相对应的“苦难意识”是人类的的普遍意识。《活着》表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也表现了余华对人类生存的不断追问。本文从苦难的表现形式、苦难的产生根源以及苦难的超越三个方面对“苦难意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活着》;死亡;苦难;苦难意识 一、“死亡”——“苦难”的表现形式 余华是一位特别关注苦难的作家,也很善于表现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苦难不再是罪恶、杀戮、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失了,血腥的场面没有了,随处而在的暴力收束了。在《活着》中,他将这种苦难的铺叙推向极致,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现象展览”,毫不夸张地说,《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出现在读者眼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 无疑,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以短短的篇幅,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的。福贵的父亲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母亲死于疾病,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儿子有庆因输血给县长太太而死,女儿凤霞死于分娩大出血,女婿二喜被吊车吊起的水泥石板打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系列的死亡故事,使福贵习惯了死亡,却使读者在重复死亡的旋律中难以喘息,叫人在某种无法躲藏的残酷真实面前,在一次又一次几乎制度化的劫难经历中,与世道人心有所领悟。引导读者进入更为不真的苦难世界中,正如一曲重复演奏的悲凉曲调,使读者在痛苦的声音中挣扎。 显然,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产的痛苦、丧亲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丧母的痛苦、战场上的死亡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困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的痛苦、女儿因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抚养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在这一系列痛苦之中,对福贵来说,最痛苦的还是亲人的一一死亡: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厚道的女婿······ 余华是一位叙述苦难、再现苦难的高手,他关注人间形形色色的苦难,也善于表现这无尽的苦难,在《活着》中,死亡成了苦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某种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598811018.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摘要:余华是当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突破传统小说在形式、语言方面的限制和常规模式,在叙述形式、叙述语言、叙述母题、叙述结构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特有的品质。本文将从他作品的先锋话语、暴力与死亡母题、叙述模式等几个方面探究其小说作品的先锋性表现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1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与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而语言的创新不是没有规则的,它来自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在余华的小说中,语言不再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只是概念化言语的所谓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以符号来代替:濒死者标号为“7”,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4”,与17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3”,垂钓者是“6”。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2“疯狂的幻觉世界”———“小说的真实”对“再现现实的反拨”余华在他的《虚伪的作品》一篇中这样说道,“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余华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活着》中文版前言中这么说:“事实上我只能成为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如此,我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与传统的叙述不同,余华设计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并借助这个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极端而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了一幅世界图景与人性中兽性的一面,而这个叙述者在小说中既不做过多的议论,也不作价值的评判,仅仅只起一种结构的作用。这种叙述上的冷漠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的策略,小说以一种“局外人”的观点和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构造了“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初读余华的小说,就像在听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深夜寂静无人的街头无尽地倾诉。心理学证明,所谓精神病患者,其显著的心理特征便是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而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余华前期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的世界,一个狂人的世界。如《四月三日事件》里那个十八岁的迫害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处处暗藏杀机、危机四伏的世界。小说中的狂人所感知的那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对于真实世界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作为作家的余华似乎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已经脱离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所构筑的小说世界可以看成是他作为旁观者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叙述。《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类带有一种寓言意味的作品,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可捉摸和生活的荒诞。《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主人公甚至同作者同名,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硬被说成是他的朋友,他出于无奈与同情,不得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为他买花圈,装出很悲痛的样子为他守灵,甚至给他的母亲当孝子。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不可能发生,但他让读者想到现实生活中许多曾经强加在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及那些不得不做出的付出。而《死亡叙述》和《河边的错误》简直就是冷峻的写实,《死亡叙述》叙述了一个司机的看似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
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 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 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从先锋创作到温情写实——对余华小说的艺术探讨 学生姓名:殷强 学号:1102010442 所在院系: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届次:2015届 指导教师:管军 职称(学位):副教授 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制
淮南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诚信承诺书 1.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从先锋创作到温情写实——对余华小说的艺术探讨》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没有弄虚作假,没有抄袭、剽窃别人的内容; 2.毕业论文(设计)所使用的相关资料、数据、观点等均真实可靠,文中所有引用的他人观点、材料、数据、图表均已注释说明来源; 3. 毕业论文(设计)中无抄袭、剽窃或不正当引用他人学术观点、思想和学术成果,伪造、篡改数据的情况; 4.本人已被告知并清楚:学院对毕业论文(设计)中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将严肃处理,并可能导致毕业论文(设计)成绩不合格,无法正常毕业、取消学士学位资格或注销并追回已发放的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等严重后果; 5.若在省教育厅、学院组织的毕业论文(设计)检查、评比中,被发现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本人愿意接受学院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名): 日期:年月日
目录 前言 (2) 一、关于余华 (2) (一)余华生平 (2) (二)余华道路 (3) 二、先锋余华 (4) (一)先锋文学 (4) (二)小说主题 (5) 三、转型之路 (7) (一)转型原因 (7) (二)再度启程 (8) 四、现实余华 (9) (一)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 (9) (二)小说里的温情 (11) 五、小说艺术 (11) (一)细部刻画 (12) (二)重复叙事 (12) 六、结语 (12) 参考文献 (14) 致谢 (16)
论余华小说创作转型后的艺术走向 姜 欣 (平顶山工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44) 摘 要: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转型后,文本主题更多的是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现状和人性境遇给予温情的关注。在艺术上借助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用朴素、准确、简洁的语言表现生活的本真面目;以随和的民间姿态、悲悯的情怀、诙谐幽默的审美趣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淡薄而坚毅的内在力量,成功地实现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升华与超越。 关键词:余华;创作转型;叙述技巧;语言;审美趣味 中图分类号:I2071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08)08-0003-07 先锋小说出现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原有的一元化社会价值体系里增添了多元和相对的因素,文化线形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突破常规,超越传统的创作冲动,这种冲动鲜明地体现在先锋小说的创作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浪潮的汹涌而至,消费文化开始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80年代激情澎湃的抽象“主体”,在90年代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压力下实实在在的“个体”,精神生产面临着重大重组,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以特殊的精神姿态和人性思考介入先锋小说创作行列的余华,不仅是先锋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先锋小说整体转型中,以其在叙事形式和话语实践中的突出表现而著称,而且最重要的是从精神先锋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开拓,为先锋小说的整体转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转型后,余华小说创作的主题虽然依旧是人的死亡和生存,但更多的是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现状和人性境遇给予温情的关注。在艺术上借助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表现生活的本真面目,使得叙述的风格和表达方式由冷静、强悍、暴烈转向温暖、缓和与诗意;注重用朴素、简练、准确的语言反映老百姓真实的生命存在,描写的内容从虚拟的现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悲悯的情怀、诙谐幽默的审美趣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淡薄而坚毅的内在力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升华与超越。 一、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 余华摒弃了此前小说创作中形式炫耀的色彩,在对国内外经典著作阅读中,意识到了“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写出最丰富的作品。”[1]“小说之道在于 第二十三卷第八期 楚 雄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Vol123 No18 2008年8月 JO URNAL O F CHUX I O NG NO R M AL UN I VERS I TY Aug12008 3收稿日期:2008-06-26 作者简介:姜 欣(1968—),女,辽宁大连人,平顶山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