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历史论文论文
- 格式:doc
- 大小:68.50 KB
- 文档页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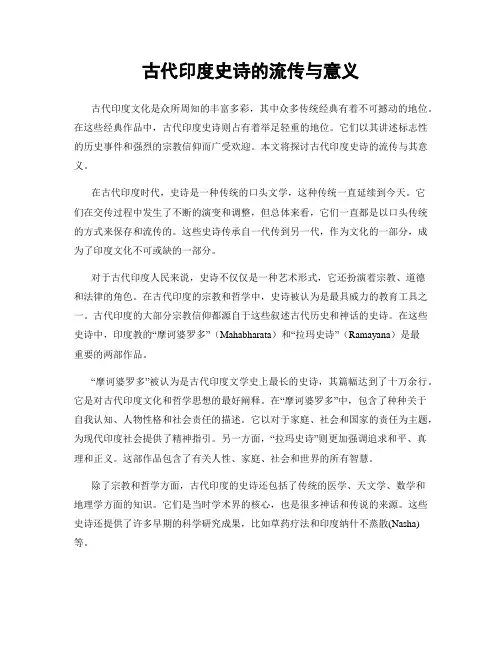
古代印度史诗的流传与意义古代印度文化是众所周知的丰富多彩,其中众多传统经典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在这些经典作品中,古代印度史诗则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们以其讲述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和强烈的宗教信仰而广受欢迎。
本文将探讨古代印度史诗的流传与其意义。
在古代印度时代,史诗是一种传统的口头文学,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们在交传过程中发生了不断的演变和调整,但总体来看,它们一直都是以口头传统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
这些史诗传承自一代传到另一代,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了印度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古代印度人民来说,史诗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还扮演着宗教、道德和法律的角色。
在古代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中,史诗被认为是最具威力的教育工具之一。
古代印度的大部分宗教信仰都源自于这些叙述古代历史和神话的史诗。
在这些史诗中,印度教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拉玛史诗”(Ramayana)是最重要的两部作品。
“摩诃婆罗多”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其篇幅达到了十万余行。
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最好阐释。
在“摩诃婆罗多”中,包含了种种关于自我认知、人物性格和社会责任的描述。
它以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为主题,为现代印度社会提供了精神指引。
另一方面,“拉玛史诗”则更加强调追求和平、真理和正义。
这部作品包含了有关人性、家庭、社会和世界的所有智慧。
除了宗教和哲学方面,古代印度的史诗还包括了传统的医学、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
它们是当时学术界的核心,也是很多神话和传说的来源。
这些史诗还提供了许多早期的科学研究成果,比如草药疗法和印度纳什不蒸散(Nasha)等。
然而,古代印度史诗在现代社会中,只是被一小部分人阅读甚至听说。
由于其长句和极其复杂的表述方式,很多人对其感到困惑。
然而,我们现今仍能够从史诗中找到许多关于人性、法律、道德和哲学的有益知识,这对我们的现代社会仍然非常有价值。
在总体来看,古代印度史诗作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哲学和书面传统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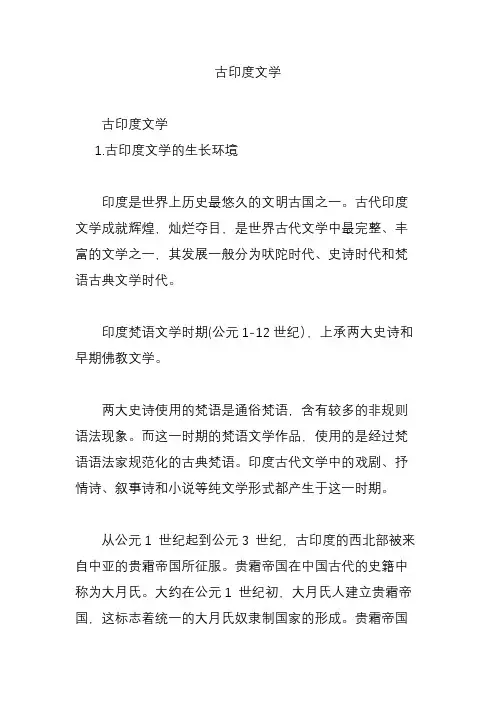
古印度文学古印度文学1.古印度文学的生长环境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古代印度文学成就辉煌,灿烂夺目,是世界古代文学中最完整、丰富的文学之一,其发展一般分为吠陀时代、史诗时代和梵语古典文学时代。
印度梵语文学时期(公元1-12世纪),上承两大史诗和早期佛教文学。
两大史诗使用的梵语是通俗梵语,含有较多的非规则语法现象。
而这一时期的梵语文学作品,使用的是经过梵语语法家规范化的古典梵语。
印度古代文学中的戏剧、抒情诗、叙事诗和小说等纯文学形式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公元1 世纪起到公元3 世纪,古印度的西北部被来自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征服。
贵霜帝国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称为大月氏。
大约在公元1 世纪初,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这标志着统一的大月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贵霜帝国建立后,势力日强,进一步南侵印度,到公元1 世纪末,发展到鼎盛时代,其领土扩展到北印度恒河流域中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贵霜帝国是与当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和中国的东汉帝国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帝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政局并不稳定。
从公元3 世纪起,贵霜帝国逐渐衰落。
印度著名的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马鸣,就生活在一二世纪贵霜帝国时期,他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梵语古典文学作品。
贵霜帝国衰落后,北印度又重新分裂成许多小国。
公元4 世纪初。
摩揭陀重新兴起,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起笈多王朝(约公元320 年——公元5 世纪中叶)。
经过后继者三摩答剌笈多和旃陀罗笈多二世的不断征伐,至5 世纪初,笈多王朝统一整个北印度和中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孔雀王朝之后的又一个庞大帝国。
笈多王朝属于印度古代历史上的盛世。
笈多王朝全盛时,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梵语文学和佛教艺术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梵语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
笈多王朝帝王大力奖励文学和学术活动,三摩答剌笈多本人就有" 诗王" 之称。
最杰出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就是超日王(即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宫庭" 九宝"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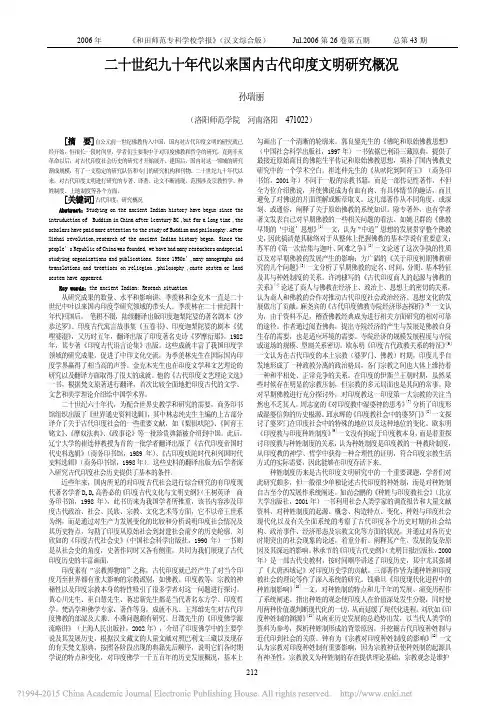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古代印度文明研究概况孙瑞丽(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摘 要]自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国内对古代印度文明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印度佛教和哲学的研究,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对古代印度社会历史的研究才开始展开。
建国后,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渐成规模,有了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刊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古代印度文明进行研究的专著、译著、论文不断涌现,范围涉及宗教哲学、种姓制度、土地制度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古代印度;研究概况Abstract:Studying on the ancient Indian history have begun since the intruduction of Buddism in China after 1century BC ,but for a long time ,the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Buddism and philosophy .After Xinhai revolution,research of the ancient Indian history began.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e have had many reseachers andspecial studying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Since 1990s’,many monographs and translations and treatises on reliegion ,philosophy ,caste sestem or land sestem have appeared.Key words:the ancient Indian: Reseach situation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水平和影响讲,季羡林和金克木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国内印度学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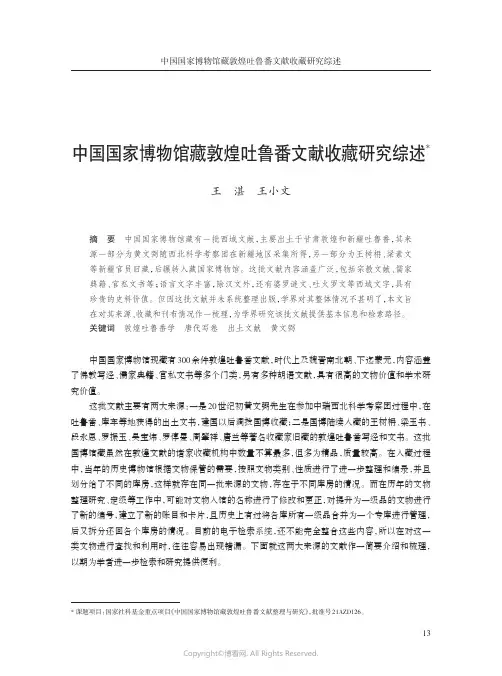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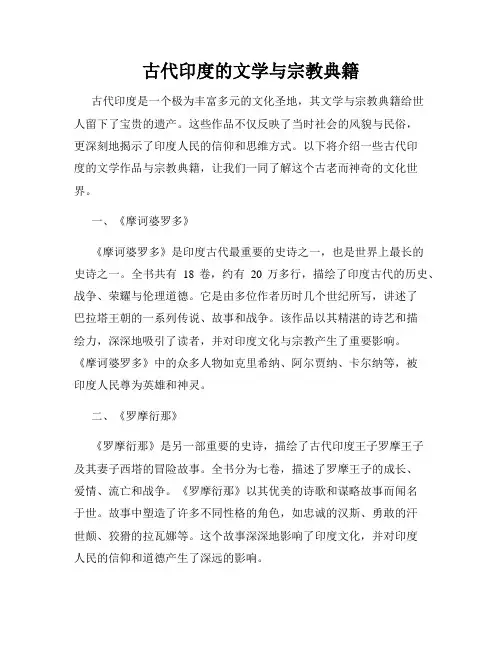
古代印度的文学与宗教典籍古代印度是一个极为丰富多元的文化圣地,其文学与宗教典籍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与民俗,更深刻地揭示了印度人民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以下将介绍一些古代印度的文学作品与宗教典籍,让我们一同了解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文化世界。
一、《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重要的史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
全书共有18卷,约有20万多行,描绘了印度古代的历史、战争、荣耀与伦理道德。
它是由多位作者历时几个世纪所写,讲述了巴拉塔王朝的一系列传说、故事和战争。
该作品以其精湛的诗艺和描绘力,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并对印度文化与宗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摩诃婆罗多》中的众多人物如克里希纳、阿尔贾纳、卡尔纳等,被印度人民尊为英雄和神灵。
二、《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是另一部重要的史诗,描绘了古代印度王子罗摩王子及其妻子西塔的冒险故事。
全书分为七卷,描述了罗摩王子的成长、爱情、流亡和战争。
《罗摩衍那》以其优美的诗歌和谋略故事而闻名于世。
故事中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角色,如忠诚的汉斯、勇敢的汗世颠、狡猾的拉瓦娜等。
这个故事深深地影响了印度文化,并对印度人民的信仰和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吠陀》《吠陀》是古印度的宗教典籍,是印度教最早期的基础文献之一。
它是由一些古代印度领袖、圣贤创作的,被认为是神圣的教义和颂歌的集合。
《吠陀》分为四个部分:《利特吠陀》、《雅各吠陀》、《萨摩吠陀》和《阿塔尔吠陀》。
这些典籍描述了古代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了许多主题,如宗教仪式、法律、哲学、宇宙观等。
这些典籍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圣的指南,它们对印度宗教、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婆罗多》《婆罗多》是古代印度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是印度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它是以故事形式叙述的戏剧、诗歌和道德讲演的集合。
《婆罗多》的主要内容包括许多战争、爱情故事以及关于人类梦想、欲望和情感的描绘。
这个巨大的文学作品以其各种形式和题材的多样性而闻名,是古代印度文化的珍贵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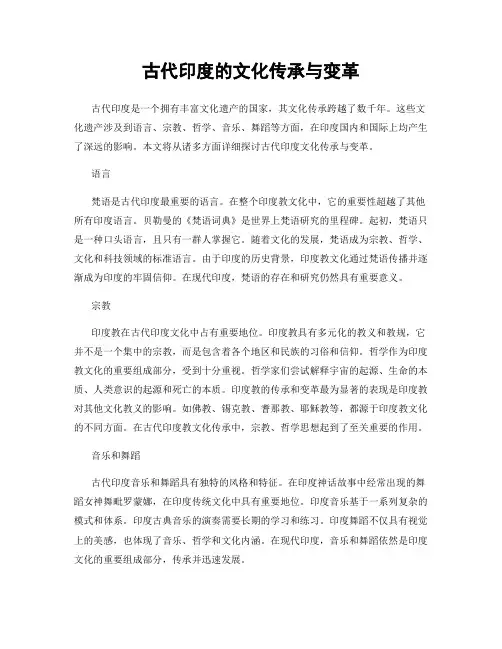
古代印度的文化传承与变革古代印度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其文化传承跨越了数千年。
这些文化遗产涉及到语言、宗教、哲学、音乐、舞蹈等方面,在印度国内和国际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诸多方面详细探讨古代印度文化传承与变革。
语言梵语是古代印度最重要的语言。
在整个印度教文化中,它的重要性超越了其他所有印度语言。
贝勒曼的《梵语词典》是世界上梵语研究的里程碑。
起初,梵语只是一种口头语言,且只有一群人掌握它。
随着文化的发展,梵语成为宗教、哲学、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标准语言。
由于印度的历史背景,印度教文化通过梵语传播并逐渐成为印度的牢固信仰。
在现代印度,梵语的存在和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印度教在古代印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教具有多元化的教义和教规,它并不是一个集中的宗教,而是包含着各个地区和民族的习俗和信仰。
哲学作为印度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十分重视。
哲学家们尝试解释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人类意识的起源和死亡的本质。
印度教的传承和变革最为显著的表现是印度教对其他文化教义的影响。
如佛教、锡克教、耆那教、耶稣教等,都源于印度教文化的不同方面。
在古代印度教文化传承中,宗教、哲学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音乐和舞蹈古代印度音乐和舞蹈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征。
在印度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舞蹈女神舞毗罗蒙娜,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印度音乐基于一系列复杂的模式和体系。
印度古典音乐的演奏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练习。
印度舞蹈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也体现了音乐、哲学和文化内涵。
在现代印度,音乐和舞蹈依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并迅速发展。
艺术古代印度的艺术涉及到石刻、壁画、雕塑和绘画。
印度石刻源自于早期的写经板和石柱,它们表示宗教和政治领域的规定。
在这些石刻上描绘了一些史诗故事,这些故事通常涉及到印度教的宗教信仰和教义。
这些石刻通过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力使得古代印度文化传承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结论在印度的文化传承和变革中,梵语、宗教、音乐和舞蹈以及艺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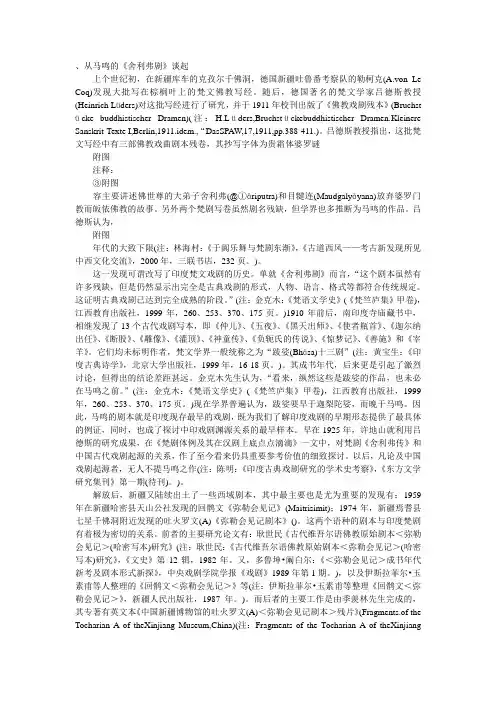
、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
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 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SPAW,17,1911,pp.388-411.)。
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附图注释:③附图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①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
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作品。
吕德斯认为,附图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
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规定。
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
)1910年前后,南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
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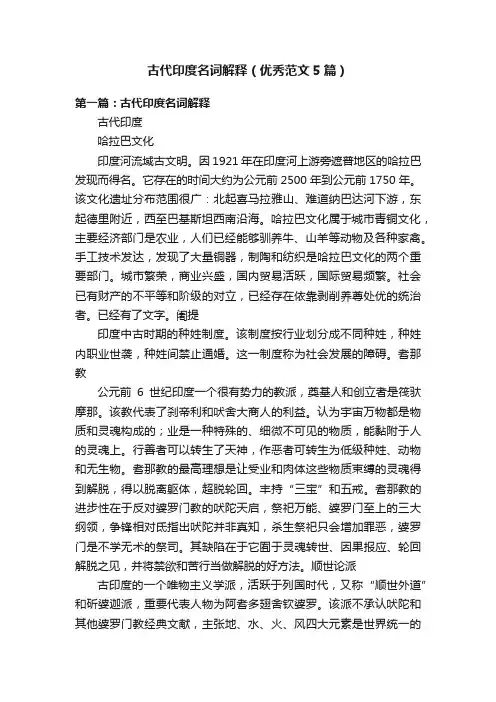
古代印度名词解释(优秀范文5篇)第一篇:古代印度名词解释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印度河流域古文明。
因1921年在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巴发现而得名。
它存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50年。
该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很广:北起喜马拉雅山、难道纳巴达河下游,东起德里附近,西至巴基斯坦西南沿海。
哈拉巴文化属于城市青铜文化,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人们已经能够驯养牛、山羊等动物及各种家禽。
手工技术发达,发现了大量铜器,制陶和纺织是哈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部门。
城市繁荣,商业兴盛,国内贸易活跃,国际贸易频繁。
社会已有财产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对立,已经存在依靠剥削养尊处优的统治者。
已经有了文字。
阇提印度中古时期的种姓制度。
该制度按行业划分成不同种姓,种姓内职业世袭,种姓间禁止通婚。
这一制度称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耆那教公元前6世纪印度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奠基人和创立者是筏驮摩那。
该教代表了刹帝利和吠舍大商人的利益。
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能黏附于人的灵魂上。
行善者可以转生了天神,作恶者可转生为低级种姓、动物和无生物。
耆那教的最高理想是让受业和肉体这些物质束缚的灵魂得到解脱,得以脱离躯体,超脱轮回。
丰持“三宝”和五戒。
耆那教的进步性在于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争锋相对氐指出吠陀并非真知,杀生祭祀只会增加罪恶,婆罗门是不学无术的祭司。
其缺陷在于它囿于灵魂转世、因果报应、轮回解脱之见,并将禁欲和苦行当做解脱的好方法。
顺世论派古印度的一个唯物主义学派,活跃于列国时代,又称“顺世外道”和斫婆迦派,重要代表人物为阿耆多翅舍钦婆罗。
该派不承认吠陀和其他婆罗门教经典文献,主张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人死后没有灵魂和轮回。
该派激烈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人生而平等,本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认为人应该入世求快乐,反对苦行、禁欲。
该派观点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受到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也被视为异端邪说,作品基本全部被毁灭,目前仅存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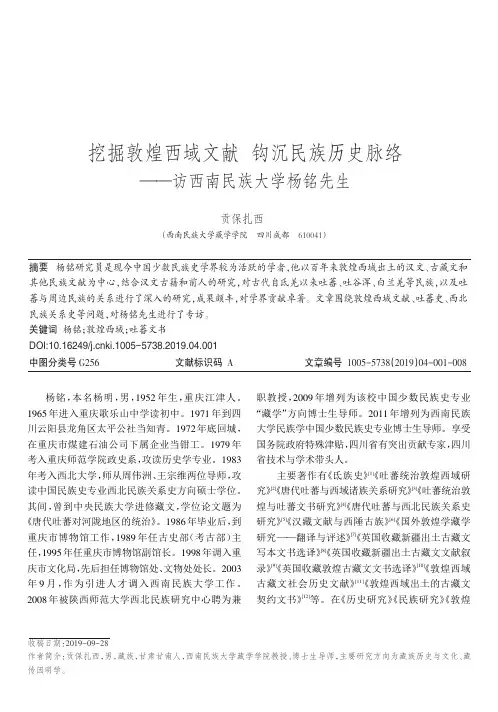
挖掘敦煌西域文献钩沉民族历史脉络——访西南民族大学杨铭先生贡保扎西(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摘要杨铭研究员是现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界较为活跃的学者,他以百年来敦煌西域出土的汉文、古藏文和其他民族文献为中心,结合汉文古籍和前人的研究,对古代自氐羌以来吐蕃、吐谷浑、白兰羌等民族,以及吐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对学界贡献卓著。
文章围绕敦煌西域文献、吐蕃史、西北民族关系史等问题,对杨铭先生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杨铭;敦煌西域;吐蕃文书DOI:10.16249/ki.1005-5738.2019.04.001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19)04-001-008杨铭,本名杨明,男,1952年生,重庆江津人。
1965年进入重庆歌乐山中学读初中。
1971年到四川云阳县龙角区太平公社当知青。
1972年底回城,在重庆市煤建石油公司下属企业当钳工。
1979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攻读历史学专业。
1983年考入西北大学,师从周伟洲、王宗维两位导师,攻读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北民族关系史方向硕士学位。
其间,曾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藏文,学位论文题为《唐代吐蕃对河陇地区的统治》。
1986年毕业后,到重庆市博物馆工作,1989年任古史部(考古部)主任,1995年任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
1998年调入重庆市文化局,先后担任博物馆处、文物处处长。
2003年9月,作为引进人才调入西南民族大学工作。
2008年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聘为兼职教授,2009年增列为该校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藏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2011年增列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技术与学术带头人。
主要著作有《氐族史》[1]《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2]《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3]《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4]《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5]《汉藏文献与西陲古族》[6]《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7]《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文书选译》[8]《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叙录》[9]《英国收藏敦煌古藏文文书选译》[10]《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11]《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12]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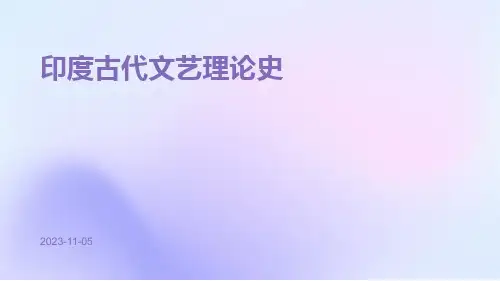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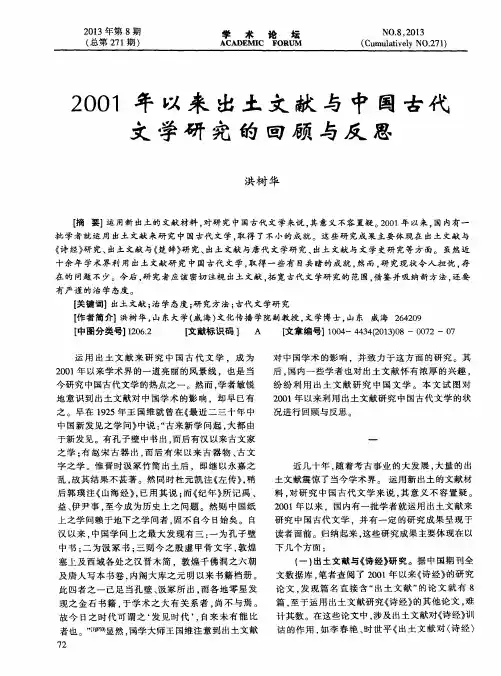
古代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古代中国和印度作为东亚和南亚地区两个重要的古代文明国家,其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领域。
两个国家之间在语言、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交流与相互影响。
本文将以一些典型的方面来进行讨论。
首先,语言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的基础。
古代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文字传统。
在语言方面,中印两国有很多共同之处。
比如,中印两国的语言都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
虽然语法和词汇上存在差异,但在音韵和词义上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梵语和中文都是古代汉藏语系中的重要语言,梵文在佛教传播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哲学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家和墨家等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而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主要以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对印度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两国在哲学思想上存在差异,但都强调了人类的解脱和生命的意义。
各自的哲学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影响和借鉴。
此外,艺术也是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灿烂的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传统。
中国的山水画和印度的瑜伽雕塑都是两国艺术的代表作品。
这些艺术形式表达了两国民众对自然和宗教的热爱和崇拜。
在音乐方面,印度的印度音乐和中国的古琴音乐都是独特而又各具特色的音乐形式,它们通过音乐的艺术语言传达了对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表达。
最后是宗教。
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思想在古代中国影响巨大,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使中国迎接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的道教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尤其是影响了印度的修行和瑜伽思想。
总结起来,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涉及了语言、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多个层面。
两个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和相互借鉴,共同构建了东亚和南亚古代文明的瑰宝。
有关西域的历史文献
西域(即古代中国的西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明与西方文
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包含了今天的新疆地区以及西藏、甘肃等地。
西
域的历史在古代文献中有广泛的记载,这些文献对于研究西域历史、
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具有重要价值。
最早的有关西域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史记》,该书是我国最
早的纪传体历史专著,由司马迁撰写。
其中,《大宛列传》、《大宛、句踐列传》和《西域列传》等篇目详细记载了西域各国的状况、居民、地理位置以及与中原的交往情况。
汉代的《西域记》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当时大致
上一带国家与中原的关系,例如匈奴、月氏、大夏、梵船等国家的信息。
唐代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详尽记载唐朝时期对西域各国使节、历史沿革、文化风貌等情况的历史文献。
这本书是根据玄奘法师在西
天取经的经历所写,成为了研究唐代对外交往以及西域传统文化的重
要参考资料。
明清时期的《西域总志》和《新疆通志》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包
括西域地理、民族、宗教、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古代文献纪录了西域各国王侯、使节到中原
朝贡的情况,例如《通典》、《维摩诘五计真经尊胜集经款》、《义
守原经》等,这些文献为了解当时西域与中原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提供
了珍贵资料。
总之,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西域的历史资料丰富多样,这些文
献为我们了解西域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中原与西域交往提供了重要
参考。
印度的古代文学和诗歌印度拥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学传统,古代的印度文学和诗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和文化背景,也传承了印度人民的智慧和情感。
本文将探讨印度古代文学和诗歌的特点,以及其对印度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影响。
1. 古代印度文学的分类印度古代文学主要分为梨俱吠陀文学、史诗文学、瑜伽文学和戏剧文学四大类别。
梨俱吠陀文学包括《梨俱吠陀》、《协同吠陀》等经典,代表了古代宗教和哲学思想;史诗文学则以《摩诃婆罗多》和《拉玛传》为代表,讲述了古代英雄和神话传说;瑜伽文学涵盖了印度古代文学中的修行、冥想和内心探索的主题;戏剧文学则以《纳塔亚沙斯特拉》等作品见长,展现了古代印度戏剧的表演艺术和情感体验。
2. 古代印度诗歌的特点印度古代诗歌的特点是形式多样、语言华丽和主题丰富。
其中,梵文是古代印度诗歌的主要创作语言,以其丰富多彩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为古代印度文学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
古代印度诗歌多采用形象生动、修辞辛辣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比喻、暗喻和象征等手法来传达情感和思想。
主题方面,古代印度诗歌涵盖了爱情、自然、宗教、道德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古代印度人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3. 古代印度文学对印度文化的影响古代印度文学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的风貌和发展历程,也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古代印度文学中关于宗教和哲学的思想奠定了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
古代印度文学中的英雄和神话故事激发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英勇精神,成为了他们面对生活困难和挑战的力量源泉。
4. 古代印度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古代印度文学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印度本土,古代文学成为了当代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他们借鉴了古代文学的表达方式和主题,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
同时,在国际文学舞台上,古代印度文学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文学史整理(中印对照)
开头
印度文学是一个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尽管从历史上看,印度与中国南亚相邻,但两个国家的文学有着不同的发展和特点。
本文旨在对印度文学史进行整理,并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
古代文学
* 印度古代文学以吠陀经为代表。
吠陀经包括很多篇章,其中《摩诃婆罗多》、《拉姆史诗》、《布哈拉塔》等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文学的杰作。
*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诗经》、《楚辞》等。
中国古代文学也有诸多杰作,但在形式和类别上又有所不同。
中古文学
* 中古时期,印度的文学成果颇为丰硕。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四大名著”:《罗摩衍那》、《大涅磐经》、《浮屠经》和《瑜伽经》。
* 在中国,中古文学是诸多流派并存的时期。
其中唐诗是中国
文学的代表,其统一而清新的风格深受后人喜爱。
近代文学
* 近代印度文学的代表作品包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多元化、开放性强,反映了时代的多样性。
* 而中国的近代文学则包括了《红楼梦》、《金瓶梅》等。
这
些作品在揭示社会现实、反映人性缺陷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
结论
印度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个国家的文学
都有其独特的代表作品和风格,但也有着相通之处。
本文所述只是
两个文化的冰山一角,希望读者对印度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
古代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古代的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这种交流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有所表现,更体现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医学等方面。
本文将探讨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尝试回顾其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是印度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
佛教经过长期的发展与传播,在中国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
而佛教的传入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2世纪,汉朝时期的中国僧人鸠摩罗什带着佛经从西域传入中国,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与婆罗门教的压迫以及人们对彻底解脱的渴望密切相关。
佛教在印度影响了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并通过佛经和修行方法的传播而逐渐扩散到印度以外的地区。
二、印度文学的传播古代印度的悠久文学传统不仅在本土深受推崇,也透过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国。
其中,《摩诃婆罗多》被誉为是古印度史诗的瑰宝,其故事情节丰富多样,凝聚了印度人民的智慧和思想。
这部史诗通过翻译和解读,被引入到中国,对中国文学的演绎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在唐朝,一些文士学者开始将印度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使得中国的文学受到了印度文化的熏陶。
三、医学和数学的交流古代印度和中国也在医学和数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印度的医学传统以《阿育吠陀》为代表,这部经典被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医学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印度医学的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吸收和发展,对中国的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印度的数学成就也传入了中国。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数学家无子提耶的《阿耶尔汗迪》和《算经》被译成中文,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四、艺术与建筑的交流印度和中国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交流同样十分丰富多彩。
古代印度以其精美的壁画、雕塑和佛教造像而著称。
这些艺术品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文学和文化成就古代印度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在文学和文化方面也有着非常卓越的成就。
从早期的吠舍时期,再到维吾尔王朝和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持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在本文中,我将简要探讨古代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和成就。
在古代印度的吠舍时期,印度文学的发展步入了繁荣时期。
此时期,印度著名的四部吠舍经典——《吠舍经》、《易经》、《诗经》和《礼经》被创作。
这些经典不仅在印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成为印度东方哲学和学院的瑰宝,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这些古老的文学遗物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书籍和文物也被保存下来,如《吠陀》、《经典》、《国际学校》等。
由于印度曾被许多王朝统治,如克什特拉王朝、坎大哈王朝、玛哈利希王朝等,这些王朝带来了大量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艺术,这促进了印度文化的多元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印度成为了一个拥有广泛文化遗产的国家。
印度的文化主要包括音乐、绘画、剧院、雕塑等领域。
此外,印度还以玛哈巴拉塔和拉姆亚纳为主的一些重要史诗文学而闻名。
玛哈巴拉塔是古代印度最杰出的史诗之一,也是古代印度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它以故事的方式记录了古代印度的文化和历史。
玛哈巴拉塔的创作历时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它详细描述了印度王国的起源、成长和发展,并阐明了各个王国之间的关系。
它的作者是威尼斯·瓦尔马基,他以许多传奇人物和事件取代了史实,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
玛哈巴拉塔不仅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还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除了玛哈巴拉塔之外,拉姆亚纳同样是另一个对古代印度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影响的重要文学杰作。
拉姆亚纳讲述了一个印度王子娶妻后后半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冒险、爱情、自我发现和旅程。
拉姆亚纳强调了忠诚、正直、勇敢和良知这些重要的价值观,他的作品还包括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元素。
在印度的文学中也有一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印度文化和人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
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 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SPA W,17,1911,pp.388-411.)。
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附图注释:③附图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①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
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作品。
吕德斯认为,附图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
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规定。
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
)1910年前后,南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
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18页。
)。
其成书年代,后来更是引起了激烈讨论,但得出的结论差距甚远。
金克木先生认为,“看来,纵然这些是跋娑的作品,也未必在马鸣之前。
”(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跋娑要早于迦梨陀娑,而晚于马鸣。
因此,马鸣的剧本就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既为我们了解印度戏剧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最具体的例证,同时,也成了探讨中印戏剧渊源关系的最早样本。
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利用吕德斯的研究成果,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对梵剧《舍利弗传》和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作了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细致探讨。
以后,凡论及中国戏剧起源者,无人不提马鸣之作(注:陈明:《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待刊)。
)。
解放后,新疆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西域剧本,其中最主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发现有:1959年在新疆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1974年,新疆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
这两个语种的剧本与印度梵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前者的主要研究论文有: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2年。
又,多鲁坤•阚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89年第1期。
),以及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而后者的主要工作是由季羡林先生完成的,其专著有英文本《中国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注: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Museum,China.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Mouton deGruyter,1998.)和中文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注: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这些新材料的阐释,为印度文学在新疆的传播史实,做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西域出土的这些戏剧史料,对讨论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先生对此已有多次申述,最近在《新日知录》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他指出,印度最早剧本的产生时间(及其与中国、希腊剧本产生时间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古典戏曲的文体特色(韵散结合)、剧本中的丑角问题等,都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注:季羡林:《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9页。
)。
这为我们指明了好几个研究课题。
二、西域所见的印度佛教文学作品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五章“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已指出庞大的印度佛教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文学成分。
深浦正文的《佛教文学概论》则将佛教文学体裁分为譬喻、本生、佛传、理想、赞颂等十种,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将原始佛教的典籍,分为阿含类、@②奈耶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五大类(注:山田龙城:《梵语佛典の诸文献》,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
中译本名为《梵语佛典导论》(许洋主译),收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9册),华宇出版社,1984年。
)。
后三者即为文学类。
下面试以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譬喻文学郭良@③的《佛教譬喻经文学》一文,对佛藏(特别是巴利文三藏)中的譬喻经一类作品,作了总体的文学价值描述(注:郭良@③:《佛教譬喻经文学》,《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62-66、73页。
)。
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是第一部以譬喻文学这一种佛教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注: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8,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年。
陈明书评,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增刊,154-156页。
其修改稿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编《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57-59页。
)。
不过,该书仅仅研究现存的汉译佛经中的譬喻文学作品,而没有涉及梵文、巴利文的相关作品,更没有注意到在西域出土的梵语文书中也有数量不等的“譬喻”类文献资料。
德国所藏吐鲁番的梵文写本中,有不少的佛教文学作品。
诗歌附图注释:(17)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127-138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此见该书155-156页。
的文书(编号SI P/38)和一件无标题的譬喻文书(编号SI P/63)(注:G.M.Bongard-Levin andM.I.V 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Buddhist Studies,1986.)。
阿富汗近年出土的@④卢文佛经写卷,“根据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的研究,从这批@④卢文的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经典,大致有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
在譬喻类的经典中,提到了公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大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⑤pavarman。
邵瑞祺的看法,这些譬喻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释迦牟尼时代那些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有关,另一类则似乎是以当时由月氏人统治的乾陀罗作为背景。
这两种类型的譬喻故事,虽然抄写在不同的卷子上,但却混编在了一块。
”(注: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Fragments,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9页。
)对邵瑞琪的分辨出的譬喻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价值,王邦维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业已指出,“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
”(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
)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详见下文。
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中的奇葩。
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
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
附录于氏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
)。
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
)。
《佛所行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早由饶宗颐先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
又,参见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