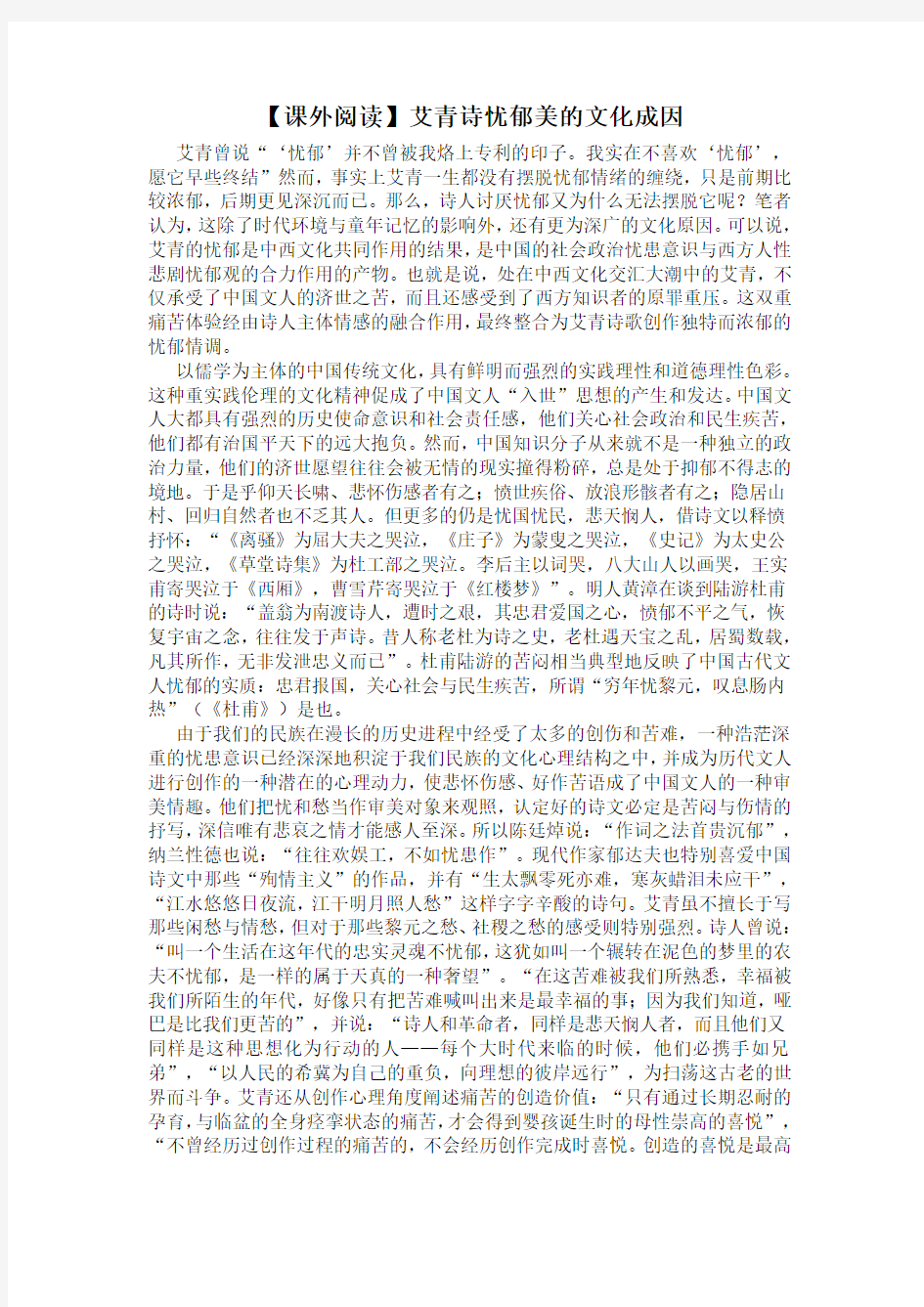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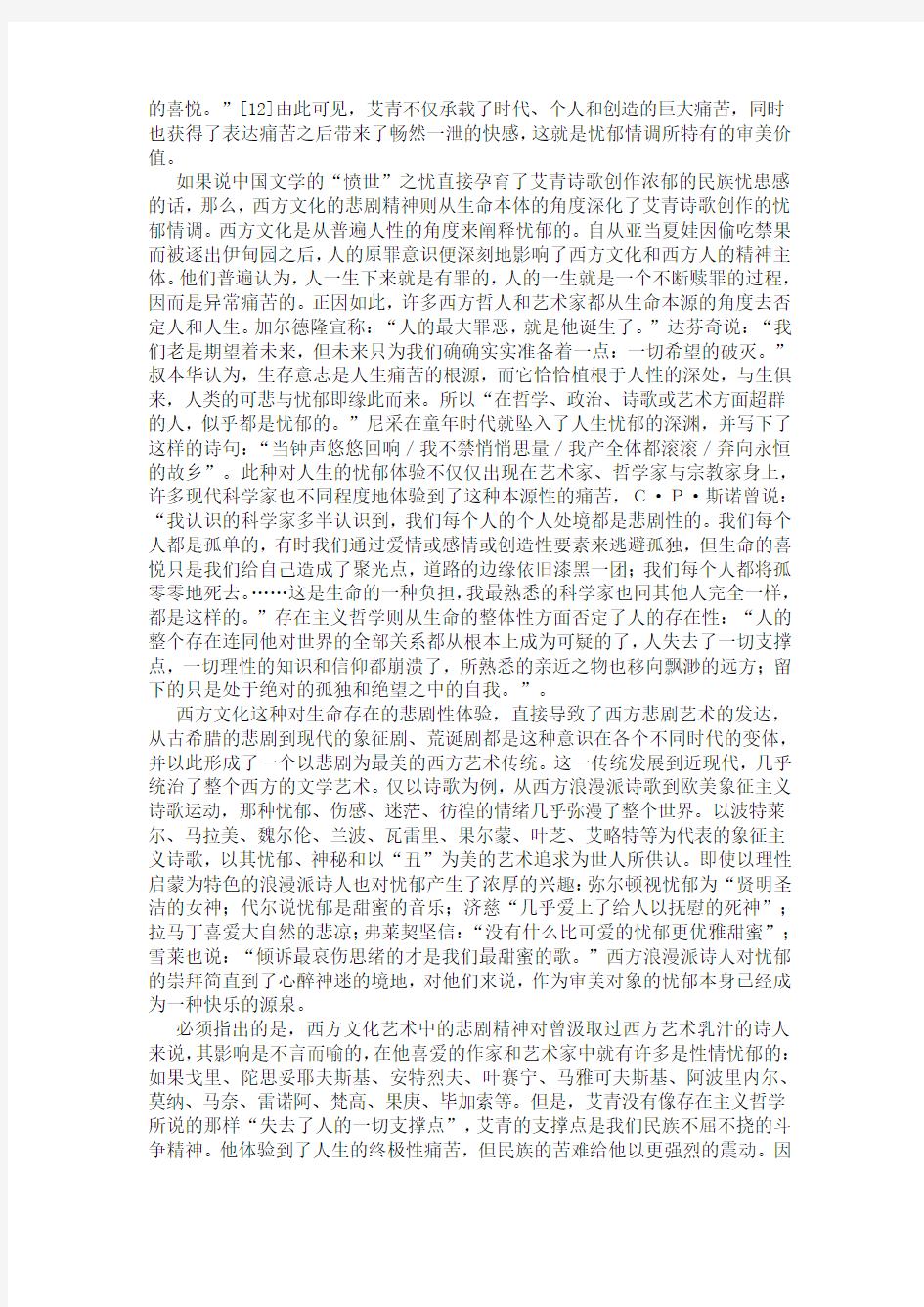
【课外阅读】艾青诗忧郁美的文化成因
艾青曾说“‘忧郁’并不曾被我烙上专利的印子。我实在不喜欢‘忧郁’,愿它早些终结”然而,事实上艾青一生都没有摆脱忧郁情绪的缠绕,只是前期比较浓郁,后期更见深沉而已。那么,诗人讨厌忧郁又为什么无法摆脱它呢?笔者认为,这除了时代环境与童年记忆的影响外,还有更为深广的文化原因。可以说,艾青的忧郁是中西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忧患意识与西方人性悲剧忧郁观的合力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处在中西文化交汇大潮中的艾青,不仅承受了中国文人的济世之苦,而且还感受到了西方知识者的原罪重压。这双重痛苦体验经由诗人主体情感的融合作用,最终整合为艾青诗歌创作独特而浓郁的忧郁情调。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色彩。这种重实践伦理的文化精神促成了中国文人“入世”思想的产生和发达。中国文人大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社会政治和民生疾苦,他们都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济世愿望往往会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总是处于抑郁不得志的境地。于是乎仰天长啸、悲怀伤感者有之;愤世疾俗、放浪形骸者有之;隐居山村、回归自然者也不乏其人。但更多的仍是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借诗文以释愤抒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明人黄漳在谈到陆游杜甫的诗时说:“盖翁为南渡诗人,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念,往往发于声诗。昔人称老杜为诗之史,老杜遇天宝之乱,居蜀数载,凡其所作,无非发泄忠义而已”。杜甫陆游的苦闷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忧郁的实质:忠君报国,关心社会与民生疾苦,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是也。
由于我们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了太多的创伤和苦难,一种浩茫深重的忧患意识已经深深地积淀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成为历代文人进行创作的一种潜在的心理动力,使悲怀伤感、好作苦语成了中国文人的一种审美情趣。他们把忧和愁当作审美对象来观照,认定好的诗文必定是苦闷与伤情的抒写,深信唯有悲哀之情才能感人至深。所以陈廷焯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纳兰性德也说:“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现代作家郁达夫也特别喜爱中国诗文中那些“殉情主义”的作品,并有“生太飘零死亦难,寒灰蜡泪未应干”,“江水悠悠日夜流,江干明月照人愁”这样字字辛酸的诗句。艾青虽不擅长于写那些闲愁与情愁,但对于那些黎元之愁、社稷之愁的感受则特别强烈。诗人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灵魂不忧郁,这犹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年代,好像只有把苦难喊叫出来是最幸福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哑巴是比我们更苦的”,并说:“诗人和革命者,同样是悲天悯人者,而且他们又同样是这种思想化为行动的人——每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必携手如兄弟”,“以人民的希冀为自己的重负,向理想的彼岸远行”,为扫荡这古老的世界而斗争。艾青还从创作心理角度阐述痛苦的创造价值:“只有通过长期忍耐的孕育,与临盆的全身痉挛状态的痛苦,才会得到婴孩诞生时的母性崇高的喜悦”,“不曾经历过创作过程的痛苦的,不会经历创作完成时喜悦。创造的喜悦是最高
的喜悦。”[12]由此可见,艾青不仅承载了时代、个人和创造的巨大痛苦,同时也获得了表达痛苦之后带来了畅然一泄的快感,这就是忧郁情调所特有的审美价值。
如果说中国文学的“愤世”之忧直接孕育了艾青诗歌创作浓郁的民族忧患感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悲剧精神则从生命本体的角度深化了艾青诗歌创作的忧郁情调。西方文化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阐释忧郁的。自从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的原罪意识便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精神主体。他们普遍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赎罪的过程,因而是异常痛苦的。正因如此,许多西方哲人和艺术家都从生命本源的角度去否定人和人生。加尔德隆宣称:“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达芬奇说:“我们老是期望着未来,但未来只为我们确确实实准备着一点:一切希望的破灭。”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而它恰恰植根于人性的深处,与生俱来,人类的可悲与忧郁即缘此而来。所以“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的人,似乎都是忧郁的。”尼采在童年时代就坠入了人生忧郁的深渊,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量/我产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此种对人生的忧郁体验不仅仅出现在艺术家、哲学家与宗教家身上,许多现代科学家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了这种本源性的痛苦,C·P·斯诺曾说:“我认识的科学家多半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处境都是悲剧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有时我们通过爱情或感情或创造性要素来逃避孤独,但生命的喜悦只是我们给自己造成了聚光点,道路的边缘依旧漆黑一团;我们每个人都将孤零零地死去。……这是生命的一种负担,我最熟悉的科学家也同其他人完全一样,都是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则从生命的整体性方面否定了人的存在性:“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远方;留下的只是处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
西方文化这种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直接导致了西方悲剧艺术的发达,从古希腊的悲剧到现代的象征剧、荒诞剧都是这种意识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变体,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以悲剧为最美的西方艺术传统。这一传统发展到近现代,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方的文学艺术。仅以诗歌为例,从西方浪漫派诗歌到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运动,那种忧郁、伤感、迷茫、彷徨的情绪几乎弥漫了整个世界。以波特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瓦雷里、果尔蒙、叶芝、艾略特等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以其忧郁、神秘和以“丑”为美的艺术追求为世人所供认。即使以理性启蒙为特色的浪漫派诗人也对忧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弥尔顿视忧郁为“贤明圣洁的女神;代尔说忧郁是甜蜜的音乐;济慈“几乎爱上了给人以抚慰的死神”;拉马丁喜爱大自然的悲凉;弗莱契坚信:“没有什么比可爱的忧郁更优雅甜蜜”;雪莱也说:“倾诉最哀伤思绪的才是我们最甜蜜的歌。”西方浪漫派诗人对忧郁的崇拜简直到了心醉神迷的境地,对他们来说,作为审美对象的忧郁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快乐的源泉。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文化艺术中的悲剧精神对曾汲取过西方艺术乳汁的诗人来说,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他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中就有许多是性情忧郁的:如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烈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波里内尔、莫纳、马奈、雷诺阿、梵高、果庚、毕加索等。但是,艾青没有像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那样“失去了人的一切支撑点”,艾青的支撑点是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体验到了人生的终极性痛苦,但民族的苦难给他以更强烈的震动。因
此,为民族命运而担忧,为不幸的人们而呐喊,为祖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构成了艾青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正像诗人自己所说:“英雄应该是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受着整个世纪所给予的绞刑。”艾青自己正是这样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