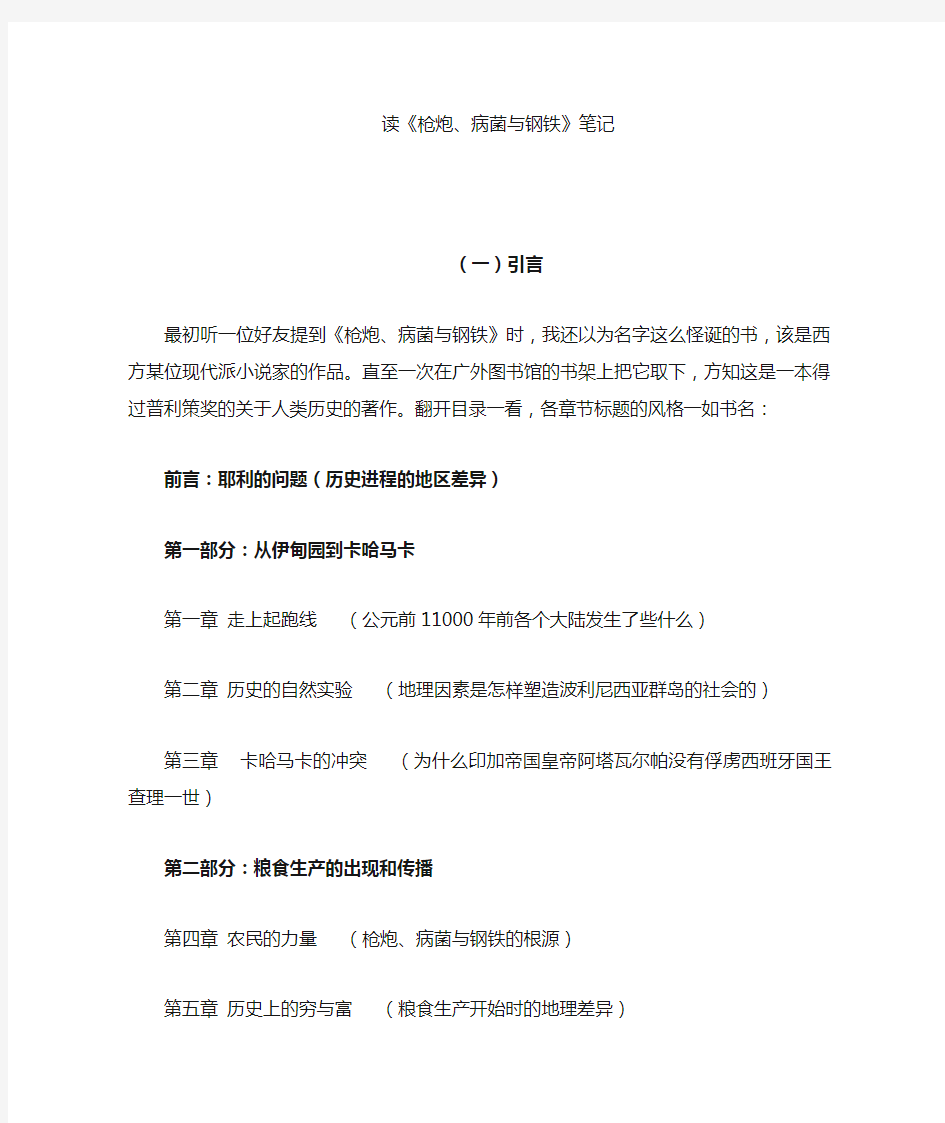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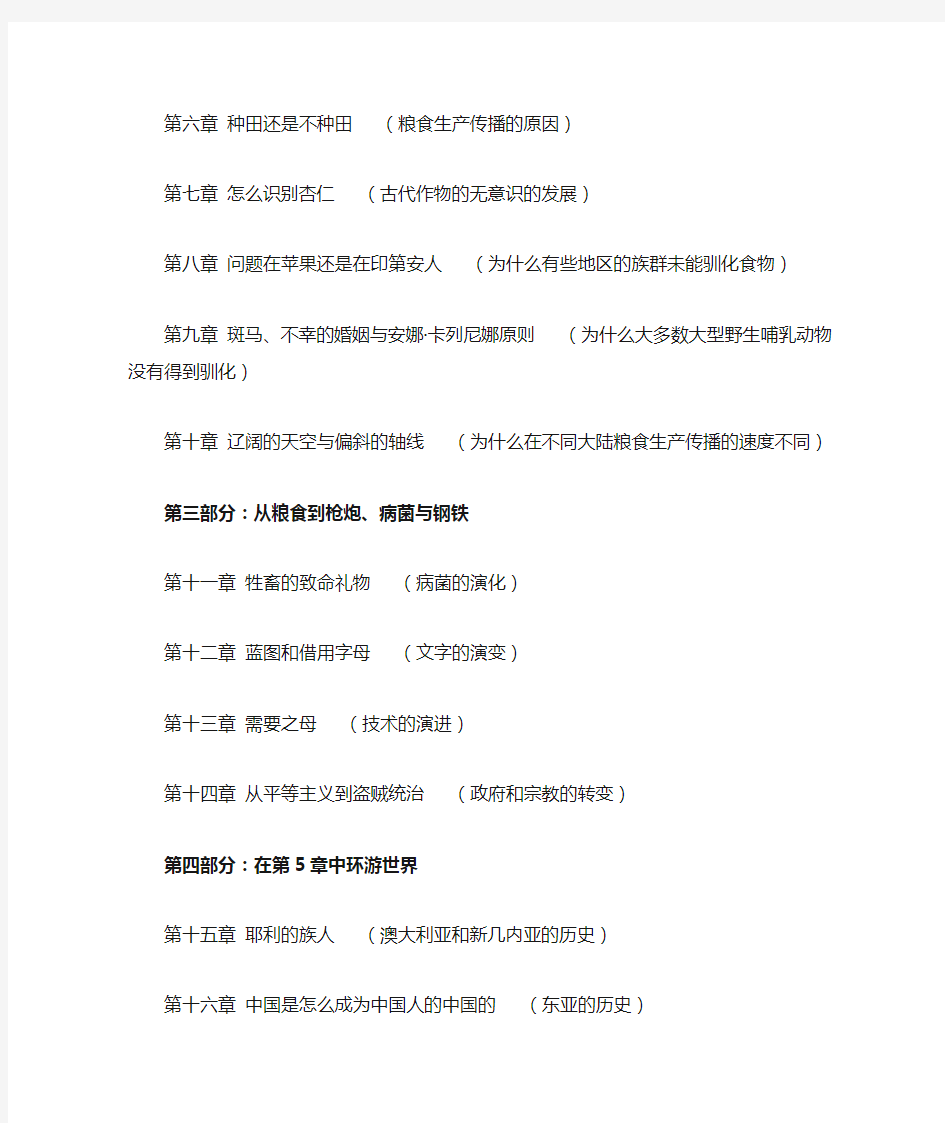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笔记
(一)引言
最初听一位好友提到《枪炮、病菌与钢铁》时,我还以为名字这么怪诞的书,该是西方某位现代派小说家的作品。直至一次在广外图书馆的书架上把它取下,方知这是一本得过普利策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著作。翻开目录一看,各章节标题的风格一如书名:
前言:耶利的问题(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
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章走上起跑线(公元前11000年前各个大陆发生了些什么)
第二章历史的自然实验(地理因素是怎样塑造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社会的)
第三章卡哈马卡的冲突(为什么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没有俘虏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第二部分: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
第四章农民的力量(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根源)
第五章历史上的穷与富(粮食生产开始时的地理差异)
第六章种田还是不种田(粮食生产传播的原因)
第七章怎么识别杏仁(古代作物的无意识的发展)
第八章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族群未能驯化食物)
第九章斑马、不幸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为什么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
第十章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为什么在不同大陆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不同)
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病菌的演化)
第十二章蓝图和借用字母(文字的演变)
第十三章需要之母(技术的演进)
第十四章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政府和宗教的转变)
第四部分:在第5章中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耶利的族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历史)
第十六章中国是怎么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东亚的历史)
第十七章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南岛人扩张的历史)
第十八章两个半球的碰撞(欧亚大陆与美洲历史的比较)
第十九章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非洲的历史)
后记: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此种行文风格,似乎与香港对外国影片名字的翻译一样,有故意吸引读者眼球之嫌。但是这本315千字的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的确有别于一般描述历史的书。让人阅读时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但它又没有《历史是什么玩意儿》这类读物那种搞怪的习气。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兼语言学家,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良好的家庭熏陶,使他从小就对语言、历史和写作感兴趣。在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他的研究领域为分子生理学、地理生物学以及演化生物学。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做鸟类演化研究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的一起生活,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的社会。他因此说:“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
戴蒙德之所以写这本书,缘于一次在新几内亚的经历。当地一位叫耶利的仅上过中学的政治家问他:“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的货物呢?”
戴蒙德认为这是一个“简单但切中要害的问题”。新几内亚人和欧美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可以说是众多落后地区族群和欧美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的一个缩影。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世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在作出类似这样的解释:当公元1500年左右大洋航道刚开辟之时,葡萄牙、西班牙等等民族君主国,已经拥有坚船利炮(即戴蒙德说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由此获得了对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巨大优势。(一个著名的戏剧性事件就是,1532年在秘鲁的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皮萨罗率领一群168个西班牙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竟然迅速地击败了8万人之多的印加帝国军队,俘获了皇帝阿塔瓦尔帕。)此后欧洲各国在一边掠夺烧杀一边贸易的海外殖民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使本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实现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民主化,从而迈向现代化道路。欧洲及欧洲人重建的北美,越来越大地拉开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距离,并持续至今。
但是戴蒙德认为,从公元1500年就已经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只是现代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或说“近似原因”)。他想寻找的是根本原因(或说:“终极原因”):这个世界时如何形成公元1500年的那个模样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戴蒙德斥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由于智力上的差异所造成。因近代以来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自诩为“上帝的选民”的他们,坚信世上各民族有优劣之分。(极端例子如希特勒)。他们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例如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13000年之久,但直到近代还过着原始生活。而欧洲人只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就在美洲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在这本书里,戴蒙德用充分的证据和科学的理论,将这种解释逐个戳破。他指出,在美洲殖民的欧洲人,只是把欧亚大陆已有的文明移植过去,并非在新大陆创造新文明。他甚至认为新几内亚人比欧美人聪明,这是由他在与新几内亚人的长久交往经历得出的。
他解释,在因频繁的部落战争导致死亡率高居不下的新几内亚,聪明的人往往更容易存活,然后把基因遗传到下一代。所以能在社会上生存的人,往往是高智力的人。而在和平稳定、医学昌明的欧美社会里的人群中,智力上往往高低不一。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欧美社会的孩童花大量时间来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所提供的娱乐。而新几内亚的孩童却把时间用以从事积极的活动上,例如与别的儿童游戏或与大人
谈话、劳动。而据科学研究表明,这种童年刺激对智力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戴蒙德总结:“现代石器部落通常比工业化民族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
另外一种说法是从气候、资源上分析的。例如认为高纬地区因为天气寒冷,能促使人类动脑筋想办法维持生存。同理,资源匮乏促使人类设法搞发明创造弥补不足的说法。高纬地区漫长的冬夜,也让人类有足够的呆在室内进行思考的时间。(余秋雨也在其《欧洲之旅》里提到丹麦的漫长冬夜诞生了像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哲学家和像奥斯特这样的科学家)乍一看,这种理论很有道理。可是戴蒙德指出:按照这个思路,能否说在物产丰富之的热带地区,人类不用为生存而挣扎,从而获得更多搞发明创造的休闲时间?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才方便人类产生了利用资源的科学技术?由此看来,仅以气候和资源作为终极原因,是不可靠的。
那么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戴蒙德从人类的起源开始分析:
公元前700万年,人类从非洲猿的一支开始演化,在不断地演化中又逐渐迁移到世界各地。直到公元前11000年时,即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时,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都已经被分化成多个族群的人类所占据。此时,各大陆上族群都处于狩猎采集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了解了公元前11000年至公元1500年内各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世界为什么会变成公园1500年的那个模样,从而找出“终极原因”。
在寻求答案时,作者综合运用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个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等等的众多学科知识。才使得这本书角度新颖、视野开阔,严谨科学而又不失幽默地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决定了以后人类社会命运的史前史。
(二)夹叙夹议做摘要
1,粮食生产的重大作用
简单地说,粮食生产是指把野生植物驯化为作物并加以栽培、把野生动物驯化为牲畜加以蓄养,来获得食物及其它产物。粮食生产的出现的原因,学界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后,人口增长速度超越了自然界提供的食物的再生速度。在人口压力之下,人类不得不拓宽食物来源渠道。一说是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动植物的数量增多,为农业的起源提供基础。一说是历代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得到经验日增,发现了自然规律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把它们综合起来,也许是更全面的答案。
无论它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它的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在人类史上掀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它使人类的身份从狩猎采集者变为农民,经济性质从攫取性变为生产性,生活方式从到处迁徙所变为定居。定居生活本身就拥有巨大的优越性:它缩短了人类生育周期,有利于人口繁衍增长。因为流浪者不能随身携带众多的孩子,甚至因此采取某些节育措施。同理,流浪者所不能随身携带的其他东西,都可以被定居农民积累在住处附近。物品的累积,为发明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刚出现之初,农民生活方式和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之间之间,还存在着竞争。有时从事农业所得,还不如狩猎采集所得之多。但时间越久,农业的优越性就越明显。前面提到的
定居的优越性就是一例。
除此之外,农业发展最直接的结果是引起食物的增多,其来源也较为稳定。作物提供了碳水化合物(谷物)、维生素、植物纤维(棉花)、油等等,牲畜则提供了蛋白质(肉类)、动物纤维(羊毛)、动力(拉犁、拉磨)、作物肥料(粪便)、军事工具(马匹)等等。食物增多进而引起定居人口增多。定居的人口增多,意味着潜在的发明家增多;也意味着社会规模扩大,社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二者促使社会进步得更快。因此人口增多反过来又促使了农业规模扩大和农业技术发展。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相辅相成
农业发展带来的剩余粮食,是人类文明的培养基。剩余粮食变成了交易的货物,文字在商贸活动中应运而生。(例如新月沃地的苏美尔人所创的锲形文字,最早是为了记录商品货物交易)。剩余粮食养活了专职的手艺人,这些人是早期的艺术家和发明家;养活了专职的祭司,这些宗教领袖是发明文字的早期知识分子,往往被政治领袖兼任;养活了专职的军队,用以发动对外战争和抵御外敌,夺取和保护更多的资源(人口多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军事优势),壮大社会的力量;养活了从上至下的一整个行政组织,这是国家统治阶层的雏形。
沿着这个方向,农业使人类社会得形态逐步由族群发展成部落,再到酋长管辖地,最后演变成国家。经济专门化趋势日增,社会复杂程度日增,导致原本平等主义的公有制原始社会,变成等级森严的私有制阶级社会。由少数不从事生产的人组成的统治阶层建立的“盗贼统治”,奴役着多数生产者。
——但我们又不得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的极大进步。私有制的产生,带来贫富悬殊的同时,又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作为剥削工具的国家组织,又在调动人力物力修建水利工程以发展农业方面,在发动侵略战争或抵御外敌方面,在建立文化机构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相形之下,在平等主义的原始社会里,一个成员得到的所有,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平分。看似美好的制度,实质上使社会永远处于一种低级的、无进步的状态,该制度下得社会成员永远地共同贫困。
2,致命的产物
一般人很少会想到,粮食生产的另外一个重大产物竟然是——病菌。
历史上流行于人类社会,曾夺去无数生命的疾病,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等等杀手,都是来自于人类蓄养的牲畜。往往在农民住房的旁边,就是猪圈、羊圈、牛棚。亲密的接触多了,病菌从各种牲畜传播至人体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时间久了以后,经过演变的病菌竟只在人类中传播了。关于病菌是怎样想法设法传播繁衍的,戴蒙德在本书里有精彩详尽的描述,此处不赘。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人口稠密的人类社会里,病菌才有生存、繁衍和传播的可能。而要出现人口稠密的社会,只有在生产粮食的地区成为可能。历代的农民因为长期与这些病菌接触,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有的死去,有的康复),渐渐获得了对这些病菌的免疫力。而当带有这些病菌的健康人,一旦进入某些从未有过此种病菌的地区之时,当地毫无免疫力的居民就会感染疾病乃至死亡。
“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到前的土著人杀死了95%。”戴蒙德写道:“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是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遗传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
3,粮食生产的发源
要之,粮食生产的出现,连同火的使用、工业革命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尽管它带来了可怕的病菌,但其积极作用作用无论怎么夸大也不足为过。然而,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展农业。要进行粮食生产,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前面提到,粮食生产是指把野生植物驯化为作物并加以栽培、把野生动物驯化为牲畜加以蓄养。既然如此,那么发展农业必须先得有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
何谓“驯化野生植物”?一开始则是无意识的,例如某狩猎采集者吃了野果后把果核吐在某的地方,过了若干时间后,他发现该处竟然长出了一株同样结果的植物。受到的启发多了,便开始有意挑选对自身有利(例如果实大、味道甜美)的动植物后代来栽培。何谓“驯化野生动物”?戴蒙德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和饲养为人类所利用。”
请看下表:《欧亚大陆与美洲的历史轨迹》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附近的“两河地区)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独立农业发源地,时间分别为公元前8500年和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而美洲的安第斯地区、亚马孙河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部的农业却迟了大约5000年。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快慢程度?斯塔夫里阿诺斯
原来,虽然地球上的野生动植物不计其数,但是适合驯化的却很少,最后成功驯化为牲畜和作物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在地域上分配极不均匀。导致了一些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另外一些地区则“输在起跑线上”,欧亚大陆与美洲就是一个例子。
在世界上56种大种子禾本科植物中,有39种之多分布在欧亚大陆,而美洲只有11种。在世界上可供驯化的148候补哺乳动物之中,有71种分布在欧亚大陆,而美洲只有24种。而在候补哺乳动物中,成功驯化成牲畜的比率,在欧亚大陆是28%,在美洲大陆仅为4%。这并不是印第安人特别笨,不懂得驯化的方法,事实上,就连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解决当初印第安人的难题。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新几内亚人一样,早在很久以前就把可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成功驯化了。他们所不能驯化的,大多是今天也无法驯化的。
这是因为,驯化动植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植物的驯化,需要合适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还有产量高、雌雄同株自花传粉(以保持有利的基因变异)等生物条件。而动物的驯化则提出更高的要求:食物消耗量小、生长速度快、能在圈养中交配繁衍、性情较为温和、不容易受惊、具备跟随群体中的某个领袖的本能,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就是戴蒙德所说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他套用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改为:“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不可驯化之处”。
因为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品种数量的不同,以及用以驯化野生动植物的场所(自然环境)的不同,使得欧亚大陆拥有小麦、大麦、稻米、粟、高粱、小米、豌豆、以及牛、猪、绵羊、山羊、马等一整套作物与大型哺乳动物牲畜,而美洲只有玉米、南瓜、甘薯等少量作物及仅仅羊驼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牲畜。(因世界各地都无差别地拥有驯化的狗,故在此姑且忽略不计)。有一些地区,例如澳大利亚东南角、美洲加利福尼亚地区,在地理上很适合生产粮食可就是缺乏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在欧洲人到来以前,从未兴起过农业。而在引入牲畜和作物以后,一跃而成现代粮仓。
也有人认为存在着某些“文化障碍”,使得某些土著不思进取、极端保守。戴蒙德也承认,不同社会对外来事物、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然而他又指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印第安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在看见欧洲人带来的各种先进技术后,往往迅速地予以采纳,甚至成为内行。他们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这种技术,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大陆缺少发展这种技术的客观条件。例如印第安人以善于养马骑马著称,而马匹在被欧洲人带来之前,在美洲是不存在的。在直接可见的先进面前,“文化障碍”往往退居次要。
4,粮食生产的传播与交流
粮食生产的发源固然重要,而粮食生产的传播与交流同样重要。这涉及到各地区的交通条件。
无论对于作物、牲畜等农业资源,还是对于文字、钢铁、枪炮等科学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都需要便利的交通。各地区向外输出本地资源,向内输入外来资源,以此互补长短、相互促进。如果交通不便,不要说向别处学习,就连保持自身已经取得的果也变得困难。例如某些太平洋孤岛上的一些族群,由于与世隔绝,人口又少,竟然渐渐地遗弃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工具,主动地朝后倒退,更不必说搞发明创造了。
交通是否便利取决于该地生态障碍的强弱。戴蒙德为此阐述了“大陆轴线”的概念:从整体上讲,欧亚大陆主轴线为东西走向,这一方向大致与纬线平行。在此轴线上的各地区,尽管相隔遥远,但也拥有相近的日长和温度带,故在气候上也较为相近。因而新月沃地的作物和牲畜,也能传播至西欧、北非、印度等地并生存下来。例如小麦、大麦能从从新月沃地传至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也能传至欧洲。的新月沃地的书写系统和冶金技术,也能造福于离中心很远的地区。而美洲、非洲的轴线为南北走向,沿此方向上行进,相当于越纬度而行。这势必要跨越日长和温度带都截然不同的地区,因此尽管两地相隔不远,但隔绝程度如同大洋上的孤岛。玉米在墨西哥得到驯化了几千年之后,仍然不能到达美国的西南部。安第斯山脉培育的羊驼,无法跨越狭窄的巴拿马地峡热带雨林区和墨西哥沙漠区,北美东部的农业区也因此失去了羊驼作为打破零牲畜状态机会。玛雅文明的书写系统,无法为其他印第安社会所注意并效仿。西非的高粱,无法在南非存活。南北美洲相互隔绝的印第安社会之间的交流,近似于无。非洲内部各地的交流,也因撒哈拉大沙漠、刚果丛林等生态障碍而大受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里,反复强调地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斯氏通过研究个大陆的地理生态条件得出:在与外界交流的方便程度上,欧亚大陆为最高,非洲大陆次之,美洲大陆再次之,大洋洲排在最后。这个排序与各大陆的发展程度刚好吻合,也与各大陆在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吻合。欧亚大陆本来就有巨大农业潜力,便利的交通不啻如虎添翼,充分享受到了我在摘要的第1点提到的“粮食生产的巨大作用”。而其他大陆的农业前景本来就惨淡,重重的交通障碍,无异雪上加霜。粮食生产的起源基础与传播条件两组因素的综合起来,其作用更像乘法而不是加法,进一步把个大陆发展程度的差异大大拉开。
有意思的是,戴蒙德又补充,最有利于文化、科技的传播的交通条件应该是适中的。交通过于便利或者过于不便都不好。正因为中国内部交通太过发达,导致自公元前221年以来就处在高度集中的统一政权之下。当某位专制君主做出某个愚蠢的决定时,全国都不得不服从这一命令。例如停止航海活动,又如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纱机,在十四世纪从一种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而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一直得不到统一的欧洲,因为存在着许多发明创造的核心,所以尽管某些核心朝向消极方向,而始终存在另外一些核心朝向积极方向,而不至于集体堕落。例如,哥伦布在前后请求了欧洲三个不同国君后而遭拒绝后,投奔西班牙才得以扬帆出航。“如果欧洲在这头三个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
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5,回答耶利的问题
在科学地研究、分析完各个方面之后,戴蒙德知道该怎么回答耶利提出的问题了:
各个大陆1,在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数量上的不同(决定粮食生产的起源)
2,在与其他地区交流的方便程度上的不同(决定粮食生产及其衍生的文化、技术的传播)
3,在面积上的不同(更大的面积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更多可供相互交流的地区)
4,在人口上的不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潜在的发明家,以及竞争更加激烈社会,而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上述第1、2点决定)决定了不同大
陆的发展程度,最终造成了公元前1500年的那种差异。
欧亚大陆因其得天独厚的环境,得以走在其他大陆族群的前面。公元1500年时,新月沃地早已因为生态恶化而丧失了领先地位;君主专制的中国在经历辉煌之后开始走向黄昏;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变得“生气勃勃”(斯塔夫里阿诺斯语)的欧洲,越发富有创造力和侵略性。后起之秀的欧洲成为了欧亚大陆13000年发展成果的集大成者,以财富为目的,以武力为手段,以宗教为借口,开始去征服、掠杀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而不是相反。
当今新几内亚人和白人的祖先,在智力上并无差异。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客观环境里,才有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因而造成了持续至今的新几内亚人与欧美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其他落后地区族群与欧美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戴蒙德说,如果13000年时处在同一水平的远古印第安人、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与远古欧亚人,去到的是与现在相反的大陆,例如前者去到的是欧亚大陆,后者去到的是美洲大陆、非洲或澳大利亚。那么历史将会变成:发展程度高的前者携带者枪炮、病菌与钢铁去征服发展程度低的后者。
戴蒙德在第四章里浓墨重彩地描述,欧洲人在1500年后开始的侵略活动,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以前,源于中国华南的南岛人,源于西非的班图人,由于从事农业获得了对其他地区的优势,已经分别远远地扩张到马达加斯加和南部非洲。凭着粮食生产积累而得的力量,携带着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等产物的族群向外扩张殖民,征服技术和政治上落后的地区的族群,这就是历史的最广泛模式。
这一结论,是对种族主义理论的有力打击。为了说明是环境而不是智力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影响,戴蒙德早在第二章提到一个“历史的自然实验”。波利尼西亚群岛人(即南太平洋诸岛上的人)都源于同一个祖先(因而智力上相同),只是他们的祖先在对外扩张中,去了在岛屿气候、地址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上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岛屿,分散各岛的波利尼西亚人独立地生活若干时段后,一部分人变成了阶级分明的国家下的农民(如夏威夷群岛),另一部分人则依然是平等主义原始部落里的狩猎采集者(如查塔姆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竟同时存在着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国家等不同的社会类型。再强调一次,这些农民和狩猎采集者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发的祖先的后代!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这个“自然实验”,就是整个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剖面:人类从非洲起源,扩散到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成各种各样的社会。
(三)自己的一些想法
既然人类能够远渡重洋去到太平洋诸岛,那为什么又不用来到这些岛屿的方法,去与外面世界交流,而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呢?难道他们来到这些岛屿纯属偶然因素,事先毫无准备?仅例如某天在海上划独木舟时遭遇风暴而偏离航线所致?但是,对于南岛人在不迟于公元300年横跨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加的这一惊人事件,戴蒙德经过种种分析后认为南岛人的扩张是有准备的。
更有,戴蒙德在简介人类是如何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时,颇为煞费苦心地利用数学计算解释为什么人类能在短短2000年内,就能从北美阿拉斯加地区迁徙到南美地区。但是在阐述美洲南北走向的主轴线时,有不遗余力地大谈南北之间的交通是多么艰难。这相互矛盾之处让我感到很困惑:既然从亚洲远道而来、最终成为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能够跋涉长途,越过南北之间的重重生态障碍,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新居处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反而在跨地交流方面变得那么困难了呢?
对于戴蒙德的“大陆主轴线”,在大致上我是认同的。中学时代的地理知识告诉我,其实偌大的欧亚大陆也在地形、气候上也是出了名的复杂,从阿尔卑斯山脉、到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从地中海气候、高原山地气候到温带沙漠气候到温带季风气候,几乎无所不包。就连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中国,也有古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可以说,在大陆内部交通方面,欧亚大陆其实比美洲大陆好不了很多。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文化技术交流之所以那么频繁,我认为是欧亚大陆的文明相对来讲是太发达了,膨胀的人口压力促成了强大的对外扩散动力,使一批难在本地难以找到良田的农民向外迁出,客观上起到传播交流的作用。而且欧亚大陆以其巨大面积而拥有新月沃地、印度、中国等可供交流的较大的文明中心。而美洲各农业区的农业在先天上就存在缺陷,连自身也难以满足,对外扩散力度的则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