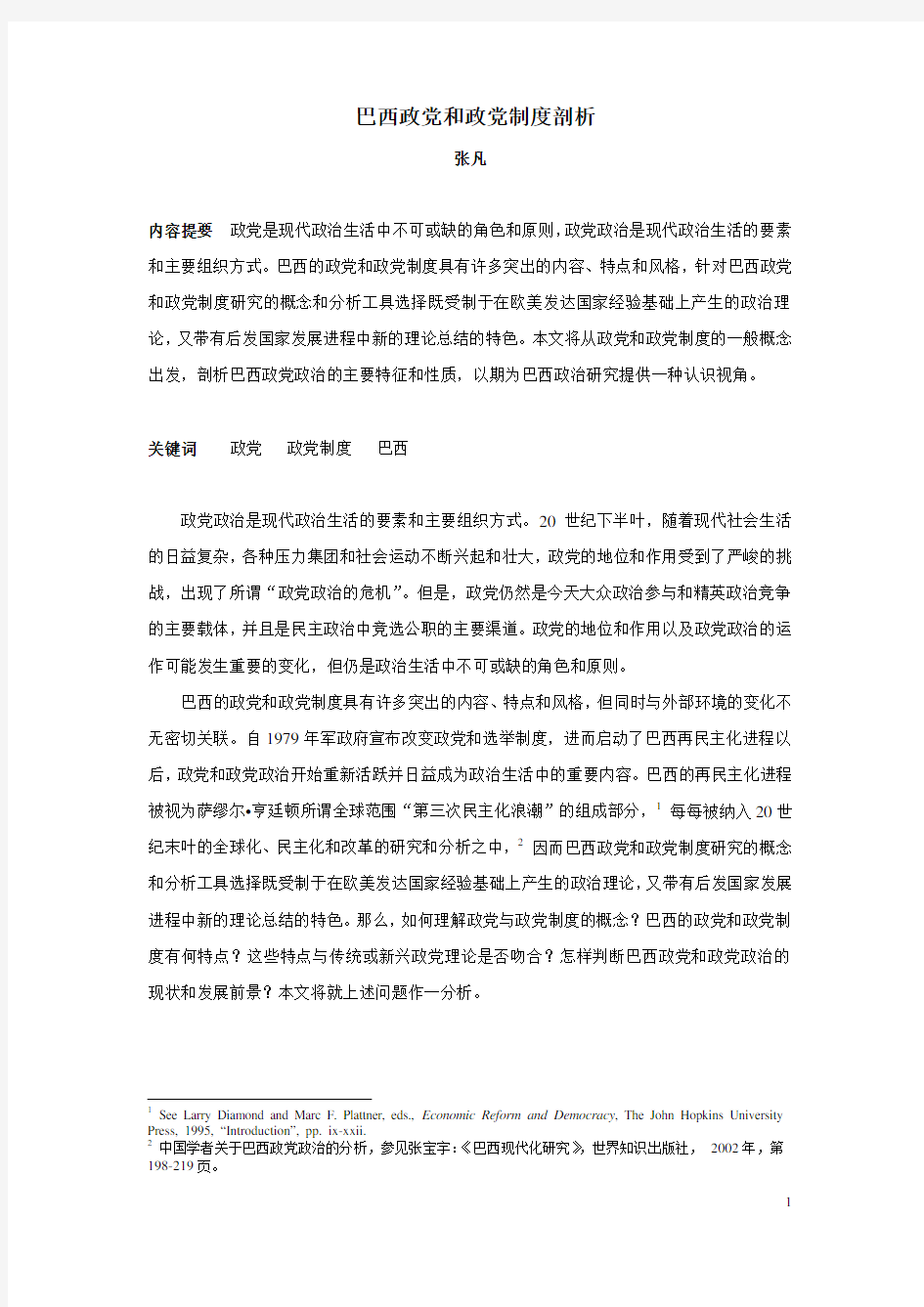

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剖析
张凡
内容提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原则,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要素和主要组织方式。巴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具有许多突出的内容、特点和风格,针对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的概念和分析工具选择既受制于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论,又带有后发国家发展进程中新的理论总结的特色。本文将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一般概念出发,剖析巴西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性质,以期为巴西政治研究提供一种认识视角。
关键词政党政党制度巴西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要素和主要组织方式。20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各种压力集团和社会运动不断兴起和壮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出现了所谓“政党政治的危机”。但是,政党仍然是今天大众政治参与和精英政治竞争的主要载体,并且是民主政治中竞选公职的主要渠道。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党政治的运作可能发生重要的变化,但仍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原则。
巴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具有许多突出的内容、特点和风格,但同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无密切关联。自1979年军政府宣布改变政党和选举制度,进而启动了巴西再民主化进程以后,政党和政党政治开始重新活跃并日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巴西的再民主化进程被视为萨缪尔?亨廷顿所谓全球范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组成部分,1每每被纳入20世纪末叶的全球化、民主化和改革的研究和分析之中,2因而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的概念和分析工具选择既受制于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论,又带有后发国家发展进程中新的理论总结的特色。那么,如何理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概念?巴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有何特点?这些特点与传统或新兴政党理论是否吻合?怎样判断巴西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本文将就上述问题作一分析。
1See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Economic Reform and Democrac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troduction”, pp. ix-xxii.
2中国学者关于巴西政党政治的分析,参见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第198-219页。
政党与政党制度:一般含义
政党是人们以通过竞选或其他手段赢得政府权力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政党的特征在于以赢得公职行使政府权力为目标(虽然有些小党参加竞选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个活动的平台而非赢得权力);政党是拥有正式“持证”成员的组织机构(区别于松散的社会运动);政党通常具有广泛的议题,即关注政府政策的每一个主要领域(虽然有些小党可能议题专一,类似压力集团);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己的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诉求。1一般而言,政党被视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纽带:在国家一端,政党关乎政府的组成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社会一端,政党则具有利益的形成和表达功能。虽然笼统而言可将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与群众性政党以及革命性政党与宪政型政党,但绝大多数现代政党,特别是所谓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国家中的政党属于群众性和宪政型政党,即强调其组织和成员的拓展和扩大,以及其社会基础和选民支持的构建和稳固;同时其运作以其他政党的存在、选举竞争的规则以及政党与国家机构的分离为前提。
竞选成为政党活动的中心任务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予以特别强调,甚至政党本身就被定义为竞选机器。2选举之于政治制度,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又是不同集团利益诉求和政治竞争的手段。选举为达成代议制政府的两项要求铺平了道路,即代表性和政府向人民负责。在这种体制下,政党活动包括两个不同的领域:竞选和决策。政党通过争取选民支持赢得政府公职,并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合法角色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由此形成了代议制民主中的政治机制,政党成为公民和公共政策联系链条的中心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政党不仅是利益诉求的代表者,而且还是利益诉求的整合者,即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引导、动员的作用,进而塑造政治竞争和大众参与的方式和方向,促进公众政治身份和认同的形成与发展。3
政党在一个国家内的存在形态和模式构成了该国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首先涉及各个政党内部的结构异同:权力集中型政党的制度与权力分散型政党的制度不同,全能型政党的制度与限制性政党的制度不同,柔性政党的制度与刚性政党的制度不同等等。但政党制度还包括比单个政党分析更多的内容:政党的数目、政党的规模、政党的联盟、政党的地理和政治分布等等。政党制度正是由上述所有因素间的特定关系来界定的。因此,政党制度可分为一
1 Andrew Heywood,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218.
2例如,政党是“任何参加竞选并能够通过竞选推举公职候选人的政治团体”。见Scott Mainwaring and Timothy R. Scully, eds.,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
3参见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Economy, Policy and Society,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udon, 2003, pp.44-45.
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大党小党或稳定不稳定政党制度以及权力向左转移或稳恒政党制度等等。1政党制度是多种复杂因素的产物,其中有些因素是某国特有的,例如历史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种族构成、民族竞争等等。但至少有三种因素具有普遍的影响,即阶级结构对政党的巨大作用、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所谓“技术性”因素如选举制度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形塑效应。2
关于政党制度的论述,虽然在学术界存在比较广泛的共识,但它毕竟是欧洲北美政党政治经验的产物。随着所谓“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的出现,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政党制度理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判断就是,包括巴西在内的大多数“第三次浪潮”政党制度具有其自身独有的若干特征。过去的政党制度理论至少忽视了3个重要问题。第一,政党制度类型研究偏重政党数目和意识形态取向,虽然对欧美国家政党制度分析不无裨益,但对于“第三次浪潮”国家而言,同样重要的一个角度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涉及政党竞争模式的稳定性、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的合法性以及政党的组织结构等问题。第二,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强调社会分化对于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作用,拉美国家政党研究也往往采用这一方法。但仅仅强调社会分化的影响对于理解拉美和“第三次浪潮”政党制度是远远不够的。第三,对社会分化以及选举制度作用的强调没有充分注意国家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塑造并重塑政党制度的能力,而事实上在许多“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政治精英正是按照自身目标创建政党,而国家则常常视政党制度为政治威胁进而不断破坏这些制度。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存废兴衰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操纵国家机器的政治精英。3显然,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分析,不能脱离先进国家政党政治经验及其理论结晶,但也不能无视后发国家自身固有的特点。那么,巴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具有哪些特征呢?
巴西的政党与政党制度:特征及其解释
巴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之所以值得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的焦点话题之一,主要取决于巴西本身的一些特点。第一,巴西是所谓“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中地位和作用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其政党政治状况对于全球民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滞后,与巴西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甚相称;第三,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相
1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64, p. 203. 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请参阅袁东振、徐世澄著:《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60-163页。
2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64, pp. 203-205.
3See Scott P.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4.
对不成熟,并不直接导致政局的不稳,而是体现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困难。
关于巴西政党的一个公认的突出特征是政党发展的不充分和相对滞后。“虚弱”或“脆弱”是讨论巴西政党时最常用的限定词。巴西政党的脆弱主要表现在政党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偏好的致命缺陷上。一方面,政党成员很少具备基本的忠诚度和纪律性;另一方面,除个别政党个别时期有所不同外,几乎所有政党都可以归入所谓“全方位”政党1类型。与此同时,巴西政党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政党,而且相对滞后于拉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乌拉圭等。
巴西政党制度的问题表现在其独具特色的多党制和制度化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民主化进程启动以后,巴西政坛上涌现出一大批不具备清晰政治纲领的政党。世纪之交(2000年),在国会众议院有17个政党拥有议席;参议员来自9个政党。虽然关于多党制与两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但多党制本身并不构成政治体制运行的障碍,前提是制度能够提供清晰的多种方案,使选民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和认同做出选择。但巴西的问题恰恰在于多党体制与政治竞争的不够明晰结合到了一起。一般而言,多党存在会使基于社会、宗教或政治分野的政党形象和诉求更加清晰,但巴西政党间的界限却十分混乱复杂,政党成员改换门庭司空见惯,政党联盟(包括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间联盟)是政治舞台上的常态。2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制度化水平的低下,即政党竞争格局和体制的不稳定、政党社会基础的薄弱、政党合法性的相对不足、以及政党组织的涣散。3对于上述观点的解释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巴西具有广泛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实践时间较为短暂,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除个别例外)出现的时间较晚、经验较少,而政党制度又多次被中断、更替,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最能够说明巴西政党生命力的一点是,除了分裂为两个党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等3个小党外,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成立于1966年(即当时的巴西民主运动)。其它拥有国会议席的党均产生于1979年以后。自19世纪30年代巴西出现社会名流组成的党派以来,巴西至少存在过7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帝国时期的两党制(1830年代至1889年);旧共和国时期不同各州的一党制安排(1890年至1930年);多党政体雏型(1930年至1937年);多党民主制(1946年至1964年);军政府时期的两党制(1966年至1979年);威权体制下向多党制的过渡(1979年至1984年);
1关于“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的含义,参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100页。
2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p. 57.
3参见Scott P.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pp. 63-135.
以及多党民主制的回归(1985年至今)。1虽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结构变迁剧烈且分化日甚,但政党政治仍属于精英政治的范畴:政治精英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决定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兴亡、存废。这在1930年代的瓦加斯时期、1960年代的军政府时期、以及1980年代的再民主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2换言之,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特征只是精英政治的产物。
与政治精英操控政党政治密切相关,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的特征还可以从制度方面做出解释。政治精英刻意地通过制度安排(主要是选举规则)鼓励并营造出大批权力分散、纪律性差、个人色彩极浓的“全方位”政党。代议制民主所要求的代表性和责任原则在实践中都打了折扣。巴西国会选举的比例代表制表面看来能够使巴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产生民意代表,但议席分配规则的不合理损害了制度安排原则的代表性。参议院选举遵循联邦原则各州平等,不考虑各州人口数量的巨大差距。众议院选举则规定了各州议席分配的上下限:每州不得低于8席或不得高于70席。这意味着人口众多的大州代表性不足。3与此同时,责任原则要求选民能够在明确的政党和政策选项中做出取舍,民意代表与选民之间具有稳定的联系。然而,巴西的选民往往处于信息混乱或信息极不充分的状态。多级选举(全国、州、地方)、多种投票方式(众院及州、市议会实行比例代表制,参院实行相对多数制,总统、州长、市长为两轮多数制)、开放式候选人名单(选民可以按政党投票或者将选票直接投给候选人)、选区划分以州为单位(选民需面对众多参选的候选人)、以及频繁的政党联盟,这一切使普通公民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辨别如此众多的候选人和竞选联盟,当选的民意代表也很难向相对固定选民群体确认责任关系。这种状况等于鼓励多党存在,因为小党亦有可能在以州为单位的选区中赢得一席或通过出售电视宣传时间与联盟内其他政党作交易;同时,党内初选与政党间竞选合二而一,同一政党内部的争斗甚至重于政党间的竞争。选举规则使政党功能的发挥偏离了正轨。4
由此不难理解巴西政党政治中许许多多虽不完全独特但却十分突出的现象。首先,巴西的选举波动性5相对而言居各国最高之列,这是选民政党认同薄弱的一个后果。在1982-1998年间,平均约有30%的选民在相继的选举中转换了所投的党派(几乎同期即1Scott Mainwaring and Timothy R. Scully, eds.,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p. 354-355.
2关于巴西再民主化进程精英性质的一种意见,可参阅Julia Buxton and Nicola Phillips, eds., Case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32.
3这一规则对于劳工党和巴西社会民主党等以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因而也是人口众多各州为选民基础的政党明显不利。
4参见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pp.50-52; Lincoln Gordon, Brazi l’s Second Chance: En Route toward the First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153-156.
5即“选举变换”,指选票在两种选择之间的变动,或从一党转向另一党,或从投票变为弃权,等等。参见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236页。
1985-1996年欧洲国家平均指数为11.0%)。在1990-2002年的联邦众院和州议会选举中,全国平均波动指数分别为38.3%和36.7%,有些州高达54.0%。1第二,多党特别是众多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纲的小党存在与政治分肥相伴而行,政客特别是议员们视公职为个人奖赏而非公共责任。无论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州一级,议员们不仅享有大量合法津贴、住房和旅行补贴,会议费用乃至法外的裙带、贿票便利,而且为讨好支持者频繁动用公共资源包括公职的设立与任命以及各类公共工程的拨款等等。2第三,政党体系和竞争格局制度化水平低下使总统难以通过政党渠道凝聚政治支持,而是广泛依赖分肥政治,进而对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实施产生腐蚀作用,造成所谓“治理难题”。另一方面,政党的弱化也损害了大众的参与和代表性,强化了精英政治:政客个人成为代表性的主渠道,进而破坏了政党的民主合法性和责任原则。如果政党名称变化多端、主要政党存废无常、忠诚与纪律无人重视、政党联盟虽属常规但并不持久,政党的责任便无从谈起。研究巴西政党政治的难题之一就是弄清一大批政党的名称及其沿革。联邦议员不守党纪或改换党派更是一大突出特点。在1987-1988年制宪国会期间,有363次唱名表决议案获得通过但反对票比率超过25%,在这类表决中,各政党议员反对本党主流意见的比率分别是:巴西民主运动党35%,巴西工党30%,自由阵线党24%,民主社会党21%,民主工党14%,劳工党2%。1989-1994年联邦众院的221次唱名表决中(议案获通过但至少面临10%反对票),各政党议员违背本党多数意见的平均比率为:巴西工党15%,巴西社会民主党和巴西民主运动党均为13%,民主社会党12%,自由阵线党11%,巴西工党9%,劳工党2%。在1987-1990年的立法机构中,至少82名议员在1987年2月至1988年9月间改换党派,1988年9月至1990年1月为57人,1990年1月至10月间为58人。在1990年当选的503名联邦众议员中,4年间有260人名改换党派,其中18%(47人)转向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党派。3
长期以来,劳工党是巴西政党发展中的一个例外。本党议员违背党纪或改换党派的比率微乎其微。在政治纲领、社会基础、组织结构等方面,劳工党在各政党中可以说都具有极大优势,无人能望其项背。但是,随着与中右政党结盟并赢得2002年总统大选,党内意见分歧逐步尖锐化。特别是腐败丑闻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以后,党内在政府政策和议会辩论中不同
1Quoted from 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p.59.
2关于巴西政客特别是议员的信誉度问题,1989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公众认为政客“照顾亲朋好友”的占30.1%,“损公肥私”44.8%,“维护选民利益”9.1%,“其他或不详”16.1%。See Jose Alvaro Moises, “Elec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azil: Change and Continuitie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 ol.25(1993), p.602. Quoted from Lincoln Gordon, Brazil’s Second Chance, p.157.
3参见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6-82; S.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pp.142-147.
声音渐多渐强,甚至出现分裂和脱党现象。1究竟劳工党能否影响巴西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抑或同化于传统的政治文化,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巴西政党政治:基本判断和发展前景
上述关于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描述与分析所呈现的图景可概括为“虚弱的政党”和“脆弱的政党制度”。这样一种观点是巴西乃至拉美政党研究中较为广泛的共识。它不仅依据传统政党理论关于政党特征和政党制度含义的基本思想评判巴西政党政治,而且也采纳“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分析中关于政党体系制度化的论述探讨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演变。由此可以看到巴西政党(除个别例外)在纲领、组织、社会基础、合法性、竞争规则等方面与成熟、稳固民主制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理解上述判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传统政党理论包含着实证(即事实分析)和规范(即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有关“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的研究中,政党制度的分析工具由专注于政党数目和意识形态拓展到以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为焦点,无疑使政党政治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步。但是这种进步应该说是实证意义上的,而在规范的意义上,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等基本诉求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因此,关于巴西政党政治的基本判断仍是以民主政治原则为依归的。然而,分析到此并没有结束,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至少有二:第一,作为历史形成的、有一定制度基础的巴西政党政治状况有没有它的某些合理性?第二,如果更全面地审视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它们有没有某些积极的方面?
首先,巴西的政党政治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精英政治的特点。政治主要表现为社会上层利益和意志的博弈、冲突和妥协。政党与政党制度,特别是政党竞争规则、选举制度的发展演变取决于政治精英的选择、设计和力量。因此,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合理性首先表现为它们的状况与政治精英的利益相吻合。这可以从巴西政治史上政党兴衰和政党制度存废的频繁程度中得到实证支持。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精英对政坛的把持与大众参与的趋势毕竟会形成某种紧张关系。因而政党政治状况的合理性还与精英层揆情度理进行调整和改革的种种尝试有关。一方面,政治精英能够努力应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要求而作出必要调整,例如再民主化进程初期,面对解决“社会债务”(即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呼声和扩大政治参与、国家权力下放(即非集中化)的要求,1988年新宪法的制定者们不仅决定设置保障广泛的社会平等权利的条款,而且确立了政治参与的新形式(诸如公民立法创制权、
1较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006年1月国会众院表决是否取消宪法关于政党结盟必须在联盟和州一级保持一致条款时,劳工党77名议员中有63人违背卢拉总统的意旨,投票反对取消这一条款。
全民公决和参与决策、强化联邦制等)并维护代议制政府的某些特定组织规则(诸如两院制、比例代表制、多党制等),进而保证了政治的分散化和政治舞台上多重否决角色的存在。但随着1990年代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财政危机的发生,货币稳定、公共帐户调整、社会经济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主要政党(首先是中间政党,继而是左翼政党)的政策均发生了转变,接受稳定计划和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而接受并维护总统的权威,即开始强调宪法中关于权力集中的一面(例如认可总统通过临时法令实施有关政策)。1新世纪以来,经济改革成败的争论、社会问题的再次突显以及政坛力量新的分化组合已使某种新的议程开始酝酿。
另一方面,面对学术界和媒体对政党组织和运作的批评,有关政党立法和选举制度改革的呼声和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例如,在1987-1988年制宪国会期间,一个由总统任命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曾建议实施新的选举制度,半数议员将由人口大致相等的单名选区选举产生,而另半数议员则出自在全国范围内有足够力量摊到比例代表制名额的政党。小党将由于设定全国范围3%的得票率门槛而出局。同时,议员改换党派的行为由于设置当届国会转党将失去议席的条款而受到抑制。1995年新的政党组织法出台,全国得票率门槛定为5%,而且得票必须至少分布于三分之一的州且每州得票率不得低于2%。2需要注意的是,在巴西,政治改革虽然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其深度和广度难以确定,但它始终没有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议事日程之外。而这一切并非是理论和规范的需要,应该说它也是政治实践的要求,与政治精英的利益并不冲突。
第二,将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状况仅仅描绘成一片灰色图景不无偏颇之处。与政党政治乃至整个政治改革的呼声和努力相伴随,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实践也呈现出若干积极的趋势。公民选举参与率3是衡量政党动员能力的重要指标。再民主化进程以来,巴西各类主要选举(总统、州长、国会)的公民参与率与同期发达国家情况差别不大。1950年代,发达国家平均参与率为78%,1990年代末期下降到70%。巴西再民主化进程以来总统选举的平均参与率为73%(1990-2002年)。由于行政部门居于政治体系的核心,选民对总统和州长的关注远大于对议员和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选举参与率较总统选举参与率为低。但随着选举程序安排的调整以及电子计票器的出现,国会选举参与率大幅提高,1998年和2002年分
1参见Argelina Cheibub Figueiredo and Fernando Limongi, “Congress and Decision-Making in Democratic Brazil”, in 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pp. 42-61.
2 Lincoln Gordon, Brazil’s Second Chance, p. 157.
3指有效参与率,即具有选民资格的人实际参加投票并将选票投给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党。
别达到63%和77%。1与此同时,随着左翼政治力量的上升,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几率增大(2002年卢拉当选总统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其组织、扩大其影响,这势必在原来由传统政党控制的各州造成更激烈的政党对峙、竞争,加大主要对手所需付出的成本、代价,进而使政党的重组成为可能。考虑到政党立法的改进,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分散、脆弱状态有望得到遏制,相对稳定的政党竞争格局将会(虽然缓慢)逐步形成。
1Maria D’Alva Kinzo and James Dunkerley, eds., Brazil since 1985, pp. 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