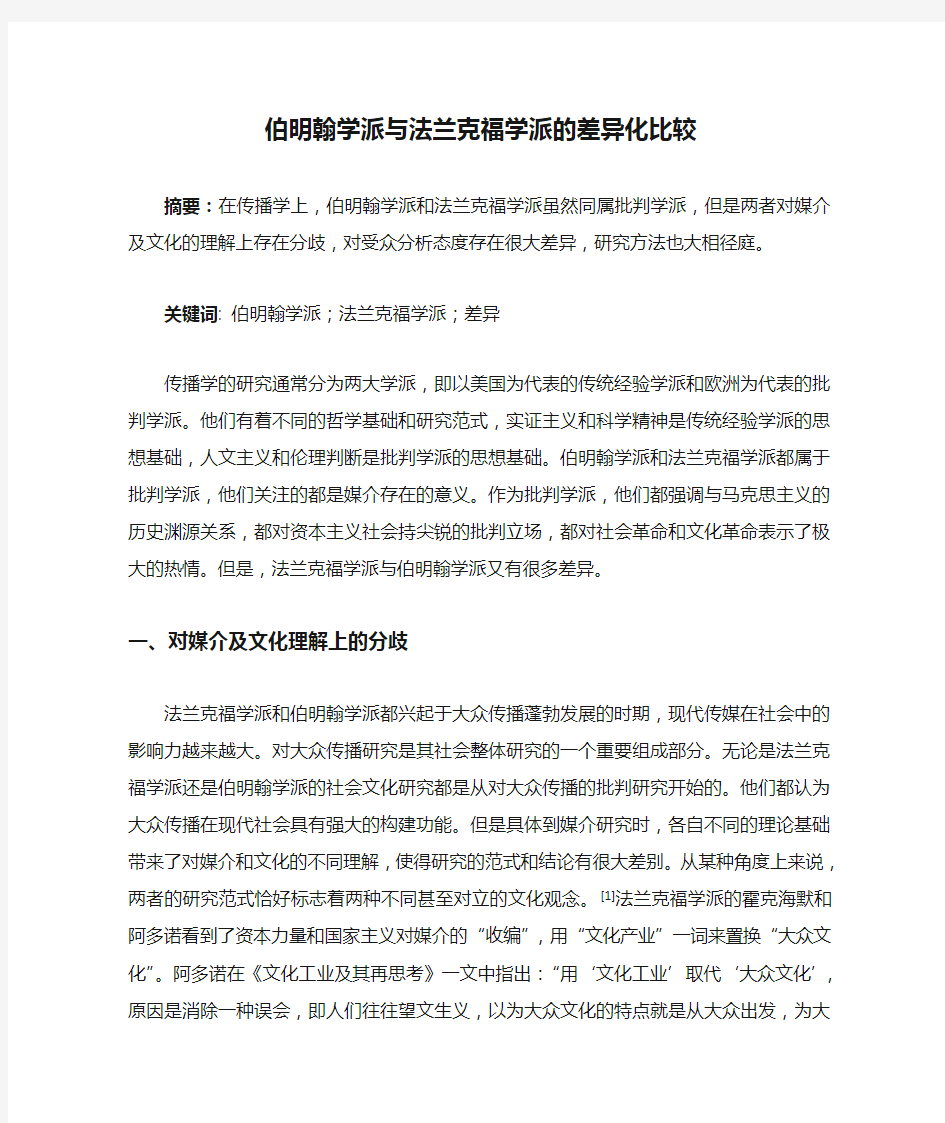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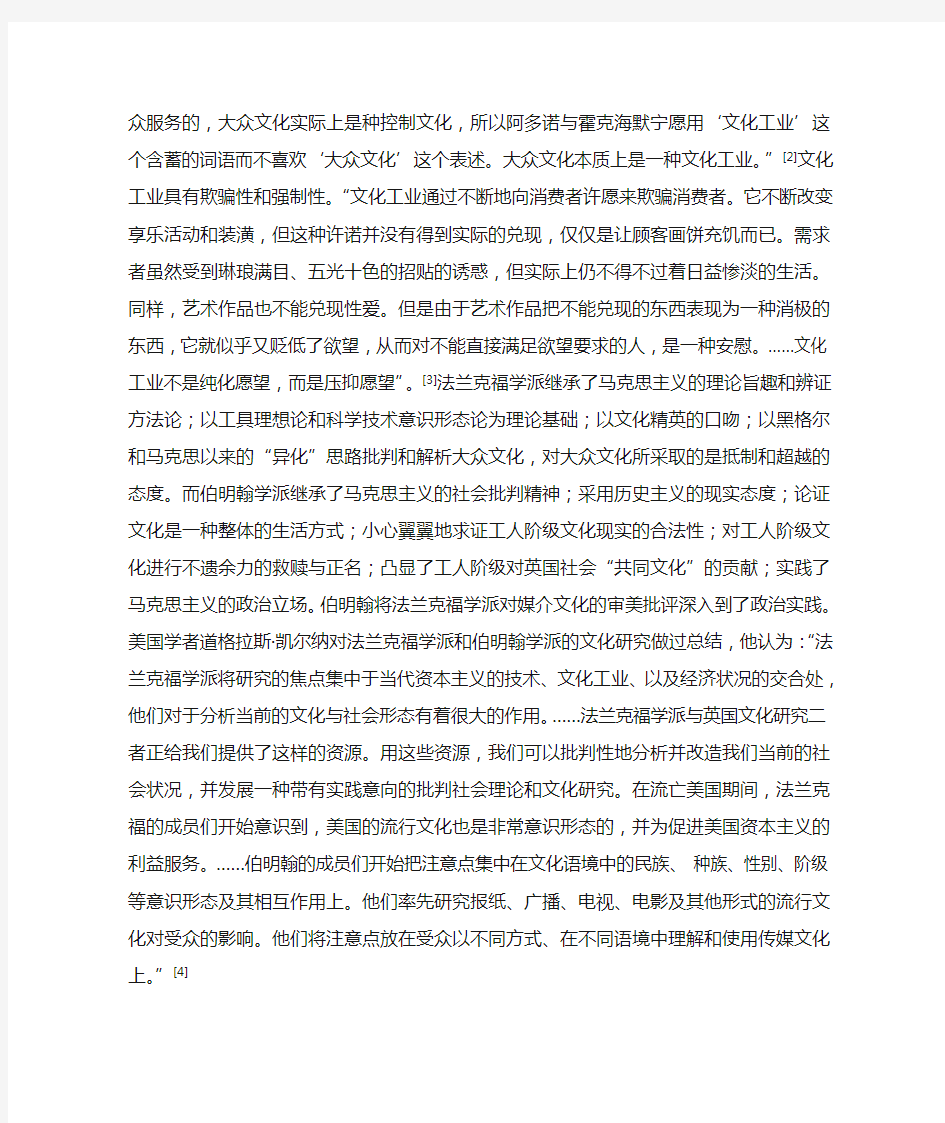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
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工业。”[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3]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以工具理想论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而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论证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伯明翰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审美批评深入到了政治实践。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他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4]
二、受众分析态度上的对立
受众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上。受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但是纵观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历程,不同学派站在
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其结果也各不相同。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传统的经验学派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5]结果将受众看作是无知的“傻瓜”、被动的“靶子”,媒介一击即到。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简化了传播的复杂性,早已被研究者抛弃。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受众是铁板一块的,被动的客体。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描述大众传播的受众:“资本主义的生产用灵和肉紧紧地控制住他们,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为他们提供的东西”,[6]“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7]大众传播的“消费者可以随便地把他的冲动、欲望投射到摆在他面前的商品上面。观赏、聆听、阅读一个形象的主体将会忘乎所以、无所谓、幻灭于其中,直到全面被控制的地步’。[8]这样,受众便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他们被“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9]促进变革的“痛苦意识”己被虚假的“幸福意识”所取代,他们沉沦俗世、其乐陶陶。大众传播受众所遭受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全面被控,他们的生活行为风格、消费习惯甚至内在需求和内心愿望,全部受到大众传播的控制。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的消费者不是上帝,而是奴隶,虽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0]作为麻木不仁、心满意足的奴隶,大众传播受众目光短浅、软弱无力,既不会发现、更不会反抗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不公,对于现实的政治关怀己经转变为彻底的“明哲保身主义”。[11]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播的受众基木上持一种批判的、悲观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和他们对“晚期资木主义”社会可能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失望相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晚期资木主义”的“工人
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12]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现实主体已经丧失,在马尔库塞那里,解放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审美乌托邦”。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他们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协商而产生的;充分肯定受众在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说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13]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的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霍尔在新的研究模式融入符号学的方法,认为媒介传递的信息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在由受众收到后来进行解码。媒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阅读方式不止一个,受众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体性。在霍尔提出三种解读方式以后,莫利开创性的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到传媒研究中去,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揭示了受众接受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受众研究。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研究方法的差异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学派,都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其他学科里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都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在具体分析媒介文化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运用政治
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民族志+符号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德国,继承了精于理论思维,长于逻辑分析以及抽象概括的欧洲传统,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了浓重的思辨色彩。德国学者们常对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推崇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对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各种价值观念提出怀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成为批判学派的武器。他们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入手,揭示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工具性,并指出媒介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是一致的。伯明翰学派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媒介文化现象。威廉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来研究亚文化群体,霍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介讯息的编码和解码。莫利把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民族志是源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深入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亚文化。作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最传统的形式,民族志是编译其他文化社会生活描述的重要工具。它需要对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并且有可能的话,民族志学者需要亲身参与到所要研究的文化中去,并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他们所目睹的东西。有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详细描述之后,就可以对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形成关于文化如何运作的假设。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天地。
总之,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视角和旨趣上、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两者研究的重心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围绕着对媒介权力“异化”的批判而展开的。
注释:
[1] 周宪.精英的或民粹的——两种文化研究范式及其启示[OL]. 2006-4-2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OL] 2006-5-9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洪佩郁译.启蒙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78. 133.
[4] Douglas Kellner.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 .
2006-3-15 蔡祺,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新闻大学,2004,(夏).
[6][8] 唐正序,冯宪光主编.文艺学基本理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德)马尔库塞.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M].重庆:重庆出版社,.
[13]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